试论汉末魏晋文人的世纪病心态
- 格式:pdf
- 大小:156.70 KB
- 文档页数: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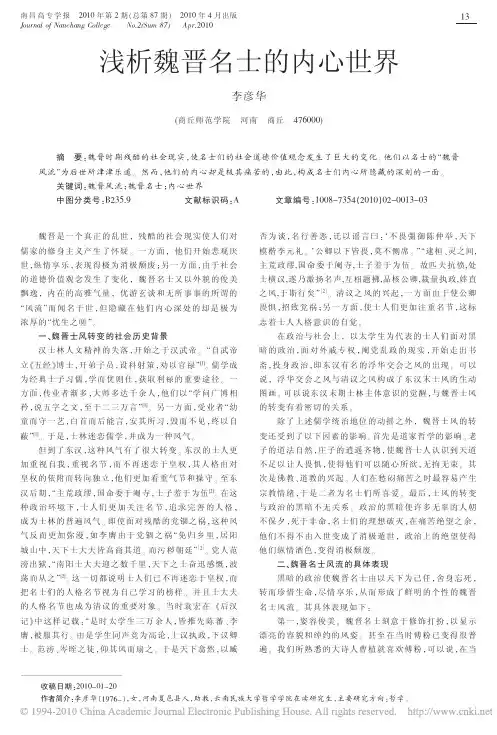
收稿日期:2010-01-20作者简介:李彦华(1976-),女,河南夏邑县人,助教,云南民族大学哲学学院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哲学。
魏晋是一个真正的乱世,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人们对儒家的修身主义产生了怀疑。
一方面,他们开始悲观厌世,纵情享乐,表现得极为消极颓废;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魏晋名士又以外貌的俊美飘逸,内在的高雅气量,优游玄谈和无所事事的所谓的“风流”而闻名于世,但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却是极为浓厚的“忧生之嗟”。
一、魏晋士风转变的社会历史背景汉士林人文精神的失落,开始之于汉武帝。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1]。
儒学成为经典士子习儒,学而优则仕,获取利禄的重要途径。
一方面,传业者渐多,大师多达千余人,他们以“学问广博相矜,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1]。
另一方面,受业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而不见,终以自蔽”[1]。
于是,士林迷恋儒学,并成为一种风气。
但到了东汉,这种风气有了很大转变。
东汉的士人更加重视自我,重视名节,而不再迷恋于皇权,其人格由对皇权的依附而转向独立,他们更加看重气节和操守。
至东汉后期,“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2]。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士人们更加关注名节,追求完善的人格,成为士林的普遍风气。
即使面对残酷的党锢之祸,这种风气反而更加弥漫,如李膺由于党锢之祸“免归乡里,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
而污秽朝廷”[2]。
党人范滂出狱,“南阳士大夫迎之数千里,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2]。
这一切都说明士人们已不再迷恋于皇权,而把名士们的人格名节视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并且士大夫的人格名节也成为清议的重要对象。
当时袁宏在《后汉记》中这样记载:“是时太学生三万余人,皆推先陈蕃、李膺,被服其行。
由是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上议执政,下议卿士。
范滂、岑晊之徒,仰其风而扇之。
于是天下翕然,以臧否为谈,名行善恶,讬以谣言曰:‘不畏彊御陈仲举,天下模楷李元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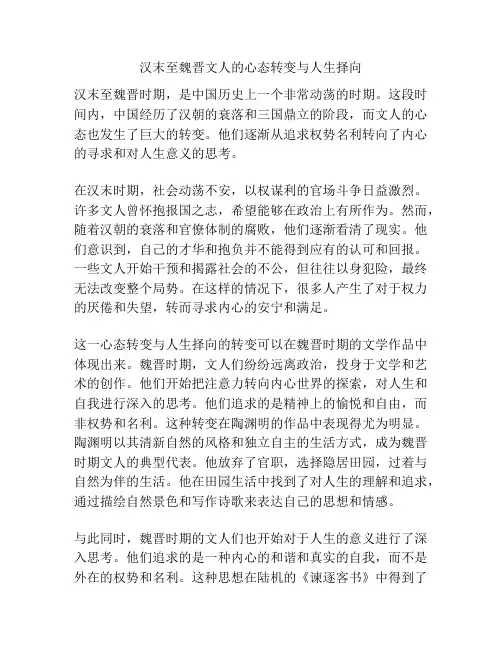
汉末至魏晋文人的心态转变与人生择向汉末至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
这段时间内,中国经历了汉朝的衰落和三国鼎立的阶段,而文人的心态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他们逐渐从追求权势名利转向了内心的寻求和对人生意义的思考。
在汉末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以权谋利的官场斗争日益激烈。
许多文人曾怀抱报国之志,希望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然而,随着汉朝的衰落和官僚体制的腐败,他们逐渐看清了现实。
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并不能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回报。
一些文人开始干预和揭露社会的不公,但往往以身犯险,最终无法改变整个局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产生了对于权力的厌倦和失望,转而寻求内心的安宁和满足。
这一心态转变与人生择向的转变可以在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
魏晋时期,文人们纷纷远离政治,投身于文学和艺术的创作。
他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内心世界的探索,对人生和自我进行深入的思考。
他们追求的是精神上的愉悦和自由,而非权势和名利。
这种转变在陶渊明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陶渊明以其清新自然的风格和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成为魏晋时期文人的典型代表。
他放弃了官职,选择隐居田园,过着与自然为伴的生活。
他在田园生活中找到了对人生的理解和追求,通过描绘自然景色和写作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与此同时,魏晋时期的文人们也开始对于人生的意义进行了深入思考。
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内心的和谐和真实的自我,而不是外在的权势和名利。
这种思想在陆机的《谏逐客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陆机在这篇信中表达了对于魏晋时代官场的不满和对自由独立生活的向往。
他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追求自己内心的真实和坦荡,而不是被外在的权力和社会规范所束缚。
他宣扬了“宁可坐拥贫贱而心安,不愿苟求富贵而失心灵”的观点,强调了与社会观念和权势的脱离,以及心灵自由的追求。
这种心态转变与人生择向的转变,不仅在文学上得以体现,也对当时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人们的思想追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于后世的文化发展和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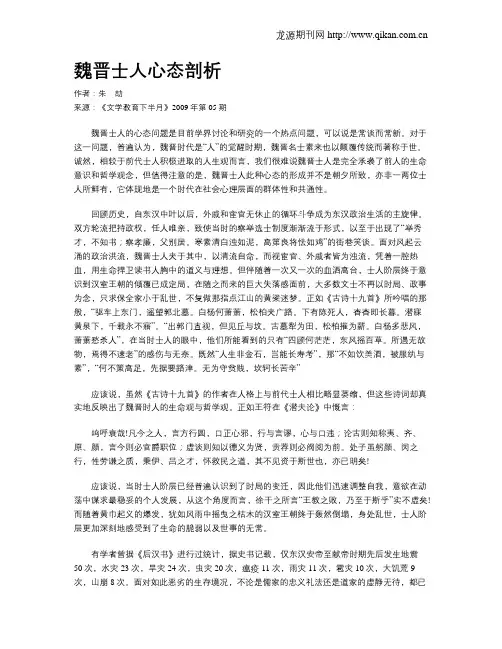
魏晋士人心态剖析作者:朱劼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09年第05期魏晋士人的心态问题是目前学界讨论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可以说是常谈而常新。
对于这一问题,普遍认为,魏晋时代是“人”的觉醒时期,魏晋名士素来也以颠覆传统而著称于世。
诚然,相较于前代士人积极进取的人生观而言,我们很难说魏晋士人是完全承袭了前人的生命意识和哲学观念,但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士人此种心态的形成并不是朝夕所致,亦非一两位士人所鲜有,它体现地是一个时代在社会心理层面的群体性和共通性。
回顾历史,自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和宦官无休止的循环斗争成为东汉政治生活的主旋律。
双方轮流把持政权,任人唯亲,致使当时的察举选士制度渐渐流于形式,以至于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街巷笑谈。
面对风起云涌的政治洪流,魏晋士人夹于其中,以清流自命,而视宦官、外戚者皆为浊流,凭着一腔热血,用生命捍卫读书人胸中的道义与理想。
但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血洒高台,士人阶层终于意识到汉室王朝的倾覆已成定局,在随之而来的巨大失落感面前,大多数文士不再以时局、政事为念,只求保全家小于乱世,不复做那指点江山的黄粱迷梦。
正如《古诗十九首》所吟唱的那般,“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
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
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
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
“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
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在当时士人的眼中,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有“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的感伤与无奈。
既然“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那“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贫贱,坎轲长苦辛”应该说,虽然《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在人格上与前代士人相比略显萎缩,但这些诗词却真实地反映出了魏晋时人的生命观与哲学观。
正如王符在《潜夫论》中慨言:呜呼衰哉!凡今之人,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论古则知称夷、齐、原、颜,言今则必官爵职位;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贡荐则必阀阅为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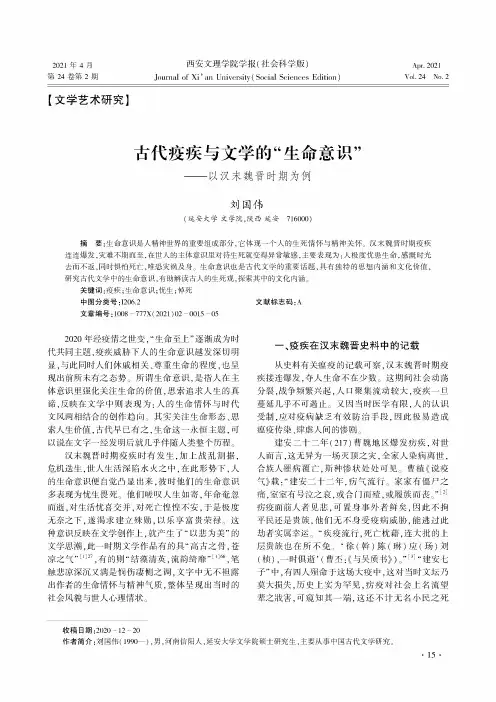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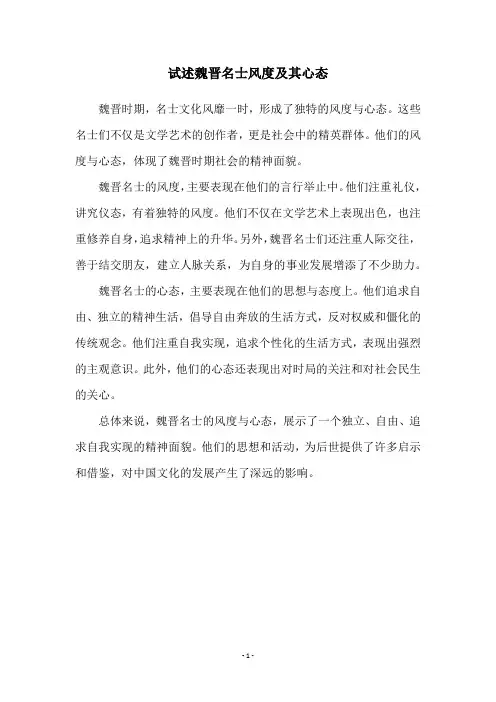
试述魏晋名士风度及其心态
魏晋时期,名士文化风靡一时,形成了独特的风度与心态。
这些名士们不仅是文学艺术的创作者,更是社会中的精英群体。
他们的风度与心态,体现了魏晋时期社会的精神面貌。
魏晋名士的风度,主要表现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中。
他们注重礼仪,讲究仪态,有着独特的风度。
他们不仅在文学艺术上表现出色,也注重修养自身,追求精神上的升华。
另外,魏晋名士们还注重人际交往,善于结交朋友,建立人脉关系,为自身的事业发展增添了不少助力。
魏晋名士的心态,主要表现在他们的思想与态度上。
他们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生活,倡导自由奔放的生活方式,反对权威和僵化的传统观念。
他们注重自我实现,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方式,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意识。
此外,他们的心态还表现出对时局的关注和对社会民生的关心。
总体来说,魏晋名士的风度与心态,展示了一个独立、自由、追求自我实现的精神面貌。
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为后世提供了许多启示和借鉴,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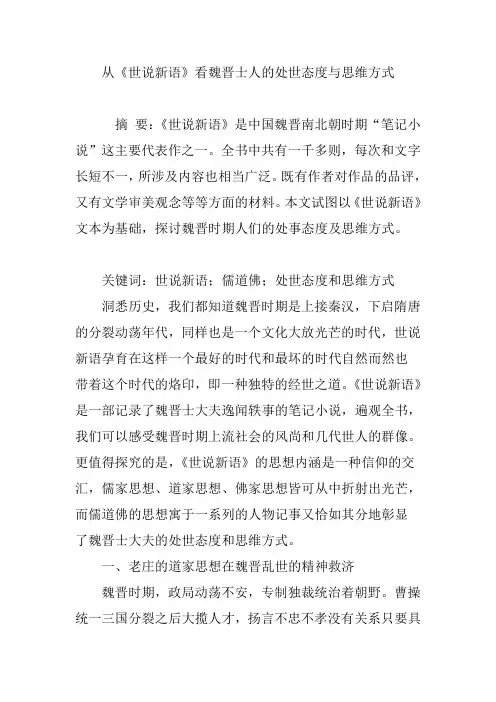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处世态度与思维方式摘要:《世说新语》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这主要代表作之一。
全书中共有一千多则,每次和文字长短不一,所涉及内容也相当广泛。
既有作者对作品的品评,又有文学审美观念等等方面的材料。
本文试图以《世说新语》文本为基础,探讨魏晋时期人们的处事态度及思维方式。
关键词:世说新语;儒道佛;处世态度和思维方式洞悉历史,我们都知道魏晋时期是上接秦汉,下启隋唐的分裂动荡年代,同样也是一个文化大放光芒的时代,世说新语孕育在这样一个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自然而然也带着这个时代的烙印,即一种独特的经世之道。
《世说新语》是一部记录了魏晋士大夫逸闻轶事的笔记小说,遍观全书,我们可以感受魏晋时期上流社会的风尚和几代世人的群像。
更值得探究的是,《世说新语》的思想内涵是一种信仰的交汇,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皆可从中折射出光芒,而儒道佛的思想寓于一系列的人物记事又恰如其分地彰显了魏晋士大夫的处世态度和思维方式。
一、老庄的道家思想在魏晋乱世的精神救济魏晋时期,政局动荡不安,专制独裁统治着朝野。
曹操统一三国分裂之后大揽人才,扬言不忠不孝没有关系只要具有经世之才即可,后因猜忌心日益加重残杀杨修,又因孔融对时事的批判而以不孝罪名加害于他。
司马懿取代曹氏天下之后也因猜忌杀害竹林七贤的嵇康。
整个混乱混沌的魏晋时代笼罩在漆黑的政治漩涡之中。
对知识分子的肆意残杀使得士人对朝不保夕的恐慌与日俱增,于此,老庄哲学成为了这一时期士大夫的精神良药。
魏晋士大夫厌恶乱世,回避政治,崇尚老庄的逍遥境界以此来寻求处事上的超然。
例如: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
行无辙迹,居无室庐,暮天席地,纵意所如。
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以天地为一朝,万年为一瞬,日月为门窗,八荒为庭院,将饮酒作为唯一要务的逍遥生活即是对老庄哲学的外化,是士大夫在乱世中用逍遥派的安逸对我自我的救赎和对世道的抗拒。

——魏晋文人的生存与创作心态兰亭集序补充材料世说新语》——魏晋文人的生存与创作心态[内容摘要]:《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一部从汉末到东晋士族阶层的遗闻轶事和言谈轶事小说。
其中大部分是描写魏晋文人的。
本文主要通要四个方面来阐述魏晋文人的生存与创作心态,从而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原形以及精神状态。
[关键词]:文学自觉魏晋风度玄学《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一部拾掇了从汉末到东晋士族阶层的遗闻轶事和言谈的轶事小说集。
全书分为三十六篇,每一篇都围绕着篇目主题引出若干个小故事。
全书涉及的各类人物有一千五百余人,而这些人大多属于文人。
从这部《世说新语》对这些文人言行活动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晋文人的生活原形,了解他们的生存环境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从而了解当时的时风,即“魏晋风度”。
一、自我的觉醒与魏晋风度魏晋时代是文人的自觉时代。
从《世说新语》中我们看到的与以往任何时期都完全不同的魏晋人,尤其是魏晋文人的人生。
他们的思想言行,体现的是人的自我觉醒意识。
他们完全突破了两汉以来儒学传统的束缚,进入了一个思想自由、人性觉醒、个性张扬和价值多元的时代。
可以说,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动乱,但精神却是最自由、解放,最赋予智慧、狂放的时期。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社会心理、创作心理对文人产生了影响,动荡的社会促使文人们面对现实、直面人生,去积极主动的描写社会现实和个人感受,去追求人生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
主要是人们对生死的忧惧,感慨人生的短暂。
例如曹操的《短歌行》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陶渊明的《拟挽歌辞》说:“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等等。
他们唱出的都是同一感叹,同一思绪。
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出来了。
“它实质上标志着人的一种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和信仰的条件下,人对生命意义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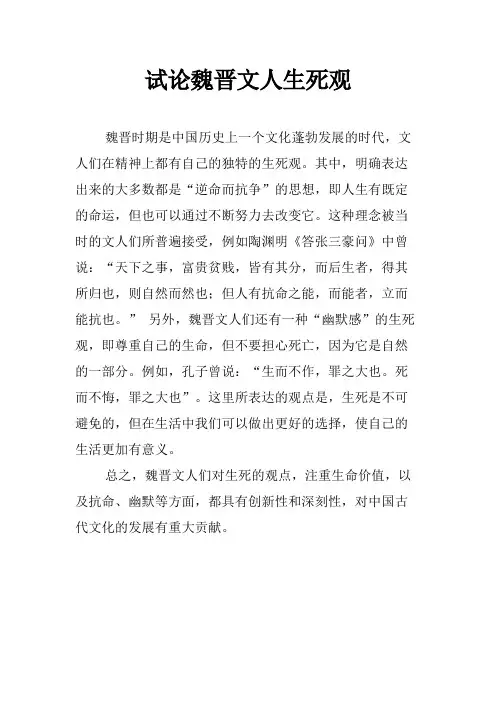
试论魏晋文人生死观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文人们在精神上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生死观。
其中,明确表达出来的大多数都是“逆命而抗争”的思想,即人生有既定的命运,但也可以通过不断努力去改变它。
这种理念被当时的文人们所普遍接受,例如陶渊明《答张三豪问》中曾说:“天下之事,富贵贫贱,皆有其分,而后生者,得其所归也,则自然而然也;但人有抗命之能,而能者,立而能抗也。
” 另外,魏晋文人们还有一种“幽默感”的生死观,即尊重自己的生命,但不要担心死亡,因为它是自然的一部分。
例如,孔子曾说:“生而不作,罪之大也。
死而不悔,罪之大也”。
这里所表达的观点是,生死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使自己的生活更加有意义。
总之,魏晋文人们对生死的观点,注重生命价值,以及抗命、幽默等方面,都具有创新性和深刻性,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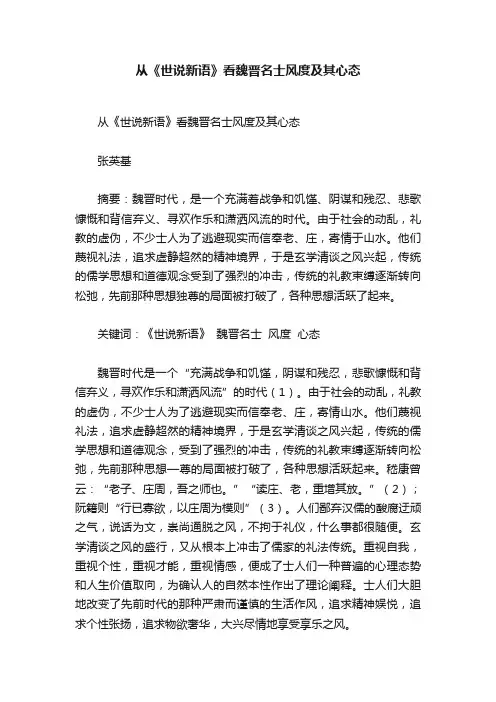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风度及其心态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风度及其心态张英基摘要:魏晋时代,是一个充满着战争和饥馑、阴谋和残忍、悲歌慷慨和背信弃义、寻欢作乐和潇洒风流的时代。
由于社会的动乱,礼教的虚伪,不少士人为了逃避现实而信奉老、庄,寄情于山水。
他们蔑视礼法,追求虚静超然的精神境界,于是玄学清谈之风兴起,传统的儒学思想和道德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传统的礼教束缚逐渐转向松弛,先前那种思想独尊的局面被打破了,各种思想活跃了起来。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名士风度心态魏晋时代是一个“充满战争和饥馑,阴谋和残忍,悲歌慷慨和背信弃义,寻欢作乐和潇洒风流”的时代(1)。
由于社会的动乱,礼教的虚伪,不少士人为了逃避现实而信奉老、庄,寄情山水。
他们蔑视礼法,追求虚静超然的精神境界,于是玄学清谈之风兴起,传统的儒学思想和道德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传统的礼教束缚逐渐转向松弛,先前那种思想—尊的局面被打破了,各种思想活跃起来。
嵇康曾云:“老子、庄周,吾之师也。
”“读庄、老,重增其放。
”(2);阮籍则“行已寡欲,以庄周为模则”(3)。
人们鄙弃汉儒的酸腐迂顽之气,说话为文,崇尚通脱之风,不拘于礼仪,什么事都很随便。
玄学清谈之风的盛行,又从根本上冲击了儒家的礼法传统。
重视自我,重视个性,重视才能,重视情感,便成了士人们一种普遍的心理态势和人生价值取向,为确认人的自然本性作出了理论阐释。
士人们大胆地改变了先前时代的那种严肃而谨慎的生活作风,追求精神娱悦,追求个性张扬,追求物欲奢华,大兴尽情地享受享乐之风。
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时局极其黑暗、险恶,士人们为了全身远祸,或崇尚老、庄,清谈玄理,排调戏谑;或崇尚自然,高洁自恃,隐遁山林;或不拘礼俗,注重人格,追求精神解放;或纵酒行乐,放诞不羁,我行我素;或竞豪斗富,穷奢极欲,物欲熏心。
他们富于才华,浓于情感,沉醉于所谓“名士风度”之中,要把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坦露出来。
所谓“名士风度”,大致体现在以下诸方面:其一、讲究雅量,喜怒忧惧,不形于色,追求一种优雅从容的风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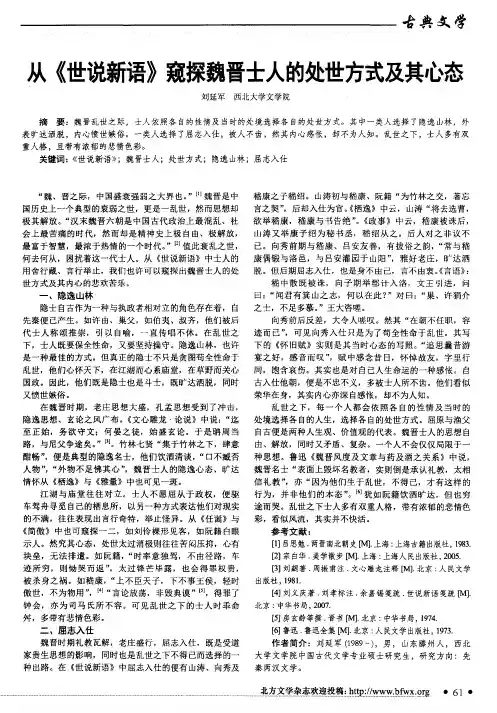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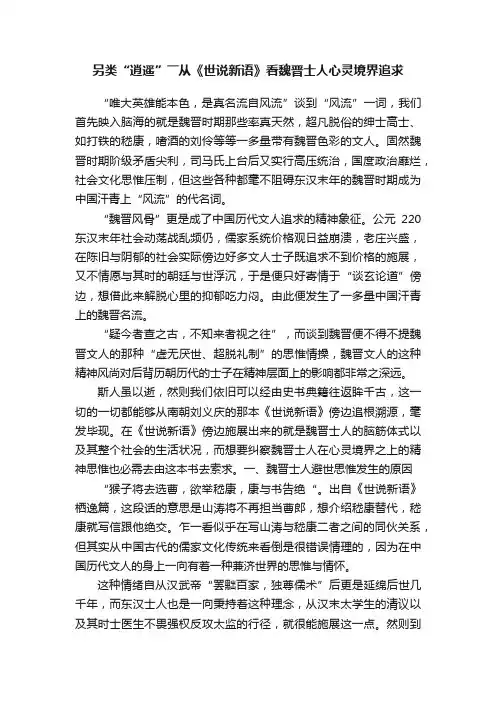
另类“逍遥”――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心灵境界追求“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流自风流”谈到“风流”一词,我们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魏晋时期那些率真天然,超凡脱俗的绅士高士、如打铁的嵇康,嗜酒的刘伶等等一多量带有魏晋色彩的文人。
固然魏晋时期阶级矛盾尖利,司马氏上台后又实行高压统治,国度政治靡烂,社会文化思惟压制,但这些各种都毫不阻碍东汉末年的魏晋时期成为中国汗青上“风流”的代名词。
“魏晋风骨”更是成了中国历代文人追求的精神象征。
公元220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儒家系统价格观日益崩溃,老庄兴盛,在陈旧与阴郁的社会实际傍边好多文人士子既追求不到价格的施展,又不情愿与其时的朝廷与世浮沉,于是便只好寄情于“谈玄论道”傍边,想借此来解脱心里的抑郁吃力闷。
由此便发生了一多量中国汗青上的魏晋名流。
“疑今者查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而谈到魏晋便不得不提魏晋文人的那种“虚无厌世、超脱礼制”的思惟情操,魏晋文人的这种精神风尚对后背历朝历代的士子在精神层面上的影响都非常之深远。
斯人虽以逝,然则我们依旧可以经由史书典籍往返眸千古,这一切的一切都能够从南朝刘义庆的那本《世说新语》傍边追根溯源,毫发毕现。
在《世说新语》傍边施展出来的就是魏晋士人的脑筋体式以及其整个社会的生活状况,而想要纠察魏晋士人在心灵境界之上的精神思惟也必需去由这本书去索求。
一、魏晋士人避世思惟发生的原因“猴子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
出自《世说新语》栖逸篇,这段话的意思是山涛将不再担当曹郎,想介绍嵇康替代,嵇康就写信跟他绝交。
乍一看似乎在写山涛与嵇康二者之间的同伙关系,但其实从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传统来看倒是很错误情理的,因为在中国历代文人的身上一向有着一种兼济世界的思惟与情怀。
这种情绪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更是延绵后世几千年,而东汉士人也是一向秉持着这种理念,从汉末太学生的清议以及其时士医生不畏强权反攻太监的行径,就很能施展这一点。
然则到了魏晋时期为何很多其时名望甚高的士人都不肯意为朝廷效力了呢?甚至于到了司马氏上台之后很多名流面临朝廷的征召更是直接唱起了反调,这在某种层面上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么在此就必需得谈一谈魏晋盛行的那种虚无避世的名流思惟发生的原因了。
浅议高中语文教材中魏晋文人的生死观作者:孟骞来源:《考试周刊》2013年第11期生死观是人类一直面对的问题。
尤其当我们面对未知的死亡,出于人类的本能,我们忧惧,但同样也对生命的去向抱有关怀和期望。
古往今来,中西方哲人对生存与死亡问题不停地探索与反思,希腊先哲柏拉图认为“灵魂不朽”,孔子则拷问“未知生,焉知死”;海德格尔认为人是“向死而生”,庄子则将“生死存亡”视为“一体”。
提到中国人的生死观,魏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文人生死观最值得关注。
高中语文教材触及不少魏晋文人生死观的问题,以下就是我的几点理解。
一、感慨人生短暂,渴望建功立业。
代表人物:曹操。
翻阅历史长卷,“魏晋”二字总是承载了太多内容。
这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长期分裂动荡时期,那一段历史,是蘸着鲜血写就的,字里行间充斥着血腥和死亡。
曹魏代汉、司马氏篡位、八王之乱、十六国之乱、饥荒、疫病,天灾人祸接踵而至。
宗白华先生说过: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
魏晋之乱,催生出人们的觉醒认识,人们比任何时期都更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生死问题也被提到了一个空前重要的位置。
高中语文人教版必修二收录了曹操的著名诗篇《短歌行》,他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对人生如易晞的朝露转瞬即逝的短暂,有着浓浓的感伤。
人生苦短,生命无常,本是汉乐府诗歌里的常见主题,如《薤露》中“薤上露,何易晞。
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薤上之露,转瞬即逝,而人的生命尚不能与之相比,因为朝露虽易晞,但明朝仍可复落,而人的生命却是人死一去何时归。
这是人们在社会大动乱时期萌生的极度悲伤情绪,更是在悲哀中对生命的沉思。
同样也是感慨于生命的哀愁短促,曹操的《短歌行》并未止步于哀叹,更与“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西门行》)主张的及时行乐有着本质区别。
他悲生命短促,是因一统中原的鸿鹄之志迟迟无法实现,他叹忧思难忘,是因朝思暮想贤才来归却久久未得,他这就不能不产生苦闷和感慨,但是,这种苦闷和感慨,也只有对事业和理想执著追求的人,只有不满现实而又积极要求改变现实的人,才可能产生,它决然不同于没落阶层的颓废和感伤。
学术报告听后感魏晋人士心态与魏晋文学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专业:建筑学专业班级:建筑 111 班学号: 1108070143 学生姓名:王雪莹指导教师:邢学树2015年7月魏晋人士心态与魏晋文学魏晋文学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文学,整个文学基调就是悲剧性的,提倡及时行乐,沉迷声色。
由于是乱世,人更加自由,自由的社会就是思潮爆发的社会,也是由于乱世文人异士对生命也存在不稳定性,所以文学主题一般为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三类。
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暂,死亡的不可避免,还有对生死的思考。
1、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2、增加生命的长短,服食求仙;3、增加社交密度,及时行乐;4、不以生死为念,顺其自然。
游仙主题与生死主题密切相关,主要是想象神仙的世界,表现对那个世界的向往以及企求长生的愿望。
隐逸主题包括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形成这个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景观。
相对而言,这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显得自由活跃,各种学说同时并兴,百家争鸣,思想解放的时代。
建安风骨与魏晋风流体现的就是任性,有才华的任性。
建安风骨是指在建安时期作品内在的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简练刚健的特点。
曹操父子三人便是建安时期政治中心也是文坛的领军人物。
魏晋风流指的是魏晋名士在年间淋漓玄谈。
人们对人物的品评由道德风范转向人物外貌,进而发展到人物的精神气质。
魏晋名士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
风度不仅仅是个人文化素质与精神状态在言谈与仪表上的反应,对于一定的社会阶层来说,风度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集中塑造了他们的社会形象。
它不仅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现象,而且深深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从而构成了这一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现象。
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等人,正好反映了魏晋名士的时代精神。
它讲求保持认得自然性与生活上的率性而为,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思想。
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是魏晋风流的基本特点,阮籍嵇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关于写论魏晋生死观的作文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它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承载着厚重的历史。
古往今来,我们中华儿女以各种方式对其进行诠释、总结和发扬。
但如果用一个词概括呢?那便是——生死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曾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在这句话中,作者把人的价值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即“生”,而另外一部分则是“死”。
前半句将人的价值提升到了很高的地步;后半句则引出一个哲理性的问题,即“当你离开这个世界时,会带走什么呢?你能够带走多少财富?”所以从中可看出他们的生死观念是相同的。
并且还强调了不同之处,“或”字既体现了他们认识的差异,又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他们的生与死都是客观存在的,无法避免,也无需躲闪。
所谓“古来圣贤皆寂寞”,他们是真正看透了生死,彻悟了生命的本质,才得出这般见解吧。
只要好好利用每一天,珍惜身边拥有的美好事物,把握住自己的幸福,享受此刻拥有的快乐,那么就算是活上千年万年也是毫无意义的啊!因为这些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呀。
就像陶渊明写的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不正是他追求的最终目标吗?他想找寻的不正是田园生活的平静与恬淡吗?但可悲的是,现实却令他失望至极。
虽被官场排挤打击,却依旧坚守自己的信仰。
回归自然,对于许多诗人来说,也成为了他们摆脱痛苦的唯一途径,即使“众人皆醉我独醒”,亦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尽管这很难……这何尝不是魏晋名士崇尚自由、追求个性的真实写照。
正因如此,他们宁愿放弃功名利禄,纵情山水间,洒脱飘逸,留下“竹林七贤”的盛誉,同时,也令后人敬佩。
再次谈起陶渊明,更加想念他在四十一岁时辞官回家,游玩田园的情景。
太阳暖洋洋的,树木葱茏,空气清新甜润,让人神清气爽,满怀惬意。
倘若他能继续待在朝廷做官,必定可保全晚节,得善终罢。
毕竟“天才难于寿”嘛,再有学问也敌不过疾病的折磨啊!。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国民族学类核心期刊2007年第2期J.N ORTHWEST UNIVER SIT Y FOR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No.2.2007试论汉末魏晋文人的世纪病心态丁沂璐(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30)[摘 要]汉末魏晋,世纪末思想弥漫,究其原因,不外三点:首先,东汉末年,大疫流行,死人如麻,引起了士人集团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其次,汉末政治,宦官横行,党锢之祸,士林血腥,有识之士已经洞观天下将乱,这更进一步加深了士人们的世纪末恐惧心理。
此后,黄巾揭竿,董卓乱政,军阀混战,政治血腥,战乱分裂持续了80余年,整个中原大地千里坟场,万家丘墟。
这种惨象使建安、正始文人,触景生怀,伤心绝望,慨叹人生苦短,生命无常。
[关键词]汉末魏晋;文人;世纪病[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07)02-0113-05西方19世纪文学中有个流行词,叫“世纪病”,即世纪末思想。
它有深刻的社会、哲理和情感内涵,是忧生、忧时的文人对天下要乱、末日将临的一种心灵感应。
这种心灵感应,在东汉末年弥漫士林,造成了知识人群深重的心理灾难。
本文拟从天灾、人祸、文学三个方面来阐述汉末魏晋文人的“世纪病”心态,倾听他们的忧生之嗟、暮年之叹,体验现实的残酷,感受文学的温暖。
一、天灾———大瘟疫对士人身心的戕害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曾多次受到灾荒和动乱的侵扰,每产生一次大的灾荒、动乱,就会伴随着一次大的瘟疫爆发。
而汉末魏晋时期正是大瘟疫出现比较集中的时期,历史在曲折中改写,人类对疾病有着太多的无奈。
东汉末年,大疫流行,死人如麻,据《后汉书・灵帝纪》记载,从公元171-185年,15年内大疫5次暴发流行,其中尤以公元182年的大瘟疫为甚。
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就是趁大疫流行,咒说符水为人疗病,才取得人民的信任,立太平道的。
这5次大疫,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其影响深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以至思想领域。
因染瘟疫而死的人不计其数。
东汉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中沉痛地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尤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可见这种“伤寒”的死亡率极高。
《通鉴》记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
”可知流行瘟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
就是后来的赤壁之战,根据流行病学者的考证,让“强虏灰飞烟灭”的,不光是周瑜、诸葛亮的大火,更重要的是有“战争瘟疫”之称的斑疹伤寒。
当天下太平时,大疫不至于导致大乱,但有社会危机发生时,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
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可以说就是这些大疫直接导致的后果。
当时,对生命的忧患、对死亡的恐惧弥漫[收稿日期]2007-01-25[作者简介]丁沂璐(1983-),女,甘肃兰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到整个社会。
如《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诗所表达的: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
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
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
潜寂黄泉下,千载永不寤。
由黄巾起义到晋武帝泰始元年重新统一中国为止,战乱分裂绵延持续80余年,在这期间,瘟疫仍反复发作,人口锐减。
千里横尸,万里白骨,文人大为哀痛。
很多人认为汉末三国时期中国人口锐减是战争所致,殊不知其因并不仅是战乱,更重要的是饥荒和瘟疫。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记载:“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
丁未,大司马曹仁薨。
是月大疫。
”裴松之注:“贼中疠气疾疫,夹江涂地,恐相污染。
”汉献帝建安年间,瘟疫流行更加凶猛,席卷了整个中原地区。
特别是公元217年(建安22年)疫病猖獗,死者不计其数。
面对战争、瘟疫带来的惨状,曹操不得不发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叹。
魏文帝曹丕回忆他的少年时代时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
”又说“疾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
”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死亡的恐惧,对瘟疫的无可奈何。
那时中原“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
瘟疫疾病加上战乱兵灾,使建安正始时代成为一个色彩阴暗悲怆的时代。
由于疾病肆虐,不仅平民,当时的名士贵族,多夭折短寿。
例如所谓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以及当时的名士王弼、何晏诸辈,多数死于四十岁左右。
正始年间,善养生的阮籍,也仅活了五十余岁。
贵族士人尚如此,平民之命可想而知。
瘟疫猖獗疾病肆虐使生存问题日益尖锐化。
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寿命,服食各种药物。
所以《古诗十九首》中才有“服食求神仙,常为药所误”的悲叹。
后来魏晋文人服食“五石散”,其实也是为了防疫治病。
而“五石散”的药性发作会影响人的性格、行为,因此魏晋名士形骸放浪、无拘无束的所谓名士风度,实质上掩盖了他们对死亡恐惧的难言之隐。
明白了这些,就能深刻理解为何魏晋时期哲学中流行虚无主义,文学中充满忧生之嗟,暮年之叹的原因。
关于汉末大疫,何新先生在《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一文中认为,瘟疫是匈奴对汉朝生物战争的产物,汉末中原大瘟疫,就是这种战争产物的延续。
后半句话对笔者的启发很大,至于前半句,笔者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大瘟疫在汉代之前就时有发生,且有史可查,而汉代的大疫并不是匈奴用下过蛊的牛羊使汉军染病才导致的。
历史上,人类遭受这种大规模的传染病的袭击由来已久。
从商代开始就有“瘟疫”的文献记载。
《吕览》说:“疠疾,气不和之疾。
”认为气候反常易发生瘟疫,至于说到大规模的疾疫,成书于秦汉之间的《内经》中就有“瘟疬大行,远近咸若”的记载。
从以上文献资料来看,在汉匈战争之前我国已有大规模的瘟疫发生。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的于希贤先生认为,公元1—3世纪(西汉末至魏晋)是地理环境的突变时期。
“气候变迁异常激烈,导致生物圈和人类智慧圈的失调及震荡。
此间一些奇怪的病症、瘟疫就会预想不到地突然出现。
”[1]连东汉医学经典《伤寒论》也是以气候不正为根据来注意接触传染的防治的。
可见,汉朝的瘟疫肆虐与匈奴施巫术并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何新先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二、人祸———大动乱对士人身心的摧残在社会大治与稳定的时期,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个帝明臣智的统治集团在主持大政;相反,在社会大乱或动荡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个腐朽的集团把持着政权。
东汉后期正是后一种情形。
东汉末年,王权削弱,外戚专权,宦官干政,军阀混战,瘟疫大行,“盘石之宗”不复存在。
但是统治阶级仍然是“妖童美妾充满了内庭,女乐倡优排列于深堂”[2],国家一片乌烟瘴气。
外戚、宦官、军阀,无论哪方上台,带给人民的都是灾难。
东汉桓帝在位时,梁太后临朝,朝政完全控制在外戚梁冀手里。
当时,京都民谣:“直如弦,死道边。
曲如钩,反封侯。
”[3]就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不公正。
那时梁冀专擅威柄,事无巨细,都由他决断,对此汉桓帝非常不满。
梁皇后死后,桓帝与宦官单超共谋翦除梁冀,梁氏之煊赫显贵昙花一现。
宦官单超等五人,因诛灭梁氏有功,同日被封为列侯,时称“五侯”。
此后至灵帝末年的30年间,东汉的朝政一直为宦官所把持,宦官势力达到顶盛。
宦官本是一群不学无术的皇帝家奴,他们深居宫中,与世隔绝,“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
身体的缺陷使他们面对权势比常人更贪婪。
他们只争自己的权利得失,对于治国良策根本茫然无知。
所以宦官虽为后起势力,作恶却比外戚更甚。
他们专揽权柄,朝政日乱;安插亲信,培植党羽;兼并土地,掠夺民宅;收受货财,竞起第宅。
在宦官专权之下,东汉的朝政更加腐败,也更黑暗混乱。
东汉桓、灵之际的黑暗统治,引起了以天下家国为己任的士大夫集团的强烈不满。
他们与宦官集团之间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东汉末的两次“党锢”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延熹九年,司隶校尉李膺及党人二百余人,被遣归乡里,禁锢终身,不许作官。
第二次“党锢”事件从建宁二年始,延续十余年之久,且株连甚广,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甚至包括五服之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
东汉末年的“党锢”事件反映了东汉统治阶级政治危机的日益加深,它加速了东汉王朝的败亡。
当时,关于天下要乱、汉室将亡的说法已经纷纷纭纭。
如《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记:初,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单 :“此何祥也?” 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
天示恒象,此其应也。
”内黄殷登默而记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
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单 之言,其验兹乎!”(笔者按:《三国志》追记灵帝“黄龙见谯”之事,以为天下将乱,王者当兴。
后来曹丕代汉,当时人物还在,可为一证。
)又《后汉书・郭太传》记郭太言:或劝林宗仕进者。
对曰:“吾夜观乾象,昼查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
”又《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记: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又《后汉书・何 传》记:初, 见曹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汉家王朝已到了行将就木的光景,当时的有识之士已预见到了天下要亡,世界末日就要到来。
于是乎,他们中的有些人就希望天下大乱,以利于自己大展鸿图。
《古诗十九首》中“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诗句,就表达了他们的这种思想。
然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却表现了对死亡的恐惧,对人类希望的渺茫。
他们觉得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朝露,转瞬若尘,于是,《古诗十九首》中就表达了他们对人生的绝望。
如《青青陵上柏》中“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诗句,用松柏之常青、涧石之常存来反衬人生之短暂,它抒发了对生命的这种绝望情绪。
《今日良宴会》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明月皎夜光》中“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的诗句,都通过人生短暂,时光易逝,物象寂寥,深秋凄清,象征了汉家王朝的日薄垂暮。
于是,他们不禁发出了“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的对富贵荣华超越绝望的悲叹和对人生易逝、节序如流的感伤。
东汉末年大瘟疫反复发作,威胁着时人的生命,更压迫着文士的神经。
他们惧怕瘟疫,憎恨瘟疫,又无计可施。
于是发出了“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的哀鸣。
这种鸟之将死的哀嚎,体现了文士们的无助、悲凉,充满了无常绝望的世纪末情绪。
他们的朋友、亲戚都死光了,曹操说:“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令吾凄怆伤怀。
”古诗“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的描写,就表现了这种亲故罹灾,人鬼相隔的惨象。
在此危机四伏、朝不保夕的环境中,有一部分感到人生短促、求宦无望的文人,又不禁发生一连串的纵情享乐思想,“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表面上看这些诗句表现了他们放涤情志的人生享乐主义,但是,潇洒的外表下面掩盖的还是对死亡的恐惧和绝望。
这里还有个问题需要探讨,《古诗十九首》是无名氏的作品,如何断定是汉末文人的创作?关于这个问题,我赞同梁启超先生的观点,认为《古诗十九首》大都产生在建安时代,甚至更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