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人形象
- 格式:pdf
- 大小:57.40 KB
- 文档页数: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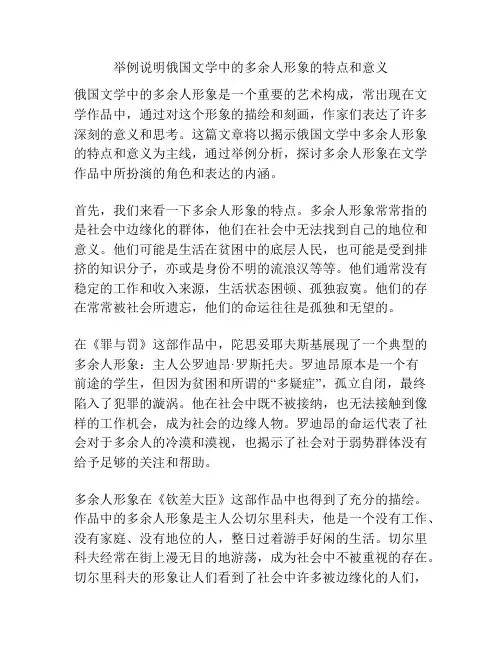
举例说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的特点和意义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是一个重要的艺术构成,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对这个形象的描绘和刻画,作家们表达了许多深刻的意义和思考。
这篇文章将以揭示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特点和意义为主线,通过举例分析,探讨多余人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表达的内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多余人形象的特点。
多余人形象常常指的是社会中边缘化的群体,他们在社会中无法找到自己的地位和意义。
他们可能是生活在贫困中的底层人民,也可能是受到排挤的知识分子,亦或是身份不明的流浪汉等等。
他们通常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生活状态困顿、孤独寂寞。
他们的存在常常被社会所遗忘,他们的命运往往是孤独和无望的。
在《罪与罚》这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现了一个典型的多余人形象:主人公罗迪昂·罗斯托夫。
罗迪昂原本是一个有前途的学生,但因为贫困和所谓的“多疑症”,孤立自闭,最终陷入了犯罪的漩涡。
他在社会中既不被接纳,也无法接触到像样的工作机会,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物。
罗迪昂的命运代表了社会对于多余人的冷漠和漠视,也揭示了社会对于弱势群体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帮助。
多余人形象在《钦差大臣》这部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描绘。
作品中的多余人形象是主人公切尔里科夫,他是一个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地位的人,整日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
切尔里科夫经常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成为社会中不被重视的存在。
切尔里科夫的形象让人们看到了社会中许多被边缘化的人们,他们没有奋斗的目标,没有充实的生活,他们只是一个多余的存在。
多余人形象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社会中的不公平和边缘化现象,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样的形象的刻画,提醒人们对于社会中边缘群体的关注和关怀。
多余人形象是作家们对社会中虚弱群体的关怀和呼唤,是对人们共情和同理心的唤起。
通过揭示多余人的命运,作家们希望唤起社会对于这些人的关注,改变社会对于边缘群体的态度和偏见,使他们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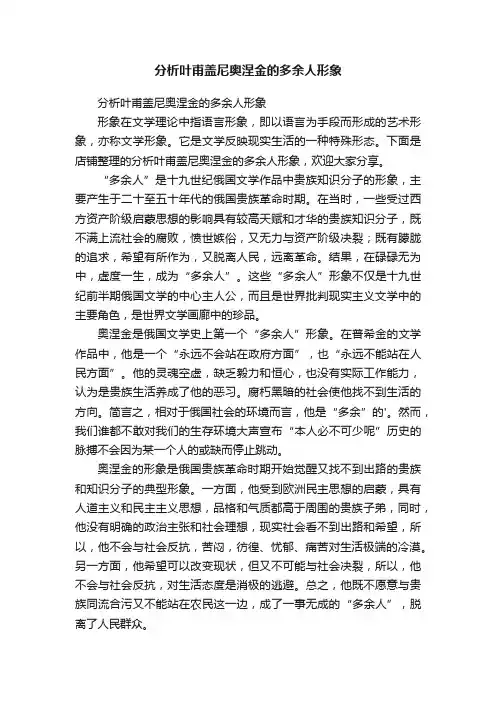
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形象在文学理论中指语言形象,即以语言为手段而形成的艺术形象,亦称文学形象。
它是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特殊形态。
下面是店铺整理的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欢迎大家分享。
“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主要产生于二十至五十年代的俄国贵族革命时期。
在当时,一些受过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具有较高天赋和才华的贵族知识分子,既不满上流社会的腐败,愤世嫉俗,又无力与资产阶级决裂;既有朦胧的追求,希望有所作为,又脱离人民,远离革命。
结果,在碌碌无为中,虚度一生,成为“多余人”。
这些“多余人”形象不仅是十九世纪前半期俄国文学的中心主人公,而且是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主要角色,是世界文学画廊中的珍品。
奥涅金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在普希金的文学作品中,他是一个“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也“永远不能站在人民方面”。
他的灵魂空虚,缺乏毅力和恒心,也没有实际工作能力,认为是贵族生活养成了他的恶习。
腐朽黑暗的社会使他找不到生活的方向。
简言之,相对于俄国社会的环境而言,他是“多余”的'。
然而,我们谁都不敢对我们的生存环境大声宣布“本人必不可少呢”历史的脉搏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或缺而停止跳动。
奥涅金的形象是俄国贵族革命时期开始觉醒又找不到出路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一方面,他受到欧洲民主思想的启蒙,具有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品格和气质都高于周围的贵族子弟,同时,他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现实社会看不到出路和希望,所以,他不会与社会反抗,苦闷,彷徨、忧郁、痛苦对生活极端的冷漠。
另一方面,他希望可以改变现状,但又不可能与社会决裂,所以,他不会与社会反抗,对生活态度是消极的逃避。
总之,他既不愿意与贵族同流合污又不能站在农民这一边,成了一事无成的“多余人”,脱离了人民群众。
奥涅金之所以是奥涅金,在于他所产生的“多余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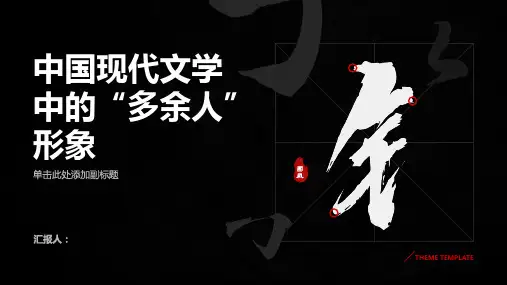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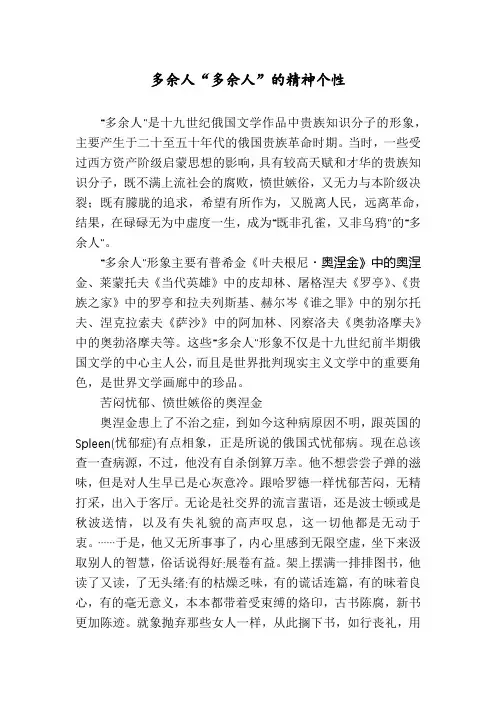
多余人“多余人”的精神个性“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主要产生于二十至五十年代的俄国贵族革命时期。
当时,一些受过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具有较高天赋和才华的贵族知识分子,既不满上流社会的腐败,愤世嫉俗,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既有朦胧的追求,希望有所作为,又脱离人民,远离革命,结果,在碌碌无为中虚度一生,成为“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多余人”。
“多余人”形象主要有普希金《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皮却林、屠格涅夫《罗亭》、《贵族之家》中的罗亭和拉夫列斯基、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别尔托夫、涅克拉索夫《萨沙》中的阿加林、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
这些“多余人”形象不仅是十九世纪前半期俄国文学的中心主人公,而且是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重要角色,是世界文学画廊中的珍品。
苦闷忧郁、愤世嫉俗的奥涅金奥涅金患上了不治之症,到如今这种病原因不明,跟英国的Spleen(忧郁症)有点相象,正是所说的俄国式忧郁病。
现在总该查一查病源,不过,他没有自杀倒算万幸。
他不想尝尝子弹的滋味,但是对人生早已是心灰意冷。
跟哈罗德一样忧郁苦闷,无精打采,出入于客厅。
无论是社交界的流言蜚语,还是波士顿或是秋波送情,以及有失礼貌的高声叹息,这一切他都是无动于衷。
……于是,他又无所事事了,内心里感到无限空虚,坐下来汲取别人的智慧,俗话说得好:展卷有益。
架上摆满一排排图书,他读了又读,了无头绪:有的枯燥乏味,有的谎话连篇,有的昧着良心,有的毫无意义,本本都带着受束缚的烙印,古书陈腐,新书更加陈迹。
就象抛弃那些女人一样,从此搁下书,如行丧礼,用黑色塔夫绸蒙上书架,连同上面那些尘封的书籍。
我跟他一样,远离闹市,抛开社交界的缛礼繁文,彼此情投意合,结为至交,我喜欢他的性格超群:常常于无意中陷入幻想,头脑冷静,智慧过人,连他的怪癖也不可模仿。
……我们倾吐积愫,置腹推心,谈得投机,津津有味。

世界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选修)一.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多余人”一词源于19世纪的俄罗斯文坛,自多余人鼻祖奥涅金之后,出现了毕巧林、罗亭、奥勃洛莫夫等形象系列。
赫尔岑将此类形象称为“多余人”。
1、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奥涅金愤世嫉俗又远离人民,厌恶贵族社会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自视清高,不愿虚度一生,又无明确的生活目标。
2、莱蒙托夫《当代英雄》:毕巧林的悲剧是俄国19世纪30年代贵族青年的悲剧,正如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序言》中指出:“决不是某一个人的肖像,这是一幅由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构成的肖像。
”3、屠格涅夫《罗亭》:罗亭是19世纪40年代贵族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罗亭自称:“我生来就像一根风滚草——一种茎梗容易折断,籽实被风一吹就像球似的滚得很远的植物。
”4、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奥勃洛摩夫生活在俄国农奴制死气沉沉的年代里,终日无所事事,躺卧成了他唯一的姿势。
这一形象暗示着贵族革命时期的结束,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时期的开始。
5、俄国文学的“多余人”:虽然是病态的畸形人,但在思想上却是“报晓的先觉者”,他们精神上的富有和思想上的敏锐,语言批判的锋利足可以使他们成为“英雄”,但意志上的怯懦和行动上的懒散,又使他们成了没有希望的精神叛逆者,或者说“失败的英雄”。
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从20年代开始,我国文坛陆续地出现一批中国式的“零余者”,不仅无法否认俄国文学对他们的深刻影响,更无法否认这批“零余者”与“多余人”的血缘关系。
1、鲁迅《孤独者》:魏连殳曾经认同西方进化论和个性解放,从而成为反封建的战士,但贫困迫使魏连殳违弃初衷,“躬行我先前所憎恨、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敬仰、所主张的一切”,并以一种愤懑无奈的心情与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人生,在一片赞扬声中,独自咀嚼着失败的悲哀死去。
2、柔石《二月》:萧涧秋是一个游离、彷徨于大革命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典型。
他是个极想有所为的青年,但时代的忧伤、身世的零落、气质的敏感构成的多情、孤独、软弱,却使他无所为,是彷徨中典型的“零余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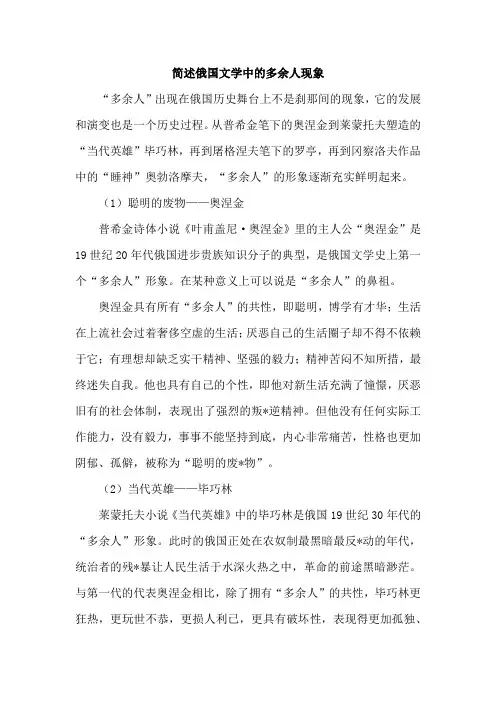
简述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现象“多余人”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不是刹那间的现象,它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
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到莱蒙托夫塑造的“当代英雄”毕巧林,再到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再到冈察洛夫作品中的“睡神”奥勃洛摩夫,“多余人”的形象逐渐充实鲜明起来。
(1)聪明的废物——奥涅金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是19世纪20年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
奥涅金具有所有“多余人”的共性,即聪明,博学有才华;生活在上流社会过着奢侈空虚的生活;厌恶自己的生活圈子却不得不依赖于它;有理想却缺乏实干精神、坚强的毅力;精神苦闷不知所措,最终迷失自我。
他也具有自己的个性,即他对新生活充满了憧憬,厌恶旧有的社会体制,表现出了强烈的叛*逆精神。
但他没有任何实际工作能力,没有毅力,事事不能坚持到底,内心非常痛苦,性格也更加阴郁、孤僻,被称为“聪明的废*物”。
(2)当代英雄——毕巧林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是俄国19世纪30年代的“多余人”形象。
此时的俄国正处在农奴制最黑暗最反*动的年代,统治者的残*暴让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的前途黑暗渺茫。
与第一代的代表奥涅金相比,除了拥有“多余人”的共性,毕巧林更狂热,更玩世不恭,更损人利已,更具有破坏性,表现得更加孤独、更加忧郁。
“狂热好动”与“人格分裂”是毕巧林的两大个性。
他是一个极端的冷热矛盾结合体。
一方面渴望生活,具有丰富的感情与奔放的激情,另一方面又对生活和人类丧失信心,往往激情与冷漠并存,显得喜怒无常。
他年轻聪明富有激情,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也因此对社会看的更透彻,心灰意冷的更彻底,可又止不住幻想,幻想过后又是更大的失望。
所以毕巧林的玩世不恭、碌碌无为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已是一个拥有高度自觉的自我意识的个体,一个冷静地怀疑着、分析着、求索着的个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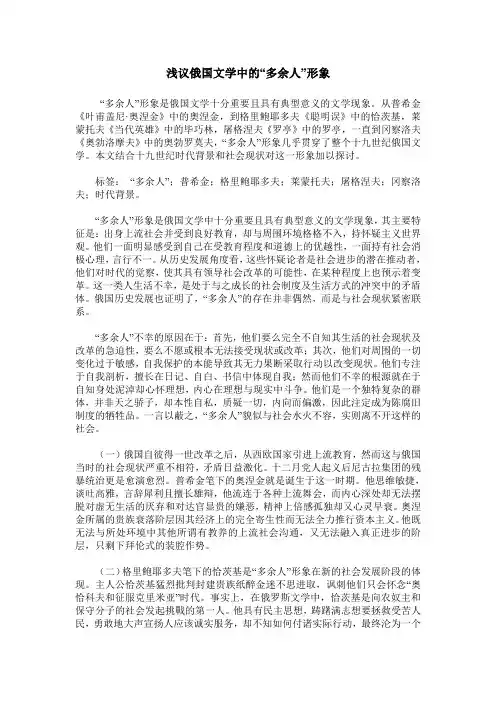
浅议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多余人”形象是俄国文学十分重要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
从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到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中的恰茨基,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一直到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罗莫夫,“多余人”形象几乎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俄国文学。
本文结合十九世纪时代背景和社会现状对这一形象加以探讨。
标签:“多余人”;普希金;格里鲍耶多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时代背景。
“多余人”形象是俄国文学中十分重要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其主要特征是:出身上流社会并受到良好教育,却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持怀疑主义世界观。
他们一面明显感受到自己在受教育程度和道德上的优越性,一面持有社会消极心理,言行不一。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些怀疑论者是社会进步的潜在推动者,他们对时代的觉察,使其具有领导社会改革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变革。
这一类人生活不幸,是处于与之成长的社会制度及生活方式的冲突中的矛盾体。
俄国历史发展也证明了,“多余人”的存在并非偶然,而是与社会现状紧密联系。
“多余人”不幸的原因在于:首先,他们要么完全不自知其生活的社会现状及改革的急迫性,要么不愿或根本无法接受现状或改革;其次,他们对周围的一切变化过于敏感,自我保护的本能导致其无力果断采取行动以改变现状。
他们专注于自我剖析,擅长在日记、自白、书信中体现自我;然而他们不幸的根源就在于自知身处泥淖却心怀理想,内心在理想与现实中斗争。
他们是一个独特复杂的群体,并非天之骄子,却本性自私,质疑一切,内向而偏激,因此注定成为陈腐旧制度的牺牲品。
一言以蔽之,“多余人”貌似与社会水火不容,实则离不开这样的社会。
(一)俄国自彼得一世改革之后,从西欧国家引进上流教育,然而这与俄国当时的社会现状严重不相符,矛盾日益激化。
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尼古拉集团的残暴统治更是愈演愈烈。
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就是诞生于这一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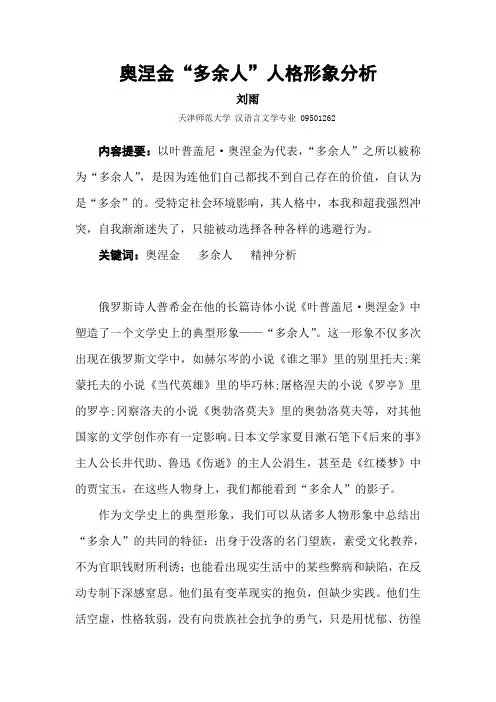
奥涅金“多余人”人格形象分析刘雨天津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09501262内容提要:以叶普盖尼·奥涅金为代表,“多余人”之所以被称为“多余人”,是因为连他们自己都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自认为是“多余”的。
受特定社会环境影响,其人格中,本我和超我强烈冲突,自我渐渐迷失了,只能被动选择各种各样的逃避行为。
关键词:奥涅金多余人精神分析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在他的长篇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中塑造了一个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多余人”。
这一形象不仅多次出现在俄罗斯文学中,如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里的别里托夫;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里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里的罗亭;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里的奥勃洛莫夫等,对其他国家的文学创作亦有一定影响。
日本文学家夏目漱石笔下《后来的事》主人公长井代助、鲁迅《伤逝》的主人公涓生,甚至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都能看到“多余人”的影子。
作为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我们可以从诸多人物形象中总结出“多余人”的共同的特征:出身于没落的名门望族,素受文化教养,不为官职钱财所利诱;也能看出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在反动专制下深感窒息。
他们虽有变革现实的抱负,但缺少实践。
他们生活空虚,性格软弱,没有向贵族社会抗争的勇气,只是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社会上无所作为。
“多余人”形象诞生于现实主义文学,必然是对现实社会生活中“多余人”生存状况的真实记录。
“多余人”大多是悲剧的,可是“多余人”的悲剧是如何诞生的?贵族知识分子们的“多余人”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关于这个问题,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依德提出的人格结构分析理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弗洛伊德在其著作《自我与本我》一书中将人格的结构概括为三个方面:本我、自我和超我。
本我(id)是在潜意识型态下的思想,代表思绪的原始程序——人最为原始的、属满足本能冲动的欲望,如饥饿、生气、性欲等;本我为与生俱来的,亦为人格结构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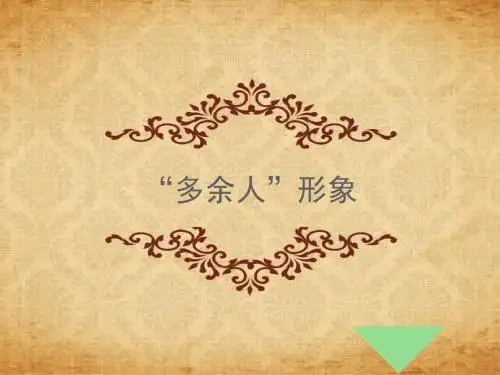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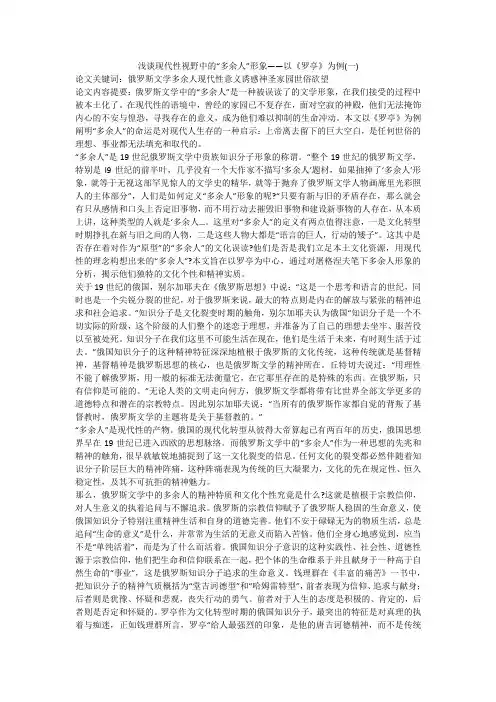
浅谈现代性视野中的“多余人”形象——以《罗亭》为例(一)论文关键词:俄罗斯文学多余人现代性意义诱惑神圣家园世俗欲望论文内容提要: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是一种被误读了的文学形象,在我们接受的过程中被本土化了。
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曾经的家园已不复存在,面对空寂的神殿,他们无法掩饰内心的不安与惶恐,寻找存在的意义,成为他们难以抑制的生命冲动。
本文以《罗亭》为例阐明“多余人”的命运是对现代人生存的一种启示:上帝离去留下的巨大空白,是任何世俗的理想、事业都无法填充和取代的。
“多余人”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形象的称谓。
“整个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特别是l9世纪的前半叶,几乎没有一个大作家不描写‘多余人’题材,如果抽掉了‘多余人’形象,就等于无视这部罕见惊人的文学史的精华,就等于抛弃了俄罗斯文学人物画廊里光彩照人的主体部分”,人们是如何定义“多余人”形象的呢?“只要有新与旧的矛盾存在,那么就会有只从感情和口头上否定旧事物,而不用行动去摧毁旧事物和建设新事物的人存在,从本质上讲,这种类型的人就是‘多余人…。
这里对“多余人”的定义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文化转型时期挣扎在新与旧之间的人物,二是这些人物大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这其中是否存在着对作为“原型”的“多余人”的文化误读?他们是否是我们立足本土文化资源,用现代性的理念构想出来的“多余人”?本文旨在以罗亭为中心,通过对屠格涅夫笔下多余人形象的分析,揭示他们独特的文化个性和精神实质。
关于19世纪的俄国,别尔加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说:“这是一个思考和语言的世纪,同时也是一个尖锐分裂的世纪,对于俄罗斯来说,最大的特点则是内在的解放与紧张的精神追求和社会追求。
”知识分子是文化裂变时期的触角,别尔加耶夫认为俄国“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的迷恋于理想,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被处死。
知识分子在我们这里不可能生活在现在,他们是生活于未来,有时则生活于过去。
摘要:19世纪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
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
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
“多余人”作为一个人物系列,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环境,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
然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性。
本文着重分析“多余人”形象共同特征以及他们的发展变化规律。
关键词:多余人共同特征发展与演化现实意义正文:19世纪上半叶,西欧各先进国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而俄国封建农奴制内部,新的资本主义已经萌生,同时,农民起义、暴动风起云涌,专制的危机已渐露倪端,农奴制度的崩溃已不可逆转,1812年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民族意识普遍觉醒,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对专职农奴制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日益高涨。
在这种情势下,贵族青年中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分化:一部分人渴望为祖国做一番事业,要求改变现存制度,这些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另一部分人仍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企图永久保持贵族特权地位;而第三种人则是贵族青年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感到时代的风暴即将来临,不甘心和贵族阶级一道灭亡,但阶级的局限又使他们没有勇气与能力去参加革命斗争,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景,因此终日彷徨苦闷、焦躁不安,即染上了当时人们所说的“时代的忧郁病”,这一类人也即我们所谓的“多余人”。
“多余人”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中,后来被俄罗斯文学界和批评界用来称谓具有类似奥涅金的性格气质和历史命运的那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
“多余人”之多余是指贵族知识分子相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而言,他们具有思考能力,智慧过人,但却无法脱离他们委身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并采取行动,或者,按照赫尔岑所说,他在其安身立命的环境中时“多余的人”,他并不具有从这种环境中脱身出来的一种坚毅的性格的必要力量,他们收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善于独立思考,对社会、生活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都试图发现生活的真理和寻找内心的和谐与自由,但是屡屡受挫,以至于无法适应现实生活而被现实生活拒之门外。
略论中国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人物形象浅析内容提要:“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生活在中国封建末世的曹雪芹,经历了曹氏家庭由盛到衰豪华奢侈的生活之后,带着泣血刻骨之痛,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写出了富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红楼梦》。
贾宝玉这个具有悲剧性命运的人物,其内涵虽然丰富,但仍然是现实社会中一个多余人的典型。
贾宝玉无“补天”之才而被强逼“补天”。
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木石前盟”终被“金玉良缘”替代。
宝玉为晴雯凭吊,做祭文“芙蓉女儿诔”。
这与中国封建社会“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大相径庭。
贾宝玉虽然具有一定的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和平等的意识,但身为贵公子的他,受时代之局限性,仍然摆脱不了旧式封建思想的“胎记”。
贾宝玉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始终找不到一条通向自由生活的路,才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式人物,他在现实社会中仍是一个多余人的典型。
文学小说中的多余人形象,是指一些面对现实社会生活感到厌倦和不满,但又摆脱不了世俗的习惯和偏见的人。
他们有聪明的头脑,想过有意义的生活,但又缺乏勇气和毅力,整日苦闷忧郁,不能自拔,终于成为一事无成的“多余人”。
多余人形象的出现,与作者及作品所处的社会实际无不联系,有时甚至是作者自身的写照。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生活在中国封建末世的曹雪芹,经历了曹氏家庭由盛到衰豪华奢侈的生活之后,带着泣血刻骨之痛,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写出了富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红楼梦》(后四十回为高鹗续作)。
其中,贾宝玉是最具有个性色彩、最为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
从“脂砚斋”至今评贾宝玉,众说纷纭,角度各一,或褒或贬,瑕玉互见。
而笔者斗胆认为,贾宝玉这个具有悲剧性命运的人物,其内涵虽然丰富,但仍然是现实社会中一个多余人的典型。
何以如是之称,这就要紧密联系曹雪芹所生活的封建时代和《红楼梦》中所反映的贾宝玉的个性意识来认识。
曹雪芹作《红楼梦》,多数研究者认为是在乾隆年间,时值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当时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试析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与中国现代文学“零余者俄国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生活在贵族阶级趋向没落的时期,在反动的专制政体和农奴制下感到窒息,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因为远离人民,无法摆脱贵族立场,缺乏生活目的,不能有所作为。
正如赫而岑所说的:“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同时也“永远不能站到人民方面”,只能作为一个社会的“多余人”。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赫而岑《谁的罪过》里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里的毕乔林;屠格涅夫《罗亭》里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等,都是“多余人”的代表。
普希金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小说是用诗体写成的,是一个重大的创新。
它的发表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确立的标志。
奥涅金的形象是俄国封建社会贵族青年的一种典型,他虽然受过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不满于贵族社会的庸碌,自视清高,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但贵族的生活方式又使他灵魂空虚,毫无能力,无所作为,成了社会的“多余人”。
这样,奥涅金就成为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
小说通过这一形象,塑造了二十年代贵族青年的典型,反映了当时贵族青年的苦闷、彷徨和追求。
在揭露和批判贵族社会的腐败和丑恶方面具有相当的力量。
奥涅金也因此在俄国多余人形象系列中成为最重要的,最具色彩的,最有代表性的多余人形象。
在其他多余人形象中,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乔林,在二三十年代曾是贵族社会里的佼佼者,是一个对上流社会强烈不满的贵族青年。
可是他摆脱不了贵族生活,没有理想,玩世不恭,感到苦闷绝望;他时时进行自我心理分析,既否定一切,也蔑视自己,因而也成为社会的“多余人”。
还有屠格涅夫《罗亭》里的罗亭,也是多余人形象,他能言善辩,热情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四十年代黑暗统治时,起过进步作用。
但到五十年代需要行动的时候,“多余人”只是一些语言多于行动的人,已经担负不起改革现实的任务了。
如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尽管他“有黄金般的心灵”,但他只不过是一个剥削阶级寄生虫的典型。
“多余人”艺术形象分析与研究“多余人”是文学、艺术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特殊形象之一。
他们通常出现在俄罗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文学作品中,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大师的作品中。
这些人物通常被描绘为聪明、敏感、有才华,但却饱受内心的痛苦和挣扎。
本文将从“多余人”艺术形象入手,深入分析这些角色的个性、内心世界、特点等,同时探讨其艺术价值和产生背景。
矛盾性格:他们通常具有复杂的内心世界,既敏感又脆弱,既富有激情又充满痛苦。
他们的行为和决定常常受到内心矛盾的困扰,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性格。
知识分子形象:这些人物通常是有文化、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追求真理、美和正义,但却往往在现实面前感到无助和困惑。
社会边缘人:他们不属于社会的主流群体,常常被视为局外人或边缘人。
他们与社会格格不入,却又无法彻底脱离社会。
悲剧命运:这些人物的命运通常以悲剧收场,他们的矛盾性格和无助感导致他们无法与周围的人建立和谐的关系,最终常常陷入孤独和绝望。
“多余人”艺术形象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
他们通常被描绘为具有强烈的内心活动和复杂的情感世界。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罪与罚》中,主角拉斯科尔尼科夫便是一个典型的“多余人”形象。
他具有极高的聪明才智,但却陷入了罪恶与良心的挣扎之中。
作者通过细腻的心理描绘和激烈的情感冲突,展现了一个复杂而真实的“多余人”形象。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人公列文也是一个典型的“多余人”形象。
他身处上流社会,却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感到困惑和不安。
他追求真爱,却陷入伦理与情感的矛盾之中。
作者通过列文的视角,展示了19世纪俄罗斯社会的矛盾和复杂性。
“多余人”艺术形象的产生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在俄罗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现实感到困惑和无助。
这一时期,俄罗斯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多余人”形象,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等。
“多余人”形象的现实意义摘要: 19世纪前半叶,在俄国文学中出现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
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谘罗摩夫等一系列形象。
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形象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本文着重阐述“多余人”形象的社会现实意义。
关键词多余人典型特征现实意义一、“多余人”及其典型特征19世纪上半叶,西欧各先进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而俄国封建农奴制内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已经萌生,专制政体的危机已经初露短倪,农奴制度的崩溃已不可避免。
同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以及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影响和推动下,引发了贵族青年深刻的阶级分化:他们之中绝大部分,隐约感觉到时代和社会的变动,极不满意现实,厌恶当局,又脱离群众,远离革命;既不甘心沉沦到底,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因而在生活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在现实社会中感到沉沦压抑,精神上焦躁不安,又彷徨不定,这样也就决定了他们一生当中必然无所事事、毫无作为、空虚而又无聊。
这类人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被称为“多余人”。
俄国文学史上的“多余人”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具有一些相似或相近的特征:他们大多出身贵族阶级,有着良好的教养和聪明的头脑,大多数人接受过西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最初活跃在上流社会,很快便厌倦了那里空虚乏味的生活,想寻求有意义的新生活,然而,他们脱离人民大众,又不了解俄国的社会实际情况,陈腐的贵族教育既没有使他们获得有用的知识,更没有培养他们克服困难的毅力,几经挣扎,最终还是一事无成,成为毫无用处的“多余人”,同时,激烈的内心矛盾与冲突、沉重的精神痛苦与郁闷也是这类人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历程“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莱蒙托夫塑造毕巧林,到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这一形象逐渐变得鲜明和丰满。
从充满激情、骚动不安的奥涅金;到忧郁、悲观、矛盾、孤愤的毕巧林;再到充满时代热情,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过的罗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