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阳辞赋散文研究
- 格式:doc
- 大小:13.87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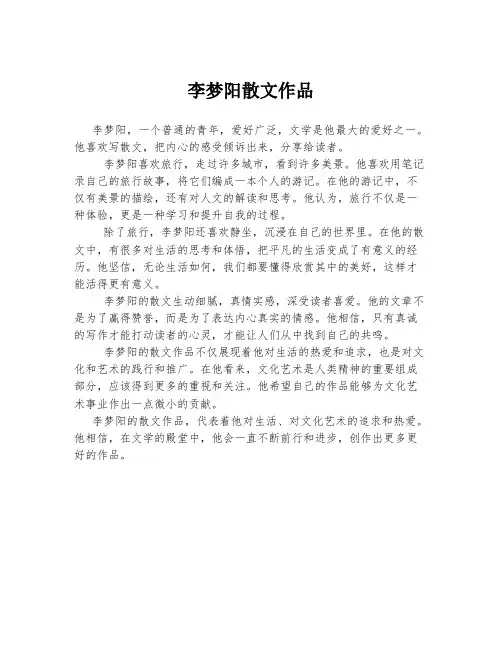
李梦阳散文作品
李梦阳,一个普通的青年,爱好广泛,文学是他最大的爱好之一。
他喜欢写散文,把内心的感受倾诉出来,分享给读者。
李梦阳喜欢旅行,走过许多城市,看到许多美景。
他喜欢用笔记录自己的旅行故事,将它们编成一本个人的游记。
在他的游记中,不仅有美景的描绘,还有对人文的解读和思考。
他认为,旅行不仅是一种体验,更是一种学习和提升自我的过程。
除了旅行,李梦阳还喜欢静坐,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在他的散文中,有很多对生活的思考和体悟,把平凡的生活变成了有意义的经历。
他坚信,无论生活如何,我们都要懂得欣赏其中的美好,这样才能活得更有意义。
李梦阳的散文生动细腻,真情实感,深受读者喜爱。
他的文章不是为了赢得赞誉,而是为了表达内心真实的情感。
他相信,只有真诚的写作才能打动读者的心灵,才能让人们从中找到自己的共鸣。
李梦阳的散文作品不仅展现着他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也是对文化和艺术的践行和推广。
在他看来,文化艺术是人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关注。
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为文化艺术事业作出一点微小的贡献。
李梦阳的散文作品,代表着他对生活、对文化艺术的追求和热爱。
他相信,在文学的殿堂中,他会一直不断前行和进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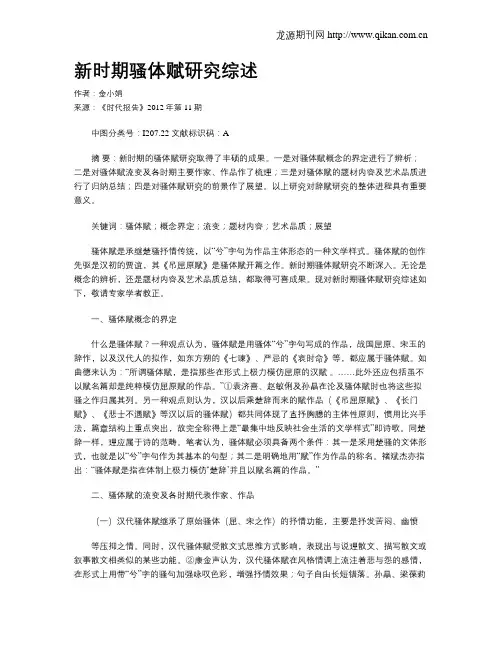
新时期骚体赋研究综述作者:金小娟来源:《时代报告》2012年第11期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摘要:新时期的骚体赋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是对骚体赋概念的界定进行了辨析;二是对骚体赋流变及各时期主要作家、作品作了梳理;三是对骚体赋的题材内容及艺术品质进行了归纳总结;四是对骚体赋研究的前景作了展望。
以上研究对辞赋研究的整体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骚体赋;概念界定;流变;题材内容;艺术品质;展望骚体赋是承继楚骚抒情传统,以“兮”字句为作品主体形态的一种文学样式。
骚体赋的创作先驱是汉初的贾谊,其《吊屈原赋》是骚体赋开篇之作。
新时期骚体赋研究不断深入。
无论是概念的辨析,还是题材内容及艺术品质总结,都取得可喜成果。
现对新时期骚体赋研究综述如下,敬请专家学者教正。
一、骚体赋概念的界定什么是骚体赋?一种观点认为,骚体赋是用骚体“兮”字句写成的作品,战国屈原、宋玉的辞作,以及汉代人的拟作,如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等,都应属于骚体赋。
如曲德来认为:“所谓骚体赋,是指那些在形式上极力模仿屈原的汉赋。
……此外还应包括虽不以赋名篇却是纯粹模仿屈原赋的作品。
”①袁济喜、赵敏俐及孙晶在论及骚体赋时也将这些拟骚之作归属其列。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汉以后乘楚辞而来的赋作品(《吊屈原赋》、《长门赋》、《悲士不遇赋》等汉以后的骚体赋)都共同体现了直抒胸臆的主体性原则,惯用比兴手法,篇章结构上重点突出,故完全称得上是“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即诗歌。
同楚辞一样,理应属于诗的范畴。
笔者认为,骚体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采用楚骚的文体形式,也就是以“兮”字句作为其基本的句型;其二是明确地用“赋”作为作品的称名。
褚斌杰亦指出:“骚体赋是指在体制上极力模仿…楚辞‟并且以赋名篇的作品。
”二、骚体赋的流变及各时期代表作家、作品(一)汉代骚体赋继承了原始骚体(屈、宋之作)的抒情功能,主要是抒发苦闷、幽愤等压抑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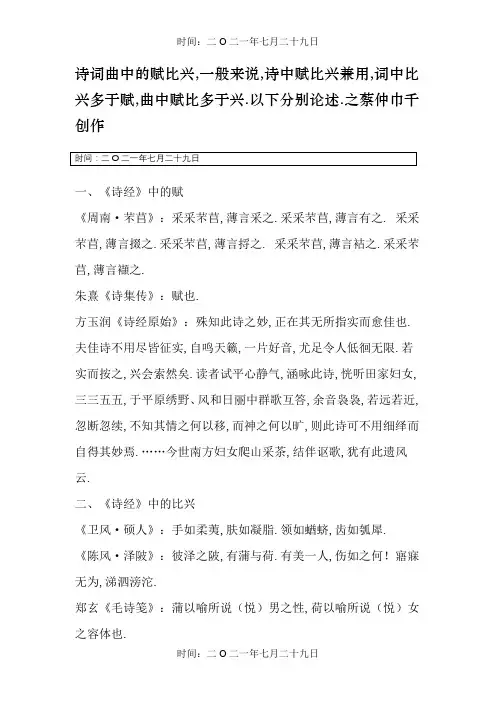
一、《诗经》中的赋《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朱熹《诗集传》:赋也.方玉润《诗经原始》:殊知此诗之妙,正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夫佳诗不用尽皆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徊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用细绎而自得其妙焉.……今世南方妇女爬山采茶,结伴讴歌,犹有此遗风云.二、《诗经》中的比兴《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郑玄《毛诗笺》:蒲以喻所说(悦)男之性,荷以喻所说(悦)女之容体也.三,赋比兴暗示手法的作用赋是最基本的,最经常使用的一种暗示手法.它的特点就是敷陈、直言,即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比分为比如和比力.比体诗的特点是以彼物写此物,诗中所描写的事物其实不是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对象,而是借用打比如的方法,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例如,《硕鼠》一诗中,就是运用了比的暗示手法,通过描写令人憎恶的老鼠,将奴隶主贪婪残酷的赋性暗示的淋漓尽致.为什么不直接表达而要用比呢?运用比力表达喜爱的事物,可以使它栩栩如生,给人亲切之感;用它暗示丑陋的事物,可以使它原形毕露,给人厌恶之感.兴,即起兴,在一首诗的开头,或一章诗的开头.先让我们来看一首诗.《风雨》中运用兴的暗示手法的句子是“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风雨如悔,鸡鸣不已.”为什么不直接说出要写的内容,而要先言他物呢?通过对《诗经》的研究,有些诗中的兴起到了渲染气氛的作用,例如,《风雨》写的是在薄暮时节,外面下班着小雨,刮着风,女主人公正在思念着自己的夫君,此时,听见了外面的鸡鸣声.烘托出女主人公的相思、愁怅之情.兴在这里就起到了渲染了一种凄凉的气氛,加深抒情女主人公的相思之情.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有些诗中的兴没有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与下文也没有什么联系.例如,《黄鸟》的“交交黄鸟,止于棘,止于楚,止于桑.与下文的子车家的三个儿子为秦穆公殉葬没有联系,兴就起到了提示、渲染一种气氛,帮我们完成从日常生活到诗歌欣赏的过度作用.人们经常把比、兴两种暗示手法截然分开,在研究中我们认为,比兴两种暗示手法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些诗中是有一定联系的,例如,《氓》中,就是用自然现象来女主人公感情生活的变动,由起兴的诗句来引出表达感情生活的诗句,由叶子的鲜嫩而至的枯黄,来比如感情生活的幸福而至的痛苦,这里的兴就具有了比的作用.兴在诗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失去它,诗歌也就失去了美学价值,失去了感染力.赋是最基本的,最经常使用的一种暗示手法.它的特点就是敷陈、直言,即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比分为比如和比力.比体诗的特点是以彼物写此物,诗中所描写的事物其实不是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对象,而是借用打比如的方法,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例如,《硕鼠》一诗中,就是运用了比的暗示手法,通过描写令人憎恶的老鼠,将奴隶主贪婪残酷的赋性暗示的淋漓尽致.为什么不直接表达而要用比呢?运用比力表达喜爱的事物,可以使它栩栩如生,给人亲切之感;用它暗示丑陋的事物,可以使它原形毕露,给人厌恶之感.兴,即起兴,在一首诗的开头,或一章诗的开头.先让我们来看一首诗.《风雨》中运用兴的暗示手法的句子是“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风雨如悔,鸡鸣不已.”为什么不直接说出要写的内容,而要先言他物呢?通过对《诗经》的研究,有些诗中的兴起到了渲染气氛的作用,例如,《风雨》写的是在薄暮时节,外面下班着小雨,刮着风,女主人公正在思念着自己的夫君,此时,听见了外面的鸡鸣声.烘托出女主人公的相思、愁怅之情.兴在这里就起到了渲染了一种凄凉的气氛,加深抒情女主人公的相思之情.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有些诗中的兴没有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与下文也没有什么联系.例如,《黄鸟》的“交交黄鸟,止于棘,止于楚,止于桑.与下文的子车家的三个儿子为秦穆公殉葬没有联系,兴就起到了提示、渲染一种气氛,帮我们完成从日常生活到诗歌欣赏的过度作用.人们经常把比、兴两种暗示手法截然分开,在研究中我们认为,比兴两种暗示手法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些诗中是有一定联系的,例如,《氓》中,就是用自然现象来女主人公感情生活的变动,由起兴的诗句来引出表达感情生活的诗句,由叶子的鲜嫩而至的枯黄,来比如感情生活的幸福而至的痛苦,这里的兴就具有了比的作用.兴在诗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失去它,诗歌也就失去了美学价值,失去了感染力.“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暗示手法. 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携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如之意.《诗经》中用比如的处所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动.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零的变动来比如恋爱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如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暗示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力共同的手法.“兴”字的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年夜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没有意义上的关系,暗示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晓风》,开头“鴥彼晓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其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成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如、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发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力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如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季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纷歧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国风·周南·关雎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国风·召南·驺虞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国风·召南·江有汜比: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国风·卫风·硕人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国风·卫风·淇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小雅·鹤鸣兴: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卷耳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夭赋比兴是诗经的主要三种暗示手法.是中国古代对诗歌暗示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年夜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赋:平铺直叙,铺陈、排比.相当于现在的排比修辞方法.比:比如.相当于现在的比如修辞方法.兴:托物起兴,先言他物,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事物、思想、感情.相当于现在的象征修辞方法.兴就是以情寓于象中,此象乃是意象也,故兴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赋陈,一作铺陈.铺排,是铺陈、排比的简称.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铺陈与排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用的.铺排系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依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秘闻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 在赋体中,尤其是富丽华美的汉赋中,赋法被广泛地采纳.汉乐府和汉代某些五言诗也与汉赋互相影响,更将铺陈与排比相结合,相得益彰.比比即喻,是其中最基本的手法,用得最为普遍. 一般说,用来作比的喻体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形象生动,鲜明突失事物(事情)的特征.兴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激发读者的联想,增强了意蕴,发生了形象鲜明、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纷歧.汉代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发生了较年夜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如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如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暗示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分歧,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这里,除讲“赋”的特点是暗示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力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暗示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难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诗经》的解释,经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年夜义”,例如把恋爱诗《关雎》说成暗示“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分歧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外,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而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暗示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获得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份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年夜量运用了比如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年夜”,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暗示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需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该有诗味或“滋味”(《诗品序》),从而把艺术的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暗示特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和对传统的突破.正是由于这一点,后来一些株守传统观念的人对钟嵘的这一贡献不单不予供认,而且颇加非议,如说他“解比兴,又与诂训殊乖”(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钟嵘还正确地指出“赋、比、兴”“三义”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不能割裂开来看待和运用.他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因此,他要求兼采三者之长:“闳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即认为真正的好诗,既不能单用“比兴”以致“意深”、晦涩,又不能单用“赋”法以致“意浅”、芜累,只有兼采三者之长,酌情运用,才华感动听,“使味之者无极”.钟嵘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写诗要把事情写清楚,为读者所了解,就少不了要用“赋”的手法.同时,诗歌要抒发情思,驰骋想象,感染读者,耐人寻味,就又少不了要用“比兴”的手法.钟嵘的“闳斯三义,酌而用之”以及“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观点,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的,对后代诗论有很年夜的影响.唐宋时期的论述唐代评论家对“比兴”的论述,又有新的发展,即不单仅把它看作暗示手法,而是赋予了美刺讽谕的内容要求.这跟郑玄的说法,是有继承关系的.不外,郑玄是用政教美刺去牵强附会地解释“比兴”的转义和《诗经》的篇章;唐人则是运用“比兴”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创作主张,强调诗歌应发挥美刺讽谕的作用,这就不存在牵强附会的问题.刘勰、钟嵘谈论“比兴”,有时也是涉及内容的,如刘勰所说的“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钟嵘所说的“兴托不奇”、“托谕清远”(《诗品》卷中)等.唐代评论家更进一步把“比兴”称之为“兴寄”,如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修竹篇序》,元稹批评唐初“沈、宋之不存寄兴”(《叙诗寄乐天书》),而认为自己的诗“稍存兴寄”(《进诗状》)等,所说“兴寄”,也就是“比兴”.陈子昂又说:“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喜(嘉)马参军相遇醉歌序》)殷□也批评齐梁诗风说:“理则缺乏,言常有余,都无比兴,但贵轻艳.”(《河岳英灵集》序)所说“比兴”,也就是“兴寄”.可见,唐人论“比兴”,年夜都是从美刺讽谕着眼的.柳宗元就明确地指出:“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杨评事文集后序》)白居易甚至还把“美刺兴比”作为一个词组来使用,如说:“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谓之讽谕诗.”(《与元九书》)他们标举“兴寄”或“比兴”,强调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发挥社会作用,这对增进唐诗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宋代宋代学者对“赋、比、兴”作了比力深入的研究.欧阳修在《诗转义》中、郑樵在《诗辨妄》中,都对汉儒解诗的牵强附会之风提出了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仲蒙和朱熹,他们对“赋、比、兴”的解释,对后世发生了很年夜的影响.李仲蒙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引)他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所谓“叙物”,不单是一个“铺陈其事”的问题,还必需和“言情”结合起来,把作者的情感和客观的物象暗示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这就比传统的解释年夜年夜前进了一步,更加符合诗歌创作中对“赋”这一暗示手法的要求,从而对后来关于“赋”的研究发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为数未几的古代叙事诗中,也存在着这类范例.例如长达1745字的叙事诗《孔雀西北飞》,除发端两句用“孔雀西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外,通篇全用“赋”体,而叙述惟妙惟肖、入迷入化,正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覆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其后象北朝的《木兰诗》、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也都具用“赋”法而暗示出类似的特点.所谓“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单是一个运用比如进行修辞的问题,还必需在比如中寄托作者深挚的感情.这样的“比”法,自然就会具有艺术的感染力,而不会象汉赋那样成为各种比如性的词采的堆砌排比.所谓“触物”,即接触外物而引起作者主观感情的感动,也就是梅尧臣所说的“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又把情感浸透、寄托于所描写的物象中.显然,李仲蒙对“赋、比、兴”的论述,较之他以前的许多解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的这些论点,后来曾被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杨慎的《升庵诗话》等辗转引载,后人的见解也年夜都是对他的观点的引申和发挥,很少新的突破.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这和黄彻所说的“赋者,铺陈其事;比者,引物连类;兴者,因事感发”(见《诗人玉屑》),基本是相同的.朱熹虽然比力准确地说明了“赋、比、兴”作为暗示手法的基本特征,但他的概括不如李仲蒙的解释更切合文学创作的实际.他的说法之所以在后世发生了较年夜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学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受到统治者年夜力建议的缘故.朱熹虽然也批评过汉儒解说《诗经》中某些迂腐论点,可是,他自己论诗也不乏微言年夜义的迂腐见解,如他在《诗集传》中注《关雎》一诗说:“兴也.”“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像这样来分析《关雎》的“兴”义,显然是受了《诗序》、《毛传》、《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而且他也没有象钟嵘那样注意到“三义”在创作中不成或缺的互相作用,往往把一首诗简单地归之为“赋也”、“比也”或“兴也”,甚至对《楚辞》也这样加以分解,结果不能不生穿硬凿,招致后人的讥议.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就说:“风诗三百,……后人强事臆测,系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年夜义的做法,在宋及宋以后仍是比力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牵强附会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年夜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年夜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不单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年夜兴文字狱,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明清时期的研究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诗集自序》)在那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艺术思维和暗示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否则的话,就会影响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力精辟的.另外,像王夫之所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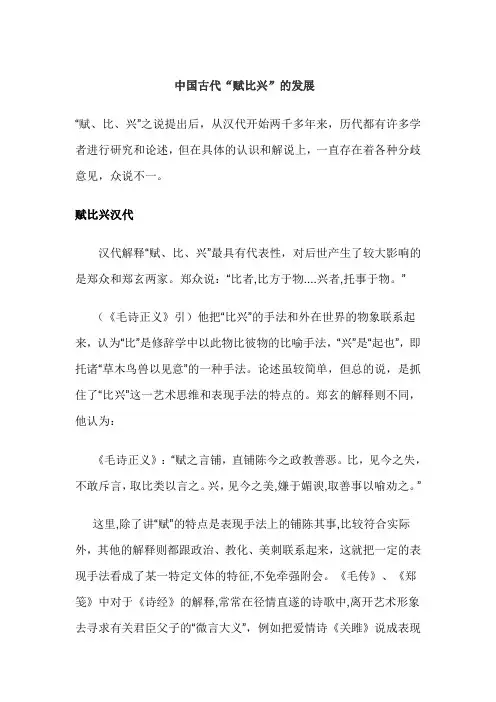
中国古代“赋比兴”的发展“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
赋比兴汉代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
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
”(《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
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
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毛诗正义》:“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
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
《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
”(《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
赋比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
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
”(《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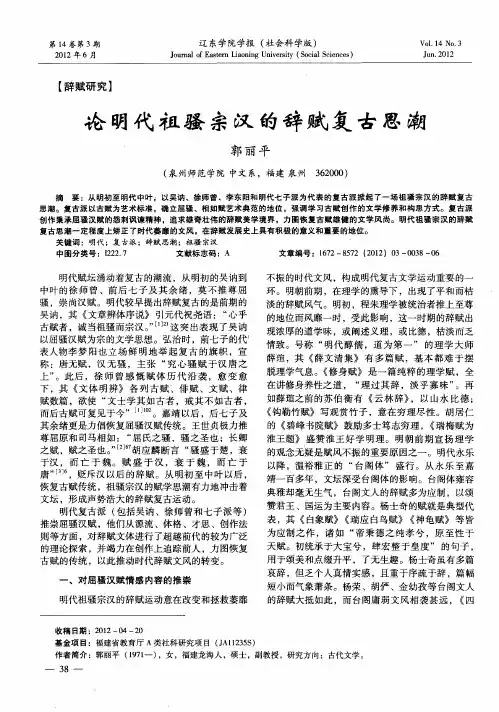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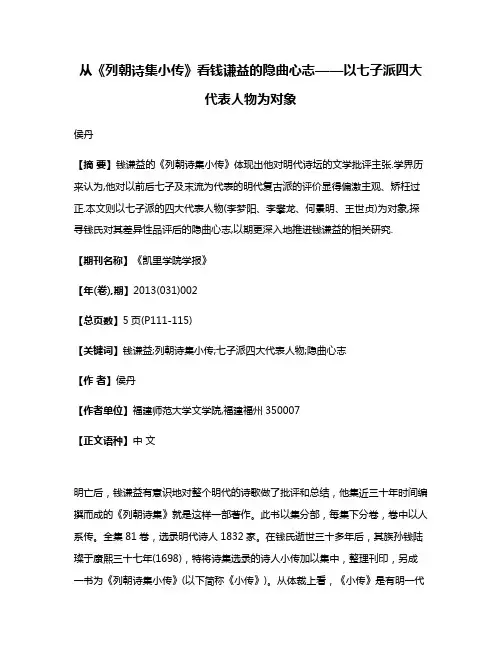
从《列朝诗集小传》看钱谦益的隐曲心志——以七子派四大代表人物为对象侯丹【摘要】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体现出他对明代诗坛的文学批评主张.学界历来认为,他对以前后七子及末流为代表的明代复古派的评价显得偏激主观、矫枉过正.本文则以七子派的四大代表人物(李梦阳、李攀龙、何景明、王世贞)为对象,探寻钱氏对其差异性品评后的隐曲心志,以期更深入地推进钱谦益的相关研究.【期刊名称】《凯里学院学报》【年(卷),期】2013(031)002【总页数】5页(P111-115)【关键词】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七子派四大代表人物;隐曲心志【作者】侯丹【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正文语种】中文明亡后,钱谦益有意识地对整个明代的诗歌做了批评和总结,他集近三十年时间编撰而成的《列朝诗集》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此书以集分部,每集下分卷,卷中以人系传。
全集81卷,选录明代诗人1832家。
在钱氏逝世三十多年后,其族孙钱陆璨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特将诗集选录的诗人小传加以集中,整理刊印,另成一书为《列朝诗集小传》(以下简称《小传》)。
从体裁上看,《小传》是有明一代的诗苑传;从内容上看,它是明代诗歌发展的一部流变史;从理论上看,它是钱氏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之一。
《小传》于甲、乙两集中论及明初诗人,言其生平部分多为钱氏自述;论其诗才,则多引他人之语,钱氏很少作褒贬,似显其客观公允的一面。
如论袁凯诗,引李梦阳、何景明、程嘉燧之言;论高启诗,用张习、程嘉燧语;论刘崧诗,引刘永之序其诗之言;论孙蕡诗,引黄佐、《明兴杂记》言。
可是从丙集(即弘治年)开始,钱氏直接品评诗人的情况大增。
尤其是对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以及相关的诗人,无论是追随者还是反对者,钱氏均直接参与褒贬评论。
对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及其追随者的关注,是钱氏在整部《小传》中着力最多的部分,他曾在《题徐季白诗卷后》一文中所言:“余之评诗,与当世牴牾者,莫甚于二李及弇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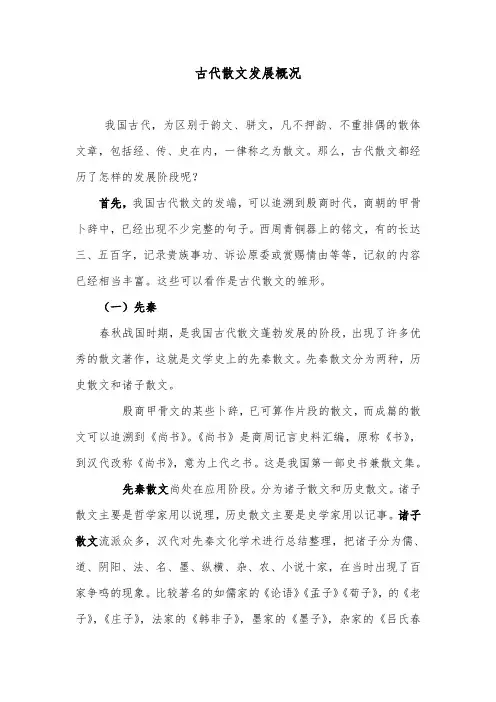
古代散文发展概况我国古代,为区别于韵文、骈文,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在内,一律称之为散文。
那么,古代散文都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呢?首先,我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
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的长达三、五百字,记录贵族事功、诉讼原委或赏赐情由等等,记叙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
这些可以看作是古代散文的雏形。
(一)先秦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
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殷商甲骨文的某些卜辞,已可算作片段的散文,而成篇的散文可以追溯到《尚书》。
《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汇编,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上代之书。
这是我国第一部史书兼散文集。
先秦散文尚处在应用阶段。
分为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
诸子散文主要是哲学家用以说理,历史散文主要是史学家用以记事。
诸子散文流派众多,汉代对先秦文化学术进行总结整理,把诸子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在当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
比较著名的如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的《老子》,《庄子》,法家的《韩非子》,墨家的《墨子》,杂家的《吕氏春秋》等。
诸子散文往往寓理于形,借助形象陈义说理,其中含有叙事成分,还有许多寓言故事和生动的比喻。
先秦时期的历史散文以记言、记事为主。
内容更丰富,形式多样。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料编纂的一部编年史,是一部大事记,《春秋》记事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一字一句都暗含褒贬之意,后人称之为“微言大义”或“春秋笔法”。
现存的有《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世称“春秋三传”。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相传为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春秋》所作,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
《左传》被推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初步成熟。
《国语》是一部国别史,是各国史料的汇编,一般认为左丘明所写,文学性不如《左传》,但也有许多精彩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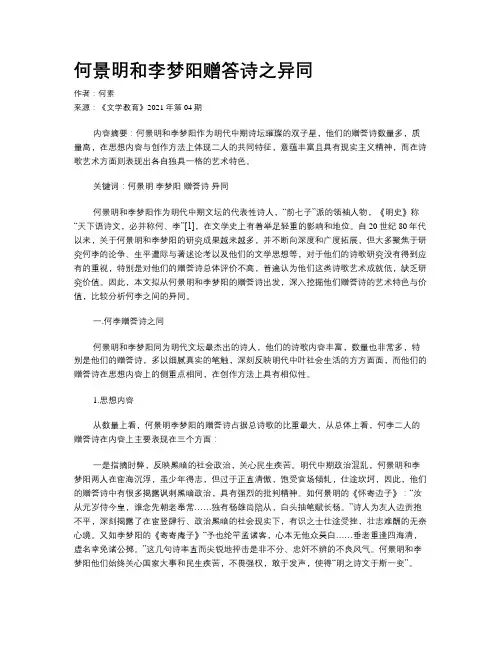
何景明和李梦阳赠答诗之异同作者:何素来源:《文学教育》2021年第04期内容摘要:何景明和李梦阳作为明代中期诗坛璀璨的双子星,他们的赠答诗数量多,质量高,在思想内容与创作方法上体现二人的共同特征,意蕴丰富且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而在诗歌艺术方面则表现出各自独具一格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何景明李梦阳赠答诗异同何景明和李梦阳作为明代中期文坛的代表性诗人,“前七子”派的领袖人物,《明史》称“天下语诗文,必并称何、李”[1],在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地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何景明和李梦阳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并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但大多聚焦于研究何李的论争、生平遭际与著述论考以及他们的文学思想等,对于他们的诗歌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对他们的赠答诗总体评价不高,普遍认为他们这类诗歌艺术成就低,缺乏研究价值。
因此,本文拟从何景明和李梦阳的赠答诗出发,深入挖掘他们赠答诗的艺术特色与价值,比较分析何李之间的异同。
一.何李赠答诗之同何景明和李梦阳同为明代文坛最杰出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内容丰富,数量也非常多,特别是他们的赠答诗,多以细腻真实的笔触,深刻反映明代中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他们的赠答诗在思想内容上的侧重点相同,在创作方法上具有相似性。
1.思想内容从数量上看,何景明李梦阳的赠答诗占据总诗歌的比重最大,从总体上看,何李二人的赠答诗在内容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指摘时弊,反映黑暗的社会政治,关心民生疾苦。
明代中期政治混乱,何景明和李梦阳两人在宦海沉浮,虽少年得志,但过于正直清傲,饱受官场倾轧,仕途坎坷,因此,他们的赠答诗中有很多揭露讽刺黑暗政治,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
如何景明的《怀寄边子》:“汝从元岁侍今皇,谁念先朝老奉常……独有杨雄尚陪从,白头抽笔赋长杨。
”诗人为友人边贡抱不平,深刻揭露了在宦竖肆行、政治黑暗的社会现实下,有识之士仕途受挫,壮志难酬的无奈心境。
又如李梦阳的《寄寄庵子》“予也纶竿孟诸客,心本无他众莫白……垂老重逢四海清,虚名幸免诸公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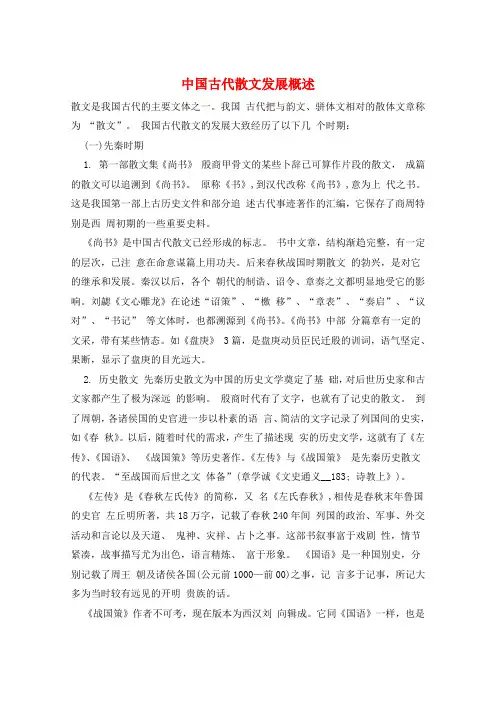
中国古代散文发展概述散文是我国古代的主要文体之一。
我国古代把与韵文、骈体文相对的散体文章称为“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一)先秦时期1. 第一部散文集《尚书》殷商甲骨文的某些卜辞已可算作片段的散文,成篇的散文可以追溯到《尚书》。
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上代之书。
这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
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
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
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 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
《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
如《盘庚》 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
2. 历史散文先秦历史散文为中国的历史文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历史家和古文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殷商时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记史的散文。
到了周朝,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了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
以后,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这就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
《左传》与《战国策》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
“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章学诚《文史通义__183; 诗教上》)。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共18万字,记载了春秋240年间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占卜之事。
这部书叙事富于戏剧性,情节紧凑,战事描写尤为出色,语言精炼、富于形象。
《国语》是一种国别史,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诸侯各国(公元前1000—前00)之事,记言多于记事,所记大多为当时较有远见的开明贵族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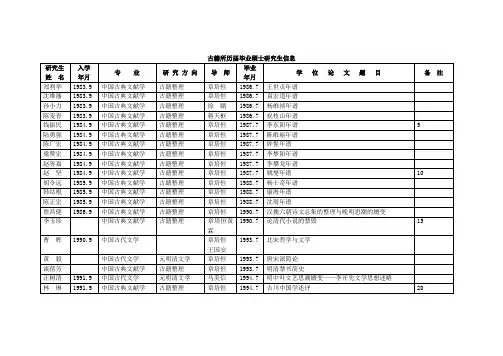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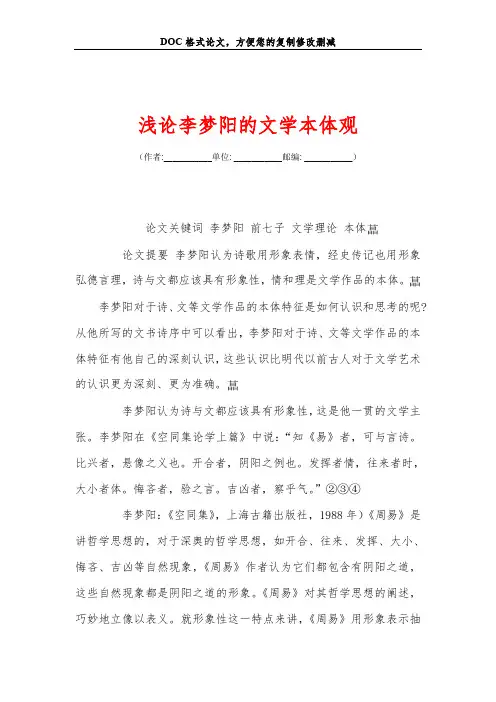
浅论李梦阳的文学本体观(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论文关键词李梦阳前七子文学理论本体论文提要李梦阳认为诗歌用形象表情,经史传记也用形象弘德言理,诗与文都应该具有形象性,情和理是文学作品的本体。
李梦阳对于诗、文等文学作品的本体特征是如何认识和思考的呢?从他所写的文书诗序中可以看出,李梦阳对于诗、文等文学作品的本体特征有他自己的深刻认识,这些认识比明代以前古人对于文学艺术的认识更为深刻、更为准确。
李梦阳认为诗与文都应该具有形象性,这是他一贯的文学主张。
李梦阳在《空同集论学上篇》中说:“知《易》者,可与言诗。
比兴者,悬像之义也。
开合者,阴阳之例也。
发挥者情,往来者时,大小者体。
悔吝者,验之言。
吉凶者,察乎气。
”②③④李梦阳:《空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周易》是讲哲学思想的,对于深奥的哲学思想,如开合、往来、发挥、大小、悔吝、吉凶等自然现象,《周易》作者认为它们都包含有阴阳之道,这些自然现象都是阴阳之道的形象。
《周易》对其哲学思想的阐述,巧妙地立像以表义。
就形象性这一特点来讲,《周易》用形象表示抽象的哲学道理,诗歌用形象表示情感,二者有相通之处。
李梦阳把诗歌与《周易》做比较,看到了形象在《周易》与诗歌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他认为:“知《易》者,可与言诗”。
在《论学下篇》中,李梦阳又说:“古诗妙在形容之耳。
所谓水月镜花。
所谓人外之人,言外之言,宋以后则直陈之矣。
于是,求工于字句。
所谓心劳日拙者也。
形容之妙,心了了而口不能解,卓如跃如,有而无,无而有。
”②在这里,“形容”即是形象之义。
所谓“古诗妙在形容之耳”,就是说古诗好就好在具有形象性。
宋人做诗,只言理性,不述形象,其作品缺少形象之妙,李梦阳是极力贬斥其拙的。
李梦阳不仅仅认为诗歌具有形象性,而且还认为散文也应具有形象性。
在《论学上篇》中,他说:“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非宋儒废之也,文者自废之也。
论明代前七子李何之争明代中叶,李梦阳与何景明都是当时文坛上的活跃人物,位文士都是“前七子文学运动”的领袖。
弘治年问,在他们俩之间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文学学术研究争论。
现存何景明的《与李空同论诗书》、李梦阳的《驳何氏论文书》及《再与何氏论文书》三篇文章,就是当时进行争论的书信。
从这三封书信中,基本上可以看出他们争论的问题和性质。
在中国文学史上,后人历来认为李梦阳的两篇文章表现了他的文学摸拟思想,指责李梦阳是“刻意古范,铸形宿模”。
其实, 仔细分析,这个结论是很难成立的。
所谓的文学模拟思想其实是何景明对李梦阳的诋毁之词,也是后人附和何景明言词的人云亦云之语。
如果详细阅读一下他们的这几篇文章,就会清楚地发现他们争论的问题和性质是什么了。
事实证明李梦阳的文艺思想根本不是摸拟思想。
李何之争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我们分别论述之。
、李何二人在主张文学复古的同时,都确认作文有不可改变的法式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说:“仆尝谓诗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也。
上考古圣之言,中汉绪论,下采魏、晋声诗,莫之有易也。
”何景明的观点很清楚,他不仅认为诗文有不可易之法,而且上考古圣之言,中徵秦汉绪论,下采魏晋声诗,莫之有易也。
” 何景明把诗文之法式看得很宝贵,不过,他尊重的法式是“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
李梦阳亦认为诗文有法。
在《驳何氏论文书》中,他说:“古之工,如佳如斑,堂非不殊,户非同也,至其为方也圆也,弗能舍规矩。
何也?规矩者,法也。
仆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
假令仆窍古辞以为文,谓之影子诚可。
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袭其辞,犹斑圆佳之圆,佳方班之方。
而佳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夫筏我二也,犹兔之蹄,鱼之筌,舍之可也。
规矩者,方圆之自也,即欲舍之,乌乎舍?子试筑一堂、开一户,措规矩而能之乎?”在这段引文里,李梦阳用木匠之“方圆规矩”比喻“法”的客观性,是为了说明文必有法式这一客观事实的。
第32卷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32第1期Journal of Hube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No.1,2012初入仕途与连番下狱———李梦阳研究之二石麟(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黄石435002)〔摘要〕在经历灰色的幼年、少年生活之后,李梦阳刚刚二十出头就连续完成了秀才、举人、进士的三级跳,由此,他步入仕途。
不料,父母相继离世,成为他入仕的第一道障碍。
回家乡守孝五年之后,李梦阳正式步入官场。
但谁能料到,连番的牢狱之灾正在等待着这位意气风发的青年士子。
与此同时,以李梦阳为领袖的文学复古活动,也正在明中叶弘治年间如火如荼地开展。
〔关键词〕李梦阳;为官;入狱;复古;诗风〔中图分类号〕I206.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733(2012)01-0005-06弱冠之年,李梦阳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二十一岁中举,次年成进士,他开始了生命历程的辉煌阶段。
不料,父母相继离世,成为他入仕的第一道障碍。
丁忧守制五年之后,李梦阳正式步入仕途。
可他哪里知道,等待他的竟是一场意料之外的牢狱之灾。
一李梦阳于弘治三年(1490)与左氏成亲之后,次年便生一子,取名李枝。
不久,梦阳又回到庆阳(时属陕西,今属甘肃),准备博取功名。
为什么要从河南跑到陕西参加考试呢?因为当时的“高考”政策与今天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考生参加秀才、举人两级考试都必须回原籍进行,而李梦阳的籍贯正是庆阳。
这一次,命运之神热烈地拥抱了这位出身贫寒的李家儿,他得到了“贵人”的赏识和提携:“时邃庵杨提学陕西,见公,大奇之,补为弟子员。
”(徐缙《明江西按察司副使空同李公墓表》)此处所谓“弟子员”,乃“秀才”之别称。
而所谓“邃庵”者,姓杨,名一清,字应宁,邃庵其号也,云南安宁人。
杨一清乃成化八年进士,由中书舍人历官提学副使。
正是这位杨大人在陕西当教育厅长时,“赏识李献吉,召置门下”。
2018年第07期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No .07,2018(总第190期) JOURNAL OF M UDAN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Serial No .190[收稿日期]2018-06-13[作者简介]胡剑(1994-),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李梦阳复古诗论中的“格调”范畴胡 剑(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摘 要] 李梦阳作为明代中叶的风云人物,其掀起的复古思潮,对后世影响深远。
李梦阳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敢于突破,提出取法汉魏盛唐的“格调”论说,有力地冲击了“雍容典雅”的台阁诗风。
审视李梦阳“格古”、“调逸”的主张,不难发现,他的诗论不仅强调诗歌的体式,亦重视诗歌的抒情特质。
尽管李梦阳部分诗作出现拟古太甚的情况,但是人无完人,拟古失真并不是李梦阳的初衷,而且其后期创新性提出“真诗乃在民间”,此主张对复古过甚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
“格调”说作为李梦阳复古诗学主张的核心,使得文学回归本体,新的诗坛格局在此论说下得到开创。
[关键词] 李梦阳;格调;复古;真诗[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23(2018)07-0006-05 明中叶弘治、正德年间,在前七子的倡导下,诗文复古运动如荼如火地展开。
此次复古运动以李梦阳为主导,以“格调”说为核心,不仅使得当时的文章辞赋为之一变,亦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严迪昌先生有言:“论明诗,李梦阳承上启下,为最大关捩。
”[1]追溯源流,明代贵文重经的学术风气是在前七子领袖李梦阳这里得到根本的改变,诗坛在其力挽狂澜之下,得到重组,台阁文风退出主流,格调复古诗风登上历史舞台。
可以说,李梦阳对明代文学做出了跨时代的贡献,在他的引导下,文坛还其诗于古,明诗获得了一次历史性的大解放。
对李梦阳复古诗论的研究,历代诗论家对“格调”说褒贬不一,本文以李梦阳复古诗论中的“格调”之说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复古思想的成因,从“格调”说的理论内涵入手,围绕“格调”追摹的对象、“格调”下的“主情”观、“格调”在实践中的运用及其意义此三个方面,考察李梦阳复古诗论中的“格调”范畴,望能揭示其价值。
同名巧对李梦阳
李梦阳,明代文学家。
字献吉,又字天赐,号空同子,甘肃庆阳人,弘治进士,曾任户部郎中,有《空同集》。
李梦阳性格诙谐,非常爱才,常出联命对,借以考试后生们的才华。
他在江西督学时,有一个童子和他同名同姓。
在唱名时,就开玩笑说:你怎么和我同名呢?现在我出联让你对,对不上,你就改名,不要丢梦阳的人。
于是他随口念道:
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这分明是借战国时期赵国的大臣蔺相如和西汉时期的辞赋家司马相如同名作文章,以其名同人异,切合当时的现实。
当然蔺相如的文采比起司马相如差得很多,言下之意是说李梦阳这个童子比不上他这位大文学家李梦阳。
其实,李梦阳这个童子也很有才学,他略假思索即对:
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此亦无忌。
魏无忌即战国时期魏国贵族信陵君,就是窃符救赵的公子无忌。
长孙无忌是唐代大臣,唐太宗长孙皇后之兄。
此联以其无忌,双关两人不要顾忌,李督学觉得有理,非常赞赏这位童子的才智,于是马上改变了态度。
经细心考察,证明确有才能,于是亲自推荐,予以重用。
唐赋的叙事价值及其文学史意义周兴泰; 王萍【期刊名称】《《云南社会科学》》【年(卷),期】2019(000)006【总页数】7页(P166-172)【关键词】唐赋; 赋体文学; 叙事思维; 叙事语调【作者】周兴泰; 王萍【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文学院; 南昌工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224明代李梦阳、何景明、胡应麟等复古派文人主张“唐无赋”说①李梦阳曰:“山人商宋、梁时,犹学宋人诗。
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
’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
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问汉,曰:‘无骚哉!’山人于是则又究心骚赋于唐汉之上。
”(《潜虬山人记》)何景明曰:“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
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
”(《何子·杂言》)胡应麟曰:“骚盛于楚,衰于汉,而亡于魏。
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
”(《诗薮·内编》),实乃其祖骚宗汉心态之反映。
他们因批判律赋而否定所有体裁的唐赋作品,观点未免过于偏激。
其实,细察《文苑英华》与《全唐文》,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基本认识:唐不仅有赋,而且数量繁多、众体皆备、优秀之作频见。
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就从文体演变的角度,对唐赋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推崇备至:“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
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
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昌其盈矣。
”②孙福轩、韩泉欣:《历代赋论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10页。
这一评价客观来看是较为允当的。
众所周知,中国人擅于抒情,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深远悠长。
但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进程看,叙事与文学也存在紧密联系,由此形成了与抒情传统并行的叙事传统。
赋体虽旧,但唐人也尝试用它来叙事,这与唐人喜用传奇体写小说有关。
将唐赋放在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总体视阈下进行观照,它取得了突出的叙事成就,并对后世小说、戏剧等叙事文体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章:明代讽刺赋的内容与主题引言明代的讽刺赋若从内容上分类,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是表达对社会上黑暗邪恶的势力进行批判和讽刺;第二是揭露社会问题,反映百姓当时生活于水深火热的情况;第三是对于人性的弱点与丑恶进行挖苦与嘲讽;第四是讽刺当时的社会制度;最后是讽刺当时的政治局势。
第一节:讽刺社会黑暗与腐朽的势力表达对当时社会黑暗势力不满是讽刺赋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作品虽然主要产生在后期,但即使在明代初期和繁荣安定的时期,也不乏这类鞭挞社会黑暗的讽刺赋出现。
与其它明确针对某种社会弊端不同的是:这类作品大多是笼统地讽刺社会价值观的沦落,或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腐朽势力。
例如明初著名文学家刘基(1311-1375)所创作的辞赋当中,其中一部分就是属于讽刺类的,就比如这首《伐寄生赋》:余山居,树群木嘉果骈植。
人事错迕,斤斧不修,野鸟栖息,粪其上,茁异类,日夕滋长,旧本就悴。
余睹而悲之,乃募趫捷,腰斧凿,升其巅,剜条剔根,聚其遗而燔之。
于是老幹挺立,新荑濯如,若疮疡脱身,大奸去国,斧钺之时用大矣哉!作伐寄生赋:天生五材兮,资土而成。
汝独何为兮?附丽以生。
疣赘蛭嘬兮,枝牵蔓萦,瘠人以肥已兮,偷以长荣。
状似小人之窃据兮。
谓城社之可凭。
观其阴不庇物,材匪中器。
华不羞于几筵。
实不谐于五味。
来鸟乌之哤聒。
集虫豸以刺蚝。
果被之而实萎。
卉蒙之而本悴。
坛杏无所容其芬芳,甘棠曷能成其蔽芾?亶无庸而有害。
矧眶睫之可置。
尔乃建修竿,升木末,运斤生风,以翦以伐。
脱纒牵于乔竦,落纎蕤之骚屑,剜藓肤以除根,斆去毒而刮骨。
于是巨蠧既夷,新荑载蕃,迎春而碧叶云潝,望秋而硕果星繁。
信知谷钺之神用,宁能裕蛊以生患也耶?嗟夫!农植嘉榖,恶草是芟,物犹如此,人何以堪!独不闻夫三桓竞爽,鲁君如寄,田氏厚施,姜陈易位,大贾入秦,柏翳以亡,园谋既售,芊化为黄!蠧凭木以槁木,奸凭国以盗国,鬼居肓而人殒,枭寄巢而母食。
坚冰戒乎履霜,羸豕防其躅踯。
李梦阳辞赋散文研究
李梦阳是明代中叶的重要作家,以他为首发起的文学复古运动,倡言兴复古学,并以此对抗靡弱的台阁体与重性理的性气诗,天下响应,有明一代文体为之丕变。
此后,虽然李攀龙、王世贞等代兴,公安派、竟陵派等特起,但李梦阳一直稳为文坛霸主,而且,对他的学习和争论还一直延续到了清代。
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巨大与深远。
迨至今日,李梦阳的文学理论问题已被讨论得相当深、广,其“复古”旗帜下追求“真情”和“真人”的美学内涵已日益深入人心;然而,对于其实际创作的研究则相对滞后得多,至今尚无一本研究其诗歌、辞赋或者散文创作的专著面市。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来探讨李梦阳辞赋和散文(尤其是碑志
文和序记文)创作的实际情况和所取得的成就,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与他相关的文
学理论,如“唐无赋”、“文必秦汉”等的真正内涵。
全文分三章。
第一章为李梦阳辞赋研究,着重在全面和细致地分析李梦阳全部赋作的基础上,描画出其赋作的整体面貌,并探讨其赋作与其文学理论的契合程度。
第一节主要介绍李梦阳辞赋的创作概况。
首先把李梦阳的赋作分成逞辞大赋、骚体赋、诗体赋和骈体赋四大类,并把六篇赋体杂文也分列其中;接着对李梦阳各赋的创作时间和题材进行了尽可能的考察,指出李梦阳的辞赋创作在同侪之中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题材也相当广泛;其辞赋创作贯穿了一生,从刚入仕为官的弘治十一年(1498)一直到逝世时的嘉靖八年(1528),且主要集中在正德三年到九年,而这正是李梦阳仕宦生涯的最后一段
岁月。
第二节主要是按逞辞大赋、骚体赋、诗体赋和骈体赋的先后顺序来分类考察李梦阳赋作内容上的继承与趋新,从而指出其赋作学习汉赋处相对较少,他更
多地是“祖骚”;其诗体赋创作也大都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诗体赋而有一些新的特点;其骈体赋创作占辞赋总数的四分之一强,有力地证明了“唐无赋”的内涵之一就是唐及唐以后的所有赋作李梦阳一概吐弃。
第三节主要探讨李梦阳赋作的抒情特色,指出李梦阳的赋作有极强烈的抒情意味,而且以哀怨忧伤为主、慷慨愤激为辅,主要的抒情方式为深沉婉转和直抒胸臆。
第四节在明确李梦阳把“赋”与“骚”划归“诗”的范畴的基础上,将李梦阳的诗论与辞赋作品结合起来,探讨其辞赋创作的艺术特点,如句式的新变、语言的古奥等。
第二章为李梦阳碑志文研究,着重对李梦阳的碑文和墓志铭(传、行实、祭文三类也适当纳入)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第一节为李梦阳的散文理论。
鉴于目前学界对李梦阳散文理论研究的不够重视和深入,从散文本体观、功用观等几个方面相对系统地勾勒了李梦阳的散文理论。
第二节主要探讨了其碑志文的三大主题取向,即对家人和亲友的深切悼念,悲士不遇,以及李梦阳对“理欲同行而异情”视角下的商人风貌的刻画。
并特别指出,在李梦阳看来,商人其实是一种形象,是其“理欲同行而异情”理论视角下“天理”和“情欲”相互牵制,并折衷调和的一种具体表现和符号。
“天理”和“情欲”第三节主要以“感动读者的程度”为标准来衡量李梦阳碑志文的情感力量,并指出其有激切和抑郁两大情感特色。
特别是后者,向为论者所忽视。
第四节主要是从理论和碑志文创作实际两方面来对“文必秦汉”说进行商榷,指出以“文必秦汉”说为李梦阳的散文复古口号是错误的,他的碑志文中有不少取法魏晋骈文和唐代韩愈处,而从他的部分记文中甚至可见到沾染宋人记文写作习气处。
此外,从其碑志来看,李梦阳古文创作不仅努力学习史传,而且向汉赋也多有借鉴。
第三章为李梦阳序记文研究,着重对李梦阳的书体文、序文和记文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第一节为空同书序文研究。
本节在简要分析了李梦阳的书体文、诗文集序之后,重点探讨了其赠序文,并揭示了它积极论议时政的主题取向,悲士不遇的情感内核,以及沉郁的情感特质。
最后,从四个方面探讨了空同序体文的论议特点。
第二节为空同记文研究。
本节主要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楼台亭记文。
该体文章是空同记文的最大组成部分,而且内容也相当驳杂。
我们重点考查了李梦阳记文创作简洁、明秀的一面,接着强调了其部分记文“专尚议论”的特点,以及这与宋代记文的关系。
第二部分为游记。
游记是李梦阳为文“力追秦汉”的很好的佐证,同时也显示了他高超的叙事能力与极精炼的用字造语能力。
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适当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