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伤寒论》方现代临床应用举隅
- 格式:pptx
- 大小:1.95 MB
- 文档页数: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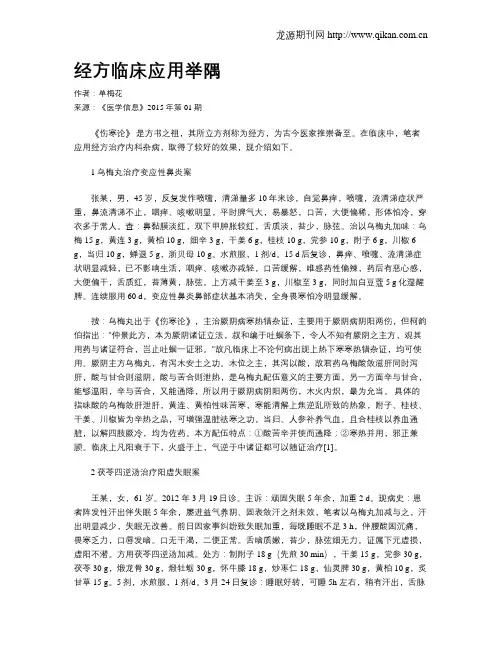
经方临床应用举隅作者:单梅花来源:《医学信息》2015年第01期《伤寒论》是方书之祖,其所立方剂称为经方,为古今医家推崇备至。
在临床中,笔者应用经方治疗内科杂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介绍如下。
1乌梅丸治疗变应性鼻炎案张某,男,45岁,反复发作喷嚏,清涕量多10年来诊,自觉鼻痒,喷嚏,流清涕症状严重,鼻流清涕不止,咽痒、咳嗽明显,平时脾气大,易暴怒,口苦,大便偏稀,形体怕冷,穿衣多于常人。
查:鼻黏膜淡红,双下甲肿胀较红,舌质淡,苔少,脉弦。
治以乌梅丸加味:乌梅15 g,黄连3 g,黄柏10 g,细辛3 g,干姜6 g,桂枝10 g,党参10 g,附子6 g,川椒6 g,当归10 g,蝉退5 g,浙贝母10 g。
水煎服,1剂/d。
15 d后复诊,鼻痒、喷嚏、流清涕症状明显减轻,已不影响生活,咽痒、咳嗽亦减轻,口苦缓解,唯感药性偏辣,药后有恶心感,大便偏干,舌质红,苔薄黄,脉弦。
上方减干姜至 3 g,川椒至 3 g,同时加白豆蔻 5 g化湿醒脾。
连续服用60 d,变应性鼻炎鼻部症状基本消失,全身畏寒怕冷明显缓解。
按:乌梅丸出于《伤寒论》,主治厥阴病寒热错杂证,主要用于厥阴病阴阳两伤,但柯韵伯指出:"仲景此方,本为厥阴诸证立法,叔和编于吐蛔条下,令人不知有厥阴之主方,观其用药与诸证符合,岂止吐蛔一证邪。
"故凡临床上不论何病出现上热下寒寒热错杂证,均可使用。
厥阴主方乌梅丸,有泻木安土之功。
木位之主,其泻以酸,故君药乌梅酸敛滋肝同时泻肝,酸与甘合则滋阴,酸与苦合则泄热,是乌梅丸配伍意义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辛与甘合,能够温阳,辛与苦合,又能通降,所以用于厥阴病阴阳两伤,木火内炽,最为允当。
具体的指味酸的乌梅敛肝泄肝,黄连、黄柏性味苦寒,寒能清解上焦逆乱所致的热象,附子、桂枝、干姜、川椒皆为辛热之品,可增强温脏祛寒之功,当归、人参补养气血,且合桂枝以养血通脏,以解四肢厥冷,均为佐药。
本方配伍特点:①酸苦辛并使而通降;②寒热并用,邪正兼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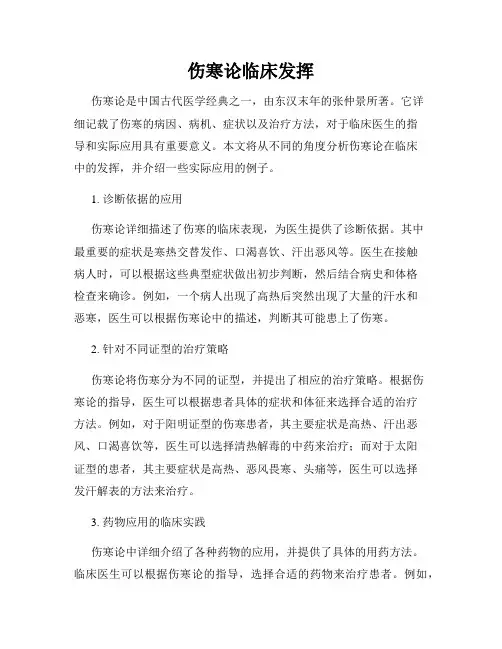
伤寒论临床发挥伤寒论是中国古代医学经典之一,由东汉末年的张仲景所著。
它详细记载了伤寒的病因、病机、症状以及治疗方法,对于临床医生的指导和实际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伤寒论在临床中的发挥,并介绍一些实际应用的例子。
1. 诊断依据的应用伤寒论详细描述了伤寒的临床表现,为医生提供了诊断依据。
其中最重要的症状是寒热交替发作、口渴喜饮、汗出恶风等。
医生在接触病人时,可以根据这些典型症状做出初步判断,然后结合病史和体格检查来确诊。
例如,一个病人出现了高热后突然出现了大量的汗水和恶寒,医生可以根据伤寒论中的描述,判断其可能患上了伤寒。
2. 针对不同证型的治疗策略伤寒论将伤寒分为不同的证型,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疗策略。
根据伤寒论的指导,医生可以根据患者具体的症状和体征来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
例如,对于阳明证型的伤寒患者,其主要症状是高热、汗出恶风、口渴喜饮等,医生可以选择清热解毒的中药来治疗;而对于太阳证型的患者,其主要症状是高热、恶风畏寒、头痛等,医生可以选择发汗解表的方法来治疗。
3. 药物应用的临床实践伤寒论中详细介绍了各种药物的应用,并提供了具体的用药方法。
临床医生可以根据伤寒论的指导,选择合适的药物来治疗患者。
例如,伤寒论中提到了黄连、黄芩等苦寒药的应用,这些药物可以清热解毒。
在临床实践中,医生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苦寒药进行治疗。
4. 预防和防控措施伤寒论还提出了一些预防和防控措施,对于疾病的预防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例如,伤寒论中提到了水土清洁、饮食卫生等措施,可以有效地预防伤寒的发生。
在临床实践中,医生可以根据伤寒论的指导,向患者提供相关的预防措施,帮助他们预防疾病的发生。
总结起来,伤寒论是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医学经典,其在临床中的发挥不容忽视。
医生可以通过借鉴伤寒论的理论和方法,更好地诊断、治疗和预防伤寒等相关疾病,提高临床医学的水平和质量。
当然,在实际应用中,医生也应该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实际情况,综合考虑病人的特点和需求,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以取得更好的疗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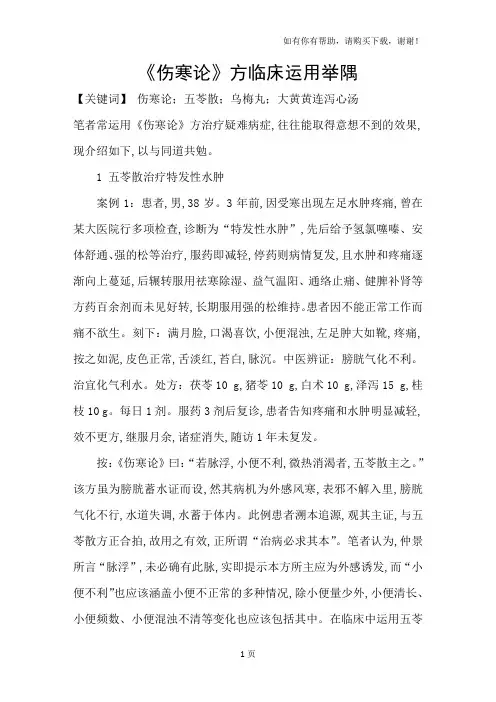
《伤寒论》方临床运用举隅【关键词】伤寒论;五苓散;乌梅丸;大黄黄连泻心汤笔者常运用《伤寒论》方治疗疑难病症,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现介绍如下,以与同道共勉。
1 五苓散治疗特发性水肿案例1:患者,男,38岁。
3年前,因受寒出现左足水肿疼痛,曾在某大医院行多项检查,诊断为“特发性水肿”,先后给予氢氯噻嗪、安体舒通、强的松等治疗,服药即减轻,停药则病情复发,且水肿和疼痛逐渐向上蔓延,后辗转服用祛寒除湿、益气温阳、通络止痛、健脾补肾等方药百余剂而未见好转,长期服用强的松维持。
患者因不能正常工作而痛不欲生。
刻下:满月脸,口渴喜饮,小便混浊,左足肿大如靴,疼痛,按之如泥,皮色正常,舌淡红,苔白,脉沉。
中医辨证:膀胱气化不利。
治宜化气利水。
处方:茯苓10 g,猪苓10 g,白术10 g,泽泻15 g,桂枝10 g。
每日1剂。
服药3剂后复诊,患者告知疼痛和水肿明显减轻,效不更方,继服月余,诸症消失,随访1年未复发。
按:《伤寒论》曰:“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
”该方虽为膀胱蓄水证而设,然其病机为外感风寒,表邪不解入里,膀胱气化不行,水道失调,水蓄于体内。
此例患者溯本追源,观其主证,与五苓散方正合拍,故用之有效,正所谓“治病必求其本”。
笔者认为,仲景所言“脉浮”,未必确有此脉,实即提示本方所主应为外感诱发,而“小便不利”也应该涵盖小便不正常的多种情况,除小便量少外,小便清长、小便频数、小便混浊不清等变化也应该包括其中。
在临床中运用五苓散治疗各个部位原因不明的顽固性水肿,只要抓住“外感风寒诱发”、“小便不利”这两个关键,就能获桴鼓之效,不必拘泥于腰以上或腰以下。
2 乌梅丸治疗顽固性腹泻案例2:患者,男,73岁。
慢性腹泻7年余,此次因进食生冷及睡凉席诱发。
大便溏薄急迫,日八九次,无腹痛及里急后重,伴有腰痛,小便短赤,舌质红,舌苔白中有剥脱,脉细数。
西医诊断为慢性结肠炎。
先予理中汤、四神丸、真人养脏汤等方加减无效,后观其舌脉,结合其病因,考虑为寒热错杂之证,以乌梅丸加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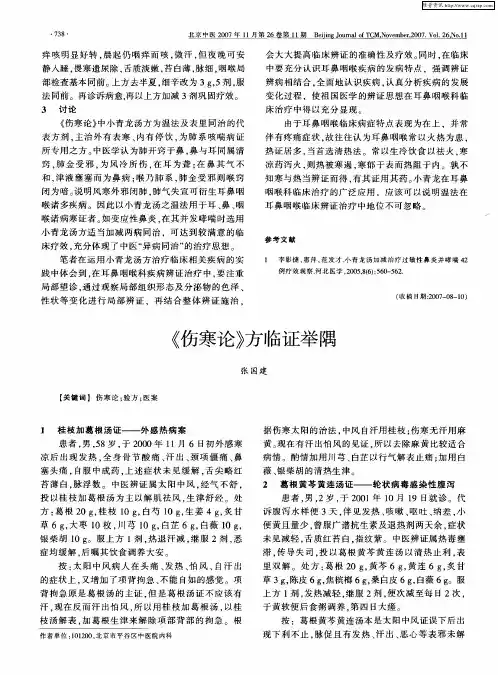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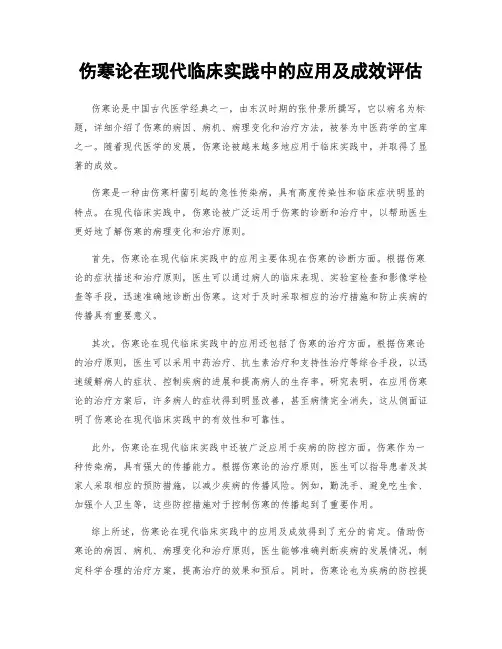
伤寒论在现代临床实践中的应用及成效评估伤寒论是中国古代医学经典之一,由东汉时期的张仲景所撰写。
它以病名为标题,详细介绍了伤寒的病因、病机、病理变化和治疗方法,被誉为中医药学的宝库之一。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伤寒论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临床实践中,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伤寒是一种由伤寒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具有高度传染性和临床症状明显的特点。
在现代临床实践中,伤寒论被广泛运用于伤寒的诊断和治疗中,以帮助医生更好地了解伤寒的病理变化和治疗原则。
首先,伤寒论在现代临床实践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伤寒的诊断方面。
根据伤寒论的症状描述和治疗原则,医生可以通过病人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等手段,迅速准确地诊断出伤寒。
这对于及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和防止疾病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伤寒论在现代临床实践中的应用还包括了伤寒的治疗方面。
根据伤寒论的治疗原则,医生可以采用中药治疗、抗生素治疗和支持性治疗等综合手段,以迅速缓解病人的症状、控制疾病的进展和提高病人的生存率。
研究表明,在应用伤寒论的治疗方案后,许多病人的症状得到明显改善,甚至病情完全消失,这从侧面证明了伤寒论在现代临床实践中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此外,伤寒论在现代临床实践中还被广泛应用于疾病的防控方面。
伤寒作为一种传染病,具有强大的传播能力。
根据伤寒论的治疗原则,医生可以指导患者及其家人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以减少疾病的传播风险。
例如,勤洗手、避免吃生食、加强个人卫生等,这些防控措施对于控制伤寒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伤寒论在现代临床实践中的应用及成效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借助伤寒论的病因、病机、病理变化和治疗原则,医生能够准确判断疾病的发展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提高治疗的效果和预后。
同时,伤寒论也为疾病的防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方针。
其长期以来被广大医生所采用,并不断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伤寒论作为一种古代医学经典,仍然需要结合现代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运用,以更好地适应现代临床实践的需求,并为临床医生提供更加精确、有效的治疗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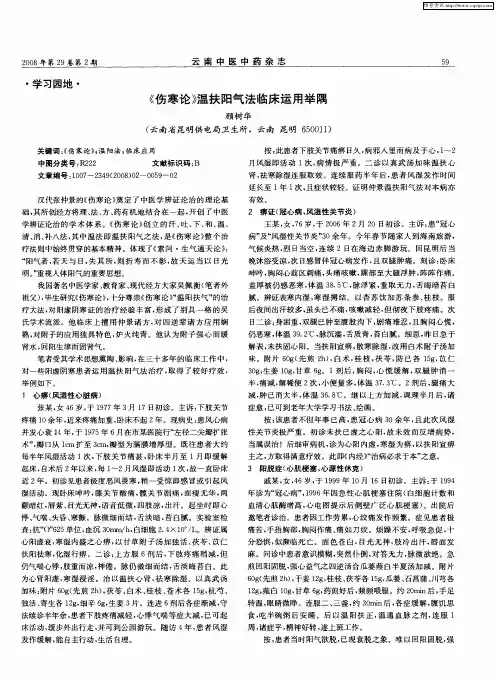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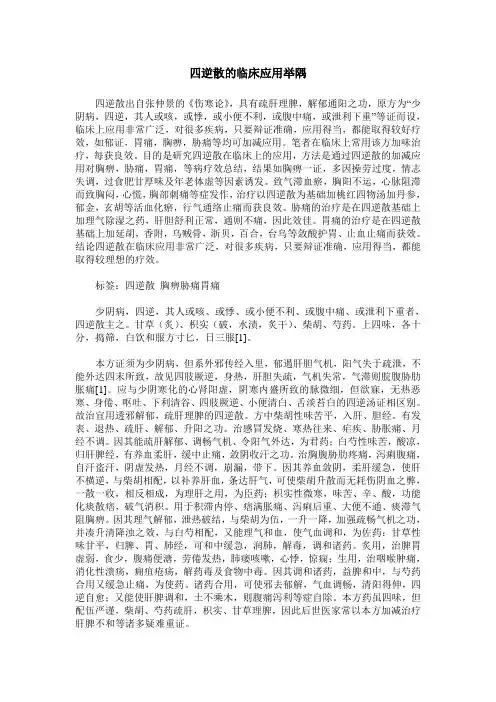
四逆散的临床应用举隅四逆散出自张仲景的《伤寒论》,具有疏肝理脾,解郁通阳之功,原方为“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等证而设,临床上应用非常广泛,对很多疾病,只要辩证准确,应用得当,都能取得较好疗效,如郁证,胃痛,胸痹,胁痛等均可加减应用。
笔者在临床上常用该方加味治疗,每获良效。
目的是研究四逆散在临床上的应用,方法是通过四逆散的加减应用对胸痹,胁痛,胃痛,等病疗效总结,结果如胸痹一证,多因操劳过度,情志失调,过食肥甘厚味及年老体虚等因素诱发。
致气滞血瘀,胸阳不运,心脉阻滞而致胸闷,心慌,胸部刺痛等症发作,治疗以四逆散为基础加桃红四物汤加丹参,郁金,玄胡等活血化瘀,行气通络止痛而获良效。
胁痛的治疗是在四逆散基础上加理气除湿之药,肝胆舒利正常,通则不痛,因此效佳。
胃痛的治疗是在四逆散基础上加延胡,香附,乌贼骨,浙贝,百合,台乌等敛酸护胃、止血止痛而获效。
结论四逆散在临床应用非常广泛,对很多疾病,只要辩证准确,应用得当,都能取得较理想的疗效。
标签:四逆散胸痹胁痛胃痛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甘草(炙)、枳实(破,水渍,炙干)、柴胡、芍药。
上四味,各十分,捣筛,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1]。
本方证须为少阴病,但系外邪传经入里,郁遏肝胆气机,阳气失于疏泄,不能外达四末所致,故见四肢厥逆,身热,肝胆失疏,气机失常,气滞则脘腹胁肋胀痛[1]。
应与少阴寒化的心肾阳虚,阴寒内盛所致的脉微细,但欲寐,无热恶寒、身倦、呕吐、下利清谷、四肢厥逆、小便清白、舌淡苔白的四逆汤证相区别。
故治宜用透邪解郁,疏肝理脾的四逆散。
方中柴胡性味苦平,入肝、胆经。
有发表、退热、疏肝、解郁、升阳之功。
治感冒发烧、寒热往来、疟疾、胁胀痛、月经不调。
因其能疏肝解郁、调畅气机、令阳气外达,为君药;白芍性味苦,酸凉,归肝脾经,有养血柔肝,缓中止痛,敛阴收汗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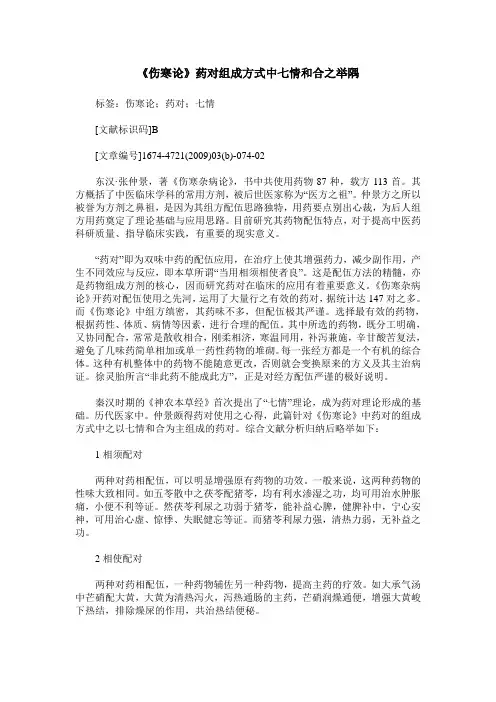
《伤寒论》药对组成方式中七情和合之举隅标签:伤寒论;药对;七情[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4721(2009)03(b)-074-02东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书中共使用药物87种,载方113首。
其方概括了中医临床学科的常用方剂,被后世医家称为“医方之祖”。
仲景方之所以被誉为方剂之鼻祖,是因为其组方配伍思路独特,用药要点别出心裁,为后人组方用药奠定了理论基础与应用思路。
目前研究其药物配伍特点,对于提高中医药科研质量、指导临床实践,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药对”即为双味中药的配伍应用,在治疗上使其增强药力,减少副作用,产生不同效应与反应,即本草所谓“当用相须相使者良”。
这是配伍方法的精髓,亦是药物组成方剂的核心,因而研究药对在临床的应用有着重要意义。
《伤寒杂病论》开药对配伍使用之先河,运用了大量行之有效的药对,据统计达147对之多。
而《伤寒论》中组方缜密,其药味不多,但配伍极其严谨。
选择最有效的药物,根据药性、体质、病情等因素,进行合理的配伍。
其中所选的药物,既分工明确,又协同配合,常常是散收相合,刚柔相济,寒温同用,补泻兼施,辛甘酸苦复法,避免了几味药简单相加或单一药性药物的堆砌。
每一张经方都是一个有机的综合体。
这种有机整体中的药物不能随意更改,否则就会变换原来的方义及其主治病证。
徐灵胎所言“非此药不能成此方”,正是对经方配伍严谨的极好说明。
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首次提出了“七情”理论,成为药对理论形成的基础。
历代医家中。
仲景颇得药对使用之心得,此篇针对《伤寒论》中药对的组成方式中之以七情和合为主组成的药对。
综合文献分析归纳后略举如下:1相须配对两种对药相配伍,可以明显增强原有药物的功效。
一般来说,这两种药物的性味大致相同。
如五苓散中之茯苓配猪苓,均有利水渗湿之功,均可用治水肿胀痛,小便不利等证。
然茯苓利尿之功弱于猪苓,能补益心脾,健脾补中,宁心安神,可用治心虚、惊悸、失眠健忘等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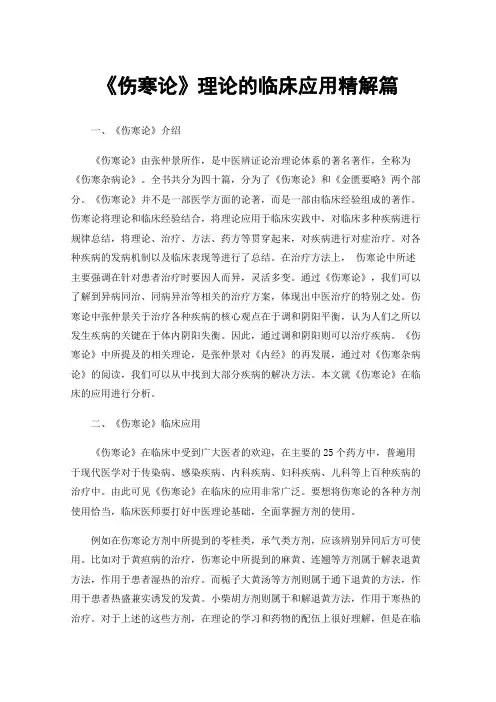
《伤寒论》理论的临床应用精解篇一、《伤寒论》介绍《伤寒论》由张仲景所作,是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体系的著名著作,全称为《伤寒杂病论》。
全书共分为四十篇,分为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个部分。
《伤寒论》并不是一部医学方面的论著,而是一部由临床经验组成的著作。
伤寒论将理论和临床经验结合,将理论应用于临床实践中,对临床多种疾病进行规律总结,将理论、治疗、方法、药方等贯穿起来,对疾病进行对症治疗。
对各种疾病的发病机制以及临床表现等进行了总结。
在治疗方法上,伤寒论中所述主要强调在针对患者治疗时要因人而异,灵活多变。
通过《伤寒论》,我们可以了解到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等相关的治疗方案,体现出中医治疗的特别之处。
伤寒论中张仲景关于治疗各种疾病的核心观点在于调和阴阳平衡,认为人们之所以发生疾病的关键在于体内阴阳失衡。
因此,通过调和阴阳则可以治疗疾病。
《伤寒论》中所提及的相关理论,是张仲景对《内经》的再发展,通过对《伤寒杂病论》的阅读,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大部分疾病的解决方法。
本文就《伤寒论》在临床的应用进行分析。
二、《伤寒论》临床应用《伤寒论》在临床中受到广大医者的欢迎,在主要的25个药方中,普遍用于现代医学对于传染病、感染疾病、内科疾病、妇科疾病、儿科等上百种疾病的治疗中。
由此可见《伤寒论》在临床的应用非常广泛。
要想将伤寒论的各种方剂使用恰当,临床医师要打好中医理论基础,全面掌握方剂的使用。
例如在伤寒论方剂中所提到的苓桂类,承气类方剂,应该辨别异同后方可使用。
比如对于黄疸病的治疗,伤寒论中所提到的麻黄、连翘等方剂属于解表退黄方法,作用于患者湿热的治疗。
而栀子大黄汤等方剂则属于通下退黄的方法,作用于患者热盛兼实诱发的发黄。
小柴胡方剂则属于和解退黄方法,作用于寒热的治疗。
对于上述的这些方剂,在理论的学习和药物的配伍上很好理解,但是在临床实际应用中要如何区别呢?例如五苓散和猪苓汤,同样是属于利水剂,但是却存在不同之处。
例如,五苓散采取术桂暧肾利水,而猪苓汤则采取滑石利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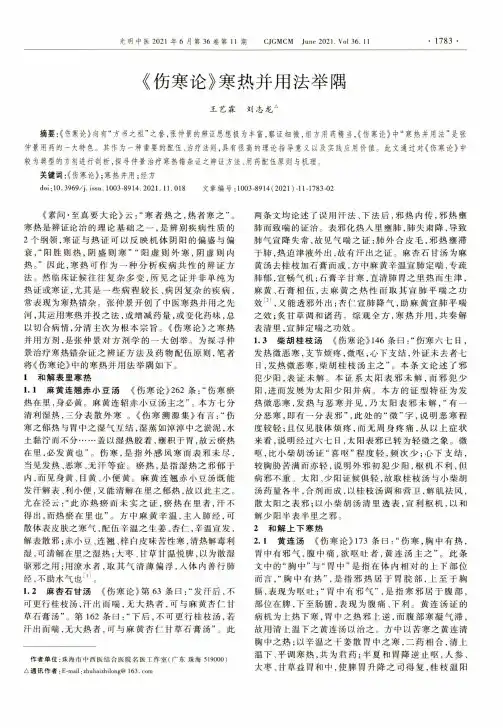
《伤寒论》方临证应用体会2017-08-12读《伤寒论》最重要的是用于临床,不仅要明白条文的意义,还需前后文义对照相互贯通,并结合各家的注释和自身的理解,再通过临床实践去掌握。
浙江省名中医牟重临教授深研经典,临床使用经方得心应手。
笔者随师临证,体会牟师通常采用的方法是:从条文意义,推导病机;以方测证,联系相关理论引伸临床应用;对一些错综复杂的病证,则抓主证与主方,随证配合用药,使用方切中病机;对复杂多变的病症,常与时方交互使用,使经方与时方起着互补作用。
下面试以举案例解析所述观点,以飨读者。
1 抓住病机,推导临床应用掌握《伤寒论》方证,要理解条文意义,抓住病机,推导临床应用。
如大青龙汤治太阳病、溢饮,临证要掌握“发热、恶寒、无汗而烦躁”之主症,即表实里热证,立治法为解表清里而使用本方。
例1:王某,男,35岁。
2003年10月7日初诊。
头痛反复发作5年,每受风寒则头部疼痛剧烈,常用各种止痛片得以缓解。
诊见:前额头痛连及后项,恶寒肢冷,无汗,烦热口干,二便正常,舌红、苔薄白,脉象浮数小滑。
外表为风寒所束,内有郁热,证属大青龙汤证。
处方:麻黄、桂枝各6 g,苦杏仁10 g,石膏30 g,细辛、甘草各5 g,生姜2片,红枣5枚。
每天1剂,水煎服。
服3剂即头痛消失。
再以上方加减调理10余天,诸症悉除,追访1年未复。
从方证来看,大青龙汤是属于表实里热证,以发表清里治法,主药是麻黄、桂枝配石膏。
大青龙汤是表示一个治法,方从法立,临床治疗表实里热病证不一定用大青龙汤,比如以细辛、防风配合生石膏、炒栀子治疗神经性头痛;白芷、川芎配黄芩、蒲公英等治疗鼻窦炎头痛等表现表实里热者,亦颇有效,此乃师其法,毋泥其方。
当然,被誉为医方之祖的《伤寒论》方无疑是范本,须通透理解方能不囿于教条而运用自如。
抓住大青龙汤证的表实里热表现,并不限于仲景所论之病,可推向临床治疗多种疾病,如外感高热、流感咳嗽、支气管肺炎、过敏性鼻炎、急性肾炎、荨麻疹等都是按表实里热病机使用。
《伤寒论》方及其运用经方即经典之方,为后世对仲景方的尊称。
包括《伤寒论》所载113方,及《金匮要略》所载262方。
《伤寒论》方(下称伤寒方)是经方的一部分。
由于仲景把方剂与辨证紧密结合,而且立方精而不杂,用药有的放矢,其用药之精要,药物配伍之严谨,后世莫不奉为圭臬,所以尊仲景为医圣,奉《伤寒论》《金匮要略》为医经,其中的方剂就成了经方,正如明·喻昌说:“两书所载方剂是众法之宗,群方之祖。
”《汉书·艺文志》载有经方十一家,计《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三十卷,《风寒热十六病方》二十六卷等,这里的经方是指久经实践检验的效方。
它是汉代以前的、非特定意义的经验方,显然与专指仲景方的经方不同。
晋唐时期,《伤寒杂病论》还只是些手抄秘本在民间相传,影响不大。
直到宋代官方组织林亿等人校正刊行,其后《伤寒论》又经金·成无已注解,才使它得以盛行。
由于它本身实用价值大,倍受医家的欢迎,对仲景其人亦十分崇敬。
如刘河间说:“仲景者,亚圣也,虽仲景之书未备圣人之教,亦几于圣人”。
于是便形成了推祟《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善用仲景方的经方派。
唐代开始,搜集整理经验方的风气很盛,《圣济总录》《普济方》《外台秘要》相继推出。
到了宋代,官方组织编写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尤为盛行,至金元四大家学说兴起,新的医学流派得以形成,这就是时方派。
由上可知,在汉代所记载的经方,乃指当时所总结的汉以前的经验方,宋代以来的所谓经方,实指仲景方而言,与之相对应的时方,则指仲景以外的方。
二、《伤寒论》方的特色仲景方对中医方药影响极大,宋·林亿校正《伤寒论》刊行50多年后初刻的《本草衍义》就在序言中推祟仲景用药法,所选医案大多应用仲景方。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大量引用《伤寒论》的内容。
宋以后无不以仲景方作为骨干方。
仲景方的特色介绍于下:(一)药精效宏,配伍严谨选药精良,配伍严明是仲景制方两大特点。
在选药方面,药味偏少,用量有度。
《伤寒杂病论》柴胡药对配伍作用探析及临床运用举隅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为中医经典著作,被奉为“方书之祖”。
该书所载方剂组方严谨,主次分明,变化巧妙,疗效确切,千百年来一直沿用于临床。
本研究通过对仲景常用柴胡药对的整理与分析以及病案举隅,使对柴胡药对的配伍功用有更加明晰的认识。
标签:伤寒杂病论;柴胡;药对;应用An exploration of compatible effect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n drug pair of bupleurum in Treatise on Febril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ZHANG?Ying1??LUO?Yinxing1??WANG?Xianling21.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450004,China;2.He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450046,China[Abstract] Treatise on Febril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 by ZHANG Zhongjing is a traditional classic theoretic works, which are the ancestor of Chinese prescription books.Herbal prescription composing principles of Treatise on Febril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 is rigorous and priorities straight.Changes of it is ingenious. The curative effect of it is stable.It is always used in clinical, for thousands of years. Compatible effects on drug pair of bupleurum are clearer through the arrangement and analysis of the drug pair of bupleurum used always by Zhongjing and exemplification of medical records.[Key words] Treatise on Febril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 Bupleurum; Drug pair; Application《伤寒杂病论》是我国一部临床医学巨著,以用药精专、组方严谨、疗效卓著,被誉为“经方之祖”,奠定了后世医方的基础。
中医经典古方临证运用举隅(四)中医传承,承传中医《中医经典古方临证运用举隅》(四)那么这个病人西医诊断为发热、荨麻疹、巧克力囊肿,而我们中医呢,诊断为表郁轻证。
看看这病人啊,皮肤这样子,你看这些病人都像不像你们家的邻居得的病,像不像你们的患者得的病,就这么个情况来了,我们用了桂麻各半汤合升降散去大黄加荆芥、防风。
我们把伤寒和温病结合在一块,因为它开始不光出疹子,还有一些像斑一样的东西,斑多是阳明,多是温邪,那么有寒有温邪相杂,我们用这些方法来(治疗)。
有寒有温邪,有风有寒、热,我们用这些方子来透他的表邪。
你看服药当天晚上微汗出,体温37.4℃,周身瘙痒明显好转。
这是随访的,我这病历全部都是真实病历,而且呢,什么时候随访都会有记载的啊,多长时间退的热都会有记载,服四剂药后,现周身瘙痒无,皮疹明显好转。
你看,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个桂麻各半,桂二麻一,桂麻二越婢一的这个(病例),有些人用了这些方子不好使,用了以后呢,他没好,我又给大家推荐第二类方子,叫做十五味祛风败毒散,就是说一般来说那个方子管用了,但为什么没有好呢?那我就用第二首,A方案,B方案,C方案对不对,你得有几首。
你不能来了我就一个方案,治好了我就是神医,治不好我就庸医,那还了得吗?是不是?你也不可能一个方把所有的病全治好了,那还了得吗?天下只有一法——桂枝法……天下只有一法——四逆法,那还了得吗?要那么多法干啥呢?张仲景的书写两法就行了,还写三百九十七法干啥?把中医就怎么样了?——庸俗化了。
十五味祛风败毒散呢,来源于《寿世保元》,是明朝的医家龚廷贤《寿世保元》里面的方子。
大家看一下这方子,大家拍一下,拍一下拿回家里就照着这方子抄,一抄按这是中央一频道一看,好了这类疾病通通扫干,它是治风疮疥癣,瘾疹,紫白癜风、赤游风,血风臁疮丹瘤及破伤风。
一共15味药,在上部加桔梗,在下部加牛膝,如果实际情况在下,去蝉蜕、僵蚕,我们临床就是这样看病。
中医是用的方,我反复讲,不是用的药,方里面有药,肯定是由药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