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对汉乐府的继承发展
- 格式:docx
- 大小:19.91 KB
- 文档页数: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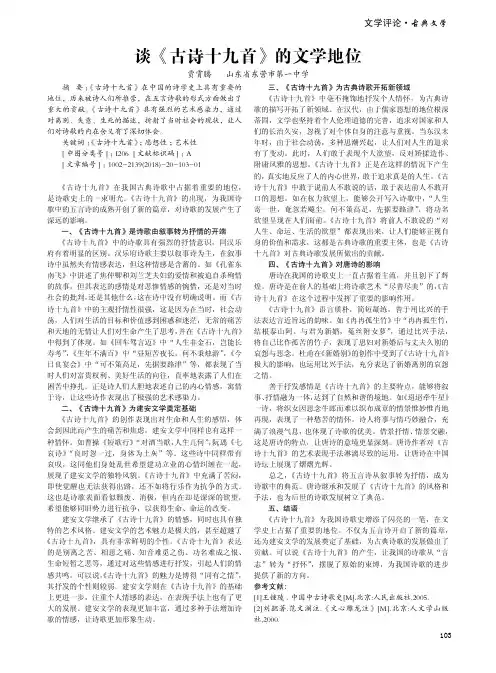
文学评论·古典文学谈《古诗十九首》的文学地位贾霄腾 山东省东营市第一中学摘 要:《古诗十九首》在中国的诗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历来被诗人们所推崇,在五言诗歌的形式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古诗十九首》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通过对离别、失意、生死的描述,折射了当时社会的现状,让人们对诗歌的内在含义有了深切体会。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思想性;艺术性[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0-103-01《古诗十九首》在我国古典诗歌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诗歌史上的一束明光。
《古诗十九首》的出现,为我国诗歌中的五言诗的成熟开创了新的篇章,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古诗十九首》是诗歌由叙事转为抒情的开端《古诗十九首》中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抒情意识,同汉乐府有着明显的区别。
汉乐府诗歌主要以叙事诗为主,在叙事诗中虽然夹有情感表达,但这种情感是含蓄的。
如《孔雀东南飞》中讲述了焦仲卿和刘兰芝夫妇的爱情和被迫自杀殉情的故事,但其表达的感情是对悲惨情感的惋惜,还是对当时社会的批判,还是其他什么,这在诗中没有明确说明。
而《古诗十九首》中的主观抒情性很强,这是因为在当时,社会动荡,人们对生活的目标和价值感到困惑和迷茫,无常的痛苦和天地的无情让人们对生命产生了思考,并在《古诗十九首》中得到了体现。
如《回车驾言迈》中“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生年不满百》中“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今日良宴会》中“可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等,都表现了当时人们对富贵权利、美好生活的向往,直率地表露了人们在困苦中挣扎。
正是诗人们大胆地表述自己的内心情感,寓情于诗,让这些诗作表现出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二、《古诗十九首》为建安文学奠定基础《古诗十九首》的创作表现出对生命和人生的感悟,体会到因此而产生的痛苦和焦虑。
建安文学中同样也有这样一种情怀。
如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阮瑀《七哀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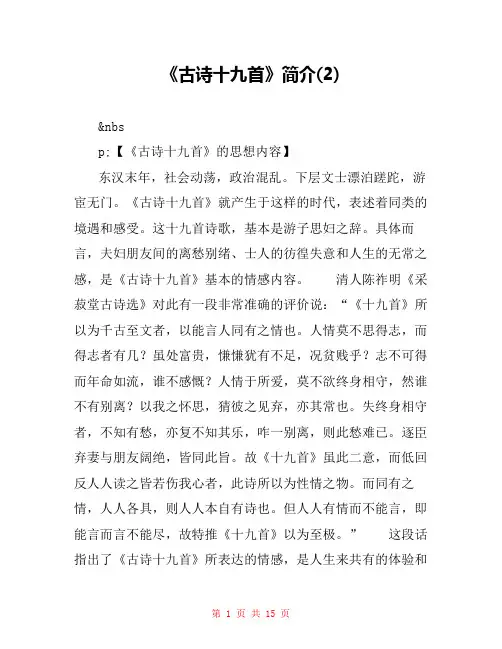
《古诗十九首》简介(2) 【《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治混乱。
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
《古诗十九首》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表述着同类的境遇和感受。
这十九首诗歌,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
具体而言,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士人的彷徨失意和人生的无常之感,是《古诗十九首》基本的情感内容。
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对此有一段非常准确的评价说:“《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
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
失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咋一别离,则此愁难已。
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
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
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
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
”这段话指出了《古诗十九首》所表达的情感,是人生来共有的体验和感受。
如:表现思念故乡怀念亲人的《涉江采芙蓉》、《去者日以疏》;表现思妇对游子深切思念和真挚爱恋的《凛凛岁云暮》、《客从远方来》和《迢迢牵牛星》;表现游士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的某些观念:《回车驾言迈》、《明月皎夜光》。
总之,《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是“人同有之情”。
因而,这些诗歌能够永久地感动人,千古常新。
同时,它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士子的社会境遇、精神生活与人格气质,并由此透视出汉末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有相当重要的认识意义。
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学者所谓“逐臣弃友、思妇劳人、托境抒情、比物连类、亲疏厚薄、死生新故之感,质言之、寓言之、一唱而三叹之”(王康《古诗十九首绎后序》),良非虚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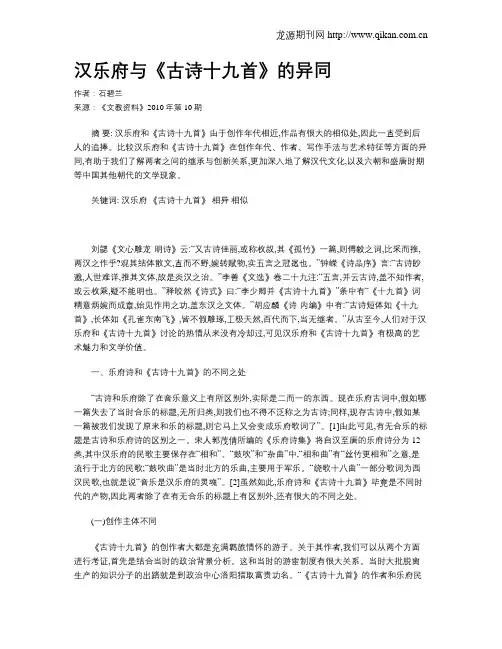
汉乐府与《古诗十九首》的异同作者:石碧兰来源:《文教资料》2010年第10期摘要: 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由于创作年代相近,作品有很大的相似处,因此一直受到后人的追捧。
比较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在创作年代、作者、写作手法与艺术特征等方面的异同,有助于我们了解两者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关系,更加深入地了解汉代文化,以及六朝和盛唐时期等中国其他朝代的文学现象。
关键词: 汉乐府《古诗十九首》相异相似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赋物,实五言之冠冕也。
”钟嵘《诗品序》言:“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故是炎汉之治。
”李善《文选》卷二十九注:“五言,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
”释皎然《诗式》曰:“李少卿并《古诗十九首》”条中有“《十九首》词精意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盖东汉之文体。
”胡应麟《诗·内编》中有:“古诗短体如《十九首》,长体如《孔雀东南飞》,皆不假雕琢,工极天然,百代而下,当无继者。
”从古至今,人们对于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讨论的热情从来没有冷却过,可见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有极高的艺术魅力和文学价值。
一、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的不同之处“古诗和乐府除了在音乐意义上有所区别外,实际是二而一的东西。
现在乐府古词中,假如哪一篇失去了当时合乐的标题,无所归类,则我们也不得不泛称之为古诗;同样,现存古诗中,假如某一篇被我们发现了原来和乐的标题,则它马上又会变成乐府歌词了”。
[1]由此可见,有无合乐的标题是古诗和乐府诗的区别之一。
宋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将自汉至唐的乐府诗分为12类,其中汉乐府的民歌主要保存在“相和”、“鼓吹”和“杂曲”中,“相和曲”有“丝竹更相和”之意,是流行于北方的民歌;“鼓吹曲”是当时北方的乐曲,主要用于军乐。
“绕歌十八曲”一部分歌词为西汉民歌,也就是说“音乐是汉乐府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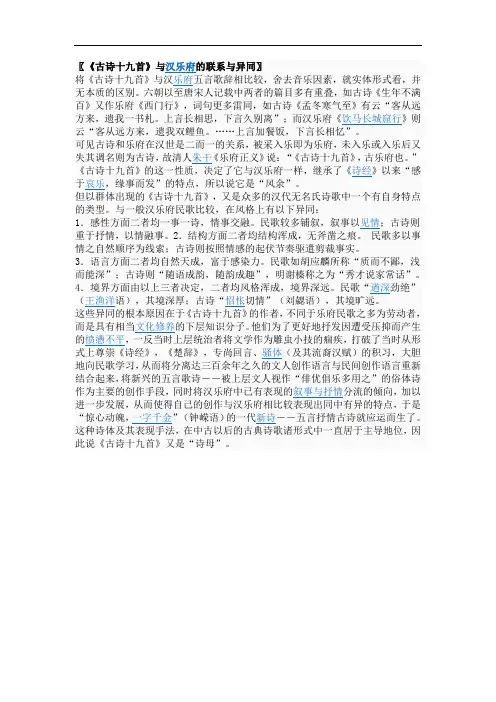
〖《古诗十九首》与汉乐府的联系与异同〗将《古诗十九首》与汉乐府五言歌辞相比较,舍去音乐因素,就实体形式看,并无本质的区别。
六朝以至唐宋人记载中两者的篇目多有重叠,如古诗《生年不满百》又作乐府《西门行》,词句更多雷同,如古诗《孟冬寒气至》有云“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
上言长相思,下言久别离”;而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则云“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
……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
可见古诗和乐府在汉世是二而一的关系,被采入乐即为乐府,未入乐或入乐后又失其调名则为古诗,故清人朱干《乐府正义》说:“《古诗十九首》,古乐府也。
”《古诗十九首》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它与汉乐府一样,继承了《诗经》以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所以说它是“风余”。
但以群体出现的《古诗十九首》,又是众多的汉代无名氏诗歌中一个有自身特点的类型。
与一般汉乐府民歌比较,在风格上有以下异同:1.感性方面二者均一事一诗,情事交融。
民歌较多铺叙,叙事以见情;古诗则重于抒情,以情融事。
2.结构方面二者均结构浑成,无斧凿之痕。
民歌多以事情之自然顺序为线索;古诗则按照情感的起伏节奏驱遣剪裁事实。
3.语言方面二者均自然天成,富于感染力。
民歌如胡应麟所称“质而不鄙,浅而能深”;古诗则“随语成韵,随韵成趣”,明谢榛称之为“秀才说家常话”。
4.境界方面由以上三者决定,二者均风格浑成,境界深远。
民歌“遒深劲绝”(王渔洋语),其境深厚;古诗“怊怅切情”(刘勰语),其境旷远。
这些异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不同于乐府民歌之多为劳动者,而是具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下层知识分子。
他们为了更好地抒发因遭受压抑而产生的愤懑不平,一反当时上层统治者将文学作为雕虫小技的痼疾,打破了当时从形式上尊崇《诗经》,《楚辞》,专尚回言、骚体(及其流裔汉赋)的积习,大胆地向民歌学习,从而将分离达三百余年之久的文人创作语言与民间创作语言重新结合起来,将新兴的五言歌诗--被上层文人视作“俳优倡乐多用之”的俗体诗作为主要的创作手段,同时将汉乐府中已有表现的叙事与抒情分流的倾向,加以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得自己的创作与汉乐府相比较表现出同中有异的特点,于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钟嵘语)的一代新诗--五言抒情古诗就应运而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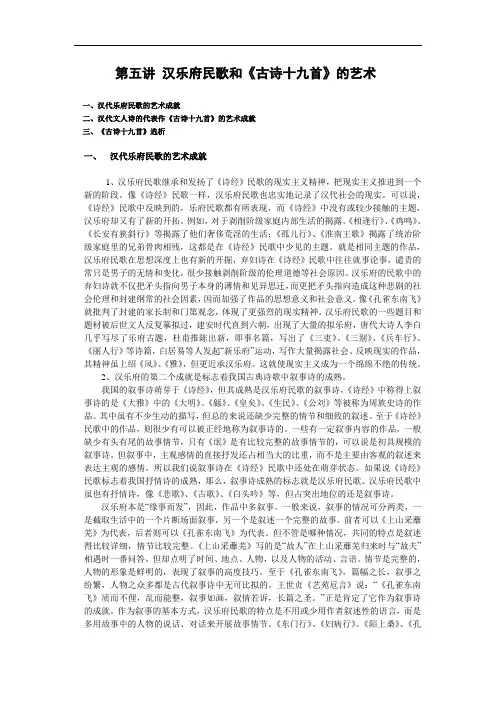
第五讲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的艺术一、汉代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二、汉代文人诗的代表作《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三、《古诗十九首》选析一、汉代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1、汉乐府民歌继承和发扬了《诗经》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把现实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像《诗经》民歌一样,汉乐府民歌也忠实地记录了汉代社会的现实。
可以说,《诗经》民歌中反映到的,乐府民歌都有所表现,而《诗经》中没有或较少接触的主题,汉乐府却又有了新的开拓。
例如,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内部生活的揭露。
《相逢行》、《鸡鸣》、《长安有狭斜行》等揭露了他们奢侈荒淫的生活;《孤儿行》、《淮南王歌》揭露了统治阶级家庭里的兄弟骨肉相残,这都是在《诗经》民歌中少见的主题。
就是相同主题的作品,汉乐府民歌在思想深度上也有新的开掘,弃妇诗在《诗经》民歌中往往就事论事,谴责的常只是男子的无情和变化,很少接触剥削阶级的伦理道德等社会原因。
汉乐府的民歌中的弃妇诗就不仅把矛头指向男子本身的薄情和见异思迁,而更把矛头指向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伦理和封建纲常的社会因素,因而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
像《孔雀东南飞》就批判了封建的家长制和门第观念,体现了更强烈的现实精神。
汉乐府民歌的一些题目和题材被后世文人反复摹拟过,建安时代直到六朝,出现了大量的拟乐府,唐代大诗人李白几乎写尽了乐府古题,杜甫推陈出新,即事名篇,写出了《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等诗篇,白居易等人发起“新乐府”运动,写作大量揭露社会、反映现实的作品,其精神虽上绍《风》、《雅》,但更近承汉乐府。
这就使现实主义成为一个绵绵不绝的传统。
2、汉乐府的第二个成就是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中叙事诗的成熟。
我国的叙事诗萌芽于《诗经》,但其成熟是汉乐府民歌的叙事诗,《诗经》中称得上叙事诗的是《大雅》中的《大明》、《緜》、《皇矣》、《生民》、《公刘》等被称为周族史诗的作品。
其中虽有不少生动的描写,但总的来说还缺少完整的情节和细致的叙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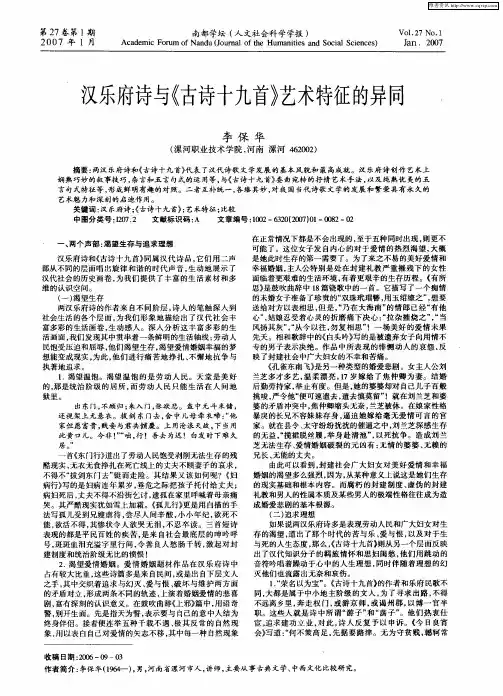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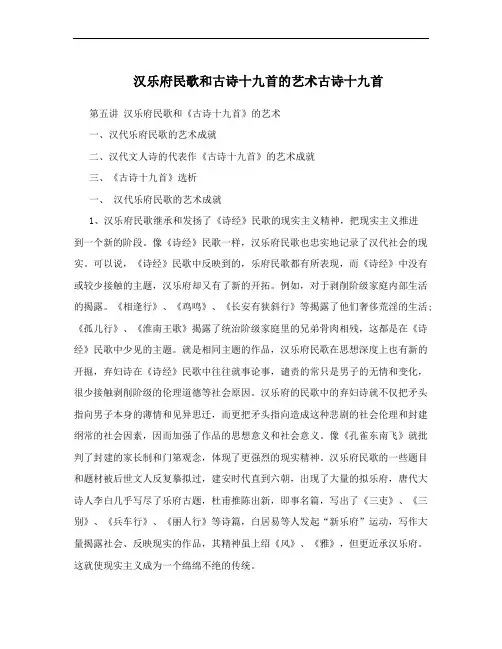
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的艺术古诗十九首第五讲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的艺术一、汉代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二、汉代文人诗的代表作《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三、《古诗十九首》选析一、汉代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1、汉乐府民歌继承和发扬了《诗经》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把现实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像《诗经》民歌一样,汉乐府民歌也忠实地记录了汉代社会的现实。
可以说,《诗经》民歌中反映到的,乐府民歌都有所表现,而《诗经》中没有或较少接触的主题,汉乐府却又有了新的开拓。
例如,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内部生活的揭露。
《相逢行》、《鸡鸣》、《长安有狭斜行》等揭露了他们奢侈荒淫的生活;《孤儿行》、《淮南王歌》揭露了统治阶级家庭里的兄弟骨肉相残,这都是在《诗经》民歌中少见的主题。
就是相同主题的作品,汉乐府民歌在思想深度上也有新的开掘,弃妇诗在《诗经》民歌中往往就事论事,谴责的常只是男子的无情和变化,很少接触剥削阶级的伦理道德等社会原因。
汉乐府的民歌中的弃妇诗就不仅把矛头指向男子本身的薄情和见异思迁,而更把矛头指向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伦理和封建纲常的社会因素,因而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
像《孔雀东南飞》就批判了封建的家长制和门第观念,体现了更强烈的现实精神。
汉乐府民歌的一些题目和题材被后世文人反复摹拟过,建安时代直到六朝,出现了大量的拟乐府,唐代大诗人李白几乎写尽了乐府古题,杜甫推陈出新,即事名篇,写出了《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等诗篇,白居易等人发起“新乐府”运动,写作大量揭露社会、反映现实的作品,其精神虽上绍《风》、《雅》,但更近承汉乐府。
这就使现实主义成为一个绵绵不绝的传统。
2、汉乐府的第二个成就是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中叙事诗的成熟。
我国的叙事诗萌芽于《诗经》,但其成熟是汉乐府民歌的叙事诗,《诗经》中称得上叙事诗的是《大雅》中的《大明》、《緜》、《皇矣》、《生民》、《公刘》等被称为周族史诗的作品。
其中虽有不少生动的描写,但总的来说还缺少完整的情节和细致的叙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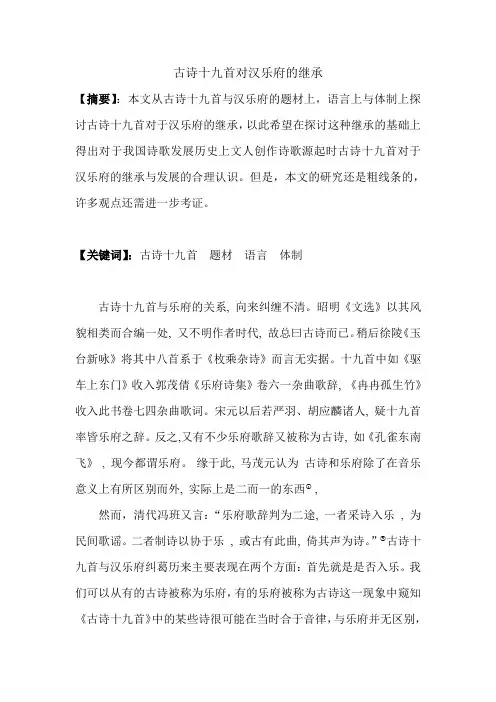
古诗十九首对汉乐府的继承【摘要】:本文从古诗十九首与汉乐府的题材上,语言上与体制上探讨古诗十九首对于汉乐府的继承,以此希望在探讨这种继承的基础上得出对于我国诗歌发展历史上文人创作诗歌源起时古诗十九首对于汉乐府的继承与发展的合理认识。
但是,本文的研究还是粗线条的,许多观点还需进一步考证。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题材语言体制古诗十九首与乐府的关系, 向来纠缠不清。
昭明《文选》以其风貌相类而合编一处, 又不明作者时代, 故总曰古诗而已。
稍后徐陵《玉台新咏》将其中八首系于《枚乘杂诗》而言无实据。
十九首中如《驱车上东门》收入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一杂曲歌辞, 《冉冉孤生竹》收入此书卷七四杂曲歌词。
宋元以后若严羽、胡应麟诸人, 疑十九首率皆乐府之辞。
反之,又有不少乐府歌辞又被称为古诗, 如《孔雀东南飞》, 现今都谓乐府。
缘于此, 马茂元认为古诗和乐府除了在音乐意义上有所区别而外, 实际上是二而一的东西① ,然而,清代冯班又言:“乐府歌辞判为二途, 一者采诗入乐, 为民间歌谣。
二者制诗以协于乐, 或古有此曲, 倚其声为诗。
”②古诗十九首与汉乐府纠葛历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就是是否入乐。
我们可以从有的古诗被称为乐府,有的乐府被称为古诗这一现象中窥知《古诗十九首》中的某些诗很可能在当时合于音律,与乐府并无区别,另一些诗因为文人“不娴于音律”而为徒诗。
所以,是否入乐是不能成为二者的区别的。
其次就是主名问题,二者都是无主名之作。
《文选》以此作为二者的区别实在难以讲通。
可以这样理解,乐府民歌是群众的集体创作,集体创作而无主名是很自然的,《古诗十九首》也无主名,而文人之作一般应有主名,选家知道这些诗乃文人所作,且格凋相近,于是暂且编为一组,称之为古诗。
所以我们可以说《古诗十九首》与乐府民歌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它是由集体创作的乐府民歌向文人创作的徒诗过渡时期的产物。
《古诗十九首》对乐府民歌的继承关系是相当明显的。
无论是题材、语言,还是体制都可以看到乐府民歌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直接脱胎于乐府民歌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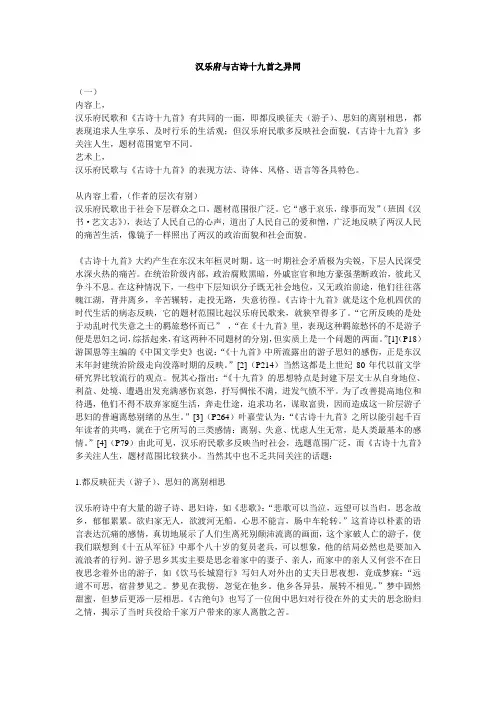
汉乐府与古诗十九首之异同(一)内容上,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有共同的一面,即都反映征夫(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都表现追求人生享乐、及时行乐的生活观;但汉乐府民歌多反映社会面貌,《古诗十九首》多关注人生,题材范围宽窄不同。
艺术上,汉乐府民歌与《古诗十九首》的表现方法、诗体、风格、语言等各具特色。
从内容上看,(作者的层次有别)汉乐府民歌出于社会下层群众之口,题材范围很广泛。
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表达了人民自己的心声,道出了人民自己的爱和憎,广泛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痛苦生活,像镜子一样照出了两汉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
《古诗十九首》大约产生在东汉末年桓灵时期。
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极为尖锐,下层人民深受水深火热的痛苦。
在统治阶级内部,政治腐败黑暗,外戚宦官和地方豪强垄断政治,彼此又争斗不息。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下层知识分子既无社会地位,又无政治前途,他们往往落魄江湖,背井离乡,辛苦辗转,走投无路,失意彷徨。
《古诗十九首》就是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生活的病态反映,它的题材范围比起汉乐府民歌来,就狭窄得多了。
“它所反映的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的羁旅愁怀而已”,“在《十九首》里,表现这种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便是思妇之词,综括起来,有这两种不同题材的分别,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1](P18)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说:“《十九首》中所流露出的游子思妇的感伤,正是东汉末年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
”[2](P214)当然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文学研究界比较流行的观点。
倪其心指出:“《十九首》的思想特点是封建下层文士从自身地位、利益、处境、遭遇出发充满感伤哀怨,抒写惆怅不满,迸发气愤不平。
为了改善提高地位和待遇,他们不得不放弃家庭生活,奔走仕途,追求功名,谋取富贵,因而造成这一阶层游子思妇的普遍离愁别绪的丛生。
”[3](P264)叶嘉莹认为:“《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能引起千百年读者的共鸣,就在于它所写的三类感情:离别、失意、忧虑人生无常,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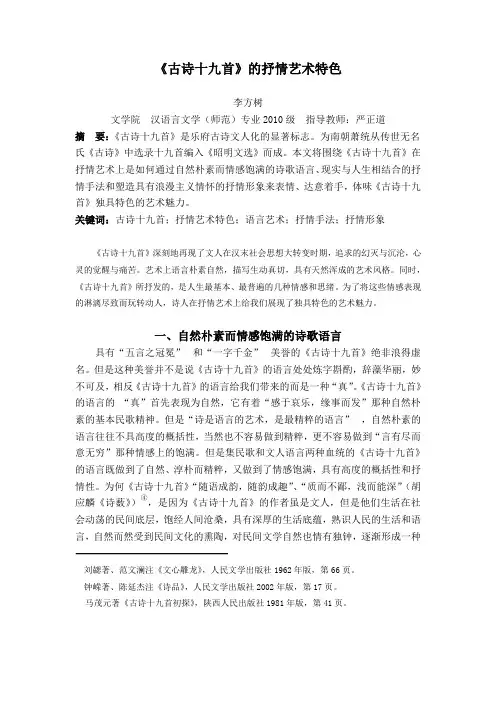
《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特色李方树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2010级指导教师:严正道摘要:《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
为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昭明文选》而成。
本文将围绕《古诗十九首》在抒情艺术上是如何通过自然朴素而情感饱满的诗歌语言、现实与人生相结合的抒情手法和塑造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抒情形象来表情、达意着手,体味《古诗十九首》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抒情艺术特色;语言艺术;抒情手法;抒情形象《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
艺术上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
同时,《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
为了将这些情感表现的淋漓尽致而玩转动人,诗人在抒情艺术上给我们展现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
一、自然朴素而情感饱满的诗歌语言具有“五言之冠冕”和“一字千金”美誉的《古诗十九首》绝非浪得虚名。
但是这种美誉并不是说《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处处炼字斟酌,辞藻华丽,妙不可及,相反《古诗十九首》的语言给我们带来的而是一种“真”。
《古诗十九首》的语言的“真”首先表现为自然,它有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那种自然朴素的基本民歌精神。
但是“诗是语言的艺术,是最精粹的语言”,自然朴素的语言往往不具高度的概括性,当然也不容易做到精粹,更不容易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那种情感上的饱满。
但是集民歌和文人语言两种血统的《古诗十九首》的语言既做到了自然、淳朴而精粹,又做到了情感饱满,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抒情性。
为何《古诗十九首》“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质而不鄙,浅而能深”(胡应麟《诗薮》)④,是因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虽是文人,但是他们生活在社会动荡的民间底层,饱经人间沧桑,具有深厚的生活底蕴,熟识人民的生活和语言,自然而然受到民间文化的熏陶,对民间文学自然也情有独钟,逐渐形成一种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6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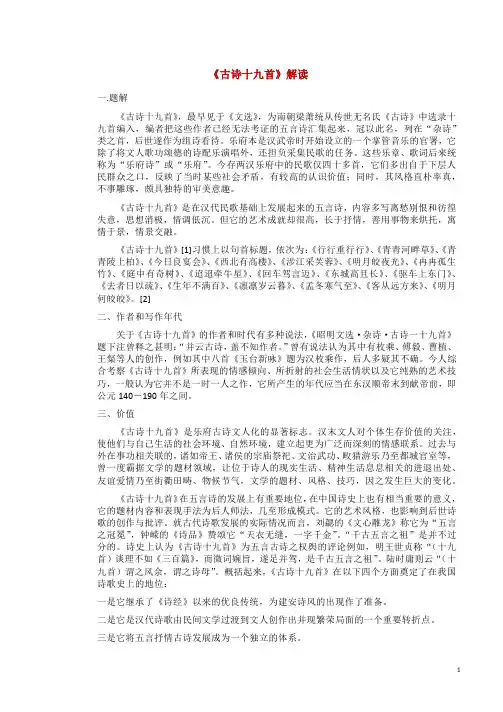
《古诗十九首》解读一.题解《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文选》,为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编者把这些作者已经无法考证的五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
乐府本是汉武帝时开始设立的一个掌管音乐的官署,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配乐演唱外,还担负采集民歌的任务。
这些乐章、歌词后来统称为“乐府诗”或“乐府”。
今存两汉乐府中的民歌仅四十多首,它们多出自于下层人民群众之口,反映了当时某些社会矛盾,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同时,其风格直朴率真,不事雕琢,颇具独特的审美意趣。
《古诗十九首》是在汉代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言诗,内容多写离愁别恨和彷徨失意,思想消极,情调低沉。
但它的艺术成就却很高,长于抒情,善用事物来烘托,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古诗十九首》[1]习惯上以句首标题,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
[2]二、作者和写作年代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有多种说法,《昭明文选·杂诗·古诗一十九首》题下注曾释之甚明:“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
”曾有说法认为其中有枚乘、傅毅、曹植、王粲等人的创作,例如其中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
今人综合考察《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倾向、所折射的社会生活情状以及它纯熟的艺术技巧,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它所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即公元140-190年之间。
三、价值《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
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
浅析《古诗》的抒情艺术浅析《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古诗十九首》是由汉代无名文人创作的五言抒情短诗,最早著录于萧统的《文选》。
《古诗十九首》自出现以来,就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被誉为“五言之冠冕”。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古诗十九首》和《诗经》往往相提并论,它之所以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主要是因为它在艺术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马茂元先生指出:“《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总结了汉代乐府的光辉成就,替建安文学奠定了牢固的基石。
它正是由两汉发展到魏晋,南北朝诗歌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古诗十九首》是以抒情见长的,它发展了汉乐府抒情性的一面,使五言诗发展成为成熟的抒情诗。
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早期抒情诗的典范,呈现出了和前代抒情诗截然不同的风貌。
《古诗十九首》所抒之情是自我之情,关注的是一己之情。
在真正意义上表现了人的本身,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各种正常的感情。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大多数是中下层文人,他们常年漂泊在外,为的是能步入仕途,建立功业。
东汉承袭了西汉的察举制度,有地方察举贤良方正,孝廉,茂才,明经等,然后待诏而行。
所以东都洛阳就成了许多文人士子的游学,读书之地,谋求功名利禄的场所。
但是追求功名富贵的人一天天的增多,而官僚机构的容纳毕竟是有限的,这就形成了得机幸进者少,失意向隅者多的现象。
而且东汉末年是政治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
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政治上的腐化和堕落已达到顶点。
在这种情况下,中下层文人失去了正常仕进的机会,倍感前途的渺茫和无望。
这样的遭遇,使得他们彷徨苦闷,难以抑制心中的悲哀,发而为诗。
就充满了“怨”的色彩。
但是这种“怨”是哀而怨,不同于《诗经》中的“怨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着眼的是自身,他们无意于反映深广的社会现实,他们要抒发的是自己的人生感慨,所忧所怨都与自身的遭遇有关。
令他们感伤的是功业难成“无为守贫贱,轗轲常苦辛》(《今日良宴会》);朋友的遗弃“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明月皎夜光》);知音难觅“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西北有高楼》);相思成疾“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行行重行行》);人生苦短“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驱车上东门》)。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昭明文选》,作者为东汉时期已不可考的一些下层文人。
他们或直抒胸臆,或借题发挥,书法的大都是个人的厉害得失,怀才不遇,以及穷困潦倒的各种忧愤之情。
由于这些作品本无统一名称,但在内容风格上相近,萧统讲这些作品编在一起,题名为《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早期文人五言诗的重要作品,对后代具有很大影响,钟嵘说它“几乎一字千金”,亦被刘勰喻为“五言之冠冕”。
建安风骨是前人概括出的建安时期作品的风格特点。
建安诗人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苦难,展示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抒发作家建功立业的理想壮志和积极进取精神;也流露出人生短促、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情绪。
这些作品意境宏大,笔调明朗,形成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色。
永明体又称新体诗,最早出现于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
此时,声律说有了突破发展,诗人自觉地把声律说自觉地运用于诗歌创作,产生了面目一新的新体诗。
这些新体诗自觉地运用“四声”、避免“八病”,形成了“永明体”。
永明体的代表作家有谢朓、沈约、王融。
变文简称为“变”,它是在佛教僧侣所谓“唱导”的影响下,继承汉魏六朝乐府诗、志怪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逐渐发展成熟的一种说唱体的通俗文学。
变文和后世的“演义”相类似,即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们容易明白。
变文以长篇叙事为主,极善于敷衍故事,充分发挥了佛教文学的想象奇特、色彩瑰丽、布局宏大、场景宏伟的特点。
变文在艺术形式上也有独特的创造。
除了叙事曲折、描写生动、想象丰富、语言通俗外,体制上韵文与散文相结合是其重要特点。
变文对唐代文人创作,特别是传奇的创作,对后代的诸宫调、宝卷、鼓词、弹词等讲唱文学和杂剧、南戏等戏曲文学,也有积极的影响。
□沉郁顿挫沉郁顿挫是指感情而言,“沉郁”者,“意”也,“沉郁”是指有深挚、沉雄,郁结,抑塞的感情内容;“顿挫”者,“法”也,“顿挫”是指感情的力度,深度,浓度,侧重于意和思想,是指感情表达的方式。
《古诗十九首》对汉乐府的继承发展20世纪末期, 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等中国学人对肇始于美国的口头诗学展开了系统的引介、翻译, 将它进行吸纳、转化和本土化, 创造性地解决本民族的问题。
在进入中国学界的20多年中, 口头诗学“不仅催生了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史诗学的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 而且渐为民间文学以外的其他邻近学科提供了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的理论参照与技术路线”。
一直以来, 汉乐府的研究大都呈现为“文学本位”研究态势, 重视汉乐府的“本”, 将它作为一种独立完足的意义单元, 忽视它的演唱性质。
但我们应该明白, 汉乐府是音乐歌舞表演的产物。
对于汉乐府而言, “文本”的概念来源于“演述中的创作”, 演唱者、受众、演唱场所等其他与演唱有关的要素, 汉乐府的意义由他们共同创造出来的, 而口头诗学则为研究汉乐府的生成过程提供了理论支撑, 以程式为切入点, 分析汉乐府的口承性让我们更好地认识程式在汉乐府创作、演唱、流布中的地位。
《古诗十九首》是一组代表着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的诗歌, 对魏晋以来文人五言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被刘勰誉之为“五言之冠冕”。
《古诗十九首》与汉乐府有着紧密的关联, 存在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古诗十九首》以书面的形式保留了大量的口头艺术特征, 它们已经深入到《古诗十九首》的语词、体式、结构单元、叙事话语等诸多方面。
程式是口头诗学的理论精髓, 是“在相同的格律条件下为表达一种特定的基本观念而经常使用的一组词”。
在此基础上, 根据汉语诗歌生成规律与结构形态, 本文的程式指反复出现的由两个以上的字构成且表达某种特定内容的语词。
程式是汉乐府重要的口传特征, 它在汉乐府由口头演唱的状态转换成书面状态的过程中保留下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 中国学人已经认识到了汉乐府中的程式现象。
余冠英在《乐府歌辞的拼凑和分割》中指出“套语”是古乐府歌辞拼合方式之一:“套语, 在乐府诗句里常见‘今日乐相乐, 延年万岁期', ‘今日乐相乐, 延年寿千霜', ‘吾欲竟此曲, 此曲愁人肠', ‘吾欲竟此曲, 此曲悲且长', 或‘愿令皇帝陛下三千岁', ‘欲令皇帝陛下三千万'之类, 大同小异, 已成套语, 随意凑合, 无关意义。
【国学】常读常新的古诗十九首甜甜仿似和一个人相识的过程,在倾听其心声和品读其思想前,了解他一些相关的情况能为日后的深交作下铺垫。
同样,小编在带大家解读《古诗十九首》为何常读常新之前,查户口式的“扫盲”就是为后续触摸诗魂作前奏铺垫。
《古诗十九首》,顾名思义,是由十九首古诗组合而成的组诗。
编者为南朝梁萧统。
他把这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作者的五言诗从传世的《古诗》中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并列在“杂诗”类之首,编入《文选》。
在题材、语言和体制上,《古诗十九首》是对汉代民歌特别是汉乐府的继承和发展。
题材上,多写离愁别恨和彷徨失意,思想总体上较消极,情调低沉。
诗句中有对汉乐府诗歌的提炼甚至直接套用。
但它的艺术成就却很高,长于抒情,善用事物来烘托,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语言上,因创作年代与汉乐府相去不远,以叠字为特色。
与此同时,可窥见其继承《诗经》重章叠句、善用比兴手法的痕迹,吟咏起来蕴藉悠长,回味无穷。
可见,钟嵘会在其《诗品》中作出论断:“古诗其体源于国风”。
体制上,《古诗十九首》句式整饬,以纯五言为主,不仅与以“四言为主,偶见五言,但又无通篇五言”的《诗经》不同,也和“句不限字数,篇不限句数”的汉乐府所不同。
因此,有学者认为,《古诗十九首》是集体创作的乐府民歌向文人创作的徒诗过渡时期的产物。
和《诗经》、汉乐府民歌相似,《古诗十九首》的作者考证亦颇具争议。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这并非同一时期所作,也不是出自一人之手。
根据诗歌内容题材和语言风格方面的特征,人们推测,它们产生于东汉末期前后。
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首倡创作于“两汉”的观点,此外,根据诗歌语言显然是经过锤炼而有别于自然无斧凿典型民歌的特征,有学者认为这组诗歌多出自文人之手。
刘勰又说《冉冉孤生竹》一篇为傅毅所作,王世贞则猜测“杂有枚生或张衡、蔡邕作”,而徐陵在《玉台新咏》中推测其中八首为汉初枚乘所作。
因缺乏证据,后人多认为这些观点不可信。
但不管怎样,《古诗十九首》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xx与古诗十九首之异同(一)内容上,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有共同的一面,即都反映征夫(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都表现追求人生享乐、及时行乐的生活观;但汉乐府民歌多反映社会面貌,《古诗十九首》多关注人生,题材范围宽窄不同。
艺术上,汉乐府民歌与《古诗十九首》的表现方法、诗体、风格、语言等各具特色。
从内容上看,(作者的层次有别)汉乐府民歌出于社会下层群众之口,题材范围很广泛。
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表达了人民自己的心声,道出了人民自己的爱和憎,广泛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痛苦生活,像镜子一样照出了两汉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
《古诗十九首》大约产生在东汉末年桓灵时期。
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极为尖锐,下层人民深受水深火热的痛苦。
在统治阶级内部,政治腐败黑暗,外戚宦官和地方豪强垄断政治,彼此又争斗不息。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下层知识分子既无社会地位,又无政治前途,他们往往落魄江湖,背井离乡,辛苦辗转,走投无路,失意彷徨。
《古诗十九首》就是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生活的病态反映,它的题材范围比起汉乐府民歌来,就狭窄得多了。
“它所反映的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的羁旅愁怀而已”,“在《十九首》里,表现这种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便是思妇之词,综括起来,有这两种不同题材的分别,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1](P18)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说:“《十九首》中所流露出的游子思妇的感伤,正是东汉末年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
”[2](P214)当然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文学研究界比较流行的观点。
倪其心指出:“《十九首》的思想特点是封建下层文士从自身地位、利益、处境、遭遇出发充满感伤哀怨,抒写惆怅不满,迸发气愤不平。
为了改善提高地位和待遇,他们不得不放弃家庭生活,奔走仕途,追求功名,谋取富贵,因而造成这一阶层游子思妇的普遍离愁别绪的丛生。
”[3](P264)叶嘉莹认为:“《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能引起千百年读者的共鸣,就在于它所写的三类感情:离别、失意、忧虑人生无常,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
《古诗十九首》对汉乐府的继承发展20世纪末期, 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等中国学人对肇始于美国的口头诗学展开了系统的引介、翻译, 将它进行吸纳、转化和本土化, 创造性地解决本民族的问题。
在进入中国学界的20多年中, 口头诗学“不仅催生了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史诗学的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 而且渐为民间文学以外的其他邻近学科提供了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的理论参照与技术路线”。
一直以来, 汉乐府的研究大都呈现为“文学本位”研究态势, 重视汉乐府的“本”, 将它作为一种独立完足的意义单元, 忽视它的演唱性质。
但我们应该明白, 汉乐府是音乐歌舞表演的产物。
对于汉乐府而言, “文本”的概念来源于“演述中的创作”, 演唱者、受众、演唱场所等其他与演唱有关的要素, 汉乐府的意义由他们共同创造出来的, 而口头诗学则为研究汉乐府的生成过程提供了理论支撑, 以程式为切入点, 分析汉乐府的口承性让我们更好地认识程式在汉乐府创作、演唱、流布中的地位。
《古诗十九首》是一组代表着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的诗歌, 对魏晋以来文人五言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被刘勰誉之为“五言之冠冕”。
《古诗十九首》与汉乐府有着紧密的关联, 存在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古诗十九首》以书面的形式保留了大量的口头艺术特征, 它们已经深入到《古诗十九首》的语词、体式、结构单元、叙事话语等诸多方面。
程式是口头诗学的理论精髓, 是“在相同的格律条件下为表达一种特定的基本观念而经常使用的一组词”。
在此基础上, 根据汉语诗歌生成规律与结构形态, 本文的程式指反复出现的由两个以上的字构成且表达某种特定内容的语词。
程式是汉乐府重要的口传特征, 它在汉乐府由口头演唱的状态转换成书面状态的过程中保留下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 中国学人已经认识到了汉乐府中的程式现象。
余冠英在《乐府歌辞的拼凑和分割》中指出“套语”是古乐府歌辞拼合方式之一:“套语, 在乐府诗句里常见‘今日乐相乐, 延年万岁期’, ‘今日乐相乐, 延年寿千霜’, ‘吾欲竟此曲, 此曲愁人肠’, ‘吾欲竟此曲, 此曲悲且长’, 或‘愿令皇帝陛下三千岁’, ‘欲令皇帝陛下三千万’之类, 大同小异, 已成套语, 随意凑合, 无关意义。
”由整个诗句构成常见于汉乐府的程式有“常恐秋节至”“易知复难忘”“作使邯郸倡”“黄金络马头”等。
由三个字组成的程式与其他语言成分结合而构成一个完整的诗句, 如“青龙对道隅”与“青龙对伏趺”“左手持刀尺”和“左手持强弹”“道隘不容车”和“狭斜不容车”“冉冉府中趋”和“盈盈府中趋”等。
由两个字组成的程式也常见于汉乐府民歌, 它与三个字组成的语言成分结合而构造出一个完整的诗句, 如“自名为罗敷”和“自名秦罗敷”“头上倭堕髻”和“头上玳瑁光”。
当然, 在当时的实际演唱中, 汉乐府使用的程式远要多于今天以稿本形态存留的汉乐府。
赵敏俐指出汉乐府歌诗里的语言程式化是口头传唱的结果, 体现了口头诗学的残余特征, 将它视为一种创作技巧。
他推测汉乐府的语言程式是音乐表演的衍生物, 肯定它是口头诗人在现场创编的压力下使用的固定套式, 而非文人诗人案头吟唱的产物。
他说道:“由于汉乐府歌诗的这种程式化是在形成的过程中, 对于音乐表演方式的重视胜过对语言的重视, 所以才会出现乐调的相对固定而歌辞中时见套语、重复等现象。
……音乐在里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歌舞艺人们只要对乐调熟悉, 就可以按照固定的乐调即兴演唱, 并随口加入一些套语, 使所表演的诗歌符合习惯, 符合消费者的欣赏习惯, 从而得到他们的欢迎。
余冠英将汉乐府歌诗的“程式”归于汉乐府“重声不重辞”与“完全为合乐的方便”。
齐天举把《孔雀东南飞》与《古艳歌》并置, 讨论口头诗人使用“套语”编织新歌的方式, 重点论述的是汉乐府诗的拼凑与分割问题。
程式是演唱传统的产物, 对演唱者和受众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诚然, 离开了真实的说唱语境, 程式便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创造活力, 成为一种苍白的陈词滥调。
但是, 当我们以口头诗学理论重新估价它们, 便会发现它们在演唱和受众的接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是演唱者构筑一个完整演唱事件不可或缺的部件, 也是受众顺畅接受说唱活动的保证。
它不是简单的重复, 而是在一定框架内有着变化的构筑部件。
赵敏俐高度评价了汉乐府使用的“程式”持有的功能:“正是由于套语的使用, 使汉乐府的歌诗演唱可以比较容易地纳入相应的音乐调式之中, 也容易被消费者所接受, 因而才会使一首诗在社会上很快地流传开来。
”他一再重申汉乐府演唱与语言程式的关系, 提出“为了顺利流畅地表达而充分地使用套语”与“歌诗的写作要符合汉乐府相和诸调的表演套路”的观点。
我们必须将程式放在具体的演唱语域里阐发它的传统内涵和功能。
以汉乐府演唱结束时使用的程式化语句为例, 根据古代典籍记载, 在王公贵族的宴饮集会上, 口头诗人经常会演唱歌辞给主人和宾客助兴, 在每次宴集结束以前, 都会演唱一些程式化的表示祝福或祈愿的词语。
胡应麟《诗薮·古体杂言》有云:“乐府尾句, 多用‘今日乐相乐’等语, 至有与题意及上文略不相蒙者, 旧亦疑之。
盖汉魏诗皆以被之弦歌, 必燕会间用之。
尾句如此, 率为听乐者设, 即《郊祀》延年意也。
”有时, 表示结尾的程式有一种劝诫的含义, 如“多谢后世人, 戒之慎勿忘”。
顾颉刚对此曾说:“末云‘多谢后世人, 戒之慎勿忘’, 这种唱罢时对于听众的叮咛的口气, 与今大鼓书中《单刀赴会》的结尾说‘这就是五月十三圣贤爷单刀会, 留下了仁义二字万古传’, 《吕蒙正教书》的结尾说‘明公听了这个段, 凡事要忍心莫要高’是很相像的。
”正是因为程式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汉乐府中常见前后文意不一致或无关的现象, 余冠英认为这些割截拼凑完全是为合乐的方便。
赵敏俐认为演唱中的口头诗人“似乎不太关心语言的修饰, 只是顺着故事的发展次序, 凭着自己对于演唱套路的熟悉来进行即兴表演, 比较随意地组合成了一首歌”。
朝戈金对口头史诗中叙述内容的不一致做出过科学合理的解释, 说道:“至于叙述中的‘缺陷’, 那是由于歌手是依照着固定的主题来结构故事的, 一些高度模式化了的传统主题, 是适合拼合在一起以构成故事的, 但是它们又在细节的某些方面彼此矛盾或不一致, 而此时的歌手正全神贯注于表演, 未必会意识到在他的演唱中, 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这种所谓文本的缺陷, 是口头表演中所难以避免的, 它未必与‘年代累层’或‘片断汇聚’这些口传文化现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或许, 这种观点能够较为科学合理地解释汉乐府中拼凑分割和文意互不相属的现象。
汉乐府中的程式在口头诗人长期使用过程中逐渐定型, 成为口头诗人演唱汉乐府惯用的构筑诗句的部件。
随后, 它们逐渐为文人所接受, 文人使用它们来创作自己的书面诗歌。
《古诗十九首》大量使用了汉乐府中的程式化诗句, 体现了文人对汉乐府演唱传统的承继。
(一) 由多个诗行构成的程式。
汉乐府《西门行》:“人生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 何不秉烛游。
”古诗十九首之《生年不满百》:“生年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 何不秉烛游。
”(17)(二) 由一个诗行组成的程式。
1. 汉乐府《饮马长城窟》:“青青河畔草。
”古诗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
2. 汉乐府《陇西行》:“行行重行行”。
古诗十九首之《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
3. 汉乐府《古杨柳行》:“浮云蔽白日”。
古诗十九首之《行行重行行》:“浮云蔽白日”。
(三) 由一个诗行中的某些词构成的程式。
1. 汉乐府《饮马长城窟》:“上言加餐饭, 下言长相忆”。
古诗十九首之《孟冬寒气至》:“上言长相思, 下言久离别”。
2. 汉乐府《艳歌何尝行》:“忧来生别离”。
古诗十九首之《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3. 汉乐府《古歌》:“衣带日趋缓”。
古诗十九首之《行行重行行》:“衣带日以缓”。
4. 汉乐府《妇病行》:“弃置勿复道”。
古诗十九首之《行行重行行》:“弃捐勿复道”。
5. 汉乐府《长歌行》:“青青园中葵”。
古诗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
6. 汉乐府《白头吟》:“今日斗酒会”。
古诗十九首之《今日良宴会》:“今日良宴会”。
7. 汉乐府《长歌行》:“驱车出北门, 遥观洛阳城”。
古诗十九首之《驱车上东门》:“驱车上东门, 遥望郭北墓”。
8. 汉乐府《陇西行》:“桂树夹道生”。
古诗十九首之《驱车上东门》:“松柏夹广路”。
9. 汉乐府《饮马长城窟》:“客从远方来, 遗我双鲤鱼”。
古诗十九首之《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 遗我一书札”。
古诗十九首之《客从远方来》:“客从远方来, 遗我一端绮”。
可以看出, 《古诗十九首》中的程式与汉乐府有很大的相似性, 有的甚至是直接套用。
这也见出《古诗十九首》与汉乐府在程式的使用上有着承继关系。
考察《古诗十九首》自身使用的语词, 可以发现许多语词都是反复出现, 呈现程式化的特征:(一) 由一个诗行构成的程式。
1.《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
《客从远方来》:“客从远方来”。
2.《行行重行行》:“相去万余里”。
《客从远方来》:“相去万余里”。
3.《行行重行行》:“思君令人老”。
《冉冉孤生竹》:“思君令人老”。
(二) 由一个诗行中的某些词构成的程式。
1.《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 郁郁园中柳。
”《青青陵上柏》:“青青陵上柏, 磊磊涧中石。
”2.《青青河畔草》:“皎皎当窗牗, 纤纤出素手。
”《迢迢牵牛星》:“纤纤擢素手, 扎扎弄机杼。
”3.《迥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
《冉冉孤生竹》:“悠悠隔山陂”。
4.《驱车上东门》:“驱车上东门”。
《青青陵上柏》:“驱车策驽马”。
5.《东城高且长》:“被服罗裳衣”。
《驱车上东门》:“被服纨与素”。
6.《东城高且长》:“思为双飞燕”。
《西北有高楼》:“愿为双鸿鹄”。
7.《孟冬寒气至》:“遗我一书札”。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
8.《迥车驾言迈》:“四顾何茫茫”。
《驱车上东门》:“白杨何萧萧”。
9.《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
1 0.《青青陵上柏》:“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
”《今日良宴会》:“人生寄一世, 奄忽若鹰尘。
”《驱车上东门》:“人生忽如寄, 寿无金石固。
”《迥车驾言迈》:“人生非金石, 岂能长寿考?”11.《行行重行行》:“游子不顾返”。
《青青河畔草》:“荡子行不归”。
《古诗十九首》共有254诗行, 其中“程式”数量共计53行, 其程式频密度约为21%。
古法语诗歌研究者使用程式频密度判定一首诗歌是否为口头创作的作品, 他说:“我想作这样的具体限定:总的说来, 如果纯粹的重复少于20%, 那么它就可能是来源于书面的或书写的创作;而当程式的频密度超过了20%, 即可证明它是口头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