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文学概述
- 格式:doc
- 大小:36.00 KB
- 文档页数: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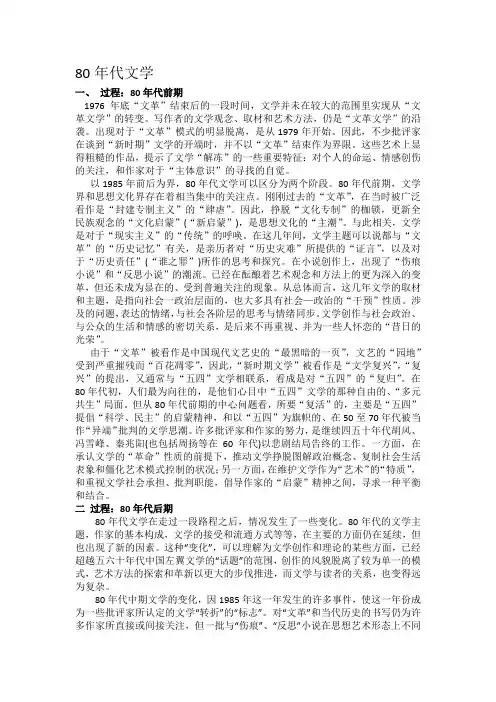
80年代文学一、过程:80年代前期1976年底“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文学并未在较大的范围里实现从“文革文学”的转变。
写作者的文学观念、取材和艺术方法,仍是“文革文学”的沿袭。
出现对于“文革”模式的明显脱离,是从1979年开始。
因此,不少批评家在谈到“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时,并不以“文革”结束作为界限。
这些艺术上显得粗糙的作品,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特征:对个人的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和作家对于“主体意识”的寻找的自觉。
以1985年前后为界,80年代文学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
80年代前期,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存在着相当集中的关注点。
刚刚过去的“文革”,在当时被广泛看作是“封建专制主义”的“肆虐”。
因此,挣脱“文化专制”的枷锁,更新全民族观念的“文化启蒙”(“新启蒙”),是思想文化的“主潮”。
与此相关,文学是对于“现实主义”的“传统”的呼唤。
在这几年间,文学主题可以说都与“文革”的“历史记忆”有关,是亲历者对“历史灾难”所提供的“证言”,以及对于“历史责任”(“谁之罪”)所作的思考和探究。
在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的潮流。
已经在酝酿着艺术观念和方法上的更为深入的变革,但还未成为显在的、受到普遍关注的现象。
从总体而言,这几年文学的取材和主题,是指向社会一政治层面的,也大多具有社会—政治的“干预”性质。
涉及的问题,表达的情绪,与社会各阶层的思考与情绪同步。
文学创作与社会政治、与公众的生活和情感的密切关系,是后来不再重视、并为一些人怀恋的“昔日的光荣”。
由于“文革”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文艺史的“最黑暗的一页”,文艺的“园地”受到严重摧残而“百花凋零”,因此,“新时期文学”被看作是“文学复兴”,“复兴”的提出,又通常与“五四”文学相联系,看成是对“五四”的“复归”。
在80年代初,人们最为向往的,是他们心目中“五四”文学的那种自由的、“多元共生”局面。
但从80年代前期的中心问题看,所要“复活”的,主要是“五四”提倡“科学、民主”的启蒙精神,和以“五四”为旗帜的、在50至70年代被当作“异端”批判的文学思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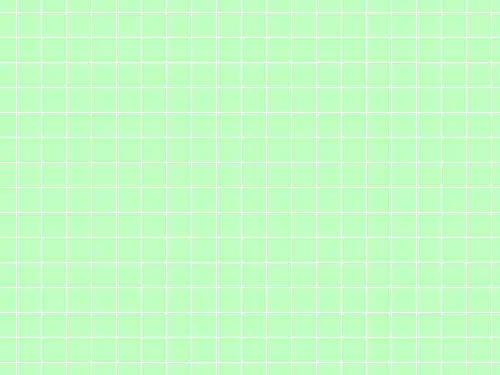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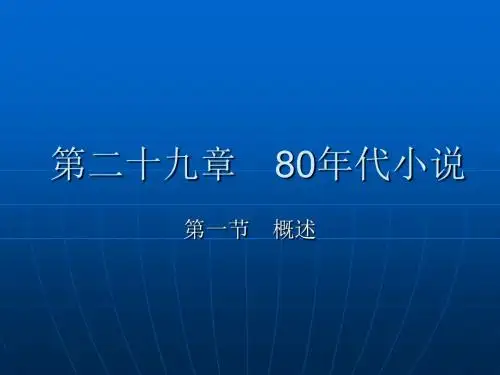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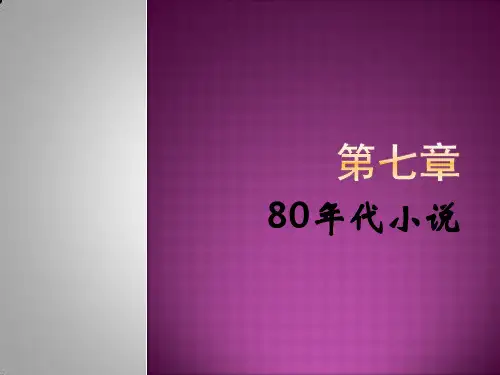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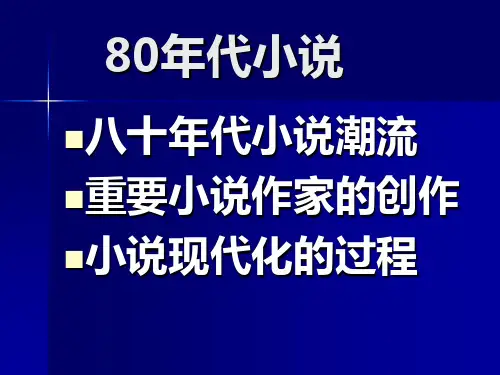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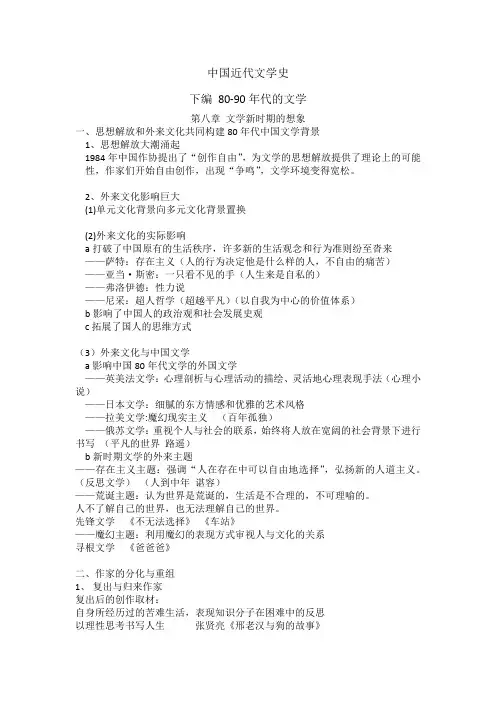
中国近代文学史下编80-90年代的文学第八章文学新时期的想象一、思想解放和外来文化共同构建80年代中国文学背景1、思想解放大潮涌起1984年中国作协提出了“创作自由”,为文学的思想解放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作家们开始自由创作,出现“争鸣”,文学环境变得宽松。
2、外来文化影响巨大(1)单元文化背景向多元文化背景置换(2)外来文化的实际影响a打破了中国原有的生活秩序,许多新的生活观念和行为准则纷至沓来——萨特:存在主义(人的行为决定他是什么样的人,不自由的痛苦)——亚当·斯密:一只看不见的手(人生来是自私的)——弗洛伊德:性力说——尼采:超人哲学(超越平凡)(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体系)b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观和社会发展史观c拓展了国人的思维方式(3)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学a影响中国80年代文学的外国文学——英美法文学:心理剖析与心理活动的描绘、灵活地心理表现手法(心理小说)——日本文学:细腻的东方情感和优雅的艺术风格——拉美文学:魔幻现实主义(百年孤独)——俄苏文学:重视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始终将人放在宽阔的社会背景下进行书写(平凡的世界路遥)b新时期文学的外来主题——存在主义主题:强调“人在存在中可以自由地选择”,弘扬新的人道主义。
(反思文学)(人到中年谌容)——荒诞主题:认为世界是荒诞的,生活是不合理的,不可理喻的。
人不了解自己的世界,也无法理解自己的世界。
先锋文学《不无法选择》《车站》——魔幻主题:利用魔幻的表现方式审视人与文化的关系寻根文学《爸爸爸》二、作家的分化与重组1、复出与归来作家复出后的创作取材:自身所经历过的苦难生活,表现知识分子在困难中的反思以理性思考书写人生张贤亮《邢老汉与狗的故事》2、知青作家(知青生活)知青文学记录了他们在近十年动荡中的生活历程和心灵轨迹,具有“自序传”的性质(1)在伤痕文学的浪潮中扮演重要角色,以控诉、揭露和义愤代表一代人的觉醒卢新华《伤痕》(2)走出伤痕后,重新审视生活,出现思辨、哲理化的倾向王安亿《本次列车终点》(3)相对集中和独立的状态开始打破,逐渐融入到整个文学进程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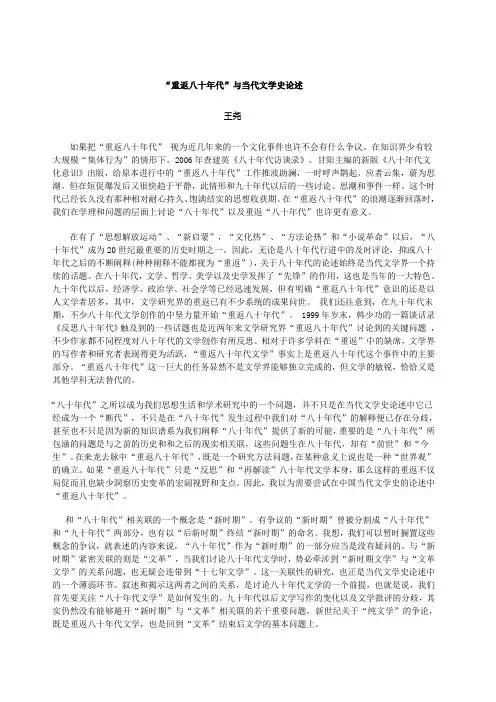
“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王尧如果把“重返八十年代” 视为近几年来的一个文化事件也许不会有什么争议。
在知识界少有较大规模“集体行为”的情形下,2006年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主编的新版《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出版,给原本进行中的“重返八十年代”工作推波助澜,一时呼声鹊起、应者云集,蔚为思潮。
但在短促爆发后又很快趋于平静,此情形和九十年代以后的一些讨论、思潮和事件一样。
这个时代已经长久没有那种相对耐心持久、饱满结实的思想收获期。
在“重返八十年代”的浪潮逐渐回落时,我们在学理和问题的层面上讨论“八十年代”以及重返“八十年代”也许更有意义。
在有了“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文化热”、“方法论热”和“小说革命”以后,“八十年代”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
因此,无论是八十年代行进中的及时评论,抑或八十年代之后的不断阐释(种种阐释不能都视为“重返”),关于八十年代的论述始终是当代文学界一个持续的话题。
在八十年代,文学、哲学、美学以及史学发挥了“先锋”的作用,这也是当年的一大特色。
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已经迅速发展,但有明确“重返八十年代”意识的还是以人文学者居多,其中,文学研究界的重返已有不少系统的成果问世。
我们还注意到,在九十年代末期,不少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开始“重返八十年代”。
1999年岁末,韩少功的一篇谈话录《反思八十年代》触及到的一些话题也是近两年来文学研究界“重返八十年代”讨论到的关键问题,不少作家都不同程度对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有所反思。
相对于许多学科在“重返”中的缺席,文学界的写作者和研究者表现得更为活跃,“重返八十年代文学”事实上是重返八十年代这个事件中的主要部分。
“重返八十年代”这一巨大的任务显然不是文学界能够独立完成的,但文学的敏锐,恰恰又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
“八十年代”之所以成为我们思想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并不只是在当代文学史论述中它已经成为一个“断代”,不只是在“八十年代”发生过程中我们对“八十年代”的解释便已存在分歧,甚至也不只是因为新的知识谱系为我们阐释“八十年代”提供了新的可能,重要的是“八十年代”所包涵的问题是与之前的历史和和之后的现实相关联,这些问题生在八十年代,却有“前世”和“今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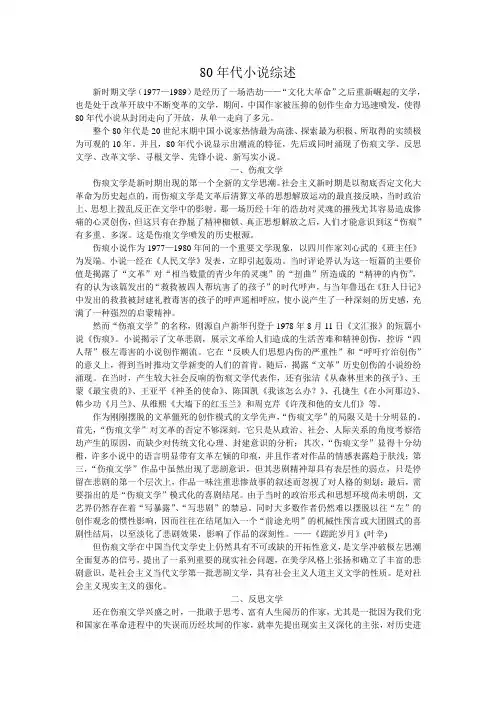
80年代小说综述新时期文学(1977—1989)是经历了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崛起的文学,也是处于改革开放中不断变革的文学,期间,中国作家被压抑的创作生命力迅速喷发,使得80年代小说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单一走向了多元。
整个80年代是20世纪末期中国小说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所取得的实绩极为可观的10年。
并且,80年代小说显示出潮流的特征,先后或同时涌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
一、伤痕文学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
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而伤痕文学是文革后清算文革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最直接反映,当时政治上、思想上拨乱反正在文学中的影射。
那一场历经十年的浩劫对灵魂的摧残尤其容易造成惨痛的心灵创伤,但这只有在挣脱了精神枷锁、真正思想解放之后,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伤痕”有多重、多深。
这是伤痕文学喷发的历史根源。
伤痕小说作为1977—1980年间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以四川作家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
小说一经在《人民文学》发表,立即引起轰动。
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
小说揭示了文革悲剧,展示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生活苦难和精神创伤,控诉“四人帮”极左毒害的小说创作潮流。
它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
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
在当时,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伤痕文学代表作,还有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王蒙《最宝贵的》、王亚平《神圣的使命》、陈国凯《我该怎么办?》、孔捷生《在小河那边》、韩少功《月兰》、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和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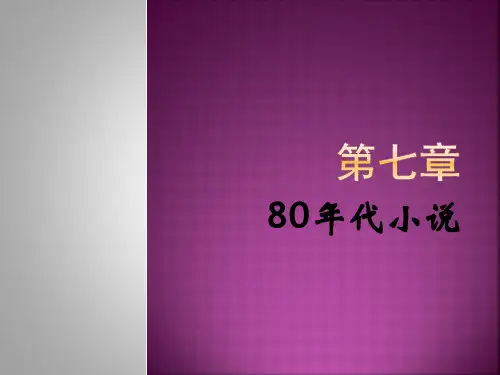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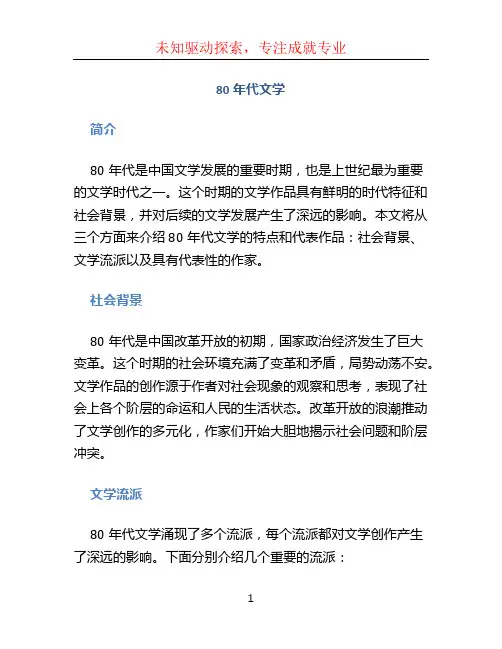
80年代文学简介80年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上世纪最为重要的文学时代之一。
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社会背景,并对后续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介绍80年代文学的特点和代表作品:社会背景、文学流派以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社会背景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家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变革。
这个时期的社会环境充满了变革和矛盾,局势动荡不安。
文学作品的创作源于作者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和思考,表现了社会上各个阶层的命运和人民的生活状态。
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多元化,作家们开始大胆地揭示社会问题和阶层冲突。
文学流派80年代文学涌现了多个流派,每个流派都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面分别介绍几个重要的流派: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是80年代最为重要的流派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
作家们通过描述真实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展现了社会现象和人民的苦难。
代表作品有贾平凹的《废都》、余华的《活着》等。
这些作品真实地描绘了普通人民在变革时期的生活状态,反映了社会的多样性和人民的感受。
乡土文学乡土文学强调对乡土生活深入的观察和真实的刻画。
作家们通过对农民生活、村庄和自然环境的描写,展现了中国乡村的风土人情和农民的命运。
《鹿鼎记》和《红高粱》都是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品。
这个流派的兴起,使得文学创作从城市逐渐拓展到了农村和乡村,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元素和创作手法。
后现代文学80年代还涌现了许多涉及后现代文学的作品,这些作品通常具有对传统叙事的颠覆和对语言的创新。
后现代文学以《茅盾文集》等作品为代表,打破了传统文学的限制和刻板印象,采用了多样化的叙述和非线性的结构。
后现代文学的兴起,将文学作品推向了更为自由和无拘束的境地,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新的篇章。
具有代表性的作家80年代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成为时代的缩影,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下面介绍几位80年代的文学代表作家:贾平凹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80年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中国当代文学简述1980年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这一时期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文学的复兴时期。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改革开放政策下,中国开始经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改革与开放,这也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1980年代初期,一些作家开始以较为自由的文风,创作了一系列的小说与散文,展现了他们对个体自由、社会问题以及人性的深刻思考。
这些作家包括王蒙、路遥、杨绛等,他们的作品中常常涉及到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同时也展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思考。
随着时间的推移,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社会逐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对当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开放与经济的发展,更多的人开始有了时间和机会去阅读、创作与思考。
另一方面,新的文学风格和题材也开始涌现出来。
在1980年代后期,民国时期文人杂志《十月》的恢复创刊引起了当时文坛的巨大反响。
这让许多年轻作家有了一个发表作品的平台,并且借此机会引进了大量的外来文化和文学思潮。
这些新的作家们开始关注现代性、自我认同、性别、城市生活等新的题材和问题,并且运用不同的创作手法和风格,形成了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学流派。
1980年代后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往往被称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作品注重实验性与多样性,通过语言、结构与叙事等方面的突破尝试,以及对现实与历史的重新解读与探索,呈现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总的来说,19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社会变革的巨大影响,还展现了作家对个体自由、人性、社会现实以及传统文化的深刻思考和批判。
同时,这一时期也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的重大转变。
80年代文学总论相对于之前的70年代文学,80年代则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新时期的文学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在反省和躁动中继续着自己的旅程。
当代文学中最重要的时期大概就是80年代了吧,之前的30年现在都不多提了,90年代则有些乏善可陈陷入衰落,80年代大概是目前当代文学界所共同怀念的那个“黄金时代”了。
不过对于大陆当代的通俗小说来说,90年代中后期才是它刚刚开始迈开步伐的时候,由于国内的特殊状况,这一类别在现当代的发展经受了几次中断,每次都要重头开始发展,这或许是其难以继续前行的原因——没有历史包袱并不意味着能够轻装前进,更多时候意味着在创作和阅读上没有足够的资源凭依,意味着更多地被产业制度所控制。
|新时期文学(制度和活动)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将文革之后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这被看做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另一次重大转折。
文革中被毁坏的当代文学体制得到修复和重建,而其第一项工作就是给在文革和十七年文学中遭到批判的作品和作者正名,这杯称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而在文学观上,也提出了“文艺民主”的观点,将口号更改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最高的标准则是四项基本原则。
这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期盼,要求汲取五四时期那种多元共生和精神解放的资源(行吧,反正通俗小说不在“多元共生”的内部),建立一个自由宽容的新时期文学环境。
不过对于文学复兴的想象,一开始就包含了两条道路的分歧,有的人认为转折意味着复归文革之前十七年文学的主流状况,坚持毛所开启的人民(工农兵)文学道路,而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转折意味着复活十七年文学中被压抑的非主流文学,建立和五四时期启蒙文学的关联。
这种内部的分歧造成的则是,50-70年代确立的主流文学已经失去它的绝对地位,一体化的文学格局已经开始解体了。
80年代依然有一些批判运动,但是这些批判活动大多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没有形成十七年那样的规模。
而在80年代,文学奖励制度才开始奖励起来,诞生了一些奖项。
中国八十年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时期,它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高峰之一、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和文化形态的变迁。
在这种背景下,八十年代文学在中国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和思想。
八十年代文学的特点之一是自主性和个体意识的强烈。
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对于自由和个人独立思考的追求成为了当时文学界的主流。
作家们开始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想法,不再受到政治压力的限制。
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更加真实、生动和直观,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变化和人们的内心世界。
八十年代文学还以批判性思维和反思为特点。
在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变革中,人们开始对过去的错误和黑暗进行深度反思,并通过文学作品进行批判和剖析。
这些作品揭示了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以及人类的悲剧和痛苦。
它们关注社会的边缘群体和底层人民的命运,强调人性的复杂和多样性。
八十年代文学还在探索文学形式和艺术手法方面做出了很多新的尝试。
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形式的多样化,为作家们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空间和表达方式。
他们注重形式的独特性和突破性,通过使用多样的语言风格和艺术手法,给读者以不同的艺术享受和审美体验。
在八十年代文学中,有许多重要的作家和作品。
例如,北岛的诗集《蓝色诗选》和余华的小说《活着》都象征着八十年代文学的独特风格和影响力。
北岛的诗歌以简洁、直接的表达方式,深入人心地传达了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和对人性的关怀;余华的小说以其独特的叙述角度和生动的描写,揭示了人在苦难中的尊严和力量。
□第三編1978年—1989年第十章八十年代文學思潮一理论思潮的阵歇性波动80年代的文学思潮大致以1985年为界,前期以高度政治化的“思想解放”为主,后期逐渐走向反文化性的文化热。
(一)“思想解放”与“拨乱反正”1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辨识和争鸣。
1980年“二为方针”(“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明确提出,对新时期文艺复苏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现实主义的争论:围绕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诸方面问题而展开,并通过对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而逐步深入。
(二)80年代前期文学思潮特征1文学取得了和现实生活发展的同步性,文学创作以现实主义为主潮。
2文学领域内,从题材、主旨到手法、方法、风格都开始了全方位的向旧有格局的告别。
3自觉地、大规模地把西方20世纪以来各种现代文学、思潮作为革新文艺的主要参照。
4对文学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是此期规模最大、对文学产生广远影响的、最深刻的文艺思想激荡。
(三)80年代后期文学思潮思潮特征:1着眼于新格局的建立。
文学要求回到自身的呼声日渐普遍和高涨,文学在表现时代时如何进一步展现自己的独特性是作家们普遍关心和思考的问题。
表现在创作与文艺理论观念上。
2文学的本体性备受关注。
“表现生活”已完全代替了“反映生活”,艺术观念发生整体位移,文学创作的“现代性”特征愈加鲜明,文学从观念到创作开始了全方位突破。
影响较大的争鸣:1方法年是指1985年和1986年,又被称为“观念年”。
这两年间,文学批评方法的更新问题成为文学界的热门话题。
从1984年开始,经过1985年一年的发展,流行于当代西方的各种批评方法被大规模介绍进来,同时被批评家迅速运用到对新时期文学乃至过去文学的研究实践中。
有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文化分析等,尤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所谓“三论”的引入和运用最为普遍,代表性论文有林兴宅的《论阿Q的性格系统》、刘再复的《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等。
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第七章八十年代文学概述第一节八十年代的文学环境(一):政治环境——思想上自由解放,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发生变化。
(二):经济环境:市场经济的确立-文学价值的重新确立。
(三):外来影响——西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四):作家因素——作家的构成和创作意识。
1:八十年代作家构成。
(1):复出作家(归来派作家)(2):知青作家(和知青文学区分)。
(3):中年作家。
(4):从性别角度看,可以分出一个特定的群体“女性作家”。
(5):新派作家。
有莫言、刘索拉、徐星、马原、余华、苏童、叶兆言、方方等。
2:八十年代作家意识。
(1):时代、历史的忧患意识。
(2):创新意识(现代意识)第二节80年代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一):八十年代文学意识80年代文学环境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民族民主国家。
这样的文学环境造就了新的文学意识——现代性文学意识,即在现代化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思想意识,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现代性意识很复杂,包括:启蒙意识(五四文学),民族国家意识(左翼、解放区文学),现代主义意识(海派)等。
在中国现代,由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现代意识表现为两种,17年和文革可以看作是民族国家意识的极端发展。
八十年代现代性意识表现在两个方面:1:启蒙意识2:现代意识(二):80年代文学创作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85年为界,之前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存在着相当集中的关注点;之后,文学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1:小说创作,85年之前在创作手法上主要表现为现实主义,主题与文革的历史记忆有关。
先后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
它们有相同的思想基点——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深切思考,前者破,后者立。
以伤痕、反思为发端,引起了作家们在启蒙主义精神指引下,对文革以及文革前的历史作全面反思。
继伤痕、反思文学之后出现的“知青文学”也属于这一类型的创作。
85年之后,小说开始转向自身现代性的实验,先后有寻根文学、现代派实验、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和新历史小说出现。
一过程:80年代前期1976年底“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文学并未在较大的范围里实现从“文革文学”的转变。
写作者的文学观念、取材和艺术方法,仍是“文革文学”的沿袭。
出现对于“文革”模式的明显脱离,是从1979年开始。
因此,不少批评家在谈到“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时,并不以“文革”结束作为界限。
(注:如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指出,他们把“当代文学思潮史”的下限划在1979年,而不是划在“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原因是1979年以前,“文艺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禁锢”;“文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文艺创作有了新的突破”,是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
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成为文艺史上转折的里程碑”。
《中国当代文学思想史》第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当然,在此之前,已有一些作品预示了这种“转变”的发生。
如发表于1977年11月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刘心武)和发表于1978年8月的短篇《伤痕》(卢新华)(注:分别刊载于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和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上海)。
)。
这些艺术上显得粗糙的作品,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特征:对个人的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和作家对于“主体意识”的寻找的自觉。
以1985年前后为界,80年代文学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
80年代前期,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存在着相当集中的关注点。
刚刚过去的“文革”,在当时被广泛看作是“封建专制主义”的“肆虐”。
因此,挣脱“文化专制”的枷锁,更新全民族观念的“文化启蒙”(“新启蒙”),是思想文化的“主潮”。
与此相关,文学是对于“现实主义”的“传统”的呼唤。
在这几年间,文学主题可以说都与“文革”的“历史记忆”有关,是亲历者对“历史灾难”所提供的“证言”,以及对于“历史责任”(“谁之罪”)所作的思考和探究。
在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的潮流;诗歌创作的主要构成,则是“复出诗人”的“归来的歌”,和青年诗人的“朦胧诗”创作;戏剧,特别是话剧也大多是与“文革”有关的“社会问题剧”。
已经在酝酿着艺术观念和方法上的更为深入的变革,但还未成为显在的、受到普遍关注的现象。
从总体而言,这几年文学的取材和主题,是指向社会一政治层面的,也大多具有社会—政治的“干预”性质。
涉及的问题,表达的情绪,与社会各阶层的思考与情绪同步。
文学创作与社会政治、与公众的生活和情感的密切关系,是后来不再重视、并为一些人怀恋的“昔日的光荣”。
由于“文革”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文艺史的“最黑暗的一页”,文艺的“园地”受到严重摧残而“百花凋零”,因此,“新时期文学”被看作是“文学复兴”,“复兴”的提出,又通常与“五四”文学相联系,看成是对“五四”的“复归”。
在80年代初,人们最为向往的,是他们心目中“五四”文学的那种自由的、“多元共生”局面。
但从80年代前期的中心问题看,所要“复活”的,主要是“五四”提倡“科学、民主”的启蒙精神,和以“五四”为旗帜的、在50至70年代被当作“异端”批判的文学思潮。
许多批评家和作家的努力,是继续四五十年代胡风、冯雪峰、秦兆阳(也包括周扬等在60年代)以悲剧结局告终的工作。
一方面,在承认文学的“革命”性质的前提下,推动文学挣脱图解政治概念、复制社会生活表象和僵化艺术模式控制的状况;另一方面,在维护文学作为“艺术”的“特质”,和重视文学社会承担、批判职能,倡导作家的“启蒙”精神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和结合。
对“写真实”和“现实主义”的重申和坚持,公开发表周恩来、陈毅60年代初关于文艺政策“调整”的讲话(注:周恩来《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年3月6日)等。
),为50年代以来受到批判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秦兆阳)等文章的观点辩护,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质疑,都说明了推动“新时期”文学“复兴”的人们,最初继续的是五六十年代“未竟”的工作,接过的是他们的旗帜(注:见《文艺报》1979年3月召开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作家、批评家的发言,《文艺报》1979年第4期《总结经验,把文艺理论批评工作搞上去》。
)。
1979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注:当时文艺界对这篇文章反响热烈,《上海文学》等刊物还组织了有较大规模的讨论。
),对于这一在中国左翼文学界长期流传的“根本性”观念的质疑,也是在左翼文学观的框架内,来反对把文艺变成单纯的政治传声筒,而寻求不离开文艺“特性”的文艺的政治功用:它申明的是左翼文学中受压抑的派别(胡风、冯雪峰、秦兆阳等)的思想路线。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开端所处理的问题,展开的论争,是五六十年代,或更早时间发生于左翼文学的“陈旧”话题,或这些话题的延伸。
这包括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写真实”,“现代派”文学,人性和人道主义等。
在80年代初与文学有关的思想理论问题的论争中,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探讨》(注:刊发于1983年3月16日《人民日报》。
据王元化《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广州《南方周末》1997年12月12日)称,在周扬与王元化、王若水、顾骧一起讨论后,由王元化、王若水、顾骧起草。
王元化主要撰写有关重视认识论问题的部分,王若水撰写有关人道主义部分。
在此之前,王元化已就认识论和知性方法的问题,发表过文章(刊发于1979年上海《学术月刊》和1981年《上海文学》上的《论知性的分析方法》等)。
王若水在这一时期,也撰写了多篇论人道主义的文章。
最著名的是《为人道主义辩护》(上海《文汇报》1983年1月17日)。
周扬的文章由王元化定稿,周扬作最后润色,并由周扬于1983年3月7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演讲。
)是重要的、产生很大争议的文章。
文章试图清算几十年来中国“左”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哲学根源,来推动思想解放的深化。
它的影响与其说是在理论上的,不如说更主要是现实问题的针对性上的。
它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批评了“终极真理”的观点。
提出在认识论上考虑用感性、知性、理性的三范畴,去代替感性和理性的两范畴,以划分知性与理性的区别;认为知性和理性相混淆,以为一旦形成概念,就掌握了本质,是导致简单化、概念化的根源。
文章提出的另一重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文章不同意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
在阐释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它是80年代前期“思想解放运动”思潮中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的“异化”概念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下的解放,而且是从一切异化形式束缚下的解放。
文章引出的最大“麻烦”,是认为不仅是资本主义,而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存在“异化”,包括经济领域的异化,政治领域的异化(权力异化)和思想领域的异化(个人崇拜,或宗教异化)。
这篇文章既得到热烈支持,也很快受到激烈批评(注:在周扬发表讲话后,本来定于3月9日结束的“学术报告会”突然决定延期,并开始对讲话的观点进行批评。
3月16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周扬讲话时,同时刊发会上对这一讲话的批评发言:《黄楠森等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摘要》。
)。
对周扬文章系统的、最具权威性的批评,由胡乔木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注:这是胡乔木1984年1月3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
经修改后刊于《红旗》1984年第2期。
)一文中进行,指出“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带有根本性质错误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牵涉到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的问题。
随后,周扬做了公开的自我批评(注:1983年11月,周扬在对新华社记者谈话中作了自我批评。
在11月中国文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我在今年3月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报告会上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
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参见《文艺报》1983年第12期。
)。
1983年至1984年间开展的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文学问题和现象被作为“精神污染”列举的事项,除了周扬等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观点外,还包括:“把西方‘现代派’作为我国文艺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创作上“热衷于表现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渲染各种悲观、失望孤独、恐惧的阴暗心理”,“把‘表现自我’当成惟一的和最高的目的”等等。
(注:参见1983年第11期《文艺报》社论和12期座谈会报道。
)二过程:80年代后期80年代文学在走过一段路程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80年代的文学主题,作家的基本构成,文学的接受和流通方式等等,在主要的方面仍在延续,但也出现了新的因素。
这种“变化”,可以理解为文学创作和理论的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五六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话题”的范围,创作的风貌脱离了较为单一的模式,艺术方法的探索和革新以更大的步伐推进,而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也变得远为复杂。
在80年代中期或稍后,“文革”后一度享誉的“复出”作家、诗人,有的创作仍获取新的进展,而许多人则已越过自己创作“高峰”。
在面对文学观念、方法变革的巨大压力下,缺乏调整自己步调的潜力,或者显得迟滞,或者新作日见减少。
“朦胧诗”的作者也大多走过他们的鼎盛期,80年代初大量涌现的青年诗人,到80年代中期以后仍保持活跃姿态的,并不是很多。
有的“知青”小说家的创作也出现了停滞状态。
显然,当代作家和作品的“生命力”普遍短暂的问题,在80年代并没有成为历史。
为文学写作所作的准备的不足,和开放之后文学潮流急遽的变化,使作家的更替出现超出一般时期的速度。
当然,各种“类型”作家中,都存在沉稳而坚实者,尤其是被称为“知青作家”中的一部分。
他们和更年轻的作者一起,构成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
80年代中期文学的变化,因1985年这一年发生的许多事件,使这一年份成为一些批评家所认定的文学“转折”的“标志”。
对“文革”和当代历史的书写仍为许多作家所直接或间接关注,但一批与“伤痕”、“反思”小说在思想艺术形态上不同的作品已经出现。
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安忆的《小鲍庄》,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的《爸爸爸》,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均发表于这一年(注:马原等的这些小说,分别刊于1995年的《上海文学》第2期、《上海文学》第1、7期、《现代人》第2期、《人民文学》第3期、《中国作家》第2期、《文学月报》1985年第5期、《中国作家》第2期、《人民文学》第6期、《人民文学》第8期、《西藏文学》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