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英译国内外研究述评
- 格式:pdf
- 大小:253.06 KB
- 文档页数: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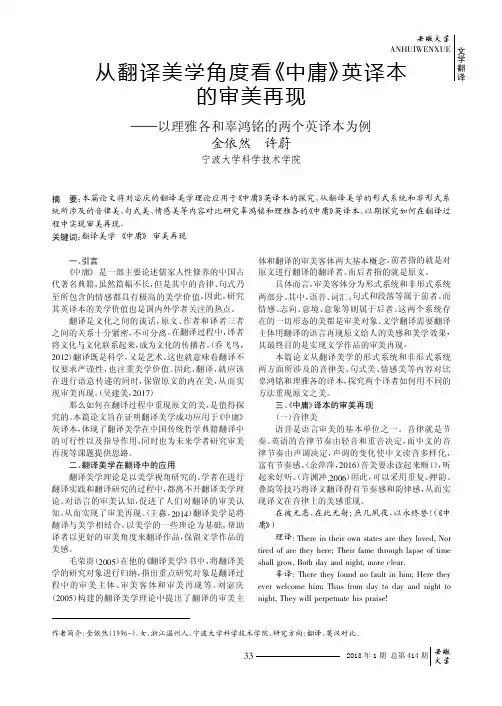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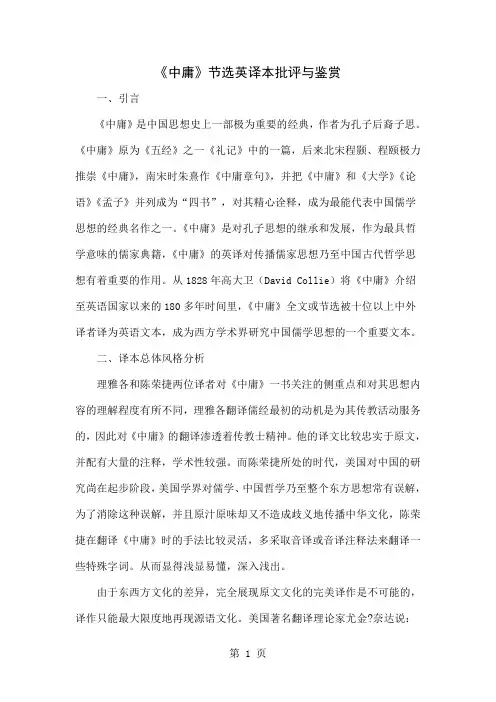
《中庸》节选英译本批评与鉴赏一、引言《中庸》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极为重要的经典,作者为孔子后裔子思。
《中庸》原为《五经》之一《礼记》中的一篇,后来北宋程颢、程颐极力推崇《中庸》,南宋时朱熹作《中庸章句》,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成为“四书”,对其精心诠释,成为最能代表中国儒学思想的经典名作之一。
《中庸》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为最具哲学意味的儒家典籍,《中庸》的英译对传播儒家思想乃至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着重要的作用。
从1828年高大卫(David Collie)将《中庸》介绍至英语国家以来的180多年时间里,《中庸》全文或节选被十位以上中外译者译为英语文本,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文本。
二、译本总体风格分析理雅各和陈荣捷两位译者对《中庸》一书关注的侧重点和对其思想内容的理解程度有所不同,理雅各翻译儒经最初的动机是为其传教活动服务的,因此对《中庸》的翻译渗透着传教士精神。
他的译文比较忠实于原文,并配有大量的注释,学术性较强。
而陈荣捷所处的时代,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美国学界对儒学、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东方思想常有误解,为了消除这种误解,并且原汁原味却又不造成歧义地传播中华文化,陈荣捷在翻译《中庸》时的手法比较灵活,多采取音译或音译注释法来翻译一些特殊字词。
从而显得浅显易懂,深入浅出。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完全展现原文文化的完美译作是不可能的,译作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说:“翻译是在接受语中寻找和源语信息尽可能接近自然的对等话语,首先是意义上的对等,其次才是风格的对等”(Nida,1969)。
因此,本文着重探讨译者对《中庸》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及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译介程度。
三、《中庸》书名的翻译“中庸”一词源自《论语》。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杨伯峻在注《论语》时,释“中”为“折中,无过,也无不及,调和”;释“庸”为“平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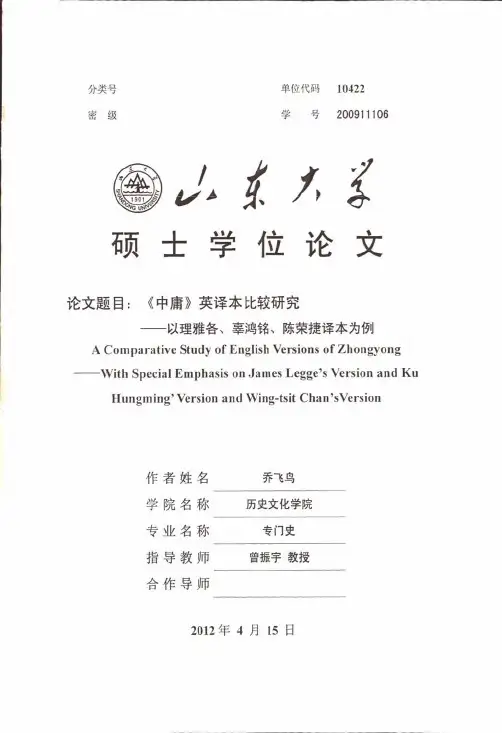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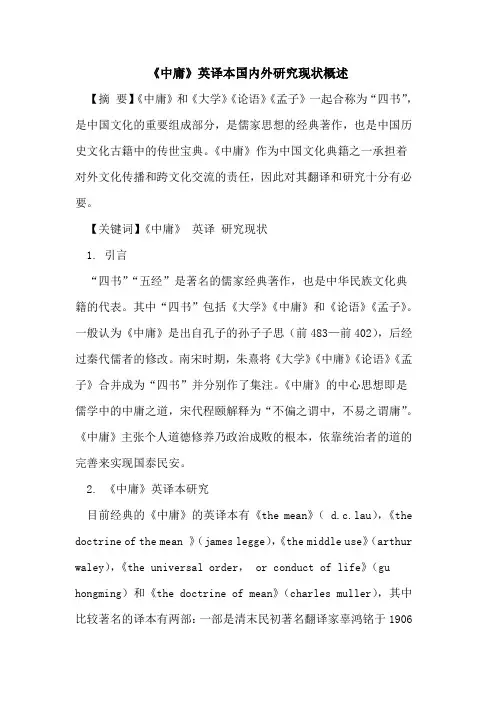
《中庸》英译本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摘要】《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一起合称为“四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传世宝典。
《中庸》作为中国文化典籍之一承担着对外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流的责任,因此对其翻译和研究十分有必要。
【关键词】《中庸》英译研究现状1. 引言“四书”“五经”是著名的儒家经典著作,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典籍的代表。
其中“四书”包括《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
一般认为《中庸》是出自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后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
南宋时期,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并成为“四书”并分别作了集注。
《中庸》的中心思想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宋代程颐解释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庸》主张个人道德修养乃政治成败的根本,依靠统治者的道的完善来实现国泰民安。
2. 《中庸》英译本研究目前经典的《中庸》的英译本有《the mean》( u),《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james legge),《the middle use》(arthur waley),《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gu hongming)和《the doctrine of mean》(charles muller),其中比较著名的译本有两部:一部是清末民初著名翻译家辜鸿铭于1906年推出的译著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另一部是出自于19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英译的五卷本《中国经典》中the doctrine of the mean,这是外国译者《中庸》英译的经典之作。
截至目前,国外关于中国儒家典籍的翻译研究还没有涉及。
而国内关于《中庸》英译的研究始于21世纪,《中庸》的英译研究在近十年来才逐渐受到重视,主要表现在各种研究的期刊和硕博论文的涌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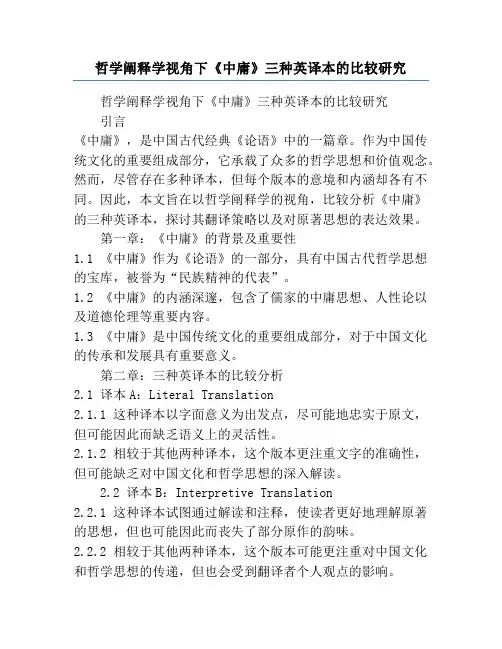
哲学阐释学视角下《中庸》三种英译本的比较研究哲学阐释学视角下《中庸》三种英译本的比较研究引言《中庸》,是中国古代经典《论语》中的一篇章。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了众多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
然而,尽管存在多种译本,但每个版本的意境和内涵却各有不同。
因此,本文旨在以哲学阐释学的视角,比较分析《中庸》的三种英译本,探讨其翻译策略以及对原著思想的表达效果。
第一章:《中庸》的背景及重要性1.1 《中庸》作为《论语》的一部分,具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宝库,被誉为“民族精神的代表”。
1.2 《中庸》的内涵深邃,包含了儒家的中庸思想、人性论以及道德伦理等重要内容。
1.3 《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章:三种英译本的比较分析2.1 译本A:Literal Translation2.1.1 这种译本以字面意义为出发点,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但可能因此而缺乏语义上的灵活性。
2.1.2 相较于其他两种译本,这个版本更注重文字的准确性,但可能缺乏对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深入解读。
2.2 译本B:Interpretive Translation2.2.1 这种译本试图通过解读和注释,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的思想,但也可能因此而丧失了部分原作的韵味。
2.2.2 相较于其他两种译本,这个版本可能更注重对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传递,但也会受到翻译者个人观点的影响。
2.3 译本C:Adaptive Translation2.3.1 这种译本试图在保留原著风貌的同时,与读者产生共鸣,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和表现力。
2.3.2 相较于其他两种译本,这个版本可能更注重文化的适应性,但也可能在忠实于原文方面存在一定的失真。
第三章:比较分析的结果和意义3.1 三种版本都有其各自的优缺点,没有一种版本能完全表达原著的全部含义和内涵。
3.2 三种版本的存在使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中庸》,拓宽了阅读的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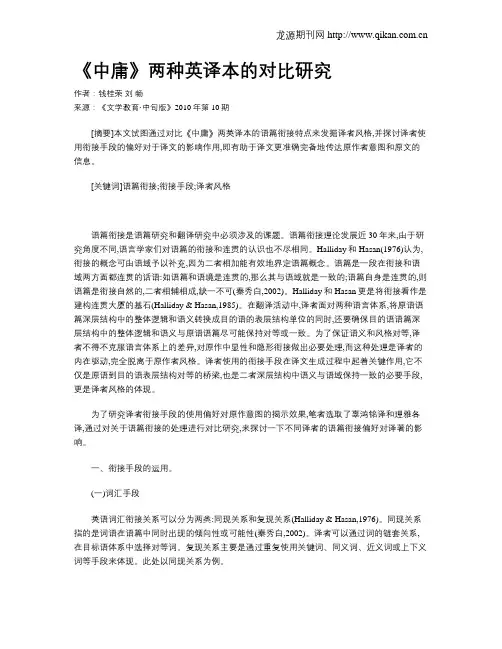
《中庸》两种英译本的对比研究作者:钱桂荣刘畅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0年第10期[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比《中庸》两英译本的语篇衔接特点来发掘译者风格,并探讨译者使用衔接手段的偏好对于译文的影响作用,即有助于译文更准确完备地传达原作者意图和原文的信息。
[关键词]语篇衔接;衔接手段;译者风格语篇衔接是语篇研究和翻译研究中必须涉及的课题。
语篇衔接理论发展近30年来,由于研究角度不同,语言学家们对语篇的衔接和连贯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Halliday和Hasan(1976)认为,衔接的概念可由语域予以补充,因为二者相加能有效地界定语篇概念。
语篇是一段在衔接和语域两方面都连贯的话语:如语篇和语境是连贯的,那么其与语域就是一致的;语篇自身是连贯的,则语篇是衔接自然的,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秦秀白,2002)。
Halliday和Hasan更是将衔接看作是建构连贯大厦的基石(Halliday & Hasan,1985)。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面对两种语言体系,将原语语篇深层结构中的整体逻辑和语义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单位的同时,还要确保目的语语篇深层结构中的整体逻辑和语义与原语语篇尽可能保持对等或一致。
为了保证语义和风格对等,译者不得不克服语言体系上的差异,对原作中显性和隐形衔接做出必要处理,而这种处理是译者的内在驱动,完全脱离于原作者风格。
译者使用的衔接手段在译文生成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它不仅是原语到目的语表层结构对等的桥梁,也是二者深层结构中语义与语域保持一致的必要手段,更是译者风格的体现。
为了研究译者衔接手段的使用偏好对原作意图的揭示效果,笔者选取了辜鸿铭译和理雅各译,通过对关于语篇衔接的处理进行对比研究,来探讨一下不同译者的语篇衔接偏好对译著的影响。
一、衔接手段的运用。
(一)词汇手段英语词汇衔接关系可以分为两类:同现关系和复现关系(Halliday & Hasan,1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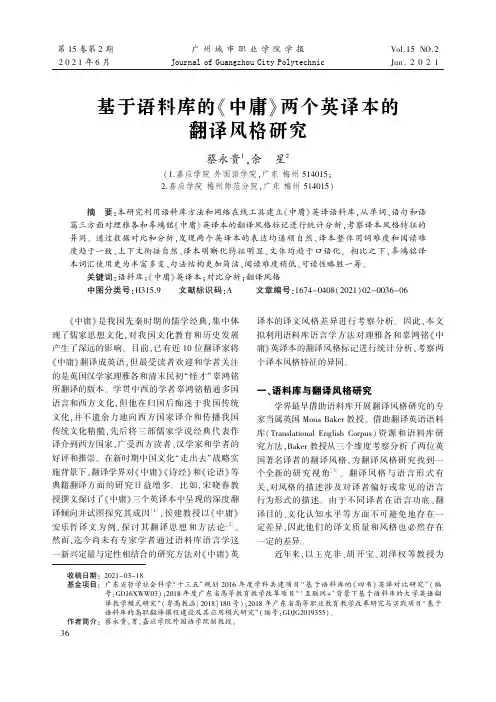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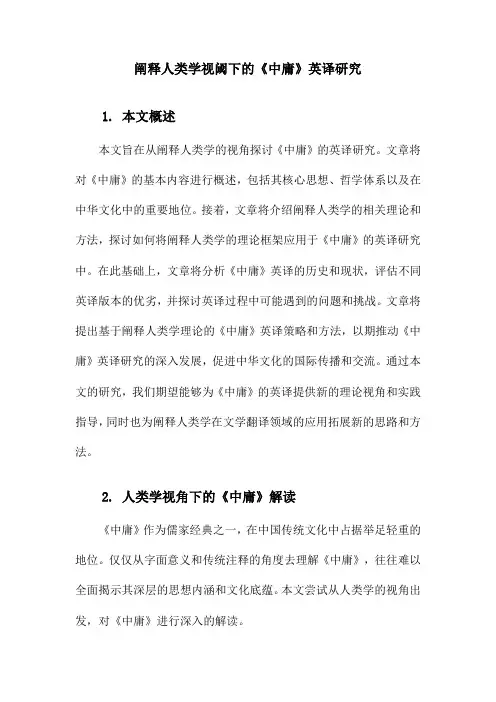
阐释人类学视阈下的《中庸》英译研究1. 本文概述本文旨在从阐释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中庸》的英译研究。
文章将对《中庸》的基本内容进行概述,包括其核心思想、哲学体系以及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接着,文章将介绍阐释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探讨如何将阐释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应用于《中庸》的英译研究中。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分析《中庸》英译的历史和现状,评估不同英译版本的优劣,并探讨英译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文章将提出基于阐释人类学理论的《中庸》英译策略和方法,以期推动《中庸》英译研究的深入发展,促进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和交流。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为《中庸》的英译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指导,同时也为阐释人类学在文学翻译领域的应用拓展新的思路和方法。
2. 人类学视角下的《中庸》解读《中庸》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仅仅从字面意义和传统注释的角度去理解《中庸》,往往难以全面揭示其深层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
本文尝试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对《中庸》进行深入的解读。
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社会、行为和思想的学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传统文献。
在人类学视阈下,《中庸》不再仅仅是一部儒家经典,而是一部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的重要文献。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中庸》所强调的“中庸之道”并非简单的折中或调和,而是一种追求和谐与平衡的生活方式。
这种和谐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更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
这种追求和谐的思想,与古代中国人对宇宙万物的整体观和有机观紧密相连,体现了他们对自然和社会的深刻理解。
《中庸》所倡导的“诚”也是人类学视角下值得关注的概念。
在古代中国社会中,“诚”被视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品质,它要求人们在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基础上,追求内心的真实和纯粹。
这种对“诚”的强调,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真实、真诚和坦诚的价值观的追求,也是他们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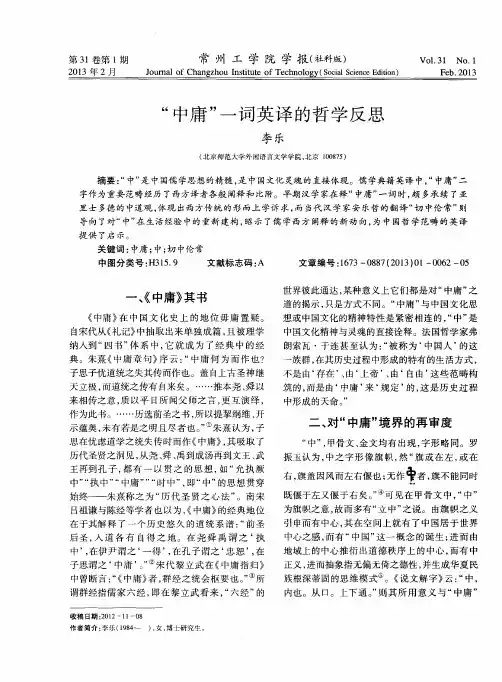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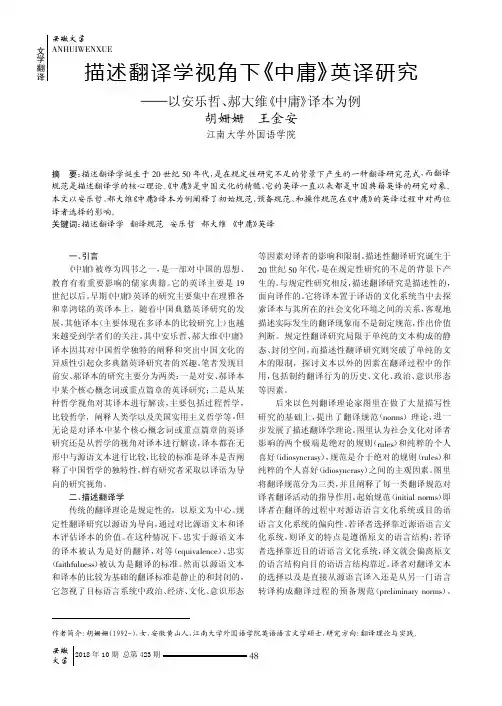
安徽文学ANHUIWENXUE 安徽文学2018年10期总第423期作者简介:胡姗姗(1992-),女,安徽黄山人,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描述翻译学视角下《中庸》英译研究———以安乐哲、郝大维《中庸》译本为例胡姗姗王金安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摘要:描述翻译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是在规定性研究不足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翻译研究范式,而翻译规范是描述翻译学的核心理论。
《中庸》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它的英译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典籍英译的研究对象。
本文以安乐哲、郝大维《中庸》译本为例阐释了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在《中庸》的英译过程中对两位译者选择的影响。
关键词:描述翻译学翻译规范安乐哲郝大维《中庸》英译一、引言《中庸》被尊为四书之一,是一部对中国的思想、教育有着重要影响的儒家典籍。
它的英译主要是19世纪以后。
早期《中庸》英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英译本上,随着中国典籍英译研究的发展,其他译本(主要体现在多译本的比较研究上)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其中安乐哲、郝大维《中庸》译本因其对中国哲学独特的阐释和突出中国文化的异质性引起众多典籍英译研究者的兴趣。
笔者发现目前安、郝译本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对安、郝译本中某个核心概念词或重点篇章的英译研究;二是从某种哲学视角对其译本进行解读,主要包括过程哲学,比较哲学,阐释人类学以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等。
但无论是对译本中某个核心概念词或重点篇章的英译研究还是从哲学的视角对译本进行解读,译本都在无形中与源语文本进行比较,比较的标准是译本是否阐释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鲜有研究者采取以译语为导向的研究视角。
二、描述翻译学传统的翻译理论是规定性的,以原文为中心。
规定性翻译研究以源语为导向,通过对比源语文本和译本评估译本的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忠实于源语文本的译本被认为是好的翻译,对等(equivalence )、忠实(faithfulness )被认为是翻译的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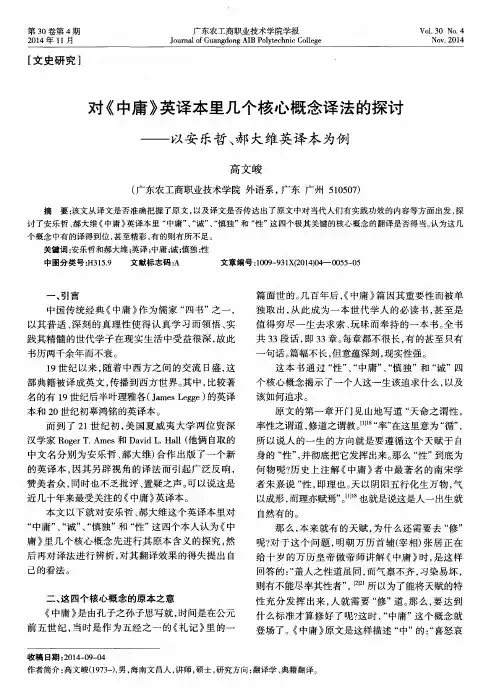
试析理雅各英译《中庸》中的误译与文化误读张昆(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合肥230009)摘要:理雅各英译《中庸》有功于汉学西传甚巨,中西学者皆赞其译文“典雅”“严谨”。
但中国语言文化博大精深,理氏英译中曲解误译亦所在多有。
指纠其曲解误译,对于准确传达《中庸》真意,向世界还原真实的中国儒学典籍,有实际意义。
关键词:理雅各《中庸》英译误译文化误读《中庸》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极为重要的经典%《中庸》原为《礼记》中一篇,后被儒学大师朱熹摘出,与《论语》《孟子》《大学》并为四书,并对其精心诠释,成为最能代表中国儒家思想的经典名作之一%王国维谓“此书为诸儒哲学之根柢”“古今儒家哲学之渊源也”“译此书,可谓知务者矣”。
(王国维,2011:95)理雅各(James Legge)在助手王韬的协助下英译的《四书》《五经》(英文名为The Chinese Classics,《中国经典》)是19世纪欧学的之作,向来被视为儒家经典的译,%英国学家约瑟(John Edkins)就认为理氏译文几乎懈可,:“论家想要理雅各的,就中国一家的,为的《中国经典》是中国经书的%”(Legge, 2000-20)可认,理氏译对中国儒学在之作用%,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译者对原语语的理对作文哲学思想的理,译对原的译。
匸,中国学者,但迄今并的,对理氏《中庸》英译的今重国理论学的译译的%夫误之,后世之传其谬而莫能名者,可胜道也哉%口此承讹袭误,显然影响世界人民对中国道德文化和哲学精神的正确理文化认同%所以,对理氏译中的译文化失真,必要全梳理和专门指纠%为此,笔者认真理雅各的《中庸》译,训诂学对其中明显!进行剖析,旨在抛砖引玉,以待者,使中国文经典的译更接近义,发扬中国哲学之真思想、真精神%以下分别举证%1.语言理解不足造成的误读中庸所语言是中国古语,字少义,词义的样与模糊,语法的复杂……都要求译者熟精思,潜心涵泳,切己省察,才可明达文义,得其立言之旨%叶嘉莹、周汝昌之师,北大文坛大师顾随先生所言:“读经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固书皆当此,其经%,不认识,用心稍微不到,小有轻重,便不是%”(顾随,2013:5)理氏既未能深考,而贪多务博,译本之病,首源于此,兹列举下:例1<3子之中庸也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理雅各翻译:The superior man's embodying the course of the Mean is because he is a superior man,and so always maintains the Mean.The mean man's acting contrary to the course of the Mean is because he is a mean man,and has no caution.”: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又能随时以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之心,又所忌惮也%(朱熹,1983:19)%此朱熹在《朱子语录》中解释明了:“君子,只是个。
第21卷第6期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21No.62020年11月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Nov.2020澳大利亚首例‘中庸“英译本考略宋晓春(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82)㊀[收稿日期]㊀2020-07-01㊀[基金项目]㊀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中庸“英译与中庸翻译思想研究 (13CYY013)㊀[作者简介]㊀宋晓春(1976 ),女,湖南花垣人,博士,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学研究㊁典籍翻译㊂[摘㊀要]㊀以乔斯顿和王平合作翻译的首例澳大利亚‘中庸“英译本为研究对象,研究其中 疏典并译 的典籍翻译新体例,并从译本所依据的中国经典注疏出发,考评译著中所包含的两种译本对译者重译初衷的彰显㊂研究发现:整体来说,译者在译文中传递了三种经典注疏的不同,尤其体现在诸如 中庸 慎独 赞天地之化育 等翻译方面,但在对 诚 不显惟德 等译名的处理上尚有欠缺㊂[关键词]㊀‘中庸“;英译; 疏典并译 ;翻译体例;典籍翻译[中图分类号]H315.9㊀[文献标识码]A㊀[文章DOI]10.15883/j.13-1277/c.202006001407㊀㊀‘中庸“已有20余种全译本,均出自于英美和中国本土学者,除此之外,其它英语国家似乎关注较少㊂2012年澳洲学者乔斯顿(Ian Johns-ton)和王平(Wang Ping)合作出版的‘大学㊃中庸“(Daxue &Zhongyong )最新译本(以下简称为乔&王译本),打破了这一格局,这是迄今为止英美之外的英语国家学者出版的首部‘大学㊃中庸“英译本,该译本在译本体例㊁译名选择㊁翻译阐释取向等诸多方面均极具特色,对该译本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海外学界对中国经典研究㊁翻译和接受的最新动态㊂同时,在 中国文化走出去 文化战略背景下,在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兴盛 和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国家文化发展理念的引领下,研究该译本中所折射出的中学西传历史㊁发展和影响等,就显得十分切合时代主旋律,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深远的社会现实意义㊂[1]48因此,本文以该译本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其译本中的 疏典并译 翻译体例以及该体例下的翻译阐释特征,以期对中国经典外译究竟该选择什么形式这一焦点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实证参考㊂一㊁ 疏典并译 的体例考察在对 疏典并译 体例考察之前,首先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译者的情况,2012年出版的‘中庸“新译本的译者乔斯顿其实是澳大利亚的一名外科医生,因对医学做出了杰出贡献曾被授予 澳大利亚勋章 (The Order of Australia)㊂但医学并不是其唯一醉心的事业,在其整个从医生涯中,他一直坚持不懈地追求他的另一个终身兴趣,即对古典语言和文学的兴趣,并获得了中文博士学位和古希腊研究的博士学位㊂乔斯顿出版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和诗歌翻译的译著,其中中国诗译集两部:Singing of Scented Grass (2003)(‘香草吟“)和Waiting for the Owl :Poems and Songs from AncientChina (‘等待猫头鹰:中国古诗词选译“),古代中国哲学著作的翻译有The Mozi :A Complete Transla-tion ‘ 墨子⓪全译“(2010)㊁Daxue and Zhongyong(‘大学㊃中庸“)(2012)㊁The Book of Master Mo(‘墨子“)(2014)㊁Record of Daily Knowledge andCollected Poems and Essays :Selections (‘顾炎武 日知录⓪及其诗文选译“)(2016)等㊂因其在翻译方面的特殊贡献,2011年被授予新南威尔士总理翻第6期宋晓春㊀澳大利亚首例‘中庸“英译本考略15㊀译奖(NSW Premiers translation prize)㊂乔斯顿和王平合译的‘大学㊃中庸“译本给人最初和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译本的厚度㊂‘大学㊃中庸“原文一起不过五千余字,但乔&王译本却有566页㊂其译本如此之厚有三方面原因:(1)译本中列出了原典的原文和原典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三种重要注疏的原文和翻译;(2)根据疏解不同形成了两种译本;(3)译本中译者以双行小注的形式加入了自己评论㊂因为这一译本将原典和疏解并置译出,本文姑且将这种最新的翻译体例称之为 疏典并译 翻译体例,该体例由总引㊁专引㊁两种英译本和三个附录构成㊂1.总引总引全面描述了翻译对象㊁选择缘由㊁预设读者和翻译准则㊂关于选择‘大学㊃中庸“来翻译的缘由主要还是源于译者对中国古代经典哲学的喜好,将经典注疏与原典并置译出是出于对西方读者的考虑,是为了帮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原典,一方面了解‘大学㊃中庸“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阐释也随之变化的全貌;另一方面了解朱熹的哲学观,了解朱熹是如何将‘大学㊃中庸“重组,并将之推入到新儒哲学的中心㊂翻译所遵循的标准是准确㊁直接的翻译,尽量保留原文的简洁性,尽可能基于注疏来翻译㊂2.专引除了总引之外,‘大学“‘中庸“译本开始之前亦有各自单独的引言,关于‘中庸“的引言介绍了‘中庸“书名的含义㊁ 中 与 庸 二字的关系㊁前人对 中庸 的英译名㊁‘中庸“作者及成书时间的考证㊁‘中庸“文本的组成㊁‘礼记“版‘中庸“和朱熹版‘中庸“在结构安排方面的区别,以及郑玄注㊁孔颖达疏和朱熹注的具体差异㊂3.两种英译本在‘中庸“专引之后,就是两种‘中庸“的英译本,首先是依据郑玄注㊁孔颖达疏而译出的英译本(以下简称为译本一或T1),然后是依据朱熹注而译出的英译本(以下简称为译本二或T2),两种译本都采纳了中国传统的 双行小注 体(interlinear commentary)而分段进行翻译,并在中间插入所依据的注疏,以及译者本人的评论㊂具体来说,第一种译本的翻译体例为 原文(选用‘礼记“中的版本)+译者按语+郑玄注+原文的英译+郑玄注的英译+孔颖达疏+孔颖达疏的英译 ,第二种译本的体例 中庸章句序+中庸章句序的英译+子程子曰+子程子曰的英译+原文(‘中庸集注“中的版本)+译者按语+原文的英译+朱熹注+朱熹注的英译 ㊂4.三个附录译本正文之后为三个附录,附录1为 ‘礼记“溯源 ,附录2 ‘中庸“注疏史概略㊁历代译者和译本 ,附录3 术语 ㊂其中‘中庸“注疏史概略㊁历代译者和译本的附录列出了从郑玄开始到清末年间最为重要的注疏者,包括马融㊁郑玄㊁戴颙㊁陆德明㊁李光地等㊂从以上对乔&王译本体例的介绍,可以看出典籍翻译中 疏典并译 体例的显著优势,读者可以根据译本中的译文,以及注疏英译文,辅以译者的评论,了解到中国自汉代至宋朝年间,中国学界对‘中庸“的理解全貌㊂二㊁译本考评:两种诠释传统与两种翻译进路㊀㊀从上述体例的介绍可知乔&王译本实际上包含了两种英译本,是将同一原典在同一个译著中根据其依据的注疏的不同翻译为两种版本㊂第一种译本主要依据郑玄注和孔颖达疏(以下简称T1),将这两种疏解并置的原因主要是遵循中国经学将汉代经学和唐代经学合并为汉唐经学这一传统,另外也是基于孔颖达疏中所代表的隋唐经学中所提倡的注不驳经,疏不破注的特点,孔颖达的‘礼记正义“是在郑玄注‘礼记“的基础上,以宗郑为主而成的㊂乔&王译本中的第二种翻译是以代表我国经学诠释史上另一大诠释进路的朱熹注为依据(以下简称T2),这一翻译安排可以看出译者熟谙我国经学史㊂基于乔&王译本中显著区别于前人的 疏典并译 的翻译特点,译文读者是否会因此有所期待?期待通过阅读两种不同的译本,可以体味到中国经学诠释的不同路径和翻译风格㊂比如依据郑玄注㊁孔颖达疏的译本是否会更倾向于直译,而依据朱熹注的译本是否会更注重于传输其中的哲学思想,也就是说在译法的选择上更加灵活,更倾向于意译,或者是创造性的翻译?带着这样的期待与疑问,通过细致比读原典㊁注疏和译文,遴选出一些典型译例,按照是否体现出所依据注疏的思想,分为两大类:(1)体现了郑玄㊁孔颖达和朱熹三种注疏之间区别的例证;(2)没有体现这三种注疏之间区别的例证,然后对其16㊀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分别加以考辨㊂(一)郑玄注㊁孔颖达疏和朱熹注区别的彰显1. 中庸 译名的翻译乔&王译本中‘中庸“书名分别为 Zhongyong中庸:Using the Centre [2]211和 Zhongyong中庸:Central and Constant ㊂[2]399该译名的差别体现了注疏的差异,‘礼记㊃中庸“郑玄释为: 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为用也㊂庸,用也㊂ ‘礼记㊃中庸“孔颖达‘疏“云: 案郑‘目录“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㊂庸,用也㊂ [3]1625因而乔&王译本取其共通之处,即 用 ,而译为 Using the Centre ㊂朱熹沿用了程颐释 中庸 说: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㊂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的观点,将 中庸 解为: 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㊂庸,平常也㊂ 因而在译本二,遵朱熹的注解而英译为 Central and Constant ㊂当然,用 Using the Centre 来翻译 中庸 似乎有过于生硬㊁让人不解之嫌,但从这两个不同的译名,以及对其来源的分析,足以见典籍翻译中注疏对译者的影响之大!2. 慎独 的翻译慎独 出现在‘中庸“开篇第一章,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㊂莫见乎隐,莫显乎微㊂故君子慎其独也㊂ 乔&王译本翻译如下:T1:This is why the noble man is on guard and cautious where he is not seen;this is why he is fearful and apprehensive where he is not heard. Therefore, the noble man is cautious when he is alone.[2]215 T2:This is why the noble man is on guard and cautious about what he does not see;it is why he is fearful and apprehensive about what he does not hear. Therefore,the noble man is careful about his inner self.[2]407两种译文在句式上完全相同,但在用词上有所区别,如译文一用 where 作从句的先行词, 独 译为 alone ,而译文二用 what 作从句的先行词, 独 译为 inner self ,产生这样差别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其倚仗注疏之间的差异㊂首先考察‘礼记㊃中庸“篇郑玄注曰: 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㊂ [3]206,397孔颖达坚持 疏不破注 的原则释为: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 者, 故君子慎其独也 者,以其隐微之处,恐其罪恶彰显,故君子之人恒慎其独居㊂言虽曰独居,能谨慎守道也㊂ [3]1625两人均以 闲居 独居 来解 慎其独 中 独 ,说的是君子在 不见睹,不见闻 , 幽隐之处,谓人不见之地 要谨慎守道,主要侧重指的是一种空间上的 独 ㊂朱熹部分延续了郑玄和孔颖达的阐说,也曾用 独处 来解 君子慎其独之 独 ㊂据‘朱子语类“载, 戒慎恐惧乎其所不睹不闻,是从见闻处戒慎恐惧到那不睹不闻之处㊂这不睹不闻是功夫尽头㊂所以慎独,则是专指独处而言㊂ [4]1501此处的独处 与郑玄㊁孔颖达的 闲居 独居 独处 和 隐居 含义相同㊂但朱熹对 慎独 的解释也不囿于郑玄㊁孔颖达等前人的解说,在‘中庸章句“中他进一步发展了郑玄㊁孔颖达的 慎独 说㊂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㊂故君子慎其独也㊂ 朱熹在‘中庸章句“中注为: 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㊂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己动,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着见明显而过于此者㊂ [5]17-18明确地将 慎独 的 独 阐释为 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 ㊂‘朱子语类“卷六十二有这样的解释, 问 慎独 ,莫只是 十目所视,十手所指 处,也与那暗室不欺时一般否? 先生是之㊂又云: 这独也又不是恁地独时,如与众人对坐,自心中发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独处㊂ 即 慎独 之 独 不仅可指身所独居,也可指虽与众人一处,但内心之中的 己所独知 ㊂由此可见,朱熹从外在空间以及内在心里上对 慎独 之 独 的阐释,其内涵远厚于郑玄与孔颖达的阐释㊂也就是说郑玄与孔颖达阐释的 独 强调外在空间无人独处之 独 ,强调君子要慎于外在之言行,而朱熹之 慎独 则是不仅指外在的,而且更强调 耳目见闻之所不及而心独知之之地耳 以及 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 之内心的慎㊂阐明了郑玄㊁孔颖达和朱熹对 慎独 之 独 的阐释差异,再回到乔&王译本中的两种译文,我们就会明白前述的选词差别所产生的缘由,即译本一选用先行词 where 和 alone 来凸显郑玄㊁孔颖达对 独 在空间上的不为人所见㊁所闻之 独处 的诠释㊂而在译本二中,根据朱熹在‘中庸章句“中的理解,将前一种译本中的 where 替代为 what , alone 用 inner self 代之,来区分对 慎独 的两种不同侧重点的阐释, where 强调空间第6期宋晓春㊀澳大利亚首例‘中庸“英译本考略17㊀上的 独处 ,而 what 就模糊了这一层含义;用 alone 而没有用 lonely ,一般认为前者侧重于空间上的独处,而后者则侧重于心理上的孤独,第二种译本用了 inner self ,强调内在的㊁内心的自我,显著地体现了朱熹注与郑玄注㊁孔颖达疏之间的差异㊂3. 赞天地之化育 之翻译赞天地之化育 出现在‘中庸“第22章, 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㊂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㊂ 这一部分讲至诚之人能尽人之性㊁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从而与天地参㊂乔&王分别译为 Someone who is able to com-plete the natures of things can then assist Heaven and Earth in their transforming and creating. 和 Some-one who is able to complete the natures of things can then assist the transforming and nourishing[functions] of Heaven and Earth.这两种译文中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对 赞 和 育 的翻译㊂ 赞 在两种译本中被统一译为 as-sist , 育 则分别译为 creating 和 nourishing ㊂要评价 赞 译为 assist 是否恰当,就要回到译本所依据的疏解㊂译本一所依据的郑玄注: 赞,助也㊂育,生也㊂助天地之化生㊂ 孔颖达疏曰: 既能尽人性,则能尽万物之性,故能赞助天地之化育㊂ [3]1632两人均将 赞 注疏为 赞助 ㊂朱熹继承了郑孔的解释,注 赞 为 犹助也㊂ [5]33显然三者对 赞 的诠释一致,均为 赞助或助 之意,因而统一译为 assist 也是恰当的㊂但是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还有进一步的解释, 赞天地之化育 ,人在天地中间,虽只是一理,然天人所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不得底㊂如天能生物,而耕种必用人;水能润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薪?必用人㊂裁成辅相,须是人做,非赞助而何? 虽然继续将 赞 解释为 赞助 ,但与之不同的是,朱熹还进一步诠释 赞天地之化育 为 裁成辅相 ㊂所谓 裁成辅相 ,源自‘周易㊃泰“所引‘象“曰: 天地交,泰,后以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㊂ [6]1987关于 裁成辅相 ,二程也做过解释说: 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须圣人裁成辅相之㊂如岁有四时,圣人春则教民播种,秋则教民收获,是裁成也;教民锄耘浇灌,是辅相也㊂ [7]除了此处用了 裁成辅相 ,朱熹还在‘周易本义“中讲述相关内容时也用了该词,他说: 天生得许多人物,与你许多道理㊂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生得圣人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 是也㊂盖天做不得底,却须圣人为他做也㊂[4]259又曰: 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圣人便为制下许多礼数伦序,只此便是裁成处㊂至大至小之事皆是㊂固是万物本自有此理,若非圣人裁成,亦不能如此齐整,所谓 赞天地化育而与之参 也㊂ [4]1759足见天地之间有 天地之所不能为,做不得底,而圣人能之 之事,需要圣人的 裁成辅相 ,这就是朱熹对 赞天地之化育 的看法㊂这样的诠释是以一种强调人与天地相互补充㊁相互协调,自然和谐的诠释㊂因而两种译文都选用 assist 来翻译 赞 是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倚仗郑孔疏解中 育 为 生 的解释选用 creating 来翻译,倚仗朱熹注的译文则另外选用了 nourishing 一词, nourishing 有 滋养㊁养育㊁给予很多关注 等义,淡化了 creating 一词中所体现出的显著主体性, creating 一词虽有助天地化育之意,但同时也可能有主导㊁改造甚至恣意破坏自然之意,而 nourishing 一词用在 赞天地之化育 之翻译中,避免了 creating 一词所可能产生的隐含之意,突显了上述朱熹注中对人与天地自然一体的和谐境界的强调,亦体现了其与郑孔注的差异㊂(二)未尽译者之初衷的翻译1. 诚 的翻译诚 为中国文化关键词㊂中国文化关键词承载着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中国人在意义世界的存在方式㊂[8]49 诚 是‘中庸“的核心义理,朱熹在‘中庸章句“中更是明确提出 诚 为‘中庸“之枢纽,以 诚 贯通‘中庸“全篇,因此考察‘中庸“的译本是避不开对 诚 翻译的讨论㊂乔&王译本对 夫微之显㊂诚之不可揜如此夫㊂ (16章),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㊂ 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㊂ (17章) 诚者,天之道也㊂诚之者,人之道也㊂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㊂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㊂ (18章)等章节的译文中虽然两种译本倚仗的注疏不同,但译名却完全相同, 诚 均采用音译+汉字的方式译为 cheng诚 ㊂阅读这样版本的译文给人一种印象,即认为郑玄㊁孔颖达和朱熹对 诚 的阐释是一致的㊂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可以回到三者的注疏原典,比读一下三位注18㊀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疏者对以上部分的阐释㊂首先看第一例,按照朱熹对‘中庸“的章节划分, 夫微之显㊂诚之不可揜如此夫㊂ 是 诚 一词最早出现的章节,即第16章,该章引孔子语 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㊂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㊂ 夫微之显㊂诚之不可揜如此夫㊂ 对于该部分,‘礼记正义㊃中庸“郑玄注曰: 言神无形而著,不言而诚㊂ 孔颖达疏曰: 夫微之显 者,眼鬼神之状,微昧不见,而精灵与人为吉凶,是从 微之显 也㊂ 诚之不可揜 者,言鬼神诚信,不可揜蔽㊂善者,必降之以福;恶者,必降之以祸㊂ [3]1628孔颖达把鬼神之无形与人之吉凶相联系,以说明鬼神之 诚 ,以 诚信 解诚㊂与郑玄㊁孔颖达不同,朱熹‘中庸章句“以阴阳二气言鬼神,指出: 以二气言,则鬼者阴之灵也,神者阳之灵也㊂以一气言,则至而伸者为神,反而归者为鬼,其实一物而已㊂ 对于所谓 夫微之显㊂诚之不可揜如此夫 ,朱熹注曰: 诚者,真实无妄之谓㊂阴阳合散,无非实者㊂故其发见之不可揜如此㊂ 朱熹在‘中庸或问“还说: 曰 诚之不可揜如此夫 ,则是以为鬼神之德所以盛者,盖以其诚耳㊂[9]上述引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郑孔注中诚 被阐释为 诚信 ,而朱熹注中 诚 则被释为 真实无妄 ,其中的差异非常明显,且朱熹还对 诚 与 信 的关系做过阐述: 问诚㊁信之别㊂曰: 诚是自然底实,信是人做底实 ㊂故曰: 诚者,天之道㊂ 这是圣人之信㊂若众人之信,只可唤作信,未可唤作诚㊂诚实自然无妄之谓㊂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彻底是仁,义彻底是义㊂叔器问: 诚与信如何分? 曰: 诚是个自然之实,信是个人所为之实 ㊂‘中庸“说 诚者,天之道也 ,便是诚㊂若 诚之者,人之道也 便是信㊂信不足以尽诚,犹爱不足以尽仁㊂ [4]103显然,在朱熹看来, 诚 和 信 是不能等同的㊂再继续比读 诚者,天之道也㊂诚之者,人之道也 的两种诠释㊂朱熹‘中庸章句“中 诚 是天所固有的理之本然,理即为天所固有,同时也是人的先天本性㊂以这一说法为前提,‘中庸章句“注为 诚者,真实无妄之谓㊂天理之本然也㊂此处,朱熹亦是把 诚 解说为 真实无妄 ,但从天道与人道统一的层面对 诚 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诚 是 天理之本然 ,即为天所固有,也为人性所固有,是天道和人道的合一,是人的先天本性㊂‘礼记正义㊃中庸“篇中郑玄注曰: 诚者 ,天性也, 诚之者 ,学而诚之者也㊂ 孔颖达疏曰: 此经明至诚之道,天之性也,则人当学其至诚之性,是上天之道不为而诚,不思而得㊂若天之性有杀,信著四时,是天之道㊂ 诚之者,人之道也 者,言人能勉力学此至诚,是人之道也㊂不学则不得,故云人之道㊂ 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者,此覆说上文 诚者,天之道也 ,唯圣人能然,谓不勉励而自中当于善,不思虑而自得于善,从容间暇而自中乎道,以圣人性合于天道自然,故云 圣人也 ㊂ [3]1632显然在郑玄㊁孔颖达那里, 诚 是天之性,只有圣人能够具备 诚 的天性,能够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 ,而与天之性相符合;常人则需要通过努力学习,才能达到 诚 ,所以‘礼记正义㊃中庸“中郑玄㊁孔颖达认为 诚 为圣人所固有,不为常人所固有,但并不认为 诚 为天所固有,或者用朱熹所言曰 天理之本然 ,而是天所赋予人的先天本性,是天地之间的木㊁金㊁水㊁火㊁土转化而成的,但并不意味着天也有 诚 ,或者说并不意味着 诚 是天地之道㊂综上论述,无论从字词训诂层面,抑或是哲学内涵诠释层面,郑玄注㊁孔颖达疏和朱熹注的差异都是非常显著的㊂虽然乔&王在两种译本中译出了相应的疏解,但译本正文中却没有进行区别性的翻译,而是采用了完全相同的译法㊂在‘中庸“译本引言中关于 诚 ,尤其是 诚者 和 诚之者 部分,乔&王认为虽然朱熹 诚者 和 诚之者 的区别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解释,但与其他注疏者相比,朱熹的诠释无本质性的区别㊂显然从他的这一论述和译本正文中的处理,译者没有把握朱熹通过诠释 诚者,天之道也 所要传递的天道观,因而译名的选择也差强人意㊂2. 不显惟德 的翻译不显 在‘中庸“中出现了两次,首次出现是在第26章, 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㊂ 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㊂纯亦不已㊂ 乔&王的两种译本都用了 How brilliant it was 来翻译 于乎不显 的显 ㊂孔颖达此处的疏解为: 纯,谓不已㊂显,谓光明㊂诗人叹之云,于乎!不光明乎,言光明矣㊂[3]1633其中 于乎!不光明乎,言光明矣 将不显释为显, 不 字在此处的功用意在强调,朱熹注 于乎不显 为 不显,尤言 岂不显 也 ,与孔颖达疏一致,因而乔&王译本中用了感叹句 How brilliant it第6期宋晓春㊀澳大利亚首例‘中庸“英译本考略19㊀was 来翻译 不显 ,完全准确地传递了郑孔注疏和朱熹注的诠释㊂不显 第二次出现在‘中庸“第33章 诗曰, 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 ㊂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㊂两种译本中的译文均是 He makes no dis-play of his virtue,yet the hundred princes take him as an exemplar.对于第三十三章出现的 不显 ,朱熹注和郑玄注以及孔颖达疏的差异却是非常明显的㊂朱熹在该章的注曰: 不显 ,说见二十六章,此借引以为幽深玄远之意㊂承上文言天子有不显之德,而诸侯法之,则其德愈深而效愈远矣㊂笃,厚也㊂ 笃恭 ,言不显其敬也㊂ 笃恭而天下平 ,乃圣人至德渊微,自然之应,中庸之极功也㊂ [5]40可见,对这一章出现的 不显 ,朱熹认为是指文王之德之 幽深玄远 而作 不显之显 来解释,因而倚仗朱熹注所产生的译文 He makes no display of his virtue 是准确地表达了朱熹对该诗文的诠释㊂但对三十三章所引‘诗“曰 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 ,郑玄注为: 不显,言显也㊂ 孔颖达疏曰: 不显乎?文王之德,言其显矣㊂以道德显著,故天下百辟诸侯皆刑法之㊂ [3]1635-1636郑玄㊁孔颖达均将 不显 言为 显 ,此处倚仗郑玄㊁孔颖达之疏解的译文 He makes no display of his virtue 的翻译没有准确地表达 不显,言显也 之意,两种完全相同的翻译也不符合所倚仗注疏不同而译文也应相应不同的读者期待㊂简而言之,关于第三十三章的 不显 ,乔&王译本的不足在于,还是延续了第二十六章中 不显 之意,没有注意到郑玄㊁孔颖达和朱熹在第三十三章对 不显 诠释的差异,其实译者在翻译三种注的时候应该对此差异已然了解,但在译本正文中却没有显示出这些差异,着实令人遗憾㊂三㊁余论以上虽然列出了一些乔&王译本中没有体现出所倚仗注疏差别的译例,而且细心的读者倘若细细比读,仍然可以找出诸多其它例证㊂但整体而言,与其详实的引言㊁严谨的考证㊁细致的术语解说,还有对历代英译本的梳理相比较,这些不足并不能撼动其 疏典并译 体例的开创之功,也不能掩盖译本中诸多佳译妙词㊂韦拉格[10]在‘道“(DAO)杂志上对乔&王译本进行了述评,认为 乔&王译本没有体现出经典不同时期注疏之流变的本质,而是仅仅列出各注疏的原文和译文,没有阐释出其中的道德或历史的深刻内涵,没有将不同的疏解放在不断进化演变的学术史中去研究和翻译㊂而是泛泛地㊁流于俗套地将郑玄之注归为语文学类的注释,孔颖达之疏归为蕴含了一些哲学思考的文学 历史的注疏,朱熹注则主要为哲学阐释 ㊂对于韦拉格的批判,我们认为首先乔&王将郑玄注㊁孔颖达疏与朱熹注之间的差异整体性地概括为语文学和哲学阐释的差异,并非留于俗套,而是抓住了汉唐和宋代两大经学学派的诠释差异的核心,即汉学重训诂,而宋学重义理,也是遵循了学界对经学在演变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派别之两派说,即把经学分为汉学和宋学两派,此说由清四库馆臣提出, 自汉宋以后,垂耳千年, 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㊁宋学两家㊂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经部总叙“),此外,‘四库全书总目 四书章句集注⓪提要“亦称: 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㊂ 以偏重于考证,或是偏重于义理,来区分汉学与宋学㊂其后,江藩在其‘国朝韩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中,亦将经学分为汉学和宋学两大派㊂虽然对汉学和宋学的细节没有细加区分,如汉学中存在着西汉今文经学和东汉古文经学,而宋学中也有讲义理而不及训诂和讲义理亦重视训诂辨伪两种倾向之别[11],但是两派说还是确立的,因此,乔&王从这两大派别中分别选取最具有代表性人物的注疏作为其翻译的依据,也是成立的㊂当然,正如上文中所指出的,译本中的确存在疏漏和不足,对于这些不足,译者也尝试从不同的副文本渠道予以弥补,比如说在译著总引言和‘中庸“专引中,译者对三种注疏在具体章句中的阐释差异进行了说明,在术语表附录中对核心术语的含义进行了解释,除去这些,细心地读者如果仔细阅读各种疏解的翻译,也会得知三种注疏诠释之差异㊂另外,郑玄注㊁孔颖达疏㊁朱熹注本身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思想,译者要在译本中将这些差异全部予以展现,的确困难重重,且对译者的学术背景和语言素养的要求又是何其之高,乔斯顿乃学医出生,完全出自于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热爱而自发学习汉语㊁学习中国经典㊁了解中国文化,并进而着手翻译介绍中国经典,以严谨的态度,本着对西方读者的关怀之心,首创出 疏典并译 的翻译。
作者: 李乐
作者机构: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100875
出版物刊名: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62-66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1期
主题词: 中庸;中;切中伦常
摘要:“中”是中国儒学思想的精髓,是中国文化灵魂的直接体现。
儒学典籍英译中,“中庸”二字作为重要范畴经历了西方译者各般阐释和比附。
早期汉学家在释“中庸”一词时,颇多承续了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观,体现出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诉求,而当代汉学家安乐哲的翻
译“切中伦常”则导向了对“中”在生活经验中的重新建构,昭示了儒学西方阐释的新动向,为中国哲学范畴的英译提供了启示。
推而行之_《中庸》英译研究推而行之:《中庸》英译研究《中庸》作为儒家经典之一,载有了先贤的智慧和思想,在中外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然而,对于《中庸》的英译问题,却一直存在争议和探讨。
本文将从研究该书的英译现状、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等方面展开讨论,并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
一、英译现状与问题目前,《中庸》的英译版本众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杜维明的《中庸英译》和James Legge的《Great Learning and Doctrine of the Mean》两个版本。
然而,即便有这些版本,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些困扰。
首先,翻译《中庸》所涉及的语言和文化差异问题不容小觑。
英语与中文在词汇、语法和表达方式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翻译时要保持原著的内涵和意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次,《中庸》作为古文经典,其语言简练精炼,往往采用了寓意深远、意境悠远的表达方式。
如何在翻译中保持原著的韵味和语言特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最后,译者的理解与诠释也对翻译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一个兼具哲学和文学意义的经典著作,《中庸》中的许多词句和理念需要综合理解和解读,而不仅仅是简单地逐字逐句进行翻译。
二、可能的解决方案面对上述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策略来解决翻译问题。
首先,译者需要准确理解原文的含义和内涵。
对于《中庸》这样的典籍,理解其思想精髓是翻译的关键。
只有深入研究,准确把握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才能更好地进行翻译。
其次,译者可以采用灵活多样的翻译策略。
由于中英语言和文化差异较大,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文字说明、使用注释、还原原文风貌等方式,在保持原意的同时,适当调整句子结构和表达方式,以使译文更加易读和易懂。
最后,译者应该有勇气创新。
对于那些难以准确翻译的词句或含义深远的理念,译者可以灵活运用英语表达方式,并附上适当的注释或解释,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
三、个人见解与总结针对《中庸》的英译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尊重原著的思想精髓,同时结合翻译的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翻译策略。
Vol.19No.22引言《中庸》作为儒家经典之一,一直为翻译者所重视。
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中庸》英译本是早期的翻译版本之一。
理雅各翻译了多部儒家典籍,其中包括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且都被收入《中国经典》。
晚清名士辜鸿铭(1857—1928)认为理雅各的翻译不能让人满意,因为“他的文学训练还很不足,没有足够的评判能力和文学感知力”(辜鸿铭2017:2),于是亲自翻译四书,因种种原因,最终只完成了三部,即《论语》《大学》《中庸》。
由于理雅各和辜鸿铭在文化认同、翻译目的上的不同,他们在翻译中国儒家经典时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理雅各于1815年出生于苏格兰,1831年进入阿伯丁大学英王学院,后获得硕士学位;1837年进入希伯利神学院攻读神学,其间萌发来中国传教的意愿,于是在1838年开始学习汉语。
理雅各语言天赋极佳,此前已经擅长拉丁文和希腊语,这之后长期坚持研读中国典籍。
1840年,理雅各到达马六甲,工作于英华书院,并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
1843年,英华书院迁入香港,理雅各跟随来到香港并从此在香港度过了30年左右的时间。
期间,理雅各广泛地了解中国文化,接触各阶层中国人民。
他曾到广东考察科举考场,大为震撼,并意识到儒家及其经典的重要性,认为儒家经典是了解中国的钥匙(王辉2003:37)。
1847年,理雅各立志研究中国文化,翻译中国典籍,以帮助传教。
辜鸿铭于1857年生于南洋的马来西亚,父亲为中国人,母亲为西洋人。
辜鸿铭从小就展示出极佳的语言天赋。
十岁时,辜鸿铭被一对英国夫妇带到英国培养,并开始了在西洋的求学之旅。
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拉丁文和希腊语等9种语言,前后获得13个博士学位。
1881年,辜鸿铭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国文化,从此走上宣扬中国文化的道路,并在1885年前往中国,做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手下的外文秘书。
他在统筹洋务的同时精研国学。
当时,中国人对外国的俯视已变成了仰视。
《中庸》英译国内外研究述评*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首部‘四书’英译本研究”(项目编号:2016BWX024)的成果之一。
1.引言四书五经是中国儒家学术思想的经典书籍,其思想内涵和学术价值涵盖了道德思想、核心价值观、商务交际等领域。
作为《四书》其中之一的《中庸》一书,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就我们搜集到的近年来的研究文献看出,在哲学界以及汉语学界,众多专家学者对《中庸》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在翻译学界,乃至外语学界,对这部凝结着精髓思想的《中庸》研究,至今前人鲜有涉及。
2.国外研究《中庸》作为一本哲学著作,可称其为儒家的人生哲学、个人修为的宝典,因此一直深受西方研究哲学、宗教、儒家的许多学者的关注,比如,杜维明的《<中庸>论文集》(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 An Essay on Chung-yung)于1976年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其著作《<中庸>洞见》由段得智翻译,中英文对照本于200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外,安乐哲,郝大维,彭国祥的《<中庸>新论:哲学与宗教性的阐释》,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下,对《中庸》中“诚”、“性”、“情”、“礼”和“教”等最为重要的观念及其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揭示了其蕴含的一个完整连贯的结构的哲学意义以及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宗教性(安乐哲,郝大维,彭国祥,2002)。
3.国内研究国内对《中庸》的研究此起彼伏,以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领域居多,出版和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
在国内译者的《中庸》译本中,以辜鸿铭的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1906) 最为著名。
在清末明初年间,他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里。
但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国内专门对《中庸》英译的研究还不多见,相比较而言,对于辜鸿铭的译本研究稍多一些。
《中庸》英译国内外研究述评
发表时间:2018-07-23T17:53:32.360Z 来源:《知识-力量》2018年7月下作者:赵秋盈[导读] 四书五经是中国儒家学术思想的经典书籍,其思想内涵和学术价值涵盖了道德思想、核心价值观、商务交际等领域。
作为《四书》其中之一的《中庸》一书,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郑州师范学院)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首部‘四书’英译本研究”(项目编号:2016BWX024)的成果之一。
1.引言
四书五经是中国儒家学术思想的经典书籍,其思想内涵和学术价值涵盖了道德思想、核心价值观、商务交际等领域。
作为《四书》其中之一的《中庸》一书,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就我们搜集到的近年来的研究文献看出,在哲学界以及汉语学界,众多专家学者对《中庸》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在翻译学界,乃至外语学界,对这部凝结着精髓思想的《中庸》研究,至今前人鲜有涉及。
2.国外研究
《中庸》作为一本哲学著作,可称其为儒家的人生哲学、个人修为的宝典,因此一直深受西方研究哲学、宗教、儒家的许多学者的关注,比如,杜维明的《<中庸>论文集》(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 An Essay on Chung-yung)于1976年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其著作《<中庸>洞见》由段得智翻译,中英文对照本于200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外,安乐哲,郝大维,彭国祥的《<中庸>新论:哲学与宗教性的阐释》,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下,对《中庸》中“诚”、“性”、“情”、“礼”和“教”等最为重要的观念及其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揭示了其蕴含的一个完整连贯的结构的哲学意义以及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宗教性(安乐哲,郝大维,彭国祥,2002)。
3.国内研究
国内对《中庸》的研究此起彼伏,以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领域居多,出版和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
在国内译者的《中庸》译本中,以辜鸿铭的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1906) 最为著名。
在清末明初年间,他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里。
但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国内专门对《中庸》英译的研究还不多见,相比较而言,对于辜鸿铭的译本研究稍多一些。
通过在中国知网上搜索我们发现,有55篇文章专门对辜鸿铭《中庸》译本进行了研究,即倪培民(2005),王辉(2006、2007),王华(2008),王之光、陈佩佩(2009),朱萍(2009),陈佩佩(2010),郑玉凤、陈可陪(2010),李佳(2010),经晶(2010),陈梅、文军(2013),侯健(2013),丁大刚、李照国(2013),宋晓春(2013、2014),江晓梅(2015),段慧玉(2015),束慧娟(2016),于培文(2016),侯健(2016),刘永利、刘军平(2017),以及李娜(2017)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中,王国维对辜鸿铭《中庸》译本及翻译本身进行了评论。
围绕这篇文章,先后有3篇文章问绕王国维的观点进行了讨论(徐珺,2014:40)。
分别是马向辉(2008)的“不可通约性视域下的王国维议论——‘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的现代阐释”,1991年袁锦祥发表的详细阐述王国维对辜氏译本以及翻译态度的文章“王国维评辜译《中庸》”,以及王辉(2006)的逐条分析了王国维所谓辜氏译本的“大病”与“小误”的文章“辜鸿铭英译儒经的文化用心——兼评王国维‘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
此外,有15篇文章对《中庸》多中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例如:赵常玲(2017)“功能语境视角下的《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赵常玲、何伟(2016)的“功能语境视角下的《中庸》英译比较研究”,乔飞鸟(2012)的“《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钱桂荣、刘畅(2010)的“《中庸》两种英译本的对比研究”,赵辉(2010)的“《中庸》诊释方法新议——以英译《中庸》为中心的比较研究”,以及两篇硕士论文对不同译文进行的分析:分别是刘畅(2010)的“《中庸》三译本中语篇衔接机制的使用统计及译者风格分析”和丁水芳(2011)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下的《中庸》英译研究——以辜鸿铭和安乐哲译本为例”。
我们还发现有一篇硕士论文(刘玉兰,2008)虽然也对《中庸》的多个译本进行了研究,但并非如此,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假设。
刘玉兰(2008)在硕士论文《多角度主体性对翻译的操控——以<中庸>为例》里,将德里达结构主义影响下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作为框架,选取了从19世纪至21世纪《中庸》的四个英文译本。
4.结语
本文主要选取四书之一的《中庸》作为切入点,对其研究现状做了简要评析。
从中可以看出,《中庸》的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中国,对国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然而,客观地讲,学界对《中庸》的翻译研究还存在不足,即大多集中于辜鸿铭以及理雅各的译本,对其他译者译本的研究甚少;此外,研究的视角也大多聚焦于翻译方法和译本的语言比较上,缺乏语言学研究的内部关照及整体分析。
总之,文中涉及的想法仅是笔者的愚见,很多不够成熟,但学界的精髓本身就不在于得出特定的结论,而在于为之进行探索研究的过程,所以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学者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Jakobson, R. (1959).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A].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Toury, G. Translation Across Cultures [M]. New Delhi: Bahri, 1987.
[3]安乐哲,郝大维,彭国祥. 《中庸》新论:哲学与宗教性的诠释[J].中国哲学史,2002(3).
[4]杜维明. 《中庸》论文集[C]. 夏威夷: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76.
[5]王辉. 后殖民视域下的辜鸿铭《中庸》译本[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1).
[6]王辉. 理雅各《中庸》译本与传教士东方主义 [J].孔子研究,2008(5).
[7]徐珺. 汉文化经典外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赵常玲,何伟.功能语境视角下的《中庸》英译比较研究[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12).
[9]赵常玲. 功能语境视角下的《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7(3).
作者简介:赵秋盈(1984年8月—),女,河南省郑州市,硕士研究生,郑州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及词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