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
- 格式:docx
- 大小:35.88 KB
- 文档页数: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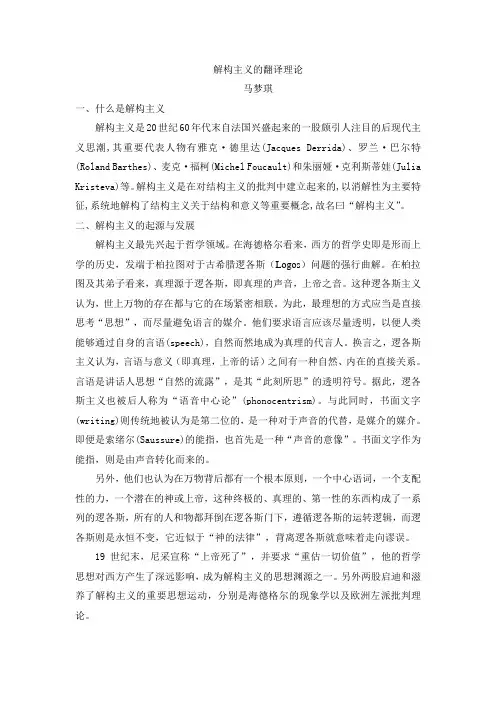
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马梦琪一、什么是解构主义解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末自法国兴盛起来的一股颇引人注目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其重要代表人物有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麦克·福柯(Michel Foucault)和朱丽娅·克利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
解构主义是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以消解性为主要特征,系统地解构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故名曰“解构主义”。
二、解构主义的起源与发展解构主义最先兴起于哲学领域。
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的哲学史即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发端于柏拉图对于古希腊逻各斯(Logos)问题的强行曲解。
在柏拉图及其弟子看来,真理源于逻各斯,即真理的声音,上帝之音。
这种逻各斯主义认为,世上万物的存在都与它的在场紧密相联。
为此,最理想的方式应当是直接思考“思想”,而尽量避免语言的媒介。
他们要求语言应该尽量透明,以便人类能够通过自身的言语(speech),自然而然地成为真理的代言人。
换言之,逻各斯主义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一种自然、内在的直接关系。
言语是讲话人思想“自然的流露”,是其“此刻所思”的透明符号。
据此,逻各斯主义也被后人称为“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
与此同时,书面文字(writing)则传统地被认为是第二位的,是一种对于声音的代替,是媒介的媒介。
即便是索绪尔(Saussure)的能指,也首先是一种“声音的意像”。
书面文字作为能指,则是由声音转化而来的。
另外,他们也认为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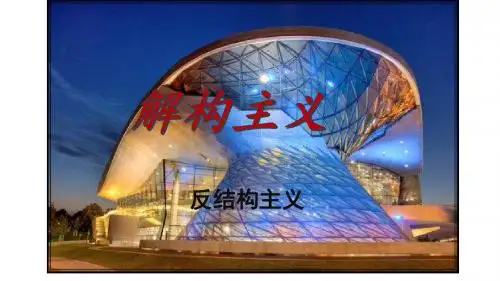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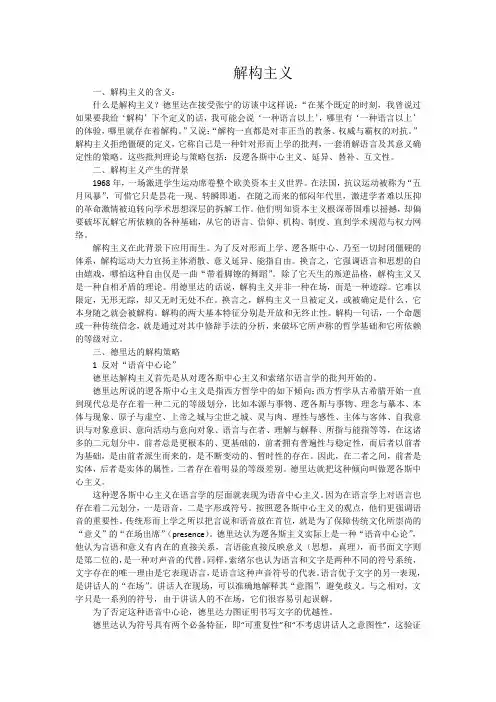
解构主义一、解构主义的含义:什么是解构主义?德里达在接受张宁的访谈中这样说:“在某个既定的时刻,我曾说过如果要我给‘解构’下个定义的话,我可能会说‘一种语言以上’,哪里有‘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哪里就存在着解构。
”又说:“解构一直都是对非正当的教条、权威与霸权的对抗。
”解构主义拒绝僵硬的定义,它称自己是一种针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一套消解语言及其意义确定性的策略。
这些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延异、替补、互文性。
二、解构主义产生的背景1968年,一场激进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
在法国,抗议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可惜它只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在随之而来的郁闷年代里,激进学者难以压抑的革命激情被迫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
他们明知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摇撼,却偏要破坏瓦解它所依赖的各种基础,从它的语言、信仰、机构、制度、直到学术规范与权力网络。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用而生。
为了反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乃至一切封闭僵硬的体系,解构运动大力宣扬主体消散、意义延异、能指自由。
换言之,它强调语言和思想的自由嬉戏,哪怕这种自由仅是一曲“带着脚镣的舞蹈”。
除了它天生的叛逆品格,解构主义又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
用德里达的话说,解构主义并非一种在场,而是一种迹踪。
它难以限定,无形无踪,却又无时无处不在。
换言之,解构主义一旦被定义,或被确定是什么,它本身随之就会被解构。
解构的两大基本特征分别是开放和无终止性。
解构一句话,一个命题或一种传统信念,就是通过对其中修辞手法的分析,来破坏它所声称的哲学基础和它所依赖的等级对立。
三、德里达的解构策略1 反对“语音中心论”德里达解构主义首先是从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索绪尔语言学的批判开始的。
德里达所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指西方哲学中的如下倾向: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到现代总是存在着一种二元的等级划分,比如本源与事物、逻各斯与事物、理念与摹本、本体与现象、原子与虚空、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灵与肉、理性与感性、主体与客体、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意向活动与意向对象、语言与在者、理解与解释、所指与能指等等,在这诸多的二元划分中,前者总是更根本的、更基础的,前者拥有普遍性与稳定性,而后者以前者为基础,是由前者派生而来的,是不断变动的、暂时性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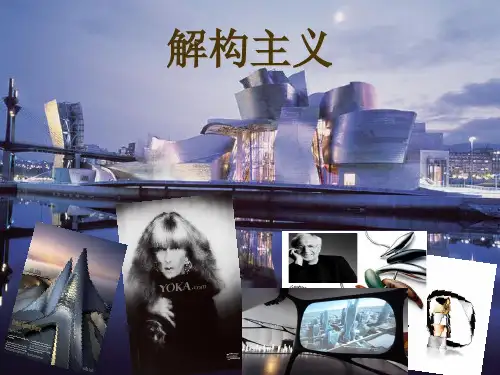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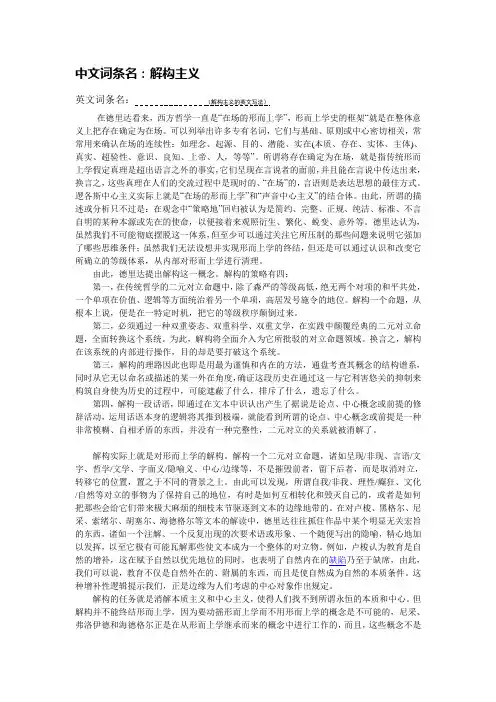
中文词条名:解构主义英文词条名:(解构主义的英文写法)在德里达看来,西方哲学一直是“在场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史的框架“就是在整体意义上把存在确定为在场。
可以列举出许多专有名词,它们与基础、原则或中心密切相关,常常用来确认在场的连续性:如理念、起源、目的、潜能、实在(本质、存在、实体、主体)、真实、超验性、意识、良知、上帝、人,等等”。
所谓将存在确定为在场,就是指传统形而上学假定真理是超出语言之外的事实,它们呈现在言说者的面前,并且能在言说中传达出来,换言之,这些真理在人们的交流过程中是现时的、“在场”的,言语则是表达思想的最佳方式。
逻各斯中心主义实际上就是“在场的形而上学”和“声音中心主义”的结合体。
由此,所谓的描述或分析只不过是:在观念中“策略地”回归被认为是简约、完整、正规、纯洁、标准、不言自明的某种本源或先在的使命,以便接着来观照衍生、繁化、蜕变、意外等。
德里达认为,虽然我们不可能彻底摆脱这一体系,但至少可以通过关注它所压制的那些问题来说明它强加了哪些思维条件;虽然我们无法设想并实现形而上学的终结,但还是可以通过认识和改变它所确立的等级体系,从内部对形而上学进行清理。
由此,德里达提出解构这一概念。
解构的策略有四:第一,在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命题中,除了森严的等级高低,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单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
解构一个命题,从根本上说,便是在一特定时机,把它的等级秩序颠倒过来。
第二,必须通过一种双重姿态、双重科学、双重文学,在实践中颠覆经典的二元对立命题,全面转换这个系统。
为此,解构将全面介入为它所批驳的对立命题领域。
换言之,解构在该系统的内部进行操作,目的却是要打破这个系统。
第三,解构的理路因此也即是用最为谨慎和内在的方法,通盘考查其概念的结构谱系,同时从它无以命名或描述的某一外在角度,确证这段历史在通过这一与它利害悠关的抑制来构筑自身使为历史的过程中,可能遮蔽了什么,排斥了什么,遗忘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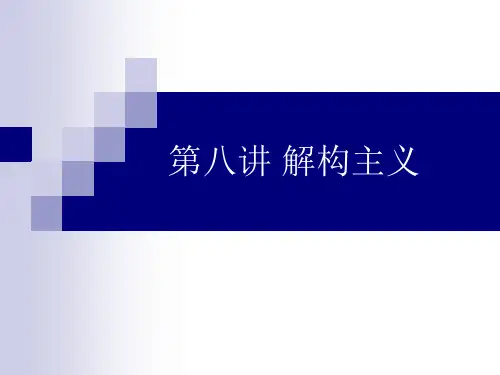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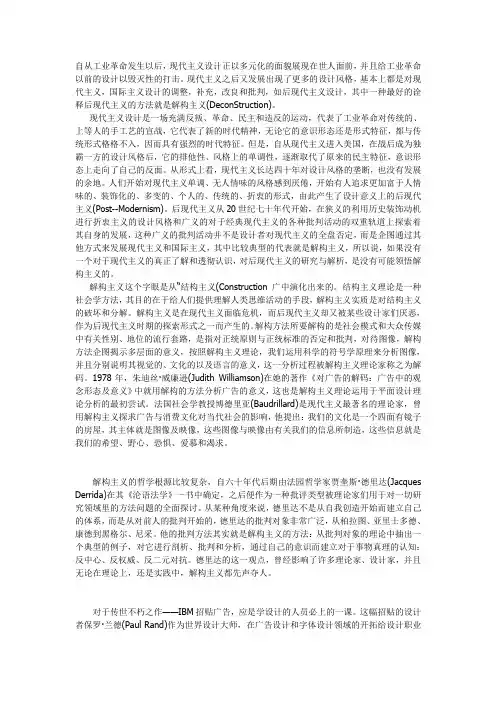
自从工业革命发生以后,现代主义设计正以多元化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并且给工业革命以前的设计以毁灭性的打击。
现代主义之后又发展出现了更多的设计风格,基本上都是对现代主义,国际主义设计的调整,补充,改良和批判,如后现代主义设计,其中一种最好的诠释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就是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
现代主义设计是一场充满反叛、革命、民主和造反的运动,代表了工业革命对传统的、上等人的手工艺的宣战,它代表了新的时代精神,无论它的意识形态还是形式特征,都与传统形式格格不入,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
但是,自从现代主义进入美国,在战后成为独霸一方的设计风格后,它的排他性、风格上的单调性,逐渐取代了原来的民主特征,意识形态上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从形式上看,现代主义长达四十年对设计风格的垄断,也没有发展的余地。
人们开始对现代主义单调、无人情味的风格感到厌倦,开始有人追求更加富于人情味的、装饰化的、多变的、个人的、传统的、折衷的形式,由此产生了设计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从20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狭义的利用历史装饰动机进行折衷主义的设计风格和广义的对于经典现代主义的各种批判活动的双重轨道上探索着其自身的发展,这种广义的批判活动并不是设计者对现代主义的全盘否定,而是企图通过其他方式来发展现代主义和国际主义,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解构主义,所以说,如果没有一个对于现代主义的真正了解和透彻认识,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与解析,是没有可能领悟解构主义的。
解构主义这个字眼是从“结构主义(Construction广中演化出来的。
结构主义理论是一种社会学方法,其目的在于给人们提供理解人类思维活动的手段,解构主义实质是对结构主义的破坏和分解。
解构主义是在现代主义面临危机,而后现代主义却又被某些设计家们厌恶,作为后现代主义时期的探索形式之一而产生的。
解构方法所要解构的是社会模式和大众传媒中有关性别、地位的流行套路,是指对正统原则与正统标准的否定和批判,对待图像,解构方法企图揭示多层面的意义,按照解构主义理论,我们运用科学的符号学原理来分析图像,并且分别说明其视觉的、文化的以及语言的意义,这一分析过程被解构主义理论家称之为解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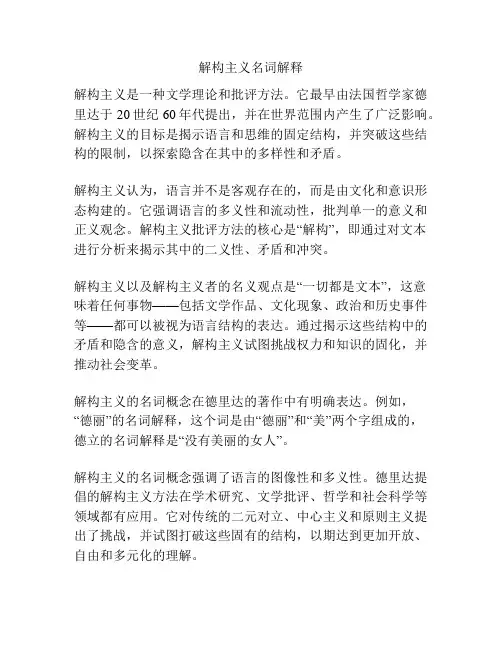
解构主义名词解释解构主义是一种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
它最早由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解构主义的目标是揭示语言和思维的固定结构,并突破这些结构的限制,以探索隐含在其中的多样性和矛盾。
解构主义认为,语言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由文化和意识形态构建的。
它强调语言的多义性和流动性,批判单一的意义和正义观念。
解构主义批评方法的核心是“解构”,即通过对文本进行分析来揭示其中的二义性、矛盾和冲突。
解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者的名义观点是“一切都是文本”,这意味着任何事物——包括文学作品、文化现象、政治和历史事件等——都可以被视为语言结构的表达。
通过揭示这些结构中的矛盾和隐含的意义,解构主义试图挑战权力和知识的固化,并推动社会变革。
解构主义的名词概念在德里达的著作中有明确表达。
例如,“德丽”的名词解释,这个词是由“德丽”和“美”两个字组成的,德立的名词解释是“没有美丽的女人”。
解构主义的名词概念强调了语言的图像性和多义性。
德里达提倡的解构主义方法在学术研究、文学批评、哲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都有应用。
它对传统的二元对立、中心主义和原则主义提出了挑战,并试图打破这些固有的结构,以期达到更加开放、自由和多元化的理解。
然而,解构主义的名词解释也受到了批评。
一些人认为,解构主义的方法过于抽象和复杂,无法直接应用于实际问题。
此外,解构主义的批评方法有时被认为过分强调矛盾和多义性,忽视了文本的整体意义和作者的意图。
总的来说,解构主义是一种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强调语言和思维中固定结构的矛盾和多义性。
它试图挑战权力和知识的固化,以推动社会变革。
虽然解构主义的名词解释受到争议,但它在学术和文化领域都有重要影响,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学科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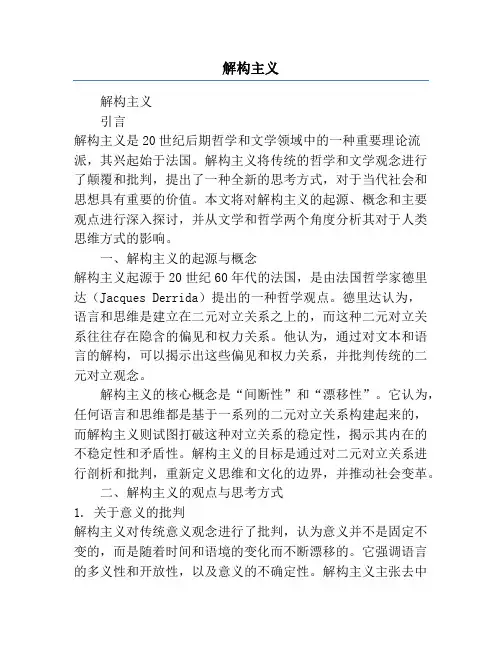
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引言解构主义是20世纪后期哲学和文学领域中的一种重要理论流派,其兴起始于法国。
解构主义将传统的哲学和文学观念进行了颠覆和批判,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对于当代社会和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
本文将对解构主义的起源、概念和主要观点进行深入探讨,并从文学和哲学两个角度分析其对于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
一、解构主义的起源与概念解构主义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是由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提出的一种哲学观点。
德里达认为,语言和思维是建立在二元对立关系之上的,而这种二元对立关系往往存在隐含的偏见和权力关系。
他认为,通过对文本和语言的解构,可以揭示出这些偏见和权力关系,并批判传统的二元对立观念。
解构主义的核心概念是“间断性”和“漂移性”。
它认为,任何语言和思维都是基于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关系构建起来的,而解构主义则试图打破这种对立关系的稳定性,揭示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和矛盾性。
解构主义的目标是通过对二元对立关系进行剖析和批判,重新定义思维和文化的边界,并推动社会变革。
二、解构主义的观点与思考方式1. 关于意义的批判解构主义对传统意义观念进行了批判,认为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和语境的变化而不断漂移的。
它强调语言的多义性和开放性,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
解构主义主张去中心化和不断重新解释意义,将文本和语言从固定的定义中解放出来,从而推动了对传统概念和价值观的重新思考。
2. 对权力关系的挑战解构主义认为,语言和思维中存在着权力关系的问题,这种权力关系往往体现在二元对立关系中。
它通过对这种权力关系的揭示和批判,拆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观念,展示了这些观念中的偏见和隐含的权力结构。
解构主义试图从权力关系的角度重新定义思维和文化的边界,推动社会的平等和公正。
3. 文本和语言的超越解构主义认为,文本和语言不仅仅是传递意义和信息的工具,它们本身有着超越意义和信息的特点。
解构主义试图揭示文本和语言的边界性和不稳定性,并超越传统的主题和结构,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学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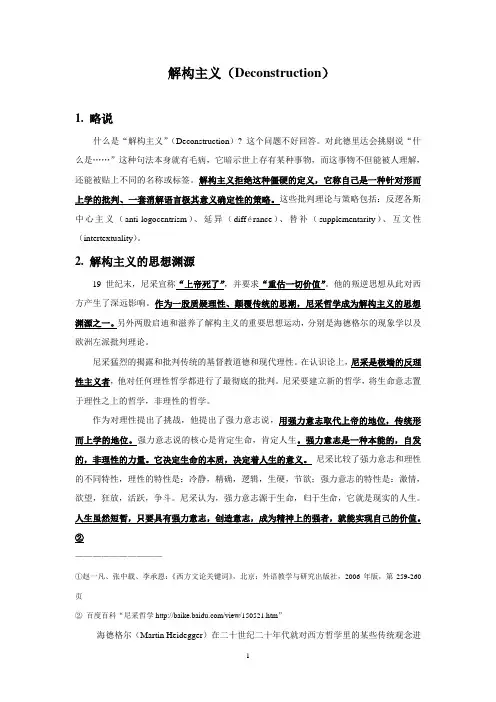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1. 略说什么是“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对此德里达会挑剔说“什么是……”这种句法本身就有毛病,它暗示世上存有某种事物,而这事物不但能被人理解,还能被贴上不同的名称或标签。
解构主义拒绝这种僵硬的定义,它称自己是一种针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一套消解语言极其意义确定性的策略。
这些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2. 解构主义的思想渊源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并要求“重估一切价值”。
他的叛逆思想从此对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一股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思潮,尼采哲学成为解构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
另外两股启迪和滋养了解构主义的重要思想运动,分别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以及欧洲左派批判理论。
尼采猛烈的揭露和批判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和现代理性。
在认识论上,尼采是极端的反理性主义者,他对任何理性哲学都进行了最彻底的批判。
尼采要建立新的哲学,将生命意志置于理性之上的哲学,非理性的哲学。
作为对理性提出了挑战,他提出了强力意志说,用强力意志取代上帝的地位,传统形而上学的地位。
强力意志说的核心是肯定生命,肯定人生。
强力意志是一种本能的,自发的,非理性的力量。
它决定生命的本质,决定着人生的意义。
尼采比较了强力意志和理性的不同特性,理性的特性是:冷静,精确,逻辑,生硬,节欲;强力意志的特性是:激情,欲望,狂放,活跃,争斗。
尼采认为,强力意志源于生命,归于生命,它就是现实的人生。
人生虽然短暂,只要具有强力意志,创造意志,成为精神上的强者,就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②——————————①赵一凡、张中载、李承恩:《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260页②百度百科“尼采哲学/view/150521.htm”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对西方哲学里的某些传统观念进行了“解构”。
解构主义打破秩序然后再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
解构主义是对现代主义正统原则和标准批判地加以继承,运用现代主义的语汇,却颠倒、重构各种既有语汇之间的关系,从逻辑上否定传统的基本设计原则(美学、力学、功能),由此产生新的意义。
用分解的观念,强调打碎,叠加,重组,重视个体,部件本身,反对总体统一而创造出支离破碎和不确定感。
解构主义一旦被定义,或被确定为是什么,它本身随之就会被解构掉。
解构的两大基本特征分别是开放性和无终止性。
解构在建筑上:解构主义{HYPERLINK "/view/151928.htm"|建筑师设计的共同点是赋予建筑各种各样的一一而且与显著的水平、垂直或这种简单集合形体的设计倾向相比,解构主义的建筑却运用相贯、偏心、反转、回转等手法,具有不安定且富有运动感的形态的倾向。
解构主义相信传统是无法砸烂的,后人应该不断地用新的眼光去解读。
而且,即使承认上没有真理,也并不妨碍每个人按照自己的阐释确定自己的理想。
弗兰克·盖里盖里的作品相当独特,极具个性,他的大部分作品中很少掺杂社会化和意识形态的东西。
盖里使用断裂的几何图形以打破传统习俗,对他而言,断裂意味着探索一种不明确的社会秩序。
在许多实例中,盖里将形式脱离于功能,所建立的不是一种整体的结构,而是一种成功的想法和抽象的城市机构。
在很多时候,他把工作当成雕刻一样对待,这种三位结构图通过集中处理就拥有了多种形式。
弗兰克·盖里作品经常是盖里的灵感发源地,他对的兴趣可以从他的作品中了解到。
同时,使他初次使用开放的结构,并让人觉得是一种无形的改变,而非刻意。
盖里设计的通常是超现实的、抽象的,偶尔还会使人深感迷惑,因此它所传递的信息常常使人误解。
虽然如此,盖里设计的还是呈现出其独特、高贵和神秘的气息。
盖里仿佛与都市格格不入,他采用多种材料、运用各种形式,并将、神秘以及梦想等元素融入他的体系中。
盖里在早期的工作中就大胆运用开阔的空间、各种原材料以及不拘泥的形式建造。
解构主义解构主义解构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潮,源于法国的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思想。
它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涉及文学、哲学、艺术、建筑等多个领域。
解构主义所倡导的是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试图揭示固有概念和观念的不稳定性,挑战二元对立和固定化的思维模式,以达到对历史和文化的解构和重建。
解构主义的前提是一种对固定二元对立的怀疑态度。
传统上,人们习惯将事物划分为对立的两个极端,如好与坏、男与女、黑与白等。
然而,解构主义主张这种二元对立实际上是虚构的,因为没有事物是完全固定的或绝对的。
解构主义认为,事物的意义并不是固定的,而是由语言和文化进行建构的。
因此,解构主义试图揭示这种固定性的虚假性,并提出了一种对语言和文本的批判性阐释方式。
解构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差异”和“延迟”。
在传统的二元对立体系中,一方的存在必然排斥另一方的存在。
然而,在解构主义的观点下,事物的存在是相对的,通过与其他事物的对比和区别来确定。
事物之间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的延迟是解构主义的关注点。
差异是指事物之间的差别,而延迟是指在差异的基础上推迟决定或识别事物的边界。
通过扩大差异和延迟边界的认定,解构主义试图打破二元对立的限制,并以新的视角来看待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文学领域,解构主义对传统文本的阐释提出了挑战。
传统上,文本被认为有一个明确的含义和结构,在读者阅读时传达给读者。
然而,解构主义主张文本的意义是多样和动态的,不是由作者单方面决定的。
解构主义通过关注文本中的差异性和模棱两可的部分,试图展现文本的复杂性和多义性。
事实上,解构主义认为文本具有自己的内在矛盾和隐含的意义,需要读者进行主动的解读和阐释。
在艺术领域,解构主义试图挑战传统艺术的创作和观赏方式。
传统上,艺术被认为是一种符号和象征的表达,通过艺术作品来传达某种特定的主题或观念。
然而,解构主义批评传统艺术的固定意义和结构,主张拆解和重构艺术作品。
解构主义解构主义是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构主义60年代缘起于法国,1968年5月法国爆发的反政府学生运动造成的法国社会生活转向,是导致法国思想界、学术界由结构主义走向解构主义(也称后结构主义)的重要契机。
解构主义者看来,现存语言体系实际上是现存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的基础,通过对语言结构的破坏进而达到对传统成规的解构。
解构主义思潮具有反传统、反权威、反理性的特征,大体导源于此。
解构主义是对现代主义正统原则和标准批判地加以继承,运用现代主义的语汇,却颠倒、重构各种既有语汇之间的关系,从逻辑上否定传统的基本设计原则(美学、力学、功能),由此产生新的意义。
用分解的观念,强调打碎,叠加,重组,重视个体,部件本身,反对总体统一而创造出支离破碎和不确定感。
解构主义及解构主义者就是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
当然这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而且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比如创作习惯、接受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
反正是打破秩序然后再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
0解构主义的巴尔特、拉康、福柯、巴尔赫的理论中就已初露端倪,但真正确立这一理论的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
1967年,德里达三部重要著作《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相继出版,成为解构主义理论被确立起来的标志。
在文论界,文学批评领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构主义运动,最后在美国形成了以保罗·德·曼、希利·米勒、杰弗里·哈特曼等为代表的“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批评。
第一节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批判1.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雅克·德里达(Jacque Derride,1930——2004)解构主义领袖,基于对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的批判,提出了“解构主义”的理论。
他的核心理论是对于结构本身的反感,认为符号本身已能够反映真实,对于单独个体的研究比对于整体结构的研究更重要。
当代建筑思潮分析——解构主义1 前言2解构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2.1哲学起源2.2 解构主义建筑起源3建筑的解构主义浪潮4 解构主义建筑问题及发展5结语关键词解构主义建筑非线性彼得埃森曼1前言20世纪是各种风格与主义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一时期产生的比以往任何世纪都多,从构成主义到表现主义,从功能主义、国际风格到新的粗野主义、后现代和解构主义;这集中地反映了各种流派思潮对建筑观念的挑战和探索,如芝加哥学派、维也纳学派、未来学派、风格派、包豪斯学派等。
可以说20世纪40年代~60年代是现代主义建筑、国际主义建筑风格垄断时期,70年代到现在为止是后现代主义时期,产生后现代风格的土壤是后现代的社会意识形态,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个性思潮也逐渐从理论走向现实,各种各样的优秀作品争相现世,解构主义大师如彼得.埃森曼,弗兰克.盖里,扎哈.哈迪德等也纷纷活跃在世界各地,引领了解构主义世界的潮流。
2解构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2.1哲学起源解构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以人文哲学为背景,二战后欧美哲学由过去占主流的理性主义与新发展起来的非理性思潮平行发展,在各分秋色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20世纪50,60年代“人本主义”哲学得到了发展空间,其主要代表流派有: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结构主义。
其中结构主义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学派,它在发展过程中吸取语言符号学的方法,对各个领域的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
建筑学中的符号学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为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和解构主义建筑的发展和完善奠定基础。
结构主义哲学受语言符号系统结构主义方法的推动,为以后语言学的解构主义的诞生促使解构哲学的产生并影响到解构主义建筑埋下了伏笔。
解构主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由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在其《论语法学》一书中确定,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科、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之后便作为一种批评类型被理论家们用于对众多研究领域方法问题的探讨。
解构主义一、解构主义的含义:什么是解构主义?德里达在接受张宁的访谈中这样说:“在某个既定的时刻,我曾说过如果要我给‘解构’下个定义的话,我可能会说‘一种语言以上’,哪里有‘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哪里就存在着解构。
”又说:“解构一直都是对非正当的教条、权威与霸权的对抗。
”解构主义拒绝僵硬的定义,它称自己是一种针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一套消解语言及其意义确定性的策略。
这些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延异、替补、互文性。
二、解构主义产生的背景1968年,一场激进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
在法国,抗议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可惜它只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在随之而来的郁闷年代里,激进学者难以压抑的革命激情被迫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
他们明知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摇撼,却偏要破坏瓦解它所依赖的各种基础,从它的语言、信仰、机构、制度、直到学术规范与权力网络。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用而生。
为了反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乃至一切封闭僵硬的体系,解构运动大力宣扬主体消散、意义延异、能指自由。
换言之,它强调语言和思想的自由嬉戏,哪怕这种自由仅是一曲“带着脚镣的舞蹈”。
除了它天生的叛逆品格,解构主义又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
用德里达的话说,解构主义并非一种在场,而是一种迹踪。
它难以限定,无形无踪,却又无时无处不在。
换言之,解构主义一旦被定义,或被确定是什么,它本身随之就会被解构。
解构的两大基本特征分别是开放和无终止性。
解构一句话,一个命题或一种传统信念,就是通过对其中修辞手法的分析,来破坏它所声称的哲学基础和它所依赖的等级对立。
三、德里达的解构策略1 反对“语音中心论”德里达解构主义首先是从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索绪尔语言学的批判开始的。
德里达所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指西方哲学中的如下倾向: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到现代总是存在着一种二元的等级划分,比如本源与事物、逻各斯与事物、理念与摹本、本体与现象、原子与虚空、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灵与肉、理性与感性、主体与客体、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意向活动与意向对象、语言与在者、理解与解释、所指与能指等等,在这诸多的二元划分中,前者总是更根本的、更基础的,前者拥有普遍性与稳定性,而后者以前者为基础,是由前者派生而来的,是不断变动的、暂时性的存在。
因此,在二者之间,前者是实体,后者是实体的属性。
二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
德里达就把这种倾向叫做逻各斯中心主义。
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语言学的层面就表现为语音中心主义。
因为在语言学上对语言也存在着二元划分,一是语音,二是字形或符号。
按照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观点,他们更强调语音的重要性。
传统形而上学之所以把言说和语音放在首位,就是为了保障传统文化所崇尚的“意义”的“在场出席”(presence)。
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语音中心论”,他认为言语和意义有内在的直接关系,言语能直接反映意义(思想,真理),而书面文字则是第二位的,是一种对声音的代替。
同样,索绪尔也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它表现语言,是语言这种声音符号的代表。
语言优于文字的另一表现,是讲话人的“在场”。
讲话人在现场,可以准确地解释其“意图”,避免歧义。
与之相对,文字只是一系列的符号,由于讲话人的不在场,它们很容易引起误解。
为了否定这种语音中心论,德里达力图证明书写文字的优越性。
德里达认为符号具有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这验证了他所说的文字优越。
在更大的范围说,总体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
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
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2 瓦解二元对立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集中体现于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中。
在传统二元对立中,两个对立项并非和平共处,而是处于一个鲜明的等级秩序中。
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方面占据了强制性位置,它统治着另一项。
以言语/文字为例,言语优越于文字,是更高层次上的存在。
它是确立二者关系的中心,而文字则是从属性的。
德里达则认为,对立项之间仅有一些差异,而无孰优孰劣的等级秩序。
不仅如此,对立项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的关系。
他身体力行地发起多项针对二元对立及其等级制的解构。
以上述言语/文字为例,他证明文字不仅不劣于言语,作为元书写的文字,反过来还宽宏大量地包括了言语。
3 发明延异概念在《多重立场》一书中,德里达集中地谈论了延异和撒播这两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认为,延异(diffeˊrance)这个主题,当它带有一个无声的字母“a”时,它实际上既不起一个“概念”的作用,也不起一个词的作用。
但这并不妨碍它产生概念上的结果和语言上或名义上的具体物。
而且虽然这一点不能被直接注意到,但是它被这一“字母”及其奇怪“逻辑”的不断作用所印出,同时也被它们撕裂。
这就是说,延异是通过自行的改变来引进一种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从没有过的书写方式和阅读方式,这种书写方式和阅读方式没法用西方原有的话语进行定义,因为它本身就是反定义的。
在德里达看来,定义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的一个结果,因为定义追求的是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最终指向一个本体,而延异要反对的恰恰是确定性。
所以,德里达说延异不是一个“概念”,它只是一个“主题”。
延异形成的是不同向度的语言之“束”或者说语言之链,每一个语言之束都是一个历史的和系统的交织中心,要封闭这一网络、中断它的构造、跟踪一个不再是新标记的边缘,这在结构上尤其不可能。
这就是说,延异所形成的文本是没有边际、无限延伸的,它必将在自我的延宕与分延中不断自我生成。
由于延异有这样的变动不居的特性,它可以和不同的主题相互交织,从而形成不同的对延异的替补性的语词。
德里达认为,像书写物、保留、切入、踪迹、间隔、空白、替补、药、边缘—界限—边界等等词语都可以作为延异的替代物,所以,要想说延异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都是困难的。
延异有点类似于“沸腾的熔炉”,将一切确定性的概念都熔烂于其中。
它的结果不只是通过封闭的自身作用简单地还诸自身,它们像链一样扩展到一篇文本的全部实践和理论中,而且每次的方式都不一样。
因此,延异有点类似于尼采的“透视主义”,而不同于黑格尔所说的“扬弃”。
因为黑格尔的扬弃总是一个绝对物设定一个自身的他者,在自身的他者中返回自身,这样,一方面最终造成的是一个封闭的全体,另一方面形成的却是一个具有统一性方向的曲线结构;而延异首先反对的就是这种封闭,同时它是向不同方向扩散的。
关于延异,德里达有个生动比喻,说它就像一把扎束的花,其中有着“复杂的组织结构,不同的花枝和不同的词意,各自朝不同的方向散漫开去。
与此同时,每一枝花又与其它花枝或意义紧密联系,形成一种交错结构。
”需要说明,作为延异特征之一的散漫,除了时间上的延迟、空间上的差异这两层含义外,还含有一种“播撒”之意。
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完全控制流动的象征符号游戏,没有人能够约束文字的差异区别。
在德里达这里,语言被看成延迟和差异永无止境的游戏,而意义也只能从无数可供选择的意义差异中产生。
由于作为意义归宿的在场已经不复存在,符号的确定意义被层层地延异下来,又向四面八方指涉开去,犹如种子一样到处播撒,因而它根本没有中心可言。
德里达认为播撒是一切文字固有的能力,它永远无休止地瓦解文本,揭露文本的凌乱与重复。
这样通过播撒,任何文本实际上都宣告了不完整、非自足性,播撒标志着一种不可还原和生生不息的意义多样性。
播撒作为文本的文本性的结果,是宣告任何一篇文本都有裂口而不完整。
任何一种新的解释或误解,都成为原文不完整和不稳定的证据。
解读原文既是对原文意义的发掘,又是对它的意义的抹煞。
这样,德里达的追问已经抵达对“根源”匮乏的分析层次。
4关于“替补”德里达完成了他对于传统二元对立的解构后,自然而然走上一条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替补”之路。
他所谓替补,实质上是一连串无休止的语言代替。
替补是一种漫无边际的延伸系列,它使在场持续不断地被延异。
德里达在《文字语言学》中强调,一方面替补既是一种补充增加,是存在的增补和积累;另一方面,它是虽附加的、次要的,但在增补过程中又成了取代者。
同时,替补不是转换,因为替代者的位置已由结构中的空白标志所确立。
替补因存在的空虚而起,是存在不完善的证明,它的根本指向是彻底否定存在的根源和形而上学绝对真理的神话。
德里达用替补这一概念完成了对形而上学不容质疑的先验假定前提和基本概念的颠覆,将追问本源、追求真理、抱持永恒意义的回归之路置换成一条永远走向不确定性、增补性、替代性的敞开之路。
同时,对形而上学将虚假设定的前提作为出发点并据为真理的做法加以质疑,并提供了一种依据可疑的出发点、一句不真的概念去反向思维以重新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原来有内在结构的文本在德里达那里成了一个无限开放的东西,文本里面的东西不断涌出,文本外面的东西不断进来对原有的东西进行增补,从而形成一个相互交织的文本的“意指链”。
“增补补充自身,它是一种过剩,一种充实丰富另一种充实,是存在最充分的限度”,“它使自己介入或悄悄插进替代的行列;倘若它充填,就好像一件东西充填虚空之处。
如果它再现和制造意象,那是因为存在先前的欠缺”。
这样,文本的原初意义就不可理解,人们在文本的理解上也不可能达成共识。
于是,德里达说,收信人“死了”,理解的权威“死了”,文本成了四处飘零、无家可归的孤儿。
5关于“互文性”解构主义认为,文字不是外在实物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符号的推迟和差异的永无止境的游戏。
文本也不再是外在世界的再现,与之相反,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中,客观世界也被文本化了。
或者说,整个世界都被归纳为一个文本。
德里达还认为,阅读与写作无孔不入地渗入我们的知识和经验世界,而我们的世界除了解释,别无他者。
阐释者无法超越解释,因为他被囚禁于语言牢笼之中,必须面对修辞和差异构成的无休止的符号游戏,所以他的解释也是永无止境的。
在此前提下,德里达提出了他的互文性观念:一篇作品既不属于某一个作家也不属于某个时代,它的文本贯穿了各个时代,带有不同作家的文本痕迹。
所以针对一个文本的解释和阅读也只能是开放性的而且千差万别。
任何一个新文本,都与以前的文本、语言、代码互为文本,而过去文本的痕迹,则通过作者的扬弃而渗入他的作品。
互文性,不仅是语言互文,更是一种文化思想的互文。
四、罗兰•巴特的解构主义文学理论除德里达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法国还有一批文论家从结构主义阵营退出,转向解构主义。
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罗兰•巴特。
巴特对自己原先奉行的结构主义进行了清算和嘲讽,他在《S/Z》中曾这样说:“据说某些佛教徒凭着苦修,终于能在一粒蛋豆里见出一个国家。
这正是前期作品分析家想做的事:在单一的结构里,……见出全世界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