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自由概念(四)
- 格式:docx
- 大小:25.17 KB
- 文档页数: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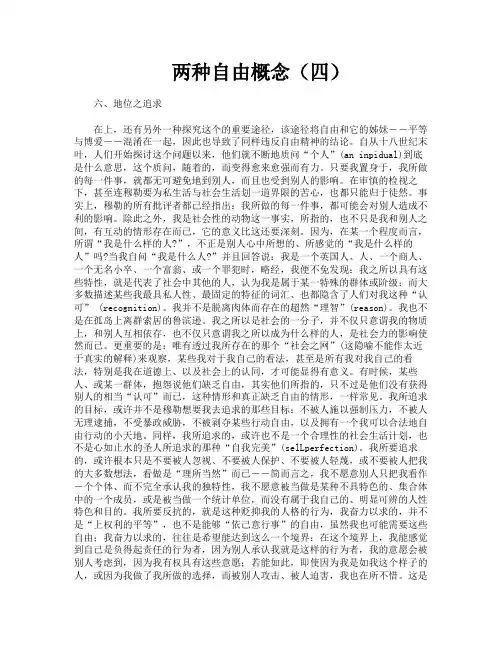
两种自由概念(四)六、地位之追求在上,还有另外一种探究这个的重要途径,该途径将自由和它的姊妹――平等与博爱――混淆在一起,因此也导致了同样违反自由精神的结论。
自从十八世纪末叶,人们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以来,他们就不断地质问“个人”(an inpidual)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质问,随着的,而变得愈来愈强而有力。
只要我置身于,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就都无可避免地到别人,而且也受到别人的影响。
在审慎的检视之下,甚至连穆勒要为私生活与社会生活划一道界限的苦心,也都只能归于徒然。
事实上,穆勒的所有批评者都已经指出: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会对别人造成不利的影响。
除此之外,我是社会性的动物这一事实,所指的,也不只是我和别人之间,有互动的情形存在而已,它的意义比这还要深刻。
因为,在某一个程度而言,所谓“我是什么样的人?”,不正是别人心中所想的、所感觉的“我是什么样的人”吗?当我自问“我是什么人?”并且回答说:我是一个英国人、人、一个商人、一个无名小卒、一个富翁、或一个罪犯时,略经,我便不免发现:我之所以具有这些特性,就是代表了社会中其他的人,认为我是属于某一特殊的群体或阶级;而大多数描述某些我最具私人性、最固定的特征的词汇、也都隐含了人们对我这种“认可” (recognition)。
我并不是脱离肉体而存在的超然“理智”(reason)。
我也不是在孤岛上离群索居的鲁滨逊。
我之所以是社会的一分子,并不仅只意谓我的物质上,和别人互相依存,也不仅只意谓我之所以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社会力的影响使然而已。
更重要的是:唯有透过我所存在的那个“社会之网”(这隐喻不能作太近于真实的解释)来观察,某些我对于我自己的看法,甚至是所有我对我自己的看法,特别是我在道德上、以及社会上的认同,才可能显得有意义。
有时候,某些人、或某一群体,抱怨说他们缺乏自由,其实他们所指的,只不过是他们没有获得别人的相当“认可”而已,这种情形和真正缺乏自由的情形,一样常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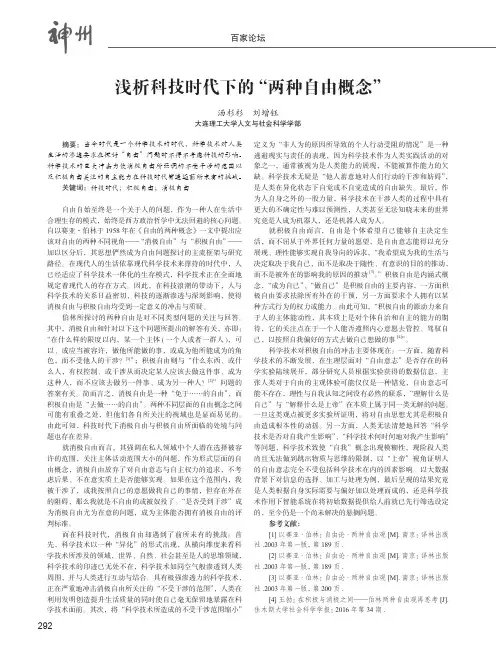
292百家论坛浅析科技时代下的“两种自由概念”汤杉杉 刘增钰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摘要:当今时代是一个科学技术的时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的渗透要求在探讨“自由”问题时不得不考虑科技的影响。
科学技术的巨大冲击力使消极自由所强调的不受干涉的范围以及积极自由关注的自主能力在科技时代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关键词:科技时代;积极自由;消极自由自由自始至终是一个关于人的问题,作为一种人在生活中合理生存的模式,始终是西方政治哲学中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
自以赛亚·伯林于1958年在《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中提出应该对自由的两种不同视角——“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加以区分后,其思想俨然成为自由问题探讨的主流框架与研究路径。
在现代人的生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来撑持的时代中,人已经适应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生存模式,科学技术正在全面地规定着现代人的存在方式。
因此,在科技浪潮的带动下,人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日益密切,科技的逐渐渗透与深刻影响,使得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均受到一定意义的冲击与质疑。
伯林所探讨的两种自由是对不同类型问题的关注与回答。
其中,消极自由和针对以下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解答有关,亦即:“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他人的干涉?[1]”;积极自由则与“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2]”问题的答案有关。
简而言之,消极自由是一种“免于……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去做……的自由”。
两种不同层面的自由概念之间可能有重叠之处,但他们各自所关注的视域也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可知,科技时代下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所面临的处境与问题也存在差异。
就消极自由而言,其强调在私人领域中个人潜在选择被容许的范围,关注主体活动范围大小的问题,作为形式层面的自由概念,消极自由放弃了对自由意志与自主权力的追求,不考虑后果、不在意实质上是否能够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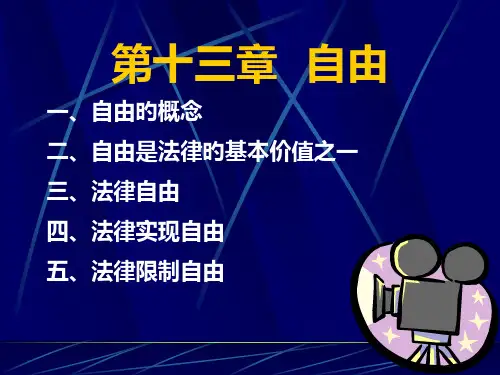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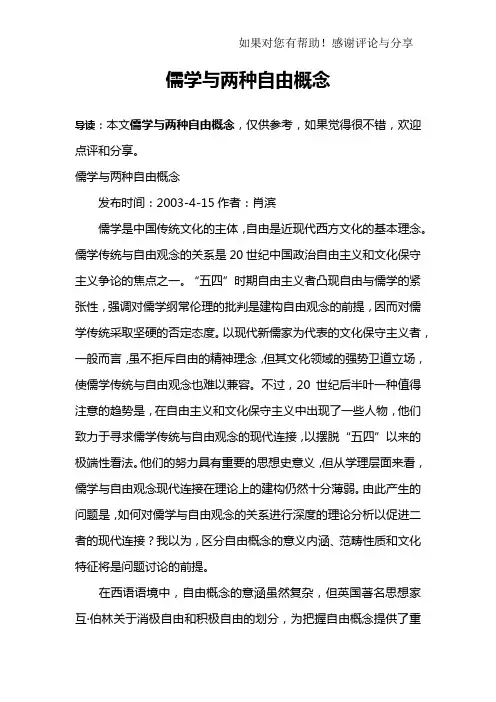
儒学与两种自由概念导读:本文儒学与两种自由概念,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儒学与两种自由概念发布时间:2003-4-15作者:肖滨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
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
“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凸现自由与儒学的紧张性,强调对儒学纲常伦理的批判是建构自由观念的前提,因而对儒学传统采取坚硬的否定态度。
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而言,虽不拒斥自由的精神理念,但其文化领域的强势卫道立场,使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也难以兼容。
不过,20世纪后半叶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出现了一些人物,他们致力于寻求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以摆脱“五四”以来的极端性看法。
他们的努力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但从学理层面来看,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在理论上的建构仍然十分薄弱。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对儒学与自由观念的关系进行深度的理论分析以促进二者的现代连接?我以为,区分自由概念的意义内涵、范畴性质和文化特征将是问题讨论的前提。
在西语语境中,自由概念的意涵虽然复杂,但英国著名思想家互·伯林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为把握自由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
根据伯林的论述,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与两组不同的问题有关:前者涉及控制的范围问题,后者涉及控制的来源问题。
正是基于对这两组不同问题的回答,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
消极自由的内涵是;个人拥有不受他人控制独立地作出选择和活动的范围;自由本身不能不受到法律的限制,因为存在着与自由的价值同等或比自由的价值更高的价值;必须保留最低限度的自由,因而公共权力对自由的限制本身不能不受到限制。
在此意义上,消极自由概念的实质是,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元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因而应当在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的公共权威之间,划定一条边际界限。
![自由的分类[整理版]](https://uimg.taocdn.com/addef210eef9aef8941ea76e58fafab069dc44ae.webp)
一、自由的分类英国伯林——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消极的自由——免于···的自由。
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进行了界定,指出消极自由的含义是“我们一般说,就没有人或者人的群体干涉我的活动而言,我是自由的。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自由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人能够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
因而,消极自由的本质就在于“不干预”,即个人免于他人乃至国家的专断意志的干预。
哈耶克也有类似的论述,在他的《自由秩序原理》一书开篇所讨论的就是自由的问题。
在他看来,自由指的是一种人的状态,“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状态,亦被称为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在此,自由是免于···的自由,仅仅涉及与他人的关系,在此自由观下,对于自由的侵犯只来自于人的强制,特别是来自政府等强制性权利道德强制。
至于呢由于能力挥着其他方面原因造成的不能为或者受限制,如脚破了无法跑步,乃至经济上的贫困,道德上的自持等,都与自由观念无关。
自由就是自由,不是平等、公平、正义,不是文化,也不是人类的幸福或平静的良心。
与之相对,积极自由“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期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
我希望成为主体,而不是他人行为的对象,我希望我的行为出于我自己理性、有意识之目的,而不是出于外来的原因”。
就积极自由来说,随着自我的不断扩张,实现自我的力量便越来越巨大,自由在此就不再是那种免于强制的状态或领域,而变成了自我控制、自我实现,是做···的自由。
关于两种自由的区分,显然没有考虑到自由不单纯是与不受外部强制有关,而且还与人的生命的自我操作有关。
关于消极自由的定义,其错误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即便是就不受强制来说,它只是谈到了外部强制,而忽视了心理动机问题,即自由与人的主观因素有关,如何克服人心理上的各种因素对于自由的制约,这是重要的从主体实现角度看,自由即使没有外在的阻碍,也可能有内在的阻碍,免于外部强制的消极自由观念,显示是表面的和粗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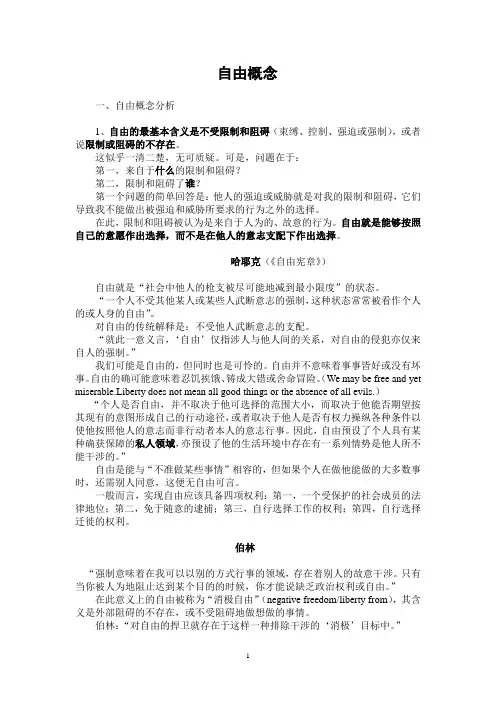
自由概念一、自由概念分析1、自由的最基本含义是不受限制和阻碍(束缚、控制、强迫或强制),或者说限制或阻碍的不存在。
这似乎一清二楚,无可质疑。
可是,问题在于:第一,来自于什么的限制和阻碍?第二,限制和阻碍了谁?第一个问题的简单回答是:他人的强迫或威胁就是对我的限制和阻碍,它们导致我不能做出被强迫和威胁所要求的行为之外的选择。
在此,限制和阻碍被认为是来自于人为的、故意的行为。
自由就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出选择,而不是在他人的意志支配下作出选择。
哈耶克(《自由宪章》)自由就是“社会中他人的枪支被尽可能地减到最小限度”的状态。
“一个人不受其他某人或某些人武断意志的强制,这种状态常常被看作个人的或人身的自由”。
对自由的传统解释是:不受他人武断意志的支配。
“就此一意义言,‘自由’仅指涉人与他人间的关系,对自由的侵犯亦仅来自人的强制。
”我们可能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是可怜的。
自由并不意味着事事皆好或没有坏事。
自由的确可能意味着忍饥挨饿、铸成大错或舍命冒险。
(We may be free and yet miserable.Liberty does not mean all good things or the absence of all evils.)“个人是否自由,并不取决于他可选择的范围大小,而取决于他能否期望按其现有的意图形成自己的行动途径,或者取决于他人是否有权力操纵各种条件以使他按照他人的意志而非行动者本人的意志行事。
因此,自由预设了个人具有某种确获保障的私人领域,亦预设了他的生活环境中存在有一系列情势是他人所不能干涉的。
”自由是能与“不准做某些事情”相容的,但如果个人在做他能做的大多数事时,还需别人同意,这便无自由可言。
一般而言,实现自由应该具备四项权利:第一,一个受保护的社会成员的法律地位;第二,免于随意的逮捕;第三,自行选择工作的权利;第四,自行选择迁徙的权利。
伯林“强制意味着在我可以以别的方式行事的领域,存在着别人的故意干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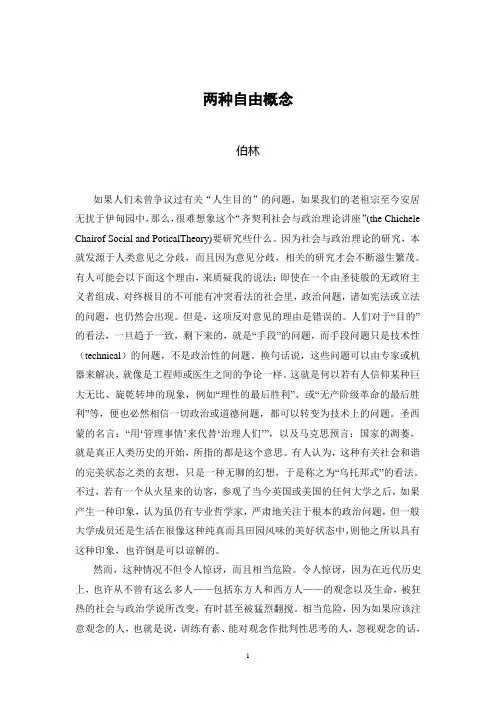
两种自由概念伯林如果人们未曾争议过有关“人生目的”的问题,如果我们的老祖宗至今安居无扰于伊甸园中,那么,很难想象这个“齐契利社会与政治理论讲座”(the Chichele Chairof Social and PoticalTheory)要研究些什么。
因为社会与政治理论的研究,本就发源于人类意见之分歧,而且因为意见分歧,相关的研究才会不断滋生繁茂。
有人可能会以下面这个理由,来质疑我的说法:即使在一个由圣徒般的无政府主义者组成、对终极目的不可能有冲突看法的社会里,政治问题,诸如宪法或立法的问题,也仍然会出现。
但是,这项反对意见的理由是错误的。
人们对于“目的”的看法,一旦趋于一致,剩下来的,就是“手段”的问题,而手段问题只是技术性(technical)的问题,不是政治性的问题。
换句话说,这些问题可以由专家或机器来解决,就像是工程师或医生之间的争论一样。
这就是何以若有人信仰某种巨大无比、旋乾转坤的现象,例如“理性的最后胜利”、或“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胜利”等,便也必然相信一切政治或道德问题,都可以转变为技术上的问题。
圣西蒙的名言:“用‘管理事情’来代替‘治理人们’”,以及马克思预言:国家的凋萎,就是真正人类历史的开始,所指的都是这个意思。
有人认为,这种有关社会和谐的完美状态之类的玄想,只是一种无聊的幻想,于是称之为“乌托邦式”的看法。
不过,若有一个从火星来的访客,参观了当今英国或美国的任何大学之后,如果产生一种印象,认为虽仍有专业哲学家,严肃地关注于根本的政治问题,但一般大学成员还是生活在很像这种纯真而具田园风味的美好状态中,则他之所以具有这种印象,也许倒是可以谅解的。
然而,这种情况不但令人惊讶,而且相当危险。
令人惊讶,因为在近代历史上,也许从不曾有这么多人——包括东方人和西方人——的观念以及生命,被狂热的社会与政治学说所改变,有时甚至被猛烈翻搅。
相当危险,因为如果应该注意观念的人,也就是说,训练有素、能对观念作批判性思考的人,忽视观念的话,观念有时候就会形成一股不受拘制的动力,对广大人群产生无可抗拒的影响力,这些力量会变得极为暴烈,不是理性批判所能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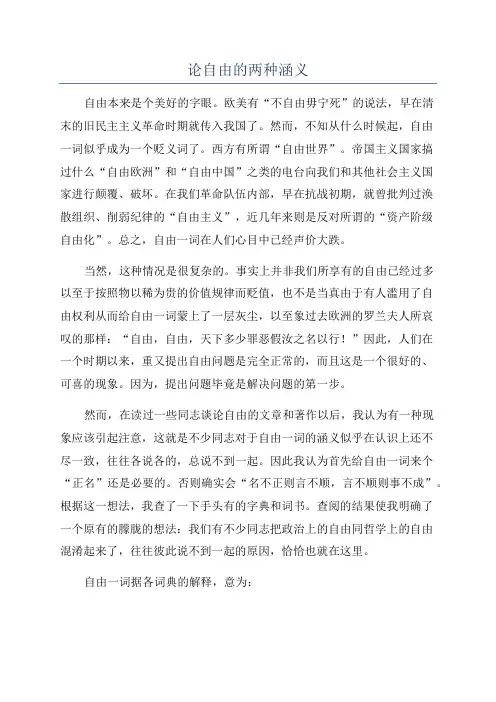
论自由的两种涵义自由本来是个美好的字眼。
欧美有“不自由毋宁死”的说法,早在清末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传入我国了。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由一词似乎成为一个贬义词了。
西方有所谓“自由世界”。
帝国主义国家搞过什么“自由欧洲”和“自由中国”之类的电台向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破坏。
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早在抗战初期,就曾批判过涣散组织、削弱纪律的“自由主义”,近几年来则是反对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总之,自由一词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声价大跌。
当然,这种情况是很复杂的。
事实上并非我们所享有的自由已经过多以至于按照物以稀为贵的价值规律而贬值,也不是当真由于有人滥用了自由权利从而给自由一词蒙上了一层灰尘,以至象过去欧洲的罗兰夫人所哀叹的那样:“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因此,人们在一个时期以来,重又提出自由问题是完全正常的,而且这是一个很好的、可喜的现象。
因为,提出问题毕竟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然而,在读过一些同志谈论自由的文章和著作以后,我认为有一种现象应该引起注意,这就是不少同志对于自由一词的涵义似乎在认识上还不尽一致,往往各说各的,总说不到一起。
因此我认为首先给自由一词来个“正名”还是必要的。
否则确实会“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根据这一想法,我查了一下手头有的字典和词书。
查阅的结果使我明确了一个原有的朦胧的想法:我们有不少同志把政治上的自由同哲学上的自由混淆起来了,往往彼此说不到一起的原因,恰恰也就在这里。
自由一词据各词典的解释,意为:一、“不受拘束,不受限制。
如自由参加,自由发表”(《现代汉语词典》)。
二、“率行己意”(《汉语词典》)。
三、“自己能做主。
古乐府《孔雀东南飞》:‘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辞海》)。
四、源出拉丁文Liberta,指从被束缚被压迫中解放出来(《法学词典》、《社会学简明词典》)。
但是接下来,在进一步解释“自由”的概念时各种词典大同小异,都是将“自由”一词分为政治上的和哲学上的两种不同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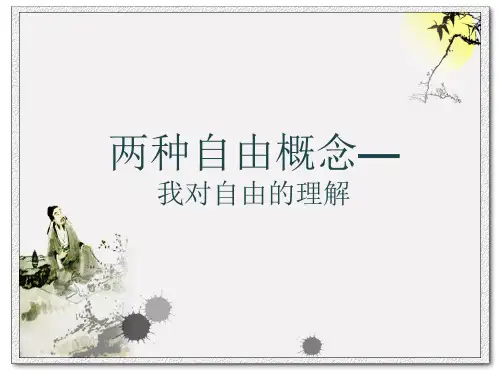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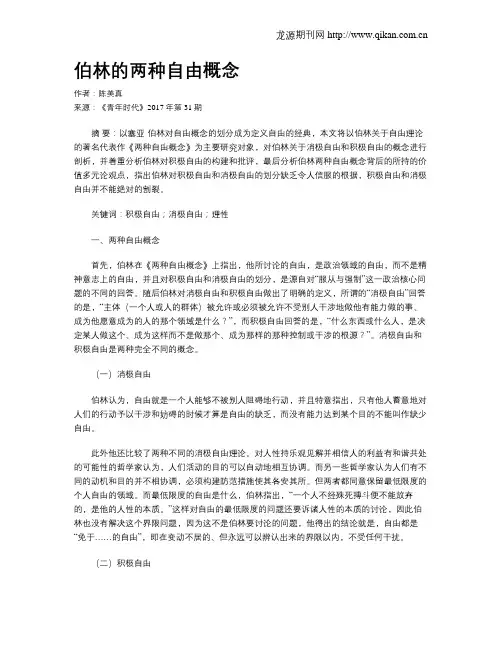
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作者:陈美真来源:《青年时代》2017年第31期摘要:以塞亚·伯林对自由概念的划分成为定义自由的经典,本文将以伯林关于自由理论的著名代表作《两种自由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伯林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进行剖析,并着重分析伯林对积极自由的构建和批评,最后分析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背后的所持的价值多元论观点,指出伯林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划分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据,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并不能绝对的割裂。
关键词:积极自由;消极自由;理性一、两种自由概念首先,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上指出,他所讨论的自由,是政治领域的自由,而不是精神意志上的自由,并且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划分,是源自对“服从与强制”这一政治核心问题的不同的回答。
随后伯林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所谓的“消极自由”回答的是,“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而积极自由回答的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
(一)消极自由伯林认为,自由就是一个人能够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并且特意指出,只有他人蓄意地对人们的行动予以干涉和妨碍的时候才算是自由的缺乏,而没有能力达到某个目的不能叫作缺少自由。
此外他还比较了两种不同的消极自由理论。
对人性持乐观见解并相信人的利益有和谐共处的可能性的哲学家认为,人们活动的目的可以自动地相互协调。
而另一些哲学家认为人们有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并不相协调,必须构建防范措施使其各安其所。
但两者都同意保留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的领域。
而最低限度的自由是什么,伯林指出,“一个人不经殊死搏斗便不能放弃的,是他的人性的本质。
”这样对自由的最低限度的问题还要诉诸人性的本质的讨论,因此伯林也没有解决这个界限问题,因为这不是伯林要讨论的问题,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自由都是“免于……的自由”,即在变动不居的、但永远可以辨认出来的界限以内,不受任何干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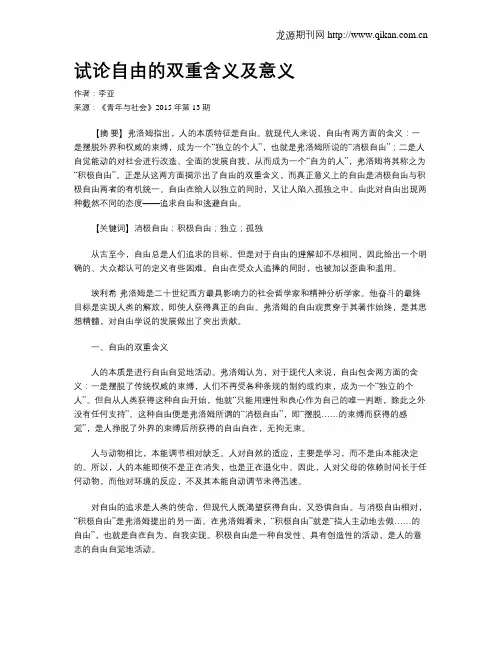
试论自由的双重含义及意义作者:李亚来源:《青年与社会》2015年第13期【摘要】弗洛姆指出,人的本质特征是自由。
就现代人来说,自由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摆脱外界和权威的束缚,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人”,也就是弗洛姆所说的“消极自由”;二是人自觉能动的对社会进行改造、全面的发展自我,从而成为一个“自为的人”,弗洛姆将其称之为“积极自由”。
正是从这两方面揭示出了自由的双重含义,而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者的有机统一。
自由在给人以独立的同时,又让人陷入孤独之中。
由此对自由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追求自由和逃避自由。
【关键词】消极自由;积极自由;独立;孤独从古至今,自由总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但是对于自由的理解却不尽相同,因此给出一个明确的、大众都认可的定义有些困难。
自由在受众人追捧的同时,也被加以歪曲和滥用。
埃利希·弗洛姆是二十世纪西方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
他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类的解放,即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
弗洛姆的自由观贯穿于其著作始终,是其思想精髓,对自由学说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自由的双重含义人的本质是进行自由自觉地活动。
弗洛姆认为,对于现代人来说,自由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摆脱了传统权威的束缚,人们不再受各种条规的制约或约束,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人”。
但自从人类获得这种自由开始,他就“只能用理性和良心作为自己的唯一判断,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支持”。
这种自由便是弗洛姆所谓的“消极自由”,即“摆脱……的束缚而获得的感觉”,是人挣脱了外界的束缚后所获得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人与动物相比,本能调节相对缺乏。
人对自然的适应,主要是学习,而不是由本能决定的。
所以,人的本能即使不是正在消失,也是正在退化中。
因此,人对父母的依赖时间长于任何动物,而他对环境的反应,不及其本能自动调节来得迅速。
对自由的追求是人类的使命,但现代人既渴望获得自由,又恐惧自由。
与消极自由相对,“积极自由”是弗洛姆提出的另一面。
自由的概述是什么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就是不由于外力,是自己作主。
那么你对自由了解多少呢?以下是由店铺整理关于什么是自由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自由的定义1、意指由宪法或根本法所保障的一种权利或自由权,能够确保人民免于遭受某一专制政权的奴役、监禁或控制,或是确保人民能获得解放。
2、任性意义的自由。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自由放任。
3、按规律办事意义下的自由,所谓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
4、自律意义下的自由。
康德在此意义上使用自由一词。
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中,对自由的定义为:“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
”——《人权宣言》第4条,1789年自由的概述自由是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
自由也是一种社会概念。
自由是社会人的权利。
与自由相对的,是奴役。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1、表达自由2、信仰自由3、免于匮乏的自由4、免于恐惧的自由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重申了这四大自由的精神。
20世纪下半时期,以赛亚·伯林开始用“两种自由”的概念来划分自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他认为,积极自由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作为主体的人做的决定和选择,均基于自身的主动意志而非任何外部力量。
当一个人是自主的或自觉的,他就处于“积极”自由的状态之中。
这种自由是“去做、、、的自由”。
而消极自由指的是在“被动”意义上的自由。
即人在意志上不受他人的强制,在行为上不受他人的干涉,也就是“免于强制和干涉”的状态。
很多人为了抵制自由观念,把自由的观念绝对化,认为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所以,他们否认自由的存在与意义。
他们提出“自由王国”的哲学定义,指的是一种绝对的自由。
而事实上,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相对的自由。
自由本来就以不侵害别人的自由的为前提,是限制的和有条件的。
但这种限制,并不意味着自由观念的无意义,相反,在限制之外,存在广阔的自由天地,这恰恰是需要保护的。
柏林的两种自由理论杨桂花1142055323 11级工业设计(3)班周二(7~9)摘要:以赛亚·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区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并批判后者而倡导前者,而是为指出众多价值之间的不可公度性,进而明确指出一元论是导致不同的自由与价值被误解的罪魁祸首。
他提出的“两种自由”观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前者是“摆脱……”的自由,后者是“成为……的”自由,伯林的这一区分对后来的自由主义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价值多元一、两种自由概念(一)消极自由概念正常的说法是,在没有其它人或群体干涉我的行动程度之内,我是自由的。
在这个意义下,政治自由只是指一个人能够不受别人阻扰而径自行动的范围。
我本来是可以去做某些事情的,但是别人却防止我去做——这个限度以内,我是不自由的;这个范围如果被别人压缩到某一个最小的限度以内,那么,我就可以说是被强制(coerced),或是被奴役(enslaved)了。
但是,强制一词无法涵盖所有“不能”的形式——例加我无法跳过英尺高;我是瞎子,所以不能阅读;或者,我无法了解黑格尔好作中比较晦涩的部分等。
如果基于以上这些理由,而说:在以上这些限度以内,我是被别人强施以压力、被别人所奴役,英国古典政治哲学家在使用“自由”这个字的时候,他们所指的,也就是上述这个意思(注三)。
自由的范围可能有多大、应该有多大,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
他们认为不能漫无限制,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人们就可以漫无界限地干涉彼此的行为;这种“自然的”(natural)自由,也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在这种混乱中,要不是人类的最低限度之需求,无法获得满足,就是弱者的自由,会被强者所剥夺。
因为他们体认到:人类诸多目的与活动,不会自动地趋于和谐,同时,无论他们信从什么学说,因为他们对其他目标,诸如正义、幸福、文化、安全、以及各种程度的平等,持有极高的评价,所以他们愿意为其它的价值,而限制自由。
两个自由的概念一、两组不同的问题对一个人施以强制,就是剥夺他的自由,问题是:剥夺他的什么自由?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个道德家都颂扬自由。
正如“幸福”、“善良”、“自然”、“实相”一样,“自由”这个名词的意义也很模糊,所以,几乎能够容纳绝大部分的解释。
我并不想去探讨这个变幻莫测的字眼的起源,也不打算去研究思想史家为它所提出来的两百多种意涵。
我所要探讨的,只是这个名词在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但却是最重要的两个意义,各自背后都包含了许多历史事件。
同时,我敢说未来也有许多历史事件,将会与这两种意义下的“自由”,发生关连,我将和前此许多人一样,把我所要探讨的第一种“自由”(freedom or liberty,我用这两个词眼来表示同一种意思)的政治意义,称为“消极的”(negative)自由;这种“消极的自由”,和针对以下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解答有关,亦即:“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第二种意义的自由,我称之为“积极的”(Positive)自由,则和以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虽然可能有重叠之处,但却显然是不同的问题。
“消极”自由的观念正常的说法是,在没有其他人或群体干涉我的行动程度之内,我是自由的。
在这个意义下,政治自由只是指一个人能够不受别人阻扰而径自行动的范围。
我本来是可以去做某些事情的,但是别人却防止我去做——这个限度以内,我是不自由的;这个范围如果被别人压缩到某一个最小的限度以内,那么,我就可以说是被强制(coerced),或是被奴役(enslaved)了。
但是,强制一词无法涵盖所有“不能”的形式——例加我无法跳过英尺高;我是瞎子,所以不能阅读;或者,我无法了解黑格尔好作中比较晦涩的部分等。
《两种自由概念》读书心得第一篇:《两种自由概念》读书心得《两种自由概念》读书心得我们今天在谈论自由的时候,一般会将其划分为两种,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而这个概念是1958年由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的演讲中正式区分的,哲学家,政治学家们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对自由的思考,当然与历史的发展有关。
我们反思自由与奴役,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反思近现代辉煌的成就,当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的文明有多脆弱,有时候总会泛起一种无力感,想改变,却不知从何做起。
1944年,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通往奴役之路》,1945年,卡尔·波普尔出版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他们都是著名的犹太学者,深受极quan主义的迫害,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是最拥护民主和自由主义的,他们信奉“看不见的手”,一直以来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忠实拥护者,只有民主,才能保证多数人不成为少数人的奴隶,才能让犹太金融财团的利益最大化,让共济hui 影响乃至操纵这个世界,而不会被元首或者暴君这样的人把别人的私有财产吞得干干净净,还要使人面临被物理消灭的惨景。
有人说,被资本奴役,不会被比被上帝奴役自由得多,然而,至少很多人都和我持同样的观点:宁愿被资本奴役,也不愿意被极权,被个人和集团永远垄断的暴力政治法律去奴役,因为,民主至少能够避免最坏的一种情况,也许它不是价值最合理的,不是结果最正义的,但它至少不会为了实现所谓的伟大目标,把反对者都物理消灭吧?伯林在文章一开始谈论目的和手段的问题时,就指出了思想观念对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并且最大的危险是它不是理性批判所能左右。
他说:“令人惊讶,因为在近代历史上,也许从不曾有这么多人——包括东方人和西方人——的观念以及生命,被狂热的社会与政治学说所改变,有时甚至被猛烈翻搅。
”纵观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历史,这句话显然深刻地展现了这样一个事实,正如伯林所言,哲学家的意识活动,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而对于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两次世界大战、意识形态冲突等事件,处处能够找到这样的影子,真实地刻画出了如此残酷的现实。
对柏林《自由论》中“两种自由概念”的反思作者:段俊沽来源:《大经贸》 2019年第1期段俊沽【摘要】柏林是二十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哲学家,其对两种自由观念的阐释,对西方传统自由理论的批判和继承,多元论价值观的整合与创新。
他对两种自由概念的提出,在当代自由主义思想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开创了新的自由主义时代。
自由概念的理解问题是自由主义基本价值观念的争论焦点之一。
【关键词】柏林自由论消极自由积极自由自由一、自由与不自由1、什么是自由。
“自由”是建构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它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受到人们的普遍的关注。
柏拉图认为,自由是理性驾驭灵魂中的激情和欲望,康德认为,自由是指意志除了道德法则以外再不依靠任何事情而言的,“自由就是自律”是康德的核心思想之一。
贡斯当界定古代的自由是指公民能够取得什么样的自由,以及个人自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赋予。
柏林最重要的贡献则在于其细致地划分与阐述了自由的概念,其最核心的含义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免于……”的消极自由,而是“去做……”的积极自由。
2、什么是不自由。
柏林认为,“消极自由”的核心含义是不存在外在干涉与强制。
“消极自由”的人可以被理解为“在不侵犯别人权利的前提下,一个人能够不被别人阻碍的行动,并且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以及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
密尔以及洛克也说到,“必须确保存在一个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的领域,否则人的自然能力将得不到正常的发挥”。
柏林在《自由论》中指出,有些人将自由与实现自由的能力相混淆。
只有当你被人为地阻止达到某个目的的时候,才能说缺乏政治权利或自由。
纯粹的没有能力达到某个目的不能叫缺乏政治自由的牺牲品。
二、柏林的自由观——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柏林在表达消极自由时,消极自由的概念就是个体自由的做他想做的事情,不被别人或别的群体的干涉,个体的行动范围和他的行动的目标不受别的力量的干涉和挤压。
消极自由强调的是选择自由,个人自由的权利需要得到国家的保障和个人的承认,国家赋予个人的权利的大小和执行程度等,社会对个人自由的接受和开化的程度等都决定了消极自由的范围。
伯林:两种自由概念(注释部分)注1:当然我并没有暗示,反过来说就是正确的。
注2:哈维修斯曾经清楚说明这一点,他说:“自由的人是不被枷锁束缚、不被囚禁的人,同时,也是不像奴隶那样,被惩罚所恐吓的人…不能像老鹰那样飞翔,或者像鲸鱼那样游泳,并不就是缺乏自由。
”注3:霍布士说:“自由的人即是能够做他想做的事,而不受到阻碍的人”;法律总是一种“锁链”,即使它使你免于其他更重要的枷锁,如某种更具压抑性的法则、习俗、或专断的专制制度、混乱状况的束缚等,也是一样。
边沁所说的内容,大抵和此相同。
注4: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大多数的思想家都相信:所有他们认为“善”的事,都互相密切地联接在一起、或至少是可以相容的——穆勒的这种想法,不过是这一种倾向的另一个例证而已。
前后不一致、至少是乖离的要素,会被人为方法束缚在一个专制的体系之下,或因为面临了共同的敌对观念,而维系在一起,这种例子,在思想史中和民族史中都屡见不鲜。
等到危险时期一过,本来彼此互相支持的观念,就会产生冲突,而这种现象,往往破坏了本来的体系,但是却为人类带来了重大的好处。
注5:请参见维利(MichelVilley)对此所做的有价值的讨论——即《权利哲学史》一书。
维氏认为“主体权利”(subjective right)的观念雏形,是奥坎所构想出来的。
注6:基督教(以及犹太教、回教)认为:神圣、自然的法则,具有绝对的权威,并且认为上帝之前,人人平等—训一信仰,和“个人有权过自己所喜欢的生活”这种信仰,是很不相同的。
注7:富有想象力、原创性的人,创造的天才、以及各式各样的“少数集团”,所受到的迫害,所感受到的压力,包括来自制度与习俗的压力,和前此以及其后的君主政体比较而言,到底是在菲特烈大帝(Fredreick the Great)时代的普鲁士(Prussia)中比较轻微呢?或者是约瑟夫二世(Josef 11)时代的奥地利,比较轻微呢?——这的确是个值得争论的问题。
两种自由概念(四)六、地位之追求在历史上,还有另外一种探究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该途径将自由和它的姊妹——平等与博爱——混淆在一起,因此也导致了同样违反自由精神的结论。
自从十八世纪末叶,人们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以来,他们就不断地质问“个人”(an individual)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质问,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得愈来愈强而有力。
只要我置身于社会,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就都无可避免地影响到别人,而且也受到别人的影响。
在审慎的检视之下,甚至连穆勒要为私生活与社会生活划一道界限的苦心,也都只能归于徒然。
事实上,穆勒的所有批评者都已经指出: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会对别人造成不利的影响。
除此之外,我是社会性的动物这一事实,所指的,也不只是我和别人之间,有互动的情形存在而已,它的意义比这还要深刻。
因为,在某一个程度而言,所谓“我是什么样的人?”,不正是别人心中所想的、所感觉的“我是什么样的人”吗?当我自问“我是什么人?”并且回答说:我是一个英国人、中国人、一个商人、一个无名小卒、一个富翁、或一个罪犯时,略经分析,我便不免发现:我之所以具有这些特性,就是代表了社会中其他的人,认为我是属于某一特殊的群体或阶级;而大多数描述某些我最具私人性、最固定的特征的词汇、也都隐含了人们对我这种“认可” (recognition)。
我并不是脱离肉体而存在的超然“理智”(reason)。
我也不是在孤岛上离群索居的鲁滨逊。
我之所以是社会的一分子,并不仅只意谓我的物质上,和别人互相依存,也不仅只意谓我之所以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社会力的影响使然而已。
更重要的是:唯有透过我所存在的那个“社会之网”(这隐喻不能作太近于真实的解释)来观察,某些我对于我自己的看法,甚至是所有我对我自己的看法,特别是我在道德上、以及社会上的认同,才可能显得有意义。
有时候,某些人、或某一群体,抱怨说他们缺乏自由,其实他们所指的,只不过是他们没有获得别人的相当“认可”而已,这种情形和真正缺乏自由的情形,一样常见。
我所追求的目标,或许并不是穆勒想要我去追求的那些目标:不被人施以强制压力,不被人无理逮捕,不受暴政威胁,不被剥夺某些行动自由,以及拥有一个我可以合法地自由行动的小天地。
同样,我所追求的,或许也不是一个合理性的社会生活计划,也不是心如止水的圣人所追求的那种“自我完美”(selLperfection)。
我所要追求的,或许根本只是不要被人忽视、不要被人保护、不要被人轻蔑,或不要被人把我的大多数想法,看做是“理所当然”而已——简而言之,我不愿意别人只把我看作—个个体、而不完全承认我的独特性,我不愿意被当做是某种不具特色的、集合体中的一个成员,或是被当做一个统计单位,而没有属于我自己的、明显可辨的人性特色和目的。
我所要反抗的,就是这种贬抑我的人格的行为,我奋力以求的,并不是“法律上权利的平等”,也不是能够“依己意行事”的自由,虽然我也可能需要这些自由;我奋力以求的,往往是希望能达到这么一个境界:在这个境界上,我能感觉到自己是负得起责任的行为者,因为别人承认我就是这样的行为者,我的意愿会被别人考虑到,因为我有权具有这些意愿;若能如此,即使因为我是如我这个样子的人,或因为我做了我所做的选择,而被别人攻击、被人迫害,我也在所不惜。
这是一种对“地位”与“被人认可”的热切期望:“英国最贫穷的小子也和最伟大的人一样,有属于他自己的生活”。
我渴望被人了解、被人认可,即使因此而不受人欢迎、甚至受人唾弃,也无所谓。
而能够给我这种认可,从而让我觉得“我是个有分量的人”,却只是与我属于同一社会的成员,而从历史上、道德上、经济上、甚或伦理上说来,这个社会也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从属于它的社会。
(注19)我那个别的“自我”,并不是某种可以从我和别人的关系中点,脱离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可以从我的某些特征中分离出来的东西;而这些特征,主要也是由别人对我的态度,所构成的。
因此举例而言,当我要求摆脱政治上、及社会上的依赖性时,我所要求的,其实是希望别人能够改变他们对我的态度,因为,这些人的意见和行为,助使我决定了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看法。
以上这些对个人而言为真确的道理,对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性等群体而言,也同样真确,因为这些群体,都是由具有自觉的需求和目标的个人所组成的。
被压迫的阶级、或国家,所要求的,通常并不是纯粹能使其成员依照自己的意思而行动的自由,也不是社会与经济机会的平等;更不是要在一个有理性的立法者所设计出来的、毫无冲突的有机状态之中,取得一席之地。
被压迫的阶级或国家,往往要求别对它们的阶级、国家、肤色,或种族给予一种认可,承认它们是一个独立的活动根源,是一个具有自我意志的团体,也是一个想要依照自我意志而行动的团体(至于这意志是否良善、是否合法,是另——回事);它们不希望被人统治、被人施以教育、或被人指导行事,无论这种统治、教育、或指导的行为,是如何轻微,它们都不以为然,因为那种做法是不尽合乎人性的,因此也就不尽是自由的。
这样的说明,要比康德那种纯粹理性者的说法:“家长保护主义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大专制”,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家长保护主义”之所以专制,原因并不是由于它比赤裸裸的、残酷的、昏庸的暴政,更具压迫性,也不只是由于它忽略了融于我内心的那种“超越的理性”(the transcendental reason),而是因是它对下述概念构成了侮辱,这概念即是:我作为一个人,有权利决心按照我自己的目的去生活,这目的未必是合理的、或有益的,但毕竞是我自己的目的,尤其重要的是,别人也应承认我有如此生活的权利。
因为,如果没有得到这样的认可的话,我就可能无法承认自己的地位,我就可能会怀疑“我是一个绝对独立的人”这样的主张,是否真实。
因为,“我是怎样的人”,大部分是取决于我的感觉、和我的想法;而我的感觉和想法如何,则取决于我所从属的那个社会中,一般人所有的感觉和想法。
照柏克的意思来说,我并不是这个社会中可以独立存在的一个原子,而是一种社会模式中的组合成分——这个譬喻很具危险性,但是却是不可少的。
在不被人承认我是能够自我主宰的个人情况下,我可能会觉得不自由,但是作为一个没有被人完全承认、没有获得人们充分尊重的团体中的一分子,我同样也会感到不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希望能够脱离我的整体阶级、社团、国家、种族、或职业团体。
有时候,这种追求地位的欲望,会变得非常强烈,以致于我宁可被我自己的种族、或社会阶级中的某些人羞辱,或施以不当的统治,因为他们虽然苛待了我,但是,他们至少是把我当做一个“人”、一个“竞争者”、一个“地位相等的人”(an equal)来看待;我宁可如此,而不愿意被某些较高级、或较疏远的群体中的人物,以善意和容忍的态度相待,因为这些人物不承认我是我心目中的我。
当今,许多个体与群体,以及各种职业团体、阶级、国家、与种族,强烈呐喊要求“被承认”,最主要的追求,也就正是这一点。
我从我所属的社会成员的手上,虽然可能得不到“消极” 的自由,然而,他们毕竟是我从属社会中的一分子;他们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们;这种了解,就可以让我在我的内心感觉到,我是一个“有分量的人”。
如今,在大多数权威型的民主国家(au thoritarian democracies)中,人民有时宁可有意识地选择被他们自己的成员统治,而不愿意被最开明的寡头政府统治,其原因便是这种得到“互相认可’’(reciprocal recognition)的欲望;某些新近获得独立的亚非国家人民,当他们被某些小心、公正、温雅而善意的外来官员统治时,怨言不少,而当他们被自己族内、或国内的人物,用极粗鲁的方式来治理时,却反而较少抱怨,其原因,有时也是由于有这种扩求“互相认可”的欲望存在的关系。
除非对这种现象有所了解。
否则,那些失去穆勒所说的基本人权的整个民族,它们的理想与行为,便会成为不可理解的矛盾现象。
事实上,这些民族虽然丧失了穆勒所说的基本人权,但是却能绝对诚恳地表示说: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所享有的自由,反而比广泛地拥有此类人权时为多。
然而,我们却不能轻易认为,这种追求“地位”与“认可”的欲望,就是追求“消极的”、或“积极的”个人自由的欲望。
这种欲望和自由同样是人类所深切需要、并热烈为其而战的东西,它和自由相似,但是它本身却不是自由;它虽然隐含了整个群体的“消极”自由之意涵,却和团结、博爱、互谅、以平等方式结合的需求等,更为接近,而所有这些观念,有时都被称为社会自由(socialfreedom),虽然这种称呼,有时也会令人产生误解。
社会性与政治性的用语,必然都是模糊不清的。
有时候,我们想要使政治语汇变得更加精确,结果却反而使它们变得失去作用。
可是,对于各种语汇的用法采取太过松懈的态度,却也对真理无益。
无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自由概念,其本质都是对某些东西、或某些外人的拒斥,例如拒斥非法侵入我的领域之人,或是拒斥声称对我拥有权威的人;或是拒斥萦绕于怀的欲望、恐惧、心理症、非理性力量等,总之,是拒斥各种各样的侵扰者或专制者。
至于追求“被认可”的欲望,却是一种不同的欲望,它追求灵性的结合、更密切的了解、利益的契合,以及一种彼此共同依存、共同为某些事理而牺牲的生活。
人类在臣服于寡头统治、或独裁者的权威之时,却会认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获得解放了,究其原因,只有一种可能,那便是把追求自由的欲望,和以上所提到的这种深刻的、普遍的对“地位”与“了解”之渴求,混淆在一起,然后又把追求自由的欲望,当做是追求“社会的自我导向”(social self—direction)的缘故。
而在这种情况下,获得解放的“自我”,其实不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
社会群体对其成员的控制与约束,已经不是一种允许个体自由活动的“自我约束”、或要求个体自动自发的“自我控制”;把这种社会群体,当做纯粹是诸多个人与诸多“自我”,是一种谬误的观念,关于这种谬误观念,已有许多人撰文论及。
然而,即使是从“有机的”(organic)观点来看,我们把“被认可”与“地位”的需求,看做是某种第三种意义下的“自由”需求,是否合适?是否有价值?也不无值得商榷之处。
人类向某一群体要求“认可”,则这个群体本身,也应当具有相当程度的“消极”自由,即:不受外来权威的控制,否则,它的认可,也无法使追求这种认可的人,得到他所需要的“地位”。
但是,我们可以把追求更高地位的努力,亦即摆脱卑贱地位的期望,称作“为自由而奋斗”吗?如果把“自由”一字的意义,限制在我们以上讨论的意义之下,岂非纯粹是一种迂腐焙学的做法?或者,如我所怀疑的:我们不是在冒着一种危险,把任何一种社会情况的改进,都称为是“自由的增加”,这样做,不是反而会使“自由”这个字的意义扩张无度,变得模糊,从而使它在实际上,变得根本毫无意义可言?然而,我们却不能把这个情况,又当做是“自由”的观念,与“地位”、“团结”、“博爱”、“平等”的观念,或某种此类观念的结合体之间的混淆,就含糊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