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与盛唐诗歌的经典化诗歌的
- 格式:rtf
- 大小:148.65 KB
- 文档页数: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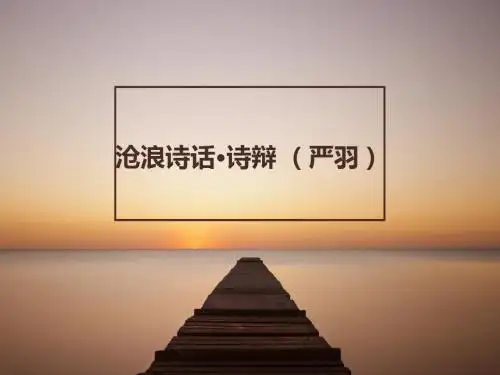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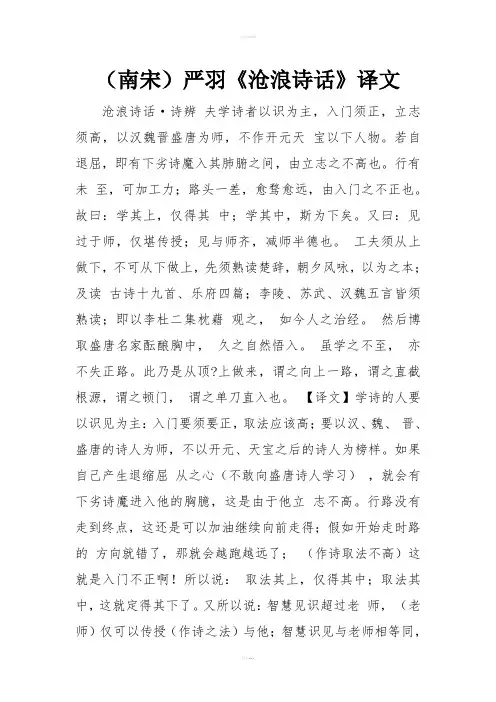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译文沧浪诗话·诗辨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
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
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
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
又曰: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
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风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
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
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
此乃是从顶?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
【译文】学诗的人要以识见为主:入门要须要正,取法应该高;要以汉、魏、晋、盛唐的诗人为师,不以开元、天宝之后的诗人为榜样。
如果自己产生退缩屈从之心(不敢向盛唐诗人学习),就会有下劣诗魔进入他的胸臆,这是由于他立志不高。
行路没有走到终点,这还是可以加油继续向前走得;假如开始走时路的方向就错了,那就会越跑越远了;(作诗取法不高)这就是入门不正啊!所以说:取法其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这就定得其下了。
又所以说:智慧见识超过老师,(老师)仅可以传授(作诗之法)与他;智慧识见与老师相等同,(他所接受于老师的)就要减少到老师的一半了。
学诗的工夫要从学习最好的作品开始,而不可从低下的作品学起。
先要熟读《楚辞》,朝夕诵读吟咏,以作为学诗之根本;下及《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诗和汉魏五言古诗都必须熟读;再将李白、杜甫的诗集反复研读,好像现在的人研治经书那样,然后广泛吸取盛唐名家诗之精华,酝酿于胸中,时间长了就自然深入领悟(作诗的奥妙)了。
这样,虽然未必达到(学诗的)最高境界,也不会失去(学诗的)正路。
这就是(佛教禅宗所说的)从顶门上做起,可以说是向上的门路,可以说是直接寻求到根本,可以说是顿入了法门,可以说单刀直入之法。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对唐诗的品评作者:黄梦来源:《科学与财富》2017年第30期摘要:《沧浪诗话》是严羽所著的关于诗的理论著作,是整个两宋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
其共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篇。
其中“诗辨”阐述理论观点,是整个《沧浪诗话》的总纲;“诗体”主要探讨诗歌的体制、风格、流派;“诗法”研究诗歌的写作方法;“诗评”是严羽的批评实践,呈现的是其作为整个《沧浪诗话》总纲“诗辨”中的众多诗学观念,评论历代诗人诗作,从各方面展开基本观点。
而“考证”对一些诗篇的文字、篇章、写作年代和撰人进行考辨,相对其他四篇来说,“考证”较为琐碎,偶尔也反映作者的一些文学观念、文学思想。
本文主要研究《沧浪诗话?诗评》中对唐诗的品评,其中涉及具体作品、作者等等。
关键词:《沧浪诗话》;诗评;唐诗纵观当今学界对严羽《沧浪诗话》的研究,一般侧重于“别材”、“别趣”、“妙悟”、“以禅喻诗”等理论的研究,对“诗评”中的具体批评实践涉及较少,事实上,“诗评”中的批评方法和批评标准等,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了解严羽的诗学理论诗具有很重要的价值的。
下面我们就从《沧浪诗话·诗评》中有关唐诗的内容来阐述我的观点。
《沧浪诗话·诗评》是严羽对诗歌史和文人诗歌创作的具体批评,其中主要涉及诗歌的时代特点、风格及风格的变化、作者人格及具体创作等一系列问题,总共有五十则。
对于唐诗的品评共计有三十一则,分别是(以下原文都选自严羽《沧浪诗话》中华书局2014年版):一、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本朝诸公,分明别是一副言语。
如是此,方许具一只眼。
二、盛唐人,有似粗而非粗处,有似拙而非拙处。
三、五言绝句: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韩退之是一样,王荆公是一样,本朝诸公是一样。
四、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人诗,已有一二可入盛堂者,要当论其大概耳。
五、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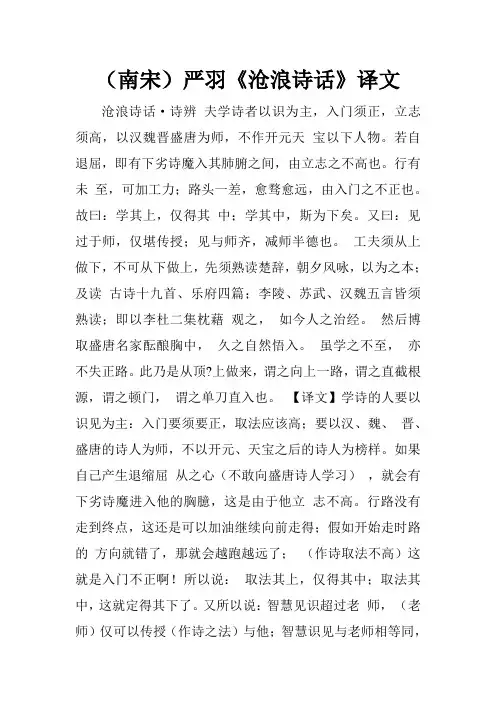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译文沧浪诗话·诗辨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
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
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
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
又曰: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
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风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
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
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
此乃是从顶?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
【译文】学诗的人要以识见为主:入门要须要正,取法应该高;要以汉、魏、晋、盛唐的诗人为师,不以开元、天宝之后的诗人为榜样。
如果自己产生退缩屈从之心(不敢向盛唐诗人学习),就会有下劣诗魔进入他的胸臆,这是由于他立志不高。
行路没有走到终点,这还是可以加油继续向前走得;假如开始走时路的方向就错了,那就会越跑越远了;(作诗取法不高)这就是入门不正啊!所以说:取法其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这就定得其下了。
又所以说:智慧见识超过老师,(老师)仅可以传授(作诗之法)与他;智慧识见与老师相等同,(他所接受于老师的)就要减少到老师的一半了。
学诗的工夫要从学习最好的作品开始,而不可从低下的作品学起。
先要熟读《楚辞》,朝夕诵读吟咏,以作为学诗之根本;下及《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诗和汉魏五言古诗都必须熟读;再将李白、杜甫的诗集反复研读,好像现在的人研治经书那样,然后广泛吸取盛唐名家诗之精华,酝酿于胸中,时间长了就自然深入领悟(作诗的奥妙)了。
这样,虽然未必达到(学诗的)最高境界,也不会失去(学诗的)正路。
这就是(佛教禅宗所说的)从顶门上做起,可以说是向上的门路,可以说是直接寻求到根本,可以说是顿入了法门,可以说单刀直入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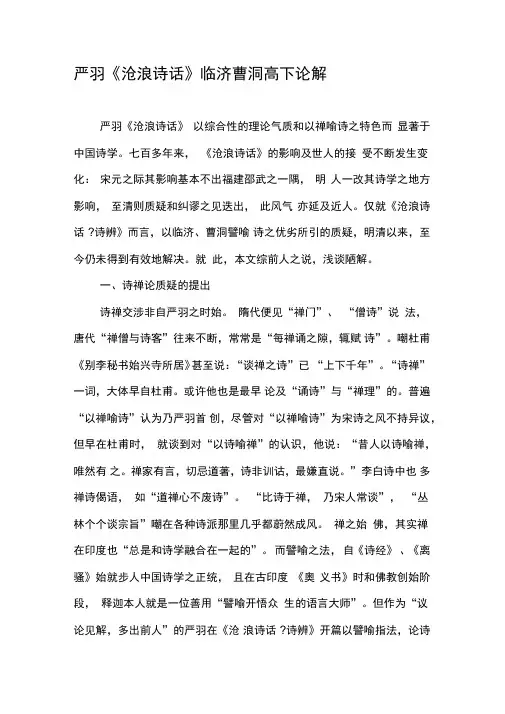
严羽《沧浪诗话》临济曹洞高下论解严羽《沧浪诗话》以综合性的理论气质和以禅喻诗之特色而显著于中国诗学。
七百多年来,《沧浪诗话》的影响及世人的接受不断发生变化:宋元之际其影响基本不出福建邵武之一隅,明人一改其诗学之地方影响,至清则质疑和纠谬之见迭出,此风气亦延及近人。
仅就《沧浪诗话?诗辨》而言,以临济、曹洞譬喻诗之优劣所引的质疑,明清以来,至今仍未得到有效地解决。
就此,本文综前人之说,浅谈陋解。
一、诗禅论质疑的提出诗禅交涉非自严羽之时始。
隋代便见“禅门”、“僧诗”说法,唐代“禅僧与诗客”往来不断,常常是“每禅诵之隙,辄赋诗”。
嘲杜甫《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甚至说:“谈禅之诗”已“上下千年”。
“诗禅”一词,大体早自杜甫。
或许他也是最早论及“诵诗”与“禅理”的。
普遍“以禅喻诗”认为乃严羽首创,尽管对“以禅喻诗”为宋诗之风不持异议,但早在杜甫时,就谈到对“以诗喻禅”的认识,他说:“昔人以诗喻禅,唯然有之。
禅家有言,切忌道著,诗非训诂,最嫌直说。
”李白诗中也多禅诗偈语,如“道禅心不废诗”。
“比诗于禅,乃宋人常谈”,“丛林个个谈宗旨”嘲在各种诗派那里几乎都蔚然成风。
禅之始佛,其实禅在印度也“总是和诗学融合在一起的”。
而譬喻之法,自《诗经》、《离骚》始就步人中国诗学之正统,且在古印度《奥义书》时和佛教创始阶段,释迦本人就是一位善用“譬喻开悟众生的语言大师”。
但作为“议论见解,多出前人”的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开篇以譬喻指法,论诗禅之关系时却在明清招来了不少非议。
《诗辨》云:“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
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
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
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林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
……”李维桢质疑“论禅则非。
临济、曹洞有何高下?”。
陈继儒发问“此老以禅喻诗,瞳目霄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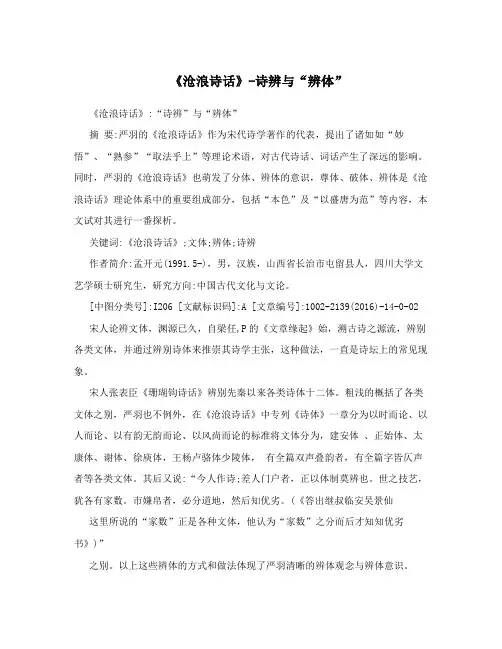
《沧浪诗话》-诗辨与“辨体”《沧浪诗话》:“诗辨”与“辨体”摘要:严羽的《沧浪诗话》作为宋代诗学著作的代表,提出了诸如如“妙悟”、“熟参”“取法乎上”等理论术语,对古代诗话、词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严羽的《沧浪诗话》也萌发了分体、辨体的意识,尊体、破体、辨体是《沧浪诗话》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本色”及“以盛唐为范”等内容,本文试对其进行一番探析。
关键词:《沧浪诗话》;文体;辨体;诗辨作者简介:孟开元(1991.5-),男,汉族,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县人,四川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2 宋人论辨文体,渊源已久,自梁任,P的《文章缘起》始,溯古诗之源流,辨别各类文体,并通过辨别诗体来推崇其诗学主张,这种做法,一直是诗坛上的常见现象。
宋人张表臣《珊瑚钩诗话》辨别先秦以来各类诗体十二体。
粗浅的概括了各类文体之别,严羽也不例外,在《沧浪诗话》中专列《诗体》一章分为以时而论、以人而论、以有韵无韵而论、以风尚而论的标准将文体分为,建安体、正始体、太康体、谢体、徐庾体,王杨卢骆体少陵体,有全篇双声叠韵者,有全篇字皆仄声者等各类文体。
其后又说:“今人作诗;差人门户者,正以体制莫辨也。
世之技艺,犹各有家数。
市嫌帛者,必分道地,然后知优劣。
(《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这里所说的“家数”正是各种文体,他认为“家数”之分而后才知知优劣书》)”之别。
以上这些辨体的方式和做法体现了严羽清晰的辨体观念与辨体意识。
一、“辨体”的含义在宋代一直就有“文章以体制为先”[1]的说法,至于何谓“辨体”,《文体明辨》徐师曾认为,“辨体”是随着文章学的发展,而发生的:“盖自秦汉而下,文愈盛;文愈,故类愈增。
(《文体明辨自序》)”[2]明人徐师曾认为,辨体即“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经典作品的辨析,溯清各类文体、风格、体貌的分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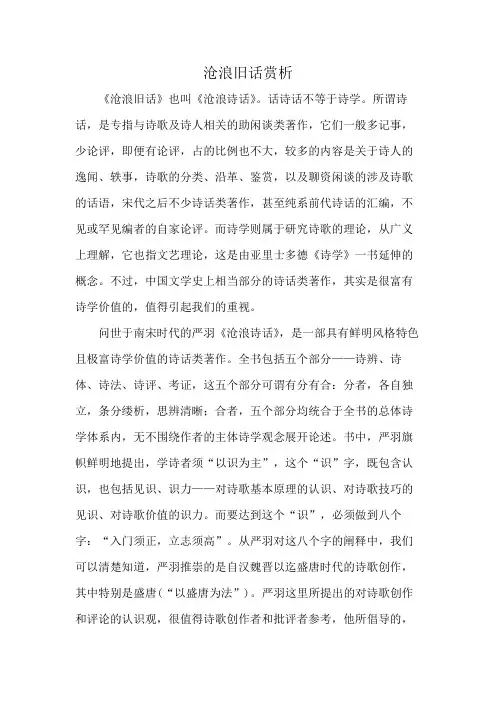
沧浪旧话赏析
《沧浪旧话》也叫《沧浪诗话》。
话诗话不等于诗学。
所谓诗话,是专指与诗歌及诗人相关的助闲谈类著作,它们一般多记事,少论评,即便有论评,占的比例也不大,较多的内容是关于诗人的逸闻、轶事,诗歌的分类、沿革、鉴赏,以及聊资闲谈的涉及诗歌的话语,宋代之后不少诗话类著作,甚至纯系前代诗话的汇编,不见或罕见编者的自家论评。
而诗学则属于研究诗歌的理论,从广义上理解,它也指文艺理论,这是由亚里士多德《诗学》一书延伸的概念。
不过,中国文学史上相当部分的诗话类著作,其实是很富有诗学价值的,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问世于南宋时代的严羽《沧浪诗话》,是一部具有鲜明风格特色且极富诗学价值的诗话类著作。
全书包括五个部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这五个部分可谓有分有合:分者,各自独立,条分缕析,思辨清晰;合者,五个部分均统合于全书的总体诗学体系内,无不围绕作者的主体诗学观念展开论述。
书中,严羽旗帜鲜明地提出,学诗者须“以识为主”,这个“识”字,既包含认识,也包括见识、识力——对诗歌基本原理的认识、对诗歌技巧的见识、对诗歌价值的识力。
而要达到这个“识”,必须做到八个字:“入门须正,立志须高”。
从严羽对这八个字的阐释中,我们可以清楚知道,严羽推崇的是自汉魏晋以迄盛唐时代的诗歌创作,其中特别是盛唐(“以盛唐为法”)。
严羽这里所提出的对诗歌创作和评论的认识观,很值得诗歌创作者和批评者参考,他所倡导的,
是他认为的诗歌发展的正道,这包括了楚辞、古诗十九首、乐府诗、汉魏五言诗等在内的整个这一路的诗歌,其中既有楚辞,也同时包含了古诗十九首、乐府诗、汉魏五言诗,以及杜诗等作品,它们所反映表现的内容及其艺术风格,与《诗经》的一脉相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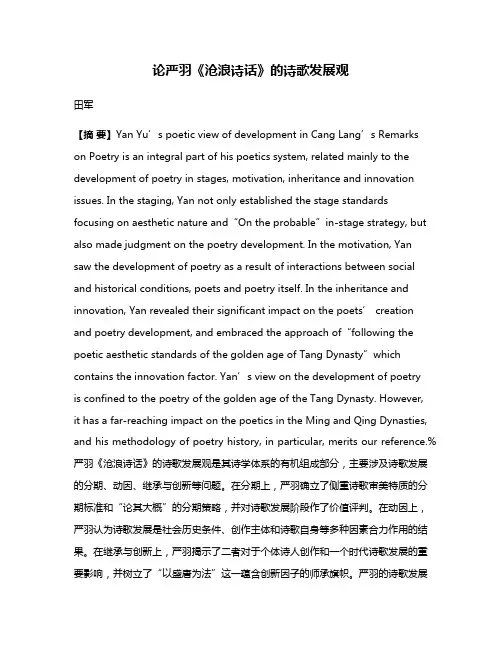
论严羽《沧浪诗话》的诗歌发展观田军【摘要】Yan Yu’s poetic view of development in Cang Lang’s Remarkson Poetry is an integral part of his poetics system, related main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in stages, motivatio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ssues. In the staging, Yan not only established the stage standards focusing on aesthetic nature and“On the probable”in-stage strategy, but also made judgment on the poetry development. In the motivation, Yan saw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as a result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poets and poetry itself. In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Yan revealed their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oets’ creation and poetry development, and embraced the approach of“following the poetic aesthetic standards of the gold en age of Tang Dynasty”which contains the innovation factor. Yan’s view on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is confined to the poetry of the golden age of the Tang Dynasty. However,it has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poetic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his methodology of poetry history, in particular, merits our reference.% 严羽《沧浪诗话》的诗歌发展观是其诗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要涉及诗歌发展的分期、动因、继承与创新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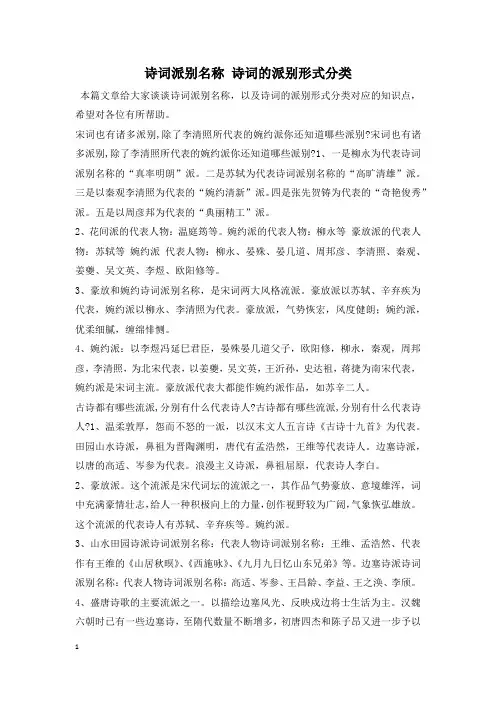
诗词派别名称诗词的派别形式分类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诗词派别名称,以及诗词的派别形式分类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宋词也有诸多派别,除了李清照所代表的婉约派你还知道哪些派别?宋词也有诸多派别,除了李清照所代表的婉约派你还知道哪些派别?1、一是柳永为代表诗词派别名称的“真率明朗”派。
二是苏轼为代表诗词派别名称的“高旷清雄”派。
三是以秦观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清新”派。
四是张先贺铸为代表的“奇艳俊秀”派。
五是以周彦邦为代表的“典丽精工”派。
2、花间派的代表人物:温庭筠等。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柳永等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轼等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晏殊、晏几道、周邦彦、李清照、秦观、姜夔、吴文英、李煜、欧阳修等。
3、豪放和婉约诗词派别名称,是宋词两大风格流派。
豪放派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婉约派以柳永、李清照为代表。
豪放派,气势恢宏,风度健朗;婉约派,优柔细腻,缠绵悱恻。
4、婉约派:以李煜冯延巳君臣,晏殊晏几道父子,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为北宋代表,以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史达祖,蒋捷为南宋代表,婉约派是宋词主流。
豪放派代表大都能作婉约派作品,如苏辛二人。
古诗都有哪些流派,分别有什么代表诗人?古诗都有哪些流派,分别有什么代表诗人?1、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一派,以汉末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为代表。
田园山水诗派,鼻祖为晋陶渊明,唐代有孟浩然,王维等代表诗人。
边塞诗派,以唐的高适、岑参为代表。
浪漫主义诗派,鼻祖屈原,代表诗人李白。
2、豪放派。
这个流派是宋代词坛的流派之一,其作品气势豪放、意境雄浑,词中充满豪情壮志,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
这个流派的代表诗人有苏轼、辛弃疾等。
婉约派。
3、山水田园诗派诗词派别名称:代表人物诗词派别名称:王维、孟浩然、代表作有王维的《山居秋暝》、《西施咏》、《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
边塞诗派诗词派别名称:代表人物诗词派别名称: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益、王之涣、李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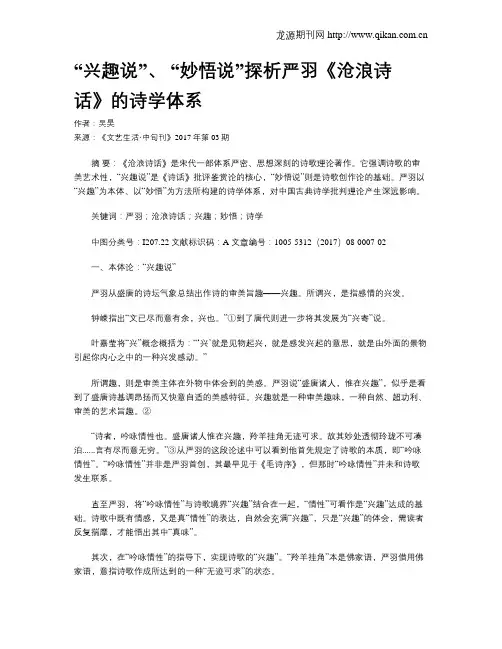
“兴趣说”、“妙悟说”探析严羽《沧浪诗话》的诗学体系作者:吴昊来源:《文艺生活·中旬刊》2017年第03期摘要:《沧浪诗话》是宋代一部体系严密、思想深刻的诗歌理论著作。
它强调诗歌的审美艺术性,“兴趣说”是《诗话》批评鉴赏论的核心,“妙悟说”则是诗歌创作论的基础。
严羽以“兴趣”为本体、以“妙悟”为方法所构建的诗学体系,对中国古典诗学批判理论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严羽;沧浪诗话;兴趣;妙悟;诗学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08-0007-02一、本体论:“兴趣说”严羽从盛唐的诗坛气象总结出作诗的审美旨趣——兴趣。
所谓兴,是指感情的兴发。
钟嵘指出“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
”①到了唐代则进一步将其发展为“兴寄”说。
叶嘉莹将“兴”概念概括为:“‘兴’就是见物起兴,就是感发兴起的意思,就是由外面的景物引起你内心之中的一种兴发感动。
”所谓趣,则是审美主体在外物中体会到的美感。
严羽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似乎是看到了盛唐诗基调昂扬而又快意自适的美感特征。
兴趣就是一种审美趣味,一种自然、超功利、审美的艺术旨趣。
②“诗者,吟咏情性也。
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言有尽而意无穷。
”③从严羽的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到他首先规定了诗歌的本质,即“吟咏情性”。
“吟咏情性”并非是严羽首创,其最早见于《毛诗序》,但那时“吟咏情性”并未和诗歌发生联系。
直至严羽,将“吟咏情性”与诗歌境界“兴趣”结合在一起,“情性”可看作是“兴趣”达成的基础。
诗歌中既有情感,又是真“情性”的表达,自然会充满“兴趣”,只是“兴趣”的体会,需读者反复揣摩,才能悟出其中“真味”。
其次,在“吟咏情性”的指导下,实现诗歌的“兴趣”。
“羚羊挂角”本是佛家语,严羽借用佛家语,意指诗歌作成所达到的一种“无迹可求”的状态。
何谓“无迹可求”?“诗有词、理、意兴。
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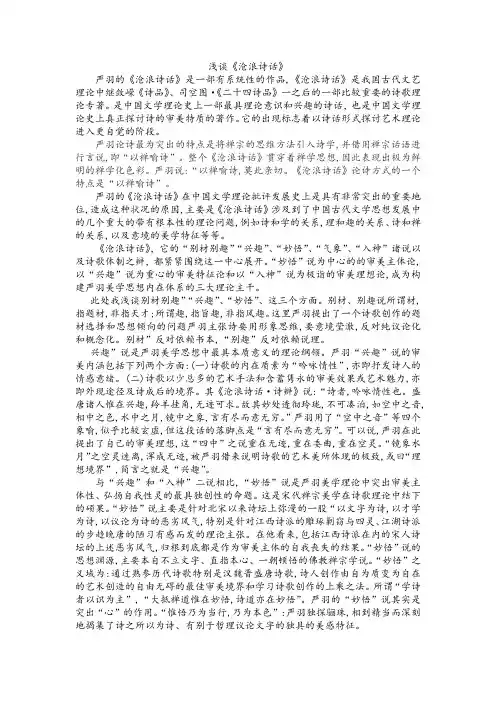
论严羽的盛唐诗歌观丁志超【摘要】严羽在《沦浪诗话》中,反复强调以盛唐为师,标举盛唐诗为第一义,以盛唐诗为评价诗歌的标准,高度推崇盛唐诗人,“盛唐诗”成为严羽论诗的核心.然而,严羽眼中的“盛唐诗”深深地带有其个人诗论色彩,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特殊性.严羽的盛唐诗歌观与其诗学旨趣密不可分,给后世带来深远的影响.【期刊名称】《合肥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33)001【总页数】5页(P73-77)【关键词】严羽;沧浪诗话;盛唐诗【作者】丁志超【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以盛唐为宗,把盛唐诗提高到极高的地位。
他提出将唐诗“以时而论”分为”唐初、盛唐、大历、元和和晚唐”,直接影响了后世的“四唐说”。
他反复强调以盛唐为法,号召学诗者应以盛唐为师。
严羽似乎是推崇盛唐气象的诗歌风格,实际上,他的“盛唐说”有其内在丰富的诗学旨趣,体现在他对盛唐时限的模糊表述、诗人的选择、盛唐诗风的概括上,他都不只是将盛唐诗作为一个时期的诗歌加以推崇,而是和他的诗论主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严羽的“盛唐诗歌观”并不孤立在他的诗歌体系之外,他提出“盛唐说”也带有其时代的背景和个人的倾向。
严羽极其推崇盛唐诗,以盛唐诗为“第一义”,号召学诗者从盛唐入手。
《诗辨》云:“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
”又说,“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
”又说,“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
”严羽将汉魏晋与盛唐并举,共尊为“第一义”,认为是学诗者的楷模。
然而,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到“盛唐”或”唐诗”的次数远远超过“汉魏晋之诗”,他将汉魏晋和盛唐并举,其实却是尊古扬今、借古述今的笔法;看似尊崇汉魏,其实号召大家更应该学习的是盛唐。
何以见之?严羽论诗,以“悟”字为本。
事实上,严羽在《诗辩》的开篇以“禅家者流”等数语表明“以禅喻诗”的基本态度之后,他就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评价诗人又说“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实将”妙悟“拔高到其诗学理论核心的地位,是论诗的标准。
“以盛唐为法”与民族审美认同孙蓉蓉内容提要 “以盛唐为法”是《沧浪诗话》中的一个理论。严羽提出“以盛唐为法”,
是因为盛唐的诗歌符合其“诗的宗旨”,并且盛唐诗歌的“雄壮”、“浑厚”还寄托着他自己的审美理想。从殷始经司空图到严羽,都将“盛唐”诗歌作为典范,从而形成了一个宗奉“盛唐”的民族审美认同。然而,严羽的“以盛唐为法”一说,引起了后人较多的争议,被认为是开启了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实际上,明代文学上的复古思潮是在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形成的,它有着复杂的内涵,其中包含有对民族审美认同的问题。
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是我国文论史上的一部影响深远的诗论著作,《沧浪诗话》中提出的系列理论,如“别材别趣”说、“兴趣”说、“妙悟”说和“以盛唐为法”说等等,提高和发展了我国古代以审美论诗的理论,建立了一套同儒家诗论相抗衡的理论体系。严羽提出“以盛唐为法”,是因为盛唐诗歌符合其作诗的宗旨,寄托了他的审美理想,体现出他对民族审美的认同。然而,“以盛唐为法”的提出,却引起了后人较多的争议,被认为是明代前后七子“诗必盛唐”说的先声,于是“以盛唐为法”就成为了一种复古主义的理论主张。那么,严羽为何要提出“以盛唐为法”,其理论内涵是什么,它与“诗必盛唐”说有何关系,在“复古”的背后又隐含有什么样的理论问题,本文欲对此作一研究和探讨,以期对“以盛唐为法”及其与民族审美关系的问题有一正确的认识。一 “以盛唐为法”的提出“以盛唐为法”是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篇中提出的理论,它与“别材别趣”说等其他理论共同构成了严羽的诗论体系。“以盛唐为法”的提出,不仅是因为盛唐诗歌符合严羽的“诗的宗旨”,而且盛唐诗歌的“笔力雄壮”和“气象浑厚”体现出了严羽的审美理想。“以盛唐为法”是《沧浪诗话》诗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诗辨》篇提出:“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①将盛唐诗作为诗歌的最高典范,提出“以盛唐为法”,这是严羽诗论的重要观点之一。《沧浪诗话》的著述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对于宋代诗歌中存在的“尚理而病于意兴”(《诗评》)的问题,严羽认为有必要“诗辨”,即辨析、辨明诗歌的性质和特点。因此,《沧浪诗话》首先提出了“别材别趣”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辨》)。所谓“别材”,指诗歌具有自己特殊的题材,即“诗者,吟咏情性也”(《诗辨》),而不是像一般著作研究学问或传授知识的。所谓“别趣”,又是指诗歌具有特殊的旨趣,它不是以阐明道理为目的,而是像“盛唐诸人,惟在兴趣”(《诗辨》)那样,他们的诗作深得“别趣”的要旨,从自己的“兴趣”即审美感受出发,它给予读者的也是一种审美体验和审美享受。因而这样诗作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诗辨》),它是一个完整的、浑融的整体,而不是条目式的机械组合。严羽提出“别材别趣”说时,特别以“盛唐诸人”作为例证加以说明和强调,即“盛唐诸人,惟在兴趣”。而与之相反的是“近代诸公”,他们“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诗辨》),
论《沧浪诗话》与“以禅喻诗”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文学批评特别是诗学批评的代表作。
严羽的诗歌理论是针对宋诗中的江西诗派提出来的,自己也以“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诗辨》)自诩。
全书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门,卷末附有《与吴景仙论诗书》一文,以第一部分为核心。
其中以禅论诗、妙悟之论、别材别趣之说、兴趣、气象之说等是严氏主要的诗歌理论。
“以禅喻诗”是严氏诗论最重要的观点,“妙悟”又是“以禅喻诗”的核心。
标签:严羽;以禅喻诗诗话,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论诗之体,它始创于欧阳修,而后历经数代,到清发展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主要形式。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著作,如继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之后,南宋又有张戎的《岁寒堂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钱钟书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将后三者定位为“鼎足”之三者。
其中《沧浪诗话》它集宋代诗学研究之大成,是“宋代诗话的压轴之作,也是宋代文学批评特别是诗学批评的代表作,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沧浪诗话》全书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门,卷末附有《与吴景仙论诗书》一文,以第一部分为核心。
严羽论诗立足于它“吟咏性情”的基本性质,《福建文苑传》亦以“扫除美刺,独任性灵”总括严氏诗论。
全书完全不涉及诗与儒道的关系及其在政治、教化方面的功能,而重视诗的艺术性和由此造成的对人心的感发,这与理学家的文学观恰成对立。
1 严羽写《沧浪诗话》的时代背景我们知道,诗歌艺术发展到唐代,已经达到了古典诗歌艺术的最高峰。
宋诗要有新的创造,必须独辟蹊径。
散文化和议论化便成为当时宋代诗坛的一个特色,这确实是宋代诗歌出现了新现象。
但是江西诗派却过分强调,他们过多地发议论、讲道理,排比典故、掉书袋,片面追求文字工巧,这些倾向的恶性发展,违背了诗歌发展的艺术规律,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被奉为江西派之祖的黄庭坚就提出诗歌创作要“以理为主”,认为“词意高深要从学问中来”(《论诗帖》),强调“无一字无来历”,“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再答洪驹父书》),提出“夺胎法”和“换骨法”(参看《冷斋夜话》卷一),主张创作要对古人名作“不易其意而造其语”,“窥入其意而形容之”。
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解释:羚羊夜宿,挂角于树,脚不着地,以避祸患。
旧时多比喻诗的意境超脱。
——《沧浪诗话·诗辩》言有尽而意无穷。
解释:语言完了而意味却无穷无尽。
——《沧浪诗话·诗辩》语贵脱洒,不可拖泥带水解释:语言以干净利落为贵,不能拖沓冗长。
——《沧浪诗话·诗法》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解释:写诗需要别样的才能,和学问的多少没有关系;写诗需要别样的意趣,和抽象的说理没有关系。
——《沧浪诗话·诗辩》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
解释:见识胜过老师,才仅仅堪受到老师的传授;见识和老师一个水平,往往只能接受老师的一半才德。
——《沧浪诗话·诗辩》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洟满襟,然后为识离骚。
否则如戛釜撞瓮耳。
解释:读《离骚》久了,才能读真味来,必须要抑扬顿挫地朗诵直到泪洒衣襟,然后才算得上是读懂了《离骚》,否则读起来就会像是敲击釜瓮一样沉闷无味。
——《沧浪诗话·诗评》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解释:写文章当以达意传情的清晰、透彻为目标的道理。
——《沧浪诗话·诗法》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
解释:学写诗的人要以见识为主:入门要正,效法的榜样要高;应该把汉、魏、晋、盛唐时代的诗人树为榜样,不必把开元、天宝以后的诗人树为榜样。
——《沧浪诗话·诗辩》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解释:所以盛唐诗歌的妙处就是,透彻玲珑,不能直接把握,就像是空中的声音、脸上的神色、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诗句是有限的,意韵却是无穷的。
——《沧浪诗话·诗辩》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
解释:悟的程度有浅有深,有不同的领域,有的人悟得透彻,有的人只是一知半解。
——《沧浪诗话·诗辩》诗者,吟咏情性也。
《沧浪诗话》研究资料综述引言:《沧浪诗话》是宋代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自其问世以来,便受到历代文人学者的关注,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注释与批评。
历代学者主要围绕《沧浪诗话》中的“以禅喻诗”、“妙悟说”、“兴趣说”等诗歌理论进行讨论和研究。
《沧浪诗话》的研究资料数量较多,成果丰硕,理论观点较为成熟。
近年来,虽然研究热度有所下降,但亦有学者以新方法研究《沧浪诗话》,其中不乏一些可供借鉴的新视角和新观点。
一、“以禅喻诗”理论研究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说自己在《诗辩》中“以禅喻诗,莫此亲切。
”明确提出了自己在《沧浪诗话》中使用了“以禅喻诗”的方法,来论述他的诗歌主张。
严羽在《沧浪诗话》这样的诗歌理论中有援禅入诗之嫌,这不符合儒家温柔敦厚之义,所谓“诗教自尼父论定,何缘坠入佛事”。
因此,后世文人学者,围绕严羽的诗禅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郭绍虞在《沧浪诗话校释》中从多个方面解释了严羽的诗禅说,他一方面说明了诗禅之说不起于沧浪,而是受到了当时的时代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更说明了诗禅说可能引起的种种歧解。
他认为许多学者反对严羽:“援禅入诗”的行为,是后人对于严羽的诗禅说的误会,不是严羽的原意:“其实沧浪只是以禅喻诗,而诸家则是以禅衡诗。
”[1]郭绍虞还指出严羽的诗禅说,有以禅论诗与以禅喻诗二义。
“以禅论诗,是就禅理与诗理相通之点而言的。
以禅喻诗,是就禅法与诗法相类之点而比拟的。
”[2]南宋处于中国禅道发展到烂熟阶段的后期,文人士大夫学禅、说禅蔚然成风,援禅入诗,以禅论诗,以禅喻诗,成为风起云涌的诗坛时尚。
黄庭坚、吕本中、范温、韩驹、吴可、曾几、龚相、赵蕃等等都曾以禅论诗或以禅喻诗,道儒佛三学兼修的苏轼更是结合古典道学“虚静”观和佛学“空”观,提出了著名的“空静”说。
王妍卓在《严羽〈沧浪诗话〉及其体悟性诗学》[4]中指出“严羽以禅喻诗的目的并非以禅入诗,《沧浪诗话》也并非意在宣扬禅学。
严羽标举盛唐,以李白、杜甫为代表也可作为一个旁证。
解读《沧浪诗话.考证》中的李杜诗歌以前的人对于考证作品时代,原有两种方法:鉴赏与考据。
在《沧浪诗话考证》中严羽较少用的是考据,而多用鉴赏。
鉴赏重在直觉感悟,“感悟”又是以“辨家数如辨苍白”为基础,做到这一点,就要对各家的风格体制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对各家诗的“兴趣”、“气象”有一个全面把握。
在《诗辨》、《诗法》中严羽阐述了自己的写作主张,而《考证》中又运用这些主张对前人诗歌作一种考证。
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说:“仆于作诗,不敢自负,至识则自谓有一日之长,于古今体制,若辨苍素,甚者望而知之”。
又说“不遇盘根,安别利器”(《沧浪诗话校释》)。
那么我们就把严羽考证对象当作盘根,而把严羽重鉴赏的考证方法当作利器,看看究竟利器是否锋利。
严羽曾在《诗评》中说:“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
而对于唐人诗,他最推崇的莫过于李杜,他说:“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
而对于李白的评价则是:“观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
太白天才豪逸,语多卒然而成者。
学者于每篇中,要识其安身立命处可也”。
又说“李杜诸公,如金翅擘海,香象渡河”。
(《沧浪诗话校释》)所以在《考证》中严羽不惜用三分之一的篇幅考证李杜的诗。
第一条是推翻前人对李杜的庸俗之见,另外有五条是考证李白的诗,六条是论证杜甫的诗歌。
严羽的时代是苏、黄齐名,当时的人认为那些苏黄互相称赞的话隐含着讥讽之意。
由后代推论前代,就认为李杜不可能不互相嫉妒。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说,杜甫集子中说李白诗的地方很多,如“李白斗酒诗百篇”,如“清新瘐开府,俊逸鲍参军”,“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之句,好像是讥讽他写得太快、太俊美。
李白诗中有“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为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来作诗苦”。
好像是讥讽杜甫作诗太愁苦。
再加上杜甫称赞李白的诗居多,李白称赞杜甫的诗少。
因此许多人都认为李杜“名既相逼,不能无相忌”(《考证》),严羽认为这是凭借庸俗的见解来猜测圣贤的心理。
《沧浪诗话》与盛唐诗歌的经典化 【内容提要】 严羽《沧浪诗话》是集宋代诗学辨体理论大成的理论著作,它对明清诗学批评 理论影响最大的是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 是宋代诗学批评辨唐宋诗风差异的理论总结,也是对江西诗派的全面清算,同 时显示了严羽试图在儒家理学体系之外建构诗学话语的努力,指引着明清诗学 批评的基本路径,具有极其重要的诗学批评史意义。
【关键词】《沧浪诗话》;盛唐诗歌;宋代诗学
严羽《沧浪诗话》是整个宋代诗话中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著作,也是集宋 代诗学辨体理论之大成的理论著作,它对明清诗学批评的最大影响是在标榜格 调的理论旗帜下对唐诗尤其是盛唐诗歌的经典化。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宇 文所安教授认为:“《沧浪诗话》的流行产生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把盛唐 诗经典化了,盛唐诗从此成为诗歌的永恒标准,其代价是牺牲了中晚唐诗人。 虽然盛唐代表诗歌高峰的信念可以一直追溯到盛唐时代,但严羽给盛唐赋予了 一种特殊的权威,一种类似禅宗之正统的文学之正统。绝对的诗歌价值存在于 过去的某个历史时刻,这种观念,或好或坏,一直左右着后世读者对诗歌的理 解。以盛唐诗为正统的观念时不时受到谨逊的限制或激烈的反对,但它始终是 一种约定俗成的认识,其他见解都围绕着它做文章。”①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 侧重于强调诗学批评中存在着某种凌驾于具体创作之上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 与典范,这种标准与典范首先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上,即任何一种文学体裁 都具有某种最典范的创作阶段,这一阶段该体裁的创作具有整齐划一的时代风 格,而这一风格则是超越时代的典型范本,必然成为后世长期师法遵循但永远 无法达到的创作楷模。对这种典型范本的归依与膜拜是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重 要特征,也是格调派诗学复古的潜在内涵。 首先,《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是从 贬抑宋诗新变的成就,重新思考诗歌发展路径开始的,具有正本清源的意味, 也是宋代诗学批评辨析唐宋诗风差异的理论总结。 在严羽确立盛唐诗审美规范之前,北宋诗人黄庭坚、陈师道试图从中唐诗 人杜甫、韩愈的刻意锤炼、辞必己出出发来奠定宋诗的崛奇拗峭、朴拙生硬的 诗风;南宋诗人如陆游、杨万里试图从古诗及唐诗的美文传统中寻找新的审美 规范来补救江西诗派末流的枯瘦艰涩、拗硬奇险的弊病,但是他们所景仰与效 法的只是中晚唐诗歌的清新自然、圆转流丽的诗歌风格,与严羽取法乎上,效 法盛唐的雄浑雅健、华采空灵的诗歌风格迥异。尤其是宋代诗人对传统儒家道 德气节价值观与以美刺讽谏为中心的诗歌政治功能的强化,冲淡了其文学风格 论的独特的诗学意义。故《沧浪诗话•诗评》称:“唐人诗与本朝人诗,未论 工拙,直是气象不同。”② 《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尤其是建立在对江西诗派的全面清算 的基础上的。严羽在论述具体诗体上,如:“五言绝句中,众唐人人是一样, 少陵是一样,韩退之是一样,王荆公是一样,本朝诸公是一样。”尤其是论宋 诗演变发展及其与唐诗的承继与新变非常深刻:“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 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 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 始自出己意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功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 内称为江西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 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他明确批评苏、黄与江西诗 风道:“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诗之至此,可谓一厄也。”③他从整体上肯 定了唐宋诗之间的明显而又巨大的差异,把宋诗当作与唐诗完全不同的审美规 范的产物,并且在两种不同诗学取向之间作出非常鲜明的价值品评,对以苏、 黄为代表的宋诗的卖弄学问,堆砌典故的习气非常不满,是对张戒的“诗妙于 子建,成于李、杜,坏于苏、黄”(《岁寒堂诗话》)的继承与发展。 严羽指出论诗的风格不宜倡导“雄浑雅健”,因为“健”字只宜于文而不 宜于诗,是对诗文体制风格特征的深入细致的辨析,是对江西诗派以文为诗倾 向的刻意防范,他说:“又谓盛唐之诗„雄深雅健‟,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 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若《诗辨》„雄浑悲壮‟之语为得诗之体也。毫厘 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未 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之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 不同如此。”(《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他认为苏轼、黄庭坚的诗,相对 于汉魏古诗与盛唐律诗,正如未师从孔子之前的勇而无礼的子路,过于劲健与 雄壮,缺乏的是浑成自然、含蓄蕴藉的气度,不符合“气象浑沌”的审美标准。 严羽反对以“健”论诗,语出刘克庄称引张嵘语对黄庭坚的批评:“鲁直自以 为出于《诗》与《楚辞》,过矣,盖规模汉、魏以下者也。……其古、律诗酷 学少陵,雄健太过,遂流而入于险怪。要其病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 语。”(《后村诗话》)如果说严羽主张“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对江西诗 派后学淆乱诗歌体制的针砭的话,王士祯对于盛唐诗歌风格的辨析尤其是对明 人所效法的空疏肤阔的唐诗的批判与对王、孟、韦、柳含蓄蕴藉风格的推崇, 则是对明代格调派的矫枉,其立论的目的各异,而其对于唐诗风格的辨体意识 则是一脉相承的。
如果说严羽批评江西诗派学唐是变而不得其正的话,那么他批评当时的江 湖诗派则是学唐而不得其门而入。严羽倡导盛唐诗歌的“正眼法藏”,更是直 接对四灵师法晚唐诗的反动。严羽首先以禅喻诗,从宏观的诗体演变的角度为 诗歌发展史伸正黜变,他说:“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 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 也。”先树立了评判的标准,然后就对南宋后期诗风批判道:“正法眼无传久 矣。唐诗之说未倡,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倡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 谓唐诗诚止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耶? ”严羽认为,当时四灵与江湖诗派诗歌 的最大的问题是在学唐取向上的误导,为此,他呐喊疾呼,以图起衰救弊,使 诗歌复归于“正法眼”,他说:“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 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S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 辟支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 ”(《沧浪诗话•诗辨》)四灵本以倡 导“唐音”自命,可严羽认为四灵专宗晚唐姚、贾是误入歧途,是导致当时诗 学流弊的主耍原因。 由此可见,严羽认为,宋诗三百年的发展路径是完全错误的,学唐者也是 在沿袭唐诗的流弊。对宋诗特征与创作成就的否定,为严羽辨唐宋诗体制、树 立尊唐抑宋的话语权威,尤其是为盛唐诗歌的经典化,奠定了理论前提。 其次,《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显示了严羽试图在理学思想体 系之外建构诗学话语的努力。 宋代理学家打着宣扬性命义理的口号,认为诗歌只是“艺焉而已”(周敦 颐语),是供人娱乐的玩物,在“学诗用功甚妨事”(程颐《二程遗书》卷18) 的极端观点下,取消了独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理学家偶尔也吟诗作文,可大 都搁置诗歌艺术特征于不顾,一味于诗中谈性议理,忽视了诗歌作为独立的文 体所具有的基本审美特征,完全沦为了阐述理学思想的工具。朱熹对于文道合 一的明确论述在宋代道学家的文论中无疑具有典范意义,他说:“道者,文之 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 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 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朱 子语类》卷139)
严羽《沧浪诗话》的辨体批评主要从诗体艺术形式与风格的角度出发,论 诗往往舍弃经典,与刘勰、韩愈等人首先标举“明道尊经”大异。《沧浪诗话》 中除《诗体》中有“《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 一句 之外,更无称引《诗经》之处,根本没有涉及到《诗经》的经典示范意义。这 种形式主义的理论倾向构成了《沧浪诗话》的最大的诗学意义,就是在宋代理 学话语背境f寻求诗学批评超载r儒家道统外的独立的存在意义,谋图建立一 种与“道统”道不同不相与谋的“诗统”。严羽的这种意图与努力,是宋代诗 学曰趋专业化的产物,对于儒家道统的话语权威是具有颠覆意义的。《沧浪诗 话》代表着一种想在儒家正统道统之外,另建独立于整个宋儒理学之外的诗学 话语体系的一种努力,这种诗学话语体系的存在的根基就在于,必须承认有独 力于儒家理学话语之外的自成体系的诗学的存在,这种诗学应该有自己的独立 的价值体系、权威系统与批评话语,应该是自我满足而非依附性的存在。也许 严羽是无意的,但他的这种试图挣脱理学话语约束的努力及其在明代诗学批评 的重大影响,都昭示了他的反儒学的本质,而以禅喻诗只是其批评手段之一。 最后,《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也指引着明清诗学批评的基本 路径,也蕴涵着理论的误区,具有重要的诗学批评史意义与影响。 明代前后七子复古派诗学批评突出地肯定诗歌审美特征,把审美特征的兴 衰演变作为考察与评价前代诗歌成就的标准,与宋代理学影响K的诗学批评强 调政教伦理有明显区别。如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开篇就明确标榜“诗在六 经中别是一教”,就明显受《沧浪诗话》的影响。从现代文艺学的角度看来, 严羽《沧浪诗话》具有独到的批评史意义。我们从明中后期以理学家为主体的 唐宋派、清代标榜宋儒理学的思想家以及代表清代官方正统舆论的《四库全书 总目》对明代诗学批评尊唐风尚的贬抑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对 盛唐诗歌的经典化,包含有自觉与宋代诗学批评乃至宋型文化立异的因素,在 其本质上带有动摇宋儒理学思想的意义。 但明代诗学批评家在继承严羽的辨体批评理论的同时,都忽视了他存在着 一个明显的逻辑上的矛盾。严羽论诗,首在辨别家数,曾自诩道:“辨家数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