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书
- 格式:doc
- 大小:32.50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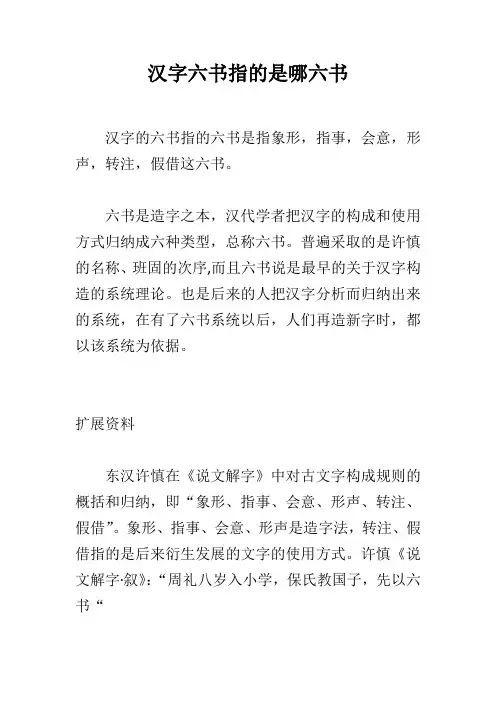
汉字六书指的是哪六书
汉字的六书指的六书是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六书。
六书是造字之本,汉代学者把汉字的构成和使用方式归纳成六种类型,总称六书。
普遍采取的是许慎的名称、班固的次序,而且六书说是最早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
也是后来的人把汉字分析而归纳出来的系统,在有了六书系统以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该系统为依据。
扩展资料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古文字构成规则的概括和归纳,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法,转注、假借指的是后来衍生发展的文字的使用方式。
许慎《说文解字∙叙》:“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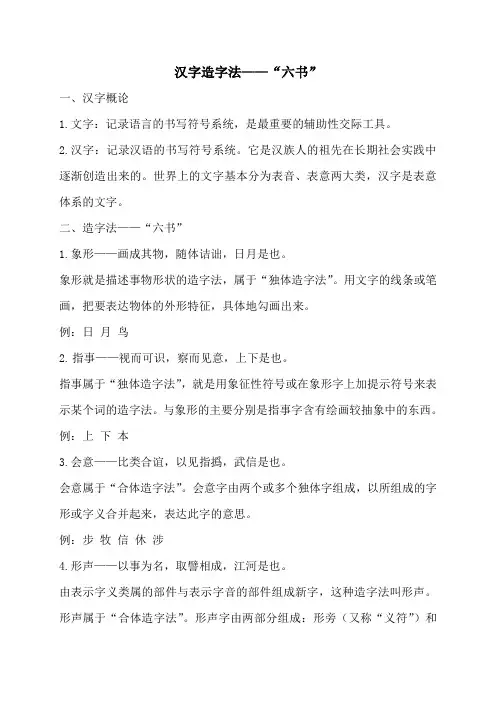
汉字造字法——“六书”一、汉字概论1.文字: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是最重要的辅助性交际工具。
2.汉字: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
它是汉族人的祖先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
世界上的文字基本分为表音、表意两大类,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
二、造字法——“六书”1.象形——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象形就是描述事物形状的造字法,属于“独体造字法”。
用文字的线条或笔画,把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
例:日月鸟2.指事——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指事属于“独体造字法”,就是用象征性符号或在象形字上加提示符号来表示某个词的造字法。
与象形的主要分别是指事字含有绘画较抽象中的东西。
例:上下本3.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
会意属于“合体造字法”。
会意字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成,以所组成的字形或字义合并起来,表达此字的意思。
例:步牧信休涉4.形声——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由表示字义类属的部件与表示字音的部件组成新字,这种造字法叫形声。
形声属于“合体造字法”。
形声字由两部分组成:形旁(又称“义符”)和声旁(又称“音符”)。
形旁表示字的性质、属性,声旁则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
左形右声:诚、愉、情、描左声右形:鹤、放、鸭、飘上形下声:管、巅、雳、芳上声下形:烫、忌、汞、堡水形内声:圈、固、病、氏内形外声:辫、辩、问、闻5. 转注——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转注属于“用字法”。
不同地区因为发音有所不同,以及地域上的隔阂,以致对同样的事物会有不同的称呼。
当这两个字是用来表达相同的东西,词义一样时,它们会有相同的部首或部件。
6.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假借就是同音替代,也是一种“用字法”。
口语里有的词没有相应的文字对应,于是就找一个和它发音相同的同音字来表示它的含义。
例:早晚的“早”写成“蚤”。
《礼记·乐记》:发扬蹈厉之已蚤。
屈伸的“伸”写成“信”。
《周易·系辞下》:尺蠖之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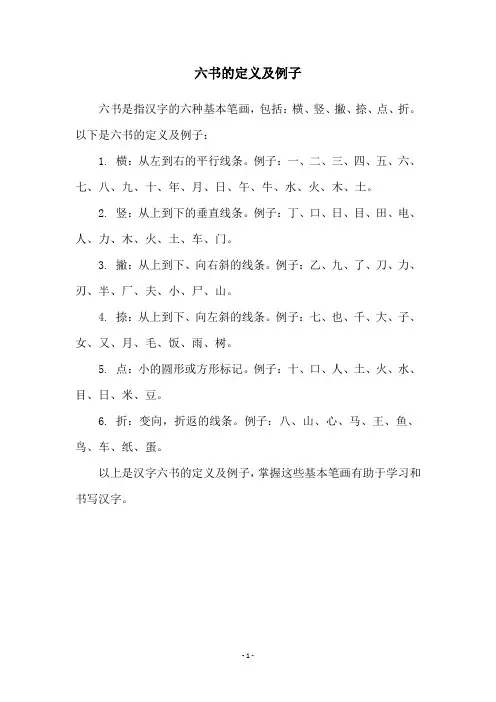
六书的定义及例子
六书是指汉字的六种基本笔画,包括:横、竖、撇、捺、点、折。
以下是六书的定义及例子:
1. 横:从左到右的平行线条。
例子: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年、月、日、午、牛、水、火、木、土。
2. 竖:从上到下的垂直线条。
例子:丁、口、日、目、田、电、人、力、木、火、土、车、门。
3. 撇:从上到下、向右斜的线条。
例子:乙、九、了、刀、力、刃、半、厂、夫、小、尸、山。
4. 捺:从上到下、向左斜的线条。
例子:七、也、千、大、子、女、又、月、毛、饭、雨、树。
5. 点:小的圆形或方形标记。
例子:十、口、人、土、火、水、目、日、米、豆。
6. 折:变向,折返的线条。
例子:八、山、心、马、王、鱼、鸟、车、纸、蛋。
以上是汉字六书的定义及例子,掌握这些基本笔画有助于学习和书写汉字。
- 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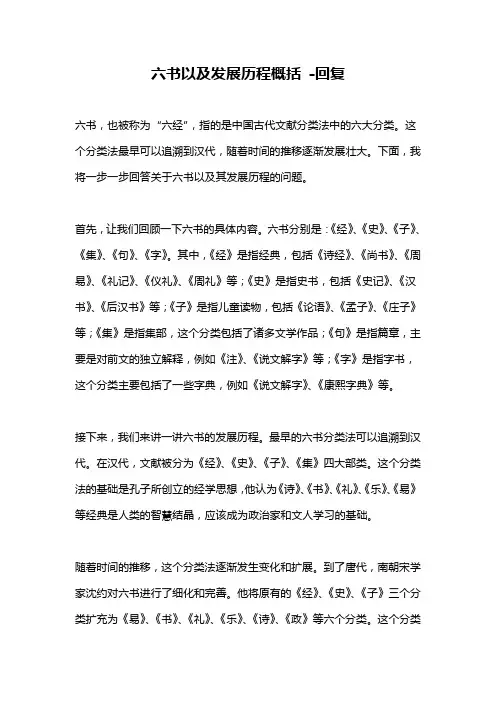
六书以及发展历程概括-回复六书,也被称为“六经”,指的是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法中的六大分类。
这个分类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展壮大。
下面,我将一步一步回答关于六书以及其发展历程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六书的具体内容。
六书分别是:《经》、《史》、《子》、《集》、《句》、《字》。
其中,《经》是指经典,包括《诗经》、《尚书》、《周易》、《礼记》、《仪礼》、《周礼》等;《史》是指史书,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子》是指儿童读物,包括《论语》、《孟子》、《庄子》等;《集》是指集部,这个分类包括了诸多文学作品;《句》是指篇章,主要是对前文的独立解释,例如《注》、《说文解字》等;《字》是指字书,这个分类主要包括了一些字典,例如《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六书的发展历程。
最早的六书分类法可以追溯到汉代。
在汉代,文献被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
这个分类法的基础是孔子所创立的经学思想,他认为《诗》、《书》、《礼》、《乐》、《易》等经典是人类的智慧结晶,应该成为政治家和文人学习的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分类法逐渐发生变化和扩展。
到了唐代,南朝宋学家沈约对六书进行了细化和完善。
他将原有的《经》、《史》、《子》三个分类扩充为《易》、《书》、《礼》、《乐》、《诗》、《政》等六个分类。
这个分类法加入了对政府和社会生活的注重,凸显了政治的重要性。
宋代后期,程朱理学的兴起对六书分类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程朱理学强调经学的核心地位,将《经》、《史》、《子》三个分类作为“三纲五常”的基础。
这种观点在明清两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了社会主流思想。
此时的六书分类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教育、政府和文化领域。
而在现代,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知识的不断积累,六书分类法逐渐显露出一些不足之处。
尤其是在十九世纪末,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人们开始对传统经典进行重新思考和解读。
此时,六书分类法受到了批评和质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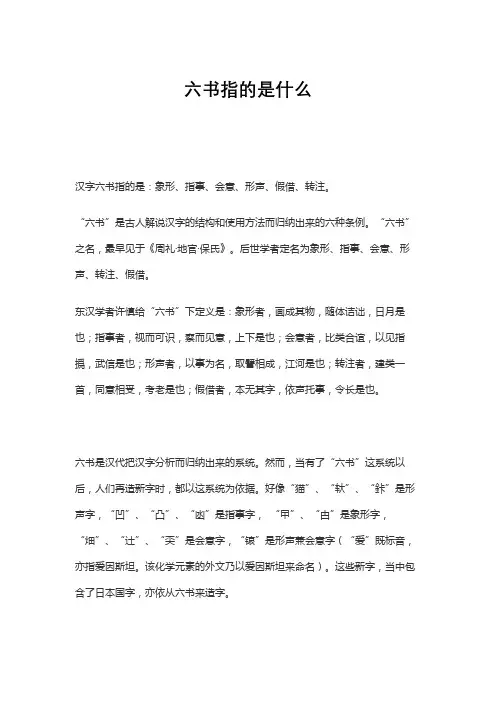
六书指的是什么
汉字六书指的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
“六书”是古人解说汉字的结构和使用方法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
“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
后世学者定名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东汉学者许慎给“六书”下定义是: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六书是汉代把汉字分析而归纳出来的系统。
然而,当有了“六书”这系统以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这系统为依据。
好像“猫”、“轪”、“鉲”是形声字,“凹”、“凸”、“凼”是指事字,“曱”、“甴”是象形字,“畑”、“辻”、“奀”是会意字,“锿”是形声兼会意字(“爱”既标音,亦指爱因斯坦。
该化学元素的外文乃以爱因斯坦来命名)。
这些新字,当中包含了日本国字,亦依从六书来造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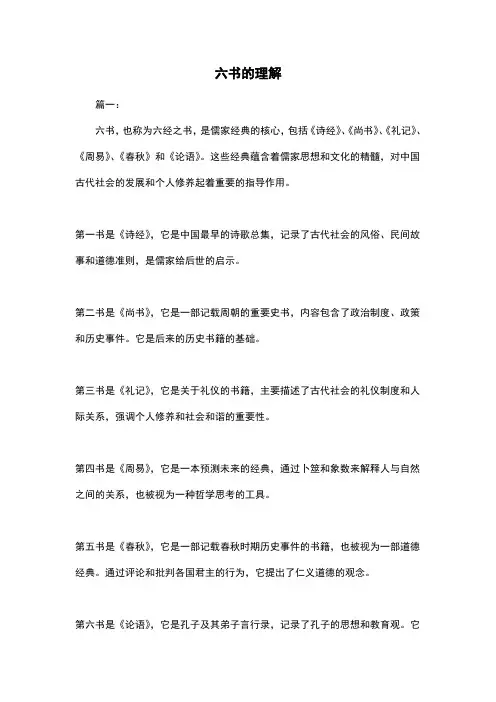
六书的理解篇一:六书,也称为六经之书,是儒家经典的核心,包括《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和《论语》。
这些经典蕴含着儒家思想和文化的精髓,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个人修养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一书是《诗经》,它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记录了古代社会的风俗、民间故事和道德准则,是儒家给后世的启示。
第二书是《尚书》,它是一部记载周朝的重要史书,内容包含了政治制度、政策和历史事件。
它是后来的历史书籍的基础。
第三书是《礼记》,它是关于礼仪的书籍,主要描述了古代社会的礼仪制度和人际关系,强调个人修养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性。
第四书是《周易》,它是一本预测未来的经典,通过卜筮和象数来解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被视为一种哲学思考的工具。
第五书是《春秋》,它是一部记载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书籍,也被视为一部道德经典。
通过评论和批判各国君主的行为,它提出了仁义道德的观念。
第六书是《论语》,它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录,记录了孔子的思想和教育观。
它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主张以仁爱为核心的人际关系。
这六书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后来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们不仅影响了儒家思想的发展,也对其他学派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今,虽然六书的地位在中国文化中已经逐渐被其他学科和文化形式所取代,但它们仍然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重要窗口,对于个人修养和社会和谐的追求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因此,对于学习六书的理解和传承,对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篇二:六书是中国古代修辞学的重要理论,指的是比喻、夸张、对仗、排比、拟人和讽刺这六种修辞手法。
这六种修辞手法在文学作品中被广泛运用,以增添表达的艺术性和感染力。
首先,比喻是将两个或多个事物进行类比,通过对比和隐喻的方式,使读者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受到描述的对象。
比喻的使用可以使抽象的概念更具形象性和感知性,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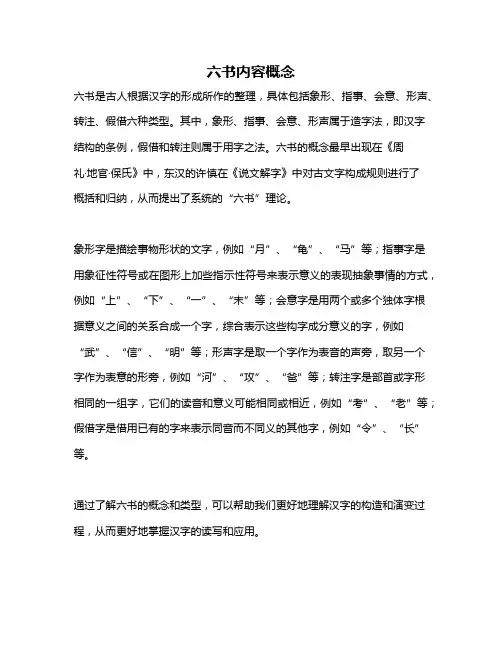
六书内容概念
六书是古人根据汉字的形成所作的整理,具体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类型。
其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属于造字法,即汉字结构的条例,假借和转注则属于用字之法。
六书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周礼·地官·保氏》中,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古文字构成规则进行了
概括和归纳,从而提出了系统的“六书”理论。
象形字是描绘事物形状的文字,例如“月”、“龟”、“马”等;指事字是用象征性符号或在图形上加些指示性符号来表示意义的表现抽象事情的方式,例如“上”、“下”、“一”、“末”等;会意字是用两个或多个独体字根据意义之间的关系合成一个字,综合表示这些构字成分意义的字,例如“武”、“信”、“明”等;形声字是取一个字作为表音的声旁,取另一个字作为表意的形旁,例如“河”、“攻”、“爸”等;转注字是部首或字形相同的一组字,它们的读音和意义可能相同或相近,例如“考”、“老”等;假借字是借用已有的字来表示同音而不同义的其他字,例如“令”、“长”等。
通过了解六书的概念和类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汉字的构造和演变过程,从而更好地掌握汉字的读写和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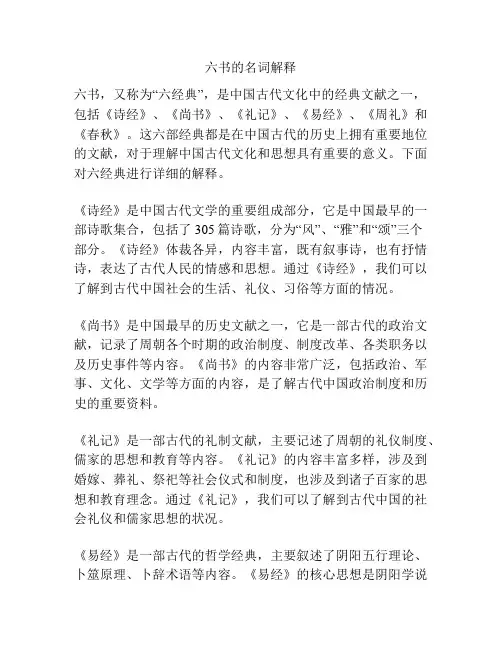
六书的名词解释六书,又称为“六经典”,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经典文献之一,包括《诗经》、《尚书》、《礼记》、《易经》、《周礼》和《春秋》。
这六部经典都是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拥有重要地位的文献,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下面对六经典进行详细的解释。
《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集合,包括了305篇诗歌,分为“风”、“雅”和“颂”三个部分。
《诗经》体裁各异,内容丰富,既有叙事诗,也有抒情诗,表达了古代人民的情感和思想。
通过《诗经》,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中国社会的生活、礼仪、习俗等方面的情况。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之一,它是一部古代的政治文献,记录了周朝各个时期的政治制度、制度改革、各类职务以及历史事件等内容。
《尚书》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政治、军事、文化、文学等方面的内容,是了解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和历史的重要资料。
《礼记》是一部古代的礼制文献,主要记述了周朝的礼仪制度、儒家的思想和教育等内容。
《礼记》的内容丰富多样,涉及到婚嫁、葬礼、祭祀等社会仪式和制度,也涉及到诸子百家的思想和教育理念。
通过《礼记》,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中国的社会礼仪和儒家思想的状况。
《易经》是一部古代的哲学经典,主要叙述了阴阳五行理论、卜筮原理、卜辞术语等内容。
《易经》的核心思想是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通过这些理论可以解释事物的生成和变化规律。
《易经》对于古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也对于后世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礼》是一部关于周朝制度、仪式和礼制的文献,它是中国古代礼制文献中的重要部分。
《周礼》包括了社会制度、官制、职官名称、封地制度、官员选拔等内容,对于了解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有着重要的意义。
《春秋》是一部官修的历史编年体史书,它是以公历年代记述周朝国家大事为主,记录了战争、政治、犯罪等方面的历史事件。
《春秋》的记载内容非常简略,但它是后世历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对于研究古代中国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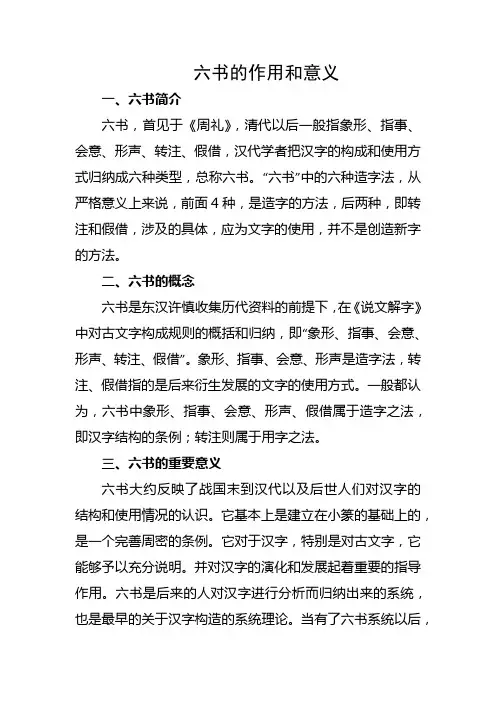
六书的作用和意义
一、六书简介
六书,首见于《周礼》,清代以后一般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汉代学者把汉字的构成和使用方式归纳成六种类型,总称六书。
“六书”中的六种造字法,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前面4种,是造字的方法,后两种,即转注和假借,涉及的具体,应为文字的使用,并不是创造新字的方法。
二、六书的概念
六书是东汉许慎收集历代资料的前提下,在《说文解字》中对古文字构成规则的概括和归纳,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法,转注、假借指的是后来衍生发展的文字的使用方式。
一般都认为,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属于造字之法,即汉字结构的条例;转注则属于用字之法。
三、六书的重要意义
六书大约反映了战国末到汉代以及后世人们对汉字的结构和使用情况的认识。
它基本上是建立在小篆的基础上的,是一个完善周密的条例。
它对于汉字,特别是对古文字,它能够予以充分说明。
并对汉字的演化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六书是后来的人对汉字进行分析而归纳出来的系统,也是最早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
当有了六书系统以后,
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该系统为依据。
所以“六书理论”是我国文字学史上的一个伟大创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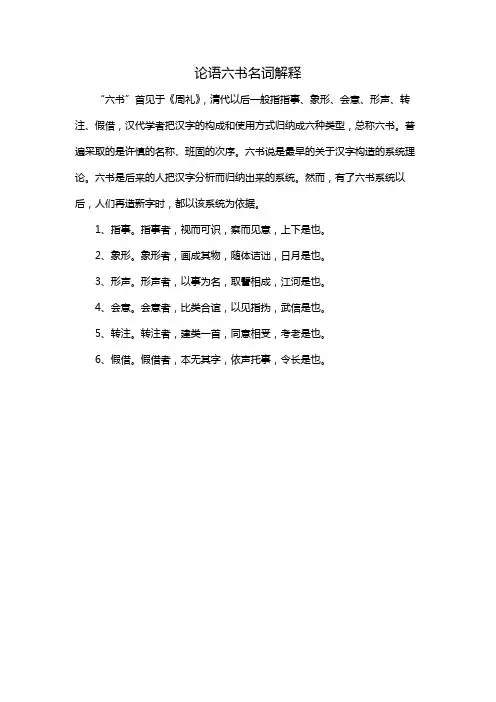
论语六书名词解释
“六书”首见于《周礼》,清代以后一般指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汉代学者把汉字的构成和使用方式归纳成六种类型,总称六书。
普遍采取的是许慎的名称、班固的次序。
六书说是最早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
六书是后来的人把汉字分析而归纳出来的系统。
然而,有了六书系统以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该系统为依据。
1、指事。
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2、象形。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3、形声。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4、会意。
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㧑,武信是也。
5、转注。
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6、假借。
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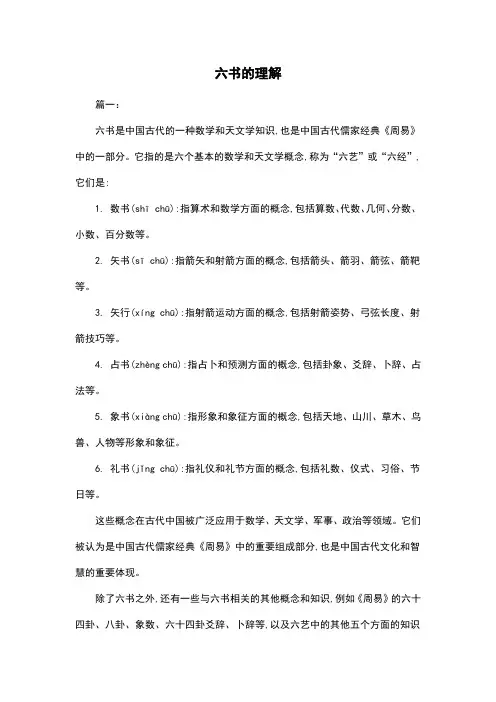
六书的理解篇一:六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数学和天文学知识,也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周易》中的一部分。
它指的是六个基本的数学和天文学概念,称为“六艺”或“六经”,它们是:1. 数书(shī chū):指算术和数学方面的概念,包括算数、代数、几何、分数、小数、百分数等。
2. 矢书(sī chū):指箭矢和射箭方面的概念,包括箭头、箭羽、箭弦、箭靶等。
3. 矢行(xíng chū):指射箭运动方面的概念,包括射箭姿势、弓弦长度、射箭技巧等。
4. 占书(zhèng chū):指占卜和预测方面的概念,包括卦象、爻辞、卜辞、占法等。
5. 象书(xiàng chū):指形象和象征方面的概念,包括天地、山川、草木、鸟兽、人物等形象和象征。
6. 礼书(jǐng chū):指礼仪和礼节方面的概念,包括礼数、仪式、习俗、节日等。
这些概念在古代中国被广泛应用于数学、天文学、军事、政治等领域。
它们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周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和智慧的重要体现。
除了六书之外,还有一些与六书相关的其他概念和知识,例如《周易》的六十四卦、八卦、象数、六十四卦爻辞、卜辞等,以及六艺中的其他五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如书法、音乐、绘画、舞蹈等。
这些概念和知识在现代中国仍然被广泛应用于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领域。
篇二:六书是指古代中国儒家经典《论语》中提出的一套论述问题的方法,包括六个部分,分别是《易传》、《书传》、《诗经》、《礼记》、《春秋》和《左传》。
下面是对六书的理解以及拓展:1. 《易传》:指《易经》中的“易”部分,即“变化”之意。
六书中最早提到的一本书,也是最重要的一本书。
《易经》以六十四卦的形式,通过对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观察和分析,阐述“变化”的本质和规律,提出了“君子变于道”的观点。
六书中的《易传》不仅为儒家思想奠定了基础,也对后来的道家、佛家等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书传》:指《书经》中的“书”部分,即“书籍”之意。
汉字的六书
汉字的六书,又称“六家”,是中国古代汉字书写规范的总称,它包括以下六部著作:
一、《金文》:是商朝的金文书写样式,这种书写样式逐渐发展成为后世文字的重要基础。
二、《尔雅》:是春秋时期的书写样式,融合了商朝金文和诸侯国的书写风格,是当时书写样式的主流。
三、《篆书》: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创立的书法样式,为了防止战乱,发布了统一的篆体书法,以保持文字的统一。
四、《隶书》:是汉朝以后汉字书写的规范,其表达方式简洁直观,使得大众能够迅速掌握和传播,在后世书法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五、《楷书》:是宋朝书法家王羲之创立的书法,它融合了前代书法的优点,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并被世人所推崇,被誉为“书中之王”。
六、《行书》:是宋朝书法家张旭创立的书法,他借鉴了文言文的书写形式,将繁琐的文字改编成简洁而有力的书法,使书写变得更加生动。
简述六书的内容
六书具体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古人把汉字的造字方法归纳为六种,总称“六书”。
汉字六书是指汉字的六种构造条例,是后人根据汉字的形成所作的整理,而非造字法则。
六书是后来的人把汉字分析而归纳出来的系统。
六书大致反映了战国末到汉代以及后世人们对汉字的结构和使用情况的认识。
它基本上是建立在小篆的基础上的,是一个完善周密的条例。
它对于汉字,特别是对古文字,它能够予以充分说明。
并对汉字的演变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六书理论”是我国文字学史上的一个伟大创见。
造字六书介绍六书指的是汉字的造字方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词语信息“六书”是古人解说汉字的结构和使用方法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
“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
后世学者定名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东汉学者许慎给“六书”下定义是:象形者,画成其事,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讬事,令长是也。
概念是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古文字构成规则的概括和归纳,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法,转注、假借指的是后来衍生发展的文字的使用方式。
许慎《说文解字?叙》:“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讬事,令长是也。
"“六书”的这个概念始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
”东汉郑玄注引郑众说:“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①、假借、谐声②也”(注:①处事,即“指事”;②谐声,即“形声”)。
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六书之名定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许慎《说文解字叙》把六书之名定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一般都认为,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属于造字之法,即汉字结构的条例;转注、假借则属于用字之法。
六书大约反映了战国末到汉代人们对汉字的结构和使用情况的认识。
它基本上是建立在小篆的基础上的,是一个不够完善周密的条例。
古代的六书指的是什么
古代的六书是《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
六书同时也是指汉字构字的六种方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六书一词出于《周礼》:“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指《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
同时六书也指汉字构字的六种方法,分别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汉字的形体构造分为内部结构和外形结构两部分。
内部结构指汉字的构造方法,或称造字方法,传统叫做六书。
其中象形、指事是“造字法”,会意、形声是“组字法”,转注、假借是“用字法”。
六书一、六书简介六书,又称为“六经”,是中国古代文人学习和创作的基本方法和要素。
它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核心,对于诗词、文章、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都有重要影响。
六书是由六个字句构成的,分别是比、兴、象、用、兼、排。
这六个字句分别代表了文学作品的六个方面,包括比喻、兴起、描写、运用、兼并和排比。
二、比(喻)比喻是文学作品中常用的修辞手法之一,通过将不同的事物进行类比,以达到说明、描绘或者感染读者的目的。
比喻可以使作品更加形象、生动,并且能够引发读者的共鸣。
比喻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通过暗示来传达作者的意图。
比喻常常运用在描写自然景物、人物心理、社会现象等方面,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和思考的空间。
三、兴(起)兴起是文学作品的起承转合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是指作品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使读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和思想上的共鸣。
兴起可以通过描写精彩的情节、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表达深刻的思想和感情等方式来实现。
兴起是作品的灵魂,它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让读者更加愿意去阅读和思考。
四、象(描)象描是文学作品中描写事物形象的一种手法。
通过精细的描写,使读者能够感知到作品中事物的真实感和生动感。
象描可以通过文字来描绘物体的外貌、形态、颜色、质地等方面,也可以通过描写物体的声音、气味、味道等方面来实现。
通过象描,作品能够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感知力。
五、用(法)用法是指文学作品中运用语言的方式和技巧。
通过巧妙的运用语言,使作品更加生动、有趣、有力。
用法可以包括修辞手法、语言技巧、句式结构等方面。
修辞手法包括比喻、拟人、夸张、反问、排比等等,通过运用这些手法,使作品更加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
语言技巧包括运用词语的准确性、形象性、音韵美等方面,通过运用这些技巧,使作品更加精彩和有味道。
六、兼(并)兼并是指文学作品中综合运用各种手法和要素,使作品更加完整和丰富。
通过兼并,作品能够更好地表达作者的意图和思想,同时也能够给读者带来更多的思考和感受。
六书的详细讲解“六书”是古人解说汉字的结构和使用方法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
“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
后世学者定名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东汉学者许慎给“六书”下定义是:象形者,画成其事,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讬事,令长是也。
概念:是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古文字构成规则的概括和归纳,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法,转注、假借指的是后来衍生发展的文字的使用方式。
许慎《说文解字∙叙》:“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讬事,令长是也。
"“六书”的这个概念始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
”东汉郑玄注引郑众说:“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①、假借、谐声②也”(注:①处事,即“指事”;②谐声,即“形声”)。
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六书之名定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许慎《说文解字叙》把六书之名定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一般都认为,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属于造字之法,即汉字结构的条例;转注、假借则属于用字之法。
“六书说”是最早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
汉代学者创立“六书”说,对文字学的发展是有巨大功绩的。
此后一干多年的汉字研究,大多以《说文》为中心,“六书”为基本理论。
过去的文字学者在讲汉字构造的时候,一般都遵循“六书”的说法,把汉字分成象形、指事等六类。
“六书说”建立起了汉字构造学权威,在崇经媚古的时代里,研究文字学的人都把“六书”奉为不可违逆的指针。
尽管他们对象形、指事等“六书”的理解往往各不相同,却没有一个人敢跳出“六书”的圈子去进行研究。
大家写了很多书和文章,对“六书”的一些问题,诸如怎样给“转注”下定义,究竟应该把哪些字归人象形,哪些字归人指事,哪些字归人会意等等争论不休,但又争论不出有意义的结果来。
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此举不够明智,白白浪费了很多精力,还影响了对文字学其他领域的研究。
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里就曾说过:“。
··…六书说能给我们什么?第一,它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界说,个人可有个人的说法。
其次,每个文字如用六书来分类常常不能断定它应属哪一类。
单从这两点说,我们就不能只信仰六书而不去找别的解释了。
”‘〕裘锡圭先生评唐先生的话时也说:“这段话也许说得有点过头,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川,」为了完善汉字的结构理论,后代的学者试图突破“六书”理论的框架,作了许多改造“六书”的尝试,其中影响较大的学说有:清代学者戴震的“四体二用说”,1935年唐兰先生提出的“三书说”,1956年陈梦家等人提出的“新三书说”、当代一些学者提出的“平面结构”和“层次结构”以及北师大王宁先生提出的“结构一功能”分析法等等。
这些学说的提出说明:虽然“六书说”为中国文字学奠定了基础,给古文字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但同时也应看到它的局限性。
“六书”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第一,“六书”是分析近古文字亦即小篆的结果,它既不能全部解释古文字,也不能全部解释今文字。
第二,“六书说”不够明确,历代的理解虽说大休相近,但也有不少歧异之处。
“六书说”的问题的确不少,汉代学者对汉字构造的研究不可能十全十美。
“六书”理论是历史上汉字创制者与使用者总结出来的汉字形体结构规则,在近两千年的汉语文字学史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它的价值与功用是不可否认的。
同时,也应看到,传统“六书”说是前人提出的一种汉字构形理论,如同历史上任何一种“学说”或理论观点一样,不能不受其产生时代客观与主观历史条件的局限,其有得也有失。
后人关于“六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六书”命名与划界是否合理,这实质上涉及“六书”能否涵盖全部汉字,是否与汉字一一对应的问题;二是造字之法与用字之法的讨论,这实质是涉及“六书”是否处于同一范畴、同一层面的问题。
讨论者的分歧与争议,有的是《说文》本身历史局限造成的,有的则是讨论者认识上的差异所至。
实际上,在运用“六书”对汉字进行形体结构分析时,对于典型的只包含一种造字方法的汉字,可以作对应的分析。
而对于蕴含多种造字方法的汉字,如有一种方式为主体,则可按主体归类;如其主体方式不明显,可只作分析说明,不必强行归类。
“六书”的前四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与后二书分属于不同层面,古代学者却将它们并列在一起。
作为具有“重感悟,轻理念”的东方文化传统的我国古代学者来说,将其混同在一起,是不足为怪的(堪称中国古代学术经典的《毛诗序》中也有“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的说法,不仅将作为“诗之体”的“风、雅、颂”与“诗之用”的“赋、比、兴”相提并论,而且交错排列),但却给后来的研究者和使用者造成了不少麻烦,并形成了学术上的分歧。
争论多年的“六书”造字说与“四体两用”说没有本质上的太大的区别。
我们不妨称所谓“六书”造字说为反映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包含不同层面的广义造字说,称“四书”造字说为专门说明汉字形体结构的狭义造字说,而戴、段提出“四体两用”说,不失为“快刀斩乱麻”的做法。
由于传统“六书”说存在分类界限不明和涵盖范围缺乏周遍性的争议,特别是难以说明小篆以前的古文字(甲骨文、金文等)的构型规则,现代学者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汉字构形理论进行了新的探索,如古文字学者提出的“三书说”。
应当指出,“三书说”将“假借(或表音字)”作为一种造字方法,其不属于对汉字进行形体结构分析的狭义造字说,而是反映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广义造字说。
“三书说”将“象形”、“指事”、“会意”统称为“象形(或表意字)”,虽然避免了三者之间的纠葛,但对于人们认识汉字的形体结构来说,不免显得笼统。
事实上,人文学科不能完全用科学方法来说明,任何造字理论都难以涵盖整个汉字、乃至一个时代或一种字体的汉字的构形规则。
因此,在运用传统“六书”理论或提出新的理论来分析说明汉字结构的时候,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不要囿于历史的成说,不要受古人的局限,更不要陷入无谓的争论,以免白白浪费许多宝贵的精力和时间。
其二,要注重语言文字的逻辑性和规则性的探索,尽可能建立汉字构形的理性规则,以便为汉字教学和文字的信息处理服务;同时要承认语言文字约定俗成的性质,承认具象(或形象)思维在语言文字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认识语言文字现象的人文特征。
其三,要认识文字构形规则的相对性和多元性,不可能一种规则能够无一例外地涵盖所有文字现象,也不要因为存在某些例外而否认规则的客观存在。
汉字是一种最古老而又最具有个性的文字符号。
对于它的性质,至今说法不一。
明确汉字的性质及其形成原因,才能更好揭示“六书”的真谛。
世界各国所使用的文字多种多样,但其性质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表音文字,一类是表意文字”。
表音文字是用一套字母来拼写语词的声音,它和语言结合得比较紧密,只要掌握了字母的读音和拼写规则,就可以见形知音,听音知义,例如英语就是这种性质的文字。
表意文字,其形体直接表示出一定的意义,汉字就是这种性质的文字,它的每一个符号,通常所表示的是汉语的词或语素。
但是,无论是代表语言中的词或语素,还是代表比语素更小的单位,这些符号都同汉语中的意义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不直接同语音发生联系。
因此,从性质上说,汉字属于表意性文字。
许慎于《说文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又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这是许慎对《说文》所收字的形体的基本分类,即区分为“文”和“字”两大类:“象形、指事”是对“依类象形”的“文”的解说,“会意、形声”是对“孳乳浸多”的“字”的解说。
因为前两者是本于物象,而后两者是以“文”为根而孳生的。
假借和转注是用字方法,而不是造字方法。
这就是说,许慎所谓“六书”并不是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完备的分类。
其分类比较粗疏,对“六书”本身的界说过于简略,每书所举例字太少,又未加具体分析,正因为此,给后来的论争留下了极大的空间。
因此,有必要对“六书”重新回以剖析,以再现其本原意义。
(一)象形《说文叙》曰:“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可见象形字是描写物体的形状,线条(笔划)随着物体的轮廓而弯曲;它是由图画蜕变出来表示具体事物的“文”。
有的跟那个物体委曲毕肖,如鼠、目;有的只是对那个物体略加描绘,取其特点,如牛、羊;还有的在物体的旁边或上下,把它连属的东西也画出来,或示其地位,或指其功用,或明其性质,使本体更为明显,如眉、果。
过去,曾有学者把象形分为独体与合体两类。
其实按构形方式来说,独体象形就是绘形象物,即用简洁的笔划,描绘语词所指称的物体,构成一个独立的图像,如“贝、网、子”等。
合体象形就是烘托显物,例如“牢、须、州”等。
这两类象形字,是绝大多数汉字构形的基础。
(二)指事《说文叙》曰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王筠《说文释例》曰:“视而可识,指字形言;察而见意,指字义言。
”又曰:“六书之中,指事最少,而又最难辨。
”许慎是说,见到这个字就能认识,但须仔细观察体会才能了解它所表示的意思。
在许氏的解说中,“见意”二字是关键。
参照《说文》正文里所举的例字,其构形方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号见意,例如“一、三、上、下”等;另一类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增加指示符号,表示所指的部分是什么意义,例如“刃、本、末、亦、朱”等。
前者大多取象于上古原始记事方式中的契刻记号和记绳之法,后者所加记号只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
(三)会意《说文叙》曰:“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
”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意符有目的的组合在一起,即所谓“比类合谊”;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符的结合中来反映一义,即所谓“以见指撝”。
可见,所谓“会意”,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物形体会合起来,从它们的联系或者配合上表达出一种新的,但一般又是比较抽象的意义。
会意可分为两类:一是会比图形,即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按照事理关系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语词的意义,其内容大多是某种事物过程的表象,如既(会食已)、即(会就食)等;二是会合字形,即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能独立的字在一起,凭借构件字的意义关联,使人领会出新的意义,如“从、牧、取、明”等。
(四)假借《说文叙》曰:“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许慎所界说的假借是指因音同而借字,许慎所举例字却是指因引申而借字,因而有人认为“令长”不是假借,许慎的例字举得不当。
其实是误解了许慎的原意。
许慎的原意是界说和例字彼此统一而相互阐明。
也就是说,其“假借”包括两类:一类是音同而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毫无关联,只是音同或者音近的关系;例如“熟”字,本义是食物被加热到可以吃的程度,但是后来此字被借用为疑问代词,并且为了区别本字与借字,还在本字下加形旁“火”而变成“熟”。
一类是转义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有联系,即通常所谓的引申关系。
例如“令”本义为命令,借为(今言“引申”)县令之“令”。
许慎以“令、长”为例说明假借,显然是把词义引申借字亦视为“假借”。
这在语文学时代是合情合理的。
(五)转注《说文叙》曰:“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后代学者对转注字的解说颇不统一,有形转、音转、义转三派;其中“主义派”有代表性的就有三家:“江声主‘形声即转注’说,戴震倡‘转注即互训’说,朱骏声为‘转注即引申’说。
”[3](117)要探明许慎的原意,只有采取“以许证许”的原则。
《说文叙》曰:“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据形系联,引而申之……毕终于亥。
”又解说“会意”云:“比类合谊,以见指撝”。
据此,所谓建类“之类”,应当是“方以类聚”“比类合谊”之“类”,也就是“事类”,即词语意义的事类范畴。
“一首”之“首”,即《说文叙》所言“建首”之“首”,也就是大致标志事类范畴的部首字。
因此“建类一首”就是建立事类范畴,统一部首意符。
所谓“同意”,指与部首意符所代表的类属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