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大师陈省身访谈录(悼念陈省身先生)
- 格式:doc
- 大小:21.64 KB
- 文档页数: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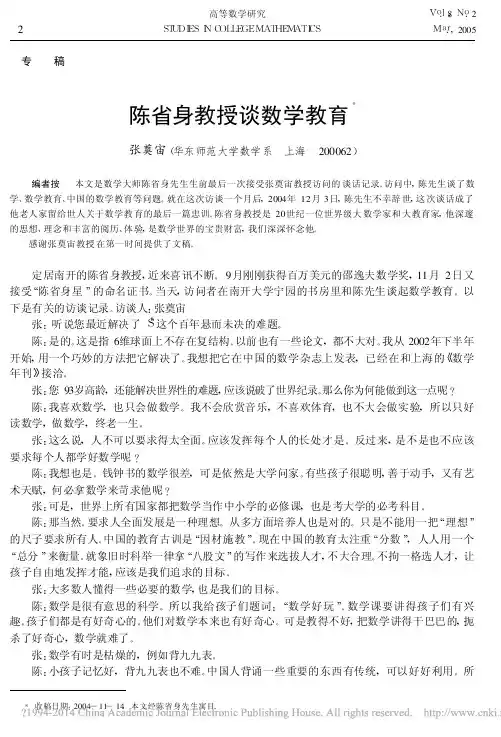
专 稿陈省身教授谈数学教育*张奠宙(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 上海 200062)编者按 本文是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张奠宙教授访问的谈话记录。
访问中,陈先生谈了数学、数学教育、中国的数学教育等问题。
就在这次访谈一个月后,2004年12月3日,陈先生不幸辞世,这次谈话成了他老人家留给世人关于数学教育的最后一篇忠训。
陈省身教授是20世纪一位世界级大数学家和大教育家,他深邃的思想、理念和丰富的阅历、体验,是数学世界的宝贵财富,我们深深怀念他。
感谢张奠宙教授在第一时间提供了文稿。
定居南开的陈省身教授,近来喜讯不断。
9月刚刚获得百万美元的邵逸夫数学奖,11月2日又接受“陈省身星”的命名证书。
当天,访问者在南开大学宁园的书房里和陈先生谈起数学教育。
以下是有关的访谈记录。
访谈人:张奠宙张:听说您最近解决了S 6这个百年悬而未决的难题。
陈:是的。
这是指6维球面上不存在复结构。
以前也有一些论文,都不大对。
我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用一个巧妙的方法把它解决了。
我想把它在中国的数学杂志上发表,已经在和上海的《数学年刊》接洽。
张:您93岁高龄,还能解决世界性的难题,应该说破了世界纪录。
那么你为何能做到这一点呢?陈:我喜欢数学,也只会做数学。
我不会欣赏音乐,不喜欢体育,也不大会做实验,所以只好读数学,做数学,终老一生。
张:这么说,人不可以要求得太全面。
应该发挥每个人的长处才是。
反过来,是不是也不应该要求每个人都学好数学呢?陈:我想也是。
钱钟书的数学很差,可是依然是大学问家。
有些孩子很聪明,善于动手,又有艺术天赋,何必拿数学来苛求他呢?张:可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把数学当作中小学的必修课,也是考大学的必考科目。
陈:那当然。
要求人全面发展是一种理想。
从多方面培养人也是对的。
只是不能用一把“理想”的尺子要求所有人。
中国的教育古训是“因材施教”。
现在中国的教育太注重“分数”,人人用一个“总分”来衡量。
就象旧时科举一律拿“八股文”的写作来选拔人才,不大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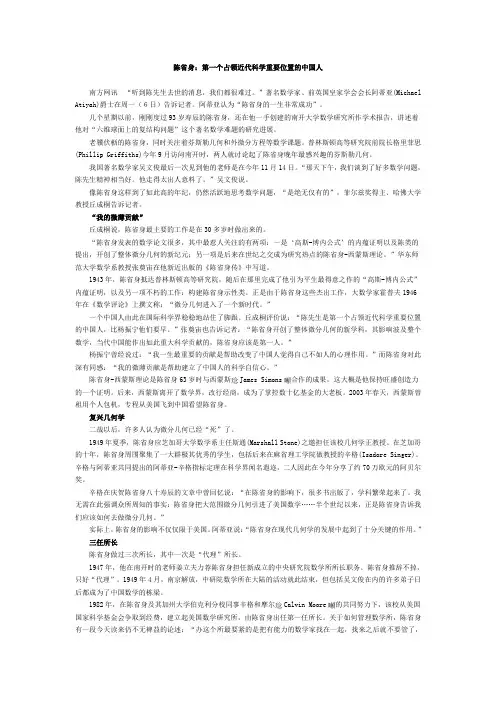
陈省身:第一个占领近代科学重要位置的中国人南方网讯“听到陈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们都很难过。
”著名数学家、前英国皇家学会会长阿蒂亚(Michael Atiyah)爵士在周一(6日)告诉记者。
阿蒂亚认为“陈省身的一生非常成功”。
几个星期以前,刚刚度过93岁寿辰的陈省身,还在他一手创建的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作学术报告,讲述着他对“六维球面上的复结构问题”这个著名数学难题的研究进展。
老骥伏枥的陈省身,同时关注着芬斯勒几何和外微分方程等数学课题。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前院长格里菲思(Phillip Griffiths)今年9月访问南开时,两人就讨论起了陈省身晚年最感兴趣的芬斯勒几何。
我国著名数学家吴文俊最后一次见到他的老师是在今年11月14日。
“那天下午,我们谈到了好多数学问题,陈先生精神相当好。
他走得太出人意料了。
”吴文俊说。
像陈省身这样到了如此高的年纪,仍然活跃地思考数学问题,“是绝无仅有的”,菲尔兹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告诉记者。
“我的微薄贡献”丘成桐说,陈省身最主要的工作是在30多岁时做出来的。
“陈省身发表的数学论文很多,其中最惹人关注的有两项:一是‘高斯-博内公式’的内蕴证明以及陈类的提出,开创了整体微分几何的新纪元;另一项是后来在世纪之交成为研究热点的陈省身-西蒙斯理论。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张奠宙在他新近出版的《陈省身传》中写道。
1943年,陈省身抵达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随后在那里完成了他引为平生最得意之作的“高斯-博内公式”内蕴证明,以及另一项不朽的工作:构建陈省身示性类。
正是由于陈省身这些杰出工作,大数学家霍普夫1946年在《数学评论》上撰文称:“微分几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一个中国人由此在国际科学界稳稳地站住了脚跟。
丘成桐评价说:“陈先生是第一个占领近代科学重要位置的中国人,比杨振宁他们要早。
”张奠宙也告诉记者:“陈省身开创了整体微分几何的新学科,其影响波及整个数学,当代中国能作出如此重大科学贡献的,陈省身应该是第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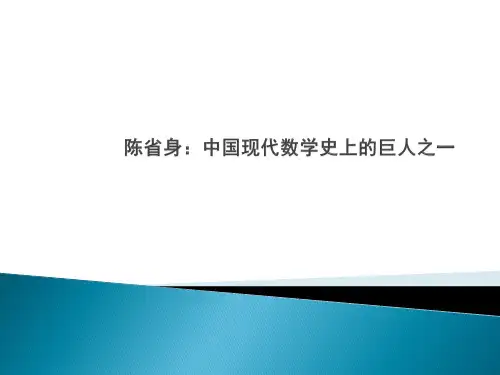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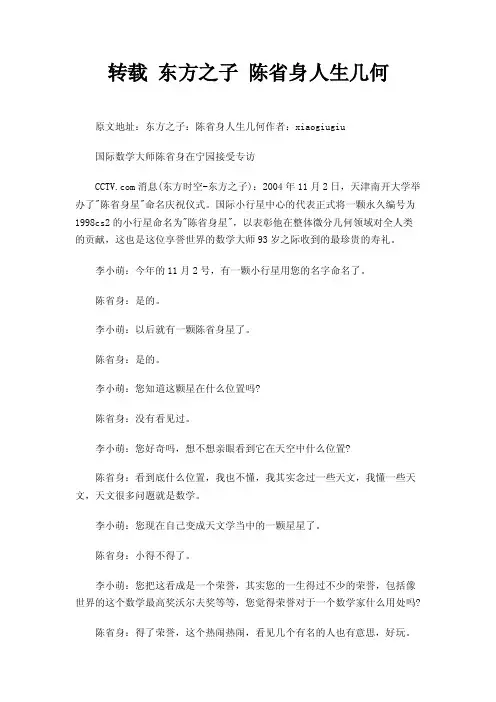
转载东方之子陈省身人生几何原文地址:东方之子:陈省身人生几何作者:xiaogiugiu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在宁园接受专访消息(东方时空-东方之子):2004年11月2日,天津南开大学举办了"陈省身星"命名庆祝仪式。
国际小行星中心的代表正式将一颗永久编号为1998cs2的小行星命名为"陈省身星",以表彰他在整体微分几何领域对全人类的贡献,这也是这位享誉世界的数学大师93岁之际收到的最珍贵的寿礼。
李小萌:今年的11月2号,有一颗小行星用您的名字命名了。
陈省身:是的。
李小萌:以后就有一颗陈省身星了。
陈省身:是的。
李小萌:您知道这颗星在什么位置吗?陈省身:没有看见过。
李小萌:您好奇吗,想不想亲眼看到它在天空中什么位置?陈省身:看到底什么位置,我也不懂,我其实念过一些天文,我懂一些天文,天文很多问题就是数学。
李小萌:您现在自己变成天文学当中的一颗星星了。
陈省身:小得不得了。
李小萌:您把这看成是一个荣誉,其实您的一生得过不少的荣誉,包括像世界的这个数学最高奖沃尔夫奖等等,您觉得荣誉对于一个数学家什么用处吗?陈省身:得了荣誉,这个热闹热闹,看见几个有名的人也有意思,好玩。
李小萌:好玩。
陈省身:好玩就是,不怎么要紧。
好玩,快乐,对数学有着浓厚而执著的兴趣,是陈省身七十年来致力于微分几何研究的主要动力。
陈省身1911年出生在浙江嘉兴。
他的求学历程几乎是一个神话:小学只上了一天,中学连跳两级,15岁考上大学,大三成为老师助手,一年获得博士学位。
32岁登上经典微分几何学的高峰而享誉国际数学界。
陈省身一生获奖无数,1961年荣获美国科技最高奖国家科学奖,1983年又荣获国际数学界最高奖沃尔夫奖。
2004年6月,他又众望所归摘得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首届邵逸夫奖,再次为中国人在世界上赢得了荣誉。
李小萌:您在今年的6月份也得了这个邵逸夫,这个奖您就获得了一百万美金的奖金。



数学大师陈省身的家教智慧师陈省身对于数学大师陈省身像摇滚巨星那样受人欢迎,他的儿子陈伯龙一直表示难以理解。
他亲眼目睹过父亲在香港科技大学演讲时的盛况。
讲座过后,学生们争先恐后冲向陈省身,将他包围,要他的签名。
就像那里坐着的不是数学家,而是一位摇滚巨星。
“摇滚巨星”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位名叫苏菲的职员用来形容陈省身的。
苏菲在天津机场偶遇一群人在接机,根据热烈的场面推测,来的要么是摇滚巨星,要么是电影明星。
可当那人坐着轮椅现身之后,她赫然发现,竟是伯克利的荣退教授陈省身。
在南开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陈先生百年诞辰举办的纪念活动上,陈伯龙对在场的数学家说,我们正在向一位伟大的数学家致敬,不过对我来说,他只是我的父亲。
他还说:“我的父亲是个普通人,只不过恰好具有数学天分。
”这位得过最高学术荣誉的大数学家是几代数学家的偶像,被认为影响了数学和物理学的走向。
可是,对于他的一子一女来说,“陈省身”永远是那个热爱全世界的美食、喜欢奶酪“越臭越好”、在餐馆里点菜比别人更为拿手的父亲。
帮着孩子寻找最有机会成功的位置,并且给出最好的建议陈伯龙和陈璞都继承了陈省身过人的智商。
但是,他们都没有子承父业。
陈伯龙读研究生时念过数学专业——“对我来说这好像是非常自然的选择。
”他说。
但是,在参加了第一个数学讨论班之后,他意识到,自己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数学家。
当他还是个本科高年级学生的时候,就修过一门“微分几何”课。
遇上难题时,他周末回家就向被公认为“微分几何之父”的父亲求助。
陈省身亲自教他。
“可惜,我不是个很好的学生。
我从未真正理解过螺旋的数学。
”他说。
尽管在微分几何上面临困难,陈伯龙还是决定以数学为研究生的专业,直到他参加了数学讨论班。
此时,陈省身建议他尝试一下精算学,进入商业而不是学术领域。
“他认为,我是个做事负责任、有条理的人,商业世界或许更适合我。
”在父亲的建议下,陈伯龙学习了精算,最终进入保险业,迄今为止,他做了大约40年的养老保险顾问。

一生做好一件事1 2004年12月,数学大师陈省身逝世,走完了93岁的人生。
我从纪念他的文章中知道,他有一个信条:“一生只做一件事。
”他对人说:自己只会做一件事,就是研究数学。
并且他要求自己:一生做好一件事。
他爱数学,有一个原因是:数学简单,只要一张白纸和一枝笔就行。
不错,陈省身生活在红尘之中,浮嚣之声一定会传到耳朵里。
但是,当他面对一道道数学题,面对白纸或黑板时,他会如老僧入定一样,把这个尘世都摒绝于外。
于是,他的一生得到最大的成功,他的生命能量发挥到极致。
杨振宁说,陈省身是可以和欧几里得、高斯和嘉当并列的数学伟人。
2 法国马赛有一位叫多梅尔的警官,为了缉捕一名奸杀女童埃梅的罪犯,查了十几米高的文件和档案,打了30多万次电话,足迹踏遍四大洲,行程达80多万公里。
多年来,由于他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追捕上,结果两任妻子都离他而去,他仍矢志不移,经过52年漫长的追捕,终于将罪犯捉拿归案。
那年,当他拿手铐铐住凶手时,已经是75岁高龄。
他兴奋地说:“小埃梅可以瞑目了,我也可以退休了。
”有记者问他,这样做值吗?他回答说:“一个人一生只要干好一件事,这辈子就没有白过。
”3 法国大画家雷杜德,他一生只画玫瑰,任凭环境如何变化,时代如何更替,他都心无旁鹜,只管画他的玫瑰。
他一生记录了170 多种玫瑰的姿容,组成了《玫瑰图谱》画册,在此后的180 多年里,以各种语言和文字出版了200 多种版本,平均每年都有新的版本问世。
雷杜德,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画他的玫瑰,但他画的玫瑰成了画中的极品,无人逾越。
雷杜德以他无比的执著,一生只挖一口井,即画玫瑰这口井,不管其它井里有黄金还是有白银,他都不为所动,不心生贪念,一生只坚守画玫瑰这口井,终于在这口井里“挖”出了玫瑰的芬芳和美丽。
4世界著名的昆虫学家法布尔,一生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研究他的昆虫。
一次,一位青年苦恼地对他说:“我每天不知疲倦,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花在我爱好的事业上,可结果总是收效甚微。

张恭庆:陈省身先生是一位完人南开新闻网讯(记者张国)“他的学问做得最好,没有哪个中国人能做到这个高度。
他的为人也最好,在世界上的威望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达到。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张恭庆日前到南开大学吊唁相交多年的师长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恭庆眼含热泪说:“大家公认陈省身先生是一位完人。
”张恭庆说,与陈省身20余年的交往让自己受惠终生。
1978年底,我国派遣首批50位学者出国进修,张恭庆和另一位中科院院士姜伯驹是仅有的两位数学界代表。
正是由于陈省身的帮助,他们得以入选。
当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陈省身分别致信纽约大学柯朗研究所和普林斯顿大学,向两校最好的数学教授力荐这两位中国年轻人。
而其余人尚未确定去向。
“陈先生作了周密安排,他对我们的帮助根本讲不完。
”张恭庆孤身赴美后,人生地不熟,徘徊在纽约火车站。
陈省身非常细心,特别嘱托洛克菲勒大学的逻辑学家王浩教授去车站,将张恭庆接回家住了一周。
此前,张恭庆根本不曾想过会与陈先生有交往,虽然听说他极为谦和,对后辈十分关心,却不曾料到自己能获得陈的举荐。
他说,陈省身是他所接触的第一位伟大的数学家。
1972年,他曾听过陈在国内的演讲,为他的学问所折服。
陈是名满天下的大数学家,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数学教师,“只能远远地看着先生,心中充满了景仰”。
1983年,陈省身邀请张恭庆到其主持的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工作。
二人交往渐多、了解愈深。
张恭庆对陈省身越来越钦佩:“陈先生的伟大成就自然不必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为人。
”“大家由衷地敬重陈先生,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
他为人谦和,却非常自尊、自信,为中国人自豪,具有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很多国外数学家都高度尊敬他,将他当作家中长者。
他与这些人在一起完全应付自如。
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
”张恭庆还记得当年陈省身把身旁所有念数学的中国人请来吃饭,给他们以鼓励。
在张恭庆看来,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数学之所以比其他学科进步更快,陈省身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领导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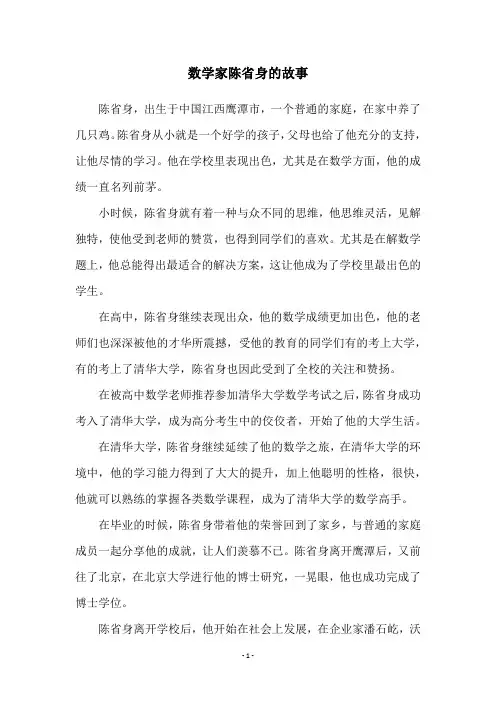
数学家陈省身的故事陈省身,出生于中国江西鹰潭市,一个普通的家庭,在家中养了几只鸡。
陈省身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的孩子,父母也给了他充分的支持,让他尽情的学习。
他在学校里表现出色,尤其是在数学方面,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小时候,陈省身就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思维,他思维灵活,见解独特,使他受到老师的赞赏,也得到同学们的喜欢。
尤其是在解数学题上,他总能得出最适合的解决方案,这让他成为了学校里最出色的学生。
在高中,陈省身继续表现出众,他的数学成绩更加出色,他的老师们也深深被他的才华所震撼,受他的教育的同学们有的考上大学,有的考上了清华大学,陈省身也因此受到了全校的关注和赞扬。
在被高中数学老师推荐参加清华大学数学考试之后,陈省身成功考入了清华大学,成为高分考生中的佼佼者,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在清华大学,陈省身继续延续了他的数学之旅,在清华大学的环境中,他的学习能力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加上他聪明的性格,很快,他就可以熟练的掌握各类数学课程,成为了清华大学的数学高手。
在毕业的时候,陈省身带着他的荣誉回到了家乡,与普通的家庭成员一起分享他的成就,让人们羡慕不已。
陈省身离开鹰潭后,又前往了北京,在北京大学进行他的博士研究,一晃眼,他也成功完成了博士学位。
陈省身离开学校后,他开始在社会上发展,在企业家潘石屹,沃尔玛,英特尔等大公司从事数学领域的工作。
他不仅仅带领研究团队开展数学研究,而且他把他的研究成果纳入到了公司的业务中,帮助公司开发出一系列的新产品,使公司的业务大增,带来巨大的经济利润。
今天,陈省身已经成为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在世界数学界享有盛名,他的数学成就也给当今的数学家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和灵感,也为世界科技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虽然他已经去世了,但他留给我们的智慧和精神,将继续传承。
附件二怀念恩师陈省身先生陈永川——摘自《南开大学报》第908期我与陈先生相识、相交18年,这在我已经度过的40岁人生中不算短暂。
回忆起18年恩师对我的教诲,可谓感慨万千。
陈先生除了数学以外,很喜欢给我讲人生的道理。
但他最强调的还是要做好的数学,要让自己有看家本领。
什么是好的数学,选择很重要。
他认为课题的选择是发展中国数学的关键问题。
要选择好的课题,不仅需要远见,还需要勇气。
陈先生在回忆起他自己的成就时,总是归结为他很幸运,说他是在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去到了正确的地方,找到了正确的老师。
他总说,不要盲目地跟潮流。
他是在别人都想去美国的时候,选择去了德国。
他选择的微分几何方向在当时也不是最热门的方向。
他的这些选择表明了他的智慧和勇气。
陈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明白了做数学需要选择和人生也需要选择。
陈先生在待人和处事上,胸襟宽广。
他讲话言简意赅,寓意深刻。
他幽默地说,他这个国际数学大师的头衔也不知是谁叫出来的,现在大家都这么称呼他了。
有一次,师母向我感慨,陈先生对自己要求这么高,是不是想成圣人。
先生也风趣地教导我,出了名的人就不能做坏事了,说话就必须小心了,特别是不能讲朋友的坏话,做好人和做坏人的差距往往在一念之间。
我知道陈先生所说的朋友指的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人都应该称为朋友。
陈先生很讲究持之以恒。
他常常教导我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有耐心,做研究要做一些好的小问题,循序渐进。
他也告诫大学生不要好高骛远,只有先把小事做好了,然后才能做大事。
先生的教诲使我明白了“耐心”二字的丰富内涵。
陈先生讲,做数学也需要练兵,功夫是慢慢练出来的。
陈先生的计算功夫很深厚,他能通过复杂的计算得到奇妙和深刻的结果。
陈先生喜欢武林的术语,“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有一次到他美国的家中做客,谈到这个话题时,我认为应该把“行家一出手”改为“行家一开口”。
没想到先生极为赞同。
先生特别强调刻苦的重要性,他说:“灵感完全是苦功的结果,要不灵感不会来。
陈省身——从数学家到爱国者的瑰丽人生国际数学联盟及陈省身奖基金会在香港宣布成立全球数学大奖“陈省身奖”,以表彰终身成就卓越的数学家,并纪念已故国际数学泰斗陈省身教授。
这是该联盟第一个向华人数学家致敬的奖项。
“陈省身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负责的第4个大奖,其他3项也均以数学家命名,分别为设于1932年的“菲尔兹奖”,是40岁以下数学家的最高荣誉;始于1982年的“内万林纳奖”,信息科学领域奖项;2006年开始颁发的“高斯奖”,在应用数学领域授奖。
而“陈省身奖”为终身成就奖,并且不限数学分支,授予“凭借数学领域的终身杰出成就赢得最高赞誉的个人”。
陈省身是谁?他是怎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成就?他为什么能获得国际数学界如此高的赞誉和表彰?……是的,当看到“陈省身奖”这4个字时,我们心中的种种疑问不禁油然而生。
本篇文章将解读一代世界级数学大师——陈省身。
标签:陈省身;数学;人物陈省身(Shiing-shen Chern),世界级的数学大师。
他的数学,至纯至美。
他的一生,至简至定。
他开创并领导着整体微分几何、纤维丛微分几何、“陈省身示性类”等领域的研究。
他是唯一获得世界数学界最高荣誉“沃尔夫奖”的华人,被国际数学界尊为“微分几何之父”“当今最伟大的数学家”。
曾先后主持、创办了三大数学研究所,造就了一批世界知名的数学家,其中华人科学家有杨振宁、廖山涛、吴文俊、丘成桐等。
晚年情系故园,每年回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主持工作,培育新人,只为实现心中的一个梦想:使中国成为21世纪的数学大国。
他不遗余力地为把中国建成数学大国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
数学——一生的兴趣和选择陈省身,1911年10月28日生于浙江嘉兴秀水县,因那年是辛亥年,所以号“辛生”,名字则出自《论语》——“吾日三省吾身”。
他只上过一天小学。
8岁那年,陈省身才去浙江秀水县城今嘉兴市里的县立小学上学。
可那天下午放学时,不知什么缘故,老师却用戒尺挨个打学生的手心。
追忆对陈省身的两次访谈及其他
张友余
【期刊名称】《高等数学研究》
【年(卷),期】2011(014)005
【摘要】追忆陈省身先生在他所接受的两次访谈中对中国数学界提出的殷切期望,介绍杨武之先生教书育人的事绩和成功经验.%In memory of the centennial of the birth of Shiing-Shen Chern, this paper revisits Chern's views and expectations for Chinese mathematics and mathematicians, and recalls the great teaching career and success stories of Mr. W.Z. Young.
【总页数】3页(P4-6)
【作者】张友余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数学系,陕西西安71006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N092;G649.29
【相关文献】
1.追忆陈省身--在陈省身数学奖设立二十周年及陈省身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 [J],
高伟山
2.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前两次工业革命有何不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杨虎涛教授访谈录 [J], 李雪
3.追忆广州会议——薛攀皋先生访谈录 [J], 熊卫民
4.当代最伟大的几何学家——陈省身先生访谈录 [J], 孙存金;郭培中
5.感人至深的领袖风度——追忆毛主席对我的两次教诲 [J], 熊复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走近数学大师这场雨从睡梦中就下起来,到中午了还在哗啦啦下个不停。
天地间白茫茫一片,街道,车辆,树木,路旁的建筑,撑开了的伞,全都湿漉漉的,显然洗去了不少市面上的喧嚣与浮躁,以及与浮躁同样轻飘飘的漫漫杨絮。
从天津西站到南开大学大约要走二三十分钟,出租司机是一位长相粗犷神色生动的中年人,高喉咙大嗓门,非常热情,一路上用他那地道的天津腔跟我们说话。
我们跟他说起陈先生,他立马接过话说,陈省身?知道。
大数学家,不得了!天津人懂点儿事的谁不知道啊!市长是谁咱不管他,你要说这陈省身,那可是人才哪。
司机一边骄傲着,一边还要左顾右盼,忙着找路旁哪儿有花店,以方便我们给陈先生买鲜花。
在随后同陈先生交谈时,我曾将这件事讲给陈老听,并说人们可以不知道市长是谁,但却知道数学家,这是一个好现象。
陈先生神情沉静地说,也有些是夸张了的。
宁园坐落在南开大学校园东南隅,浅黄色的小楼为两层建筑,周围绿树掩映,草木环绕,是南开大学专为陈省身先生建造的。
宁园门前是一斜道,汽车可以直接开上去,也便于陈老的轮椅行进,这样富于人性化的设计,能看出人们对陈先生的尊敬与爱戴。
进入楼厅,只见陈先生坐在轮椅上,鹤发童颜,上身穿一件紫红色的对襟唐装,显得特别雍容高贵。
我们从长桌的这一端望着他,犹如望着一座遥远星辰的降临,他那高风绝尘的风度与智慧,那温馨而持久的光芒,都令人不能忘怀。
甫一坐定,陈先生就颇有些出其不意地说,你们今天应该向我道喜。
看到我们面露疑惑,陈先生停顿了一下才解释说,以前患有静脉血栓,前些时候还住了两个来月的医院。
今天上午刚又去查了,一看,血栓竟然没了。
我们听明白后,忙说这倒真是件喜事,好消息。
陈先生如小孩儿一般得意,连连说,是,好消息,好消息。
世界上最要紧的是自由陈省身的父亲是秀才出身,他的名字来源于曾子的一段语录:“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陈省身只上过一天小学,原因是家里太珍爱他,怕他年幼体弱,上学不安全。
直到八岁那年,陈省身才去秀水县城里的县立小学上学。
可那天下午放学时,不知什么缘故,老师却用戒尺挨个打学生的手心。
陈省身虽然因为老实没挨打,可这件事却对他刺激太大,从此便不肯再迈进小学校门一步。
对小孩子不能管得太凶,管得太多的小孩子不会有出息。
陈省身先生说,我小的时候上学很晚,但出来以后家里就没再管过,后来的每一步路也都是靠自己。
现在好多家长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把孩子管得连气都喘不过来,这样管出来的孩子你怎么能让他将来有自己的发展?陈省身小时候全靠在家跟家人学习,自学了许多内容,后来读了四年中学,便直接越过考大学本科前本应补读两年的预科,以十五岁的年纪考取了南开理学院。
试想,假如陈省身也早早就落入私塾先生的手掌,天天心惊胆战地被戒尺打手心,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后来名满天下的数学大师。
记得十来年前我第一次去幼儿园接女儿时,只一探头,原先色彩斑斓的梦想刹那间就被一种强烈的失望所淹没了:女儿和所有的小朋友一起背着手,挺着小胸脯,贴墙坐在小凳上。
她们战战兢兢地望着阿姨,脸上尽是讨好和紧张。
板着面孔的阿姨不让她们闹,不许她们叫,不准她们动,就连撒尿都要先来后到,举手报告。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人,能有多大出息?所以,一个人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社会上,都受到了太多的限制,太多的压抑。
人性不能张扬,社会自然也就要受到窒息。
陈省身先生说,这个世界上,最要紧的就是自由。
不管在哪里,不管是什么行道,凡是管得越凶的地方,就越不会有大的发展。
记者: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尽管国家贫穷落后,但却出了不少人才。
数学也好,物理也好,都有一批世界级的大家冒了出来。
比如说,在您大学毕业的一九三○年之前,光是在国外以数学工作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十几个之多,后来就更多了。
依您看,这其中有些什么样的原因?陈省身:至少有一个原因是我们这一群人在国外。
国外环境相对好一些,学术上的事情,搞研究的条件有保障。
环境好你自然就容易有成就。
中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怎么样在国内发展这么一种环境,使得国内的人也可以做第一流的科学工作。
记者:环境太重要了。
习惯使人麻木,在另外一种不同的环境中观察,很容易就能看出一种环境的状态。
没有好的土壤,人才就没办法生长起来。
陈省身:对极了。
中国现在也还是有人才的。
很可惜,前些年国家对人才太不注意了。
现在好些了。
这个需要时间,需要政府支持。
记者:您回国定居有两年了,在数学方面或其他科技方面,能不能感觉到,国内是否在向上走的一个趋势?陈省身:是的,往前走。
我老是讲,南开的数学现在就很好。
记者:不次于芝加哥大学?陈省身:不见得差。
在南开,现在我们找了一大批年轻的人才,很不容易。
至于有些人出去了,不愿意回国,主要还是国内现在的待遇低了一点。
另外,在国外朋友多,工作比较容易,条件很好,有效率。
中国的行政部门管得有些多。
记者:这个管是指什么个管?是干涉太多吗?陈省身:嗯,干涉太多。
干涉太多,哪怕是好意的,想帮忙的,从长远看效果也不好。
最好是不理他,他自己知道该怎么搞。
真正的天才是自己蹦出来的。
你要知道,顶理想的就是他一个人做工作。
大家都鼓吹交流,讲科学需要合作,需要互相帮忙,这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
真正好的工作,第一流的工作,是一个人做出来的。
一个人的创见是自己努力和灵感的结晶,很少是和一群人讨论的结果。
有时候,一个人忽然一下子就有了一个很好的想法。
值得注意的是,你有了这个很好的想法,有时候不见得当时就能知道,也许要等多少年之后,才发现这个方法的绝妙之处。
记者:您的话特别耐人寻味。
自由状态有助于人才的出头,有助于奇思异想。
所以,陈寅恪鼓吹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所以,对人才最大的爱护,是给他自由。
陈省身:对极了,自由。
最好的科学是发现出来的,不是计划出来的。
可是国内你要做什么东西,政府都要你的报告,而看报告的人往往并不真正懂,这也只能浪费时间。
记者:咱们打报告是为了上项目,要经费,那么,国外不写报告,像类似于经费这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陈省身:在国外,一般情况下他不大需要经费,因为他这个待遇好,比如在美国,一个普通教授一年的薪金在十万美元以上,可以不理政府,一般的问题自己可以处理好。
再比如中国的科学家成为院士要申请,奖金要申请,什么都要先申请,外国没这个。
制度之下,这也可能是没办法的事情。
从前一个数学家的最高标准,是从国外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我们国家现在所急需做的,是充实各大学的研究院,充实博士学位,人才由自己训练。
我想,最要紧的是,政府要让大家放开手脚,要多给予支持,不支持科学就不能发展。
最好是多一点钱。
记者:这恰恰可能是我们最缺少的了。
没有好的环境不能干事,没有钱那也干不成事。
陈省身:不过,有些人是不应该支持的。
他不大行,打报告打得倒很好。
现在中国出了一种新八股,一二三四,报告打得好极了,真正的工作他却不会做,所以并不行的。
记者:您在国外多年,可能感觉强烈一些。
其实,有什么样的气候就会长什么样的草,国内的这种新八股并不太新,也有一段历史了。
假大空。
陈省身:奇怪的是,这样的东西竟然还能起一点作用。
做事业首先要学会选择数学研究的最高标准是创造性:要达到前人未达到的境界,要找到科学最深刻的关键。
陈省身先生说,数学研究与其它科学相比,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它是向多方面发展的。
当今的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往往有几个主题。
但数学的研究方向对个人来说,自由选择的余地比较大。
所以工作不必集中于几个大的中心,研究人员可以较为分散。
一个有能力有决心的人,可以随不同的途径,完成自己的志愿。
在南开,陈省身先生做出主修数学的第一次选择,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数学能力一向比较好,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上第一堂化学实验课,在吹玻璃管时手足无措,从此便对各种理化实验有了畏惧。
二年级时,陈省身师从中国现代几何学的创始人、哈佛博士姜立夫先生,开始研习几何学,初步领略到了数学王国壮美绮丽的无限风光。
不过,这时的陈省身并没有梦想成为一名数学家,而只是觉得可能会做一名中学数学教师。
一九三○年,陈省身在南开大学毕业时,决定报考清华大学数学系,投身到不久前从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的孙光远教授门下学习。
在陈省身看来,孙光远教授是当时回国的数学博士中惟一还在继续作研究,并在国外发表论文的学者,这当然令他由衷钦佩,于是便随孙先生潜心研究投影微分几何学。
在此期间,陈省身和华罗庚成为清华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一九三二年,著名微分几何学权威布拉希克教授由德国汉堡大学来华访问,作了以“微分几何的拓朴问题”为题的系列演讲,令陈省身大开眼界。
同时,陈省身在密切关注世界数学动向中开始意识到,他这几年下了大功夫的投影微分几何已经远离当前数学发展的主流,前途不大,而他后来做出巨大建树的所谓“大范围微分几何”,即研究微分流性上的几何性质,此时已被他隐约感觉到了。
一九三四年夏,陈省身从清华研究生院毕业,并顺利通过了美庚款的留学考试。
美庚款的留学所在地按理说应该是在美国,而且当时的许多留学生一般也都愿意去美国,但陈省身对布拉希克教授心仪已久,觉得到德国这样的世界数学中心留学必定适合于自己,最后终于如愿所遂。
在汉堡不到两年,陈省身便获得了博士学位,其研究内容涉及到了法国大数学家E•嘉当的理论在微分几何上的应用。
尽管嘉当的理论是超时代的,但陈省身当时已经被嘉当的数学天才所折服,所以,陈省身又放弃了留在汉堡大学研究代数数论的优越时机,于一九三六年决定转学法国巴黎大学,追随嘉当,进行更精深的数学探索,并且,后来得以借助这位伟大数学家的肩膀,在几何学的高峰上迅速攀登上升。
一九三七年,陈省身回国,先在清华,后因战争迁至西南联大。
在这几年,他的数学研究成果开始为世界数学界所瞩目。
一九四三年夏,他应聘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三年间,陈省身先生开辟了微分几何的广阔空间,其著名的“陈氏示性类”研究成果,对数学乃至理论物理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他后来的一系列以“整体微分几何”为主的研究成就,被誉为“影响遍及整个数学”,而陈先生在回顾自己数十年的治学历程时,认为这一切结果之所以发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自己漫长人生的每一步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记者:我曾看过一个资料。
有一次,台湾清华大学请您和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一起参加一个座谈会,中间有位姓黄的教授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如何选择研究的方向和领域?杨振宁先生说,大学中有很多优秀的研究生,他们自己和老师都不能预测未来的成就有多大,可是二三十年后,成就却可能悬殊。
事后一回想,成功的同学在当时不见得就比不成功者优秀许多。
这其中的一个基本道理是,有人走对了路,左右逢源,而有人却走错了路,再努力也很难有大成就。
我们知道杨振宁先生曾是您的学生,他的这些见解,和您做学问首先要做出正确选择的观点也是非常一致的。
陈省身:选择有时几乎就能决定一个人整个的命运,当然,这种选择是指关键时刻的那几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