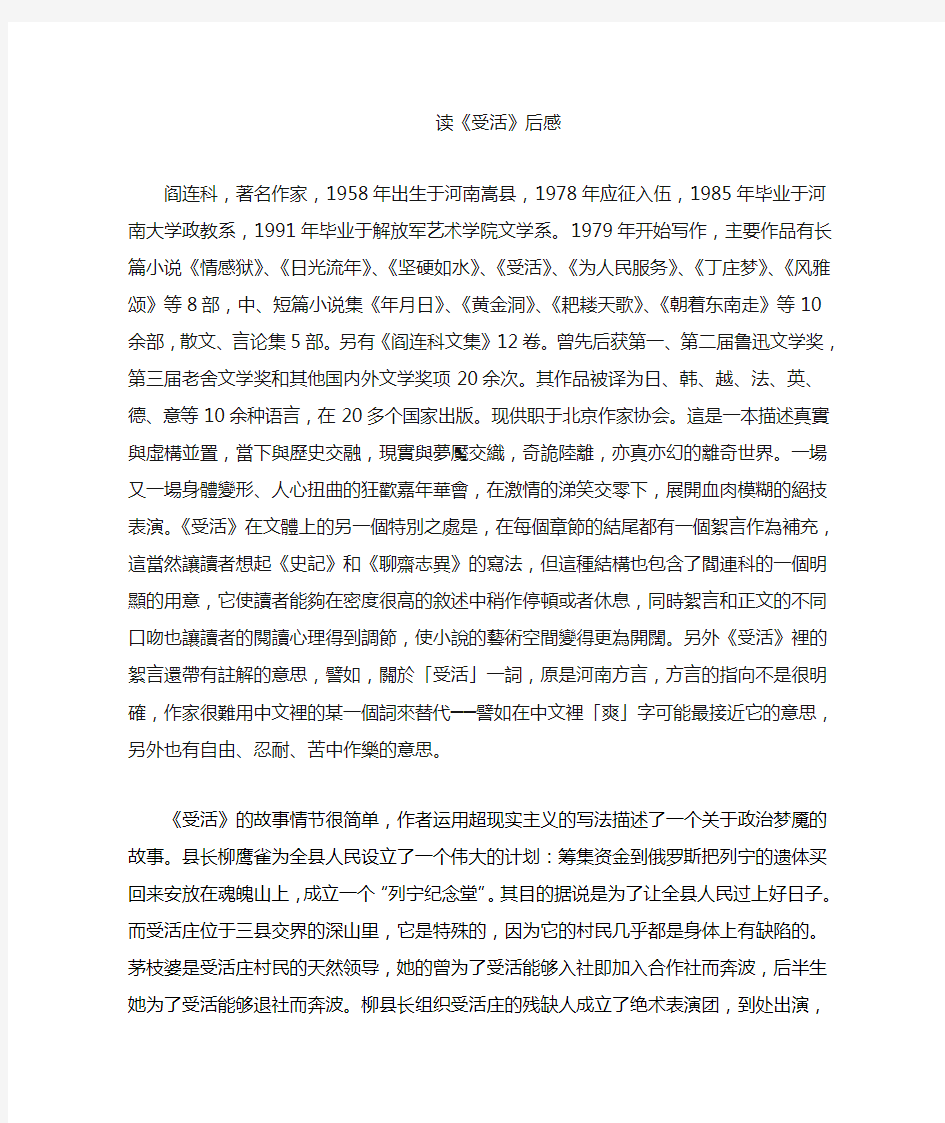

读《受活》后感
阎连科,著名作家,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雅颂》等8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10余部,散文、言论集5部。另有《阎连科文集》12卷。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其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等10余种语言,在20多个国家出版。现供职于北京作家协会。這是一本描述真實與虛構並置,當下與歷史交融,現實與夢魘交織,奇詭陸離,亦真亦幻的離奇世界。一場又一場身體變形、人心扭曲的狂歡嘉年華會,在激情的涕笑交零下,展開血肉模糊的絕技表演。《受活》在文體上的另一個特別之處是,在每個章節的結尾都有一個絮言作為補充,這當然讓讀者想起《史記》和《聊齋志異》的寫法,但這種結構也包含了閻連科的一個明顯的用意,它使讀者能夠在密度很高的敘述中稍作停頓或者休息,同時絮言和正文的不同口吻也讓讀者的閱讀心理得到調節,使小說的藝術空間變得更為開闊。另外《受活》裡的絮言還帶有註解的意思,譬如,關於「受活」一詞,原是河南方言,方言的指向不是很明確,作家很難用中文裡的某一個詞來替代──譬如在中文裡「爽」字可能最接近它的意思,另外也有自由、忍耐、苦中作樂的意思。
《受活》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作者运用超现实主义的写法描述了一个关于政治梦魇的故事。县长柳鹰雀为全县人民设立了一个伟大的计划:筹集资金到俄罗斯把列宁的遗体买回来安放在魂魄山上,成立一个“列宁纪念堂”。其目的据说是为了让全县人民过上好日子。而受活庄位于三县交界的深山里,它是特殊的,因为它的村民几乎都是身体上有缺陷的。茅枝婆是受活庄村民的天然领导,她的曾为了受活能够入社即加入合作社而奔波,后半生她为了受活能够退社而奔波。柳县长组织受活庄的残缺人成立了绝术表演团,到处出演,以筹集购买列宁遗体的资金,而他这样作给于茅枝婆的承诺是过后让受活庄退社。整个故事就是围绕着购买列宁遗体这条线索而展开的。
閻連科在《受活》裡進行了一場野心宏大的語言歷險,它的完成不僅對作家本人來說意義非凡,而且對於當代大陸小說界而言,更是一種充滿刺激性和建設性的小說書寫方式力量。
中国自古就有“天高皇帝远”的说法,这充分说明了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和广泛性,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基层政治权力运行逻辑的变异以及其与高层政治理念的断裂。事实上,阎连科正是给我们刻画了底层的政权运行逻辑。柳鹰雀是个虚假的政治人物,说虚假是因为他虽身处政权编制内部却缺乏政治理念和政治眼光。他的养父为他指引了一条步步高升的道路,于是他每一次得到升迁都会在更高一级的职位的下面划上红线以激励自己向更高的职位看齐。柳鹰雀步步升迁的过程很荒诞可也是很真实的。他有着独特的思维,购买列宁遗体是这种思维最为典型的体现,这种思维总能得到上级的关注,于是他步步升迁。这是一种为当官而政治的思维,其实也就是当官的逻辑之一。另外,柳县长为政的手法也影射了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政治现象――群众动员运动。柳县长的伟大计划激发了全县人民的热情,人民视这个计划为最大的神圣事件,在这个计划败破之前几乎没有任何人对它有一丝的怀疑。可在事情败破之后,人们发现它原本便是这么荒诞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我没有仔细研讨过,只是人民群众在这场政治事件中的表现实在让我有疑问。群众是盲目的吗?群众被什么遮蔽了双眼?群众又为什么丧失了思考的能力?群众到底有多少参与和影响政治的能力和必要呢?所以这是为官的第二个逻辑――群众动员。(谈到此,我想起了波特兰罗素在《社会改造原理》中表达的观点,罗素是个唯心主义者,他认为冲动比有意识的目标在形成人的生活方面有更大的影响。虽然这些体验和理由还没有颠覆唯物史观在我脑中的位置,可是我的确开始象吴毅老师那样思考了,是人民群众还是社会精英创造了历史?他们是如何创造的?)
对于柳鹰雀这个体制精英来说,茅枝婆是非体制精英,她是受活庄的天然领导,村民都愿意听她的调遣。因为感受到了加入合作社的好,她为处于三县交界无人管理的受活庄奔波入社,好不容易入社了,可是大饥荒马上来了。受活庄的残缺人勤奋劳作,平静而有序,互助而团结,所以他们依旧粮棉满仓。只是他们的粮食也绝对满足不了外界整个的饥荒,人的肚子饿了,人性也就丧失了,受活庄几乎是被洗劫一空的。为此,受活饿死了好多人,于是人们又开始怀念起以前
没有入社的日子来了,他们抱怨茅枝婆,茅枝婆的下半生就为受活人寻求退社。茅枝婆在本书中是个有着理想却悲剧的人物,作者在描写她时有一种关于怜悯和希望的温情,只是就连这种温情也无法影响茅枝婆政治上的无为和生活上的悲苦,作者为茅枝婆安排了一个在我看来是最好的结局:茅枝婆穿着自己缝制的十几套寿衣死去了,在临死前她看到了自己一生为之奔波的关于退社的政府文件。
读茅枝婆的故事我深深的被触动了。她是受活的天然领导,她领着一群残缺人好好的劳作和生活,她为村民谋福利,她为了村民的事而殚精竭虑。可就是她无法影响柳县长组织成立绝术表演团,她甚至用生命的代价也无法阻止受活人的离开。茅枝婆这个民间精英被体制精英柳县长处处排挤,即使如此,茅枝婆也永远是和受活人连在一起的,她在每一次与外界的争执中都尽最大可能来保护受活人的利益。可似乎一切的努力都是无力的,甚至她的努力在外界看来又几分可笑。茅枝婆是个政治上的悲观角色。通过茅枝婆来看人民群众,我又在想,人民容易被什么样的政治说教激发,人们会为什么政治目标鼓舞,人们相信怎样的政治逻辑,人们对什么又政治体验,而人们的政治到底该如何来作?在政治事件中人民群众处于怎样的方位?人民群众内部有多少关于政治的张力?
茅枝婆似乎是传统社区中“家长式”的人物,她似乎有着传统的思想与行动,可是我却不愿这样来理解她。我更多的把她当成理想式的人物,她有着对于受活人纯粹的关爱之心,她没有进入政治(当然是指柳县长之流视野内的政治),但她却是个真正的政治人。她政治上的才能与号召力建立在自己原始而纯粹的政治理念上,可是在遭遇到任何外界的政治压力时这种理念是那样的无力。什么样的政治才是适合这世界的运转的?我们所遭遇到的政治难道只会是政治权术的堆砌吗?
以文学眼光来说政治问题似乎有些不合适宜,可我还要提出一个纯文学的问题。阎连科无疑是用颇为荒诞的想象力来构建《受活》的,可以我之见,作者的荒诞手法并不纯熟。这点可以从购买列宁遗体这个事件的结局看出。作者为此事件安排的结局是柳县长派去购买列宁遗体的团队被止于京城,省长斥责柳县长这帮人是政治疯。超现实的荒诞事件却止于这个现实主义的理由,看来不合时宜。也许是因为除此之外无法止笔,所以作者选择了这个现实主义的理由,而后作者又描述了一个同样荒诞的发展:柳县长身残后入住受活庄了。至此故事结束了,
柳县长的归宿是受活庄,而茅枝婆的归宿却是由自己的精神建构起来的天堂。
不知道作者安排这样的结局是想给谁以讽刺?希望?而我看到茅枝婆的死却是异常的平静。她穿着寿衣生活,她是个时刻准备受死的人,所以她死的干净,死得其所。不过我依然惊诧于柳鹰雀最后入住受活。止是对柳鹰雀的希望还是对于受活的希望?这是对柳县长本身的讽刺还是对政治制度的讽刺?或者根本就是对人民大众的讽刺?作者没有答案,我也没有答案,可但愿将来能有答案。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 2003年第4期 文学纵横阎连科小说修辞解读 徐 漫 摘 要:作家阎连科小说中的小人物身上折射出一种虽微弱但执着的理想主义光辉,同时,也在小说语言上进行修辞探索和美学追求,从而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和回味无穷的美感。 关键词:小说语言 修辞格 文本智慧 多种修辞格兼而有之在阎连科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他善兼取多种修辞格而用之,才思喷涌,构思巧妙,想像新奇,联想丰富,得心应手,引人入胜。他的多种修辞格兼用中,意境灵动,意象独特。尤其是其中所蕴藏的诗意和韵味,不仅丰富了作品所展示的内容,同时也使读者获得了解读与欣赏的喜悦激动和审美情趣。例如: 离开港口时,有许多胡子老兵,泪水砰砰啪啪跌落在舰栏上,如落夹的豆粒在甲板上滚来滚去。 ( 1949年的门和房 ) 这段话兼用摹绘、比喻和夸张三种修辞格。 砰砰啪啪 的摹声, 落夹的豆粒 的新奇比喻和 滚来滚去 的夸张,将 胡子老兵 离开故土时的无奈和依依不舍,以及舰艇在汹涌海浪中的颠簸起伏表现得惟妙惟肖,读者脑际浮现着一幅伤感的动态的画面。 他看见这泥屋门口的丝瓜,昨儿他来时还只是绿旺旺地在院墙上爬挂着,今儿一醒来丝瓜花竟又 浓又烈开了一院墙,把泥坯木架的院墙都染得通红 了。用小麦壳和泥糊成的屋墙上,居然长着一层小 麦芽,又嫩又绿,仿佛那四周的屋墙原本是竖起的 四面草地儿。院里的甬路两旁,长满了蓑草、茅草、 野菊、齿角芽、车轮花、葛根旺和有浓稠甜味的紫香 蒿。小白花、小红花和小黄花在草间开得无所顾 忌,把用料礓砂石铺成的甬路挤得扭腰歪脖儿。喇 叭花盛气凌人地爬在所有的草顶上,几分邪荡地开 满一世界。不消说那花草中间有着野蜜和狂蝶,有 不知名的飞蛾和草虫。院子里涌满了草腥和花香。 到处是白光和影儿。虫蛾在花草上飞舞时磨翅、撞 头、似黄似红的香味在日光中飘散时有震耳的响 动。野草为争夺空中的场地扭扭打打。( 朝着东 南走 ) 在上述的段落中,其语言修辞中可以看出作家兼用转类、比喻、比拟和通感等四种修辞格,把门前屋院描绘得如诗如画。 绿旺旺 作为状语修饰的对象是 爬挂 ,如果将语序调整为 绿旺旺的丝瓜 , 绿旺旺 作为定语修饰 丝瓜 ,则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相符。而作家突破正常的汉语语法规范,运用转类修辞,突出了 丝瓜 旺盛的生命力和生长动感,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 染得通红 的隐喻和 仿佛那四周的屋墙原本是竖起的四面草地儿 的明喻的运用,都令读者赏心悦目,我们好似身临童话般的境界,又好似在欣赏水粉画。各色小花 在草间开得无所顾忌 ,把 甬路挤得扭腰歪脖儿 、 喇叭花盛气凌人 、 几分邪荡地开满一世界 、 野草为争夺空中的 26
现代知识分子的沉沦与救赎——论阎连科的长篇小说《风雅颂》 洪治纲/欧阳光明CCHong Zhigang, Ouyang Guangming 【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专题号】J3 【复印期号】2009年02期 【原文出处】《南方文坛》(南宁)2008年6期第101~105页 【英文标题】Depravity and Salvation of Modern Intellectuals: The Novel Feng Ya Song by Yan Lianke 【作者简介】洪治纲,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欧阳光明,暨南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阎连科无疑是一位充满了忧患意识和叙事激情的作家。长期以来,他总是借助丰沛的艺术想像和狂放不羁的话语方式,不断地深入到当代社会内部,尤其是围绕着各种隐秘的权力结构形态,展示了种种尖锐且又不乏荒诞色彩的人性景观。特别是在那些以耙耧山脉一带的中原文化为背景的作品(像《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年月日》、《受活》等)中,阎连科不仅生动地演绎了各种欲望喧嚣与人性狂欢的生存场景,还揭示了乡村社会结构中权力之间彼此勾连且又相互倾轧的复杂状态,传达了作者内心深处极度焦灼与愤懑的精神状态。可以说,在中国当代作家群里,我们几乎很少看到有人像他那样,对现实永远保持着高度紧张的关系。也正是这种紧张关系,使得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一种“剑走偏锋”的极端方式,为他内心的某种理想,不断地向各种现实伦理发出巨大的挑战。 这种持之以恒的挑战姿态,在他的长篇新作《风雅颂》中再一次展示出来。在这部小说里,阎连科以中国最有名的高等学府“清燕大学”为背景,通过一位大学教授、《诗经》研究专家杨科的荒诞命运,在充满诙谐和反讽的叙事语调中,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气质和精神操守进行了一次无情的解构。 “混乱时代”的知识分子及其生存境域 严格地说,《风雅颂》并不是一部非常优秀的长篇。从内涵上看,作者对当代中国大学内部的体制结构以及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域的了解,还只是满足于一些共识性的经验之上,缺乏精深有效的思考。尽管有人认为,他“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踹了一 脚”①,但其意义也仅限于这种发泄的层面。从叙事上看,小说虽然延续了作者一以贯之的黑色幽默式的反讽基调,但在处理人物内心深处的一些精神状态时,脸谱化甚至平面化的倾向亦十分明显。但是,这部小说之所以让我们产生某种内心的震动和阐释的欲望,主要在于,阎连科非常敏感地触及了中国当代文化体制中存在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即一种被规则化和制度化的时代病症——它在强大的工具主义实用原则的驱动下,使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不得不接受被现实制度扭曲了的命运。“事实上,艺术和学术活动的独特和有价值之处,正是它没有直接受控于工具主义风气。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不是着手生产顾客需要的东西,而是追求实现更高远的目标。”②而在实际生活中,实利化的求知和无私的真理性的求知之间的界限却被模糊了,它导致了缺乏实用价值的人文知识分子越来越走向边缘,也越来越失去精英化的角色。而在《风雅
阎连科小说修辞论 阎连科在他的小说中建构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耙耧世界”。从《寻找土地》、《年月日》到《日光流年》、《受活》,阎连科力图从“形式进入意义”,刻意回避了小说的故事性、情节性,漠视人物形象塑造,有意识增强形式表达上的结构化,增强语言的丰富性,突显人类的本质生存意义。 本文借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理论,通过对作者写作意图的分析,来分析阎连科小说的“为谁写”和“怎么写”。从具体的创作过程来说,作者最首要的修辞选择是语言选择。 作为土生土长的河南农民之子,豫西方言则成为了阎连科的“终极词汇”。首先,阎连科通过对“方言”的整理,来试图恢复被“共同语”所完全屏蔽掉的历史真相。 其次,以絮言与正文互文,使现实、历史、传说很自如地相互沟通。正文与絮言在互文中表现出一种自由叙事的精神,同时让以往完全由作者控制意义的“封闭文本”呈现出开放的状态,取消了“文本意义”的“绝对性”与作者的“独断性”,让不同的读者能达到不同的理解。 最后,“狂欢化”的文革语言,与特定语境中的政治相关联,形成独特的历史语境,而人虽然表现上是话语的操纵者,事实上一直为话语所控制。在独特而荒诞的历史语境中,叙述者以自身的癫狂叙述了特定时代的癫狂,用话语将一种特定的历史语境进行夸张性“还原”,让“狂欢化”的语言来显示出自己的荒诞性,从而达到对于历史苦难的更深层次的理解。 布斯认为,作者必须通过“自然的客体”对自我象征意义的表现来唤起读者的情感。在阎连科的小说创作中,有一个特别的“自然客体”值得关注——那就
是“身体”。 阎连科让“身体”在场,让“身体”处于日常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成为一切社会符号与意义的承担者。他从身体与存在、身体与疾病、身体与欲望三个角度来表达人与世界的关系。 首先,身体必须依托粮食与繁衍而保住肉身的存在,其次,他创造残病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关于“身体与健康”的看法,人的疾病、人的抗争、人的失败,这是人所必须经历的生命历程,而身体与时间的战争将永不止息。最后,人类的情欲与外在的压抑因素总处于一种具体的对抗之中,身体的压抑往往会导致情绪的癫狂,从个人的情欲想象到情欲引发的革命事件,都使人看到了身体是如何受规训的,而欲望的力量是如何突破外在的禁忌得以实现的。 同时,在阎连科的身体叙事中,女体被物化为一种自然景观,对应的是男性心中的本能,而本能在接受文明的规训之后,往往直接被扼杀或被激发,成为自然的破坏者。女体,始终无法进入历史,与荒野保持着同一性。 这种命运,正是命运对于人类、权力对于规训者绝对权威的映照。阎连科在小说中表达了自己的时空修辞意识,在文本的结构修辞上,根据不同类型的读者设定了“情智双结构”。 首先,阎连科放弃对线性时间的把握,从人物的心理时间走进他的世界,展示的是编年之外的“真实个体”与“真实事件”。因此,在阎连科的小说中,时间只是一种循环,呈现出“圆形”而非“线性”时间状态。 他利用对时间的控制,让历史走出编年,回到具体的事件与生命体验之中,传递了历史过程中被忽略的生命真相,达到了对“此在”的本质理解与关照,从历史回到事件,突显出历史的“盲点”。同时,在圆形的时间中,阎连科精心构建了一个
论阎连科的童年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刘富斌 指导教师刘保亮 摘要 童年经历作为个体成长经历的第一个阶段,人类在这个阶段所形成的对于世界的认知往往是根深蒂固的,这种认知对于个体的影响深远而巨大。作家是一个依赖于自身认识进行艺术创作的群体,童年经历对作家的影响直接融入到文学创作过程,体现在文学作品中。阎连科自幼生活于穷苦的豫西乡村,封闭的农村环境,加上革命的时代背景,以及长久的笼罩在整个家庭的贫穷和病痛,使得阎连科对于穷困、疾病、权利、城乡差距有着直接的感受,也正是因为家庭的贫困使得阎连科很早便辍学打工,这些独特的童年经历,使阎连科对于社会底层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而广泛的底层话语也成为其核心的创作价值所在。阎连科赖以成名的“瑶沟系列”“耙耧山脉系列”也正是来源于其童年农村的生活经历,童年对于苦难和病痛的深刻认知也成为其文学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主题构件。可以说,这种童年经历在直接影响着阎连科自身人生道路选择并形成了其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同时,融入到其文学创作过程中,成为其文学创作重要的主题来源和创作风格形成的重要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阎连科;童年;创作主题;创作风格
The childhood experiences of Yan lianke's impact on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ABSTRACT Childhood experience as an individual experiences growing up of the first stage, at this stage of human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tends to be ingrained, the effect of the cognitive for individual deep and vast. The writer is a dependent on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f art creation, childhood experiences on the writer's influence directly into the literary creation process, reflected in literary works. Lianke have been living in the poor western countryside, closed rural environment, plus the time background of revolution, and for a long time over the whole family poverty, and pain, naturally makes for rights,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poverty, disease, and there is a direct feeling, it is because of family poverty make lianke work very early drop-out, these unique childhood experiences, naturally makes for the bottom has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understanding, and a wide range of the creation of discourse has become the core of the underlying value. Lianke's famous "yao ditch series" and "series" palou area mountains is also comes from its rural childhood life experience, his childhood for suffering and pain deep cognition has become the very important theme in the literature of artifacts. Naturally, so to speak, the childhood experiences in a direct impact on their life path choice and formed its unique "world outlook, the outlook on life, values" at the same time, into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in the process,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his literature creation important source and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factor for the formation of style. KEY WORDS: Yan lianke ;childhood ;Creative theme;writing style
石剑锋:《阎连科谈<炸裂志>》,《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9月29日。 《炸裂志》里的“炸裂村”或“炸裂市”依然位于您文学地图上的耙耧山脉,但看完小说,我们知道小说里这座利维坦式的城市更可能是中国南方某一座城市。“炸裂”特指哪些城市呢? 阎连科:其实这部小说写的就是深圳、海南或其他新兴大城市的故事。小说里这座叫炸裂的城市,它的发展和深圳极其相似。我做的无非是把深圳或者海南搬到了我所熟悉的河南某个地方,也就是我文学地理位置上的耙耧山脉。这部小说完全来自于一次对深圳的偶然好奇。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去深圳开一个笔会,大家都说深圳非常开放,这里的开放无非是指有很多大楼,但到了晚上还是一片寂静。可是过了十年再去,就完全不同了。但最令我感触的不是深圳的发展,而是有一次从香港去深圳。在从香港到深圳的一瞬间,你感受到两个城市的迥异之处:一个极其有秩序,一个极其无秩序。深圳的发展虽然极其惊人,但代表的却是中国任何一个大都市,也可以表现中国当下的状态。对我来说,我想写的故事、人物忽然找到了他们的舞台。这个舞台可以是深圳,也可以是海南或者其他新兴发展的城市。这些城市的迅速发展让人不可思议,它的扭曲和荒诞也超过我们的想象。也就是在那个一瞬间,我忽然感觉到,我可以写那个故事了!到了小说中,炸裂这个村庄最后发展成一座超级大城市,成为直辖市,这座城市甚至还有野心成为独立国家。 在《炸裂志》的开头,这座城市的发家来自于小说主角孔明亮带领村民扒火车。您这么写,是想说明发展背后有不可告人的某些秘密吗? 阎连科:这部小说的开头,炸裂村里的男人是扒火车的,女人是卖淫的。这些细节、情节的真实性是不需要去考察的。深圳这样的城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但在中国人的记忆中,1980年代很多有各种问题的人都到深圳、海南去发展了。这些人都不是我们概念中的老实人。我们确实知道,1980年代南下淘金,淘到第一桶金的很多并非诚实可靠的人,而是最有能力但最靠不住的人,甚至不少是从监狱里出来的。这部小说把我们带回到1980年代的记忆中。扒火车是有象征性的。无论是扒火车还是火车提速,在其背后隐藏着原罪,也就是偷盗的不只是火车上的物资,小说里偷盗这个行为把我们的人心也盗走了。从那开始,人心就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可以回望1980年代对万元户的崇拜,中国人现在对金钱的崇拜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我们看到炸裂村的发展是从男盗女娼开始的,但这恰恰也是无数真实的生活片段连接起来的。比如,我听某个地方的村民说,他们区政府里的领导,不少人都在监狱里待过。这不是作为笑话来说的,而是想说,现在有的基层干部成了什么样子?也就是这些真实的生活片段,成了我的故事的一部分。在这部小说里,几乎没有一个正常人,更不要说小说里主角孔明亮四兄弟。老大一心要当校长,老二明亮后来当了市长,老三要带三千万百姓去远征。这些人都不可思议。老四看上去很正常,但其实也是有问题。他在事业、家庭方面都不想,一心想着把所有人拉回正轨,但他的力量那么微弱。其实在那样一个环境下,他也是不正常的。明亮的妻子周颖用女人去获取一切,也是不正常的。所以,这样一部小说,要么作家不正常,要么小说里的所有人物确实不正常。
阎连科长篇小说文体研究 阎连科是河南代表作家之一,也是一位极具文体创新意识的小说家。三十年以来,他勤奋高产,笔耕不辍。 自短篇起步,以中篇过渡,至今以长篇蜚声文坛,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阎连科为我们奉献了许许多多直击心灵的佳作。透过这些作品,我们看到了不曾见过的世界,有旧时东京市井中小人物的生活百态,有农民子弟、底层军人艰辛的成长历程,还有当代乡村发展的荒诞现实。 从市井到乡村,从现实到魔幻,阎连科娴熟地变换讲故事的方式,以耙耧山脉为圆心渐渐耕耘出了一个自足的世界。阎连科后期的长篇小说之所以能成为创作生涯的里程碑,不仅仅因为题材有所创新,更多是由于其文体自觉意识的萌发,对他而言,单单是讲故事的方式就能催生故事本身。 本文以阎连科长篇小说的文体为研究对象,从语言和结构两方面来发掘阎连科的小说特质,以期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指导写作。绪论部分简单介绍作者的成长背景,对其创作阶段进行梳理,同时概述了对于阎连科长篇小说文体的研究现状,以及论题对于现实的指导意义。 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围绕阎连科长篇小说的语言特点,从方言土语、修辞手法、语言风格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探讨作者采用方言、变换辞格的效果及其意义,指出其小说语言博采众长,源于本土又高于本土,借助丰富多变的修辞手法,形成了虽显艰涩却绚烂奇谲的语言风格。第二章研究了阎连科长篇小说中体裁的杂糅,归纳出其小说与剧本、公文、诗歌或歌谣杂糅的三种现象,分析这种对传统文体的改造在文中的具体表现,赏析种种杂糅所呈现的效果。 第三章以长篇小说文体创新的代表作《受活》、《日光流年》、《炸裂志》为例,
分别阐述“絮言体”、“索源体”、“方志体”这三种作者独立创造的结构的词语来源,进而分析种种结构在文中的具体表现以及所含意义。结语从作家个人对于贫穷和疾病的体验、故土民间文化的熏染以及其他作家的影响三个方面来对阎连科长篇小说多元杂糅的整体特点进行归因。
1.阎连科谈“平民意识” 阎连科《当代作家评论》1991. 1 2.阎连科将会怎样——阎连科创作漫谈朱向前《文学评论家》1991.2 3.论《瑶沟人的梦》的艺术特色谢馨藻《湖南科技大学学报》1991.3 4.瑶沟的世界及其他——评阎连科的四部中篇小说张德祥《文论月刊》1991.11 5.和平环境下的军人灵魂——读阎连科《和平雪》于秋雨《小说评论》1992.6 6.阎连科小说的人格力量黄献国《当代作家评论》1993. 1 7.农民情结:难圆的梦——阎连科小说漫评徐国俊《当代作家评论》1993.4 8.阎连科小说创作散论丁临一《文学评论》1993. 4 9.未被吉星高照的阎连科丁临一《当代作家评论》1993. 5 10.乡土的梦想——论阎连科近年来的小说创作赵顺宏《小说评论》1993.6 11.生命的谛视——读阎连科近年中篇小说林舟《当代作家评论》1994.4 12.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新时军旅文学一个重要主题的相关阐释朱向前《文学评论》1994.5 13.对农民军人的爱与知——阎连科印象兼跋《和平寓言》朱向前《小说评论》1994.6 14.《和平战》:健康人格与偏狭心理吴然《小说评论》1994.6 15.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阎连科军旅小说创作的定位朱向前《当代作家评论》1994.6 16.《乡村死亡报告》评论小辑《青年文学》1995.7 17.“恋土”:一个纠缠着河南作家的情结张喜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2 18.仰仗土地的文化阎连科《当代作家评论》1997. 1 19.大悲悯的情怀——评《阎连科文集》王侃《牡丹》1997. 2 20.乡土的歌哭与守望——读阎连科的乡土小说林舟《当代文坛》1997.5 21.咀嚼生命——读阎连科及他的小说《年月日》薛胜利《东方艺术》1997.5 22.守望乡土——阎连科素描张文欣《牡丹》1997. 5 23.立足本地的艰难远行——解读阎连科的创作道路柳建伟《小说评论》1998.2 24.论“瑶沟人系列小说”的价值与局限曹书文《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3 25.抗战精神与民族意识――《年月日》与《老人与海》人文精神比较师华《人文杂志》1998.4 26.仅仅仰仗土地文化是不够的——关于长篇小说《生死晶黄》致阎连科西南《小说评论》1998. 5 27.“农家军歌”变奏――读阎连科中篇小说《大校》张玉华《解放军文艺》1999.2 28.超越于皈依的困厄――浅析《大校》的文化批判意义瑶维荣《解放军文艺》1999.3 29.被挤压下的生命寻找人生之光——阎连科《日光流年》解读王晓岚《吕梁高专学报》1999. 1 30.“不是我展现人物,而是人物展现我”——阎连科访谈录阎连科、侯丽艳《牡丹》1999. 2 31.阎连科小说人物探析谭笑风《中州大学学报》1999. 2 32.一部世纪末的奇书力作――阎连科《日光流年》讨论纪要王蒙等《东方艺术》1999.2 33.长篇小说:新的文学风向标——以1998年的几部作品为考察个案朱向前《东方艺术》1999. 3 34.反抗与悲剧——读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南帆《当代作家评论》1999.4 35.《日光流年》及其他何向阳《当代作家评论》1999. 4 36.关于《日光流年》对话阎连科、侯丽艳《小说评论》1999.4 37.死亡与时间——长篇小说《日光流年》主题揭示及其他冯敏《小说评论》1999.5 38.听见一种声音万里《小说选刊》2001. 1 39.陌生的世界不懈的寻求——读阎连科的《朝着东南走》刘峰《当代文坛》2000.2
阎连科小说中的村长形象研究 阎连科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有着独特风格的作家,他凭借一系列优秀作品赢得了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与好评。阎连科是农民出身,河南伏牛山脉和耙耧山脉交界处的小村庄是生他养他的家乡,也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所在。 农民与作家的双重身份在阎连科身上重叠,但他总是把农民这个身份看得更重一些,他立足乡土、守望乡土。乡村养育了阎连科,但同时带给他的还有无尽的黑暗,乡土世界落后、贫穷、愚昧的面貌从小就给他留下了阴影。 他在成长中既受惠于乡土,又目睹乡土世界藏污纳垢的那一面,在此背景下,对土地的“又爱又恨”刺激着阎连科剥去一切外壳,追寻乡土的真实面目,这成为了他作为一名作家的自觉。在阎连科的小说中,乡村世界的人际关系复杂得像一张分不开的网,生活在乡土中的人们,手中若是没有些权力,是不可能有立足之地的。 阎连科在表现“耙耧世界”乡土权力运作时,往往借助小说中的村长形象来展开,塑造了一系列饱满的村长形象。本文即以阎连科小说中的村长形象为研究对象,试图对阎连科笔下的村长形象进行考察,在权力关系复杂的小说的乡土世界里,探究作家对权力的态度,对乡土真实书写的不懈追求,以及对反映乡土世界人情、人性的责任担当,并试图阐释农民出身的阎连科对土地的爱与恨。 “我就是王法”是阎连科笔下的村长形象的真实写照,在权力视域下,村长形象可以分为“掌权者”和“逐权者”两个类型。掌权者们手中的权力可细分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话语权力、长老权力四类,而无论掌握了这其中的哪一类权力,村长们都是“耙耧世界”中皇帝一般的存在,能够对无权者进行权力的宰制。 逐权者一类的村长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会不择一切手段实现目标,在
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 2000年度—— 长篇小说 01.《中国:一九五七》尤凤伟《江南》2000年第4期 02.《富萍》王安忆《收获》2000年第4期 03.《大浴女》铁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3 04 .《怀念狼》贾平凹《收获》2000年第3期 05.《大漠祭》雪漠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8 中篇小说 01.《青衣》毕飞宇《花城》2000年第3期 02.《追上来啦》熊正良《人民文学》2000年第11期 03.《拯救父亲》白莲春《人民文学》2000年第9期 04.《谁家有女初长成》严歌苓《当代》2000年第5期 05.《不要问我》东西《收获》2000年第5期 06.《重瞳》潘军《花城》2000年第1期 07.《生活秀》池莉《十月》2000年第5期 08.《纪念碑》薛荣《上海文学》2000年第8期 09.《太阳为谁生出来》何玉茹《长城》2000年第4期 10.《库兰》红柯《当代》2000年第6期 短篇小说 01.《上海女人》杨显惠《上海文学》2000年第7期 02.《清源寺》徐小斌《百花州》2000年第4期 03.《援军》赵琪《解放军文艺》2000年第10期 04.《河柳图》迟子建《作家》2000年第10期 05.《一点红》蒋韵《山西文学》2000年第9期 06.《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阿成《啄木鸟》2000年第11期 07.《冬天我们跳舞》唐颖《收获》2000年第2期 08.《准备好了吗》戴来《收获》2000年第3期 09.《保卫樱桃》裘山山《人民文学》2000年第10期 10.《蛐蛐蛐蛐》毕飞宇《作家》2000年第2期 2001年度—— 短篇小说 1 《湖道》漠月《雨花》2001年3期 2 《日子》陈忠实《人民文学》2001年8期 3 《遍地白花》刘庆邦《钟山》2001年2期 4 《乡村、穷亲戚和爱情》魏微《花城》2001年5期 5 《逃亡》杨显惠《上海文学》2001年2期 6 《鞋匠与市长》赵本夫《中国作家》2001年12期
阎连科的“欲望乡村”——以《坚硬如水》和《丁庄梦》为例 摘要: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和《丁庄梦》两部作品描绘出一幅“乡村世界的欲 望图景”,“权欲”、“情欲”、“财欲”发酵,与时代背景、个体命运、人性情感发生 交织,完成对欲望的完整叙述。欲望描写带有个人情感需求和普遍意义价值,引 起我们对乡村世界欲望小说的思考。 关键词:乡村世界、权欲、情欲、财欲 许多作家都有其独特的“叙述世界”作为其小说的铺展空间,阎连科也不例外。阎 连科是带有浓烈地域色彩的作家,他出生于河南农村,瑶沟为他提供了创作空间、影响了创作风格,其中原乡土小说既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又具有反映中国乡村群 像的普世价值,带有反思和批判意味。在阎连科的乡土世界中,权力、情感与金 钱的饥渴为这个本应质朴的世界添上一抹浓烈的“欲望”的色调。 一、《坚硬如水》中的“权欲”和“情欲” 《坚硬如水》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一个刀锋上的时代,在极端的社会条件下,人的欲望也随之膨胀并走向极端。主人公高爱军对于权力和情爱的追求近乎 癫狂,当欲望与外界失衡,欲望的火焰便会反噬自身,注定了其悲剧性的结局。 (一)高爱军的权力魔怔与时代梦魇 《坚硬如水》中的权力欲望主要表现在人物高爱军身上,高爱军对权力有着狂热 变态的追求。他为了得到权力而向权力屈服,娶了村支书的女儿程桂枝。之后更 是不择手段,与夏红梅一起制造伪证,扳倒镇长,丧失道德底线,凡是阻碍其在 权力的道路上狂奔的人和物都要灭亡。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人们对个人的狂热崇拜渗透进日常观念和生活的 方方面面,这个时代对权力的追求是普遍性的。作者用大篇幅的文革特有“红色” 语言渲染那个时代的氛围,用个体放大的欲望去消解和掩盖时代的残忍,用一种“后现代”的书写方式完成对文革时代的调侃。个人是集体的映射,个体呈现是时 代的扭曲与压迫。 高爱军的成长背景设置在“二程故里”,宋代理学家二程的后裔集聚的地方,也是 封建观念最浓厚的地方。小说中外界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浪对程岗村没有丝毫影响 就足以说明其与外界脱节的封闭与落后。程岗镇相当于一个充满封建势力和压抑 人性的地方。在这种乡村权力架构中,自私自利、胜者为王的观念深入人心,没 有人同情弱势群体,这种封建权力的不对等性浸染了人的认知意识,对成长中的 人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受到的压迫在自己有足够能力时必然返还给施压主体, 形成人对权力的初步渴求。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我爹出门去唤接生婆,到镇口上日本人把刺刀捅进他的肚子里,旋即肠子就瀑布一样流出来,火辣辣把鬼子的刺刀缠绕着,血腥腥把祖 国的土地弥漫着,红旺旺将民族的仇恨燃烧着……”[1]高爱军具有“丧父”的特征, 其成长没有庇护,心灵更易受创。近代研究表明,幼年丧父的男子长大后会有强 烈的恋母情节。在生活中,寻求父亲的替代品,把对父亲的爱与恨、对父亲的渴 求与崇拜投射到一个权威人物身上。[2]并且其父亲的死就充满了血腥、暴力与民 族间类似于“权力”的压榨,为后文做了暗示与铺垫,安全感的匮乏更增加了对自 己的保护欲,希望能通过自小所见的无所不能的权力来填补自己的安全空白,无 形中在脑海中建立起对权力潜在的渴求欲。 (二)情感欲望 1.情欲的物化
阎连科的阅读故事 “在我生命最初的阅读阶段,书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取之不尽的银行,不断地阅读,就是从银行不断地取款,为我所用。到了现在,阅读确实已经像品茶像吃饭,像日常喝点小酒,书已经变成我的拐杖了,成为我行走的另外一条腿,它帮助我行走得更远。可能最终等到我老了,躺在病床上了,阅读才会从我的生命中慢慢消失。”8月25日,著名作家阎连科对本刊记者娓娓道来他和阅读之间的故事。 《西游记》:启动想象力的机器 上世纪60 年代,阎连科的大姐得了股骨头坏死,但那时候没有X 光,不知道什么病,只能经常在床上躺着。她经常躺在床上看书。每天晚上在油灯下手不释卷。阎连科的母亲心疼油,忍不住就吆喝:“那是啥稀罕,深更半夜也不睡,快把灯灭了!”阎连科纳闷儿:是啥东西迷住了姐?就偷偷去翻着看,原来是《西游记》,就趴在床边看起来。这部神话传说,仿佛是一个启动他想象力的机器,使年龄不大的阎连科,从此获得了丰富的想象力。 没几天,他看完了《西游记》,发现了一个和现实生活 的世界完全不一样的熠熠生辉的小说世界,从此开始酷 爱看书。但那个时候是文革时期,看的书非常有限,基
本都是红色经典。很多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红色经典", 像《红日》、《红岩》等,他都是在姐姐床头读完的。 当他把姐姐的存书风卷残云般饕餮一空,然后又千方百 计四处找书看。书使人丰富,因为读书,阎连科与他的 同龄人很快拉开了距离,越来越深地沉入书中的生 活…… 《分界线》:孤岛上看到的一叶小舟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中期,阎连科考进了高中,每天到十里之外去上学,晚上在煤油灯下看小说,星期天同父母一块儿下地挣工分,到了假期,又得跟着有亲戚的建筑队去搬砖、提灰做小工,每天能挣一块几毛钱。 每每想到读完高中之后,就将同父亲、母亲一样,永生永世地伏在黄土之上,阎连科心里就会生出无尽的惆怅和无奈,开始对学校、乡村和土地,还有所处的环境产生一种莫名的厌恶与恐惧,那时候,他最大、最美好的愿望,就是高中毕业之后,离开农村,逃离土地,到城里找一份每到月底就可以到会计面前签字领工资的工作。 就在这稍有些绝望的紧要关头,阎连科读到了张抗抗的长篇小说:《分界线》。对他来说,这是一部异常伟大和不朽的著作。她对阎连科的意义,要远远超过《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那样的世界名著。 阎连科通过《分界线》了解到,张抗抗是下乡到北大荒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4-6题。 说田野 阎连科 ①说起田野,委实人为地有了过多的诗意。但它诗性的本质,却是极少有人去发现,去展示,去述说。我们看到的田野的文字,如同山梁上叠起的阳光,一杆杆、一束束,把黄褐色的土地照得很是溢光流彩了,十二分地金银化了,可那些真正从土地深处溢入生活营养了人生的东西,却被写诗的笔忽略去了。也读到过田野上生发的苦难的文字,泪成得很呢,血也红得很,然那土地对泪和血的吸收却是不见了的,至于血泪在和土地融合之后,新的温馨的丰沃,也是很少有人看到。 ②我想,田之所以称为田野,并不是因为收割前它四处漫流着黄灿灿的麦香,不是秋天那个很少的天数里,山上山下,漫无边际地到处都是红彤彤的色泽。这些都未免太为诗情,太为次要。我是这样想的,你既然是田野,你不生长庄稼你干什么?作家和诗人都是田野的外姓人家,只有农民们不是。那些人喜欢面对田野惊惊乍乍。老成的农民们,面对田野是什么也不说的,他们月深年久的沉默,和田野深处那没有形声的诗性,其实有着无尽的沟通和暗合。如果你们觉得我还像个农民,记得我的祖祖辈辈都还埋在田野里的话,或多或少,就请信我这么一句:真正的田野是没有的。诗是诗人们的诗,文是文人们的文,田野上并没有那些优美的景物,没有那些诗文。 ③真正理解田野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就是农民。农民不把田野称田野,农民称田野只说一个字:地。田野这词语本身,就是被诗化了的。几分的诗意,就隐含了几分美美妙妙的假。地,才是还原了田野的本身哩。 ④地也并不是说有土就是地,必须有劳作,有风不调、雨不顺,必须有许许多多的人,不知从哪一辈开始,祖先们就都埋在那里,连骨头都化成了雾浓浓的土,不小心才会偶见一块布满细小蜂窝的骨核,这才算勉勉强强有了地样。还应该说的,地上不一定要有战马的蹄痕,牛蹄比战马的蹄痕更为接近地心。马蹄太历史化了。田野已经被历史压得潮汗浸浸,那些真正在田野或地里生存的人,却大多被历史挤到了马路边上,且似乎也是该着的,他们也那么地不以为然。 ⑤我以为,地也好,田野也好,诗也好,文也好,真正的田野,不是土的丰厚或者贫薄,不是丰收或者歉收,不是马蹄或者牛蹄,该是庄稼和荒草之间,秋天和冬天之间,活着和死去之间,孤孤寂寂地站了一个人;男人也好,女人也罢,但他(她)是必必然然的农民,脸上布满了爷爷的皱纹,搭了一缕奶奶枯干在额上的灰白的头发,远远地瞧去,宛若一柱被雷击劈了的桩木,近了,你才看见,他或她的怀里,拖了一个死了的孩娃。孩娃的肚子鼓着,嘴角挂了浅红灿灿的笑。他是吃了新的将熟的毛豆胀死了的,所以他死了还笑。那人是去找埋藏孩娃的地方,走了千里万里,昼行夜宿,黄昏前赶到了田野的一沃田头,说这里好哩,旱能浇,涝能排,你就在这儿活吧孩娃,你爷你奶还在家等着生老病死,我回去给 他们准备棺材去了。也就把孩子埋在那儿走了。一路上没有回头望那小小的新坟,却叮叮当当留下一路的歌声:“一路的庄稼一路的土,一路的活人一路的丘,今天我从庄稼地里过,明天我往庄稼地里留。”这歌声是土地真正深刻的诗哩。 ⑥这个时候,土地才真正有了历史,有了诗性,成了田野。我一直认为,历史并不是时间的持续,人生也不是时间的记忆,只有埋了孩子还一路唱着从土地上直走过的脚印才是时间、历史和记忆。那留下了这种脚印的土地,是真正的人生命运和田野的诗性。 (摘编自《阎连科散文》,有改动)4.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章以“说田野”为标题,由田野所具备的诗性本质引出话题,先指出有些人不是真正清楚其含义,再用农民与土地的沟通、暗合来阐述田野的内蕴。 B.作者认为,先有土,经过血汗的奋战和浇灌,才逐渐成为地;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先辈们前赴后继,把土地沃成田野,赋予了田野诗性。 C.埋了孩子还唱着歌的农民,和很多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一样,因为承受了太多的苦难,见惯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所以他们变得隐忍、麻木。 D.全文“说”田野,“说”既含描写之意,又有“论”的意味。“说”的对象是田野,也有田野上劳作的人;“论”了田野的内涵,也赞美了田野的诗性。 5.本文第⑤段在语言运用上极具特色,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5分)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ab7261472.html, 阎连科乡土小说探讨 作者:陈浩然 来源:《名家名作》2019年第07期 [摘; ; ; ;要]中国乡土小说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最为典型的还是鲁迅和沈从文为主的写作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思想逐渐开放,中国文化开始向着国际化发展,很多西方思想逐步深入中国,因此我国乡土小说的写作手法发生了转变,同时揭示了更多的文化意义,阎连科就是典型作者之一,对其文学观念和写作手法进行探索,分析他的乡土小说特点,希望能对当代乡土小说的研究给予一定的启发。 [关; 键; 词]阎连科;乡土小说;文学研究 我国的乡土小说经过了几个发展时期:“鲁迅时期”“沈从文时期”“新时期”等,这几个时期的乡土小说各具特色,都反映了每个时期一定的社会现象和文学特色。从其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是受到一定限制和约束的,不能大胆直接地反映一些社会现象,表达方式也都是若隐若现。但是阎连科的乡土小说却能独树一帜,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地域代表性,本文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一、阎连科乡土小说文学特点 阎连科属于新时代的乡土小说作家之一,他勇于探索,不断尝试文学创新。他的写作风格既包括了莫言等现代小说家的写作特点,同时也有自身特色。人们称之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因为他的小说敢于揭露现实社会的真实性,既有看似荒诞的故事情节,同时也深刻描绘了中国苦难的社会现实。 他利用仰视的姿态去揭示平凡而真实的乡土世界,从民间最基础的人和事物出发,关注人性、生存状态,用多样化的表现手法去描述他眼中的乡土世界。此外,阎连科的小说充分利用了语言和感官双重体验进行创作,描述性语言比较多,因此给读者一种色彩冲击力和触碰之感,将乡村中富含的模糊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因此,阎连科的乡土小说是兼具绝望和无奈、痛苦和同情的。 二、阎连科乡土小说的艺术世界 阎连科的乡土小说揭示了一个特殊的艺术世界,通过《我的现实我的主义》《发现小 说》这两部理论著作,可以透视出阎连科的文学观,即“神实主义”。 1.阎连科艺术世界中的文学观 阎连科是一个善于挑战、勇于揭露现实社会的作家,很多最底层、最丑陋的社会现象经常在他的创作中得以凸显。他曾经说过:“现实很重要,真实更重要。”但是现实中很多作家都碍
读《受活》后感 阎连科,著名作家,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雅颂》等8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10余部,散文、言论集5部。另有《阎连科文集》12卷。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其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等10余种语言,在20多个国家出版。现供职于北京作家协会。這是一本描述真實與虛構並置,當下與歷史交融,現實與夢魘交織,奇詭陸離,亦真亦幻的離奇世界。一場又一場身體變形、人心扭曲的狂歡嘉年華會,在激情的涕笑交零下,展開血肉模糊的絕技表演。《受活》在文體上的另一個特別之處是,在每個章節的結尾都有一個絮言作為補充,這當然讓讀者想起《史記》和《聊齋志異》的寫法,但這種結構也包含了閻連科的一個明顯的用意,它使讀者能夠在密度很高的敘述中稍作停頓或者休息,同時絮言和正文的不同口吻也讓讀者的閱讀心理得到調節,使小說的藝術空間變得更為開闊。另外《受活》裡的絮言還帶有註解的意思,譬如,關於「受活」一詞,原是河南方言,方言的指向不是很明確,作家很難用中文裡的某一個詞來替代──譬如在中文裡「爽」字可能最接近它的意思,另外也有自由、忍耐、苦中作樂的意思。 《受活》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作者运用超现实主义的写法描述了一个关于政治梦魇的故事。县长柳鹰雀为全县人民设立了一个伟大的计划:筹集资金到俄罗斯把列宁的遗体买回来安放在魂魄山上,成立一个“列宁纪念堂”。其目的据说是为了让全县人民过上好日子。而受活庄位于三县交界的深山里,它是特殊的,因为它的村民几乎都是身体上有缺陷的。茅枝婆是受活庄村民的天然领导,她的曾为了受活能够入社即加入合作社而奔波,后半生她为了受活能够退社而奔波。柳县长组织受活庄的残缺人成立了绝术表演团,到处出演,以筹集购买列宁遗体的资金,而他这样作给于茅枝婆的承诺是过后让受活庄退社。整个故事就是围绕着购买列宁遗体这条线索而展开的。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列小题。 打 阎连科 (1)我每每想起我父亲,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 (2)我记得的第一次痛打是我七八岁的当儿。那时候,每年的春节之前,父亲都会千方百计存下几块钱,换成一沓儿簇新的一角的毛票,放在他的苇席下,待到了初一那天,发给他的儿女和正月来走亲戚的孩娃们。可是那一年,父亲要给大家发钱时,那几十上百张一毛的票儿却没有几张了。那一年,我很早就发现那苇席下藏有新的毛票儿。每天上学时,我总是从那席下偷偷地抽走一张,在路上买一个烧饼吃。 (3)从初一到初五,父亲没有给我脸色看,更没有打我和骂我,他待我如往年无二,让我高高兴兴过完了一个春节。可到了初六,父亲问我偷钱没有。我说没有,父亲便厉声让我跪下了。反复问我偷没有,我都说没有,父亲便狠力地朝我脸上掴起耳光来。我的脸又热又痛,到了实在不能忍了,我才说那钱确是我偷的,全都买了烧饼吃掉了。然后,父亲就不再说啥儿,把他的头扭.到一边去。不看我,可等他再扭头回来时,我看见他眼里含着的泪。 (4)第二次,仍是在我十岁之前,我和几个同学到人家地里偷黄瓜。仅仅因为偷黄瓜,父亲也许不会打我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其中还有人偷了人家那一季卖黄瓜的钱。那钱是人家一年的口粮,不把钱还给人家,人家一家就无法度过那年的日子。
(5)父亲知道后,也许认定那钱是我偷的,毕竟我有前科。他让我跪在院落的一块石板地上,先噼里啪啦把我痛打一顿后,才问我偷了人家的钱没有。我说没有,父亲就又噼里啪啦地朝我脸上打,直打得他没有力气了,才坐下直盯盯地望着我。那一次,我的脸肿了。因为心里委屈,夜饭没吃,我便早早地上了床去。睡到半夜父亲却把我摇醒,好像求我一样问:“你真的没拿人家的钱?”我朝父亲点了一下头。然后然后父亲就拿手去我脸上轻轻摸了摸,又把他的脸扭到一边,看着窗外的夜色和月光。一会儿他就出去了,坐在院落里,孤零零地坐在我跪过的石板地上的一张凳子上,望着天空,让夜露潮润着,直到我又睡了一觉起床小解,父亲还在那儿静静地坐着没有动。 (6)第三次,父亲是最最应该打我的,应该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可是父亲没打我。那时我已经十几岁。到乡公所里去玩耍,看见一个乡干部屋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精美铝盒的刮脸刀,我便把手从窗缝伸进去,把那刮脸刀盒偷出来,回去对我父亲说,我在路上拾了一个刮脸刀。 (7)父亲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我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素洁的乡村孩子了。到后来,那个刮脸刀,父亲就长长久久地用将下来了。每隔三朝两日,我看见父亲对着刮脸刀里的小镜刮脸时,心里就特别温暖和舒展,好像那是我买给父亲的礼物一样。多年后,我当兵回家休假时,看见病中的父亲还在用着那个刮脸刀架在刮脸,心里才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楚升上来。我对父亲说:“这刮脸刀你用了十多年,下次回来我给你捎一个新的吧。”父亲说:“不用,还好哩,结实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