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
- 格式:pdf
- 大小:262.00 KB
- 文档页数: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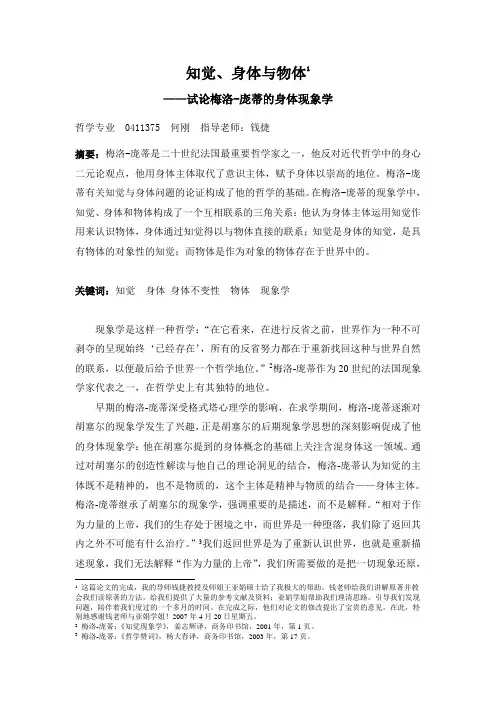
知觉、身体与物体1——试论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哲学专业 0411375 何刚指导老师:钱捷摘要:梅洛-庞蒂是二十世纪法国最重要哲学家之一,他反对近代哲学中的身心二元论观点,他用身体主体取代了意识主体,赋予身体以崇高的地位。
梅洛-庞蒂有关知觉与身体问题的论证构成了他的哲学的基础。
在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中,知觉、身体和物体构成了一个互相联系的三角关系:他认为身体主体运用知觉作用来认识物体,身体通过知觉得以与物体直接的联系;知觉是身体的知觉,是具有物体的对象性的知觉;而物体是作为对象的物体存在于世界中的。
关键词:知觉身体身体不变性物体现象学现象学是这样一种哲学:“在它看来,在进行反省之前,世界作为一种不可剥夺的呈现始终‘已经存在’,所有的反省努力都在于重新找回这种与世界自然的联系,以便最后给予世界一个哲学地位。
”2梅洛-庞蒂作为20世纪的法国现象学家代表之一,在哲学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
早期的梅洛-庞蒂深受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在求学期间,梅洛-庞蒂逐渐对胡塞尔的现象学发生了兴趣,正是胡塞尔的后期现象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促成了他的身体现象学:他在胡塞尔提到的身体概念的基础上关注含混身体这一领域。
通过对胡塞尔的创造性解读与他自己的理论洞见的结合,梅洛-庞蒂认为知觉的主体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质的,这个主体是精神与物质的结合——身体主体。
梅洛-庞蒂继承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强调重要的是描述,而不是解释。
“相对于作为力量的上帝,我们的生存处于困境之中,而世界是一种堕落,我们除了返回其内之外不可能有什么治疗。
”3我们返回世界是为了重新认识世界,也就是重新描述现象,我们无法解释“作为力量的上帝”,我们所需要做的是把一切现象还原,1这篇论文的完成,我的导师钱捷教授及师姐王亚娟硕士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钱老师给我们讲解原著并教会我们读原著的方法,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文献及资料;亚娟学姐帮助我们理清思路,引导我们发现问题,陪伴着我们度过的一个多月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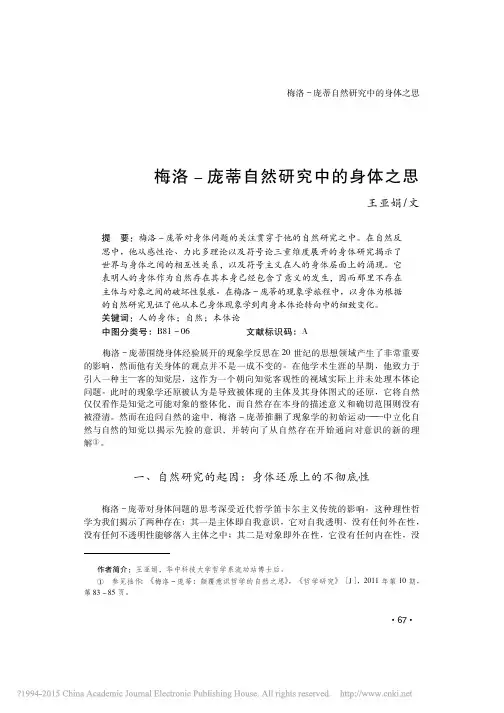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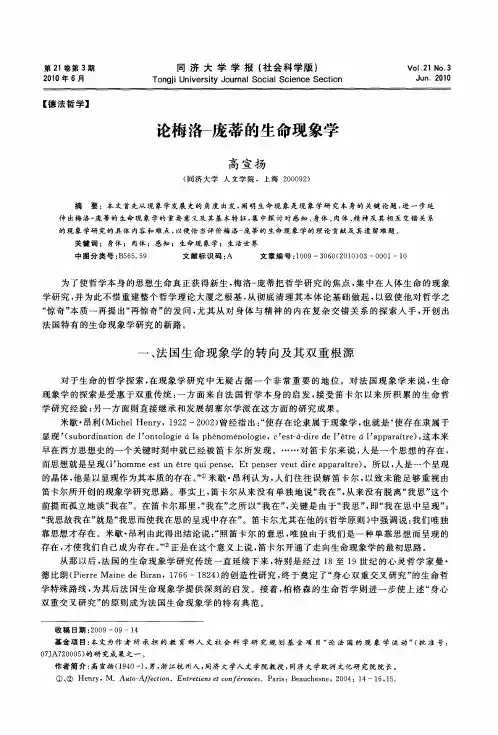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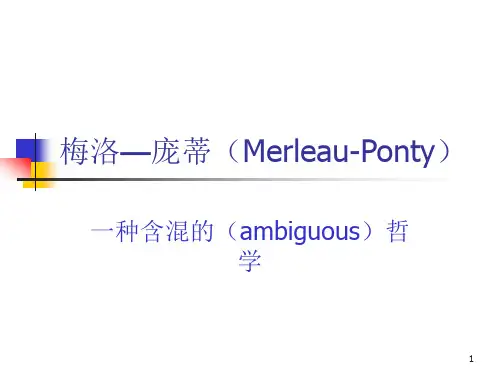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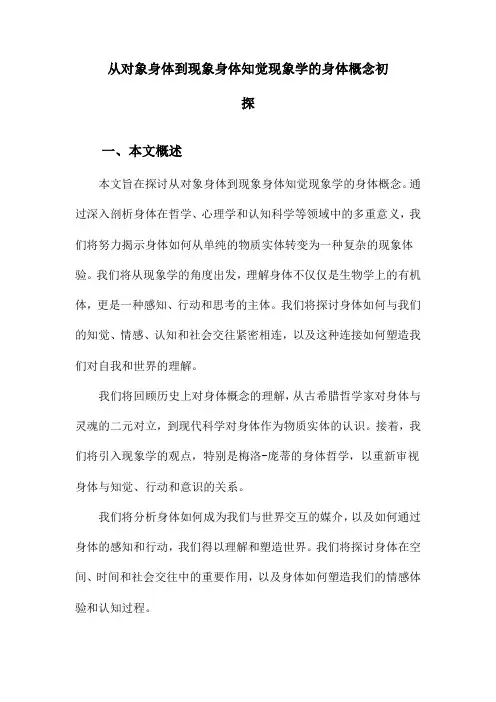
从对象身体到现象身体知觉现象学的身体概念初探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从对象身体到现象身体知觉现象学的身体概念。
通过深入剖析身体在哲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领域中的多重意义,我们将努力揭示身体如何从单纯的物质实体转变为一种复杂的现象体验。
我们将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理解身体不仅仅是生物学上的有机体,更是一种感知、行动和思考的主体。
我们将探讨身体如何与我们的知觉、情感、认知和社会交往紧密相连,以及这种连接如何塑造我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
我们将回顾历史上对身体概念的理解,从古希腊哲学家对身体与灵魂的二元对立,到现代科学对身体作为物质实体的认识。
接着,我们将引入现象学的观点,特别是梅洛-庞蒂的身体哲学,以重新审视身体与知觉、行动和意识的关系。
我们将分析身体如何成为我们与世界交互的媒介,以及如何通过身体的感知和行动,我们得以理解和塑造世界。
我们将探讨身体在空间、时间和社会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身体如何塑造我们的情感体验和认知过程。
我们将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如何将身体的概念应用于、机器人技术和虚拟现实等领域,以及如何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更深入地理解身体在知觉现象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期望能够深化对身体概念的理解,揭示身体在知觉现象学中的核心地位,并为我们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提供新的视角和启示。
二、对象身体与现象身体的区分在探讨身体知觉现象学的身体概念时,我们必须首先区分两种身体观念:对象身体和现象身体。
这两种观念在哲学、心理学以及科学研究中都有各自的体现,并对我们如何看待和理解身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象身体,是指被视为客观存在、可通过观察和研究来把握的身体。
在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身体往往被看作是各种器官、组织和生理系统的集合体。
这种观念下的身体,是可测量、可分析、可改造的对象,其存在和性质独立于观察者的主观意识。
在对象身体观念中,身体的功能和形态被看作是决定其价值和意义的关键因素。
然而,现象身体则是一种不同的理解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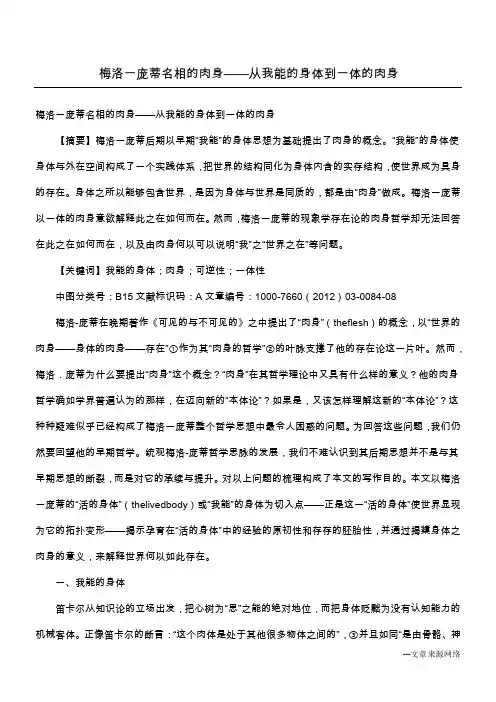
梅洛一庞蒂名相的肉身——从我能的身体到一体的肉身梅洛一庞蒂名相的肉身——从我能的身体到一体的肉身【摘要】梅洛一庞蒂后期以早期“我能”的身体思想为基础提出了肉身的概念。
“我能”的身体使身体与外在空间构成了一个实践体系,把世界的结构同化为身体内含的实存结构,使世界成为具身我们仍为它的拓扑变形——揭示孕育在“活的身体”中的经验的原初性和存存的胚胎性,并通过揭橥身体之肉身的意义,来解释世界何以如此存在。
一、我能的身体笛卡尔从知识论的立场出发,把心树为“思”之能的绝对地位,而把身体贬黜为没有认知能力的机械客体。
正像笛卡尔的断言:“这个肉体是处于其他很多物体之间的”,③并且如同“是由骨骼、神经、筋肉、血管、血肉、血液和皮肤组成的一架机器一样”。
④笛卡尔的机械身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思想,它使人们完全忽略了身体自身的体验以及身体体验意义的重要性。
,比如,医学领域中发现幻肢痛现象:因受伤而截肢的患者,当刺激应用在肢干而不是截肢面,患者在身体体验中感到仍然拥有那已被截去的肢体;在战场上受伤截肢的患者仍然能在幻肢处感到炸去那支胳膊的炮弹片。
“如果依赖于生理条件并因此是第三者原因的结果,那么幻肢在另一个情境下何以能够在个人解释,内在制约性并不是构成身体的那些可见的物质器官,而是经由身体的物质器官体现的积淀的经验,是身体与世界交织、由身体认同的实效意义与开放性。
身体的这种内在“实存”使身体不是物体,而是具有认知能力的“活的身体”,是“即便残肢或残疾却仍然朝向世界”的“我能”的身体。
④因此,“拒绝机能不全仅仅是面向世界的我们的内在性的背面,一个内隐的否定,即当我们面对任务,兴趣,处境,熟悉的地平线时,拥有一个幻胳膊就是想一如既往地进行胳膊所能操作的一切活动,就是还想保留伤残之前一直拥有的实践领域”。
⑤为了更好地揭示被传统的观点密封的身体的神奇能力和身体自身的系统,梅洛-庞蒂从一个精神性盲患者在运动类型上表现出来的运用身体的态度,把我们带入到对身体以及它的空间性的认识并揭示了思之能的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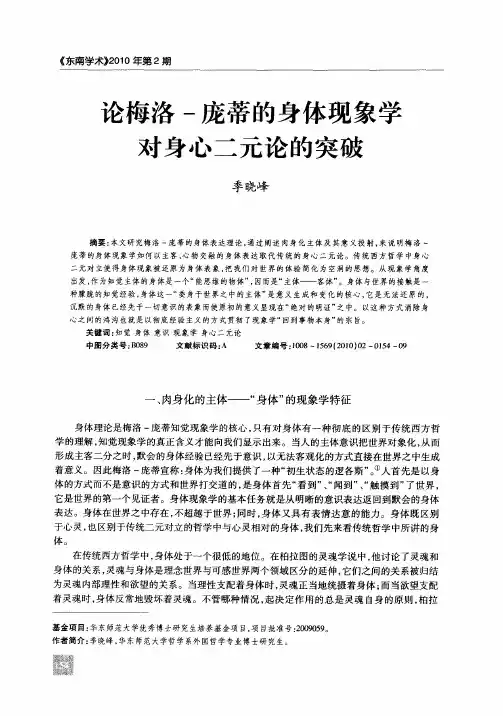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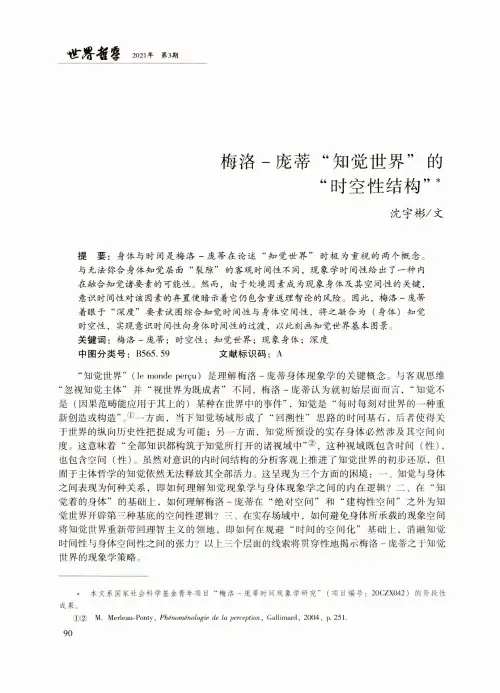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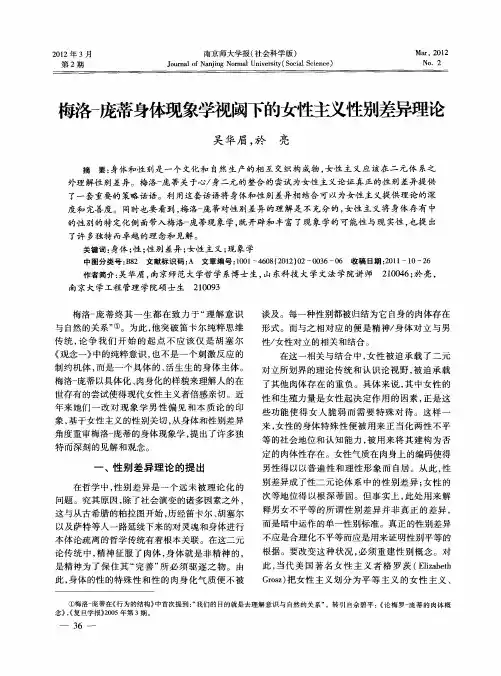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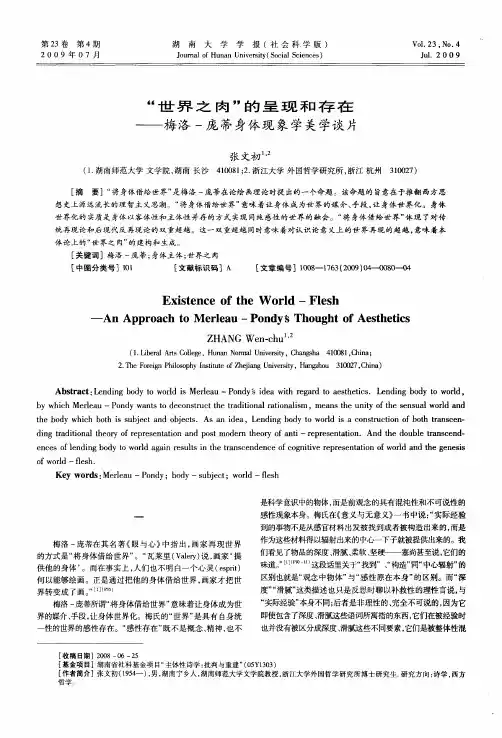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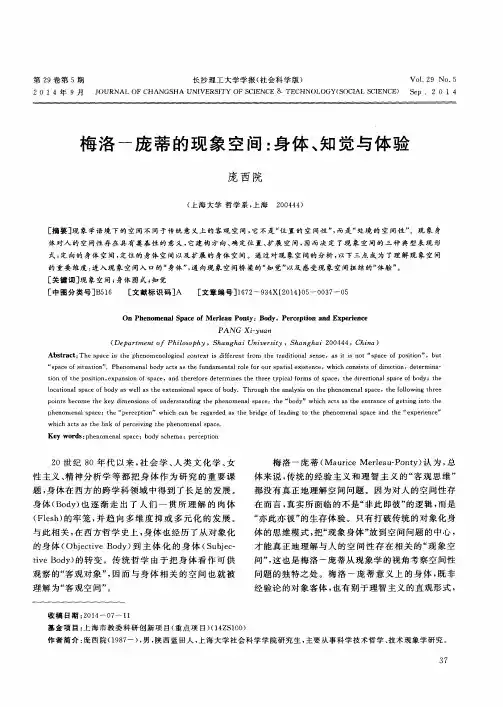
论的身体现象学对身心二元论的突破一、概述身体现象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哲学研究路径,致力于揭示身体经验的本质和意义。
它对于身心二元论的突破,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更深化了我们对身体和心灵的认知。
在身心二元论的传统观念中,身体被视为物质的、被动的存在,而心灵则被看作是精神的、主动的主体。
这种对立和分离导致了我们对身体经验和身体感受的忽视,使得身体在哲学思考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
身体现象学的出现,为我们打破这种二元对立提供了新的可能。
它强调身体不仅是物质的存在,更是意义和经验的载体。
身体现象学认为,身体经验是我们与世界最直接、最原初的联系方式,是我们感知和理解世界的基础。
通过对身体经验的深入研究,身体现象学揭示了身体与心灵的紧密联系,以及身体在认知、情感和社会交往中的重要作用。
在身体现象学的视角下,身体不再是被动的物质存在,而是主动的、有意识的、与世界相互作用的主体。
这种转变不仅为我们重新认识身体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我们理解身心关系、探索人的本质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将从身体现象学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其对身心二元论的突破及其重要意义。
1. 介绍身心二元论的历史背景和基本观点身心二元论是一种哲学观点,它主张人的身体和心灵是两个本质不同、相互独立的实体。
这一理论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
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看来,人的灵魂(心灵)是理性和不朽的,而身体则是物质的和可朽的。
他们强调灵魂对身体的支配和超越,认为身体是灵魂的囚笼,只有灵魂才能追求真理和智慧。
随着哲学的发展,身心二元论逐渐成为了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在笛卡尔的哲学体系中,身心二元论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展。
笛卡尔认为,人的身体是一个有限的物质实体,而心灵则是一个无限的非物质实体。
他通过“方法论怀疑”的方法,推导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强调了心灵的独立性和优先性。
在笛卡尔看来,心灵是第一性的,身体是第二性的,心灵可以脱离身体而存在,而身体则不能脱离心灵。
梅洛—庞蒂触觉观的现象学研究梅洛—庞蒂触觉观的现象学研究梅洛—庞蒂触觉观的现象学研究旨在探究人类触觉经验的本质和意义。
这一观点提出了触觉是我们与世界直接接触和理解的主要方式,并且在人类对于外界的认识和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触觉,我们可以感受到物体的形状、质地、温度等各种属性,进而对外界进行感知和理解。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深入探讨梅洛—庞蒂触觉观的核心观点以及它在现象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梅洛—庞蒂认为触觉是人类最直接的感官,通过触觉,我们可以与外界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触觉是一种身体直接经验的方式,我们通过触摸物体来感知它们的存在和属性。
与其他感官相比,触觉可以说是最为密切、直接的感知方式。
触觉的直接性体现在它与我们的身体紧密相连。
梅洛—庞蒂认为,我们的身体与世界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它们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
我们的身体通过感知,将自己与外界进行无缝连接。
触觉作为感知的一种方式,可以使我们直接体验到外界的物质实体,感受到它们的质地、温度、形状等属性。
在触觉中,我们不仅仅是被动地感受到外界的刺激,同时还能够通过身体的主动性来与之互动。
我们可以通过触摸来改变物体的位置、形状、质地等,进而对其进行理解和认识。
梅洛—庞蒂还强调了触觉对于认知的重要性。
触觉不仅仅是一种感知经验,更是一种认识手段。
通过触觉,我们能够感知到外界事物的各种属性,进而对其进行理解和认知。
触觉的具体感知内容与我们对于事物的概念密切相关。
例如,在我们触摸到球体时,我们能够感知到它的光滑和圆润,这与我们对于球体的概念是密切相关的。
触觉与我们的意识密切相关,它能够唤起我们对于事物的记忆和情感,从而影响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
梅洛—庞蒂还认为触觉是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手段。
通过触觉,我们可以与他人进行触摸的接触,从而表达情感,传递信息。
例如,母亲通过触摸婴儿的脸颊来表达关爱和亲密。
触觉能够产生密切的身体感受,通过触碰,我们能够共享和传递情感。
因此,触觉在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神的肉身——科幻电影中的身体现象学李岩摘要:在科幻电影中,充斥着对科学所造成的身体的异化恐慌,以身体工具属性转化为主题的电影,探索被身体所规范的权力范式的转化,强化相关的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断裂、冲突与和解。
神经与认知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确认了身体是制造意义与幻觉的机器,表明了身体与工具、后代与造物在多重意识形态意象上达成统一。
自动化生产迫使人类的身体观在知觉空间、身份空间以及生命空间这三个层面发生转向,由此宣布了后现代语境的终结与新生命形式的诞生。
关键词:身体空间;生命政治;科幻电影;身体现象学作者简介:李岩,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J9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23)03-0052-12自古以来,人类便意识到身体在自由度与神圣性方面的困境。
在前现代意识形态中,身体(soma)被认为是灵魂的容器。
身体的问题,直接指向本体论问题内涵与外延的两个关键内核:自我与感知。
意识对主体的建构与对外部实在界的感知,均由身体这一复杂系统所整合与建构,而一旦我们预设出某种主体,则意味着对身体的内外知觉系统的二元论背叛。
事实上,灵魂与肉身(incarnation)仅是一种语言学层面的误读,我们主观上为同一性的自然现象发明了两个不同名字,这正如基特勒对数字媒介所做的批判——“软件不存在”①,而鲍德里亚所谓的“超真实”也只是被“狡猾地”遮蔽了自身物质性的幻象。
所谓灵魂,其实质是在细胞与菌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比较视野下中国科幻电影工业与美学研究”(21ZD1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亚太电影促进会(NETPAC)研究”(19YJC760049)。
①Friedrich Kittler,There Is No Software,The truth of the technological world:essays on the genealogy of prese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221.52《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群活动中所涌现的“行动者网络”(ANT),或是神经元触突与神经递质间的动态电化学信号拓扑结构。
第25卷第1期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 ol.25No.1 2019年1月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S)Jan. 2019 DOI: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9.01.022论舒斯特曼对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的批判张晓东(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山东济南,250199)摘要:舒斯特曼在《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一书中对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的批判存在曲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曲解梅洛−庞蒂对哲学“跛行”的赞赏,把梅洛−庞蒂对时代政治的哲学反思曲解为梅洛−庞蒂主张哲学的不作为;二是认定梅洛−庞蒂在身体经验与身体反思之间制造二元对立,夸大梅洛−庞蒂对经验论身体观和唯理论身体观的批评;三是把梅洛−庞蒂对身体视角性的界定认作对身体局限性的辩护,把梅洛−庞蒂对身体图式的阐释理解为对反思性身体意识的排斥。
经过舒斯特曼的“有罪推定”,梅洛−庞蒂被塑造成排斥实用主义身体美学方案、痴迷身体本质缺陷的守旧“圣徒”。
批判性地反思舒斯特曼对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的曲解,对于理解实用主义与现象学的身体观的差异,促进身体美学兼收并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身体美学;身体意识;沉默的我思;身体图式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9)01−0177−07理查德·舒斯特曼在《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一书中评论了福柯、梅洛−庞蒂等六位哲学家的身体理论,赞赏其理论的优点,考察其理论的局限。
有研究者认为,舒斯特曼透过评论,“阐释了独特的身体美学观” [1](封底)。
也有反对者认为,舒斯特曼这本书通篇都是美学评论,而非美学理论,舒斯特曼所谓的身体美学只有身体,没有美学,更没有哲学。
在讨论舒斯特曼究竟有没有身体美学之前,我们先把视角投向这本书的第二章,“沉默跛行的身体哲学:梅洛−庞蒂身体关注的不足之处”。
梅洛—庞蒂与身体现象学——兼论西方哲学中的“身体性”问题的演变2006-12-313:15:46李重梅洛·庞蒂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那么哲学作为一门对“世界问题”的最根本把握的学问自然也应该从对身体的思考开始。
事实上,身体问题,实与人的问题密切相关,一部关于人的哲学其实就是一部对人的“身体的解释,或者误解”的哲学。
随着当代哲学研究的日益深入,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推波助澜,“身体性”问题从“遮蔽”逐渐走向“澄明”,成为日前西方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
本文试图从不同时期的西方哲学文本出发,试就“身体性”问题进行一番梳理和思考一,肉身的缺席:作为一种“练习死亡”的哲学如果说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发展史对于“肉体”而言犹如一场漫漫黑夜的话,那么这场黑夜的序幕则是从柏拉图那里开始的。
我们不妨先来考虑一下柏拉图在《斐多篇》中的关于灵魂的著名神话:双轮马车的驭手理性,手里挽着马色骏马和黑色骏马的缰绳,白色骏马代表着人的精神饱满,比较顺从于理性的指挥;而不听话的黑马代表着嗜好和欲望,驭手必须不时地挥鞭才肯就范。
这里的人的形象意指理性-灵魂,而作为欲望和嗜好载体的肉体是以兽的形象示人,鞭子和缰绳则表征着对肉体的规训和惩罚。
在柏拉图看来,肉身之狱不仅是高耸的令人恐怖与战栗的围墙,同时,它更是一个温柔的陷阱,罪恶的渊薮,堕落的胎盘,灵魂与肉体的结合只不过是理念堕落的结果。
柏拉图说:“只要我们固守在身体之中,使灵魂受到肉体的污染而变得不完满,我们就无法令人满意地去把握对象,这些对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真理。
……我们无疑相信,要想获得纯粹的知识,必须摆脱肉体,用灵魂注视事物本身。
从这种观点来看,我们所期望和决心获得的智慧,只有在我们死后而不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才有可能……看来只要我们活着,除非绝对必要,尽可能避免与肉体的交往、接触,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接近知识。
”[1]P17我们知道,英语哲学中“理论”(Theory)是从希腊语动词theatai(看)来的,这个动词又是名词theatre(剧场)的词根,另外,理性(Idea)是也从希腊语中eidos(看)演变而来。
正如德里达告诉我们的,“在其希腊文化的谱系中,欧洲观念的整个历史,欧洲语言中观念一词(idein,eidos,idea)的整个语意学,如我们所知——如我们所见,是将看和知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在柏拉图那里,“用灵魂注视事物本身”才是获取纯粹知识的唯一途径,“看”是灵魂专属的权力。
考之古籍,“看”在《说文》中的意思是,“看,睎也。
(睎,望也。
)”,也就是用手加额遮目而远望。
为什么只能以“远望”而非“切身”作为接近真理的手段?其中隐藏着这样一个的阴谋,即通过对肉体的遮蔽和隐匿,将肉体悬隔于事物本身很远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灵魂“看”的纯粹性,柏拉图那个很有名的“洞喻”不正是对此的生动释说。
很显然,在这里柏拉图是把肉体与灵魂这两者绝对对立起来,并且认为人的肉体,即感觉器官不可能获得知识,只有灵魂在超然状态下才能够获得知识和理性,以此主张灵魂必须与肉体分离。
顺是,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宣称,真正的哲学家一直是在学习死亡,练习死亡,一直在追求死之状态。
死亡无非是指肉体的死亡和寂灭,而灵魂得以最终摆脱“皮囊”的捆罚,获得轻松自在。
至此,柏拉图将这种对肉体的宰制高扬为哲学以及哲学家的应有之意。
“练习死亡”的哲学态度开始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漫长统治。
当代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讲,“两千年的西方哲学史都是柏拉图的注脚”。
虽然有关灵肉二分思想的隐秘而曲折的起源在柏拉图那里,但是只有在近代意识哲学那里,特别是笛卡尔那里,灵魂和肉体的关系才真正获得了一种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地位,继而也就将“身体性”问题第一次堂而皇之地摆放到哲学思辨殿堂之中了。
如果说,作为肉体的身体在大多数时候受到的是宗教和哲学的双重磨难,那么在意识哲学阶段,作为肉体的身体摆脱了道德上的委屈感,却受到的是来自于知识的压迫和诘难。
[2]P4众所周知,意识哲学是一种崇尚知识和智性的文化潮流,是由笛卡尔“我思”哲学所开创的,由洛克特别是康德所确立起来的,而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鼎盛的近代认识论哲学。
而这种认识论依旧是一种“理想的认识论”,即“指一种与常识的认识理论相区别的非常识的认识理论,一种以追求绝对的逼真、严格的科学为宗旨的理论。
”[3]肉体是常识的认识理论产生的根源,因此,肉体由于其作为一种感性、偶然性、不确定性、错觉和虚幻的存在,是永远被排除在严格科学和真理大门之外的。
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为典型代表。
在他的哲学中,肉体和心灵是两个独立不依的实体,彼此互不联系,二者是根本不同的:肉体的属性是广延的,心灵的属性是思维。
但是在笛卡尔看来,肉体和心灵决然不是等量齐观的。
在笛卡尔的“我思哲学”中,作为肉体的身体是“虚伪的”、“骗人的”[4]P90,是作为怀疑对象被完全被最终悬置的东西。
因此,笛卡尔实质上仍然坚持一种心“尊”身“卑”姿态,心灵是不含物性的纯粹意识,肉体则是没有灵性的纯粹事物。
人或者主体主要属于思维、心灵范畴,身体及其周遭环境只具有从属的意义。
也就是说,人主要与高贵的精神或良知、良能联系在一起,他超然于身体及其伴随的感觉、欲望之外。
身体问题在笛卡尔这里得到了认真的思考,但是另一方面,正如美国哲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在其《形而上学》所指出的那样:“很清楚,如果一个人把他的身体和心灵当作两种不同的东西区分开来,就会产生如此巨大的难题,以至任何荒诞不经的理论,只要提供某些关于消除这类难题的希望,就会显得似乎有理。
一旦把身体和心灵割裂开,就会产生足以使哲学家们世世代代去研究的种种问题。
”[5]P17,因此,之后的哲学家像莱布尼茨的“预定和谐论”、斯宾诺莎的“身心合一论”等都是在试图解决身心的同一性问题。
这一努力直到黑格尔才算是登峰造极了,身体的问题最终被划归为“绝对理念”的异化结果,人被彻底的抽象为意识和精神,人的历史被抽象为意识和精神的历史。
然而,就像当代美国著名分析哲学家塞尔(J.R.Searle)所言,近代哲学在处理身心关系实质上是一种“还原主义的思维偏向”,作为肉体的身体被强行纳入到巨大的思辨体系之中,肉体仅仅被还原成了一个概念或者符号,抑或是一驾毫无生气的机器。
无怪乎,尼采后来在评价西方近代哲学时,如此气急败坏的指责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是一种“被阉割”的哲学、“太监”的哲学。
在近代意识哲学中,“人们不怎么在哲学中谴责身体了,但这也意味着身体消失了,消失在心灵对知识的孜孜探索中。
以前,人们压制身体,是因为身体是个问题;现在,人们忽视身体,是因为身体不再是个问题。
”[2]P8二,肉欲的乌托邦:作为一种“肉体专制”的哲学《易经》有云:物不可以终泰,故受之以否。
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
当意识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肉体”也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中”迎来了它的第一缕曙光。
在这样一个被称之为“哲学肉身化”的运动中,费尔巴哈首先吹起了战斗的号角,他说,“身体属于我的存在;不仅如此,身体中的全部都是我自己,是我特有的本质。
”,“旧哲学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命题:‘我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一个仅仅思维的实体,肉体是不属于我的本质的’;新哲学则以另一个命题为出发点:‘我是一个实在的感觉的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们的自我,我的实体本身。
’”[6]P169。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言的那样,“(费尔巴哈)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最终他还是“重新陷入唯心主义”之中[7]P50。
因此,费尔巴哈以“感性的对象”为其哲学坐标中心的努力并非成功之举,其不是西方传统意识哲学的革命者,而依然是这一西方传统哲学的忠实的传薪人。
与费尔巴哈的欲说还休不同,尼采蔑视自柏拉图到黑格尔以来的所有哲学传统,他明确提出了“一切从身体出发”的口号。
尼采对意识哲学可谓是鞭辟近里乃至一剑封喉,他尖锐地指出:“‘灵魂’、‘精神’,最后还有‘不死的灵魂’,这些都是发明来蔑视肉体的,使肉体患病――‘成仙’。
”[8]P106。
尼采所言的身体,已经不是仅仅作为灵魂或者意识附庸的“被阉割”的身体,而是有血有肉的,有着爱恨情仇的身体,不是以灵魂或者意识为准绳,而是“以身体为准绳”。
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说:“我就是肉体,就是灵魂。
”“我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不过是身体上某物的称呼……所谓心灵者,也是你身体的一种工具,你的大理智中一个工具、玩具”。
在尼采看来,唯一的存在是生命,生命之外一无所有,存在是生命之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的永恒回复,而生命是肉体,因此,不是上帝(理性)创造了肉体,而是肉体创造了上帝(理性),肉体的生生死死的本性也就赋予在了上帝的本性之上,因此,尼采的上帝即不是笛卡尔的那个永恒、无欺的存在之为存在的基础,也不是基督教中的那个全知全能的彼岸之物,而是“有死”的上帝,继而也就有了他那句惊世骇俗的名言“上帝死了”的腾空出世。
这样,肉体第一次作为了哲学研究中心,作为了“真理领域中对世界作出估价的解释学中心”,尼采甚至还提出了“哲学就是医学或者生理学”。
如果说,费尔巴哈以鲜活的“肉体”为利刃,将西方传统哲学千年来苦心营造的“纯粹”自由王国击的粉身粹骨,那么尼采的出现则断然扭断了意识哲学的叙事线索,真正为整个20世纪的“肉身化”的哲学话语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从柏拉图开始的“练习死亡”的西方传统哲学在这里发生的偏转,可以说,由原来的“我思,故我在”变为“我欲,故我在”或者“我身体,故我在”。
尼采这些振聋发聩的呼声在后现代哲学的域场之中很快的回荡开去。
随着西方世界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理性主义的幽灵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而得以借尸还魂,由原来的思辨理性一跃成为了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
技术为人类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高质量的生活条件。
人们坚信,凭借科学技术,人不仅可以无限制地控制自然,并且人类自身也会得到自由和解放,最终实现人的发展和完满。
但是事与愿违,19世纪,特别是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接踵而来的是频繁经济政治危机和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社会又产生了一系列积重难返的新的问题,诸如人的异化、南北差距、两极分化、生态恶化和霸权主义等等。
此时,肉体刚从道德领域,真理领域的辖制中步履蹒跚地走出来,但是却又落入到了由现代技术所编织的新的陷阱之中,即肉体沦为了生产领域中的一部生产机器,成为一种工具符号,肉体的日常话语权被剥夺殆尽。
“奥斯威辛”事件的发生,昭示了现代技术理性对肉体的毁灭性企图。
正如先贤大哲们所言“异化与对象化走着同一条道路”(黑格尔),抑或是“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荷尔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