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与声无哀乐论
- 格式:doc
- 大小:41.50 KB
- 文档页数:15

简论嵇康《声无哀乐论》思想
《声无哀乐论》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嵇康的代表作之一,该论文探讨了音乐的本质和音乐创作的标准,认为音乐应该是无声的,纯粹的语言,只有发人深思的作品才能称之为好作品。
在《声无哀乐论》中,嵇康首先批判后汉时期流行的音乐,认为当时的音乐太过激昂,不能带给人们真正的快乐,反而会让人感到疲惫不堪。
他提出了“仁人居则安,知人居则惠”的观点,认为好的音乐应该有助于人们内心的平静和安逸,而不是让人激动不安。
嵇康进一步论述了音乐和道德的关系。
他认为音乐应该是道德和品德的表达,好的音乐能够感化人心,引导人们进入高尚的精神境界。
他强调音乐的价值不仅在于艺术层面,更在于其对人性的影响。
嵇康也提出了关于艺术创作标准的看法。
他认为好的音乐作品不仅是要符合音乐本身的规律,还应该满足人类精神活动的需要。
而作为音乐家,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有高尚的艺术追求,把心灵灌注到音乐中,传达自己对生命、对人性、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和感悟。
《声无哀乐论》不仅是一篇探讨音乐思想的文章,更是一篇关于人性和社会的思考。
嵇康通过对音乐的研究,提出了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标准,强调艺术创作应该符合人类精神的需要,从而为后世的古代文化、思想、艺术创作等领域影响深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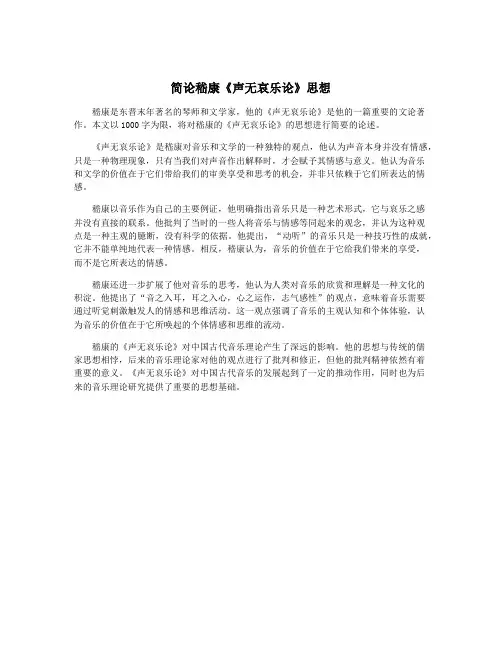
简论嵇康《声无哀乐论》思想
嵇康是东晋末年著名的琴师和文学家,他的《声无哀乐论》是他的一篇重要的文论著作。
本文以1000字为限,将对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的思想进行简要的论述。
《声无哀乐论》是嵇康对音乐和文学的一种独特的观点,他认为声音本身并没有情感,只是一种物理现象,只有当我们对声音作出解释时,才会赋予其情感与意义。
他认为音乐
和文学的价值在于它们带给我们的审美享受和思考的机会,并非只依赖于它们所表达的情感。
嵇康以音乐作为自己的主要例证,他明确指出音乐只是一种艺术形式,它与哀乐之感
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他批判了当时的一些人将音乐与情感等同起来的观念,并认为这种观
点是一种主观的臆断,没有科学的依据。
他提出,“动听”的音乐只是一种技巧性的成就,它并不能单纯地代表一种情感。
相反,嵇康认为,音乐的价值在于它给我们带来的享受,
而不是它所表达的情感。
嵇康还进一步扩展了他对音乐的思考,他认为人类对音乐的欣赏和理解是一种文化的
积淀。
他提出了“音之入耳,耳之入心,心之运作,志气感性”的观点,意味着音乐需要
通过听觉刺激触发人的情感和思维活动。
这一观点强调了音乐的主观认知和个体体验,认
为音乐的价值在于它所唤起的个体情感和思维的流动。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对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思想与传统的儒
家思想相悖,后来的音乐理论家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和修正,但他的批判精神依然有着
重要的意义。
《声无哀乐论》对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后
来的音乐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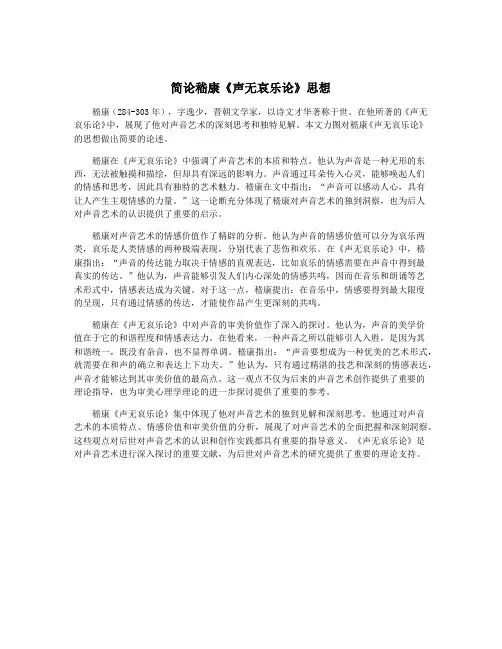
简论嵇康《声无哀乐论》思想嵇康(284-303年),字逸少,晋朝文学家,以诗文才华著称于世。
在他所著的《声无哀乐论》中,展现了他对声音艺术的深刻思考和独特见解。
本文力图对嵇康《声无哀乐论》的思想做出简要的论述。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强调了声音艺术的本质和特点。
他认为声音是一种无形的东西,无法被触摸和描绘,但却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声音通过耳朵传入心灵,能够唤起人们的情感和思考,因此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嵇康在文中指出:“声音可以感动人心,具有让人产生主观情感的力量。
”这一论断充分体现了嵇康对声音艺术的独到洞察,也为后人对声音艺术的认识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嵇康对声音艺术的情感价值作了精辟的分析。
他认为声音的情感价值可以分为哀乐两类,哀乐是人类情感的两种极端表现,分别代表了悲伤和欢乐。
在《声无哀乐论》中,嵇康指出:“声音的传达能力取决于情感的直观表达,比如哀乐的情感需要在声音中得到最真实的传达。
”他认为,声音能够引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因而在音乐和朗诵等艺术形式中,情感表达成为关键。
对于这一点,嵇康提出:在音乐中,情感要得到最大限度的呈现,只有通过情感的传达,才能使作品产生更深刻的共鸣。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对声音的审美价值作了深入的探讨。
他认为,声音的美学价值在于它的和谐程度和情感表达力。
在他看来,一种声音之所以能够引人入胜,是因为其和谐统一,既没有杂音,也不显得单调。
嵇康指出:“声音要想成为一种优美的艺术形式,就需要在和声的确立和表达上下功夫。
”他认为,只有通过精湛的技艺和深刻的情感表达,声音才能够达到其审美价值的最高点。
这一观点不仅为后来的声音艺术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也为审美心理学理论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嵇康《声无哀乐论》集中体现了他对声音艺术的独到见解和深刻思考。
他通过对声音艺术的本质特点、情感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分析,展现了对声音艺术的全面把握和深刻洞察。
这些观点对后世对声音艺术的认识和创作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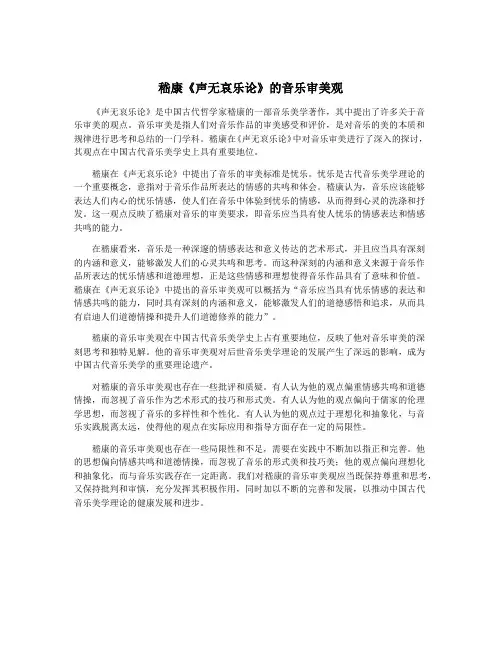
嵇康《声无哀乐论》的音乐审美观《声无哀乐论》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嵇康的一部音乐美学著作,其中提出了许多关于音乐审美的观点。
音乐审美是指人们对音乐作品的审美感受和评价,是对音乐的美的本质和规律进行思考和总结的一门学科。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对音乐审美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观点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提出了音乐的审美标准是忧乐。
忧乐是古代音乐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对于音乐作品所表达的情感的共鸣和体会。
嵇康认为,音乐应该能够表达人们内心的忧乐情感,使人们在音乐中体验到忧乐的情感,从而得到心灵的洗涤和抒发。
这一观点反映了嵇康对音乐的审美要求,即音乐应当具有使人忧乐的情感表达和情感共鸣的能力。
在嵇康看来,音乐是一种深邃的情感表达和意义传达的艺术形式,并且应当具有深刻的内涵和意义,能够激发人们的心灵共鸣和思考。
而这种深刻的内涵和意义来源于音乐作品所表达的忧乐情感和道德理想,正是这些情感和理想使得音乐作品具有了意味和价值。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提出的音乐审美观可以概括为“音乐应当具有忧乐情感的表达和情感共鸣的能力,同时具有深刻的内涵和意义,能够激发人们的道德感悟和追求,从而具有启迪人们道德情操和提升人们道德修养的能力”。
嵇康的音乐审美观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反映了他对音乐审美的深刻思考和独特见解。
他的音乐审美观对后世音乐美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重要理论遗产。
对嵇康的音乐审美观也存在一些批评和质疑。
有人认为他的观点偏重情感共鸣和道德情操,而忽视了音乐作为艺术形式的技巧和形式美。
有人认为他的观点偏向于儒家的伦理学思想,而忽视了音乐的多样性和个性化。
有人认为他的观点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与音乐实践脱离太远,使得他的观点在实际应用和指导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嵇康的音乐审美观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和不足,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指正和完善。
他的思想偏向情感共鸣和道德情操,而忽视了音乐的形式美和技巧美;他的观点偏向理想化和抽象化,而与音乐实践存在一定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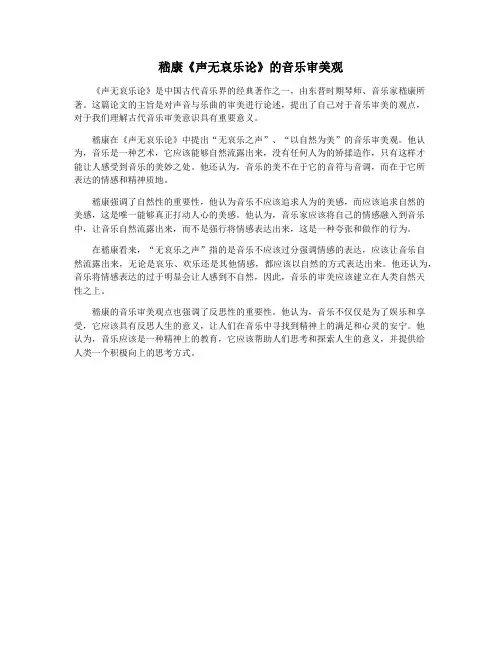
嵇康《声无哀乐论》的音乐审美观
《声无哀乐论》是中国古代音乐界的经典著作之一,由东晋时期琴师、音乐家嵇康所著。
这篇论文的主旨是对声音与乐曲的审美进行论述,提出了自己对于音乐审美的观点,
对于我们理解古代音乐审美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提出“无哀乐之声”、“以自然为美”的音乐审美观。
他认为,音乐是一种艺术,它应该能够自然流露出来,没有任何人为的矫揉造作,只有这样才
能让人感受到音乐的美妙之处。
他还认为,音乐的美不在于它的音符与音调,而在于它所
表达的情感和精神质地。
嵇康强调了自然性的重要性,他认为音乐不应该追求人为的美感,而应该追求自然的
美感,这是唯一能够真正打动人心的美感。
他认为,音乐家应该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音乐中,让音乐自然流露出来,而不是强行将情感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夸张和做作的行为。
在嵇康看来,“无哀乐之声”指的是音乐不应该过分强调情感的表达,应该让音乐自
然流露出来,无论是哀乐、欢乐还是其他情感,都应该以自然的方式表达出来。
他还认为,音乐将情感表达的过于明显会让人感到不自然,因此,音乐的审美应该建立在人类自然天
性之上。
嵇康的音乐审美观点也强调了反思性的重要性。
他认为,音乐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和享受,它应该具有反思人生的意义,让人们在音乐中寻找到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灵的安宁。
他
认为,音乐应该是一种精神上的教育,它应该帮助人们思考和探索人生的意义,并提供给
人类一个积极向上的思考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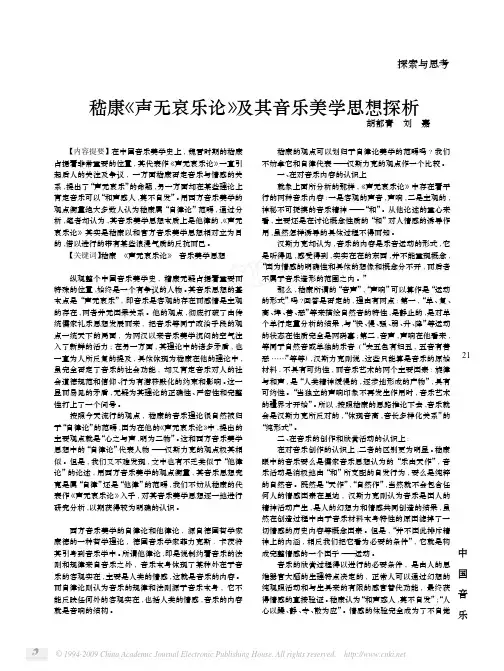
中国音乐21探索与思考嵇康《声无哀乐论》及其音乐美学思想探析胡郁青刘嘉【内容提要】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魏晋时期的嵇康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其代表作《声无哀乐论》一直引起后人的关注及争议,一方面嵇康否定音乐与情感的关系,提出了“声无哀乐”的命题,另一方面却在某些理论上肯定音乐可以“和声感人,莫不自发”。
用西方音乐美学的观点衡量绝大多数人认为嵇康属“自律论”范畴,通过分析,笔者却认为,其音乐美学思想本质上是他律的,《声无哀乐论》其实是嵇康以和官方音乐美学思想相对立为目的,借以进行的带有某些浪漫气质的反抗而已。
【关键词】嵇康《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思想纵观整个中国音乐美学史,稽康无疑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位置,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其音乐思想的基本点是“声无哀乐”,即音乐是客观的存在而感情是主观的存在,两者并无因果关系。
他的观点,彻底打破了由传统儒家礼乐思想发展而来,把音乐等同于政治手段的观点一统天下的局面,为两汉以来音乐美学沉闷的空气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在另一方面,其理论中的诸多矛盾,也一直为人所反复的提及,具体体现为嵇康在他的理论中,虽完全否定了音乐的社会功能,却又肯定音乐对人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信仰、行为有潜移默化的约束和影响。
这一显而易见的矛盾,无疑为其理论的正确性、严密性和完整性打上了一个问号。
按照今天流行的观点,嵇康的音乐理论很自然被归于“自律论”的范畴,因为在他的《声无哀乐论》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就是“心之与声,明为二物”。
这和西方音乐美学思想中的“自律论”代表人物———汉斯力克的观点极其相似。
但是,我们又不难发现,文中也有不乏类似于“他律论”的论述,用西方音乐美学的观点衡量,其音乐思想究竟是属“自律”还是“他律”的范畴,我们不妨从嵇康的代表作《声无哀乐论》入手,对其音乐美学思想逐一地进行研究分析,以期获得较为明确的认识。
西方音乐美学的自律论和他律论,源自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一种哲学理论,德国音乐学家菲力克斯.卡茨将其引身到音乐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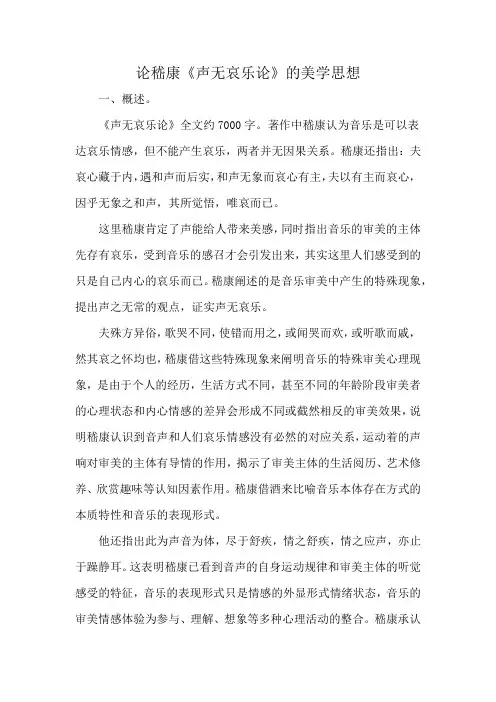
论嵇康《声无哀乐论》的美学思想一、概述。
《声无哀乐论》全文约7000字。
著作中嵇康认为音乐是可以表达哀乐情感,但不能产生哀乐,两者并无因果关系。
嵇康还指出:夫哀心藏于内,遇和声而后实,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而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其所觉悟,唯哀而已。
这里嵇康肯定了声能给人带来美感,同时指出音乐的审美的主体先存有哀乐,受到音乐的感召才会引发出来,其实这里人们感受到的只是自己内心的哀乐而已。
嵇康阐述的是音乐审美中产生的特殊现象,提出声之无常的观点,证实声无哀乐。
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其哀之怀均也,嵇康借这些特殊现象来阐明音乐的特殊审美心理现象,是由于个人的经历,生活方式不同,甚至不同的年龄阶段审美者的心理状态和内心情感的差异会形成不同或截然相反的审美效果,说明嵇康认识到音声和人们哀乐情感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运动着的声响对审美的主体有导情的作用,揭示了审美主体的生活阅历、艺术修养、欣赏趣味等认知因素作用。
嵇康借酒来比喻音乐本体存在方式的本质特性和音乐的表现形式。
他还指出此为声音为体,尽于舒疾,情之舒疾,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耳。
这表明嵇康已看到音声的自身运动规律和审美主体的听觉感受的特征,音乐的表现形式只是情感的外显形式情绪状态,音乐的审美情感体验为参与、理解、想象等多种心理活动的整合。
嵇康承认音响及其运动的方式能使人躁静、专散,但是音乐审美活动是主客体,音心相对应的特殊规律。
嵇康承认了音乐是能引起人情绪上的躁静,同时也否认音声表现哀乐,他坚持音声的本体的独立存在,同样也看到了音乐审美的特殊规律。
二、音乐的本质问题。
从本质上来说,音乐首先从创作方面就具有强烈的人的主观意识,在表演形式上,每一个表演者在表演的过程中都增加了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及把握,都夹带着自己的情感意识,而音乐的听众和欣赏者作为主体,本身更是带有自己的主观色彩去理解音乐所要表达的含义。
然而,嵇康这种仅仅只是强调音乐的客观性和自然属性的观点是片面的,他一方面否定了音乐的人为主观意识,认为音乐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物质,同时也否定了音乐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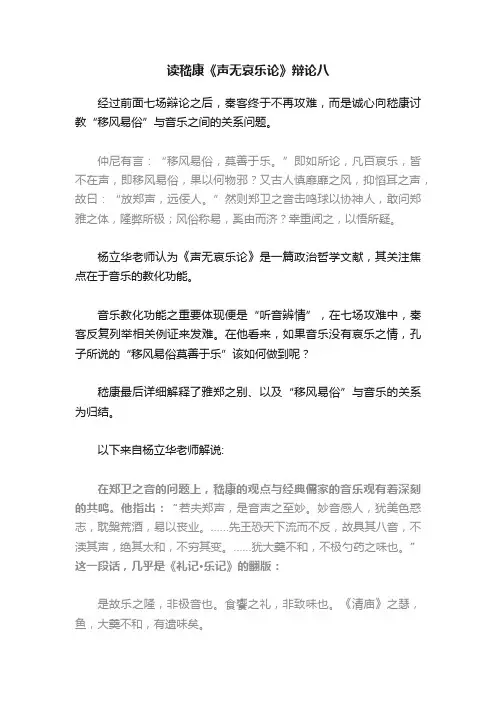
读嵇康《声无哀乐论》辩论八经过前面七场辩论之后,秦客终于不再攻难,而是诚心向嵇康讨教“移风易俗”与音乐之间的关系问题。
仲尼有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即如所论,凡百哀乐,皆不在声,即移风易俗,果以何物邪?又古人慎靡靡之风,抑慆耳之声,故曰:“放郑声,远佞人。
”然则郑卫之音击鸣球以协神人,敢问郑雅之体,隆弊所极;风俗称易,奚由而济?幸重闻之,以悟所疑。
杨立华老师认为《声无哀乐论》是一篇政治哲学文献,其关注焦点在于音乐的教化功能。
音乐教化功能之重要体现便是“听音辨情”,在七场攻难中,秦客反复列举相关例证来发难。
在他看来,如果音乐没有哀乐之情,孔子所说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该如何做到呢?嵇康最后详细解释了雅郑之别、以及“移风易俗”与音乐的关系为归结。
以下来自杨立华老师解说:在郑卫之音的问题上,嵇康的观点与经典儒家的音乐观有着深刻的共鸣。
他指出:“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
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丧业。
……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渎其声,绝其太和,不穷其变。
……犹大羹不和,不极勺药之味也。
”这一段话,几乎是《礼记·乐记》的翻版: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
食饗之礼,非致味也。
《清庙》之瑟,鱼,大羹不和,有遗味矣。
最好的音乐不是穷极变化的“妙音”,而是平静中正的“太和”之声。
而这也正是雅颂与郑卫之音的分野。
由此我想到了《论语·述而》中的“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在通常的解释里,这都被视为孔子音乐修养的体现:孔子听到了韶乐这样至高至妙的音乐,流连其中,以致数月食不甘味。
从此处的讨论看,这样的解读显然有悖于经典儒家对音乐的理解。
因此,我觉得这里的“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不应该解释为“想不到音乐的美妙会达到这样的程度”,而应读为“我并不期望音乐这样美妙或者音乐没有必要这样美妙”才是。
马克斯·韦伯曾经以其他文明何以未能产生出欧洲那样理性的复调音乐作为其宗教社会学的出发点之一,恐怕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和想象居然还会有这样一种文明:它从根源处拒绝那些穷神极妙的乐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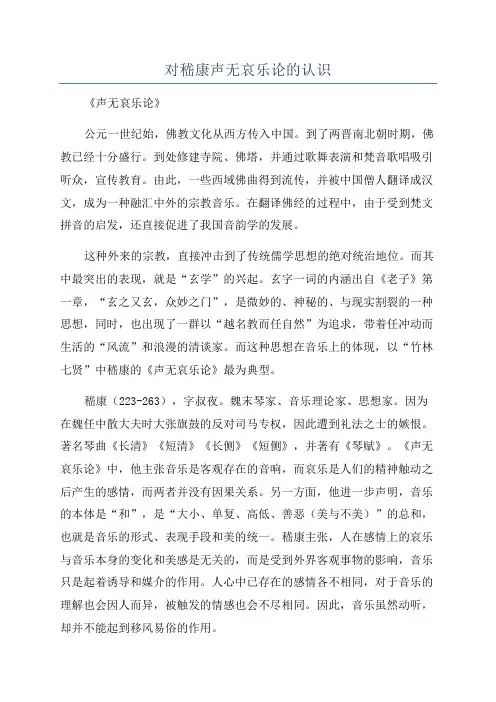
对嵇康声无哀乐论的认识《声无哀乐论》公元一世纪始,佛教文化从西方传入中国。
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十分盛行。
到处修建寺院、佛塔,并通过歌舞表演和梵音歌唱吸引听众,宣传教育。
由此,一些西域佛曲得到流传,并被中国僧人翻译成汉文,成为一种融汇中外的宗教音乐。
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梵文拼音的启发,还直接促进了我国音韵学的发展。
这种外来的宗教,直接冲击到了传统儒学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
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玄学”的兴起。
玄字一词的内涵出自《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微妙的、神秘的、与现实割裂的一种思想,同时,也出现了一群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追求,带着任冲动而生活的“风流”和浪漫的清谈家。
而这种思想在音乐上的体现,以“竹林七贤”中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最为典型。
嵇康(223-263),字叔夜。
魏末琴家、音乐理论家、思想家。
因为在魏任中散大夫时大张旗鼓的反对司马专权,因此遭到礼法之士的嫉恨。
著名琴曲《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并著有《琴赋》。
《声无哀乐论》中,他主张音乐是客观存在的音响,而哀乐是人们的精神触动之后产生的感情,而两者并没有因果关系。
另一方面,他进一步声明,音乐的本体是“和”,是“大小、单复、高低、善恶(美与不美)”的总和,也就是音乐的形式、表现手段和美的统一。
嵇康主张,人在感情上的哀乐与音乐本身的变化和美感是无关的,而是受到外界客观事物的影响,音乐只是起着诱导和媒介的作用。
人心中已存在的感情各不相同,对于音乐的理解也会因人而异,被触发的情感也会不尽相同。
因此,音乐虽然动听,却并不能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
嵇康的主张对于官方的礼乐思想是极大的挑战。
他大胆反对两汉以来完全无视音乐的艺术性,把音乐简单地等同与政治的观点。
他将音乐的形式美、实质内容与欣赏者的理解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而这也成为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重要的源头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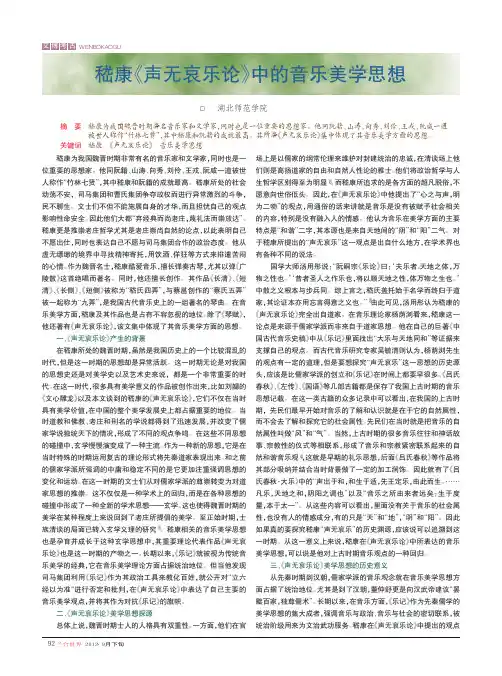
兰台世界2012·9月下旬嵇康为我国魏晋时期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和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
他同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一道被世人称作“竹林七贤”,其中嵇康和阮籍的成就最高。
嵇康所处的社会动荡不安,司马集团和曹氏集团争夺政权而进行异常激烈的斗争,民不聊生。
文士们不但不能施展自身的才华,而且担忧自己的观点影响性命安全。
因此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
嵇康更是推崇老庄哲学尤其是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以此表明自己不愿出仕,同时也表达自己不愿与司马集团合作的政治态度。
他从虚无缥缈的境界中寻找精神寄托,用饮酒、佯狂等方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
作为魏晋名士,嵇康酷爱音乐,擅长弹奏古琴,尤其以弹《广陵散》这首绝唱而著名。
同时,他还擅长创作。
其作品《长清》、《短清》、《长侧》、《短侧》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被一起称为“九弄”,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一组著名的琴曲。
在音乐美学方面,嵇康及其作品也是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除了《琴赋》,他还著有《声无哀乐论》,该文集中体现了其音乐美学方面的思想。
一、《声无哀乐论》产生的背景在嵇康所处的魏晋时期,虽然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比较混乱的时代,但是这一时期的思想却是异常活跃。
这一时期无论是对我国的思想史还是对美学史以及艺术史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
在这一时代,很多具有美学意义的作品被创作出来,比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本文谈到的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它们不仅在当时具有美学价值,在中国的整个美学发展史上都占据重要的地位。
当时道教和佛教、老庄和刑名的学说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并改变了儒家学说独统天下的情况,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争鸣。
在这些不同思想的碰撞中,玄学慢慢演变成了一种主流。
作为一种新的思想,它是在当时特殊的时期运用复古的理论形式将先秦道家表现出来。
和之前的儒家学派所强调的中庸和稳定不同的是它更加注重强调思想的变化和运动。
在这一时期的文士们从对儒家学派的尊崇转变为对道家思想的推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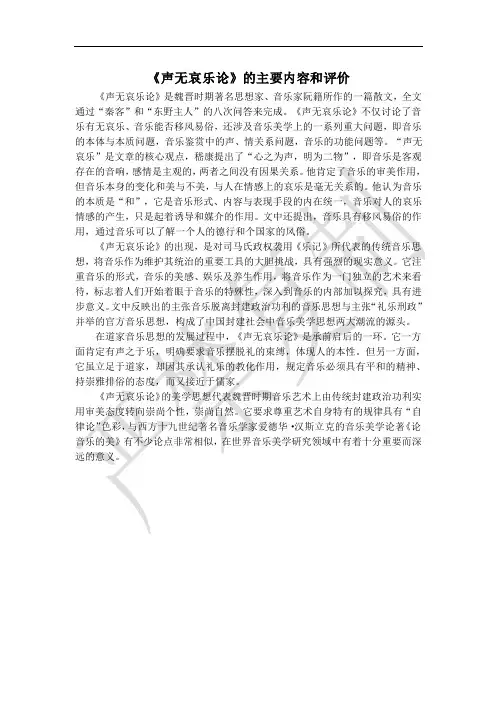
《声无哀乐论》的主要内容和评价《声无哀乐论》是魏晋时期著名思想家、音乐家阮籍所作的一篇散文,全文通过“秦客”和“东野主人”的八次问答来完成。
《声无哀乐论》不仅讨论了音乐有无哀乐、音乐能否移风易俗,还涉及音乐美学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即音乐的本体与本质问题,音乐鉴赏中的声、情关系问题,音乐的功能问题等。
“声无哀乐”是文章的核心观点,嵇康提出了“心之为声,明为二物”,即音乐是客观存在的音响,感情是主观的,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他肯定了音乐的审美作用,但音乐本身的变化和美与不美,与人在情感上的哀乐是毫无关系的。
他认为音乐的本质是“和”,它是音乐形式、内容与表现手段的内在统一,音乐对人的哀乐情感的产生,只是起着诱导和媒介的作用。
文中还提出,音乐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通过音乐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德行和个国家的风俗。
《声无哀乐论》的出现,是对司马氏政权袭用《乐记》所代表的传统音乐思想,将音乐作为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工具的大胆挑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它注重音乐的形式,音乐的美感、娱乐及养生作用,将音乐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来看待,标志着人们开始着眼于音乐的特殊性,深入到音乐的内部加以探究,具有进步意义。
文中反映出的主张音乐脱离封建政治功利的音乐思想与主张“礼乐刑政”并举的官方音乐思想,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音乐美学思想两大潮流的源头。
在道家音乐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声无哀乐论》是承前启后的一环。
它一方面肯定有声之于乐,明确要求音乐摆脱礼的束缚,体现人的本性。
但另一方面,它虽立足于道家,却因其承认礼乐的教化作用,规定音乐必须具有平和的精神、持崇雅排俗的态度,而又接近于儒家。
《声无哀乐论》的美学思想代表魏晋时期音乐艺术上由传统封建政治功利实用审美态度转向崇尚个性,崇尚自然。
它要求尊重艺术自身特有的规律具有“自律论”色彩,与西方十九世纪著名音乐学家爱德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论著《论音乐的美》有不少论点非常相似,在世界音乐美学研究领域中有着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嵇康《声无哀乐论》的音乐审美观
嵇康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他对音乐艺术的审美观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认识。
他为人所津津乐道的音乐审美观就是:“声无哀乐。
”那么他这一观点的具体内涵是怎样的呢?
嵇康认为,音乐是由声音组成的,它和各种乐器的演奏方式、乐器的特点、唱法的区别、曲调的不同以及情绪的变化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曲优美的乐曲,必须符合和谐、流畅、清脆等基本条件。
而一个好的演奏家,则需要具备音乐感知能力、演奏技巧和心灵沟通的能力等。
嵇康的“声无哀乐”观点,是从人类音乐千百年的发展中,得出的一个结论。
他认为良好的音乐作品应该是独立有魅力的,不受情感的左右,也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喜好而被改变。
在嵇康看来,音乐的美学价值要求体现音乐本身的完美与独立,而不是任由外界的因素对其进行干扰和歪曲。
他相信人们的耳朵是真正的艺术判断者,良好的音乐作品必须需要在静默时刻就能够被体会到其美感,而不是单凭文字和音乐结合起来才能体会到。
嵇康的“声无哀乐”观点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现今社会,音乐艺术已变得商业化,市场的态度是否能让人们对音乐的感受变成了关键。
嵇康认为,音乐的价值不在于其商业价值和是否为人们所接受,而是在于其本身的完美和无限的魅力。
- 18 -2023年 第1期嵇康,字叔夜,善弹琴,具有很高的音乐造诣,著有《声无哀乐论》《琴赋》,其《嵇氏四弄》与《蔡氏五弄》合称为“九弄”。
《声无哀乐论》中,秦客与东野主人通过八次辩论,证明了“声无哀乐”的核心思想。
修海林在《论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中提道:“《声论》的特点,一是它的思辨性强;二是它较之先秦两汉的音乐美学思想,更深入地对音乐艺术审美特征及自身特殊规律进行了探讨。
”[1]修海林在文章中对音乐思想进行了细致研究,但并未对思辨性展开论述。
因而,本文意从思辨性的角度对嵇康“声无哀乐”这一命题进行研究分析。
一、礼乐相合或礼乐分离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乐最开始伴随着祭祀典仪出现。
上古史料中的乐从未单独出现过,相比于礼,乐总是处于依附地位。
因而在先秦时期并不能单独论述乐,无法将礼乐分开研究。
西周建立礼乐制度之后,礼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为维护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的重要手段,乐也随之带有更强的功用化意味。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推崇礼乐制度,这一观念进而成为秦汉以来的主流思想,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礼乐结合是再正常不过的。
所以,礼乐结合是传统雅士思想观点的基本。
主张礼乐结合还是传统的音乐美学观念。
传统经学之士主张,乐应继承雅颂传统,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多股肱之臣都持礼乐结合的观点,他们是传统音乐美学的代表人物。
例如魏晋时的高堂隆提出:“求取亡国不度之器,劳役费损,以伤德政,非所以兴礼乐之和,保神明之休也。
”(《三国志·魏书》)西晋哲学家傅玄认为:“商君始残礼乐。
至乎始皇遂灭其制。
……日纵桀纣之淫乐,二年而灭。
”(《全晋文》)北魏刁雍在《兴礼表》中主张少数民族政权以汉族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礼乐等概念。
由此可知,大部分宫廷重臣都是持礼乐相合的观点,这也是传统的官方音乐美学思想。
主张礼乐分离是汉魏以来随着社会环境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兴观点。
自东汉末年的桓、灵二帝开始,战伐不断,社会动荡,百姓生活悲惨困苦,时代呼吁着一种新鲜的思想体系。
简论嵇康《声无哀乐论》思想嵇康是中国东晋时期的文学家、音乐家,他的文学才华和音乐造诣都非常高。
他与陶渊明、山谷重厚和刘义庆被称为“琅琊四才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声无哀乐论》是嵇康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重要的音乐哲学论著。
这篇论文写于公元300年左右,内容主要讨论了人与音乐的关系。
嵇康认为人在听音乐时会受到哀乐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会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声无哀乐论》的核心思想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嵇康认为音乐是一种无形的语言,它具有独特的表达能力。
他认为音乐不同于文字和言语,它可以直接影响人的情感和心灵。
而且,音乐的艺术表达是通过声音和节奏来实现的,这种表达方式具有独特的魅力和感染力。
嵇康强调了音乐与情感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音乐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激发和调动人的情感。
音乐能够表达人的喜怒哀乐,可以让人产生共鸣和共情。
他主张人们在欣赏音乐时应该尽情发泄情感,将内心的压抑和忧伤通过音乐来释放出来。
嵇康对音乐的艺术目的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他认为音乐的艺术目的不仅仅是要让人产生愉悦和享受,更重要的是要引发人的思考和感悟。
他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能够触动人的心灵,让人对生活和人生产生思考和领悟。
他强调艺术家要有独立思考和富有创造力的精神,通过音乐来传递真善美的思想和价值观。
嵇康对音乐的社会功能进行了探讨。
他认为音乐不仅仅是一种个体的感受和表达,更是一种社会的联系和凝聚力。
音乐能够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和理解,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他认为音乐是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调节器,通过音乐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一部探讨音乐哲学的重要著作。
他通过分析音乐对人的哀乐影响,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音乐理论,并对音乐的艺术目的和社会功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嵇康的思想对中国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代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简论嵇康《声无哀乐论》思想1. 引言1.1 嵇康的背景嵇康(约223-263年),字安期,汝南郡阳翟县(今河南省栾川县)人,东晋末年著名文学家、音乐家。
嵇康自幼聪颖,博学多才,喜好音乐。
他在南阳时结交了许多文学家和音乐家,培养了自己的文学才华和音乐造诣。
嵇康的才情被当时的文士所称道,被誉为“江东才子”。
嵇康在文学领域的成就也非常突出,他擅长诗歌创作,尤其以七言绝句见长。
他的诗歌清新脱俗,富有音乐感和韵律感,常常表现对自然景物和人情世故的感慨和思考。
嵇康还著有《声无哀乐论》,在论述声音的美学理论方面也有重要贡献。
嵇康是一位多才多艺,才情横溢的文学家和音乐家,他的作品在当时享有盛誉,对后世的文学与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1.2 《声无哀乐论》的出处《声无哀乐论》是中国古代文论家嵇康的一篇论文,大约成书于东晋时期。
这篇论文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论兼论文艺美学的著作,被称为“论文大家”“齐物论”以来最重要的文论之一。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探讨了声音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揭示了声音与情感之间的联系,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美学观点。
这篇论文对当代文学研究和音乐美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于我们理解嵇康的声音美学思想及其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正文2.1 嵇康对声音的理解嵇康认为,声音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是在空气中传播的振动。
他将声音分为哀乐两类,认为哀乐是声音的本质。
在《声无哀乐论》中,嵇康提出了“声无哀乐”这一观点,强调了声音的客观性和中立性。
嵇康认为,声音本身并没有喜怒哀乐之分,只有在人们的心灵中产生情感波动时,声音才会被赋予不同的情感色彩。
他认为,要理解声音,首先要摒弃主观的情感倾向,客观地接受声音本身的存在。
嵇康认为,声音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不应受人的主观情感干扰。
在嵇康看来,声音是一种不可言说的美,它超越了言语的界限,可以直接触动人的心灵。
他认为,声音之美在于它的纯粹性和中立性,它能够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让人们在沉浸于声音之美中感受到心灵的净化和升华。
嵇康“声⽆哀乐”的意蕴情感的邪正并⽆关于⾳乐,它完全是由⼈⼼决定的。
正因如此,所以嵇康说:“乐之为体,以⼼为主。
故‘⽆声之乐,民之⽗母’也。
⾄⼋⾳会谐,⼈之所悦,亦总谓之乐,然风俗移易,不在此也。
”“⽆声之乐,民之⽗母”,语见《礼记•孔⼦闲居》:“孔⼦⽈:‘民之⽗母,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三⽆。
⽆声之乐,⽆体之礼,⽆服之丧,此之谓三⽆。
’”它的原意是说只要⼈的内⼼是欢愉和顺的,那么是否形为⾳声并不重要,因为⾳声只不过是⼀种表现形式,它的有⽆对情感的欢哀并⽆影响。
虽然嵇康这⾥的引⽤在语意上已有变化,也就是说在他⼼⾥声与情的关系已不是⼀种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者乃属不同的事物,前者的和谐对后者的宣泄,作⽤也很⼤,但是在强调情感的独⽴性上,他与《礼记》的看法则是完全⼀致的。
⼗分明显,在嵇康看来,⼈情的厚薄与⾳声的善恶乃是两回事,风俗的淳杂、世情的诚伪是绝不能拿⾳声来衡量的。
然⽽遗憾的是由于有很多⼈不了解⾳理,所以他们对⾳声的判断总是颠倒的。
在“太和”之乐⽅⾯尤其如此。
嵇康《琴赋》云:“愔愔琴德,不可测兮,体清⼼远,邈难极兮。
良质美⼿,遇今世兮,纷纶翕响,冠众艺兮。
识⾳者希,孰能珍兮,能尽琴德,唯⾄⼈兮。
”虽然只是对琴德⽽发,但应该说对整个“太和”之乐都是适⽤的。
上⽂已证,“太和”之乐只有民风纯正的上古社会以及德通上古的“⾄⼈”才有资格享⽤,衰弊时代由于⼈⼼已发⽣异化,对“太和”之乐的使⽤只能使⼈的情欲变得更加放纵。
可是由于⼈们不了解⾳声与⼈情⼈⼼的关系,反⽽将“太和”之乐视为“淫邪”之声,并把它列为黄⾊禁地,仿佛谁接触了它,谁就变成⼗恶的佞⼈。
孰不知衰弊时代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都衰弊,对于“太和”之乐,那些德通上古也即具有上古遗风的“⾄⼈”仍是可以继续享⽤的。
正是以这⼀思想为基础,所以嵇康认为那些被儒家所看重的“中和”之乐,对于德通上古的“⾄⼈”是并不合⽤的。
那么如何看待嵇康的这⼀认识呢?事实上要真正弄明嵇康“声⽆哀乐”的意义,我们必须将它与魏晋名⼠对“礼”的态度结合起来讲。
《声无哀乐论》的产生原因及其评价问题摘要:《声无哀乐论》的产生与魏晋士人阶层的习好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的音乐成为士人们曲折地与统治阶级斗争的武器。
嵇康为了批判把音乐和政治完全等同起来的观点,提出了“声无哀乐”的论点。
我们要认识到其积极的意义,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其无法突破的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声无哀乐论;嵇康;矛盾一、简述《声无哀乐论》嵇康的重要性很早就被人们认识到了,早在六朝时期就已有定评。
嵇康的代表作品《声无哀乐论》在南朝甚至成了清谈家必备的谈资。
南齐王僧虔在《戒子书》中曾说,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言家口实”之一。
‘“总之,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魏晋时期的嵇康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并一直引起后人的关注及争议。
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嵇康的此论著无可争辩地是音乐美学史上一部极其重要的文论。
而引起争议的原因,则多因为此著本身所体现出的矛盾:嵇康一方面否定音乐与情感的关系,提出了“声无哀乐”的命题,另一方面却在某些理论上肯定音乐可以“和声感人,莫不自发”。
嵇康触及到了美学中的一个核心命题,进行了一次极其罕见的有关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的讨论,但美中不足的是,他的美学观念无法做到理论及其实践的整合统一,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其自身的矛盾所在。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的出现是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的特殊性分不开的。
只有对《声无哀乐论》产生的原因进行全面的剖析,才能对其意义与价值有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
二、作为艺术精神演进过程中的一环作为文化的传承者与创新者,魏晋士人的音乐活动和音乐观明显地反映出时代艺术精神的演进。
魏晋以前,在音乐的发展中,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
儒家思想为中国的音乐提供了主题和内容。
同时,因其以伦理代替艺术,以善取代美,对音乐本身的发展起到了遏制作用。
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学是士人们摒弃了儒家思想后的必然选择。
中国土人身上向来体现了孔孟之道,这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作为“社会的人”的行动指导。
而老庄思想则反映了他作为“个体的人”对心灵自由的向往。
. . .. . . .. .专业 . . 嵇康与《声无哀乐论》 嵇康(223—262年),字叔夜,末著名的思想家、诗人与音乐家。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封建社会秩序经过东汉末年黄巾农民起义的打击而一度遭到破坏之后。当时、蜀、吴三国鼎立,社会处于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的状态,人民流离失所,痛苦不堪。在思想上,以五经博士为代表的汉儒正统思想随着东汉政权的崩溃已无法维持其统治的地位,统治阶级纷纷对它重新估价,并寻求为新的门阀士族服务的思想武器“清谈玄学”来代替它。
嵇康就是玄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氏拥有实权的时候,以宗室的关系做过中散大夫的官职。司马氏掌权以后,他以反对派的姿态与阮藉、向秀、山涛、伶、阮咸、王戎等人号称“竹林七贤”,避居宗室聚居的山阳,与司马氏相对抗。在众人之中,嵇康对司马氏的攻击尤为激烈,因而被司马氏所杀害。
《声无哀乐论》从“客”问“东野主人”开始,引出本篇的主旨问题,这是一篇以提问开始,阐述主人的观点,其中对方从不同侧面反对主人的观点,这样一正一反的对话方式,每个人从不同角度阐述自己对音乐与人的心情感的是否存在影响,进而对音乐的本质做了细致的论述。结构如下:
一,第一轮的论战由反方代表客先提问开始,曰:“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提问,主要以声音是否具有哀与乐的属性。主人认为曾经的理论都已经是旧的,甚至是错误的,使得后世的人混. . .. . . .. .专业 . . 淆了名称与本质的关系,世间的万物,宇宙中的一切事物,无论从视觉到听觉还是味觉,不会因外物的侵蚀而有所改变,既是事物的本质属性不变。声音当然不会因为人们的爱与憎,悲与乐有所改变。这就是作者的论点,万事万物是因其自然规律而独自存在,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而改变。既“声无哀乐”。
世间的事物以其自己应有的状态存在,作者还从味觉方面举例说明,味觉分为甜和苦两类,如果由于某甲聪明而喜爱甜或苦,某乙愚笨而讨厌甜或苦,两者之间并不相干,喜欢、讨厌是一回事,聪明、愚笨又是一回事,难道可以用我的口味标准去衡量,与我口味相同的人我就喜欢他,与我口味不同的人我就讨厌他,我喜欢的味道就是好的味道,我讨厌的味道就是坏的味道吗?由此得出外界和心应该区别开,客观和主观也各有其名。衡量音乐的标准应当以好与不好为主,与悲哀和快乐的感情无关,悲哀和快乐自然是先有情感的存在然后才会发生,和音乐没有必然联系,名称和实质去掉之后自然就显现出来。作者的观点很鲜明,自然之理不因为外物和人的心情绪变化而变化,音乐只是表达自身所具有的基本属性,人类的情绪包括高兴、愤怒、悲哀、快乐、喜爱、憎恨、惭愧、恐怖。这些事人们在接触事物表达感情时有所区别而无法超越的畴。这一切都是独立存在的。
这是他们第一轮唇枪舌战,看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谁也无法说服谁而达到一致的统一认识。 . . .. . .
.. .专业 . . 二,然客反驳作者的说法,他认为哀与乐之情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即感情发自于心,而音乐产生于人的心世界;虽然音乐寄托于各种各样的袅袅声音中流露而出,然能够懂得音乐的人是能够自然而然的感觉到,没有误解。他举例子说明,俞伯牙弹琴,钟子期能够知道他心里所想是《高山》还是《流水》,孔子的学生颜渊听到有人在哭泣,就自然感觉到有生离死别的痛苦。这几个例子说明,感情的表现可以从一定的声音中得到启发与理解。情绪悲伤的人,声音中就流露出悲哀,这是人类感情的自然反应,不可违背的规律。他始终认为音乐本身具有哀和乐的本质属性,即音乐能使人悲哀也能使人快乐。
在这一轮的争辩中,作者以抓住对方论证中存在的漏点开始,即声音与人的心无法达到一致,虽然心中有苦但表面谈笑风生,情绪欢快的人也能做出槌胸叹息的样子,能瞒过善于观察者的怀疑。作者从反面找出对方的错误,进一步阐述声音的存在没有哀乐之分,音乐的容并不能完全表达古人与今人的全部感情世界。音乐有其存在的多种方式,每种方式的存在只能表达当时情景。作者在本段中着重批判了儒家的世俗性和对音乐的虚妄,为了神化一些事情而编造出来的——想让天下之人为音乐所迷惑,掩盖音乐的原理。想以此来愚弄后人。达到以儒家的思想治理天下的虚妄。
作者进一步反诘对方,以对方之理来推之:“音乐能让人悲哀又能使人快乐,所以悲哀与快乐不但能够用音乐表现出来,更有着实际的意义,但是绘画有好看、难看之分,音乐有好听、难听之分,这是事物. . .. . . .. .专业 . . 的属性,而人们是否喜爱,这是人的感情变化引起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却干预不了心,人的感情变化不过是借助于外界事物表现出来而已。至于人的哀乐感情,自然和一定的事物有关,先形成于心,只是由于听到了和谐的声音才表露出来,所以前面已经论述了音乐是没有固定容的,现在是借用这些话肯定他的实质。不能认为哀乐情绪发自于音乐,就像爱憎感情产生于贤愚一样。”作者又以喝酒为例子,喝醉酒的人会表现出喜或怒的感情,从表面看,欢乐和悲哀的感情由于音乐而发,就说音乐有悲哀和快乐的感情,同样也不能认为人的喜怒感情由于酒的作用而产生,不能说酒有“喜酒”和“怒酒”的道理啊。
三,上一轮很难分出是与非,进入第三轮论战,反方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感情来自心,由表情上显露。这是公认的。感情有起伏,音乐有动静,所以声音是能够表达显露在外的哀与乐的。只是由于人的接受能力的差异会有所不同,照此看来,人对声音的感知是与每个人的先天理解力有着必然的联系。不能因为人们对音乐的理解程度深与浅就否定音乐外在表象。反方依然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从对方的观点推之,聪明与愚笨,可爱和可憎的辩证关系,顺而推之人的哀与乐的感情,他依然承认音乐能使人快乐,也能使人悲哀,他认为音乐有哀与乐之名与实,不能够将名实一齐去掉。反方步步紧追,抓住作者的某一方面大谈特谈,只是为自己找出足够的理论驳倒对方,树立自己的观点。
作者以对方的观点出发,即人心应和感觉而变动,声音随着这种变动而发生,感情有起伏,音乐有动静,哀与乐的感情,必然形之于声音。. . .. . . .. .专业 . . 那么钟子期虽然听变化着的音乐,也能有聪明独到的见解。只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而且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都唱一首歌曲,在一种乐器上弹几个音,试问钟子期能够听出他们各自的感情吗?很显然是不能的,因为音乐的本质与人的心不可能达到一致的表达。任何牵连都无非是错误的。
作者又以人类的自然感情笑与泪为例子,吃辛辣的菜肴与敞怀大笑,烟熏了眼睛与抹泪哀泣,同样都是流泪,让善于烹调的厨师品尝也不能说高兴的眼泪是甜的,悲伤的眼泪是苦的。这是人的在体液,是不会表现任何哀乐之情,以此推之任何存在的事物由于其自然本质属性是不会因外界而变化的。音乐有自然和谐,与人情无关,和谐的声音完成于钟磬之乐,高度和谐的声音得之于管弦之声。
四,新的一轮论战由此开始,反方称有些例子有缺陷,招致攻击,但他依然认为声音会对人的感情与情绪产生影响。举例说明,春秋时期的介卢听到牛的哀鸣,就知道它产生的三条小牛做了祭祀的贡品;师旷吹律管就知道南风不占上风,楚国军队要打败战;羊舌子容的母亲听婴儿的嚎哭,就有不祥的预感,知道家要败落。以此推论,世间事物的盛衰吉凶,无不存在于声音之中。这些都是历史记载的,完全运用历史的不可辩驳性,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作者并不示弱,看着对方步步紧逼阵势,也毫不示弱,他从对方的例子着手指出,牛能知道小牛做了贡品而悲伤,母亲听见小孩的哭声,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相通之处可言,作者完全从立论的角度出发找出对. . .. . . .. .专业 . . 方论证的错误。诘难二,师旷吹律管知风向,楚国而败。此处毫无关联的东西被对方牵扯到一起,风完全是自然界之气体,它的流动不会因为律管而进入部,同理为什么一定南风来自楚国,风是随节气变化而有不同风向,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不会随人的思想而转化。律管是一种乐器,有它自己的构造,而奏出美妙的乐曲。空气对乐器只是起到节奏的变化。不会改变其声音的本质。风无形不可见,风声与律管音高不相通。这样的例子只是为了当时统治者的需要假托一种现象预测战争的胜败,安抚人心罢了。三诘,母亲听到婴儿的啼哭预知家败,简直很荒唐的例子,这完全属于巫术之类的假象。这是很难也不曾被验证过。再说声音与感情的道理,就好比外形与心的关系,有外形相同而性情不一的,有外貌不同而性情一样的。婴儿不具有凶与吉的预示功能,琴瑟本身也不具有胜败的预兆,因此人的主观感情和客观存在的音乐,显然是两种不同的事物。两种事物的性质明确了,那么要了解人的性情就不应该以观察外貌做结论,考察心也无须借助于听辨声音。这三个例子都不能成功的论证对方的观点,已经错误的事情,难道还要错下去就是很可悲的事情了。
这一轮双方依然难分上下。双方分别举例论证彼此的观点,作者指出对方举例论证中的缺陷,彼此之间不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不足以说明声音的外在属性,即有无哀与乐。然对方依然承认音乐的强大互动作用,不能只把人类的感情归结于单一的人情世故。人类的感情依然离不开音乐固有的属性。 . . .. . . .. .专业 . . 五,反方仍然诘难对方指出,心情平和的人,听了筝、笛、琵琶的演奏会容貌烦躁而情绪激动;听琴瑟的弹奏会安静且心情悠闲。同一种乐器的演奏,乐器不同,感情也随之变化,而且演奏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会变现不同的感情。烦躁或安静是由于音乐的缘故,那么音乐就不能排除哀和乐的作用。高度和谐的音乐能够感化一切,既承认音乐无所不包,为什么只将感情的复杂变化归结于人情,显然这是不对的。
主人回诘难,说:“琵琶、笛、筝令人烦躁激动”,又说:“曲子不同而感情随之变化。”这是一般人常有的感觉。琵琶类乐器音高而短促,节奏快而富于变化,声音高加之节奏快,所以让人烦躁激动。好像铃铎震耳欲聋,钟鼓震撼人心,这是由于音乐的声音有大小,所以让人有躁动和安静的区别。琴瑟一类的乐器音调较低又加之变化较少,如果不细心静听,就不能全部领略清澈和谐之妙,所以要安静地听才能使之心情闲适。要说乐曲不同,也就像不同乐器的声音罢了。声音基本表现为和谐,能够使人情绪欢快而心满意足,然而音乐是以简单、复杂、音的高低、好听、不好听为其本体,人的情绪是以烦躁、安静、专注、松散予以应和。好像在都市里闲逛,目光随意而情绪松弛,聆听音乐则感情投入而表情端庄,这是由于音乐的本体其美妙在于快慢的变化,感情对声音的应和,也只是停留在烦躁或安静的程度而已。此处作者指出对方概念的混淆,声音与乐曲是不同的,乐器演奏的是声音的高低,而人的心情则主要表现为烦躁和安静,声音对人的刺激只是人对其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