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汉学家的独到点评为什么汉语如此的难
- 格式:pdf
- 大小:25.13 KB
- 文档页数:15

海外学习汉语的主要困难有哪些随着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汉语在国际交流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开始学习汉语。
然而,对于他们来说,学习汉语并非易事,面临着诸多困难。
首先,汉语的语音是一大挑战。
汉语的声调系统对于母语非声调语言的学习者来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部分。
汉语有四个声调,分别是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而且还有轻声。
声调的不同会导致词义的变化,例如“妈”“麻”“马”“骂”,仅仅因为声调的差异,意思就完全不同。
这要求学习者要有敏锐的听觉感知和准确的发音控制,对于习惯了非声调语言的学习者来说,要准确掌握声调的变化并非易事。
其次,汉字的书写是另一个难题。
汉字是表意文字,其形态结构与拼音文字有很大的不同。
汉字数量众多,结构复杂,笔画繁多。
每个汉字都有其独特的形状和笔画顺序,需要学习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记忆和练习。
而且,汉字中有很多形似字和多音字,容易混淆。
例如“己”“已”“巳”,“喝”和“渴”,这对于学习者的辨别能力和记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语法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困难。
汉语的语法规则与许多其他语言有很大的差异。
例如,汉语的语序比较灵活,虚词的使用也较为复杂。
汉语中的量词丰富多样,如“一只猫”“一匹马”“一条鱼”,不同的名词需要搭配不同的量词,这对于母语中没有量词概念的学习者来说是一个难点。
此外,汉语中的动词没有时态和人称的变化,而是通过时间状语和词汇来表达,这与很多印欧语系的语言有很大的不同。
词汇的积累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汉语的词汇丰富多样,包含了大量的成语、俗语、惯用语等。
这些词汇往往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对于外国学习者来说,理解和运用这些词汇需要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的了解。
例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等成语,如果不了解其背后的故事和文化背景,很难准确理解和运用。
文化差异也会给海外学习者带来困扰。
语言和文化是紧密相连的,汉语中很多词汇和表达方式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价值观念等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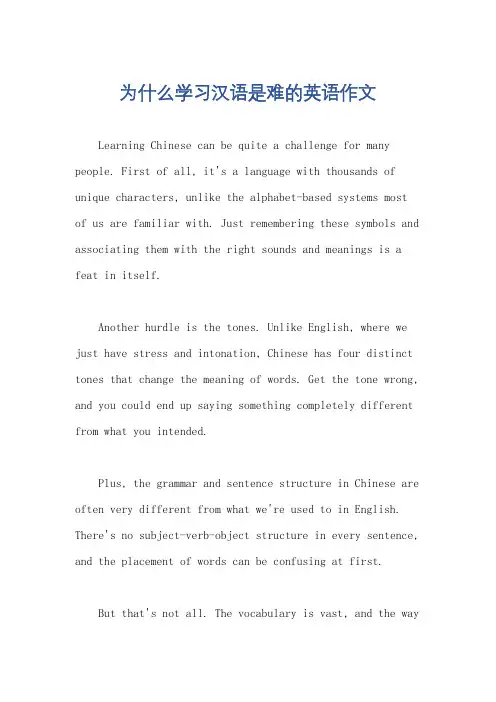
为什么学习汉语是难的英语作文Learning Chinese can be quite a challenge for many people. First of all, it's a language with thousands of unique characters, unlike the alphabet-based systems most of us are familiar with. Just remembering these symbols and associating them with the right sounds and meanings is a feat in itself.Another hurdle is the tones. Unlike English, where we just have stress and intonation, Chinese has four distinct tones that change the meaning of words. Get the tone wrong, and you could end up saying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what you intended.Plus, the grammar and sentence structure in Chinese are often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we're used to in English. There's no subject-verb-object structure in every sentence, and the placement of words can be confusing at first.But that's not all. The vocabulary is vast, and the wayit evolves with regional dialects can be baffling. What might be said in Beijing might sound totally different in Shanghai, even if they're both speaking Mandarin.Oh, and let's not forget the characters again. They're not just for reading and writing; they're also used in everyday life, like in shop signs or on packages. Not being able to recognize these characters can make navigating China quite difficult.In conclusion, learning Chinese is a multi-faceted challenge that requires dedication, patience, and a lot of practice. But with enough effort, it's a rewarding experience that opens up a whole new world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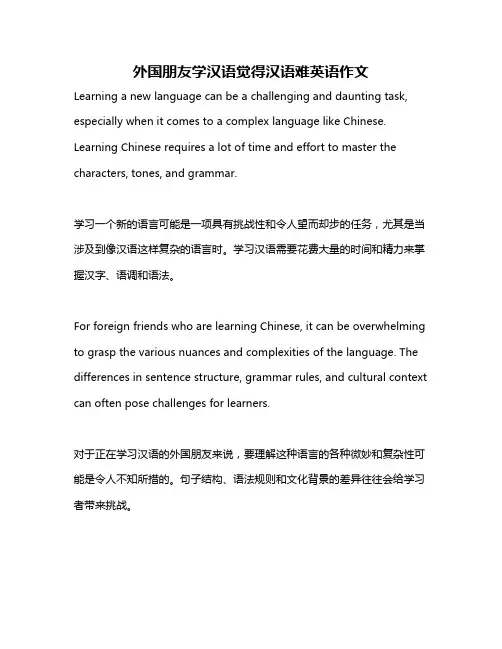
外国朋友学汉语觉得汉语难英语作文Learning a new language can be a challenging and daunting task,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a complex language like Chinese. Learning Chinese requires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to master the characters, tones, and grammar.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可能是一项具有挑战性和令人望而却步的任务,尤其是当涉及到像汉语这样复杂的语言时。
学习汉语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掌握汉字、语调和语法。
For foreign friends who are learning Chinese, it can be overwhelming to grasp the various nuances and complexities of the language. The differences in sentence structure, grammar rules, and cultural context can often pose challenges for learners.对于正在学习汉语的外国朋友来说,要理解这种语言的各种微妙和复杂性可能是令人不知所措的。
句子结构、语法规则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往往会给学习者带来挑战。
One of the biggest difficulties for English speakers learning Chineseis the tonal aspect of the language. Mandarin Chinese has four distinct tones, each of which can change the meaning of a word. Mastering tones requires a lot of practice and a keen ear for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them.对于学习汉语的英语母语者来说,最大的困难之一是语言的声调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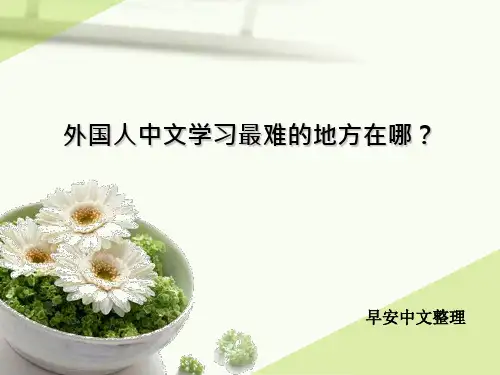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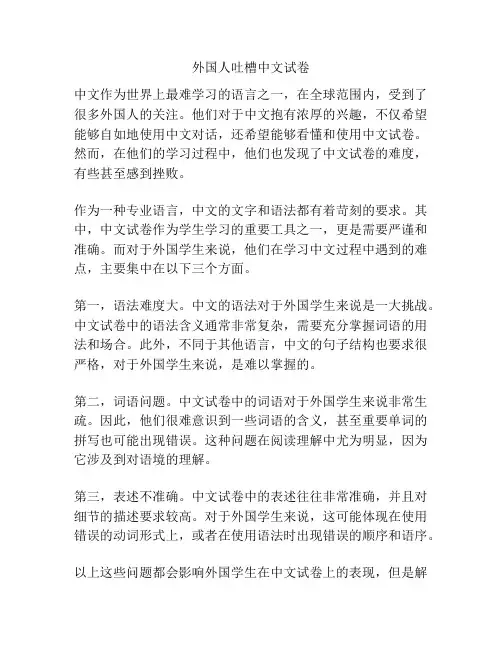
外国人吐槽中文试卷中文作为世界上最难学习的语言之一,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很多外国人的关注。
他们对于中文抱有浓厚的兴趣,不仅希望能够自如地使用中文对话,还希望能够看懂和使用中文试卷。
然而,在他们的学习过程中,他们也发现了中文试卷的难度,有些甚至感到挫败。
作为一种专业语言,中文的文字和语法都有着苛刻的要求。
其中,中文试卷作为学生学习的重要工具之一,更是需要严谨和准确。
而对于外国学生来说,他们在学习中文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语法难度大。
中文的语法对于外国学生来说是一大挑战。
中文试卷中的语法含义通常非常复杂,需要充分掌握词语的用法和场合。
此外,不同于其他语言,中文的句子结构也要求很严格,对于外国学生来说,是难以掌握的。
第二,词语问题。
中文试卷中的词语对于外国学生来说非常生疏。
因此,他们很难意识到一些词语的含义,甚至重要单词的拼写也可能出现错误。
这种问题在阅读理解中尤为明显,因为它涉及到对语境的理解。
第三,表述不准确。
中文试卷中的表述往往非常准确,并且对细节的描述要求较高。
对于外国学生来说,这可能体现在使用错误的动词形式上,或者在使用语法时出现错误的顺序和语序。
以上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外国学生在中文试卷上的表现,但是解决方法并不难。
首先,对于语法难度大的问题,外国学生可以通过反复练习中文语法规则来改善,还可以通过与中国友人多加交流,提高他们的口语和交际能力。
其次,对于生疏的单词问题,外国学生可以在练习之前多用在线词汇翻译工具来解决。
最后,在表述不准确的问题上,外国学生需加强写作练习,不断提高自身的写作能力。
总体来说,中文试卷对于外国学生来说可能是有一些困难的,但是只要他们掌握了基本的语法和语言知识,它们就可以很好地通过中文试卷。
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练习,外国学生可以轻松地掌握中文试卷,使他们在短时间内获得更好的成绩和平稳的学习过程。

为什么外国人都说,中文是全世界最难的语言?真的难吗?
联合国统计过语言难度,汉语第一,日语第五。
中文的偏旁部首共有254个,能组合出来厚厚的字典,字之间又能组合出词典、成语词典、歇后语词典。
再加上63个拼音,阴平阳仄四个音调,就算老外能听懂,会说正确的发音。
但是同一个字,不同的发音还有不同的意思啊。
举个栗子,干和干,内涵完全不一样啊!
更让外国人崩溃的是一模一样的词,却有不同的意思,比如说:方便
我接触过很多老外,有些老外只学了一两年汉语,就能说的比很多中国人都好。
我在沈阳大学中见过很多黑人留学生,一口地道的东北话比小沈阳还溜,闭上眼睛根本想象不出来对方是个外国人。
我在广州还见过很多非法居留的黑人,一口广府粤语一点不比本地人差。
1、汉语与英语、德语之类是不同语系,学另一种语系就意味着另起炉灶。
2、汉语是三维语言,英语之流是二维语言,由低级像高级发展自然不容易。
3、深厚的中华文化,想各类成语、俗话、历史典故。
正如穷则变,变着通。
用学同类型语言的方法学汉语的死板方式自然学不会。
综上,汉语对外国人难只是一个伪命题,乍一看难而已,可能入门困难一点,毕竟语系不同,但只要外国人肯认真学,下功夫,想学好也不是非常难的事。
PS:我问过一个会好几门外语的德国人,你觉得哪门语言最难。
他说日语吧。
欧洲人称日语为“魔鬼的语言”,至今他的日语水平不如汉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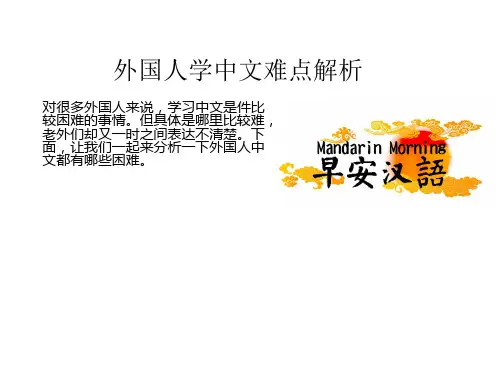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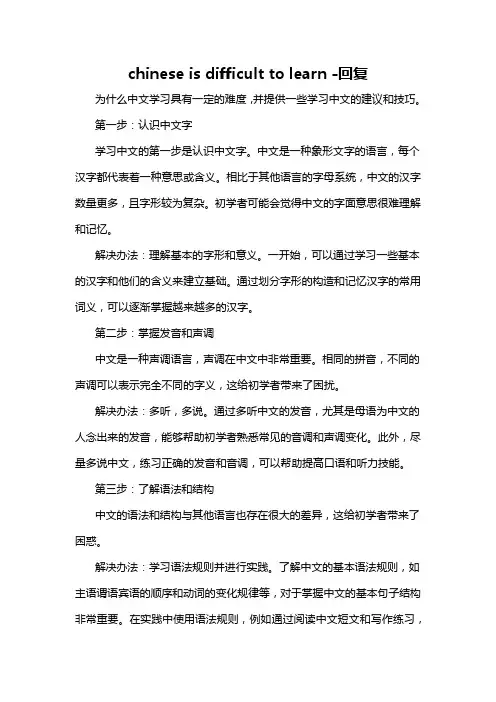
chinese is difficult to learn -回复为什么中文学习具有一定的难度,并提供一些学习中文的建议和技巧。
第一步:认识中文字学习中文的第一步是认识中文字。
中文是一种象形文字的语言,每个汉字都代表着一种意思或含义。
相比于其他语言的字母系统,中文的汉字数量更多,且字形较为复杂。
初学者可能会觉得中文的字面意思很难理解和记忆。
解决办法:理解基本的字形和意义。
一开始,可以通过学习一些基本的汉字和他们的含义来建立基础。
通过划分字形的构造和记忆汉字的常用词义,可以逐渐掌握越来越多的汉字。
第二步:掌握发音和声调中文是一种声调语言,声调在中文中非常重要。
相同的拼音,不同的声调可以表示完全不同的字义,这给初学者带来了困扰。
解决办法:多听,多说。
通过多听中文的发音,尤其是母语为中文的人念出来的发音,能够帮助初学者熟悉常见的音调和声调变化。
此外,尽量多说中文,练习正确的发音和音调,可以帮助提高口语和听力技能。
第三步:了解语法和结构中文的语法和结构与其他语言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给初学者带来了困惑。
解决办法:学习语法规则并进行实践。
了解中文的基本语法规则,如主语谓语宾语的顺序和动词的变化规律等,对于掌握中文的基本句子结构非常重要。
在实践中使用语法规则,例如通过阅读中文短文和写作练习,可以加深对语法规则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第四步:积累词汇和表达中文词汇量丰富,每个词汇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和用法。
初学者可能会觉得记忆这些词汇和短语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解决办法:多读多写。
通过阅读中文文章、书籍和材料,积累词汇和短语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此外,多写中文,练习使用词汇和短语,可以帮助巩固记忆和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第五步:培养学习兴趣和习惯学习中文需要耐心和恒心,保持学习兴趣和习惯对于持续学习非常重要。
解决办法:创造各种学习中文的机会。
参加中文学习班或找到一个学习中文的伙伴,可以提供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观看中文电影和听中文音乐也是锻炼听力和理解能力的好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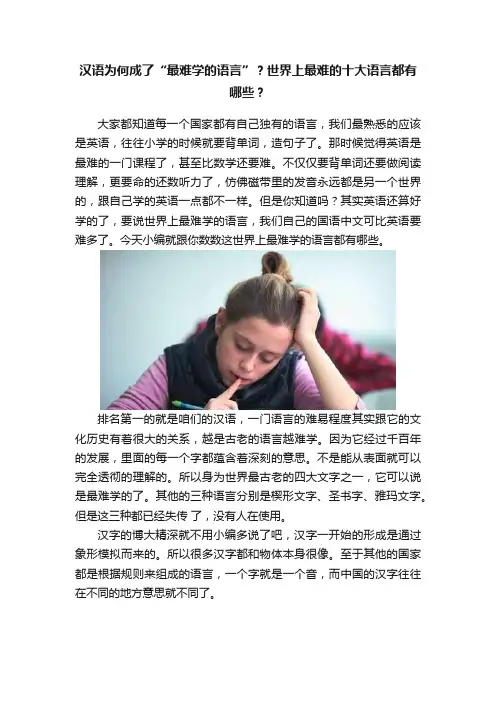
汉语为何成了“最难学的语言”?世界上最难的十大语言都有哪些?大家都知道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有的语言,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英语,往往小学的时候就要背单词,造句子了。
那时候觉得英语是最难的一门课程了,甚至比数学还要难。
不仅仅要背单词还要做阅读理解,更要命的还数听力了,仿佛磁带里的发音永远都是另一个世界的,跟自己学的英语一点都不一样。
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英语还算好学的了,要说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我们自己的国语中文可比英语要难多了。
今天小编就跟你数数这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都有哪些。
排名第一的就是咱们的汉语,一门语言的难易程度其实跟它的文化历史有着很大的关系,越是古老的语言越难学。
因为它经过千百年的发展,里面的每一个字都蕴含着深刻的意思。
不是能从表面就可以完全透彻的理解的。
所以身为世界最古老的四大文字之一,它可以说是最难学的了。
其他的三种语言分别是楔形文字、圣书字、雅玛文字。
但是这三种都已经失传了,没有人在使用。
汉字的博大精深就不用小编多说了吧,汉字一开始的形成是通过象形模拟而来的。
所以很多汉字都和物体本身很像。
至于其他的国家都是根据规则来组成的语言,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而中国的汉字往往在不同的地方意思就不同了。
还有一个特别的难点就是汉字的读音多样,都有四种读音。
而每一种读音的意思都是截然不同的。
比如哦字,每一声的意思都是不一样的,读第一声的时候是一种发音,第二声的时候代表的是疑问的意思,第三声是一种答应的意义,第四重则带有一点点的语气,好像有点突然领悟的意思。
光是这一个哦字就够复杂的了,更何况其他的字呢?另外汉语中的文字有很多读音都是一样的,读音一样但是意思不一样,用法也是大不相同。
这就需要有一定的词语储备才行。
比如“布置”一般是用在布置房间,而“部置”则是用在排兵布阵这样的事情上。
是不是有点晕了呢?要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想搞通这个同音不同意思的就真的是太难了。
还有汉语的听力跟英语的听力要难,比如大家总是调侃用周杰伦的语音来当八级中文听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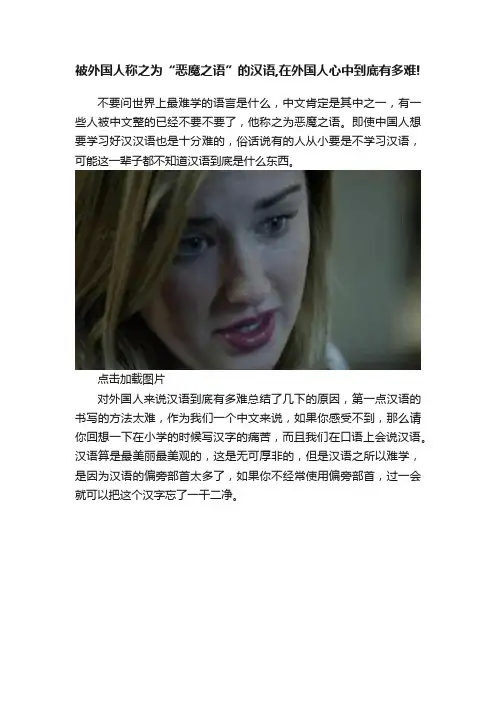
被外国人称之为“恶魔之语”的汉语,在外国人心中到底有多难!
不要问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是什么,中文肯定是其中之一,有一些人被中文整的已经不要不要了,他称之为恶魔之语。
即使中国人想要学习好汉汉语也是十分难的,俗话说有的人从小要是不学习汉语,可能这一辈子都不知道汉语到底是什么东西。
点击加载图片
对外国人来说汉语到底有多难总结了几下的原因,第一点汉语的书写的方法太难,作为我们一个中文来说,如果你感受不到,那么请你回想一下在小学的时候写汉字的痛苦,而且我们在口语上会说汉语。
汉语算是最美丽最美观的,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汉语之所以难学,是因为汉语的偏旁部首太多了,如果你不经常使用偏旁部首,过一会就可以把这个汉字忘了一干二净。
点击加载图片
第2点就是不会有很多的空格,相比较英语而言,可以说汉语字和字之间没有间距,尽管汉语也有很多常用的偏旁部首,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没有英语那样的规律。
点击加载图片
第3点就是汉语中夹杂许多古汉语,如果是学习通俗的汉语,也能让外国人无所适从,那么文言文直接放弃吧,古汉语包囊着中国5000年的文化底蕴和积累,对汉字学习才能有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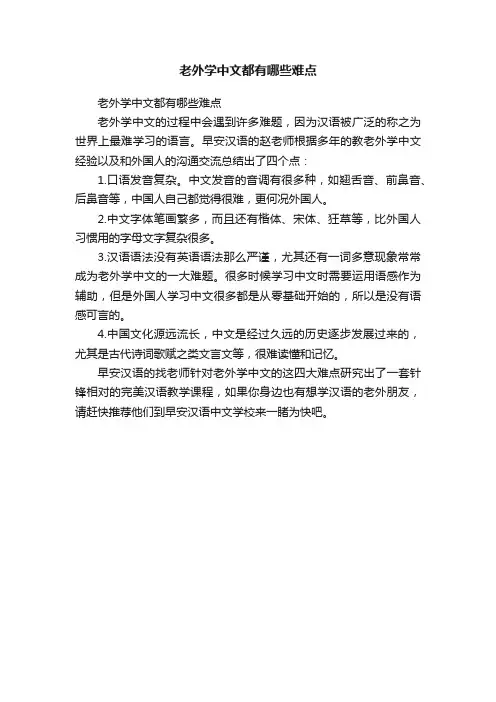
老外学中文都有哪些难点
老外学中文都有哪些难点
老外学中文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难题,因为汉语被广泛的称之为世界上最难学习的语言。
早安汉语的赵老师根据多年的教老外学中文经验以及和外国人的沟通交流总结出了四个点:
1.口语发音复杂。
中文发音的音调有很多种,如翘舌音、前鼻音、后鼻音等,中国人自己都觉得很难,更何况外国人。
2.中文字体笔画繁多,而且还有楷体、宋体、狂草等,比外国人习惯用的字母文字复杂很多。
3.汉语语法没有英语语法那么严谨,尤其还有一词多意现象常常成为老外学中文的一大难题。
很多时候学习中文时需要运用语感作为辅助,但是外国人学习中文很多都是从零基础开始的,所以是没有语感可言的。
4.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文是经过久远的历史逐步发展过来的,尤其是古代诗词歌赋之类文言文等,很难读懂和记忆。
早安汉语的找老师针对老外学中文的这四大难点研究出了一套针锋相对的完美汉语教学课程,如果你身边也有想学汉语的老外朋友,请赶快推荐他们到早安汉语中文学校来一睹为快吧。
外国人学中文难点分析
外国人学中文难点究竟难在那里呢?首先,汉语的四声调对老外来说是个大难题。
外国人如果一旦下定决心要学习好汉语,那就得时时刻刻注意中国人的讲话声调,要刻意模仿中国人的四声。
没有这个自觉意识和开口行动是很难掌握好四声的。
外国人学中文难点中语言本身的差异,汉语的词类种类繁多,用法也颇纠结复杂。
比方说较突出的一个词类难点就是汉语里的量词,这个量词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一辆车,一只笔,一栋楼房,一位妇女”中国人对此总是脱口而出,毫无偏差。
可是对外国人来说,如何正确选择运用量词就成了个大难题。
在学习外语时,任何人都可能犯一种叫做“母语负迁移”的毛病。
何为“母语负迁移”呢?简单说,就是在学习者不熟悉目的语规则的情况下,只能依赖母语知识,并将母语规则生搬硬套地运用到目的语身上。
外国人在开始学习汉语时,很容易在他们的“汉语”身上发现其母语的影子并嗅到其母语的味道
汉语貌似直白简单,其实是九曲回肠,沟壑纵横。
没有长时间对汉语的亲密接触揣摩,是难以理解其内部的细微复杂涵义的。
外国人学中文难点汉字相对于很多外国人字母而言,中国笔画的横竖撇捺是何其曲折与莫测也。
简单的汉字若长久不写,即使中国人自己也会倍感生疏,有无从下笔之感更何况外国人。
汉语为什么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世界十大最难学语言排名!汉语,即汉族的传统语言,是中国通用语言,国际通用语言之一,属汉藏语系,同中国境内的藏语、壮语、傣语、侗语、黎语、彝语、苗语、瑶语,中国境外的泰语、缅甸语等都是亲属语言。
汉语是孤立语,一般有三到十五种声调。
汉语的文字系统汉字是一种意音文字,兼具表意和表音功能。
汉语包含口语和书面语两部分,古代书面汉语被称为文言文,现代书面汉语被称为白话文,以现代标准汉语为规范。
汉语有标准语和方言之分。
现代标准汉语即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现代标准汉语中,除轻声外共有四个声调。
汉语为什么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世界十大最难学语言排名!最难学的语言是神马?对于很多人而言最难学的语言是“其它国家的语言”,比如日语、韩语、英语之类的,完全看不懂,但对于其它国家的人来说,最难学的语言又是什么?答案是:汉语!没错,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没有之一),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布的“世界上最难学的十大语言排名”中,汉语便位于第一,是不是很意外?问题来了,汉语为什么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这得从下面几方面进行解析。
1、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四大文字之一其它三类古老文字是:楔形文字,苏美尔人所创造;圣书字,古埃及人创造,又称埃及象形文字;玛雅文字,美洲玛雅人创造。
但是,这三类古老的文字均已相继成为历史的陈迹,唯汉字独存。
也就是说,世界上最古老的、还在使用的文字,只有汉字(语)。
几千年的文化都凝聚在汉语文字之中,不用小编多说大家也应该知道,越是深奥的语言文字越是难学、难理解。
2、汉语是世界上唯一的,并且还在使用的表意文字表意文字是一种图形符号只代表语素,而不代表音节的文字系统,即一个文字表达的是意思,而不是发音,其它国家的文字都是表音的。
打个比方,我们之所以能够读懂几千年前的诗词,因为我们能够理解诗词的意思,而不是读音。
再打个比方,英语单词Computer,表达的就是这个发音,如果电脑是另一个读音,那么就不会写成这个样子了。
盘点老外学汉语的崩溃
盘点老外学汉语的崩溃是一种令人心碎的现象。
虽然有很多因素
会让老外学习汉语变得困难,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汉语的拼音
的抵抗力。
无论外国人怎么努力,学习汉语拼音都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坎。
而学习汉语拼音可能是老外学汉语中最艰辛的过程,因为它不像
西方语言,只需要学习几组不同的元音和辅音就够了,而汉语的拼音
有数十个不同的声母、韵母等等,学习起来就显得十分艰难了。
另外,老外学汉语可能会面临的另一个棘手问题是语言的繁复性,尤其是汉语的语法结构和句式特别复杂,许多句子的构造都很难理解,所以学习起来就更难了。
此外,在汉语表达中,一词多义和繁杂的文
法规则也是另一个老外学汉语时无法逃避的挑战之一。
而所有这些都令老外学汉语变得很难,他们会不断地碰壁,感到
很艰难,这是一个循环,最后老外可能会因此感到崩溃。
但是,坚持
不懈的耐心是学习汉语的关键,只要咬紧牙根,坚持学习,总有一天
会有收获的,并可以演讲流利的中文。
为什么学习汉语是难的英语作文Why Learning Chinese Can Be Difficult for English SpeakersLearning a new language is always a challenging task, but for English speakers, learning Chinese can often seem like an insurmountable hurdle. There are numerous reasons why this ancient and complex language can pose difficulties for those accustomed to the structure and vocabulary of English.Firstly, the writing system of Chinese is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the alphabetic system used in English. Characters, or "kanji," are unique symbols that represent words or syllables, rather than sounds. This requires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memorization and practice for English speakers, who are accustomed to mapping sounds to letters. The complexity of the characters themselves, often consisting of numerous strokes and intricate details, adds to the difficulty.Secondly,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Chinese differs greatly from English. Chinese is a topic-prominent language, meaning that the subject of a sentence is often implied rather than explicitly stated. This can be confusing for English speakers, who rely on subjects and verbs to form the backbone of their sentences. Additionally, Chinese uses particles and tone to convey meaning, which are absent in English. These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require a great deal of sensitivity and practice to master.Thirdly, the vocabulary of Chinese is vast and diverse. Unlike English, which has borrowed extensively from other languages, Chinese has a unique vocabulary that is largely unrelated to other tongues. This means that English speakers must start from scratch in building up their Chinese vocabulary, without the benefit of any preexisting connections. Furthermore, the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can b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ir spelling, requiring a separate set of skills to master.Finally,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Chinese adds another layer of complexity. Chinese is deeply rooted in its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history, and many expressions and idioms have specific cultural meanings that are difficult for foreigners to grasp.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ng these cultural nuances is essential for trulymastering the language.In conclusion, learning Chinese can be a daunting task for English speakers due to its unique writing system, grammatical structure, vast vocabulary, and cultural context. However, with persistence and dedication, the challenges can be overcome, and the rewards of speaking this beautiful and ancient language can be immense.。
一个美国汉学家的独到点评为什么汉语如此的难任何一个喜欢思考的人看到这这篇研究文章标题后可能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对谁难?”这是个合乎情理的问题。
毕竟,中国人学起来似乎没问题。
当中国幼童们经历“可怕的两岁”时,正是他们的汉语把他们的父母搞得焦头烂额,而且再等上几年,也正是这些小孩就会真的用那些难到让人没办法的中文字潦草地写情书和购物单了。
那么我说“难”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篇文章的语调会带有很多的牢骚和抱怨,所以我不如直接明确说出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对我来说难,一个母语是英语的人在成年时试图学习汉语,经历教科书、录音带、会话伙伴等等这样一整个过程,整个一个语无伦次的过程。
我的意思是对我来说难----对很多其他的西方人来说难,他们耗费人生的一年又一年,用脑袋来撞击中国的长城。
如果这就是我所要表达的全部,那么我的陈述就太空洞了。
汉语对我来讲当然难。
毕竟,任何一门外语对一个非母语的人来说都难,对吧?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如此。
对一个学习者来说,并非所有的外语都同等程度的难。
取决于你的母语是什么。
一个法国人学意大利语通常比一个美国人学起来更容易,而一般美国人学德语比日本人快得多,如此等等。
那么,我现在争辩的是,汉语比你有可能打算去学的任何其它一种语言都难。
我的意思是,汉语不仅仅是对我们(母语为英语者)来说难,而是在绝对程度上难。
也就是说,汉语对中国人他们自己来说都难。
要是你不相信,可以去问一个中国人。
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愉快地告诉你他们的语言很难,可能是全世界最难的。
(很多人甚至以此自豪,就如同一些纽约人事实上会为生活在美国最不适宜居住的城市而自豪一样。
)也许所有的中国人都该因生为中国人而获颁一枚奖章。
无论如何,他们总体上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他们的母语所具备的珠穆朗玛峰般的地位,他们站在其“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峰顶上,注视着卤莽愚蠢的老外们呼哧呼哧地沿着陡峭的山坡往上攀爬。
每个人都听说过一个被广泛认定的事实:英语里有句成语----“这对我来说如同希腊文”,如果你在全世界所有语言里寻找这句成语的对等表达,并由此达成一个“哪门语言最难”的共识,那么这一语言学调查的结果是,汉语轻松赢得“标准难以读懂语言”称号。
(比如,法语里有句成语C""""est du chinois,“这是中文啊”,等于是说:“没法看懂”。
其它语言也有类似的表达)。
那么,问题出现了,中国人他们自己又把哪种语言看作是难到没办法的呢?那么,在中文里寻找对等的表达,你就会找到Gēn tiānshū yíyàng 意思是:“跟天书一样”。
这一语言奇谈是有其事实根据的;汉语的难到叫人心碎的名声可说是名至实归。
那些不是因为喜欢享受而选择学这门语言的人会被极其糟糕的付出/效果比例搞得焦头烂额。
而那些恰恰是被这门语言的令人沮丧的复杂和困难所吸引的人则永远不会失望。
不管这些人是因为什么缘故开始的,每一个选择学习汉语的人早迟都会问自己:“我到底是怎么了,干吗在做这个?”那些还能回想起自己最初目的的人,会明智地立刻选择放弃,因为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为其在冗长和乏味中挣扎。
而那些只是说“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现在没法止步”的人,会有一些成功的机会,因为他们有那种莽撞的固执。
好,既然已经解释了一些我的意思,我现在回到我一开头的问题:为什么汉语如此见鬼般的难?(一)因为书写系统很荒谬漂亮、复杂、神秘----但是荒谬。
我,和很多学汉语的学生一样,最初被汉语所吸引首先就是因为其书写系统,那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令人着迷的符号之一。
你学的汉字越多,汉字也变得越诡秘和令人上瘾。
对汉文字的研究可以令人一辈子全心身投入,而且很快你就会发现你每天从事的任务就是毫无希望地试图用你不断漏水的长期记忆口袋在汉字的汪洋大海里一滴一滴地积累。
汉字的美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当中国人开始意识到普世无文盲的重要性时,这些像形符号乃是一种裹脚这一点就变得清晰起来----某些恋物癖者可能喜欢它们的样子,但是它们对于日常使用来说是不太实用的。
原因之一,要掌握足够的汉字以达到功能上的非文盲简直就是不合情理的难。
有人可能又会问:“和什么相比难?”答案很容易得出:比西班牙语、希腊语、俄语、印地语,或者任何其它理智、“正常”的语言都难,这些语言最多只需要几十个符号就能拼写出本语言中的任何东西。
约翰?德佛兰西思在他的《汉语言:事实与幻想》一书里称,他的中国同事估计,一个母语为普通话的人需要花费七到八年时间来掌握三千个汉字,而他的法国和西班牙同事估计他们各自国家的学生达到同样的程度只需要那个时间的一半。
自然,这种估计多少有些粗糙和凭印象(“同样的程度”到底是什么不清楚),但是总体隐含的东西是明白无误的:汉语书写系统在绝对意义上比字母书写系统更难学习。
即便是中国儿童在大脑处于顶尖吸收状态时,其学习汉字所碰到的麻烦也大于其它国家相应年龄的儿童学习本国文字遇到的麻烦。
只需要想象一下像我这样反应较迟缓的刚过青春期的人在学习本国语言过程中所经历过的困难就知道了。
每个人都听说过汉语之所以难学是因为需要记住大量的汉字,而这是绝对真实的。
一些热门的书和文章将此轻描淡写为:“尽管中文里有[10,000, 25,000, 50,000 你可任选一]个不同的汉字,其实你只需要掌握2,000个左右就可以阅读报纸了。
” 胡说八道。
当初我掌握了2,000个汉字时,我没法顺利阅读报纸。
每一行都有好几个字我得查字典,而且即便是查过了之后,我对文章具体说的什么仍然似懂非懂(我所理解的“阅读”在这一背景下是指“阅读并基本读懂文章而不是非得再去查好几十个汉字”;否则这种宣称就很空洞。
)这一神话得以传播所依据的事实是,如果你看汉字出现频率,任何报纸95%以上的汉字都轻松地被包含在那头2,000个最常用汉字里。
然而,这一统计没有告诉你的是:仍然有大量你不熟悉的单词是由这些熟悉的汉字组成的。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请注意在英语里,你知道up和tight各自的含义并不等于你就知道uptight的含义。
)而且,正如任何学过任何语言的人都知道,你常常很熟悉一段文字里的每一个词,却仍然没法弄懂在说什么。
阅读理解并非仅仅是知道一大堆词这么简单;你必须能够感觉到词与词之间在大量的上下文里是怎样组合的。
另外,还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即便你知道在一段给定文字里的95%的汉字,那剩下的5%常常正好是了解文章主要观点所需要知道的最关键的汉字。
一个母语非英语的人在读到一篇标题为“JACUZZIS FOUND EFFECTIVE IN TREATING被发现对静脉炎有疗效”]的文章时如PHLEBITIS” [“JACUZZIS果不知道JACUZZIS和PHLEBITIS[静脉炎]是什么,那么在理解上也走不了多远。
对于那些置身汉学领域的人而言,阅读的问题常常是个足以让人肝火飚升的问题。
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敢于站在一群同事面前大声朗读任意选出的一段文字?然而,自卑情结或者怕丢面子使得许多教师和学生不自觉地在阴谋般的静默中互相配合,每个人都假装通过四年汉语课,勤奋的学生能够轻松浏览从《论语》到鲁迅的的任何文字,仅仅偶尔停下来查阅(当然是用他们的汉-汉词典啦)某个出现率很低的恼人汉字而已。
当然,其他的人面对困难会更诚实一些。
那天,我的一个学了十年或以上汉语的研究生同学对我说:“我那个研究,阻力真的很大,原因就是我还是没法读汉语。
读两到三页就要花掉好多个钟头,可我又不能用跳过的办法来救自己一命。
”如果这句坦诚话出自一个已学了十年----比如说法国文学----的学生之口,那会把人惊呆的,然而这样的话我却一直不间断地从与我从事相同工作的人口中听到(至少在那种没有什么防备、喝多了一点青岛啤酒后的场合下,开始倾诉论文进展缓慢的苦衷)。
我的一个老师曾经告诉我他和他的同事们有时会玩的一个游戏竞赛:在亚洲语言图书馆,从中国部的书架上任意抽出一本书,然后看谁能最先说出这本书是谈什么的。
任何曾花费时间在东亚语言藏书部做过研究的人都可以证明这样的竞赛的确有足够难度----至于去读那本书,还是别提了吧。
对于那些急不可耐想要开始饱揽海量丰富的中文材料、却又不得不在头几年里依靠教师提供的味道平平的罐头餐、课本例子以及仔细选编的提胃品过活的学生而言,这样的一种状况是很让人灰心丧气的。
反观学习通常的西方语言,对照是惊人的。
学了大约一年法语后,我已经可以大量阅读了。
我阅读了常见类型的小说----萨特的La nausée,伏尔泰的Candide, 加缪的Létranger----外加无数的报纸,杂志,漫画书,等等。
工作量很大但是不怎么费劲;当时所有我真正需要的,是一部好词典和一私家车库摆摊售旧货时我买到的一本磨损了的法语语法。
这种方法用到汉语上面就不行了。
学完三年的汉语之后,我还没有读过一本中文小说。
我发现要读真是太难了,慢得要命,而且没有收获感。
报纸也一样,仍然令人望而却步,读一篇文章,每十个字就得用词典查一个字。
扫描人民日报第一版面时,不能完全读懂单个标题也是常见的事。
就在那时,有人建议我读《红楼梦》,还给了我一套精美的三卷版。
我只有笑了。
那套书至今仍然摆在我的书架上,犹如一个胖胖的佛爷,只有前二十页左右填满了各种潦草写下的定义和问号,其余的书页崭新----未被开垦过的处女地。
学了汉语六年之后,我的程度是依然无法在没有英文翻译对照的陪伴参考下阅读此书。
(说“阅读此书”,我的意思是“为享受而读”。
假如有谁用枪指着我的脑袋,再把一本词典塞进我的手里,我也能这本书看完吧。
)汉语书写系统的另一个荒谬在于有繁体和简体两套文字(幸好部分字是相同的----天降慈悲!)繁体仍然在台湾和香港使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采用了简体。
任何学汉语的外国学生多少都得被迫熟悉两套文字。
(二)因为汉语没有使用字母的常识想象一下一个普通中国成年人决定要学英语。
需要什么样的技巧来掌握其书写系统?很容易:26个字母。
(当然了,大小写,加上手写体和几个变体。
外加一些引号,撇号,顿号,括号,等等,----所有这些汉语书写系统里也有)这些字母怎么写?从左到右,以空白来区分单词。
暂时撇开拼写和用这些字母造词的问题,这个学英语的中国人需要多少时间来掌握英语书写系统的组成部分?大概一两天左右。
再来看一个决定学汉语的美国本科生。
此人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掌握汉语书写系统?没有任何与字母产生对应的东西,尽管有各种反复出现的组成汉字的部分。
有多少这样的组成部分呢?别问了,回答是无法令人满足的一团乱麻。
那取决于你怎样定义“组成部分”(笔画?偏旁部首?),外加很多其它冗长的细节。
可以说,这个数字相当大,大大超过26个罗马字母。
那么这些组成部分怎样组成汉字呢?一些在另一些的左边,一些在另一些的右边,在其它的周围,在其它的里面----几乎任何情况都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