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史学的特点
- 格式:pdf
- 大小:270.28 KB
- 文档页数: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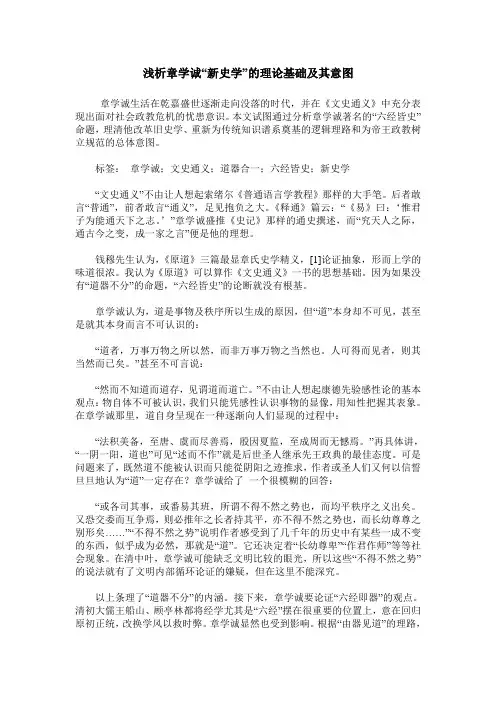
浅析章学诚“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及其意图章学诚生活在乾嘉盛世逐渐走向没落的时代,并在《文史通义》中充分表现出面对社会政教危机的忧患意识。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章学诚著名的“六经皆史”命题,理清他改革旧史学、重新为传统知识谱系奠基的逻辑理路和为帝王政教树立规范的总体意图。
标签:章学诚;文史通义;道器合一;六经皆史;新史学“文史通义”不由让人想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那样的大手笔。
后者敢言“普通”,前者敢言“通义”,足见抱负之大。
《释通》篇云:“《易》曰:‘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章学诚盛推《史记》那样的通史撰述,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便是他的理想。
钱穆先生认为,《原道》三篇最显章氏史学精义,[1]论证抽象,形而上学的味道很浓。
我认为《原道》可以算作《文史通义》一书的思想基础。
因为如果没有“道器不分”的命题,“六经皆史”的论断就没有根基。
章学诚认为,道是事物及秩序所以生成的原因,但“道”本身却不可见,甚至是就其本身而言不可认识的:“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
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
”甚至不可言说:“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见谓道而道亡。
”不由让人想起康德先验感性论的基本观点:物自体不可被认识,我们只能凭感性认识事物的显像,用知性把握其表象。
在章学诚那里,道自身呈现在一种逐渐向人们显现的过程中:“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
”再具体讲,“一阴一阳,道也”可见“述而不作”就是后世圣人继承先王政典的最佳态度。
可是问题来了,既然道不能被认识而只能從阴阳之迹推求,作者或圣人们又何以信誓旦旦地认为“道”一定存在?章学诚给了一个很模糊的回答:“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
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尊之别形矣……”“不得不然之势”说明作者感受到了几千年的历史中有某些一成不变的东西,似乎成为必然,那就是“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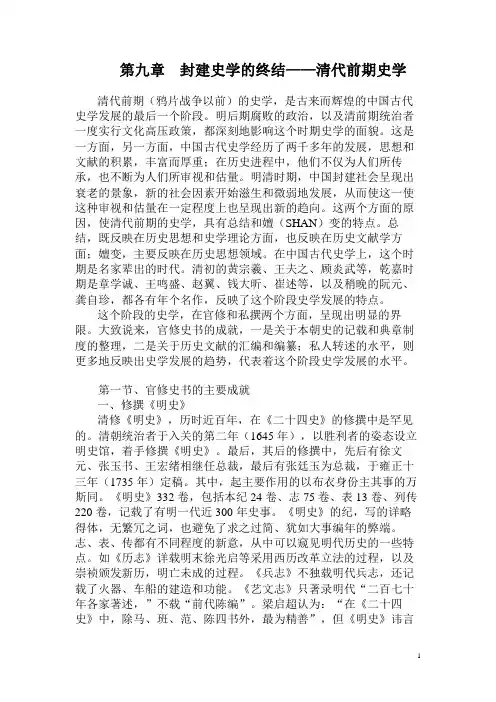
第九章封建史学的终结——清代前期史学清代前期(鸦片战争以前)的史学,是古来而辉煌的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
明后期腐败的政治,以及清前期统治者一度实行文化高压政策,都深刻地影响这个时期史学的面貌。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史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思想和文献的积累,丰富而厚重;在历史进程中,他们不仅为人们所传承,也不断为人们所审视和估量。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出衰老的景象,新的社会因素开始滋生和微弱地发展,从而使这一使这种审视和估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新的趋向。
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使清代前期的史学,具有总结和嬗(SHAN)变的特点。
总结,既反映在历史思想和史学理论方面,也反映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嬗变,主要反映在历史思想领域。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这个时期是名家辈出的时代。
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乾嘉时期是章学诚、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等,以及稍晚的阮元、龚自珍,都各有年个名作,反映了这个阶段史学发展的特点。
这个阶段的史学,在官修和私撰两个方面,呈现出明显的界限。
大致说来,官修史书的成就,一是关于本朝史的记载和典章制度的整理,二是关于历史文献的汇编和编纂;私人转述的水平,则更多地反映出史学发展的趋势,代表着这个阶段史学发展的水平。
第一节、官修史书的主要成就一、修撰《明史》清修《明史》,历时近百年,在《二十四史》的修撰中是罕见的。
清朝统治者于入关的第二年(1645年),以胜利者的姿态设立明史馆,着手修撰《明史》。
最后,其后的修撰中,先后有徐文元、张玉书、王宏绪相继任总裁,最后有张廷玉为总裁,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定稿。
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以布衣身份主其事的万斯同。
《明史》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记载了有明一代近300年史事。
《明史》的纪,写的详略得体,无繁冗之词,也避免了求之过简、犹如大事编年的弊端。
志、表、传都有不同程度的新意,从中可以窥见明代历史的一些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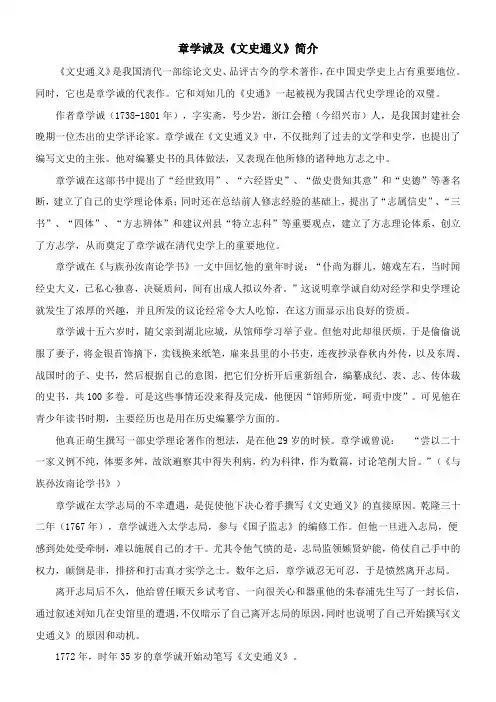
章学诚及《文史通义》简介《文史通义》是我国清代一部综论文史、品评古今的学术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同时,它也是章学诚的代表作。
它和刘知几的《史通》一起被视为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作者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
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
章学诚在这部书中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断,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同时还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建立了方志理论体系,创立了方志学,从而奠定了章学诚在清代史学上的重要地位。
章学诚在《与族孙汝南论学书》一文中回忆他的童年时说:“仆尚为群儿,嬉戏左右,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
”这说明章学诚自幼对经学和史学理论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所发的议论经常令大人吃惊,在这方面显示出良好的资质。
章学诚十五六岁时,随父亲到湖北应城,从馆师学习举子业。
但他对此却很厌烦,于是偷偷说服了妻子,将金银首饰摘下,卖钱换来纸笔,雇来县里的小书吏,连夜抄录春秋内外传,以及东周、战国时的子、史书,然后根据自己的意图,把它们分析开后重新组合,编纂成纪、表、志、传体裁的史书,共100多卷。
可是这些事情还没来得及完成,他便因“馆师所觉,呵责中废”。
可见他在青少年读书时期,主要经历也是用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
他真正萌生撰写一部史学理论著作的想法,是在他29岁的时候。
章学诚曾说:“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为数篇,讨论笔削大旨。
”(《与族孙汝南论学书》)章学诚在太学志局的不幸遭遇,是促使他下决心着手撰写《文史通义》的直接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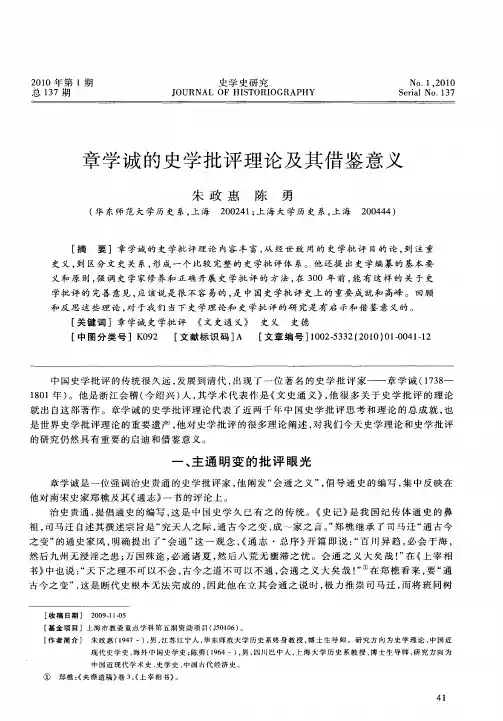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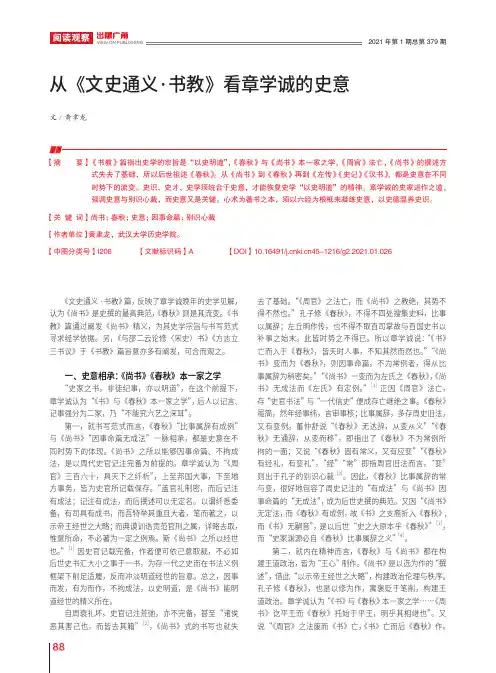
882021年第1期总第379期VIEW ON PUBLISHING从《文史通义·书教》看章学诚的史意文/黄聿龙【摘 要】 《书教》篇指出史学的宗旨是“以史明道”,《春秋》与《尚书》本一家之学,《周官》法亡,《尚书》的撰述方式失去了基础,所以后世祖述《春秋》。
从《尚书》到《春秋》再到《左传》《史记》《汉书》,都是史意在不同时势下的流变。
史识、史才、史学须统合于史意,才能恢复史学“以史明道”的精神。
章学诚的史家述作之道,强调史意与别识心裁,而史意又是关键。
心术为著书之本,须以六经为根柢来凝练史意,以史德温养史识。
【关 键 词】尚书;春秋;史意;因事命篇;别识心裁【作者单位】 黄聿龙,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45-1216/g2.2021.01.026《文史通义·书教》篇,反映了章学诚晚年的史学见解,认为《尚书》是史撰的最高典范,《春秋》则是其流变。
《书教》篇通过阐发《尚书》精义,为其史学宗旨与书写范式寻求经学依据。
另,《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方志立三书议》于《书教》篇旨意亦多有阐发,可合而观之。
一、史意相承:《尚书》《春秋》本一家之学“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在这个前提下,章学诚认为“《书》与《春秋》本一家之学”,后人以记言、记事强分为二家,乃“不能究六艺之深耳”。
第一,就书写范式而言,《春秋》“比事属辞有成例”与《尚书》“因事命篇无成法”一脉相承,都是史意在不同时势下的体现。
《尚书》之所以能够因事命篇、不拘成法,是以周代史官记注完备为前提的。
章学诚认为“《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纤析”,上至邦国大事,下至地方事务,皆为史官所记载保存。
“盖官礼制密,而后记注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无定名。
以谓纤悉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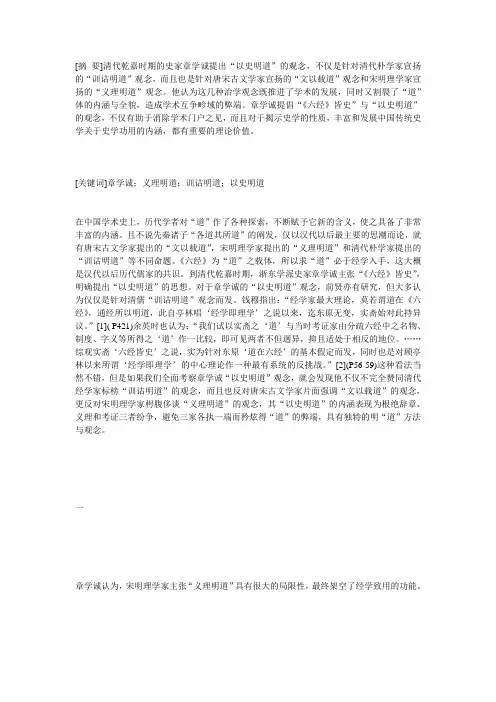
[摘要]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章学诚提出“以史明道”的观念,不仅是针对清代朴学家宣扬的“训诂明道”观念,而且也是针对唐宋古文学家宣扬的“文以载道”观念和宋明理学家宣扬的“义理明道”观念。
他认为这几种治学观念既推进了学术的发展,同时又割裂了“道”体的内涵与全貌,造成学术互争畛域的弊端。
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与“以史明道”的观念,不仅有助于消除学术门户之见,而且对于揭示史学的性质,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关于史学功用的内涵,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章学诚;义理明道;训诂明道;以史明道在中国学术史上,历代学者对“道”作了各种探索,不断赋予它新的含义,使之具备了非常丰富的内涵。
且不说先秦诸子“各道其所道”的阐发,仅以汉代以后最主要的思潮而论,就有唐宋古文学家提出的“文以载道”,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义理明道”和清代朴学家提出的“训诂明道”等不同命题。
《六经》为“道”之载体,所以求“道”必于经学入手,这大概是汉代以后历代儒家的共识。
到清代乾嘉时期,浙东学派史家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明确提出“以史明道”的思想。
对于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前贤亦有研究,但大多认为仅仅是针对清儒“训诂明道”观念而发。
钱穆指出:“经学家最大理论,莫若谓道在《六经》,通经所以明道,此自亭林唱‘经学即理学’之说以来,迄东原无变,实斋始对此持异议。
”[1]( P421)余英时也认为:“我们试以实斋之‘道’与当时考证家由分疏六经中之名物、制度、字义等所得之‘道’作一比较,即可见两者不但迥异,抑且适处于相反的地位。
……综观实斋‘六经皆史’之说,实为针对东原‘道在六经’的基本假定而发,同时也是对顾亭林以来所谓‘经学即理学’的中心理论作一种最有系统的反挑战。
”[2](P56-59)这种看法当然不错,但是如果我们全面考察章学诚“以史明道”观念,就会发现他不仅不完全赞同清代经学家标榜“训诂明道”的观念,而且也反对唐宋古文学家片面强调“文以载道”的观念,更反对宋明理学家枵腹侈谈“义理明道”的观念,其“以史明道”的内涵表现为根绝辞章、义理和考证三者纷争,避免三家各执一端而矜炫得“道”的弊端,具有独特的明“道”方法与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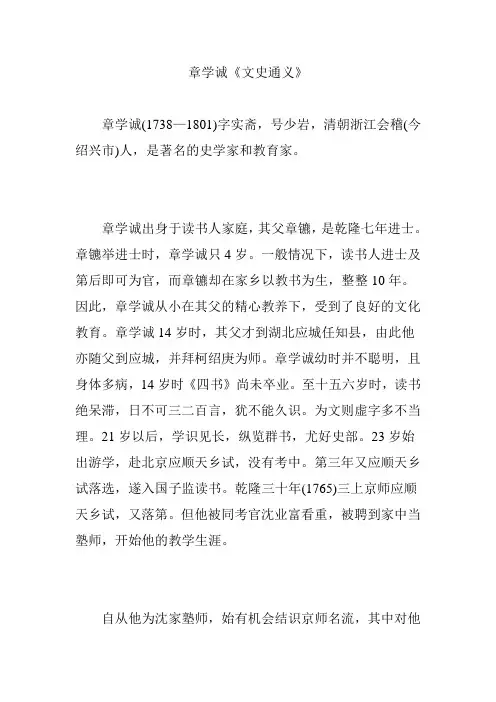
章学诚《文史通义》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清朝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
章学诚出身于读书人家庭,其父章镳,是乾隆七年进士。
章镳举进士时,章学诚只4岁。
一般情况下,读书人进士及第后即可为官,而章镳却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整整10年。
因此,章学诚从小在其父的精心教养下,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
章学诚14岁时,其父才到湖北应城任知县,由此他亦随父到应城,并拜柯绍庚为师。
章学诚幼时并不聪明,且身体多病,14岁时《四书》尚未卒业。
至十五六岁时,读书绝呆滞,日不可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
为文则虚字多不当理。
21岁以后,学识见长,纵览群书,尤好史部。
23岁始出游学,赴北京应顺天乡试,没有考中。
第三年又应顺天乡试落选,遂入国子监读书。
乾隆三十年(1765)三上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
但他被同考官沈业富看重,被聘到家中当塾师,开始他的教学生涯。
自从他为沈家塾师,始有机会结识京师名流,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翰林院编修朱筠。
章学诚拜朱筠为师,学习古文,并与邵晋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汪辉祖、黄景仁等学者交游。
乾隆三十三年,他又应顺天乡试落榜。
是年因其父卒,他必须分出精力来养家糊口。
34岁时,朱筠为安徽学政,章学诚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等人皆从之游。
是年他开始撰写《文史通义》。
章学诚39岁时任国子监典籍。
40岁时才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
然而,他以为与时俗不合,不愿做官,故此依然寄食官宦之家做塾师,一边教学,一边著述。
乾隆四十六年他离开户部尚书梁国治家到河南谋事。
事未谋成,却中途遇盗,行李及平生著作尽失。
由此生活无着,只得暂回直隶肥乡县主讲清漳书院。
后来又移家至永平县(今河北卢龙县)主讲敬胜书院,继续撰写《文史通义》。
自此以后,他或受聘编写县志,或主讲书院,以讲学著述为业。
他先后主讲于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后来经友人推荐入毕沅幕府。
时毕沅以湖广总督暂留任河南巡抚,对章学诚很器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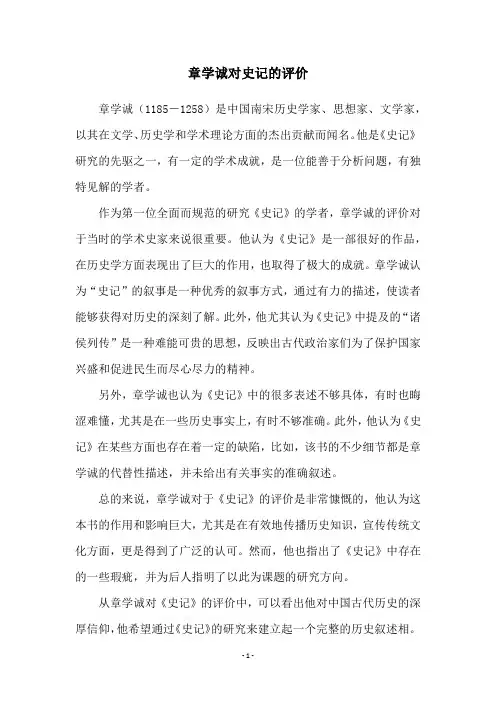
章学诚对史记的评价
章学诚(1185-1258)是中国南宋历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以其在文学、历史学和学术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而闻名。
他是《史记》研究的先驱之一,有一定的学术成就,是一位能善于分析问题,有独特见解的学者。
作为第一位全面而规范的研究《史记》的学者,章学诚的评价对于当时的学术史家来说很重要。
他认为《史记》是一部很好的作品,在历史学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作用,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章学诚认为“史记”的叙事是一种优秀的叙事方式,通过有力的描述,使读者能够获得对历史的深刻了解。
此外,他尤其认为《史记》中提及的“诸侯列传”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思想,反映出古代政治家们为了保护国家兴盛和促进民生而尽心尽力的精神。
另外,章学诚也认为《史记》中的很多表述不够具体,有时也晦涩难懂,尤其是在一些历史事实上,有时不够准确。
此外,他认为《史记》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比如,该书的不少细节都是章学诚的代替性描述,并未给出有关事实的准确叙述。
总的来说,章学诚对于《史记》的评价是非常慷慨的,他认为这本书的作用和影响巨大,尤其是在有效地传播历史知识,宣传传统文化方面,更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然而,他也指出了《史记》中存在的一些瑕疵,并为后人指明了以此为课题的研究方向。
从章学诚对《史记》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深厚信仰,他希望通过《史记》的研究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历史叙述相。
同时,他也着重强调了《史记》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和模糊之处,为学术界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建议,使我们对更多关于古代史家的认识和指导获得进一步的阐发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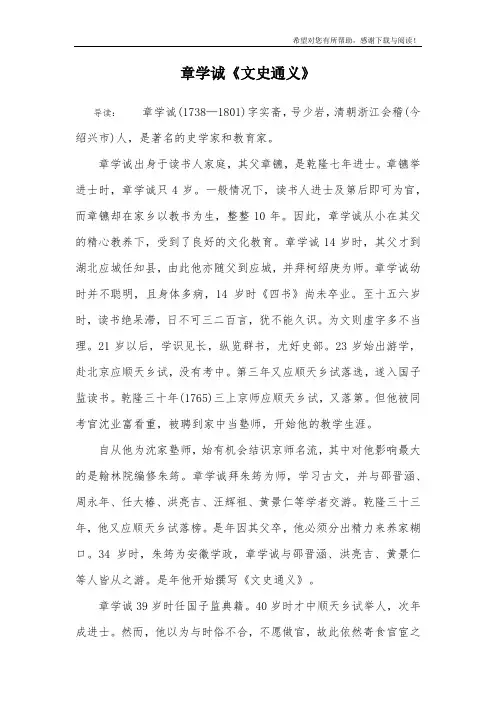
章学诚《文史通义》导读: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清朝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
章学诚出身于读书人家庭,其父章镳,是乾隆七年进士。
章镳举进士时,章学诚只4岁。
一般情况下,读书人进士及第后即可为官,而章镳却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整整10年。
因此,章学诚从小在其父的精心教养下,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
章学诚14岁时,其父才到湖北应城任知县,由此他亦随父到应城,并拜柯绍庚为师。
章学诚幼时并不聪明,且身体多病,14岁时《四书》尚未卒业。
至十五六岁时,读书绝呆滞,日不可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
为文则虚字多不当理。
21岁以后,学识见长,纵览群书,尤好史部。
23岁始出游学,赴北京应顺天乡试,没有考中。
第三年又应顺天乡试落选,遂入国子监读书。
乾隆三十年(1765)三上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
但他被同考官沈业富看重,被聘到家中当塾师,开始他的教学生涯。
自从他为沈家塾师,始有机会结识京师名流,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翰林院编修朱筠。
章学诚拜朱筠为师,学习古文,并与邵晋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汪辉祖、黄景仁等学者交游。
乾隆三十三年,他又应顺天乡试落榜。
是年因其父卒,他必须分出精力来养家糊口。
34岁时,朱筠为安徽学政,章学诚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等人皆从之游。
是年他开始撰写《文史通义》。
章学诚39岁时任国子监典籍。
40岁时才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
然而,他以为与时俗不合,不愿做官,故此依然寄食官宦之家做塾师,一边教学,一边著述。
乾隆四十六年他离开户部尚书梁国治家到河南谋事。
事未谋成,却中途遇盗,行李及平生著作尽失。
由此生活无着,只得暂回直隶肥乡县主讲清漳书院。
后来又移家至永平县(今河北卢龙县)主讲敬胜书院,继续撰写《文史通义》。
自此以后,他或受聘编写县志,或主讲书院,以讲学著述为业。
他先后主讲于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后来经友人推荐入毕沅幕府。
时毕沅以湖广总督暂留任河南巡抚,对章学诚很器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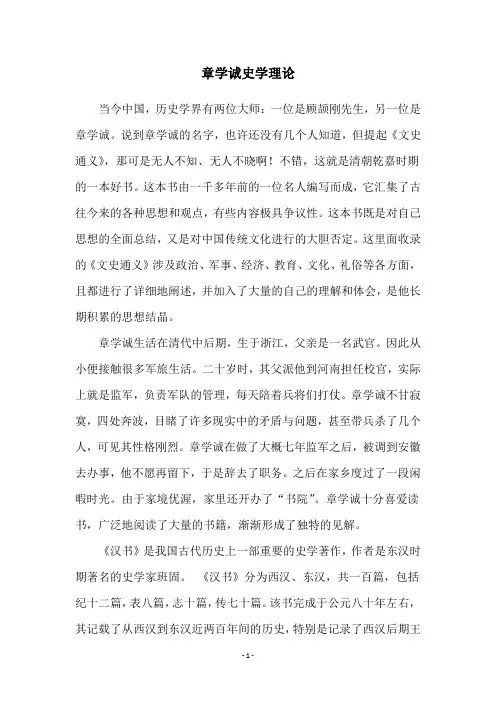
章学诚史学理论当今中国,历史学界有两位大师:一位是顾颉刚先生,另一位是章学诚。
说到章学诚的名字,也许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但提起《文史通义》,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不错,这就是清朝乾嘉时期的一本好书。
这本书由一千多年前的一位名人编写而成,它汇集了古往今来的各种思想和观点,有些内容极具争议性。
这本书既是对自己思想的全面总结,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大胆否定。
这里面收录的《文史通义》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礼俗等各方面,且都进行了详细地阐述,并加入了大量的自己的理解和体会,是他长期积累的思想结晶。
章学诚生活在清代中后期,生于浙江,父亲是一名武官。
因此从小便接触很多军旅生活。
二十岁时,其父派他到河南担任校官,实际上就是监军,负责军队的管理,每天陪着兵将们打仗。
章学诚不甘寂寞,四处奔波,目睹了许多现实中的矛盾与问题,甚至带兵杀了几个人,可见其性格刚烈。
章学诚在做了大概七年监军之后,被调到安徽去办事,他不愿再留下,于是辞去了职务。
之后在家乡度过了一段闲暇时光。
由于家境优渥,家里还开办了“书院”。
章学诚十分喜爱读书,广泛地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渐渐形成了独特的见解。
《汉书》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作者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班固。
《汉书》分为西汉、东汉,共一百篇,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
该书完成于公元八十年左右,其记载了从西汉到东汉近两百年间的历史,特别是记录了西汉后期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然而,《汉书》里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人物评价过于偏颇。
比如,汉元帝一心只想求神仙、服丹药,荒淫无度;比如汉宣帝,立意改变风俗,恢复井田制,却只使用权谋,不讲德政。
第二,对战争的描写不够详细。
例如刘秀消灭赤眉、绿林的战役,没有将战斗场面叙述得尽善尽美,也没有加上作战双方将领的言行,不够真实可信。
第三,汉代没有留下多少文字材料,《汉书》虽然记载了众多重大历史事件,但仍有大量内容无法考证,这也是《汉书》存在的最大缺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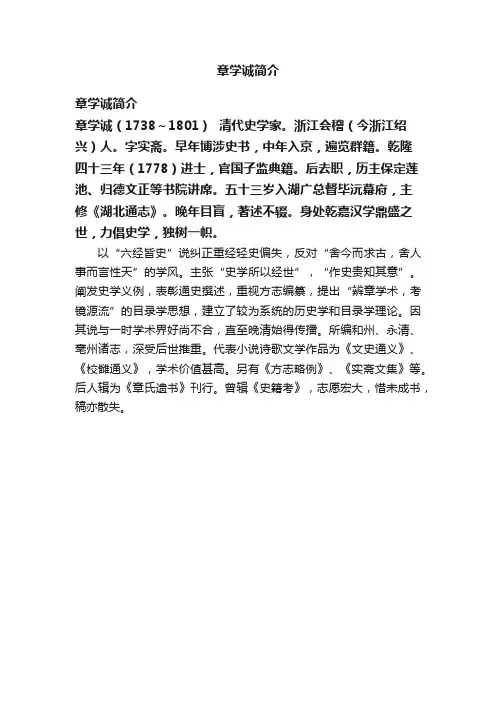
章学诚简介
章学诚简介
章学诚(1738~1801)清代史学家。
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字实斋。
早年博涉史书,中年入京,遍览群籍。
乾隆
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国子监典籍。
后去职,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席。
五十三岁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主
修《湖北通志》。
晚年目盲,著述不辍。
身处乾嘉汉学鼎盛之世,力倡史学,独树一帜。
以“六经皆史”说纠正重经轻史偏失,反对“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的学风。
主张“史学所以经世”,“作史贵知其意”。
阐发史学义例,表彰通史撰述,重视方志编纂,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历史学和目录学理论。
因其说与一时学术界好尚不合,直至晚清始得传播。
所编和州、永清、亳州诸志,深受后世推重。
代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为《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学术价值甚高。
另有《方志略例》、《实斋文集》等。
后人辑为《章氏遗书》刊行。
曾辑《史籍考》,志愿宏大,惜未成书,稿亦散失。
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基本内容【作文题目】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基本内容,被概括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创独到之说。
下面请看本站作文栏目为您带来的作文题目及要求。
要求:(一)明确:①写议论文,②不少于800字。
(二)范围:历史、社会等文化方面的论文,均可。
(三)内容:(1)记叙、描写、抒情结合,要对现实生活中人或事物有所感受,并能借助联想和想象写出来。
(2)如果是小说,就要有故事情节,情节曲折动人。
(3)如果是诗歌,就要表达出某种思想感情。
《史籍考》提出了“通古今之变”和“辨伪存真”的主张,其具体内容为:“一曰‘通古今之变’,则不可不明乎世运之所趋,而与古人之心以相印也;明乎世运之所趋,则足以知其人才之所以不得不出,学术之所以不得不因而变也。
知其人才之所以不得不出,学术之所以不得不因而变,则知所以因之以兴贤能而调士夫之不足以胜任者;知所以因之以兴贤能而调士夫之不足以胜任者,则知所以代之以刑政之不逮,而因其变而矫之于其所不及,而与之共理者;知所以代之以刑政之不逮,而因其变而矫之于其所不及,而与之共理者,则凡唐虞三代,吾人俱可以无愧色矣。
”(《章氏遗书·中说·总论》)。
《明史》的作者李贽提出的观点,后来被归纳为“别真伪,去伪饰,存其真,灭其伪”,即“破邪显正”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文史通义》提出了文学和史学的关系问题,它认为“六经、诸子之文,皆史之流也”。
“诸子之文虽或近史,然亦有文无质者,譬之乐章,纯以音律谐婉,不事节奏,其文畅而已矣。
”(《中说·内篇·自纪下》)这些观点都对后来产生很大影响。
此外,章学诚在历史研究中还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他在讲学、著述中常常强调考证和比较,这在今天仍然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历史实际是不能割断的,所以对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不能只凭个人好恶加以褒贬。
章学诚虽然重视比较、重视历史研究的方法,但同时也强调历史研究中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反对盲从。
刘知幾与章学诚史学思想之比——《史通》与《文史通义》读书札记刘知幾与章学诚同为中国古代的史学大家,他们的史学思想代表了当时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其代表作《史通》及《文史通义》则是两人思想精髓的体现,他们的史学思想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与繁荣。
章学诚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刘知幾的思想,因此两人的思想在史学批判理论、史家修养理论等方面存在诸多共通,但同时两人又在史识与史德、史法与史意及史书编纂等地方各有其独到的见解。
一、史学批判理论的共通之处在中国古代史学批判发展历程中,刘知幾奠定了古代史学批判的理论基础,而章学诚则完善了史学批判理论,使其更加理论化、系统化。
因此,他们的史学批判思想存在着共通之处,表现在:一、注重秉笔直书,讲求实事求是。
刘知幾在《直书》和《曲笔》篇中总结了历代史家两种截然相反的“直书”与“曲笔”操守,他本人倾向于撰述能够“秉笔直书”,反对“文过饰非”。
他强调史家写史要有“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实录”精神(《史通·直书》)。
在史书文风上,他强调贵在“质朴”,切不可“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史通·载言》),否则就会在写作时失实,导致以文害事。
章学诚继承和发扬了刘知幾这种“秉笔直书”的修史之法,并强调史学“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章学诚强调史家应“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文史通义·史德》),即在史书的书写中应尽量尊重客观史实而不要过分地掺杂个人的主观臆测成分。
二、强调史学的现实功能,即“经世致用”。
刘知幾在修史过程中一直坚持着“以史为鉴,以史辅政,以史教化”的立言宗旨。
他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史通·曲笔》),同时又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
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史通·直笔》),他坚信史书的记事载言,能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
简析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学术界对章氏“六经皆史” 说思想渊源的讨论, 颇为纷扰。
最有代表性的争议是钱钟书等博洽的溯源工作遭到了仓修良等尖锐的辩驳。
然而, 在笔者看来, 更为重要的是, 对章学诚来说, 他以什么样的方式获致这一观念, 从而能够或者接受或者批判或者改造某些资源来建构自己的学说。
所以本文特从章氏的为学取径入手来探讨“六经皆史” 说的缘起, 以避漫无归宿。
我们认为, “六经皆史” 说乃是章学诚奋力开拓出来的“文史校雠” 之学的成果, 此说之发轫尤其要从其成学过程去探寻。
乾隆二十九年(1764), 27 岁的章学诚已经有了明确的志向:“丈夫生不为史臣, 亦当从名公巨卿, 执笔充书记, 而因得论列当世, 以文章见用于时, 如纂修志乘, 亦其中之一事也。
”重“史” 重“文” , 重视“纂修志乘” , 注重经“世” 致“用” , 似乎很早就是他的志趣所在。
章学诚是一位格调古雅、自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好唱高调的学者,他所师法的古人, 决不仅限于刘向刘歆父子、刘勰、刘知几, 而必欲由“刘知几、曾巩、郑樵其人” 上攀迁、固、向、歆而追本孔夫子。
所谓“ 《春秋》经世之学” 也就是将上文提到的“校雠之学” 进一步明确其旨趣, “ 著作之能” 与“条理之别” , 虽各有侧重, 实相济为功, 而义之所归就在于“校雠师法,不可不传;而著录专家, 不可不立也。
” 这也就是日后学诚自称所“从事” 的“ 文史校雠” 之学。
至此, 章学诚非常清楚要开拓什么样的学问了, 其学术的基本精神也已经确立, 如影随形, 他关于六经的见解也进入了新境地。
章学诚在给钱大昕的信中说:“盖向、歆所为《七略》、《别录》者, 其叙六艺百家, 悉惟本于古人官守, 不尽为艺林述文墨也。
” 可见在草创之处, 他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新解与向、歆父子的原有看法混在一起了, 因为从《汉书·艺文志》来看, 他们是将“九流” (即此函所谓“百家”) “本于古人官守” , 即有所谓“诸子出于王官说” 或称为“九流出于王官说” , 并没有将“六艺” “悉惟本于古人官守” 。
作家杂志Writer Magazine 2012No.4章学诚是清朝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当时的学术界以考据为主流,章学诚却走了一条读书通大意的路子。
关于章学诚的学术渊源,学者对其“六经皆史”论有诸多的探索,而对于其整体学术的源自却鲜少提及。
为什么在乾嘉时代会产生章学诚这么一位与众不同的学者呢?本文试从章学诚整体学术渊源的角度,采用文献整理和分析综合的方法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清代学术背景从学术领域的角度来看,经学是清学的主流,史学则处于非主流的地位。
事实上,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经史并重,清政府又开《明史》馆,招募天下英才,因此,经学与史学的地位是一样的。
但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稳固,明史的修成,经学与小学的地位开始突出,“学风一变而矜尚四书五艺了”。
至乾隆、嘉庆年间,经学达到鼎盛,“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中坚,两百数十年间,最能体现此一中坚地位者,莫过于活跃在乾隆、嘉庆间学术舞台上的乾嘉学派”。
乾嘉时期是经学极盛的时代,与史学相比,“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以至于研究经学的人也要比研究史学的人高出一个档次。
赵翼自序《廿二史札记》云:“闲居无事,翻书度日,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流览,爰取为日课。
”赵氏身为史学大家,已自行低视史学,可见当时经学地位之崇高,史学地位之卑下。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清初是考据与义理并重,所谓汉宋兼采。
到了阎若璩和胡渭辨伪的时候,汉学才开始占上风。
阎氏撰《古文尚书疏证》,胡氏撰《易图明辨》,这些都使得宋儒借以发挥义理的理论依据遭到破坏,宋学的根基被动摇。
至乾隆、嘉庆二朝,“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汉学达到鼎盛。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是汉学占上风的时代,学风所及,不独限于经学,整个学术界几乎均为考据学风所笼罩。
“考据”是乾嘉时期盛行的一种治学方法,其方法源于治经,也以经学为核心,但却没有局限于经学。
考证这种方法相比于经学这个领域,在当时更具有普遍性,以至于刘师培认为,用“考证学”比用“经学”更能够概括当时的学风。
章学诚《文史通义》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清朝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
章学诚出身于读书人家庭,其父章镳,是乾隆七年进士。
章镳举进士时,章学诚只4 岁。
一般情况下,读书人进士及第后即可为官,而章镳却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整整10 年。
因此,章学诚从小在其父的精心教养下,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
章学诚14 岁时,其父才到湖北应城任知县,由此他亦随父到应城,并拜柯绍庚为师。
章学诚幼时并不聪明,且身体多病,14 岁时《四书》尚未卒业。
至十五六岁时,读书绝呆滞,日不可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
为文则虚字多不当理。
21 岁以后,学识见长,纵览群书,尤好史部。
23 岁始出游学,赴北京应顺天乡试,没有考中。
第三年又应顺天乡试落选,遂入国子监读书。
乾隆三十年(1765) 三上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
但他被同考官沈业富看重,被聘到家中当塾师,开始他的教学生涯。
自从他为沈家塾师,始有机会结识京师名流,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翰林院编修朱筠。
章学诚拜朱筠为师,学习古文,并与邵晋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汪辉祖、黄景仁等学者交游。
乾隆三十三年,他又应顺天乡试落榜。
是年因其父卒,他必须分出精力来养家糊口。
34 岁时,朱筠为安徽学政,章学诚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等人皆从之游。
是年他开始撰写《文史通义》。
章学诚39 岁时任国子监典籍。
40 岁时才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
然而,他以为与时俗不合,不愿做官,故此依然寄食官宦之家做塾师,一边教学,一边著述。
乾隆四十六年他离开户部尚书梁国治家到河南谋事。
事未谋成,却中途遇盗,行李及平生著作尽失。
由此生活无着,只得暂回直隶肥乡县主讲清漳书院。
后来又移家至永平县(今河北卢龙县)主讲敬胜书院,继续撰写《文史通义》。
自此以后,他或受聘编写县志,或主讲书院,以讲学著述为业。
他先后主讲于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后来经友人推荐入毕沅幕府。
时毕沅以湖广总督暂留任河南巡抚,对章学诚很器重。
章学诚史学的特点章学诚,字实齐,浙江会稽人,生于清乾隆三年(公元一七三八年),卒于嘉庆六年(公元一八○一年)。
他生在专门汉学、不谈义理的时代,他的学问不合时好,以致他的言行,在死后一直被埋没多年。
但也正是他,在那样的时代,发出了一种对汉学的抗议,部分地继承了十七世纪大儒的传统。
所谓“部分地”,是说他的成就是在文化史学方面,他还不能全面地深刻地光大清初大儒的近代意识。
他自己说:余仅能议文史耳,非知道者也。
然议文史,而自拒文史于道外,则文史亦不成其为文史矣。
因推原道术,为书得十三篇,以为文史缘起,亦见儒之流于文史,儒者自误以谓有道在文史外耳。
(“章氏遗书”卷二十九“外集”二“姑孰夏课甲编小引”)学诚所说的文史不外于道,其语气虽然谨慎,但他的这种文化哲学或文化史学的理论,便足以成为当时对汉学最出色的抗议,诚如他所说的“所撰著,归正朱先生(筠)外,朋辈征逐,不特甘苦无可告语,且未有不视为怪物,诧为异类者”(同上卷二十二“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他在专门汉学的空气中,是遭受着异端之嫌疑的。
但他自信不疑,卓然有见。
所以他又说:学者祈向,贵有专属,博群反约,原非截然分界……。
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远。
……十年闭关,出门合辙,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正须不羡轻隽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毁誉,循循勉勉,即数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为者而为之,乃有一旦庶儿之日,斯则可为知者道,未易一一为时辈言耳。
(“章氏遗书”卷二十二“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学诚的“文史通义”,是他的代表作。
他在“与汪龙庄书”中说: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
姑择其近情而可听者,稍刊一二,以为就正同志之质,亦尚不欲遍示于人也。
(同上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他自三十五岁起开始写“文史通义”,至“稍刊一二”之年,中经二十四年的光景。
因恐“惊世骇俗”,他只是“择其近情而可听者”刻印出求,当不能尽所欲言。
而他的另一重要著作“校雠通义”不只不能全刻出来,而且原稿也被盗了。
被盗的原因大可寻味。
因为他这时正得罪了一个权贵,出走河南,很可能是为了他好为议论,招人诟厉,以致有人故意来同他这样捣乱的。
学诚言论风度的不投时好,见于李威“从游记”。
他记朱筠事说:及门章学诚议论如涌泉,先生(指朱筠)乐与之语。
学诚姗笑无弟子礼,见者愕然,先生反为之破颜,不以为异。
使“见者愕然”的他的言论风度,是不合于乾嘉时代的世俗好恶的。
学诚自己给钱大昕的信也说: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辩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
……世俗风尚必有所偏。
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
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
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
……韩退之“报张司业书”谓“释老之学,王公贵人方且祟奉,吾岂敢昌言排之?”乃知“原道”诸篇当日未尝昭揭众目。
太史公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不知者以为珍重秘惜,今而知其有戒心也。
……今世较唐时为尤难矣。
……若夫天壤之大,岂绝知音,针芥之投,宁无暗合?则固探怀而出,何所秘焉?(同上卷二十九外集二“上钱辛楣宫詹书”)他在这封信里,把那种畏戒时趋的情境毕现出来。
他所谓“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可以说就是对于当代“专门汉学”的抗议。
这时汉学的主持者正是康熙以来的文化政策执行者,奔赴者则是他所谓的利禄文士,这何尝还有清初学者活生生的气象容乎其间?这种风气,他在“文史通义”中更慨乎言之。
我们仔细研究,几乎“文史通义”每篇都有反对当时“专门汉学”的议论。
“原学”下篇曾举其要旨说: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
……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
……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
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
是故开者虽不免于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气之迎,敝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之托,此亦自然之势也。
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同上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下)这种史论虽然是一种循环论,但显明地是对于汉学风气而发的,因为他开头即云“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
清初学者并没有把义理、文辞和学问分家。
即以博雅如顾炎武,也不过以考证为手段,而他所重视的是经世致用。
炎武所谓“理学即经学”的主旨,是有所谓“当世之务”的前提的,这和乾嘉学者的经学来比较,的确是两个东西,不容混同。
以经学挽救理学的空谈是一会事,而以经学只限于训诂名物又是一会事,手段并不就是目的。
学诚把手段叫做“功力”。
他说:王伯厚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
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惧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
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
(“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博约”中)学诚在“文史通义”“假年”篇,更明白攻击着汉学空气。
他首先设喻说“学问之于身心,犹饥寒之于衣食也,不以饱暖慊其终身,而欲假年以穷天下之衣食,非愚则罔也。
”最后他竟以“妖孽”二字痛斥汉学了。
(注意:他之痛斥汉学,并不基于扶宋学,同时他也接受反宋学的传统,所谓“取其所以精”,因此,他是在正途上,而与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在歧路上是相反的。
)他说:今不知为己,而骛博以炫人,天下闻见不可尽,而人之好尚不可同。
以有尽之生,而逐无穷之闻见,以一人之身,而逐无端之好尚,尧舜有所不能也。
孟子曰:“尧舜之智,而不遍物”,……今以凡猥之资,而欲穷尧舜之所不遍,且欲假天年于五百焉,幸而不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
(同上卷六“文史通义”内篇六“假年”)他更有两段明白的议论,因忌戒为怀,都编于“外篇”。
他说:或曰,联文而后成辞,属辞而后著义,六书不明,五经不可得而诵也。
然则数千年来,诸儒尚无定论,数千年人不得诵五经乎?故生当古学失传之后,六书七音,天性自有所长,则当以专门为业,否则粗通大义而不凿,转可不甚谬乎古人,而五经显指,未尝遂云霾而日食也。
(同上卷八“文史通义”外篇二“说文字原课本书后”)就经传而作训故,虽伏郑大儒不能无强求失实之弊。
……离经传而说大义,虽诸子百家未尝无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机无意而自呈也。
(同上卷十三“校雠通义”外篇“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第一段话,是对于“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之说而发的。
第二段话,更说到在六经之外去求道,也未尝不可。
学诚把汉学最基本的知识——音韵学,作为少数专家之业看待,而认为离经的诸子并不是叛道的,指出他们也有“精微神妙”的见解。
这样近代文化史学家的大胆言论,是继承清初学者的优良的传统精神的。
学诚以“立言之士,以意为宗”,在“文史通义”“辨似”篇针对了文章家、考据家有以下的批判:学问之始,未能记诵。
博涉既深,将超记诵。
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
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至其地,则舍舟车矣。
一步不行者,则亦不用舟车矣。
不用舟车之人,乃托舍舟车者为同调焉,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程子见谢上蔡多识经传,便谓玩物丧志,毕竟与孔门一贯不似)。
(同上卷三“文史通义”内篇三)这段话有两方面的批评,一方面批评汉学永远在资舟车的旅途中,不知有其目的地,更不知知识“自在性”与“自为性”的发展,即是所谓“博涉既深,将超记诵”。
另一面批评宋学永远站在此岸而遥视彼岸,不用舟车的工具而想冥造出目的地的景象。
王夫之的知识论在这一点上有丰富的内容。
学诚虽未引证过夫之的话,但含有夫之时代的遗绪。
然而学诚的文史之学毕竟在当时的汉学封锁中不能成为显学,而且到了晚年他也只得变通一些自己的主张,和汉学妥协,故修志一事便成了他的主要工作(虽然他争修志的义例),在修志的樊篱里埋没了他的天才的发展。
他虽竭力辨解真学伪学,但也不能不说,“君子假兆以行学,而遇与不遇听乎天”了(“章氏遗书”卷六“文史通义”内篇六“感遇”)。
他更进一步说明其中的原因:圣贤岂必远于人情哉?君子固穷,枉尺直寻,羞同诡御,非争礼节,盖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
……后之学术曲而难。
学术虽当,犹未能用,必有用其学术之学术,而其中又有工拙焉。
身世之遭遇,未责其当否,先责其工拙。
学术当而趋避不工,见摈于当时;工于遇而执持不当,见讥于后世。
沟壑之患逼于前,而工拙之效驱于后。
呜呼,士之修明学术,欲求寡过,而能全其所自得,岂不难哉!且显晦,时也;穷通,命也。
才之生于天者有所独,而学之成于人者有所优,一时缓急之用,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相合者,亦势也。
(同上)皮锡瑞引“四库提要”对于二千年经学得失的评语,解释说:“琐者,国朝汉学也。
‘提要’之作,当惠、戴讲汉学专宗许、郑之时,其繁称博引,间有如汉人三万言说‘粤若稽古’者。
”(“经学历史”)由理学的烦琐到考证的烦琐,其烦琐的对象不同,而拘束个性的独立发展,则殊无二致。
学诚就在这个时候出来挽持风气,主张“以意为宗”“全其所自得”。
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二书,即自命是颇“乖时人好恶”的(见前引)。
我们仔细研究以上二书的内容,“文史通义”略当今日的文化史,“校雠通义”则当今日的学术史。
他说:人不幸而为古人,不能阅后世之穷变通久,而有未见之事与理;又不能一言一动,处处自作注解,以使后人之不疑;又不能留其口舌,以待后生掎摭之时,出而与之质辨。
惟有升天入地,一听后起之魏伯起尔!然百年之后,吾辈亦古人也,设身处地,又当何如?……鄙人所业文史校雠: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皆不能不驳正古人。
……古人差谬,我辈既已明知,岂容为讳?但期于明道,非争胜气也。
(同上卷七“文史通义”外篇一“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古人有未见之事理”这句话,在当时经学支配的世界是有力的抗议。
故在他看来,宗许宗郑,都是一种自我的束缚;因为对于古人的差谬,今人是可以批评的。
他对于戴震的“郑学齐记”有一篇“书后”,其中说:戴君说经,不尽主郑氏说,而其与任幼植书,则戒以轻畔康成。
人皆疑之,不知其皆是也。
大约学者于古未能深究其所以然,必当墨守师说。
及其学之既成,会通于群经与诸儒治经之言,而有以灼见前人之说之不可以据,于是始得古人大体,而进窥天地之纯。
故学于郑,而不敢尽由于郑,乃谨严之至,好古之至,非蔑古也。
乃世之学者,喜言墨守。
……墨守而愚,犹可言也;墨守而黠,不可言矣。
愚者循名记数,不敢稍失,犹可谅其愚也;黠者不复需学,但袭成说,以谓吾有所受者也。
盖折衷诸儒,郑所得者十常七八。
黠者既名郑学,即不劳施为,常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也。
夫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不如自求“心得”者之什一二矣,而犹自矜其七八,故曰德之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