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小说两篇
- 格式:ppt
- 大小:753.50 KB
- 文档页数: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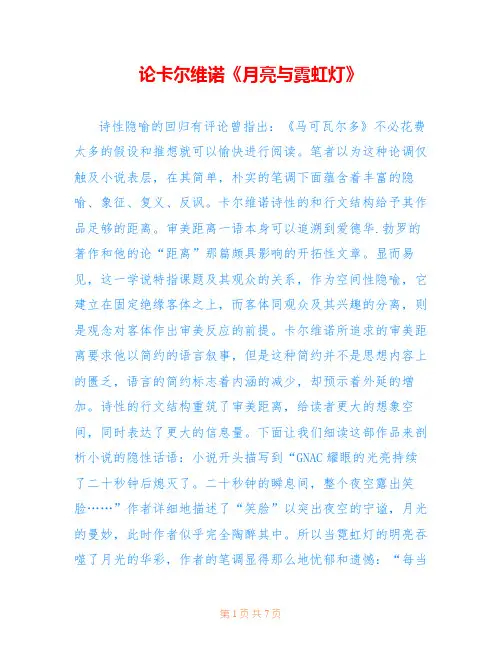
论卡尔维诺《月亮与霓虹灯》诗性隐喻的回归有评论曾指出:《马可瓦尔多》不必花费太多的假设和推想就可以愉快进行阅读。
笔者以为这种论调仅触及小说表层,在其简单,朴实的笔调下面蕴含着丰富的隐喻、象征、复义、反讽。
卡尔维诺诗性的和行文结构给予其作品足够的距离。
审美距离一语本身可以追溯到爱德华.勃罗的著作和他的论“距离”那篇颇具影响的开拓性文章。
显而易见,这一学说特指课题及其观众的关系,作为空间性隐喻,它建立在固定绝缘客体之上,而客体同观众及其兴趣的分离,则是观念对客体作出审美反应的前提。
卡尔维诺所追求的审美距离要求他以简约的语言叙事,但是这种简约并不是思想内容上的匮乏,语言的简约标志着内涵的减少,却预示着外延的增加。
诗性的行文结构重筑了审美距离,给读者更大的想象空间,同时表达了更大的信息量。
下面让我们细读这部作品来剖析小说的隐性话语:小说开头描写到“GNAC耀眼的光亮持续了二十秒钟后熄灭了。
二十秒钟的瞬息间,整个夜空露出笑脸……”作者详细地描述了“笑脸”以突出夜空的宁谧,月光的曼妙,此时作者似乎完全陶醉其中。
所以当霓虹灯的明亮吞噬了月光的华彩,作者的笔调显得那么地忧郁和遗憾:“每当它亮的时候,夜空变得平平坦坦、漆黑一片,月亮蓦然惨淡无光,星星失去了光彩。
”耀眼闪亮的霓虹灯与静谧和谐的夜空构成了两个对立的意象。
前者无疑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后者则是自然界的原始性征。
霓虹灯射出的强烈磷光使猫惊恐地逃逸表现了现代文明对自然的入侵,暗示着自然界的生物在现代文明的侵袭下无处藏身。
接下来,马可瓦尔多一家登场了。
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马可瓦尔多们并不富裕,仅仅“住在霓虹灯对面一幢楼的阁楼里”。
率先出场的是18岁的大女儿伊索丽娜,GANC的闪亮使她“情不自禁地寻味着舞厅里快乐的舞、五彩缤纷的灯光”,她是一个醉心于现代娱乐的女郎。
月光被吞噬并没有让她觉得有什么遗憾,令她兴奋得反而是霓虹灯的闪耀。
伊索丽娜的形象代表着被现代工业俘虏的一批人,他们醉心于工业社会的五光十色、缤纷艳丽,他们被工业文明的衣香鬓影深深吸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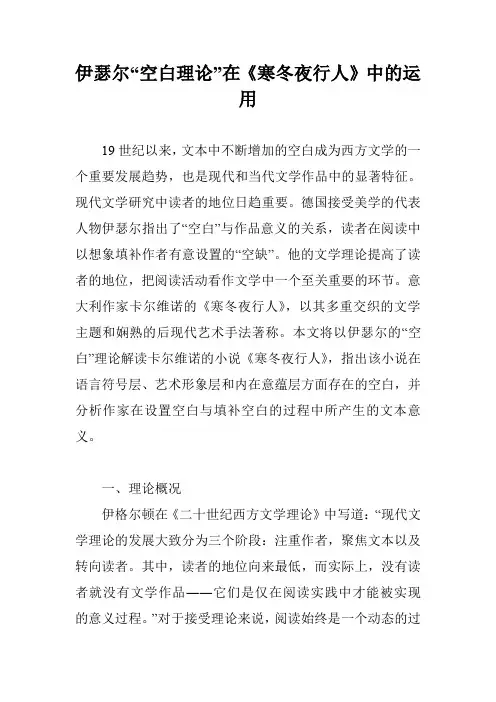
伊瑟尔“空白理论”在《寒冬夜行人》中的运用19世纪以来,文本中不断增加的空白成为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也是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显著特征。
现代文学研究中读者的地位日趋重要。
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伊瑟尔指出了“空白”与作品意义的关系,读者在阅读中以想象填补作者有意设置的“空缺”。
他的文学理论提高了读者的地位,把阅读活动看作文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以其多重交织的文学主题和娴熟的后现代艺术手法著称。
本文将以伊瑟尔的“空白”理论解读卡尔维诺的小说《寒冬夜行人》,指出该小说在语言符号层、艺术形象层和内在意蕴层方面存在的空白,并分析作家在设置空白与填补空白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文本意义。
一、理论概况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写道:“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注重作者,聚焦文本以及转向读者。
其中,读者的地位向来最低,而实际上,没有读者就没有文学作品――它们是仅在阅读实践中才能被实现的意义过程。
”对于接受理论来说,阅读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有读者才能将文学作品从一般存在物中解脱出来。
阅读不是一往直前的线性运动,而是反复回荡、前后修正的动态运动。
在西方,最先在文学的接受理论中提出“空白”一词的是德国接受美学的创始人之一沃尔夫冈・伊瑟尔,他在代表作《文本的召唤结构》一文中明确使用了“空白”一词,指出它是文本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机制,并深入研究了空白与作品意义的关系。
在《阅读活动》中,他更详细地阐释了关于空白的接受理论观点。
在他看来,文学研究应当充分重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文学文本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图示化”的框架,这个框架在各个层面上都有许多空白,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去填补与充实。
正是这些空白,把读者”牵涉到事件中,以提供未言部分的意义。
”所谓“空白”,就是指文本中未实写出来的或未明确写出来的部分,它们是文本中已实写出的部分向读者所暗示或提示的东西,需要读者根据自己的想象加以填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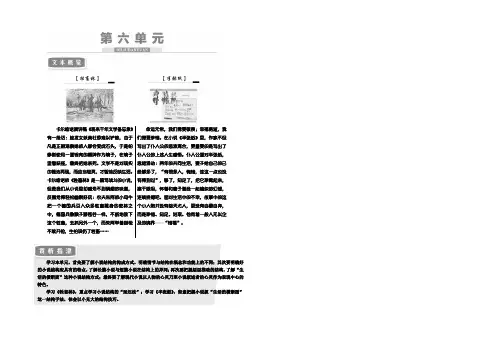
卡尔维诺演讲稿《将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有一段话:蛇发女妖美杜莎难以铲除,由于凡是正眼观察她的人都会变成石头,于是帕修斯使用一面锃亮的盾牌作为镜子,在镜子里看妖怪,最终把她杀死。
文学不是对现实的简洁再现,而应当轻灵、才智地反映生活。
卡尔维诺的《牲畜林》是一篇写战斗的小说,但是我们从小说里却感觉不到硝烟的味道,反倒觉得轻松幽默好玩:农夫朱阿的小母牛把一个德国兵引入众多牲畜藏身的密林之中,德国兵像猴子掰苞谷一样,不断地放下这个牲畜,去抓另外一个,而朱阿举着猎枪不敢开枪,生怕误伤了牲畜……命运无常,我们需要敬畏;幸福易逝,我们需要珍惜。
在小说《半张纸》里,作家不但写出了仆人公的悲欢离合,更重要的是写出了仆人公的上述人生感悟。
仆人公面对半张纸,思绪涌动:两年的共同生活,妻子给自己的已经够多了,“有很多人,惋惜,连这一点也没有得到过”,够了,知足了,把它珍藏起来,擦干眼泪,怀着和妻子曾经一起编织的幻想,连续拼搏吧。
面对生活中的不幸,故事中的这个小人物并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自暴自弃,而是珍惜、知足、进取。
他有着一般人无以企及的境界——“惜福”。
学习本单元,首先要了解小说结构的构成方式,明确情节与结构在概念和功能上的不同;其次要明确好的小说结构应具有的特点,了解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在结构上的异同;再次要把握层层推动的结构,了解“生活的横断面”这种小说结构方式;最终要了解现代小说以人物的心灵乃至小说叙述者的心灵作为表现中心的特色。
学习《牲畜林》,重点学习小说结构的“延迟法”;学习《半张纸》,留意把握小说抓“生活的横断面”这一结构手法,体会以小见大的结构技巧。
第11课牲畜林对应同学用书P53一、读准字音 (一)单音字1.稠.密(ch óu ) 2.膘.肥(bi āo ) 3.毡.帽(zh ān ) 4.马厩.(ji ù) 5.蹩.脚(bi é) 6.蹑.手蹑脚(ni è) 7.大方..(mi ǎn ti ǎn ) (二)多音字1.栖⎩⎪⎨⎪⎧栖.息(q ī)栖.栖(x ī)2.圈⎩⎪⎨⎪⎧ 圈.养(ju àn )圆圈.(qu ān )3.漂⎩⎪⎨⎪⎧ 秀丽..(pi ào )漂.泊(pi āo ) 4.挣⎩⎪⎨⎪⎧摆脱..(zh èn ɡ)挣.扎(zh ēn ɡ) 5.扛⎩⎪⎨⎪⎧扛.东西(k áng )力能扛.鼎(g āng )6.屏⎩⎪⎨⎪⎧开屏.(p ín ɡ)屏.气(b ǐn ɡ)7.剥⎩⎪⎨⎪⎧剥.夺(b ō)剥.皮(b āo )二、写准字形1.⎩⎪⎨⎪⎧ch óu (稠)密ch óu (惆)怅 2.⎩⎪⎨⎪⎧板l ì(栗)罂s ù(粟) 3.⎩⎪⎨⎪⎧xi ù(嗅)觉xi ù(溴)元素 4.⎩⎪⎨⎪⎧chu ò(绰)号泥n ào (淖) 5.⎩⎪⎨⎪⎧s ī(厮)杀s ī(撕)裂s ī(嘶)叫6.⎩⎪⎨⎪⎧mi ǎn (腼)腆沉mi ǎn (湎)mi ǎn (缅)怀三、用准词语 1.生疏 熟习例 句 和你哥哥生疏的那位医生熟习眼科手术,你就放心治疗吧。

《树上的男爵》是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创作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柯希莫成长在一个传统的贵族家庭里,父母对他寄予厚望,但他却有着自己的想法,在 12 岁时为了逃离父亲的权威和专制,爬上了树并在树上生活了一生的故事。
在树上的柯希莫与自然界的动物们为邻,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经历了许多奇妙的冒险和挑战,也见证了家族和社会的变迁。
他在树上探索着自我和生命的意义,成为了一个独特而又自由的个体。
这部小说通过柯希莫在树上的生活,探讨了个体与社会、自由与责任、人与自然等主题,是一部充满哲理和诗意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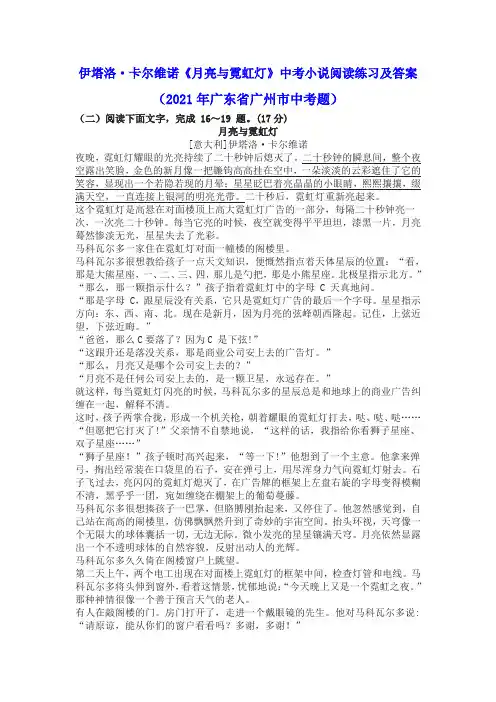
伊塔洛·卡尔维诺《月亮与霓虹灯》中考小说阅读练习及答案(2021年广东省广州市中考题)(二)阅读下面文字,完成 16~19 题。
(17分)月亮与霓虹灯[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夜晚,霓虹灯耀眼的光亮持续了二十秒钟后熄灭了。
二十秒钟的瞬息间,整个夜空露出笑脸,金色的新月像一把镰钩高高挂在空中,一朵淡淡的云彩遮住了它的笑容,显现出一个若隐若现的月晕;星星眨巴着亮晶晶的小眼睛,熙熙攘攘,缀满天空,一直连接上银河的明亮光带。
二十秒后,霓虹灯重新亮起来。
这个霓虹灯是高悬在对面楼顶上高大霓虹灯广告的一部分,每隔二十秒钟亮一次,一次亮二十秒钟。
每当它亮的时候,夜空就变得平平坦坦,漆黑一片,月亮蓦然惨淡无光,星星失去了光彩。
马科瓦尔多一家住在霓虹灯对面一幢楼的阁楼里。
马科瓦尔多很想教给孩子一点天文知识,便慨然指点着天体星辰的位置:“看,那是大熊星座,一、二、三、四,那儿是勺把,那是小熊星座。
北极星指示北方。
”“那么,那一颗指示什么?”孩子指着霓虹灯中的字母 C 天真地问。
“那是字母 C,跟星辰没有关系,它只是霓虹灯广告的最后一个字母。
星星指示方向:东、西、南、北。
现在是新月,因为月亮的弦峰朝西隆起。
记住,上弦近望,下弦近晦。
”“爸爸,那么C要落了?因为C 是下弦!”“这跟升还是落没关系,那是商业公司安上去的广告灯。
”“那么,月亮又是哪个公司安上去的?”“月亮不是任何公司安上去的,是一颗卫星,永远存在。
”就这样,每当霓虹灯闪亮的时候,马科瓦尔多的星辰总是和地球上的商业广告纠缠在一起,解释不清。
这时,孩子两掌合拢,形成一个机关枪,朝着耀眼的霓虹灯打去,哒、哒、哒……“但愿把它打灭了!”父亲情不自禁地说,“这样的话,我指给你看狮子星座、双子星座……”“狮子星座!”孩子顿时高兴起来,“等一下!”他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拿来弹弓,掏出经常装在口袋里的石子,安在弹弓上,用尽浑身力气向霓虹灯射去。
石子飞过去,亮闪闪的霓虹灯熄灭了,在广告牌的框架上左盘右旋的字母变得模糊不清,黑乎乎一团,宛如缠绕在棚架上的葡萄蔓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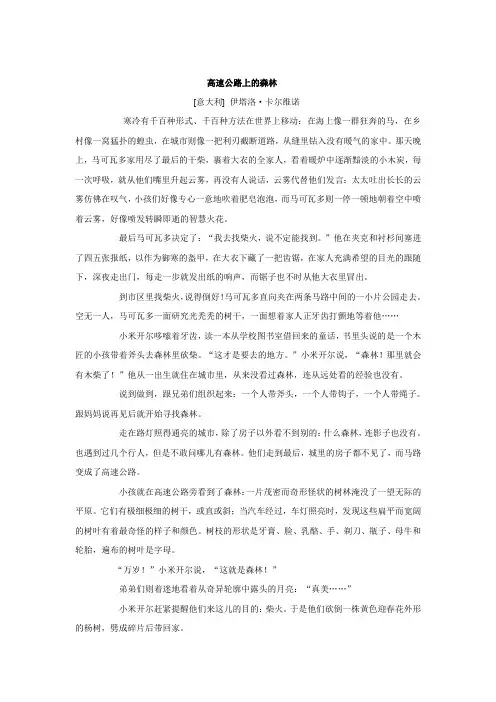
高速公路上的森林[意大利] 伊塔洛·卡尔维诺寒冷有千百种形式、千百种方法在世界上移动:在海上像一群狂奔的马,在乡村像一窝猛扑的蝗虫,在城市则像一把利刃截断道路,从缝里钻入没有暖气的家中。
那天晚上,马可瓦多家用尽了最后的干柴,裹着大衣的全家人,看着暖炉中逐渐黯淡的小木炭,每一次呼吸,就从他们嘴里升起云雾,再没有人说话,云雾代替他们发言:太太吐出长长的云雾仿佛在叹气,小孩们好像专心一意地吹着肥皂泡泡,而马可瓦多则一停一顿地朝着空中喷着云雾,好像喷发转瞬即逝的智慧火花。
最后马可瓦多决定了:“我去找柴火,说不定能找到。
”他在夹克和衬杉间塞进了四五张报纸,以作为御寒的盔甲,在大衣下藏了一把齿锯,在家人充满希望的目光的跟随下,深夜走出门,每走一步就发出纸的响声,而锯子也不时从他大衣里冒出。
到市区里找柴火,说得倒好!马可瓦多直向夹在两条马路中间的一小片公园走去。
空无一人,马可瓦多一面研究光秃秃的树干,一面想着家人正牙齿打颤地等着他……小米开尔哆嗦着牙齿,读一本从学校图书室借回来的童话,书里头说的是一个木匠的小孩带着斧头去森林里砍柴。
“这才是要去的地方。
”小米开尔说,“森林!那里就会有木柴了!”他从一出生就住在城市里,从来没看过森林,连从远处看的经验也没有。
说到做到,跟兄弟们组织起来:一个人带斧头,一个人带钩子,一个人带绳子。
跟妈妈说再见后就开始寻找森林。
走在路灯照得通亮的城市,除了房子以外看不到别的:什么森林,连影子也没有。
也遇到过几个行人,但是不敢问哪儿有森林。
他们走到最后,城里的房子都不见了,而马路变成了高速公路。
小孩就在高速公路旁看到了森林:一片茂密而奇形怪状的树林淹没了一望无际的平原。
它们有极细极细的树干,或直或斜;当汽车经过,车灯照亮时,发现这些扁平而宽阔的树叶有着最奇怪的样子和颜色。
树枝的形状是牙膏、脸、乳酪、手、剃刀、瓶子、母牛和轮胎,遍布的树叶是字母。
“万岁!”小米开尔说,“这就是森林!”弟弟们则着迷地看着从奇异轮廓中露头的月亮:“真美……”小米开尔赶紧提醒他们来这儿的目的:柴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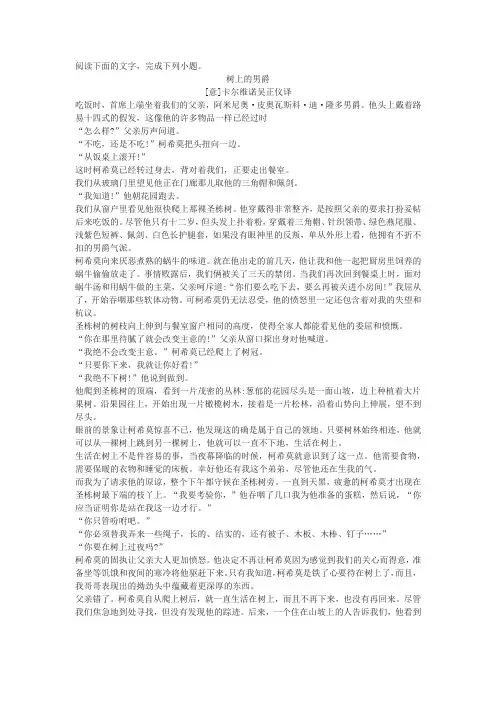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树上的男爵[意]卡尔维诺吴正仪译吃饭时,首席上端坐着我们的父亲,阿米尼奥·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男爵。
他头上戴着路易十四式的假发,这像他的许多物品一样已经过时“怎么样?”父亲厉声问道。
“不吃,还是不吃!”柯希莫把头扭向一边。
“从饭桌上滚开!”这时柯希莫已经转过身去,背对着我们,正要走出餐室。
我们从玻璃门里望见他正在门廊那儿取他的三角帽和佩剑。
“我知道!”他朝花园跑去。
我们从窗户里看见他很快爬上那裸圣栋树。
他穿戴得非常整齐,是按照父亲的要求打扮妥帖后来吃饭的。
尽管他只有十二岁,但头发上扑着粉,穿戴着三角帽、针织领带、绿色燕尾服、浅紫色短裤、佩剑、白色长护腿套,如果没有眼神里的反叛,单从外形上看,他拥有不折不扣的男爵气派。
柯希莫向来厌恶煮熟的蜗牛的味道。
就在他出走的前几天,他让我和他一起把厨房里饲养的蜗牛偷偷放走了。
事情败露后,我们俩被关了三天的禁闭。
当我们再次回到餐桌上时,面对蜗牛汤和用蜗牛做的主菜,父亲呵斥道:“你们要么吃下去,要么再被关进小房间!”我屈从了,开始吞咽那些软体动物。
可柯希莫仍无法忍受,他的愤怒里一定还包含着对我的失望和杭议。
圣栋树的树枝向上伸到与餐室窗户相同的高度,使得全家人都能看见他的委屈和愤慨。
“你在那里待腻了就会改变主意的!”父亲从窗口探出身对他喊道。
“我绝不会改变主意。
”柯希莫已经爬上了树冠。
“只要你下来,我就让你好看!”“我绝不下树!”他说到做到。
他爬到圣栋树的顶端,看到一片茂密的丛林:葱郁的花园尽头是一面山坡,边上种植着大片果树。
沿果园往上,开始出现一片橄榄树木,接着是一片松林,沿着山势向上伸展,望不到尽头。
眼前的景象让柯希莫惊喜不已,他发现这的确是属于自己的领地。
只要树林始终相连,他就可以从一裸树上跳到另一棵树上,他就可以一直不下地,生活在树上。
生活在树上不是件容易的事,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柯希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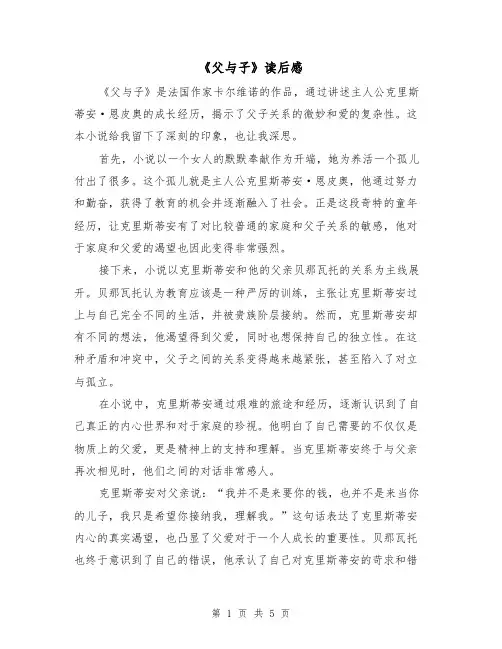
《父与子》读后感《父与子》是法国作家卡尔维诺的作品,通过讲述主人公克里斯蒂安·恩皮奥的成长经历,揭示了父子关系的微妙和爱的复杂性。
这本小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深思。
首先,小说以一个女人的默默奉献作为开端,她为养活一个孤儿付出了很多。
这个孤儿就是主人公克里斯蒂安·恩皮奥,他通过努力和勤奋,获得了教育的机会并逐渐融入了社会。
正是这段奇特的童年经历,让克里斯蒂安有了对比较普通的家庭和父子关系的敏感,他对于家庭和父爱的渴望也因此变得非常强烈。
接下来,小说以克里斯蒂安和他的父亲贝那瓦托的关系为主线展开。
贝那瓦托认为教育应该是一种严厉的训练,主张让克里斯蒂安过上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并被贵族阶层接纳。
然而,克里斯蒂安却有不同的想法,他渴望得到父爱,同时也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父子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甚至陷入了对立与孤立。
在小说中,克里斯蒂安通过艰难的旅途和经历,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真正的内心世界和对于家庭的珍视。
他明白了自己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父爱,更是精神上的支持和理解。
当克里斯蒂安终于与父亲再次相见时,他们之间的对话非常感人。
克里斯蒂安对父亲说:“我并不是来要你的钱,也并不是来当你的儿子,我只是希望你接纳我,理解我。
”这句话表达了克里斯蒂安内心的真实渴望,也凸显了父爱对于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
贝那瓦托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承认了自己对克里斯蒂安的苛求和错失了对儿子的真正爱护。
最终,父子之间的隔阂被逐渐消除,他们开始重新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
《父与子》通过克里斯蒂安和贝那瓦托之间的故事,深刻地描绘了父子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亲情的强大力量。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饱满,情节跌宕起伏,让人感受到了作者深厚的情感表达能力和思想深度。
通过对于父爱的探讨,小说也引发了我对于自己与家庭、父母之间关系的思考,让我更加珍视父母的付出和理解他们的苦心。
总的来说,阅读《父与子》给了我很多的思考和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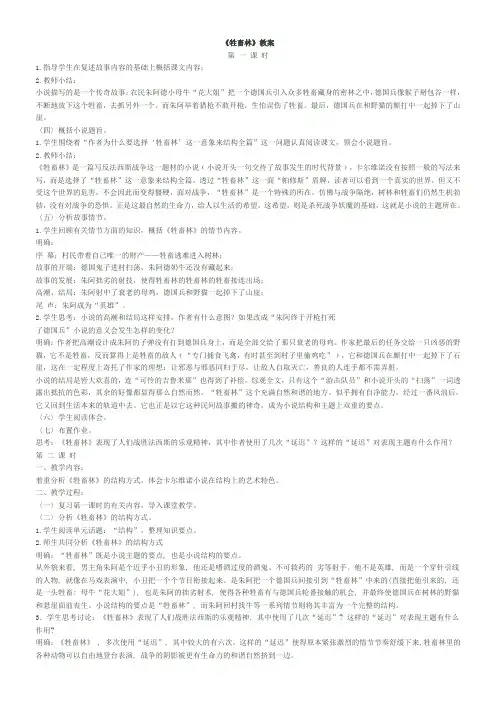
《牲畜林》教案第一课时1.指导学生在复述故事内容的基础上概括课文内容;2.教师小结:小说描写的是一个传奇故事:农民朱阿德小母牛“花大姐”把一个德国兵引入众多牲畜藏身的密林之中,德国兵像猴子掰包谷一样,不断地放下这个牲畜,去抓另外一个。
而朱阿举着猎枪不敢开枪,生怕误伤了牲畜。
最后,德国兵在和野猫的厮打中一起掉下了山崖。
〈四〉概括小说题旨。
1.学生围绕着“作者为什么要选择‘牲畜林’这一意象来结构全篇”这一问题认真阅读课文,领会小说题旨。
2.教师小结:《牲畜林》是一篇写反法西斯战争这一题材的小说﹙小说开头一句交待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卡尔维诺没有按照一般的写法来写,而是选择了“牲畜林”这一意象来结构全篇。
透过“牲畜林”这一面“帕修斯”盾牌,读者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但又不受这个世界的危害,不会因此而变得僵硬,面对战争,“牲畜林”是一个特殊的所在,仿佛与战争隔绝,树林和牲畜们仍然生机勃勃,没有对战争的恐惧。
正是这最自然的生命力,给人以生活的希望,这希望,则是杀死战争妖魔的基础,这就是小说的主题所在。
〈五〉分析故事情节。
1.学生回顾有关情节方面的知识,概括《牲畜林》的情节内容。
明确:序幕:村民带着自己唯一的财产——牲畜逃难进入树林;故事的开端:德国鬼子进村扫荡,朱阿德奶牛还没有藏起来;故事的发展:朱阿拙劣的射技,使得牲畜林的牲畜林的牲畜接连出场;高潮、结局:朱阿射中了衰老的母鸡,德国兵和野猫一起掉下了山崖;尾声:朱阿成为“英雄”。
2.学生思考:小说的高潮和结局这样安排,作者有什么意图?如果改成“朱阿终于开枪打死了德国兵”小说的意义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明确:作者把高潮设计成朱阿的子弹没有打到德国兵身上,而是全部交给了那只衰老的母鸡。
作家把最后的任务交给一只凶恶的野猫,它不是牲畜,反而算得上是牲畜的敌人﹙“专门捕食飞禽,有时甚至到村子里偷鸡吃”﹚,它和德国兵在厮打中一起掉下了石崖,这在一定程度上寄托了作家的理想:让邪恶与邪恶同归于尽,让敌人自取灭亡,善良的人连手都不需弄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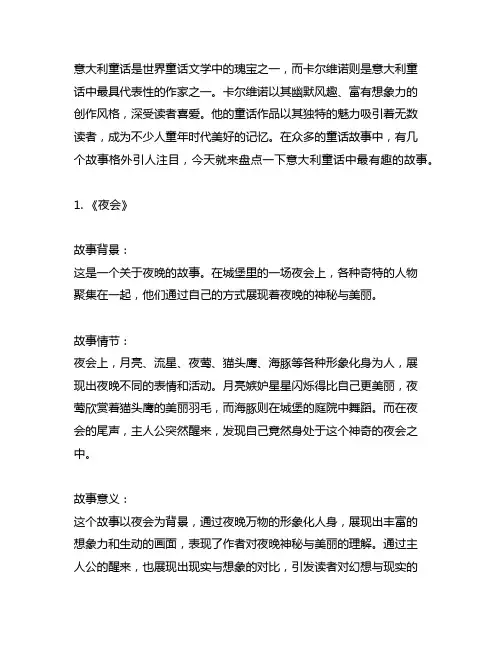
意大利童话是世界童话文学中的瑰宝之一,而卡尔维诺则是意大利童话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卡尔维诺以其幽默风趣、富有想象力的创作风格,深受读者喜爱。
他的童话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读者,成为不少人童年时代美好的记忆。
在众多的童话故事中,有几个故事格外引人注目,今天就来盘点一下意大利童话中最有趣的故事。
1. 《夜会》故事背景:这是一个关于夜晚的故事。
在城堡里的一场夜会上,各种奇特的人物聚集在一起,他们通过自己的方式展现着夜晚的神秘与美丽。
故事情节:夜会上,月亮、流星、夜莺、猫头鹰、海豚等各种形象化身为人,展现出夜晚不同的表情和活动。
月亮嫉妒星星闪烁得比自己更美丽,夜莺欣赏着猫头鹰的美丽羽毛,而海豚则在城堡的庭院中舞蹈。
而在夜会的尾声,主人公突然醒来,发现自己竟然身处于这个神奇的夜会之中。
故事意义:这个故事以夜会为背景,通过夜晚万物的形象化人身,展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和生动的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夜晚神秘与美丽的理解。
通过主人公的醒来,也展现出现实与想象的对比,引发读者对幻想与现实的思考。
2. 《酒神巴科》故事背景:这是一个充满幽默和讽刺的故事。
主人公巴科是一个生活在意大利城市佛洛伦萨的酒神,他以一双奇特的眼睛观察着人间世界。
故事情节:巴科似乎是世人眼中的一个神秘人物,他总是出现在一些热闹的酒馆和夜总会中,与人们交谈并为他们解围。
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观察着人们的生活和情感,同时也用自己的方式幽默地讽刺和解构一些世俗的观念。
故事意义:这个故事以巴科的视角展现了人间百态,传达了一种对世俗现实的讽刺和反思。
通过巴科与其他人的对话和互动,也向读者展现了一种特殊的智慧和幽默感。
整个故事充满着讽刺与幽默,带给读者别样的阅读体验。
3. 《隐形的城市》故事背景:这是一部以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的游记为背景的童话小说。
作品以一种虚构的形式,讲述了波罗在东方经历的种种奇异景象和传奇故事。
故事情节:在这部小说中,波罗在东方的游历,发现了一座座隐形的城市,这些城市各自拥有独特的特征和传奇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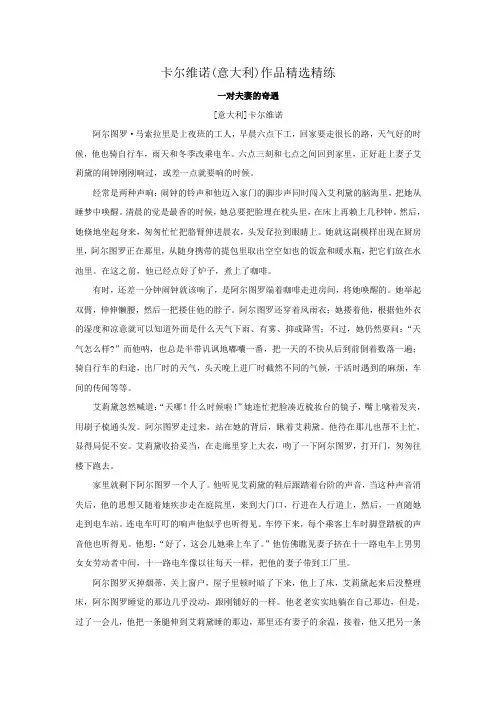
卡尔维诺(意大利)作品精选精练一对夫妻的奇遇[意大利]卡尔维诺阿尔图罗·马索拉里是上夜班的工人,早晨六点下工,回家要走很长的路,天气好的时候,他也骑自行车,雨天和冬季改乘电车。
六点三刻和七点之间回到家里,正好赶上妻子艾莉黛的闹钟刚刚响过,或差一点就要响的时候。
经常是两种声响:闹钟的铃声和他迈入家门的脚步声同时闯入艾利黛的脑海里,把她从睡梦中唤醒。
清晨的觉是最香的时候,她总要把脸埋在枕头里,在床上再赖上几秒钟。
然后,她倏地坐起身来,匆匆忙忙把胳臂伸进晨衣,头发耷拉到眼睛上。
她就这副模样出现在厨房里,阿尔图罗正在那里,从随身携带的提包里取出空空如也的饭盒和暖水瓶,把它们放在水池里。
在这之前,他已经点好了炉子,煮上了咖啡。
有时,还差一分钟闹钟就该响了,是阿尔图罗端着咖啡走进房间,将她唤醒的。
她举起双臂,伸伸懒腰,然后一把搂住他的脖子。
阿尔图罗还穿着风雨衣;她搂着他,根据他外衣的湿度和凉意就可以知道外面是什么天气下雨、有雾、抑或降雪;不过,她仍然要问:“天气怎么样?”而他呐,也总是半带讥讽地嘟囔一番,把一天的不快从后到前倒着数落一遍;骑自行车的归途,出厂时的天气,头天晚上进厂时截然不同的气候,干活时遇到的麻烦,车间的传闻等等。
艾莉黛忽然喊道:“天哪!什么时候啦!”她连忙把脸凑近梳妆台的镜子,嘴上噙着发夹,用刷子梳通头发。
阿尔图罗走过来,站在她的背后,瞅着艾莉黛。
他待在那儿也帮不上忙,显得局促不安。
艾莉黛收拾妥当,在走廊里穿上大衣,吻了一下阿尔图罗,打开门,匆匆往楼下跑去。
家里就剩下阿尔图罗一个人了。
他听见艾莉黛的鞋后跟踏着台阶的声音,当这种声音消失后,他的思想又随着她疾步走在庭院里,来到大门口,行进在人行道上,然后,一直随她走到电车站。
连电车叮叮的响声他似乎也听得见。
车停下来,每个乘客上车时脚登踏板的声音他也听得见。
他想:“好了,这会儿她乘上车了。
”他仿佛瞧见妻子挤在十一路电车上男男女女劳动者中间,十一路电车像以往每天一样,把他的妻子带到工厂里。
卡尔维诺的《黑羊》比起把“Blacksheep”直译为“黑羊”,其实它意译成“害群之马”将更符合这篇故事的构想。
与卡尔维诺的其它小说相同,这篇故事同样被嵌入了一个干瘪的、了无生趣的逻辑世界中。
在《黑羊》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是现实世界的偷窃者。
在破晓时分,这些偷窃者提着偷来的东西回家。
同样地,他们也会发现自己的东西被他人偷走。
然而这种看似危害极大的行为却达成了一种巧妙的平衡——因为每家每户都会被盗,但也都能获取自己真正需要的物品。
这样,整个社会的结构反而相当稳定,社会上也不存在富人和穷人。
大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然而这种平衡因一个诚实人的到来被打破了。
由于有人不去偷窃了,所以整个社会会出现贫富差距。
富人开始害怕自己的东西被盗,于是就雇用穷人中的最穷都来看管,这就意味着要设立警察局和监狱。
于是没多久,社会中便不再有偷窃行为了。
人们只会谈论富人和穷人。
从整个故事的逻辑来看,其实卡尔维诺无非是给传统的“商品交换”套上了“偷窃的外壳,而诚实人的守信行为去被褪色成了一种悖逆社会原则的行为,这样的行为不仅动荡了社会秩序,甚至会导致了整个世界遭受变革。
这场变革就是原始经济向资本经济过渡的过程。
卡尔维诺以这种不寻常的逻辑阐述了这场变革,便给这个故事披上了讽刺小说的外衣:善行难以生存,而恶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本质。
卡尔维诺笔下的“黑羊”坚守着现世道德观下的诚实,而在《黑羊》的世界观中,他的存在违背了原则。
卡尔维诺坚信“童话是真实的”。
于是在逃开了政治之后,卡尔维诺开始生活在自己的童话中,却又在构想一个个童话中,表达出自己对现实的精准判断,并最终与卡夫卡、福克斯、马尔克斯等戴上了相同的王冠。
在他的小说里,“黑羊”们要么把脆弱的世界撞出缺口,要么被强大的世界挤压得难以生存,正如现世中,那些充满激情、斗志昂扬的共产主义梦想家一样,他们把自己变成了“黑羊”,然而在此之后,他们却永远失去了生存的动力。
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腐朽没落的原始经济,而是当时极为强势的资本主义世界。
《良心》卡尔维诺阅读答案《良心》卡尔维诺原文阅读来了一场战争,一个叫吕基的小伙子去问他是否能作为一个志愿者参战。
人人都对他赞扬有加。
吕基走到他们发步枪的地方,领了一把枪说:“现在我要出发了,去杀一个叫阿尔伯托的家伙。
”他们问他阿尔伯托是谁。
“一个敌人。
”他回答,“我的一个敌人。
”他们跟他解释说他应该去杀某一类敌人,而不是他自己随便想杀就杀谁。
“怎么?”吕基说:“你们以为我是笨蛋吗?这个阿尔伯托正是那类敌人,是他们中的一个。
当我听说你们要和那么多人打仗,我就想我也得去,这样我就能把阿尔伯托杀了。
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
我了解这个阿尔伯托,他是个恶棍。
他背叛了我,几乎没个由头,他让我在一个女人那儿变成了小丑。
这是旧话了。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那我可以把整个经过跟你们讲一下。
”他们说行了,这已经够了。
“那么,”吕基说:“告诉我阿尔伯托在哪儿,我这就去那儿和他干一场。
”他们说他们不知道。
“不要紧。
”吕基说,“我会找到人告诉我的。
迟早我要逮住他。
”他们说他不能那样做,他得去他们叫他去的地方打仗,杀恰好在那里的人。
关于阿尔伯托,他们是一无所知。
“你们看,”吕基坚持说:“我真是应该跟你们讲一下那件事。
因为这个家伙是个真正的恶棍,你们去打他是完全应该的。
”但是其他人不想知道。
吕基看不出这是什么原因:“抱歉,也许我杀这个或哪个敌人对你们而言是一样的,可是如果我杀了一个和阿尔伯托没关系的人,我会难受的。
”其他人不耐烦了。
其中一个人颇费了番口舌,跟他解释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不可以认定自己要杀的某人是敌人。
吕基耸了耸肩。
“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他说,“你们就别把我算上了。
”“你已经来了,你就得呆下去。
”他们吼道。
“向前走,一、二,一、二!”这样他们就把他送上战畅了。
吕基闷闷不乐。
他可以随手杀人,但那不过是为了看看他是否可以找到阿尔伯托,或者阿尔伯托的家人。
他每杀一个人,他们就给他一个奖章,但他闷闷不乐。
“如果我杀不了阿尔伯托,”他想,“那我杀那么一大堆人是一点都不值得的。
《黑羊》的寓意卡尔维诺的寓言小说《黑羊》透露着这样一种雄心:他似乎想像巴尔扎克当年用笔征服欧洲一样,他也在雄心勃勃地用笔征服我们这个文明程度越俩越高的世界。
事实上他的雄心不仅在他最初的写作中已经初露端倪,而且在他的身后已经变成了现实。
假如他尚健在,诺贝尔文学奖是非他莫属的。
卡尔维诺不仅与博尔赫斯被世界文坛公认为是“作家的作家,”而且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一样已经成为当下的一种时尚。
《黑羊》还给我们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卡尔维诺这位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的作家利用手中的笔给我们人类开辟了一条光明的大道,他的追求和目标是对无边的意识疆域的可能性的一种强韧的开拓。
他本人追求无限,因而他的写作也成了无限的写作。
这是一篇仅有千余字的小说,小说充满了悲怆和无奈的情绪。
我们的阅读快感会很快被我们的尴尬和苦涩所取代。
从来没有人达到这样的写作高度,在一千多字的文字里能够完美地展现我们这个世界的荒诞、冷酷、凶残、粗暴、专制、掠夺的属性。
而且,还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内涵。
卡尔维诺轻而易举地卡住了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卑劣人性最敏感的神经,使我们的隐痛变成血淋淋的伤口。
我们甚至还可以设想,文明的进程从来都是以牺牲那些不应该牺牲人的生命和利益为代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牺牲是公众共谋的结果。
因为,我们都是《黑羊》小说中的“贼”或者强盗。
卡尔维诺令人惊讶地在《黑羊》之中塑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国家,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是贼。
他们幸福而又祥和地居住在一起。
但是每到晚上,他们就去偷别人的东西。
甲偷乙,乙偷丙。
每个人拎着偷来的东西回家时就发现自己的家里也失窃了。
我们惊讶地发现这个国家和我们现实社会有如此众多的相似之处,因为我们的幸福对大多数人而言是建立在公众的道德、公众的伦理以及现存的秩序的认同的基础之上的,其中还包括了公众的生存方式、公众行为的标准等等。
假如我们把人生和社会视为一种游戏,那么游戏的规则则是需要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的。
谁违反了游戏的规则,谁就会得到相应的惩罚。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高速公路上的森林[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寒冷有千百种形式、千百种方法在世界上移动:在海上像一群狂奔的马,在乡村像一窝猛扑的蝗虫,在城市则像一把利刃截断道路,从缝里钻入没有暖气的家中。
那天晚上,马可瓦多家用尽了最后的干柴,裹着大衣的全家人,看着暖炉中逐渐黯淡的小木炭,每一次呼吸,就从他们嘴里升起云雾,再没有人说话,云雾代替他们发言:太太吐出长长的云雾仿佛在叹气,小孩们好像专心一意地吹着肥皂泡泡,而马可瓦多则一停一顿地朝着空中喷着云雾,好像喷发转瞬即逝的智慧火花。
最后马可瓦多决定了:“我去找柴火,说不定能找到。
”他在夹克和衬杉间塞进了四五张报纸,以作为御寒的盔甲,在大衣下藏了一把齿锯,在家人充满希望的目光的跟随下,深夜走出门,每走一步就发出纸的响声,而锯子也不时从他大衣里冒出。
到市区里找柴火,说得倒好!马可瓦多直向夹在两条马路中间的一小片公园走去。
空无一人,马可瓦多一面研究光秃秃的树千,一面想着家人正牙齿打颤地等着他……小米开尔哆嗦着牙齿,读一本从学校图书室借回来的童话,书里头说的是一个木匠的小孩带着斧头去森林里砍柴。
“这才是要去的地方。
”小米开尔说,“森林!那里就会有木柴了!”他从一出生就住在城市里,从来没看过森林,连从远处看的经验也没有。
说到做到,跟兄弟们组织起来:一个人带斧头,一个人带钩子,一个人带绳子。
跟妈妈说再见后就开始寻找森林。
走在路灯照得通亮的城市,除了房子以外看不到别的:什么森林,连影子也没有。
也遇到过几个行人,但是不敢问哪儿有森林。
他们走到最后,城里的房子都不见了,而马路变成了高速公路小孩就在高速公路旁看到了森林:一片茂密而奇形怪状的树林淹没了一望无际的平原。
它们有极细极细的树干,或直或斜;当汽车经过,车灯照亮时,发现这些扁平而宽阔的树叶有着最奇怪的样子和颜色。
树枝的形状是牙青、脸、乳酪、手、剃刀、瓶子、母牛和轮胎,遍布的树叶是字母。
“万岁!”小米开尔说,“这就是森林!”弟弟们则着迷地看着从奇异轮廊中露头的月亮:“真美……”小米开尔赶紧提醒他们来这儿的目的:柴火。
卡尔维诺的战争题材短篇小说 [摘要]卡尔维诺的短篇小说有着非常独特的魅力,战争小说是短篇小说最常见的主题之一,他对战争的处理极为别致。他的大多数短篇小说中战争是一种背景,小说对战争的游离更让人认识战争。也有少数作品是直面战争,表明作者对战争的态度,关怀在战争中被裹挟的个人的命运,思考战争引发的种种问题。
[关键词]卡尔维诺;战争;游离;现实 国内对卡尔维诺作品津津乐道的是他的中长篇小说,如《看不见的城市》、《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寒冬夜行人》等,对他的短篇小说关注不够。也有少数研究者关注到卡尔维诺短篇的独特品质,洪治纲《短篇小说,或一些问题》[1]把卡尔维诺与欧·亨利、辛格、博尔赫斯等世界一流短篇小说大师相提并论,并简明扼要地指出卡尔维诺短篇的寓言和诗性特质,可惜没有展开论述。卡尔维诺短篇小说的非凡魅力尚未得到广泛认知。笔者认为卡尔维诺的短篇小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现实主义的,如马可瓦多系列、战争系列,这类小说关注现实,但对现实的处理方式很特别,虽关注现实但却又对现实轻描淡写,笔触常常逸出现实之外,但正是这“旁逸”的“轻”击中了现实的本质,即现实与历史背后荒谬的逻辑与机制,写法极为俏皮有趣。另一类是寓言小说,如《黑羊》、《呼喊特丽莎的人》,虽然深刻,但不见道德说教,读来诗意盎然,充满诗性的哲理美。本文因篇幅关系只论及卡尔维诺短篇小说中的战争题材作品,这类作品极为别致,战争题材小说是卡尔维诺最主要的现实主义类型小说之一。他是在20世纪40年代登上文学舞台的,那时战争是最不容忽视的现实,战争题材也是他早期小说最主要的题材之一。他的大多数短篇小说中战争是一种背景,小说对战争的游离更让人认识战争。也有少数作品是直面战争,表明作者对战争的态度,关怀在战争中被裹挟的个人的命运,思考战争引发的种种问题。
一、战争与游离战争 卡尔维诺的大部分战争主题的短篇小说,虽然一开始就进入战争的背景,但小说很快游离战争,这游离让人感觉似乎和现实走远了,从某种角度看正是依靠这种游离才真正接近现实,让人更加认识战争的本质。如《好游戏玩不长》中的两个孩子乔瓦尼诺和赛来内拉玩打仗的游戏。孩子们扮演敌我双方如何轰炸,如何匍匐前进,如何冲锋陷阵,甚至扮演阵亡者。这战争游戏玩得可是热火朝天,不亦乐乎,直到孩子们遇到三个真正的士兵。真正的士兵却不像孩子们那么亢奋,而是忧郁的。小说借助孩子的视角写了真正的士兵是什么样的,“他正躺在草地上,举着步枪,而头盔,肩包,干粮袋,行军水壶,手榴弹,防毒面具是一个压在另一个之上地堆在他身上,就像是一场由不同物件构成的雪崩,把他给埋没了,在所有这些东西上,是从一株含羞草上扯下并捆在一起的枝叶,树枝的裂缝露出了木头的红心,还有一片片被剥掉的树皮。那个士兵,从地上把脸转向孩子,几乎都没有挪动头盔,只是把头在头盔里转着,一直转到把一面脸颊贴在地上。他的眼睛是灰色的,忧郁,唇间含着一片樱桃叶。”[2]49在战斗的间歇,孩子们看到的士兵被种种物件埋没着,似乎在影射因为战争他们失去了自我。士兵玩头盔,玩树枝和嘴含樱桃叶,真正士兵不经意的小动作暗示着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孩子们严肃的战争游戏形成叙事的张力。后来两个孩子去到了参谋部,小说又通过孩子的视角描写了将军如何谋划布局,在孩子的眼里将军的形象有点愚笨,将军说的话孩子们听不懂的小说用省略号代替,造成了将军语焉不详的效果。这样一来,士兵和将军的形象就被解构了。孩子们被赶出军事参谋部后,他们继续玩游戏,玩炸掉军团参谋部、炸掉师参谋部的游戏。孩子的知识有限,只知道师是最高编制,因此游戏到此结束,孩子中的一个说:“我觉得不剩下什么了,”“所有的都被炸掉了。”孩子们玩别的游戏去了,这就是小说的结局。这个结局也是意味深长的,在孩子们的战争游戏中,他们对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毁灭了的游戏结局不以为意,因为那不是真的,可真正的战争不是游戏。在这篇小说中,虽与战争有关,但并不正面写战争,杀敌立功士兵和将军在孩子们的眼里都很滑稽,但小说对孩子们的战争游戏却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真正的战争和战争游戏的形成反讽,引发人们对战争毁灭性的本质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