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中的田园视景与抒情性问题
- 格式:doc
- 大小:37.50 KB
- 文档页数: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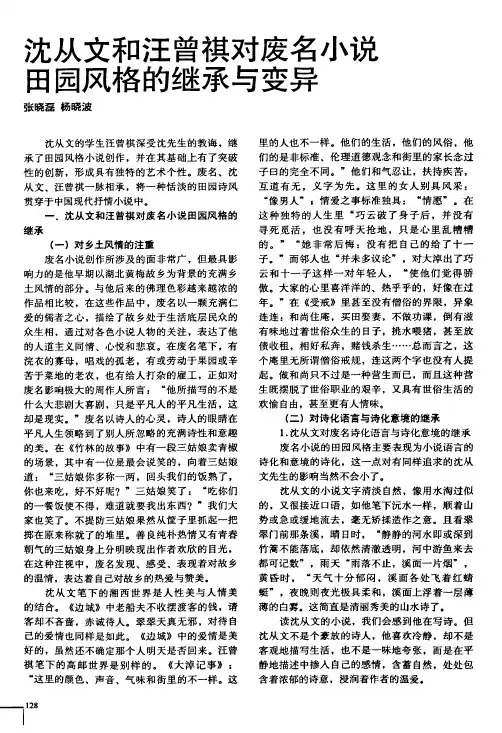
沈从文和汪曾祺对废名小说田园风格的继承与变异张晓磊杨晓波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深受沈先生的教诲,继承了田园风格小说创作,并在其基础上有了突破性的创新,形成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
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一脉相承,将一种恬淡的田园诗风贯穿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中。
一.沈从文和汪曾祺对废名小说田园风格的继承(一)对乡土风情的注重废名小说创作所涉及的面非常广,但最具影响力的是他早期以湖北黄梅故乡为背景的充满乡土风情的部分。
与他后来的佛理色彩越来越浓的作品相比较,在这些作品中,废名以一颗充满仁爱的儒者之心,描绘了故乡处于生活底层民众的众生相,通过对各色小说人物的关注,表达了他的人道主义同情、心悦和悲哀。
在废名笔下,有浣衣的寡母,唱戏的孤老,有或劳动于果园或辛苦于菜地的老农,也有给人打杂的雇工,正如对废名影响极大的周作人所言:。
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是现实。
”废名以诗人的心灵,诗人的眼睛在平凡人生领略到了别人所忽略的充满诗性和意趣的美。
在《[竹林的故事》中有一段三姑娘卖青椒的场景,其中有一位是最会说笑的,向着三姑娘道:。
三姑娘你多称一两,回头我们的饭熟了,你也来吃,好不好昵?”三姑娘笑了:。
吃你们的一餐饭使不得,难道就要我出东西?”我们大家也笑了。
不提防三姑娘果然从筐子里抓起一把掷在原来称就了的堆里。
善良纯朴热情又有青春朝气的三姑娘身上分明映现出作者欢欣的目光,在这种注视中,废名发现、感受、表现着对故乡的温情,表达着自己对故乡的热爱与赞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人性美与人情美的结合。
《[边城》中老船夫不收摆渡客的钱,请客却不吝啬,赤诚待人。
翠翠天真无邪,对待自己的爱情也同样是如此。
程边城》中的爱情是美好的,虽然还不确定那个人明天是否回来。
汪曾祺笔下的高邮世界是别样的。
《大淖记事》:。
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的不一样。
这一128I 里的人也不一样。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家长念过子日的完全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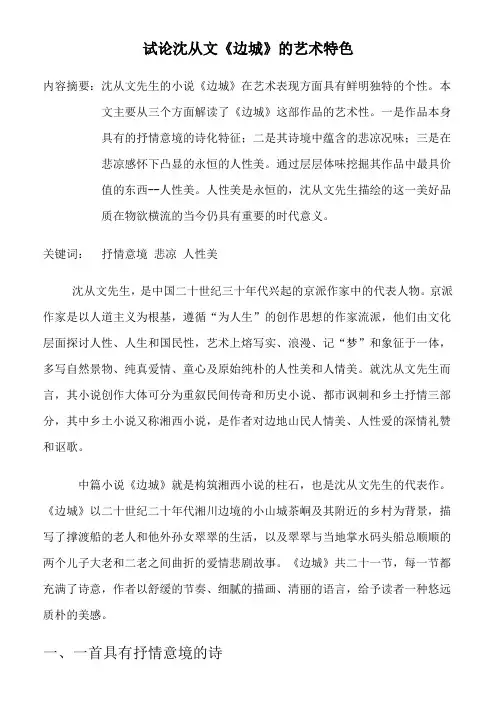
试论沈从文《边城》的艺术特色内容摘要: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边城》在艺术表现方面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解读了《边城》这部作品的艺术性。
一是作品本身具有的抒情意境的诗化特征;二是其诗境中蕴含的悲凉况味;三是在悲凉感怀下凸显的永恒的人性美。
通过层层体味挖掘其作品中最具价值的东西--人性美。
人性美是永恒的,沈从文先生描绘的这一美好品质在物欲横流的当今仍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抒情意境悲凉人性美沈从文先生,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京派作家中的代表人物。
京派作家是以人道主义为根基,遵循“为人生”的创作思想的作家流派,他们由文化层面探讨人性、人生和国民性,艺术上熔写实、浪漫、记“梦”和象征于一体,多写自然景物、纯真爱情、童心及原始纯朴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就沈从文先生而言,其小说创作大体可分为重叙民间传奇和历史小说、都市讽刺和乡土抒情三部分,其中乡土小说又称湘西小说,是作者对边地山民人情美、人性爱的深情礼赞和讴歌。
中篇小说《边城》就是构筑湘西小说的柱石,也是沈从文先生的代表作。
《边城》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湘川边境的小山城茶峒及其附近的乡村为背景,描写了撑渡船的老人和他外孙女翠翠的生活,以及翠翠与当地掌水码头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大老和二老之间曲折的爱情悲剧故事。
《边城》共二十一节,每一节都充满了诗意,作者以舒缓的节奏、细腻的描画、清丽的语言,给予读者一种悠远质朴的美感。
一、一首具有抒情意境的诗《边城》因其全篇弥漫着悠然袅袅的诗意,而常被人称作“一部田园牧歌式的杰作”、“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刘西渭语)。
在沈从文先生的诗化小说长廊中,《边城》无疑是高居其王冠之上的宝石。
首先,作品中的人、事、物皆被镀了一层诗意的光辉。
在故事情节方面,是以翠翠和二老的爱情为诗情的载体,悠然道来二人故事中“爱”与“美”的特质。
翠翠本身就是美的,纯的。
“翠翠在风日里长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养着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想不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1)沈从文先生用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翠翠的纯美与柔和,翠翠像一件带有灵魂的美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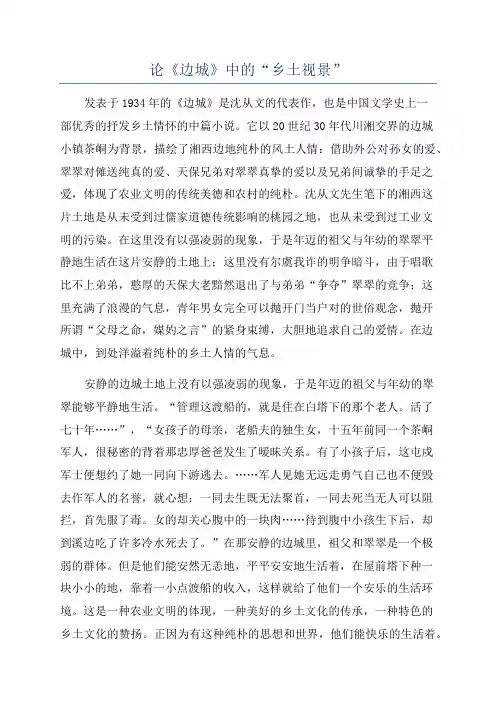
论《边城》中的“乡土视景”发表于1934年的《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
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描绘了湘西边地纯朴的风土人情:借助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体现了农业文明的传统美德和农村的纯朴。
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湘西这片土地是从未受到过儒家道德传统影响的桃园之地,也从未受到过工业文明的污染。
在这里没有以强凌弱的现象,于是年迈的祖父与年幼的翠翠平静地生活在这片安静的土地上;这里没有尔虞我诈的明争暗斗,由于唱歌比不上弟弟,憨厚的天保大老黯然退出了与弟弟“争夺”翠翠的竞争;这里充满了浪漫的气息,青年男女完全可以抛开门当户对的世俗观念,抛开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紧身束缚,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
在边城中,到处洋溢着纯朴的乡土人情的气息。
安静的边城土地上没有以强凌弱的现象,于是年迈的祖父与年幼的翠翠能够平静地生活。
“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白塔下的那个老人。
活了七十年……”,“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峒军人,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
有了小孩子后,这屯戍军士便想约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
……军人见她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
女的却关心腹中的一块肉……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
”在那安静的边城里,祖父和翠翠是一个极弱的群体。
但是他们能安然无恙地,平平安安地生活着,在屋前塔下种一块小小的地,靠着一小点渡船的收入,这样就给了他们一个安乐的生活环境。
这是一种农业文明的体现,一种美好的乡土文化的传承,一种特色的乡土文化的赞扬。
正因为有这种纯朴的思想和世界,他们能快乐的生活着。
安静的边城土地上没有尔虞我诈的明争暗斗。
天保大老,对翠翠的爱是深刻的,是真诚的,他想尽办法去争取翠翠,又是走车路,又走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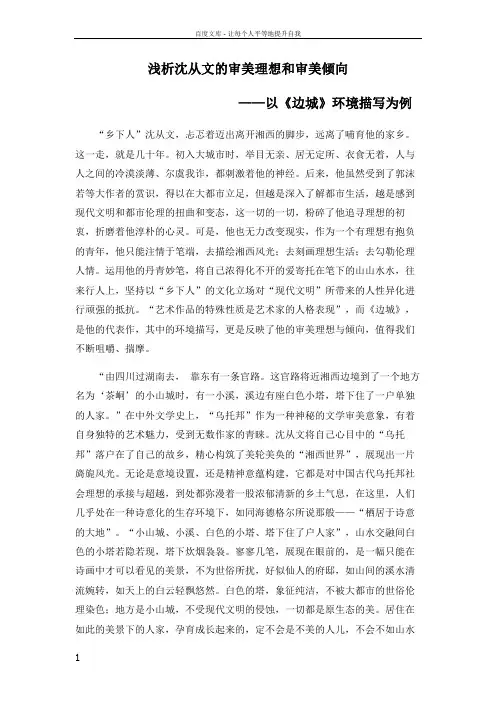
浅析沈从文的审美理想和审美倾向——以《边城》环境描写为例“乡下人”沈从文,忐忑着迈出离开湘西的脚步,远离了哺育他的家乡。
这一走,就是几十年。
初入大城市时,举目无亲、居无定所、衣食无着,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淡薄、尔虞我诈,都刺激着他的神经。
后来,他虽然受到了郭沫若等大作者的赏识,得以在大都市立足,但越是深入了解都市生活,越是感到现代文明和都市伦理的扭曲和变态,这一切的一切,粉碎了他追寻理想的初衷,折磨着他淳朴的心灵。
可是,他也无力改变现实,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他只能注情于笔端,去描绘湘西风光;去刻画理想生活;去勾勒伦理人情。
运用他的丹青妙笔,将自己浓得化不开的爱寄托在笔下的山山水水,往来行人上,坚持以“乡下人”的文化立场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人性异化进行顽强的抵抗。
“艺术作品的特殊性质是艺术家的人格表现”,而《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其中的环境描写,更是反映了他的审美理想与倾向,值得我们不断咀嚼、揣摩。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
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
”在中外文学史上,“乌托邦”作为一种神秘的文学审美意象,有着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受到无数作家的青睐。
沈从文将自己心目中的“乌托邦”落户在了自己的故乡,精心构筑了美轮美奂的“湘西世界”,展现出一片旖旎风光。
无论是意境设置,还是精神意蕴构建,它都是对中国古代乌托邦社会理想的承接与超越,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浓郁清新的乡土气息,在这里,人们几乎处在一种诗意化的生存环境下,如同海德格尔所说那般——“栖居于诗意的大地”。
“小山城、小溪、白色的小塔、塔下住了户人家”,山水交融间白色的小塔若隐若现,塔下炊烟袅袅。
寥寥几笔,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只能在诗画中才可以看见的美景,不为世俗所扰,好似仙人的府邸,如山间的溪水清流婉转,如天上的白云轻飘悠然。
白色的塔,象征纯洁,不被大都市的世俗伦理染色;地方是小山城,不受现代文明的侵蚀,一切都是原生态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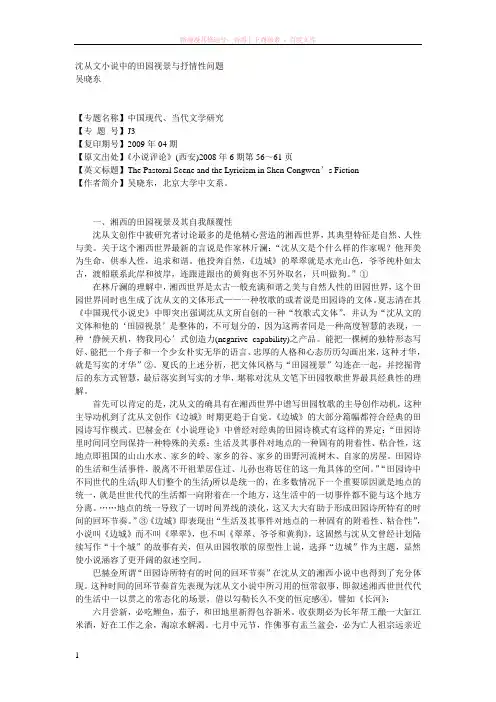
沈从文小说中的田园视景与抒情性问题吴晓东【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专题号】J3【复印期号】2009年04期【原文出处】《小说评论》(西安)2008年6期第56~61页【英文标题】The Pastoral Scene and the Lyricism in Shen Congwen’s Fiction【作者简介】吴晓东,北京大学中文系。
一、湘西的田园视景及其自我颠覆性沈从文创作中被研究者讨论最多的是他精心营造的湘西世界,其典型特征是自然、人性与美。
关于这个湘西世界最新的言说是作家林斤澜:“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呢?他拜美为生命,供奉人性,追求和谐。
他投奔自然,《边城》的翠翠就是水光山色,爷爷纯朴如太古,渡船联系此岸和彼岸,连跟进跟出的黄狗也不另外取名,只叫做狗。
”①在林斤澜的理解中,湘西世界是太古一般充满和谐之美与自然人性的田园世界,这个田园世界同时也生成了沈从文的文体形式——一种牧歌的或者说是田园诗的文体。
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即突出强调沈从文所自创的一种“牧歌式文体”,并认为“沈从文的文体和他的‘田园视景’是整体的,不可划分的,因为这两者同是一种高度智慧的表现,一种‘静候天机,物我同心’式创造力(negarive capability)之产品。
能把一棵树的独特形态写好、能把一个舟子和一个少女朴实无华的语言、忠厚的人格和心态历历勾画出来,这种才华,就是写实的才华”②。
夏氏的上述分析,把文体风格与“田园视景”勾连在一起,并挖掘背后的东方式智慧,最后落实到写实的才华,堪称对沈从文笔下田园牧歌世界最具经典性的理解。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沈从文的确具有在湘西世界中谱写田园牧歌的主导创作动机,这种主导动机到了沈从文创作《边城》时期更趋于自觉。
《边城》的大部分篇幅都符合经典的田园诗写作模式。
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中曾经对经典的田园诗模式有这样的界定:“田园诗里时间同空间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生活及其事件对地点的一种固有的附着性、粘合性,这地点即祖国的山山水水、家乡的岭、家乡的谷、家乡的田野河流树木、自家的房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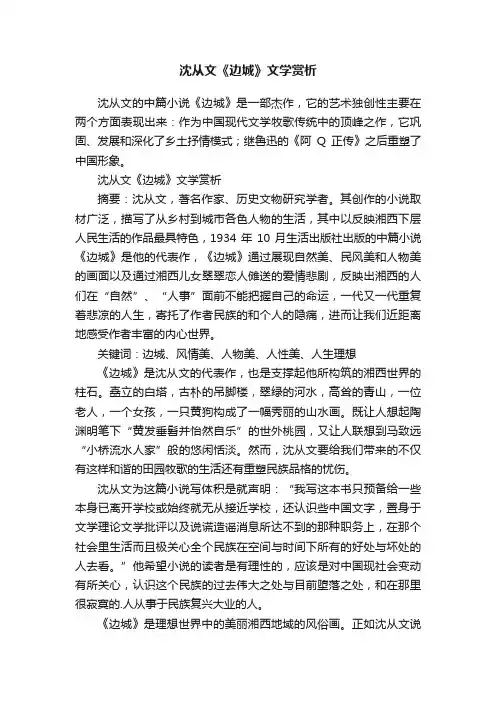
沈从文《边城》文学赏析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是一部杰作,它的艺术独创性主要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统中的顶峰之作,它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继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重塑了中国形象。
沈从文《边城》文学赏析摘要:沈从文,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学者。
其创作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1934年10月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边城》通过展现自然美、民风美和人物美的画面以及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的人们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凉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进而让我们近距离地感受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边城、风情美、人物美、人性美、人生理想《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也是支撑起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的柱石。
矗立的白塔,古朴的吊脚楼,翠绿的河水,高耸的青山,一位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构成了一幅秀丽的山水画。
既让人想起陶渊明笔下“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世外桃园,又让人联想到马致远“小桥流水人家”般的悠闲恬淡。
然而,沈从文要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有这样和谐的田园牧歌的生活还有重塑民族品格的忧伤。
沈从文为这篇小说写体积是就声明:“我写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
”他希望小说的读者是有理性的,应该是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之处与目前堕落之处,和在那里很寂寞的.人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
《边城》是理想世界中的美丽湘西地域的风俗画。
正如沈从文说“我要表现的事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
”[1]因此小说用前三章描绘了湘西的山水风景以及当地的风俗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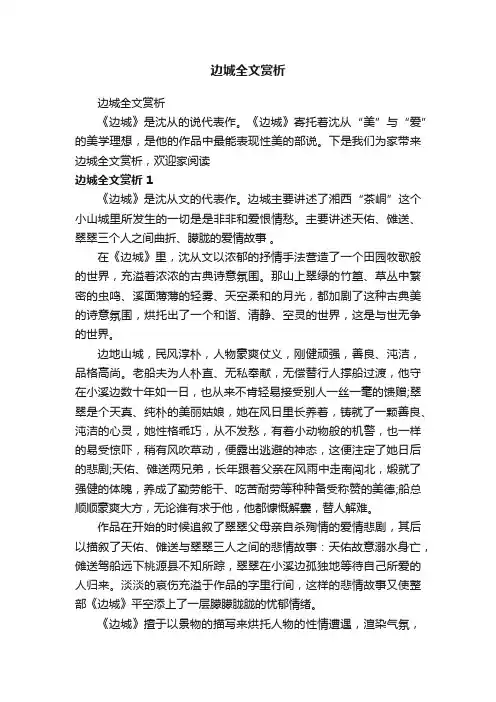
边城全文赏析边城全文赏析《边城》是沈从的说代表作。
《边城》寄托着沈从“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性美的部说。
下是我们为家带来边城全文赏析,欢迎家阅读边城全文赏析 1《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
边城主要讲述了湘西“茶峒”这个小山城里所发生的一切是是非非和爱恨情愁。
主要讲述天佑、傩送、翠翠三个人之间曲折、朦胧的爱情故事。
在《边城》里,沈从文以浓郁的抒情手法营造了一个田园牧歌般的世界,充溢着浓浓的古典诗意氛围。
那山上翠绿的竹篁、草丛中繁密的虫鸣、溪面薄薄的轻雾、天空柔和的月光,都加剧了这种古典美的诗意氛围,烘托出了一个和谐、清静、空灵的世界,这是与世无争的世界。
边地山城,民风淳朴,人物豪爽仗义,刚健顽强,善良、沌洁,品格高尚。
老船夫为人朴直、无私奉献,无偿替行人撑船过渡,他守在小溪边数十年如一日,也从来不肯轻易接受别人一丝一毫的馈赠;翠翠是个天真、纯朴的美丽姑娘,她在风日里长养着,铸就了一颗善良、沌洁的心灵,她性格乖巧,从不发愁,有着小动物般的机警,也一样的易受惊吓,稍有风吹草动,便露出逃避的神态,这便注定了她日后的悲剧;天佑、傩送两兄弟,长年跟着父亲在风雨中走南闯北,煅就了强健的体魄,养成了勤劳能干、吃苦耐劳等种种备受称赞的美德;船总顺顺豪爽大方,无论谁有求于他,他都慷慨解囊,替人解难。
作品在开始的时候追叙了翠翠父母亲自杀殉情的爱情悲剧,其后以描叙了天佑、傩送与翠翠三人之间的悲情故事:天佑故意溺水身亡,傩送驾船远下桃源县不知所踪,翠翠在小溪边孤独地等待自己所爱的人归来。
淡淡的哀伤充溢于作品的字里行间,这样的悲情故事又使整部《边城》平空添上了一层朦朦胧胧的忧郁情绪。
《边城》擅于以景物的描写来烘托人物的性情遭遇,渲染气氛,推动情节的发展。
如丹塌的白塔、哗哗的浊流、惨淡的黄昏、桃色的薄云。
这些景物描写,揉进了人物的际遇和思想感情,尽显凄清、寂寥之情;人物的情思显得朦朦胧胧,似有似无,却又是异样的纯净透明,翠翠在爱的幻想中展开想像的翅膀,享受精神上的爱情,那是一个情窦初开的纯洁少女的纯真情怀,是那样的纯净和透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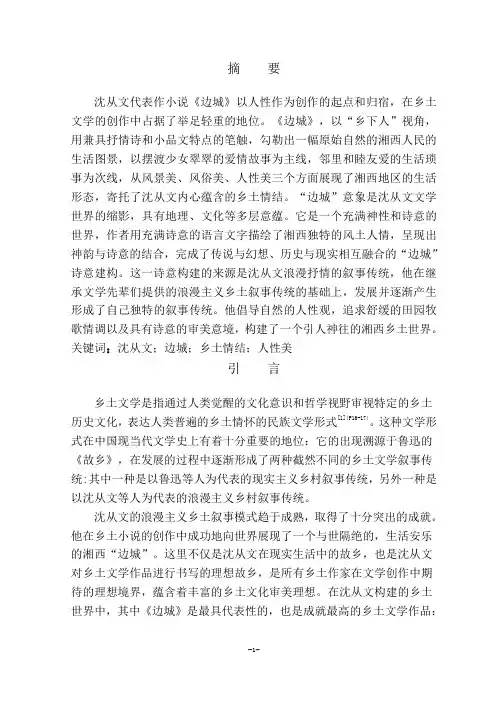
摘要沈从文代表作小说《边城》以人性作为创作的起点和归宿,在乡土文学的创作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边城》,以“乡下人”视角,用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特点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原始自然的湘西人民的生活图景,以摆渡少女翠翠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邻里和睦友爱的生活琐事为次线,从风景美、风俗美、人性美三个方面展现了湘西地区的生活形态,寄托了沈从文内心蕴含的乡土情结。
“边城”意象是沈从文文学世界的缩影,具有地理、文化等多层意蕴。
它是一个充满神性和诗意的世界,作者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文字描绘了湘西独特的风土人情,呈现出神韵与诗意的结合,完成了传说与幻想、历史与现实相互融合的“边城”诗意建构。
这一诗意构建的来源是沈从文浪漫抒情的叙事传统,他在继承文学先辈们提供的浪漫主义乡土叙事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并逐渐产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传统。
他倡导自然的人性观,追求舒缓的田园牧歌情调以及具有诗意的审美意境,构建了一个引人神往的湘西乡土世界。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乡土情结;人性美引言乡土文学是指通过人类觉醒的文化意识和哲学视野审视特定的乡土历史文化,表达人类普遍的乡土情怀的民族文学形式[1](P16-17)。
这种文学形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溯源于鲁迅的《故乡》,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乡土文学叙事传统:其中一种是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乡村叙事传统,另外一种是以沈从文等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乡村叙事传统。
沈从文的浪漫主义乡土叙事模式趋于成熟,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
他在乡土小说的创作中成功地向世界展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生活安乐的湘西“边城”。
这里不仅是沈从文在现实生活中的故乡,也是沈从文对乡土文学作品进行书写的理想故乡,是所有乡土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期待的理想境界,蕴含着丰富的乡土文化审美理想。
在沈从文构建的乡土世界中,其中《边城》是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成就最高的乡土文学作品:它用简单的文字以及平实的语言再次向读者展现了在茶峒小镇中悠闲生活的村民,以及关于船女翠翠的亲情与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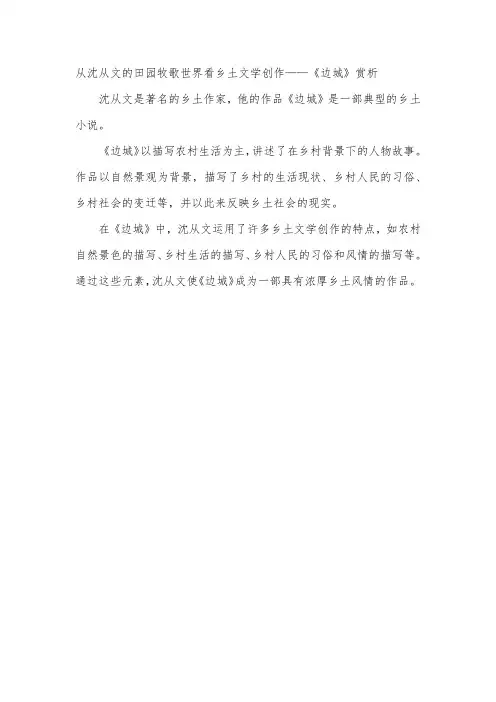
从沈从文的田园牧歌世界看乡土文学创作——《边城》赏析沈从文是著名的乡土作家,他的作品《边城》是一部典型的乡土小说。
《边城》以描写农村生活为主,讲述了在乡村背景下的人物故事。
作品以自然景观为背景,描写了乡村的生活现状、乡村人民的习俗、乡村社会的变迁等,并以此来反映乡土社会的现实。
在《边城》中,沈从文运用了许多乡土文学创作的特点,如农村自然景色的描写、乡村生活的描写、乡村人民的习俗和风情的描写等。
通过这些元素,沈从文使《边城》成为一部具有浓厚乡土风情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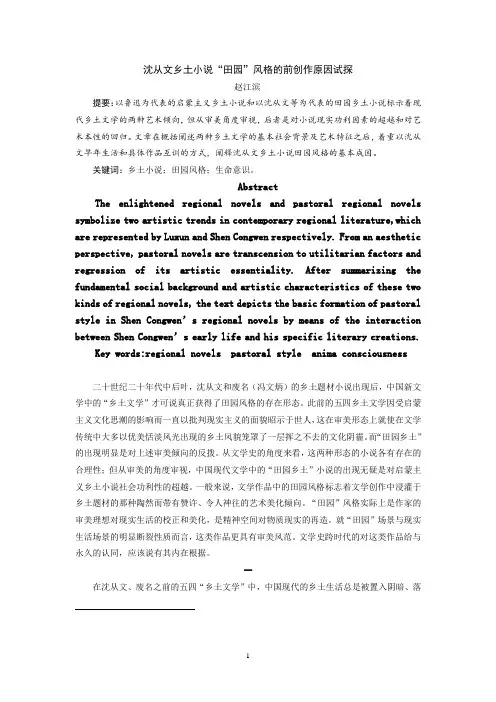
沈从文乡土小说“田园”风格的前创作原因试探赵江滨提要: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乡土小说和以沈从文等为代表的田园乡土小说标示着现代乡土文学的两种艺术倾向,但从审美角度审视,后者是对小说现实功利因素的超越和对艺术本性的回归。
文章在概括阐述两种乡土文学的基本社会背景及艺术特征之后,着重以沈从文早年生活和具体作品互训的方式,阐释沈从文乡土小说田园风格的基本成因。
关键词:乡土小说;田园风格;生命意识。
AbstractThe enlightened regional novels and pastoral regional novels symbolize two artistic trends in contemporary regional literature,which are represented by Luxun and Shen Congwen respectively. From an aesthetic perspective, pastoral novels are transcension to utilitarian factors and regression of its artistic essentiality. After summarizing the fundamental social background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wo kinds of regional novels, the text depicts the basic formation of pastoral style in Shen Congwen’s regional novels by mean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hen Congwen’s early life and his specific literary creations.Key words:regional novels pastoral style anima consciousness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叶,沈从文和废名(冯文炳)的乡土题材小说出现后,中国新文学中的“乡土文学”才可说真正获得了田园风格的存在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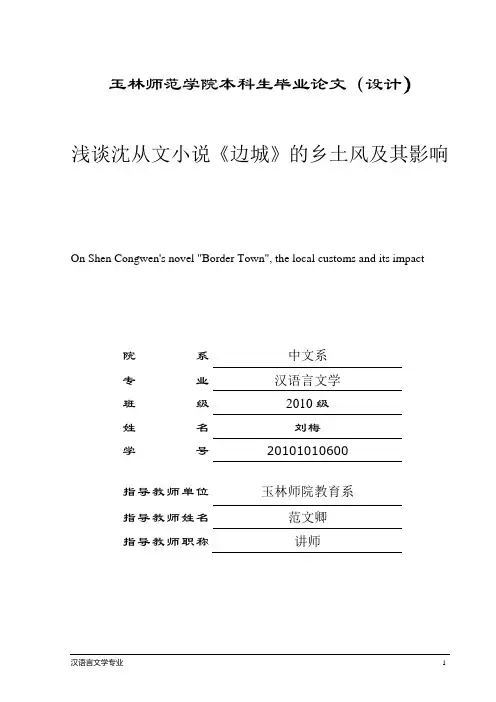
玉林师范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浅谈沈从文小说《边城》的乡土风及其影响On Shen Congwen's novel "Border Town", the local customs and its impact院系中文系专业汉语言文学班级2010级姓名刘梅学号20101010600指导教师单位玉林师院教育系指导教师姓名范文卿指导教师职称讲师目录封面 (1)中文论文标题 (2)中文摘要 (3)中文关键词 (4)论文正文 (5)注释 (6)参考文献 (7)英文论文标题 (8)英文摘要 (9)英文关键词 (10)作者签名浅谈沈从文小说《边城》的乡土风及其影响汉语言文学刘梅指导老师:范文卿[摘要]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湖南乡土文学的杰出代表。
他的代表作《边城》,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
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出了绵延千里的沅水流域的风光;创造出了闪耀着纯真性格的人物,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营造出了淳朴和谐的社会气息;刻画出了湘西充满魅力的民俗。
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民风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后世作家的创作。
[关键词]民族特色;民俗民风;自然景物;影响湘西位于湖南西部,是云贵高原和雪峰山之间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被历代统治者称为“中国的盲肠”,也是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
沈从文这位从湘西土家苗族山寨走出的“乡下人”,用他手中的笔构筑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湘西世界”。
《月下小景》、《八骏图》、《长河》……无一不涂上“湘西”的标记,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1934年问世的《边城》。
它有如一幅美丽的自然山水画,一桢趣味盎然的湘西人情风俗画。
沈从文说:“我的作品稍稍异同于同时代的作家之处,在一开始写作时,取材的侧重在我的家乡,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流域。
从《边城》看沈从文小说的乡村文化价值取向贾德学【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解读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所建构的充满自然人性与牧歌情调的湘西世界,深入剖析沈从文独特的乡村文化价值取向,并从作者乡土出身、苗族血缘及其内心深处的文化自卑情结客观因素和他通过人性美的渴盼与呼唤来重塑民族文化品格理想的主观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沈从文独特乡村文化价值取向产生的根源,阐明沈从文在湘西乡土世界中营建的“人性小庙”在激发人们对真善美和纯洁人性的呼唤追求中的积极现实意义。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乡村文化;价值取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无疑是最具独立意识和独特风格的作家之一。
他的整个小说创作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心理倾斜:对乡下人热情和对城里人讥讽,并且以城乡对峙的结构构成了其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在这里,作者通过塑造在纯净的大自然中生活的16岁的翠翠、河边的老艄公、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等一系列富有神性之光的理想人物,努力建构了一个充满自然人性与牧歌情调的湘西世界,在这个远离都市、富有诗意的世外桃源中,流露出一代文豪沈从文钟情于乡村的文化价值取向,寄寓着他尊崇人性、追求真善美的人生理想。
一、《边城》是寄寓着作者审美观念和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边城》是沈从文发表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代表作。
作品描写了一位驾船老人和他的外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的生活,以及当地掌水码头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翠翠以致酿为悲剧的故事。
作者以清丽的笔触,讲述了一个哀婉而美丽的爱情故事。
全篇在一种远离都市喧嚣的古朴宁静的氛围中展开,真实地再现了湘西边境的山城茶峒的优美自然风光、恬静的生活画面、古朴的民情风俗,使《边城》成为寄寓着作者对“生命”、“美”、“爱”等人生理想执着追求的世外桃源。
1、《边城》的美,首先在于它给我们展示了湘西秀丽迷人的自然风光。
小说中所描绘的山城茶峒依山傍水,有蜿蜒如长蛇的城墙,湾泊着小小篷船的码头,山民们住着半水半陆的吊脚楼,一切都极富湘西地域特色。
《边城》课文赏析《边城》课文赏析“边城”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是他远离“边城”而作于都市的梦。
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边城》课文赏析,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边城》课文赏析《边城》是沈从文美丽而带点伤感的恋乡梦,是沈从文理想的世界,诗意的世界。
边城的人民,诗意地生活,诗意地栖居。
《边城》进述的是一个哀婉而凄美的爱情故事: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
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
他们热情助人、纯朴善良。
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了当地船总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下情苗。
傩送的哥哥天保喜欢上美丽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
而地方上的王团总也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
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做个摆渡人。
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
天保知道翠翠喜欢傩送,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
傩送觉得自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抛下翠翠出走他乡。
外公为翠翠的婚事操心担忧,在风雨之夜去世。
留下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小说以翠翠的爱情悲剧作为线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湘西地方的风情美和人性美。
沈从文以如椽巨笔,为我们绘就了一幅如诗如画、如梦如烟、田园牧歌式的美丽的湘西世界。
沈从文在后来曾经表白:“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小说以牧歌式的情调描绘出田园诗般的边城世界。
这里的人民保持着淳朴自然、真挚善良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他们诚实勇敢、乐善好施、热情豪爽、轻利重义、守信自约,“凡事只求个心安理得”,就连吊脚楼****的性情也浸染着边民的淳厚,俨然是一个安静的平和的桃源仙境。
这里的人民,诗意地生活,诗意地栖居。
这是抒情诗,也是风俗画。
《边城》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显然受到中国传统艺术写意传神笔法较深的熏陶,它的人物更具东方式的恬静的美,如翠翠是湘西山川灵气化育而成的自然之女,天真、纯洁、活泼,柔情似水:翠翠在风吹日晒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
论田园风格是如何构建的——以《边城》为例摘要:沈从文的《边城》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文学评论家进行研究和解读。
有的学者研究其中的民俗文化,有的研究其中的写作手法,还有的则研究它的影响。
田园风格的构建是《边城》一大特色,作者在描写中注重环境,轻人物、故事的叙述手法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关键词:《边城》;构建技巧;环境中国文人大多具有田园情结,几乎每个诗人心中都有一个充满乡土气息,风景如画的“桃花源”。
在那里他们可以畅所欲言,在那里他们可以吟诗作画,在那里他们可以感受田间乐趣。
陶渊明的一首《饮酒·其五》,让世人感知到他内心的恬适,一篇《桃花源记》让世人体会到他对美好宁静生活的向往;唐代杜牧的《清明》让人身临其境,感受清明时节小村庄的朦胧美;宋代著名才子苏东坡也是如此,他虽放荡不羁,文风豪迈,但依然逃脱不了那田园情结的束缚,一首《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让人沉醉于西湖之美。
与此同时在《红楼梦》的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宝玉机敏动诸宾”中,曹雪芹就通过贾宝玉之口将“稻香村”布局在大观园中,是否是因为曹雪芹有田园情结,才有“稻香村”呢?一《边城》中田园风格的构建(一)田园小说与抒情小说抒情小说,有两类,一类是激情小说,一类是田园小说。
激情小说更注重作者情感的宣泄,如:《野草》《凤凰涅槃》。
田园小说则擅长用意境来暗示感情,《边城》就是如此。
沈从文善于用多种笔墨写小说,被认为是文体作家,有文体“魔术师”的称呼。
他所写的《边城》,田园风格构建技巧纯熟,所表达的感情真挚美好。
(二)重视环境田园小说在文体上,重环境而轻人物、故事,环境由山水和风俗组成。
又因为日常生活的诗意化,田园小说注重风俗民情。
在《边城》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茶峒”这个小山城。
1 茶峒的环境(1)它位于哪儿——“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
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2)它四周的环境怎么样——“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一面,城墙俨然如一长蛇……”(3)它有什么——“这地方城中只驻扎一营由昔年绿营屯丁改编而成的戍兵,及五百家左右的住户。
解析:沈从文《边城》的乡土精神家园情结文/郑地引导语:古往今来,无论历史的风尘如何湮灭,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洗涤,总有这样一句话回荡在我们的耳畔:家乡是每个人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
是啊,蔚蓝的天空,白云依旧流淌;汹涌的大海,礁石依旧站立;纷繁冗杂的尘世,我们依旧坚守,坚守我们的精神家园,那是一份淡泊,一份宁静,一份心底的欢唱,一份永恒的情结。
1923年沈从文为追寻新的生活和理想走出了湘西来到了北京。
久居都市,他对城市争权夺利的政治内幕和文明道德掩饰下的病态人生体察越来越深,对健康质朴自在自为的故乡湘西的一切越是感到眷恋和依恋。
由于造化的帮助,一双刚从洞穴中出来的原始初民的眼光被沈从文获得了,这眼光,不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干扰破坏,因此他笔下保留了湘西世界封存在原始自然状态的原汁原味。
沈从文在这荒疆边地,搜新捕怪,志异猎奇,所写种种,皆是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阅历。
沈从文是现代人,却来自半原始状态的湘西,瑶曲和神话在这里还是鲜活的,支配着居民的心理和生活方式。
统观沈从文的创作可以发现:在沈从文的情感倾向中,鄙视嘲讽都市文明人病态人生,礼赞远离现代文明的古朴村镇村民原始的道德风尚,这种浓挚的质朴性原始主义情结大都凝聚在他的《边城》小说中。
如果说沈从文笔下流泻的是一曲曲边地牧歌的话,那么《边城》则是其中最优美悠扬的乐章。
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究竟具有怎样原始诱人的风光风情?首先是美丽、恬静、和谐的人与自然。
“边城”是一座美丽的小城,依山傍水自然形成,山是高山,水是碧水。
傍城有一条小溪缓缓流淌,溯流而上,依旧是碧波涟涛绿水青山还有桃杏花里的人家,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如同流淌的溪水一样安详、清明。
男子在屋前劈柴,女人穿了自家织就而又浆洗得极硬的土蓝布衣裳,“在日光下一面做事,一面说话,一切永远那么寂静,所有的人每个日子都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
这里有梦有期待而更多地是顺其自然,老船夫在这种安详和期待中过着每一个时日,从二十几岁直到死去一直尽心的守着渡口迎来送往,甚至对女儿的死他也不怨天尤人。
沈从文《菜园》与他其他小说的写作风格有些不一样,小说写的是悲剧故事,但整个作品却用抒情的笔调来大肆渲染美的景色和美好人性,使得小说更加加剧了悲剧感,从而达到文本的立体效果。
本站精心为大家整理了浅析沈从文的《菜园》写作意境,希望对你有帮助。
浅析沈从文的《菜园》写作意境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一贯淡化情节,营造美的意境,小说《菜园》也不例外。
《菜园》说的是几个有涵养、守住美好道德的小人物,在时代的腥风血雨里,走上不归路的故事。
小说中的“儿子”和漂亮的“儿媳”因为政治变故被无情地杀戮,三年后悲恸的母亲也自缢身亡。
文本中没有满纸的血和泪,却充满美的意境和美的人性,其中透着一缕淡淡的哀愁,让小说读来如一首抒情诗回味无穷,余音袅袅。
中国的古代文学传统讲究诗歌的“意境”,即艺术创作所追求的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境界。
在现代小说里,意境同样可以作为重要构成元素,用来渲染人物、增强艺术感染力。
中国一些现代作家都自觉地将诗歌写作的这一技巧运用到小说创作中去,比如废名、沈从文等现代作家。
《菜园》也是沈从文的一篇较为特别的作品。
这位自诩只想建造“人性的希腊小庙”的“乡下人”,从小看惯了故乡土著军阀和土匪的残忍的杀戮,而故土湘西的风土人情在其笔下是那么温馨、可人。
20年代末30年代初,寓居于北京的沈从文在艰辛的生活里挣扎,湘西成了他精神的寄托。
《菜园》一开始,作者对人物的家世故作轻松地娓娓道来,接着无限深情地描绘这菜园优美的田园风光,诗的韵味慢慢铺展开来,菜园的景致仿佛是世外桃源一般:“两人常常沉默着半天不说话,听柳上晚蝉拖长了声音飞去,或者听溪水声音。
溪水绕菜园折向东去,水清见底,常有小虾、小鱼,鱼小到除了看玩就无用处。
那时节,鱼大致也在休息了。
”“动风时,晚风中必混有素馨兰花香和茉莉花香。
菜园中原有不少花木的。
在微风中掠鬓,向天空柳枝空处数点初现的星,做母亲的想着古人的诗歌,可想不起谁曾写下形容晚天如落霞孤鹜一类好诗句。
又总觉得有人写过这样恰如其境的好诗,便笑着问那个男子,是不是能在这样情境中想出两句好诗。
沈从文小说中的田园视景与抒情性问题吴晓东【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专题号】J3【复印期号】2009年04期【原文出处】《小说评论》(西安)2008年6期第56~61页【英文标题】The Pastoral Scene and the Lyricism in Shen Congwen’s Fiction【作者简介】吴晓东,北京大学中文系。
一、湘西的田园视景及其自我颠覆性沈从文创作中被研究者讨论最多的是他精心营造的湘西世界,其典型特征是自然、人性与美。
关于这个湘西世界最新的言说是作家林斤澜:“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呢?他拜美为生命,供奉人性,追求和谐。
他投奔自然,《边城》的翠翠就是水光山色,爷爷纯朴如太古,渡船联系此岸和彼岸,连跟进跟出的黄狗也不另外取名,只叫做狗。
”①在林斤澜的理解中,湘西世界是太古一般充满和谐之美与自然人性的田园世界,这个田园世界同时也生成了沈从文的文体形式——一种牧歌的或者说是田园诗的文体。
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即突出强调沈从文所自创的一种“牧歌式文体”,并认为“沈从文的文体和他的‘田园视景’是整体的,不可划分的,因为这两者同是一种高度智慧的表现,一种‘静候天机,物我同心’式创造力(negarive capability)之产品。
能把一棵树的独特形态写好、能把一个舟子和一个少女朴实无华的语言、忠厚的人格和心态历历勾画出来,这种才华,就是写实的才华”②。
夏氏的上述分析,把文体风格与“田园视景”勾连在一起,并挖掘背后的东方式智慧,最后落实到写实的才华,堪称对沈从文笔下田园牧歌世界最具经典性的理解。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沈从文的确具有在湘西世界中谱写田园牧歌的主导创作动机,这种主导动机到了沈从文创作《边城》时期更趋于自觉。
《边城》的大部分篇幅都符合经典的田园诗写作模式。
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中曾经对经典的田园诗模式有这样的界定:“田园诗里时间同空间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生活及其事件对地点的一种固有的附着性、粘合性,这地点即祖国的山山水水、家乡的岭、家乡的谷、家乡的田野河流树木、自家的房屋。
田园诗的生活和生活事件,脱离不开祖辈居住过、儿孙也将居住的这一角具体的空间。
”“田园诗中不同世代的生活(即人们整个的生活)所以是统一的,在多数情况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点的统一,就是世世代代的生活都一向附着在一个地方,这生活中的一切事件都不能与这个地方分离。
……地点的统一导致了一切时间界线的淡化,这又大大有助于形成田园诗所特有的时间的回环节奏。
”③《边城》即表现出“生活及其事件对地点的一种固有的附着性、粘合性”,小说叫《边城》而不叫《翠翠》,也不叫《翠翠、爷爷和黄狗》,这固然与沈从文曾经计划陆续写作“十个城”的故事有关,但从田园牧歌的原型性上说,选择“边城”作为主题,显然使小说涵容了更开阔的叙述空间。
巴赫金所谓“田园诗所特有的时间的回环节奏”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这种时间的回环节奏首先表现为沈从文小说中所习用的恒常叙事,即叙述湘西世世代代的生活中一以贯之的常态化的场景,借以勾勒长久不变的恒定感④。
譬如《长河》:六月尝新,必吃鲤鱼,茄子,和田地里新得包谷新米。
收获期必为长年帮工酿一大缸江米酒,好在工作之余,淘凉水解渴。
七月中元节,作佛事有盂兰盆会,必为亡人祖宗远亲近戚焚烧纸钱……。
八月敬月亮,必派人到镇上去买月饼,办节货,一家人团聚赏月。
“三个分句分叙的六、七、八月农家主要生活样式,在‘必’的约束下,变成铁打一般不可动摇的规律,凝固在生生不息的时间流动之中。
”⑤《边城》中更精心设计的“时间的回环节奏”还表现为节庆的复现,小说第三章这样交代节日在边城所充当的特殊角色:“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过年,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能成为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
”正因如此,作者选择了端午和中秋作为小说主要情节发生的时节,叙事者讲述的进行时中的故事发生在当下的端午,第四章又回溯两年前的端午发生在翠翠和傩送身上的故事,男女主人公的记忆便与端午节联系在一起。
这种节日的复现,既为人物的活动确定了核心的时间关节点,也有助于营造具有地域色彩的民俗环境和背景,凸现了民间节庆在乡土生活中重要性。
边城世界的深厚蕴涵正凝聚在风俗、节庆之中,年复一年的节日维系的是边城世界的秩序感、恒常感以及与过去世代的连续感。
正有赖于这种地点的统一性与时间的回环节奏,湘西的田园视景在《边城》中才获得了沈从文创作中前所未有的完整性与自足性。
而《边城》在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在于,它使沈从文此前在其它湘西题材的小说中尚显零散化的田园视景一举获得了整体性和统一性,进而使湘西世界获得了一个文化幻景意义上的整体图式。
如果说在其它湘西小说中,沈从文的田园视景还由于题材以及作者价值意向的不同而具有一种差异性,但由于《边城》的出现,湘西世界以往的内部的差异性则开始服从于这一田园视景的整体图式。
而正是从田园视景的整体性这个意义上说,在《边城》中最后定型的湘西世界的意义才无比重大,田园视景也才有了诗性乌托邦的意义。
但是,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沈从文的田园视景必然具有一种先天不足。
因为现代社会无法容纳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桃花源。
一切现代的田园牧歌与乌托邦图景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虚构的幻美性。
这使《边城》毕竟不同于传统的田园诗。
与传统田园牧歌中永恒的时间性构成区别的是,《边城》中无法祛除偶然性的线性时间元素的介入。
如果说《边城》前两章的恒常叙事部分更趋于中国传统的静态的山水画,那么,一旦进入了展开具体情节的叙事流程,小说就进入了线性时间的具体性与一次性,进入了动态的日常生活和现代历史。
所以作为节庆的端午和中秋的意义在小说中就发生了转变,节日的功能就从民俗学图景的恒常展示,转为替主人公的生命活动提供场景,小说的重心也就由民俗学展览进入了具体人生的写相,从永恒的民俗学时间转入进行与流逝中的现代历史时间。
偶然性时间因素的介入,因此使故事时间具有了具体性,事件也具有了一次性。
小说结尾部分爷爷的死亡和白塔的倒掉都是线形时间中不可重复的事件,尤其是《边城》那个著名的结尾,使小说以及边城世界开始向未来时间敞开,从而使时间有了单线性,而不再呈现节日时间的回环性节奏: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
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在这个意义上说,偶然性时间的介入,标志着边城牧歌图景开始变得复杂化。
偶然性的时间因素给《边城》的叙事带来了不可确知性,也带来小说结尾的开放性。
这种结尾的开放性标志着《边城》这部小说现代视域的生成。
现代小说结尾与传统意义上的故事结局的最大区别就是现代小说更迷恋一种非确定性。
本雅明在他著名的文章《讲故事的人》中指出:“童话总这样说:‘从此他们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
’”⑥这就是童话的惯常的大团圆终结,这种大团圆终结同时也意味着时间性和可能性的终结,当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之后,也就意味着关于童话故事的主人公讲故事人已经无话可说了。
而现代小说的结尾则以卡夫卡为典型:“卡夫卡是那种注定无结尾的文学的代表。
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有如摩西,永远看不到乐土。
布朗肖说,不可能结尾,就是不可能在作品中死亡,不可能通过死亡自我解脱。
”⑦小说的不可能结尾正对应着终结的不可能性。
而现代性是指向未来的乌托邦,现代小说的终结也必然处在时间的远方。
当《边城》的结尾把偶然性的时间因素引入田园视景,也就把现代性的维度引入小说,小说的结尾也必然是指向未来的,开放的,无法在现世兑现的。
这种不确定性本身最鲜明地表现了小说的现代本性。
因此,《边城》的叙事是一个时间的现代性乃至历史性逐渐凸现的过程。
《边城》临近结尾即已显露变徵之音,借用沈从文习用的语汇,小说开始由“常”入“变”,即从乌托邦的恒常性进入到生命的变动不居的一次性。
从开放性结尾的角度说,《边城》表现出一种意义图式的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还体现在《边城》中的田园视景的自我颠覆性。
《边城》的意义既生成于牧歌秩序本身,也生成于这一秩序的被质疑。
郑树森即指出:“沈从文的田园模式,其实暗示强力,城乡之间,文明和原始之间,对比对立,而其笔调既有反讽,又有哀伤。
”⑧所以《边城》不单呈现了一个纯粹的田园视景,其中的“所说”和“所示”之间有天然的缝隙。
《边城》的牧歌倾向也与自身的颠覆性指向并存。
“所说”(牧歌)与“所示”(内部的自我分裂)互相纠葛冲突,展示了一个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图景。
这种自我分裂迹象在沈从文此前的小说《灯》中已经包含了,当《灯》的结尾男主人公不经意间透露出那个忠心耿耿的老仆人的故事是一个虚构的时候,其湘西视景已然面临被颠覆的危险。
在此,沈从文自己暴露了小说的虚构性,在某种意义上就不啻一种冒险:湘西世界的真实形态的瓦解的风险。
小说结构内部由此暴露出了缝隙和断裂,冲击着田园叙事和牧歌图景的单一性指向,意味着湘西世界内部依然包孕着田园视景的“他者”——现代性。
所以,《边城》是有内在的缝隙的。
杰姆逊称“史诗话语里的形式和内容、词语和对象之间已经存在着一种基本的构成性的断裂”⑨。
《边城》中的田园诗的话语方式与真正的对象的本来样态之间也正存在着这种断裂。
田园牧歌生成的同时也蕴涵了被颠覆的因子。
正如王德威对沈从文的断言:“他的叙事既是对田园牧歌的逼真再现,但同时也使之土崩瓦解。
”⑩二、“牧歌”是怎样叙述出来的从修辞的层面具体讨论沈从文笔下田园视景的生成,有助于我们感受湘西田园牧歌的人工性。
我们要问的问题因此就转换为:沈从文笔下的“牧歌”是怎样被叙述出来的。
其一是“自然化”。
王德威在分析沈从文的小说《柏子》时曾对“自然”和“自然化”两个范畴进行了如下区分:“对于这个故事的复杂性的诠释方法之一,是区分‘自然’(nature)与‘自然化’(naturalization)的观念。
我们在阅读沈的抒情叙事时经常将前者视为理所当然,相对于此,后者则表达了沈在描绘现实时的修辞与观念策略。
在这里,‘自然’指的是未经污染的理想源泉,而‘自然化’则指的是将历史流变化作天长地久的文化/意识形态范式。
”“我所关心的是更为‘文学性’的问题:……他如何把本来事出有因、决不‘自然的’主题、现象写得‘自然’而然起来,以及他又如何在这样的‘自然’书写时,设下疑影或留了裂隙,从而把看来清朗的文体交织得极尽复杂微妙。
”(11)对“自然”和“自然化”的区分使我们意识到,许多看上去是“自然”的东西,其实都是人为的“自然化”的结果,其中就有不自然的成分。
而关键是沈从文对自己的这种“自然化”的过程是相当自觉的。
在《一个人的自白》中,沈从文透露了自己创作中的重要的叙事策略:“作品中的乡土情感,混和了真实和幻念,而把现实生活痛苦印象一部分加以掩饰,使之保留童话的美和静,也即由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