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
- 格式:ppt
- 大小:304.50 KB
- 文档页数: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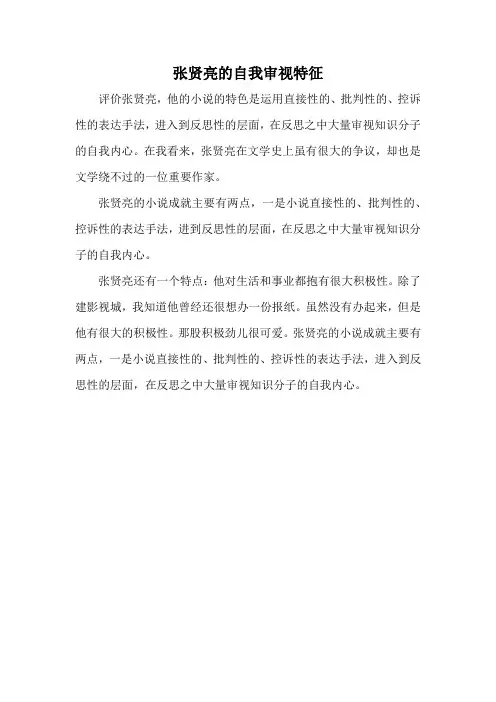
张贤亮的自我审视特征
评价张贤亮,他的小说的特色是运用直接性的、批判性的、控诉性的表达手法,进入到反思性的层面,在反思之中大量审视知识分子的自我内心。
在我看来,张贤亮在文学史上虽有很大的争议,却也是文学绕不过的一位重要作家。
张贤亮的小说成就主要有两点,一是小说直接性的、批判性的、控诉性的表达手法,进到反思性的层面,在反思之中大量审视知识分子的自我内心。
张贤亮还有一个特点:他对生活和事业都抱有很大积极性。
除了建影视城,我知道他曾经还很想办一份报纸。
虽然没有办起来,但是他有很大的积极性。
那股积极劲儿很可爱。
张贤亮的小说成就主要有两点,一是小说直接性的、批判性的、控诉性的表达手法,进入到反思性的层面,在反思之中大量审视知识分子的自我内心。

张贤亮《绿化树》读书笔记《绿化树》这部中篇小说,是当代作家张贤亮的代表作之一,首次发表于《十月》1984年第二期。
作品以第一人称“我”为主线,真实地叙述了“文革”中的知识分子被流放到西北地区后的独特经历。
作者通过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描写,深入思考与解读了饥饿、性饥渴和精神世界的困顿等问题,展现了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的苦难遭遇。
这部小说使用现实主义手法,兼具浪漫主义诗情,真实而艺术地再现了特定的时代图景。
小说的主角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名字,这使得读者可以将自己,或者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遭遇与心境投射到这个角色上。
主角在流放之地,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知识分子的尊严,去做各种粗活重活,甚至与牲口争夺食物。
他的生存本能被极度地激发出来,但同时,他的精神世界也在苦难中得到了升华。
从某个角度看,《绿化树》可以看作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寓言。
知识分子在苦难中学会了与自己的心灵对话,发现了生活中最简单却也最珍贵的乐趣。
例如,当他吃到马缨花为他准备的带着一点点肉的骨头时,他感到“一股暖流从心里流过,在我全身激起了无比的幸福感和力量。
”这一点点的肉,带给了他无比的幸福和力量,也是他在极度困境中的一种慰藉。
在小说中,食物不仅仅是满足饥饿的工具,更成为了一种情感的载体。
主角与马缨花、谢队长、海喜喜等人的交往中,食物成为了一种传递情谊的媒介。
这种情感是纯粹的、不带任何杂质的。
例如,当海喜喜知道主角需要食物时,他没有选择用金钱交易,而是将食物赠予主角。
这种无私的援助让主角深受感动,也让读者感受到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简单而纯粹。
没有太多的利益纷争,没有太多的复杂情感。
人们更愿意用真诚的态度去对待彼此。
这一点在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马缨花、谢队长、海喜喜等人对待主角的态度是真诚的,他们愿意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
这部小说不仅仅是对知识分子遭遇的写照,更是对人性的一种探索。
在极端的困境中,人们会展现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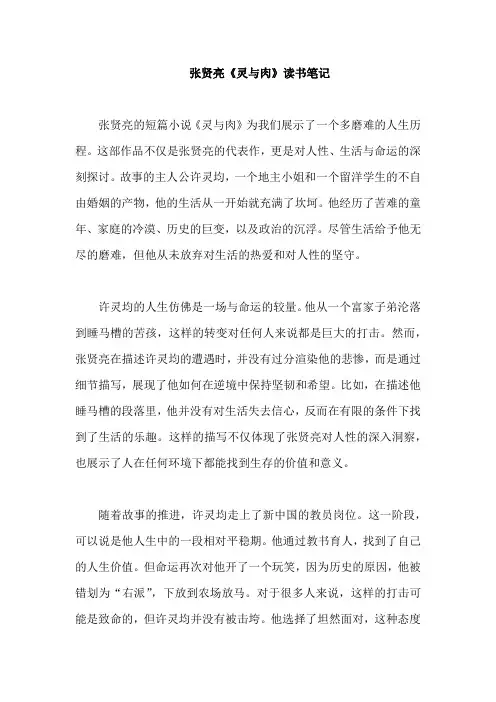
张贤亮《灵与肉》读书笔记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多磨难的人生历程。
这部作品不仅是张贤亮的代表作,更是对人性、生活与命运的深刻探讨。
故事的主人公许灵均,一个地主小姐和一个留洋学生的不自由婚姻的产物,他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坎坷。
他经历了苦难的童年、家庭的冷漠、历史的巨变,以及政治的沉浮。
尽管生活给予他无尽的磨难,但他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坚守。
许灵均的人生仿佛是一场与命运的较量。
他从一个富家子弟沦落到睡马槽的苦孩,这样的转变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
然而,张贤亮在描述许灵均的遭遇时,并没有过分渲染他的悲惨,而是通过细节描写,展现了他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坚韧和希望。
比如,在描述他睡马槽的段落里,他并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反而在有限的条件下找到了生活的乐趣。
这样的描写不仅体现了张贤亮对人性的深入洞察,也展示了人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找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随着故事的推进,许灵均走上了新中国的教员岗位。
这一阶段,可以说是他人生中的一段相对平稳期。
他通过教书育人,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但命运再次对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历史的原因,他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农场放马。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样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但许灵均并没有被击垮。
他选择了坦然面对,这种态度既是对命运的抗争,也是对自我价值的坚守。
《灵与肉》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命运史,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通过许灵均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下人们的无奈和坚韧。
张贤亮并没有刻意去美化或者美化那个时代,而是真实地呈现了那个时期人们的真实生活状态。
这种真实感使得这部小说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张贤亮作为一位文学家,他自己的生活也充满了坎坷。
他因为各种政治原因多次受到打压和迫害,甚至在监狱中度过了很长时间。
这些经历无疑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灵与肉》中的许灵均,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张贤亮自身的写照。
两人都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但都选择了坚守和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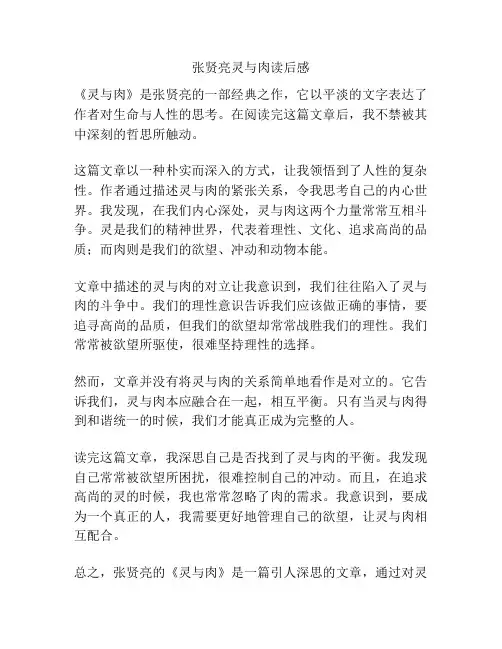
张贤亮灵与肉读后感
《灵与肉》是张贤亮的一部经典之作,它以平淡的文字表达了作者对生命与人性的思考。
在阅读完这篇文章后,我不禁被其中深刻的哲思所触动。
这篇文章以一种朴实而深入的方式,让我领悟到了人性的复杂性。
作者通过描述灵与肉的紧张关系,令我思考自己的内心世界。
我发现,在我们内心深处,灵与肉这两个力量常常互相斗争。
灵是我们的精神世界,代表着理性、文化、追求高尚的品质;而肉则是我们的欲望、冲动和动物本能。
文章中描述的灵与肉的对立让我意识到,我们往往陷入了灵与肉的斗争中。
我们的理性意识告诉我们应该做正确的事情,要追寻高尚的品质,但我们的欲望却常常战胜我们的理性。
我们常常被欲望所驱使,很难坚持理性的选择。
然而,文章并没有将灵与肉的关系简单地看作是对立的。
它告诉我们,灵与肉本应融合在一起,相互平衡。
只有当灵与肉得到和谐统一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成为完整的人。
读完这篇文章,我深思自己是否找到了灵与肉的平衡。
我发现自己常常被欲望所困扰,很难控制自己的冲动。
而且,在追求高尚的灵的时候,我也常常忽略了肉的需求。
我意识到,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我需要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欲望,让灵与肉相互配合。
总之,张贤亮的《灵与肉》是一篇引人深思的文章,通过对灵
与肉的对立与统一进行描述,使我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它让我意识到,灵与肉的平衡是我们成为完整人的重要条件,只有当我们找到这种平衡,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真正意义上的活得更加有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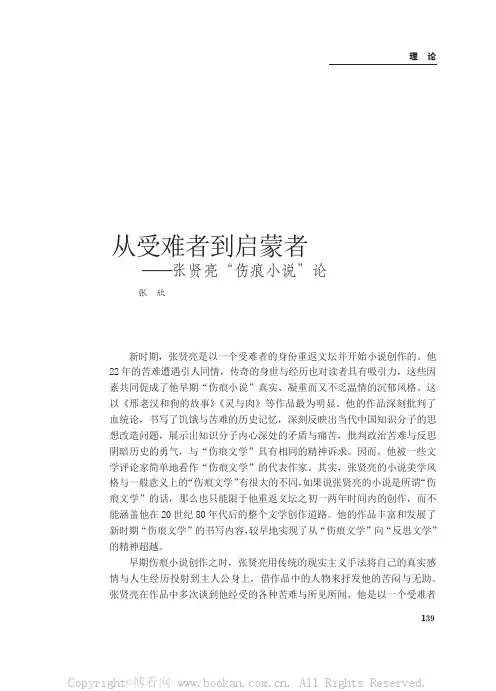
从受难者到启蒙者 ——张贤亮“伤痕小说”论 张 欣新时期,张贤亮是以一个受难者的身份重返文坛并开始小说创作的。
他22年的苦难遭遇引人同情,传奇的身世与经历也对读者具有吸引力,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他早期“伤痕小说”真实、凝重而又不乏温情的沉郁风格。
这以《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等作品最为明显。
他的作品深刻批判了血统论,书写了饥饿与苦难的历史记忆,深刻反映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展示出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矛盾与痛苦,批判政治苦难与反思阴暗历史的勇气,与“伤痕文学”具有相同的精神诉求。
因而,他被一些文学评论家简单地看作“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
其实,张贤亮的小说美学风格与一般意义上的“伤痕文学”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张贤亮的小说是所谓“伤痕文学”的话,那么也只能限于他重返文坛之初一两年时间内的创作,而不能涵盖他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整个文学创作道路。
他的作品丰富和发展了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书写内容,较早地实现了从“伤痕文学”向“反思文学”的精神超越。
早期伤痕小说创作之时,张贤亮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将自己的真实感情与人生经历投射到主人公身上,借作品中的人物来抒发他的苦闷与无助。
张贤亮在作品中多次谈到他经受的各种苦难与所见所闻,他是以一个受难者139的口吻来叙述这些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的。
因此,他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就显得格外真实,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从“反右”一直延续到“文革”的极左政治让张贤亮的诗人梦破碎了,他的青春岁月也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蹉跎。
母亲去世,他不能在堂前尽孝,由此产生的自责和愧疚之情缠绕、折磨着他,作家心底的伤痛之深是可想而知的。
这不但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剧。
因此,“伤痕文学”的出现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它是从创伤性的心理积淀中追寻导致创伤的社会历史生活的根由。
批评家在肯定这些小说政治立场的前提下,对张贤亮早期伤痕小说的艺术得失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例如,有评论家指出,“由于张贤亮同志的创作敢于解放思想,也就敢于冲破长期来只能歌颂不许暴露这个老框框”“作者并非为暴露而暴露,而是通过暴露来激发人们对于‘四人帮’的仇恨,对于党的热爱和对于四个现代化的向往与责任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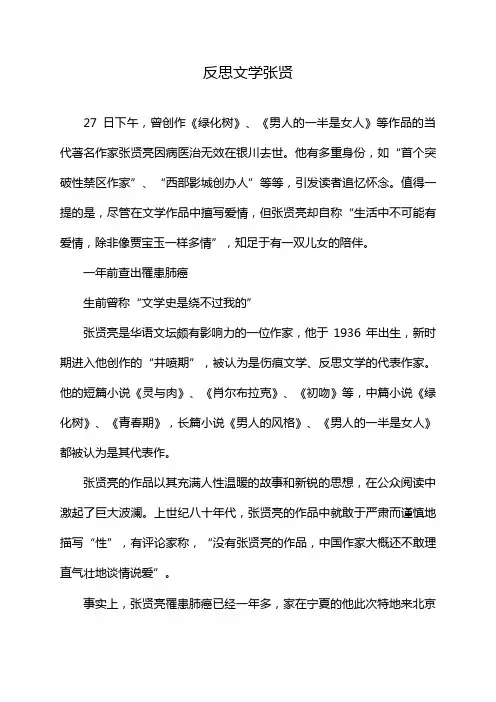
反思文学张贤27日下午,曾创作《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的当代著名作家张贤亮因病医治无效在银川去世。
他有多重身份,如“首个突破性禁区作家”、“西部影城创办人”等等,引发读者追忆怀念。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文学作品中擅写爱情,但张贤亮却自称“生活中不可能有爱情,除非像贾宝玉一样多情”,知足于有一双儿女的陪伴。
一年前查出罹患肺癌生前曾称“文学史是绕不过我的”张贤亮是华语文坛颇有影响力的一位作家,他于1936年出生,新时期进入他创作的“井喷期”,被认为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代表作家。
他的短篇小说《灵与肉》、《肖尔布拉克》、《初吻》等,中篇小说《绿化树》、《青春期》,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都被认为是其代表作。
张贤亮的作品以其充满人性温暖的故事和新锐的思想,在公众阅读中激起了巨大波澜。
上世纪八十年代,张贤亮的作品中就敢于严肃而谨慎地描写“性”,有评论家称,“没有张贤亮的作品,中国作家大概还不敢理直气壮地谈情说爱”。
事实上,张贤亮罹患肺癌已经一年多,家在宁夏的他此次特地来北京协和医院医治,但最终病情恶化辞世。
媒体引述作家冯骥才回忆称,“一年前,他查出了肺癌,当时已经是晚期,情况很不乐观。
最初得知消息的李小林(巴金之女)告诉了我,我当时就掉眼泪了,然后我慢慢静下来,觉得我首先得安慰他,就给他打电话,没想到他反过来还安慰我。
”老友高洪波则表示,今年3月份,罹患癌症的张贤亮来北京看病,“我们几个作家老朋友,包括张抗抗等,在北京相聚了一次,张贤亮半开玩笑地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但文学史是绕不过我的’”。
他透露,当时张贤亮吃中药过敏,身上痒得难受,但他很坚强,依然充满着对病的蔑视。
“当代文学史确实是绕不过他的。
不幸被他说中,我们真的是见了最后一面”。
“他发病发得很突然,前年十月我遇到他,他悄悄跟我讲了病情,我当时完全不相信,我觉得他在开玩笑,或是小题大做。
”作家梁晓声回忆,“我以为是一般的肺病,还嘲笑他。


张贤亮创作的艺术特点
张贤亮,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风哥》被划为“右派分⼦”,押送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2年。
1979年中共11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后创作⼩说、散⽂、评论、电影剧本,成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之⼀。
代表作品有:短篇⼩说《灵与⾁》《肖尔布拉克》等;中篇⼩说《⼟牢情话》《绿化树》等;长篇⼩说《男⼈的⼀半是⼥⼈》等。
张贤亮创作的特⾊:
(1)劳动妇⼥形象的进⼊,⼜使张贤亮的⼩说蕴含着浓浓的⼈情味,厚厚的真实感和活脱脱的⼈性化。
(2)意境与诗情。
意境和诗情在张贤亮⼩说中有机结合,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辩证的统⼀起来,也就是⽤⾮现实主义艺术提供的某些审美潜能来丰富⾃⼰的表现⼿法,完善起作品的审美内涵,从⽽客观上达到积极的审美效果。
(3)雅⾔与俗语。
张贤亮⾃⼰讲过,他使⽤的语⾔,“要洋就洋到家,要⼟就⼟到家”。
因此雅⾔和俗语这两类⽂学语⾔区分的这样鲜明⽽⼜结合得这样融洽,这就使张贤亮的⼩说在语⾔上具有了雅俗相济的宽阔风貌。

张贤亮生活糜烂
张贤亮,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名人,如今却陷入了生活的糜烂之中。
曾经的他是一个备受瞩目的明星,拥有无数的粉丝和赞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生活却变得越来越糜烂。
曾经的张贤亮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激情的年轻人,他在娱乐圈中闯荡多年,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竞争的加剧,他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
一时间,他陷入了迷茫和失落之中,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生活的糜烂并不只是指他事业的失败,更多的是他个人生活的颓废和堕落。
他沉溺于酒精和荒淫的生活,放纵自己,不顾一切地追求快乐和享乐。
他的家庭关系也因此而破裂,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离他而去,让他陷入了更加深重的绝望之中。
然而,即使生活再糜烂,也总会有一丝希望的存在。
在最黑暗的时刻,张贤亮意识到了自己的堕落和沉沦,他开始努力改变自己,寻找新的生活方向。
他戒掉了酒精,重新振作起来,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努力寻找新的机会和发展空间。
慢慢地,张贤亮的生活开始有了转机,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重新赢得了家人和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
他开始过上了健康、积极的生活,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和目标。
张贤亮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生活再糜烂,也不要轻易放弃。
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但是重要的是要勇敢面对,努力寻找解决的办法,找到重新振作的力量。
生活中总会有转机和希望的存在,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境,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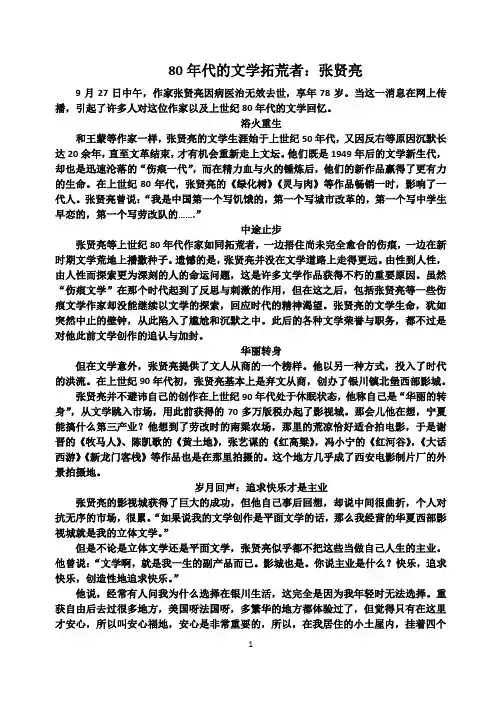
80年代的文学拓荒者:张贤亮9月27日中午,作家张贤亮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8岁。
当这一消息在网上传播,引起了许多人对这位作家以及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回忆。
浴火重生和王蒙等作家一样,张贤亮的文学生涯始于上世纪50年代,又因反右等原因沉默长达20余年,直至文革结束,才有机会重新走上文坛。
他们既是1949年后的文学新生代,却也是迅速沦落的“伤痕一代”,而在精力血与火的锤炼后,他们的新作品赢得了更有力的生命。
在上世纪80年代,张贤亮的《绿化树》《灵与肉》等作品畅销一时,影响了一代人。
张贤亮曾说:“我是中国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中途止步张贤亮等上世纪80年代作家如同拓荒者,一边捂住尚未完全愈合的伤痕,一边在新时期文学荒地上播撒种子。
遗憾的是,张贤亮并没在文学道路上走得更远。
由性到人性,由人性而探索更为深刻的人的命运问题,这是许多文学作品获得不朽的重要原因。
虽然“伤痕文学”在那个时代起到了反思与刺激的作用,但在这之后,包括张贤亮等一些伤痕文学作家却没能继续以文学的探索,回应时代的精神渴望。
张贤亮的文学生命,犹如突然中止的壁钟,从此陷入了尴尬和沉默之中。
此后的各种文学荣誉与职务,都不过是对他此前文学创作的追认与加封。
华丽转身但在文学意外,张贤亮提供了文人从商的一个榜样。
他以另一种方式,投入了时代的洪流。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张贤亮基本上是弃文从商,创办了银川镇北堡西部影城。
张贤亮并不避讳自己的创作在上世纪90年代处于休眠状态,他称自己是“华丽的转身”,从文学跳入市场,用此前获得的70多万版税办起了影视城。
那会儿他在想,宁夏能搞什么第三产业?他想到了劳改时的南梁农场,那里的荒凉恰好适合拍电影,于是谢晋的《牧马人》、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冯小宁的《红河谷》,《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作品也是在那里拍摄的。
这个地方几乎成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外景拍摄地。
第五节张贤亮林斤澜张贤亮,1936年生于南京,原籍江苏盱眙县,读初中时开始写诗,发表在《中国青年报》、《诗刊》、《星星》上,1955年中学毕业后任甘肃省委干部学校文化教员,`1957年发表长诗《大风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银川市南梁农场当农工。
1976年10月调农场学校当教员,开始重新发表作品,1981年4月调入宁夏文联从事专业创作。
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等。
有《灵与肉》等中短篇小说集数部,其中《灵与肉》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肖尔布拉克》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中篇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和《河的子孙》、《无法苏醒》,以及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
张贤亮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作家,他总是喜欢将自己苦苦思索的人生哲理融汇到作品之中。
从《灵与肉》开始,作者就试图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一个生活中的重大命题──知识分子在与体力劳动者的接触中,以及在他自身的体力劳动过程中所引起的一系列心灵变化究竟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
因此,他的作品理性色彩很浓,当然,这个理性色彩是建立在现实主义的感性生活的描写之上的。
《灵与肉》发表之后,张贤亮开始引起文坛关注。
这部作品明显地带着一种哲理的反思意味。
那时,文学尚未完全从“伤痕文学”中挣脱出来,作者就在思考怎样有意识地把这种种伤痕中能使人振奋、前进的那一面表现出来的命题。
小说描写一个受到20多年社会冷遇的右派许灵均在灵与肉的磨难中得以精神升华的故事。
一面是富豪的生身父亲的诱劝(它是一种金钱美女的享乐主义外力的象征);一面是患难与共的妻子与乡亲的善良(它是一种富有传统规范的真善美的伦理主义内驱力的召唤),许灵均最后终于坐着马车回到了大西北荒原上的那间用自己灵与肉筑成的小土屋里去了。
这是一首歌颂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赞歌,是对中华民族勤劳善良的优秀品质的礼赞;作者要讴歌的正是劳动创造人、劳动人民塑造知识分子优秀品格和真正灵魂的哲理。
120
中国作家书画院协办
作家手札张贤亮
张贤亮,国家一级作家、收藏家、书法家。
1936年生于南京,祖籍江苏盱眙县。
代表作:《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
立体文学作品:镇北堡西部影城、老银川一条街。
50年代初读中学时即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从北京移居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农场“劳动改造”长达二十二年。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后创作小说、散文、评论、电影剧本,成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之一。
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等职,并任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2014年9月27日因病去世,享年78
岁。
活在活着的人的心里,
就是没有死去。
作家手札。
张贤亮《河的子孙》读书笔记《河的子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作者张贤亮用他独特的笔触描绘了人与自然、命运与抗争之间的纠葛。
书中不仅展现了生活中各种不同的条件和形形色色的目的,更深入地挖掘了人们在各种命运中的抗争与选择。
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它成功地捕捉到了生活中瞬息万变的色彩。
人类的生活活动处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之下,每一个角色、每一个事件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动机。
这使得每个章节都充满了戏剧性,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五彩斑斓的大舞台,见证着各种情感和命运的交织。
其中,最触目的无疑是人的事业和意愿。
在张贤亮的笔下,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或勇敢、或迷茫、或坚定、或彷徨。
他们的选择和决策都与河的子孙——那些在河水中流淌的生命息息相关。
河,这一象征着生命之源和命运之流的意象,贯穿全书,成为串联起每个角色的线索。
书中的河不仅仅是一条物理意义上的河流,它更是时间和历史的见证者。
它目睹了人类的繁荣与衰落、战争与和平、欢乐与痛苦。
与此同时,河也成为了人们心灵的寄托和灵魂的归宿。
在河的怀抱中,人们找寻着自我,体验着生命中的波澜与平静。
而在这些变故和事件中,张贤亮没有忽视对人性深度的探索。
他通过描绘人们面对困境时的挣扎与选择,展现出人性的复杂与多面。
有时,人们因为追求自由和美丽而奋斗;有时,他们为了生存和欲望而妥协;甚至有时,缺陷和不幸也能激发出人们内在的力量和勇气。
这些情感和冲突在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鲜明,使读者对人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河的子孙》并不仅仅是一部描绘人与自然关系的小说。
它更深入地探讨了命运与抗争的主题。
在面对命运的波折时,人们如何坚守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困境与挫折?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隐藏在书中的字里行间。
这本书还给我留下了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它对悲剧美的刻画。
在张贤亮的笔下,悲剧并不只是令人痛心的结局,而是一种对生命真谛的领悟。
当人们在命运面前显得无力和渺小时,那种悲剧性的美更能引发读者对生命的思考和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