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学正统观念的特点_马小能
- 格式:pdf
- 大小:134.56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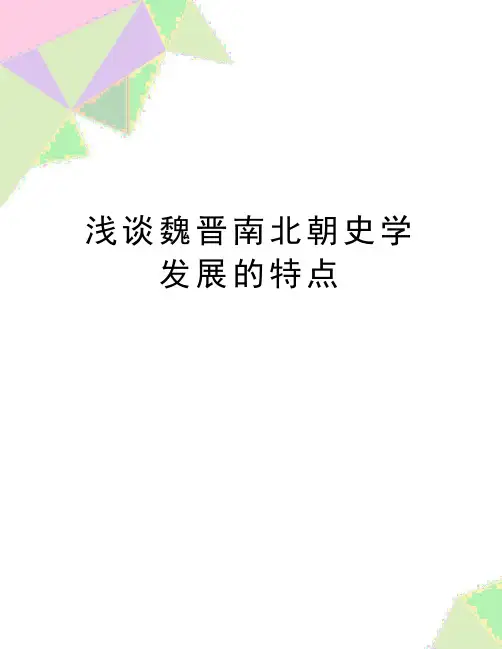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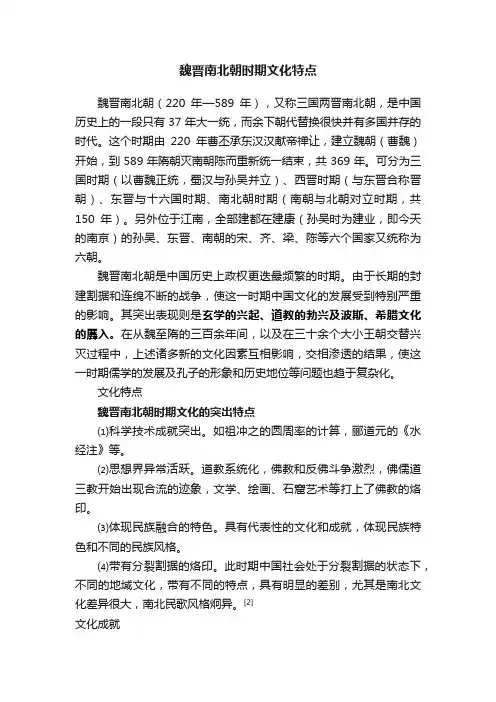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特点魏晋南北朝(220年—589年),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只有37年大一统,而余下朝代替换很快并有多国并存的时代。
这个时期由220年曹丕承东汉汉献帝禅让,建立魏朝(曹魏)开始,到589年隋朝灭南朝陈而重新统一结束,共369年。
可分为三国时期(以曹魏正统,蜀汉与孙吴并立)、西晋时期(与东晋合称晋朝)、东晋与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南朝与北朝对立时期,共150年)。
另外位于江南,全部建都在建康(孙吴时为建业,即今天的南京)的孙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等六个国家又统称为六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
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
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
在从魏至隋的三百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
文化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突出特点⑴科学技术成就突出。
如祖冲之的圆周率的计算,郦道元的《水经注》等。
⑵思想界异常活跃。
道教系统化,佛教和反佛斗争激烈,佛儒道三教开始出现合流的迹象,文学、绘画、石窟艺术等打上了佛教的烙印。
⑶体现民族融合的特色。
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和成就,体现民族特色和不同的民族风格。
⑷带有分裂割据的烙印。
此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下,不同的地域文化,带有不同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差别,尤其是南北文化差异很大,南北民歌风格炯异。
[2]文化成就宋元话本。
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
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转变。
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被后人奉为圭臬。
此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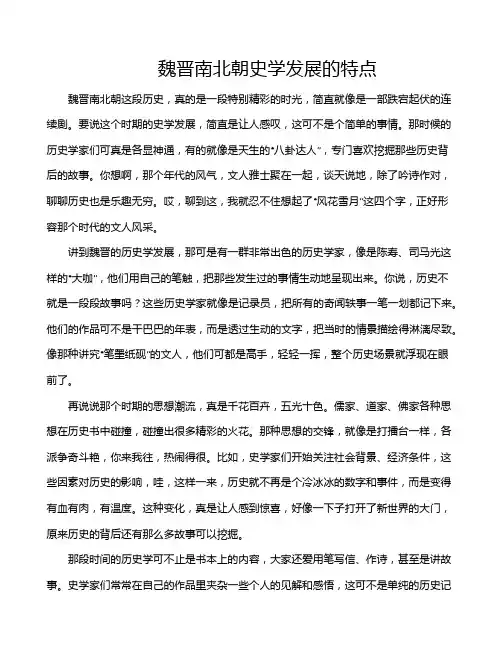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真的是一段特别精彩的时光,简直就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连续剧。
要说这个时期的史学发展,简直是让人感叹,这可不是个简单的事情。
那时候的历史学家们可真是各显神通,有的就像是天生的“八卦达人”,专门喜欢挖掘那些历史背后的故事。
你想啊,那个年代的风气,文人雅士聚在一起,谈天说地,除了吟诗作对,聊聊历史也是乐趣无穷。
哎,聊到这,我就忍不住想起了“风花雪月”这四个字,正好形容那个时代的文人风采。
讲到魏晋的历史学发展,那可是有一群非常出色的历史学家,像是陈寿、司马光这样的“大咖”,他们用自己的笔触,把那些发生过的事情生动地呈现出来。
你说,历史不就是一段段故事吗?这些历史学家就像是记录员,把所有的奇闻轶事一笔一划都记下来。
他们的作品可不是干巴巴的年表,而是透过生动的文字,把当时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
像那种讲究“笔墨纸砚”的文人,他们可都是高手,轻轻一挥,整个历史场景就浮现在眼前了。
再说说那个时期的思想潮流,真是千花百卉,五光十色。
儒家、道家、佛家各种思想在历史书中碰撞,碰撞出很多精彩的火花。
那种思想的交锋,就像是打擂台一样,各派争奇斗艳,你来我往,热闹得很。
比如,史学家们开始关注社会背景、经济条件,这些因素对历史的影响,哇,这样一来,历史就不再是个冷冰冰的数字和事件,而是变得有血有肉,有温度。
这种变化,真是让人感到惊喜,好像一下子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原来历史的背后还有那么多故事可以挖掘。
那段时间的历史学可不止是书本上的内容,大家还爱用笔写信、作诗,甚至是讲故事。
史学家们常常在自己的作品里夹杂一些个人的见解和感悟,这可不是单纯的历史记录,而是带着作者的情感与思想。
这就像你跟朋友聊天一样,不光是说事,还会带点个人的色彩,让整件事情更有趣、更贴近人心。
你读到那些文字,简直就像是在听老朋友的唠嗑,轻松自在,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人情味的时代。
不得不提的是,那个时代的书籍和文献的传播也开始有了新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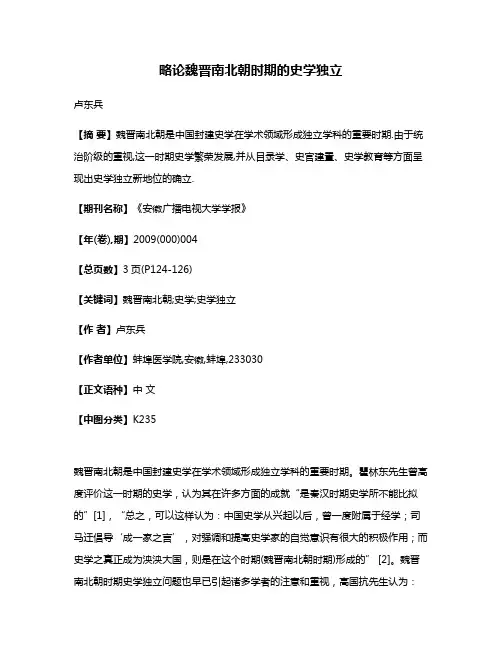
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独立卢东兵【摘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史学在学术领域形成独立学科的重要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重视,这一时期史学繁荣发展,并从目录学、史官建置、史学教育等方面呈现出史学独立新地位的确立.【期刊名称】《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年(卷),期】2009(000)004【总页数】3页(P124-126)【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史学;史学独立【作者】卢东兵【作者单位】蚌埠医学院,安徽,蚌埠,23303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35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史学在学术领域形成独立学科的重要时期。
瞿林东先生曾高度评价这一时期的史学,认为其在许多方面的成就“是秦汉时期史学所不能比拟的”[1],“总之,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史学从兴起以后,曾一度附属于经学;司马迁倡导‘成一家之言’,对强调和提高史学家的自觉意识有很大的积极作用;而史学之真正成为泱泱大国,则是在这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 [2]。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独立问题也早已引起诸多学者的注意和重视,高国抗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3]周一良先生在概括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时也指出这一阶段史学发展的第一个特点是史学的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
这也就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独立的学科。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第2辑,1987年。
史学成为独立学科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显著标志,而从目录学、史官制度、史学教育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这一时期的史学独立地位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史学繁荣发展的基本面貌魏晋南北朝370年,既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动乱时期,又是孕育着历史进步的变动时代。
这些都对史学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各个政权的统治者面对频繁的政权更替、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和尖锐激烈的阶级、民族矛盾,迫切需要借鉴前代王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也迫切需要宣扬本政权开国创业的伟绩,因而在建国之后几乎都设置史官,组织人力编修前代史书和本朝国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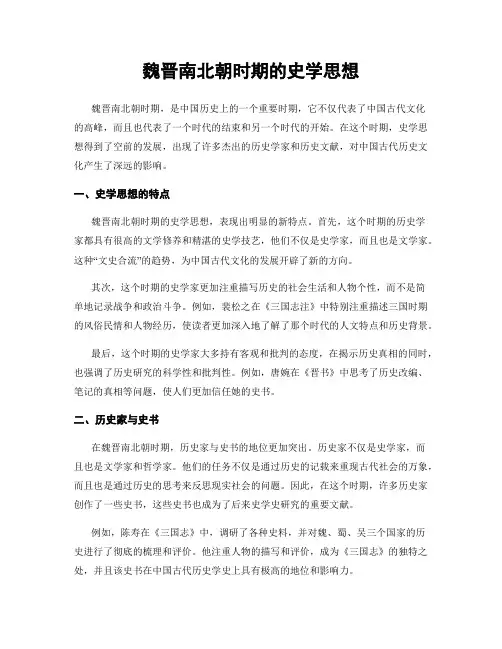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不仅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而且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在这个时期,史学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历史学家和历史文献,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史学思想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思想,表现出明显的新特点。
首先,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和精湛的史学技艺,他们不仅是史学家,而且也是文学家。
这种“文史合流”的趋势,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
其次,这个时期的史学家更加注重描写历史的社会生活和人物个性,而不是简单地记录战争和政治斗争。
例如,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特别注重描述三国时期的风俗民情和人物经历,使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那个时代的人文特点和历史背景。
最后,这个时期的史学家大多持有客观和批判的态度,在揭示历史真相的同时,也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批判性。
例如,唐婉在《晋书》中思考了历史改编、笔记的真相等问题,使人们更加信任她的史书。
二、历史家与史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家与史书的地位更加突出。
历史家不仅是史学家,而且也是文学家和哲学家。
他们的任务不仅是通过历史的记载来重现古代社会的万象,而且也是通过历史的思考来反思现实社会的问题。
因此,在这个时期,许多历史家创作了一些史书,这些史书也成为了后来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例如,陈寿在《三国志》中,调研了各种史料,并对魏、蜀、吴三个国家的历史进行了彻底的梳理和评价。
他注重人物的描写和评价,成为《三国志》的独特之处,并且该史书在中国古代历史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力。
再如,范晔的《后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经过撰改正式出版的机关史,本书是中国后汉中期史的最重要史料,不仅是史学家们进行历史研究和撰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者了解中国历史的渠道。
三、史学家的代表人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很多,其中以顾祝同、范晔、唐婉、陈寿、裴松之、韦昭等人为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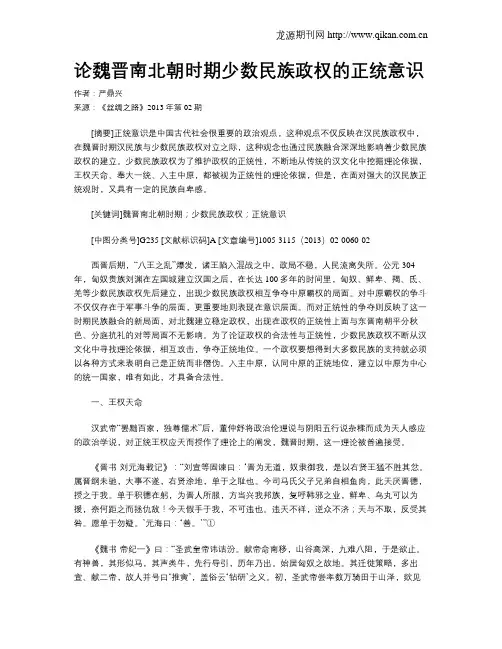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作者:严鼎兴来源:《丝绸之路》2013年第02期[摘要]正统意识是中国古代社会很重要的政治观点,这种观点不仅反映在汉民族政权中,在魏晋时期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政权对立之际,这种观念也通过民族融合深深地影响着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
少数民族政权为了维护政权的正统性,不断地从传统的汉文化中挖掘理论依据,王权天命、奉大一统、入主中原,都被视为正统性的理论依据,但是,在面对强大的汉民族正统观时,又具有一定的民族自卑感。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正统意识[中图分类号]G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2-0060-02西晋后期,“八王之乱”爆发,诸王陷入混战之中,政局不稳,人民流离失所。
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建立汉国之后,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政权先后建立,出现少数民族政权相互争夺中原霸权的局面。
对中原霸权的争斗不仅仅存在于军事斗争的层面,更重要地则表现在意识层面。
而对正统性的争夺则反映了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新局面,对北魏建立稳定政权,出现在政权的正统性上面与东晋南朝平分秋色、分庭抗礼的对等局面不无影响。
为了论证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少数民族政权不断从汉文化中寻找理论依据,相互攻击,争夺正统地位。
一个政权要想得到大多数民族的支持就必须以各种方式来表明自己是正统而非僭伪。
入主中原,认同中原的正统地位,建立以中原为中心的统一国家,唯有如此,才具备合法性。
一、王权天命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董仲舒将政治伦理说与阴阳五行说杂糅而成为天人感应的政治学说,对正统王权应天而授作了理论上的阐发,魏晋时期,这一理论被普遍接受。
《晋书·刘元海载记》:“刘宣等固谏曰:‘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
属晋纲未驰,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
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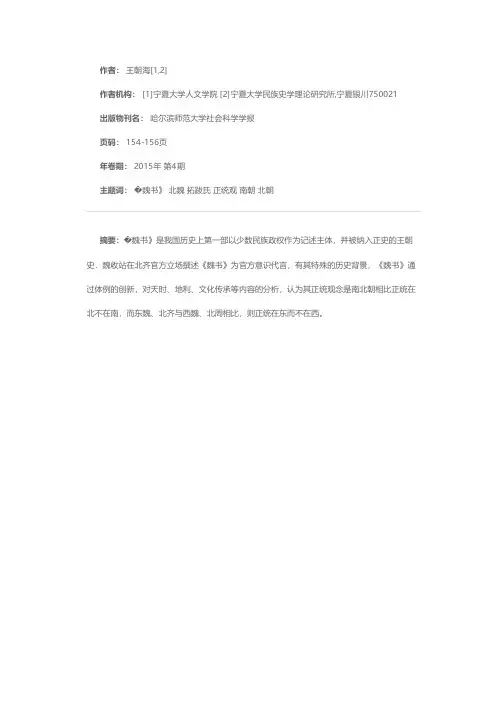
作者: 王朝海[1,2]
作者机构: [1]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2]宁夏大学民族史学理论研究所,宁夏银川750021出版物刊名: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页码: 154-156页
年卷期: 2015年 第4期
主题词:�魏书》 北魏 拓跋氏 正统观 南朝 北朝
摘要:�魏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少数民族政权作为记述主体,并被纳入正史的王朝史.魏收站在北齐官方立场撰述《魏书》为官方意识代言,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魏书》通过体例的创新,对天时、地利、文化传承等内容的分析,认为其正统观念是南北朝相比正统在北不在南,而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相比,则正统在东而不在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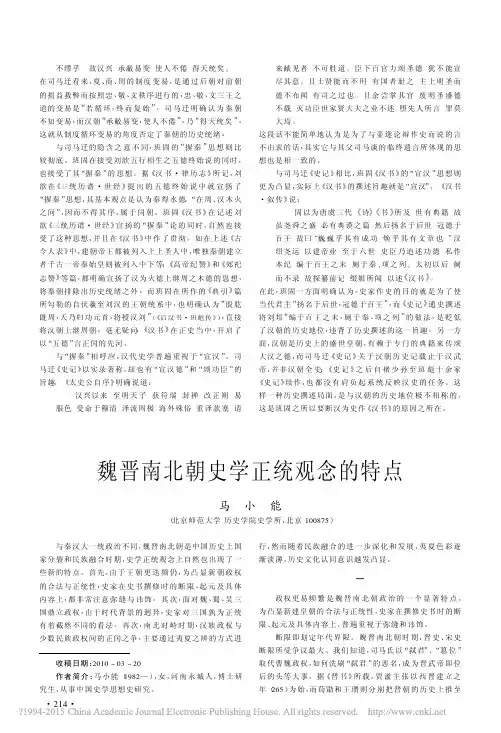
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在司马迁看来,夏、商、周的制度变易,是通过后朝对前朝的损益救弊而按照忠、敬、文秩序进行的,忠、敬、文三王之道的变易是“若循环,终而复始”。
司马迁明确认为秦朝不知变易,而汉朝“承敝易变,使人不倦”,乃“得天统矣”。
这就从制度循环变易的角度否定了秦朝的历史统绪。
与司马迁的隐含之意不同,班固的“摒秦”思想则比较彻底。
班固在接受刘歆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的同时,也接受了其“摒秦”的思想。
据《汉书·律历志》所记,刘歆在《三统历谱·世经》提出的五德终始说中就宣扬了“摒秦”思想,其基本观点是认为秦得水德,“在周、汉木火之间”,因而不得其序,属于闰朝。
班固《汉书》在记述刘歆《三统历谱·世经》宣扬的“摒秦”论的同时,自然也接受了这种思想,并且在《汉书》中作了贯彻。
如在上述《古今人表》中,建朝帝王都被列入上上圣人中,唯独秦朝建立者千古一帝秦始皇则被列入中下等;《高帝纪赞》和《郊祀志赞》等篇,都明确宣扬了汉为火德上继周之木德的思想,将秦朝排除出历史统绪之外。
而班固在所作的《典引》篇所勾勒的自伏羲至刘汉的王朝统系中,也明确认为“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后汉书·班彪传》),直接将汉朝上继周朝。
毫无疑问,《汉书》在正史当中,开启了以“五德”言正闰的先河。
与“摒秦”相呼应,汉代史学普遍重视于“宣汉”。
司马迁《史记》以实录著称,却也有“宣汉德”和“颂功臣”的旨趣。
《太史公自序》明确说道: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颂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耻之;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这段话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为了与壶遂论辩作史而说的言不由衷的话,其实它与其父司马谈的临终遗言所体现的思想也是相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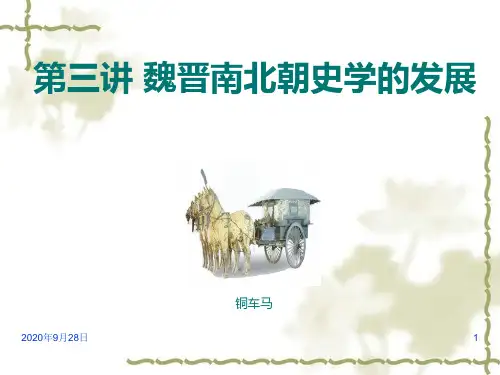
15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分裂和民族融合是这一时代显著的特征。
由于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此起彼伏,弑君篡位、改朝换代如同走马灯,促使当时的统治者重视运用史学来总结前朝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并为自己的政权创造正统理论,从而都促进了史学繁荣。
瞿林东先生曾高度评价这一时期的史学,认为其在许多方面的成就“是秦汉时期史学所不能比拟的”。
本文主要从魏晋南北朝史学繁荣发展的基本面貌、史学的经世特点、史学的玄学色彩以及史学独立等四个方面简要分析总结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特点,体察中国史学史的演变历程。
一、史学繁荣发展的基本面貌魏晋南北朝历时370年,既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动乱时代,又是思想文化开放创新、孕育着历史进步的变动时代。
这些都对史学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逐渐形成了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基本面貌。
(一)南朝私人撰史趋于兴盛,北朝官修史书有了相当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私人撰史兴盛,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上巍为壮观的景象,同时也涌现出如西晋之王铨、南朝宋之范晔、梁之吴均,北魏之崔鸿等一大批优秀的史家。
这其中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史官制度不健全。
受门阀制度影响,负责修史的人往往并不十分合适,致使私人修史之风渐起。
其次,门阀制度的推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门阀政治,通过九品中正制来选拔官员,因此社会盛行品评人物的风气。
于是重视家传、编写谱系成为时尚,具有家学传统的修史者更是把修史当作一种献身于“名山”的事业。
最后,史学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记》、《汉书》已是“师法相传”;梁、陈到唐,“《汉书》学”已经形成,为世所重。
(二)史书种类和数量迅速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的数量呈现出一个高峰。
《隋志》著录史书817部,13264卷;通计亡书,合874部,16558卷,而这些书绝大部分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除了数量,史书的品种、类别也增多了。
萧梁时期阮孝绪编撰《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
南北朝时期的统一之道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而又有趣的时期,这段时间孕育了许多统一之道的思考和实践。
在这个时期,南北朝相互对抗,政权更迭频繁,大量的战争和内乱使得社会秩序丧失,人民生活困苦。
然而,在这种动荡的背景下,一些思想家和统治者尝试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实现统一,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探讨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统一之道需要以文化为基础。
在南北朝时期,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战争和政权更迭,各地的民众生活困苦。
为了实现统一,一些统治者认识到将人们的心思从战争中转移出来,培养和弘扬文化,对实现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南朝刘宋朝廷的文化推行政策。
刘宋朝以文化为核心,鼓励文人雅士,推崇儒家思想,重视教育和文化建设。
通过培养文化人才,提倡文化教育,刘宋朝政府成功地团结了一大批有志于国家统一的知识分子,为创造南朝统一的社会氛围奠定了基础。
在南北朝时期,佛教也起到了重要的统一作用。
佛教因其广泛的影响力和思想体系的魅力成为了南北朝时期实现统一的重要力量。
佛教强调和平、慈悲和智慧,与当时的战乱和社会压力形成鲜明对比。
佛教信徒常常被视为有积极影响力的人士,他们倡导宽容、忍耐和劝诫,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缔造一个统一稳定的社会。
因此,佛教在南北朝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统一之道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除了文化之外,南北朝的统一之道还离不开一种融合和包容的态度。
在这个时期,南方和北方的人们往往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语言习俗和风俗习惯。
为了实现统一,一些统治者采取了一种包容和融合的态度,尊重各地区的特色,并且努力吸收各地区的优点。
刘宋朝治理南方时,尊重南方的神明信仰,鼓励各地方特色发展。
而北魏统治者则将自己的首都建在洛阳,以尊重和接纳南方人的文化特征。
这种包容和融合的态度使得南北方民众感觉到他们的差异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共同发展的基础。
最后,南北朝时期的统一之道也需要一种有效的统治方式。
在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繁,每个新的朝代都需要建立自己的统治机制,稳定国家秩序。
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发展与史学特点 [转帖 2008-12-15 19:51:21]字号:大中小【原文出处】《河北师院学报:社科版》(石家庄)1995年04期第21-29页[编者按]我院历史系为庆贺著名历史学家胡如雷先生七十寿辰,约请校内外作者撰文,拟编辑出版一本《古史论集》;瞿林东和下面孟繁清、孙继民先生的三篇文章,是其中的一部分;学报征得有关方面的支持,先行发表出来,以示同贺。
考察一个时期的史学,必首先考察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的发展,才有可能认识这一时期的史学同历史的联系,进而认识这一时期的史学的面貌和特点。
这是阐述一个时期的史学之各种表现及总的进程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许多历史研究者都把它们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而且各有自己的根据。
本文是把它们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来看待,这主要是基于门阀地主在这个时期占有统治上的主导地位而确认的。
①当然,这两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在把它们划分为一个时期的基础上,也还可以把它们作为两个阶段来看待。
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历来有不同的评价。
司马光认为:魏晋皇室“骨肉相残”,“而胡、羯、氐、羌、鲜卑争承其弊,剖裂中原,齑醢生民,积骸成丘,流血成渊,几三百年,岂不哀哉!”②司马光指出了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原处于分裂、争战之中,社会经济遭到破坏,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不论是十六国,还是北朝,各封建皇朝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它们并不完全是无所作为的,这一点,司马光却没有指出来。
其实,早在唐初,人们对此已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唐高祖李渊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有几句话是涉及到对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的评价的。
他说:自有晋南徒,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各殊徽号,删定礼仪。
至于发述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
③李渊用“嘉谋善政”、“立言著绩”不乏于时来评价南北朝时期各个皇朝的历史,显然不同于把这时期的中原的历史视为漆黑一团的看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隋唐统一在历史的长河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这个时期从公元220年的三国时代开始,一直到公元589年的隋朝建立,大约经历了370多年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而这些变革,也为隋唐统一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点要想深入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首先要了解这个时期的特点。
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社会出现了分裂,北方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逐渐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民族政权,如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等。
南方地区则因地广人稀,政治经济衰退,出现了南朝的刘宋、南齐、梁、陈四个朝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些重要的特点,比如贵族专权、文化多元、经济萎缩等等。
在政治上,这段时期的王朝基本上都是由一些强大的贵族来掌握权力,而这些贵族多半靠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奴隶来获得财富和权力。
在文化上,本来属于汉族文化的构成要素逐渐多元化,诸如佛教、道教、外来民族文化等开始逐渐深入到中国文化里。
二、南北朝的统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朝的统一本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北方各族政权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而南方地区却一直处于被动局面,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被北方政权所控制的状态。
但是,南北朝统一的愿望是始终存在的,而这个愿望也最终在隋朝和唐朝的建立中得以实现。
在南北朝末期,北方的北周王朝逐渐崩溃,而南方的陈朝却由于内部分裂和经济困境等原因愈加萎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隋文帝杨坚充分抓住了机会,武力和外交相结合,最终在南北朝互相争斗的局面中得以顺利登上皇位,成立了强大的隋朝。
三、隋朝的统一成就隋朝的建立,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政治上,隋朝礼制大大推动了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交通等诸多领域的发展。
此外,隋朝还大力发展了运河工程,将大运河修建得更加完善。
这使得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商品交流加速,促进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繁荣。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entral Plains Historiography in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作者: 马小能[1]
作者机构: [1]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新乡453000
出版物刊名: 河南图书馆学刊
页码: 136-139页
年卷期: 2020年 第11期
主题词: 魏晋南北朝;中原史学;门阀;玄学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史学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范晔《后汉书》、袁宏《后汉纪》、司马彪《续汉书》等。
就其特点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原史学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
地域特征。
受门阀观念影响,中原地区的谱牒学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受民族意识影响,中原史学表现出浓郁的史学经世情结;受玄学思潮影响,中原史学带有明显的援玄入史的玄化倾向;受儒学思潮影响,中原史家还不约而同地把“忠孝节义”作为撰写史著的一大主题;此外,方志、人物杂传、史钞、史论等各类杂史著述的出现,充分说明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领域呈现出继续扩大的态势。
作者: 马小能[1]
作者机构: [1]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所,北京100875
出版物刊名: 学习与探索
页码: 214-216页
年卷期: 2010年 第4期
主题词: 魏晋南北朝;正统观念;史学;民族融合;国家分裂;中国历史;三国鼎立;大一统
摘要:与秦汉大一统政治不同,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家分裂和民族融合时期,史学正统观念上自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由于王朝更迭频仍,为凸显新朝政权的合法与正统性,史家在史书撰修时的断限、起元及具体内容上,都非常注意弥缝与讳饰。
其次,面对魏、蜀、吴三国鼎立政权,由于时代背景的迥异,史家对三国孰为正统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在司马迁看来,夏、商、周的制度变易,是通过后朝对前朝的损益救弊而按照忠、敬、文秩序进行的,忠、敬、文三王之道的变易是“若循环,终而复始”。
司马迁明确认为秦朝不知变易,而汉朝“承敝易变,使人不倦”,乃“得天统矣”。
这就从制度循环变易的角度否定了秦朝的历史统绪。
与司马迁的隐含之意不同,班固的“摒秦”思想则比较彻底。
班固在接受刘歆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的同时,也接受了其“摒秦”的思想。
据《汉书·律历志》所记,刘歆在《三统历谱·世经》提出的五德终始说中就宣扬了“摒秦”思想,其基本观点是认为秦得水德,“在周、汉木火之间”,因而不得其序,属于闰朝。
班固《汉书》在记述刘歆《三统历谱·世经》宣扬的“摒秦”论的同时,自然也接受了这种思想,并且在《汉书》中作了贯彻。
如在上述《古今人表》中,建朝帝王都被列入上上圣人中,唯独秦朝建立者千古一帝秦始皇则被列入中下等;《高帝纪赞》和《郊祀志赞》等篇,都明确宣扬了汉为火德上继周之木德的思想,将秦朝排除出历史统绪之外。
而班固在所作的《典引》篇所勾勒的自伏羲至刘汉的王朝统系中,也明确认为“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后汉书·班彪传》),直接将汉朝上继周朝。
毫无疑问,《汉书》在正史当中,开启了以“五德”言正闰的先河。
与“摒秦”相呼应,汉代史学普遍重视于“宣汉”。
司马迁《史记》以实录著称,却也有“宣汉德”和“颂功臣”的旨趣。
《太史公自序》明确说道: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颂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耻之;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这段话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为了与壶遂论辩作史而说的言不由衷的话,其实它与其父司马谈的临终遗言所体现的思想也是相一致的。
与司马迁《史记》相比,班固《汉书》的“宣汉”思想则更为凸显,实际上《汉书》的撰述旨趣就是“宣汉”。
《汉书·叙传》说: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
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
在此,班固一方面明确认为,史家作史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当代君主“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而《史记》通史撰述将刘邦“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的做法,是贬低了汉朝的历史地位,违背了历史撰述的这一旨趣。
另一方面,汉朝是历史上的盛世皇朝,有赖于专门的典籍来传颂大汉之德,而司马迁《史记》关于汉朝历史记载止于汉武帝,并非汉朝全史;《史记》之后自褚少孙至班彪十余家《史记》续作,也都没有肩负起系统反映汉史的任务。
这样一种历史撰述局面,是与汉朝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的。
这是班固之所以要断汉为史作《汉书》的原因之所在。
魏晋南北朝史学正统观念的特点马小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所,北京100875)收稿日期:2010-03-20作者简介:马小能(1982—),女,河南永城人,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
与秦汉大一统政治不同,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家分裂和民族融合时期,史学正统观念上自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由于王朝更迭频仍,为凸显新朝政权的合法与正统性,史家在史书撰修时的断限、起元及具体内容上,都非常注意弥缝与讳饰。
其次,面对魏、蜀、吴三国鼎立政权,由于时代背景的迥异,史家对三国孰为正统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再次,南北对峙时期,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间的正闰之争,主要通过夷夏之辨的方式进行,然而随着民族融合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夷夏色彩逐渐淡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越发凸显。
一政权更易频繁是魏晋南北朝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
为凸显新建皇朝的合法与正统性,史家在撰修史书时的断限、起元及具体内容上,普遍重视于弥缝和讳饰。
断限即划定年代界限。
魏晋南北朝时期,晋史、宋史断限所受争议最大。
我们知道,司马氏以“弑君”、“篡位”取代曹魏政权,如何洗刷“弑君”的恶名,成为晋武帝即位后的头等大事。
据《晋书》所载,贾谧主张以西晋建立之年(265)为始,而荀勖和王瓒则分别把晋朝的历史上推至·412·240年和249年。
结合历史事实,不难发现,上推的目的是要将齐王芳的被废黜、魏高贵乡公曹髦的被杀作为西晋内部的政治斗争来处理,这就很好地弥缝了司马氏父子弑君的恶名。
另据《宋书·徐爰传》所载:“起元义熙,为王业之始。
”两汉政权也早在丰沛和昆阳之日就已开始。
“降逮二汉,亦同兹义,基帝创乎丰郊,绍祚本于昆邑。
”同理,刘裕亦在义熙年间建立了赫赫功名,实已受命为王。
这就很好地掩饰了其篡夺晋室皇位的“不道”行为。
起元与断限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南朝齐修国史,认为萧齐得天下乃“受之也,非取之也。
”(《南齐书·高帝纪下》)因而,所修国史,“开元纪号,不取宋年。
”(《南齐书·檀超传》)不再将年限上推。
和南朝相对应的北朝,在齐史起元问题上亦争执不一。
据《隋书》和《北齐书》所载,魏收认为《齐书》应以高祖平四胡之岁(532年)为起元。
阳休之认为应以齐显祖高洋天保元年(550)为限断。
二人相持不下,魏收寄书与李德林以征求意见。
李在答复中,指出应以“受命之元”作为《齐史》撰修的开端。
“受命之元”是指开基业而未有帝号者。
其理由是:“唯可二代相涉,两史并书,必不得以后朝创业之迹,断入前史。
若然,则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唯入魏氏列传,不作齐朝帝纪,可乎?”(《隋书·李德林传》)后代创业之迹不能断入前史,这是现实政治所要求。
由此可见,在王朝更迭频仍的情况下,断限是粉饰靠阴谋和暴力而建新皇朝的重要手段。
从史书撰述的具体内容来看,史家在宣扬本朝功业的同时,往往重视大力宣扬天命王权思想,以为新朝建立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做出论证论。
为本朝歌功颂德,是史家的职责所在。
如沈约《宋书》就是为了追“述一代盛典”(《宋书·璞子约传》)。
《北齐书》则借崔暹之言指出,“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
”(《北齐书·魏收传》)北魏史官高祐认为,“皇风大猷”,“功臣懿绩”,“成事所以昭扬”,是因为“载籍作”的缘故(《魏书·高祐传》)。
在正面歌颂之外,史家还通过为本朝避讳、同时暴露前朝之恶的形式从反面进行映衬。
《宋书》之“《后废帝纪》,但历叙帝无道之处,以见其必当废杀。
”《顺帝纪》亦但叙萧道成之功勋,绝不见篡夺之迹。
对于效忠刘宋而谋讨萧道成者,“概曰‘反’,曰有‘罪’。
”然“其党于道成而为之助力者,转谓之起义。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南齐书》则将齐末帝比作桀、纣,而暗喻梁武帝即汤、武。
如此一来,梁代齐,自然也就是合理、合法的了。
天命王权思想是神化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政治理论。
《后汉书》开篇不厌其烦地描述了“赤光照室”及诸多神秘预言。
《南齐书》和《魏书》中更有“其夜陈孝后、刘昭后同梦龙据屋上”(《南齐书·武帝纪》),“其夜复有光明”、“榆生于埋胞之坎,后遂成林”(《魏书·太祖道武帝纪》)的离奇描写。
如此一来,就给新朝统治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其统治也就被合法、正统化了。
《宋书》、《南齐书》、《魏书》还专门设有《符瑞志》、《祥瑞志》、《灵征志》等,在他们看来,讲符瑞的本质目的是要警告那些“力争之徒”、“乱臣贼子”尽快醒悟,“受命之符,天人之应”,王命实乃天授,并非逐鹿可得(《宋书·符瑞志上》)。
二东汉结束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三国魏、蜀、吴鼎立时期。
三国各为正朔,极力标榜自己为正统,而贬斥他国为非法的僭伪政权。
尤其是汉魏之间,长期互指对方为贼。
“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乃据险乘流,跨有士众,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
”(《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诸葛亮《出师表》亦表达出一种“汉贼不两立”的历史意识(《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
三国究竟以谁为正,成为当时史家研究三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问题。
西晋史家陈寿以其杰出的史才与史识,将三国历史统于《三国志》一书之中。
而《三国志》在正统观上是以曹魏为正的。
首先,《三国志》采取了帝魏而传蜀、吴的编纂原则,为曹魏君主立“纪”,而为蜀、吴君主立“传”,且将曹魏“纪”置于蜀、吴“传”之前。
《魏书》中对蜀、吴君主的继位称帝皆无其本国年号记载,而在《蜀书》、《吴书》中蜀、吴君主继位则必记曹魏之年号。
如记蜀汉后主刘禅继位,曰:“是岁魏黄初四年也。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记孙亮继位,曰:“是岁,于魏嘉平四年也。
”孙休继位:“是岁,于魏甘露三年也。
”孙皓继位:“是岁,于魏咸熙元年也。
”(《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对三国创立者的称谓也有所不同。
如对曹操,在《魏书》中称“太祖”或“公”、“魏公”、“魏王”,在《蜀书》和《吴书》中称“曹公”。
对刘备,《蜀书》中称“先主”,在《魏书》、《吴书》中则直呼其名。
对孙权,不论是《魏书》、《蜀书》还是《吴书》,一概直呼其名。
曹魏君主的死称“崩”,蜀汉君主的死则称“殂”,孙吴君主的死则称“薨”。
其本人对后主刘禅面缚衔璧、全蜀归魏一事亦极表赞美之情。
称赞刘禅此举“恢崇德度,深秉大正。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其次,陈寿在记述曹魏代汉的历史时,还大书特书符瑞之事,以明曹魏政权的建立,实乃天命所归。
《魏书·武帝纪》记曹操破袁绍之事时曰:“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
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
”《文帝纪》中则有“黄龙见谯”之异象。
“初,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飏:‘此何祥也?’飏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
天事恒象,此其应也。
’内黄殷登默而记之。
至四十五年,登尚在。
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单飏之言,其验兹乎。
’”汉献帝以为曹魏乃众望所归,于是令人“持节奉玺绶禅位”。
按:黄星是土德的象征,黄星的出现,也就“预示着曹魏要以土德代替汉朝火德了,而官渡之战曹操打败袁绍,‘天下莫敌’,说明这种黄星之瑞得到了验证。
”黄龙和黄星一样,也是土德的象征。
谯是曹操的家乡,谯地出现黄龙,意味着曹魏代汉乃天命所归。
不同的是,《文帝纪》中“不但记载了符应出现的地点、时间,更重要的是它·512·有具体的见证人和当年的历史记录,从而使这种符应之说更具有了真实性、可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