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创作的形式探索
- 格式:pdf
- 大小:130.03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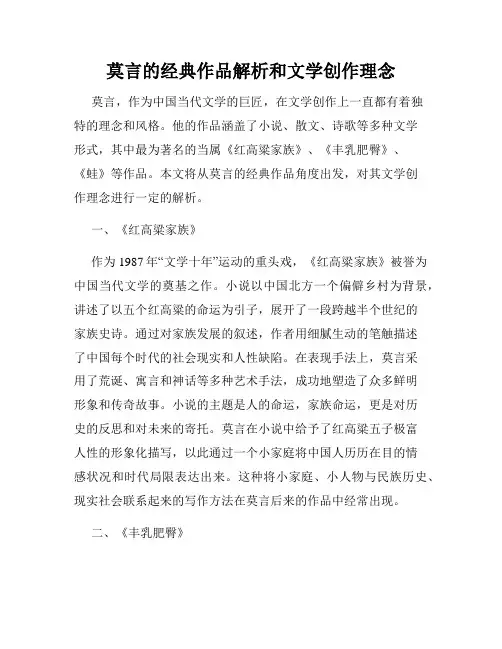
莫言的经典作品解析和文学创作理念莫言,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匠,在文学创作上一直都有着独特的理念和风格。
他的作品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学形式,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蛙》等作品。
本文将从莫言的经典作品角度出发,对其文学创作理念进行一定的解析。
一、《红高粱家族》作为1987年“文学十年”运动的重头戏,《红高粱家族》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奠基之作。
小说以中国北方一个偏僻乡村为背景,讲述了以五个红高粱的命运为引子,展开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家族史诗。
通过对家族发展的叙述,作者用细腻生动的笔触描述了中国每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和人性缺陷。
在表现手法上,莫言采用了荒诞、寓言和神话等多种艺术手法,成功地塑造了众多鲜明形象和传奇故事。
小说的主题是人的命运,家族命运,更是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寄托。
莫言在小说中给予了红高粱五子极富人性的形象化描写,以此通过一个小家庭将中国人历历在目的情感状况和时代局限表达出来。
这种将小家庭、小人物与民族历史、现实社会联系起来的写作方法在莫言后来的作品中经常出现。
二、《丰乳肥臀》《丰乳肥臀》是莫言的另一部经典之作。
小说着重描绘了中国老百姓家庭明快生动的生活,通过对五代同堂女性丰乳肥臀的描写,反映了中国女性的命途多舛、奋斗历程和生命悲欢离合。
小说着重探讨了女性家庭地位、家族兴衰和社会变化的深刻内涵。
莫言试图让读者从女性的视角出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想象世界和女性命运的变化。
小说中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对生命的崇敬、对女性的关注,是莫言笔下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三、《蛙》莫言最新的作品《蛙》是一部对当代中国草根年轻人生活的关注和呈现,莫言在小说中以一个小县城的所镇痛过镇出发,展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诸多矛盾和背景。
莫言以一家散居在农村的三代人为刻画主线,展示了走过一生的农民亲人的生活和命运,感情生活的沉浸和转向,这部小说展现了中国人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的色彩。
小说中揭示了中国社会一些最为普遍的问题,揭示了社会的界限,深刻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增加构思难度,人物个性明显鲜明,构思丰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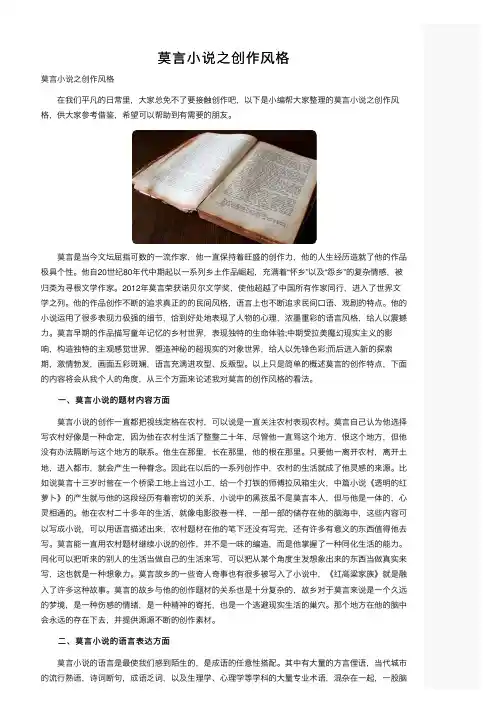
莫⾔⼩说之创作风格 在我们平凡的⽇常⾥,⼤家总免不了要接触创作吧,以下是⼩编帮⼤家整理的莫⾔⼩说之创作风格,供⼤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莫⾔是当今⽂坛屈指可数的⼀流作家,他⼀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他的⼈⽣经历造就了他的作品极具个性。
他⾃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以⼀系列乡⼟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学作家。
2012年莫⾔荣获诺贝尔⽂学奖,使他超越了中国所有作家同⾏,进⼊了世界⽂学之列。
他的作品创作不断的追求真正的的民间风格,语⾔上也不断追求民间⼝语、戏剧的特点。
他的⼩说运⽤了很多表现⼒极强的细节,恰到好处地表现了⼈物的⼼理,浓墨重彩的语⾔风格,给⼈以震撼⼒。
莫⾔早期的作品描写童年记忆的乡村世界,表现独特的⽣命体验;中期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塑造神秘的超现实的对象世界,给⼈以先锋⾊彩;⽽后进⼊新的探索期,激情勃发,画⾯五彩斑斓,语⾔充满进攻型、反叛型。
以上只是简单的概述莫⾔的创作特点,下⾯的内容将会从我个⼈的⾓度,从三个⽅⾯来论述我对莫⾔的创作风格的看法。
⼀、莫⾔⼩说的题材内容⽅⾯ 莫⾔⼩说的创作⼀直都把视线定格在农村,可以说是⼀直关注农村表现农村。
莫⾔⾃⼰认为他选择写农村好像是⼀种命定,因为他在农村⽣活了整整⼆⼗年,尽管他⼀直骂这个地⽅,恨这个地⽅,但他没有办法隔断与这个地⽅的联系。
他⽣在那⾥,长在那⾥,他的根在那⾥。
只要他⼀离开农村,离开⼟地,进⼊都市,就会产⽣⼀种眷念。
因此在以后的⼀系列创作中,农村的⽣活就成了他灵感的来源。
⽐如说莫⾔⼗三岁时曾在⼀个桥梁⼯地上当过⼩⼯,给⼀个打铁的师傅拉风箱⽣⽕,中篇⼩说《透明的红萝⼘》的产⽣就与他的这段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说中的⿊孩虽不是莫⾔本⼈,但与他是⼀体的,⼼灵相通的。
他在农村⼆⼗多年的⽣活,就像电影胶卷⼀样,⼀部⼀部的储存在他的脑海中,这些内容可以写成⼩说,可以⽤语⾔描述出来,农村题材在他的笔下还没有写完,还有许多有意义的东西值得他去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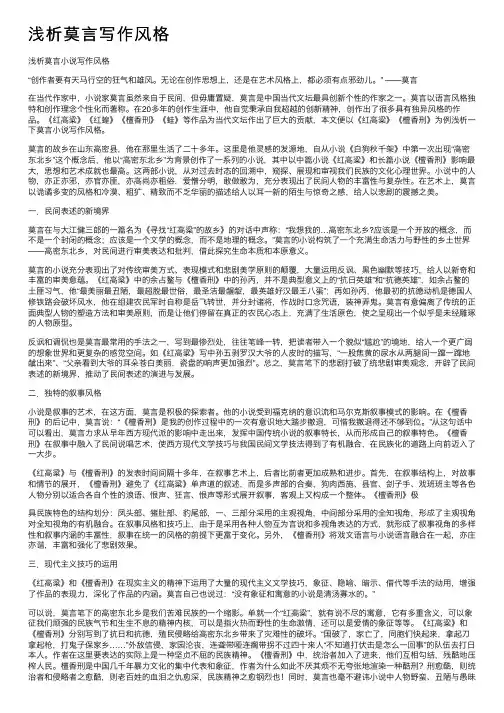
浅析莫⾔写作风格浅析莫⾔⼩说写作风格“创作者要有天马⾏空的狂⽓和雄风。
⽆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
” ——莫⾔在当代作家中,⼩说家莫⾔虽然来⾃于民间,但⽏庸置疑,莫⾔是中国当代⽂坛最具创新个性的作家之⼀。
莫⾔以语⾔风格独特和创作理念个性化⽽著称。
在20多年的创作⽣涯中,他⾃觉秉承⾃我超越的创新精神,创作出了很多具有独异风格的作品。
《红⾼粱》《红蝗》《檀⾹刑》《蛙》等作品为当代⽂坛作出了巨⼤的贡献,本⽂便以《红⾼粱》《檀⾹刑》为例浅析⼀下莫⾔⼩说写作风格。
莫⾔的故乡在⼭东⾼密县,他在那⾥⽣活了⼆⼗多年。
这⾥是他灵感的发源地,⾃从⼩说《⽩狗秋千架》中第⼀次出现“⾼密东北乡”这个概念后,他以“⾼密东北乡”为背景创作了⼀系列的⼩说,其中以中篇⼩说《红⾼粱》和长篇⼩说《檀⾹刑》影响最⼤,思想和艺术成就也最⾼。
这两部⼩说,从对过去时态的回溯中,窥探、展现和审视我们民族的⽂化⼼理世界。
⼩说中的⼈物,亦正亦邪,亦官亦匪,亦⾼尚亦粗俗,爱憎分明,敢做敢为,充分表现出了民间⼈物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在艺术上,莫⾔以诡谲多变的风格和冷漠、粗犷、精致⽽不乏华丽的描述给⼈以⽿⼀新的陌⽣与惊奇之感,给⼈以悲剧的震撼之美。
⼀.民间表述的新境界莫⾔在与⼤江健三郎的⼀篇名为《寻找“红⾼粱”的故乡》的对话中声称:“我想我的…⾼密东北乡?应该是⼀个开放的概念,⽽不是⼀个封闭的概念;应该是⼀个⽂学的概念,⽽不是地理的概念。
”莫⾔的⼩说构筑了⼀个充满⽣命活⼒与野性的乡⼟世界——⾼密东北乡,对民间进⾏审美表达和批判,借此探究⽣命本质和本原意义。
莫⾔的⼩说充分表现出了对传统审美⽅式、表现模式和悲剧美学原则的颠覆,⼤量运⽤反讽、⿊⾊幽默等技巧,给⼈以新奇和丰富的审美意蕴。
《红⾼粱》中的余占鳌与《檀⾹刑》中的孙丙,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抗⽇英雄”和“抗德英雄”,如余占鳌的⼟匪习⽓,他“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蛋”;再如孙丙,他最初的抗德动机是德国⼈修铁路会破坏风⽔,他在组建农民军时⾃称是岳飞转世,并分封诸将,作战时⼝念咒语,装神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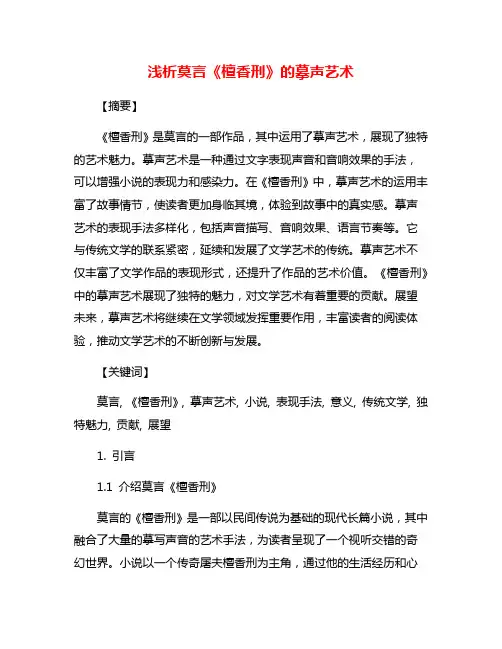
浅析莫言《檀香刑》的摹声艺术【摘要】《檀香刑》是莫言的一部作品,其中运用了摹声艺术,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摹声艺术是一种通过文字表现声音和音响效果的手法,可以增强小说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在《檀香刑》中,摹声艺术的运用丰富了故事情节,使读者更加身临其境,体验到故事中的真实感。
摹声艺术的表现手法多样化,包括声音描写、音响效果、语言节奏等。
它与传统文学的联系紧密,延续和发展了文学艺术的传统。
摹声艺术不仅丰富了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还提升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檀香刑》中的摹声艺术展现了独特的魅力,对文学艺术有着重要的贡献。
展望未来,摹声艺术将继续在文学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推动文学艺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莫言, 《檀香刑》, 摹声艺术, 小说, 表现手法, 意义, 传统文学, 独特魅力, 贡献, 展望1. 引言1.1 介绍莫言《檀香刑》莫言的《檀香刑》是一部以民间传说为基础的现代长篇小说,其中融合了大量的摹写声音的艺术手法,为读者呈现了一个视听交错的奇幻世界。
小说以一个传奇屠夫檀香刑为主角,通过他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黑暗面。
作品中的摹声艺术是莫言的创作特色之一,他巧妙地运用声音描写和声音对话等技巧,将读者带入一个充满视听感官体验的文学空间。
通过对声音的真实再现和精准描述,莫言成功地营造出一种紧张严肃的氛围,使读者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故事情节的张力和悬疑。
《檀香刑》的摹声艺术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形式表现,更加深了作品的内涵和情感表达,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别具一格的文学作品。
1.2 摹声艺术的概念摹声艺术是文学创作中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艺术手法,通过文字的运用模拟声音的传达,使读者能够在心灵深处产生一种听觉上的体验。
摹声艺术不仅仅是简单地描述声音的来源和内容,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声音的再现来表达人物情感、环境氛围和情节发展。
在文学作品中,摹声艺术能够增强作品的真实感和表现力,使读者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故事情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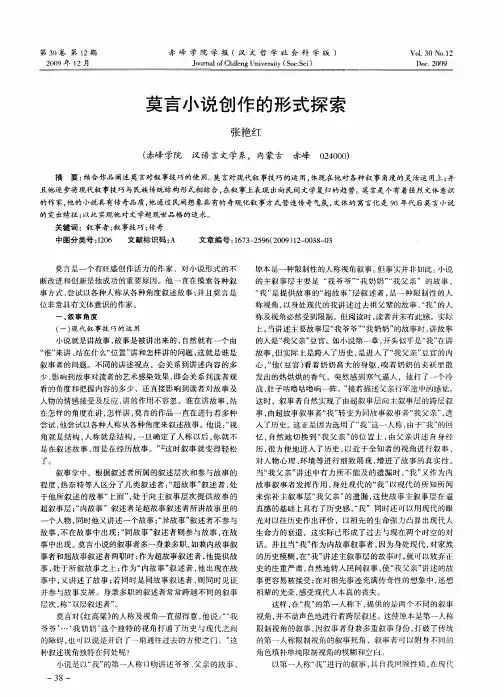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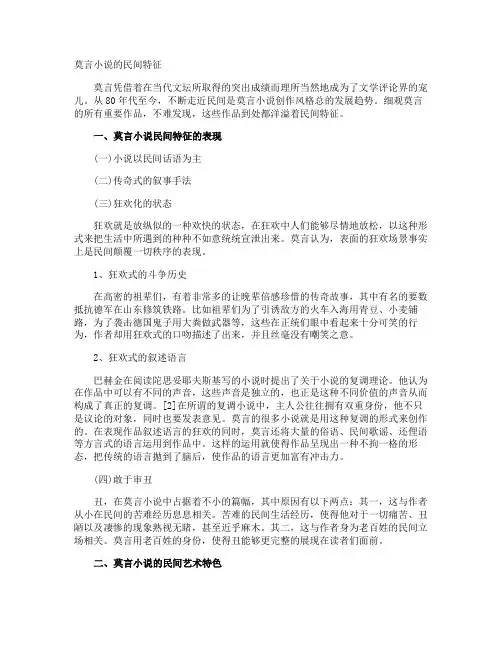
莫言小说的民间特征莫言凭借着在当代文坛所取得的突出成绩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文学评论界的宠儿。
从80年代至今,不断走近民间是莫言小说创作风格总的发展趋势。
细观莫言的所有重要作品,不难发现,这些作品到处都洋溢着民间特征。
一、莫言小说民间特征的表现(一)小说以民间话语为主(二)传奇式的叙事手法(三)狂欢化的状态狂欢就是放纵似的一种欢快的状态,在狂欢中人们能够尽情地放松,以这种形式来把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不如意统统宣泄出来。
莫言认为,表面的狂欢场景事实上是民间颠覆一切秩序的表现。
1、狂欢式的斗争历史在高密的祖辈们,有着非常多的让晚辈倍感珍惜的传奇故事,其中有名的要数抵抗德军在山东修筑铁路。
比如祖辈们为了引诱敌方的火车入海用青豆、小麦铺路,为了袭击德国鬼子用大粪做武器等,这些在正统们眼中看起来十分可笑的行为,作者却用狂欢式的口吻描述了出来,并且丝毫没有嘲笑之意。
2、狂欢式的叙述语言巴赫金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小说时提出了关于小说的复调理论。
他认为在作品中可以有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是独立的,也正是这种不同价值的声音从而构成了真正的复调。
[2]在所谓的复调小说中,主人公往往拥有双重身份,他不只是议论的对象,同时也要发表意见。
莫言的很多小说就是用这种复调的形式来创作的。
在表现作品叙述语言的狂欢的同时,莫言还将大量的俗语、民间歌谣、还俚语等方言式的语言运用到作品中。
这样的运用就使得作品呈现出一种不拘一格的形态,把传统的语言抛到了脑后,使作品的语言更加富有冲击力。
(四)敢于审丑丑,在莫言小说中占据着不小的篇幅,其中原因有以下两点:其一,这与作者从小在民间的苦难经历息息相关。
苦难的民间生活经历,使得他对于一切痛苦、丑陋以及凄惨的现象熟视无睹,甚至近乎麻木。
其二,这与作者身为老百姓的民间立场相关。
莫言用老百姓的身份,使得丑能够更完整的展现在读者们面前。
二、莫言小说的民间艺术特色(一)乡音谚语、俗语是我国民俗文化的语言精华,它往往指的是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积累起来的方言。

莫言《蛙》的叙事语言修辞探析邓梅《蛙》是莫言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采用多种文体相结合的方式创作,包括元故事、戏剧体和书信体,故事的背景跨越了多个历史时期,主要叙述了姑姑的传奇人生,洞察历史的同时也在探求生命的奥秘。
莫言的生命意识非常强,他的创作历程跨越了二十多个春秋,他将黑土地上的生命故事用各种随意的方式展现在读者面前,他坚强而激越的生命力在《丰乳肥臀》《红高粱家族》等作品中疯狂地展现出来。
然而他在创作《蛙》的时候,不再仅仅是“书写生命”,更是上升到一个“凝视生命”的高度。
平息了激情地叙述,改为理性的反思,对生命意识的关照也更加严谨和深沉。
他继承了传统小说中对人性和生命的描写,用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直面这些问题。
《蛙》对于生命意义的描写是史无前例的,是在特殊时期对生命的一种深沉反思。
《蛙》的历史题材不仅宏大,而且还富有哲学意义。
作品的精神内涵中涵盖了历史、文学、哲学等多种思想,使得这部小说的生命力更为顽强。
作者通过元故事、戏剧体和书信体的方式展现了《蛙》中“生命凝视”的多重意义:生命凝视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但是这两种类型的生命凝视的主体思想是统一的,即生命的本质意义和生命的尊严。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莫言的《蛙》进行深入分析,以求探寻作者在创作时对生命的感悟和把握。
一、敢于直面自己当我们靠近事物进行详细观察的时候,经常会忽视很多东西,这也就是所谓的盲区。
计划生育是我国特殊国情下的基本国策,在当前的生活中,这种荒诞而苦痛的政策仍然存在。
对于这种独特政策的评价,也许我们的看法还很肤浅,也许应该放在更广阔的视野和角度上去分析,才能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
但是,我们无法界定这个视野和角度的尺度,到底什么样的界限才算合理是宇宙创世纪之初还是佛教创始之时?通过这种方式去界定时间限度,不免有些虚无而失去意义。
作为没有远见的人类,是应该进行清算的时候了。
人们对《蛙》争议最多的无非是那一部话剧和五封书信的创作文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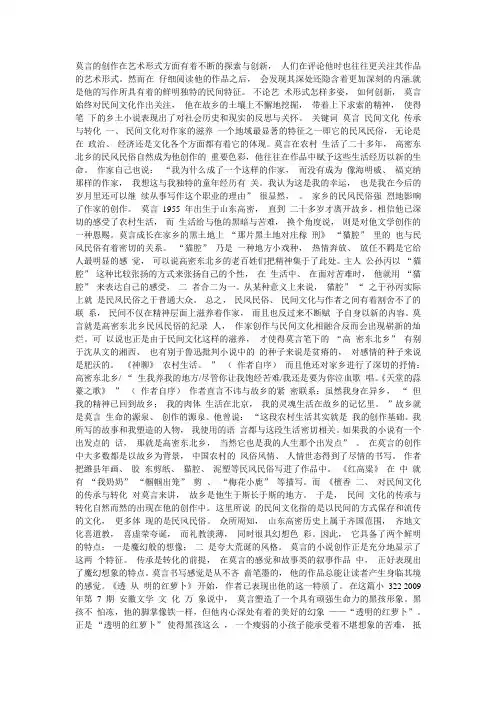
莫言的创作在艺术形式方面有着不断的探索与创新,人们在评论他时也往往更关注其作品的艺术形式。
然而在仔细阅读他的作品之后,会发现其深处还隐含着更加深刻的内涵.就是他的写作所具有着的鲜明独特的民间特征。
不论艺术形式怎样多姿,如何创新,莫言始终对民间文化作出关注,他在故乡的土壤上不懈地挖掘,带着上下求索的精神,使得笔下的乡土小说表现出了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与关怀。
关键词莫言民间文化传承与转化一、民间文化对作家的滋养一个地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即它的民风民俗,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各个方面都有着它的体现。
莫言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多年,高密东北乡的民风民俗自然成为他创作的重要色彩,他往往在作品中赋予这些生活经历以新的生命。
作家自己也说:“我为什么成了一个这样的作家,而没有成为像海明威、福克纳那样的作家,我想这与我独特的童年经历有关。
我认为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在今后的岁月里还可以继续从事写作这个职业的理由”很显然,。
家乡的民风民俗强烈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
莫言1955 年出生于山东高密,直到二十多岁才离开故乡。
相信他已深切的感受了农村生活,而生活给与他的黑暗与苦难,换个角度说,则是对他文学创作的一种恩赐。
莫言成长在家乡的黑土地上“那片黑土地对庄稼刑》“猫腔”里的也与民风民俗有着密切的关系。
“猫腔”乃是一种地方小戏种,热情奔放、放任不羁是它给人最明显的感觉,可以说高密东北乡的老百姓们把精神集于了此处。
主人公孙丙以“猫腔”这种比较张扬的方式来张扬自己的个性,在生活中、在面对苦难时,他就用“猫腔”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二者合二为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猫腔”“之于孙丙实际上就是民风民俗之于普通大众。
总之,民风民俗、民间文化与作者之间有着割舍不了的联系,民间不仅在精神层面上滋养着作家,而且也反过来不断赋予自身以新的内容。
莫言就是高密东北乡民风民俗的纪录人,作家创作与民间文化相融合反而会出现崭新的灿烂。
可以说也正是由于民间文化这样的滋养,才使得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有别于沈从文的湘西、也有别于鲁迅批判小说中的的种子来说是贫瘠的,对感情的种子来说是肥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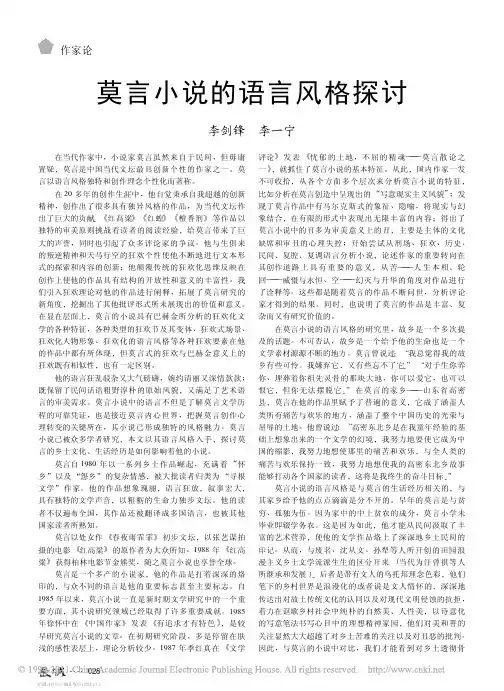
作家论莫言小说的语言风格探讨李剑锋李一宁在当代作家中,小说家莫言虽然来自于民间,但毋庸置疑,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坛最具创新个性的作家之一。
莫言以语言风格独特和创作理念个性化而著称。
在2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自觉秉承自我超越的创新精神,创作出了很多具有独异风格的作品,为当代文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红高粱》《红蝗》《檀香刑》等作品以独特的审美原则挑战着读者的阅读经验,给莫言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引起了众多评论家的争议。
他与生俱来的叛逆精神和天马行空的狂欢个性使他不断地进行文本形式的探索和内容的创新;他颠覆传统的狂欢化思维反映在创作上使他的作品具有结构的开放性和意义的丰富性。
我们引入狂欢理论对他的作品进行阐释,拓展了莫言研究的新角度,挖掘出了其他批评形式所未展现出的价值和意义。
在显在层面上,莫言的小说具有巴赫金所分析的狂欢化文学的各种特征,各种类型的狂欢节及其变体、狂欢式场景、狂欢化人物形象、狂欢化的语言风格等各种狂欢要素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但莫言式的狂欢与巴赫金意义上的狂欢既有相似性,也有一定区别。
他的语言狂乱驳杂又大气磅礴,婉约清丽又深情款款;既保留了民间话语粗野淳朴的原始风貌,又满足了艺术语言的审美需求。
莫言小说中的语言不但是了解莫言文学历程的可靠凭证,也是接近莫言内心世界,把握莫言创作心理转变的关键所在,其小说已形成独特的风格魅力。
莫言小说已被众多学者研究,本文以其语言风格入手,探讨莫言的乡土文化、生活经历是如何影响着他的小说。
莫言自1980年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大批读者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
他的作品想象瑰丽,语言狂放,叙事宏大,具有独特的文学声音,以粗粝的生命力独步文坛。
他的读者不仅遍布全国,其作品还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也被其他国家读者所熟知。
莫言以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初步文坛,以张艺谋拍摄的电影《红高粱》的原作者为大众所知。
1988年《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随之莫言小说也享誉全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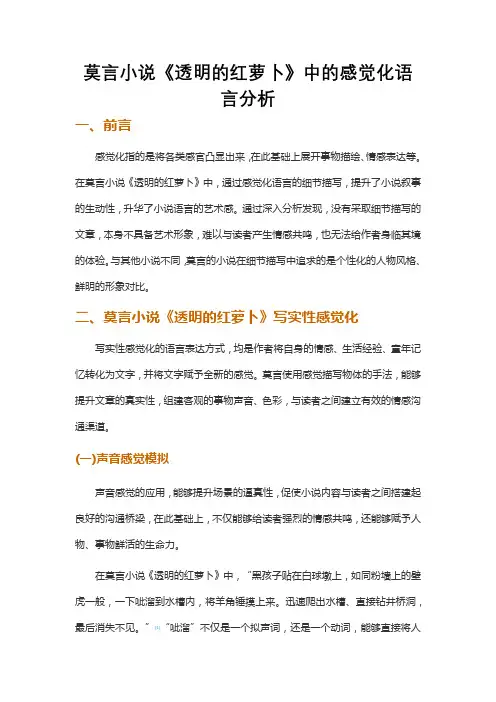
莫言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的感觉化语言分析一、前言感觉化指的是将各类感官凸显出来,在此基础上展开事物描绘、情感表达等。
在莫言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通过感觉化语言的细节描写,提升了小说叙事的生动性,升华了小说语言的艺术感。
通过深入分析发现,没有采取细节描写的文章,本身不具备艺术形象,难以与读者产生情感共鸣,也无法给作者身临其境的体验。
与其他小说不同,莫言的小说在细节描写中追求的是个性化的人物风格、鲜明的形象对比。
二、莫言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写实性感觉化写实性感觉化的语言表达方式,均是作者将自身的情感、生活经验、童年记忆转化为文字,并将文字赋予全新的感觉。
莫言使用感觉描写物体的手法,能够提升文章的真实性,组建客观的事物声音、色彩,与读者之间建立有效的情感沟通渠道。
(一)声音感觉模拟声音感觉的应用,能够提升场景的逼真性,促使小说内容与读者之间搭建起良好的沟通桥梁,在此基础上,不仅能够给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还能够赋予人物、事物鲜活的生命力。
在莫言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子贴在白球墩上,如同粉墙上的壁虎一般,一下呲溜到水槽内,将羊角锤摸上来。
迅速爬出水槽、直接钻井桥洞,最后消失不见。
”[1]“呲溜”不仅是一个拟声词,还是一个动词,能够直接将人物的重点与特性凸显出来,增加小说的生动性。
使用拟声词充当实词,能够提升场景的生动性与逼真性。
(二)色彩感觉模拟色彩词语的大量使用,属于莫言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感觉化语言的鲜明特点,能够给人视觉、听觉双重感受,将色彩外鲜明的感觉呈现在读者眼前。
在莫言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使用了很多ABB叠音形式的词语,比如:红扑扑、蓝幽幽、清幽幽、油光光、黑洞洞等,这些叠加形式的词语,不仅能够强化读者的视觉效果,还能够提升小说环境的设置,将小说的重点情节全部烘托出来。
(三)其他感觉模拟除了声音、色彩感觉之外,莫言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含有大量的触觉、嗅觉、味觉描写,例如:“小黑孩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双手就会出现疼痛感,属于火急火燎的疼痛,每当出现这类情况的时候,小黑孩就会将手放在凉凉的石壁上,赶紧去回想过去的事。
莫言小说语言的艺术特色研究【摘要】莫言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其小说语言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
本文从语言表现手法、人物对话、风景描写、叙事结构和情感表达等多个方面对莫言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语言表现手法上,莫言运用生动形象的描写和言之有物的对话,展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
人物的对话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真实自然,增强了小说的生动性和可读性。
风景描写中,莫言常常运用大量细节描写和意象隐喻,呈现出独特的视角和感受。
叙事结构上,莫言常常采用非线性的叙事手法,引导读者思考。
情感表达方面,莫言善于通过细腻的描写和对比展现出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
通过对莫言小说语言艺术特色的研究,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其创作理念和文学风格,也有助于未来对其作品的深入探讨。
【关键词】莫言小说、语言艺术、表现手法、人物对话、风景描写、叙事结构、情感表达、总结、未来研究方向1. 引言1.1 背景介绍莫言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小说以其独特的语言艺术而备受瞩目。
莫言生于1955年,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力。
莫言的小说语言鲜活生动,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充满着中国乡土气息。
他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并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
莫言的小说语言丰富多彩,运用了大量的地方方言和口语,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立体。
莫言的语言表达简洁明了,情感真挚动人,引人入胜。
他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和象征手法,使作品更加富有层次感和想象力。
莫言的小说语言常常催人泪下,让读者陷入情感的波涛之中,感受到生活的真实和残酷。
莫言的小说语言艺术特色独具魅力,深受读者喜爱和推崇。
1.2 研究意义研究莫言小说语言的艺术特色具有重要的意义。
莫言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在文学界有着重要的地位,深受读者喜爱。
通过研究莫言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其创作风格和文学思想,有助于提升对莫言作品的理解和评价。
莫言小说语言的艺术特色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和变革。
41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山东 青岛266000由莫言小说的形式与内容所引起的思考——以长篇小说《酒国》为例范传兴研读文学作品,倘若只关注它的内容层面,便容易走向“大文化批评”的路数;若更关注它的形式,则又转向“新批评”的技法。
且不论两种批评方法孰优孰劣,笔者关注的却是:二者如何得兼。
莫言的《酒国》体现出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的整体性。
一、莫言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写道: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
①所谓“密度”,指“密集的事件、密集的人物、密集的思想”;所谓“难度”,指“艺术上的原创性”,“难也指结构上的难,语言上的难,思想上的难”。
莫言说,“结构就是政治”,他认为“长篇小说的结构是长篇小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家丰沛想象力的表现。
好的结构能够突显故事的意义,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单一意义。
好的结构可以超越故事,也可以解构故事”。
②由此可见,莫言的结构创新是有意识的,并且他对自己作品的结构是津津乐道的。
众所周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有一股先锋文学之风,有些作家把文学作品的形式推到了极致。
某个事物,当它的某个方面被过分放大,那就有可能走向它的相反的方向,即由原来的好转化成坏,在此,文学作品的形式创新的价值则转而走向低处。
但莫言的小说,这些年来,结构变化无常,富于创新。
我爷爷、我奶奶叙述人称的启用,意识流手法的精通,六道轮回叙述形式的巧妙借用,书信、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杂糅的写法,书信故事与剧本形式的拼嵌……这些都一次次带给读者惊讶与惊喜。
第一遍读莫言的《酒国》,叙事上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线索、情节隐匿,但这并不妨碍阅读小说片段产生的审美愉悦,包括语言、作品结构,支离破碎的情节。
《酒国》中有这样一段表述:“场景的独特性是小说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高明的小说家总是让他的人物活动在不断变换的场景中,这既掩盖了小说家的贫乏,又调动的读者的积极性。
”③这段话是意味深长的,可以从这段话出发,去研读《酒国》会有意外收获。
生命在民间──莫言《蛙》剖析张勐2009年岁末,莫言孕育了近十年的长篇小说《蛙》终于呱呱坠地。
《蛙》经由对乡土中国一部生育史的纵览、反思,折射六十年历史的风云变幻、腐朽神奇。
形式上,莫言又一次地花样翻新,将《蛙》分作五部分,前四部分采用书信体小说叙事,第五部分则选取话剧形式,由此衍生出多元繁复的叙事网络:书信体部分带出了写信人、收信人、作家之间的错综对话关系;话剧部分则在一派喜剧、闹剧形式下暗蕴着悲剧性的深层结构;书信体小说与话剧又适成“互文”,在在昭示出文本叙事基调“拟真”与“戏说”间的交错变换。
而这一系列形式迷障背后,更剪不断、理还乱的应是国家意志的“历史合理性”与民间伦理中的“生命自在性”这一对矛盾的纠缠论辩。
此外,伴随着新作的出版,莫言又在北京、上海等地做了多次演讲与访谈,这些作家自述与作品之间无形中又延展成一种新的互证、互诘的阐释空间。
鉴于此,笔者拟悉心探寻上述叙事网络结构间的种种“缝隙”,由是深入拓展,开掘小说的思想蕴藉与形式意味。
一、小说的预设读者《蛙》在文体上分别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诸封长信与一部话剧构成。
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第一人称叙事擅长“独语”,运用书信体小说形式应更适宜于“对话”。
然而,若将《蛙》称之为“书信体小说”,每封“书信”与“小说”却都是割裂的,其语体亦截然有别:前者取知识分子话语,略带学生腔;后者主要取民间话语。
除却个别段落作者有意透露“知识分子或其他角色与民间人物交错进行的”叙事体那未及缝合的针脚处①──如“我母亲”与“有文化的哥哥”的复调式表达;就整体而言,知识分子叙事已如洪炉化雪,不露痕迹地融入了民间叙事中。
在小说部分中,叙事者径自滔滔不绝,言说间鲜有与收信者的直接思想情感交流。
如是,令人不免猜度莫言之所以采用书信体小说言说的动因与目的。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则是部分批评家所指出的:这是“莫言向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种‘献媚’策略”②。
众所周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与莫言情同谊深,他曾多次谈及,莫言将是中国诺贝尔文学奖最有竞争实力的候选人。
莫言小说意象研究莫言,当代中国最为杰出的作家之一,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深入人心的主题,多次斩获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
他的作品不仅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也展现了他对人类内心世界的独到见解。
在莫言的小说中,意象研究不仅是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也是他探索人类内心世界的关键工具。
在莫言的小说中,意象的运用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
他通过对自然、人物、社会现象等具体形象的描绘,将抽象的内心情感和思想转化为具象的视觉形象,让读者通过感性的认识去理解理性的主题。
这种转换与贯通的手法,使莫言的小说充满了生命力和表现力。
以《丰乳肥臀》为例,莫言借助母亲的形象,通过对她孕育和抚养孩子的艰辛经历的描绘,表达了母爱的伟大和无私。
同时,通过将母亲与自然界的生物起来,如鸟儿、动物等,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生动而具体的意象,使读者对母爱的认识更加深入和直观。
在《生死疲劳》中,莫言通过描写主人公在六道轮回中的生死轮回,展现了他对生命的探索和思考。
他通过将人物与动物相互转换,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跨物种意象。
这种意象不仅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也呈现了生命的无常和不确定性。
而在《晚熟的人》中,莫言通过对故乡的描绘,展现了他对乡土中国的眷恋和对现代社会的反思。
他通过将人物与社会背景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具有深刻社会寓言性质的意象。
这些意象不仅揭示了社会的真实面貌,也呈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莫言小说中的意象研究,不仅是一种艺术手法,更是一种深入人心的力量。
莫言的《红高粱》是新历史小说的经典之作,通过对农村、家族、历史等关键词的深度挖掘,成功地塑造了一段生动而独特的历史图景。
在《红高粱》中,莫言通过对农村的描绘,展现了一个封闭、保守的社会环境。
小说中的村庄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世界,村民们过着简朴的生活,遵循着传统的价值观念。
这种封建氛围为故事开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社会背景,让读者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当时的历史时代特点。
在家族方面,莫言对家族历史、文化和族谱的讲述,展示了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家族体系。
莫言创作中的“深描”和“地方性知识”新探索——任红红《莫言人类学书写中的乡村世界》序张志忠获“诺奖”之后的莫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涌现出了不少高水平高质量的论著,这使当下的莫言研究日益走向深入和壮阔,呈现了一派繁荣景象。
同时,也毫不讳言,莫言研究的创新也日益困难。
当我读到任红红即将出版的专著《莫言人类学书写中的乡村世界》时,甚感欣慰。
人类学的视野,在莫言研究中已经取得积极的成果,而且还会继续成为莫言研究学术创新的一大界面。
季红真可谓最早一批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莫言小说创作,并取得了突出成就的学者。
早在1988年,她就发表了《现代人的民族民间神话一莫言散论之二》《神话世界的人类学空间:释莫言小说的语义层次》等文。
近年来,她还发表了《故事结构的古老原型一莫言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多重性表意功能之二》《大生态系统的外部形体一莫言小说女性身体的表意功能之三》《大地诗学中心灵磁场的核心故事一莫言小说的生殖叙事》等文。
如果与她1987年就将日本学者祖父江孝男的《简明文化人类学》译介到中国联系起来,她对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学问题(尤其是莫言和萧红的小说),无疑有着自觉的理论意识。
2003年,张清华发表了《叙述的极限一论莫言》的宏文,指出:“莫言的意义,正在于他依据人类学的博大与原始的精神对伦理学的冲破。
他由此张大了叙事世界的空间,几乎终结了以往文学叙事中’善一恶’、’道德一历史’冲突的历史诗学模式,也改造了人性中’道德’的边界和范畴,构建了他的’生命本体论’的历史诗学。
”-1]2015年,他又发表了《细读〈透明的红萝卜〉:童年的爱情何以合法》一文,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莫言的成名作进行颇富新见的解读。
像季红真一样,他也在不同的学术场合和文章中表达了对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莫言小说的广阔前景。
不同于季红真对莫言小说中诸如“神话”“原型”“结构”“系统”“表意”“功能”“生殖”等涉及“人类学”本源性、结构性、深层性问题的极大关注,也不同于张清华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作为揭示和探究人类的复杂精神现象标本的极大热情,任红红的专著《莫言人类学书写中的乡村世界》通过借鉴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深描”理论、克利福德&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乡村与城市》、安德鲁•郎利的《艺术为证:维多利亚时代》文化研究理论,探寻莫言小说-260-fg创作中的"深描”和“地方性知识”0探索对汉民族乡村世界的人类学知识书写的价值,及其虚构与想象中个性化书写的人类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