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百年研究
- 格式:docx
- 大小:16.63 KB
- 文档页数: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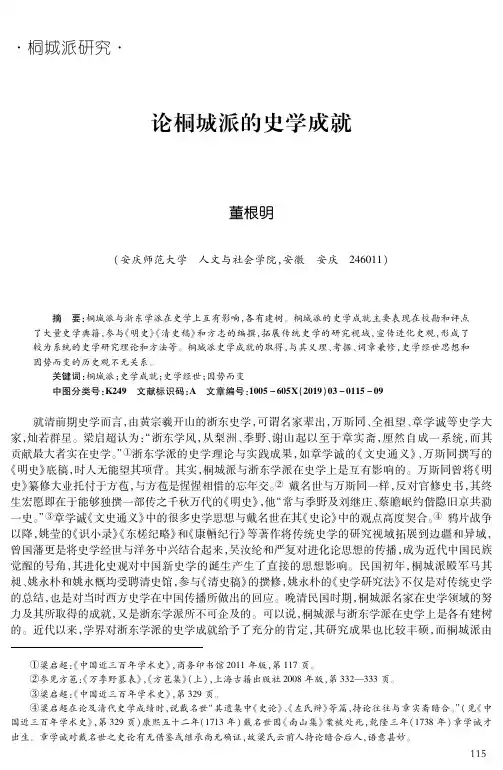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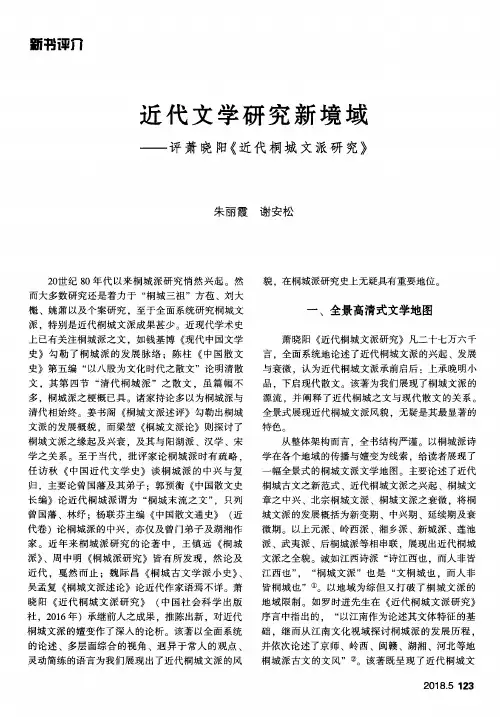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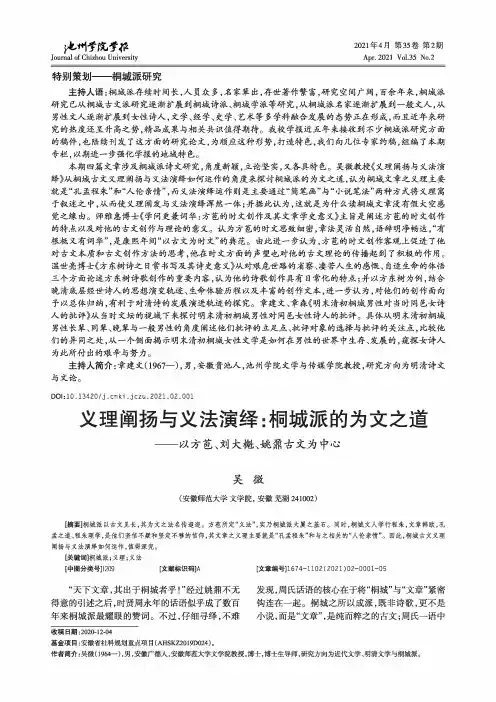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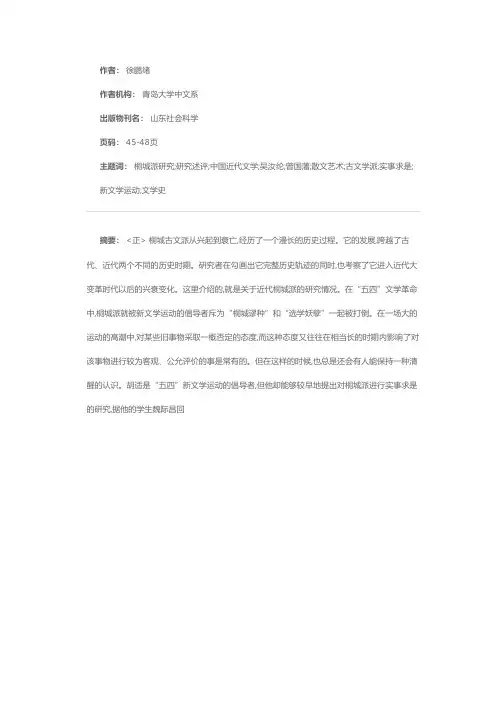
作者: 徐鹏绪
作者机构: 青岛大学中文系
出版物刊名: 山东社会科学
页码: 45-48页
主题词: 桐城派研究;研究述评;中国近代文学;吴汝纶;曾国藩;散文艺术;古文学派;实事求是;
新文学运动;文学史
摘要: <正> 桐城古文派从兴起到衰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它的发展,跨越了古代、近代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研究者在勾画出它完整历史轨迹的同时,也考察了它进入近代大变革时代以后的兴衰变化。
这里介绍的,就是关于近代桐城派的研究情况。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桐城派就被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斥为“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一起被打倒。
在一场大的运动的高潮中,对某些旧事物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又往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对该事物进行较为客观、公允评价的事是常有的。
但在这样的时候,也总是还会有人能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
胡适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但他却能够较早地提出对桐城派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据他的学生魏际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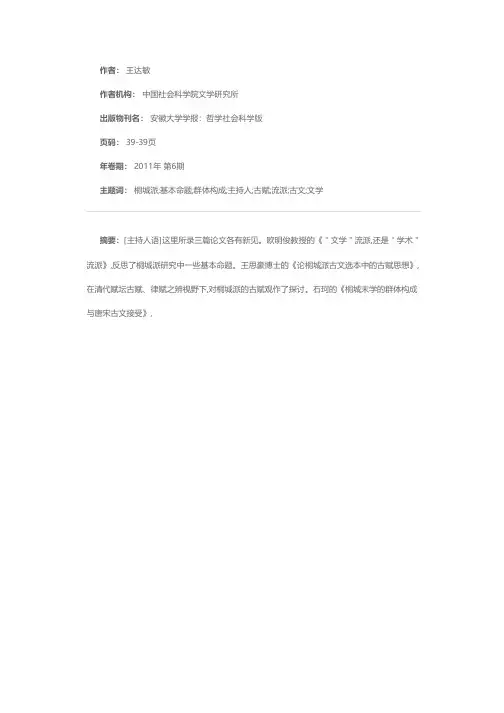
作者: 王达敏
作者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出版物刊名: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39-39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6期
主题词: 桐城派;基本命题;群体构成;主持人;古赋;流派;古文;文学
摘要:[主持人语]这里所录三篇论文各有新见。
欧明俊教授的《"文学"流派,还是"学术"流派》,反思了桐城派研究中一些基本命题。
王思豪博士的《论桐城派古文选本中的古赋思想》,在清代赋坛古赋、律赋之辨视野下,对桐城派的古赋观作了探讨。
石珂的《桐城末学的群体构成与唐宋古文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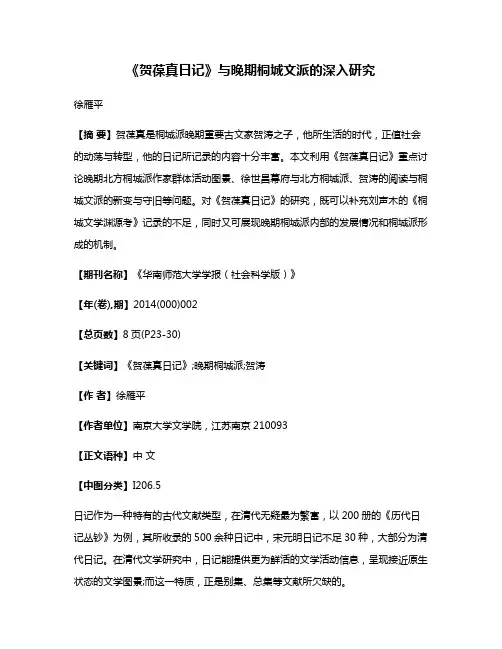
《贺葆真日记》与晚期桐城文派的深入研究徐雁平【摘要】贺葆真是桐城派晚期重要古文家贺涛之子,他所生活的时代,正值社会的动荡与转型,他的日记所记录的内容十分丰富。
本文利用《贺葆真日记》重点讨论晚期北方桐城派作家群体活动图景、徐世昌幕府与北方桐城派、贺涛的阅读与桐城文派的新变与守旧等问题。
对《贺葆真日记》的研究,既可以补充刘声木的《桐城文学渊源考》记录的不足,同时又可展现晚期桐城派内部的发展情况和桐城派形成的机制。
【期刊名称】《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4(000)002【总页数】8页(P23-30)【关键词】《贺葆真日记》;晚期桐城派;贺涛【作者】徐雁平【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5日记作为一种特有的古代文献类型,在清代无疑最为繁富,以200册的《历代日记丛钞》为例,其所收录的500余种日记中,宋元明日记不足30种,大部分为清代日记。
在清代文学研究中,日记能提供更为鲜活的文学活动信息,呈现接近原生状态的文学图景;而这一特质,正是别集、总集等文献所欠缺的。
日记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作为备忘,近似流水账,寥寥数字,不易引发阅读兴味;二是有意保存所见所闻,当作一种著述,故记录者投入心力较多,且能坚持,呈现的是一种有热情的文字。
贺葆真的日记,当列入后一类。
他用心力撰写日记,在他的日记中至少能找到五条“内证”。
考察贺氏生平,贺葆真留存于世的文字,也只有这部颇有文献和文学价值的日记。
贺葆真,字性存,生于光绪四年(1878)八月十二日,卒于1949年,①贺葆真生年,据贺培新编《武强贺氏家谱》,为光绪四年,见《武强贺氏家谱》,第118页,《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本。
然据《贺葆真日记》卷一“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葆真年十八”,则贺葆真生年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
一为家谱记载,一为日记自记,出入较大,暂不能断定何说更为确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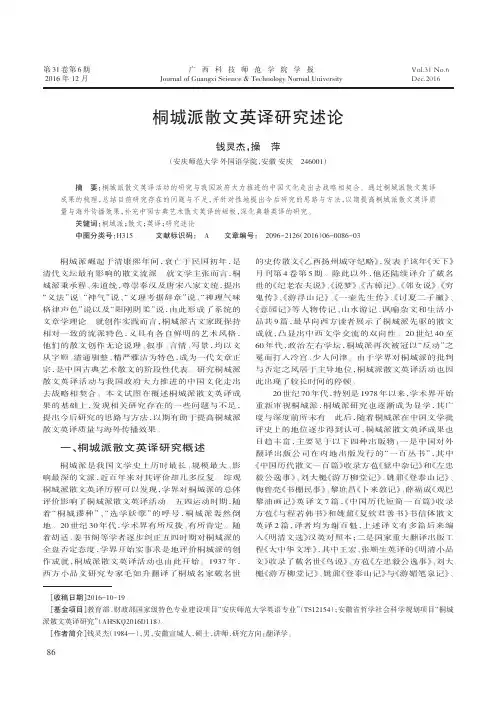
桐城派崛起于清康熙年间,衰亡于民国初年,是清代文坛最有影响的散文流派。
就文学主张而言,桐城派秉承程、朱道统,尊崇秦汉及唐宋八家文统,提出“义法”说、“神气”说、“义理考据辞章”说、“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说以及“阳刚阴柔”说,由此形成了系统的文章学理论。
就创作实践而言,桐城派古文家既保持相对一致的流派特色,又具有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他们的散文创作无论说理、叙事、言情、写景,均以文从字顺、清通驯整、精严雅洁为特色,成为一代文章正宗,是中国古典艺术散文的阶段性代表。
研究桐城派散文英译活动与我国政府大力推进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相契合。
本文试图在概述桐城派散文英译成果的基础上,发现相关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不足,提出今后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以期有助于提高桐城派散文英译质量与海外传播效果。
一、桐城派散文英译研究概述桐城派是我国文学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文派,近百年来对其评价却几多反复。
综观桐城派散文英译历程可以发现,学界对桐城派的总体评价影响了桐城派散文英译活动。
五四运动时期,随着“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呼号,桐城派轰然倒地。
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有所反拨、有所肯定。
随着胡适、姜书阁等学者逐步纠正五四时期对桐城派的全盘否定态度,学界开始实事求是地评价桐城派的创作成就,桐城派散文英译活动也由此开始。
1937年,西方小品文研究专家毛如升翻译了桐城名家戴名世的史传散文《乙酉扬州城守纪略》,发表于该年《天下》月刊第4卷第5期。
除此以外,他还陆续译介了戴名世的《纪老农夫说》、《说梦》、《古樟记》、《邻女说》、《穷鬼传》、《游浮山记》、《一壶先生传》、《讨夏二子撇》、《意园记》等人物传记、山水游记、讽喻杂文和生活小品共9篇,最早向西方读者展示了桐城派先驱的散文成就,凸显出中西文学交流的双向性。
20世纪40至60年代,政治左右学坛,桐城派再次被冠以“反动”之冕而打入冷宫、少人问津。
由于学界对桐城派的批判与否定之风居于主导地位,桐城派散文英译活动也因此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停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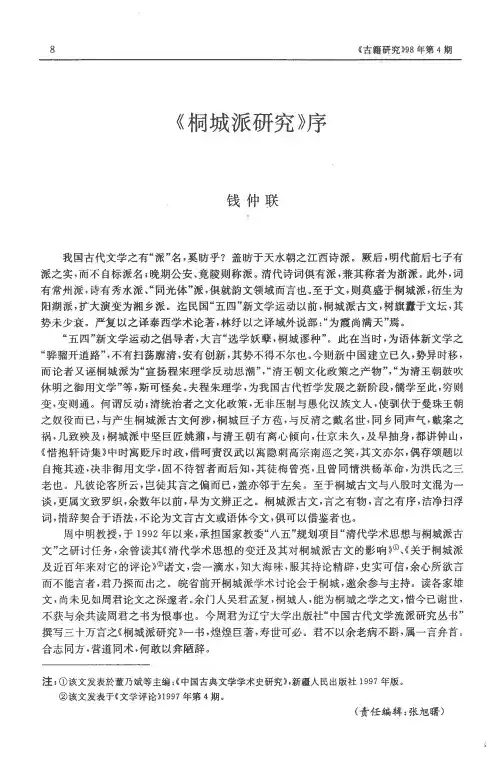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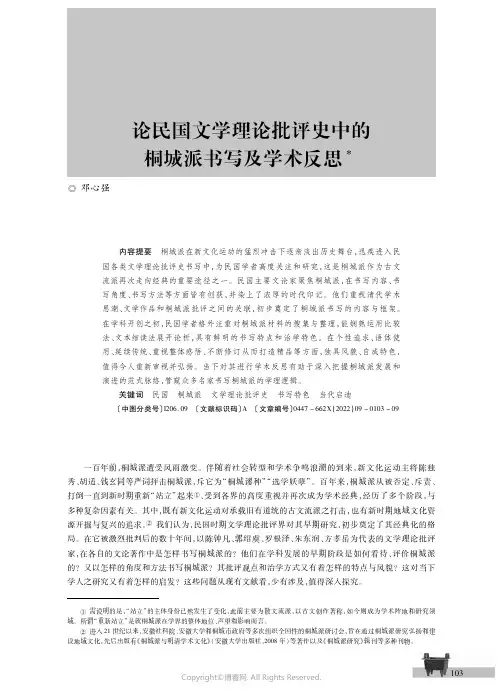
论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的桐城派书写及学术反思◎邓心强内容提要 桐城派在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下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迅疾进入民国各类文学理论批评史书写中,为民国学者高度关注和研究,这是桐城派作为古文流派再次走向经典的重要途径之一。
民国主要文论家聚焦桐城派,在书写内容、书写角度、书写方法等方面皆有创获,并染上了浓厚的时代印记。
他们重视清代学术思潮、文学作品和桐城派批评之间的关联,初步奠定了桐城派书写的内容与框架。
在学科开创之初,民国学者格外注重对桐城派材料的搜集与整理,能娴熟运用比较法、文本细读法展开论析,具有鲜明的书写特点和治学特色。
在个性追求、语体使用、延续传统、重视整体感悟、不断修订从而打造精品等方面,独具风貌、自成特色,值得今人重新审视并弘扬。
当下对其进行学术反思有助于深入把握桐城派发展和演进的范式脉络,管窥众多名家书写桐城派的学理逻辑。
关键词 民国 桐城派 文学理论批评史 书写特色 当代启迪〔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2)09-0103-09 一百年前,桐城派遭受风雨激变。
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学术争鸣浪潮的到来,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严词抨击桐城派,斥它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百年来,桐城派从被否定、斥责、打倒一直到新时期重新“站立”起来①、受到各界的高度重视并再次成为学术经典,经历了多个阶段,与多种复杂因素有关。
其中,既有新文化运动对承载旧有道统的古文流派之打击,也有新时期地域文化资源开掘与复兴的追求。
②我们认为,民国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界对其早期研究,初步奠定了其经典化的格局。
在它被激烈批判后的数十年间,以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方孝岳为代表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在各自的文论著作中是怎样书写桐城派的?他们在学科发展的早期阶段是如何看待、评价桐城派的?又以怎样的角度和方法书写桐城派?其批评观点和治学方式又有着怎样的特点与风貌?这对当下学人之研究又有着怎样的启发?这些问题从现有文献看,少有涉及,值得深入探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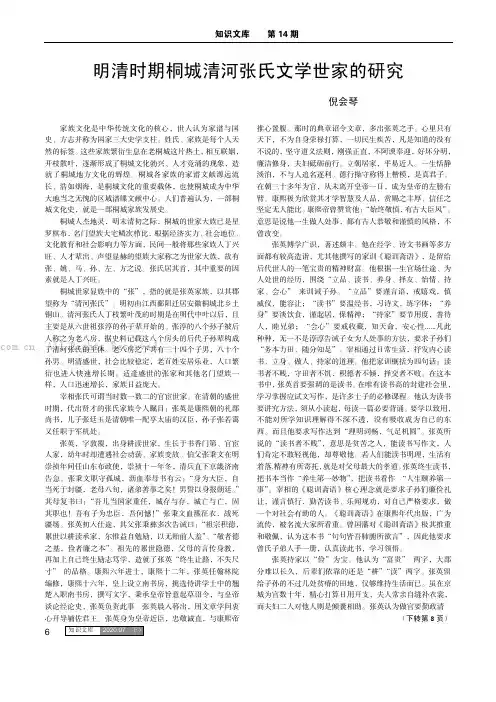
明清时期桐城清河张氏文学世家的研究倪会琴家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世人认为家谱与国史、方志并称为国家三大史学支柱。
姓氏、家族是每个人天然的标签。
这些家族繁衍生息在老桐城这片热土,相互联姻,开枝散叶,逐渐形成了桐城文化勃兴、人才竞涌的现象,造就了桐城地方文化的辉煌。
桐城各家族的家谱文献源远流长、浩如烟海,是桐城文化的重要载体,也使桐城成为中华大地当之无愧的区域谱牒文献中心。
人们普遍认为,一部桐城文化史,就是一部桐城家族发展史。
桐城人杰地灵,明末清初之际,桐城的世家大族已是星罗棋布,名门望族大宅鳞次栉比,根据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文化教育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民间一般将那些家族人丁兴旺、人才辈出、声望显赫的望族大家称之为世家大族,故有张、姚、马、孙、左、方之说。
张氏居其首,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人丁兴旺。
桐城世家显族中的“张”,指的就是张英家族,以其郡望称为“清河张氏”。
明初由江西鄱阳迁居安徽桐城北乡土铜山。
清河张氏人丁枝繁叶茂的时期是在明代中叶以后,且主要是从六世祖张淳的孙子辈开始的。
张淳的八个孙子被后人称之为老八房,据史料记载这八个房头的后代子孙辈构成了清河张氏的主体。
老八房之下共有三十四个子男,八十个孙男。
明清盛世,社会比较稳定,老百姓安居乐业,人口繁衍也进入快速增长期。
适逢盛世的张家和其他名门望族一样,人口迅速增长,家族日益庞大。
宰相张氏可谓当时数一数二的官宦世家。
在清朝的盛世时期,代出贤才的张氏家族令人瞩目:张英是康熙朝的礼部尚书,儿子张廷玉是清朝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孙子张若霭又任职于军机处。
张英,字敦覆,出身耕读世家,生长于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幼年时却遭遇社会动荡、家族变故。
伯父张秉文在明崇祯年间任山东布政使,崇祯十一年冬,清兵直下京畿济南告急。
张秉文职守孤城,沥血奉母书有云:“身为大臣,自当死于封疆,老母八旬,诸弟善事之矣!男誓以身报朝廷。
”其母复书曰:“吾儿当国家重任,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固其职也!吾有子为忠臣,吾何憾!”张秉文血溅征衣,战死疆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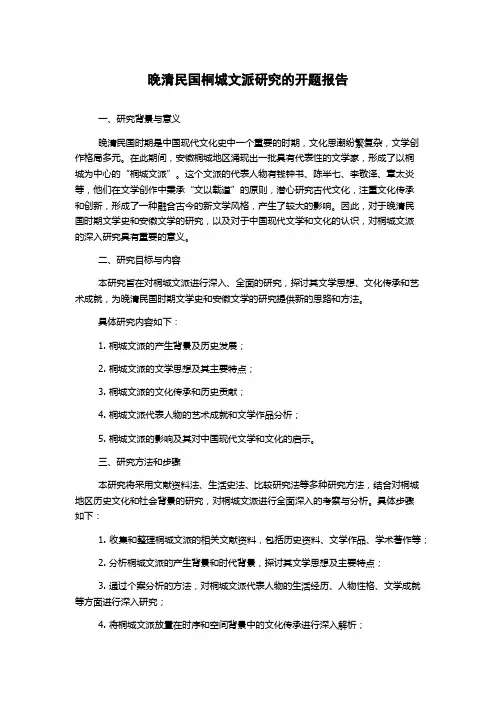
晚清民国桐城文派研究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与意义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中一个重要的时期,文化思潮纷繁复杂,文学创作格局多元。
在此期间,安徽桐城地区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形成了以桐城为中心的“桐城文派”。
这个文派的代表人物有钱钟书、陈半七、李敬泽、章太炎等,他们在文学创作中秉承“文以载道”的原则,潜心研究古代文化,注重文化传承和创新,形成了一种融合古今的新文学风格,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因此,对于晚清民国时期文学史和安徽文学的研究,以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认识,对桐城文派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目标与内容本研究旨在对桐城文派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探讨其文学思想、文化传承和艺术成就,为晚清民国时期文学史和安徽文学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具体研究内容如下:1. 桐城文派的产生背景及历史发展;2. 桐城文派的文学思想及其主要特点;3. 桐城文派的文化传承和历史贡献;4. 桐城文派代表人物的艺术成就和文学作品分析;5. 桐城文派的影响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启示。
三、研究方法和步骤本研究将采用文献资料法、生活史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结合对桐城地区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的研究,对桐城文派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与分析。
具体步骤如下:1. 收集和整理桐城文派的相关文献资料,包括历史资料、文学作品、学术著作等;2. 分析桐城文派的产生背景和时代背景,探讨其文学思想及主要特点;3. 通过个案分析的方法,对桐城文派代表人物的生活经历、人物性格、文学成就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4. 将桐城文派放置在时序和空间背景中的文化传承进行深入解析;5. 控制研究结论的误差,开展论文的撰写和分析,总结桐城文派的影响力和贡献, 并提出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的启示。
四、论文预期成果本研究的预期成果有:1. 对桐城文派的历史沿革、文学思想和文化传承做出全面深入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2. 对桐城文派代表人物的生活经历、人物性格、文学成就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对今后的个案研究提供参考资料;3. 通过对桐城文派的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认识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4. 发表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为研究生阶段的学术水平提升提供实践机会。
作者: NULL
出版物刊名: 江淮论坛
页码: 92-94页
主题词: 桐城派;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古代文艺理论;桐城派研究;新文学运动;中国文坛;安徽;最大流;散文;作家
摘要: <正> 桐城派是清代散文的一个最大流派,先后统治中国文坛二百余年,南北影响十几省,前后作家有六百余人。
桐城派自清初产生起,就毁誉繁兴,但自“五四”时新文学运动兴起,被斥为“桐城谬种”以后,除在一些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有专章进行评介外,很少专门研究和讨论。
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年间,《江海学刊》、《天津日报》、《安徽历史学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一些关于桐城派的研究、讨论文章,大都收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六三年出版的《桐城派研究论文集》中。
这以后,很少有关于“桐城派”的文章发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八○年发表了《桐城派。
作者: 周中明
作者机构: 安徽大学中文系
出版物刊名: 文学评论
页码: 111-120页
主题词: 桐城派;程朱理学;中国文学;戴名世;曾国藩;清代文化政策;桐城文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史;文学创作
摘要: 桐城派的产生是对明代“空疏不学”文风的反拨,其之所以“别树一宗”,笼盖有清一代,并非由于清代文化政策或传统势力的支持影响,更主要是因为它的理论的一定合理性。
桐城派的基本思想倾向属于封建正统、复古、保守,但这些都需要加以具体地、历史地辩证分析,全盘肯定与一笔抹倒都是不科学、不公允的。
近百年来对它的研究批评令人深思寻味,仍可进一步讨论,但应“必有史实为依据”。
《近代桐城文派研究》:桐城派研究新视域路海洋【期刊名称】《衡阳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38)004【总页数】3页(P166-168)【作者】路海洋【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正文语种】中文桐城派研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随着1985年全国第一届桐城派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一批有分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相继涌现,其中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 (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周中明«桐城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学苑出版社,2007年)等,尤为学界所推崇.近年来,桐城派研究“持续升温”,俞樟华、胡吉省«桐城派编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用编年的形式来反映桐城派的发展历程,记述桐城派上千弟子的事迹和成就”.萧晓阳«近代桐城文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则突破前人藩篱,对近代桐城文派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其学术价值毋庸置疑,尤其值得关注.本文即扼要分析萧著的特点和学术建树,谈谈它对推进新世纪桐城派研究的贡献.如果将萧著放在桐城派研究史发展历程中进行考查,不难发现,其最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第一次对近代桐城文派进行了系统论述.近百年来,研究桐城派的成果可谓夥矣,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近代桐城文派一直被“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的光焰所淹,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对此,萧著明确指出,目前学界“对于桐城派的认识尽管已经不囿于清代前期,但是学术界很少深入关注桐城派在近代的发展过程”,而实际上“自道光至于宣统,近代桐城之文先后相继,贯穿于整个近代”.基于这样的观念,萧著总体按时间先后,系统描述、探讨了近代桐城文派从兴起到衰微的整个过程.书首两部分为前言、引言.前言为全书精义之总说,引言则是对全书研究对象的内涵、外延界定及对既有研究文献的综述,为全书之缘起.主体部分共五章,依次论析了近代桐城古文的渊源、背景、传承途径与空间分布、风貌与质性嬗变轨迹,以及近代桐城古文从新范式建立到中兴、衰微的具体历程,由此构成了近代桐城文派研究比较完整的体系.萧著的全面性或说体系性,突出体现在对近代桐城文派“内涵”的立体探研上,即既从渊源、背景层面分析了近代桐城文派兴起、嬗变的文学与文化动因,又从理论观念、文学创作、文学影响层面论述了近代桐城文派内在递嬗的轨迹、面貌.尤其在对作家作品的观照上,范围和深度都较前人有所拓展、深化.萧著在引言部分概括“目前研究桐城派的困境”时提到,“近百年来学者所涉及的作家中,多关注文学大家的研究,对于与之有密切关联的作家尚未深入研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萧著依据地域将近代桐城文派分为七个主要支派,即岭西派、上元派、湘乡派、莲池派、新城派、武夷派和后桐城派,并对这七个支派的大部分代表作家进行了各有侧重的论述.萧著这方面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近代桐城文派作家进行了更加合理的“归类”;其二,对这些作家的作品风貌、特点作了更加细致的分析、揭示.这是对李详«论桐城派» (1909)、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 (1924)以来学界相关研究积累的接续和合理深化.可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如萧著第四章论述以张裕钊、吴汝纶、贺涛、王树枏等为代表的北宗桐城文派,其有两点值得肯定:第一,明确拈出“北宗桐城古文”的概念,并对各代表作家的生平、创作作了比较深入、贴切的分析,同时“对于与之有密切关联的作家”李刚己、赵衡、贾恩绂、刘春霖、宫岛大八诸人作了扼要的论析、介绍;第二,在“北宗桐城古文”内部,又将张裕钊、吴汝纶为首的莲池派与贺涛、王树枏、李刚己等北宗其他古文家区分开来.对照吴孟复先生的名著«桐城文派述论»来看,吴著将萧著提到的“北宗桐城古文”归为湘乡派的支流或说延伸,并认为“有些人过高地估价了湘乡派”,但从张、吴、贺、王等人古文创作的内在特点来看,其与曾国藩之文已有了一些内在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将“北宗桐城古文”与湘乡派古文等分开来审视,似更合理、更细致一些.可以说,萧著中此类细致研究,是对桐城派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与推进.梅曾亮在«答朱丹木书»中有一段话,学者经常引用:“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其实,“随时而变”或说因时适变,不但是梅曾亮的古文观,也是方苞、姚鼐、曾国藩等人比较一致的观点,俞樟华、胡吉省«桐城派编年»对此就有简要概述,正如周中明«桐城派研究»所论:“桐城派绵延长达二百余年,其所以有如此长的生命力,重要的内因之一,就在于它没有凝固僵化,而是不断注入活力,使之处在发展变化的动态之中.”萧著则不但将因时适变视为近代桐城文派发展演变的基本特点,而且全书的论述都紧紧围绕这个特点来展开.为了把握桐城文脉因时适变的特征,萧著从文学史的高度对近代桐城文派的发展进行了俯瞰式的考察.如在论桐城“义法”之嬗变时,萧著首先指出,“自桐城派之初创,到桐城之文之陵替,‘义法’说的内涵在不断丰富、演变”;其次,分三个阶段依次概括了桐城“义法”的演变,即初创时期的以辨理论事为宗、定型时期的翰藻义理兼备、分化时期的涵融各体之文,这一分析是符合实际的.“义法”是桐城古文的核心概念,“义法”内涵的丰富、演变对应着创作内容、形式、风格特点的转变,萧著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近代桐城文派研究»的主体部分,作者就以此作为内在理路,比较清晰地展示出了道光以降桐城古文流变的面貌.其中对以梅曾亮为代表的道咸上元派、岭西派古文的论析,颇具典型性.萧著认为,梅曾亮是推动近代桐城古文实现内在转变的第一位宗师,他引骈入散、写作诗化的古文,建立了桐城古文的新范式:“近代古文新范式实始于梅曾亮化雅从俗之文.”“梅曾亮的古文继承了江南文化中的诗性感悟、宣城诗文中诗画之境.甚至弹词之情韵与明清小说中细腻的表现方式也在其古文中得到了体现,古文体式倾向骈偶化与诗境化.”而道咸之际文风之丕变,无疑与梅曾亮引骈入散、引俗入雅、以诗入文的古文范式相关涉,萧著«前言»所谓“岭西朱琦、龙启瑞、王拯、彭昱尧与龙继栋等山水之文得其(梅曾亮)诗境之美”“梅曾亮与邵位西、孙衣言等人酬答,文辞不废绮丽,许宗衡以情韵之文主盟京师文坛,与朱琦、叶润臣、冯鲁川、杨汀鹭、潘祖荫、孙衣言等人文酒宴会,切磋艺文,为上元文章嫡传.”甚至曾国藩的时务之文与梅曾亮之文也有内在的关联.由此,梅曾亮在桐城古文发展史上的地位、影响,基本得到厘清.事实上,结合萧著对道咸以降各阶段桐城古文发展的论述,我们基本能够把握近代桐城古文对清代前期桐城之文的“内涵更新”问题,这一研究比前人走得更远.当然,萧著对近代桐城文派因时适变性质的考查,并未仅局限于桐城古文系统本身,而是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大的“野心”,那就是希望从古今文学演变的角度,揭示桐城古文向现代白话散文嬗变的内在可能性,这在全书的“结语”中有清楚体现:“纵观中国近现代散文之嬗变,在近百年间,散文经历了从桐城古文、逻辑文到现代美文的演进;在嬗变中伴随着语言形式由古文、俗语到白话的渐变,文章主旨由表达群体意志、叙述客观现象向抒写个人情思转变;表明散文精神经历了由道德法则、逻辑祈向到审美维度的演进,近现代散文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近代散文在向营构意境的美文嬗变过程中,注入了现代人文精神,为现代散文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空间.”客观地讲,萧著对桐城古文尤其近代桐城古文向现代散文嬗变趋势的分析,是全面、细致、公允而值得充分重视的.近代桐城文派的发展、演变,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多维面相的文化现象,要想深入揭示这一现象的面貌和意义,仅从文学的视角来探研显然是不够的,这是学界共识.近百年来,桐城派研究者们已经从文学及学术文化、社会政治与文学关系等角度,对桐城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对桐城派学术渊源的梳理、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对桐城派与学术及人文地理关系的考查、周中明«桐城派研究»对桐城派与清代文化政策、学术思想及程朱理学关系的论析,都比较有代表性.萧著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视角,这首先体现在从地域和家族文化的角度,立体观照近代桐城文派.书中对江南文化包括书院传授、地域性文酒之会助益近代桐城文学发展的扼要考查,对不同地域古文圈的“归类”、分析,对梅曾亮古文创作家族文化背景和姚濬昌家族古文传承的探研,都有代表性.如在对梅曾亮古文濡染家风的研究中,萧著简要梳理了梅曾亮的“家学文章”,指出梅氏先祖梅鼎祚、曾祖榖成、祖文鼎、伯祖鉁、父冲、母侯芝、外祖侯学诗、舅侯云锦等所形成的家族门风,对梅氏古文兼擅骈俪之美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对曾亮母侯芝“骈俪生色”的弹词创作之于梅氏古文骈俪倾向影响的分析,尤有新意.应当说,萧著对梅曾亮古文家族背景的分析,超迈前人、成效显著.萧著的研究视角除了地域、家族文化,当然也包括前人已经涉及的社会政治、学术文化、师友传承等.比前人做得更好一些,主要是通过师友传承梳理,更加清晰地呈现出了近代桐城古文文脉传衍的面貌,这在萧著主体部分有充分展现,不详述.如果将前面讲的“多维度”从研究视角扩展到广义的研究思路、方法角度,那么我们还能看出萧著的另外一些特点.这里重点说一个方面,即历时性论述与共时性总结相结合.历时、共时考查相结合,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不过要想做到得当、有效的“结合”并非易事,萧著在这一点上是做得比较好的.就框架结构而言,«近代桐城文派»大体分为两部分,前言、引言、第一章是一部分,第二到第五章是另一部分.前者厘清研究对象内涵、渊源、背景及总体风貌、特点,属共时性考查,后者具体呈现近代桐城古文嬗变历程,为历时性考查;前者既展现出后者发展、演变的“历史语境”,又总结出后者推衍的内在依据,后者则既不断回应前者,又具体印证、发挥前者的论断.如此前后结合、“双管齐下”,使读者对近代桐城文派的内、外两方面的面貌、特征有了颇为深入的了解.这样的“结合”确实得当而有效.总的说来,萧晓阳«近代桐城文派研究»第一次对近代桐城文派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研,视角新颖、视野宏阔、方法得当,抓住了近代桐城文派嬗变的关键特征,揭示出一些在以前隐而未彰的事实,得出了一系列客观、可信的结论,解决了不少重要学术问题.在继承中有新拓展、新建树,将近百年以来的近代桐城文派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罗时进教授在«序»中有这样评述:“作为近代桐城派研究的新创获,相信在桐城派学术史上,在近代文学研究中,这本专著自会引起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已经指出了萧著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意义,本文所论萧著的全景式的风貌、俯瞰式的描述、多维度的演绎正是这一评述的注释. «近代桐城文派研究»或有其不足之处,然其优点与建树人所共见:它不只是开辟了桐城派研究的崭新视阈,无疑也是二十一世纪桐城文派研究的一部力作,标志着桐城文派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者系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桐城派文化的创新与现代传承研究作者:陆一李以晨汪宇来源:《科学与财富》2020年第23期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更新,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加需要我们新一代去传承和创新。
桐城派文化,是我国清朝最大的散文流派,也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铜陵市,作为桐城派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责任有义务地对桐城派文化进行传承创新。
将桐城派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与校园、教育、地域特色以及旅游业相结合成为了我们的主要工作。
本文主要任务是解决桐城派文化在铜陵学院以及铜陵市的传承创新问题。
在该文中,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铜陵市的地域特色,从校內和校外两个方面,对桐城派文化在铜陵地区的发展给出了实用的建议,并对桐城派文化的发展对铜陵学院、铜陵市的发展所能产生的影响给出了一定的见解。
关键词:传承;创新;教育;专业特色;地理优势;旅游业桐城派是清代文学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流传地域最广、人数最多、影响最深的散文流派[1],被后世称“桐城古文派”,亦称“桐城派”。
它以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
桐城派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一座历史丰碑。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对于优秀的历史文化,尤其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桐城派文化经过了历史的打磨和检验,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
秉持着文化创新与传承的精神,我们应采取相关措施促进桐城派文化传承创新和地区发展。
一、发掘可利用的教学资源。
铜陵学院作为铜陵市唯一的高等院校,应该主动地发挥其教育资源的最大价值。
(一)铜陵学院可以通过整合校内的教学资源,开设专业的桐城派文化课程,对校内的桐城派文化研究成员开设必要的桐城派文化专业知识培训,对桐城派文化感兴趣的同学们,也可学习相关的桐城派文化选修课程。
桐城派百年研究
其昶、姚永概、姚永朴交谊深厚,但他的散文理论却与桐城派针锋相对,力辟文章宗派之说。
其《论桐城派》一文详叙桐城派源流,指出桐城末流仅重视起承转合、形式结构、文言虚词,不过是八股文的变种而已(注:《国粹学报》第49期。
)。
其后在致钱基博、陈含光、王翰芬、孙德谦、张江裁、王渥然等人的信中,屡屡抨击桐城派,影响甚大。
他人之匡正也”(注:陈独秀:《答胡适之(文学革命)》,《新青年》3卷3号。
)受其“十八妖魔”说的影响,曾为古文阵营大将的钱玄同反戈相向,致书陈独秀赞同文学革命主张,说“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
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注:《新青年》2卷6号。
)此后,钱玄同又多次重申“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说,津津乐道,颇为自得。
稍后的傅斯年对此深表赞同,说“桐城家者,最不足观,循其义法,无适而可。
”(注: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新青年》4卷1号。
)新文化运动先驱对桐城派的全面批判与全盘否定,目的在于动摇古文正宗地位,推行白话文,建立“活的文学”、“人的文学”,在当时有其重大的
拟由沈尹默整理的姚鼐、曾国藩的著作。
1922年3月他又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一节专论曾国藩死后的桐城湘乡派,肯定古文是古文学中“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认为“唐宋八家的古文和桐城派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
”而且由于“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1935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进一步发展了自己这一观点:“姚鼐、曾国藩的古文差不多统一了十九世纪晚期的中国散文。
”“古文经过桐城派的廓清,变成通顺明白的文体。
”他曾对学生魏际昌说:“桐城派出在我们安徽,过去叫它做‘谬种、妖孽’,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呢?希望能够研究一下”(注: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后记》,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
这体现了胡适治学的求实精神,而看到桐城派在古典文学与白话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堪称胡适的一大贡献,颇能启迪后人。
同样是新文学家,周作人在“五四”落潮后,重新拾起批判的武器,对桐城派仍持否定性评价。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一长篇学术讲演中,他在批判以韩愈为首的唐宋八大家的基础上批判桐城派,认为桐城文章“比较那些假古董为通顺,有几篇还带些文学意味。
而且平淡简单,含蓄而有余味,在这些地方,桐城派的文章,有时比唐宋八大家的还好”。
但这改变不了桐城派“载道”文学、遵命文学的性质,“他们的文章统
系也终和八股文最相近”。
后来在他的散文小品中,周作人一再表达了这一看法,并被不少学人认同。
朱自清在其名作《经典常谈》中言及桐城派与八股文的关系,指出:“明、清两代的古文大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八股文出身的,清代中叶,古文有桐城派,便是八股文的影响。
”“方苞受八股文的束缚太甚”,刘大櫆姚鼐“都是用功八股文的”,以此造成桐城派文有序而“有物之言”太少。
此论在当时学界颇具代表性。
了详尽而合乎实际的描述。
钱基博对桐城派各时期近20位代表作家别集进行了认真研读,撰写了近10万字的心得,将其附录于所著《中国文学史》后,对各家师承、创作风格、艺术特色进行了精当的点评。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他详细论述了多位桐城派后期作家作品产生的来龙去脉和生活基础,从深广的历史背景中探讨“文章得失升降之故”,其中网罗各家遗闻遗事颇多,体现了钱基博知人论世的文学史观。
此外,钱氏关于桐城派的专论还有《复陈赣一先生论桐城文书》、《〈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黄仲苏先生〈朗诵法〉序》等。
章贵‘简’贵‘疏’,反对‘繁密’;刘大櫆详论‘去陈言’之法;林纾主张学古人当知古人之病;诸如此类,都有可取之处。
”(注:舒芜:《〈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点校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这种否定桐城派政治倾向而肯定其文学主张的立场,虽不无偏颇,但在当时很有代表性。
与“中体西用”论》,周中明:《呼吁重新评价桐城派》,钱念孙:《桐城派的逆向研究》,均见《安徽史学》1995年第2期。
)。
综观这20多年来的桐城派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的收获。
第一,研究成果数量繁富,形式多样。
复林纾诗文选译》,梧桐整理的
派名家的文学主张与创作风格,结合时代背景和文章实例,析其异同,明其流变。
为彰显桐城派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何著开篇回顾了清代以前中国散文在“在载道与崇文的两难选择中”艰难跋涉的历程,以“晚辈学人对桐城文派的缅怀”为终章,大胆断言:“无论在体裁、内容的规定上,还是在表现手法、语言文字上,桐城散文都扮演了从古代散文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散文的中介者的角色。
”这就把胡适、姜书阁言而未明的观点完全揭示出来并推进了一大步。
杨怀志、江小角主编的《桐城派名家评传》,选择22位名家作为论述对象,对其生平事迹、思想倾向、文论主张、创作实践和历史贡献,一一予以系统的介绍、分析和评衡。
提要钩玄,史论融贯,被誉称“为桐城派研究领域贡献了一项创造性的成果。
”周中明白1992年起承担国家教委“八五”规划
项目“清代学术思想与桐城派古文”的研究任务,发表了《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及其对桐城派古文的影响》《、关于桐城派及近百年来对它的评论》等论文。
1999年出版32万字的力作《桐城派研究》。
作者实事求是地描述了戴名世至姚永概诸家的家世生平、性格特点、思想、师承、文论建树、创作成就,对桐城派产生的地域环境、政治背景、学术风气,以及桐城派与清朝文化政策适应性和矛盾性的两面,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多发前人所未言。
更为可贵的是,周著在详细考证史料的基础上,对现行观点或吸收、或辨析、或质疑、或创新,既自成体系,又具集大成特色。
国藩为桐城派“中兴圣主”之说,以曾氏为界将桐城派划为两段,即自方苞至梅曾亮之徒为第一期,自曾国藩至吴闾生之徒为第二期。
马厚文的《桐城文派源流考》(注:《艺谭》1981年第1期。
)和何天杰的专著均持此说。
王凯符提出三段说,即第一个时期是桐城派的始创时期,时间大体在康熙乾隆年间,戴名世、方苞、刘大櫆为代表人物。
第二个时期是姚鼐和他的弟子门人活动的时期,以姚鼐为中心,多方培养和罗致人才,扩大影响,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作家集团。
第三个时期为鸦片战争
的代表人物。
姚莹所处的时代,进步思潮的主流是睁眼看世界,就这个意义上讲,姚莹仍是具有时代特色的进步思想代表之一。
嘉庆年间,桐城学风开始转型,涌现一批以青年学子为主体,以姚莹为代表的经世派人物。
这一思想文化史上的区域性现象是清代社会与学风演变的一个标识。
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收有长篇论文《姚莹交游述略》,介绍了嘉庆、道光年间与姚莹交往的十几位名士,涉及刘开、方东树、梅曾亮、管同处较多。
作者通过对这个以姚莹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考察,认为姚莹及其友辈,是嘉道间“调和汉宋”、通经致用,敦崇经世之学这一新学风的倡导者、开拓者,在他们身上,反映了学术变化的动向和时代发展的趋向。
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在义法方面,他与桐城派毫无芥蒂,但在语言、载道方面却又大相径庭。
他之所以不肯承认自己是桐城派,也不按桐城派的清规戒律行事,是出于自知之明与写作自由的追求,桐城中人引他为知己,是出于统一战线的考虑,外人把他列为桐城派,则是不很美丽的有意的“误会”。
曾宪辉的《林纾文论浅说》(注:《福建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
)对林纾的文论体系进行了精细分析,认为从林纾的尊尚对象、讲意境和守义法、以阳刚阴
论》(《新亚学报》第16卷,1993年版)和《桐城派在清代兴盛的原因》(《台北华学月刊》1980年第104、105期),周启赓《桐城派文论》(陈国球主编《香港地区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版),邝健行《方苞与戴名世》(《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学报》1990年第20卷)、《桐
城派前期作家对时文的观点与态度》(《新亚学报》第3卷,1980年版),叶龙《桐城古文略论》(《大陆杂志》1966年第32卷,第12期)和《林纾的古文及其与桐城派的区别》(《香港新亚生活》第9卷,第8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