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坚简介
- 格式:ppt
- 大小:4.92 MB
- 文档页数: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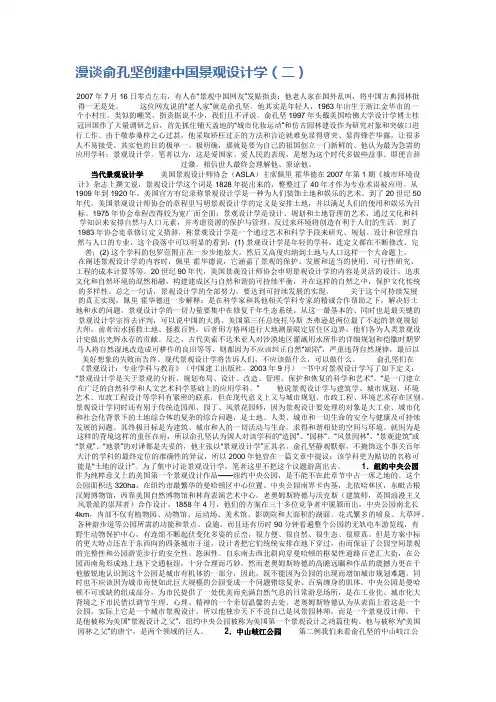
漫谈俞孔坚创建中国景观设计学(二)2007年7月16日零点左右,有人在“景观中国网友”发贴指责:他老人家在国外乱叫,将中国古典园林批得一无是处。
这位网友说的“老人家”就是俞孔坚。
他其实是年轻人,1963年出生于浙江金华市的一个小村庄。
类似的嘲笑、指责据说不少,我们且不评说。
俞孔坚1997年头戴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桂冠回国作了大量调研之后,首先抓住铺天盖地的“城市化妆运动”和仿古园林建设作为研究对象和突破口进行工作。
由于敬恭桑梓之心过甚,他采取矫枉过正的方法和言论就难免显得唐突、显得锋芒毕露,让很多人不易接受。
其实他的目的极单一、极明确,那就是要为自己的祖国创立一门新鲜的、他认为最为急需的应用学科:景观设计学。
笔者以为,这是爱国家、爱人民的表现,是想为这个时代多做些益事。
即便言辞过激,相信世人最终会理解他、原谅他。
当代景观设计学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主席佩里·霍华德在2007年第1期《城市环境设计》杂志上撰文说,景观设计学这个词是1828年提出来的,整整过了40年才作为专业术语被应用。
从1909年到1920年,美国官方有纪录称景观设计学是一种为人们装饰土地和娱乐的艺术。
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的章程里写明景观设计学的定义是安排土地,并以满足人们的使用和娱乐为目标。
1975年协会章程改得较为宽广而全面:景观设计学是设计、规划和土地管理的艺术,通过文化和科学知识来安排自然与人口元素,并考虑资源的保护与管理,反过来环境将创造有利于人们的生活。
到了1983年协会宪章修订定义措辞,称景观设计学是一个通过艺术和科学手段来研究、规划、设计和管理自然与人口的专业。
这个段落中可以明显的看到:(1) 景观设计学是年轻的学科,连定义都在不断修改、完善;(2) 这个学科的包罗范围正在一步步地放大,然后又高度归纳到土地与人口这样一个大命题上。
在阐述景观设计学的内容时,佩里·霍华德说,它涵盖了景观的保护、发展和适当的使用、可行性研究、工程的成本计算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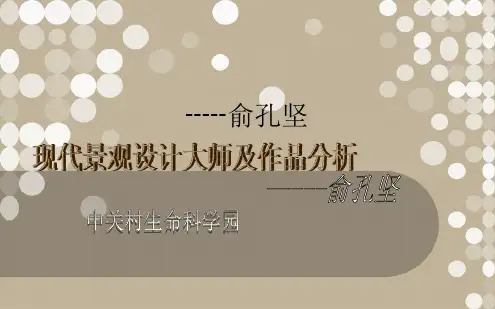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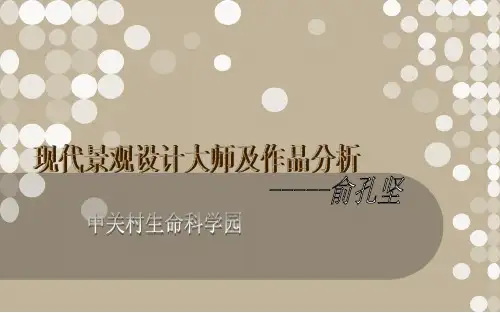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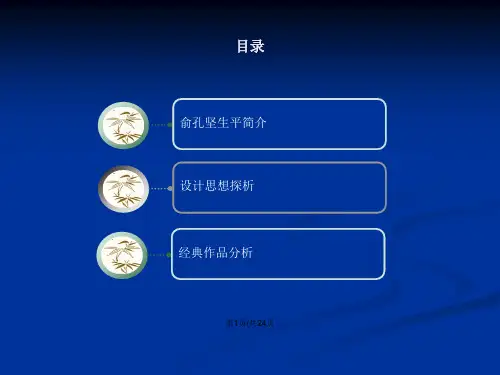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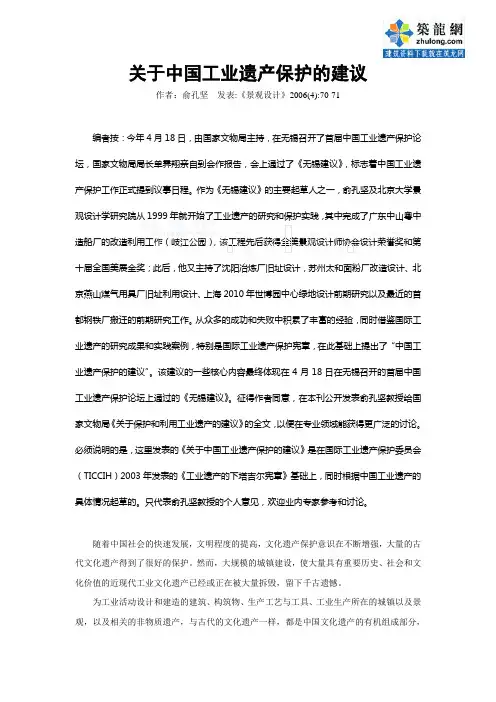
关于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建议作者:俞孔坚发表:《景观设计》2006(4):70-71编者按:今年4月18日,由国家文物局主持,在无锡召开了首届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亲自到会作报告,会上通过了《无锡建议》,标志着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工作正式提到议事日程。
作为《无锡建议》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俞孔坚及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从1999年就开始了工业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实践,其中完成了广东中山粤中造船厂的改造利用工作(岐江公园),该工程先后获得全美景观设计师协会设计荣誉奖和第十届全国美展金奖;此后,他又主持了沈阳冶炼厂旧址设计,苏州太和面粉厂改造设计、北京燕山煤气用具厂旧址利用设计、上海2010年世博园中心绿地设计前期研究以及最近的首都钢铁厂搬迁的前期研究工作。
从众多的成功和失败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借鉴国际工业遗产的研究成果和实践案例,特别是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宪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建议”。
该建议的一些核心内容最终体现在4月18日在无锡召开的首届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上通过的《无锡建议》。
征得作者同意,在本刊公开发表俞孔坚教授给国家文物局《关于保护和利用工业遗产的建议》的全文,以便在专业领域能获得更广泛的讨论。
必须说明的是,这里发表的《关于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建议》是在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2003年发表的《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基础上,同时根据中国工业遗产的具体情况起草的。
只代表俞孔坚教授的个人意见,欢迎业内专家参考和讨论。
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文明程度的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在不断增强,大量的古代文化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然而,大规模的城镇建设,使大量具有重要历史、社会和文化价值的近现代工业文化遗产已经或正在被大量拆毁,留下千古遗憾。
为工业活动设计和建造的建筑、构筑物、生产工艺与工具、工业生产所在的城镇以及景观,以及相关的非物质遗产,与古代的文化遗产一样,都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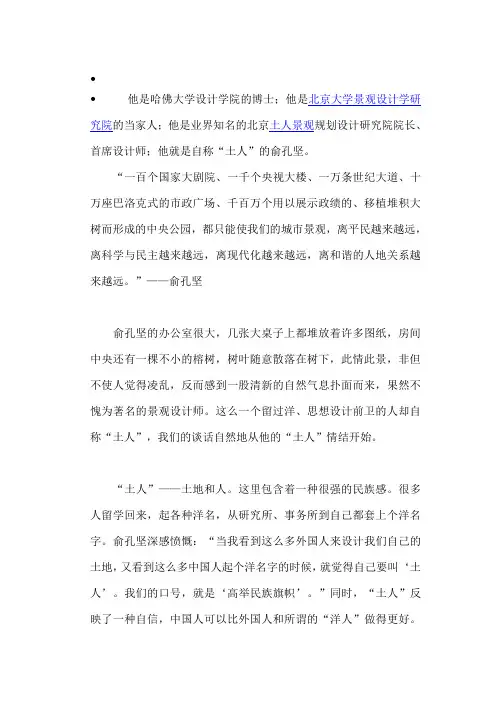
∙∙他是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博士;他是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的当家人;他是业界知名的北京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首席设计师;他就是自称“土人”的俞孔坚。
“一百个国家大剧院、一千个央视大楼、一万条世纪大道、十万座巴洛克式的市政广场、千百万个用以展示政绩的、移植堆积大树而形成的中央公园,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越来越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越来越远。
”——俞孔坚俞孔坚的办公室很大,几张大桌子上都堆放着许多图纸,房间中央还有一棵不小的榕树,树叶随意散落在树下,此情此景,非但不使人觉得凌乱,反而感到一股清新的自然气息扑面而来,果然不愧为著名的景观设计师。
这么一个留过洋、思想设计前卫的人却自称“土人”,我们的谈话自然地从他的“土人”情结开始。
“土人”——土地和人。
这里包含着一种很强的民族感。
很多人留学回来,起各种洋名,从研究所、事务所到自己都套上个洋名字。
俞孔坚深感愤慨:“当我看到这么多外国人来设计我们自己的土地,又看到这么多中国人起个洋名字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要叫‘土人’。
我们的口号,就是‘高举民族旗帜’。
”同时,“土人”反映了一种自信,中国人可以比外国人和所谓的“洋人”做得更好。
“这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专业理想,自己的土地要由自己来设计。
外国人可以到中国来做设计,中国人也可以走出去。
”决不轻言放弃俞孔坚是浙江金华老家的第一个大学生,怀揣着母亲交给他的一包家乡的泥土进入了北京林业大学园林系。
大学的生活很艰苦。
俞孔坚一个月只有4斤米、12块钱,天天吃白菜、馒头;一到夏天就想把冬天的衣服卖掉,晚上想起猪头肉就流口水。
与他比起来,城里的同学不但穿得光鲜、洋气,而且外语也很好;他一张嘴说外语就脸红。
在自卑的同时,俞孔坚学习非常刻苦,早晨最早起来看书,一个学期后,外语成绩就在班上名列第一。
然而,在大学分班时俞孔坚受到了一次很大的打击,可以说,正是这次打击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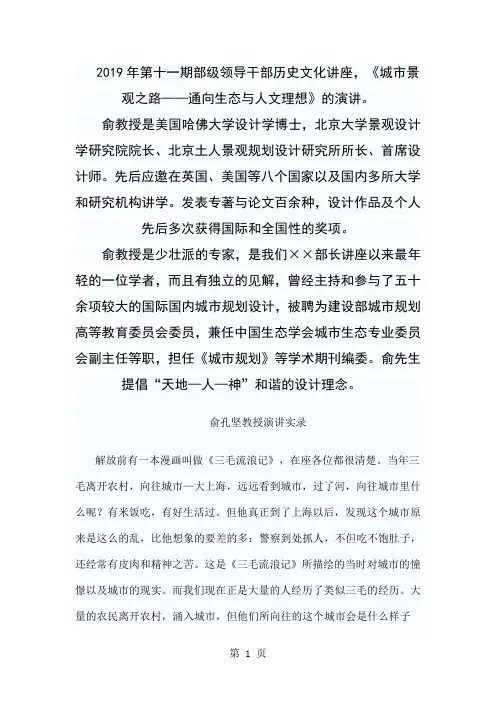
2019年第十一期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城市景观之路——通向生态与人文理想》的演讲。
俞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所所长、首席设计师。
先后应邀在英国、美国等八个国家以及国内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讲学。
发表专著与论文百余种,设计作品及个人先后多次获得国际和全国性的奖项。
俞教授是少壮派的专家,是我们××部长讲座以来最年轻的一位学者,而且有独立的见解,曾经主持和参与了五十余项较大的国际国内城市规划设计,被聘为建设部城市规划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生态学会城市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担任《城市规划》等学术期刊编委。
俞先生提倡“天地—人—神”和谐的设计理念。
俞孔坚教授演讲实录解放前有一本漫画叫做《三毛流浪记》,在座各位都很清楚。
当年三毛离开农村,向往城市—大上海,远远看到城市,过了河,向往城市里什么呢?有米饭吃,有好生活过。
但他真正到了上海以后,发现这个城市原来是这么的乱,比他想象的要差的多:警察到处抓人,不但吃不饱肚子,还经常有皮肉和精神之苦。
这是《三毛流浪记》所描绘的当时对城市的憧憬以及城市的现实。
而我们现在正是大量的人经历了类似三毛的经历。
大量的农民离开农村,涌入城市,但他们所向往的这个城市会是什么样子图-1 飞机上看杭州郊区:几乎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土地。
图-2 杭州城区:“天堂”都地狱这般,何况其它城市?杭州湾是这样,长江三角洲是这样,珠江三角洲是这样。
两大危机:民族身份与人地关系与中国城市有关的第一大危机是当代中国民族身份的危机。
我们到底是谁。
第二个就是人地关系的危机,就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地球上继续待下去。
2.1 民族身份危机所谓的民族身份就是梁启超所说的中华民族与文化“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的个性与特性。
当代中国我们要重新回答这个问题。
历史上没有这个问题,我们民族的身份很明确,我们是黄种人,我们有康熙大帝,有乾隆大帝,有故宫,有长城,这都象征着这个民族是中华民族,是个封建帝国,身份是很清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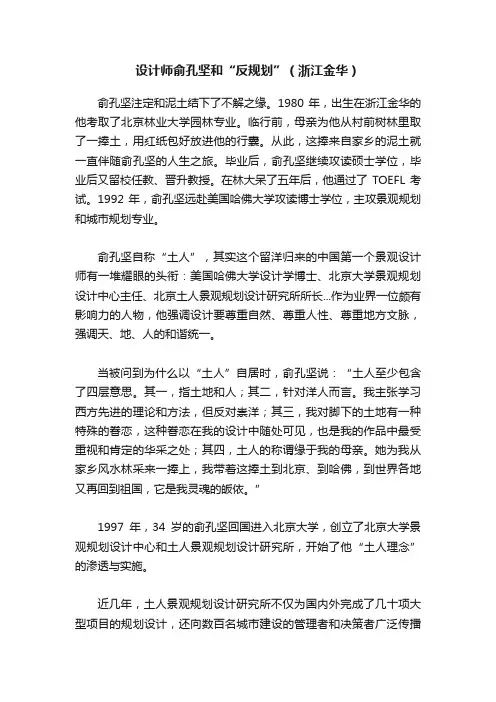
设计师俞孔坚和“反规划”(浙江金华)俞孔坚注定和泥土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0年,出生在浙江金华的他考取了北京林业大学园林专业。
临行前,母亲为他从村前树林里取了一捧土,用红纸包好放进他的行囊。
从此,这捧来自家乡的泥土就一直伴随俞孔坚的人生之旅。
毕业后,俞孔坚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又留校任教、晋升教授。
在林大呆了五年后,他通过了TOEFL考试。
1992年,俞孔坚远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攻景观规划和城市规划专业。
俞孔坚自称“土人”,其实这个留洋归来的中国第一个景观设计师有一堆耀眼的头衔: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中心主任、北京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所所长...作为业界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强调设计要尊重自然、尊重人性、尊重地方文脉,强调天、地、人的和谐统一。
当被问到为什么以“土人”自居时,俞孔坚说:“土人至少包含了四层意思。
其一,指土地和人;其二,针对洋人而言。
我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理论和方法,但反对崇洋;其三,我对脚下的土地有一种特殊的眷恋,这种眷恋在我的设计中随处可见,也是我的作品中最受重视和肯定的华采之处;其四,土人的称谓缘于我的母亲。
她为我从家乡风水林采来一捧上,我带着这捧土到北京、到哈佛,到世界各地又再回到祖国,它是我灵魂的皈依。
”1997年,34岁的俞孔坚回国进入北京大学,创立了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中心和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所,开始了他“土人理念”的渗透与实施。
近几年,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所不仅为国内外完成了几十项大型项目的规划设计,还向数百名城市建设的管理者和决策者广泛传播国际先进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开发思想。
“反规划”与城市生态建设“反规划”的提出,缘于传统城市规划编制方法的弊端。
传统的城市规划总是先预测近中远期的城市人口规模,然后根据国家人均用地指标确定用地规模,再依此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和不同功能区的空间布局,这一传统途径有许多弊端,包括:第一、法定的“红线”明确划定了城市建设边界和各个功能区及地块的边界,甚至连绿地系统也是在一个划定了城市用地红线之后的专项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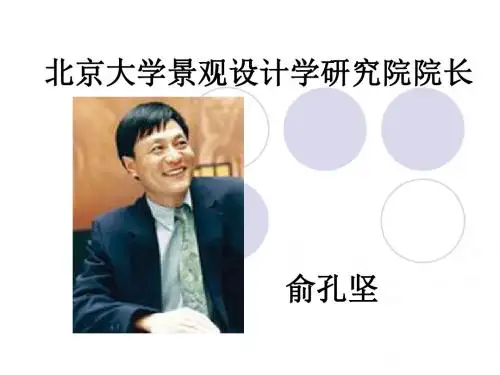

俞孔坚获年度特别贡献奖俞孔坚获年度特别贡献奖10月12日,由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指导,中国绿化基金会、人民网、绿色中国杂志社共同主办的大型公益活动“2021绿色中国年度焦点人物评选活动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
2021绿色中国年度焦点人物各奖项获得者揭晓。
其中,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院院长俞孔坚获特别贡献奖。
俞孔坚1995年获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全国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1997年回国创办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并在北京大学创办两个硕士学位点:景观设计学硕士和风景园林职业硕士。
1998年创办国家甲级规划设计单位——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目前已成为350多人的国际知名设计院。
出版著作15部,并完成大量城市与景观的设计项目;促成了景观设计师成为国家正式认定的职业,并推动了景观设计学科在中国的确立。
俞孔坚的城市和景观设计作品遍布全国和海外,曾九度获得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荣誉设计和规划奖,五次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两次获得全球最佳景观奖,两次获得国际青年建筑师优秀奖,三次获世界滨水设计杰出奖,并获2021年世界建筑奖, 2021年ULI全球杰出奖,中国第十届美展金奖等国内外重要奖项。
组委会给出的颁奖词为:他是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景观设计学家,多次获得全球性奖项;他的作品充满生态和人文的精神,他倡导“天、地、人、神”和谐的设计理念。
他创办的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不仅发展成为国际一流的知名设计院,并促成了景观设计师这一新职业的认定,为景观设计学科在中国的确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俞孔坚发表获奖感言时说,非常高兴,但同时又掩盖不了内心的忧虑,为什么?我看到的是江河在消失,湿地在死亡,地下水在下降,雾霾越来越严重,所以我想用我的知识来唤醒更多人的忧患,用我的技术和技艺来设计我们生态美丽的家园。
我们为什么非要做五十年一遇的防洪堤呢?原创2016-07-06俞孔坚俞孔坚,景观设计师,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第一个获得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荣誉设计奖的中国人,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
我们把大江大河全部裹上水泥,用无度的水利工程来试图防范我们的水患。
但水患越来越严重,裹掉了大自然的那双脚,江河自己不能调节雨涝。
2014年,俞孔坚在一席曾经分享如上的观点。
在全国大面积暴雨洪灾的当口,我们再一次推送这篇演讲给大家。
文章略有删节,建议直接看视频。
大脚革命俞孔坚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把乡下姑娘当作是土和丑的,只有是裹了脚才被认为是美的。
比如这两个姑娘的形象截然相反,一个脸很黑,脚很大,身体很结实健壮,另一个脸很白,脚很小,三寸金莲,我们一直认为后一个是典型的中国美女,腰不能站直,直了就不雅了。
中国古代对脚有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三寸叫金莲,四寸叫银莲,五寸叫铁莲,再大就嫁不出去了,只能劳动,只能在乡下干活了。
所以在中国,大家认为西施是最美的。
西施走路弯腰,是因为她有病,后来有人研究她是得了心脏病,我们怎么会把一个病态的人看成是美,而把一个健康的能干活的大脚看成是丑的呢?这是因为千百年来,美是少数城市人定义的。
少数城市贵族为了有别于乡巴佬,为了有别于乡下人,定义了所谓的美和品位,他的手段就是把正常的人变为不正常的人,把健康的人变为不健康的人,把能干活的人变为不事生产的人,这是我们对待人的审美观。
中国的五四文学革命,就是让卖豆浆和油条的语言登了大雅之堂,变成了诗歌,变成了今天的白话文,那么我今天要讲的,是关于土地的、关于我们生存环境的一场革命,一场设计的白话文革命。
大家也许会庆幸我们现在不裹脚了,为什么一百年前中国人这么傻,要把脚裹起来?也许一百年之后的人会说,今天的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傻,因为我们还在裹脚,我们的审美观仍然是小脚的审美观,我们的价值观仍然是小脚的价值观。
你们看看我们的城市,再看看我们乡下的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