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班固历史观差异比较
- 格式:doc
- 大小:32.50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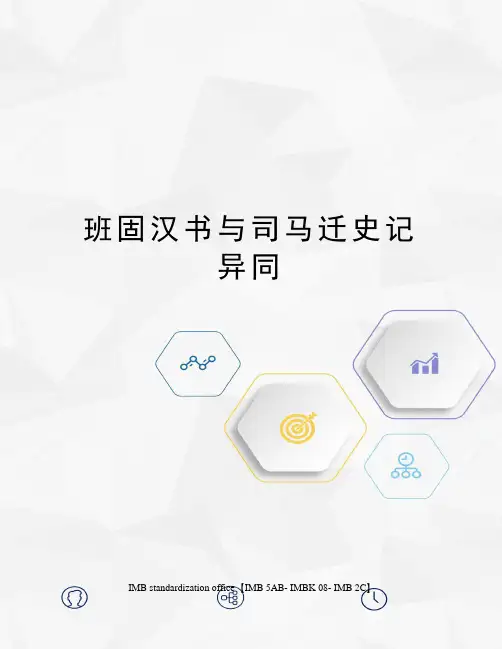
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IMB standardization office【IMB 5AB- IMBK 08- IMB 2C】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史记》与《汉书》都是我国经典的历史学巨作,同属“二十四史”,两者都是史传散文,作者都是汉代史学家,体裁均为纪传体。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汉书》的许多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
班固不仅在体例编撰上注意师法《史记》,而且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倾向。
和司马迁一样,班固在《汉书》中也对一些爱国英雄加以赞颂;其次,班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西汉王朝后期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昏庸,佞幸、外戚的横行霸道都有所批判。
和《史记》一样,《汉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史记》首创纪传体,这种体裁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历史,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有利于君主独尊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同时各种题材相互配合,又丰富了书的内容,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
此外,两书作者都有深厚的文学造诣,文采斐然,使得两部史学着作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同创于汉代的两部纪传体鸿篇巨制也存在着很多不同。
首先,体例方面,《汉书》体例基本上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从二书体例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体例的差别根本在于二人背后治史理念的差异:《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目的是为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重通变思想、重历史现实、重社会各阶层、重表现历史发展之脉络。
《汉书》重刘氏正统,用断代史、重上层社会、重正统、重体例之严谨。
从史学思想上的比较来看,司马迁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体例,本身就体现了他重视人为作用的思想,“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
而他也尝试对历史变化规律进行探讨,认为统治者应该顺应民众求利的自然之势来制定政策和组织经济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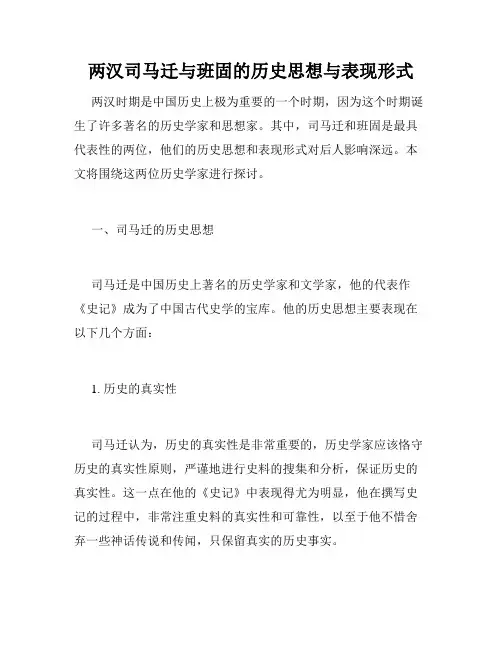
两汉司马迁与班固的历史思想与表现形式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因为这个时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
其中,司马迁和班固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位,他们的历史思想和表现形式对后人影响深远。
本文将围绕这两位历史学家进行探讨。
一、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代表作《史记》成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宝库。
他的历史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历史的真实性司马迁认为,历史的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应该恪守历史的真实性原则,严谨地进行史料的搜集和分析,保证历史的真实性。
这一点在他的《史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以至于他不惜舍弃一些神话传说和传闻,只保留真实的历史事实。
2. 历史的意义司马迁认为,历史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记录,更重要的是历史的意义。
他强调历史的价值,并通过历史对社会、人类的发展、变迁进行分析和研究。
他在史记中对于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从中提取出了历史意义,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思想。
3. 对于社会制度的观察司马迁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他对于社会的制度和变革具有很高的敏感度。
在史记中,他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进行了深入观察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见解,为后人认识中国古代历史和社会变迁提供了很大的启示。
二、班固的历史思想班固是东汉时期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代表作《汉书》是对于西汉历史的全面记录和评述。
他在历史思想方面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历史的宏大班固在《汉书》中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人物,其中涉及到了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政治斗争、军事战争等等,而且他的书写手法非常宏大,通过这种方式展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庞大和辽阔。
2. 历史的延续性班固认为,历史是一种延续性的现象,过去的历史对于现在和未来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在《汉书》中详细地记录了西汉历史的发展和变迁,通过这种方式揭示出历史的延续性,并强调历史应该得到正确的诠释和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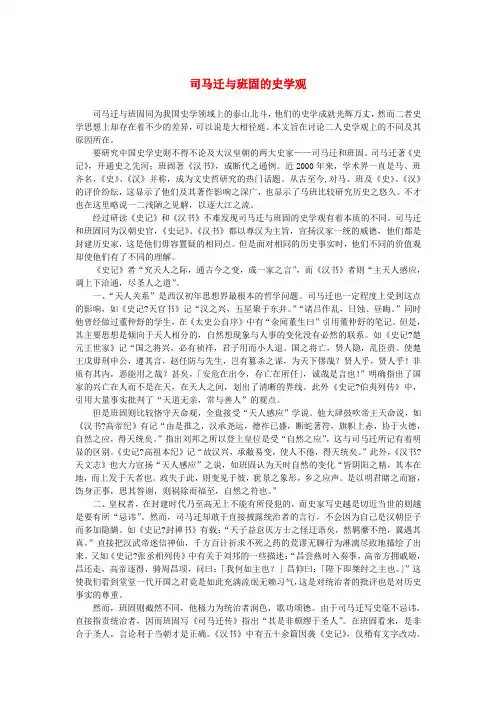
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观司马迁与班固同为我国史学领域上的泰山北斗,他们的史学成就光辉万丈,然而二者史学思想上却存在着不少的差异,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本文旨在讨论二人史学观上的不同及其原因所在。
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则不得不论及大汉皇朝的两大史家——司马迁和班固。
司马迁著《史记》,开通史之先河;班固著《汉书》,成断代之通例。
近2000年来,学术界一直是马、班齐名,《史》、《汉》并称,成为文史哲研究的热门话题。
从古至今,对马、班及《史》、《汉》的评价纷纭,这显示了他们及其著作影响之深广,也显示了马班比较研究历史之悠久。
不才也在这里略说一二浅陋之见解,以逐大江之流。
经过研读《史记》和《汉书》不难发现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观有着本质的不同。
司马迁和班固同为汉朝史官,《史记》、《汉书》都以尊汉为主旨,宣扬汉家一统的威德,他们都是封建历史家,这是他们毋容置疑的相同点。
但是面对相同的历史事实时,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却使他们有了不同的理解。
《史记》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汉书》者则“主天人感应,调上下洽通,尽圣人之道”。
一、“天人关系”是西汉初年思想界最根本的哲学问题。
司马迁也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点的影响,如《史记?天官书》记“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
”“诸吕作乱,日蚀、昼晦。
”同时他曾经做过董仲舒的学生,在《太史公自序》中有“余闻董生曰”引用董仲舒的笔记。
但是,其主要思想是倾向于天人相分的,自然想现象与人事的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史记?楚元王世家》记“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
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
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僇哉?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明确指出了国家的兴亡在人而不是在天,在天人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线。
此外《史记?伯夷列传》中,引用大量事实批判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点。
但是班固则比较恪守天命观,全盘接受“天人感应”学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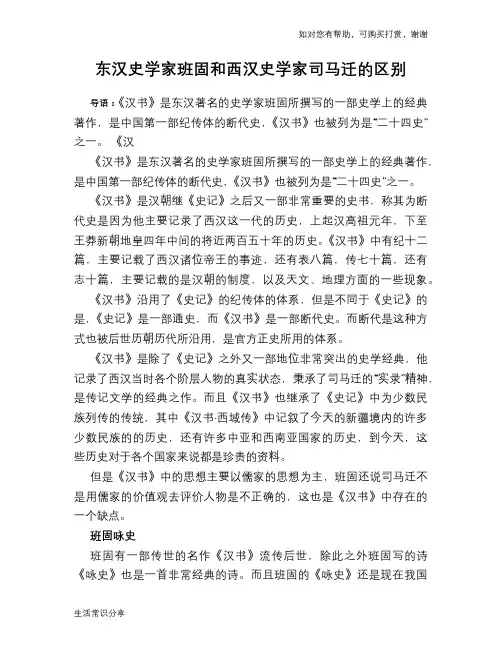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东汉史学家班固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区别
导语:《汉书》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班固所撰写的一部史学上的经典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也被列为是“二十四史”之一。
《汉
《汉书》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班固所撰写的一部史学上的经典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也被列为是“二十四史”之一。
《汉书》是汉朝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非常重要的史书,称其为断代史是因为他主要记录了西汉这一代的历史,上起汉高祖元年,下至王莽新朝地皇四年中间的将近两百五十年的历史。
《汉书》中有纪十二篇,主要记载了西汉诸位帝王的事迹,还有表八篇,传七十篇,还有志十篇,主要记载的是汉朝的制度,以及天文、地理方面的一些现象。
《汉书》沿用了《史记》的纪传体的体系,但是不同于《史记》的是,《史记》是一部通史,而《汉书》是一部断代史。
而断代是这种方式也被后世历朝历代所沿用,是官方正史所用的体系。
《汉书》是除了《史记》之外又一部地位非常突出的史学经典,他记录了西汉当时各个阶层人物的真实状态,秉承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是传记文学的经典之作。
而且《汉书》也继承了《史记》中为少数民族列传的传统,其中《汉书·西域传》中记叙了今天的新疆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的的历史,还有许多中亚和西南亚国家的历史,到今天,这些历史对于各个国家来说都是珍贵的资料。
但是《汉书》中的思想主要以儒家的思想为主,班固还说司马迁不是用儒家的价值观去评价人物是不正确的,这也是《汉书》中存在的一个缺点。
班固咏史
班固有一部传世的名作《汉书》流传后世,除此之外班固写的诗生活常识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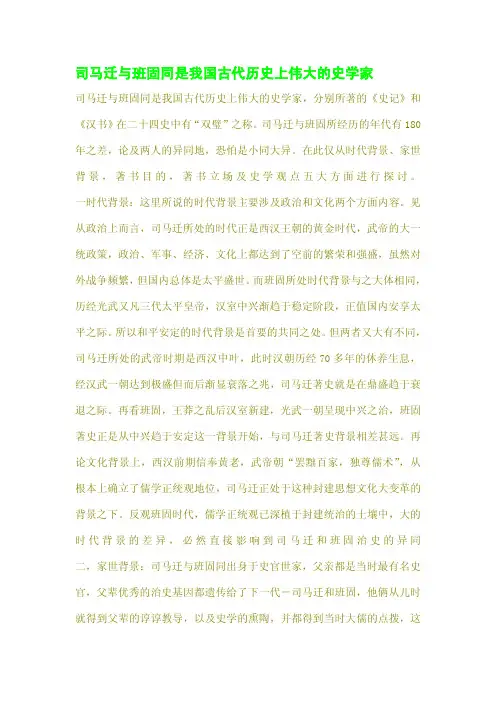
司马迁与班固同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与班固同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分别所著的《史记》和《汉书》在二十四史中有“双璧”之称。
司马迁与班固所经历的年代有180年之差,论及两人的异同地,恐怕是小同大异。
在此仅从时代背景、家世背景,著书目的,著书立场及史学观点五大方面进行探讨。
一时代背景:这里所说的时代背景主要涉及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内容。
见从政治上而言,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王朝的黄金时代,武帝的大一统政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强盛,虽然对外战争频繁,但国内总体是太平盛世。
而班固所处时代背景与之大体相同,历经光武又凡三代太平皇帝,汉室中兴渐趋于稳定阶段,正值国内安享太平之际。
所以和平安定的时代背景是首要的共同之处。
但两者又大有不同,司马迁所处的武帝时期是西汉中叶,此时汉朝历经70多年的休养生息,经汉武一朝达到极盛但而后渐显衰落之兆,司马迁著史就是在鼎盛趋于衰退之际。
再看班固,王莽之乱后汉室新建,光武一朝呈现中兴之治,班固著史正是从中兴趋于安定这一背景开始,与司马迁著史背景相差甚远。
再论文化背景上,西汉前期信奉黄老,武帝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根本上确立了儒学正统观地位,司马迁正处于这种封建思想文化大变革的背景之下。
反观班固时代,儒学正统观已深植于封建统治的土壤中,大的时代背景的差异,必然直接影响到司马迁和班固治史的异同二,家世背景:司马迁与班固同出身于史官世家,父亲都是当时最有名史官,父辈优秀的治史基因都遗传给了下一代-司马迁和班固,他俩从儿时就得到父辈的谆谆教导,以及史学的熏陶,并都得到当时大儒的点拨,这足以使他俩为后来的著史打下了深厚的功低!这是相同的一点,再说不同的,是大大的不同,就家世地位的高低和显赫来说,司马迁更显得寒酸,其父谈只是个史官,迁也是袭其父职,做的最高的官也只是中书令,家底并不殷实,朝中更无人,以致于无钱赎命只得接受腐刑。
而班固,家世显赫,其父彪乃先朝元老,资格甚老,其弟超更是经营西域有功,深得朝廷宠幸,而自身又依附于掌朝的窦氏家族,也深得皇帝宠幸,可谓是八面玲珑,与司马迁的穷酸形成鲜明对比!三,著书目的:司马迁和班固著书的初衷都是继承父志,完成其父未完之事,司马谈欲著一通史,其子司马迁子承父愿,著《史记》;班固父班彪本作《续后史记》,而未完已卒,班固在《续后史记》基础上作《汉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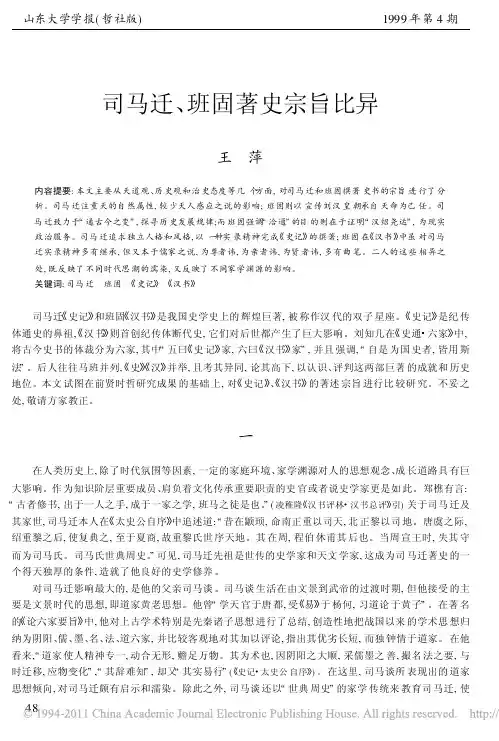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王 萍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析。
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
司马迁致力于 通古今之变 ,探寻历史发展规律;而班固强调 洽通 的目的则在于证明 汉绍尧运 ,为现实政治服务。
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 史记 的撰著;班固在 汉书 中虽对司马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但又本于儒家之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多有曲笔。
二人的这些相异之处,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
关键词:司马迁 班固 史记 汉书司马迁 史记 和班固 汉书 是我国史学史上的辉煌巨著,被称作汉代的双子星座。
史记 是纪传体通史的鼻祖, 汉书 则首创纪传体断代史,它们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刘知几在 史通 六家 中,将古今史书的体裁分为六家,其中 五曰 史记 家,六曰 汉书 家 ,并且强调, 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 。
后人往往马班并列, 史 汉 并举,且考其异同,论其高下,以认识、评判这两部巨著的成就和历史地位。
本文试图在前贤时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 史记 、 汉书 的著述宗旨进行比较研究。
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时代氛围等因素,一定的家庭环境、家学渊源对人的思想观念、成长道路具有巨大影响。
作为知识阶层重要成员、肩负着文化传承重要职责的史官或者说史学家更是如此。
郑樵有言: 古者修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
(凌稚隆 汉书评林 汉书总评 引)关于司马迁及其家世,司马迁本人在 太史公自序 中追述道: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
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
司马氏世典周史。
可见,司马迁先祖是世传的史学家和天文学家,这成为司马迁著史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他良好的史学修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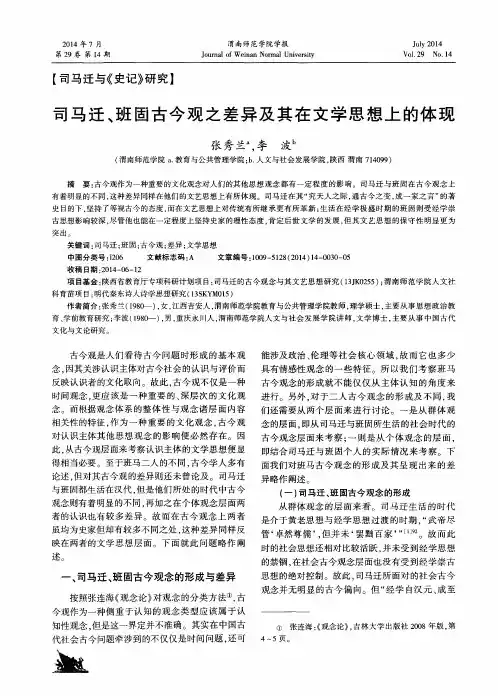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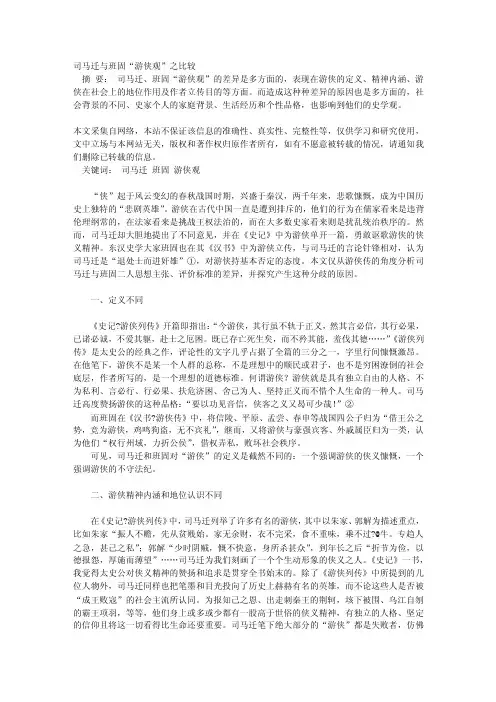
司马迁与班固“游侠观”之比较摘要:司马迁、班固“游侠观”的差异是多方面的,表现在游侠的定义、精神内涵、游侠在社会上的地位作用及作者立传目的等方面。
而造成这种种差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社会背景的不同、史家个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和个性品格,也影响到他们的史学观。
本文采集自网络,本站不保证该信息的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等,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文中立场与本网站无关,版权和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不愿意被转载的情况,请通知我们删除已转载的信息。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游侠观“侠”起于风云变幻的春秋战国时期,兴盛于秦汉,两千年来,悲歌慷慨,成为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悲剧英雄”。
游侠在古代中国一直是遭到排斥的,他们的行为在儒家看来是违背伦理纲常的,在法家看来是挑战王权法治的,而在大多数史家看来则是扰乱统治秩序的。
然而,司马迁却大胆地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在《史记》中为游侠单开一篇,勇敢讴歌游侠的侠义精神。
东汉史学大家班固也在其《汉书》中为游侠立传,与司马迁的言论针锋相对,认为司马迁是“退处士而进奸雄”①,对游侠持基本否定的态度。
本文仅从游侠传的角度分析司马迁与班固二人思想主张、评价标准的差异,并探究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
一、定义不同《史记?游侠列传》开篇即指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游侠列传》是太史公的经典之作,评论性的文字几乎占据了全篇的三分之一,字里行间慷慨激昂。
在他笔下,游侠不是某一个人群的总称,不是理想中的顺民或君子,也不是穷困潦倒的社会底层,作者所写的,是一个理想的道德标准。
何谓游侠?游侠就是具有独立自由的人格、不为私利、言必行、行必果、扶危济困、舍己为人、坚持正义而不惜个人生命的一种人。
司马迁高度赞扬游侠的这种品格:“要以功见音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②而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将信陵、平原、孟尝、春申等战国四公子归为“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继而,又将游侠与豪强宾客、外戚属臣归为一类,认为他们“权行州域,力折公侯”,借权弄私,败坏社会秩序。

司马迁和班固区别_班固评价司马迁司马迁和班固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被奉为是史学的经典。
那两人有什么区别呢?班固对司马迁作何评价?下面是店铺为你搜集司马迁和班固区别的相关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司马迁和班固区别但是二人也有一些差别,这些差别也都体现在了他们的作品上。
《史记》是一部通史,而《汉书》是一部断代史,这是一个差别也就不再多做赘述了。
另外,《史记》可以说是一本私人的著作,是司马迁的外孙将《史记》呈给皇帝,《史记》才得以被广泛的阅读。
而《汉书》则不然,因为在成书之前皇帝就已经知道班固在写这本书,到后面《汉书》都已经有一些国史的味道了,与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有着很大的差别。
另外司马迁和班固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思想差异,司马迁时期,儒家思想还没有被推倒那么高的位置,所以司马迁在评价很多历史人物的时候并没有单单用儒家思想的价值观来做单一的评价,而是加入了许多自己的看法和别人的看法。
而班固则不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班固则成为这个运动的产物。
班固已经把儒家的思想作为自己的主要思想,而且这种思想还具有排他性,因此班固开始批评司马迁没有用儒家的思想来对人物进行评价。
任何时候,思想的单一都会造成闭塞和极端,所以这也是班固和《汉书》的一个缺点。
思想的多元化也能够使文章更加的生动、更加贴近真实的历史,显然在这一点上《汉书》和《史记》比起来尤为不足。
班固评价司马迁班固是《汉书》的作者,司马迁是《史记》的作者,《汉书》和《史记》都是我国四史之一。
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是说班固对司马迁写史记的评价。
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这句话,出现在班固的《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中对司马迁以及他的著作《史记》的评价。
原句是: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弊也,予按,此正是迁之微意。
这句话的意思是: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中,很多关于是非判断方面是存在一些错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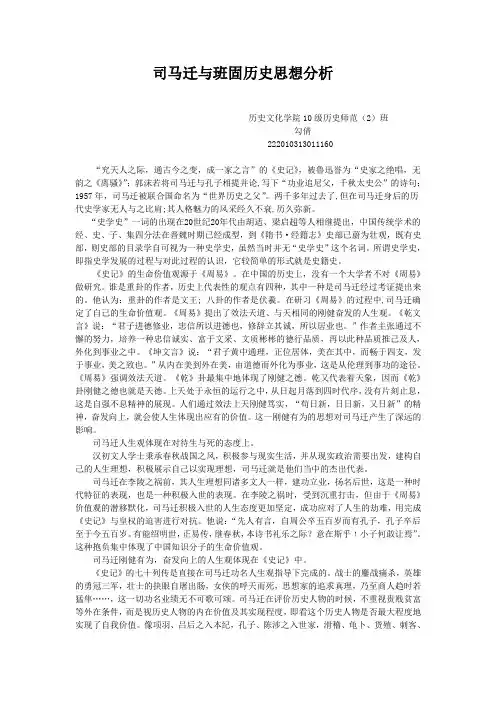
司马迁与班固历史思想分析历史文化学院10级历史师范(2)班勾倩222010313011160“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郭沫若将司马迁与孔子相提并论,写下“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的诗句;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
两千多年过去了,但在司马迁身后的历代史学家无人与之比肩;其人格魅力的风采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史学史”一词的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由胡适、梁启超等人相继提出,中国传统学术的经、史、子、集四分法在晋魏时期已经成型,到《隋书·经籍志》史部已蔚为壮观,既有史部,则史部的目录学自可视为一种史学史,虽然当时并无“史学史”这个名词。
所谓史学史,即指史学发展的过程与对此过程的认识,它较简单的形式就是史籍史。
《史记》的生命价值观源于《周易》。
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学者不对《周易》做研究。
谁是重卦的作者,历史上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其中一种是司马迁经过考证提出来的。
他认为:重卦的作者是文王; 八卦的作者是伏羲。
在研习《周易》的过程中,司马迁确定了自己的生命价值观。
《周易》提出了效法天道、与天相同的刚健奋发的人生观。
《乾文言》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作者主张通过不懈的努力,培养一种忠信诚实、富于文采、文质彬彬的德行品质,再以此种品质推己及人,外化到事业之中。
《坤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致也。
”从内在美到外在美,由道德而外化为事业,这是从伦理到事功的途径。
《周易》强调效法天道。
《乾》卦最集中地体现了刚健之德。
乾又代表着天象,因而《乾》卦刚健之德也就是天德。
上天处于永恒的运行之中,从日起月落到四时代序,没有片刻止息,这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展现。
人们通过效法上天刚健笃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奋发向上,就会使人生体现出应有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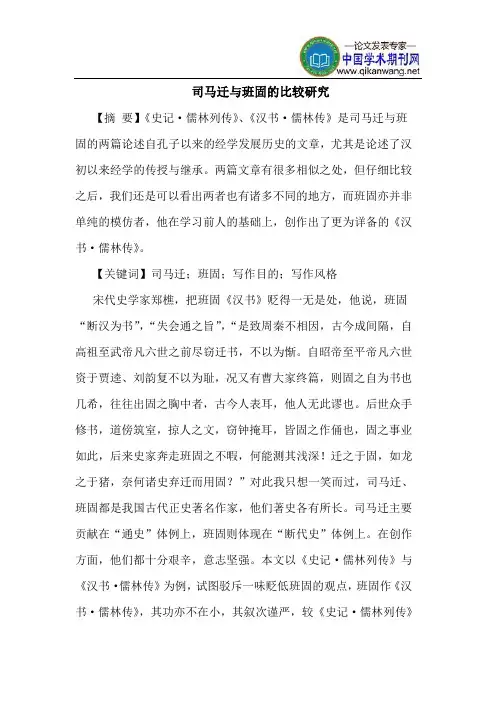
司马迁与班固的比较研究【摘要】《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是司马迁与班固的两篇论述自孔子以来的经学发展历史的文章,尤其是论述了汉初以来经学的传授与继承。
两篇文章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仔细比较之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两者也有诸多不同的地方,而班固亦并非单纯的模仿者,他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创作出了更为详备的《汉书·儒林传》。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写作目的;写作风格宋代史学家郑樵,把班固《汉书》贬得一无是处,他说,班固“断汉为书”,“失会通之旨”,“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
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韵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
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对此我只想一笑而过,司马迁、班固都是我国古代正史著名作家,他们著史各有所长。
司马迁主要贡献在“通史”体例上,班固则体现在“断代史”体例上。
在创作方面,他们都十分艰辛,意志坚强。
本文以《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为例,试图驳斥一味贬低班固的观点,班固作《汉书·儒林传》,其功亦不在小,其叙次谨严,较《史记·儒林列传》详备远甚。
一我们必须承认,《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以致与后者对前者有抄袭的嫌疑,如下面两段: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
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於齐。
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
是时独魏文侯好学。
後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於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
浅析司马迁与班固史学观的差异内容摘要:《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汉书》的作者班固是我国历史上两位重要的史学家。
虽然同为纪传体史书,但是两部书中所体现出的两位史家的史学观确实不同的。
本文将就两部史书中所体现出的二人不同的史学观进行分析,同时对二人不同史学观的形成也有所探究。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史记》/《汉书》/史学观中国历史上司马迁和班固可谓是史学上的双子星座,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分别开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的先河。
固然,作为优秀的史学家两人有着很多相似点,但是二人在史学观方面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本文将就二人史学观的不同之处进行浅析。
首先就家学渊源的差异来说,对二人史学观的形成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生活于汉初,那个时期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而司马谈也是崇尚道教思想的。
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中表现出的更多是道家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而没有一味地崇尚儒家,他还指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①这些都是和他受到其父的影响分不开的。
班固的父亲班彪也是一位史学家,他对班固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他曾撰有《王命论》,更多的是强调汉承尧运,天命有归,王者兴衰,“通篇贯穿着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的儒家经学思想”②。
再者,班固本人也是《白虎通》的撰写者,书中主要宣扬谶纬思想感应学说。
故而《汉书》中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儒家正统思想,宣扬一些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思想,而缺少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
为此,班固曾在《汉书》这样表达了他对司马迁的不满,“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叙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③“是非谬于圣人”正说明司马迁的批判精神,能够无所畏惧,信笔直书,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爱憎掩功过,更加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
而班固作为一个正统史观的史家,并且还是奉旨修书,故而书中会有不同于司马迁犀利的批判的地方。
如对于吕后,司马迁为其立本纪,主要是出于历史事实考虑,惠帝在位,实权则由吕后掌握;而班固则给惠帝另立本纪,并置于《吕后纪》前面。
中国史学史论文从《史记》《汉书》游侠传比较司马迁与班固之著史思想中国古代的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对于我们理解历史和传承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史记》和《汉书》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经典之作,代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历程和重要思想。
而其中关于游侠传的内容,更是以司马迁和班固两位史学家的著作为主要讨论对象。
本文将从《史记》和《汉书》的游侠传入手,比较司马迁和班固在史学思想方面的差异和相似之处。
首先,我们来看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被誉为中国史学的奠基人。
他的《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纪传体(记述历史实事)和表(编制历代君臣的年表)两部分组成。
他以王侯将相和大事为主线,通过纪传体的形式叙述了从五帝到西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的历史,并通过编纂历代君臣的年表,展示了千年历史的发展脉络。
与司马迁相比,班固的《汉书》在史学思想上有一些差异。
班固是东汉时期的史学家,他的《汉书》是一部以编年体为主要形式的纪传体通史。
不同于《史记》以王侯将相和大事为主要叙述对象,班固更多地关注汉朝的政治制度和文化风貌,着重描写汉朝君臣的生平事迹。
在《汉书》中,班固强调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关系,并对历史人物的品德进行评价,试图通过历史的批判和启示来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
游侠传是《史记》和《汉书》中一个共同的篇章,它记录了古代中国游侠精神的发展以及与国家政权的关系。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游侠传以陈胜吴广、刘邦和项羽等人为代表,反映了他们在战乱年代中的英雄事迹和传奇故事。
另一方面,在班固的《汉书》中,他以陈汤、陈平和翟方进等人为主要对象,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他们的游侠行为和为国家辅助和维护的情念。
虽然司马迁和班固在史学思想上有一些差异,但他们都致力于通过历史的研究和记录来展示古代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
司马迁注重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力求还原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而班固则更加关注历史人物和道德修养的关系,试图通过历史的反思来提高人们的品德。
司馬遷與班固對‘春秋“的看法及其歷史書寫的自我抉擇①戴晉新 内容提要 本文強調史家的史識與自我意識㊂古人的語言㊁語境與現代人或有差異,但是觀察他們對具體歷史問題的反應與歷史書寫的自我抉擇,還是可以比較古代史家間的異同,理解他們的思想㊂這種觀察與理解,是史學工作者之間的對話,對提升史學史的認識是有幫助的㊂在經學興盛而先秦諸侯史記亡佚的漢代, 孔子‘春秋“”具有經學與史學的雙重性質,如何看待它的經義與史義,與人們對先秦史學的認知有很大關係,同時兩者是互爲因果的㊂司馬遷與班固對‘春秋“的學術性質及歷史定位都有自己的看法,他們的看法源自他們的家學與時代,及由此産生的史學史意識㊂兩位史家在‘春秋“問題上所反映出的史學史意識與他們歷史書寫的自我抉擇有一定關係,同時也影響到我們對中國古代史學的認識,本文對此分别予以討論㊂關鍵詞 史學史 春秋學 司馬遷 班固 歷史書寫一、引 言關於‘史記“是否繼承以及如何繼承‘春秋“的問題,古今學者論辯多矣㊂大體而言,學者多以爲‘史記“與‘春秋“有某種特殊的内在聯繫,其意‘春秋“在前,‘史記“在①本文曾於 再造與衍義 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臺北 故宫博物院”㊁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㊁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合辦,2007年11月15 16日㊂今已作相當程度的修訂㊂後,‘春秋“亦經亦史,是經史典範,‘史記“不可能不受其影響㊂①學者對‘史記“的評價愈高,往往就愈覺得它非追隨‘春秋“不可,否則豈不有損‘春秋“的地位?②反之,若對‘史記“的評價愈低,就愈覺得它不配繼承‘春秋“㊂③直到近代以來,史學觀念改變,傳統經史解釋體系受到衝擊,‘史記“的史學史評價乃有與‘春秋“脱鉤,甚至轉勝‘春秋“之可能㊂事實上,‘史記“與‘春秋“在許多方面都是不同的兩部書,司馬遷選擇了自己的歷史書寫形式與風格,在經學瀰漫的漢代,他必須面對學術界,特别是公羊春秋一派學者的質疑,在他澄清‘史記“與‘春秋“的區别時,他必須處理環繞‘春秋“糾纏不清的經史關係,他對‘春秋“的歷史定位必然有自己的觀點㊂他的觀點如何,又如何影響他對‘史記“的襟抱?這是本文想要探討的問題之一㊂班固的‘漢書“受‘史記“的影響最大也最直接,是否繼承‘春秋“就没有那麽敏感,當然在文化傳承上它還是繼承‘春秋“所代表的某些價值觀念與意識型態,但是實際上它繼承‘史記“的體裁與書寫文體更爲明顯㊂班氏父子雖然批評‘史記“的某些體例與思想,但還是承認太史公爲良史,④自己作史時的基本構想還是選擇了‘史記“,在他們的選擇與判斷中當然也包括了對‘春秋“的學術定性與歷史定位㊂這是本文想要討論的問題之二㊂①②③④司馬遷在‘史記㊃太史公自序“中一方面説 繼春秋”,一方面又對壺遂説 君比之春秋,謬矣”,引起學者不同的取捨與解讀;然而自司馬貞説 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史記索隱㊃序“),張守節也説司馬遷 紹太史,繼‘春秋“”(‘史記正義㊃序“),其後調停與銓釋 繼春秋”的論述多至不可勝計㊂茲舉近人數例如下:徐復觀認爲司馬遷繼承孔子 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的精神和 以達王事而已矣”的目的;説見‘論史記“,‘大陸雜誌“55卷5㊁6期,1977年㊂楊向奎視司馬遷爲前期公羊學派的重要人物,‘史記“繼承了公羊春秋的歷史哲學,當然是一部繼‘春秋“的作品;説見‘司馬遷的歷史哲學“,‘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1期㊂阮芝生認爲司馬遷通古今之變後所得出的結論是 以禮義防于利”,這一思想仍當歸本於孔子,尤其是孔子的‘春秋“;説見‘試論司馬遷所説的 通古今之變”“,‘沈剛伯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㊂阮氏又説司馬遷 究天人之際”的思想乃從孔子義命之學轉手而來;説見‘試論司馬遷所説的 究天人之際”“,‘史學評論“第6期,1983年㊂杜維運認爲 究天人之際”與 通古今之變”深化了司馬遷的歷史解釋,其史學有一深奥的世界,此一深奥的世界使‘史記“完全可以繼承‘春秋“;説見‘中國史學史“第1册,臺北:作者發行,1993年,216頁㊂典型的例子如近人金毓黻説: 遷之作‘史記“,嘗比於孔子之作‘春秋“㊂其述先人之言曰 然又不敢自居以示謙,故曰 ㊂然如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謂拾遺補藝,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其自命如是之高,謂其不比於孔子之作‘春秋“,不可得也㊂”見‘中國史學史“,臺北:漢聲出版社,1972年重刊本,38頁㊂例如歐陽修説: 孔子既没,異端之説復興, 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 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集諸説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㊂”見‘歐陽文忠集“卷四三‘帝王世次圖序“,臺北:中華書局,1966年㊂班彪對司馬遷的評論見‘後漢書㊃班彪傳上“;班固的評論承襲乃父,見‘漢書㊃司馬遷傳“贊㊂司馬遷與班固對‘春秋“的認識源自他們的家學與時代,及由此産生的史學史意識①㊂司馬遷的史學史意識傾向思想文化史,不斤斤於古代的史官之學,他説的 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②超越記言㊁記事之學豈可以道里計?班固的史學史觀念比較傾向學術史,經㊁史殊途,一代之史,目的在續前史㊁述本朝㊂兩位史家在‘春秋“問題上反映出的史學史意識與他們歷史書寫的自我抉擇有很大關係,同時也影響到我們對中國古代史學的認識㊂這是本文想討論的問題之三㊂‘春秋“㊁‘史記“㊁‘漢書“,歷代的研究何止汗牛充棟?③本文涉及的問題不敢説有什麽新意,衹是想從史家的史學史意識觀察其史學思考與作爲,或者反過來説,從史家的史學思考與作爲觀察其史學史意識㊂ 史學”與 史學史”都是後來才有的名詞④,以言古人,未免唐突;但作爲分析思想的語言工具,似又不得不然㊂二㊁司馬遷如何看待‘春秋“的形成與歷史定位春秋”本有專名與通名二義,專名指孔子‘春秋“,即‘春秋經“;通名原指先秦諸侯史記⑤,如‘墨子㊃明鬼下“説的周㊁燕㊁宋㊁齊‘春秋“⑥,‘孟子㊃離婁下“説的魯之‘春秋“㊂‘史記“中的 春秋”不專指‘春秋經“,前人考之已詳⑦,本文衹討論與‘春秋①②③④⑤⑥⑦當時尚無 史學”與 史學史”的名詞,但是馬㊁班對於史官之學的傳承與前史的得失都有所認識,這從‘史記㊃太史公自序“㊁‘漢書㊃序傳“㊁‘後漢書㊃班彪傳“中他們的述作之旨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們是具有今日所謂 史學史意識”的㊂‘漢書㊃司馬遷傳“引‘報任安書“㊂這三部經典的研究積累有一些統計數字,但熟悉經典研究的人都知道水平的參差與意見的重復使統計數字的意義降到最低,其中尤以採用主題或關鍵詞的電腦檢索結果爲甚㊂中文 史學”一詞首次出現於319年後趙石勒置 史學祭酒”(‘晉書“卷一〇五‘載記五“), 史學史”一詞的出現似以胡適1924年在‘讀書雜誌“上發表的‘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一文爲最早㊂這兩個名詞今天都已包括它們在西方語彙中的意涵㊂這個問題衹要根據‘國語㊃晉語七“㊁‘國語㊃楚語上“㊁‘墨子㊃明鬼“㊁‘孟子㊃離婁下“㊁‘左傳㊃昭公二年“㊁‘史通㊃六家“等資料中所提到的 春秋”即可考定,前人所考甚詳,茲不贅論㊂參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前言,臺北:源流出版社,1982年,1 58頁㊂墨子引此四國春秋,雖然意在明鬼,但從其論證的方式看,乃是廣徵歷史記載爲證,其所謂‘春秋“係通義而非專指某一部書,因此周有周的‘春秋“,燕有燕的‘春秋“,宋有宋的‘春秋“,齊有齊的‘春秋“,‘春秋“衹是史書的通名㊂參金德建‘司馬遷所見書考“ 司馬遷所稱春秋係指左傳考”㊁ 司馬遷所稱春秋亦指公羊傳考”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105 115頁;其他論及司馬遷所指春秋爲何的還有很多,茲不備舉㊂經“有關的部分㊂司馬遷對孔子‘春秋“的看法散見於‘太史公自序“㊁‘三代世表“㊁‘十二諸侯年表“㊁‘趙世家“㊁‘孔子世家“㊁‘儒林列傳“㊁‘滑稽列傳“㊁‘司馬相如列傳“㊁‘匈奴列傳“等篇中,間有‘春秋“書法的引述舉例㊂這些不同篇章論及‘春秋“時,繁簡有别,内容㊁觀點或有出入,似乎呈現侯格睿(Grant Hardy)所謂司馬遷 多重敘事”的趣味①,同時容易導致後人引證時的各取所需與各安其意㊂雖然如此,司馬遷的主要觀點還是可歸納爲二:第一,他深信孔子作‘春秋“,‘春秋“確是含有孔子特殊目的與作用的書;第二,孔子乃因史記而作‘春秋“,‘春秋“與其所因史記之間的差異主要是孔子的筆削㊂關於孔子爲何作‘春秋“,司馬遷引用多方面的史料説明,在‘孔子世家“中他説: 子曰: 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稱焉㊂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㊂這是巧妙地剪接了‘論語㊃衛靈公“裏面的話②㊂同篇又云: 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㊂這是改寫‘孟子㊃滕文公下“孟子引述孔子的話㊂在‘太史公自序“中他也引其父司馬談的話: 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㊂同篇在回答壺遂的質問時他又引董仲舒的話: 周代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㊂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①②侯格睿指出‘史記“五體與西方傳統史學的編纂方法十分不同,從不同的視角不衹一次地敘述同一事件,而且對同一事件的敘述也並不完全一致,在西方史家看來,這似乎對歷史真相有某種程度的忽略,可是司馬遷在他的敘述中又經常顯示對事實真相的關注㊂侯格睿的解釋是:與西方史學一元化的敘述相比較,司馬遷自相矛盾的敘述在許多方面能更加準確地反映過去㊂司馬遷特有的歷史觀念是承認史家和證據的侷限,提出多重解釋的可能,並集中於道德的省察㊂説詳Grant Hardy, Can a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an Contribute to Modern Western Theory?”in History and Theory,February1994,譯文見陳恒㊁耿相新主編‘新史學“第1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24 40頁㊂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這句話本出於‘論語㊃衛靈公“,爲孔子論君子的話,‘史記㊃孔子世家“拿它來解釋孔子作‘春秋“的動機,並非原來意思,而且 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不見於‘論語“,未知太史公何所據而云然㊂已矣㊂並加以發揮,説‘春秋“ 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是 王道之大者”㊁ 禮義之大宗”,萬物散聚之理㊁君臣父子之義皆在其中㊂總之,在司馬遷心目中‘春秋“確是孔子所作,是聖人之書,是董仲舒説的 王事”,也是孟子所説的 天子之事”,它總是與‘詩“㊁‘書“㊁‘禮“㊁‘樂“㊁‘易“並列,它的性質也與‘詩“㊁‘書“㊁‘禮“㊁‘樂“㊁‘易“同樣是 經”,而非一般的史㊂關於孔子如何作‘春秋“,司馬遷在‘史記“中有兩處提到孔子 因史記作春秋”(分别見‘史記㊃孔子世家“㊁‘史記㊃儒林列傳“序),一處提到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史記㊃三代世表“),都很簡單;着墨較多的解釋爲: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㊂约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㊂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㊂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㊂(‘史記㊃十二諸侯年表“序)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春秋“所記爲隱㊁哀之間二百四十二年的魯國歷史,司馬遷並没有説孔子所因的史記就是‘魯春秋“,他提出 西觀周室”説,似乎認爲孔子參考了更多的史記舊聞㊂司馬遷未能確定‘春秋經“與‘魯春秋“的關係,一方面可能是他認爲孔子是傳承道統的文化偉人,是 至聖”(‘史記㊃孔子世家“贊),‘春秋經“既爲聖人所作,它的深度與廣度都不可能衹藉一部諸侯史記産生;另一方面,也可能與他作‘史記“時已看不到‘魯春秋“等諸侯國史①,因而無從確認有關㊂總之,以他的修史經驗,‘春秋“所記既然是魯國的歷史,就不可能憑空作出,總是有所本的,必有所 因”;然而因爲尊崇孔子或失考的緣故,無法明言此所 因”者究竟爲何,所以衹好籠統地説 因史記”了㊂孔子既因史記作‘春秋“,實際的工作主要是 筆削”,即司馬遷所謂 約其文辭而指博”(‘史記㊃孔子世家“)㊁ 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史記㊃十二諸侯年表“序)㊁①‘史記㊃秦始皇本紀“: 丞相李斯曰: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㊂”‘史記㊃六國年表序“: 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㊂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㊂”‘史記㊃十二諸侯年表“的史料説明也未見諸侯史記㊂其辭微而指博”(‘史記㊃儒林列傳“)㊁ 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㊃孔子世家“),既有筆削,自然是有所本的,否則從何削起?司馬遷雖然意識到這一點,但他對於‘春秋經“的書寫形式與其所 因”的史記舊聞之間的具體關係似未注意,因而並未着墨㊂其實這是一個關鍵問題,孟子早就説過晉‘乘“㊁楚‘檮杌“㊁魯‘春秋“這類諸侯史記在内容與文體方面是同一類的,‘春秋經“的不同乃是被孔子賦予了特殊的 義”(見‘孟子㊃離婁下“)㊂司馬家是史官世家,雖説秦火燒掉諸侯史記,但他 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㊁ 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㊁ 罔羅天下放失舊聞”(‘史記㊃太史公自序“),看過許多先秦典籍,批評過 春秋有所不紀”(‘史記㊃太史公自序“㊁‘史记㊃十二諸侯年表“小序),也批評過‘秦記“ 不載日月,文略不具”(‘史記㊃六國年表“序),對先秦時期的歷史書寫應很熟悉,對所謂周官五史的制度豈能不知?對齊太史㊁晉董狐的史筆豈能無動於衷?對‘春秋“書法的史學淵源豈能不疑?這一點他似乎與孟子一樣,在凸顯聖人筆墨的同時,竟忽略了一些客觀歷史情境,甚至還説孔子‘春秋“ 蓋其詳哉”(‘史記㊃三代世表“序)①,未免過甚其詞㊂身爲太史之後的司馬遷,關於孔子‘春秋“,學術文化史的意義講了很多, 史學史”的意識流露較少,箇中原因,頗値探究㊂總之,司馬遷對於‘春秋“藴含的經義看法與今文家可謂一致,對於‘春秋“所牽涉的史義則有所迴避而顯得觀點模糊㊂三㊁班彪與班固如何看待‘春秋“的形成與歷史定位‘後漢書㊃班彪傳“説司馬遷‘史記“問世之後,續貂者衆, 好事者頗獲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班彪也作了‘後傳“數十篇, 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㊂范曄引述班彪之言曰: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 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㊂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閒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一篇,由是乘㊁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㊁國語獨章㊂又有紀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①司馬遷認爲 紀元年,正時日月”是孔子‘春秋“的特色,較諸年時月日不詳的記載 蓋其詳哉”;然孔子何以能如此?其所據史文中的年時月日表述如何?其中牽涉許多先秦史學的認知前提,無法在此一一具論㊂篇㊂春秋之後,七國並争,秦併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㊂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紀録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㊂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㊁國語,删世本㊁戰國策,據楚㊁漢列國時事,上自黄帝,下訖獲麟,作本紀㊁世家㊁列傳㊁書㊁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㊂這段簡短的史學史論述最值得注意的是完全没有提到孔子‘春秋“,其中的魯之‘春秋“,既然引的是‘孟子“,與晉‘乘“㊁楚‘檮杌“並舉, 其事一也”,指的當然是魯史原文,而非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的孔子‘春秋“㊂稱‘左氏“與‘國語“ 獨章”,而未將其與‘春秋經“㊁‘公羊傳“㊁‘穀梁傳“等混爲一談,正顯示出班彪擺脱漢代今文家的‘春秋“經㊁傳論述系統,而别有其區分經㊁史脈絡的論述立場㊂在這段文字稍後,班彪又説: 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㊂若左氏㊁國語㊁世本㊁戰國策㊁楚漢春秋㊁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㊂這一串書單與前段文字大致對應,也没提孔子‘春秋“㊂班彪在論述史籍發展時對孔子‘春秋“的認知與司馬遷在‘史記㊃三代世表“中所説 五帝㊁三代之記,尚矣㊂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㊂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顯然是大異其趣的㊂班彪的經㊁史學術分野是涇渭分明的,視孔子‘春秋“爲經而非史,因此他在續‘史記“作後傳,進行史學史的論述與批評時,並未將孔子‘春秋“列爲討論對象㊂他既提到‘孟子“,當然不會不知道孟子對 孔子‘春秋“”這一命題的看法;同時他身爲漢代通儒①,也不可能不知道公羊春秋一派有關 孔子‘春秋“”這一命題的説法㊂他將‘春秋經“排除在史籍之外顯非一時的疏失,而是刻意的,是有意識的㊂這與司馬遷視 孔子‘春秋“”亦經亦史,爲史學史論述必不可少的元素,在觀點上明顯不同㊂班彪的史學史論點建立在 世有史官”㊁ 國自有史”的普遍前提上,班固一方面承襲了這個觀點,‘漢書㊃序傳下“云: 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㊂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㊂漢紹堯運,以①‘後漢書㊃班彪傳上“范曄 論曰”稱其爲 通儒上才”㊂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㊁項之列㊂太初以後,闕而不録,故探篹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㊂所謂 世有史官”㊁ 帝王靡不同之”,與班彪的 世有史官”㊁ 國自有史”的説法可謂如出一轍㊂另一方面班固對於 孔子‘春秋“”的史學性質與影響也有自己的看法,‘漢書㊃藝文志㊃春秋家序“云: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㊁昭法式也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㊂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㊂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㊂”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㊂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也㊂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㊂及末世口説流行,故有公羊㊁穀梁㊁鄒㊁夾之傳㊂四家之中,公羊㊁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㊂‘漢書㊃司馬遷傳“贊亦云: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㊂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迄秦繆㊂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黄帝㊁顓頊之事未可明也㊂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㊂又有世本,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㊂春秋之後,七國並争,秦兼諸侯,有戰國策㊂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㊂故司馬遷據左氏㊁國語,采世本㊁戰國策㊁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㊂其言秦漢,詳矣㊂這兩段文字都在史官譜系中替孔子‘春秋“留了位置,觀點大異於班彪而略近於司馬遷,其中有關‘春秋“與‘左傳“成書背景的解釋,受到‘史記㊃十二諸侯年表“序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㊂不過,班固明言孔子 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與司馬遷僅泛稱孔子 因史記”作‘春秋“而未能確指孔子所 因”爲何,同中還是有異,考論史情,當以班説較勝㊂班固認爲孔子作‘春秋“重點在褒諱貶損之義,性質是經,若無 本事”,不免空言,乃至口授弟子而人人異端;‘左傳“論 本事”而爲傳,呈現的是歷史事實,其性質爲史㊂班固在‘漢書㊃序傳下㊃藝文志小序“中説孔子 篹書删詩,綴禮正樂,彖大易,因史立法”, 因史立法”指的就是作‘春秋“,意思很清楚,‘春秋經“的本質是 法”,不是 史”,是 以制義法”(‘史記㊃十二諸侯年表“序)的法,也是 以當王法”(‘史記㊃儒林傳“)㊁ 當一王之法”(‘史記㊃太史公自序“壺遂言)的法㊂班固認爲,孔子‘春秋“是 經”,是 法”,但是與 史”也有一定關係,即 因史”;不論孔子所因的是魯史抑或包括其他諸侯史記舊聞,孔子不可能徒托空言的作‘春秋“,必有所據;同時正因爲孔子 竊取其義”,所作當然也就不可能衹是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一般,了無深意㊂ 因史立法”,一語破的㊂孔子‘春秋“既然是 經”,是 法”,即使係因史而成,也不可能是班固心目中的 史”了㊂四、馬班的史學史意識與歷史書寫的自我抉擇司馬遷認爲自己的‘太史公書“與孔子‘春秋“是完全不同的著作,這衹要讀一讀‘太史公自序“便很清楚㊂‘史記“的體例與内容怎麽看都與‘春秋經“不像,壺遂卻要去質問司馬遷,看起來十分荒謬㊂壺遂問了兩個問題,一是孔子爲什麽作‘春秋“,一是司馬遷爲什麽作‘史記“㊂他不管内容與體例,在乎的衹是動機與目的㊂他將孔子與司馬遷的動機及目的連結起來,事出有因,因爲司馬遷像孟子一樣,以繼承孔子爲職志,還説過要 繼春秋”,這樣就産生貶天子的大不敬與自比聖人得罪今文學者的問題㊂其實,在司馬遷的觀念中,‘史記“與‘春秋“並不是一對一的特别繼承關係,①除了‘春秋“,其他典籍如‘易傳“㊁‘詩“㊁‘書“㊁‘禮“㊁‘樂“也一同被繼承㊂他所謂 繼春秋”,是廣義的思想文化繼承,而不衹是狹義的學案式繼承㊂司馬遷很慎重地將他與壺遂的問答内容寫進‘太史公自序“,就是藉此明志,同時也顯示他所承受的壓力㊂在‘太史公自序“中壺遂問完司馬遷對‘春秋“的看法後,接着又問: 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司馬遷回答説:①‘太史公自序“原是這麽寫的:太史公曰: 先人有言: 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㊁‘書“㊁‘禮“㊁‘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細玩原文, 正‘易傳“”㊁ 繼‘春秋“”與 本‘詩“㊁‘書“㊁‘禮“㊁‘樂“之際”在意義上是不宜分割的,都是紹明世與繼周孔具體内容的一部分,如衹將 繼‘春秋“”單獨提出來,與原文意思出入甚大㊂。
《史记》和《汉书》的不同点:一、思想比较1、《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史记》浓厚。
2、《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3司马迁思想解放、观点新颖、批判性强;班固则谨守传统、奉行儒教、歌颂皇权。
、二、风格比较1、感情色彩:《史记》和《汉书》都严格遵守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表现出历史学家的文章道德。
但《史记》的爱憎感情,主观色彩相当明显,而《汉书》常常变成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
2、表达上:《史记》写人妙在传神,极富艺术感染力。
而《汉书》有意节制喜怒哀乐之情的表达。
3、取材上:司马迁钟情于才智杰出而落拓不遇之人,他不以成败论英雄,更看重历史人物所具有的精神价值;而班固则出于正统观念,对历史人物或赞或批,对于那些虽齐伟却无益于维护正统观念的人士如刺客、游侠、滑稽、日者等不予立传。
4、在行文上:《汉书》谋篇布局严密有法,记事祥备而删减精当,尚剪裁而词少芜蔓;看起来虽少生气更难有奇气,却也循规蹈矩,合于矩度。
而整齐则主要针对语言而言。
司马迁纵横开阖,以气驭文,故行文跌宕,文气郁勃;而班固为文张驰有度,谨言重法,具有骈化的倾向,如《公孙弘传赞》之“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出于降虏”,《司马迁传赞》之“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等皆是。
5、在具体叙述中:《史记》司马迁写得激情澎湃、栩栩如生,而《汉书》班固则是冷静客观,娓娓道来。
6、叙事方法方面:《史记》善于叙事,笔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
而《汉书》只是通过平时的叙述以完成清晰的记事,故其生动性、文学性不及《史记》。
,7、人物刻画方面:《史记》善于运用细节刻画人物性格,而且描绘出人物的内心活动。
《汉书》只是冷静而简略的写叙述。
《汉书》传写人物的成就也略逊《史记》一筹。
虽然,两书都长于刻画人物,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司马迁与班固历史思想分析历史文化学院10级历史师范(2)班勾倩222010313011160“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郭沫若将司马迁与孔子相提并论,写下“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的诗句;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
两千多年过去了,但在司马迁身后的历代史学家无人与之比肩;其人格魅力的风采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史学史”一词的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由胡适、梁启超等人相继提出,中国传统学术的经、史、子、集四分法在晋魏时期已经成型,到《隋书·经籍志》史部已蔚为壮观,既有史部,则史部的目录学自可视为一种史学史,虽然当时并无“史学史”这个名词。
所谓史学史,即指史学发展的过程与对此过程的认识,它较简单的形式就是史籍史。
《史记》的生命价值观源于《周易》。
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学者不对《周易》做研究。
谁是重卦的作者,历史上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其中一种是司马迁经过考证提出来的。
他认为:重卦的作者是文王; 八卦的作者是伏羲。
在研习《周易》的过程中,司马迁确定了自己的生命价值观。
《周易》提出了效法天道、与天相同的刚健奋发的人生观。
《乾文言》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作者主张通过不懈的努力,培养一种忠信诚实、富于文采、文质彬彬的德行品质,再以此种品质推己及人,外化到事业之中。
《坤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致也。
”从内在美到外在美,由道德而外化为事业,这是从伦理到事功的途径。
《周易》强调效法天道。
《乾》卦最集中地体现了刚健之德。
乾又代表着天象,因而《乾》卦刚健之德也就是天德。
上天处于永恒的运行之中,从日起月落到四时代序,没有片刻止息,这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展现。
人们通过效法上天刚健笃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奋发向上,就会使人生体现出应有的价值。
司马迁与班固历史观的异同司马迁与班固历史观的异同李宏(渤海大学教育学院,辽宁锦州121013)摘要: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在历史观上的差异,对于研究《史记》,《汉书》乃至两汉历史有重要意义.以天人关系,封建正统史观,历史进化,经济观点为着眼点,并分析原因,力图找到学习两汉历史的门径.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历史观;差异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l672—8254(2007)05—0067_04收稿日期:2O0r7—06—26作者简介:李宏(1973一),女,渤海大学教育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从事秦汉史和基础教育研究一,相同点(一)都做过挣脱天命神学历史观的努力1,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司马迁的认识论.有承认天人感应,天命支配人事的一面.如《天官书》历述秦汉时期天人感应的事例.最后还概括地指出,人间发生的事.”未有不”先由天象将天意显示出来.接着人间就相应发生反映天意的事件.在这里,司马迁陷入了天人感应,天命支配人事的圈子.但是,司马迁的认识论.还有怀疑天命.以至不相信天命的一面.如《天官书》:”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褛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这就是说,占卜吉凶之书不可取法,所以孔子编次”六经”的时候,只记载了异常的自然现象,那些占验天人感应的解说都弃而不载.这表明.司马迁对天人感应之说绝非坚信不疑.而且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用历史事实对天命说提出质疑.明确表示了否定天命的思想观点.班固是非常相信天人感应思想的,这主要表现在:其一,班固认为,”太极之元”分成阴阳两极,经过譬变I化,产生天地万物.其二,班固认为,文王演《周易》,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着矣”.(t](五行志序)其三,班固认为,历史上的盛衰兴亡,吉凶祸福,都是天命所定,说:”偶合有命,悲夫!”(](寞田灌韩传赞)又说:”亦有天时,非人力所致焉.”(t]㈤仔传赞)班固虽然笃信天人感应论,但其在历史考察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事的作用.绝没有全然用阴阳灾异,天人感应解说历史而不及其余.《汉书?艺文志》不收谶纬之书,反映出其人文主义倾向.《术数略》的各类小序中阐述其对天文,历谱,五行,着阄,杂占,刑法等方面的见解.表达了对阴阳杂占,望星卜蓍的怀疑与否定的态度.他重视人事的作用,如对汉高祖刘邦,班固并没有以神意的祥瑞说明其为得渤海大学二oo七年第五期天之统的真命天子,而是多次指出其”明达”,“好谋”,”能听”的长处,有”处顺民心,作三章之约”的恭俭,立国后”日不暇给”,”规模弘运”,说明其得天下完全是人的作用,并非出于侥幸.在班固看来:”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信哉!”[1](郦陆刘叔孙传赞)帝王的功业完全是由人事决定的.2,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司马迁看到,历史演进往往存在着某种客观必然性.这种客观必然性,他称之为”势”,就是指历史发展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各种客观条件的交替综合,即一个较长时间里有各种社会力量,各种社会因素逐渐积累决定的历史趋势.《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说西汉建立后,”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之无尺土之封,故大封同姓以填万民之心.及后分裂,固其理也.”这里,司马迁揭示了汉初分封同姓是一种客观趋势,这一方面是错误地反思秦亡的教训,认为秦二世而亡是由于”无尺之封”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异姓诸侯被消灭以后,为了稳定天下,”以填万民之心”的需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分封同姓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积极作用逐渐转化为消极作用,同姓诸侯成为分裂因素.这种分封同姓的作用的转化,在司马迁看来,如同事物发展由盛而衰一样,是由其自身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决定的.班固虽然相信历史循环论,但是他并非把一切历史事变都归于天意所定,而是注重结合时势考察历史的逻辑发展.首先,班固看到许多历史现象的出现都是时势造成的.都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因素.因此主张”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百官公卿表序)如在《陈胜项籍列传》中, 他采用贾谊《过秦论》中所言,指出秦二世而亡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诸侯王表序》中,他把秦亡归于”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蕃翼之卫”.其次,班固看到时势是历史上个人取得成就的决定性因素.时势不是天的意志.而是个人所处的独特的历史环境.班固有时把折中历史机遇称为天时,”天时”这个词并非指天神的安排,而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而言.他称王莽代汉是”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王莽传赞)这句话中的”天时”即是如此(二)都兼有保守与进步的双重性1,其保守性(1)宣扬封建正统历史观司马迁以血统论为依据,建立一个以帝王为中心的传授体系.这个从五帝到汉初的帝王传授体系把黄帝作为各民族的共同祖先,是与中华民族起源的实际情况不相符的.这个体系的建立虽为民族大一统提供了依据,但在封建集权政治下却成了封建正统论的滥觞.班固在《司马迁传》中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此外,还将项羽从帝纪中拉到列传:把陈涉由世家中也降到列传,并抹去”由涉首事”的初功,突出地表现出班固维护封建正统的观点.(2)宣扬天人感应说司马迁相信气数,他说:”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各际续备”:[](天官书)他在解释社会发展形态时,认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2](高祖本纪)在历法上是”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返本”.[:](历书)这实际上就是董仲舒的三统说.班固在《天文志》中,记述了秦楚之际自然界的变异,并认为它应验于人事的变动,特别强调”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影)之象形,响之应声”.在《五行志》中,班固集中了董仲舒等人关于阴阳五行灾异学说的论述,并附会春秋以来至西汉末年某些史实,企图表明五行等自然现象的变异可以反映出政治上的得失.而人们的貌言视听思的失当.也可以影响到自然界的风雨,水旱,寒暖,蝗灾,地震等各种变化.2,其进步性(1)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司马迁的撰史宗旨就是”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察其始终”,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基本方法.他是要把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进行全过程的综合考察,从而找出历史发展的原因和去向.班固提出研究历史要”究其始终强弱之变”,[](诸侯王表序)”列其行事,以传世变”;[](货殖列传)要”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1](百官公卿表序]这里不仅讲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而且有借鉴历史的含义.他还总结历史上的任务,成功的则是”遇其时”.[1](郦陆朱娄叔孙传赞)失败者则是”不知时变”.[](宴田灌韩传赞)这些都体现了他的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2)1)2经济观点来解释历史司马迁认识到了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重要性: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天下鹋渤海大学嗲哲学学版渤海大学哲学学版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并试图从经济条件的分析中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思想意识和社会政治制度.他在《货殖列传》中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班固在《食货志》中,肯定食货为生民之本,”食足货通,然后国家民富而教化成.”在《西域传》中,班固指出汉武帝之所以能通使西域,开拓疆土,是由于”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但是后来,汉武帝连年发动对西域的战争, “师旅之费,不可胜计”,以至”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这里既说明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同时说明统治者的政策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二,不同点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和儒家正统观点的分寸上,司马迁与班固各有表里.(一)天人感应司马迁在天人关系上.不强调天命.而强调人谋.司马迁在整理上古史时,对神话传说采取审慎态度.虽说不是全部抛弃.但也基本上不予采用;司马迁否定个人命运受制于天道或某种善恶因果报应.他批判”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七十九章)的观点.例如:当项羽兵败时发出“天亡我”的怨叹.司马迁批判道”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z](项羽本纪)司马迁在对天命论提出质问和批判的同时,又强调人的作用.他在解释楚汉相争成败的原因时,通过史实的对比,强调人谋,民心的作用.司马迁用事实证明楚亡汉兴与天命无关,关键在人谋,在人心的向背,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班固宣扬天人感应说.例如在《高祖本纪》最后的”赞”语中,概述自尧到刘邦的世系延续,用来证明刘邦是古代圣贤帝王的后人;又借符瑞征兆说明汉继尧后.以火德得天下.班固在《汉书》中记载了大量用天象灾异,阴阳五行来附会征验社会问题的材料,如《五行志》,《刘向传》,《谷永杜邺传》等篇, 其中尤以《五行志》为最,连篇累牍地宣扬这方面的荒诞谬说.这些记载,充满了天意支配人事的说教,集中体现了班固错误的历史观..(二)”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论司马迁对”五德终始”持批判态度.并且还反映在对《史记》的整体安排上.按照”五德终始”,秦只能占一德,但秦却分列为两纪;而项羽根本没资格列入”五德”的次序,可他却被列入本纪.还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其对五帝,夏,商,周等均未按”五德终始”所规定的”五行”递嬗的模式组织排列.班固宣扬历史循环论及皇权神授说.在《律历志》中.他把从太昊到刘秀的世代帝王更替,按”五德”之运排列起来.他认为周是木德,继之者是火德;而秦以水德间之,这与过去共工氏的运一样”非其次序,故皆不永”;至汉高祖代秦继周,应该是火德,故汉应运而生,这是”自然之应,顺时宜矣”.他说”高祖始起,神母夜号,着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郊}已志)”依照班固所说, 刘邦的得天下符合五德的顺序,是神意的安排. 三,原因(一)所处时代历史背景是决定彼此历史观差异的重要前提司马迁时代诸子各家学说尚在流行中,使他能从古代进步思想家的思想中汲取营养;司马谈的以道家为主的学术思想和着史志向也对司马迁有重要影响.但是,司马迁毕竟是一个忠于汉王室的地主阶级史学家,他撰写《史记》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维护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在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下,随着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加强.封建正统思想逐渐建立并渗透到史学领域中来.然而,在封建正统思想尚未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又给了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实事求是地认识历史,解释历史的机会.就是在这样一个中国古代史学向封建正统史学过渡的历史时期.使司马迁成为中国古代进步史学家的优秀代表.同时也成为封建正统史学的开创者.班固所处的时代,思想领域内经历了从”独尊儒术”到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的召开.儒家思想已经神圣化,可以说,整个《汉书》都是在封建正统思想指导下写成的.因此,《汉书》的写作宗旨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也就用儒家的正统思想,将汉朝200年的历史妥帖讲通.以为汉王朝的统治服务.(二)相似的个人经历使两者对统治阶级官方的历史观既无可回避.又表现出多层面的复杂性.进而使其思想具有明显的进步性1,幼年时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埋下封嘞渤海大学二oo七年第五期建正统思想的烙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初年任太史令.司马迁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后来曾向当时的儒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又曾向孔安国学习.20岁时,司马迁走出家门,在全国周游考察,通过全国周游考察以及后来做官后为执行公务出行各地,司马迁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获得了大量历史和现实资料,为他以后撰写《史记》做了重要准备.班固出生在一个有外戚身份的宦官之家.父亲班彪是一位历史学家.通晓汉代历史,撰有《史记后传》数十篇.班固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23岁时,父亲去世,他立志要继承父亲的志向.完成父亲未完的事业.于是开始在家撰写《汉书》.班固撰写《汉书》是为了弥补《史记》的两个缺陷:一是《史记》所记西汉的历史并非西汉全史,因此要补续,以实现他父亲的遗愿.二是《史记》采用通史的体裁而将汉帝排在最后.班固认为这不能充分展现汉朝继承尧的正统地位.因而要用断代史形式重写汉朝历史,突出汉帝一尊的正统地位.2,晚年受到封建强权势力的排挤与迫害,使他们能因此有所觉醒.立志于治史.所以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和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能够从实际出发给以批判的考察和分析.体现出史学家的严肃态度和求是精神.司马迁于公元前104年便开始动笔写作《史记》,公元前98年,因为”李陵事件”被汉武帝治罪.被处以残酷的腐刑.这时,撰写一部宏伟历史巨着的信念,是司马迁忍受屈辱,继续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出狱后,司马迁作了中书令,全力倾注在《史记》的写作上,直到公元前93年前后基本完成.班固于公元78年升任玄武司马.主掌守卫宫廷玄武门.公元92年窦宪以谋逆罪被迫自杀,班固受到牵连,先是被免官职,后又被捕入狱,当年死于洛阳狱中.参考文献:[1]班固.汉书[MJ.北京:中华书局,1999.[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3]老子.道德经[MJ.韩宏伟,何宏注译-△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责任编辑蔡国相)DifferencesandSimilaritiesinSimaQianandBanGu’SHistoricalViewpointsLlHong(CollegeofEducation,BohaiUniversity,Jinzhou121003,China)Abstract:ForthestudyofShiJi,HanShuandthehistoryofWestandEastHan Dynasties,itisofgreatsignificancetocomparethedifferencesandsimilaritiesinSimaQianand BanGu’Shistoricalview—,feudalhistoricalview—point,historicalevolution,andeconomicviewpoint,SOthatabetterwaycan befoundtolearnthehistoryofWestandEastHanDynasties.Keywords:SimaQian;BanGu;historicalviewpoint;differences渤海大学哲学学版渤海大学哲学学版。
浅析司马迁与班固史学观的差异
内容摘要:《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汉书》的作者班固是我国历史上两位重要的史学家。
虽然同为纪传体史书,但是两部书中所体现出的两位史家的史学观确实不同
的。
本文将就两部史书中所体现出的二人不同的史学观进行分析,同时对二人
不同史学观的形成也有所探究。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史记》/《汉书》/史学观
中国历史上司马迁和班固可谓是史学上的双子星座,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分别开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的先河。
固然,作为优秀的史学家两人有着很多相似点,但是二人在史学观方面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本文将就二人史学观的不同之处进行浅析。
首先就家学渊源的差异来说,对二人史学观的形成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生活于汉初,那个时期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而司马谈也是崇尚道教思想的。
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中表现出的更多是道家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而没有一味地崇尚儒家,他还指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①这些都是和他受到其父的影响分不开的。
班固的父亲班彪也是一位史学家,他对班固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他曾撰有《王命论》,更多的是强调汉承尧运,天命有归,王者兴衰,“通篇贯穿着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的儒家经学思想”②。
再者,班固本人也是《白虎通》的撰写者,书中主要宣扬谶纬思想感应学说。
故而《汉书》中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儒家正统思想,宣扬一些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思想,而缺少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
为此,班固曾在《汉书》这样表达了他对司马迁的不满,“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叙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③
“是非谬于圣人”正说明司马迁的批判精神,能够无所畏惧,信笔直书,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爱憎掩功过,更加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
而班固作为一个正统史观的史家,并且还是奉旨修书,故而书中会有不同于司马迁犀利的批判的地方。
如对于吕后,司马迁为其立本纪,主要是出于历史事实考虑,惠帝在位,实权则由吕后掌握;而班固则给惠帝另立本纪,并置于《吕后纪》前面。
对于游侠,俩个人同样有着不同的观点。
对于游侠,司马迁更多的是欣赏和赞美,赞扬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
①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王萍:“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载《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49页
③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能,羞伐其德”。
①加之由于司马迁自己的个人遭遇,“从自身命运的思索中真切体会到专制统治的冷酷和对人性的扼杀,并将一种反抗意识贯注到其作品中,通过描写那些敢于反抗强暴,为自己认定的“正义”不惜生命的侠义英雄,讴歌其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
”②而作为正统史家,班固则缺少这样的思想。
对于游侠,出于更加利于汉王朝的正统地位,班固则斥责游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
在天道观方面,《史记》和《汉书》也体现出很大的不同。
司马迁更多的表现出一种自然天道观,也就是历史自然的观点;而班固表现出的则是浓厚的天命观。
司马迁的自然天道观没有过渡地强调天的作用,这一观点主要是指出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而且他还以历史自然地观点批评天命观。
例如《项羽本纪》中最后关于项羽的失败,司马迁这样写到:“乃引(指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没有强调天命的观点,而是指出项羽的失败乃是由于人的缘故,是历史的自然。
在《伯夷列传》中也批评了“天道无常,常与善人”的说法,并说“余甚感焉,偿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进一步表明司马迁实际上是批评天命观的。
司马迁天道自然的观念,“显然受到老子‘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观点的影响。
”③
班固表现出的则是浓厚的天命观,这和他受到其父班彪和董仲舒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其父班彪对班固的影响自不必说,董仲舒对他的影响可以从《汉书·董仲舒传》中看出,《董仲舒传》中完整地记录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班固对天人感应学说可以说是很推崇的,他本人在史学观上也是一种封建正统的思想,为此他视儒学为正宗。
班固作《汉书》实际上是为了尊显汉室,宣扬汉德,这种宣汉德理论基础便与董仲舒刘氏得天统而建汉朝的神学目的如出一辙。
因此他需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自然其中的天命观是极其浓厚的。
如他在《汉书·高祖纪·赞》里称:“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为符,旗帜上赤,协于上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由于在西汉末东汉初年,谶纬之学风靡一时,班固自然受其影响,故而《汉书》之中可以看到宣扬谶纬神学。
《五行志》中说道:“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
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福到,自然之符也”,显示出浓厚的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的色彩。
相反,司马迁则持以无神论的观点否定天人感应。
他在《留侯世家》中说:“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
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另外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这样写道:“星气之书,多杂吉祥,不经”。
这些表明,司马迁持有无神论的思想,并且批评天人感应说、鬼神论。
①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
②朱萍:“司马迁、班固与游侠”,载《安徽文学》,2006年第8期,
③周一平:《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20页
司马迁史学思想中有着较班固更为闪光的一点,那就是他能够以经济观点指导史学研究。
在大家所熟悉的《货殖列传》一文中,司马迁重视经济的想法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例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虽然是引自他人所说,却也体现出司马迁是认同这样的观点的。
他还指出,“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又说,“无岩处夺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也就是说,司马迁是强调了经济作用,以经济观点观察社会和历史。
“从经济决定出发,司马迁深入到了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观点。
”①《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附焉。
”这表明,仁义、道德都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实际上,司马迁是以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去指导自己研究历史的。
而班固则缺少这样的经济思想,毕竟班固一则是受正统史观的影响,另外他本人再著史过程中并没有像司马迁那样受到了那么多的磨难。
并未像司马迁那样因贫困而惨遭极刑,故而他对经济的重视并未达到司马迁的程度。
《史记》和《汉书》是两种不同体裁的史书,前者为通史,后者断代为史,这其实也是不同史学观的反映。
司马迁著史的目的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并“罔罗天下放佚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故而他作通史。
“他这样将自有中华文明以来的三千年间的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冶之,反映着秦汉大一统的天下局势,表达了自己对历史及历史人物的审美思想。
”②班固并不这么想,他认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
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万之末,厕于秦项之列。
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纪,缀辑所闻,以述《汉书》。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班固断代为史,而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河。
不同的史学观早就两位不同的史家,也成就了两部开中国史学先河的经典著作,在对待两位史学家或是阅读二人的著作时要把握好二人不同的史学观,并明确二人的史学思想的差异,这样也可以更好的理解二人的著作。
①周一平:《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26页
②陈桂成:“‘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司马迁、班固著史优劣辨”,载《梧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