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之路:女性文学三十年
- 格式:doc
- 大小:30.50 KB
- 文档页数: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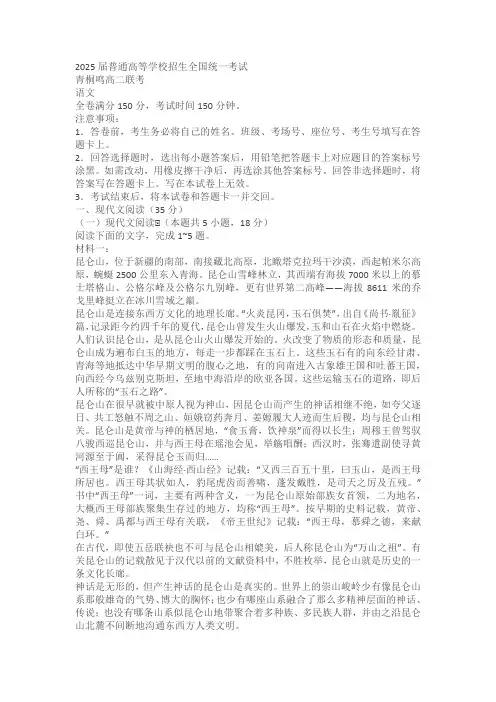
2025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青桐鸣高二联考语文全卷满分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注意事项: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班级、考场号、座位号、考生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8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昆仑山,位于新疆的南部,南接藏北高原,北瞰塔克拉玛干沙漠,西起帕米尔高原,蜿蜒2500公里东入青海。
昆仑山雪峰林立,其西端有海拔7000米以上的慕士塔格山、公格尔峰及公格尔九别峰,更有世界第二高峰——海拔8611米的乔戈里峰挺立在冰川雪域之巅。
昆仑山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地理长廊。
“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出自《尚书·胤征》篇,记录距今约四千年的夏代,昆仑山曾发生火山爆发,玉和山石在火焰中燃烧。
人们认识昆仑山,是从昆仑山火山爆发开始的。
火改变了物质的形态和质量,昆仑山成为遍布白玉的地方,每走一步都踩在玉石上。
这些玉石有的向东经甘肃、青海等地抵达中华早期文明的腹心之地,有的向南进入古象雄王国和吐蕃王国,向西经今乌兹别克斯坦,至地中海沿岸的欧亚各国。
这些运输玉石的道路,即后人所称的“玉石之路”。
昆仑山在很早就被中原人视为神山,因昆仑山而产生的神话相继不绝,如夸父逐日、共工怒触不周之山、姮娥窃药奔月、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均与昆仑山相关。
昆仑山是黄帝与神的栖居地,“食玉膏,饮神泉”而得以长生;周穆王曾驾驭八骏西巡昆仑山,并与西王母在瑶池会见,举觞唱酬;西汉时,张骞遣副使寻黄河源至于阗,采得昆仑玉而归……“西王母”是谁?《山海经·西山经》记载:“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
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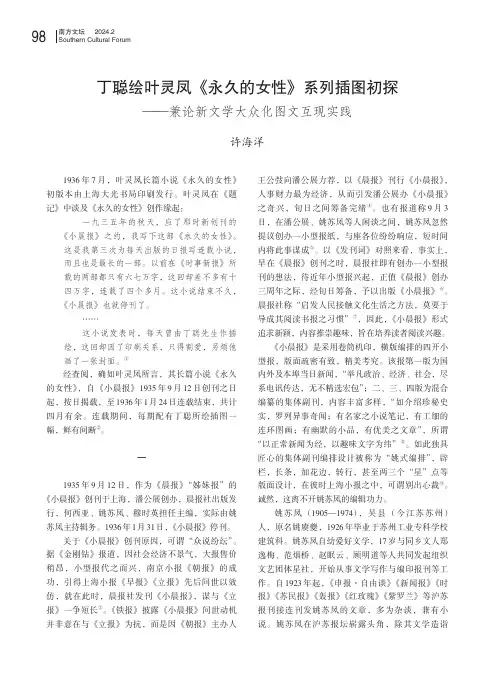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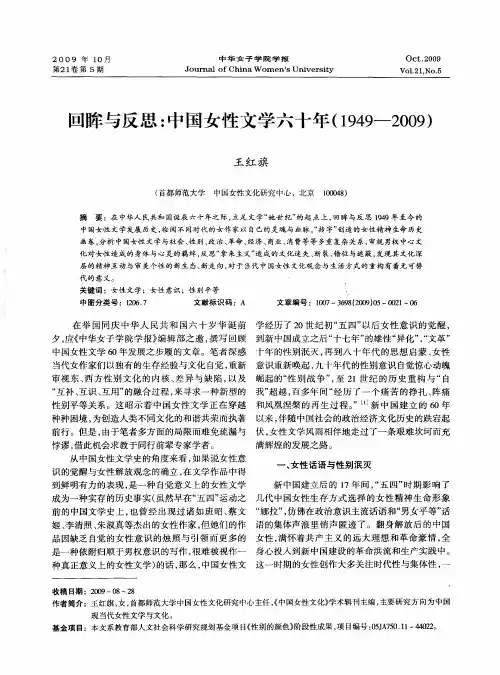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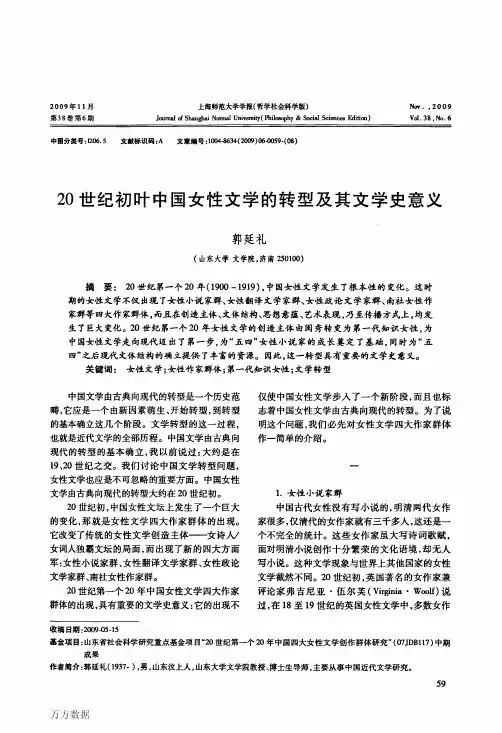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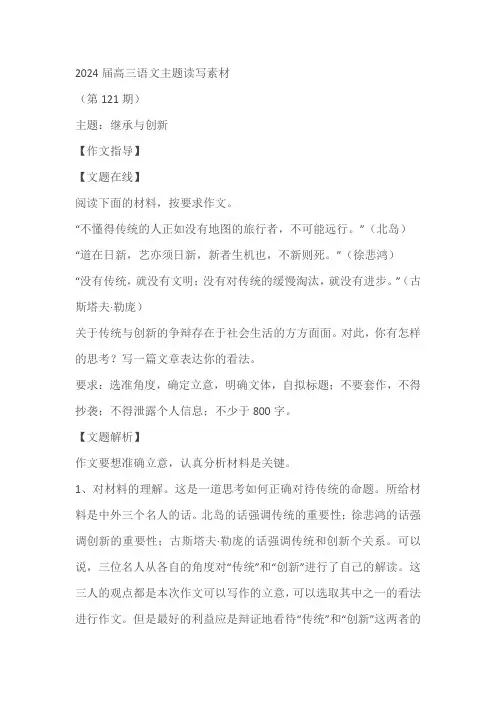
2024届高三语文主题读写素材(第121期)主题:继承与创新【作文指导】【文题在线】阅读下面的材料,按要求作文。
“不懂得传统的人正如没有地图的旅行者,不可能远行。
”(北岛)“道在日新,艺亦须日新,新者生机也,不新则死。
”(徐悲鸿)“没有传统,就没有文明;没有对传统的缓慢淘汰,就没有进步。
”(古斯塔夫·勒庞)关于传统与创新的争辩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此,你有怎样的思考?写一篇文章表达你的看法。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文题解析】作文要想准确立意,认真分析材料是关键。
1、对材料的理解。
这是一道思考如何正确对待传统的命题。
所给材料是中外三个名人的话。
北岛的话强调传统的重要性;徐悲鸿的话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古斯塔夫·勒庞的话强调传统和创新个关系。
可以说,三位名人从各自的角度对“传统”和“创新”进行了自己的解读。
这三人的观点都是本次作文可以写作的立意,可以选取其中之一的看法进行作文。
但是最好的利益应是辩证地看待“传统”和“创新”这两者的关系。
2、对关键词的理解。
材料的关键词是“传统”、“创新”。
“传统”意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现代汉语词典》)。
传统是指一个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交往活动中所积累和积淀下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各种事物的总和,它直接影响到人的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既有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文化传承、变革与创新。
“创新”是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的一种概念化过程。
有三层含义:第一,更新;第二,创造新的东西;第三,改变。
创新是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高级表现,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一个民族要想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也不能没有创新思维,一刻也不能停止各种创新。
创新在经济、技术、社会学以及建筑学等领域的研究中举足轻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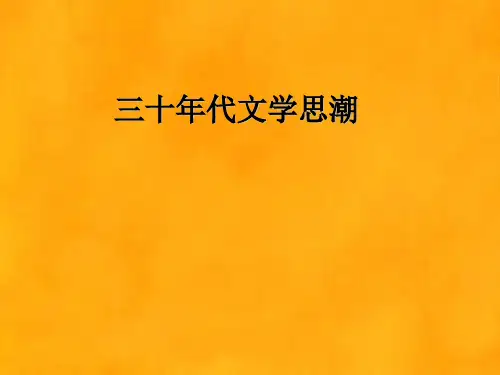

记忆MEMORY《东北女性文学的拓荒者——白朗》历 达 吴玉杰《抒写苦难,书写光明——论白朗的文学创作》 李春林《军中小卒——忆白朗》 赵郁秀《白朗年谱》——东北作家群回眸之六《鸭绿江》老主编回顾之三著名画家 王学东 即将消失的风景之二 150cm×150cm. All Rights Reserved.本栏目主持 郝万民东北作家群回眸 之六本栏目主持 吴玉杰东北女性文学的拓荒者086在东北作家群中,有一位女作家才华横溢又命途多舛,她的文章不但构思巧妙文采斐然而且能针砭时弊揭露黑暗,她在东北作家群内与萧红齐名,共同成为东北文坛上女性文学的拓荒者,20世纪50年代的她不但是著名的女作家而且是社会活动家和国际和平使者,50年代的读者没有人不知道她的名字,她就是白朗。
一、历史的颠簸与文学的执著白朗的文学创作生涯始于30年代的哈尔滨,白朗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33年至1945年,随着日寇的入侵,东北三省的沦陷,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之中,满怀着一腔爱国热血的白朗开始以笔为戈同敌人战斗。
第一个阶段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民族需要下用文学表现抗日主题,书写民众抗日的浩歌。
此阶段白朗的创作表现沦陷在日军铁蹄下的东北人民的凄楚生活,歌颂东北人民日益觉醒的民族意识和英勇的斗争精神,作品中充满着理想的战斗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
1933年8月白朗在《大同报》上发表处女作《叛逆的儿子》,这篇中篇小说通过描写两代人的冲突和隔膜,歌颂了青年人勇于打破封建制度的叛逆精神,揭露讽刺了老年人的陈腐思想。
1934年因为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迫害,白朗和罗烽被迫开始了流亡生涯。
逃亡到上海的白朗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仍然笔耕不辍。
这一阶段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叛逆的儿子》《四年间》《逃亡日记》《老夫妻》,长篇小说《狱外记》(片断),短篇小说集《伊瓦鲁河畔》,短篇小说《惊栗的光圈》《抵是一条路》,以东北沦陷为题材的《沦陷前后》《轮下》《忆故乡》等短篇小说和文章,散文集《西行散记》,日记体报告文学《我们十四个》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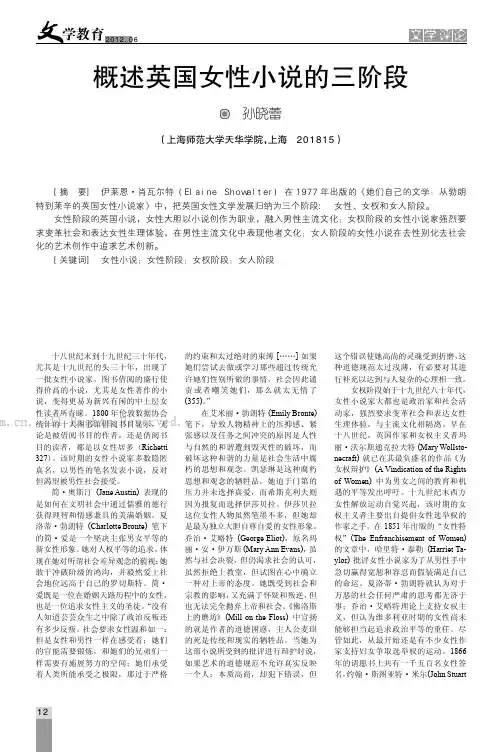
2012.06学教育12概述英国女性小说的三阶段孙晓蕾(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上海201815)[摘要]伊莱恩·肖瓦尔特(El a i ne Show a l t er )在1977年出版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中,把英国女性文学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女性、女权和女人阶段。
女性阶段的英国小说,女性大胆以小说创作为职业,融入男性主流文化;女权阶段的女性小说家强烈要求变革社会和表达女性生理体验,在男性主流文化中表现他者文化;女人阶段的女性小说在去性别化去社会化的艺术创作中追求艺术创新。
[关键词]女性小说;女性阶段;女权阶段;女人阶段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尤其是十九世纪的头三十年,出现了一批女性小说家。
图书借阅的盛行使得价高的小说,尤其是女性著作的小说,变得更易为新兴有闲的中上层女性读者所青睐。
1800年伦敦数据协会统计的十大图书馆借阅书目显示,无论是被借阅书目的作者,还是借阅书目的读者,都是以女性居多(Richetti 327)。
该时期的女性小说家多数隐匿真名,以男性的笔名发表小说,反对但渴望被男性社会接受。
简·奥斯汀(Jane Austin )表现的是如何在文明社会中通过儒雅的德行获得理智和情感兼具的美满婚姻。
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 )笔下的简·爱是一个坚决主张男女平等的新女性形象。
她对人权平等的追求,体现在她对所谓社会差异观念的藐视:她敢于冲破阶级的鸿沟,并毅然爱上社会地位远高于自己的罗切斯特。
简·爱既是一位在婚姻天路历程中的女性,也是一位追求女性主义的圣徒。
“没有人知道芸芸众生之中除了政治反叛还有多少反叛。
社会要求女性温和如一:但是女性和男性一样在感受着;她们的官能需要锻炼,和她们的兄弟们一样需要有施展努力的空间;她们承受着人类所能承受之极限,那过于严格的约束和太过绝对的束缚[……]如果她们尝试去做或学习那些超过传统允许她们性别所做的事情,社会因此谴责或者嘲笑她们,那么就太无情了(3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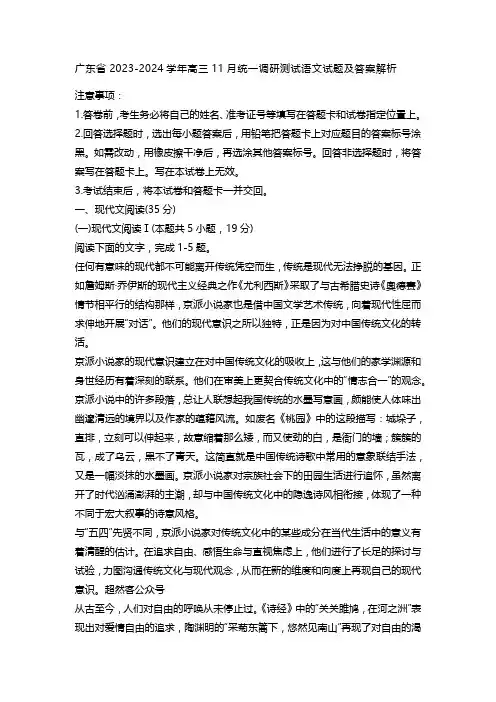
广东省2023-2024学年高三11月统一调研测试语文试题及答案解析注意事项: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等填写在答题卡和试卷指定位置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任何有意味的现代都不可能离开传统凭空而生,传统是现代无法挣脱的基因。
正如詹姆斯·乔伊斯的现代主义经典之作《尤利西斯》采取了与古希腊史诗《奧德赛》情节相平行的结构那样,京派小说家也是借中国文学艺术传统,向着现代性屈而求伸地开展“对话”。
他们的现代意识之所以独特,正是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活。
京派小说家的现代意识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上,这与他们的家学渊源和身世经历有着深刻的联系。
他们在审美上更契合传统文化中的“情志合一”的观念。
京派小说中的许多段落,总让人联想起我国传统的水墨写意画,颇能使人体味出幽邃清远的境界以及作家的蕴藉风流。
如废名《桃园》中的这段描写:城垛子,直排,立刻可以伸起来,故意缩着那么矮,而又使劲的白,是衙门的墙;簇簇的瓦,成了乌云,黑不了青天。
这简直就是中国传统诗歌中常用的意象联结手法,又是一幅淡抹的水墨画。
京派小说家对宗族社会下的田园生活进行追怀,虽然离开了时代汹涌澎湃的主潮,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隐逸诗风相衔接,体现了一种不同于宏大叙事的诗意风格。
与“五四”先贤不同,京派小说家对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在当代生活中的意义有着清醒的估计。
在追求自由、感悟生命与直视焦虑上,他们进行了长足的探讨与试验,力图沟通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从而在新的维度和向度上再现自己的现代意识。
超然客公众号从古至今,人们对自由的呼唤从未停止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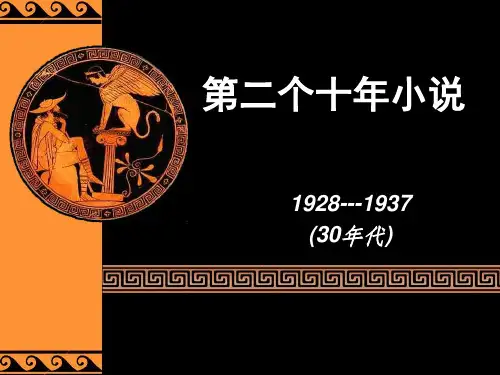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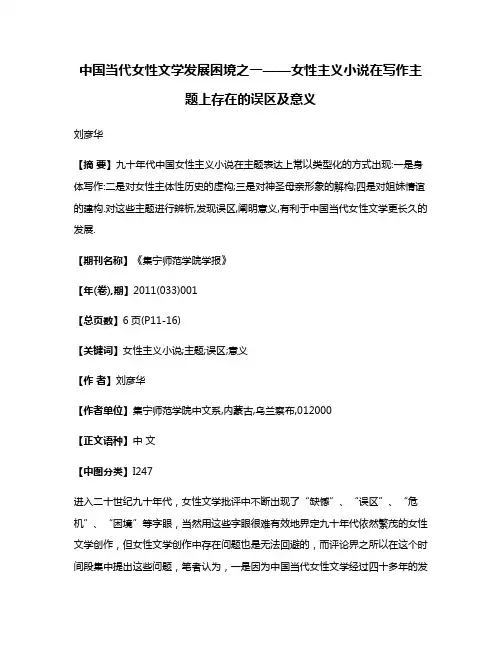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发展困境之一——女性主义小说在写作主题上存在的误区及意义刘彦华【摘要】九十年代中国女性主义小说在主题表达上常以类型化的方式出现:一是身体写作:二是对女性主体性历史的虚构;三是对神圣母亲形象的解构;四是对姐妹情谊的建构.对这些主题进行辨析,发现误区,阐明意义,有利于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更长久的发展.【期刊名称】《集宁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1(033)001【总页数】6页(P11-16)【关键词】女性主义小说;主题;误区;意义【作者】刘彦华【作者单位】集宁师范学院中文系,内蒙古,乌兰察布,012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47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文学批评中不断出现了“缺憾”、“误区”、“危机”、“困境”等字眼,当然用这些字眼很难有效地界定九十年代依然繁茂的女性文学创作,但女性文学创作中存在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而评论界之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集中提出这些问题,笔者认为,一是因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在创作实践和理论运用方面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积淀和检验后,暴露了一些问题;二是在当代女性文学发展之初,建构的热情大于自审的意识,而当冷静下来思考女性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时,回顾来路,发现了自身发展中的偏颇之处;三是当代女性文学发展中所采取的对抗姿态,以及九十年代一些极端化的个人写作方式,也招致了评论界对她的诟病。
也就是说,困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她既有理论上的,也有创作上的,对出现的困境进行认真的查找和分析,将有利于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尽快地走出困境,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如果我们把女性文学看作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即创作主体是女性,那么女性主义小说是指那些具有鲜明性别意识,对父权制文化进行解构的女性文本。
九十年代,女性主义小说在写作主题上,一直以来都有她关注的共同点,那就是致力于女性独立、平等、自主的发展之路。
但具体的文本表达却像园中的花朵,千差万别,丰富多样。
细究这些文本就会发现,这些文本的主题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很深,常常以类型化的方式出现,大致归纳起来有四种:一是身体写作;二是对女性主体性历史的虚构;三是对神圣母亲形象的解构;四是姐妹情谊的建构。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的边缘人形象分析一、简述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作为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不仅展现了华裔女性的独特经历,还反映了华裔社群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
在这些作品中,华裔女性往往被塑造成为边缘人的形象。
这种边缘性不仅源于她们在种族和文化身份上的差异,还涉及到她们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社会职业等方面的挑战。
本文将通过分析几部具有代表性的华裔女性文学作品,探讨这些作品中所呈现的边缘人形象,并分析这些形象产生的原因和意义。
本文还将讨论如何在文学研究中更好地理解和表现边缘人形象,以及这一形象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和启示。
1. 女性在文学中的地位及其所面临的边缘化问题。
在文学领域中,女性角色的刻画长久以来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
尤其在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女性地位及其边缘化问题成为了众多作品探讨的核心主题之一。
由于历史、文化和社会原因,华裔女性在文学作品中常常被描绘成边缘人形象,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境。
在种族和性别双重歧视下,华裔女性在许多作品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
她们在家庭、社会和职场方面都遭受着不平等待遇,这使得她们更容易陷入边缘化的境地。
以任璧莲(GishJen Wei)的小说《典型华裔美国女孩成长之路》这部作品通过描述主人公梅锦的故事,揭示了华裔美籍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所承受的种种压力以及边缘化问题的严重性。
在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华裔女性也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惑。
由于历史原因,华裔移民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传统在融合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矛盾和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华裔女性往往难以寻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进而容易陷入迷茫和边缘化的状态。
以谭恩美(Amy Tan)的小说《喜福会》该书通过讲述中美两国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两代人的故事,展示了华裔女性在寻求身份认同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边缘化问题。
2.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发展及其独特性。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民国四大才女是哪四位民国时期涌现出了众多才华横溢的优秀女性,其中的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张爱玲更是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为此店铺为大家推荐了一些民国四大才女的知识,欢迎大家参阅。
1912年,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覆灭,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紧随其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民主和科学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渐渐开化。
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女性文学作家及作品。
她们以其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及审美倾向而独树一帜,令当时的男性作家耳目一新。
尤其是她们将自身大胆的人生情爱追求和不懈探索精神,渗透融合于文学作品之中,达到了更鲜活更新奇的效果,成为当时文学中的一股强劲的新鲜血液。
其中的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张爱玲更是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吕碧城简介吕碧城生于1883年,父亲吕凤岐是光绪三年丁丑科进士及第,曾任国史馆协修、山西学政等,家有藏书三万卷。
12岁那年,父亲去世,因吕家无男子,族人便以其无后继承财产为名,霸占吕家财产,与吕碧城9岁时便议定婚约的汪氏,见吕家变故,也连忙退婚。
1904年,吕碧城结识了天津《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并以绝妙文采,得到英敛之的赏识,成为该报第一位女编辑。
从此,吕碧城声誉鹊起,一发不可收。
此后,她兴办女学、提倡女权、出国游学,后因不屑袁世凯称帝,毅然辞去了大总统秘书的职位。
动荡的时代,新旧擅递,社会剧烈的变革,个人不同寻常的境遇,使碧城的词别开生面,多姿多彩,倍受世人瞩目。
吕碧城是那个时代特立独行的新女性,也是近代杰出的女词人,她的诗词创作,有着极高的天赋和才华,作为辛亥革命前后着名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被称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
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录六十六位名家词作四百九十八首,吕碧城五首殿后,有“一代词媛”之称。
文学家潘伯鹰形容她的词“足与易安俯仰千秋,相视而笑”近人钱仲联先生作《南社吟坛点将录》将吕碧城目为“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认为“(碧城)近代女词人第一,不徒皖中之秀。
作者: 李甦
作者机构: 苏州大学中文系 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出版物刊名: 文学评论
页码: 156-158页
主题词: 台湾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作家;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张爱玲;三个发展阶段;传统女性;作品;林海音
摘要: <正> 台湾女性文学,就时间上说,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
发展到八十年代的今天,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
这是一个既长又短的历史流程,产生了一大批既有影响又引起争议的女性文学才人,历数这一批才女们的芳名,是需要花费相当精力的。
台湾的女性文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传统女性的文学(Feminine literature),(二)女性主义的文学(Feminist literature),(三)女性文学(Female literature)。
台湾女性文学兴起之初,基本没有摆脱传统的影响,多表现女性的婚姻遭遇、丰厚的母爱和家庭的温暖。
在当时为数不多的女性作家中,首推张爱玲和林海音。
张爱玲的作品虽然吸收了一些西方的。
民族融合与北魏女性作家的文学成就民族融合是指不同民族之间在社会、文化、经济以及其他领域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互相学习和共同发展的状态。
在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常常是通过文化交流来实现的。
北魏时期,由于各个民族的大规模迁徙和交流,民族融合的现象十分明显。
在这个时期,女性在文学方面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北魏时期,由于南方各个地区的南朝政权相对混乱,导致了大批南方人民向北方迁移。
这种迁移使得南方和北方的文化开始融合,并为北方的文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在北方的各个地区,不同的民族也开始相互融合,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逐渐增多。
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交流,为北魏女性作家的文学成就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北魏时期的女性作家主要有两个代表人物:卞淑娴和蔡琰。
她们在北魏时期有着重要的地位,她们的作品对北魏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卞淑娴是北魏时期的一位著名女性作家,她的作品《争草》是古代文学史上的一部名篇。
《争草》以神话故事为背景,描写了女子在家族和丈夫之间的牵绊与矛盾。
作品中,卞淑娴巧妙地运用了象征、夸张等手法,将女子的情感内心描绘得淋漓尽致。
她的作品在描写女子的心理活动方面,达到了非常高的艺术水准,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蔡琰是北魏时期的另一位女性作家,她的作品也给北魏时期的文学发展带来了新的风貌。
她的作品《咏史诗》是一部史诗性的长诗,描写了北魏历史上的一系列重要事件。
蔡琰通过她的作品,展现了自己对历史事件的独特理解和感受,同时也表达了她对社会和时代的思考。
她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叙事手法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成为北魏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
民族融合与北魏女性作家的文学成就密切相关。
正是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使得北魏的文学呈现了丰富多样的特点,各民族的文化在这个时期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借鉴。
而女性作家在这种文化的大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和创造力,同时也为北魏文学史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动力。
女性文学的崛起及其代表作家
杨雪梅
【期刊名称】《卫生职业教育》
【年(卷),期】2007(025)023
【摘要】@@ 中国现代文学的众多作品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喧闹与张扬,围绕人性的各个层面,文学再次绽放出迷人的笑颜.诗歌、散文、小说以各自独特的风格不断激活深藏在普通人身上的人性,人性的复苏则唤起了文学的进程.其中,大量女性作家的崛起,更让中国文坛焕发出迷人的光彩.
【总页数】2页(P148-149)
【作者】杨雪梅
【作者单位】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甘肃,兰州,73002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03
【相关文献】
1.女性意识的觉醒与中国近现代女性文学的崛起 [J], 陈捷
2.中国女性文学的崛起、发展及其现代性特征 [J], 陈明秀
3.探析“五四”女性文学崛起的文学史意义 [J], 徐汉晖
4.清末民初女性文学崛起与社会发展的关联性研究
——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1900—1919)》 [J], 张拴刚
5.女性文学形象的崛起——从《西游记》中的女人谈起 [J], 张悦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融合之路:女性文学三十年新时期发轫期,女作家们在对人、人性、人道主义的探究中,渐次进入性别领域,女性意识得以苏醒,女性感觉得以发育,女性特征得以复位。
她们在对爱的权力、信念的追逐中,证实了“爱”对于女性生命的基础性意义;她们在对真、善、美和温柔的宣扬里,纠正了以往不谈性别差异的平等论以及无性化情状。
人的自觉和女性自觉终于获取了实质性的结合。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女作家女性意识不断地增涨,女性文学颇成气候,一道亮丽的女性文学风景线终于横空出世,照亮于文坛。
张洁、舒婷、张抗抗、王安忆、铁凝等作家的作品不胫而走,其所呈露的女性尊严、怀疑精神乃至性意识,震撼着文坛与读者。
从《方舟》到《玫瑰门》,无不让人或感动、或惊诧、或不安、或责难,它们为人们所带来的动静至今尚未止息,所带来的气息至今依然缭绕。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女性文学的标志性岁月。
女作家们不仅度过了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举行的狂欢节,她们的创作也进入到空前的高潮期、丰收期。
假如说,“五四”女性文学是由古代、传统向现代、现代性转型的话,那么,由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的世纪之交的女性文学,则为又一轮转型——向多元化的转型。
今天,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相交织的社会,人文环境以及女性主义全球化的文化语境,都在催使中国女性文学作出转型性反应;本轮转型现正处于进行态,既深刻又全面。
这轮转型不仅超越了“五四”女性文学,还回答了之前某些男士所忧虑的“女性主义文学能走多远”的疑虑。
我以为,中国女性文学正依据自己所开创的性别和超性别相融会、相整合的思路和视界,继续勇敢地向前迈进。
路上,肯定依然会遭遇到他设和自造的麻烦、曲折,甚至陷阱;但,路,一定会越走越阔广,越走越深远。
由改革开放初始作好准备,世纪之交以来正式启动的女性文学转型,就女作家的性别立场和视界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其一,以张洁为始,翟永明、陈染、林白为续,徐坤等探索和实践为继的女性主义立场与视野。
其二,以王安忆、张抗抗、铁凝、方方、范小青、王小妮等为代表,虽具深厚女性意识,对男性中心文化的解构性也时有表现,但却坚持追逐、探索超性别的立场与视野。
其三,迟子建最先提出了文学的性别和谐论,主张消解男女之间内在紧张,致使世界不至于倾斜而丧失平衡。
诚然,这三种类型的划分并无严格界限,何况各类型内部常有自我消解和矛盾情况,各类型之间的观念也常有交叉和变化,此等划分,仅为研究方便而为,绝非科学论断。
其实,最值得关注的,却在于她们的趋同方面。
随着女作家各自成长轨迹的清晰呈露,我们发现:一,新时期初始,女作家们强化女性意识的要求与实践,是具有很强历史针对性和历史合理性的;女性文学对女性意识的强调,正是对女性主体人性的强调,其为女性话语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上世纪90年代,反对男权中心话语的女性主义抬头,以女性个体经验为核心的身体写作、个人化写作,一时试图取代宏大叙事和集体经验的话语;但较快地,尤其在新世纪以来,广大女作家,包括以往较沉溺于自恋的女作家,也都不再将性别元素孤立、封闭起来,她们竭力地将性别意识、视角,同国族的、社会的、历史的,乃至宗教情怀的意识、视角整合一体,置性别元素于各相关文化结构之中。
她们似乎不再专注于女性主义称谓(原先专注于这个称谓的,也绝非多数),而要将个性主义、人性主义作为自己最真切的追求目标了。
三,面对繁复的性别歧视(以市场经济主宰的性别歧视为最突出)现象,女作家们依然不放弃对男权中心话语的解构,然而,基于对人性结构深入的透视和理解,她们对待两性关系问题,一方面感到不宜搞绝对化的性别主义,一方面则追求和谐关系的建构。
既然性别关系的基本内核属人性关系,那么,就应在彼此尊重各自主体人性的基础上,协调好“主体间性”关系。
即,双方应互为主体、彼此对话、互助互动,以求男女共生、和谐共存。
对共生共存男女关系的追求,反映在创作视界上,正是性别与超性别的交汇和融合之境。
从张洁到徐坤,持女性主义立场的女作家们,她们观念的变化以及在创作上的表现,是30年来女性文学演变的重要征兆与象征。
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那刻,还是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甚至有点寻找男人的意味;但从《方舟》到《只有一个太阳》,再到《无字》时,她却已是个相当彻底的女性主义者了。
当她撕开男人人性面具、逼近男人人格真实的时候,那种捅破自己制造的乌托邦神话的反思、忏悔劲头,令人震撼;那种失望于男人、尤其男人“精英”,无情地撕破其自私、虚伪、轻浮、庸俗、不负责任等真相时的决绝态度、愤懑神情,更令人敬畏。
然而,张洁至今仍然不愿被人归纳到“女权主义”中去,她认为,这样做只能是“画地为牢”(参见钟红对张洁的采访,《文汇报》2006年2月27日),会限制文学自身的丰富性和可能性。
张洁创作尽管有自己的年轮和转型,但其同社会的、历史的,乃至政治的、制度的关联,却始终如一。
《无字》同中国百年变革历史的纠缠,呈现得何等生动和深刻!张洁正是因她的既性别又超性别的立场和视野,才成就了她杰出的文学业绩。
翟永明抒写《女人》组诗时,那种顽强抵抗和拆解“野蛮空气”和“残酷的雄性意识”的执傲劲,热切期待女性伟大原生力、原创力焕发的激情流,至今还在激动着我们;而她那“穿黑裙的女人”和“黑夜意识”,也终于成为了女性诗歌的经典性符号。
然而,翟永明很快地向自己提出了一个“完成之后又怎样”(翟永明《完成之后又怎样》,《标准》创刊号)的问题。
她一方面继续着女性题材创作(如大型组诗《十四首素歌——致母亲》),倾心于女性家族史的谱写;一方面却沉溺于有关自由、美和艺术等命题的开拓了。
她开起了“白夜酒吧”,周游世界,一方面继续着“出自女性之喉”的表达,一方面却探索起“双性沟通对话乃至双性同体式的吟述”(陈超语)了。
翟永明犀利的性别洞察力和不断成熟的女性意识,使她原先“自白式”诗句所呈露的狂热激情有所降温,但那个体生存体验与时代生存本质的联系却更其紧密;诗作的人类性和生命意味剧增,诗歌的技艺也更其精湛。
为之,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于2007年10月授予她“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
据说,授奖词赞扬她的诗作“能量充沛,情境深邃,肌理细腻,意味幽怨”。
刘索拉、陈染也都不隐讳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
而今,她俩一个提出女人应自觉地认识到“自己身体中的双性成分”(刘索拉、西云《刘索拉:我的女性主义和女性味》,《艺术评论》2007年3期),一个则明确表示“愿意说自己是一个‘人性主义者’”(林宋瑜《陈染:破开?抑或和解?》,《艺术评论》2007年3期)。
刘索拉以为,“人没有必要保持绝对女性和绝对男性的状态,那种状态其实很愚蠢”,因为“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一大因素就是认识到自己身体中的双性成分”,人应在雌性激素和雄性激素引导下,“感知自然的双性,并顺其自然的双性”。
她觉得自己正是个能感悟双性的幸运儿,这样,既写出了兼具女性特色和历史大场面的小说《女贞汤》,又谱成了揭示女性心理阴暗面的新歌剧《惊梦》,作品的视野都是双性的,对女性自我所持有的阴暗与弱点也都不予避讳。
陈染一贯以女性性别引以为“美好和荣耀”。
但她长于哲思的思维方式,让她认可伍尔芙关于“伟大的脑子是半雌半雄的”观点。
以往,人们在短论《超性别写作与我的创作》、小说《破开》《私人生活》中,一方面发现了她对姊妹情谊、女同性恋的倾心,另一方面却注意到,她希冀男女精神结合以求人格完整的心愿。
陈染认为,认识和欣赏一个人,假如拘泥于性别的话,那就“未免肤浅。
”应该说,她是较早具超性别意识的。
晚近,在反思自己青春期锋芒的时候,她一方面提醒自己要“内敛起来”,深埋“反骨”;一方面却坚持女作家应“把男性和女性的优秀品质融合起来”,以求作品“感情和思想传达得炉火纯青的完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说:“我愿意说自己是一个‘人性主义者’。
”作为人性主义者的陈染,她的性别和超性别自有其独特的方面。
她以包容、开阔胸怀,理解和感受人性的丰富性,包括对女同性恋权利的理解和尊重;她以哲人的睿智,思考男人与女人的长短,并着力扬弃自已身上的人性弱点,以求继续“成长”。
林白,一直认为创作由生命深处而生,是个人的言说,因而更倾心于个人主义;然而,当大家把她列入女性主义时,她也不反感,并认可了自己“算得上”是个中国女性主义的“重要作家”。
2003年,她的长篇《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获得成功,《妇女闲聊录》还荣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这是她的黄河之行、深入湖北农村以及同从农村请来的“女管家”亲戚作了深入交谈之后的结果;是她从房间、从窃窃私语中走将出来后,由蓝天和大地给予她的回报。
她感慨道,写《妇女闲聊录》时有一种“回到了大地”,以及大地给了自己“温暖”的感觉。
她甚至提出,是这种“低于大地的姿势”,使自己“找到了文学的源头”(林白《世界如此辽阔》,《前世的黄金——我的人生笔记》第71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林白的感受,意味深长,难怪她要说自己的创作“远不止女性文学这一块”。
徐坤,这位我曾称之为女性文学“吉祥鸟”的实力派作家,自走上文坛以来,或以反串、易性写作,操持着对知识界虚伪自私之境的炮轰,或以女性身影正面袭击菲勒斯中心主义,女权立场清晰而顽强。
她知道,男权意识充斥于世的今天,男权话语形态覆盖于文坛的时候,女作家倘若选择不好视角,就难以呈现女性自己的身姿和发出自己的声音。
1996年,她严正提出“女性文学,说到底,无非就是争得一份说话的权利”,其所肩负的任务则为:一“反抗”,二“自我发现”。
这里,她“心底的不甘和颠覆的决绝”鲜明而突出(徐坤《因为沉默太久》,《中华读书报》1996年12月10日),其态度和言辞,果然被人称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宣言”。
然而,她渐渐地感悟到,两性关系毕竟属于“共存”关系,一味地“战争”,其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谁也不得安宁”(易文翔、徐坤《坚持自我的写作——徐坤访谈录》,《小说评论》2005年第1期)。
近些年来,她真的不再只取一端,或装扮成男人看女性,或执著于女人视点看男性,而试着男女“对看”(万燕《从徐坤看中国当代女性创作的前途》,《女性的精神》第284页,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了。
人性的“主体间性”,除了“对话”,还须“对看”;只有努力地认识对方,才能真切地对话和沟通。
从她几部长篇新作如《爱你两周半》《野草根》《八月狂想曲》等来看,徐坤已明白了多维度、多层次地展示生活的重要性,明白了作家在人与人之间搭筑起心灵桥梁的责任。
这些作品无论宏观切入,还是微观透视,都非常到位,尤其在挖掘人物内心真实方面,相当出彩。
自徐坤潜入人物内心,把握住人的最真实所在的时候,她终于让男人和女人之间既对看、又对话,既沟通又理解了,她的创造性也由此而焕发出耀眼的光彩。
王安忆、铁凝们对超性别视野的探索,同张洁、徐坤们的探索有许多相叠之处,尤其在女性主义的自审方面就相当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