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医案学完整版本
- 格式:ppt
- 大小:246.50 KB
- 文档页数: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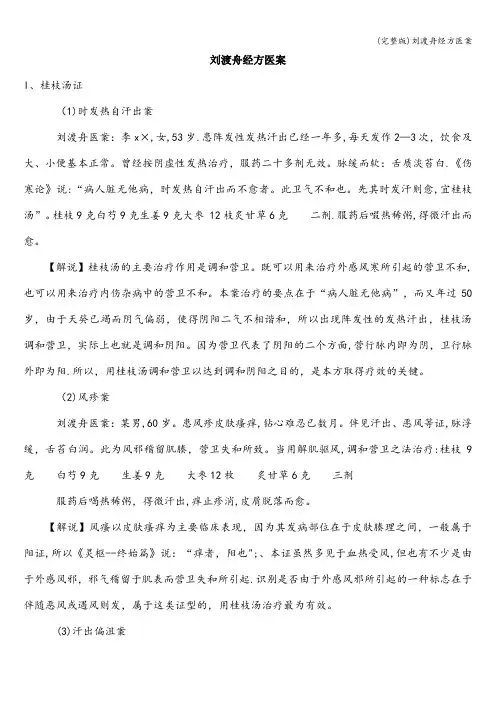
刘渡舟经方医案l、桂枝汤证(1)时发热自汗出案刘渡舟医案:李x×,女,53岁.患阵发性发热汗出已经一年多,每天发作2—3次,饮食及大、小便基本正常。
曾经按阴虚性发热治疗,服药二十多剂无效。
脉缓而软:舌质淡苔白.《伤寒论》说:“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
此卫气不和也。
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
桂枝9克白芍9克生姜9克大枣 12枝炙甘草6克二剂.服药后啜热稀粥,得微汗出而愈。
【解说】桂枝汤的主要治疗作用是调和营卫。
既可以用来治疗外感风寒所引起的营卫不和,也可以用来治疗内伤杂病中的营卫不和。
本案治疗的要点在于“病人脏无他病”,而又年过50岁,由于天癸已竭而阴气偏弱,使得阴阳二气不相谐和,所以出现阵发性的发热汗出,桂枝汤调和营卫,实际上也就是调和阴阳。
因为营卫代表了阴阳的二个方面,营行脉内即为阴,卫行脉外即为阳.所以,用桂枝汤调和营卫以达到调和阴阳之目的,是本方取得疗效的关键。
(2)风疹案刘渡舟医案:某男,60岁。
患风疹皮肤瘙痒,钻心难忍已数月。
伴见汗出、恶风等证,脉浮缓,舌苔白润。
此为风邪稽留肌腠,营卫失和所致。
当用解肌驱风,调和营卫之法治疗:桂枝9克白芍9克生姜9克大枣12枚炙甘草6克三剂服药后喝热稀粥,得微汗出,痒止疹消,皮屑脱落而愈。
【解说】风瘙以皮肤瘙痒为主要临床表现,因为其发病部位在于皮肤腠理之间,一般属于阳证,所以《灵枢--终始篇》说:“痒者,阳也";、本证虽然多见于血热受风,但也有不少是由于外感风邪,邪气稽留于肌表而营卫失和所引起.识别是否由于外感风邪所引起的一种标志在于伴随恶风或遇风则发,属于这类证型的,用桂枝汤治疗最为有效。
(3)汗出偏沮案刘渡舟医案:孙×x,男,39岁。
患左半身经常自汗出,而右半身反无汗,界限非常分明.无其它咀显不适,脉缓而略浮,舌苔薄白。
用桂枝汤调和营卫阴阳,使其相将而不相离则愈。
桂枝9克白芍9克,生姜9克.大枣l2枚炙甘草6克三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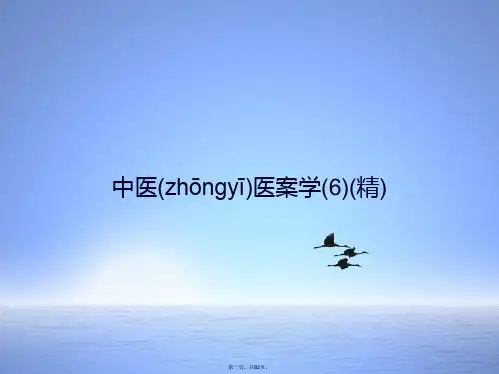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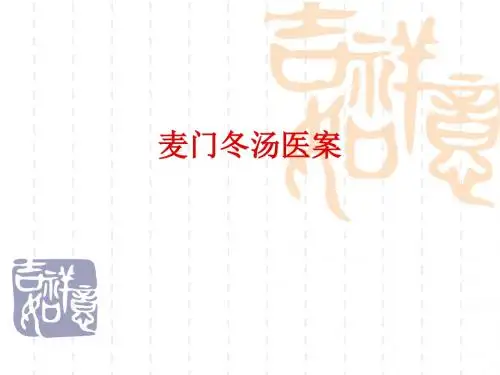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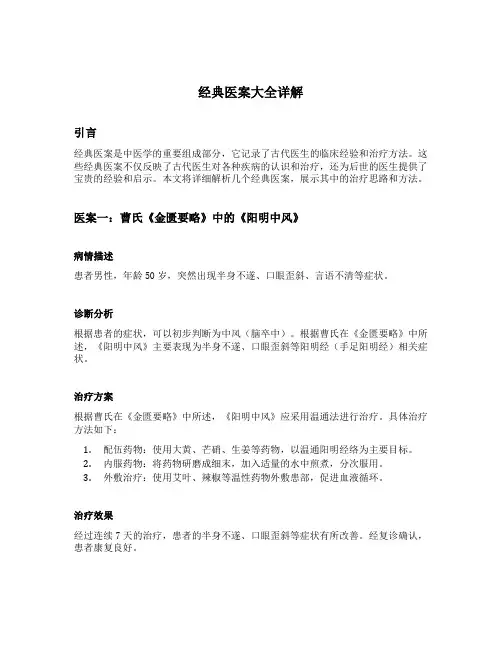
经典医案大全详解引言经典医案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记录了古代医生的临床经验和治疗方法。
这些经典医案不仅反映了古代医生对各种疾病的认识和治疗,还为后世的医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本文将详细解析几个经典医案,展示其中的治疗思路和方法。
医案一:曹氏《金匮要略》中的《阳明中风》病情描述患者男性,年龄50岁,突然出现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等症状。
诊断分析根据患者的症状,可以初步判断为中风(脑卒中)。
根据曹氏在《金匮要略》中所述,《阳明中风》主要表现为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等阳明经(手足阳明经)相关症状。
治疗方案根据曹氏在《金匮要略》中所述,《阳明中风》应采用温通法进行治疗。
具体治疗方法如下:1.配伍药物:使用大黄、芒硝、生姜等药物,以温通阳明经络为主要目标。
2.内服药物:将药物研磨成细末,加入适量的水中煎煮,分次服用。
3.外敷治疗:使用艾叶、辣椒等温性药物外敷患部,促进血液循环。
治疗效果经过连续7天的治疗,患者的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等症状有所改善。
经复诊确认,患者康复良好。
医案二:《伤寒杂病论》中的《伤寒发汗法》病情描述患者女性,年龄30岁,体温升高、出现寒战、头晕等症状。
诊断分析根据患者的表现,可以初步判断为伤寒(一种传染性传染性急性肠道传染病)。
根据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所述,《伤寒发汗法》是治疗伤寒的主要方法。
治疗方案根据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所述,《伤寒发汗法》应采用温开发汗为主要治疗方法。
具体治疗方法如下:1.药物选择:使用麻黄、桂枝、杏仁等药物,以温开发汗为主要目标。
2.内服药物:将药物研磨成细末,加入适量的水中煎煮,分次服用。
3.外敷治疗:使用温水湿敷患者的额头和背部,促进体内湿气排出。
治疗效果经过连续3天的治疗,患者的体温逐渐恢复正常,并且寒战、头晕等不适感也有所减轻。
经复诊确认,患者已基本康复。
医案三:《医宗金鉴》中的《胃脘冷满》病情描述患者男性,年龄40岁,出现胃脘冷满、食欲不振等症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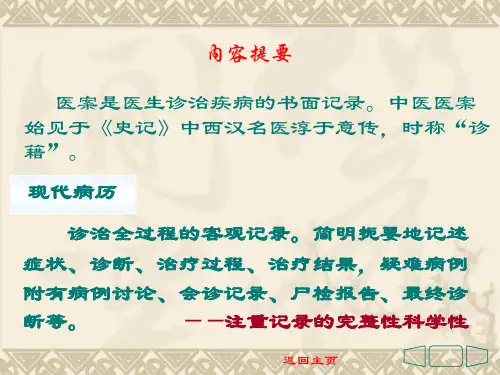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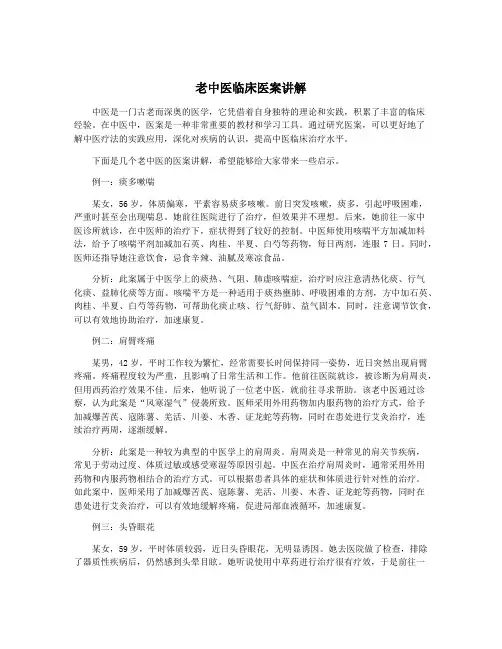
老中医临床医案讲解中医是一门古老而深奥的医学,它凭借着自身独特的理论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在中医中,医案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教材和学习工具。
通过研究医案,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医疗法的实践应用,深化对疾病的认识,提高中医临床治疗水平。
下面是几个老中医的医案讲解,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
例一:痰多嗽喘某女,56岁,体质偏寒,平素容易痰多咳嗽。
前日突发咳嗽,痰多,引起呼吸困难,严重时甚至会出现喘息。
她前往医院进行了治疗,但效果并不理想。
后来,她前往一家中医诊所就诊,在中医师的治疗下,症状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中医师使用咳喘平方加减加料法,给予了咳喘平剂加减加石英、肉桂、半夏、白芍等药物,每日两剂,连服7日。
同时,医师还指导她注意饮食,忌食辛辣、油腻及寒凉食品。
分析:此案属于中医学上的痰热、气阻、肺虚咳喘症,治疗时应注意清热化痰、行气化痰、益肺化痰等方面。
咳喘平方是一种适用于痰热壅肺、呼吸困难的方剂,方中加石英、肉桂、半夏、白芍等药物,可帮助化痰止咳、行气舒肺、益气固本。
同时,注意调节饮食,可以有效地协助治疗,加速康复。
例二:肩臂疼痛某男,42岁,平时工作较为繁忙,经常需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近日突然出现肩臂疼痛。
疼痛程度较为严重,且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工作。
他前往医院就诊,被诊断为肩周炎,但用西药治疗效果不佳。
后来,他听说了一位老中医,就前往寻求帮助。
该老中医通过诊察,认为此案是“风寒湿气”侵袭所致。
医师采用外用药物加内服药物的治疗方式,给予加减爆苦芪、寇陈薯、羌活、川姜、木香、证龙蛇等药物,同时在患处进行艾灸治疗,连续治疗两周,逐渐缓解。
分析:此案是一种较为典型的中医学上的肩周炎。
肩周炎是一种常见的肩关节疾病,常见于劳动过度、体质过敏或感受寒湿等原因引起。
中医在治疗肩周炎时,通常采用外用药物和内服药物相结合的治疗方式。
可以根据患者具体的症状和体质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如此案中,医师采用了加减爆苦芪、寇陈薯、羌活、川姜、木香、证龙蛇等药物,同时在患处进行艾灸治疗,可以有效地缓解疼痛,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加速康复。

名老中医医案巧用麻黄治疗煤气中毒刘某,男,44岁。
1980年孟冬煤气中毒,其亲属发现时已昏迷不醒,手撒遗尿,呼之不应。
急送某医院抢救后苏醒。
醒后头晕头痛,胸中闷窒,烦躁不安,恶心欲吐,周身乏力,记忆力减退,精神恍惚。
翌日晨起,诸症不减,邀余诊治。
舌苔白腻,脉沉弦有力。
辨证为余毒内伏,神明受扰。
治宜宣通气血,祛毒外出。
乃试投麻黄汤,处方:麻黄、生甘草各15g,桂枝、苦杏仁各10g,服药1剂,通体大汗,精神清爽如常人。
按:煤气余毒内伏,须有外出之路。
麻黄发汗利水,宣通气血,驱散毒邪。
徐大椿谓其“轻扬上达,无气无味,乃气味中之最轻者。
故能透出皮肤毛孔之外,又能深入凝痰积血之中,凡药力所不能到之处,此能无微不至。
较之气雄力厚者其力更大”(《神农本草经百种录》)。
邪毒内伏,使阳气内郁。
桂枝通经脉,助心阳,阳气伸展则邪无所居;苦杏仁调畅气机;生甘草泻火解毒。
纵观全方,有促进新陈代谢、加速毒素排出之功用。
杜达权老中医冬温变症治验举隅先父杜达权是广东省东莞市名老中医,从医40余年,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对复杂多变的病证,辨证准确,用药精到,疗效显著,现录冬温变症验案1则,供同道参考。
张某,男,51岁。
因冬季下乡采购时发病,初起即高热烦渴,头痛如劈。
病经1周,前医皆称冬温时邪,遂苦寒迭进,然不但无效,反日益加剧。
后延先父诊治。
诊见:全身发热如烙,头痛剧烈,面色泛红,舌红、苔黄,脉洪大滑数,但重按时乏力。
患者精神亢奋,躁扰不宁,呻吟枕席,尤其烦渴引饮,且喜热饮,1昼夜饮水达10壶。
近3昼夜未有片时安睡,日夜除渴饮外,一切食物均不欲下咽,大便4天未解,小便色黄,且时要冷水浇头部,或以玉石瓷枕等按摩头部方舒。
查前医所处方药,有凉膈散、白虎汤、承气汤、竹叶石膏汤、龙胆泻肝汤等,多为苦寒清火之剂,服后无效。
根据症状表现,似属阳热现象,而细思其脉虽洪大,但重按乏力,当是实中寓虚;且过服苦寒劫夺,反致龙雷火炽,奔腾上越,已变生坏证,与冬温本证截然不同,且渴喜热饮,服凉药而火愈炽,与王太璞所云: “热之不热,责其无火,寒之不寒,责其无水”相近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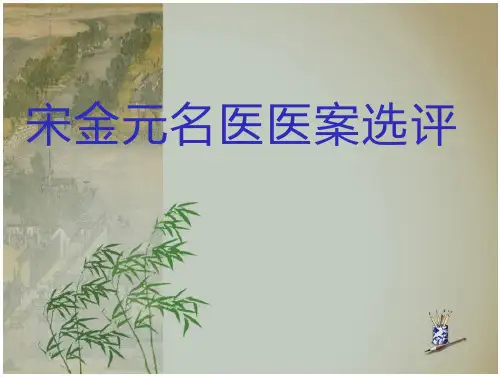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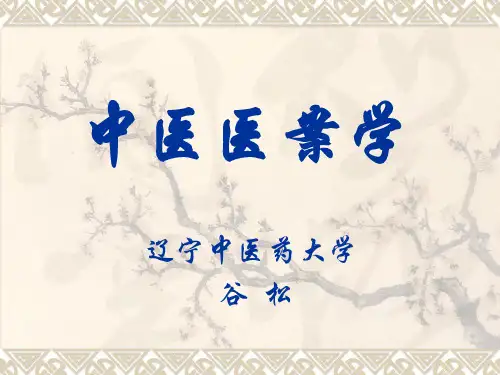
![最新[]针灸医案学终讲学课件](https://uimg.taocdn.com/79b7901c4afe04a1b171dee9.webp)
中医百例医案整理1、赵某,女,40余,五年前子宫切除,现双乳胀痛乳腺增生,自觉身体右侧有气,发胀排不出去,口干渴喜热饮,但湿湿嘴就喝不下去,中午头昏,太阳晒着就加重,不易出汗,想吃凉的但不敢吃,肝区叩击痛(+++)心下无压痛,舌干苔少花剥,脉浮寸弱,葛根40麻黄10桂枝40白芍10炙甘草20石膏80柴胡叶40黄芩15花粉20枳实15大黄(另)15厚朴80干姜20槟郎20鳖甲25茜草15旋复花10降香20木香10生姜25大枣4两剂,诸症减轻,肝区叩击痛(+)葛根40麻黄10桂枝40白芍10炙甘草20石膏80柴胡叶40黄芩15半夏15枳实15大黄(另)10干姜20鳖甲25茜草15牡蛎20生姜25四剂愈。
此案初诊时受病人情绪影响,思路混乱,虽然大方向不错但用药很杂,影响效果。
“若胁下痞鞭去大枣加牡蛎四两”2、某女40,几岁的时候家里失火得的阻塞性肺气肿,时轻时重,这一次发作,在医院输液每日八瓶(具体不详),一周后日益加重,查CT胸前积液4CM心包积液,被动体位,张口抬肩喘促,满布湿罗音哮鸣音,花剥苔,小便少,一输液就更出不来气,十枣汤一试,4克无效,第二天6克呕吐两次,喘息稍减,第三天8克上吐下泻臭秽20余次,稍觉闷气,没有其他症状,要求出院,医院有复查了一个CT:未见胸腔积液3、某女,因醉酒至胃痛干呕,头昏欲睡恶寒,买沉细无力,理中汤合麻附辛小半夏汤加桂枝2剂愈4、某女50,还风,恶寒咽痛头身痛,脉浮紧长数,发烧,先与麻黄汤,3个小时,没发汗,高热,面红体烫,服发汗片后汗出热退。
第二天复诊,已经不恶寒,体统消失,唯咽干痛失音,晨起口苦年,嘴里没味儿,大便出不来,脉浮弦,柴胡去半夏加黄连牡丹皮汤合桂枝汤加芒硝1剂愈。
这是近几年少有的麻黄汤不出汗的,是汗不得法还是胃气太弱?第二天就从太阳转少阳了,并且内热较重,柴胡证后有柴胡加芒硝汤,是为外感病罢有实而设,此病人发热后便秘是为典型。
5、某女,70余,咽干痛白粘痰,全天口苦,纳眠二便均可,右关上浮滑有力,不恶寒,半夏泻心汤小剂量3剂愈6、某男,50余,因胸闷疼胃胀,去武汉某医院检查为心脏血管狭窄,建议支架。
中医八大医案展开全文医案之一:死则甘愿偿命!(清代名医徐大椿)徐大椿碰到一位病人:酷暑之天气,病人"暑病热极,大汗不止",而且"脉微肢冷,面赤气短"。
众医按"热症"来治,开出"寒凉之药"。
徐诊断完全相反,认为是"寒症",须"温热之药"。
--病人家人不知该听哪位大夫的话。
酷暑,病人大汗,似按"热症"来治更稳一些。
而徐则完全相反,万一有误,岂不火上浇油?!徐说:"哪里有不自信而仅作尝试的道理,如果病人出现问题,我愿意以死来偿命!"结果病人喝下徐的"大热之药",一剂药汗止;身体变暖,能够睡觉。
随调方,十天病愈。
徐之敢用大热之药,是因病人虽有"大汗、面赤"等热症,但也有"肢冷"等寒症,这是寒热并杂、真寒假热的病症,需要用"参附汤"这样的热性药物进行救治。
这是从"祛寒"的角度来说的。
从"补虚"的角度来说,病人因热而大汗不止而产生"亡阳"这种阳虚病症,需要用"参附汤"这样的补虚药物进行救治。
徐也很慎重地总结,如果病人不是有"肢冷"等寒症症状,则仍是热症,误用热性药物即死!原文:毛履和之子介堂,暑病热极,大汗不止,脉微肢冷,面赤气短,医者仍作热证治。
余曰:"此即刻亡阳矣,急进参附以回其阳。
"其祖有难色。
余曰:"辱在相好,故不忍坐视,亦岂有不自信而尝试之理,死则愿甘偿命。
"方勉饮之。
一剂而汗止,身温得寐,更易以方,不十日而起。
同时,东已许心一之孙伦五,病形无异,余亦以参附进,举室皆疑骇,其外舅席际飞笃信余,力主用之,亦一剂而复。
但此证乃热病所变,因热甚汗出而阳亡,苟非脉微足冷,汗出舌润,则仍是侨证,误用即死。
医案五则原文及译文1. 医案一:“揭阳李氏骨瘤案”原文:有揭阳李氏,年六十余,困于骨瘤,大小如葱茎,悬挂于髋部,沉甚不可动,时作疼痛,牵引腰背,须臾不绝,益甚于前。
巨痛难当,疾曾求医,病难图治,牵引腰背,常卧不安,未能劳动。
吾往探病,背上有三个拳头的大小的硬块,有疫气之状,波涛似漫,旦夕侏儒点点,疼痛难忍,昼夜无寐。
案几数日,吾思此病乃肾所生,未敢轻用温补之品,从以清热凉血、疏利通络为始。
方曰:黄柏七两,芍药四两,丹皮三两,蒲公英三两,龙胆草一两,连翘二两,青皮二两,大青叶三本,葵花蜜五钱,生地五两。
用法:以上药切细,以清酒六升浸,三日后取药渣,静置十分钟,将药渣倒掉,取药液煮至一升即可。
李氏服药两剂后,瘤上渐松,痛既减,三旬愈。
吾至揭阳,李氏挽留,方驾离去。
译文:有一位姓李的老人,年龄超过六十岁,受困于一个骨瘤,大小如葱茎,悬挂在髋部,沉重,不可动弹,时常引起疼痛,拉伸腰背,情况越来越糟。
他遭受巨大的痛苦,曾寻求医治,但病情无法治愈。
他的腰背经常受到牵引,无法四肢活动,需要卧床休息。
我前去检查病情,背上有大小如三个拳头的硬块,似乎有传染疾病的特征,情况严峻,疼痛无法忍受,白天黑夜无法入睡。
经过一段时间检查,我认为这种病是由肾脏产生的,不敢轻易用温补之品,从清热凉血、疏利通络入手。
方剂如下:黄柏七两,芍药四两,丹皮三两,蒲公英三两,龙胆草一两,连翘二两,青皮二两,大青叶三本,葵花蜜五钱,生地五两。
用法如下:以上药品切割细碎,然后用清酒六升浸泡三天。
三天后,取出药籽,静置十分钟,倒掉药渣,取药液煮到一升即可。
李氏服用两剂该方剂后,瘤体逐渐变松,疼痛减轻,经过三十天康复。
我去到揭阳,李氏挽留我,但我仍然要离开。
2. 医案二:“朱门武氏中风案”原文:天顺六年(公元1647年)春,潮州五都府人,朱门武氏中风为病,口齿不清、半身不遂。
举家亦急,因患以求医。
余闻之,往省而问之,讯其病史,为半身瘫痪,口齿故善言少语。
中医医案学0801206赵东方经通读全案自以为此案为元代医家罗天益之病案,方名冲和顺气汤出自《卫生宝鉴》卷九,方中葛根(一钱半)升麻,防风,白芷(各一钱)黄(八分)人参(七分)甘草(四分)芍药,苍术(各三分)上咀.作一服.水二盏.姜三片.枣两个.煎至一盏.去渣.温服.早饭后、午前.取天气上升之时.使人之阳气易达故也.数服而愈.患者忧思不已,饮食失节,此为伤及脾胃,然脾气通于口.其华在唇,故见环唇尤甚。
脾气受损则在上不得濡润心肺,在下不得滋养肝肾,之后诸症皆见五脏气之有损,又土本克水,今水反来侮土,故黑色见于唇,此阴阳相反,病之逆也。
《上古天真论》云:阳明脉衰于上,面始焦。
始知阳明之气不足,故用冲和顺气汤。
此药助阳明生发之剂,以复其色耳。
此为阴出乘阳。
天益师承东垣之脾胃论,以实脾胃,畅气机为治病之本,方中多为补气、散气、行气之品。
纵观诸篇之论: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
所谓无胃气者,非肝不弦,肾不石也。
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
《内经》之旨,皎如日星,犹恐后人有所未达,故《灵枢经》中复申其说。
经云∶水谷入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
胃者,水谷之海,其输上在气街,下至三里。
水谷之海有余,则腹满;水谷之海不足,则饥不受谷食。
人之所受气者,谷也;谷之所注者,胃也。
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
海之所行云气者,天下也。
胃之所出气血者,经隧也。
经隧者,五脏六腑之大络也。
又云∶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
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肺,而行呼吸焉。
荣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而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
卫者,出其悍气之疾,而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
又云∶中焦之所出,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为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
医案医话40则学习辑要(上)医案医话(1):寒入太阳、厥阴两经治案何 x x,女,四十岁,冷水江市苏菜公司职工,寒冬患病。
左胁下、脐旁二寸处,腹剧痛有块,块有鸡蛋大。
发热,体温:38. 5℃。
白细胞:13500/立方毫米。
恶寒重,舌苔边白中黄,小便黄短,大便不通,脉弦紧。
住XX医院,医皆以表寒里热组方,病加重。
痛块已由鸡蛋大增至巴掌宽,满腹皆痛,舌苔黄燥裂纹,口渴喜热饮,但饮二、三口即止,全身重被复盖,仍喊双脚冷。
病日益加重,治无良策,医院决定转院手术治疗。
余思本证恶寒发热、无汗,若纯属表寒,为何脉不浮?腹满硬痛,舌苔黄燥,大便不通,若纯属阳明腑实热证,为何脉不滑数?此人素体阳虚,从脉证看,有似《金匮要略》中之寒疝。
《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云:“胁下偏痛,发热,其脉弦紧,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宜大黄附子汤”。
说明腹痛的性质为寒。
前人认为:“非温不能散其寒,非下不能除其实,非辛不能发其邪”。
故用大黄附子汤,意在温通攻下,散寒止痛。
但此汤证与本证仍有不合。
本证恶寒重,发热,无汗,为寒邪在表。
病机表里皆寒,不可攻下。
虽有实积,但因寒而积,只要寒邪温散,不治积,积亦自去。
本证既发热,说明阳气尚不至过虚而仍可抗邪,治宜温散寒邪从表而解。
以麻黄易大黄,变大黄附子汤为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10克细辛(后下)5克附子(先煎)15克此方一出,医院主治者笑而不审方,药房嘻而不检药。
谓此汤乃太阳少阴两感之方,本证表寒里热,寒热相兼,未免失之太过。
殊不知胁下乃肝经所过之处,肝藏相火,属阴中之阳,贵在敷布,生生不息。
今寒滞厥阴,气机阻滞,相火郁而为邪,津液不能随气上达下输,故见舌苔黄燥、口渴、小便黄短。
厥阴病既不象太阴病纯属于脾虚寒证,也不像少阴病寒化、热化截然分开,而是寒热同时并见,形成寒热错杂之证。
本证本寒标热,若寒邪消散,气机通畅,阳气不郁,津液敷布,不清热而热自退。
此所谓“治病求其本”。
故方中不加寒凉之品,避免牵制,阻碍逐寒之力。
黎庇留经方医案1、处方寒热,前后不同予医学既成,仍未出而问世。
腰痛先慈偶患腰痛,不能自转侧,因不能起食,即代为之亦不愿,焦甚!试自治之。
据伤寒论:风湿相搏,骨节疼烦,用甘草附子汤,其桂枝用至四钱。
为药肆老医袁锦所笑,谓桂枝最散,止可用二三分,乌可数钱也?予曰:此未知长沙书为何物,宜不赞同。
袁曰:医人已数十年,卖药亦数十年,从未见有用桂枝如是之重者。
予曰:汝尚未悉此为何方,治何病,汝惟有执之而已。
于是朝晚服之。
其药肆之桂枝,以此而尽。
翌日,能起能食,遂愈。
此症据金匮,当用肾着汤。
予见高年病重,故不得不用此方也。
过数月,家慈忽患牙痛,不能食。
以体质素健,拟白虎汤。
市药时,袁医曰:方中生石膏七八钱,而乃用炙草之补,曷不易以生甘草,为一律凉药乎?予曰:白虎之用炙草,汝实未梦见用意之所在,则不可强以不知以为知也。
渠又劝用熟石膏。
予曰:白虎之石膏,必用生:若煆之则为无用之死灰矣。
此物嫌其下坠,故伍以炙草、粳米,使其逗留胃中,以消胃热,不使下坠者,有深旨焉。
汝不过见某药治某病,无怪谓炙草为参术苓草之草而以为补也袁又曰:前数月,服桂枝四钱,日两服,合八钱,即此人乎?予曰:然!袁曰:何寒热相悬也?予曰:前患风湿相搏,今患阳明实热,症不同,药安同哉?服白虎,牙即不痛。
2、时地同,年龄同,而虚实异右滩禄元坊,黄植泉乃翁,年六十余,患外感症,屡医未愈——小便短少,目眩耳鸣,形神枯困,全身无力,难食难睡。
脉微而沉,浸浸乎危在旦夕——医者见其小便不利,专以利湿清热,削其肾气;山楂麦芽,伤其胃阳;是速之死也。
吴君以予荐。
诊毕,断曰:此阴阳大虚,高年人误药,至于此极!补救疏非易事。
若非笃信专任,不难功败于垂成。
彼谓:“已计无复之,听先生所为而已。
”于是,先以理中汤数剂,随加附子;又数剂,胃气渐增。
前之举动需人者,稍能自动。
而其身仍振振欲辟地,改用真武汤;又数剂,其心动悸,转用炙甘草汤;数剂,心悸即止,并手足之痿者,亦渐有力。
后则或真武汤,或附子汤十余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