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 讲稿
- 格式:doc
- 大小:40.50 KB
- 文档页数:5

钟嵘的《诗品》钟嵘(约468—518)字仲伟,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
初仕于齐,梁时官至西中郎将晋安王萧纲(即后之简文帝)记室。
《诗品》作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以后,已是作者的晚年。
《诗品》专论五言诗。
据《序》说,作者因见当时人们对诗歌的评价漫无准的、意见分歧,所以作此书,意在通过对诗人的品评,建立可靠的准则。
全书实际包含两个部分,《序》总论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表达作者对诗歌写作以及当代诗风的一些看法,正文将自汉魏至齐梁的一百二十家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一卷),显优劣,叙源流,指出各家利病。
这种方法是时代风气的产物。
汉末清议,士人常相聚评论人物,至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更以品第论人。
影响到文学艺术领域,在南朝产生过很多像《棋品》、《画品》一类著作,《诗品》也由此而来。
《诗品》讨论的对象比较单纯,作者也无意故作高深,具有显明浅切的特点。
对于诗歌,主要重视充沛的感情、华茂的辞采、典雅而明朗的风格。
总的说来,和时代风气是一致的,但反对声律和用典,是独特的看法。
《诗品》序一开头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提出诗是人的感情为外物所动的自然结果。
后面又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期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
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戌,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
”使穷残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这里从景物气候和生活遭遇两方面的感动论说诗歌产生的缘由,实际也简略地概括了魏晋以来诗歌中最常见的题材。
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此文专门论诗,却没有引用相传为孔子门徒所作、具有权威性的《毛诗序》对诗的意见的。
这并非偶然。
因为儒家说诗,注重于诗的政教功用,《毛诗序》所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最为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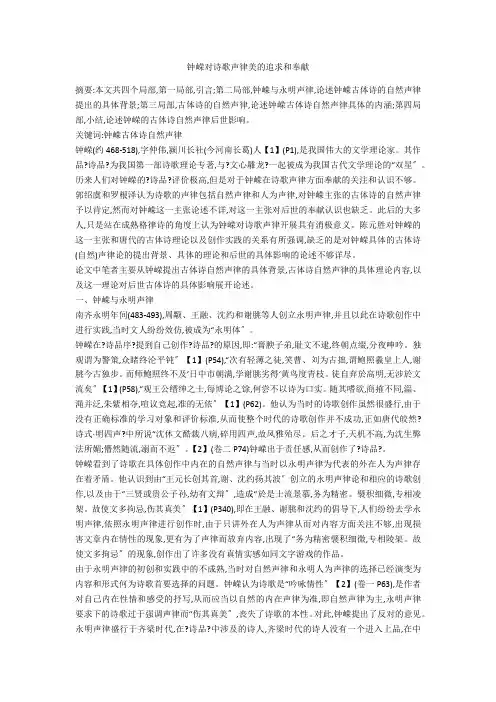
钟嵘对诗歌声律美的追求和奉献摘要:本文共四个局部,第一局部,引言;第二局部,钟嵘与永明声律,论述钟嵘古体诗的自然声律提出的具体背景;第三局部,古体诗的自然声律,论述钟嵘古体诗自然声律具体的内涵;第四局部,小结,论述钟嵘的古体诗自然声律后世影响。
关键词:钟嵘古体诗自然声律钟嵘(约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1】(P1),是我国伟大的文学理论家。
其作品?诗品?为我国第一部诗歌理论专著,与?文心雕龙?一起被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双星〞。
历来人们对钟嵘的?诗品?评价极高,但是对于钟嵘在诗歌声律方面奉献的关注和认识不够。
郭绍虞和罗根泽认为诗歌的声律包括自然声律和人为声律,对钟嵘主张的古体诗的自然声律予以肯定,然而对钟嵘这一主张论述不详,对这一主张对后世的奉献认识也缺乏。
此后的大多人,只是站在成熟格律诗的角度上认为钟嵘对诗歌声律开展具有消极意义。
陈元胜对钟嵘的这一主张和唐代的古体诗理论以及创作实践的关系有所强调,缺乏的是对钟嵘具体的古体诗(自然)声律论的提出背景、具体的理论和后世的具体影响的论述不够详尽。
论文中笔者主要从钟嵘提出古体诗自然声律的具体背景,古体诗自然声律的具体理论内容,以及这一理论对后世古体诗的具体影响展开论述。
一、钟嵘与永明声律南齐永明年间(483-493),周颙、王融、沈约和谢朓等人创立永明声律,并且以此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实践,当时文人纷纷效仿,被成为“永明体〞。
钟嵘在?诗品序?提到自己创作?诗品?的原因,即:“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
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1】(P54),“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
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
徒自弃於高明,无涉於文流矣〞【1】(P58),“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馀,何尝不以诗为口实。
随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1】(P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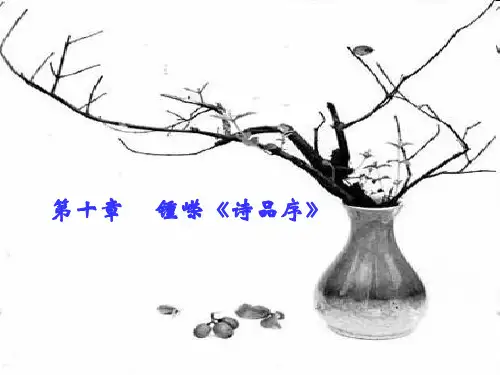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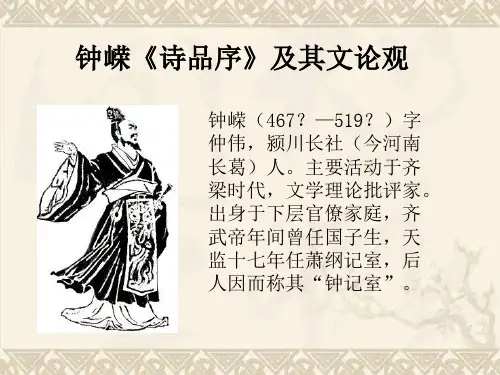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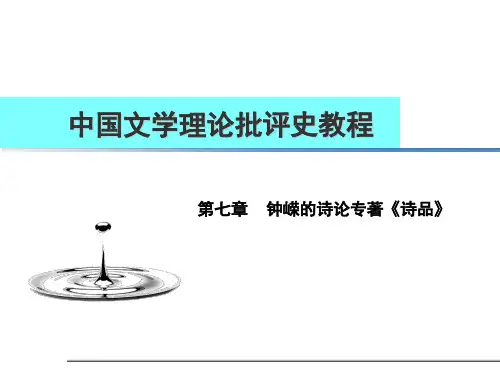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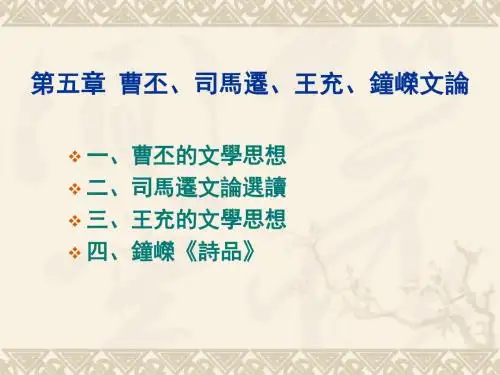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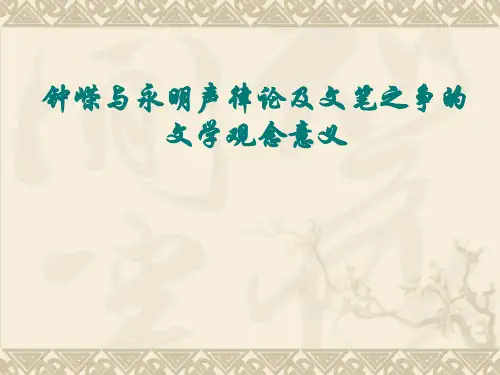

收稿日期:2012-06-07.作者简介:温燎原(1990-),男,河南信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史。
《诗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论专著,被誉为“千古论诗之祖”。
它与同时代的刘勰《文心雕龙》被称为六朝文学批评史上的双璧,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是在诗论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曰:“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
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
”[1]清人沈德潜评其为:“诗家品炙,始于钟嵘”,章学诚亦云:“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评点之书,其源亦始钟氏《诗品》,刘氏《文心》”[2];今人郭绍虞《诗话丛话》更是推其为:“诗话之始,当然首推钟嵘《诗品》。
”[3]客观地说,《诗品》虽不如《文心雕龙》那般体大精深,却也“思深意远”,仍具有较高的价值。
钟嵘以前的文学批评著述,多散见于文人别集、总集或史籍中,并无专门著述;且这些批评著述多为只言片语,大多只批评一二人之作品。
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亦。
”[4]自钟嵘《诗品》,方对前人五言诗进行系统的整理批评,故具有诸多独特的文学观念和诗学思想。
现以“感物说”、“吟咏情性说”及“文质说”为例,申说如下。
一、感物说作为具有独创性的文艺评论家,钟嵘的文学观念及其诗学思想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这些产生于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观念及文学思想,虽说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但其自身对文学批评、诗学传统及审美思想的独特领悟,则是《诗品》留给后世的最大启迪。
对于诗歌发生的探讨,钟嵘以前的各类经典已有论述。
如《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



钟嵘《诗品序》解读南朝梁钟嵘的《诗品》与刘勰的《文心雕龙》一起,代表了齐梁时期文学批评的最高成就。
宗白华曾在《美学散步》中说:“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瘐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
”可见,《诗品》产生的时期正是中国文学艺术理论批评空前活跃的时期。
钟嵘在《诗品序》中谈到自己品诗的来由时曾说:“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
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
可见“品”可以追溯到人物品评,因为在对人的品评中常用到自然喻象,所以到魏晋时期,品藻人物就开始由对人物的品评推及到自然美和艺术美的鉴赏。
同时,因为齐梁时期的文艺创作也出现“准的无依”“不显优劣”“曾无品第”的局面。
钟嵘写作《诗品》的直接的目的就是“辨彰清浊,掎摭利病”,显优劣、列品第。
钟嵘的“品”可作动词和名词两种方式来理解:作为动词,为品尝、品味之意。
它是个体的感觉,与个人的具体经验有关;又是对感觉的进一步感觉,即是对具体经验去进行品味和回味;它是美感产生的开始;它又意味着分辨或区分,在其中择优取善从美,于是才有上品中品下品之分,有三品九品之分。
作为分辨区分的结果,就是名词意义上的“品”了。
钟嵘总体上把五言诗的诗人划分为三品,一品即为一类,各类中再以风格的不同分细类,所以其理论文本的结构就是“三品论诗”。
这是《诗品》体例结构的“经”。
把三大类别的诗歌的文学风格总结为“国风”、“楚辞”和“小雅”,“国风”类的诗歌温柔敦厚且富于文采变化,钟嵘又将其分为质朴(古诗一派)与华丽(曹植一派)二派。
“楚辞”类则注重个体遭遇和个性情感的抒发,以李陵为代表。
“小雅”类将个人情感上升为哲学思考,忧患意识较突出,此派独阮藉一人。
这是《诗品》体例结构的“纬”。
《诗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接近于纯粹的文学批评。
与《文心雕龙》就文章立论不同,《诗品》专就五言诗立论,钟嵘认为五言诗“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涉江采芙蓉教学设计讲稿三维目标:1、了解《古诗十九首》;2、运用想象和联想描摹诗歌的画面;3、通过诵读、理解,体会诗歌中蕴含的感情。
教学重点:品读诗歌,把握诗歌的主旨。
教学难点:如何理解诗中的“同心而离居”的悖论式表达。
教学时数:1课时教学步骤:一、导入新课:钟嵘在《诗品》中这样评价《古诗十九首》:“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这是首《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了。
今天,我们来学习其中的《涉江采芙蓉》,来体悟其一字千金的语言魅力。
二、解题1、《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南朝萧统的《文选》,它是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的选辑,并非为一人所作。
《古诗十九首》继承了《诗经》和《楚辞》的传统,吸收了汉乐府的营养,所以不但善于运用比兴,而且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风格,艺术成就很高,被称为“五言之冠冕”(刘勰《文心雕龙》),钟嵘则称之“一字千金”。
2、古诗:这是相对于近体诗而言。
又称为“古风”、“古体诗”。
不入乐,只可诵;可换韵,不需对仗;篇幅长短不限。
与乐府诗同为汉代文学的奇葩。
三、教师范读,学生正音,朗读诗歌。
还(huán):回头,调转。
遗(wèi):赠送。
四、研读诗歌1、诗中的抒情主人公表达情感的方式是什么其目的是什么明确:表达感情的方式是采摘芙蓉;目的是“遗”远方的“同心者”。
明确:采摘花草赠给远方的亲人,这是在思念之情铭心刻骨时的自然而然的一种举动。
3、诗歌中描写“多芳草”的“兰泽”,有什么作用明确:这是环境描写。
从侧面烘托了主人公的雅洁和所表达情感的纯洁与美好。
诗中用“芙蓉”“兰泽”“芳草”,营造出一种高洁、清幽的意境。
4、三四句“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自问自答,在诗中具有怎样的表达作用明确:起过渡的作用,为表现主人公的情绪由欢欣热闹转变为下面的黯然销魂作铺垫。
5、诗人真是看到芙蓉芳草才想到“所思在远道”的吗如果不是,诗人为什么要这样写提示:“所思”是时时刻刻在他心头的,“涉江采芙蓉”也是为了她,如果诗首就开门见山地把她表出,诗就平淡无味了。
锺嵘《诗品序》气之动物,“气”,气候、节气。
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摇荡”,振动,感发。
形诸舞詠。
“舞詠”,舞蹈与歌唱。
这几句是说,气候的变化使景物也随之改变,而景物的盛衰又触发、感动着人的情感。
人的被感发的情感便要通过歌舞表现出来。
这是讲艺术创作产生的原因,是中国古代“物感”说的发展,即“由景生情,情寄诗中”。
照烛三才,“照烛”,照耀。
烛,照也。
“三才”,古人以天、地、人为“三才”。
晖丽万有,“晖丽”,辉映,光彩照耀。
“万有”,万物。
灵祗待之以致饗,“灵祗”,指天地间之神灵。
“致饗”,享用祭祀,这里指祭祀。
幽微藉之以昭告。
“幽微”,幽深微妙之物,这里指鬼神。
“昭告”,明告,告白。
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这三句沿用了《毛诗大序》的句式。
以上几句都是讲诗歌的巨大作用,在句式上大多袭用《毛诗大序》,但《诗品》讲诗歌的作用与《毛诗大序》不同。
“《毛序》偏重讲乐歌祭祀之效,及人君政教德化之功,自与锺序之纯文学诗之动天地、感鬼神不同”。
“锺嵘之诗歌效用论,具纯文学之倾向。
锺氏剔除《毛诗大序》中‘经天地,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政教、伦理之效用论,删去此小节开头‘正得失’一句,鉴乎此,则锺氏之立场、用意即可了然。
”昔《南风》之词、《南风》,传说是舜帝时的歌曲,《孔子家语·辨乐》载其辞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疑为后人伪托。
《卿云》之颂,《卿云》,传说舜帝时的歌曲。
《尚书大传·虞夏传》载:“帝乃倡之曰:‘卿云之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歌”与“颂”,互文见义。
厥义藑矣。
“厥”,其。
“藑”,深长,久远。
这几句是说,昔日有《南风》之辞,《卿云》之歌,它们的含义是很久远的。
夏歌曰:“郁陶乎予心”,“夏歌”,相传是夏朝时的歌曲,指《五子之歌》。
《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rui),作《五子之歌》”。
钟嵘《诗品序》解读教案【教学目的与要求】掌握钟嵘《诗品序》的主要理论主张【教学重、难点】对感物说、抒情论及“自然”美学原则的理解【教学方法】以讲授法为主,辅以启发和提问【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教学课时】1学时【教学资料】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
【教学内容】三、《诗品序》的思想阐发(一)论诗歌的产生与本质1.诗歌产生于外物对人的感情的激发——感物说钟嵘认为诗歌产生于外物对人的感情的激发,即感物说,《诗品序》的开篇就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气候能使自然景物发生变化,而景物变化又能感动着人心,使人的感情就受到激动,从而把内心的情感抒发出来,就形成了舞蹈、诗歌、音乐,或者说是艺术。
可以看出,钟嵘主张诗歌的产生是因为人们的性情受到了外界事物的感召和激动,他强调了外物刺激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这种“感物起情”的说法由来已久,并且是逐步发展的:它最早出现在《礼记·乐记》中,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
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音乐的产生是从人的内心发出的,而人心、情感的波动又是由于物的触动,这里的“本”,是指根本、根源于的意思。
这是这种“感物”说的首次提出,但是并没有对物的内容作具体说明。
陆机在《文赋》中也提出文学创作产生于外物对主体情感的触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随着季节的变迁,人们慨叹时光的流逝;看到万物千姿百态,又思绪纷发。
深秋季节,树叶凋落,心中感到悲凉;阳春三月,看到枝条柳嫩,心里又非常高兴。
可以看出,文学创作离不开自然景物、四时变化对作者情感有触发与刺激作用。
刘勰的《文心雕龙》对这一问题也有论述:他一方面提出“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另一方面在《时序》篇中,也开始强调“文变染乎世情,而兴废系于时序。
”刘勰不仅注意到了自然景物的作用,也注意到了社会生活以及时代的作用,这是理论上的一大进步,但是没有明确社会生活的内容。
到了钟嵘,不仅继承了“感物起情”的传统,更对这一传统有所发展,他对“物”的内容做了更加明确的分析:一方面继续强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等自然景物、气候变化对作者情感的触动。
另一方面也具体指出了社会生活内容对诗歌创作产生的重大作用,他列举了种种生活情境:“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
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一幅幅的生活场景,也同样感动着我们的心灵,激发我们去把它表达出来。
钟嵘把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穷达荣辱,也看作是诗歌创作产生的根源,这是钟嵘的创见,也是他对“感物”说的一个重要的发展。
以《诗经》第一篇是《关雎》为例,说明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优哉游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水中陆地上的水鸟的和鸣触发诗人内心的情感,感叹美好的女子应和君子相配,是以雎鸠来起兴,它触动了诗人敏感的心灵。
紧接着,依然如此,由采摘水中的水草,诗人联想到了君子对淑女的追求;荇菜的流动无方,又联想到了淑女的难求;荇菜的采之、芼之,又联想到淑女的求而得之。
可以说,这首诗应该是在雎鸠、荇菜等景物对诗人情感的触发下创作出来的,其中景对情具有很大的触动作用。
中国诗歌历来就有比兴的传统,“兴”,强调的正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即景生情,突出了外物的感召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2.诗歌的本质是表现人的情感——抒情论钟嵘认为,诗歌的本质在于对人的情感的表现,也就是被外物所激发出来的情感,如他说“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歌是人的“性情摇荡”的产物。
如《关雎》描写的是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思念和追求之情,只是以雎鸠和鸣和采摘荇菜来起兴,即景生情而已。
再比如,即使在阳春三月、春暖花开的季节,景色是明媚的,但是就没有哀伤的情感吗?春天也有伤心的人!关键还是表现诗人内心的情感。
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可谓是“愁思看春不当春”,虽然是草木茂盛、花香鸟鸣,但表现的却是国破家亡的痛苦之情,典型的是以乐景来写哀情,也使哀情更哀。
这种抒情论,摆脱了长期以来“言志”说的传统,对诗歌的本质特征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钟嵘尤其强调要抒发“怨”情,也就是人的情感要包含积极进步的社会内容。
比如他评价曹植说:“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评价《古诗》说:“多哀怨”等等,都突出了一个“怨”字。
钟嵘所强调的“怨”,其实是我国古代文艺思想史上的一个进步传统,即对黑暗的现实和政治的腐朽表示不满,对社会的不良现象进行讽刺和批评。
孔子在论文学的作用时就提出“诗可以怨”,运用诗歌对不良的现实进行批判;司马迁在评价屈原《离骚》云:“盖自怨生”,认为是屈原的内心充满怨愤不平之气,进而才写出《离骚》的。
钟嵘这里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意识,突出诗歌要抒发“怨”情,也就是情感的抒发要具有积极的社会内容,而不是空洞的无病呻吟。
这与当时六朝宫体诗的创作有关,因为当时有些宫体诗表现的是一些放纵情欲的不健康感情,是一种靡靡之音,而没有积极向上的社会内容和情感。
这是所钟嵘反对的。
钟嵘的抒情论,可以说既摆脱了儒家的“言志”说,使情感的抒发不再受到儒家礼义的约束;同时又没有六朝泛情主义的弊病,可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论诗歌创作的最高美学原则——自然上面,我们讲到了诗歌本质是自由抒情,自由的抒情,在诗歌的表现上就要求有清新、流畅的自然之美。
所以钟嵘就提出,诗歌创作应该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
1.在艺术思维上,体现为“直寻”说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观察从古到今的优美的句子,大多数都不是拼凑假借古人的词句,都是自己根据内心的感受抒写出来的。
所谓“直寻”,指的就是从感物动情中直接求得优美的词句,而不是从前人的典故或诗作中寻词觅句;也就是说,创作的灵感素材和语言都有赖于物的感召和情的摇荡,而不是靠使用典故。
进一步引申到思维上,就是说创作时要讲作者当时的真情实感,把这种真情实感用简明自然的语言直接表达出来。
这一点实际上已涉及到了中国美学中的直觉思维问题。
中国美学强调的是直觉感悟思维,注重艺术思维的直接性、形象性和契合性,多是感性的、直观的,在诗歌、音乐、绘画等艺术中都有所体现。
后来王夫之提出“即景会心”论、王国维提出“不隔”论,都受到了钟嵘“直寻”说的启发。
王夫之提出要创造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而这一点正是在钟嵘“直寻”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认为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应是心目相应一刹那自然涌现出来的,它是没有经过理性思考的,也是绝对没有虚妄的成分的。
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以“隔”与“不隔”来判断诗歌意境的优劣,认为只有“不隔”的作品才是优秀的作品。
所谓“不隔”,就是描写的诗歌境界是一种即目所见、即景会心的境界,务求做到自然传神,正像王国维自己说“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比如象陶渊明的《饮酒》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就是典型的“不隔”的境界,是陶渊明的即目所见、即景会心之作。
可以说,从钟嵘“直尋”说到王夫之的“即景会心”论,再到王国维的“不隔”论,都明显的强调了直觉思维的作用,认为诗歌创作中许多优秀佳作往往都不是靠理性思维,而是在直感的触发下产生的。
如“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等等优美的佳作都是如此。
2.在审美风格上,体现为自然论钟嵘提倡自然的审美风格,在评论谢灵运和颜延之的诗歌时曾引用汤惠休的话:“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钟嵘称赞的是“芙蓉出水”之美的,也就是“自然英旨”之美。
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上面所讲到的,反对繁琐的堆砌典故,不应该是典故的堆砌,而应是表现一种真切的感受。
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反对琐碎的声病,主张自然和谐的音律之美。
因为在钟嵘那个时代,许多诗人在创作中特别强调声律,沈约等人就大力提倡声律之说,“永明体”诗风泛滥,提倡声律是必要的,但过分的追逐,则显得有些过犹不及。
钟嵘就对这种风气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他认为“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
……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如果一味追求声律,反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古代的诗或颂,因为都是配乐的,所以不调节宫、商、角、徵、羽的五音就无法达到谐和。
但是现在的诗又不配乐,又何必要采用声调呢?他认为,只要做到音调清浊相间,贯通流畅,念起来流利,就够了。
如果文辞过多拘谨忌讳的话,反而伤害了它原本的真实和美丽。
可见,钟嵘主张的是一种自然的声律之美,一定的语言音乐美是必要的,但不能是人为的、过分的琐碎的声律。
可以说,以“直寻”说为中心的“自然英旨”论,是钟嵘对诗歌创作艺术美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