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外交辞令之说服艺术
- 格式:pdf
- 大小:411.00 KB
- 文档页数:10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中的外交辞令非常正式和庄重。
在书中,君王之间的通信常常采用一套固定的礼仪辞令,如“臣闻敬者,王之命也”、“夫敬之以好者,敢忘命乎?”等等。
这些辞令体现了古代君臣关系的严肃和尊重,使得外交交往显得庄重而庄重。
在当代外交中,我们也可以借鉴这种正式和庄重的辞令,以表达尊重和谨慎的态度。
《左传》中强调言辞的威严和正义。
在书中,左丘明通过描述君王的辞让和推诿等行为,表达了外交辞令中应当注重正义和公平的观点。
例如在记载齐国和鲁国的外交活动时,书中有“人不敢以直言告,则祸至”一句,强调了外交辞令中不应当欺瞒他人,要始终坚持正义的原则。
这种观点也可以引起我们对当代外交中言辞正义和公平的重视。
《左传》中外交辞令充满诗意和修辞。
在书中,左丘明经常使用修辞手法来表达君王的愤慨或耻辱的情绪。
例如在记载鲁襄公求救于晋国时,书中有“王京泽水;予犹悔我先臣”一句,表达了主公对自己不争气的愧疚之情。
这种富有诗意的修辞手法不仅使得外交辞令更加生动有趣,也能让对方更好地理解和感受到自己的情绪。
在当代外交中,我们也可以在外交辞令中运用一些诗意和修辞,以增加交流的艺术性和感染力。
《左传》中注重外交辞令的思辨和立场。
在书中,左丘明常常运用外交辞令来呈现君王的战略思考和政治立场。
例如在记载齐国和鲁国的外交活动时,书中有“惠后之戚,而贾其王”一句,揭示了齐国想要削弱鲁国的立场。
这种思辨和立场的呈现不仅可以帮助君王在外交交往中制定合适的策略,也能让对方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意图。
在当代外交中,我们也可以在外交辞令中展示自己的思考和立场,以增加交流的深度和广度。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中的正式庄重、威严正义、诗意修辞和思辨立场等特点,都可以引起我们对当代外交辞令的关注和思考。
在日常的外交交往中,我们可以借鉴《左传》中的外交辞令,以更好地表达和传递自己的意图,增强外交交往的效果和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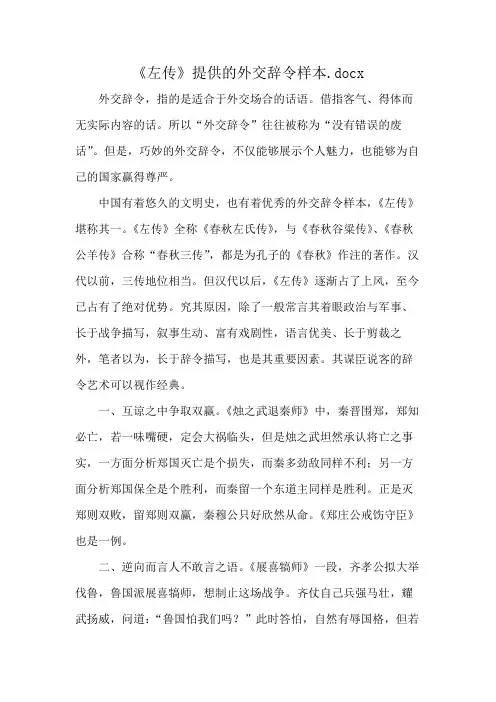
《左传》提供的外交辞令样本.docx 外交辞令,指的是适合于外交场合的话语。
借指客气、得体而无实际内容的话。
所以“外交辞令”往往被称为“没有错误的废话”。
但是,巧妙的外交辞令,不仅能够展示个人魅力,也能够为自己的国家赢得尊严。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也有着优秀的外交辞令样本,《左传》堪称其一。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与《春秋谷粱传》、《春秋公羊传》合称“春秋三传”,都是为孔子的《春秋》作注的著作。
汉代以前,三传地位相当。
但汉代以后,《左传》逐渐占了上风,至今已占有了绝对优势。
究其原因,除了一般常言其着眼政治与军事、长于战争描写,叙事生动、富有戏剧性,语言优美、长于剪裁之外,笔者以为,长于辞令描写,也是其重要因素。
其谋臣说客的辞令艺术可以视作经典。
一、互谅之中争取双赢。
《烛之武退秦师》中,秦晋围郑,郑知必亡,若一味嘴硬,定会大祸临头,但是烛之武坦然承认将亡之事实,一方面分析郑国灭亡是个损失,而秦多劲敌同样不利;另一方面分析郑国保全是个胜利,而秦留一个东道主同样是胜利。
正是灭郑则双败,留郑则双赢,秦穆公只好欣然从命。
《郑庄公戒饬守臣》也是一例。
二、逆向而言人不敢言之语。
《展喜犒师》一段,齐孝公拟大举伐鲁,鲁国派展喜犒师,想制止这场战争。
齐仗自己兵强马壮,耀武扬威,问道:“鲁国怕我们吗?”此时答怕,自然有辱国格,但若答不怕,外交谈判必然破裂。
面对此二难命题,展喜巧妙地对应:“小人恐矣,君子则否。
”进而从历史上齐鲁有盟约的角度阐述了利害关系,终于化干戈为玉帛。
三、比较之间明取舍。
《子产告范宣子轻币》一文,范宣子执政,晋国如日中天,诸朝纷纷朝贡,贡礼越送越多,郑国不堪重负。
子产劝宣子说:“子为晋国,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闻掌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
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二。
若吾子赖之,则晋国二。
诸侯二,则晋国坏;晋国二,则子之家坏。
何没没也!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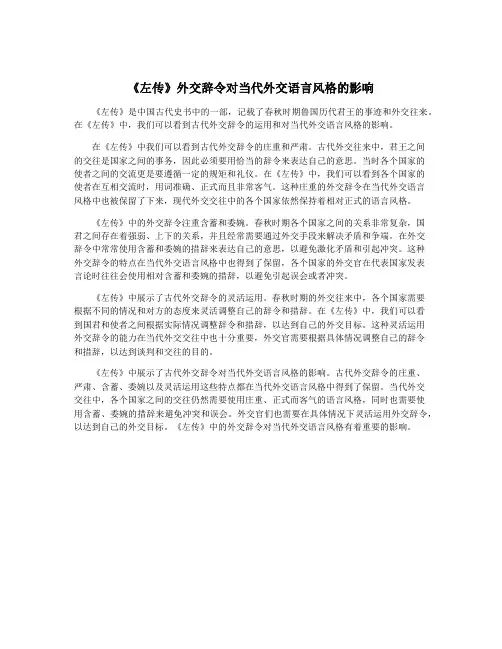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是中国古代史书中的一部,记载了春秋时期鲁国历代君王的事迹和外交往来。
在《左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外交辞令的运用和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在《左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外交辞令的庄重和严肃。
古代外交往来中,君王之间的交往是国家之间的事务,因此必须要用恰当的辞令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当时各个国家的使者之间的交流更是要遵循一定的规矩和礼仪。
在《左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的使者在互相交流时,用词准确、正式而且非常客气。
这种庄重的外交辞令在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中也被保留了下来,现代外交交往中的各个国家依然保持着相对正式的语言风格。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注重含蓄和委婉。
春秋时期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国君之间存在着强弱、上下的关系,并且经常需要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矛盾和争端。
在外交辞令中常常使用含蓄和委婉的措辞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以避免激化矛盾和引起冲突。
这种外交辞令的特点在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中也得到了保留,各个国家的外交官在代表国家发表言论时往往会使用相对含蓄和委婉的措辞,以避免引起误会或者冲突。
《左传》中展示了古代外交辞令的灵活运用。
春秋时期的外交往来中,各个国家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和对方的态度来灵活调整自己的辞令和措辞。
在《左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君和使者之间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辞令和措辞,以达到自己的外交目标。
这种灵活运用外交辞令的能力在当代外交交往中也十分重要,外交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调整自己的辞令和措辞,以达到谈判和交往的目的。
《左传》中展示了古代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古代外交辞令的庄重、严肃、含蓄、委婉以及灵活运用这些特点都在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中得到了保留。
当代外交交往中,各个国家之间的交往仍然需要使用庄重、正式而客气的语言风格,同时也需要使用含蓄、委婉的措辞来避免冲突和误会。
外交官们也需要在具体情况下灵活运用外交辞令,以达到自己的外交目标。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有着重要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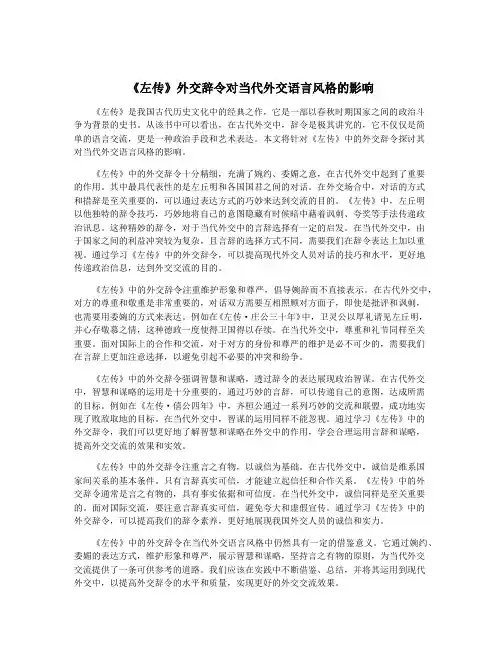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是我国古代历史文化中的经典之作,它是一部以春秋时期国家之间的政治斗争为背景的史书。
从该书中可以看出,在古代外交中,辞令是极其讲究的,它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交流,更是一种政治手段和艺术表达。
本文将针对《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探讨其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十分精细,充满了婉约、委媚之意,在古代外交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左丘明和各国国君之间的对话。
在外交场合中,对话的方式和措辞是至关重要的,可以通过表达方式的巧妙来达到交流的目的。
《左传》中,左丘明以他独特的辞令技巧,巧妙地将自己的意图隐藏有时候暗中藉着讽刺、夸奖等手法传递政治讯息。
这种精妙的辞令,对于当代外交中的言辞选择有一定的启发。
在当代外交中,由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较为复杂,且言辞的选择方式不同,需要我们在辞令表达上加以重视。
通过学习《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可以提高现代外交人员对话的技巧和水平,更好地传递政治信息,达到外交交流的目的。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注重维护形象和尊严,倡导婉辞而不直接表示。
在古代外交中,对方的尊重和敬重是非常重要的,对话双方需要互相照顾对方面子,即使是批评和讽刺,也需要用委婉的方式来表达。
例如在《左传·庄公三十年》中,卫灵公以厚礼请见左丘明,并心存敬慕之情,这种德政一度使得卫国得以存续。
在当代外交中,尊重和礼节同样至关重要。
面对国际上的合作和交流,对于对方的身份和尊严的维护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我们在言辞上更加注意选择,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和纷争。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强调智慧和谋略,透过辞令的表达展现政治智谋。
在古代外交中,智慧和谋略的运用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巧妙的言辞,可以传递自己的意图,达成所需的目标。
例如在《左传·僖公四年》中,齐桓公通过一系列巧妙的交流和联盟,成功地实现了败敌取地的目标。
在当代外交中,智谋的运用同样不能忽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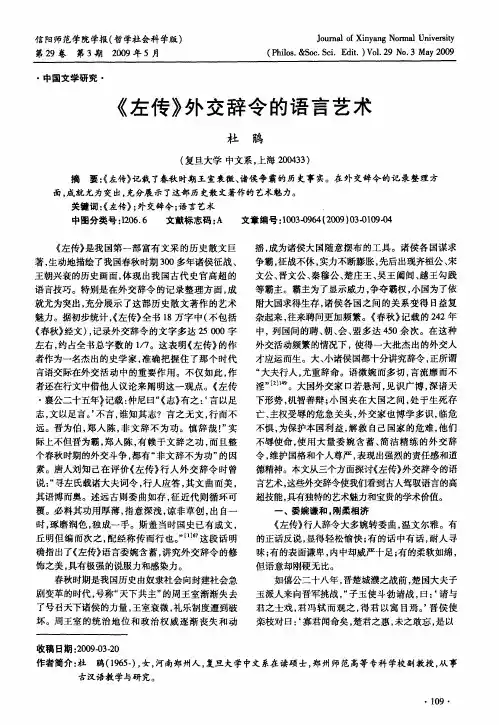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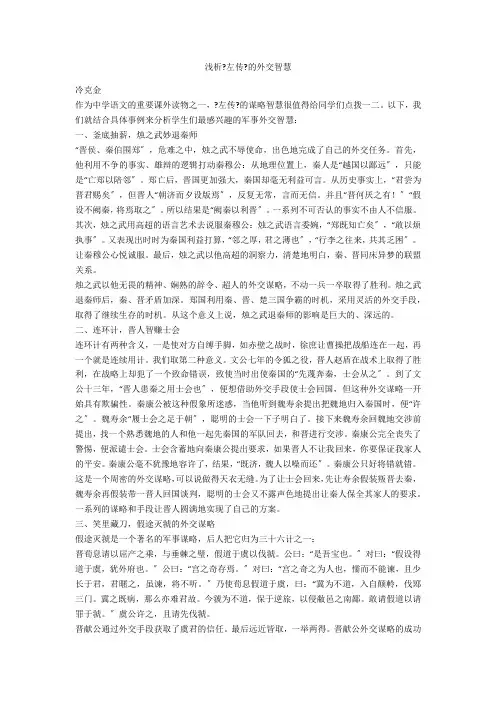
浅析?左传?的外交智慧冷克金作为中学语文的重要课外读物之一,?左传?的谋略智慧很值得给同学们点拨一二。
以下,我们就结合具体事例来分析学生们最感兴趣的军事外交智慧:一、釜底抽薪,烛之武妙退秦师“晋侯、秦伯围郑〞,危难之中,烛之武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外交任务。
首先,他利用不争的事实、雄辩的逻辑打动秦穆公:从地理位置上,秦人是“越国以鄙远〞,只能是“亡郑以陪邻〞。
郑亡后,晋国更加强大,秦国却毫无利益可言。
从历史事实上,“君尝为晋君赐矣〞,但晋人“朝济而夕设版焉〞,反复无常,言而无信。
并且“晋何厌之有!〞“假设不阙秦,将焉取之〞。
所以结果是“阙秦以利晋〞。
一系列不可否认的事实不由人不信服。
其次,烛之武用高超的语言艺术去说服秦穆公:烛之武语言委婉,“郑既知亡矣〞,“敢以烦执事〞。
又表现出时时为秦国利益打算,“邻之厚,君之薄也〞,“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
让秦穆公心悦诚服。
最后,烛之武以他高超的洞察力,清楚地明白,秦、晋同床异梦的联盟关系。
烛之武以他无畏的精神、娴熟的辞令、超人的外交谋略,不动一兵一卒取得了胜利。
烛之武退秦师后,秦、晋矛盾加深。
郑国利用秦、晋、楚三国争霸的时机,采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取得了继续生存的时机。
从这个意义上说,烛之武退秦师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
二、连环计,晋人智赚士会连环计有两种含义,一是使对方自缚手脚,如赤壁之战时,徐庶让曹操把战船连在一起,再一个就是连续用计。
我们取第二种意义。
文公七年的令狐之役,晋人赵盾在战术上取得了胜利,在战略上却犯了一个致命错误,致使当时出使秦国的“先蔑奔秦,士会从之〞。
到了文公十三年,“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便想借助外交手段使士会回国,但这种外交谋略一开始具有欺骗性。
秦康公被这种假象所迷惑,当他听到魏寿余提出把魏地归入秦国时,便“许之〞。
魏寿余“履士会之足于朝〞,聪明的士会一下子明白了。
接下来魏寿余回魏地交涉前提出,找一个熟悉魏地的人和他一起先秦国的军队回去,和晋进行交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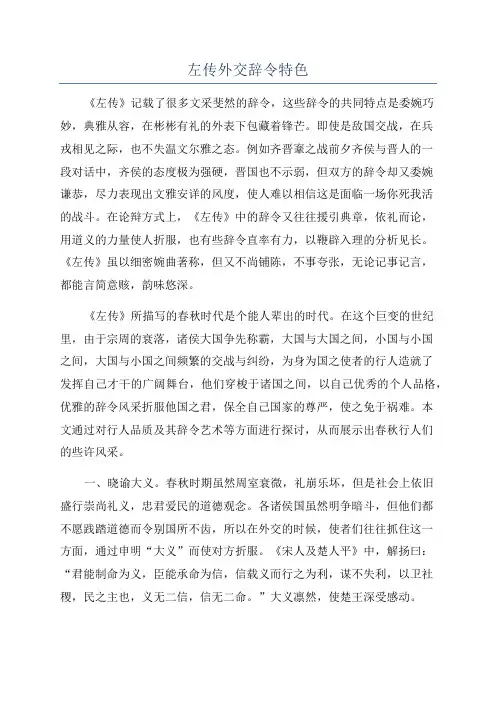
左传外交辞令特色《左传》记载了很多文采斐然的辞令,这些辞令的共同特点是委婉巧妙,典雅从容,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包藏着锋芒。
即使是敌国交战,在兵戎相见之际,也不失温文尔雅之态。
例如齐晋鞌之战前夕齐侯与晋人的一段对话中,齐侯的态度极为强硬,晋国也不示弱,但双方的辞令却又委婉谦恭,尽力表现出文雅安详的风度,使人难以相信这是面临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在论辩方式上,《左传》中的辞令又往往援引典章,依礼而论,用道义的力量使人折服,也有些辞令直率有力,以鞭辟入理的分析见长。
《左传》虽以细密婉曲著称,但又不尚铺陈,不事夸张,无论记事记言,都能言简意赅,韵味悠深。
《左传》所描写的春秋时代是个能人辈出的时代。
在这个巨变的世纪里,由于宗周的衰落,诸侯大国争先称霸,大国与大国之间,小国与小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频繁的交战与纠纷,为身为国之使者的行人造就了发挥自己才干的广阔舞台,他们穿梭于诸国之间,以自己优秀的个人品格,优雅的辞令风采折服他国之君,保全自己国家的尊严,使之免于祸难。
本文通过对行人品质及其辞令艺术等方面进行探讨,从而展示出春秋行人们的些许风采。
一、晓谕大义。
春秋时期虽然周室衰微,礼崩乐坏,但是社会上依旧盛行崇尚礼义,忠君爱民的道德观念。
各诸侯国虽然明争暗斗,但他们都不愿践踏道德而令别国所不齿,所以在外交的时候,使者们往往抓住这一方面,通过申明“大义”而使对方折服。
《宋人及楚人平》中,解扬曰:“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
”大义凛然,使楚王深受感动。
二,辩明利害。
在春秋时期变化多端的复杂局势之中,诸侯国间的战争往往采取盟约合作的方式,在获得利益的时候,就会存在着分配问题,外交使者们往往抓住这一点,挑拨盟国间的关系,从而使其统一战线瓦解,进而扭转自己的不利局势。
《烛之武退秦师》中烛之武一席“舍邻以为东道主’,分裂了齐国和晋国的合作,使郑国免除了亡国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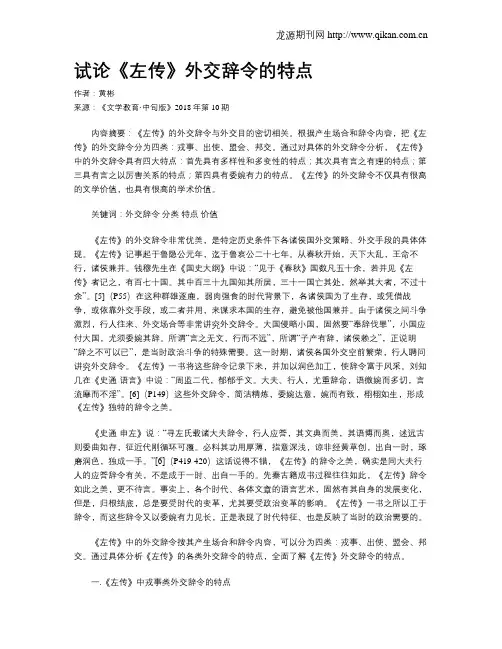
试论《左传》外交辞令的特点作者:黄彬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8年第10期内容摘要:《左传》的外交辞令与外交目的密切相关。
根据产生场合和辞令内容,把《左传》的外交辞令分为四类:戎事、出使、盟会、邦交。
通过对具体的外交辞令分析,《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具有四大特点:首先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的特点;其次具有言之有理的特点;第三具有言之以厉害关系的特点;第四具有委婉有力的特点。
《左传》的外交辞令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外交辞令分类特点价值《左传》的外交辞令非常优美,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各诸侯国外交策略、外交手段的具体体现。
《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
从春秋开始,天下大乱,王命不行,诸侯兼并。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见于《春秋》国数凡五十余,若并见《左传》者记之,有百七十国。
其中百三十九国知其所居,三十一国亡其处,然举其大者,不过十余”。
[5](P55)在这种群雄逐鹿,弱肉强食的时代背景下,各诸侯国为了生存,或凭借战争,或依靠外交手段,或二者并用,来谋求本国的生存,避免被他国兼并。
由于诸侯之间斗争激烈,行人往来、外交场合等非常讲究外交辞令。
大国侵略小国,固然要“奉辞伐罪”,小国应付大国,尤须委婉其辞。
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谓“子产有辞,诸侯赖之”,正说明“辞之不可以已”,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特殊需要。
这一时期,诸侯各国外交空前繁荣,行人聘问讲究外交辞令。
《左传》一书将这些辞令记录下来,并加以润色加工,使辞令富于风采。
刘知几在《史通·语言》中说:“周监二代,郁郁乎文。
大夫、行人,尤重辞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
[6](P149)这些外交辞令,简洁精炼,委婉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形成《左传》独特的辞令之美。
《史通·申左》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辞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刚循环可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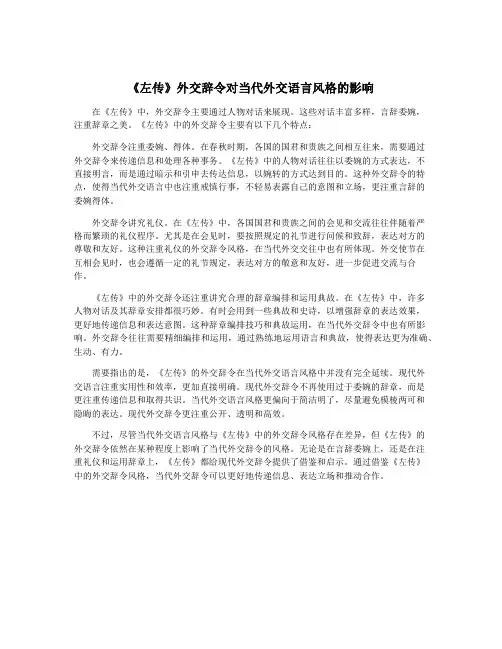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在《左传》中,外交辞令主要通过人物对话来展现。
这些对话丰富多样,言辞委婉,注重辞章之美。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外交辞令注重委婉、得体。
在春秋时期,各国的国君和贵族之间相互往来,需要通过外交辞令来传递信息和处理各种事务。
《左传》中的人物对话往往以委婉的方式表达,不直接明言,而是通过暗示和引申去传达信息,以婉转的方式达到目的。
这种外交辞令的特点,使得当代外交语言中也注重戒慎行事,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意图和立场,更注重言辞的委婉得体。
外交辞令讲究礼仪。
在《左传》中,各国国君和贵族之间的会见和交流往往伴随着严格而繁琐的礼仪程序。
尤其是在会见时,要按照规定的礼节进行问候和致辞,表达对方的尊敬和友好。
这种注重礼仪的外交辞令风格,在当代外交交往中也有所体现。
外交使节在互相会见时,也会遵循一定的礼节规定,表达对方的敬意和友好,进一步促进交流与合作。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还注重讲究合理的辞章编排和运用典故。
在《左传》中,许多人物对话及其辞章安排都很巧妙。
有时会用到一些典故和史诗,以增强辞章的表达效果,更好地传递信息和表达意图。
这种辞章编排技巧和典故运用,在当代外交辞令中也有所影响。
外交辞令往往需要精细编排和运用,通过熟练地运用语言和典故,使得表达更为准确、生动、有力。
需要指出的是,《左传》的外交辞令在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中并没有完全延续。
现代外交语言注重实用性和效率,更加直接明确。
现代外交辞令不再使用过于委婉的辞章,而是更注重传递信息和取得共识。
当代外交语言风格更偏向于简洁明了,尽量避免模棱两可和隐晦的表达。
现代外交辞令更注重公开、透明和高效。
不过,尽管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与《左传》中的外交辞令风格存在差异,但《左传》的外交辞令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当代外交辞令的风格。
无论是在言辞委婉上,还是在注重礼仪和运用辞章上,《左传》都给现代外交辞令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通过借鉴《左传》中的外交辞令风格,当代外交辞令可以更好地传递信息、表达立场和推动合作。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书之一,不仅记录了春秋时期的政治、军事等重大事件,更展现了当时的外交风采和外交辞令。
作为中国古代外交的经典之作,《左传》中的外交语言风格对当代外交语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入手,探讨其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以其精炼、严谨、婉约为特点,影响了当代外交语言的风格。
在《左传》中,外交辞令首先要符合礼制,注重言辞的得体、礼貌,遵循尊卑礼节。
《左传》中描述了鲁国大夫子路对晋国使者的接见场面,仪态得体、言词严谨、表现出深厚的儒家礼仪文化。
这种对外交辞令的崇尚礼仪,注重言辞严谨的特点,影响了当代外交语言的风格,使得外交辞令更加注重礼仪规范和言辞得体,更具有正式、严肃的特点。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注重讲究节制,克制言辞,表达含蓄,一语惊人。
在外交交往中,考虑到文化差异和对方的感受,外交辞令往往需要表达得较为含蓄。
《左传》中描述了晋国送使者向鲁国求救的情景,鲁国国君姜子牙对此的回应是“成事莫说,不成事莫说”。
这种克制言辞、表达含蓄的风格,对当代外交语言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代外交辞令也更加注重讲究节制,表达得更为含蓄,更具有风度和深度。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重视申明立场,坚持原则,注重交涉的结果。
在外交交往中,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原则非常重要,这也是《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所重视的。
《左传》中描述了晋国和齐国的交涉,齐国使者诉求晋国,晋国使者则坚持自己的原则和要求,最终争取到了有利的结果。
这种重视申明立场、坚持原则、注重交涉结果的风格,对当代外交语言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代外交辞令也更加注重申明立场,坚持原则,注重达成交涉结果。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的礼仪、克制、原则性等特点,使得当代外交辞令更加注重礼仪规范和言辞得体,更具有正式、严肃的特点;更加注重讲究节制,表达得更为含蓄,更具有风度和深度;更加注重申明立场,坚持原则,注重达成交涉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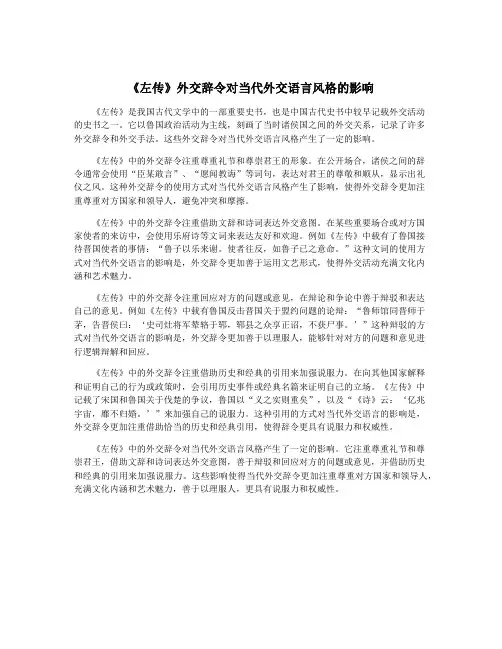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一部重要史书,也是中国古代史书中较早记载外交活动的史书之一。
它以鲁国政治活动为主线,刻画了当时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记录了许多外交辞令和外交手法。
这些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注重尊重礼节和尊崇君王的形象。
在公开场合,诸侯之间的辞令通常会使用“臣某敢言”、“愿闻教诲”等词句,表达对君王的尊敬和顺从,显示出礼仪之风。
这种外交辞令的使用方式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产生了影响,使得外交辞令更加注重尊重对方国家和领导人,避免冲突和摩擦。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注重借助文辞和诗词表达外交意图。
在某些重要场合或对方国家使者的来访中,会使用乐府诗等文词来表达友好和欢迎。
例如《左传》中载有了鲁国接待晋国使者的事情:“鲁子以乐来谢。
使者往反,如鲁子已之意命。
”这种文词的使用方式对当代外交语言的影响是,外交辞令更加善于运用文艺形式,使得外交活动充满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注重回应对方的问题或意见,在辩论和争论中善于辩驳和表达自己的意见。
例如《左传》中载有鲁国反击晋国关于盟约问题的论辩:“鲁师馆同晋师于茅,告晋侯曰:‘史司灶将军辇辂于郓,郓县之众享正诏,不获尸事。
’”这种辩驳的方式对当代外交语言的影响是,外交辞令更加善于以理服人,能够针对对方的问题和意见进行逻辑辩解和回应。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注重借助历史和经典的引用来加强说服力。
在向其他国家解释和证明自己的行为或政策时,会引用历史事件或经典名篇来证明自己的立场。
《左传》中记载了宋国和鲁国关于伐楚的争议,鲁国以“义之实则重矣”,以及“《诗》云:‘亿兆宇宙,靡不归婚。
’”来加强自己的说服力。
这种引用的方式对当代外交语言的影响是,外交辞令更加注重借助恰当的历史和经典引用,使得辞令更具有说服力和权威性。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它注重尊重礼节和尊崇君王,借助文辞和诗词表达外交意图,善于辩驳和回应对方的问题或意见,并借助历史和经典的引用来加强说服力。
《左传》的行人辞令之美郧县一中周文斌摘要:《春秋左传》是一部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复杂社会关系的重要史书。
由于时代的特殊性,致使这一时期的外交活动变得尤为频繁,而且在当时的社会中也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所以《左传》在著写时便比较注重外交上的叙事,全书在外交叙事上十分重视外交礼仪的描写、外交辞令的运用,以及从中体现处一种更为深刻的外交思想、政治观念等。
本文旨在总结分析《左传》中所描写的外交礼仪,运用的外交辞令,从中透视出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些主要的外交思想,以及政治观念、治国之策等等。
关键词:《左传》外交礼仪行人辞令叙事策略《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是配合《春秋》的编年史,相传作者是战国时鲁国史官左丘明. 。
《左传》是一部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复杂社会关系的重要史书。
春秋战国是我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进行着大分化、大改组。
《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样记载:“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在这样一个风雷激荡的时代中,战争显得十分频繁与激烈。
据《春秋》中统计:自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242年间,就发生过大小军事行动483次。
如此纷乱的社会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关节点。
王与诸侯的关系、诸侯之间的关系变得尤为紧张,于是外交活动在维护本国利益当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左传》中的外交叙事在特殊时代的影响下,成为全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版块。
《左传》在描写春秋时期的外交活动中,其精到的辞令和得当的详略是历来得到人们充分赞许的一个重要方面,其逻辑的严密、道理的明晰、词采的华瞻,委实让人叹为观止。
在描写这类外交辞令的同时,各种外交礼仪也得到了充分的关照和表现。
通过这些形象生动的记载,《左传》将这一时期的各类外交活动生动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作者虽然表面上是历史的一个记载,实际上是希望能通过这些外交辞令的描写、外交礼仪的展现以及外交活动的详细表现,让人们从中能够深刻的理解当时的社会主要思想、主流意识和作者本人对社会的看法,以及他本人对这个动荡的“礼崩乐坏”时期的主观理想和个人对社会秩序维持和修复的努力。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遗产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史书中第一部详尽记载外交事务的著作。
自春秋时期创作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言辞的含蓄和自律上,还在于其注重形式与仪式,以及倡导以德服人的外交理念。
从言辞的含蓄和自律方面看,《左传》中表达外交意愿和观点的辞令常常通过间接的方式进行,减少了直接冒犯对方的可能性。
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更能够维护外交关系的平稳和友好。
《左传》中重视言辞的自律,追求礼仪之道,强调言辞的庄重和谦逊,避免使用过于激烈或过于自负的辞令。
这种言辞的自律不仅凸显了中国外交的文化特点,也有助于和谐的外交交往。
从形式与仪式上看,《左传》注重外交活动的形式和仪式,这有助于维护外交活动的庄重和严肃性。
《左传》中记载了各国使臣进拜、贺礼的场面,使得外交活动更加正式和有仪式感。
当代外交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国家元首之间的国事访问、外交部门的正式场合等,都需要遵守一定的形式和仪式。
这种形式和仪式的规范化有助于外交关系的稳定和可预测性。
从倡导以德服人的外交理念上看,《左传》中强调以德服人,主张通过道德和仁义来影响他国和解决外交问题。
这与当代外交中的和平共处、对话与谈判等理念相契合。
当今世界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和解决争端,也更加倾向于通过和谐、合作和平等的方式来实现。
这种倡导以德服人的外交理念使得《左传》在当代外交中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言辞的含蓄和自律使得外交关系更加平稳和友好,形式与仪式的规范化增加了外交活动的庄重和严肃性,倡导以德服人的外交理念则与当代外交的理念相契合。
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和理解《左传》中的外交辞令,以便在当代外交交往中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
委婉含蓄曲折尽情——《殽之战》外交辞令的艺术特色南京市竹山中学李照东《左传》是我国先秦时期的一部历史巨著,也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
它不仅有保存史料的作用,而且也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殽之战》是《左传》中的名篇。
文中三段富有艺术魅力的外交辞令,特色鲜明。
言议从容,辞多文采;委婉含蓄,曲折尽情。
显示了春秋时代外交辞令的高超技巧。
辞令之一:弦高犒师。
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
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
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
”且使遽告于郑。
辞令写弦高途遇秦师将要伐郑,心急如焚。
怎么办?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他毅然抛弃求利之心,以国为重,当机立断,矫用郑使身份,献牛犒师;又急中生智,口出妙言巧语,周旋应敌。
“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
”出语谦恭,婉和自然,意态从容,和颜悦色。
诚恳之意可见,机巧之心难明。
“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
”更是发语巧妙,委婉得体。
乍听,热情谦和,彬彬有礼。
细想,却弦外有音,清晰可闻。
既戳穿秦师袭郑的阴谋,而又不把真象点破;在表示愿效“犬马之劳”声中,暗示郑方决非好欺。
其言之巧,在于言此意彼,意蕴隽永;其言之妙,语锋犀利,咄咄逼人,却又避开直接冒犯强秦。
“且使遽告于郑”一句,更是神来之笔。
恰如平沙千里,陡有峭崖扑面,极富神采。
不仅在语势上构成起伏,形成情节性的内容,而且又清楚点明先前弦高出语真谛所在。
话语不多,动作不大,却收到了“画龙点睛,破壁而飞”的艺术效果。
辞令之二:皇武子巧词逐客。
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
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
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辞令以来人密报之突然,穆公闻情之震惊,突出当时形势的紧张。
两个“使”字重复使用,可见事态紧急,危在旦夕:张罗肆应,刻不容缓。
[谈《左传》语言的修辞艺术]左传的语言艺术《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富有文采的历史散文巨著,它生动地描绘了中国春秋时期三百多年诸侯征战、王朝兴衰的历史画面,体现出中国古代史官高超的语言技巧,特别是在外交辞令的记录整理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充分展示了这部历史散文著作的艺术魅力。
据初步统计,《左传》全书18万字中(不包括《春秋》经文),记录外交辞令的文字多达*****字左右,约占全书总字数的七分之一。
唐人刘知己在评价《左传》语言时曾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曲而美,其语博而奥。
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
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
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行也。
”这段话明确指出了《左传》的语言委婉含蓄,讲究外交辞令的修饰之美,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正所谓“大夫行人,尤重词命。
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
本文主要探讨《左传》语言的修辞艺术,并通过这些修辞方式去领悟古人驾驭语言的高超技能。
一委婉《左传》行人辞令大多婉转委曲,温文尔雅。
有的正话反说,有的话中有话;有的表面谦卑,实却威严十足,有的柔软如棉,语意却刚硬无比。
《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前,楚国大夫子玉派人来向晋军挑战:‘“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
’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
”明明是两军对垒、刀光剑影、生死未卜的战争,斗勃在辞令上却委婉说成“士戏”,用以“寓目”,对方回答也温文尔雅,栾枝用语委婉曲折,话锋藏而不露,语态谦恭和顺,“寡君闻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诘朝将见”。
《昭公・十三年》,晋国主持召开盟会,制定各国向晋国朝贡的数额等次,子产为郑国承担过重的贡赋而在诸侯盟会上向晋国争辩。
子产首先引用周朝古制:“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
举例说明《左传》的辞令艺术-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左传》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要经典之一,被称为"春秋五传"之首。
作为史书的一种,它记录了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和各国政治斗争。
然而,与其他史书相比,《左传》以其独特的辞令艺术而备受瞩目。
辞令是指用词的精练和准确,以达到表达思想和情感的目的。
在《左传》中,辞令的运用不仅体现了作者的文学才华,更表现出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性格的细致观察和洞察力。
这种精细的辞令艺术使得《左传》独具魅力,成为一部受到广泛赞誉的文学杰作。
《左传》的辞令艺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作者通过巧妙运用词语,将复杂的历史事件和政治斗争凝练为简洁、深刻的句子。
这些句子意味深长,寓意丰富,能够达到彰显历史真相和塑造角色形象的目的。
其次,作者在描写人物性格和情感方面也展现了出色的辞令艺术。
他们运用细腻的词语,巧妙地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和心理活动,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引发读者对人物的共鸣和思考。
举例来说,比如《左传》中记载了鲁国大夫子贡的一段故事。
当子贡告别鲁国君主鲁隐公时,他用了一个简洁但意味深长的辞令:“君命不受,奚以死为!”这句话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字,却表达了子贡对君主不被听取建议的失望和悲愤之情。
这种简练的辞令表达方式,不仅省去了冗长的叙述,更体现了作者对人物心理的把握和揭示。
另外一个例子是《左传》中描述了齐庄公的一段故事。
当齐庄公得知他的大臣失言侮辱了自己后,他迅速采取了行动,并说出了这样一段辞令:“逐臧儿,不及禽兽!”这句话短小精悍,恰如其分地表达了齐庄公对大臣的失望和愤怒,同时也展现了他对权利和尊严的坚守。
通过以上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左传》中的辞令艺术不仅丰富多样,更充满了智慧和情感。
这种辞令艺术不仅赋予了《左传》以文学的美感,更使得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性格,从而体会到历史的价值和意义。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会进一步探讨《左传》中的辞令艺术,举出更多的例子,以分析其特点和对读者的影响。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一部关于政治、军事和外交的经典之作。
作为春秋时期的史书,《左传》记录了那个时代各国诸侯的政治活动、军事行动以及外交交流,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
本文将探讨《左传》对当代外交辞令的影响,主要从辞令的使用方式、意义表达以及外交智慧等方面进行分析。
《左传》对当代外交辞令的影响在于其独特的使用方式。
《左传》中的辞令往往使用间接的方式表达意思,采用含蓄、模糊的措辞,给人一种曲折、蕴藏深意的感觉。
这种使用方式使得辞令在外交交流中可以充分发挥其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即可以在不冒犯对方的情况下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利益。
与此相反,当代外交辞令往往采用更直接、明确的方式表达,包括声明、公报等形式,因此缺乏《左传》中那种委婉、含蓄的风格。
有时候过于直接的表达方式会引发误解和冲突,而《左传》中的间接方式则可以避免这些问题,这就是《左传》对当代外交辞令使用方式的一大影响。
《左传》对当代外交辞令的影响还体现在意义表达方面。
外交辞令的使用离不开意义的表达和传递。
《左传》中的辞令往往融合了丰富的文化意象和隐喻,使得意义更加丰富、深入。
《左传》中的“白马非马”一词,表达的是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存在的迷惑与矛盾。
虽然这种表达方式在当代外交中可能显得过于抽象和深奥,但仍可以借鉴其中的意义表达方式。
在当代外交中,我们可以通过使用寓意丰富的词汇和隐喻来增强表达的深度和内涵,使得辞令更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
《左传》对当代外交辞令的影响还表现在外交智慧的体现上。
《左传》中的辞令往往植根于深厚的智慧和哲学思考,展示了作者对于政治和外交的独到见解。
《左传》中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论断,表达了在外交交往中要正确认识不同国家的利益和立场,不能将自己的国家观念强加于人的智慧。
这种外交智慧可以借鉴到当代外交中,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左傳》外交辭令之說服藝術陳致宏(本文刊登於《國文天地》第23卷第6期)一、前 言《左傳》是現存記載春秋時期重要的文史資料。
而其外交辭令為歷代學者所盛贊。
《左傳》二百三十六則外交辭令,無論在辭令內容設計或語言表達技巧上,皆有值得今人借鏡學習之處。
在表達方面,間接言語行為是《左傳》外交辭令重要特色,許多不便公開明講之內容,春秋行人透過賦詩、徵引、比興等方式,間接的進行表達與溝通。
在辭令內容方面,以德、禮為外衣,行利誘、威脅之說服是一大特色。
以下分別由間接言語行為與辭令內容說服角度兩方面進行討論。
二、間接言語行為與外交賦詩間接言語行為,是指表達者因某些原因或考量,不便以公開明白的方式表達意見;轉而運用間接方式,委婉地將所欲表達之內容,寄寓於話語的表層意義之下。
對於此類話語,接受者必須配合交際當時雙方所處的主客觀語境,進行解讀,以便真正理解表達者所欲表達之真意。
《左傳》外交辭令中賦詩之屬,正是間接言語行為。
外交賦詩是指交際雙方,選賦《詩》中某詩或某詩之某章,以間接、暗示的方式,委婉地表述己意,進行言語交際的一種特殊方式。
交際雙方,在選賦某詩或某章時,是配合交際當時主客觀語境,考量國際形勢、兩國關係、雙方地位、與接受者心理等因素後,選賦最能表達己意且能令對方正確解讀之詩。
而接受者,亦在配合交際當時語境後,對表達者所賦之詩進行深層含意的解釋。
雙方運用賦詩的形式,間接地進行言語交際與溝通。
外交賦詩可算是《左傳》外交辭令中精妙之典範。
舉例說明如下。
魯昭公元年(西元前541年),正月,晉、楚、齊、魯、宋、衛、陳、蔡、鄭、許、曹等國,依弭兵之盟,尋盟(即對盟約之再確定)於虢。
盟會結束後,晉國趙孟、魯國叔孫豹、曹國大夫等人返國途經鄭國,鄭簡公依禮設宴招待。
當趙孟一行人抵達鄭國後,鄭國子皮出面迎接。
趙孟不願鄭國招待過豐,但又不便明講,於是選賦〈瓠葉〉,間接表達此意。
〈瓠葉〉全詩透過對燕飲過程之敘述,表達禮義更重於禮儀之意。
若心存禮義,則禮儀雖輕亦重;若無禮敬之心,禮儀雖重亦輕。
趙孟賦此詩暗示鄭國不必過於鋪張,簡單的宴飲亦能表達心意。
對於趙武賦詩的言外之意,子皮不能十分確定。
於是請教以能詩知禮聞名當時的魯國行人叔孫穆叔。
叔孫豹以交際當時主、客觀語境為解讀基礎,認為趙孟賦〈瓠葉〉一詩,主要是要求鄭國燕享之禮從簡。
穆叔云:「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
」之所以如此解讀,主要因為趙孟當時身體有恙,五獻之禮恐為時過長。
在無法確定的情況下,子皮仍依招待大國上卿之禮,準備豐盛的宴飲。
宴享開始後,趙孟因過於豐盛,未接受,改用一獻後,才繼續進行燕享。
分析雙方心理,趙孟所以要求燕享從簡推,主要是此時身體已弱,過長的典禮與宴飲,恐怕身體負荷不了,因此要求改為敬酒一次的一獻之禮。
另方面,趙孟辭盛禮,有提醒鄭國禮義重於禮儀之意,並暗示鄭國,切勿存貳心。
而子皮的心理方面,因晉國大國,子皮雖約略了解趙孟賦詩的言外之意,但基於對大國的禮敬,及避免引起誤解,仍舊準備五獻之禮。
待趙孟辭,而後改。
在宴飲進行之間,魯國叔孫豹賦《召南‧鵲巢》:「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此詩內容是說明諸侯之女出嫁時,迎接車隊之盛大。
魯國叔孫豹之所以賦此詩,旨在主緩和先前趙孟辭宴之事的尷尬氣氛。
如前所論,當子皮略知趙孟要求典禮從簡之意後,曾與魯國叔孫豹商議。
但基於諸多因素考量,鄭國仍備厚宴以饗趙孟。
趙孟辭謝,鄭國改從一獻之禮,燕享才繼續進行。
在此情況下,宴飲的氣氛尷尬。
於是叔孫豹賦〈鵲巢〉一詩,以諸侯嫁女,車隊百輛出迎為譬,暗指趙孟途經鄭國,鄭國亦以厚宴相待。
言外之意,替鄭國解釋何以備五獻以享趙孟。
對於穆叔的賦詩,趙孟答曰:「武不堪也。
」表示盛受不起鄭國厚宴。
魯叔孫豹又賦《召南‧采蘩》:「于以采蘩?于沼于沚。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此詩內容主要描寫婦人盡職的採蘩,以供祭祀之用。
魯叔孫豹選賦此詩,主要用意在替鄭國解釋,說明鄭國之所以未從趙孟之前所要求,將燕享之禮從簡辦理,主要是職責所在。
並非有意忽視趙孟之請。
由於當時氣氛尷尬,穆叔連賦二詩,替鄭國解釋。
為免趙孟有所誤解,叔孫豹又於賦詩後,以譬喻的方式,將事情稍微講明。
其云:「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是將鄭國比作蘩菜,說明鄭、魯等小國國力有限,今大國體恤要求宴享從簡,小國自當歡喜從命。
但今日鄭國之所以仍備厚宴,主要是出於對晉國之敬重與本身職責所在。
對於叔孫豹賦詩且說明之,趙孟遂不再提辭宴一事。
在魯國叔孫豹為鄭國解釋後,鄭國子皮賦〈野有死麇〉一詩,表達鄭國對趙孟之歉意。
為避免趙孟解讀上之誤會,子皮明言賦〈野有死麇之卒章〉,其詩云:「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此詩本是描寫男女幽會之詩。
此處則以尨喻楚,子皮希望晉、鄭兩國勿因誤會而使楚國得利。
整體而言,鄭子皮賦〈野有死麇之卒章〉一方面表達道歉之意,另方面表示鄭國服晉之心。
並要求晉國予以安全上的保障。
因為,鄭國地處南北之交,晉、楚兩國皆欲掌控。
今日鄭國歸服於晉,子皮身為鄭國執政,自然要求晉國保障鄭國之安全。
對於子皮賦詩之要求,趙孟賦《小雅‧常棣》以為回應。
趙孟選賦此詩之言外之意有二:其一,全詩內容所描寫的情況,正好符合鄭、晉二國間微妙的外交關係。
〈常棣〉一詩,描寫兄弟之間雖不免有鬩牆不合之情況,但面對外侮則能共同抵禦。
鄭國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成為晉、楚兩國必爭之地。
鄭國多次服晉,亦多次叛晉服楚。
兩國若即若離的微妙關係,正與詩中內容相似。
趙孟藉賦此詩,表達晉、鄭兩國過去雖不合,但今後將共同抵禦楚國。
其二,就當時國際形勢而言,晉、楚及各諸侯剛達成弭兵之盟(襄公二十七年)。
整個國際形勢有了新的轉變。
因弭兵之故,外交手段成為晉、楚兩國爭勝的新方式。
趙孟藉賦詩,表達晉國對鄭國之關愛,並承諾對鄭國安全之保障。
由上例可略見春秋外交賦詩之概況,交際雙方透過選賦詩之一章、某章或全詩,進行間接的言語交際行為,而是否能正確解讀,端視外交行人本身對詩的認識與文化素養,無怪乎孔子一再叮嚀其子與弟子「不學詩無以言」。
三、外交辭令內容與說服角度交際主體、交際動機、交際媒介、信息內容與交際語境是言語交際五大要素。
信息內容,是指言語交際過程中,話語符號所承載的意義。
以外交辭令而言,即辭令之內容。
在言語交際過程中,影響交際結果的因素,除主、客觀語境與交際動機外,辭令本身亦是影響外交辭令交際成敗的重要因素。
若辭令內容本身不當,不具說服力,無論輔以再高明精妙的修辭技巧,仍無法說服聽者;反之,若辭令內容本身即具說服力,即使沒有修辭潤飾,仍具有相當的說服效果。
說之以理、誘之以利、懼之以勢,是《左傳》外交辭令內容的主要說服角度。
《韓非子‧說難》云「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指出說服觀點與切入角度的適當與否,將是決定成敗的關鍵。
必須「審其有無,與其實虛,隨其嗜欲,以見其志意。
」惟盡可能的把握接受者的心理與情感,才能提高說服的成功率。
所謂「知其心,說其人」,在進行言語交際時,對於不同的說服對象,必須先審察其人格特質與主觀好惡,進而選用適當的說服角度切入,如此才能增加辭令的說服力,提高說服的成功率。
(一)、說之以理即透過辭令內容的合理性與邏輯推論,來說服聽者。
人的言行舉止、思維方式與價值觀等,往往受當代文化環境的影響與制約,在言語交際過程中,接受者主觀因素對於言語交際結果,有著相當程度的決定性。
而文化說服正是利用文化對接受者價值觀無形的制約影響,以進行說服的一種方式。
就《左傳》外交辭令而言,是指辭令內容以德、禮、忠、信、仁、義、人文、重民等文化內涵,作為外交辭令說服的主要訴求觀點。
以德、禮為外衣,以利害為內容,是《左傳》外交辭令內容的重要特色。
禮樂制度與德禮觀念是春秋貴族政治重要的構成要素,平王東遷後周室雖日微,但禮樂宗法制度尚存,因此,在國際外交場合上,各國進行外交談判時,仍多以德、禮包裝其辭令。
例如,滕薛爭長魯以禮說之(隱公十一年)、陳完以禮辭齊卿(莊公二十二年)、王孫滿以德、禮退楚莊王問鼎輕重(宣公三年)、齊賓媚人以德、禮說晉(成公二年)、曹人以德請於晉(成公十六年)、宋向戌以禮辭封(襄公九年)、駒支以德、禮說晉(襄公十四年)、子產以德、禮請輕幣(襄公二十四年)、齊、鄭二君以德請歸衛侯(襄公二十六年)、趙孟以德、禮請歸叔孫豹(昭公元年)、孔丘以德、禮退萊人(定公十年)、吳延州季子以德、禮說楚子期(哀公十年)、于尹蓋以禮說楚(哀公十五年)等,皆是以德、禮觀念為訴求之外交辭令。
其中王孫滿以德說退楚師,正是此類說服觀點代表例證。
西元前607年冬季,周匡王崩,周定王即位。
楚莊王見機不可失,遂於隔年春季以伐陸渾之戎為藉口,出兵至洛水南岸,於王畿內舉行閱兵。
面對楚國此舉,周定王遣王孫滿為使,以勞楚軍為名義與莊王會面,問明始末。
楚莊王會見王孫滿,開口便問「鼎之大小、輕重」。
鼎在春秋時期具有政治上象徵的意義,各諸侯國依其功配其爵而擁有鼎器,以代表其政治地位。
其中周王室所擁有之九鼎,政治正統的重要象徵。
楚國向被視為蠻夷,亦以蠻夷自居,因此楚國並未擁有鼎器。
楚莊王有北進中原之意,遂把握此次周王更替之際,陳兵周疆希望能取得周天子對楚國地位之認同。
面對楚莊王輕重之問,王孫滿以不卑不亢的語氣,道出夏初鑄九鼎之意義,主要為教育百姓「使民知神姦」,傳至桀因其失德遂為商所有,傳至商紂因其暴虐,鼎遂遷於周。
王孫滿道出九鼎傳承過程,主要為指出九鼎之擁有與失去,乃是以德之有無為標準。
所謂「德之休明,雖小,重也。
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
天祚明德,有所厎止。
」此正說明鼎之存否蓋以德之有無為準,有德之君,鼎雖小亦重不可去;無德之君,縱擁有大鼎亦無意義。
最後王孫滿以「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作結,指出當初周成王取得九鼎之時,曾「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周朝至今未滿七百年,天命仍舊在周。
因此,「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面對王孫滿以德、以禮為主軸的辭令內容,楚王亦不得不顧及在國際上之形象,於是退兵返國。
進一步分析,王孫滿辭令成功之因如下:其一、王孫滿能掌握楚王欲成為霸主之心態,說之以德、禮。
就春秋當時國際外交環境而言,德與禮確實是盟主、霸主所必備的重要條件。
欲成為霸主,必須取得多數國家的同盟,如齊桓公、晉文公等皆是。
就楚莊王當時形勢而言,楚國確實有先修德以取得其他國家信任與認同的必要性。
因此,王孫滿選用德、禮觀念作為主要說服觀點可謂高明矣。
其二、楚國雖有滅周之力,但尚無對抗諸侯聯軍之力。
若強攻周王室,勢必引起諸侯聯軍。
王孫滿所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主要就是指出,周王室雖以式微,但名義上仍為天下共主,除荊楚蠻夷不承認周王室地位外,各諸侯國仍尊周天子。
若楚國強行侵攻王室,則勢必為諸侯聯軍所圍。
再考量國際形勢後,楚莊王暫時退兵。
此外,齊賓媚人賂晉(成公二年)一例,亦是外交辭令以德、禮觀念說服的明顯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