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治疗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
- 格式:pdf
- 大小:273.74 KB
- 文档页数: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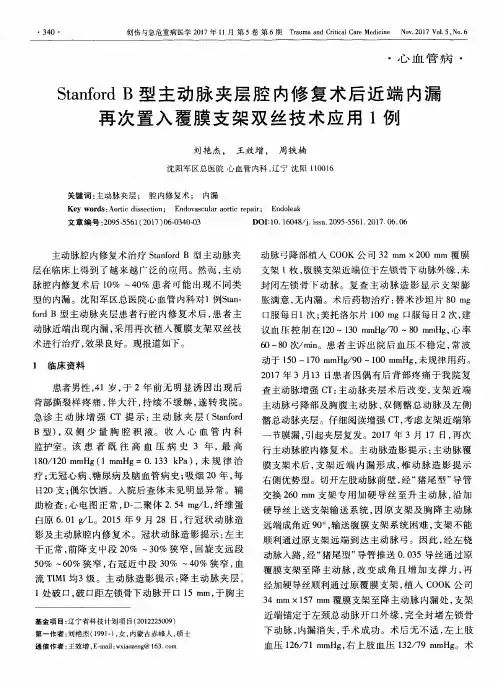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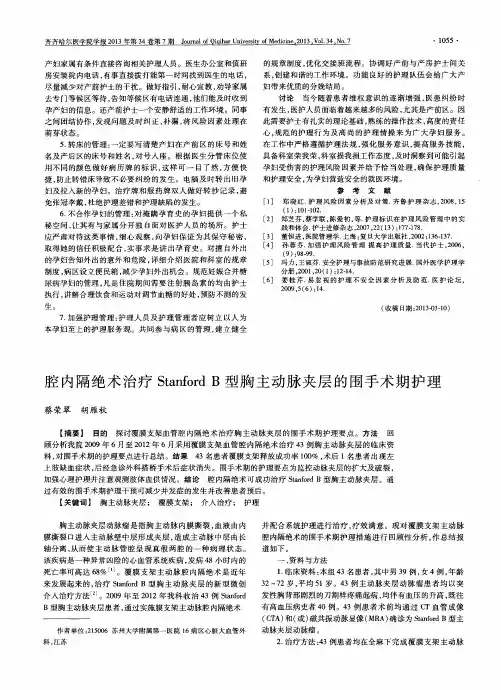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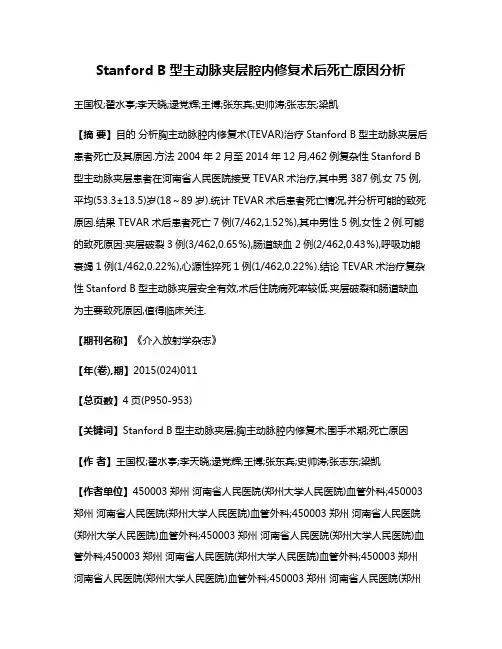
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后死亡原因分析王国权;翟水亭;李天晓;逯党辉;王博;张东宾;史帅涛;张志东;梁凯【摘要】目的分析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治疗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后患者死亡及其原因.方法 2004年2月至2014年12月,462例复杂性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在河南省人民医院接受TEVAR术治疗,其中男387例,女75例,平均(53.3±13.5)岁(18~89岁).统计TEVAR术后患者死亡情况,并分析可能的致死原因.结果 TEVAR术后患者死亡7例(7/462,1.52%),其中男性5例,女性2例.可能的致死原因:夹层破裂3例(3/462,0.65%),肠道缺血2例(2/462,0.43%),呼吸功能衰竭1例(1/462,0.22%),心源性猝死1例(1/462,0.22%).结论 TEVAR术治疗复杂性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安全有效,术后住院病死率较低.夹层破裂和肠道缺血为主要致死原因,值得临床关注.【期刊名称】《介入放射学杂志》【年(卷),期】2015(024)011【总页数】4页(P950-953)【关键词】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围手术期;死亡原因【作者】王国权;翟水亭;李天晓;逯党辉;王博;张东宾;史帅涛;张志东;梁凯【作者单位】450003郑州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人民医院)血管外科;450003郑州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人民医院)血管外科;450003郑州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人民医院)血管外科;450003郑州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人民医院)血管外科;450003郑州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人民医院)血管外科;450003郑州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人民医院)血管外科;450003郑州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人民医院)血管外科;450003郑州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人民医院)血管外科;450003郑州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人民医院)血管外科【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R541.1主动脉夹层最常见死亡原因为夹层破裂[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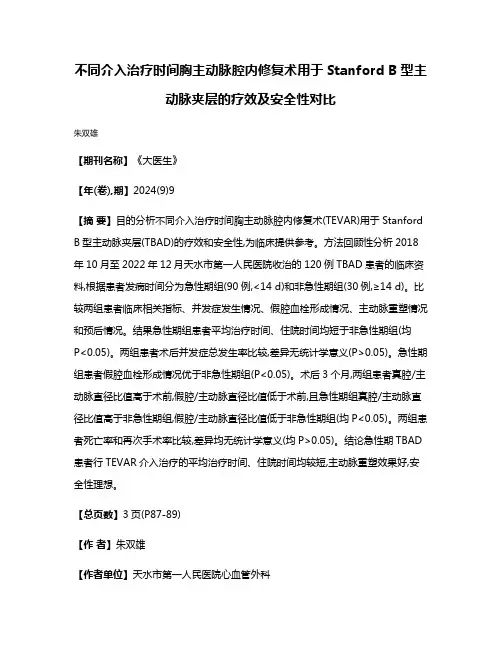
不同介入治疗时间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用于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的疗效及安全性对比朱双雄【期刊名称】《大医生》【年(卷),期】2024(9)9【摘要】目的分析不同介入治疗时间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用于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TBAD)的疗效和安全性,为临床提供参考。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0月至2022年12月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120例TBAD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发病时间分为急性期组(90例,<14 d)和非急性期组(30例,≥14 d)。
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相关指标、并发症发生情况、假腔血栓形成情况、主动脉重塑情况和预后情况。
结果急性期组患者平均治疗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非急性期组(均P<0.05)。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急性期组患者假腔血栓形成情况优于非急性期组(P<0.05)。
术后3个月,两组患者真腔/主动脉直径比值高于术前,假腔/主动脉直径比值低于术前,且急性期组真腔/主动脉直径比值高于非急性期组,假腔/主动脉直径比值低于非急性期组(均P<0.05)。
两组患者死亡率和再次手术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急性期TBAD 患者行TEVAR介入治疗的平均治疗时间、住院时间均较短,主动脉重塑效果好,安全性理想。
【总页数】3页(P87-89)【作者】朱双雄【作者单位】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R543.1【相关文献】1.不同期Stanford B型胸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后疗效及主动脉重塑临床研究2.不同期Stanford B型胸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后疗效及主动脉重塑的临床研究3.不同主动脉夹层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时机对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短期预后的影响4.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后再发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的外科治疗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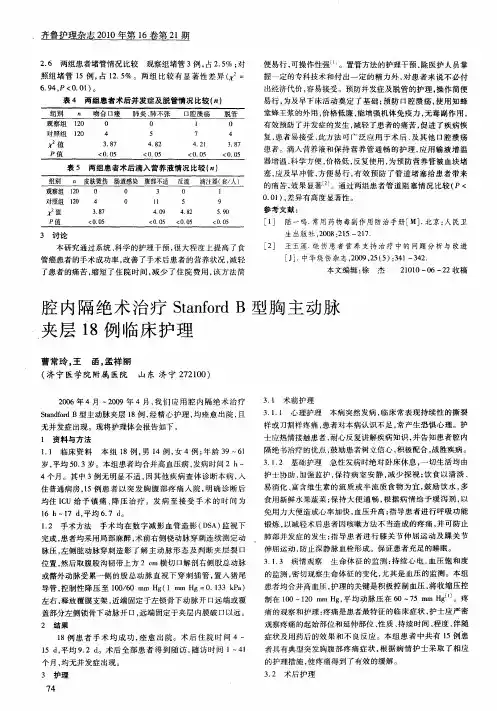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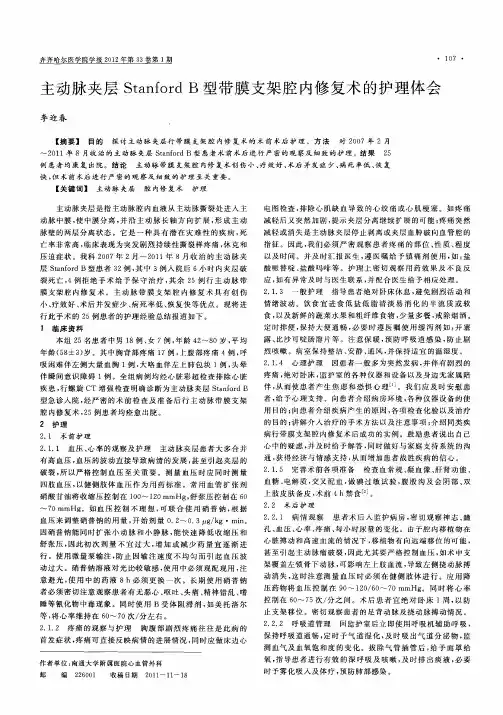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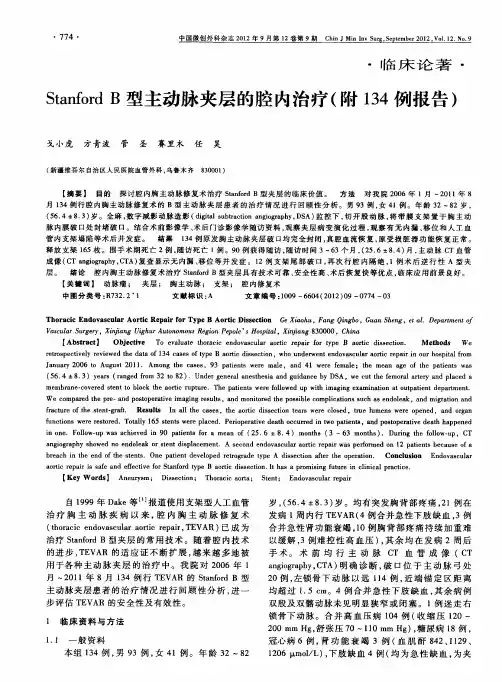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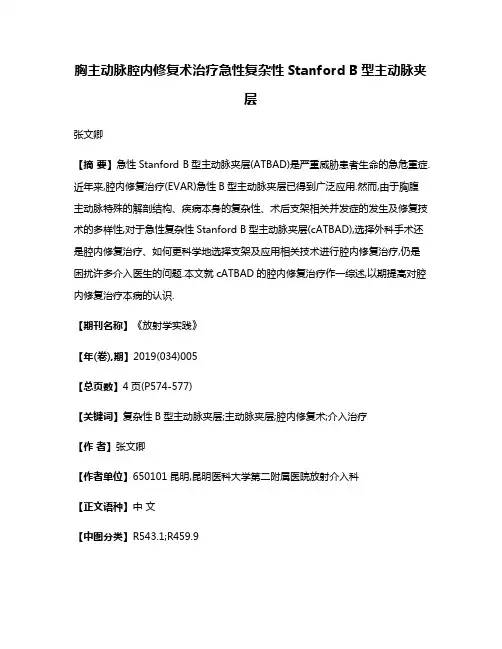
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治疗急性复杂性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张文卿【摘要】急性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ATBAD)是严重威胁患者生命的急危重症.近年来,腔内修复治疗(EVAR)急性B型主动脉夹层已得到广泛应用.然而,由于胸腹主动脉特殊的解剖结构、疾病本身的复杂性、术后支架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及修复技术的多样性,对于急性复杂性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cATBAD),选择外科手术还是腔内修复治疗、如何更科学地选择支架及应用相关技术进行腔内修复治疗,仍是困扰许多介入医生的问题.本文就cATBAD的腔内修复治疗作一综述,以期提高对腔内修复治疗本病的认识.【期刊名称】《放射学实践》【年(卷),期】2019(034)005【总页数】4页(P574-577)【关键词】复杂性B型主动脉夹层;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介入治疗【作者】张文卿【作者单位】650101昆明,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放射介入科【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R543.1;R459.9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疾病谱的改变,主动脉夹层(Aortic dissecction,AD)已经成为最常见的主动脉灾难性疾病[1]。
主动脉夹层的治疗及预后主要取决于受累的主动脉段。
根据主动脉受累情况,升主动脉夹层(Stanford A型/DeBakey Ⅰ、Ⅱ型)仍然以急诊外科手术治疗为主,胸、腹降主动脉夹层(Stanford B 型/DeBakey Ⅲ型)选择保守治疗或外科手术治疗,然而,对于复杂性病例主要选择介入血管腔内修复治疗(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EVAR)[2]。
1999年Dake等首次采用覆膜支架腔内修复治疗主动脉夹层患者,对于主动脉夹层的治疗,经历了从保守治疗、外科手术到血管腔内介入修复治疗的急剧改变[3],腔内修复治疗因创伤小、并发症少及疗效肯定等优点,近年来已逐步取代传统外科手术而成为治疗TBAD的首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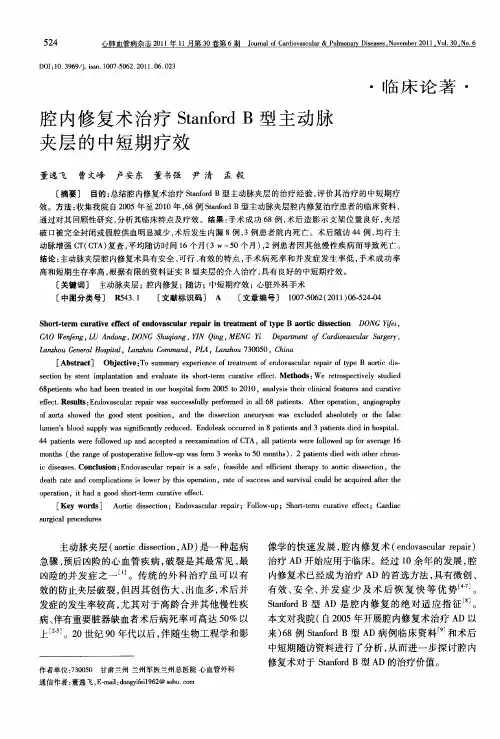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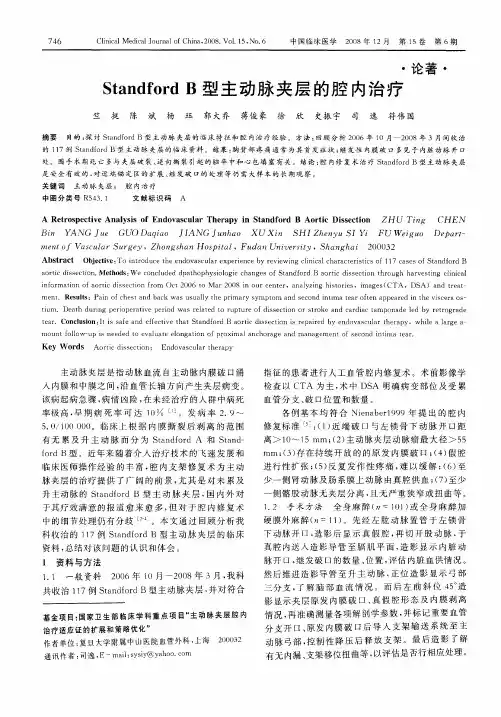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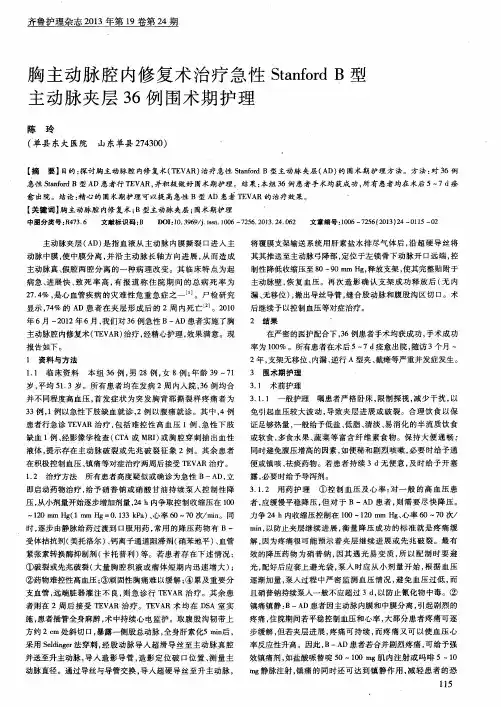
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合并左椎动脉移植1例罗翰林;陈浩;周隆书;刘伟;梁波
【期刊名称】《湖北医药学院学报》
【年(卷),期】2024(43)1
【摘要】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type B aortic dissection, TBAD)是一种严重危害生命的大血管疾病,有较高的病死率,多数TBAD具有起病急、发展快的特点。
自1996年首例TBAD腔内修复术成功实施以来,TBAD的治疗由巨创转为微创,围术期病死率和并发症发生率均显著降低[1]。
椎动脉属于后循环脑血管重要的部分,通常起自于锁骨下动脉,若起源于锁骨下动脉以外的其他动脉,即为椎动脉起源异常,亦称为迷走左椎动脉[2]。
【总页数】3页(P82-84)
【作者】罗翰林;陈浩;周隆书;刘伟;梁波
【作者单位】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国药东风总医院心胸大血管外科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54
【相关文献】
1.急性Stanford B型胸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后出现与左锁骨下动脉相通的逆向血流通道3例
2.急性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行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中部分覆盖左锁骨下动脉临床效果分析
3.单分支支架重建与单纯封闭左锁骨下动脉术在锚定区不足的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中的临床疗效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综述•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后血管重塑预测因素的研究进展杨睿,熊江,郭伟,贾贺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血管外科,北京100853)近年来,TEVAR被广泛用于治疗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type B aortic dissection,TBAD),数项RCT及荟萃分析研究均显示出其具有明显的优势,有逐渐成为TBAD—线治疗方案的趋势〔"I。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接受TEVAR的TBAD均能达到良性转归,部分患者术后仍会出现主动脉扩张、假腔不闭合等血管重塑不良情况,导致远期主动脉相关不良事件讯現因此,早期识别并控制可能预示TEVAR后血管重塑不良的因素尤为必要。
本文就此问题综述相关文献,从手术干预时机的选择、TBAD的不同亚型、支架移植物长度的控制、腹部残留裂口的影响、术后内漏的类型等角度进行探讨,最后提出应用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的研究方法对TEVAR后血管重塑结果进行展望。
1手术干预时机选择由于复杂型TBAD早期和5年死亡率分别高达16%和40%[6-7],尽早进行TEVAR干预已在学界达成了共识叫对于非复杂型TBAD,过去的研究表明在急性期(起病14d之内)实施TEVAR的血管重塑效果优于慢性期(起病超过14(1)3"。
然而,2013年一项针对大宗病例的K-M生存曲线研究发现,夹层起病后1个月之内的生存率下降比较明显阳,这引起了学界对原有分期标准能否准确评估TBAD的质疑。
Dake等问提出了一种创新性的夹层分类系统DISSECT分类法,旨在解决传统分期方法滞后而无法有效评估TEVAR效果的痛点。
这种分类法将夹层的分期从起病时开始计算并界定为3个时期,即急性期(W14d)、亚急性期(15~ 90d)和慢性期(>90d)。
随后发表的VIRTUE(前瞻性多中心注册研究)中期结果为DISSECT分类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其结果表明亚急性期术后DOI:10.3969/j.issn.1674-7429.2021.01.019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1770465)通讯作者:熊江,电子邮箱:*********************血管重塑程度与急性期相似,而在急性期进行TEVAR的风险明显高于亚急性期和慢性期⑸。
胸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内漏研究万珊杉;吴敏;王家平;杨帆;孙寰;陆发承;刘召;邢艺苑【摘要】目的探讨胸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TEVAR)治疗Stanford B型胸主动脉夹层发生内漏原因及分型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07年3月至2014年5月确诊为StandfordB型胸主动脉夹层并完成TEVAR术治疗的189例患者,观察术中及术后内漏分型及影像学表现,患者生存率和生存质量.结果 TEVAR术中和术后共25例患者发生内漏,发生率为13.2%(25/189).其中急性内漏22例,包括Ⅰ型14例(7.4%),Ⅱ型8例(4.2%);迟发性内漏3例,包括Ⅱ型2例(1.1%),Ⅲ型l例(0.5%).术后患者生存质量未下降,未出现截瘫、肾动脉缺血等严重并发症.结论 TEVAR术内漏分型、影响因素不同,内漏发生概率各异,急性和迟发性内漏中Ⅰ型和Ⅱ型内漏最为常见.【期刊名称】《介入放射学杂志》【年(卷),期】2016(025)010【总页数】4页(P908-911)【关键词】胸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内漏;分类【作者】万珊杉;吴敏;王家平;杨帆;孙寰;陆发承;刘召;邢艺苑【作者单位】650101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放射科;650101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放射科;650101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放射科;650101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放射科;650101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放射科;650101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放射科;650101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胸心血管外科;650101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放射科【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R543.16胸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TEVAR)以植入支架封闭血管内膜撕裂破口,隔绝血流向假腔流入,可达到良好治疗效果。
内漏是TEVAR术最为常见且重要并发症,必须及时处理,其持续存在有时意味着TEVAR治疗失败,甚至会导致封闭假腔再次开放、撕裂[1]。
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治疗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发表时间:2016-11-28T17:08:45.260Z 来源:《医师在线》2016年9月第17期作者:贺赟鋆[导读] 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治疗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效果肯定,并发症少,但存在较多并发症,有待于材料技术的提高获得改善。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外科,浙江,杭州,310000)摘要: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是一种复杂、相对常见、危害性大的疾病。
解剖上常表现为降主动脉壁部分撕裂后形成假腔甚至破裂。
早期,复杂的B型主动脉夹层采用开放手术治疗或积极的药物治疗,手术早期死亡率高,药物治疗容易出现夹层动脉瘤。
1999年Nienaber 和Dake提出腔内治疗B型急性主动脉夹层。
此后,主动脉腔内修复术成为主动脉夹层治疗的首选方法。
本文主要回顾主动脉夹层的进展及并发症。
关键词: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并发症1、背景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是一种复杂、相对常见、危害性大的疾病。
解剖上常表现高血压引起主动脉内膜及中膜撕裂,形成真腔和假腔并存,影响主动脉的弹性和灵活性[1]。
Olsson等的研究报道的1987~2002年的14000多例尸检报告中,22%的胸主动脉瘤和夹层病人死于就诊前,表明急性期及时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性[2]。
Hirst等报道主动脉夹层死亡每小时增加1%,80%的患者可能在前两周已经死亡[3]。
早期,复杂的B型主动脉夹层采用开放手术治疗或积极的药物治疗,手术早期死亡率高,药物治疗容易出现夹层动脉瘤。
尽早治疗能提高长期生存率[4]。
1802年, Maunoir提出 “主动脉夹层”。
1954年, DeBakey和他的助手完成第一例手术切除胸主动脉夹层动脉瘤[5]。
1999年, Nienaber等和Dake等同时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血管内支架修复治疗急性B型主动脉夹层的早期临床经验[6,7],确立了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horacic Endovascular Repair, TEVAR)的地位。
2、临床表现及诊断B型主动脉夹层未经治疗死亡率高达80%,早期诊断和治疗是改善预后的关键[8,9]。
国际认可的急性主动脉夹层的典型临床表现是突然发作且超过病人以前经历的剧烈疼痛。
症状、病史和体格检查并不是急性B型主动脉夹层的敏感依据,需要进一步完善检查如心电图、胸片、血生化和主动脉CT血管成像(CTA),以明确诊断和及时治疗稳定病情。
多重螺旋CT诊断准确性高,应用广泛,可快速采集图像和重建数据,是制定治疗方案的重要参考。
3、腔内治疗主动脉夹层急性发病后,患者如能及时得到对症治疗,包括降低血压(收缩压在120mmHg以下或平均动脉压在60~70mmHg),控制心率(小于60次/分),确保器官灌注和纠正并发症。
病情得到稳定后,可考虑腔内覆膜支架治疗。
主动脉腔内修复术(EVAR)已被医学界认为是一种安全有效手术方式,与传统的手术方式相比存在优势[10]。
手术主要通过覆膜支架经动脉植入主动脉真腔内,覆盖主动脉近端撕裂的破口,防止延迟膨胀和破裂,诱发假腔血栓形成,并促使夹层的近远端真腔扩张,假腔减小。
腔内治疗较开放手术的优点包括:避免开胸;失血少;手术时间短;病人恢复快;死亡率明显减少。
目前发现第一代覆膜支架系统存在很多问题,如主动脉夹层逆撕、支架内漏、主动脉覆膜渗漏、支架移动及弯折等。
然而,通过成功治疗胸主动脉疾病,支架系统已经迅速得到改进。
现在可用的支架系统更适合B型主动脉夹层的治疗。
并且,随着支架技术的显著提高,对患者的解剖要求明显降低,适用范围明显扩大。
这主要是归功于开窗支架技术、分支支架技术和烟囱支架技术。
对于复杂型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行腔内修复术疗效显著,但同时存在明确的手术风险,特别是解剖结构复杂的病人。
对于无症状及慢性夹层患者需要充分告知。
Parker[11]等通过搜索MEDLINE数据库获得29个关于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治疗的临床研究,并进行META分析发现,942例复杂B型主动脉夹层,技术成功率95%,住院死亡率9%,主要并发症(神经系统并发症、逆撕A型主动脉夹层、内漏、肠梗塞、大截肢、高位截瘫)8.1%。
平均随访20个月,生存率88%,再次手术10.4%(腔内手术7.6%,开放手术2.8%),主动脉破裂0.8%。
这些并发症都有待于支架系统技术改进来规避。
逆撕A型主动脉夹层是指主动脉夹层术后出现升主动脉夹层,这在主动脉腔内修复术后并不罕见,严重者可危及生命。
其实逆撕并不是只在腔内治疗后出现,开放手术及单纯药物治疗后也有相关报道[12]。
主动脉壁的脆弱性和疾病进展可导它的发生。
因此,对于扭曲的主动脉患者或马凡综合症患者,选择没有近端裸支架并提高支架的柔顺性可能避免这种灾难性并发症的发生[13]。
假腔存在明显内漏及持续灌注是随访中需要再次手术的决定因素。
许多研究报道发现假腔持续内漏与长期生存减少显著相关[14]。
假腔灌注多见于远端破口或分支动脉的倒灌(2型内漏)。
支架修补远端破口和假腔栓塞为常见的治疗方式。
Lombardi[15]和Hofferberth等[16]报道了他们二次手术处理假腔后仍能观察到部分患者存在内漏和主动脉扩张。
Hofferberth等人进一步的研究中使用主动脉假腔内栓塞技术治疗内漏,显示假腔内栓塞技术在参与术后内漏的治疗上是一个安全和有前途的辅助方法[17]。
Daniel等[18]发现左锁骨下动脉覆盖的患者II 型和复杂内漏的发生率显著增高。
主动脉夹层内漏复杂且还有很多疑问,需要进一步探索。
主动脉腔内修复技术非常依赖支架系统的不断研发和改进。
Palma等人报道58例病人使用定制支架治疗B型主动脉夹层,没有发生内漏和截瘫[19]。
但病例数均较少,需要更大规模的样本量来证实。
4.结论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治疗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效果肯定,并发症少,但存在较多并发症,有待于材料技术的提高获得改善。
参考文献[1] Greenberg R, et al. ‘Aortic dissection: new perspective and treatment paradigms’. Eur J Vasc Endovasc Surg, 2003, 26: 579-586.[2] Olsson C, et al. ‘Thoracic aortic aneurysm and dissection: increasing prevalence and improved outcomes reported in a nationwide population-based study of more than 14,000 cases from 1987 to 2002’. Circulation, 2006, 114(24): 2611–2618.[3] Hirst AE Jr, et al. ‘Dissecting aneurysm of the aorta: a review of 505 cases’. Medicine (Baltimore), 1958, 37(3): 217-79.[4] Akin I, et al. ‘Indication, timing and results of endovascular treatment of type B dissection’. Eur J Vasc Endovasc Surg, 2009, 37(3): 289-296.[5] De Bakey ME, et al. ‘Surgical Considerations of Dissecting Aneurysm of the Aorta’. Ann Surg, 1955, 142(4): 586-612.[6] Nienaber CA, et al. ‘Nonsurg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oracic Aortic Dissection by Stent-Graft Placement’. N Engl J Med, 1999, 340: 1539-45.[7] Dake MD, et al. ‘Endovascular stent-graft placement for the treatment of acute aortic dissection’. N Engl J Med, 1999, 340(20): 1546-52.[8] Hagan PG, et al.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y of Acute Aortic Dissection (IRAD): new insights into an old disease’. JAMA, 2000, 283(7): 897-903[9] Shiga T, et al. ‘Diagnostic accuracy of 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 helical computed tomography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or suspected thoracic aortic dissection: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Arch Intern Med, 2006, 166(13): 1350-1356.[10] Kato M, et al. ‘Outcomes of stent-graft treatment of false lumen in aortic dissection’. Circulation, 1998, 98: II305-II311.[11] Parker JD & Golledge J. ‘Outcome of endovascular treatment of acute type B aortic dissection’. Ann Thorac Surg, 2008, 86: 1707-1712.[12] Hata M, Sezai A, Niino T, Yoda M et al. ‘Prognosis for patients with type B acute aortic dissection: risk analysis of early death and requirement for elective surgery’. Circ J, 2007, 71: 1279-1282.[13] Dong ZH, Fu WG et al. ‘Retrograde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 After Endovascular Stent Graft Placement for Treatment of Type B Dissection’. Circulation, 2009, 119: 735-741.[14] Bernard Y, Zimmermann H, Chocron S et al. ‘False lumen patency as a predictor of late outcome in aortic dissection’. J Am Coll Cardiol, 2001, 87: 1378-1382.[15] Lombardi JV, Cambria RP, Nienaber CA et al.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clinical trial (STABLE) on the endovascular treatment of complicated type B aortic dissection using a composite device design’. J Vasc Surg, 2012, 55: 629-640.[16] Hofferberth SC, Foley PT, Newcomb AE et al. ‘Combined proximal endografting with distal bare-metal stenting for management of aortic dissection’. Ann Thorac Surg, 2012, 93: 95-102.[17] Hofferberth SC et al. ‘Aortic False Lumen Thrombosis Induction by Embolotherapy (AFTER) Following Endovascular Repair of Aortic Dissection’. J Endovasc Ther, 2012, 19: 538-545[18] Sze DY, van den Bosch MA, Dake MD, Miller DC, Hofmann LV et al. ‘Factors Portending Endoleak Formation after Thoracic Aortic Stent-Graft Repair of Complicated Aortic Dissection’. Circ Cardiovasc Intervent, 2009, 2: 105-112.[19] Palma JH, de Souza JA, Rodrigues Alves CM, Carvalho AC & Buffolo E. ‘Self-expandable aortic stentgrafts for treatment of descending aortic dissections’. Ann Thorac Surg, 2002, 73, 1138-41, discussion 1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