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启蒙、理性与神话
- 格式:doc
- 大小:37.00 KB
- 文档页数: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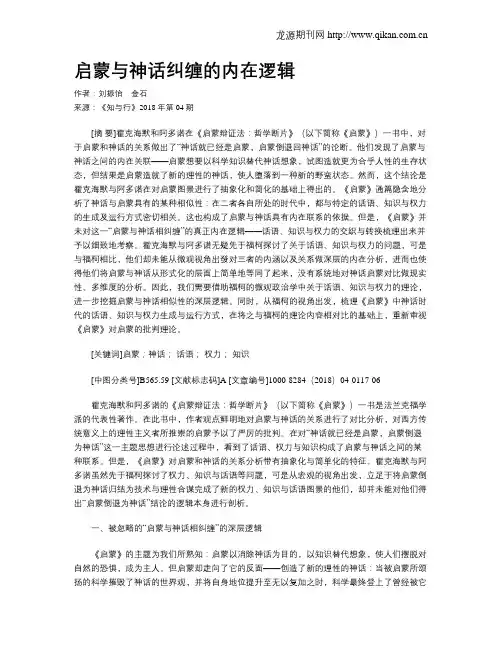
启蒙与神话纠缠的内在逻辑作者:刘振怡金石来源:《知与行》2018年第04期[摘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以下简称《启蒙》)一书中,对于启蒙和神话的关系做出了“神话就已经是启蒙,启蒙倒退回神话”的论断。
他们发现了启蒙与神话之间的内在关联——启蒙想要以科学知识替代神话想象,试图造就更为合乎人性的生存状态,但结果是启蒙造就了新的理性的神话,使人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
然而,这个结论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对启蒙图景进行了抽象化和简化的基础上得出的。
《启蒙》通篇隐含地分析了神话与启蒙具有的某种相似性:在二者各自所处的时代中,都与特定的话语、知识与权力的生成及运行方式密切相关。
这也构成了启蒙与神话具有内在联系的依据。
但是,《启蒙》并未对这一“启蒙与神话相纠缠”的真正内在逻辑——话语、知识与权力的交织与转换梳理出来并予以细致地考察。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无疑先于福柯探讨了关于话语、知识与权力的问题,可是与福柯相比,他们却未能从微观视角出發对三者的内涵以及关系做深层的内在分析,进而也使得他们将启蒙与神话从形式化的层面上简单地等同了起来,没有系统地对神话启蒙对比做现实性、多维度的分析。
因此,我们需要借助福柯的微观政治学中关于话语、知识与权力的理论,进一步挖掘启蒙与神话相似性的深层逻辑。
同时,从福柯的视角出发,梳理《启蒙》中神话时代的话语、知识与权力生成与运行方式,在将之与福柯的理论内容相对比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启蒙》对启蒙的批判理论。
[关键词]启蒙;神话;话语;权力;知识[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8)04-0117-06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以下简称《启蒙》)一书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著作。
在此书中,作者观点鲜明地对启蒙与神话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对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所推崇的启蒙予以了严厉的批判。
在对“神话就已经是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这一主题思想进行论述过程中,看到了话语、权力与知识构成了启蒙与神话之间的某种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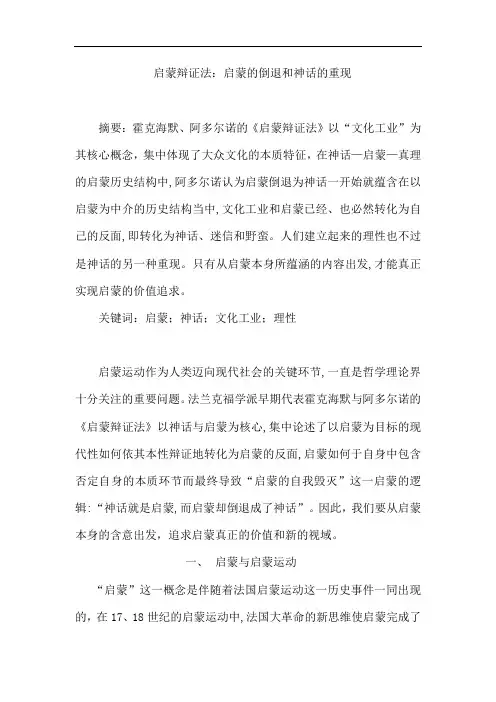
启蒙辩证法:启蒙的倒退和神话的重现摘要: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以“文化工业”为其核心概念,集中体现了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在神话—启蒙—真理的启蒙历史结构中,阿多尔诺认为启蒙倒退为神话一开始就蕴含在以启蒙为中介的历史结构当中,文化工业和启蒙已经、也必然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即转化为神话、迷信和野蛮。
人们建立起来的理性也不过是神话的另一种重现。
只有从启蒙本身所蕴涵的内容出发,才能真正实现启蒙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启蒙;神话;文化工业;理性启蒙运动作为人类迈向现代社会的关键环节,一直是哲学理论界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以神话与启蒙为核心,集中论述了以启蒙为目标的现代性如何依其本性辩证地转化为启蒙的反面,启蒙如何于自身中包含否定自身的本质环节而最终导致“启蒙的自我毁灭”这一启蒙的逻辑:“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
因此,我们要从启蒙本身的含意出发,追求启蒙真正的价值和新的视域。
一、启蒙与启蒙运动“启蒙”这一概念是伴随着法国启蒙运动这一历史事件一同出现的,在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法国大革命的新思维使启蒙完成了自己从理论到现实的转变,造就了本身的现代形式,同时启蒙也规定了现代社会的品格、方向和内容。
康德关于“启蒙”的经典定义是人必须永远具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1]启蒙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等的追求无可否认,但其和理性的最直接和最大程度的契合,是启蒙在近代最为突出的表现。
“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2]。
近代启蒙的事实也证明启蒙实现了这样的目标。
但问题是,在这些诉求得到满足之后,启蒙本身发生了翻转,这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论证的重点。
他们通过将启蒙过程描述为不完整的,对启蒙运动的进步叙事提出了质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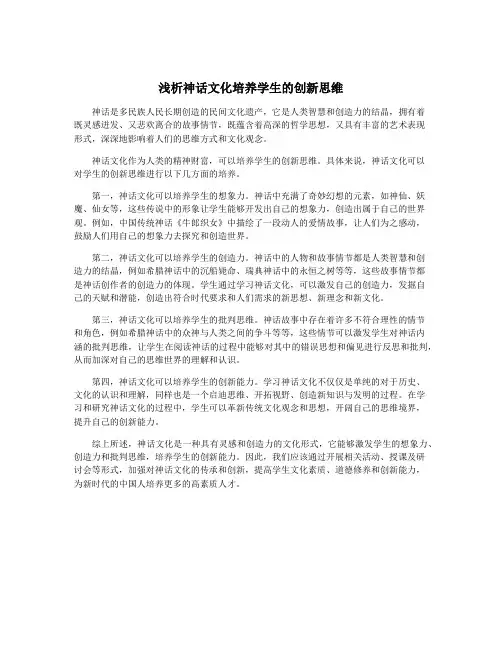
浅析神话文化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神话是多民族人民长期创造的民间文化遗产,它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拥有着既灵感迸发、又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既蕴含着高深的哲学思想,又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
神话文化作为人类的精神财富,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具体来说,神话文化可以对学生的创新思维进行以下几方面的培养。
第一,神话文化可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神话中充满了奇妙幻想的元素,如神仙、妖魔、仙女等,这些传说中的形象让学生能够开发出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世界观。
例如,中国传统神话《牛郎织女》中描绘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让人们为之感动,鼓励人们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探究和创造世界。
第二,神话文化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神话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都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例如希腊神话中的沉船毙命、瑞典神话中的永恒之树等等,这些故事情节都是神话创作者的创造力的体现。
学生通过学习神话文化,可以激发自己的创造力,发掘自己的天赋和潜能,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和人们需求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文化。
第三,神话文化可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
神话故事中存在着许多不符合理性的情节和角色,例如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与人类之间的争斗等等,这些情节可以激发学生对神话内涵的批判思维,让学生在阅读神话的过程中能够对其中的错误思想和偏见进行反思和批判,从而加深对自己的思维世界的理解和认识。
第四,神话文化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学习神话文化不仅仅是单纯的对于历史、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同样也是一个启迪思维、开拓视野、创造新知识与发明的过程。
在学习和研究神话文化的过程中,学生可以革新传统文化观念和思想,开阔自己的思维境界,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
综上所述,神话文化是一种具有灵感和创造力的文化形式,它能够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开展相关活动、授课及研讨会等形式,加强对神话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提高学生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和创新能力,为新时代的中国人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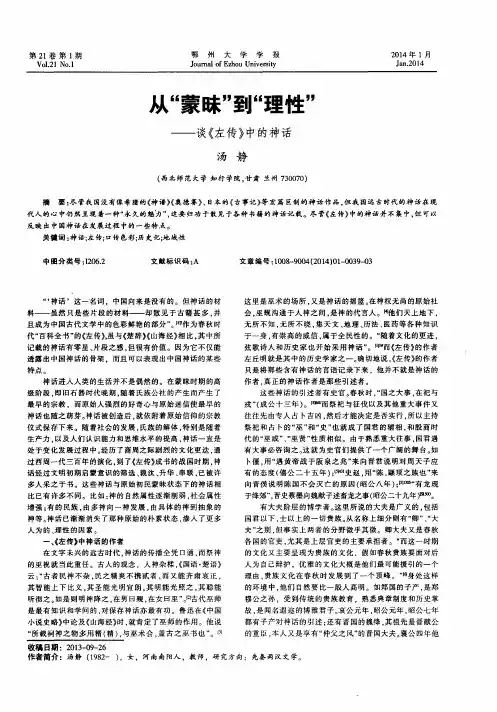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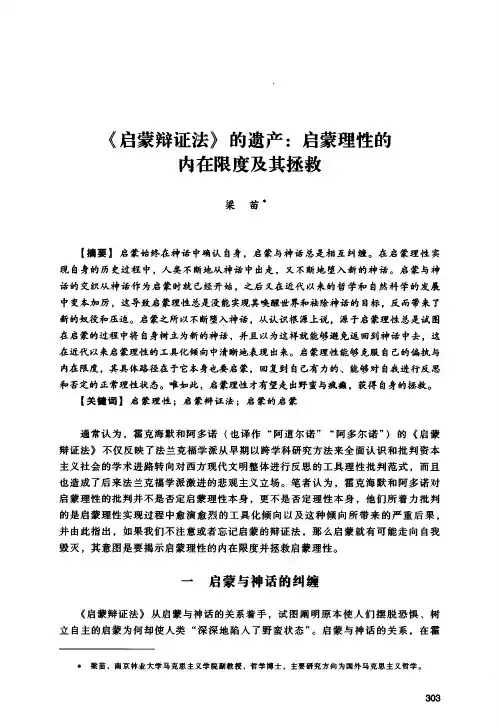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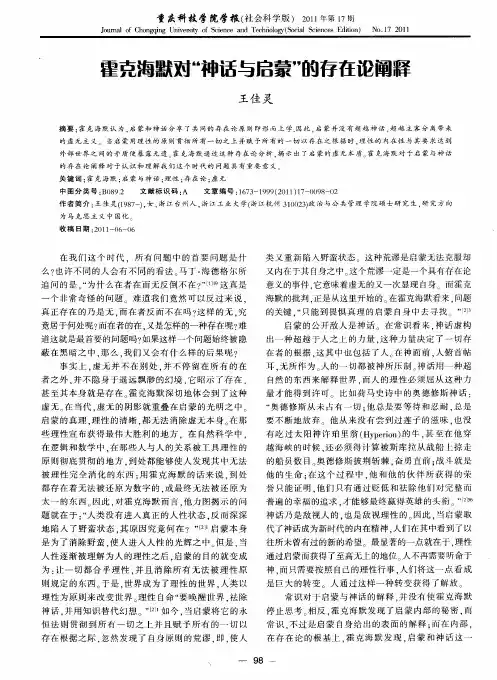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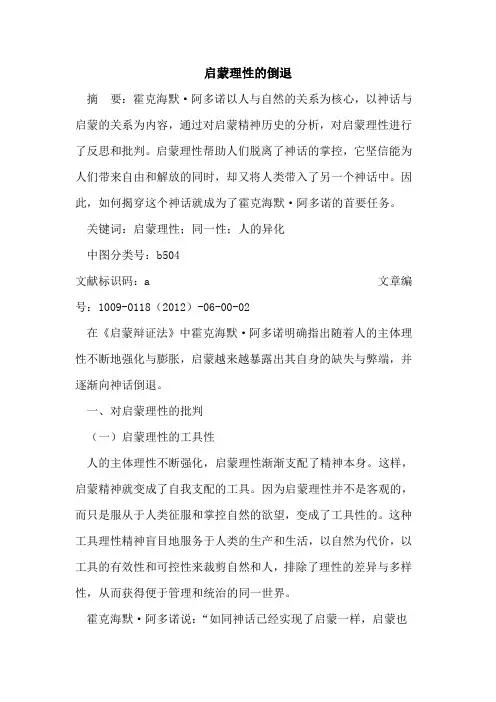
启蒙理性的倒退摘要:霍克海默·阿多诺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以神话与启蒙的关系为内容,通过对启蒙精神历史的分析,对启蒙理性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启蒙理性帮助人们脱离了神话的掌控,它坚信能为人们带来自由和解放的同时,却又将人类带入了另一个神话中。
因此,如何揭穿这个神话就成为了霍克海默·阿多诺的首要任务。
关键词:启蒙理性;同一性;人的异化中图分类号:b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02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阿多诺明确指出随着人的主体理性不断地强化与膨胀,启蒙越来越暴露出其自身的缺失与弊端,并逐渐向神话倒退。
一、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一)启蒙理性的工具性人的主体理性不断强化,启蒙理性渐渐支配了精神本身。
这样,启蒙精神就变成了自我支配的工具。
因为启蒙理性并不是客观的,而只是服从于人类征服和掌控自然的欲望,变成了工具性的。
这种工具理性精神盲目地服务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以自然为代价,以工具的有效性和可控性来裁剪自然和人,排除了理性的差异与多样性,从而获得便于管理和统治的同一世界。
霍克海默·阿多诺说:“如同神话已经实现了启蒙一样,启蒙也一步步深深地卷入神话。
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
”[1]这充分表明启蒙精神退化为神话的原因与启蒙摧毁神话的原则是同出一辙的。
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神话开启了启蒙的无尽里程,在这个不可避免的命运当中,理论观点不时地受到毁灭性的批评,而理论观点本身也变成了一种信仰。
精神概念、真理概念乃至启蒙的概念都变成了唯灵论的巫术。
色诺芬尼认为启蒙理性的神话是人造出来的,是理性的狂妄和对自然的僭越,因而是一种神话的非理性表现,终究会导致新的专制和奴役。
如果一个人按照可支配性、操纵性来对待自然,那么,他必定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
启蒙理性和神话都是出于对自然的惊恐而萌生的控制、统治的欲望,因而必然造就一种奴役自然和自己的新式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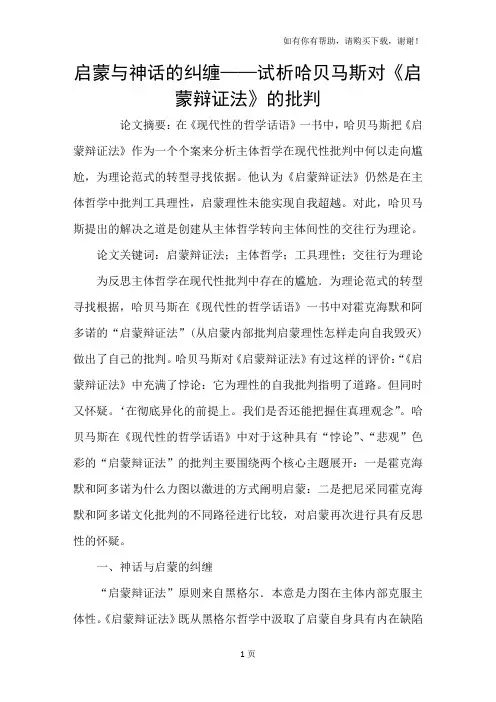
启蒙与神话的纠缠——试析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批判论文摘要: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哈贝马斯把《启蒙辩证法》作为一个个案来分析主体哲学在现代性批判中何以走向尴尬,为理论范式的转型寻找依据。
他认为《启蒙辩证法》仍然是在主体哲学中批判工具理性,启蒙理性未能实现自我超越。
对此,哈贝马斯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创建从主体哲学转向主体间性的交往行为理论。
论文关键词:启蒙辩证法;主体哲学;工具理性;交往行为理论为反思主体哲学在现代性批判中存在的尴尬.为理论范式的转型寻找根据,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从启蒙内部批判启蒙理性怎样走向自我毁灭)做出了自己的批判。
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有过这样的评价:“《启蒙辩证法》中充满了悖论:它为理性的自我批判指明了道路。
但同时又怀疑。
‘在彻底异化的前提上。
我们是否还能把握住真理观念”。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对于这种具有“悖论”、“悲观”色彩的“启蒙辩证法”的批判主要围绕两个核心主题展开:一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什么力图以激进的方式阐明启蒙:二是把尼采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文化批判的不同路径进行比较,对启蒙再次进行具有反思性的怀疑。
一、神话与启蒙的纠缠“启蒙辩证法”原则来自黑格尔.本意是力图在主体内部克服主体性。
《启蒙辩证法》既从黑格尔哲学中汲取了启蒙自身具有内在缺陷的观念,又借用了黑格尔辨证法之名。
但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观点存在很大的不同:在黑格尔体系中,启蒙与迷信的斗争是带有缺憾的进展.一种充满丰富性和内在张力的进展。
《启蒙辩证法》对理性的反思则是沉入理性内部,变成理性对自身的一种自我验证——启蒙理性的解放目标和伦理目标被其自身无情地吞噬。
再也无法将人类解放出来。
“启蒙理性不再是把自身表现为一种有待完成与提高的开放形态,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可救药的结构性衰竭与失败。
”这一点在启蒙与神话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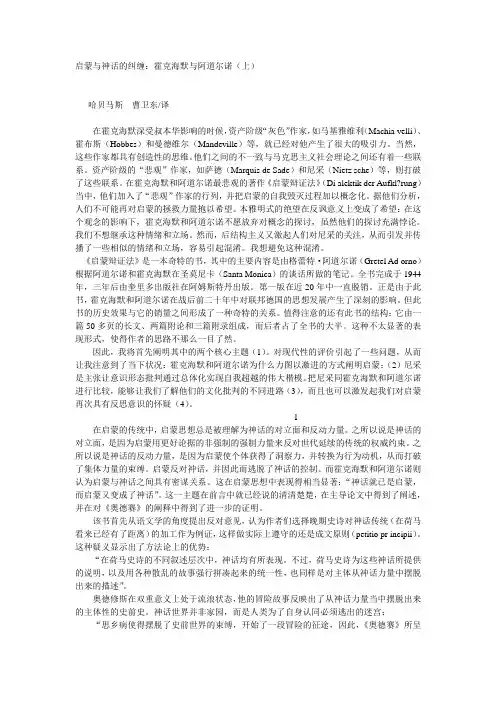
启蒙与神话的纠缠: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上)哈贝马斯曹卫东/译在霍克海默深受叔本华影响的时候,资产阶级“灰色”作家,如马基雅维利(Machia velli)、霍布斯(Hobbes)和曼德维尔(Mandeville)等,就已经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当然,这些作家都具有创造性的思维。
他们之间的不一致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之间还有着一些联系。
资产阶级的“悲观”作家,如萨德(Marquis de Sade)和尼采(Nietz sche)等,则打破了这些联系。
在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最悲观的著作《启蒙辩证法》(Di alektik der Aufkl?rung)当中,他们加入了“悲观”作家的行列,并把启蒙的自我毁灭过程加以概念化。
据他们分析,人们不可能再对启蒙的拯救力量抱以希望。
本雅明式的绝望在反讽意义上变成了希望:在这个观念的影响下,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不愿放弃对概念的探讨,虽然他们的探讨充满悖论。
我们不想继承这种情绪和立场。
然而,后结构主义又激起人们对尼采的关注,从而引发并传播了一些相似的情绪和立场,容易引起混淆。
我想避免这种混淆。
《启蒙辩证法》是一本奇特的书,其中的主要内容是由格蕾特·阿道尔诺(Gretel Ad orno)根据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在圣莫尼卡(Santa Monica)的谈话所做的笔记。
全书完成于1944年,三年后由奎里多出版社在阿姆斯特丹出版。
第一版在近20年中一直脱销。
正是由于此书,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战后前二十年中对联邦德国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此书的历史效果与它的销量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还有此书的结构:它由一篇50多页的长文、两篇附论和三篇附录组成,而后者占了全书的大半。
这种不太显著的表现形式,使得作者的思路不那么一目了然。
因此,我将首先阐明其中的两个核心主题(1)。
对现代性的评价引起了一些问题,从而让我注意到了当下状况: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为什么力图以激进的方式阐明启蒙;(2)尼采是主张让意识形态批判通过总体化实现自我超越的伟大楷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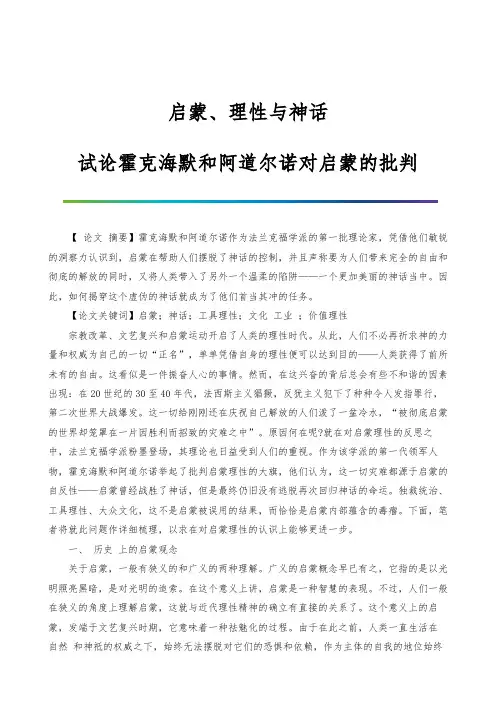
启蒙、理性与神话试论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启蒙的批判【论文摘要】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批理论家,凭借他们敏锐的洞察力认识到,启蒙在帮助人们摆脱了神话的控制,并且声称要为人们带来完全的自由和彻底的解放的同时,又将人类带入了另外一个温柔的陷阱——一个更加美丽的神话当中。
因此,如何揭穿这个虚伪的神话就成为了他们首当其冲的任务。
【论文关键词】启蒙;神话;工具理性;文化工业;价值理性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启了人类的理性时代。
从此,人们不必再祈求神的力量和权威为自己的一切“正名”,单单凭借自身的理性便可以达到目的——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这看似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
然而,在这兴奋的背后总会有些不和谐的因素出现:在20世纪的30至40年代,法西斯主义猖獗,反犹主义犯下了种种令人发指罪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这一切给刚刚还在庆祝自己解放的人们泼了一盆冷水,“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
原因何在呢?就在对启蒙理性的反思之中,法兰克福学派粉墨登场,其理论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作为该学派的第一代领军人物,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举起了批判启蒙理性的大旗,他们认为,这一切灾难都源于启蒙的自反性——启蒙曾经战胜了神话,但是最终仍旧没有逃脱再次回归神话的命运。
独裁统治、工具理性、大众文化,这不是启蒙被误用的结果,而恰恰是启蒙内部蕴含的毒瘤。
下面,笔者将就此问题作详细梳理,以求在对启蒙理性的认识上能够更进一步。
一、历史上的启蒙观念关于启蒙,一般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理解。
广义的启蒙概念早已有之,它指的是以光明照亮黑暗,是对光明的追索。
在这个意义上讲,启蒙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不过,人们一般在狭义的角度上理解启蒙,这就与近代理性精神的确立有直接的关系了。
这个意义上的启蒙,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它意味着一种祛魅化的过程。
由于在此之前,人类一直生活在自然和神祗的权威之下,始终无法摆脱对它们的恐惧和依赖,作为主体的自我的地位始终没有挺立起来,因而启蒙的作用,就明确地表现在帮助人们驱除蒙昧,成为独立的、自主的主体,成为真正的自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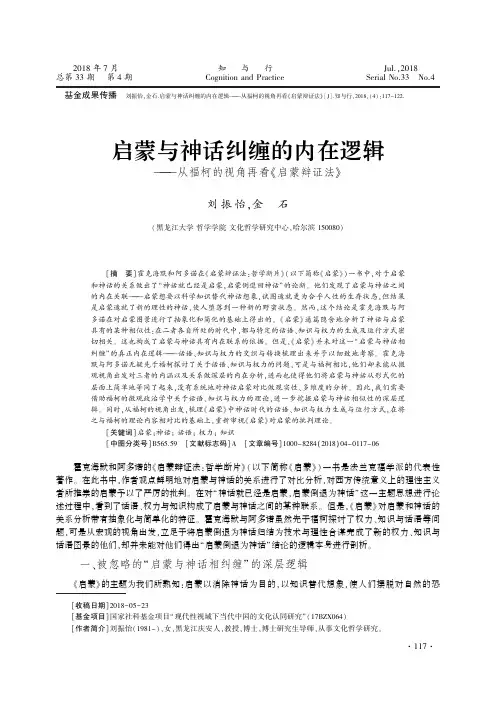
㊀㊀2018年7月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知㊀与㊀行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Jul.,2018㊀总第33期㊀第4期㊀㊀㊀㊀㊀㊀㊀㊀CognitionandPractice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SerialNo.33㊀No.4㊀基金成果传播㊀刘振怡,金石.启蒙与神话纠缠的内在逻辑 从福柯的视角再看‘启蒙辩证法“[J].知与行,2018,(4):117-122.[收稿日期]2018-05-23[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现代性视域下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研究 (17BZX064)[作者简介]刘振怡(1981-),女,黑龙江庆安人,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文化哲学研究㊂启蒙与神话纠缠的内在逻辑 从福柯的视角再看‘启蒙辩证法“刘振怡,金㊀石(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80)[摘㊀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以下简称‘启蒙“)一书中,对于启蒙和神话的关系做出了 神话就已经是启蒙,启蒙倒退回神话 的论断㊂他们发现了启蒙与神话之间的内在关联 启蒙想要以科学知识替代神话想象,试图造就更为合乎人性的生存状态,但结果是启蒙造就了新的理性的神话,使人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㊂然而,这个结论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对启蒙图景进行了抽象化和简化的基础上得出的㊂‘启蒙“通篇隐含地分析了神话与启蒙具有的某种相似性:在二者各自所处的时代中,都与特定的话语㊁知识与权力的生成及运行方式密切相关㊂这也构成了启蒙与神话具有内在联系的依据㊂但是,‘启蒙“并未对这一 启蒙与神话相纠缠 的真正内在逻辑 话语㊁知识与权力的交织与转换梳理出来并予以细致地考察㊂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无疑先于福柯探讨了关于话语㊁知识与权力的问题,可是与福柯相比,他们却未能从微观视角出发对三者的内涵以及关系做深层的内在分析,进而也使得他们将启蒙与神话从形式化的层面上简单地等同了起来,没有系统地对神话启蒙对比做现实性㊁多维度的分析㊂因此,我们需要借助福柯的微观政治学中关于话语㊁知识与权力的理论,进一步挖掘启蒙与神话相似性的深层逻辑㊂同时,从福柯的视角出发,梳理‘启蒙“中神话时代的话语㊁知识与权力生成与运行方式,在将之与福柯的理论内容相对比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启蒙“对启蒙的批判理论㊂[关键词]启蒙;神话;话语;权力;知识[中图分类号]B565.59㊀[文献标志码]A㊀[文章编号]1000-8284(2018)04-0117-06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以下简称‘启蒙“)一书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著作㊂在此书中,作者观点鲜明地对启蒙与神话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对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所推崇的启蒙予以了严厉的批判㊂在对 神话就已经是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 这一主题思想进行论述过程中,看到了话语㊁权力与知识构成了启蒙与神话之间的某种联系㊂但是,‘启蒙“对启蒙和神话的关系分析带有抽象化与简单化的特征㊂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虽然先于福柯探讨了权力㊁知识与话语等问题,可是从宏观的视角出发,立足于将启蒙倒退为神话归结为技术与理性合谋完成了新的权力㊁知识与话语图景的他们,却并未能对他们得出 启蒙倒退为神话 结论的逻辑本身进行剖析㊂㊀㊀一㊁被忽略的 启蒙与神话相纠缠 的深层逻辑‘启蒙“的主题为我们所熟知:启蒙以消除神话为目的,以知识替代想象,使人们摆脱对自然的恐惧,成为主人㊂但启蒙却走向了它的反面 创造了新的理性的神话:当被启蒙所颂扬的科学摧毁了神话的世界观,并将自身地位提升至无以复加之时,科学最终登上了曾经被它所摧毁的神坛㊂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这是因为启蒙与神话从内在逻辑上已经融为一体:神话已然是启蒙的产物,而启蒙最终又创造了新的神话㊂启蒙想要以科学的知识替代神话想象,意图创造更为理想的生存状态,但结果是启蒙造就了新的理性的神话,同时, 人类不是进入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状况,而是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 [1]1㊂这便是为我们所熟知的 启蒙逻辑 ,哈贝马斯在其‘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从现代性是 一项未完成的设计 的立场出发,称之为 启蒙与神话的纠缠 [2]122㊂在‘启蒙“一书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发现了 启蒙与神话的纠缠 所代表的启蒙与神话间的联系表现为神话与启蒙具有某种相似性㊂‘启蒙“在论述启蒙与神话的关系过程中,围绕着神话时代的话语㊁知识与权力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并不惜笔墨就原始宗教中的巫术㊁符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实则勾勒出了一副话语㊁知识与权力自神话时代就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历史性图景 神话构筑的世界观是初民所能够掌握的知识,神话禁忌与原始宗教崇拜则代表了最初的秩序以及初民所敬畏的权力㊂这恰如今天科学所描绘出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以及规范性㊁条令性的法律与制度所代表的早已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的权力㊂在摆脱了神话世界观与巫师所掌握的神权话语的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是同样不可撼动的科学权威以及深层的权力话语的控制㊂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现代人类不曾变得比神话时代更为自主㊁更为自由或更为文明㊂‘启蒙“意在对这种相似性做细致地探讨,并试图表明,虽然神话所代表的想象的世界观转化成了科学的世界图景,权力由原始的神权统治转化为了秩序性的集权统治,知识的形式发生了改变,权力运行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但不变的是尽管经历了启蒙,西方的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从未脱离过话语㊁权力与知识的内在制衡㊂在此基础上,启蒙与神话在形式上被等同了起来:神话就已经是启蒙,表现为神话就已是代表着对自然的把握与解释的知识㊁代表着对于行为的约束㊁代表着人渴望树立自主性;启蒙又倒退为神话,表现为知识取代神话获得无上神圣的地位㊁秩序性的集权统治取代神话式的叙述与说教㊁科技意图解放人类却反成为新的统治性力量扼杀人的自由㊂可以说,这便是‘启蒙“当中隐藏着的秘密:启蒙与神话都具有各自的话语㊁知识与权力的生成与运行的方式,而三者的交织与转换构成了启蒙与神话相互纠缠的内在逻辑,也构成了自神话时代就已经开始的对于人的禁锢㊂但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却仅仅将之视作启蒙与神话之间的外在相似性,未能够将之视作启蒙与神话之间的内在同构性㊂他们试图从宏观视角审视启蒙与神话间的关系,结果却将自神话时代以来的历史图景进行了抽象化㊁简单化处理㊂在对理性同一性进行批判的过程中,自身也未能摆脱理性同一性思维的运用㊂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宏观视角当中,理性思维被视为神话思维经由启蒙形成的变体,二者被对立统一了起来,分别为被视为神话与启蒙各自的精神内核;知识㊁权力与话语等则被他们视为启蒙与神话所共同拥有的特征,于是,启蒙成为神话的精神内涵,神话则成为启蒙无法逃避的梦魇,成为启蒙的起点与归宿㊂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对启蒙进行批判的过程当中,认为启蒙经由否定神话最终达到了对于自己的否定,而实际情况却是他们在对理性同一性的批判中,依旧在运用理性同一性思维对于启蒙的历史图景进行抽象与简化,这也最终导致‘启蒙“对于启蒙的批判陷入启蒙与神话相纠缠的泥潭㊂这有些类似于尼采力图克服虚无主义却最终成为 对虚无主义的最后一次卷入 一般,尼采企图在虚无主义内部瓦解虚无主义,最终成就了一种极端的虚无主义㊂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意图在理性同一性思维框架内部批判理性同一性,其结果则是无法摆脱理论的内在缺陷与悖论㊂正是因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始终未能从微观的视角审视启蒙与神话的各自特征与相互联系,未能将启蒙与神话相纠缠的逻辑系统地梳理出来并加以剖析,并进一步将神话与启蒙的相似性系统总结为话语㊁知识与权力的交织与转化这一内在深层逻辑㊂因此,‘启蒙“仅仅是形式性地得出 神话由启蒙精神创造,启蒙最终又归于神话 这种启蒙与神话相等同的直观诊断结论㊂但二者实则已经不能被放在等式的两端 科学时代的话语㊁知识与权力虽然依旧制衡人的思维与行动,三者间关系也依旧相互依存㊁制约与转化,但是已经与神话时代不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并未就三者的生成与运行方式以及相互关系的变化进行详细的论证,只是将启蒙与神话进行抽象与简化后在形式上相等同起来,势必产生了哈贝马斯所认为的 由于抽象和简化使得其论述的可信性成了问题 [2]127㊂为了更为清楚地挖掘‘启蒙“中关于启蒙与神话相纠缠的隐性逻辑,我们需要对话语㊁权力与知识的现实历史关联进行关注㊂福柯从微观视角出发所运用的考古学以及谱系学方法无疑将会是对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宏观视角出发的启蒙辩证法的良好补充㊂借由福柯的理论,我们将一窥知识㊁话语与权力间是如何相辅相成地构成一张巨大的㊁无处不在甚至深入到人的意识当中的巨大网络㊂同时,以福柯的理论为镜,从话语知识及权力的内涵以及三者间的关系出发,借之来反观‘启蒙“,我们将不难发现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是如何忽视掉了 启蒙与神话的纠缠 的内在逻辑,并在此意义上将启蒙与神话等同起来并产生了对于启蒙悲观的态度㊂㊀㊀二㊁福柯理论之镜 微观视域下的话语㊁权力与知识及三者关系福柯的 权力哲学 是以启蒙分析为背景的㊂他认为,在对启蒙和现代性问题的反思过程中,不应当 把社会或者文化的理性化过程当作一个整体,而是在几个领域中分析这样一个过程 [3]110-111㊂福柯运用考古学方法或谱系学方法对疯癫㊁疾病㊁犯罪㊁性等领域的考察过程中,逐步构建起了其独特的 微观政治学 ,并将讨论的核心放在了话语㊁权力与知识等问题上,其论述为我们重新审视启蒙提供了独到的理论视角㊂在此仅扼要地就福柯理论中的话语㊁知识与权力的概念内涵与关系做必要地分析,借之以窥探 启蒙与神话相纠缠 的内在逻辑㊂话语㊁知识与权力都是福柯理论当中的重要概念,对于三者的内涵以及关系的探讨更是构成了福柯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㊂在福柯看来,话语㊁权力与知识无论从其内涵和外延上看,都存在着依存㊁相互生成以及转化的关系㊂同时,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㊁复杂的联系㊂表现为三者间相互作用㊁相互依赖㊂福柯的 话语 既不同于语言学家索绪尔的 语言 或者 言语 概念,也不同于后来的本维尼斯特以及利科等在语言学上对于 话语 的界定㊂按照索绪尔所做的语言与言语的区分,认为语言属于形式层面,其研究对象是语言系统,包括语法㊁词汇等,言语层次则是具体运用,其研究对象则是特定的个体的语言行为㊂而本维尼斯特与利科则认为语言的单位是词,而话语的单位是语句,由词构成语句,层次发生了由结构过渡到功能的变化,话语所表达出的是一种人生活于世界中传达的意义[4]㊂相比之下,福柯的 话语 既非语言符号,也不能够被语言学所规定,其 话语 概念具有多元复杂的内涵,可以是各个学科领域中的结构,也可以代表一种 同质性的秩序 或 权力的结构 ㊂而从外延上看,广义的话语是历史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即 话语 从根本上代表着人类的一种重要的活动方式,而历史文化则是由一系列的 话语 组建而成;狭义的话语则接近于哈贝马斯的 语言的形式 ,即话语代表着 规则 ,某种一般性或特定性的 陈述 在其框架内进行[5]㊂在福柯看来,话语构成了知识的来源与理解世界的框架,话语也决定了可以言说的内容㊂由此,话语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表现为话语构成权力与知识的产生条件,同时权力与知识也建构话语㊂作为经验主义者的福柯认为知识既是由详尽的话语实践得来,而且必然与一定的话语实践相对应㊂话语构成知识的要素的总和,知识则是 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 [6]203,即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获得的,知识在详尽的话语事件中产生,并且 由话语所提供的使用和适应性确定 [6]204;同时,知识在形成后也将会逐步成为某种话语的一部分,在话语实践之中发生作用㊂与此同时,知识将借助代表某种权威的知识团体得以传播㊂进而,新的知识造就了新的权威性的话语 达成某种特定话语实践的主体在形成的知识后也将作为特定的学科或特定语境背景下的 权威 ㊂已经形成的权威也必然由其所掌握的话语权或知识而来 这一过程包含着复杂的话语更迭㊂由此可见话语和知识之间的双重关系:知识既是由话语实践产生,在此基础之上知识本身亦会构成新的话语的元素,或者可以进一步说,知识在达成后会促成新的话语实践㊂同时,二者之间的关系渗透着权力的运作㊂权力同样是福柯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㊂福柯反对传统的权力观,并且极度反对将权力等同为暴力,他认为权力 作为一种行动方式 ,是一些行动校正另一些行动的行动方式,权力的实施就是 某类行为可以将另一类可能性行为结构化 ,即 某些人的行为作用于另一些人的行为 [3]132㊂并且,这种作为 校正 的行为是无处不在的,因为在福柯看来, 权力关系植根于整个社会之网 [3]134㊂权力与话语和知识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㊂在福柯经历了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的转变后,他在话语的谱系学研究中将话语和权力明确联系了起来㊂这时权力与话语的关系表现为权力对于话语的控制,即话语的产生或者传播受到权力的操控以及制约;同时,权力通过话语得以实施,即权力的运作离不开话语的作用㊂并且,二者间的相互关系表现为以知识为中介㊂福柯通过考察发现,在古希腊时期权力是与 真理话语 直接相联系的,即 话语 代表着权威行驶着向大众 宣告 真理的权力㊂但在公元6世纪后,伴随着 真理话语 不再由外在的权威给出,即真理不再受限于被谁所说,而是开始遵从于逻辑正确性与内容科学性㊂而话语与权力间的直接关系也发生了改变,转而使得权力以更为内在的形式同知识联系在一起㊂在他的早期著作‘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就详细地论述了权力是如何通过话语得到实现的㊂通过考察 疯癫 的概念衍变史,福柯向我们展示了疯癫是何以一步步在代表着理性的权威性话语当中被不断地区别与隔离,最终成为了被理性镇压和屈服的对立面㊂知识与权力也同样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㊂福柯不同意将知识与权力完全等同起来,但明确指出知识与权力是一种共生关系,福柯将知识称作是 权力知识 ,并就此表达出权力与知识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二者间相互作用的,彼此促进或抑制 权力可以对知识具有鼓励或限制作用,知识作为一种话语同样可以赋予人以权力,或者是对权力具有制衡作用㊂在这种关系中,知识会受到权力的操控,并表现为一种权威性话语的限定或制约㊂在其‘规训与惩罚“当中,福柯更进一步明确指出 权力制造知识 ㊂同样的,知识会为权力进行辩护,福柯曾对此做形象的比喻 知识是权力的眼睛 ,知识为权力开辟了其得以实施的边界和维度,同时也为权力披上了理性和合法性的外衣㊂二者关系表现为 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 [7]㊂与此同时,知识与权力的相互作用以话语为中介,也就是权力需要借助于话语形成知识,知识同样需要进入话语之中生成权力㊂至此已经可以看出,在福柯的眼中,话语㊁知识和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是三位一体的:话语是框架与形式㊁知识是具体表达㊁权力则是实质内涵㊂并且,三者任一在自身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都会不断地为另外两者开辟新的场域,话语的产生与知识的生成以及权力的实施过程当中都在不断地促使着其交织而成的网络愈加严密以及巨大㊂在福柯的理论当中,当今西方社会在自身运行中的各个层面,包括学校㊁监狱㊁诊所等社会机构的运行,以及法律㊁规范㊁条例等社会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乃至于个体的思维㊁行动等无不在话语㊁权力与知识相互交织的网络之下运作㊂这张无形的大网已然变得日益隐秘化:实施管控的不再是统治者或者是政客,更多的是各种权威的机构㊁学科的权威以及由他们所论证合理的制度以及规范;由现代科学权威所提出的真理同法典一般让人萌生尊敬与畏惧;个体对于各类的制度㊁知识则早已经浑然接受并习以为常进行遵守㊂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福柯从微观视角出发,立足于 对特定的合理性进行分析,而不应当总是求助于普遍的理性化过程 [3]111,运用其考古学以及谱系学方法,对于话语㊁知识与权力的现实及历史予以了细致的考察,对三者的生成与运行以及相互关系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㊂而这恰是‘启蒙“所缺乏的视角,也是其理论的缺陷所在,以单一的宏观视角来抽象与简化启蒙图景,既未能够看到话语㊁知识与权力在历史中发生的变化,也未能够对三者在神话时代与现代的形态进行细致考察㊂㊀㊀三㊁再看‘启蒙“中的神话时代的话语㊁知识与权力之网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无疑发现并触摸到了由话语㊁知识与权力交织而成的网在神话时代的初级形态的边缘㊂然而,他们在对神话时代的话语㊁知识与权力的分析却并不像福柯一样是自觉进行的,他们未对三者的内涵及相互关系进行剖析,也未将三者在原始社会的形态与现代社会的特征以及相互联系上的差异相区别开来㊂因此,他们仅从宏观的视角出发,将启蒙与神话在形式上等同起来㊂若以福柯的理论为镜反观‘启蒙“,从其视角对‘启蒙“当中对话语㊁知识与权力的生成与运行方式以及相互联系进行考察,并将之与之前所提及福柯理论中的形态进行比对,将是对‘启蒙“宏观视角有益的㊁必要的补充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被启蒙精神所摧毁的神话本身已然是启蒙精神所造就的 神话就已经是启蒙,代表着秩序㊁统治与自我意识㊂即主体通过设想人神同形同性来对自然进行解释,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对自然的恐惧㊂也就是说,人通过以一种神话性的原始思维来解释自然,在把握自然的基础上达成一种自我认同以及对泛灵论的超越: 神话试图对本原进行报道㊁命名和叙述,从而进行阐述㊁确定和解本原 神话早就在叙述中成为说教 [1]5㊂可见,神话作为一种原初的话语就已是知识与权力的源头㊂从对于世界进行把握的意义上,神话中所论及的诸神与英雄的故事便是人类早期的关于自然与历史知识,‘启蒙“在对于原始宗教崇拜的论述的过程中也已经指出: 信仰与知识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1]15;而在对行为和思想进行约束的意义上,神话禁忌与其所衍生的祭祀活动则代表了权力运行的原始方式㊂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 早在语言进入历史的时候,祭祀和巫师们就成为它的大师 [1]15㊂在这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启蒙“一书当中, 语言 被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是 认识自然的符号系统 以及 反映自然的图像 [1]13,在‘启蒙“当中,已然描绘出了初民在原始社会中科学尚未萌芽的情况下,初民依靠神话中的描述来认识自然㊂神话当中对于自然的解释㊁报道以及说明便是一种知识,这种知识无疑是通过巫师这一掌控话语权的角色得以产生和传播的㊂与此同时,巫师在其 传播知识 的过程中, 增加了专门的知识和扩大了权力 [1]16,可见,在神话时代,话语同样构成知识的来源,知识也同样构建新的话语,同时,二者间的相互作用渗透着权力的运作㊂因此,我们可以说,作为一种话语,神话在其所处时代已成就了一种权力,权力的掌控者是原始宗教祭祀或巫师㊂‘启蒙“对原始宗教崇拜所进行的论述中也清晰地表达出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对于初民来说,由巫师道出的万物流溢自神灵以及其所实施的神圣仪式则成为了一种权力性话语表达㊂仪式中的种种特定的鼓声或动作,则成为了有着特殊意义代表权力的符号 已经具有固定形象的敬畏感变成了得到确立的特权统治的标志 [1]16㊂由祭司所传达的 神的旨意 更加是不可违背的㊁甚至是由衷被初民发自内心所接受的话语㊂巫师或祭司以神的名义说出的话语变成了对 神的旨意 的传达,代表着 神的意志 ,也形成了一种神话世界观㊂话语成为敬畏的对象,祭司也由此必然地成为神话时代至高无上的存在并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力㊂这种统治与服从的表现,也延伸到了原始文化中的风俗㊁习惯等各个层面上,起到对个体约束和限制的巨大作用,比如需要在生活中服从巫术中的各种禁忌㊁在狩猎中把自己打扮成野兽等㊂从神话时代开始,知识也已经成为与权力具有相同内涵的存在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在神话时代语言就已经 为其所确定的内容提供了统治条件 ,并完全同意培根关于 权力与知识是同义词 [1]2的说法 知识达成了技术与权力的共谋,代表着对自然的把握,代表着人妄图达到对自然的掌控,奢望以此达成所期望的自由㊂可以看出,自神话时代起认知就已经与权力相勾连,‘启蒙“中所论述的 神话就已经是启蒙的精神产物 即是论述人将自然作为对象采取认知性的接纳方式便带有着权力的因素,同时人对自然所思获得的知识的掌握生成了一种权力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明确指出,从神话时代起,语言即已经 成为话语权力的工具 神话时代的知识所代表的,既是对自然的权力性掌控,也是对人的制约性的宣告㊂对于普通个体而言, 在征服世界的进程中,自我学会了遵守现行秩序和接受从属地位,但他很快就把真理与管理思想等同起来 [1]10㊂总之,话语㊁知识与权力自神话时期交织在一起,左右着人的思想与行为:神话中对自然的史诗式叙述便构成了原初的神话世界观与世界历史,神话中的禁忌与对于神的敬畏则构成了原初的统治秩序 神话本身就是一种知识,神话本身亦代表着秩序㊂神话时代初民关于世界想象式的理解以及原始宗教信仰所诞生的祭祀权力的交织已然是话语㊁权力与知识相互联系的雏形,后来由启蒙理性造就的科学知识及对应的世界图景以及技术理性造就的规范化秩序化的集权统治权力便是当前时代话语㊁知识和权力相关联的更为现代㊁更为隐秘的网络㊂相比之下,‘启蒙“当中所论述的神话时代的话语与知识是相对粗糙的㊁非理性的,神话时期的权力的表现则是直接的和自在的㊂神话时代的话语㊁知识与权力各自的生成与运行机制是自在的㊁表层的,相互关系是直接的㊂而在福柯的笔下,知识和话语在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着断裂与变迁,权力机制的运行更为不易察觉,话语㊁知识与权力各自的生成与运行机制则是自为的㊁内在化,相互关系也变得更为紧密化和隐性化㊂列维-斯特劳斯就曾经指出,神话思维在文艺复兴之后退隐到了西方思想的幕后㊂这种神话思维与理性思维之间的联系即体现在话。
《启蒙辩证法》个人解读对《启蒙辩证法》及其内容和思想的研究颇多,有主要集中在对启蒙与神话、文化工业、工具理性三方面进行的研究。
我只从启蒙与神话和文化工业俩方面进行概括。
一、启蒙为何会从一个神话走向另一个神话(一)明确神话和启蒙的含义要了解“启蒙为何会从一个神话走向另一个神话”,首先需要对其所指内涵有清晰的认识。
在《启蒙辩证法》的“神话——启蒙——神话”的中,神话两次出现,但所指的内容是不同的。
简单来说,启蒙祛除“神话”,指的是神话传说,即以奥林匹斯诸神为代表的超自然力量的绝对统治。
启蒙成为一个新的“神话”,指人的理性理性的绝对统治。
两种神话虽然所指不同,但其都被成为神话,必然存在着内在的共通之处,即绝对的统治力量。
于是“神话一启蒙一神话”从内在来讲,是绝对统治——觉醒意识——绝对统治的过程。
就“启蒙”来说,霍克海姆和阿多诺所指的“启蒙”,具有两层意思。
就启蒙本身的不同发展阶段,也有变化,分为早期的“启蒙”,后期的“启蒙”。
早起兴起的启蒙,即自启蒙运动时的启蒙,宣扬解放和自由精神,即人的自我意识(理性)的产生,理性或者自我意识使个人觉醒,开始对自己之外那些绝对支配力进行反叛。
帮助人们驱除蒙昧,成为独立的、自主的主体,成为真正的自由人。
通过启蒙,人们凭借理性的力量获得自我,注重外在客体和内在主体的双向提高。
阿多诺所说的“启蒙”属于后期,指人的理性或自我意识发展到极致,把所有东西都用理性物化。
启蒙运动发展到后来,物质层面的愿景实现了,但精神层面成为人的理性占绝对支配地位,试图将自然的一切都用理性加以阐释,崇尚技术决定论,使人完全被技术层面决定,使人变得更加异化。
人受制于理性,走向了启蒙的反面,使人回到了理性的神话。
(二)启蒙本身的弊端——与神话的关联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本身不是尽善尽美,而是包含有一种使自身向神话倒退的自我摧毁的特性,尽管启蒙倡导的理性为神话祛魅了,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消蚀了自身,成为一种新神话的牺牲品。
浅析启蒙辩证法中启蒙的概念——启蒙与神话交织王棚勋【期刊名称】《改革与开放》【年(卷),期】2018(000)001【摘要】本文选取《启蒙辩证法》第1章"启蒙的概念"中启蒙与神话部分进行论述分析,以期达到对启蒙理性的成长史"管中窥豹、滴水沧海"之效.在初读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启蒙辩证法》时,难免被它晦涩的论述及专业性的佐证所折磨,无力明晰作者的主旨路径趋向并困惑不堪.因为该书旁征博引和包罗万象的理论述说要求读者具有庞大而综合的知识储备,方能彻悟该书的真正意旨.笔者体悟到若"顽强"且坚持不懈地与该书在思维上勇敢地"纠缠""肉搏",久而久之,领悟的意境便柳暗花明,而后,就如同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般爱上《启蒙辩证法》这种对人性状态彻底全面地展示、剥离.著书的写作背景是作者目睹现代人性的全面瘫痪和异化及人被禁锢和宰制丧失自由的惨状后痛心疾首、极度悲观,继而转向对启蒙理性未兑现的承诺失望透顶、怒不可遏.幸运的是,《启蒙辩证法》犹如黑暗中划破长空、刺破苍穹的流星,对重建价值理性,恢复被合理性所侵蚀的人的灵魂与精神,达致真正的人性状态,对探寻人生终极目的和追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总页数】2页(P122-123)【作者】王棚勋【作者单位】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正文语种】中文【相关文献】1.启蒙神话与启蒙救赎:《启蒙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困境的阐释与反思 [J], 叶莉;代文勃2.启蒙与神话纠缠的内在逻辑——从福柯的视角再看《启蒙辩证法》 [J], 刘振怡;金石;;3.启蒙神话与启蒙救赎:《启蒙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困境的阐释与反思 [J], 叶莉;代文勃;4.一种积极的启蒙概念——论《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的自我反思与救赎 [J], 张雨生5.一种积极的启蒙概念——论《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的自我反思与救赎 [J], 张雨生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理性与神话人类自从有了科学,特别是进入工业化与市场经济,有了所谓“理性人”这个假设,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仿佛爱上理性就成了智慧与光荣正确的代表,从而让理性具有了某些神秘的色彩,即使一些对理性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并非不相信理性,而是认为人很难做到理性。
“你不是个人!”这话不带脏字,骂人最狠。
只有理性的利益算计,不配做人。
人们不只有理性,还有非理性,比如有情感、有幻想、有梦想,甚至创造神话,这事真的值得庆幸。
否则,人就成了“肉体AI”了。
中国智慧有两个字概括了一切事物,即:阴和阳。
阴和阳变化无穷,无穷变化,就有了世间万物与万物的发展变化。
一阴不生,一阳不长,离开了任何一方,变化就无从产生。
人类需要“日神”精神,也需要“酒神”精神。
或者说,人类需要逻辑推理、数字运算,也需要“花间一壶酒,对影成三人”。
理性决定具体的行动,神话赋予行动价值与意义并“规划”未来可能的“仙境”。
理性以现实为依据,神话则是对现实的超越;理性是对可能性的论证,神话是对不可能的“可能性”想象;理性主导着人们视域内的建设,神话引导人们发现视域外的广阔天地。
神话以“不可能”,将人类引向人间奇迹。
神话一时不能被科学证明,不能用逻辑推导,也不能用经验来理解。
但是,好的神话能引起共鸣,因共鸣而被传播。
因传播而具有了神奇的力量。
当代“神话”以科幻的形式存在。
许多科幻小说由于过度重视科学基础,反而影响了想象力,也就降低了影响力。
神话激发解释,解释的结果是让神话成为现实,从而终结了神话。
然后,人们在新的现实土壤里孕育新的神话。
神话就是故事。
神话不是具有意义的故事,而是给予意义的故事。
有些神话是以历史事实与真实人物的面貌出现的。
后人通过神性化一段历史或历史人物,来引导变革与展开创造性行动。
古希腊精神就是西方人的神话。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是对这个神话的再传播,也是对这个神话的重构与发展。
源于这个重构,西方世界成为人类近现代的神话世界,被不断地解释不断地讲述。
《启蒙辩证法》与神话学传统李 菲【摘要】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了启蒙和神话相互包含、相互纠缠的辩证法。
以往的研究通常以启蒙理性为切入点,忽视了从神话来看待启蒙和理性的视角,也未注意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于神话的关注,实际上与德国浪漫主义的神话学传统密切相关。
因此,本文回到这一传统,根据其对神话与理性关系的不同理解,梳理浪漫主义神话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及其各阶段的具体内容,并探讨神话对于理性批判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
在此基础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批判了浪漫主义思想,揭示了神话与启蒙的辩证关系,也可以视为神话学传统的一种延续。
【关键词】启蒙辩证法;神话;神话学;理性批判中图分类号:B516 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9)04-0035-09作者简介:李 菲,天津人,(天津300350)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启蒙辩证法概括为“神话已然是启蒙,以及启蒙倒退为神话学”①。
这两个视角构成了《启蒙辩证法》两条相互缠绕的叙述线索,也暗示了理性批判的两个基本策略。
一是从理性主义内部出发,直面理性自身的问题并进行批判性反思,表明启蒙理性自身的悖谬。
这一思路甚至可以回溯到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等人的德国古典哲学基本观念,尽管他们最终强调一个理性的结局。
二是在理性主义的外部寻求非理性资源,通过比照,指出启蒙理性的缺陷及其后果,最终提升神话的文化要素而与理性形成对抗。
这会让人首先想起德国浪漫主义甚至更早的神话学传统,它出于对缺乏生命力的知性文化的拒斥,以及对资产阶级社会功利性原则的厌恶,将超越的希望诉诸神话所表达的乌托邦。
《启蒙辩证法》同时包含着这两种批判的可能性,只是我们因工具理性批判而熟悉前者,对后者却不甚明了,尤其是启蒙辩证法与历史上各种神话学之间的关联,仍缺乏正面研究。
对《启蒙辩证法》来说,这种关联并非无足轻重。
有学者指出,“遗留的神话残余中的超验观念、神话中的乌托邦契机的超验性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们规定着深思理性的概念,规定着积极的启蒙理念这一概念”②。
浅谈启蒙、理性与神话——试论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启蒙的批判【论文摘要】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批理论家,凭借他们敏锐的洞察力认识到,启蒙在帮助人们摆脱了神话的控制,并且声称要为人们带来完全的自由和彻底的解放的同时,又将人类带入了另外一个温柔的陷阱——一个更加美丽的神话当中。
因此,如何揭穿这个虚伪的神话就成为了他们首当其冲的任务。
【论文关键词】启蒙;神话;工具理性;文化工业;价值理性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启了人类的理性时代。
从此,人们不必再祈求神的力量和权威为自己的一切“正名”,单单凭借自身的理性便可以达到目的——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这看似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
然而,在这兴奋的背后总会有些不和谐的因素出现:在20世纪的30至40年代,法西斯主义猖獗,反犹主义犯下了种种令人发指罪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这一切给刚刚还在庆祝自己解放的人们泼了一盆冷水,“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
原因何在呢?就在对启蒙理性的反思之中,法兰克福学派粉墨登场,其理论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作为该学派的第一代领军人物,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举起了批判启蒙理性的大旗,他们认为,这一切灾难都源于启蒙的自反性——启蒙曾经战胜了神话,但是最终仍旧没有逃脱再次回归神话的命运。
独裁统治、工具理性、大众文化,这不是启蒙被误用的结果,而恰恰是启蒙内部蕴含的毒瘤。
下面,笔者将就此问题作详细梳理,以求在对启蒙理性的认识上能够更进一步。
一、历史上的启蒙观念关于启蒙,一般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理解。
广义的启蒙概念早已有之,它指的是以光明照亮黑暗,是对光明的追索。
在这个意义上讲,启蒙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不过,人们一般在狭义的角度上理解启蒙,这就与近代理性精神的确立有直接的关系了。
这个意义上的启蒙,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它意味着一种祛魅化的过程。
由于在此之前,人类一直生活在自然和神祗的权威之下,始终无法摆脱对它们的恐惧和依赖,作为主体的自我的地位始终没有挺立起来,因而启蒙的作用,就明确地表现在帮助人们驱除蒙昧,成为独立的、自主的主体,成为真正的自由人。
人们相信,经过启蒙,我们可以获得翘首以盼的解放,不再为外物所拘束,并且能如康德所说的那样,“为自然立法”。
启蒙正是背负着这样的历史重任上路的。
说到这里,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将启蒙和理性连接在一起了。
人们通过启蒙获得自由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人类理性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过程——启蒙事实上就是在树立人类理性的权威地位。
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思想家们,坚信单凭自己就可以认识外物,而且,科学的发展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启蒙开启了理性之门,同时给人类带来更多更大的希望。
不仅如此,与启蒙相联系的还有现代性的概念。
在启蒙之前,人们解决一切问题都乞求于外在的力量,他们不可能为自己设立标准。
因此,在那个时代,人类在神话中、宗教里、传统中寻找自己的行为准则。
那是闭塞的、没有时间意识的时代,未来是无止境的重复,人们唯一可以做的,仅仅是在无尽的过去中寻找已经陈腐不堪的“宝藏”。
然而,启蒙在这时打破了人类理性的沉闷,一个新的时代随之到来。
由于启蒙解放了人类的理性,人们第一次在世界上真正站立起来。
他们的眼光由仰视天堂转而俯瞰地面,自然和神灵的奴仆翻身成为世界的主人。
这种胜利的意义是巨大的,人们认识到了自身力量的强大,也就不再期求自然神秘物帮助,而是对自己充满信心。
这便加强了人们对未来的期许与渴望,因为他们相信,理性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它有足够的能量帮助我们实现一个崭新的世界。
这便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性精神。
时间不再停滞在过去,它倡导一种前进的步伐和不断开放的意识,它要求人类去寻找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解放。
自我确定的主体性和现代的时间意识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标志。
由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启蒙,就意味着驱除蒙昧,树立人类理性的自信,从而为人们带来一个彻底解放的、无拘无束的新时代。
也正由此,启蒙、理性与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构的。
二、启蒙的“狡计”虽然启蒙的“成熟状态”给予我们如此诱人的承诺,然而,在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看来,启蒙的本性并非如此温存与善良。
在美丽的面纱之下,启蒙有着它的阴暗面。
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l、从启蒙的发端处说起。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讲,启蒙的确帮助人摆脱了神话的控制,使人类走向自主与自立。
但是,这种“摆脱”并非是一种完全、彻底地与神话传统的断裂,因为,追根究源,启蒙甚至可以说是发源于神话的。
用他们的话说,“启蒙始终在神话中确认自身”。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这种论断并非没有缘由,他们通过对启蒙和神话的具体分析认识到,两者之间最大不同在于:人的统治代替了神。
而这种界限,又很容易被模糊开来:“许多神话人物都具有一种共同特征,即被还原为人类主体。
俄狄浦斯(Oedi—pus)对斯芬克斯之谜的解答:‘这就是人!’,便是启蒙精神的不变原型”。
也就是说,在启蒙中标榜的具有理性的人类的地位,事实上在神话世界中已经有所展露:物永远是被统治的对象,而在神话中虽然人被神统治着,但是神与人始终有着“同形”的亲缘关系。
这就意味着,启蒙并非如它标榜的那样展现着与神话的彻底决裂——“神话自身开启了启蒙的无尽里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启蒙的历史似乎没有它所宣称的那种“清白”。
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似乎还可以对启蒙展现出一种宽宏大量,因为,启蒙运动毕竟还是完成了将人置于神灵之上,将神话转为“人话”的过程。
因此,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还是将更多的精力集中于对“成熟”启蒙的批判上,他们认为,正是这种启蒙的完成式,才是最具威胁的。
2、启蒙的成熟态。
诚如以上所言,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承认启蒙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摆脱了神祗的控制,挺立起了个人的自主性。
但是,两位理论家的分析并未止于此,他们发现启蒙为人类布下的更大的陷阱:它在帮助人类从原始的神话当中摆脱出来的同时,又让人类陷入了另一个神话——理性的神话。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说:“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
”正是这种“陷入”,导致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种种暴劣行径,更有甚者,它还制造了文化工业对人类的隐性控制。
如果说某些恶行更容易引起人的深思的话,那么,文化工业则常常扮成糖衣炮弹的样子,引人爱慕。
因此,在这一部分的论述中,笔者除了对启蒙理性的自反性做出一般的分析之外,着重在于阐述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
(1)普遍性论述。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认为,在启蒙确定了人类主体性地位之时,首先导致的是人与自然的二元分裂(这种分裂其实在古典的神话中就有所展现,这也就是神对自然物的统治):自然从此成为人们肆意欺虐的对象,一切都要按照人类的指示来行动,一切都要服从于我们的目的。
于是,理性就演变成了纯粹功利的工具理性。
不过,在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看来,这似乎还不是最为严重的——在这样的情态之下,人们只要可以把握自己,自主的理性就仍能够为我们出谋划策。
然而,由于工具理性意识的无所不在,它最终还是侵蚀了人类的自主性本身(这便类似于传统神话中神对人的统治了)。
这种侵蚀首先意味着人对人的统治和压榨:一部分精于算计的人获得了更大的权利,他们将其他人看作工具,为实现自身目的而任意操纵。
不过,当这些“当权者”限制了他人自由的同时,他们自己也面临着异化——异化于工具理性的奴役意识,放弃了对价值理性的追求。
于是,道德、公正让位于精确的算计和缜密的运算,所有的东西都由数字来操控和把握——我们自身被理性异化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理性似乎具备了黑格尔所说的那种性质——那种绝对的、自由的本性,而人类此时就成为了它展示自身的工具。
由是,启蒙的狡计欺瞒了人类的眼睛,人类的解放再次成为幻影。
通过以下对文化工业的分析,我们则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2)文化工业:一个很好的例证。
对文化工业的具体分析出现在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合着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这篇文章里。
通过对文化工业全方位的剖析,两位理论家揭示出在“和平年代”,启蒙理性是如何凭借它隐蔽的权力遮盖人们的视听,奴役人类的心灵的。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文章的开始就指出,文化工业作为人类理性发展的产物,其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生产的大批量性以及重复性。
这主要表现在:“不管是在权威国家,还是在其他地方,装潢精美的工业管理建筑和展览中,到处都是一模一样。
辉煌雄伟的塔楼鳞次栉比,映射出具有国际影响的出色规划,按照这个规划,一系列企业如雨后的春笋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这些企业的标志,就是周围一片片灰暗的房屋,而各种商业场所也散落在龌龊而阴郁的城市之中。
”不过,以上的分析对启蒙理性并没有造成冲击,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这种批量生产恰恰满足了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使得过去稀缺的东西变得充足,这正是理性的胜利而非缺憾。
但是,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并不这样认为。
他们仅将上面的描述当作一种表面现象,而最根本的则在于这种大批量生产的本性:为消费而来。
也就是说,虽然在常人看来,产品的生产的确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然而,从根本上说,这种兴趣和需要,常常是为消费制造出来的。
人在无意识当中就被物所控制了。
那么,做出这种判断的理由何在呢?如果生产是“为消费而来”而非因喜好而起,我们为什么还对这些应当是“无聊”的东西津津乐道呢?这两个疑问事实上涉及到两个问题:其一,生产是因为消费而来这个论断的根据何在?其二,即便对第一个问题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已经被理性开蒙的人们怎么会受到如此的摆布呢?对于第一个问题,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这样几句话就能将一切说明白:“利益群体总喜欢从技术的角度来解释文化工业。
据说,正因为千百万人参与了这一再生产过程,所以这种再生产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无论何地都需要用统一的需求来满足统一的产品。
”“……技术用来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的基础,正是那些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
‘最有实力的广播公司离不开电力工业,电影工业也离不开银行,这就是整个领域的特点,对其各个分支机构来说,它们在经济上也都相互交织着”。
这也就是说,事实上,对产品生产的最终决断权是来源于“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的。
经济权力制约着技术的发展方向,技术的发展方向由此也决定了产品的类型以及人们的喜好,一切就这样被制造了出来。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被产品,进而被产品背后的利益团体所操纵了。
这样,启蒙理性的工具性特征也便暴露无遗,它不再是人类解放的基础,反而制造出了对人类的无形的奴役。
讲到这里,似乎还有一点没有清楚,那就是我们明明感到了对产品的需求和兴趣,但却并不认为是受到了什么东西的教化的。
上面的分析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已。
这个问题也便是上面第二个问题的变种:我们怎么会受到摆布呢?对于这个问题,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分析认为,其原因就在于文化工业在批量生产的同时,也制造了某种虚假的风格:正是这风格,满足了人们对自由的热望和对解放的向往,以及对个性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