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和他的翻译
- 格式:pptx
- 大小:253.40 KB
- 文档页数:15

晚清报刊上的林纾轶闻作者:陈大康来源:《世纪》2018年第02期林纾不懂外文,他依靠与人合作的方式,竟成了百年前著名的小说翻译家。
他是将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的先行者,其译作也畅行天下。
关于林纾的研究论著已有不少,但论述多围绕其译作,其实还有些相关记载散见于近代报刊易被忽略,撷取考察,亦可对林纾及其翻译有更多的了解。
一、林纾对稿酬大为惶恐不懂外语的林纾与小说翻译结缘带有点偶然性。
光绪二十四年,林纾的妻子病故,为帮他排解悲痛,其友王寿昌提议合作翻译法国小仲马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这则悲剧故事与林纾当时的心情也正合拍。
在法国留学多年的王寿昌精通法文,他口述作品内容,林纾则耳受手追,组织成文字。
林纾的古文曾得到桐城派大家吴汝纶的赏识,他又善于叙事抒情,两人的合作可谓是珠联璧合。
小说翻译后,由魏瀚出资刻印了百部,为了收回成本,林纾的另一位好友高凤谦(后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便与主持上海《中外日报》的汪康年联系,希望能帮忙销售。
汪康年当即决定买下版权,在报上连载,但由于高凤谦担心报上连载会影响单行本销路,最后是决定将《巴黎茶花女遗事》与原先《时务报》上连载的《新译包探案》《昌言报》连载的《长生术》合印成一书刊行。
汪康年动作很快,他与高凤谦谈妥后没几天,即在《中外日报》上介绍《巴黎茶花女》情节变幻,意绪凄恻,“不日出书”,并声称书稿是“本馆特向译书之人用巨资购得”。
半个月后林纾在福建看到这则广告,他的本意只想收回刻印成本,现在译书居然也可得“巨资”,这使他大为惶恐。
他赶紧写信给汪康年,说明自己是“游戏笔墨,本无足轻重”,尽管书上只署名“冷红生”,但不少人知道这是林纾的笔名,如果收取稿酬,就会有损他的清誉。
林纾要求汪康年“再行登报”声明:“前报所云致巨资为福建某君翻译此书润笔,兹某君不受,由本处捐送福建蚕学会。
”林纾信寄出半个月后,上海《中外日报》从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连续刊载了一则《(茶花女遗事)告白》:此书闽中某君所译,本馆现行重印,并拟以巨资酬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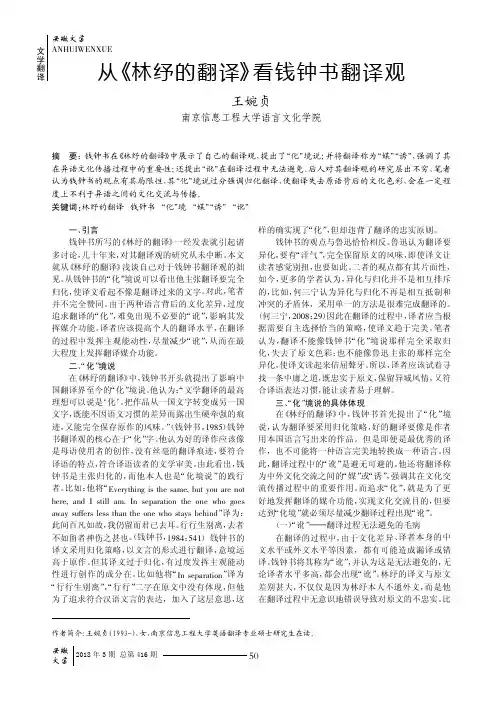
安徽文学ANHUIWENXUE 安徽文学2018年3期总第416期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翻译观王婉贞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摘要: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展示了自己的翻译观,提出了“化”境说;并将翻译称为“媒”“诱”,强调了其在异语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性;还提出“讹”在翻译过程中无法避免。
后人对其翻译观的研究层出不穷,笔者认为钱钟书的观点有其局限性,其“化”境说过分强调归化翻译,使翻译失去原语背后的文化色彩,会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异语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
关键词院林纾的翻译钱钟书“化”境“媒”“诱”“讹”作者简介:王婉贞(1993-),女,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英语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
一、引言钱钟书所写的《林纾的翻译》一经发表就引起诸多讨论,几十年来,对其翻译观的研究从未中断。
本文就从《林纾的翻译》浅谈自己对于钱钟书翻译观的拙见。
从钱钟书的“化”境说可以看出他主张翻译要完全归化,使译文看起不像是翻译过来的文字。
对此,笔者并不完全赞同。
由于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过度追求翻译的“化”,难免出现不必要的“讹”,影响其发挥媒介功能。
译者应该提高个人的翻译水平,在翻译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尽量减少“讹”,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发挥翻译媒介功能。
二、“化”境说在《林纾的翻译》中,钱钟书开头就提出了影响中国翻译界至今的“化”境说。
他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
”(钱钟书,1985)钱钟书翻译观的核心在于“化”字。
他认为好的译作应该像是母语使用者的创作,没有丝毫的翻译痕迹,要符合译语的特点,符合译语读者的文学审美。
由此看出,钱钟书是主张归化的,而他本人也是“化境说”的践行者。
比如:他将“Everything is the same,but you are not here,and I still am.In separation the one who goesaway suffers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 behind ”译为: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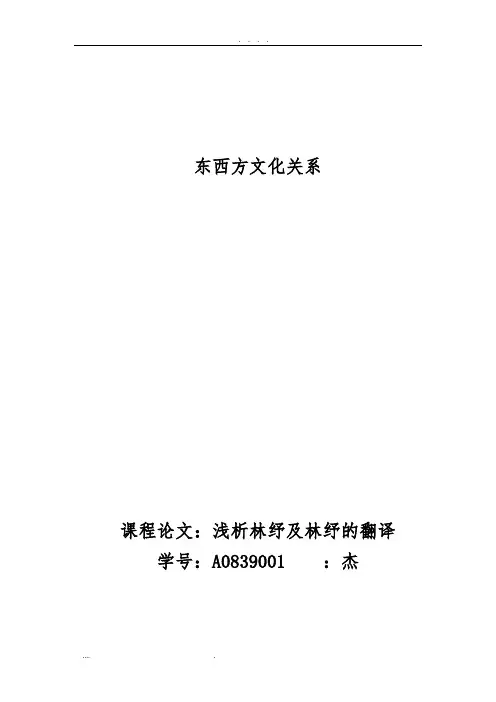
东西方文化关系课程论文:浅析林纾及林纾的翻译学号:A0839001 :杰浅析林纾及林纾的翻译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从古到今,无论是西方还是,翻译思想及理论层出不穷,关于翻译的标准也不一而言。
就翻译本身而言,一般的翻译人员无需有复杂的翻译思想,只要选择一些有价值的境外作品,用通达、符合本民族文化的要求的语言描述即可。
无论是西方还是,翻译活动千百年间从未停止,但是翻译这门职业并未获得世人应有的尊敬,也并未承认他在文化交流中应有的价值。
若单从翻译学科的角度讲,原作与译作的等值、可译与不可译性是翻译理论中争论的焦点,随着时间和文化的发展,近代西方翻译理论也各持己见。
彼得.纽马克在《翻译教程》中这样描述翻译:什么是翻译,在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将原作在文本里的表达的含义通过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但林纾的翻译若只单从翻译学科的角度看,是不能够用翻译标准来衡量其成功或失败的。
林纾的翻译与他所在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
所以只能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林纾个人和林纾的翻译。
林纾的翻译活动前后可大抵分为两个时期,辛亥革命之前,与辛亥革命之后。
林纾生活的年代是中国新旧历史交替时期,社会本身处在变革的年代,且自身政治腐败,经济科技十分落后,面临着外国列强的经济文化的双重侵略。
林纾作为一个受过封建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思想中有进步的东西,也有落后的东西。
《闽中新乐府》是林纾公开发行的第一本诗集,诗文通俗易懂,号召民众反帝救国,对封建科举制度和教育方式十分不满,因林纾生活贫苦,在他的作品里很多反映下层民众生活疾苦,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林纾鲜明的民族思想。
与维新派不同的是,他不但主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看到封建制度的腐朽和和昏庸。
这也是后来林纾从事翻译的思想基础。
林纾本应该是一个极其成功的翻译家,翻译阶段前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后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林纾笔锋渐老,且坚持自己的古文章法,为当时文化潮流所不容。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描述极为贴切:“一个老手或能手不肯或不能再费心卖力,只倚仗积累的一点熟练来搪塞敷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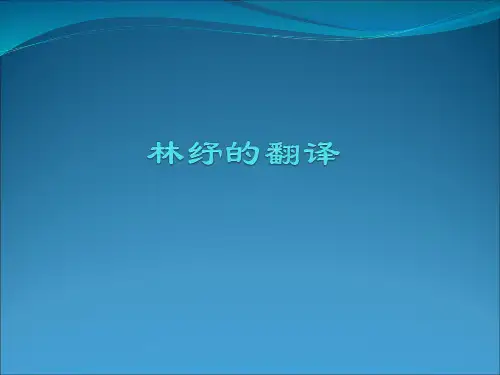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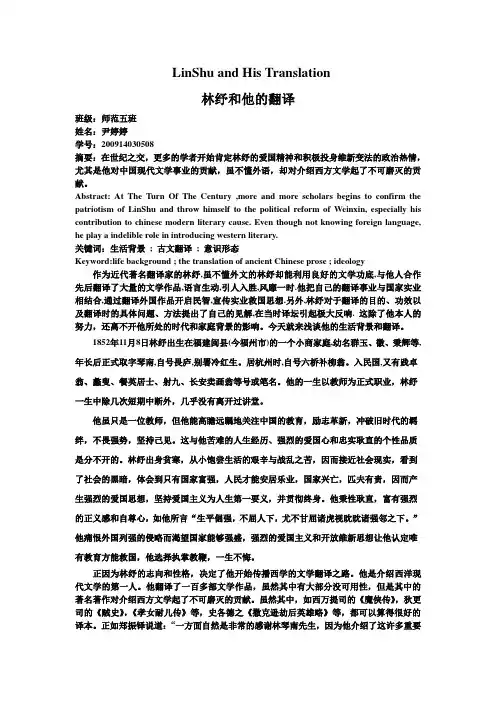
LinShu and His Translation林纾和他的翻译班级:师范五班姓名:尹婷婷学号:200914030508摘要:在世纪之交,更多的学者开始肯定林纾的爱国精神和积极投身维新变法的政治热情,尤其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事业的贡献,虽不懂外语,却对介绍西方文学起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Abstract: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more and more scholars begins to confirm the patriotism of LinShu and throw himself to the political reform of Weinxin, especially hi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cause. Even though not knowing foreign language, he play a indelible role in introducing western literary.关键词:生活背景; 古文翻译; 意识形态Keyword:life background ; the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rose ; ideology 作为近代著名翻译家的林纾,虽不懂外文的林纾却能利用良好的文学功底,与他人合作先后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语言生动,引人入胜,风靡一时.他把自己的翻译事业与国家实业相结合,通过翻译外国作品开启民智,宣传实业救国思想.另外,林纾对于翻译的目的、功效以及翻译时的具体问题、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当时译坛引起极大反响. 这除了他本人的努力,还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和家庭背景的影响。
今天就来浅谈他的生活背景和翻译。
1852年11月8日林纾出生在福建闽县(今福州市)的一个小商家庭,幼名群玉、徽、秉辉等,年长后正式取字琴南,自号畏庐,别署冷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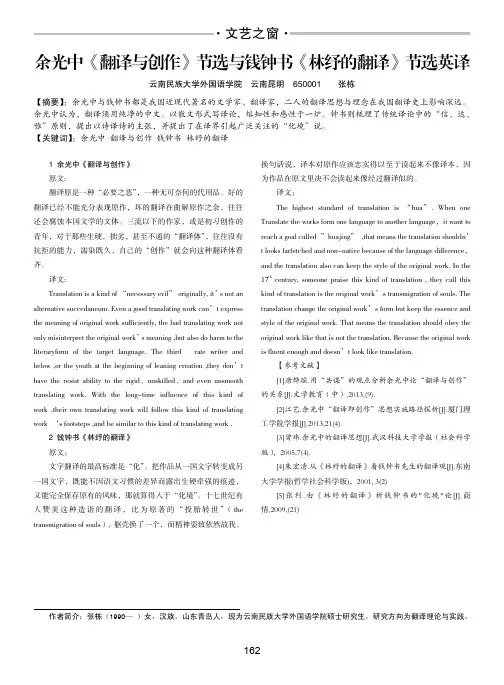
·文艺之窗·162余光中《翻译与创作》节选与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节选英译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云南昆明 650001 张栋【摘要】:余光中与钱钟书都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二人的翻译思想与理念在我国翻译史上影响深远。
余光中认为,翻译须用纯净的中文。
以散文形式写译论,熔知性和感性于一炉。
钟书则梳理了传统译论中的“信、达、雅”原则,提出以诗译诗的主张,并提出了在译界引起广泛关注的“化境”说。
【关键词】:余光中 翻译与创作 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1 余光中《翻译与创作》 原文:翻译原是一种“必要之恶”,一种无可奈何的代用品。
好的翻译已经不能充分表现原作,坏的翻译在曲解原作之余,往往还会腐蚀本国文学的文体。
三流以下的作家,或是初习创作的青年,对于那些生硬,拙劣,甚至不通的“翻译体”,往往没有抗拒的能力,濡染既久,自己的“创作”就会向这种翻译体看齐。
译文:Translation is a kind of “necessary evil” originally, it’s not an alternative succedaneum. Even a good translating work can’t express the meaning of original work sufficiently, the bad translating work not only misinterpret the original work’s meaning ,but also do harm to the literaryform of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third rate writer and below ,or the youth at the beginning of leaning creation ,they don’t have the resist ability to the rigid、unskilled、and even unsmooth translating work. With the long-time influence of this kind of work ,their own translating work will follow this kind of translating work ‘s footsteps ,and be similar to this kind of translating work .2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 原文:文字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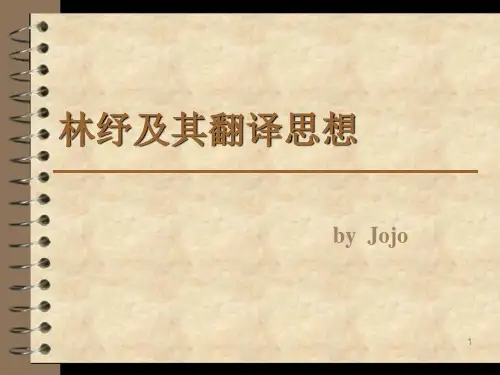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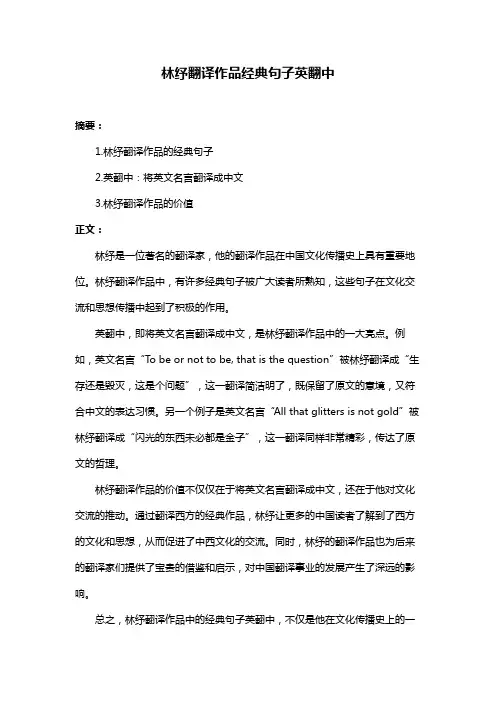
林纾翻译作品经典句子英翻中
摘要:
1.林纾翻译作品的经典句子
2.英翻中:将英文名言翻译成中文
3.林纾翻译作品的价值
正文:
林纾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他的翻译作品在中国文化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林纾翻译作品中,有许多经典句子被广大读者所熟知,这些句子在文化交流和思想传播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英翻中,即将英文名言翻译成中文,是林纾翻译作品中的一大亮点。
例如,英文名言“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被林纾翻译成“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这一翻译简洁明了,既保留了原文的意境,又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
另一个例子是英文名言“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被林纾翻译成“闪光的东西未必都是金子”,这一翻译同样非常精彩,传达了原文的哲理。
林纾翻译作品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将英文名言翻译成中文,还在于他对文化交流的推动。
通过翻译西方的经典作品,林纾让更多的中国读者了解到了西方的文化和思想,从而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同时,林纾的翻译作品也为后来的翻译家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林纾翻译作品中的经典句子英翻中,不仅是他在文化传播史上的一
座丰碑,也是中国翻译史上的宝贵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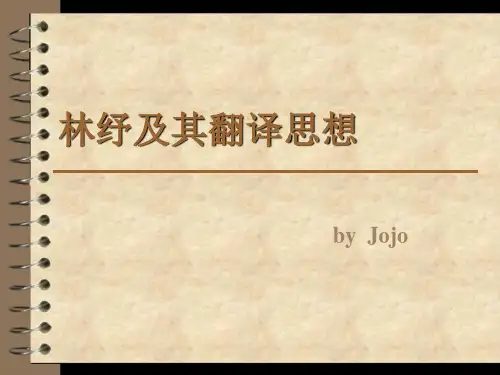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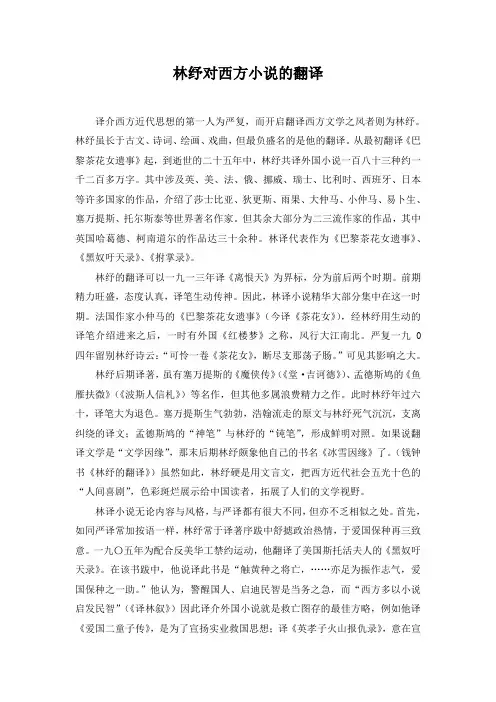
林纾对西方小说的翻译译介西方近代思想的第一人为严复,而开启翻译西方文学之风者则为林纾。
林纾虽长于古文、诗词、绘画、戏曲,但最负盛名的是他的翻译。
从最初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起,到逝世的二十五年中,林纾共译外国小说一百八十三种约一千二百多万字。
其中涉及英、美、法、俄、挪威、瑞士、比利时、西班牙、日本等许多国家的作品,介绍了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大仲马、小仲马、易卜生、塞万提斯、托尔斯泰等世界著名作家。
但其余大部分为二三流作家的作品,其中英国哈葛德、柯南道尔的作品达三十余种。
林译代表作为《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拊掌录》。
林纾的翻译可以一九一三年译《离恨天》为界标,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精力旺盛,态度认真,译笔生动传神。
因此,林译小说精华大部分集中在这一时期。
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今译《茶花女》),经林纾用生动的译笔介绍进来之后,一时有外国《红楼梦》之称,风行大江南北。
严复一九0四年留别林纾诗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可见其影响之大。
林纾后期译著,虽有塞万提斯的《魔侠传》(《堂·吉诃德》)、孟德斯鸠的《鱼雁扶微》(《波斯人信札》)等名作,但其他多属浪费精力之作。
此时林纾年过六十,译笔大为退色。
塞万提斯生气勃勃,浩翰流走的原文与林纾死气沉沉,支离纠绕的译文;孟德斯鸠的“神笔”与林纾的“钝笔”,形成鲜明对照。
如果说翻译文学是“文学因缘”,那末后期林纾颇象他自己的书名《冰雪因缘》了。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虽然如此,林纾硬是用文言文,把西方近代社会五光十色的“人间喜剧”,色彩斑烂展示给中国读者,拓展了人们的文学视野。
林译小说无论内容与风格,与严译都有很大不同,但亦不乏相似之处。
首先,如同严译常加按语一样,林纾常于译著序跋中舒摅政治热情,于爱国保种再三致意。
一九〇五年为配合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他翻译了美国斯托活夫人的《黑奴吁天录》。
在该书跋中,他说译此书是“触黄种之将亡,……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
《迦茵小传》和林纾的古文翻译①张世涛一、从清朝举人到著名翻译家“译才并世数严林”〔1〕。
说到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就不能不提林纾,他的古文翻译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在近代中国都是绝无仅有的,说他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2〕毫不夸张。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囿于政治倾向的考虑,对林纾这个不仅以翻译著名,也以保皇和反对新文化运动著名的前清举人,文学理论界充满了蔑视,翻译界也不屑一顾,这是十分可惜的。
林纾,字琴南,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
生于1852年(即清文宗咸丰二年),卒于1924年,终年73岁。
1882年11月,31岁的他得了举人(即清光绪八年壬午科),再赴京考进士不得,从此便绝弃了制举之业,尊桐城派末代宗师吴汝纶为师,专力于古文,成就颇高。
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法国归来的王子仁(号晓斋主人)向他介绍小仲马的《茶花女》,说翻译它,“子可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
”〔3〕于是他便与王子仁合作,共同翻译了这部近代中国西方文学翻译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巴黎茶花女遗事》(Ladame aux camélias),轰动一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据郑振铎的统计,他翻译成书的便有156种,出版的有132种。
〔4〕林纾这个前清举人也由此成为近代中国最著名和最高产的翻译家之一。
二、不懂外语的翻译家林纾作为一个翻译家的奇特之处是他不懂任何的外国语。
他译书时,总是由一个懂得原文的译者,口译给他听,他再把口译者的话写成中文。
他写得非常快,据陈衍《续闽川文士传》说:“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限一时许就千言,不窜一字。
”〔5〕在他翻译高峰期,每年光是出版的翻译小说便达十几部,翻译速度之快可想而知,因而他译文的谬误也在所难免。
由于他常常删改增加原文,有的人便把他的翻译当成“讹译”的代名词。
①所据《迦茵小传》为商务印书馆年重印版。
1981不懂外语,无法接触原著使他将作品的选择权全部交给了口译助手,助手文学修养和外语水平的高低对林纾的翻译质量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浅析林纾翻译中的误译作者:程攀来源:《北方文学》2019年第24期摘要:林纾是近代重要的翻译家,其译作对我国近现代翻译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林译作品在广受褒誉的同时,译作中的大量误译也受到质疑和诟病。
林纾在翻译时常常增添或删减原作内容,有学者认为林纾不懂外文且翻译“落纸如飞”,从而信手增删以至于减损了作品的情味;也有学者认为林纾此举使林译作品别具一格,令这些独具特色的译本广受读者欢迎。
林译作品中的确存在大量的误译,这其中的相当部分都是译者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当时国情而作出的调整。
这些误译可视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再创作,赋予了译文新的审美价值与实用性。
关键词:林纾;误译;再创作翻译活动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可以称之为一项十分复杂的活动。
关于翻译的关注核心应当是文本风格和文学性,还是语言的语义功能,这个争论直至今日也未尝有定论。
从文学的角度看,文学作品自然应当以美学功能为首,翻译文学亦不例外。
一般来讲,两种语言的结构和习惯用法是不尽相同的,翻译时也就难以寻求两种语言的完全对等。
这样一来,译者必定也就根据各种因素,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转换与再创作。
林纾在翻译时,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那么林译作品必然会与原作文本有出入,这是误译的一种情况。
至于林纾翻译时有意为之的改写和创作,则是误译的另一种情况,这也值得探究和关注背后的原因及其影响。
一、林纾误译的原因首先,林纾翻译中的大量误译与他不通外文且翻译极快速有一定关联。
林纾并不通外文,他的所有翻译工作都是和他人合作:通晓外文的人向林纾口述翻译,再由林纾落笔成文。
“他不懂得任何的外语,他的译书,乃由一个懂得原文的译者,口译给他听,他便依据了口译者的话写成了中文。
”(1)在此过程中,原文本经过口译者已是第一道语言的转换;林纾根据口述再写成中文,这又是第二道转换。
经过这两道程序后,译文与原文除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差别外,还难免多添了林纾主观上的些许改动。
同时,林纾翻译的速度非常快,甚至快到“往往口译者尚未说完,他的译文已写完毕。
林纾译_李迫⼤梦_⽚段赏析42《李迫⼤梦》是清末民初著名翻译家林纾于1907年出版的译作(张俊才,1982: 30),其合作者是魏易,收于他们的译⽂集《拊掌录》之中。
该作译⾃美国著名⽂学家、素有美国⽂学之⽗之称的华盛顿·欧⽂(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的著名短篇⼩说Rip V an Winkle(今译《瑞普·凡·温克尔》)。
林纾⼀⽣中究竟翻译了多少书,⾄今还是个谜,说得最少的是“成书的共有⼀百五⼗六种;其中有⼀百三⼗⼆种是已经出版的”(郑振铎,2009: 247);说得最多的是“多⾄⼆百零六种”(见刘绍唐,1978: 140)。
林纾由于古⽂造诣⾼深,语⾔表达优美,其译⽂深受清末民初的读者的喜爱。
本⽂选择删改相对较少的《李迫⼤梦》中的⼀个⽚段,让我们来欣赏⼀位古⽂⼤师对来⾃异域风情的独特体验。
WHOEVER has made a voyage up the Hudsonmust remember the Kaatskill mountains. They are a dismembered branch of the great Appalachian family,and are seen away to the west of the river, swelling upto a noble height, and lording it over the surrounding country. Every change of season, every change of weather, indeed, every hour of the day, producessome change in the magical hues and shapes of these mountains, and they are regarded by all the good wives, far and near, as perfect barometers. When the weatheris fair and settled, they are clothed in blue and purple,and print their bold outlines on the clear evening sky, but, sometimes, when the rest of the landscape is cloudless, they will gather a hood of gray vapors about their summits, which, in the last rays of the setting sun,will glow and light up like a crown of glory.At the foot of these fairy mountains, the voyagermay have descried the light smoke curling up from a village, whose shingle-roofs gleam among the trees, just where the blue tints of the upland melt away into the fresh green of the nearer landscape. It is a little village of great antiquity, having been founded by some of the Dutch colonists, in the early times of the province, just 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good Peter Stuyvesant, (may he rest in peace!) and there were some of the houses of the original settlers standing within a few years, built of small yellow bricks brought from Holland, having latticed windows and gable fronts, surmounted with weather-cocks.In that same village, and in one of these veryhouses (which, to tell the precise truth, was sadly time-worn and weather-beaten), there lived many years since, while the country was yet a province of Great Britain, a simple good-natured fellow of the nameof Rip V an Winkle. He was a descendant of the V an Winkles who ? gured so gallantly in the chivalrous days of Peter Stuyvesant, and accompanied him to the siege of Fort Christina. He inherited, however, but little ofthe martial character of his ancestors. I have observed that he was a simple good-natured man; he was, moreover, a kind neighbor, and an obedient hen-pecked husband. Indeed, to the latter circumstance might be owing that meekness of spirit which gained him such universal popularity; for those men are most apt to be obsequious and conciliating abroad, who are under the discipline of shrews at home. Their tempers, doubtless, are rendered pliant and malleable in the ? ery furnace of domestic tribulation; and a curtain lecture is worthall the sermons in the world for teaching the virtuesof patience and long-suffering. A termagant wife may, therefore, in some respects, be considered a tolerable blessing; and if so, Rip V an Winkle was thrice blessed.凡⼈苟渡⿊逞河者,与⾔加齿⼏⽽⼭,必能忆之。
林纾(1852—1924),是清末民初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其经由曾宗巩口述而翻译的《鲁滨逊漂流记》文言版本,言辞精美,文笔舒畅,体现了出众脱颖、笔墨饱满的翻译水准,令人崇敬,影响深远。
一、文化交流的沟通者林纾是福建福州人,热衷于文学阅读,受“西学东渐”思想影响,他“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决意通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来教育和启迪民智,实现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
1897年,林纾开始翻译法国小仲马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经过个人不懈的艰辛努力,他完成了这部小说的文字翻译工作,并于1899年在福州刊行印发。
作为中国介绍西洋文学的首部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经问世,便在封闭落后的中国大地刮起了一阵旋风,“为国人闻所未闻”,一纸风行全国,备受大众的赞扬与喜爱。
受此鼓励,林纾一发而不可收,在商务印书馆的诚挚邀请下,他潜心专司翻译欧美名家小说,前后共计翻译的作品高达两百余种,国别涉及美、英、法、俄、德、日、西班牙等十多个国家,国内民众称其为“泰山北斗”,外国友人誉其为“不懂外文的最佳翻译家”,名扬中外,堪称清末民初的翻译大师[1]96。
林纾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其他的则在《小说月报》和《小说世界》等杂志上发表,读者甚众。
在林纾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中,其中就包括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
令人称奇的是,翻译家林纾本人并不懂得外文,他的翻译主要是在“玩索译本,默印心中”、“质西书疑义”的状态下通过口译者的协助完成的。
有人曾经这样点评过林纾的翻译水准,说:“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一时许译就千言,不窜一字。
见者竞诧其速且工。
”在翻译的过程中,林纾凭借敏锐的文学直觉与深厚的汉文造诣,能够将口译者的言辞传达惟妙惟肖、细致精确地融会到汉语的文言文当中,即便是在口译者甚至不知道如何使用恰当的言辞表达文学作品中的内在含义时,他也能够根据作品的上下文情节善于捕捉原文作者意欲表达的内容,以精炼明白的语言写就下来[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