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六代影像中国_关于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谱系研寻_杨远婴
- 格式:pdf
- 大小:194.29 KB
- 文档页数: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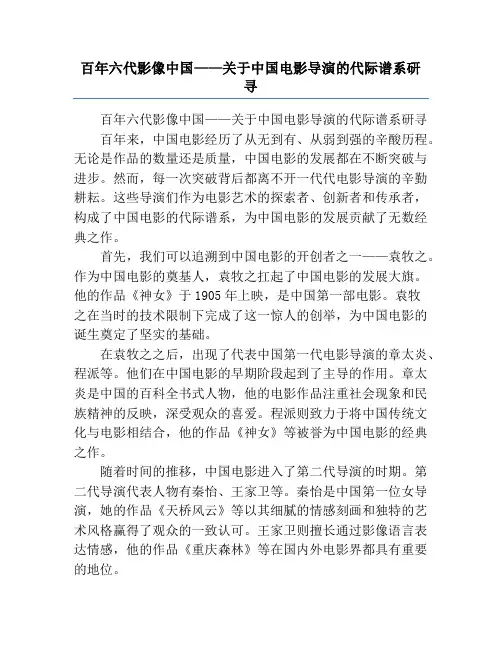
百年六代影像中国——关于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谱系研寻百年六代影像中国——关于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谱系研寻百年来,中国电影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辛酸历程。
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中国电影的发展都在不断突破与进步。
然而,每一次突破背后都离不开一代代电影导演的辛勤耕耘。
这些导演们作为电影艺术的探索者、创新者和传承者,构成了中国电影的代际谱系,为中国电影的发展贡献了无数经典之作。
首先,我们可以追溯到中国电影的开创者之一——袁牧之。
作为中国电影的奠基人,袁牧之扛起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大旗。
他的作品《神女》于1905年上映,是中国第一部电影。
袁牧之在当时的技术限制下完成了这一惊人的创举,为中国电影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袁牧之之后,出现了代表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的章太炎、程派等。
他们在中国电影的早期阶段起到了主导的作用。
章太炎是中国的百科全书式人物,他的电影作品注重社会现象和民族精神的反映,深受观众的喜爱。
程派则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电影相结合,他的作品《神女》等被誉为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电影进入了第二代导演的时期。
第二代导演代表人物有秦怡、王家卫等。
秦怡是中国第一位女导演,她的作品《天桥风云》等以其细腻的情感刻画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赢得了观众的一致认可。
王家卫则擅长通过影像语言表达情感,他的作品《重庆森林》等在国内外电影界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而第三代导演的代表,包括张艺谋、李安等人,他们将中国电影推向了国际舞台。
张艺谋的作品《红高粱》、《活着》等影片以其独特的视觉风格和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力,为中国电影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赞誉。
李安则以其对东西方文化的巧妙融合和对人物内心情感的细腻描写而成为世界级导演,他的作品《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断背山》等都在国际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有贾樟柯、王小帅等。
他们的作品大胆尝试新的表达方式,挖掘社会中的边缘群体,对中国当代社会进行深入思考和观察。
贾樟柯的《还珠格格》、《天注定》等作品引领了中国电影的另类潮流, 王小帅的《黄土地》等作品呈现出触及人性底线的灵魂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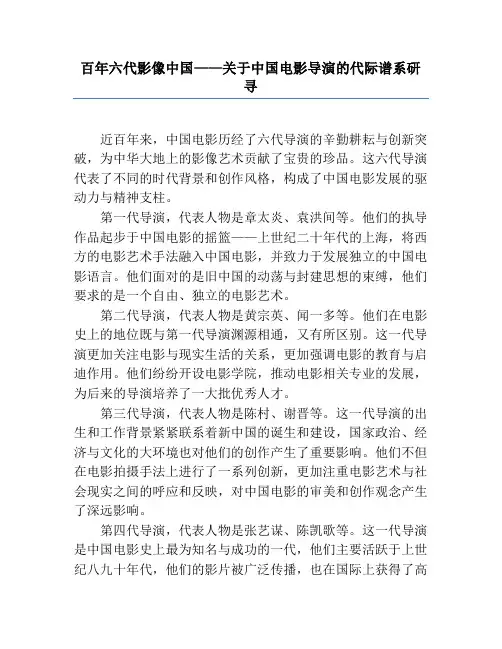
百年六代影像中国——关于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谱系研寻近百年来,中国电影历经了六代导演的辛勤耕耘与创新突破,为中华大地上的影像艺术贡献了宝贵的珍品。
这六代导演代表了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创作风格,构成了中国电影发展的驱动力与精神支柱。
第一代导演,代表人物是章太炎、袁洪间等。
他们的执导作品起步于中国电影的摇篮——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将西方的电影艺术手法融入中国电影,并致力于发展独立的中国电影语言。
他们面对的是旧中国的动荡与封建思想的束缚,他们要求的是一个自由、独立的电影艺术。
第二代导演,代表人物是黄宗英、闻一多等。
他们在电影史上的地位既与第一代导演渊源相通,又有所区别。
这一代导演更加关注电影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更加强调电影的教育与启迪作用。
他们纷纷开设电影学院,推动电影相关专业的发展,为后来的导演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第三代导演,代表人物是陈村、谢晋等。
这一代导演的出生和工作背景紧紧联系着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大环境也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们不但在电影拍摄手法上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更加注重电影艺术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呼应和反映,对中国电影的审美和创作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是张艺谋、陈凯歌等。
这一代导演是中国电影史上最为知名与成功的一代,他们主要活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的影片被广泛传播,也在国际上获得了高度赞誉。
这一代导演更加注重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对中国动荡的社会背景下的人性因素进行了深度剖析,让国内外观众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中国文化与民俗。
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是贾樟柯、王小帅等。
这一代导演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崛起的,他们的电影作品既体现了中国社会变迁的特殊性,同时也表达了导演对自我的思考与探索。
他们选择了与传统中国电影的叙事方式与审美风格不同的创作路径,更加接近于现实与生活,用真实贴近的方式描摹社会百态。
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是贾平凹、果麦等。
这一代导演是在新媒体时代崛起的,他们利用新技术和媒介手段进行影片创作,更加注重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具有较强的实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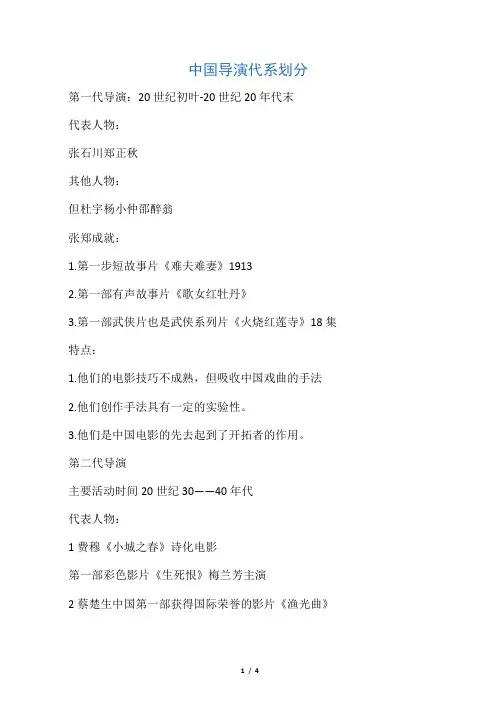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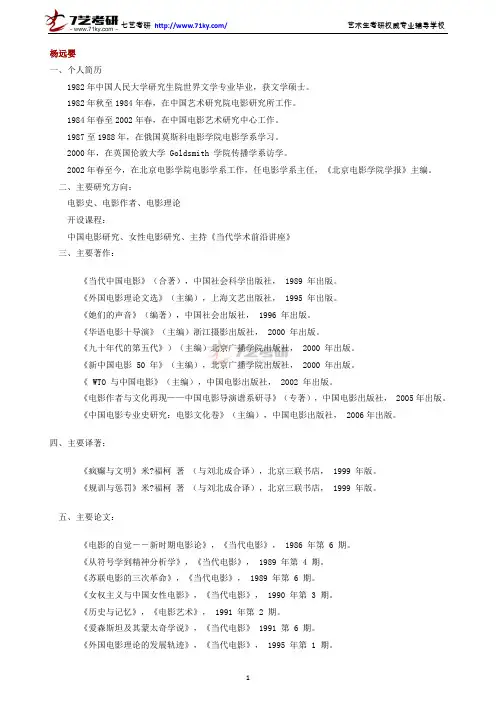
杨远婴一、个人简历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世界文学专业毕业,获文学硕士。
1982年秋至1984年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工作。
1984年春至2002年春,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工作。
1987至1988年,在俄国莫斯科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学习。
2000年,在英国伦敦大学 Goldsmith 学院传播学系访学。
2002年春至今,在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工作,任电影学系主任,《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主编。
二、主要研究方向:电影史、电影作者、电影理论开设课程:中国电影研究、女性电影研究、主持《当代学术前沿讲座》三、主要著作:《当代中国电影》(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她们的声音》(编著),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华语电影十导演》(主编)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九十年代的第五代》)(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新中国电影 50 年》(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 WTO 与中国电影》(主编),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电影作者与文化再现——中国电影导演谱系研寻》(专著),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年出版。
《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文化卷》(主编),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年出版。
四、主要译著:《疯癫与文明》米?福柯 著 (与刘北成合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规训与惩罚》米?福柯 著 (与刘北成合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五、主要论文:《电影的自觉――新时期电影论》,《当代电影》, 1986 年第 6 期。
《从符号学到精神分析学》,《当代电影》, 1989 年第 4 期。
《苏联电影的三次革命》,《当代电影》, 1989 年第 6 期。
《女权主义与中国女性电影》,《当代电影》, 1990 年第 3 期。
《历史与记忆》,《电影艺术》, 1991 年第 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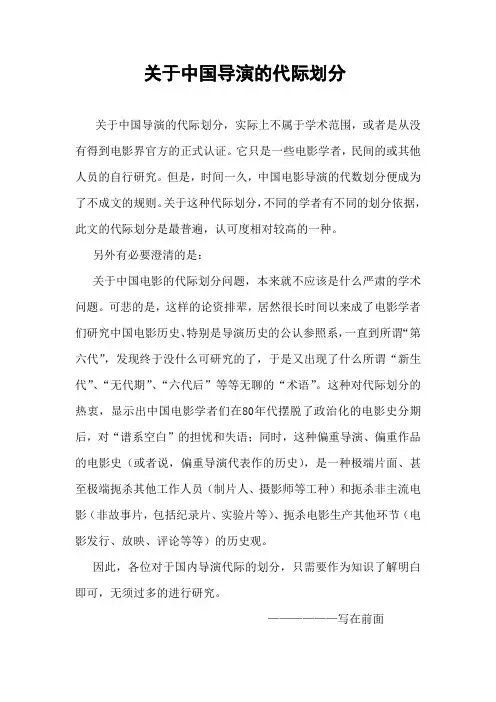
关于中国导演的代际划分关于中国导演的代际划分,实际上不属于学术范围,或者是从没有得到电影界官方的正式认证。
它只是一些电影学者,民间的或其他人员的自行研究。
但是,时间一久,中国电影导演的代数划分便成为了不成文的规则。
关于这种代际划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划分依据,此文的代际划分是最普遍,认可度相对较高的一种。
另外有必要澄清的是:关于中国电影的代际划分问题,本来就不应该是什么严肃的学术问题。
可悲的是,这样的论资排辈,居然很长时间以来成了电影学者们研究中国电影历史、特别是导演历史的公认参照系,一直到所谓“第六代”,发现终于没什么可研究的了,于是又出现了什么所谓“新生代”、“无代期”、“六代后”等等无聊的“术语”。
这种对代际划分的热衷,显示出中国电影学者们在80年代摆脱了政治化的电影史分期后,对“谱系空白”的担忧和失语;同时,这种偏重导演、偏重作品的电影史(或者说,偏重导演代表作的历史),是一种极端片面、甚至极端扼杀其他工作人员(制片人、摄影师等工种)和扼杀非主流电影(非故事片,包括纪录片、实验片等)、扼杀电影生产其他环节(电影发行、放映、评论等等)的历史观。
因此,各位对于国内导演代际的划分,只需要作为知识了解明白即可,无须过多的进行研究。
——————写在前面一、“第一代导演”活动的时间大体上是在世纪初到20年代末。
第一代导演是中国电影的开拓者(1905~1930)。
中国电影始于1905年,由任庆泰出资,刘仲伦摄影的京剧纪录片《定军山》为中国电影史首开先河。
随后,梅兰芳也应邀拍摄了《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
直至1913年郑正秋、张石川拍摄了短故事片《难夫难妻》,开始尝试摆脱戏曲舞台的挪用,进行独立的电影剧本创作。
这段时间涌现的导演总计约一百人左右,其中以张石川、郑正秋、但杜宇、杨小仲、邵醉翁为代表,活动的时间大体是在本世纪初到二十年代。
“第一代导演”是中国电影的先驱,在拍摄条件非常简陋、艰苦,又缺乏经验的条件下,创作了中国第一批故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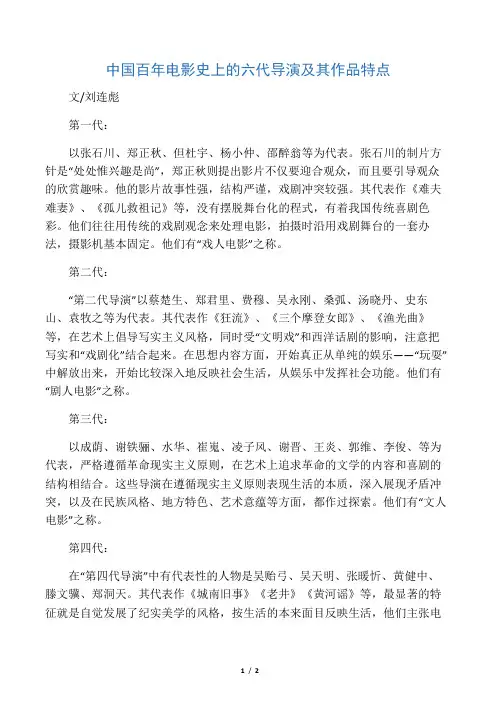
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的六代导演及其作品特点文/刘连彪第一代:以张石川、郑正秋、但杜宇、杨小仲、邵醉翁等为代表。
张石川的制片方针是“处处惟兴趣是尚”,郑正秋则提出影片不仅要迎合观众,而且要引导观众的欣赏趣味。
他的影片故事性强,结构严谨,戏剧冲突较强。
其代表作《难夫难妻》、《孤儿救祖记》等,没有摆脱舞台化的程式,有着我国传统喜剧色彩。
他们往往用传统的戏剧观念来处理电影,拍摄时沿用戏剧舞台的一套办法,摄影机基本固定。
他们有“戏人电影”之称。
第二代:“第二代导演”以蔡楚生、郑君里、费穆、吴永刚、桑弧、汤晓丹、史东山、袁牧之等为代表。
其代表作《狂流》、《三个摩登女郎》、《渔光曲》等,在艺术上倡导写实主义风格,同时受“文明戏”和西洋话剧的影响,注意把写实和“戏剧化”结合起来。
在思想内容方面,开始真正从单纯的娱乐——“玩耍”中解放出来,开始比较深入地反映社会生活,从娱乐中发挥社会功能。
他们有“剧人电影”之称。
第三代:以成荫、谢铁骊、水华、崔嵬、凌子风、谢晋、王炎、郭维、李俊、等为代表,严格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原则,在艺术上追求革命的文学的内容和喜剧的结构相结合。
这些导演在遵循现实主义原则表现生活的本质,深入展现矛盾冲突,以及在民族风格、地方特色、艺术意蕴等方面,都作过探索。
他们有“文人电影”之称。
第四代:在“第四代导演”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吴贻弓、吴天明、张暖忻、黄健中、滕文骥、郑洞天。
其代表作《城南旧事》《老井》《黄河谣》等,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自觉发展了纪实美学的风格,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他们主张电影要创新,中国电影语言要和世界接轨,要求电影语言具有现代化风格,力图运用新的电影观念来改造和发展电影。
第五代:“第五代导演”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陈凯歌、张艺谋、吴子牛、田壮壮、黄建新。
其代表作《黄土地》《红高粱》《大阅兵》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对电影语言象征、比喻、造型功能的迷恋,因而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具有极强的造型性、主观性、象征性和寓意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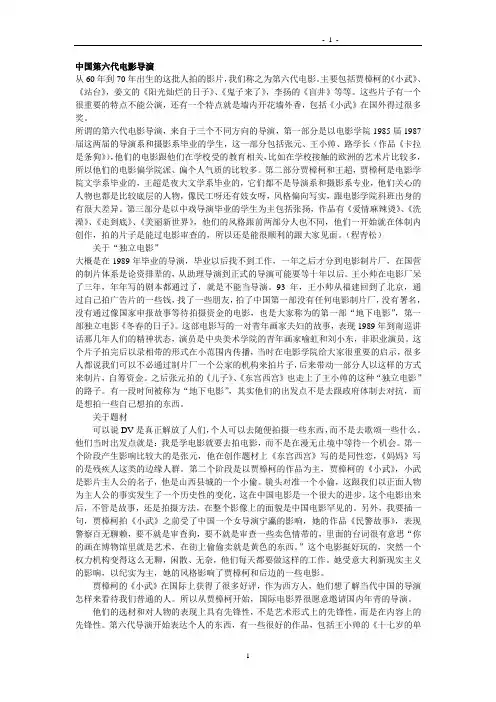
中国第六代电影导演从60年到70年出生的这批人拍的影片,我们称之为第六代电影。
主要包括贾樟柯的《小武》、《站台》,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李扬的《盲井》等等。
这些片子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不能公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包括《小武》在国外得过很多奖。
所谓的第六代电影导演,来自于三个不同方向的导演,第一部分是以电影学院1985届1987届这两届的导演系和摄影系毕业的学生,这一部分包括张元、王小帅、路学长(作品《卡拉是条狗》),他们的电影跟他们在学校受的教育相关,比如在学校接触的欧洲的艺术片比较多,所以他们的电影偏学院派、偏个人气质的比较多。
第二部分贾樟柯和王超,贾樟柯是电影学院文学系毕业的,王超是夜大文学系毕业的,它们都不是导演系和摄影系专业,他们关心的人物也都是比较底层的人物,像民工呀还有妓女呀,风格偏向写实,跟电影学院科班出身的有很大差异。
第三部分是以中戏导演毕业的学生为主包括张扬,作品有《爱情麻辣烫》、《洗澡》、《走到底》、《美丽新世界》,他们的风格跟前两部分人也不同,他们一开始就在体制内创作,拍的片子是能过电影审查的,所以还是能很顺利的跟大家见面。
(程青松)关于“独立电影”大概是在1989年毕业的导演,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一年之后才分到电影制片厂,在国营的制片体系是论资排辈的,从助理导演到正式的导演可能要等十年以后。
王小帅在电影厂呆了三年,年年写的剧本都通过了,就是不能当导演。
93年,王小帅从福建回到了北京,通过自己拍广告片的一些钱,找了一些朋友,拍了中国第一部没有任何电影制片厂,没有署名,没有通过像国家申报故事等待拍摄资金的电影,也是大家称为的第一部“地下电影”,第一部独立电影《冬春的日子》。
这部电影写的一对青年画家夫妇的故事,表现1989年到南巡讲话那几年人们的精神状态,演员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青年画家喻虹和刘小东,非职业演员。
这个片子拍完后以录相带的形式在小范围内传播,当时在电影学院给大家很重要的启示,很多人都说我们可以不必通过制片厂一个公家的机构来拍片子,后来带动一部分人以这样的方式来制片,自筹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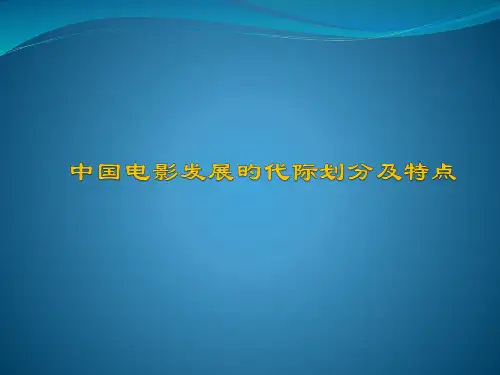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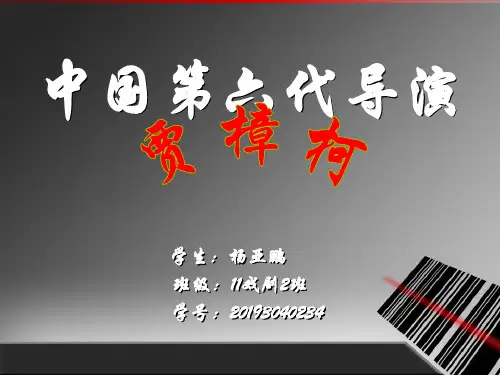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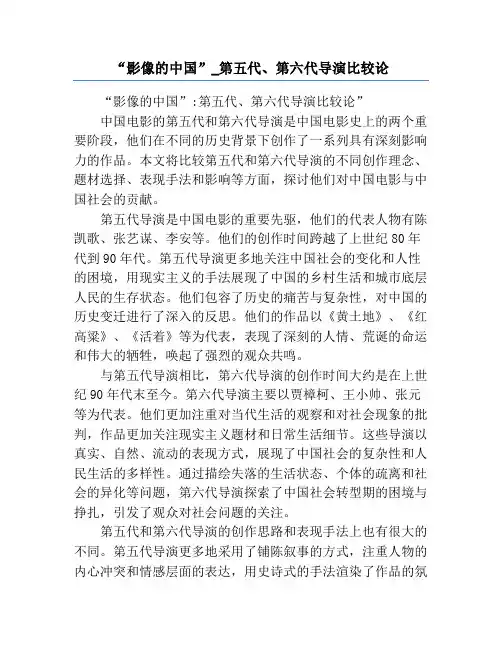
“影像的中国”_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比较论“影像的中国”: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比较论”中国电影的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两个重要阶段,他们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创作了一系列具有深刻影响力的作品。
本文将比较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的不同创作理念、题材选择、表现手法和影响等方面,探讨他们对中国电影与中国社会的贡献。
第五代导演是中国电影的重要先驱,他们的代表人物有陈凯歌、张艺谋、李安等。
他们的创作时间跨越了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
第五代导演更多地关注中国社会的变化和人性的困境,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了中国的乡村生活和城市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
他们包容了历史的痛苦与复杂性,对中国的历史变迁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他们的作品以《黄土地》、《红高粱》、《活着》等为代表,表现了深刻的人情、荒诞的命运和伟大的牺牲,唤起了强烈的观众共鸣。
与第五代导演相比,第六代导演的创作时间大约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
第六代导演主要以贾樟柯、王小帅、张元等为代表。
他们更加注重对当代生活的观察和对社会现象的批判,作品更加关注现实主义题材和日常生活细节。
这些导演以真实、自然、流动的表现方式,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人民生活的多样性。
通过描绘失落的生活状态、个体的疏离和社会的异化等问题,第六代导演探索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困境与挣扎,引发了观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的创作思路和表现手法上也有很大的不同。
第五代导演更多地采用了铺陈叙事的方式,注重人物的内心冲突和情感层面的表达,用史诗式的手法渲染了作品的氛围和情感张力。
而第六代导演则更加注重细节的观察,以纪实的方式展现社会的细微变革和个体的自我挣扎,呈现出更真实、接地气的电影语言。
这两代导演的作品对中国电影乃至世界电影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五代导演以真实的表现手法和对社会现象的批判意识,为中国电影注入了新的艺术气息。
他们的作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情感和思考,为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声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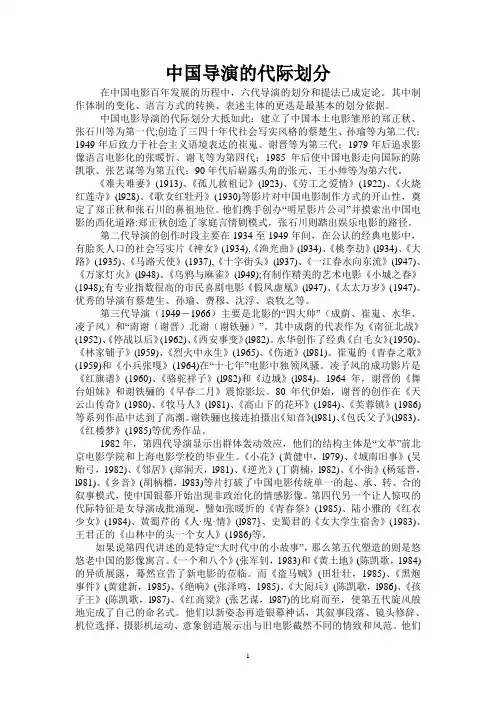
中国导演的代际划分在中国电影百年发展的历程中,六代导演的划分和提法已成定论。
其中制作体制的变化、语言方式的转换、表述主体的更迭是最基本的划分依据。
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划分大抵如此:建立了中国本土电影雏形的郑正秋、张石川等为第一代;创造了三四十年代社会写实风格的蔡楚生、孙瑜等为第二代;1949年后致力于社会主义语境表达的崔嵬、谢晋等为第三代;1979年后追求影像语言电影化的张暖忻、谢飞等为第四代;1985年后使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陈凯歌、张艺谋等为第五代;90年代后崭露头角的张元、王小帅等为第六代。
《难夫难妻》(1913)、《孤儿救祖记》(l923)、《劳工之爱情》(1922)、《火烧红莲寺》(l928)、《歌女红牡丹》(1930)等影片对中国电影制作方式的开山性,奠定了郑正秋和张石川的鼻祖地位。
他们携手创办“明星影片公司”并摸索出中国电影的西化道路:郑正秋创造了家庭言情剧模式,张石川则踏出娱乐电影的路径。
第二代导演的创作时段主要在1934至1949年间,在公认的经典电影中,有脍炙人口的社会写实片《神女》(1934),《渔光曲》(l934)、《桃李劫》(l934)、《大路》(1935)、《马路天使》(1937),《十字街头》(l937)、《一江春水向东流》(l947)、《万家灯火》(l948)、《乌鸦与麻雀》(l949);有制作精美的艺术电影《小城之春》(1948);有专业指数很高的市民喜剧电影《假凤虚凰》(l947)、《太太万岁》(1947)。
优秀的导演有蔡楚生、孙瑜、费穆、沈浮、袁牧之等。
第三代导演(1949-1966)主要是北影的“四大帅”(成荫、崔嵬、水华、凌子风)和“南谢(谢晋)北谢(谢铁骊)”。
其中成荫的代表作为《南征北战》(1952)、《停战以后》(1962)、《西安事变》(l982)。
水华创作了经典《白毛女》(1950)、《林家铺子》(l959)、《烈火中永生》(1965)、《伤逝》(l981)。
百年六代影像中国——关于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谱系研寻百年六代影像中国——关于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谱系研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和文化表达,电影通过影像和音响的融合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语言。
在电影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电影作为一种独特而又多元的现象,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思想的演进。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电影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导演,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思考,以不同的风格和视角,留下了丰富多彩的艺术遗产。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探索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谱系,分析其创作特点和对中国电影发展的影响。
第一代导演:中国电影的开拓者中国电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那个时候电影还是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正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
在这个时期,一些早期的电影艺术家成为了中国电影的开拓者。
其中最为知名的是张炎和沈河夫妇。
他们与国际接轨,引进了许多西方电影技术,为中国电影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们的作品陆续面世,创造了中国电影的黄金时期。
第二代导演:主旋律与爱国情怀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电影成为了党和政府推动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手段。
在这个阶段,电影导演开始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同时也试图通过情节和角色对人民进行教育和启发。
第二代导演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谢晋、陈毅和夏衍。
他们的作品以主旋律和批判现实为特点,强调爱国情怀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第三代导演:审美启蒙与个体主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和挑战。
在这个时期,电影导演开始更加关注个体的价值和审美追求。
他们尝试突破旧有的艺术观念和创作模式,对电影语言进行再思考和尝试。
第三代导演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张艺谋、陈凯歌和李安。
他们的作品以审美启蒙和对内心世界的探索为特点,对观众提出了更多的思考和想象空间。
第四代导演:现实主义与草根生活进入21世纪,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个阶段,影像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崛起为导演们提供了更多的创作机会和空间。
第四代导演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贾樟柯、王小帅和李楚楚。
I~||_,十艺Tit研究I I__R三三B=R匚I 中国第六代电影导演的探索之路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夏秋悦陈红梅摘要:代际划分是研究中国电影的重要方法,在中国电影蓬勃发展的今天,第六代的称谓已经延续了将近四十年。
郑洞天先生曾指出:“如果写中国电影百年史,那么到了第六代,真正的导演,作为个人艺术家的特征显示出来了。
”代际更迭,给电影生态带来了崭新面貌。
在时代背景下,中国导演第六代独特的影像风格、关注视角与美学追求,也深深影响着中国电影的新阶段和未来走向。
关键词:代际划分第六代中国电影新形势研究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很难避开对于中国电影导演的研究。
1905年,中国电影正式诞生,从以张石川、郑正秋为代表的第—代导演开始,中国的电影导演们便走上了各自创作之路。
用"划代”的方式来概述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评价不同时期的电影风格,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创举。
作为一种习惯和约定俗成的说法,"导演代际划分”虽然缺乏一定的缜密性和科学性,但在过去几十年的电影研究中举足轻重,现在仍然被用来对中国导演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关系加以介说①。
中国导演第六代以王小帅、娄烨、管虎、贾樟柯等人为代表,在继承前几代导演的风格基础上,为中国电影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随着时代的变化与电影技术的革新,第六代导演的美学探索与人文性探索在业已定型后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受限。
新的导演与创作风格不断涌现,但由于整体风格的难以把握尚未形成统一的代际称谓,中国电影的前进方向出现了新的挑战与可能性。
一、中国导演第六代的形成背景众所周知,第六代导演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他们的主体是一群从电影学院走出来的年轻人。
事实上,代际划分从第五代开始,伴随而来的是以第五代为基准的理论地位和空降于这—指称的无限话语权,反推出了其他各代之后,第六代的称谓在电影理论界和批评体系对于命名的美学冲动下,已然横亘在这批导演面前②。
一、中国电影百年六代(1905——)1.在中国电影的研究词汇中,六代导演的划分已成定论。
2.这种划分依据的是独特的行业内法则和共享的社会外因素,二者交互作用最终形成了关于导演构成非自然是集的脉络的代际发展过程。
可以说,六代导演实际上是由中国特定的社会时空所构建的精神集团。
3.代际之间区分的基本标志和要素在于制作体制的变化,语言方式的变化,表达主体的更迭。
二、第一代电影人(中国电影戏剧色彩浓重)代表人物:郑正秋、张石川、黎民伟。
时间:1905——30年代初。
代表作品:《孤儿救祖记》、《老工之爱情》、《庄子试妻》等主要功绩:1)建立了本土电影的雏形(尤其是言情与武打片类型)2)开创了主流影戏,教化电影的基本叙事模式。
三、第二代导演(中国中下层人民的真实生活得到体现)代表人物:蔡楚生、费穆等。
时间:1934——1949年。
代表作品:《渔光曲》、《桃李劫》、《新女性》、《神女》、《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太太万岁》等。
主要功绩:1)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导演和明星,制作借鉴好莱坞,理论学习苏联。
2)开创了30、"40年代的社会写实风格,具有了自觉的新文化批判意识和色彩。
3)开始使电影文化深入人心。
四、第三代导演(由于政治运动,中国电影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大倒退)代表人物:谢晋、崔嵬(三江汇合,北影四大帅,南谢,北谢)时间:1949——1976。
"代表作品:《红色娘子军》、《青春之歌》、《早春二月》、《西安事变》等。
主要功绩:1)完成了社会主义语境的电影表达,创作了红色经典。
2)主要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电影,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和本土戏剧传统;3)“文革电影”是红色经典的极端化,“三突出”创作原则是对电影艺术活动的彻底摧残和扼死。
这个时期电影以歌颂党和社会主义,光明社会为主题,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新貌。
五、第四代导演(学院派,这是中国电影的一个新时期,中国电影得到全面解放,苏醒国家实行重在经济发展,百废待兴的局面。
中 国 电 影 史Chinese Film History明星又反过来成为维护类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事实上,是明星通过制片厂的宣传运作,将其作用与效果源源不断地传送给喜欢他(她)的观众,并通过日常生活的稳定化,使观众在类型观念的潜在指引下,回到影院,再去看他(她)主演的与以前相类似的影片,并通过观看,使观众再一次获得满足,获得快感。
第三点,是关于首轮影院的问题,而20年代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当时的影片公司拥有的首轮影院是数量不多的,只仅限于几家较有势力的公司,这样,影片公司生产出来的影片第一次放映便有了几种不同的方式。
1、在自己的首轮影院放映。
2、租赁别家的首轮影院放映。
3、在二三流影院放映。
在此,我们先来看第二种,影片在别家的首轮影院放映,由于租金昂贵,且加上租期的限制,使这一影片的反馈受到了影响。
而即使很快反馈回来,假定观众非常不喜欢,影片公司要改换类型,但由于租金以及租期的问题,资金的回收便不会及时,这样便限制了制片公司的生产。
第三种放映方式,则效果更差,不仅观众稀少,反馈信息慢,而且资金的回收也相当的困难,在当时小本经营的状态下,投资另一部影片其周期便变得相当漫长。
因此,相较而言,第一种方式,便成为最好的一种方式,在自己的首轮影院放映,先前的麻烦就可迎刃而解,它不仅使影片的反馈信息及时返回,且由于范围广泛,而使这一信息相当准确,再加上资金的流转速度快,这样,便使影片公司根据不同的反馈信息,继续生产或改变原先的类型成为可能。
所以,首轮影院在20年代的中国电影业中,起码具备如下功能:(1)首轮影院的存在,是制片厂与类型之间的一个晴雨表,它告诉制片厂是继续还是停止对该类型的生产。
(2)由于中国当时的影片公司拥有首轮影院的数目太少,决定了中国的电影类型一直处于不成熟的状态,使对类型形态加以修补的可能性变得极小。
综上所述,20年代的中国电影工业与类型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当清楚,简言之,当时的中国电影工业已具备条件并生产出类型,但是,种种的不利条件又限制了类型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导致了20年代中国电影类型的待成熟化,这成为20年代中国电影工业的一大幸事,也成为一大憾事。
百年六代 影像中国关于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谱系研寻杨远婴(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研究员)提要:在中国电影的研究语汇中,六代导演的划分和提法已成定论。
独特的行业内在法则和共享的社会外在因素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中国电影导演非自然时间脉络的代际发展过程。
本文依据制作体制的变化、语言方式的转换、表述主体的更迭,对20世纪六代导演的谱系演变作出描述,刻画不同文化背景中电影导演的精神气质和求索路径,展示不同历史环境下电影观念形态和社会象征符码不断被重新塑造的过程。
生长于百年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中,每个代群的导演都经受了剧烈的身心冲击和思想转变。
在一个世纪斗换星移沧海桑田的衍化里,他们将个人的艺术抱负和政治追求投放于电影世界,从而建构了一个个时空特征鲜明的中国形象。
而在这些不同形象的背后,记录着政治的辖制,观念的约束以及手段的局限,每一代导演的成败荣辱都述说着可歌可叹的家国梦幻。
本文研寻中国导演的代际传承,力图探讨社会心理变化的依据,揣度文化方式转换的契机。
透过其间,以了悟历史政治之于人、之于艺术的强大威慑力量。
关键词:谱系研寻 代际传承 电影功能 专业抱负 社会语境 精神历程 生存条件在中国电影的研究语汇中,六代导演的划分和提法已成定论。
尽管有人表示异议,但大都出于对因强调断代集体特征而抹煞风格手法相异的不满,一般未曾质疑划分六代本身的科学性。
倘若沿袭生物繁衍规律,百年六代似乎过于密集,统领整体人文学科的文史学人仅被定尊为三代。
(1)然而电影学界的六代言说自有缘由:独特的行业内在法则和共享的社会外在因素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中国电影导演非自然时间脉络的代际发展过程,其中制作体制的变化、语言方式的转换、表述主体的更迭是最基本的分析依据。
研究者循之评说,继而约定俗成。
因此,笔者对20世纪六代导演的谱系描述对象绝非生理年龄组合,而是由社会时空所建构的文化精神集团。
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划分大抵如此:建立了本土电影雏形的郑正秋、张石川等为第一代;创造了三四十年代社会写实风格的蔡楚生、孙瑜等为第二代;1949年后致力于社会主义语境表达的崔嵬、谢晋等为第三代;1979年后追求影像语言电影化的张暖忻、谢飞等为第四代;1985年后使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陈凯歌、张艺谋等为第五代;90年代后崭露头角的张元、王小帅等为第六代。
本文希望以代际嬗变为线索,透过谱系研寻,刻画不同文化背景中电影(1)钟一冰《20世纪中国三代文史学人》,《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2月8日。
NO.10599导演的精神气质和求索路径,展示不同历史环境下电影观念形态和社会象征符码不断被重新塑造的轨迹图景。
一《难夫难妻》(1913)、《孤儿救祖记》(1923)、《劳工之爱情》(1922)。
《火烧红莲寺》(1928)、《歌女红牡丹》(1930)、《姊妹花》(1934)等影片对中国电影诸种制作方式的开山性,奠定了郑正秋和张石川的鼻祖地位。
这对携手创办世纪初中国一线电影制作工厂——“明星影片公司”的仲伯兄弟,虽然有着一瘦一胖、一文一武、一雅一俗的内外不同,但却生死相依地摸索出西化道路:郑正秋创造家庭言情剧模式,张石川踏出娱乐电影路径。
中国电影诞生地的上海,当时在外国人眼中是“东方巴黎”,在国人眼中是“十里洋场”。
这两种意象的涵义指称都是城市的资本化特征,可以说,电影在这里的出现有根有据。
无独有偶的是,郑正秋和张石川都在十五六岁的少年时分跻身商海,郑帮养父料理生意,张与舅父经营演艺。
郑正秋后来全身心于戏剧活动,但艺术创作和经营管理同时并举,常常因经济困窘作艺术妥协。
(2)张石川以商经艺,从来就是利润第一。
(3)俩人联手创办“明星公司”后,以原始积累的方式开拓电影运营,在技术和艺术的处心积虑外,时时烦扰心情的便是经济压力。
在“明星”的历史上,有《空谷兰》的难忘,有《火烧红莲寺》的辉煌,有《啼笑姻缘》的峰回路转,有《姊妹花》的内外轰动,但最令大家唏嘘的是在山穷水尽、债台高筑的草创时刻“救了祖,也救了‘明星’”的《孤儿救祖记》。
面对购置器材、养活演员、筹措新片等种种问题,身兼老板和主创的郑正秋、张石川窥探演艺市场,揣度观众心理,追求艺术和销售的双收益。
事实上,在创作和市场合二为一的商业经营轨道中,市场的盈利就是艺术的成功,艺术的成就必须体现为观众的认可。
翻阅郑、张二人的从影传记,常常掩卷感叹的是他们绝处逢生的智谋,背水一战的勇气。
在和营销市场的共谋或拼杀中,郑正秋的“教化”主旨往往屈就于张石川的言情或武侠外衣。
“明星”在早期中国电影竞争中的独占鳌头,既得益于郑、张灵活的艺术路线,也有赖于他们多变的市场方针。
投身电影之前,郑正秋痴迷戏剧,浸泡剧院,结交名角儿,撰写剧评。
情至深处,竟建立剧团,编撰剧本,登台演出。
曾几何时,郑正秋的新民社和家庭戏在上海滩脍炙人口。
而在他20岁的时候,便得到于右任的赏识、与章士钊共事、一睹孙中山风采。
(4)张石川则以敢想敢为人所共知。
他在早年帮助舅母经营“新世界游艺场”与黄楚九(当时上海的大商人)的“大世界游艺场”打擂时,居然异想天开地在车水马龙的南京路和西藏路下破土开凿通道,以招徕大流量游客。
虽然通道后因出水而弃之不用,但启用时刻确实出现壮观的景象——“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5)对此他坦言:“越是艰难的工程,越会促起人们的注意。
越是新奇的花样,越会引起大众的兴趣。
”(6)正是郑、张这种胆与识的结合,掀起了中国电影的初澜。
在研究者的笔下或口中,似乎一直扬郑贬张,这是因为郑正秋有着更多的著述,更强烈的使命感和道德感。
屈指可数的几本史学书籍,都记载着他对电影方法和功能的认知。
在确立拍摄作品原则时,郑正秋主张“以正剧为宜”,“不可无正当之主义揭示于世界”。
(7)即强调电影应表现具有社会意义的思想内容。
与侯曜等同时代人一样,他也是通过戏剧理解电影。
他首先把戏剧特质划分为八种:1.系统化的情节,2.组织过的语言,3.精美的声调,4.相当的副景,5.艺术化的动作,6.深刻的表情,7.人生真理的发挥,8.人类精神的表现。
由于置身无声电影时代,所以他认为电影就是无声的戏剧。
但他也能意识到电影的“造意”、“选地”、“配景”、“导演”、“择人”比戏剧更难。
并他指出了电影独有的“摄剧”、“洗片”、“接片”三项特征。
以戏剧家和剧评家身份进入电影创作的郑正秋无法突破戏剧的藩篱,认识摄影机的美学意味,而特别关注以“影戏”贯彻自己“创造人生”、“改良社会”、“教化民众”的艺术理想。
(8)常年身着棉袍、人称“好好先生”的郑正秋代表了当时娱乐行业中最高的艺术典范和道德形象。
他的电影观如同他的人品和文品,清晰地打着传统的烙印:笼统地将技巧和功能融于一体,从熟悉的事物作直观推理,避开具体的物质分析。
而张石川的技术论则立足于使观众“哭得痛快,笑得开心”。
他认为一个家庭妇女在影片放映后能向别人有头有尾地讲述故事,意味着影片可能受欢迎,否则就有失败的危险。
精通生意经的张石川点出了最基本的观众效应原理。
(9)30年代伊始,郑正秋、张石川已感到力所不殆。
他们拱手请入洋溢着新鲜气息的左翼热血青年,一个电影时代随之落下帷幕。
几十年后重评中国早期电影,一个同经过去的老人慨然写到:电影受五四洗礼最晚。
五四运动发轫以后,有十年以上的时间,电影领域基本上处于新文化运动的绝缘状态。
但他接着阐述到,电影在中国萌芽的时节,贫弱的中国还缺乏开创这种新型事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1913年处女作《难夫难妻》用美国依什尔的资金和设备制作;20年代好莱坞称霸上海电影市场,使国片成为外片的囊中之物。
中国电影在内外交困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挣扎求存,回顾中国电影历程,不能忽视这一事实。
(10)他的话为我们理解郑正秋、张石川电影的价值作出了历史注脚。
二 “郑正秋的逝世表示结束了电影史的一章,而蔡楚生的崛起象征另一章的开头。
”(11)柯灵先生的论断基于这样的事实:《渔光曲》第一次为中国电影赢得国际声誉(1935年在苏联莫斯科国际影展获荣誉奖)。
如果把第二代导演的创作时段限定在1934至1949年间,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时代,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导演、明星都诞生于此。
(2)(3)(4)谭春发《开一代先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
(5)程步高《影坛忆旧》,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
(6)刘思平《张石川从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8页。
(7)郑正秋《明星未来之长片正剧》,《晨星》杂志创刊号,1922年上海版。
(8)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
(9)(10)柯灵:《试为“五四”与电影画一轮廓――电影回顾录》,《中国电影研究》,香港中国电影学会,1983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