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之为“窍”:宋明儒学中的身体本体论建构(一)
- 格式:docx
- 大小:23.15 KB
- 文档页数: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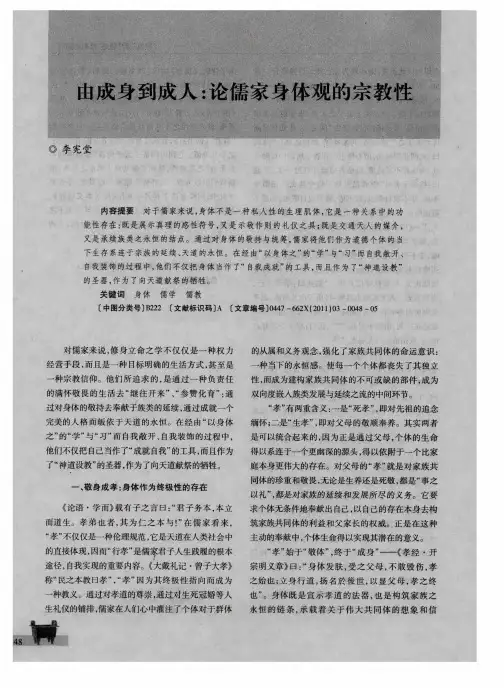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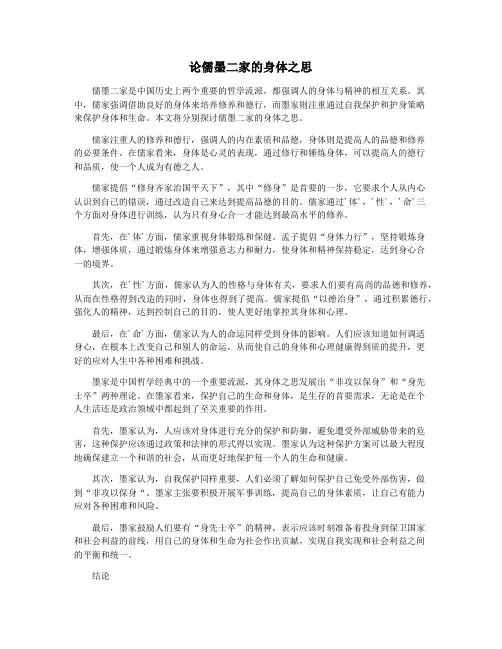
论儒墨二家的身体之思儒墨二家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哲学流派,都强调人的身体与精神的相互关系。
其中,儒家强调借助良好的身体来培养修养和德行,而墨家则注重通过自我保护和护身策略来保护身体和生命。
本文将分别探讨儒墨二家的身体之思。
儒家注重人的修养和德行,强调人的内在素质和品德,身体则是提高人的品德和修养的必要条件。
在儒家看来,身体是心灵的表现,通过修行和锤炼身体,可以提高人的德行和品质,使一个人成为有德之人。
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首要的一步,它要求个人从内心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通过改造自己来达到提高品德的目的。
儒家通过'体','性','命'三个方面对身体进行训练,认为只有身心合一才能达到最高水平的修养。
首先,在'体'方面,儒家重视身体锻炼和保健。
孟子提倡“身体力行”,坚持锻炼身体,增强体质,通过锻炼身体来增强意志力和耐力,使身体和精神保持稳定,达到身心合一的境界。
其次,在'性'方面,儒家认为人的性格与身体有关,要求人们要有高尚的品德和修养,从而在性格得到改造的同时,身体也得到了提高。
儒家提倡“以德治身”,通过积累德行,强化人的精神,达到控制自己的目的,使人更好地掌控其身体和心理。
最后,在'命'方面,儒家认为人的命运同样受到身体的影响。
人们应该知道如何调适身心,在根本上改变自己和别人的命运,从而使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得到质的提升,更好的应对人生中各种困难和挑战。
墨家是中国哲学经典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身体之思发展出“非攻以保身”和“身先士卒”两种理论。
在墨家看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身体,是生存的首要需求,无论是在个人生活还是政治领域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墨家认为,人应该对身体进行充分的保护和防御,避免遭受外部威胁带来的危害,这种保护应该通过政策和法律的形式得以实现。
墨家认为这种保护方案可以最大程度地确保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从而更好地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和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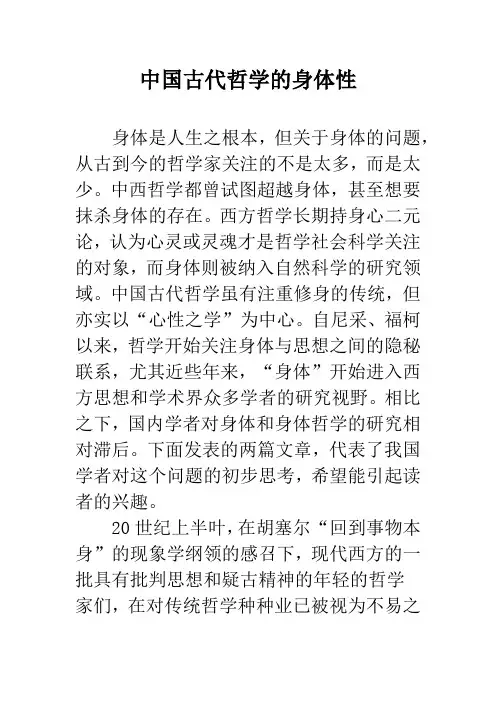
中国古代哲学的身体性身体是人生之根本,但关于身体的问题,从古到今的哲学家关注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中西哲学都曾试图超越身体,甚至想要抹杀身体的存在。
西方哲学长期持身心二元论,认为心灵或灵魂才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对象,而身体则被纳入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
中国古代哲学虽有注重修身的传统,但亦实以“心性之学”为中心。
自尼采、福柯以来,哲学开始关注身体与思想之间的隐秘联系,尤其近些年来,“身体”开始进入西方思想和学术界众多学者的研究视野。
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身体和身体哲学的研究相对滞后。
下面发表的两篇文章,代表了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思考,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20世纪上半叶,在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纲领的感召下,现代西方的一批具有批判思想和疑古精神的年轻的哲学家们,在对传统哲学种种业已被视为不易之论的本体论假定给予大胆质疑的同时,发起了一场为再造传统而先行奠基的哲学上的“寻根”运动。
在这一运动中,虽种种新见迭出不穷,但最具颠覆性和原创性的工作则属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对所谓“身体”的本体论意义的木曷橥。
与传统西方种种业已意识化的哲学不同,梅洛-庞蒂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宣称:“世界的问题,可以始于身体的问题。
”其实,梅氏这一宣言不仅是对西方传统哲学致思取向的根本纠拨,而且也为我们真正切入中国哲学、为我们溯寻中国哲学之“根”提供了路引。
也就是说,掩埋在深厚文化沃土中的中国哲学之“根”,既非西方传统思辨哲学中的那种“意识”,也非晚出的中国哲学中的所谓“天理”或“人心”,而是诚如王夫之所言,“即身而道在”,它就平中见奇地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活生生的身体之中。
这种根于身体的哲学本体论,除了表现在中国古人对宇宙的终极性思考不是发端于对世界的“惊奇”而是始于对人自身人身处境的“忧患”之外,还集中地表现在其以一种“切己自返”和“返身而诚”的方式,把人自身的身体看作是宇宙真正的起点和本源。
在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古老的《易经》中,这种宇宙真正的起点和本源就是所谓的“太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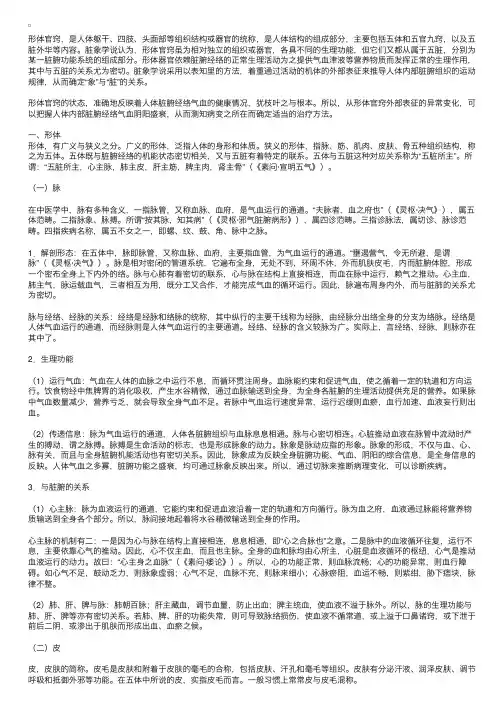
形体官窍,是⼈体躯⼲、四肢、头⾯部等组织结构或器官的统称,是⼈体结构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五体和五官九窍,以及五脏外华等内容。
脏象学说认为,形体官窍虽为相对独⽴的组织或器官,各具不同的⽣理功能,但它们⼜都从属于五脏,分别为某⼀脏腑功能系统的组成部分。
形体器官依赖脏腑经络的正常⽣理活动为之提供⽓⾎津液等营养物质⽽发挥正常的⽣理作⽤,其中与五脏的关系尤为密切。
脏象学说采⽤以表知⾥的⽅法,着重通过活动的机体的外部表征来推导⼈体内部脏腑组织的运动规律,从⽽确定“象”与“脏”的关系。
形体官窍的状态,准确地反映着⼈体脏腑经络⽓⾎的健康情况,犹枝叶之与根本。
所以,从形体官窍外部表征的异常变化,可以把握⼈体内部脏腑经络⽓⾎阴阳盛衰,从⽽测知病变之所在⽽确定适当的治疗⽅法。
⼀、形体形体,有⼴义与狭义之分。
⼴义的形体,泛指⼈体的⾝形和体质。
狭义的形体,指脉、筋、肌⾁、⽪肤、⾻五种组织结构,称之为五体。
五体既与脏腑经络的机能状态密切相关,⼜与五脏有着特定的联系。
五体与五脏这种对应关系称为“五脏所主”。
所谓:“五脏所主,⼼主脉,肺主⽪,肝主筋,脾主⾁,肾主⾻”(《素问·宣明五⽓》)。
(⼀)脉在中医学中,脉有多种含义,⼀指脉管,⼜称⾎脉、⾎府,是⽓⾎运⾏的通道。
“夫脉者,⾎之府也”(《灵枢·决⽓》),属五体范畴。
⼆指脉象、脉搏。
所谓“按其脉,知其病”(《灵枢·邪⽓脏腑病形》),属四诊范畴。
三指诊脉法,属切诊、脉诊范畴。
四指疾病名称,属五不⼥之⼀,即螺、纹、⿎、⾓、脉中之脉。
1.解剖形态:在五体中,脉即脉管,⼜称⾎脉、⾎府,主要指⾎管,为⽓⾎运⾏的通道。
“壅遏营⽓,令⽆所避,是谓脉”(《灵枢·决⽓》)。
脉是相对密闭的管道系统,它遍布全⾝,⽆处不到,环周不休,外⽽肌肤⽪⽑,内⽽脏腑体腔,形成⼀个密布全⾝上下内外的络。
脉与⼼肺有着密切的联系,⼼与脉在结构上直接相连,⽽⾎在脉中运⾏,赖⽓之推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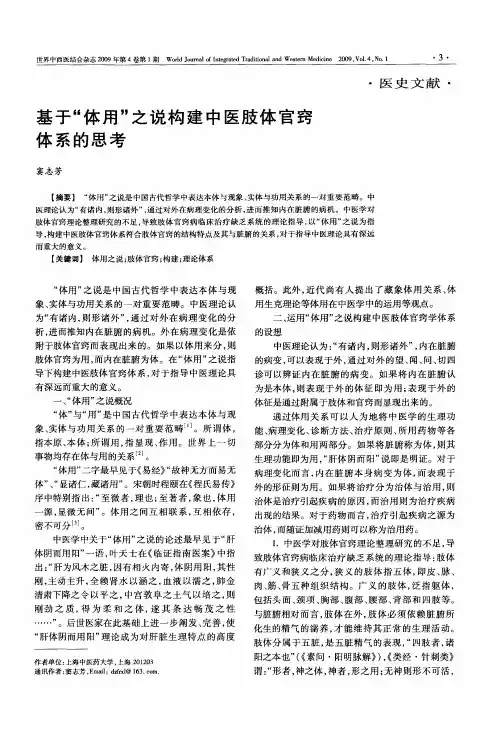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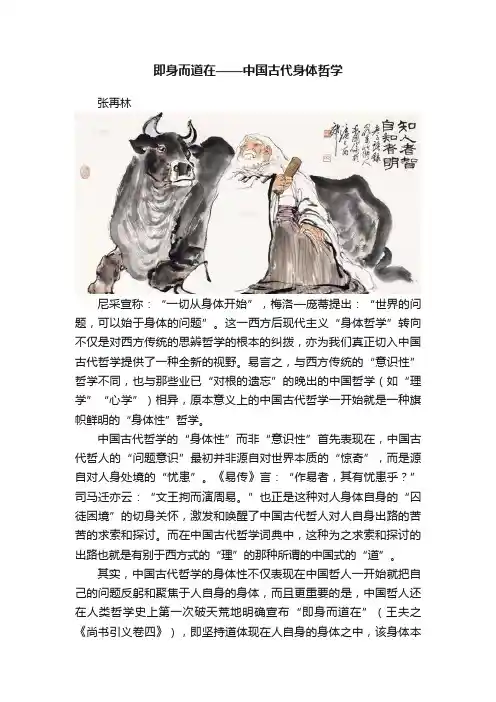
即身而道在——中国古代身体哲学张再林尼采宣称:“一切从身体开始”,梅洛—庞蒂提出:“世界的问题,可以始于身体的问题”。
这一西方后现代主义“身体哲学”转向不仅是对西方传统的思辨哲学的根本的纠拨,亦为我们真正切入中国古代哲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
易言之,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也与那些业已“对根的遗忘”的晚出的中国哲学(如“理学”“心学”)相异,原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旗帜鲜明的“身体性”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的“身体性”而非“意识性”首先表现在,中国古代哲人的“问题意识”最初并非源自对世界本质的“惊奇”,而是源自对人身处境的“忧患”。
《易传》言:“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司马迁亦云:“文王拘而演周易。
”也正是这种对人身体自身的“囚徒困境”的切身关怀,激发和唤醒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人自身出路的苦苦的求索和探讨。
而在中国古代哲学词典中,这种为之求索和探讨的出路也就是有别于西方式的“理”的那种所谓的中国式的“道”。
其实,中国古代哲学的身体性不仅表现在中国哲人一开始就把自己的问题反躬和聚焦于人自身的身体,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哲人还在人类哲学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明确宣布“即身而道在”(王夫之《尚书引义卷四》),即坚持道体现在人自身的身体之中,该身体本身就是道。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先从作为中国哲学的滥觞的古老的《易经》中的道的概念谈起。
在《易经》中,形上之道即其所谓的“太极”。
“太极”的“太”字为“大”字的引申义,故《广雅·释诂》称:“太,大也”。
而“大”字按许慎《说文》,其为象形字,即像直立的首、手、足皆具的人的身体形状。
这一字形无论是在中国古代的甲骨文还是在后来的铜器铭文中都得到了有力的印证。
因此,该词源学的考查表明,在中国古人心目中,形上之太极也即形下之人身。
而要理解这一“依形躯起念”、这一“下学可以上达”其中的吊诡,就不能不涉及中国古人对“身体”概念的独特理解,以及我们称之为的一种所谓的中国式的“身体现象学”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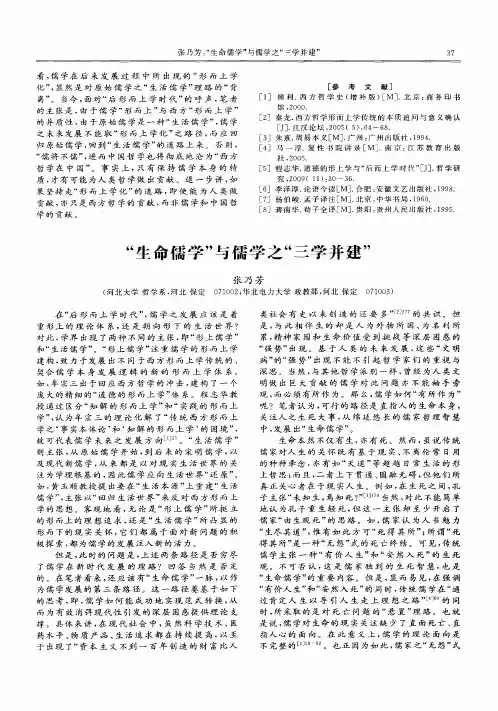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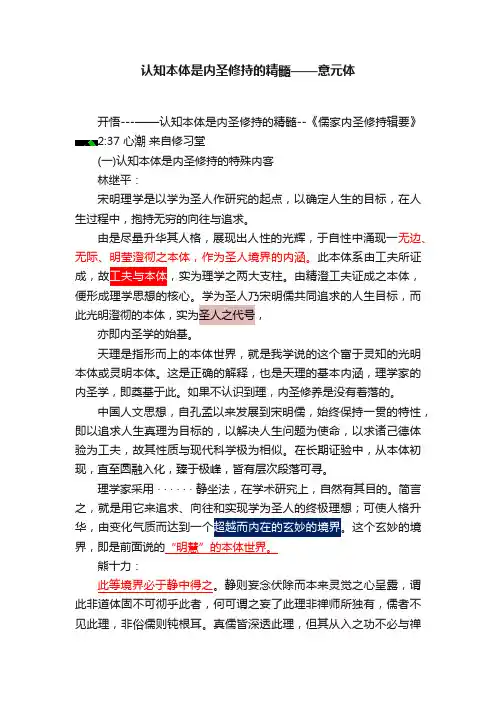
认知本体是内圣修持的精髓——意元体开悟---——认知本体是内圣修持的精髓--《儒家内圣修持辑要》2:37 心潮来自修习堂(一)认知本体是内圣修持的特殊内客林继平:宋明理学是以学为圣人作研究的起点,以确定人生的目标,在人生过程中,抱持无穷的向往与追求。
由是尽量升华其人格,展现出人性的光辉,于自性中涌现一无边、无际、明莹澄彻之本体,作为圣人境界的内涵。
此本体系由工夫所证成,故工夫与本体,实为理学之两大支柱。
由精澄工夫证成之本体,便形成理学思想的核心。
学为圣人乃宋明儒共同追求的人生目标,而此光明澄彻的本体,实为圣人之代号,亦即内圣学的始基。
天理是指形而上的本体世界,就是我学说的这个富于灵知的光明本体或灵明本体。
这是正确的解释,也是天理的基本内涵,理学家的内圣学,即奠基于此。
如果不认识到理,内圣修养是没有着落的。
中国人文思想,自孔孟以来发展到宋明儒,始终保持一贯的特性,即以追求人生真理为目标的,以解决人生问题为使命,以求诸己德体验为工夫,故其性质与现代科学极为相似。
在长期证验中,从本体初现,直至圆融入化,臻于极峰,皆有层次段落可寻。
理学家采用· · · · · · 静坐法,在学术研究上,自然有其目的。
简言之,就是用它来追求、向往和实现学为圣人的终极理想;可使人格升华,由变化气质而达到一个超越而内在的玄妙的境界。
这个玄妙的境界,即是前面说的“明慧”的本体世界。
熊十力:此等境界必于静中得之。
静则妄念伏除而本来灵觉之心呈露,谓此非道体固不可彻乎此者,何可谓之妄了此理非禅师所独有,儒者不见此理,非俗儒则钝根耳。
真儒皆深透此理,但其从入之功不必与禅师同,一旦彻悟心体,亦不以此为妙境,更须大有致力处。
虚静模式的生命活动变化虚静模式根本的要求是精神上的虚静,以此影响人体生命活动,为此首先需了解何谓静,静的层次以及各层次的表现。
(一)何谓静。
静是指练气功中的宁静的精神状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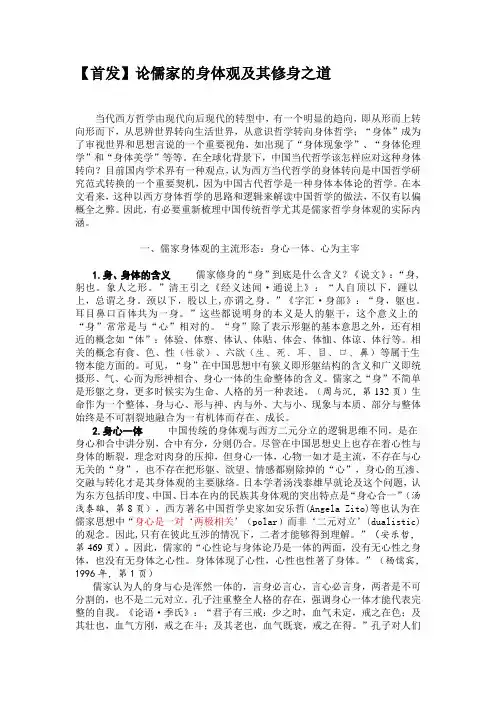
【首发】论儒家的身体观及其修身之道当代西方哲学由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型中,有一个明显的趋向,即从形而上转向形而下,从思辨世界转向生活世界,从意识哲学转向身体哲学;“身体”成为了审视世界和思想言说的一个重要视角,如出现了“身体现象学”、“身体伦理学”和“身体美学”等等。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当代哲学该怎样应对这种身体转向?目前国内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当代哲学的身体转向是中国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一个重要契机,因为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身体本体论的哲学。
在本文看来,这种以西方身体哲学的思路和逻辑来解读中国哲学的做法,不仅有以偏概全之弊。
因此,有必要重新梳理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身体观的实际内涵。
一、儒家身体观的主流形态:身心一体、心为主宰1.身、身体的含义儒家修身的“身”到底是什么含义?《说文》:“身,躬也。
象人之形。
”清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上》:“人自顶以下,踵以上,总谓之身。
颈以下,股以上,亦谓之身。
”《字汇·身部》:“身,躯也。
耳目鼻口百体共为一身。
”这些都说明身的本义是人的躯干,这个意义上的“身”常常是与“心”相对的。
“身”除了表示形躯的基本意思之外,还有相近的概念如“体”:体验、体察、体认、体贴、体会、体恤、体谅、体行等。
相关的概念有食、色、性(性欲)、六欲(生、死、耳、目、口、鼻)等属于生物本能方面的。
可见,“身”在中国思想中有狭义即形躯结构的含义和广义即统摄形、气、心而为形神相合、身心一体的生命整体的含义。
儒家之“身”不简单是形躯之身,更多时候实为生命、人格的另一种表述。
(周与沉,第132页)生命作为一个整体,身与心、形与神、内与外、大与小、现象与本质、部分与整体始终是不可割裂地融合为一有机体而存在、成长。
2.身心一体中国传统的身体观与西方二元分立的逻辑思维不同,是在身心和合中讲分别,合中有分,分则仍合。
尽管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存在着心性与身体的断裂,理念对肉身的压抑,但身心一体,心物一如才是主流,不存在与心无关的“身”,也不存在把形躯、欲望、情感都剔除掉的“心”,身心的互渗、交融与转化才是其身体观的主要脉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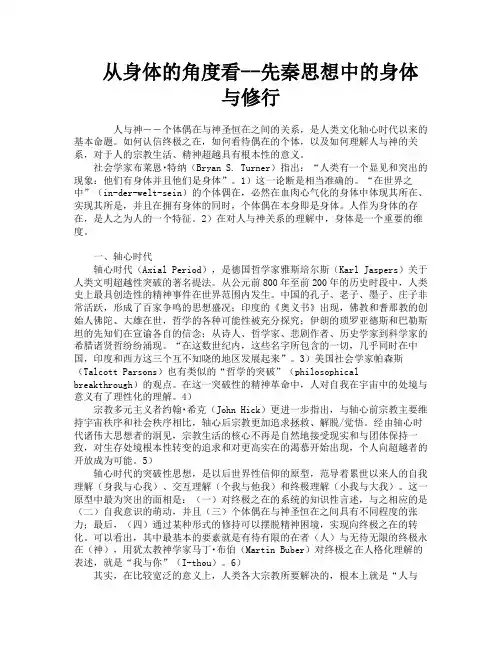
从身体的角度看--先秦思想中的身体与修行人与神――个体偶在与神圣恒在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文化轴心时代以来的基本命题。
如何认信终极之在,如何看待偶在的个体,以及如何理解人与神的关系,对于人的宗教生活、精神超越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Bryan S. Turner)指出:“人类有一个显见和突出的现象:他们有身体并且他们是身体”。
1)这一论断是相当准确的。
“在世界之中”(in-der-welt-sein)的个体偶在,必然在血肉心气化的身体中体现其所在、实现其所是,并且在拥有身体的同时,个体偶在本身即是身体。
人作为身体的存在,是人之为人的一个特征。
2)在对人与神关系的理解中,身体是一个重要的维度。
一、轴心时代轴心时代(Axial Period),是德国哲学家雅斯培尔斯(Karl Jaspers)关于人类文明超越性突破的著名提法。
从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的历史时段中,人类史上最具创造性的精神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发生。
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庄子非常活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印度的《奥义书》出现,佛教和耆那教的创始人佛陀、大雄在世,哲学的各种可能性被充分探究;伊朗的琐罗亚德斯和巴勒斯坦的先知们在宣谕各自的信念;从诗人、哲学家、悲剧作者、历史学家到科学家的希腊诸贤哲纷纷涌现。
“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
3)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也有类似的“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的观点。
在这一突破性的精神革命中,人对自我在宇宙中的处境与意义有了理性化的理解。
4)宗教多元主义者约翰・希克(John Hick)更进一步指出,与轴心前宗教主要维持宇宙秩序和社会秩序相比,轴心后宗教更加追求拯救、解脱/觉悟。
经由轴心时代诸伟大思想者的洞见,宗教生活的核心不再是自然地接受现实和与团体保持一致,对生存处境根本性转变的追求和对更高实在的渴慕开始出现,个人向超越者的开放成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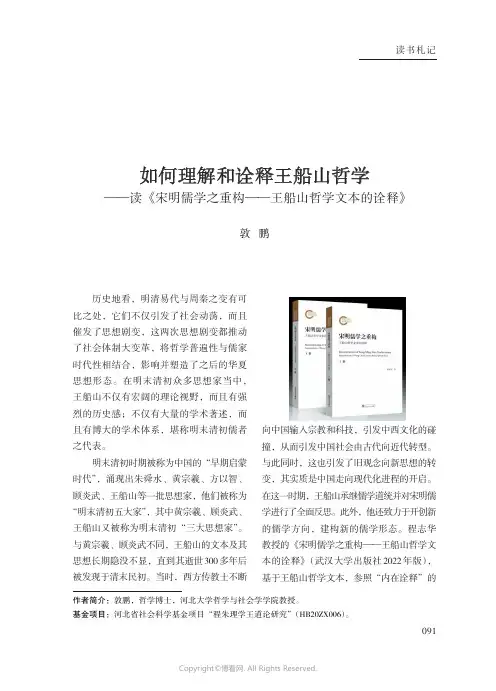
如何理解和诠释王船山哲学——读《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敦鹏历史地看,明清易代与周秦之变有可比之处,它们不仅引发了社会动荡,而且催发了思想剧变,这两次思想剧变都推动了社会体制大变革,将哲学普遍性与儒家时代性相结合,影响并塑造了之后的华夏思想形态。
在明末清初众多思想家当中,王船山不仅有宏阔的理论视野,而且有强烈的历史感;不仅有大量的学术著述,而且有博大的学术体系,堪称明末清初儒者之代表。
明末清初时期被称为中国的“早期启蒙时代”,涌现出朱舜水、黄宗羲、方以智、顾炎武、王船山等一批思想家,他们被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其中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又被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与黄宗羲、顾炎武不同,王船山的文本及其思想长期隐没不显,直到其逝世300多年后被发现于清末民初。
当时,西方传教士不断向中国输入宗教和科技,引发中西文化的碰撞,从而引发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
与此同时,这也引发了旧观念向新思想的转变,其实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的开启。
在这一时期,王船山承继儒学道统并对宋明儒学进行了全面反思。
此外,他还致力于开创新的儒学方向,建构新的儒学形态。
程志华教授的《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武汉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基于王船山哲学文本,参照“内在诠释”的作者简介:敦鹏,哲学博士,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程朱理学王道论研究”(HB20ZX006)。
091理路以及诠释之“道”“术”的策略技巧,对王船山哲学进行研究,提出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上学”“形上道德实践”三种形态,还将王船山与黄宗羲等同时代的儒者一起置于明末清初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对王船山哲学进行儒学史定位,为清代以后的儒学包括现代新儒学明确了基本方向。
一、为何要研究王船山哲学程志华教授研究王船山哲学,既有历史条件,也有逻辑原因。
就历史的条件讲,其1997年的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均是关于黄宗羲的选题,后来还出版了《困境与转型——黄宗羲哲学文本的一种解读》①。
儒家“身体”正名摘要:“身体”内涵的含混不清,是儒家身体观在当前颇受争议的关键原因之一。
从字源义的角度分析,“身”与“体”都与身体密切相关,但是二者都不能等同于现代汉语意义上的身体,而且二者在内涵上也存在着很大差异。
这决定了对儒家“身体”概念的界定,必须结合思想的角度来分析。
从儒家经典文本来看,当他们提到“身体”时,想到或意指的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这个生理意义上的肉体,而是与其他各事物密不可分,关联着体验、践履、身体力行等涵义,从而使其思想呈现出重视“身体性”的特点。
关键词:身;体;身体;身体性当前,关于儒家身体观的研究颇受争议,造成这种争议的关键原因之一就在于,对“身体”,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身”与“体”到底为何语焉不详。
由于作为合成词的“身体”一词在先秦儒家文献中尚未出现,且儒家思想中所言之“身”与“体”含义宽泛,不能等同于西方意义上的“Body”(部分学者所言之“身体”)或“Flesh”(部分学者所言之“肉体”);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一直存在两个不同的向度:一是,从当前约定俗成的“身体”观念或是西方哲学所界定的“身体”观念出发,从儒家文献中找出相关内容来加以论述;二是,不拘泥于当前约定俗成的“身体”界定,找出儒家传统文献中关于“身”和“体”的相关言论,结合儒家的核心观念,对儒家关于“身”和“体”的思想加以系统论述。
相比较而言,笔者更为认同后一向度,因为前者无法避免把西方的问题范式套用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嫌疑,更有甚者,走到西方体质人类学或是医学的视角。
名不正,则言不顺;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对儒家“身体”正名的深入研究。
要想正确理解儒家的身体观,必须先为“身体”正名。
作为合成词的“身体”一词在先秦儒家文献中还没有出现,当前可以见到的“身”、“体”连称,最早是在《孝经·开明宗义章》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然而“身体发肤”在此指的是子女的肉体以及其一切附生之物,“身体”在此并非合成词“身体”,“身”与“体”在此是相对应而分别独立的二者。
2021年第2期 现代大学教育 经典重读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一般项目“生成论教学哲学的深化发展研究”,项目编号:GD18CJY03。
收稿日期:2020-09-27作者简介:王韶芳(1985—),女,山西吕梁人,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后,从事教学哲学、教师教育研究;天津,300387。
张广君(1962—),男,内蒙古科左后旗人,教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学哲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广州,510631。
Email:zgj101@126 com。
《学记》教学观的身体之维王韶芳 张广君摘 要:身体是先秦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学记》包含仪式语境中的身体实践和治学语境中的身体实践。
从身体的维度进行审视,可以发现,《学记》蕴含以身心互渗为基础的自我实践观、以身身互动为基础的教学交往观和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生命时间观。
教学是历时性的身体出场,身体的动态生成性影响教学交往的具体样态和实施方式。
只有师生身体在时空场域中共同在场,才能形成完整的身体关系链条。
教学本质上是生命的综合体验,意味着师生身心一体的整体生成,它是具有“体知”特征的实践智慧。
关键词:《学记》;先秦儒家;身体符号;身体教学观;时代意蕴;身心一如;体知;实践智慧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21)02-0031-08 维特根斯坦(LudwigJosefJohannWittgenstein)曾说:“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图画。
”[1]然而,在两希(希腊和希伯来)文明的发展史中,身体与精神始终存在紧张的对峙。
身体曾被认为是第二自我,[2]成为首要被规训和控制的对象,也成为欲望、冲动、感性、直觉、物质的代名词,妨碍知识的出场,被柏拉图以降的哲学家们以形而上的致思路径贬低和排斥。
由笛卡尔(RenéDescartes)的“我想,所以我是”[3]开启的意识哲学逐渐加剧身心二元的矛盾和分化,身体因其有限性被禁锢在理性主义的牢笼里,反复受到道德和知识的诘难。
儒家身体观
儒家身体观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认为身体是一个神圣的本体,尊重和珍惜自己的身体是一种伦理行为。
首先,儒家身体观要求对自己的身体要有正确的观念,男女应爱护自己的身体,使其保持健康。
他们认为,身体是一个神圣的器官,必须遵守“法”,当接受关系时要尊重自己的身体,而不是忽视自己的身体。
其次,儒家身体观支持自然,保护自然。
他们认为,在整个自然界,只有接受自然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因此他们强调要受到“大道”的支配,坚持节俭节奏,循序渐进,勿将急躁、争夺当一件大事,以及“用之不竭”。
最后,儒家身体观支持维护平衡,不祭祀神,但崇尚自然。
他们强调要坚持和谐平衡、安谧自然,强调不能依赖神祈祷、大肆修建寺庙,要追求自然、害怕异端和怪异事物。
总而言之,儒家身体观认为身体是一个神圣的本体,尊重自己的身体,保护自然,维护自然平衡,而不是仅仅遵循社会规范。
身体是最宝贵的礼物,我们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断学习和磨练,实现身体的力量。
从“身体门户”到“天地门户”作者:杨滢桐来源:《西部学刊》2022年第19期摘要:“窍”是《管子》中的重要哲学范畴,它属于身体,也与天地深度交流。
“窍”包括“九窍”与“五官”,以“虚”为根本特征,以“理”为原则,在心的带领下发挥作用,使人达到“知远之证(征)”的境界。
通过“窍”,人体建立了基于气的与外界的循环沟通系统,故“窍”是身体向世界打开的门户。
“窍”也与先民自我意识萌芽相关,且通过具象比喻和类比等方式成为“象”,参与天人感应系统的塑造,成为天、地、人沟通的门户与桥梁。
关键词:窍;九窍;五官;《管子》;天人感应中图分类号:B2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19-0092-04先秦身体观的研究者多将身体视为整体,考察它与天道等其他概念的互动关系,又有考察身体下属的概念的研究(其中尤以“心”与“血气”最为突出),对“窍”的研究属于对形躯之身的考察。
在记录我国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言行事迹的先秦学术文化典籍《管子》中,“九窍”与“五官”的所指有所重合且关系密切,同归于“窍”。
陈立胜认为阴阳五行理论兴起后,身体之“窍”与天地万物之“窍”之间的同构关系得到彰显[1]。
《管子》是记载阴阳与五行两学说合流过程的文本[2],“窍”与这两个学说有密切联系,故有必要以《管子》为主要文本,结合《管子》整体的思想对“窍”做细致考察。
一、《管子》之“窍”义简疏窍,空也,有孔、穴、空和通道之义,故可指人身上的孔穴,一般以“九窍”指示。
(一)窍是身体的门户窍与“气”这一《管子》思想的核心概念紧密联系。
气是道借以生成万物的衍生体,道进入万物就必须借助于气这个由其产生、具有弥漫性,非有非无即有即无的介质来加以实现[3]。
气是生成万物的介质,一切事物都由它生成。
“五内已具,而后发为九窍。
脾发为鼻,肝发为目,肾发为耳,肺发为窍。
”[4]659肉体由形气形成,又可生出精神:“生而目视,耳听,心虑。
[键入文字]
宋明儒学中的身体本体论建构
在承继前人五脏开窍于目、开窍于耳、开窍于口、开窍于鼻、开窍于二阴这一思想基础上,理学家一方面深刻挖掘出身体之窍的本体论向度,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宋明儒学中的身体本体论建构。
提出一个完整的天地之心的发窍路线天地之心发窍于人心( 良知/ 灵知/ 虚灵/ 灵窍)-人心(通过五脏六腑)发窍于耳目口鼻四肢这一连续性的发窍结构,并借助于汉儒身体之窍与天地万物之窍之间的同构关系思想揭示出天地之心-人心(灵窍)-七窍一体结构的时间性( 七窍、灵窍律动与天地万物律动的同步性),另一方面,呈现出丰富的七窍与心窍修身经验,这些经验极大丰富了孔孟四勿与践形功夫。
儒家强调身体之窍、心窍的虚、无性格,与萨特所代表的意识现象学有着本质的区别。
儒家通身是窍的理念折射出儒家的主体性乃是扎根于生生不已、大化流行之中与他者、天地万物相互感应、相互应答的身心一如的存在,这种主体性本身就嵌在身体之中,无论是惕然动乎中,赧然见乎色之耻感,抑或是恻然动乎中之不忍、悯恤、顾惜之同感,乃至生意津津之一体生命的生机畅遂感、乐感,皆是深深嵌入身体之中觉情与实感。
1。
身体之为“窍”:宋明儒学中的身体本体论建构(一)内容摘要:在先秦儒学与医学之中,身体之“窍”(七窍/九窍)被视为“精神”的“孔窍”、“门户”与“通道”,它们内根于“五脏”,外联于天地之气。
保持“孔窍”的通畅,无论对“卫生”,抑或对“修身”均意味重要。
其中,耳、目、口三窍尤为儒家修身所注重。
阴阳五行理论兴起后,身体之“窍”与天地万物之“窍”之间的同构关系得到彰显。
在承继前人五脏“开窍于目”、“开窍于耳”、“开窍于口”、“开窍于鼻”、“开窍于二阴”这一思想基础上,理学家一方面深刻挖掘出身体之窍的本体论向度,提出一个完整的“天地之心”的发窍路线图:“天地之心”发窍于人心(“良知”/“灵知”/“虚灵”/“灵窍”)-人心(通过五脏六腑)发窍于耳目口鼻四肢这一连续性的发窍结构,并借助于汉儒身体之“窍”与天地万物之“窍”之间的同构关系思想揭示出天地之心-人心(灵窍)-七窍一体结构的时间性(“七窍”、“灵窍”律动与天地万物律动的同步性),另一方面,呈现出丰富的“七窍”与“心窍”修身经验,这些经验极大丰富了孔孟“四勿”与“践形”功夫。
儒家强调身体之窍、心窍的“虚”、“无”性格,与萨特所代表的意识现象学有着本质的区别。
儒家“通身是窍”的理念折射出儒家的“主体性”乃是扎根于生生不已、大化流行之中与他者、天地万物相互感应、相互应答的身心一如的存在,这种主体性本身就嵌在身体之中,无论是“惕然动乎中,赧然见乎色”之耻感,抑或是“恻然动乎中”之“不忍”、“悯恤”、“顾惜”之同感,乃至生意津津之一体生命的生机畅遂感、乐感,皆是深深嵌入身体之中“觉情”与“实感”。
儒家身体的这种本体论向度,不仅迥异于HansJonas所批评的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精神气质,而且为克服这种虚无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理论资源。
关键词:七窍;心窍;身体;宋明儒学;虚无主义一以“窍”指涉身体的外部器官,在先秦早已流行。
《庄子》中就有“人皆有七窍”(《应帝王》)、“百骸九窍六脏”(《齐物论》)、“九窍”(《达生》、《知北游》)等说法。
七窍者,耳二、目二、鼻孔二、口一,此为“阳窍”;九窍者,阳窍七与阴窍二(尿道、肛门)。
“九窍”与四肢一起构成了身体轮廓:“人之身三百六十节,四肢、九窍,其大具也。
”(《韩非子·解老》)窍,空也,穴也(《说文》)。
“窍”实即“窍门”、“孔窍”、“空窍”、“通道”(《管子·君臣》“四肢六道,身之体也”,直接将上四窍、下二窍称为“六道”)。
那么,它又是谁的“门户”、作为“通道”又通向何处呢?夫孔窍者,精神之户牖;血气者,五藏之使候。
(《文子·九守》)空窍者,神明之户牖也。
(《韩非子·喻老》)夫孔窍者,精神之户牖也;而气志者,五藏之使候也。
(《淮南子·精神训》)身体之“窍”成了精神、神明往来活动的渠道。
在传统中医观念里面,身体之脏腑乃是人之精神、神明之藏所,五脏亦被称为“五藏”,又谓“五神藏”。
人之心理感受与思虑均离不开此生理载体: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精志也。
《灵枢·九针论》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
(《灵枢·本藏》)五脏内部的“精神”活动通过身体之窍而反映在身体的表层:“五藏气争,九窍不通。
”(《素问·生气通天论》)“五藏不和,则七窍不通。
”(《灵枢·脉度》)当代东西身体论说均不约而同将身体划分为双重结构:表层的身体(运动器官,如四肢)和深层的身体(内器官,如肺、心、肝、胃和肠),这种划分的理论基础是,人可通过意念控制表层身体,如活动手和脚,但无法自由地控制内器官。
1]代谢活动、呼吸、内分泌、睡眠、出生、死亡等等深层身体的活动,属于隐性身体(therecessivebody)活动的领域,处于“隐性”(recessive)状态下,隐退于意识之下的“不可体验的深度”之中,它不再是现象学家津津乐道的“我能够”(Ican)的领域,这些领域的活动基本上是属于“它能够”(itcan),或者说是“我必须”(Imust)的领域。
2]传统的中医理论则着力强调这两种身体之间并没有绝然的区隔,深度的身体(五脏)通过“经络”而与表层身体相贯通(所谓“外络于肢节”):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精阳气上走于目而为精,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其宗气上出于鼻而为臭,其浊气出于胃,走唇舌而为味。
(《灵枢·邪气藏腑病形》)“五脏开窍五官”成为古代中国人对身体的普遍看法:五藏常内阅于上七窍也。
故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灵枢·脉度》)鼻之能知香臭、舌之能知无味、目之能辨五色、口之能知五谷、耳之能闻五音,均是五脏之“气”通达之结果。
五脏通过目、耳、口、鼻、二阴而开显出的功能,被分别称为“开窍于目”、“开窍于耳”、“开窍于口”、“开窍于鼻”、“开窍于二阴”(《素问·金匮真言论》)。
身体之窍作为“通道”,一端联系着身体内部的五脏,另一端则直接与天地之气相通。
这种观念在《内经》中已有系统的表述与阐发: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
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
五味入口,藏于肠胃,胃有所藏,以养五气。
气和而生,津液相生,神乃自生。
《素问·六节藏象论》黄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
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
(《素问·生气通天论》)这里面无疑已经具有强烈的“人副天数”的思想。
这一点承时贤抉发幽微,其中所含天人一贯、身心一如之义蕴已昭然若揭。
3]阴阳五行理论大盛于汉,举凡人之性情、仁义礼智信之价值与阴阳二气、金木水火土五行均与五脏六腑搭配在一起,身体之“窍”与天地万物之“窍”之间的同构关系更加显豁:性情者,何谓也?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
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
情者,静也,性者,生也。
此人所禀六气以生者也……五性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
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着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
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也。
六情者,何谓也?喜、怒、哀、乐、爱、恶谓六情,所以扶成五性。
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含六律五行之气而生,故内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五藏者,何也?谓肝、心、肺、肾、脾也。
肝之为言干也;肺之为言费也,情动得序;心之为言任也,任于恩也;肾之为言写也,以窍写也;脾之为言辨也,所以积精禀气也。
五藏,肝仁,肺义,心礼,肾智,脾信也。
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
东方者阳也,万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叶。
目为之候何?目能出泪而不能内物,木亦能出枝叶不能有所内也。
肺所以义者何?肺者,金之精;义者,断决,西方亦金,杀成万物也。
故肺象金,色白也。
鼻为之候何?鼻出入气,高而有窍,山亦有金石累积,亦有孔穴,出云布雨以润天下,雨则云消,鼻能出纳气也。
心所以为礼何?心,火之精也。
南方尊阳在上,卑阴在下,礼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锐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锐也。
耳为之候何?耳能遍内外,别音语,火照有似于礼,上下分明。
肾所以智何?肾者,水之精,智者,进止无所疑惑。
水亦进而不惑,北方水,故肾色黑;水阴,故肾双窍。
为之候何?窍能泻水,亦能流濡。
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
土尚任养,万物为之象,生物无所私,信之至也。
故脾象土,色黄也。
口为之候何?口能啖尝,舌能知味,亦能出音声,吐滋液。
(《白虎通·性情》)4]由于身体之窍内根于精神之藏所(五脏),外通于天地阴阳之气,故保持“孔窍”的通畅,无论对“卫生”,抑或对“修身”均意味重要。
五脏不和、精神淤滞固然会让九窍不通,反之,孔窍“虚”、“通”,精神亦会畅适,天地“和气”也会与五脏形成良性的互动:“孔窍虚,则和气日入。
”(《韩非子》解老)韩非子的这种观念大致反映了当时儒、道、法三家共同的看法。
5]因此,如何保任身体之窍,让天地和气日入,让邪气不侵,让精神凝聚,便成了医家与思想家共同关心的话题。
当然,善于“养精蓄锐”的道家,自然对“精神”的门户(九窍/七窍)最为警醒,庄子混沌的寓言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心态: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
倏与忽时相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
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庄子·应帝王》)庄子的这种观念后来直接引发了道家“闭九窍”的设想:闭九窍,藏志意,弃聪明,反无识,芒然仿佯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际,含阴吐阳而与万物同和者,德也……(《文子·精诚》),另参《淮南子·俶真训》)耳目口三宝,闭塞勿发扬。
(《周易参同契》)身体诸“窍”中,耳、目、口三窍尤被看重:“耳、目、口,道家谓之三要,以其为精、气、神之门户也。
”(王樵:《尚书日记·周书》)而“目”则是三者之中的翘楚,这一点无论是治身的医家抑或修身的思想家都曾特别点出。
“夫心者五藏之专精也,目者其窍也。
华色者其荣也。
是以人有德也,则气和于目,有亡忧知于色。
”(《素问·解精微论》)“目”指眼睛,“色”指脸色,“目”与“色”反映着人之内心世界。
《论语·泰伯》中“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乡党》中孔子之“逞颜色”,以及君子“九思”中“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大致都属于《礼记·玉藻》中说的“君子之容”的范畴(“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
其要都是围绕着身体之窍下功夫。
至于在孔子津津乐道的“四勿”工夫中,亦是以目窍为先。
这一点朱熹在释《阴符经》(“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
”)曾专门拈出加以发挥:“心因物而见,是生于物也;逐物而丧,是死于物也。
人之接于物者,其窍有九,而要有三。
而目又要中之要者也。
老聃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
孔子答克己之目,亦以视为之先。
西方论六根、六识必先曰眼、曰色者,均是意也。
”6]在孟子著名的“以羊易牛”话头中,“怵惕恻隐之心”也是通过“见”与“闻”目耳二窍活动表达的:“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笔者曾将此称为“形的良知”。
7]倘若说医家讲身体之“窍”乃旨在由此观察脏腑内部的“精神”状况,那么,儒家更多注重的是个体修身过程之中“诚于中而形于外”的身心一如的特质。
“七窍”与“颜色”作为内心世界的表达,与单纯言辞的表达不同,它无法遮掩、伪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