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军女性文学的温度:论映川
- 格式:doc
- 大小:34.50 KB
- 文档页数: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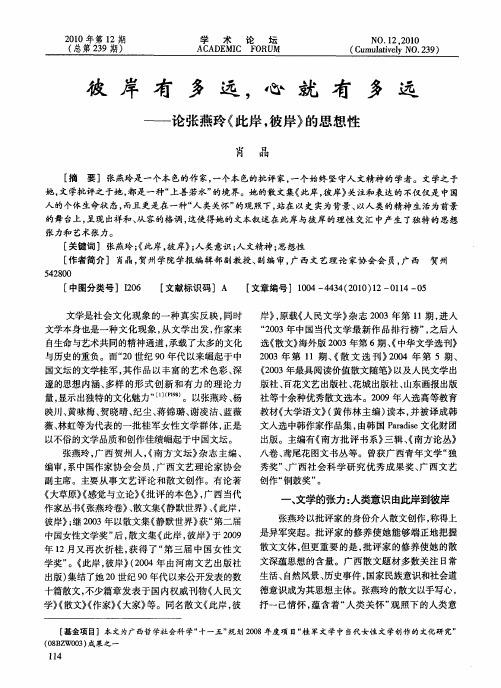


乡村到城市的历史更迭:文学桂军生态传递的家园情结摘要:土改背景下的生存生态到商品背景下的精神生态的存在意义上的更迭,显现出文学桂军两代人对于社会现实与广西乡民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思考。
20世纪50年代生存生态的交接姿态和历史质素,左右了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价值,改革开放后的壮乡乡民生存生态,又不得不置于商品化、全球化的精神生态圈层中加以考量。
文章以文学桂军两代壮族作家陆地与杨映川的两部作品为例,在历史的更迭考量下以对话与悬搁之姿态重述二人生态美学意义上的耦合调性,土改零余者与石城小怪人对现实的类型化声讨,为其创作的家园复归倾向“续航”,并最终指向其诗化家园的双重情结旨归,即回归纯粹本我的生态性诉求。
关键词:生存生态;精神生态;文学桂军;家园情结;历史更迭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438(2024)02-0074-04(1.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2.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南宁530000)文学桂军作家群体在文本创作中显现出历史的承续之关联,而作为壮族作家的陆地和杨映川,在创作承续关系外,显现出对于生态美学意义上人的存在状态的关注。
20世纪50年代生存生态的交接姿态和历史质素,左右了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价值,《美丽的南方》作为表现新中国土改运动风云的文学桂军第一部长篇小说,其地域和民族意义之外的生态美学表征,值得置放在当代眼光下加以注视。
一、“孤立”对话:土改零余者与石城小怪人土改小说在20世纪50年代并非新鲜之作,而陆地着重取写土改历史之初衷,恐怕更多的是一种对于和谐生态的追寻和人的成长意义的重视。
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小说文本,实际上是一种时间上的书写,即以时代背景为刻画,以宏大和主旋律为意味铺陈。
而改革开放后的小说创作,一方面立足于经济社会的结构价值嬗变,一方面取材于与以往生活大相径庭的新新人类生存生态,两种新中国历史的社会现实,在《美丽的南方》和《蓝百阳的石头城》中以耦合的方式呈现。

南方文坛2009I_现象解读q广西“70后"女性小说家话语方式探究罗小凤声—一一代人都要面对自己的“年代语境”,“70后”:l51.(即指70年代出生入)一代女性小说家无法不ot≥卜面对当下文学界对这一代的总体话语倾向。
棉棉、卫慧等女性小说家对于青春、爱情和生活的游戏姿态已让“70后”罩上轻飘和浮躁的标签,然而,广西的“70后”女性小说家以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穿越了年代语境给她们的定位,映川、纪尘、锦璐、凌洁、蓝薇薇、杨丽达、冷月、黄芳、紫音、梁志玲、刘永娟等以执著于自己理想世界的童话书写,深刻解剖的人性思考,充满人性关怀的底层关注,展现拯救男性和女性自我拯救、叙述女性苦难史的女性意识写作等话语方式,构筑了广西继林白之后又一道亮丽的小说风景线。
寓言般的童话书写映川一直痴心于书写童话世界的建造与破灭,充满了“寓言”色彩,正如陈晓明先生认为的:“从总体上来说,杨映川的小说一直在讲述一种女性的童话故事,这些故事明显带有女性幻想的特征,带有强烈的超越现实的愿望。
”①映川在《爱情侏罗纪》中所提供的背景“侏罗纪”距今约2.08—1.44亿年,属于地质学上中生代的第二纪,为小婵这个对现实的爱情视而不见,却寻求虚无缥缈之爱的女主人公形象的出场塑造了一个充满虚幻色彩和童话意境的遥远背景;《做只鸟吧》通过果果和树子营造的女性童话世界,宣告了女性“做只鸟吧”这个唯美、纯净的女性童话宣言;《只爱陌生人》中的白兰心拒绝身边谢远的爱情,却迷恋一个远在另一座城市里已被学校开除的研究生秦山,白兰心对秦山一无所知,只是一种沉浸于想象中的痴恋。
远离现实世界,远离世俗纷扰,充满了童话般的浪漫情调……映川的爱情故事无不建构于虚幻的童话世界里,这些童话世界终将破灭,因而映川的小说充满了寓言色彩。
映川不仅在塑造爱情故事时如此,在构造生活故事时亦是如此,如《我困了,我醒了》中塑造了一个充满人类温情的童话世界,每次遇到困难就睡觉的张钉生活在父亲、母亲和女友的温情中,最后心灵终于被这种温情唤醒了,这是映川小说下童话世界的初次胜利,彰显了映川小说中渴望逃避纷扰的现实世界,回到内心,回到纯真的童年记忆的写作理想。

从追寻纯粹到回归庸常)))论杨映川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覃春琼u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B 类项目(编号:06FZ W009)/广西-70后.女性小说家的女性话语方式研究0;梧州学院院级科研课题/杨映川与黄咏梅的比较研究0(编号:2009C034)的阶段性成果。
21世纪,女性写作尤为彰显,众语喧哗,女性文学作品频获丰收。
而在广西文坛上,批评家张燕玲欣喜地指出:/玫瑰花开了,杨映川、黄咏梅、贺晓晴等有潜力的-70后.年轻女作家群以不俗的文学品质和创作佳绩崛起。
0[1]尤其是杨映川,更是成为近年来/中国文坛盛开的一支奇葩0,广受瞩目。
随着5爱情侏罗纪65做只鸟吧65逃跑的鞋子65易容术65女的江湖65不能掉头6等佳作的陆续问世,杨映川用小说构筑了广西继林白之后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她以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独特的女性话语方式,展现了现代都市女性在社会中的生存境遇和情感创伤,塑造了一批血肉丰满并富有深度的新女性形象,显示出自己对女性命运的深度关切和人文关怀。
一、追寻/纯粹之爱0评论家陈晓明指出,从总体上说,杨映川的小说大都涉及都市女性的爱情故事,在爱情的战争中,男性的主导地位遭到挑战,女性则在寻找/纯粹0与/独立0中不断完善自我,她们面对情感日渐坚强执著,心灵也更趋成熟和完善,人性自然而然得以升华。
[2]的确,女主人公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不停息地追寻/纯粹之爱0是杨映川小说反复出现的重要主题。
杨映川笔下的女主角,尽管处于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中,但却从来没有放弃对人生理想的追求,没有放弃对诗性生活的渴望,也从来没有放弃对真爱的寻找,甚至为了追寻/纯粹之爱0不惜冒险受伤。
这从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了映川的感情理想和她对理想精神世界的坚守。
5爱情侏罗纪6中,骄傲美丽的小婵,感情经历可谓丰富多彩,从十二岁开始,就收到了各种缠绵悱恻的情书,至今呆在纸箱里的情书至少有几百封,还不算烧掉和退稿的。
前前后后大大小小谈了十几次恋爱的小婵,感情已经麻木,甚至在面对前男友威胁自杀时都可以无动于衷地建议:/你想死就去死吧,最好选择上吊。

80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杨映川小说《淑女学堂》中的女性形象分析黎芷伶( 河池学院,广西 宜州 546300 )【摘 要】杨映川小说《淑女学堂》中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们与男性斗智斗勇,与命运进行抗争,留下了“要像个男人一样去奋斗“的信念和决心。
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去分析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发现,她们仍是处在文化弱势和性别弱势的双重包围中。
要恢复女性主体的文化自觉和性别自觉,必须要打破“中心——边缘”“以及“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结构,从而真正做到女性的解放。
【关键词】《淑女学堂》;女性形象;生态女性主义杨映川在广西当代文坛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她塑造了诸多的女性人物,如果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去审视她的新作品《淑女学堂》,将会发现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开始了“进化”“演变”,充满着生态女性主义的观念。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致力于颠覆男权文化的根基,恢复并发扬母性文化传统,倡导文化的多元性,促进文化生态的和谐发展。
而这些观点为分析《淑女学堂》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一、抗争与突围:迷失的女性作品中的主人公宋紫童美丽、聪明、野心勃勃、心肠坚硬似铁、争强好胜,是一个“矛盾综合体”。
在她身上,体现出了女性在这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与男性的博弈和抗争。
在与丘麦良的博弈中,她凭借“真实的自我”赢得了丘麦良的爱情,其中她做了“最真实的自己”,“她想要什么,他希望她明明白白地告诉他。
”她曾经喜欢过丘麦良,但这种喜欢仍然比不上她的野心勃勃和嫌贫爱富。
凭借着丘麦良的金钱,宋紫童打入了南安市富人的圈子。
而在丘麦良投资失败后,宋紫童转而投入了苏璜的怀抱。
在两性的博弈中,女性战胜了男性。
在与苏璜的“爱情”较量中,宋紫童的地位处在弱势。
最初,他们包裹着“爱情”的外衣,实际上是包养与被包养的关系。
苏璜“精致、品味、成熟”,这类男人被称之为“水晶男”,为抓住这样的男人,宋紫童将自己放在了更为低下的位置,因为“如果真想得到这样一位水晶男,只有不断付出,说白了只有迁就,做他喜欢的那类女人。
《【论文学桂军崛起之激励机制】桂军小说》摘要:另一方面,《广西文学》、《红豆》、《南方文坛》等文学期刊及时发表、推介广西青年作家的新作品,也为文学桂军的“边缘崛起”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文坛“广西三剑客”东西、鬼子、李冯先后与陈凯歌、张艺谋等导演合作,创作出《天上的恋人》《幸福时光》《英雄》等影视作品,蜚声海内外,作为省级文学期刊,《广西文学》多年来一直坚持着发现、关怀、鼓励本土作家,为推介广西本土作家做了不少工作,是广西本土小说家的成长摇篮远离中心的广西,20世纪末至2l世纪初,一直在展现文学的先锋品格。
一批年轻作家所创作的作品,经常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话题。
广西文学之所以能取得丰硕的成果,与广西文艺界整体的自觉有着直接的关系。
早在1988年前后,广西文学界就对自己创作力量的薄弱开始了深刻的反思。
在焦虑与危机意识、责任感与担当意识交织中,文艺界对广西文学机制进行了初步调整,新作家得到大力发掘与扶持。
另一方面,《广西文学》、《红豆》、《南方文坛》等文学期刊及时发表、推介广西青年作家的新作品,也为文学桂军的“边缘崛起”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本文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广西文学机制的调整与文学期刊的变革两大方面探讨文学桂军崛起的激励机制。
一、90年代以来广西文学机制的调整与完善应该说,广西文学桂军的崛起不仅与广西文学界作家们的辛勤开拓相关,而且与90年代以来广西文学机制的不断调整与完善紧密相关。
1988年,为繁荣广西文艺事业,自治区人民政府设立了“振兴广西文艺铜鼓奖”,以鼓励作家艺术家、文化学者多出优秀作品,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广西文艺发展还是跟不上全国的形势,与文化先进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特别是广西的文艺队伍,长期处于一种各自为战的状态,缺乏交流和学习,许多人思想观念陈旧,缺少开拓创新意识,缺乏冲击全国文坛的信心。
1995年8月,为寻求广西文学发展的突破口,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与广西作家协会在南宁召开“广西文学创作题材规划会”。
桂军女性文学的温度:论映川摘要:21世纪的广西文坛,涌现了以映川、黄咏梅、贺晓晴、纪尘、蒋锦璐、凌洁、蓝薇薇、林虹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女作家,她们以不俗的文学品质和创作佳绩崛起于中国文坛。
而映川更是以《女的江湖》、《不能掉头》、《我困了,我醒了》、《我记仇》、《魔术师》等十几部中短长篇小说文学实践奠定了她在广西文坛“70后”桂军领头羊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映川;桂军女性文学;文学姿态;精神价值;审美向度“文学应该有能力温暖这个世界”,这是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说的;巴金先生也说过:“文学能给人光热和希望,能让人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
”进入21世纪,女性写作更为彰显,女性文学作品大量涌现。
而在广西文坛上,则涌现了以映川、黄咏梅、贺晓晴、纪尘、蒋锦璐、凌洁、蓝薇薇、林虹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女作家,她们以不俗的文学品质和创作佳绩崛起。
“以自己出类拔萃的创作改变了广西文学女作家稀少的格局,以个性化的女性写作丰富了中国的女性文学。
”[1]尤其是映川,更是成为“中国文坛一个亮点”而引人注目。
她以女性生存主题及地域文化色彩延续了其以人为本的审美立场和写实风格,她是继林白之后,又一个对当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有所贡献的文学桂军女作家,因而为新世纪桂军文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因此,2004年,映川获得第六届广西青年文学最高奖——“独秀奖”,入选200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同年,中篇小说《不能掉头》获“人民文学奖”。
2006年,获得第五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
一纪实的文学立场:映川的文学姿态映川自2000年在《上海文学》发表处女作《爱情侏罗纪》开始,就不断有力作问世。
她发表了《做只鸟吧》、《逃跑的鞋子》、《只爱陌生人》、《女的江湖》、《不能掉头》、《我困了,我醒了》、《我记仇》、《魔术师》等十几部中短长篇,这不仅奠定了她在广西文坛“70后”桂军领头羊的重要地位,而且使她在全国文坛也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映川的小说表现的都是很温暖的人生。
她站在女性主义的视角,以纪实的文学姿态,在小说文本中反映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境遇和情感创伤。
她直面现实的创作显示了一种基于价值判断又植根于思维的文学品质,有着一种从容的张力。
世纪之交的文坛上,映川的写作与张炜等男性作家一样,在文本的叙事中同样热切关注人类生存的形而上层面,他们从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形而上的生命体验,给人的感觉更多地缘自生命此岸的感受,缘自个人具体的、琐碎的日常生活,并试图尝试着在人本理想和社会的审美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文本叙事中,映川颠覆了男人为女人制定的原则。
而女人们,都向往那种能融合心灵、思想和肉体的爱情。
于是突围和奔逃成了陷落于现实生活中男女演绎的主题,对男权社会双重道德标准进行了有力的冲击,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方式构建了男性不再作为唯一的主体和视点的文学话语。
映川演绎的各色男女,正是以这种全新的观感震憾人的接受视野,也引发了人们对人生冷静而深沉的思索。
随着当下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历史推进,都市成为现代文明的汇集地,它不仅是物质高度发达的中心,也是文化极为丰富的前沿。
当代作家也热衷于表现都市生活,作家的个人都市经验成为一种创作素材被大量投入到当下的文学叙事中。
映川的爱情题材创作便是折射出她独有的都市经验,她将自己融入都市的生存焦虑的体验中,透视都市男女的情感角杀,破译当下都市生活中的危情密码。
可以说,都市是映川作品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是情节和故事变动、转折的主要载体。
她以冷静的女性视角,在小说中埋藏各种艺术隐阱和机关,给我们呈现的都市印象是一种明亮与阴影的交错,孤独的都市男女,则反映了人情淡漠的都市人生充满精神上透骨的寂寞,透彻地揭示了都市精神领域的萧条、下坠。
在虚与实的汇合中,我们看到了陷落于都市中的男女,在物欲与性欲的围困中,艰辛地找寻着身心的突围之路。
对于映川来说,反抗一种既定的生活,这似乎是作家笔下人物的选择。
传统的女性的生活角色以及长期以来受压抑的被动地位,使她们因袭着历史的重负。
随着社会发生的变化,当今妇女的思想和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对于女性来说,要想真正摆脱封建依附意识而全面地实现女性自我意识,又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轻松。
女性与传统社会的矛盾使女性步履艰难。
所以,女性走上社会后,她们肩上的担子不是减轻了,而是双倍地沉重了。
这不仅表现在精力支付、时间分配及劳动量的大小上,而且影响到她们的生活性质,使她们不得不平衡多重责任,在多元化生活的夹缝中讨生活,求进取。
在《逃跑的鞋子》中,“鞋子”的隐喻表现为物化时代情爱的缺失,使得女性在不自觉中形成了对男性从心理到文化的排斥、逃避、厌恶甚至恐惧的异化表现。
“这种心理和情感被一再放大和强化,又变成了女性对整个社会的拒斥或逃避。
”[2]这篇小说表现了男女两性之间处于对峙的状态,这种二元对立的传统模式,借用“鞋子”的隐喻,在映川的女性世界,弥漫着对男性的幻想和对男性有着莫名的厌恶的双重矛盾心结,女性总是处于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却不见采取任何行动,终日只是胡思乱想。
这使得人物形象的塑造存在着矫情和陌生化的倾向。
这种分裂的语境尽管没有迎合当下女性话语的私人性写作特点,却难以形成经典的女性文学范式,似乎有媚俗之嫌。
因此,《逃跑的鞋子》虽极尽反讽之能事,借“鞋子”找寻着身心的突围之路,有时却“不免身陷故事而缺失主体”。
这不能不说是觉醒了的女性的悲哀和女性文学腾起后的失落,呈现出一种当代的迷惘与幻想,纵使这样,仍不失温暖与精神层面上的关照。
映川的小说文本,正是以这种纪实的文学立场关注女性自身独有的问题,从而形成了被解放了的女性自觉、自主地追求解放的文学姿态。
这种追求使得女性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挑战性的文学行为,它以女性感受、女性视角为基点,打破了男性在这方面的垄断局面。
映川的小说文本因而为当代语境下重建“精神家园”提供了种种可能,以特有的写实方式追问着这个性别世界的内核和对“精神家园”的执著关照,也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开启了一条实现精神价值的通道。
二温暖的观照:映川的江湖与铁凝的《麦秸垛》、林白的《万物花开》、安妮宝贝的《莲花》和虹影的《阿难》一样,映川的《女的江湖》也是一部温暖的小说,就是故事的形而下,加上蕴涵上的形而上。
这种文学品质带着一定的温度,有着现实与理想的阻隔与交融,又不失一种人文精神的关照。
《女的江湖》里的荣灯,是一个对爱有着自己见解的女性。
在荣灯的视野中,女性的纯粹理想和男性的精神品质只有在相互交融和反复较量中才能消除彼此的极端并趋于完美。
女性用自己对爱情的诠释“唤醒了男性沉睡的责任感,培养了男性爱的能力,成功完成了对男性的改造”[3]和重塑,这种深层挖掘,则揭示出女性在男权中心话语重压下的生存真相;或以一种对女性自我身份的反省与认知的价值观,致力于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其中蕴含的是对妇女命运的深入思考。
映川最新力作长篇小说《魔术师》里的冯时,从小被父亲背叛,又被母亲背叛,成人之后又被朋友背叛,但他的内心始终有一个信念,就是“爱一个人不一定要把她娶回家,只要让她感觉到你是依靠就够了,这种感觉很好,很轻松。
”他与朱聪盈的爱情,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地老天荒”。
这种理想爱情范式就其根本而言,把大写的生命缩减、替换为小写的生命,正是映川的伊甸园理想与人性的相汇之处,它透过或进入遮蔽生命的幻景、意义和言说,直面生命本身,有着一种从容与执著的温暖。
然而,同样面对时代变迁,当某些男性获得政治身份与人生欲望的双重利益之际,女性却付出了身体与感情的惨重代价,由此传达出来的人生观、爱情观、女性观和文学意识,则见证了现代社会背景下的转型和时代风尚的变迁。
在父权制社会中,支配群体通过控制言论来控制现象,他们剥夺了女性的话语权,使之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
女性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也就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感受、体验,探索她们被男权社会压抑、遮蔽和扭曲的自我。
而映川的《不能掉头》则从男性叙事视角表现了人的成长,考验了人的向善力量,包含着对普遍人性的全面的深层次的揭示和剖析。
黄羊荒唐的出逃近似于荒诞,但人活着的尊严在温暖的爱情互救中解放了彼此,张扬了向上的人性。
人生从苦难到甜密,人性从恶到善,小说由此延伸它锐利而绵长的寓意:“当整个历史和现实都已变成了男性巨大的菲勒斯的自由穿行场,未来的云层和地面上竟相布满了男性空洞的阉割焦虑的时候,女性以她们已久的嘶哑之音,呼喊与细语出她们生命最本质的愤闷与渴望。
她们不惜以自恋自虐甚至自戕自焚的举动来争得一份属于她们自己的话语权利,表明她们心底的不甘和颠覆的决绝,这不啻于是楔入男性的一剂镇静败火的清凉药。
女性因为沉静太久,缄口的时间竟然可以以百年千年来计算,所以若不在沉默中爆发,便是在沉默中死亡。
”[4]在这个小说文本中,人物的几重执拗、顽韧、锲而不舍,共同完成了小说的主题,那就是人性的尊严感和爱情的高尚感是不容亵渎的。
在金钱至上的社会情境里,爱,仍然是不能忘记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一个作家不会仅仅因为她的写作本身获得意义,一个人的写作也不可能天然地完全孤立地获得意义。
《不能掉头》更多张显了映川对人类生存的敏感,它昭示着在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念一体化背景下人们对别样的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的向往。
正如林白将“包括被集体叙述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回忆中释放出来”[5]一样,映川的女性文学文本也将目光投向了对女性和男性生存经验的展示。
这些女作家开始反思在男性中心意识与市场的合谋下,男性也和女性一样面临新的文化困境。
她们敏锐地发现,现代社会正在以新的方式构成对两性的侵蚀与遮蔽,来自传统的性别文化的潜在压抑依然存在,在两性社会中,和谐和对话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而寻找两性对话的平台,对女性性别生活经验作人文关怀,为女性寻找身心安顿的处所,建设女性温暖话语的场景和范式,是映川直接切入这一命题的审美选择。
男女两性事实上都不完美。
女性若缺乏反思精神品位和博大的人文关怀,将同样在历史条件中重蹈悲剧性失败的覆辙。
进入新世纪,如果女性创作依然以敌视抗争的姿态呈现,依然进行不是男权就是女权、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两性战争,那么世界的情势必处于难以调和的激烈状态,而人类的发展则难以为继,两性和谐发展的终极图景只能落于无以言明的虚空中。
若将女性写作的目光更多地投注到两性对话上,既对女性关怀也对男性关怀,这将是文化多元的标志。
和解不是妥协,关怀不是无原则的让步。
而现实世界中要达到精神上的独立和人性的完整,则必须追求文化的平等和两性和谐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说, 映川的女性写作借此对两性的生存意义、性别困境等问题进了思索,传达了一种被社会公共道德和伦理法则抑制的个人经验和女性意识。
同样,映川的文学实践也是一次次心灵的温暖之旅。
三审美向度:映川的人类意识如果说对现实的人文关怀与追问构成了作家开拓审美空间的一个向度,那么同样值得重视的还有女性文学文本中的自然观照和朴素的人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