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叙事在路上_苏童短篇小说述评
- 格式:pdf
- 大小:197.75 KB
- 文档页数: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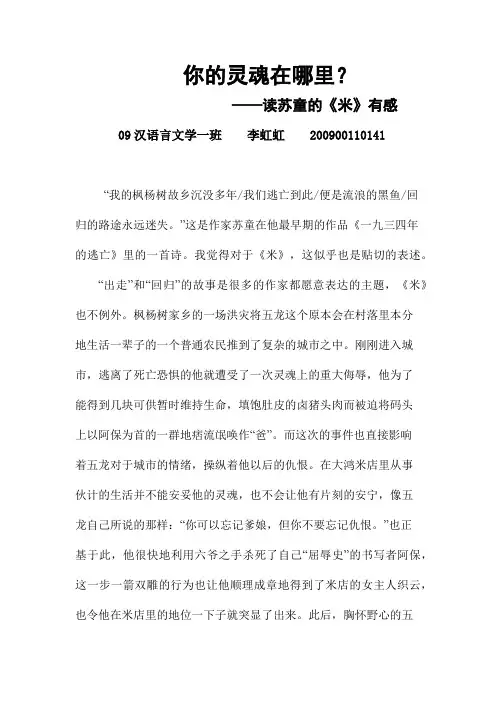
你的灵魂在哪里?——读苏童的《米》有感09汉语言文学一班李虹虹 200900110141“我的枫杨树故乡沉没多年/我们逃亡到此/便是流浪的黑鱼/回归的路途永远迷失。
”这是作家苏童在他最早期的作品《一九三四年的逃亡》里的一首诗。
我觉得对于《米》,这似乎也是贴切的表述。
“出走”和“回归”的故事是很多的作家都愿意表达的主题,《米》也不例外。
枫杨树家乡的一场洪灾将五龙这个原本会在村落里本分地生活一辈子的一个普通农民推到了复杂的城市之中。
刚刚进入城市,逃离了死亡恐惧的他就遭受了一次灵魂上的重大侮辱,他为了能得到几块可供暂时维持生命,填饱肚皮的卤猪头肉而被迫将码头上以阿保为首的一群地痞流氓唤作“爸”。
而这次的事件也直接影响着五龙对于城市的情绪,操纵着他以后的仇恨。
在大鸿米店里从事伙计的生活并不能安妥他的灵魂,也不会让他有片刻的安宁,像五龙自己所说的那样:“你可以忘记爹娘,但你不要忘记仇恨。
”也正基于此,他很快地利用六爷之手杀死了自己“屈辱史”的书写者阿保,这一步一箭双雕的行为也让他顺理成章地得到了米店的女主人织云,也令他在米店里的地位一下子就突显了出来。
此后,胸怀野心的五龙又用赶走织云和怀玉;逼嫁绮云;火烧吕公馆;参加码头兄弟会等伎俩一次次地巩固着他的仇恨,他在城市中的生存地位越高,也象征着他一次次仇恨的爆发越是厉害。
虽然那次的阴影早已被他清除,但在五龙的心里仍然对此耿耿于怀,发达之后的他用银元去诱惑年轻的搬运工叫他“爹”,然后却歇斯底里的骂道:“我最恨你们这些贱种,为了一块肉,为了两块钱,就可以随便叫人爹吗?”五龙嘲弄着别人,也嘲弄着他自己,更是肆意地将他的仇恨蔓延。
城市生活能做到的只是使他具有越来越大的恐惧,他认为那只是一个“巨大的被装饰过的坟地”,但却对他的枫杨树乡村依恋非常。
他将自己一生赚到的钱,从最初学徒时期的几个银元开始一直积攒下来,很早便计划着衣锦还乡,在故土购置土地;他对一群可能(也仅仅是可能)来自于自己家乡的杂耍艺人倾其所有,“掏出身上所有的铜板,一个个地扔进破碗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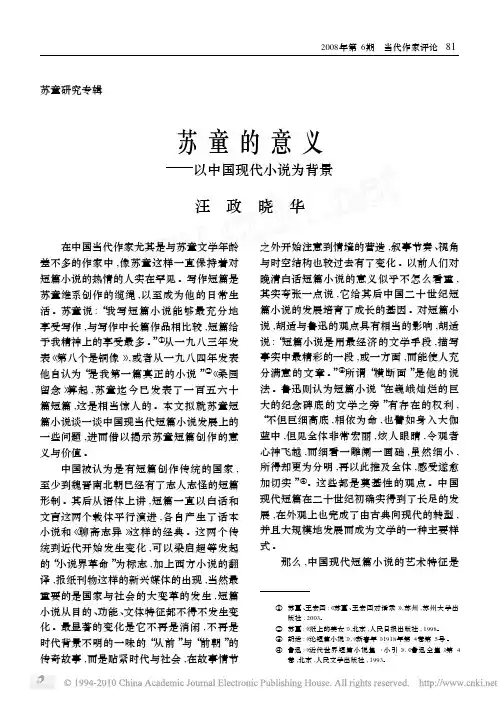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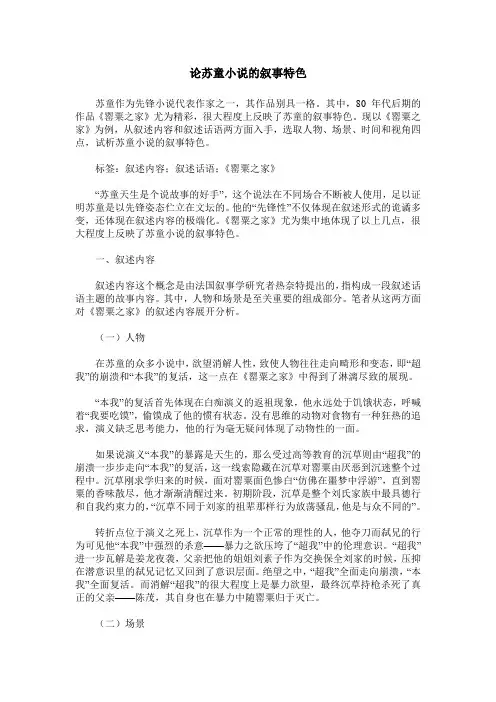
论苏童小说的叙事特色苏童作为先锋小说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别具一格。
其中,80年代后期的作品《罂粟之家》尤为精彩,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苏童的叙事特色。
现以《罂粟之家》为例,从叙述内容和叙述话语两方面入手,选取人物、场景、时间和视角四点,试析苏童小说的叙事特色。
标签:叙述内容;叙述话语;《罂粟之家》“苏童天生是个说故事的好手”,这个说法在不同场合不断被人使用,足以证明苏童是以先锋姿态伫立在文坛的。
他的“先锋性”不仅体现在叙述形式的诡谲多变,还体现在叙述内容的极端化。
《罂粟之家》尤为集中地体现了以上几点,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苏童小说的叙事特色。
一、叙述内容叙述内容这个概念是由法国叙事学研究者热奈特提出的,指构成一段叙述话语主题的故事内容。
其中,人物和场景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笔者从这两方面对《罂粟之家》的叙述内容展开分析。
(一)人物在苏童的众多小说中,欲望消解人性,致使人物往往走向畸形和变态,即“超我”的崩溃和“本我”的复活,这一点在《罂粟之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本我”的复活首先体现在白痴演义的返祖现象,他永远处于饥饿状态,呼喊着“我要吃馍”,偷馍成了他的惯有状态。
没有思维的动物对食物有一种狂热的追求,演义缺乏思考能力,他的行为毫无疑问体现了动物性的一面。
如果说演义“本我”的暴露是天生的,那么受过高等教育的沉草则由“超我”的崩溃一步步走向“本我”的复活,这一线索隐藏在沉草对罂粟由厌恶到沉迷整个过程中。
沉草刚求学归来的时候,面对罂粟面色惨白“仿佛在噩梦中浮游”,直到罂粟的香味散尽,他才渐渐清醒过来。
初期阶段,沉草是整个刘氏家族中最具德行和自我约束力的,“沉草不同于刘家的祖辈那样行为放荡骚乱,他是与众不同的”。
转折点位于演义之死上,沉草作为一个正常的理性的人,他夺刀而弑兄的行为可见他“本我”中强烈的杀意——暴力之欲压垮了“超我”中的伦理意识。
“超我”进一步瓦解是姜龙夜袭,父亲把他的姐姐刘素子作为交换保全刘家的时候,压抑在潜意识里的弑兄记忆又回到了意识层面。

杨颠峰我读苏童「原创」我读苏童作者:杨颠峰编辑:幽梦苏童的写作好像都是在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完成的,因为他的文字都太疯癫。
苏童的文字其实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捋出来的,苏童的文字衔接紧密,华丽而精致。
像水一样,清新明亮,又像一口深井,显得阴暗森然。
我对苏童的作品读得不多,留下的最多的印象,就是他对精神病患者的描摹。
苏童极其爱写疯子,似乎疯癫是他最为熟悉的一种状态。
苏童的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无逻辑,不正常,苏童不讲正常人的故事。
苏童是一个矛盾体,他写下的故事是流畅可读的,故事的内容却是病态荒诞的,苏童的作品是一种思维板块的碰撞积压产物。
在我看来苏童的理想不在于挖掘人类精神内核,而在于反映人类精神卫生。
在《米》中,织云评价五龙“脑子里装满了稀奇古怪的念头”,这实际上是苏童表达了对苏童自己的一种自我认知。
在《米》中,五龙把织云丢在米堆中亵辱,纵情遂欲,同时把米和女人都糟蹋了,苏童对这一场景评价道,“病态而疯狂”,在小说中,这针对的仅是笔下角色,在小说之外,苏童意味深远。
苏童总能恣意地把各种彼此无关的意象搭配成稀奇而巧妙的组合,正如米和女人(《米》),“魂”和手电筒(《黄雀记》),井和逃犯(《井中男孩》)。
不难看出,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荒诞印象对苏童的病态特色有重要的影响,没有它们便没有今天的苏童。
在散文《读纳博科夫》中,苏童评价纳博科夫笔下的金波特“行为古怪乖僻、言辞莫名其妙、思想庸常猥琐”,在《一点怒火,一点恐惧》中,苏童说罗伯特·库佛的作品“神经兮兮”,这些,显然都是我对苏童笔下人物和苏童自身作品的深刻印象。
作为当代中国最具特色的作家之一,苏童的文字很容易让人疑惑:那样一种奇异的文学观念从何而来?苏童的文字极具魅力,也同时拥有因个人化书写的局限而产生的排斥力。
一个作家的局限性总是固然存在的,村上春说,“没有十全十美的文章,正如没有彻头彻尾的绝望”。
对于文学的欣赏,比起情节,我更注重感觉,我之所以奉苏童为文学大师,就是因为被苏童作品中营造的感觉与极佳意境所吸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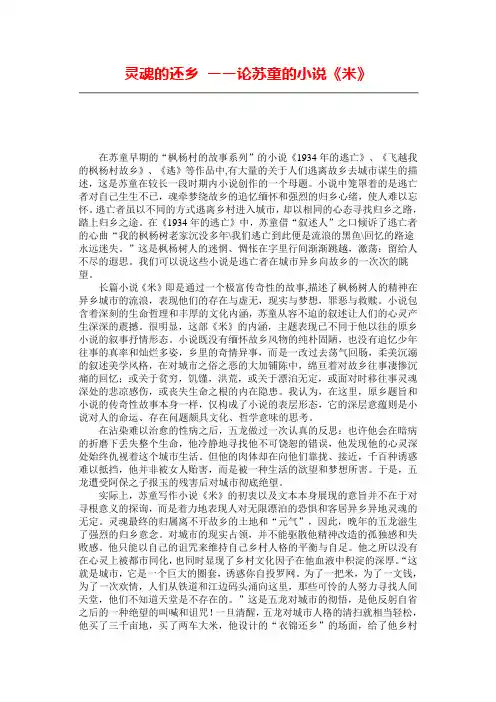
灵魂的还乡——论苏童的小说《米》在苏童早期的“枫杨村的故事系列”的小说《1934年的逃亡》、《飞越我的枫杨村故乡》、《逃》等作品中,有大量的关于人们逃离故乡去城市谋生的描述,这是苏童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小说创作的一个母题。
小说中笼罩着的是逃亡者对自己生生不已,魂牵梦绕故乡的追忆缅怀和强烈的归乡心绪,使人难以忘怀。
逃亡者虽以不同的方式逃离乡村进入城市,却以相同的心态寻找归乡之路,踏上归乡之途。
在《1934年的逃亡》中,苏童借“叙述人”之口倾诉了逃亡者的心曲“我的枫杨树老家沉没多年\我们逃亡到此便是流浪的黑鱼\回忆的路途永远迷失。
”这是枫杨树人的迷惘、惆怅在字里行间渐渐跳越,激荡;留给人不尽的遐思。
我们可以说这些小说是逃亡者在城市异乡向故乡的一次次的眺望。
长篇小说《米》即是通过一个极富传奇性的故事,描述了枫杨树人的精神在异乡城市的流浪,表现他们的存在与虚无,现实与梦想,罪恶与救赎。
小说包含着深刻的生命哲理和丰厚的文化内涵,苏童从容不迫的叙述让人们的心灵产生深深的震撼。
很明显,这部《米》的内涵,主题表现已不同于他以往的原乡小说的叙事抒情形态。
小说既没有缅怀故乡风物的纯朴固陋,也没有追忆少年往事的真率和灿烂多姿,乡里的奇情异事,而是一改过去荡气回肠,柔美沉溺的叙述美学风格,在对城市之俗之恶的大加铺陈中,绵亘着对故乡往事凄惨沉痛的回忆;或关于贫穷,饥馑,洪荒,或关于漂泊无定,或面对时移往事灵魂深处的悲凉感伤,或丧失生命之根的内在隐患。
我认为,在这里,原乡题旨和小说的传奇性故事本身一样,仅构成了小说的表层形态,它的深层意蕴则是小说对人的命运、存在问题颇具文化、哲学意味的思考。
在沾染难以治愈的性病之后,五龙做过一次认真的反思:也许他会在暗病的折磨下丢失整个生命,他冷静地寻找他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发现他的心灵深处始终仇视着这个城市生活。
但他的肉体却在向他们靠拢、接近,千百种诱惑难以抵挡,他并非被女人贻害,而是被一种生活的欲望和梦想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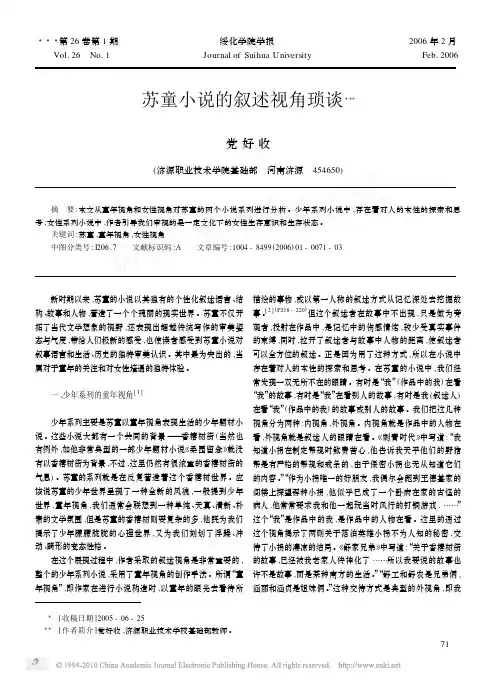
333第26卷第1期绥化学院学报2006年2月 Vol.26 No.1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 Feb.2006苏童小说的叙述视角琐谈ΞΞΞ党好收(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 河南济源 454650)摘 要:本文从童年视角和女性视角对苏童的两个小说系列进行分析。
少年系列小说中,存在着对人的本性的探索和思考;女性系列小说中,作者引导我们审视的是一定文化下的女性生存意识和生存状态。
关键词:苏童,童年视角,女性视角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499(2006)01-0071-03 新时期以来,苏童的小说以其独有的个性化叙述语言、结构、故事和人物,营造了一个个瑰丽的现实世界。
苏童不仅开拓了当代文学想象的视野,还表现出超越传统写作的审美姿态与气度,带给人们极新的感受,也使读者感受到苏童小说对叙事语言和生活、历史的独特审美认识。
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对于童年的关注和对女性境遇的独特体验。
一、少年系列的童年视角[1]少年系列主要是苏童以童年视角表现生活的少年题材小说。
这些小说大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香椿树街(当然也有例外,如他非常典型的一部少年题材小说《桑园留念》就没有以香椿树街为背景,不过,这里仍然有很浓重的香椿树街的气息)。
苏童的系列就是在反复营造着这个香椿树世界。
应该说苏童的少年世界呈现了一种全新的风貌,一般提到少年世界,童年视角,我们通常会联想到一种单纯、天真、清新、朴素的文学氛围,但是苏童的香椿树则要复杂的多,他既为我们揭示了少年朦朦胧胧的心理世界,又为我们刻划了浮躁、冲动、畸形的变态性格。
在这个展现过程中,作者采取的叙述视角是非常重要的,整个的少年系列小说,采用了童年视角的创作手法。
所谓“童年视角”,即作家在进行小说构造时,以童年的眼光去看待所描绘的事物,或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从记忆深处去挖掘故事。
[2](P218-220)但这个叙述者在故事中不出现,只是做为旁观者,投射在作品中,是记忆中的伤感情绪,较少受真实事件的束缚,同时,拉开了叙述者与故事中人物的距离,使叙述者可以全方位的叙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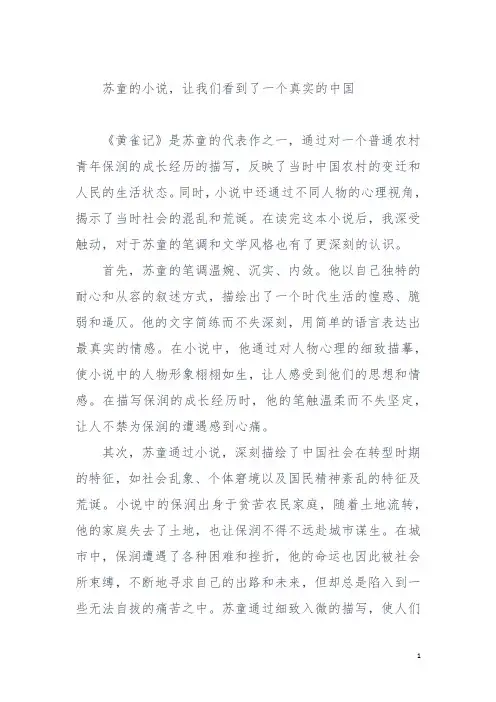
苏童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黄雀记》是苏童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一个普通农村青年保润的成长经历的描写,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变迁和人民的生活状态。
同时,小说中还通过不同人物的心理视角,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混乱和荒诞。
在读完这本小说后,我深受触动,对于苏童的笔调和文学风格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首先,苏童的笔调温婉、沉实、内敛。
他以自己独特的耐心和从容的叙述方式,描绘出了一个时代生活的惶惑、脆弱和逼仄。
他的文字简练而不失深刻,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最真实的情感。
在小说中,他通过对人物心理的细致描摹,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让人感受到他们的思想和情感。
在描写保润的成长经历时,他的笔触温柔而不失坚定,让人不禁为保润的遭遇感到心痛。
其次,苏童通过小说,深刻描绘了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的特征,如社会乱象、个体窘境以及国民精神紊乱的特征及荒诞。
小说中的保润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随着土地流转,他的家庭失去了土地,也让保润不得不远赴城市谋生。
在城市中,保润遭遇了各种困难和挫折,他的命运也因此被社会所束缚,不断地寻求自己的出路和未来,但却总是陷入到一些无法自拔的痛苦之中。
苏童通过细致入微的描写,使人们更加了解这个时代的社会现实。
此外,在小说中,苏童运用了一些象征手法,如黄雀的象征意义,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内涵,也让人印象深刻。
小说中描写的黄雀,象征着保润的命运,也象征着当时中国农村青年的命运。
黄雀的命运如同保润一样,都是在社会的变迁和冷漠中艰难求生的,这个象征不仅贴切,而且富有诗意,让人印象深刻。
总之,《黄雀记》是一部展现中国社会变迁和个体命运的优秀小说。
它通过对于一个普通农村青年的成长经历的描写,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变迁和人民的生活状态。
苏童以其独特的笔触和敏锐的观察力,刻画出了一个深刻、真实的中国社会图景,这使得《黄雀记》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我相信,这部小说会一直在读者心中发出耀眼的光芒,让人们反思社会现实,感悟生命的真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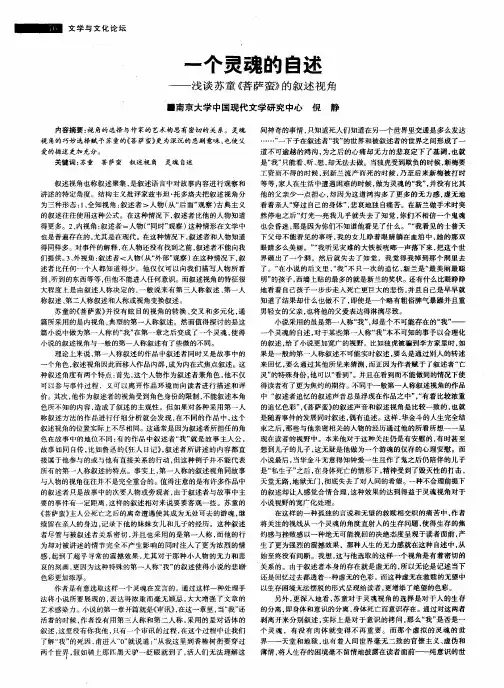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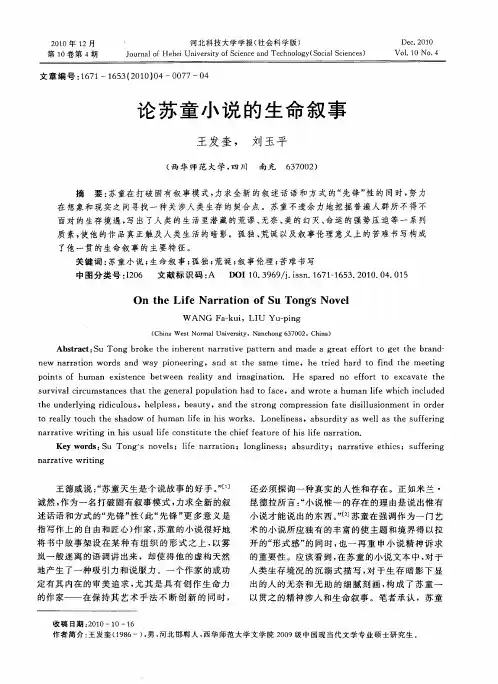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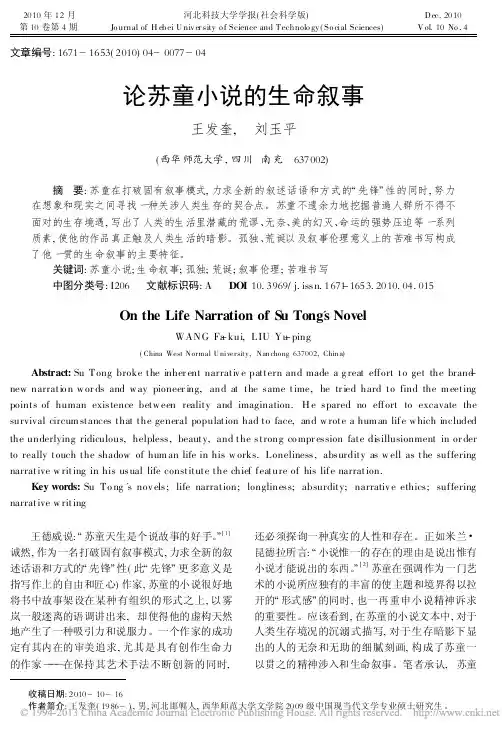
文章编号:1671-1653(2010)04-0077-04论苏童小说的生命叙事王发奎, 刘玉平(西华师范大学,四川 南充 637002)摘 要:苏童在打破固有叙事模式,力求全新的叙述话语和方式的/先锋0性的同时,努力在想象和现实之间寻找一种关涉人类生存的契合点。
苏童不遗余力地挖掘普遍人群所不得不面对的生存境遇,写出了人类的生活里潜藏的荒谬、无奈、美的幻灭、命运的强势压迫等一系列质素,使他的作品真正触及人类生活的暗影。
孤独、荒诞以及叙事伦理意义上的苦难书写构成了他一贯的生命叙事的主要特征。
关键词:苏童小说;生命叙事;孤独;荒诞;叙事伦理;苦难书写 中图分类号:I 206 文献标识码:ADOI 10.3969/j.issn.1671-1653.2010.04.015On the Life Narration of S u Tong 's NovelWANG Fa -kui,LIU Yu -ping(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Nan chong 637002,Chin a)Abstract:Su Tong broke the inher ent narrativ e pattern and made a g reat effort to get the brand -new narratio n w or ds and w ay pioneer ing,and at the same time,he tr ied hard to find the m eeting points of human existence betw een reality and imagination.H e spared no effort to excavate the survival circum stances that the general population had to face,and w rote a hum an life w hich included the underlying ridiculous,helpless,beauty,and the strong co mpr ession fate disillusionment in or der to really touch the shadow of hum an life in his w orks.Loneliness,absurdity as w ell as the suffering narrative w riting in his usual life constitute the chief feature of his life narration.Key words:Su To ng 's nov els;life narration;longliness;absurdity;narrativ e ethics;suffering narrative w riting王德威说:/苏童天生是个说故事的好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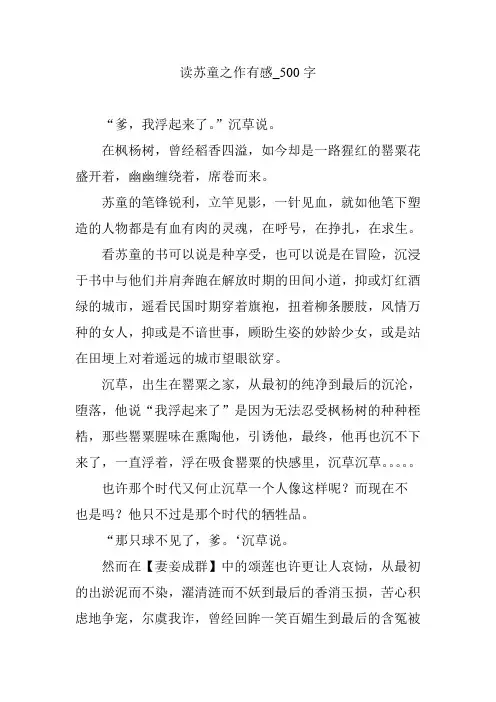
读苏童之作有感_500字
“爹,我浮起来了。
”沉草说。
在枫杨树,曾经稻香四溢,如今却是一路猩红的罂粟花盛开着,幽幽缠绕着,席卷而来。
苏童的笔锋锐利,立竿见影,一针见血,就如他笔下塑造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灵魂,在呼号,在挣扎,在求生。
看苏童的书可以说是种享受,也可以说是在冒险,沉浸于书中与他们并肩奔跑在解放时期的田间小道,抑或灯红酒绿的城市,遥看民国时期穿着旗袍,扭着柳条腰肢,风情万种的女人,抑或是不谙世事,顾盼生姿的妙龄少女,或是站在田埂上对着遥远的城市望眼欲穿。
沉草,出生在罂粟之家,从最初的纯净到最后的沉沦,堕落,他说“我浮起来了”是因为无法忍受枫杨树的种种桎梏,那些罂粟腥味在熏陶他,引诱他,最终,他再也沉不下来了,一直浮着,浮在吸食罂粟的快感里,沉草沉草。
也许那个时代又何止沉草一个人像这样呢?而现在不也是吗?他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那只球不见了,爹。
‘沉草说。
然而在【妻妾成群】中的颂莲也许更让人哀恸,从最初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到最后的香消玉损,苦心积虑地争宠,尔虞我诈,曾经回眸一笑百媚生到最后的含冤被
投井,为何?只因红颜薄命。
说实在,我偏爱苏童对人物各方面细致、有趣、玩味的描写,故事曲折跌宕,让人措手不及,十分快意。
尖锐的讽刺,干脆利落,这就是我所了解的苏童。
我轻轻合上书,为有轻叹: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从苏童长篇小说看苏童对于苦难的思考作者:杨舒来源:《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26期摘要:苏童是当代的一位先锋作家,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对于人性的思考和追问。
本篇论文主要以苏童的长篇小说为材料,从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如何面对苦难为主要内容,来探究他对于苦难文化的思考。
关键词:苦难;罪恶;逃离;死亡;解脱[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6-0-02苏童是一位拥有着敏锐的感受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
他能从时代发展的各个阶段入手,讲述社会生活对于人性的影响。
而人在种种生存境遇中遭遇的“苦难”则是苏童长篇小说中的重要主题之一。
从其作品的人物命运中我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与现实的紧张关系。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苦难,而苦难于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选择。
一、苦难对于生存衍生罪恶社会是一个大熔炉,个人很难以一己之力改变社会,所以更多时候人们往往是被动的顺应社会,在正义与邪恶,温暖与冷漠,幸福与辛酸,尊重与欺凌中被社会洗礼和重塑,在顺从与反抗中追求自身的平衡。
但当越来越多的苦难加之于一个人身上,为了生存,有时则会衍生出罪恶。
《米》中的五龙是一个从乡村逃荒到城市的青年壮汉,想凭自己的一身力气在城市中生存。
而当单纯的生存愿望遭遇城市的欺侮与压榨,那颗原本质朴的心便再不甘寂寞。
五龙一只脚才从枫杨树家乡迈进城市,另一只脚就被绊倒遭受了裆下之辱。
起初五龙对这屈辱和压榨产生的罪恶的态度是防备和回避。
而米店老板的压榨和姐妹二人的侮辱,让他体会到了社会的不公和人情的虚假,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
他开始变得焦躁,骨子里的仇恨开始生根发芽,反抗和报复的心理开始蠢蠢欲动。
之后,五龙看到码头兄弟会凭借恶行和暴力,干任何事情都易如反掌,更让五龙意识到,在这个城市,与财富和权力带给人的威力相比,生命根本不值一提。
仇恨在他心中经过一次又一次发酵,似乎已经不可遏制。
凡此种种来自城市的恶在五龙的心中孕育了以恶制恶的想法。
苏童黄雀记读后感6篇苏童黄雀记读后感6篇篇一:苏童黄雀记读后感四年,苏童带着《黄雀记》重新回到香椿街,带着偏执和任性。
小说取名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象征阴影中潜伏的危机,对人们命运的虎视眈眈。
围绕着含冤入狱懵懂少年的春天,畏首畏尾犯罪真凶的秋天和位卑心高市井红颜的夏天所展开,病相丛生,光怪陆离。
这份年届五十苏童送给自己的礼物,依旧逃脱不了其作品既定的主题——逃。
人性的卑劣,是逃的初衷。
从春心萌动到阴差阳错,从失魂落魄到万念俱灰,终究也只是一场无可隐匿的流逝而已。
小说从失魂到寻找,从犯罪到救赎,从沉沦到逃遁,从出生到死亡,步步紧逼,最终哀叹遍地。
不谈命运,最终却依旧败给了所谓注定,嘲弄之情,讽刺之意,近乎于放肆。
字里行间,萧索疯癫,扼人咽喉,不免让人无声叹息。
少年少女在逃遁,中年男女在逃离,耄耋老人在逃亡。
香椿街上的生命,步伐仓促,万般无常。
那些以前逼迫你出逃的事由,在故事一开始便凿下了深渊,兜兜转转,依旧被命运推进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挣扎也好,哭喊也罢,终究苟活于后人餐前饭后的谈资之中。
然后你才发现,这一路的忐忑不安和留意翼翼,始终是自己执拗的保护色,于外人而言,但是看的一场笑话罢了,显得分外剩余。
故事结束,始觉真相,一语成谶,万念俱灰。
生离死别、世事无常皆为生命本来赋予你的戏码,你在演绎的最初便就没有了换剧本的权利。
因此,抽丝剥茧才是真正的痛不欲生,后知后觉又怎会是一败涂地呢?用冰冷的语气讲述冷漠的故事,用孤独的文字叙写萧索的人生,苏童的书永远都不用光明正大地告知天下冬天的到来,正因全文皆是冬。
那是一种透过心脏来传递的,喷薄的绝望,也是一种逆流回心脏的,重生的勇气。
回甘的余味,会让你原谅那枝蔓无度的芜杂叙事,毫无节制的情节叙述。
然后,更好地去重新演绎何为生活,何为生命。
篇二:苏童黄雀记读后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无论黄雀是书中的人物还是现实的叙事者,仿佛都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无处安置的灵魂。
“坐下来看一段,让自己心灵慢慢静下来,这就是苏童作品的魅力。
”这是江苏省作协党组副书记范小青给苏童的评价。
继《妻妾成群》、《米》之后创作的又一长篇小说《河岸》在今年引起了大众的注意。
人们对他的作品评价不一,有人说:“苏童小说是一道美丽的陷阱,使初步者迷醉,使久留者后悔。
”或许这正是他所表达的人性深层的纠结所引起的共鸣吧。
灵魂的魅力苏童的小说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在反映的人物的孤独、逃亡、宿命意识等问题,来完全地展示人类的迷失状态。
熟悉苏童的读者一定是被他刻画人物内心意识的魅力所吸引,被那种纠结而矛盾的斗争所征服。
他说:“我之所以总是以人性中的这些意识为题材,是因为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人的孤独感是人性中重要的内容,那不是一种消极的情绪,而是内在的人性状态,一个人的孤独在某种层面上就是一群人的孤独,是一个民族的孤独。
”他正是用文字表现同一个时代背景下,同一个阶层的一群人的相同的个性,从而体现着自己的作品独特的魅力。
《河岸》是愿望苏童生于70年代,后文革时期的童年记忆一直挥之不去,深深影响着他的思想。
那短时光对于如今的年轻人来说或许只是段历史,而对于苏童来说,却是在一个孩子心里构筑成的一段难忘的经历。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部《河岸》与以往的作品不同,在内容上添加了诸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色彩,这是在从前的作品中被刻意避开的。
苏童坦言,他一直想用文字去追忆那段历史,却一直没有提笔,如今完成《河岸》的创作,对他个人来说就如同一次仪式,实现一个描述记忆的愿望。
他曾说过这是一部离他最远的作品,96·2009·SEP 文化图书BOOK■文/赫赫对话灵魂的苏童BOOK 图书文化972009·SEP ·那是因为这部小说的风格与以往不同,成为迄今为止最偏离“苏童作品”的小说。
作品中的女性在苏童的作品中,人们最熟知的是他对女性的了解,但面对外界送他的“女性专家”的绰号却谦逊地说自己并没有那么了解,至少女知识分子是不了解的。
身体和灵魂都在路上读后感《身体和灵魂都在路上》是一本著名的哲学类巨作,是作者俞可平的自传体作品。
这本书令我深受启发,给我带来了许多思考和感悟。
首先,本书通过描述作者俞可平的旅行经历,揭示了人在旅行中的身体和灵魂的变化。
作者通过自身的经历告诉我们,身体和灵魂是相互联系的,彼此影响。
在旅途中,身体的疲劳和压力也会影响到精神的状态,而精神的状态又会对身体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这让我想到自己在平时生活中,经常感到身心疲惫,精神萎靡不振,也许是因为身体和灵魂的不平衡造成的。
因此,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应该注重调节身体和精神的平衡,通过运动、休息和思考等方式来充实身体和灵魂。
其次,本书也探讨了人的成长和改变。
作者在旅途中经历了种种困难和挑战,但通过这些经历他逐渐认识到自我和人生的真谛。
他发现自己在旅途中获得了身心的成长和启示,实现了自我超越与蜕变。
这启示了我,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和挫折其实是一种成长的机会,是自我认识和改变的契机。
我们应该用积极的心态面对困难,从中寻找成长的经验和启示,不断提升自己,追求更好的自我。
最后,本书还反思了现代人的追求和生存状态。
现代社会节奏快,竞争激烈,人们的生活被繁琐的琐事和物质的追求所困扰。
因此,很多人在追求物质生活的过程中丧失了灵魂的追求和内心的自由。
而旅行被作者视为一种重建身体与自由灵魂的方式,是一种重新审视和认识自己的机会。
这让我反思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否过于功利和唯物,是否应该适时停下来,给自己一点空间和时间去旅行和思考,来重新寻找内心的自由和追求。
总的来说,《身体和灵魂都在路上》是一本富有启发和思考的好书。
通过读这本书,我不仅了解到了旅行对身体和灵魂的影响,而且得到了一些关于成长和生活方式的启示。
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次有益的心灵洗礼,让我更加深入地思考和认识自己,也更加明白了生活的真谛。
我会将书中的一些思想应用到我的生活中,追求身心的平衡和内心的自由。
[收稿日期]2011-03-25[基金项目]淮安市社科类研究项目,项目编号:C -11-20。
[作者简介]马燕(1981-),女,江苏沭阳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第33卷第7期2012年7月哈尔滨学院学报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 Vol.33No.7Jul.2012[文章编号]1004—5856(2012)07—0104—05灵魂叙事在路上———苏童短篇小说述评马燕(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江苏淮安223003)[摘要]苏童从关注人性的角度,从精神层面和灵魂的深度方面创作了一系列既具可读性又颇令人深思的短篇小说。
文章从苏童创作的源泉、内容和关注点方面入手,阐述苏童的灵魂叙事。
[关键词]苏童;短篇小说;灵魂叙事;人性[中图分类号]I207.427[文献标识码]A 读苏童的短篇小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一幅浮世绘。
苏童的短篇很多,据统计有一百二三十篇之多,并且还在源源不断的有新的作品问世。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苏童就有《桑园留恋》、《U 形铁》、《仪式的完成》等作品引人瞩目;90年代以来,苏童的短篇小说收获颇丰,从《像天使一样美丽》、《回力牌球鞋》、《什么是爱情》、《樱桃》、《美人失踪》、《把你的脚捆起来》,到《表姐来到马桥镇》、《红桃Q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海滩上的一群羊》、《巨婴》、《你丈夫是干什么的》、《奸细》、《开往瓷厂的班车》,篇篇不俗;进入21世纪,苏童又奉献给我们《白雪猪头》、《人民的鱼》、《点心》、《骑兵》、《哭泣的耳朵》、《桥上的疯妈妈》、《手》等作品,都获得好评。
尽管如此,批评界仍然对苏童的中长篇小说关注的比较多,而没有给予他的短篇小说以足够的注意。
虽说苏童的作家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中长篇奠定的,但其实在研究苏童的创作时,他的短篇小说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苏童自己也很痴迷于短篇小说,他在《我的短篇小说之“病”》中说:“大学时代我曾迷恋于契诃夫、高尔基、海明威,三人的创作风格可谓风牛马不相及,但契诃夫和海明威的短篇集使我分别领略了古典的灰暗、细腻、沉重和现代的简洁、明朗和个性化的技巧,至于高尔基的早期短篇小说,它们的流浪者情绪其实极易俘虏文学少年的心。
”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苏童对短篇的喜爱由来已久,而他从其所迷恋的大师身上也吸收了很多终身受益的养料。
几乎每年苏童都有一些短篇作品发表在各大文学刊物上。
近几年来,就有《私宴》、《西瓜船》、《二重唱》、《冬露》等,从质量来说,毋庸置疑是好的,洪治纲在《小说的全面探索和再度开拓》一文中,就对苏童2004年发表的《私宴》做了很好的评价,他说:“像苏童的《私宴》,作者借助一个老同学间的春节聚会,将成长中的内心隐痛与当下现实中的精神失衡巧妙地糅杂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异常广袤的历史空间。
……苏童的独到之处在于,他选择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叙事通道,将我们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的经济霸权者的内心欲望,引入到成长记忆与伦理交往的情感空间,使征服欲与尊严感构成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尖锐对抗。
”近来,理论界又重提“灵魂叙事”,2007年第一期的《小说评论》谢有顺专栏,谈的就是《重申灵魂叙事》。
他指出,“惯性使今日作家的创造性日益衰败”,“当思想泛滥,我讲文学的身体;当身体泛滥,我又要重申灵魂叙事了。
”无论世间怎么变,苏童不紧不慢的写着他的短篇小说,用他不疾不徐的文字描绘这人间的世态人情,在他的灵魂叙事道路上稳稳地走着。
我们不妨通过他80年代以来的一些作品来观其短篇小说创作的灵魂叙事之路。
一、打开灵魂深处的记忆人们习惯把苏童的小说分为“香椿树街”系列和“枫杨树”系列。
以“香椿树街”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尤为丰富和出色。
在《一份自传》里苏童提到“童年时代在苏州城北一条古老的街道上度过。
那段生活的记忆总是异常清晰而感人。
我的许多短篇小说都是依据那段生活写成”。
这里说的“依据那段生活写成”的短篇小说主要有:《桑园留念》、《回力牌球鞋》、《美人失踪》、《古巴刀》、《骑兵》等。
这些小说有的是80年代的作品,有的是90年代的,也有21世纪以来的作品。
在这些小说里鲜明地提到了香椿树街这个地理标志。
这说明,在苏童的创作中始终没有落下记忆这一条线索,他曾经说过,“我之所以执著于这些街道故事的经营,其原因也非常简单:炊烟下面总有人类,香椿树街上飘散着人类的气息。
”[1]《回力牌球鞋》以“陶脚上那双白色的回力牌球鞋在1947年曾经吸引了几乎每一个香椿树街少年的目光”开篇,讲的是在1947年这个黯淡的年代,一双回力牌球鞋在几个少年中间惹出的事端。
作家在小说里对少年陶心理和眼神的精确刻画,对一群男孩子的恶作剧的描绘,都十分成功,相信这一部分在程度上是得益于他对少年时期的印象。
在小说集《少年血》自序中苏童写道:“我从小生长在类似‘香椿树街’的一条街道上,我知道少年血是黏稠而富有文学意味的,我知道少年血在混乱无序的年月里如何流淌,凡是流淌的事物必有它的轨迹。
在这本集子中我试图记录了这种轨迹。
”这段话集中体现了苏童对过去岁月的追忆和对这些记忆的创造性再体验。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苏童并没有原原本本地重述他的少年生活,他所取的仅仅是那条街的影子、那个年纪的几个孩子,那经常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而已。
他并未像写回忆录那样,用一个过来人的姿态重现往日情状,事实是并非他自己说的仅仅是“试图记录了这种轨迹”而已,“少年血”这个说法本来就有一种质感的东西在里头,而不是浮于表面的那些所谓“个人经验”。
作品《美人失踪》,开头用了两个“请设想”,于是,我们就真的跟着想象了一群妇女和孩子争先恐后从家里门洞跑出来聚集围拢在街头,一边打毛衣一边交头接耳津津有味地议论有关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珠珠失踪的惊人消息的场面。
应该说,苏童描写这些场面得心应手,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也是因为作家有着切身的经历和体会。
在这里,作家打开的已经不单纯是记忆之门,而是灵魂的记忆之门。
作家甚至不必用眼睛看过,就能描绘出当时的场景,不必用鼻子闻过,就能指出当时的妇女们言语中的味道。
为什么?因为作家是用心去看过、用心去闻过。
作家用心看到的、闻到的比用眼观、鼻嗅的还要精妙,甚至也许还能看到人心的颜色。
在《古巴刀》一篇中陈辉的悲剧性命运,三霸的冷酷,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苏童写陈辉在三霸面前从熊样到绝望直至崩溃,每一步行动发展都合情合理,极为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悲剧性。
这篇小说也是以香椿树街的芸芸众生为背景的,有时这些群众人物甚至推动了故事的发展。
“我哥哥他们隔窗观望着外面的骚乱场面,他们很想知道陈辉这种人,逼急了他会做出多大的事情,他们都抱着与己无关的态度,看着陈辉手里的刀和刀向两边挥舞时划出的光带,竟然还有人向陈辉叫喊道,砍得好,砍得好!”我们首先可以确认作家本身是和陈辉、三霸这种类型的人格格不入的。
因为苏童在《一份自传》里说过:“我从小就听话,在学校里听老师的话,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在孩子堆里听孩子王的话。
我从来不具有叛逆性格和坚强的男性性格,这一点也让我不好意思。
”可见,苏童尽管体察这些畸形的心态,能够细致入微地刻画出他们的心理,甚至能够把握住一条街501第7期马燕:灵魂叙事在路上上人的阴暗面,完全是靠着与人物灵魂的打通与共鸣。
严歌苓在她的作品《穗子物语》自序中写道:“小说家只需对他(她)作品的文学价值负责。
……我只想说,所有的人物,都有一定的原型;所有的故事,难免掺有比重不同的虚构,但印象是真切的,是否客观我毫不在乎,我忠实于印象。
”对于苏童来讲,他的记忆也是忠实于他的印象的,而印象也有关内心,有关灵魂和精神,灵魂深处的记忆才是他创作的精神源泉。
二、抓住人类自身的尾巴90年代是苏童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大概创作了有六七十篇,占他迄今为止短篇小说创作的半壁江山。
有人问,作家都在关注什么?作家的社会担当是什么?作家乃手无缚鸡之力之文人,对这个社会授予的神圣责任如何去承担?我们说,作家的承担只能是文学的精神承担,而所谓文学的精神承担能力,“从文学的角度说,最主要的是对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的关怀,对人类生存苦难、精神困境的承担和对人性美善的呼唤”。
[2]苏童在《作家苏童谈写作》中说:“我关注的所有命题都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人的命运和人的问题。
……但它的终极目标,作为一个作家,我所关注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字———‘人’。
”另外,他在《急就的讲稿》中还谈道,“历史总是充满缺陷,人在历史中也总是充满缺陷,我们因此抓住了许多人类自身的尾巴,也因此发现了小说创作的巨大空间”。
从这句话里我们不难看出,作家苏童显然已经抓住了这条尾巴,在分析人的罪性方面做出了努力,进而解决了作品的灵魂归属问题。
“大家都是有罪的,只是在有罪的人当中,有的人还知罪,有的人不知罪,……”[3]在《西窗》中苏童写道“根据我以往的经验,香椿树街居民是经常生活在谎言和骗局之中的”,“就这么回事,你从西窗里还能看见什么?”他的笔调淡淡的,他的态度隐隐的,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使小老百姓的那种小奸小坏显现无遗。
这种小奸小坏或许是无伤大雅的,或许是造成不了什么社会危害的,但是,却像显微镜,把人内心深处潜藏得很深、很隐蔽的恶性放大,使其完全呈现在每一个读者的眼里,最后在读者心里泛起涟漪,这种触动,哪怕就是一霎那,也是深入灵魂的。
《骑兵》中傻子光春吃了左林的亏,为了弥补光春和他的绍兴奶奶,左林爸爸左礼生无奈答应让傻子骑着罗圈腿左林到街上去。
“左礼生迟疑地看了看藤椅上的绍兴奶奶,绍兴奶奶睁开了眼睛,她犀利而坚硬的目光使左礼生有点慌乱,左礼生嘿地一笑,说,当然能骑到街上去,左林骑你也是在外面嘛。
”看上去是平等的,但这难道不是冤冤相报吗?孩子不懂事,大人们难道也不知道吗?以暴制暴,绍兴奶奶的态度值得思考,左礼生的态度也值得思考。
“他们问绍兴奶奶,绍兴奶奶,你为什么让光春骑在左林背上呀?绍兴奶奶觉得人家问得没道理,她气呼呼地不理睬人家,倒是左礼生,自己给自己一路打着圆场,说,孩子闹着玩,让他们闹着玩去。
”左礼生很快听到了儿子膝盖不堪重负的声音,他的心都快碎了,他试图终止这场游戏,可惜傻子没同意。
这时“左礼生转过脸看绍兴奶奶,绍兴奶奶偏不回应他的信号,只是看管着孙子手里的电线。
……左礼生无奈地说,那就再骑一会儿吧。
”这其实是大人们的较量。
后来左礼生急中生智,不由分说地把傻子架到了自己身上,解救了儿子,这时,绍兴奶奶说“礼生这可使不得,孩子的事情,你大人不该夹进去,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其实大人早掺和进去了。
在这场闹剧中,左礼生和傻子奶奶的做法,实在是大有不妥。
人性是复杂的,善恶似乎也无法那么明晰的分辨出来了。
《白沙》讲的是海葬。
小林和一群搞摄影的朋友遇见了一个叫雪莱的年轻人,厌倦了生命,要自愿海葬。
雪莱下海了,无人阻拦,直至雪莱淹没在海水中,海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