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行行重行行》
- 格式:docx
- 大小:20.20 KB
- 文档页数: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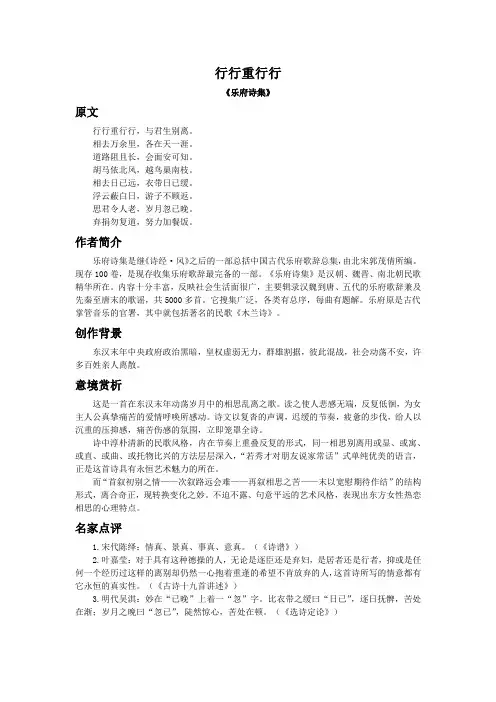
行行重行行《乐府诗集》原文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作者简介乐府诗集是继《诗经·风》之后的一部总括中国古代乐府歌辞总集,由北宋郭茂倩所编。
现存100卷,是现存收集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
《乐府诗集》是汉朝、魏晋、南北朝民歌精华所在。
内容十分丰富,反映社会生活面很广,主要辑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共5000多首。
它搜集广泛,各类有总序,每曲有题解。
乐府原是古代掌管音乐的官署,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民歌《木兰诗》。
创作背景东汉末年中央政府政治黑暗,皇权虚弱无力,群雄割据,彼此混战,社会动荡不安,许多百姓亲人离散。
意境赏析这是一首在东汉末年动荡岁月中的相思乱离之歌。
读之使人悲感无端,反复低徊,为女主人公真挚痛苦的爱情呼唤所感动。
诗文以复沓的声调,迟缓的节奏,疲惫的步伐,给人以沉重的压抑感,痛苦伤感的氛围,立即笼罩全诗。
诗中淳朴清新的民歌风格,内在节奏上重叠反复的形式,同一相思别离用或显、或寓、或直、或曲、或托物比兴的方法层层深入,“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式单纯优美的语言,正是这首诗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所在。
而“首叙初别之情——次叙路远会难——再叙相思之苦——末以宽慰期待作结”的结构形式,离合奇正,现转换变化之妙。
不迫不露、句意平远的艺术风格,表现出东方女性热恋相思的心理特点。
名家点评1.宋代陈绎:情真、景真、事真、意真。
(《诗谱》)2.叶嘉莹:对于具有这种德操的人,无论是逐臣还是弃妇,是居者还是行者,抑或是任何一个经历过这样的离别却仍然一心抱着重逢的希望不肯放弃的人,这首诗所写的情意都有它永恒的真实性。
(《古诗十九首讲述》)3.明代吴淇:妙在“已晚”上着一“忽”字。
比衣带之缓曰“日已”,逐日抚髀,苦处在渐;岁月之晚曰“忽已”,陡然惊心,苦处在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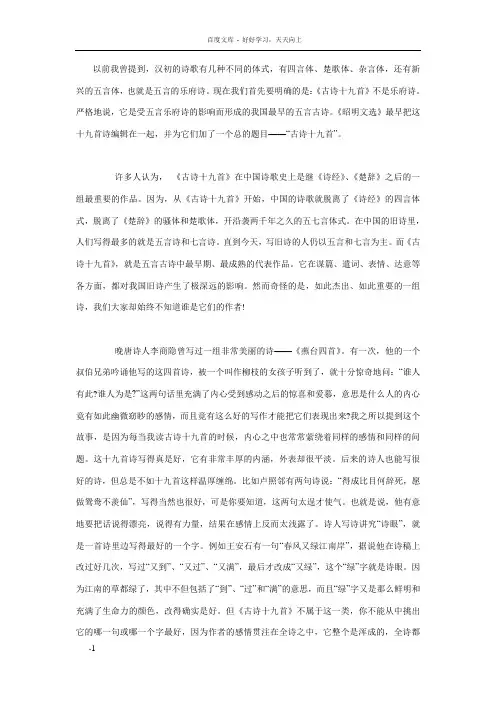
以前我曾提到,汉初的诗歌有几种不同的体式,有四言体、楚歌体、杂言体,还有新兴的五言体,也就是五言的乐府诗。
现在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古诗十九首》不是乐府诗。
严格地说,它是受五言乐府诗的影响而形成的我国最早的五言古诗。
《昭明文选》最早把这十九首诗编辑在一起,并为它们加了一个总的题目——“古诗十九首”。
许多人认为,《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一组最重要的作品。
因为,从《古诗十九首》开始,中国的诗歌就脱离了《诗经》的四言体式,脱离了《楚辞》的骚体和楚歌体,开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五七言体式。
在中国的旧诗里,人们写得最多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
直到今天,写旧诗的人仍以五言和七言为主。
而《古诗十九首》,就是五言古诗中最早期、最成熟的代表作品。
它在谋篇、遣词、表情、达意等各方面,都对我国旧诗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然而奇怪的是,如此杰出、如此重要的一组诗,我们大家却始终不知道谁是它们的作者!晚唐诗人李商隐曾写过一组非常美丽的诗——《燕台四首》。
有一次,他的一个叔伯兄弟吟诵他写的这四首诗,被一个叫作柳枝的女孩子听到了,就十分惊奇地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这两句话里充满了内心受到感动之后的惊喜和爱慕,意思是什么人的内心竟有如此幽微窈眇的感情,而且竟有这么好的写作才能把它们表现出来?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每当我读古诗十九首的时候,内心之中也常常萦绕着同样的感情和同样的问题。
这十九首诗写得真是好,它有非常丰厚的内涵,外表却很平淡。
后来的诗人也能写很好的诗,但总是不如十九首这样温厚缠绵。
比如卢照邻有两句诗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写得当然也很好,可是你要知道,这两句太逞才使气。
也就是说,他有意地要把话说得漂亮,说得有力量,结果在感情上反而太浅露了。
诗人写诗讲究“诗眼”,就是一首诗里边写得最好的一个字。
例如王安石有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据说他在诗稿上改过好几次,写过“又到”、“又过”、“又满”,最后才改成“又绿”,这个“绿”字就是诗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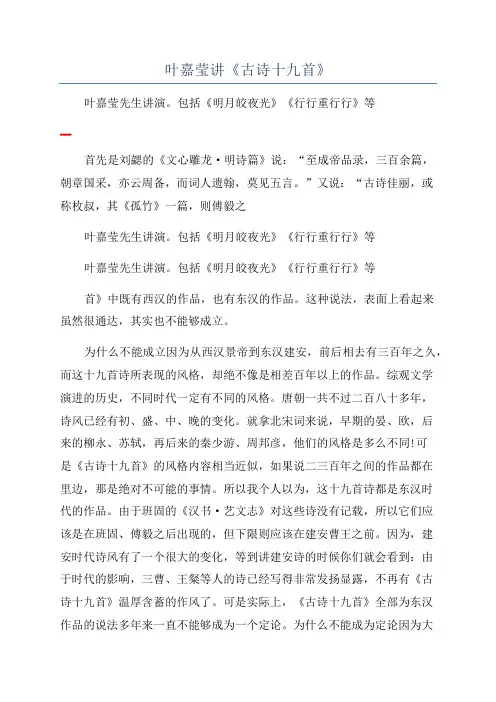
叶嘉莹讲《古诗十九首》叶嘉莹先生讲演。
包括《明月皎夜光》《行行重行行》等一首先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
”又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叶嘉莹先生讲演。
包括《明月皎夜光》《行行重行行》等叶嘉莹先生讲演。
包括《明月皎夜光》《行行重行行》等首》中既有西汉的作品,也有东汉的作品。
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通达,其实也不能够成立。
为什么不能成立因为从西汉景帝到东汉建安,前后相去有三百年之久,而这十九首诗所表现的风格,却绝不像是相差百年以上的作品。
综观文学演进的历史,不同时代一定有不同的风格。
唐朝一共不过二百八十多年,诗风已经有初、盛、中、晚的变化。
就拿北宋词来说,早期的晏、欧,后来的柳永、苏轼,再后来的秦少游、周邦彦,他们的风格是多么不同!可是《古诗十九首》的风格内容相当近似,如果说二三百年之间的作品都在里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个人以为,这十九首诗都是东汉时代的作品。
由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对这些诗没有记载,所以它们应该是在班固、傅毅之后出现的,但下限则应该在建安曹王之前。
因为,建安时代诗风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等到讲建安诗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由于时代的影响,三曹、王粲等人的诗已经写得非常发扬显露,不再有《古诗十九首》温厚含蓄的作风了。
可是实际上,《古诗十九首》全部为东汉作品的说法多年来一直不能够成为一个定论。
为什么不能成为定论因为大家都不敢断定这里边肯定就没有西汉之作。
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十九首中有这样一首诗——《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
秋蝉呜树间,玄鸟逝安适。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叶嘉莹先生讲演。
包括《明月皎夜光》《行行重行行》等斗柄指到卯的方位时就是二月仲春,指到辰的方位时是三月季春,指到巳的方位时是四月孟夏不过,这只是夏历,而夏商周三代的历法是不同的,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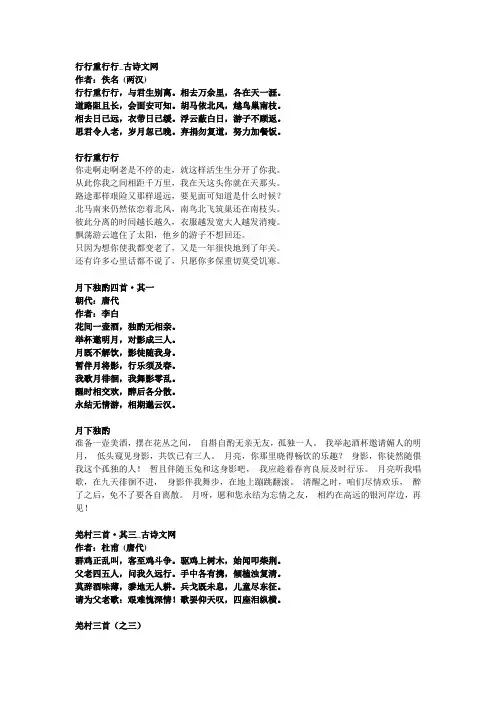
行行重行行_古诗文网作者:佚名(两汉)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行行重行行你走啊走啊老是不停的走,就这样活生生分开了你我。
从此你我之间相距千万里,我在天这头你就在天那头。
路途那样艰险又那样遥远,要见面可知道是什么时候?北马南来仍然依恋着北风,南鸟北飞筑巢还在南枝头。
彼此分离的时间越长越久,衣服越发宽大人越发消瘦。
飘荡游云遮住了太阳,他乡的游子不想回还。
只因为想你使我都变老了,又是一年很快地到了年关。
还有许多心里话都不说了,只愿你多保重切莫受饥寒。
月下独酌四首·其一朝代:唐代作者: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相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月下独酌准备一壶美酒,摆在花丛之间,自斟自酌无亲无友,孤独一人。
我举起酒杯邀请媚人的明月,低头窥见身影,共饮已有三人。
月亮,你那里晓得畅饮的乐趣?身影,你徒然随偎我这个孤独的人!暂且伴随玉兔和这身影吧,我应趁着春宵良辰及时行乐。
月亮听我唱歌,在九天徘徊不进,身影伴我舞步,在地上蹦跳翻滚。
清醒之时,咱们尽情欢乐,醉了之后,免不了要各自离散。
月呀,愿和您永结为忘情之友,相约在高远的银河岸边,再见!羌村三首·其三_古诗文网作者:杜甫(唐代)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
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
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
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
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羌村三首(之三)成群的鸡正在乱叫,客人来时,鸡又争又斗。
把鸡赶上了树端,这才听到有人在敲柴门。
四五位村中的年长者,来慰问我由远地归来。
手里都带着礼物,从榼里往外倒酒,酒有的清,有的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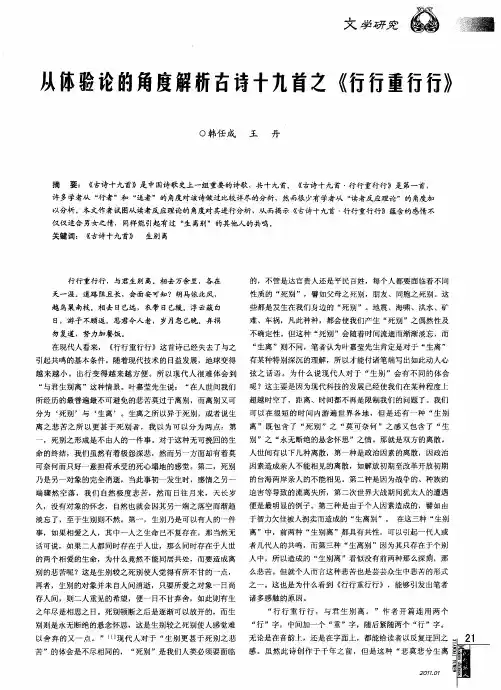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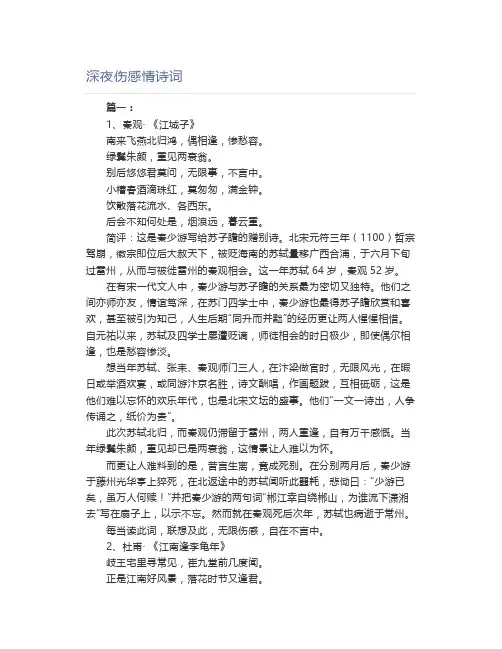
深夜伤感情诗词篇一:1、秦观· 《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
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
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
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
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
简评:这是秦少游写给苏子瞻的赠别诗。
北宋元符三年(1100)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后大赦天下,被贬海南的苏轼量移广西合浦,于六月下旬过雷州,从而与被徙雷州的秦观相会。
这一年苏轼64岁,秦观52岁。
在有宋一代文人中,秦少游与苏子瞻的关系最为密切又独特。
他们之间亦师亦友,情谊笃深,在苏门四学士中,秦少游也最得苏子瞻欣赏和喜欢,甚至被引为知己,人生后期“同升而并黜”的经历更让两人惺惺相惜。
自元祐以来,苏轼及四学士屡遭贬谪,师徒相会的时日极少,即使偶尔相逢,也是愁容惨淡。
想当年苏轼、张耒、秦观师门三人,在汴梁做官时,无限风光,在暇日或举酒欢宴,或同游汴京名胜,诗文酬唱,作画题跋,互相砥砺,这是他们难以忘怀的欢乐年代,也是北宋文坛的盛事。
他们“一文一诗出,人争传诵之,纸价为贵”。
此次苏轼北归,而秦观仍滞留于雷州,两人重逢,自有万千感慨。
当年绿鬓朱颜,重见却已是两衰翁,这情景让人难以为怀。
而更让人难料到的是,昔言生离,竟成死别。
在分别两月后,秦少游于藤州光华亭上猝死,在北返途中的苏轼闻听此噩耗,悲恸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并把秦少游的两句词“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写在扇子上,以示不忘。
然而就在秦观死后次年,苏轼也病逝于常州。
每当读此词,联想及此,无限伤感,自在不言中。
2、杜甫· 《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简评:此首诗词丽而意苦,感昔伤今之叹全从以“又”字出。
所谓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而言外黯然欲绝。
杜工部七绝,此为压卷之作!3、秦观· 《满庭芳》山抹微云,天粘衰草。
画角声断谯门。
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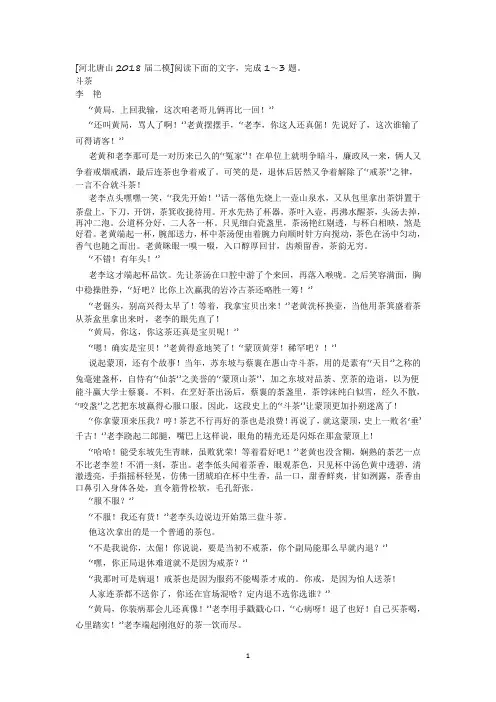
[河北唐山2018届二模]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斗茶李艳“黄局,上回我输,这次咱老哥儿俩再比一回!”“还叫黄局,骂人了啊!”老黄摆摆手,“老李,你这人还真倔!先说好了,这次谁输了可得请客!”老黄和老李那可是一对历来已久的“冤家”!在单位上就明争暗斗,廉政风一来,俩人又争着戒烟戒酒,最后连茶也争着戒了。
可笑的是,退休后居然又争着解除了“戒茶”之律,一言不合就斗茶!老李点头嘿嘿一笑,“我先开始!”话一落他先烧上一壶山泉水,又从包里拿出茶饼置于茶盘上,下刀,开饼,茶箕收拢待用。
开水先热了杯器,茶叶入壶,再沸水醒茶,头汤去掉,再冲二泡。
公道杯分好,二人各一杯。
只见细白瓷盏里,茶汤艳红剔透,与杯白相映,煞是好看。
老黄端起一杯,腕部送力,杯中茶汤便由着腕力向顺时针方向搅动,茶色在汤中匀动,香气也随之而出。
老黄眯眼一嗅一啜,入口醇厚回甘,齿颊留香,茶韵无穷。
“不错!有年头!”老李这才端起杯品饮。
先让茶汤在口腔中游了个来回,再落入喉咙。
之后笑容满面,胸中稳操胜券,“好吧?比你上次赢我的岩冷古茶还略胜一筹!”“老倔头,别高兴得太早了!等着,我拿宝贝出来!”老黄洗杯换壶,当他用茶箕盛着茶从茶盒里拿出来时,老李的眼先直了!“黄局,你这,你这茶还真是宝贝呢!”“嗯!确实是宝贝!”老黄得意地笑了!“蒙顶黄芽!稀罕吧?!”说起蒙顶,还有个故事!当年,苏东坡与蔡襄在惠山寺斗茶,用的是素有“天目”之称的兔毫建盏杯,自恃有“仙荼”之美誉的“蒙顶山茶”,加之东坡对品荼、烹茶的造诣,以为便能斗赢大学士蔡襄。
不料,在烹好茶出汤后,蔡襄的荼盏里,茶饽沫纯白似雪,经久不散,“咬盏”之艺把东坡赢得心服口服。
因此,这段史上的“斗茶”让蒙顶更加扑朔迷离了!“你拿蒙顶来压我?哼!茶艺不行再好的茶也是浪费!再说了,就这蒙顶,史上一败名‘垂’千古!”老李跷起二郎腿,嘴巴上这样说,眼角的精光还是闪烁在那盒蒙顶上!“哈哈!能受东坡先生青睐,虽败犹荣!等着看好吧!”老黄也没含糊,娴熟的荼艺一点不比老李差!不消一刻,茶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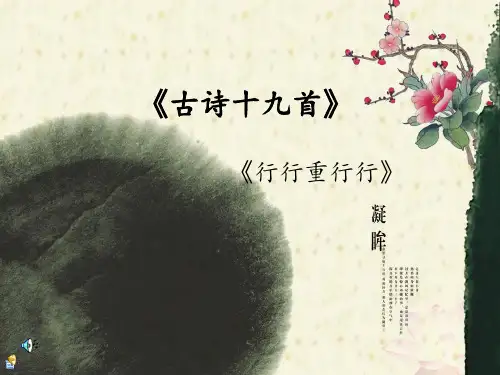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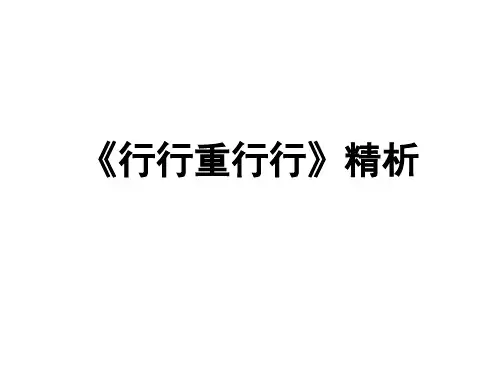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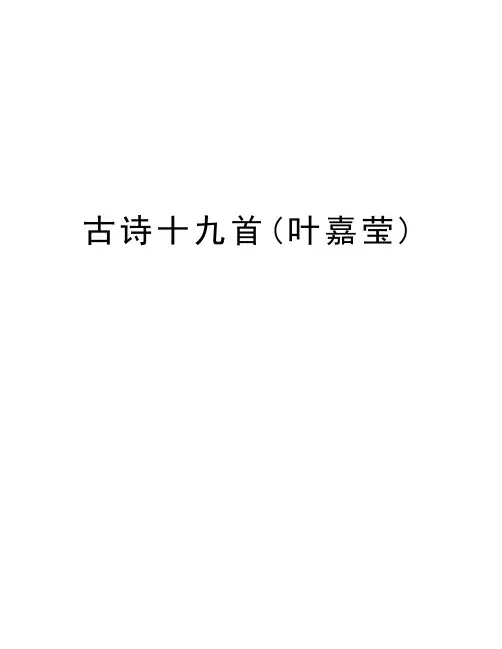
古诗十九首(叶嘉莹)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所写的感情基本上有三类:离别、失意、人生的无常。
《行行重行行》之一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也可写作“行行复行行”)《青青河畔草》之二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中国古代有一句成语叫作“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一个人的一生,总要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在中国的传统中,男子生命的价值就是得到别人的知赏和任用,很多人终生都在追求这个理想,包括像李太白那样不羁的天才。
而女子一生一世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就在于得到一个男子的赏爱,所以女子的化妆修饰都是为赏爱自己的人而做的。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这个女子把自己打扮得如此美丽,而这种做法也就暗示了她的心中有一种对感情的追求。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只追求感情上的满足,而有的人宁可忍受感情上的孤独寂寞,所要追求的乃是理想上的满足。
陶渊明也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伟大诗人。
他之所以耐得住寂寞,是因为内心之中有自己真正的持守。
他知道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不在乎那些世俗的名誉地位,不在乎别人对他说些什么,甚至也不在乎生活的贫穷潦倒。
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管是干事业还是做学问,都需要有一种勤勤恳恳和甘于寂寞的精神。
但有些人是耐不住寂寞的,为了早日取得名利地位,往往不择手段地去表现自己,所谓“尽快打出一个知名度来”,而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有时候就会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结局。
所以,这一首诗所写的乃是人生失意对你的考验,当然这也属于人生之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青青陵上柏》之三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考点06 实用类文本阅读—访谈类(练)(一)热身练一、【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师大附中高三上学期检测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对话杨庆祥: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访谈嘉宾:杨庆祥(评论家、学者、诗人)凤凰文化:是怎么想要提出“新伤痕文学”这个概念的?杨庆祥:首先,我已经注意到了有大量的作品在书写“改革开放”这段历史,而且在书写的过程中涉及到伤痕的问题。
这些作品中包括前辈作家余华的«第七天»,阎连科的«炸裂志»和最新的作品«日熄»,还包括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又发现整个批评界或者说整个文化界并没有对这种倾向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
只是从非常简单的社会学角度———比如70后、80后等等———来划分的。
我恰恰认为中国当下所谓的“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00后” 其实都是同一代人,他们都在面临整个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伤痕或阵痛。
他们分享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结构,在他们的表达里面有共同的诉求。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新伤痕文学”之所以出现的重要历史语境,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凤凰文化:既然今天主要聊“新伤痕文学”,那我们先从“旧” 的伤痕文学说起。
伤痕文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文革”的历史创伤),它是一个比较短命的文学现象,当时比较重要的作品如«班主任»、«伤痕»,现在看起来是文学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
那么属于“新伤痕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也会具有相似的局限或者说遗憾吗?杨庆祥:八十年代的旧伤痕文学有个很大的局限,对事件的描述大于对人的描述,这就导致了它变成一个非常短暂的潮流。
当然它当时被终结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
“新伤痕文学”应该从中吸取它的教训。
比如余华的«第七天»,在我的定义范畴里面它一定是“新伤痕文学”。
但如果“新伤痕文学”止步于余华的«第七天»,它可能也会变成一个短命的文学现象。
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所写的感情基本上有三类:离别、失意、人生的无常。
《行行重行行》之一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也可写作“行行复行行”)《青青河畔草》之二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中国古代有一句成语叫作“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一个人的一生,总要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在中国的传统中,男子生命的价值就是得到别人的知赏和任用,很多人终生都在追求这个理想,包括像太白那样不羁的天才。
而女子一生一世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就在于得到一个男子的赏爱,所以女子的化妆修饰都是为赏爱自己的人而做的。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这个女子把自己打扮得如此美丽,而这种做法也就暗示了她的心中有一种对感情的追求。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只追求感情上的满足,而有的人宁可忍受感情上的孤独寂寞,所要追求的乃是理想上的满足。
渊明也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伟大诗人。
他之所以耐得住寂寞,是因为心之中有自己真正的持守。
他知道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不在乎那些世俗的名誉地位,不在乎别人对他说些什么,甚至也不在乎生活的贫穷潦倒。
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管是干事业还是做学问,都需要有一种勤勤恳恳和甘于寂寞的精神。
但有些人是耐不住寂寞的,为了早日取得名利地位,往往不择手段地去表现自己,所谓“尽快打出一个知名度来”,而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有时候就会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结局。
所以,这一首诗所写的乃是人生失意对你的考验,当然这也属于人生之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青青陵上柏》之三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对《行行重行行》的文化解读摘要:《行行重行行》为《古诗十九首》的第一首,是东汉末年国家飘摇时期的一首家庭思妇诗。
诗中句子妙用叠词、化用先秦诗句、营造时空感并继承先秦比兴手法,思妇形象更是映射出汉末时代文化中的自主人格意识。
本文尝试从以上角度对《行行重行行》诗句进行文化解读。
关键词:《行行重行行》继承与发展汉末时代文化《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萧统的《文选》,是继《诗经》、《楚辞》之后我国古诗的又一大创造,其作者至今不明确,曹旭提出:“汉代主流文学样式是汉大赋而不是诗,当时的风气从汉武帝到文化人,只欣赏体式的恢弘开张,语言的金碧辉煌……因此,处于旁留,才秀人微,只能随写随弃。
”[1]马茂元认为“无论认为全部或者部分是枚乘作品,都是错误的。
无论指名为谁,都是处于传闻或臆测。
”[2]而陆机的拟作在西晋初期,由此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十九首写于东汉文人之手,并且不是一人所作。
刘勰一言“五言之冠冕”,五字道出《古诗十九首》作为五言诗的最高地位。
《行行重行行》为《古诗十九首》的第一首,是东汉末年国家飘摇时期的一首家庭思妇诗。
它延续着先秦诗风又创时空之感,它映射汉末时代文化又开启自主人格意识。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一、叠词、时空感与化用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作者开篇第一句连用两个叠词“行行”“行行”仅用单个“重”字连接,叠字重读的声调营造出一种音韵上特殊的空间感和时间感,“你走啊走,走了又走”没有着眼于年月的描写就巧妙的让我们知道她夫君离去的时间之久以及两人相隔之远。
“与君生别离”化用于《楚辞·九歌·大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活着却没有办法相聚一起,人死尚不能相见,但人活着却没有相见之期那该是多大的悲哀呀。
浠水实验高中2018届高三年级五月份第一次模拟考试语文试卷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9分)家规与国法崔永东“家规”与“国法"各有自己的领域,对稳定家族秩序和国家秩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社会,家规提倡“孝道”价值观,凸显家族利益至上,注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国法提倡“忠道”价值观,凸显国家利益至上,重视忠君爱国、无私奉献。
家规与国法之间在功能上又可以互相支撑,在内容上也可以互相补充.“家规"重在“修身、齐家”,“国法”重在“治国、平天下”,一个恪守家规的人必然能够遵守国法。
在此层面上,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
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家规连着国法。
家规是治家教子、修养心性、立身处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家训"“家戒”等内容,家训的内容旨在要求家人“必须怎么做”,家戒的内容旨在要求家人“不能怎么做”.以《河东裴氏家训》《河东裴氏家戒》为例:“立志向善,做贤子孙.贻谋燕翼,勿忘祖恩。
”“勤能补拙,俭以养廉。
丰家裕国,莫此为先。
秃惰奢靡,祸害无边。
”这就阐明了在家修身与在外治国的关联性,揭示了家规通向国法的功能性价值。
单从历史上看,家规与国法存在着很多的共同性,因其均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基础,维护儒家伦理秩序成为其共同的使命.无论是家规还是国法,它们都将儒家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转化成了制度安排,靠制度的力量来督促人们积极践行儒家道德,从而形成一种具有良风美俗的社会秩序。
家规的广义解释是家族法规,是所谓“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制定的法规,或称宗族法规。
宗族法规除了贯彻儒家伦理精神外,还凝聚了基层族群的“基本共识”,这种共识是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习惯性观念和规则,它们成了支配基层族群社会生活的“活法"。
在古代中国的广大基层社会,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往往是靠宗族组织依据“活法”进行调解之类的“准司法"活动加以化解的,此类准司法活动也可称之为“社会司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诚信教育。
孔子将道德教育置于教育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
其中的“信”就是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教育学生“主忠信”(《论语·学而》),即以诚信教育为主。
古人的诚信教育首先是在家庭里从蒙学开始,从婴幼儿抓起,以胎教、父范母仪、生活日用及讲故事等多种形式实现诚信教化。
婴幼极善模仿,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中国古代的父范母仪特别强调家长对儿童的示范教育。
父母长辈常以讲故事的形式对儿童进行诚信教育。
中国古代的诚信故事俯拾即是.如商鞅立木、季札赠剑、管鲍之谊、范式守信等;也有不少因不守信用而败德坏身甚至亡国的故事,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颇具警戒作用。
传统社会重视学校系统的诚信教育,朱熹提出了完整的德育阶段学说。
从“小学”到“大学”是循序渐进的德育过程。
8至15岁受“小学”教育,16、17岁受“大学”教育。
两者的道德教育有不同的内容、方式和方法。
“小学”阶段只是“教之以事”,注重行为的训练;“大学”阶段就是“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有为忠信孝悌者”。
朱熹还编辑“圣经贤传”和三代以来的“嘉言善行”为《小学》,作为“小学”德育教材;编著《四书集注》为“大学”教材,后成为元之后科考的必读书目。
在不同年龄段施行不同水平层次的儒家经典教育,为学习包括诚信在内的价值观的萌发、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校诚信教育,不论是私塾、官学,还是书院,皆行“明人伦”,“成德为事”。
明清之际书院风起、私塾涌现,为进行系统的诚信道德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基础。
传统学校诚信教育注重人的行为、习惯的养成,反对空言说教,注重生活细节、表里如一。
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虽在道德教育上分歧很大,但都重视生活实践,强调对道德规范的认知和信服必须与生活实践相联系,做人做事不可脱节,朱子的“格致工夫”与王阳明的“事上磨”在一定程度上互通。
传统社会的礼俗文化承载着社会诚信教育的重要使命,是一种乡土社会中自然的教育,礼俗作为一种得宜的规范和生活方式,与法律、制度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道德,有时甚至会超越道德的权威和效力。
叶嘉莹:《行行重行行》今天我们一起欣赏《古诗十九首》的第一首《行行重行行》,我先把它读一遍: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这首诗从开头到“越鸟巢南枝”的“枝”,押的是平声支韵,接下来从“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到结尾就换了仄声韵。
其中“远、缓、反、晚”四个韵脚都是上声,而“饭” 是去声。
这是因为,古代没有上声和去声的区别,“饭”也可以读成fan 。
我曾说,《古诗十九首》所写的都是人类感情的“基型”和“共相”。
所以你们看这里很妙:“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是一个男子的口吻还是一个女子的口吻是一个行者的口吻还是一个留者的口吻?中国古代传统的习惯总是喜欢先把它确定下来,所以才有很多人总是想方设法给这十九首诗确定作者。
上次我说过,有人认为其中的好几首都是枚乘写的。
那么枚乘既然是个男子,就可以确定这几首诗都是有寓托的,都是表示某种国家、忠爱之类的意思。
可是现在我们最好先把这些都放下,只看诗的本身,我们就会发现:正是由于我们不知道这首诗所写的是男子说的话还是女子说的话,是行者说的话还是留者说的话,结果反而给这首诗增加了许多的“潜能”。
“潜能”是西方接受美学中的一个词语,意思是作品中有一种潜存的能力,或者说,它潜藏有很多使读者产生联想的可能性。
另外,从《行行重行行》我们还可以看到《古诗十九首》那种质朴的特色。
它没有很多花样,走了就是走了,不管是送行者说的也好,还是远行者说的也好,总而言之是两个人分离了。
“行行重行行”,行人走啊走啊,越走越远。
我以前讲过,中国的旧诗有古体和近体之分。
近体是从南北朝以后才逐渐形成的,规定有比较严格的格律,如“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等。
因为中国文字是独体单音,读起来缺乏韵律,所以必须写成平仄间隔的形式,读起来才好听。
不过,在古诗里没有这种法则。
而且,如果你的内容果然很好,你的声音果然能配合你的感情,那么即使没有这些法则也一样能写出好诗。
“行行重行行”,就完全不符合格律诗的法则。
首先,这五个字里有四个字是重复的;其次,这五个字全是阳平声,一点儿也没有声音的起伏和间隔。
然而我说,正是如此,这五个字读起来才形成一种往而不返的声音。
——这话真是很难讲清楚。
那远行的人往前走再往前走,前边的道路是无穷无尽的,而后边留下的那个人和他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
这就是往而不返,从这里边就使你感受到一种把两个人越拉越远的力量。
如果说,“行行重行行”写出了两个人分离的一个基本的现象,那么“与君生别离”就是写由这种现象所产生的痛苦了。
所谓“生别离”,可以有两种讲法,现在我们先说第一种。
人世间的别离有生离也有死别,二者哪一个更令人悲哀呢?大家一定会说:当然是死别,因为生别还有希望再见,而死者是再也不能够复返了。
但现在我要举《红楼梦》中的一个例子来做相反的证明。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死了,贾宝玉糊里糊涂地和薛宝钗结婚了,但他心里老想着黛玉,所以他的病总是不好,神智总是不清楚。
于是有一天薛宝钗就痛痛快快地告诉宝玉说:“你不要再想你的林妹妹了,你的林妹妹早就死了! ”宝玉当时就昏过去了。
大家都责备宝钗不应该故意给宝玉这样大的打击,宝钗却说:“倘若总是不敢对他说明真相,那么他心里就永远不能安定,病也就永远不能好。
今天我告诉了他,他虽然如此痛苦,可是从此以后他这种思念就断了,他的心也就安定下来了。
”你看,宝钗这个人是很有办法也很有道理的。
后来,宝玉的病果然就好了。
所以,死别往往是一恸而绝,而生离则是在你的有生之年永远要悬念,要悲哀。
哪一个更痛苦呢?“生别离”的“生”还有另外的一种讲法,就是“硬生生”——硬生生地被分开了。
现在我打开我手中的这本书,这不叫“硬生生”地分开,因为这两页本来就不是黏结在一起的,不用费力就把它们分开了。
但我把这根粉笔掰开,这就叫“硬生生”地分开,因为它本来紧密地连接为一体,我是用力量硬把它分开的。
这对于物体来说当然无所谓,但对于两个亲密无间的人来说,就是很大的痛苦了。
那么“与君生别离”的这个“生别离”到底用哪一种讲法更好呢?我以为两种都可以。
因为这首诗的特点就是在语言上给读者提供了多方面理解的可能性,你只须用你的直觉读下去就行了,也许这两种感受同时都存在。
接下来“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说的是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之后的事情。
你看,这就是十九首之往复缠绵了,他在叙述了离别和离别的痛苦之后,又停下来进行一个反思。
这个“涯”字读yí 在这里是押的“支”韵。
他说现在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有万里之遥,我在天的这一头,而你在天的那一头,那么今后还有再见面的可能性吗?他经过反思所得出的判断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道路如此艰险而且遥远,要想再见面是很难的了。
要知道:假如仅仅是道路遥远,那么只要你有决心走下去,也许还能有一半的希望,然而现在存在了双重的困难,不但道路如此遥远,而且充满了艰难险阻——所谓“阻”,既可能是高山大河的自然界的险阻,也可能是战乱流离的人世间的险阻。
人的能力是多么有限,怎能敌得过这些无穷无尽的险阻呢! 说到这里,可以说已经不存在什么见面的希望了,就如陈祚明所说的“今若决绝,一言则已矣,不必再思矣”。
然而诗人却不肯放下,他忽然从直接叙事之中跳了出来,用两个形象的比喻来表现他的无法决绝——“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这是“比兴”的方法,“胡马”和“越鸟”两个形象用得真是很有姿态。
在古诗和汉魏乐府中,经常运用这样的方法:在绝望的悲哀之中突然宕开笔墨,插入两句从表现上看上文与下文都不甚连贯的比喻。
例如《饮马长城窟行》,在一路叙写离别相思之苦以后,突然接上去“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似乎与上下文全不衔接,也未作任何指实的说明。
可是,这两句能够使读者产生多方面的联想,作多方面的解释,因此,就使前边所写的现实的情事蓦然之间都有了一种回旋起舞的空灵之态。
这其实是一种很高明的艺术手法,也是古诗和汉魏乐府的一个特色。
而且,在古诗和乐府中,这类比喻多半取材于自然现象。
例如,“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都是自然界中司空见惯的现象,是向来如此、难以改变的事情,用这些形象来做比喻,且不论其喻意何在,只是在直觉上就已经给读者一种仿佛是命里注定一样的无可奈何之感了。
所以,古诗和汉乐府中的这一类比喻,往往既自然质朴,又深刻丰美。
对“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两句,古人有不同的讲法。
李善的《文选注》引《韩诗外传》说:“诗云‘ 代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 ,皆不忘本之谓也。
”但这“不忘本”又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从远行者的角度来看,当然是从正面写他的思乡念旧之情;从留居者的角度来看,则是说胡马尚且依恋故乡的北风,越鸟尚且选择遥望故乡的南枝,你作为一个游子,怎么能忘记了故乡和故乡的亲人呢? 这是从反面来作比喻的。
第二种说法认为,它来源于《吴越春秋》的“胡马依北风而立,越燕望海日而熙”。
这是取同类相求的意思。
就是说,“云从龙,风从虎”,所有的东西都有它相依相恋不忍离去之处;而我和你本来也是相亲相爱的一对,怎么竟然会分离这么久而不能再结合到一起呢?还有一种说法,是隋树森引纪昀所说的“此以一南一北申足‘ 各在天一涯’ 意,以起下相去之远”。
这种说法是把出处和取意都抛开不论,只从字面上看,胡马和越鸟一南一北,在直觉上就使读者产生一种南北睽违的隔绝之感。
有这么多不同意见并不是坏的,它说明,正是由于这两句的比喻给予读者十分简明真切的意象,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多的联想。
在这些联想中,既有行者对居者的怀念,也有居者对行者的埋怨;既有相爱之人不能相依的哀愁,也有南北睽违永难见面的悲慨。
此外,由于前面说到“会面安可知”,似乎已经绝望,所以这两句放在这里还给人一种重新点燃希望的感觉,鸟兽尚且如此,我们有情的人难道还不如鸟兽吗? 而且你们还要注意,这两句虽然用了《韩诗外传》和《吴越春秋》的古典,但它同时也是民间流传的比喻,你不用考证古典也一样可以明白。
对这两句,如果你想向深处追求,它可以有深的东西供给你,如果你不想向深处追求,也一样可以得到一种直接的感动。
它把古、今、雅、俗这么多联想的可能性都混合在一起了,这是它的微妙之处。
我以为,诗十九首》本来是民间流传的诗歌,但后来经过了文士的改写和润色。
就像屈原改写九歌一样,那并不是有意的造作,而是这些诗的感情很能感动人,当文士吟诵这些民间诗歌时,内心中也油然兴感——即所谓“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因此产生了共鸣,从而才亲自动手来加以修改和润色。
我想,这也正是《古诗十九首》既可以深求也可以浅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从“行行重行行”到“越鸟巢南枝”是一个段落,前边都是平声韵,接下来从“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就换了仄声韵。
从内容上来说,经过“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这么一个想像的飞扬回荡之后,现在他又回到了无法改变的现实之中,因此就产生了更深的悲慨。
词人冯正中有一句词说“天教心愿与身违”,事实与你的盼望往往是不相符合的。
日子正在一天一天地过去,尽管你不放弃希望,尽管你打算等到海枯石烂的那一天,可是人生有限,你能够等得到那一天吗?在这里,“相去日已远”和前边的“相去万余里” 乎是一个重复,但实际上并不是简单重复。
因为“万余里” 虽然很远,但毕竟还是一个有限的数字,而且它所代表的只是空间,并没有时间的含义,而“日已远”三个字则进一步用时间去乘空间,所得数字就更是无穷无尽了。
而且更妙的是,这“日已远”三个字又带出了下一句的“日已缓”,从而使人感到:离人的相思与憔悴也是一样无穷无尽的。
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也许就是从此句变化出来的。
但柳永的那两句却未免带有一些着力刻画的痕迹。
而且那个“悔”字还隐隐含有一些计较之念,不像“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在外表上所写的只是衣带日缓的一件事实,内中却含有一种尽管消瘦也毫无反省、毫无回顾的意念。
倾吐如此深刻坚毅的感情,却出以如此温柔平易的表现,这就更加令人感动。
如果说前边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两句之中含有一种希望的想像,是向上飞的;那么接下来的“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两句之中就含有一种失望的想像,是向下沉的了。
我以为,这两句是这首诗中最令人伤心的地方。
因为,前边所写的离别只是时间与空间的隔绝,两个相爱的人在情意上并没有阻隔,所以虽然离别,却也还有着一份聊以自慰的力量,而现在连这种自慰的力量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他说,天上太阳的光芒那么强烈,但也有被浮云遮住的时候;那么,美好亲密的感情就没有被蒙蔽的时候吗?而且那远行的游子不是果然就不回来了吗?这个“游子不顾反”的“顾”字,有的版本作“愿”,但我以为应该是“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