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 格式:ppt
- 大小:2.83 MB
- 文档页数:19

《北大回忆》一书中的硬伤作者:刘运峰段煜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10期北大回忆,张曼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张曼菱的《北大回忆》是一本好书。
在这本书中,作者以饱满的热情和深厚的感情,写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北大的人和事。
但遗憾的是,这本书也存在不少的差错,有的还是硬伤,给人以很不舒服的感觉。
本文就其明显的硬伤,分述于下。
一、引文的差错尽管散文的写作不像学术论文那样规范和严格,但是对于引用的主要诗文,必须做到准确无误,否则就会以讹传讹,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唐代王勃《滕王阁序》中有一句著名的话:“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北大回忆》的作者对这句话也非常喜欢,因此多次引用,可惜的是,几次引用均和原文存在差异。
如第89页中作者写道:“…穷且不堕青云之志‟。
打开天地就不穷,广交师友就不穷。
”第388页,作者书中有“刘孚坤学长有一种…穷且不堕青云之志‟的狂气”。
第136页:“他在我的心目中可谓应了一句话:…穷且不坠青云之志‟”。
两处“不堕”均为“不坠”之误。
三处引文,都少了“益坚”两个字,这样一来,就不是王勃的原话了。
第102页作者曾引用了这样的话:“…望鹌鹚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
(《楚辞》)”。
“鹌鹚”应为“崦嵫”,“《楚辞》”应为“《离骚》”。
鲁迅早年,曾从《离骚》中的“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和“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集出一副对联,那就是“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
鲁迅请教育部的同事乔大壮(字曾劬)书写出来,挂在了他的“老虎尾巴”里,用来激励自己珍惜光阴。
上联中的“崦嵫”为山名,即今甘肃天水之齐寿山,传说是太阳落下的地方。
第112页引王力先生诗:“红羊溅汝绞绡泪,白药医吾铁杖伤。
”其中“绞绡”应为“鲛绡”。
鲛绡是传说中鲛人所织的薄纱。
鲛即鲛人,绡为丝质薄纱。
王力先生的这首诗,收录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二十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手迹》,可参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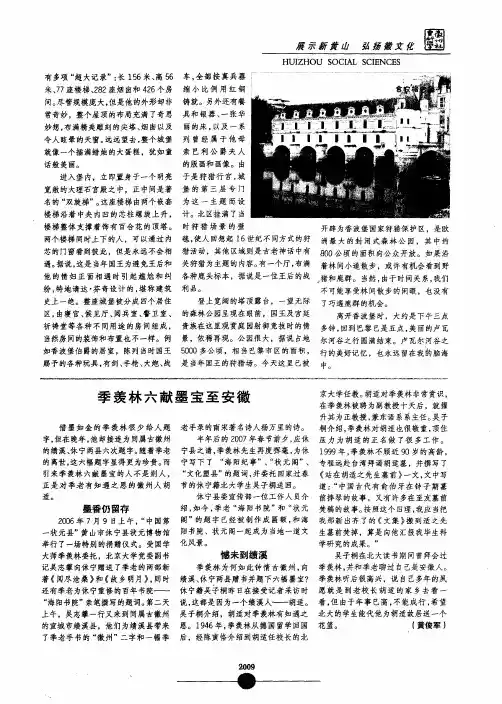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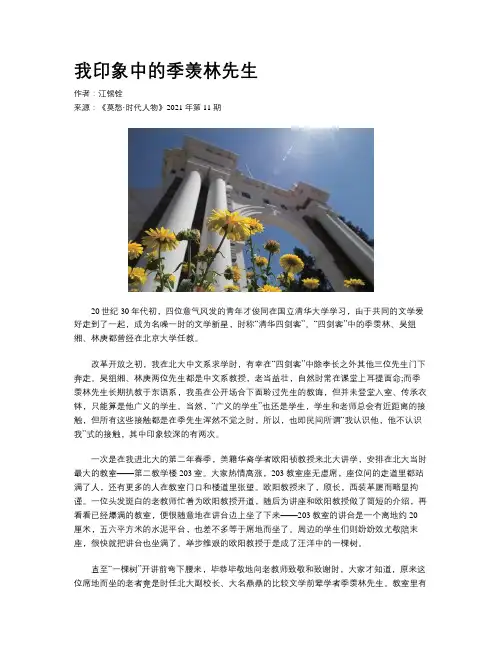
我印象中的季羡林先生作者:江锡铨来源:《莫愁·时代人物》2021年第11期20世纪30年代初,四位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同在国立清华大学学习,由于共同的文学爱好走到了一起,成为名噪一时的文学新星,时称“清华四剑客”。
“四剑客”中的季羡林、吴组缃、林庚都曾经在北京大学任教。
改革开放之初,我在北大中文系求学时,有幸在“四剑客”中除李长之外其他三位先生门下奔走。
吴组缃、林庚两位先生都是中文系教授,老当益壮,自然时常在课堂上耳提面命;而季羡林先生长期执教于东语系,我虽在公开场合下面聆过先生的教诲,但并未登堂入室、传承衣钵,只能算是他广义的学生。
当然,“广义的学生”也还是学生,学生和老师总会有近距离的接触,但所有这些接触都是在季先生浑然不觉之时,所以,也即民间所谓“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式的接触,其中印象较深的有两次。
一次是在我进北大的第二年春季,美籍华裔学者欧阳祯教授来北大讲学,安排在北大当时最大的教室——第二教学楼203室。
大家热情高涨,203教室座无虚席,座位间的走道里都站满了人,还有更多的人在教室门口和楼道里张望。
欧阳教授来了,颀长,西装革履而略显拘谨。
一位头发斑白的老教师忙着为欧阳教授开道,随后为讲座和欧阳教授做了简短的介绍,再看看已经爆满的教室,便很随意地在讲台边上坐了下来——203教室的讲台是一个离地约20厘米,五六平方米的水泥平台,也差不多等于席地而坐了。
周边的学生们则纷纷效尤敬陪末座,很快就把讲台也坐满了。
举步维艰的欧阳教授于是成了汪洋中的一棵树。
直至“一棵树”开讲前弯下腰来,毕恭毕敬地向老教师致敬和致谢时,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位席地而坐的老者竟是时任北大副校长、大名鼎鼎的比较文学前辈学者季羡林先生。
教室里有些轻微的骚动,但很快也就平静下来了。
我这才仔细地看了看季先生:面貌清癯,神情蔼然,着一件那个年代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洗得有些褪色的蓝涤卡中山装,戴一顶同样颜色的解放帽,所有的纽扣,包括风纪扣都系得严严实实。

胡适生平轶事胡适生平轶事羡林评语季羡林曾评价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并举一小事称,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百年潮》,1999年第7期,第14页)。
理性抗议1915年,在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中,出现了很多要与日本决一死战的言论。
胡适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劝学生切不可鲁莽,乱了分寸……此时言及作战……不仅于国无所改观,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躏(《胡适全集》第28卷第89-90页)。
赞扬张謇1929年,胡适赞扬民族实业家张謇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寄托国联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后,胡适一度天真地认为国联可以调停战争,并取消满洲国,到了1933年日本拒绝国联的调解并且退出国联之后,他才不主张与日本交涉。
可是,当他看到中日实力差距过大,预想到战争对国家的破坏后,又说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
(《胡适全集》第21卷第600-601页)错误立场九一八事件发生一年后,胡适发表《日本人应该醒醒了!》。
他说中国民族还是不会屈服的,日本的暴行只会让中国变成日本永久的敌人,日本人彻底忏悔侵略中国,是征服中国的唯一的办法(《胡适全集》第21卷第586-588页)。
鲁迅先生在用何家干笔名发表的《出卖灵魂的秘诀》中痛斥他出卖灵魂,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对于鲁迅杀向胡适的言论和文章,胡适一贯都是采取不理,不驳。
不仅如此,胡适在鲁迅逝世后,反而为他辩护,阻止别人骂鲁迅。
胡适主张东三省问题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再说。
他情愿以东三省几千万同胞被日本侵略者蹂躏,资源被日本掠夺50年为代价,来支持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继续剿共50年。
(《胡适全集》第21卷第605页)1935年,胡适主张放弃东北三省,致信政府,建议承认伪满洲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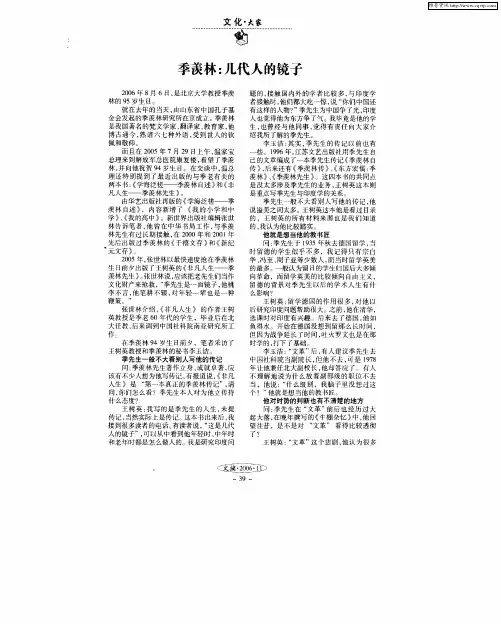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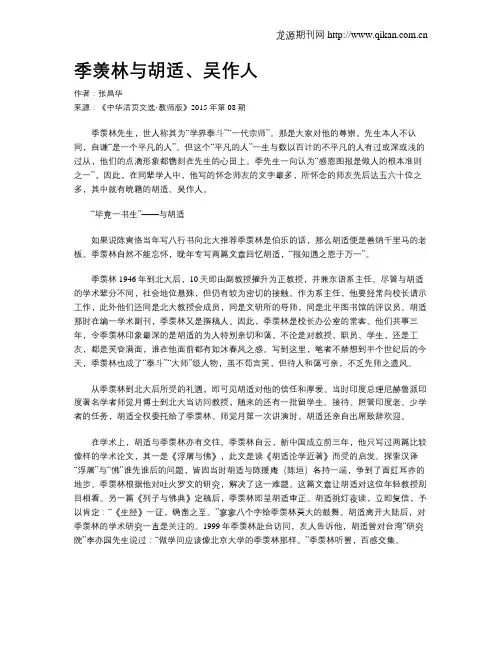
季羡林与胡适、吴作人作者:张昌华来源:《中华活页文选·教师版》2015年第08期季羡林先生,世人称其为“学界泰斗”“一代宗师”。
那是大家对他的尊崇。
先生本人不认同,自谦“是一个平凡的人”。
但这个“平凡的人”一生与数以百计的不平凡的人有过或深或浅的过从,他们的点滴形象都镌刻在先生的心田上。
季先生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因此,在同辈学人中,他写的怀念师友的文字最多,所怀念的师友先后达五六十位之多,其中就有皖籍的胡适、吴作人。
“毕竟一书生”——与胡适如果说陈寅恪当年写八行书向北大推荐季羡林是伯乐的话,那么胡适便是善纳千里马的老板。
季羡林自然不能忘怀,晚年专写两篇文章回忆胡适,“报知遇之恩于万一”。
季羡林1946年到北大后,10天即由副教授擢升为正教授,并兼东语系主任。
尽管与胡适的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但仍有较为密切的接触。
作为系主任,他要经常向校长请示工作,此外他们还同是北大教授会成员,同是文研所的导师,同是北平图书馆的评议员。
胡适那时在编一学术副刊,季羡林又是撰稿人。
因此,季羡林是校长办公室的常客。
他们共事三年,令季羡林印象最深的是胡适的为人特别亲切和蔼。
不论是对教授、职员、学生,还是工友,都是笑容满面,谁在他面前都有如沐春风之感。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季羡林也成了“泰斗”“大师”级人物,虽不苟言笑,但待人和蔼可亲,不乏先师之遗风。
从季羡林到北大后所受的礼遇,即可见胡适对他的信任和厚爱。
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到北大当访问教授,随来的还有一批留学生。
接待、照管印度老、少学者的任务,胡适全权委托给了季羡林。
师觉月第一次讲演时,胡适还亲自出席致辞欢迎。
在学术上,胡适与季羡林亦有交往。
季羡林自云,新中国成立前三年,他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其一是《浮屠与佛》,此文是读《胡适论学近著》而受的启发。
探索汉译“浮屠”与“佛”谁先谁后的问题,皆因当时胡适与陈援庵(陈垣)各持一端,争到了面红耳赤的地步。

5“文革”初期的一天,“头号反动学者”胡适的故居,安徽绩溪县上庄村突然空气紧张起来,原来从北京专程赶来一大帮“红卫兵小将”,气势汹汹地要挖掘胡适之父胡传的坟墓,以彻底肃清胡适的反动流毒。
挖人家祖坟,在农村人看来可是件丧德的骇人之举,但对于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将”们这一“革命”行动,谁又能出面过问一二?胡传的坟墓很快被掘开,可是墓中的情景却让所有在场的人大吃一惊,眼前竟是具无头之骸,这是怎么回事?众人顿时如坠烟雾。
作为名人的胡适,不少人都曾为他写过传记,其中包括张经甫、罗尔纲、李敖、唐德刚等知名学者。
在这众多的胡适传记中,都提及胡适之父胡传之死,又都称其是病逝,特别是张经甫所撰的《胡铁花(传)先生家传》对此记叙得更为详细。
然而,在胡传死后七十多年,被人掘开坟墓,竟然是具无头之尸,这就不能不令世人怀疑他的死因了。
胡传,字守三,一字铁花,号钝夫,家乡人都称其“珊先生”或“铁花公”。
胡传有兄弟五人,传为老大,自小淳朴,且聪明颖悟。
胡传长大后,刚直不阿,遇事敢为,乡里一些二流子都敬畏他,后五次赴南京应试,却屡试不果,便在家乡过着亦耕亦读的生活。
光绪八年(1882),由在京任兵部主事的族中至亲胡宝铎介绍,投奔驻防宁古塔的吴大澂,胡传千里迢迢赴东北,吴大澂一见大为惊叹说:“绝寒数千里无人烟,孑孤身何以能至?”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吴非常赏识胡传的人品和才识,称其“实为国家干济之才”。
但不久因母亲病逝,复归家守孝。
守孝期满,适逢吴大澂调为河南山东河道总督,要胡传赴郑州工地管理治河工程,胡传整天奔走于河堤之上,结果,治理黄河的经费,只花费了原来预算的一半。
自此,吴大澂对他更加器重,全力奏保,先后任知州、知府。
光绪十六年(1890),胡传调职赴台湾,任台东直隶州知州,兼领台东镇海后山军务,历任三年,军民大治。
次年(1891)胡适的母亲率领儿子们也赴台湾,同行的还有胡传的同宗至交兼家庭教师胡宣铎,及其幕友胡郎山,此外还有胡传的书童胡景全等人,胡景全专门负责跟随左右,照料胡传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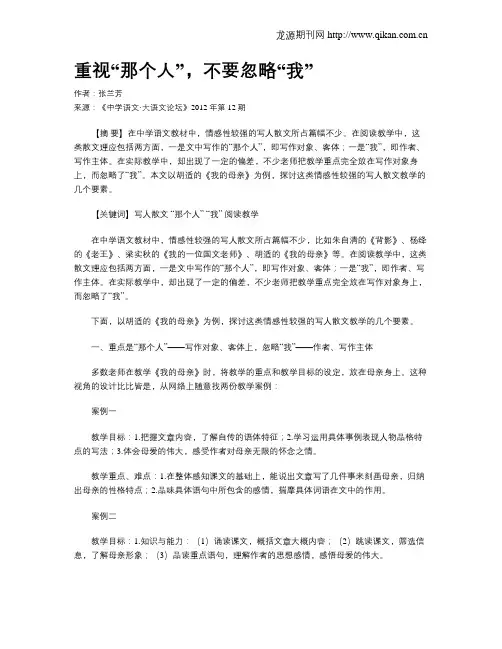
重视“那个人”,不要忽略“我”作者:张兰芳来源:《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2012年第12期【摘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情感性较强的写人散文所占篇幅不少。
在阅读教学中,这类散文理应包括两方面,一是文中写作的“那个人”,即写作对象、客体;一是“我”,即作者、写作主体。
在实际教学中,却出现了一定的偏差,不少老师把教学重点完全放在写作对象身上,而忽略了“我”。
本文以胡适的《我的母亲》为例,探讨这类情感性较强的写人散文教学的几个要素。
【关键词】写人散文“那个人” “我” 阅读教学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情感性较强的写人散文所占篇幅不少,比如朱自清的《背影》、杨绛的《老王》、梁实秋的《我的一位国文老师》、胡适的《我的母亲》等。
在阅读教学中,这类散文理应包括两方面,一是文中写作的“那个人”,即写作对象、客体;一是“我”,即作者、写作主体。
在实际教学中,却出现了一定的偏差,不少老师把教学重点完全放在写作对象身上,而忽略了“我”。
下面,以胡适的《我的母亲》为例,探讨这类情感性较强的写人散文教学的几个要素。
一、重点是“那个人”——写作对象、客体上,忽略“我”——作者、写作主体多数老师在教学《我的母亲》时,将教学的重点和教学目标的设定,放在母亲身上。
这种视角的设计比比皆是,从网络上随意找两份教学案例:案例一教学目标:1.把握文章内容,了解自传的语体特征;2.学习运用具体事例表现人物品格特点的写法;3.体会母爱的伟大,感受作者对母亲无限的怀念之情。
教学重点、难点:1.在整体感知课文的基础上,能说出文章写了几件事来刻画母亲,归纳出母亲的性格特点;2.品味具体语句中所包含的感情,揣摩具体词语在文中的作用。
案例二教学目标:1.知识与能力:(1)诵读课文,概括文章大概内容;(2)跳读课文,筛选信息,了解母亲形象;(3)品读重点语句,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感悟母爱的伟大。
2.过程与方法:(1)学生听故事,走近母亲;(2)学生读课文,了解母亲形象,体会作者思想感情;(3)学生看图片,体会母爱的伟大,表达自己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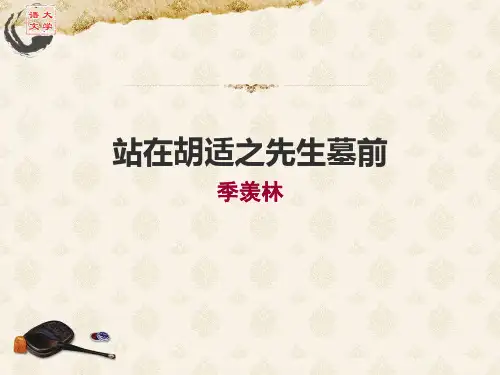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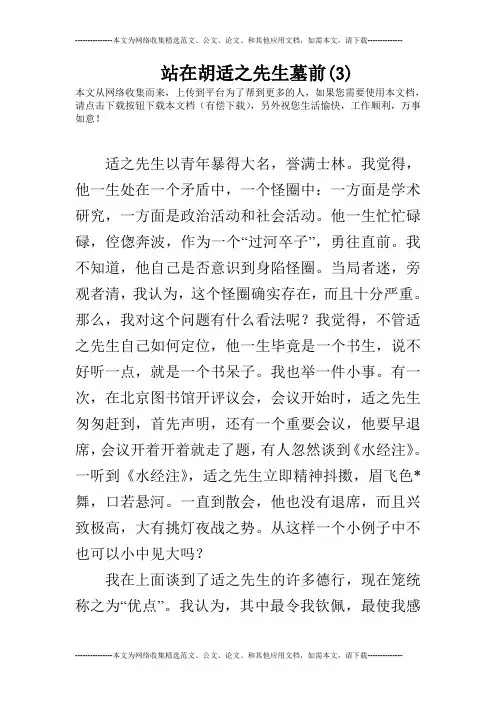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3)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
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
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
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
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我也举一件小事。
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
一听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
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
从这样一个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见大吗?我在上面谈到了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现在笼统称之为“优点”。
我认为,其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他正是这样一个人。
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讲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师”;另一方面却又有老虎拜猫为师学艺,猫留下了爬树一招没教给老虎,幸免为徒弟吃掉的民间故事。
二者显然是有点矛盾的。
适之先生对青年人一向鼓励提挈。
四十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当时还是青年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为赞赏。
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也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
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所表现,但是,格于形势,不免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
季羡林,被放大的公共知识分子季羡林先生的这些意见,尽管并非妄语或谀辞,但是没有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思考,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也就谈不上什么真知灼见。
他为自己在历次运动中“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而感到欣慰,固然良知未泯,却也容易鼓励犬儒主义。
涉及公共利益的真话不能全讲,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应该是欣慰,而应该是耻辱和愤怒。
季羡林先生的辞世,在社会公众中掀起一股悼念的热潮。
有学者不无遗憾地说,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成就。
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不了解,悼念之情从何而来?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就自不待言。
他留学德国回来时,年方36岁,就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及东方语言学系系主任,也是该系的创建人。
他的学术功底扎实,治学方法严谨,据称深得时任校长的胡适先生的欣赏。
但是,跟同辈学人相比,季先生在社会公众中并没有那么大的名气。
我想原因有这样几点:一,当时的北大人才济济,群星闪耀,以才情论,他并非最亮的那几颗之一;二,他的专业为印度语言学,他研究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文字,对于一般人来说如同天书;三,他为人谦逊,作风素朴,不沽名钓誉。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
十多年前,季先生突然在媒体上走红起来。
原因比较复杂,大抵有以下几种:一,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之后,治学严谨的学者所剩无多,都兀然耸立起来,被尊为大师;二,中国社会有敬老的传统,他年岁已高,著述颇丰,仍笔耕不辍,又平易近人,尤其令人尊敬;三,最重要的是,他被人误解或者利用,幻化为时代思潮中公众所渴望的大师。
人们对季先生至少有两大误会或者利用。
一是他的专业是印度学,却被误指为“国学”,符合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学被压制、国学被弘扬的社会环境,也满足了社会公众的虚骄之气。
因为“国学大师”的头衔,他受到了更多的尊敬和礼遇。
显然,凭着那代学人的学术良知,他为此感到不安。
在两年前出版的《病榻杂记》中,他要求摘去“国学大师”、“国宝”、“学术泰斗”三顶帽子。
冰心写景散文摘抄赏析(文档6篇)以下是网友分享的关于冰心写景散文摘抄赏析的资料6篇,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就爱阅读感谢您的支持。
第1篇这个季节,没有百花争艳,没有杜鹃泣血,只有霏霏的淫雨,只有簌簌的落花……尔后,带着浅浅的缤纷的落花随着徘徊的匆匆的流水从我心间淌过,并且将永远的流向远方……又是一个流火的夏日,又是一个有雨的日子,一切变得那么熟悉,却又是那么的陌生。
转眼间,三年的初中生活已经结束了,并且将慢慢地成为历史。
一切都只有等她远逝的时候,才会觉得亲近,觉得她弥足的珍贵。
四季无休止地在轮回,而我最美好、最宝贵的三年初中生活已经在谈笑间过去了。
不管我曾爱过还是恨过,不管我曾欢乐过还是郁闷过,但在冥冥中早已注定,我要与这初中校园有着深深、深深的缘分,因为这里,永远地记载了我最宝贵的三年青春,这里有太多的记忆会让我莫名的感动,这里留有我最鲜活的生活和最跃动的人生。
雨依旧在下,不曾停过。
一不小心,耳畔忽然响起了辛晓琪的那首《领悟》:如果可能,我还想说,被爱也爱过,我生活、我摸索,曾得到、曾失落,我珍惜、我付托,无论什么结果。
我曾爱过也恨过,曾欢乐过也郁闷过。
曾被许多人爱过的我已记不清了,只有我爱过的永远在心底保有一丝甜美;曾恨过许多人我已记不清了,只有被恨过的总让我感到一份愧疚;曾经历的无数坎坷我已记不清了,只有一次次的帮助、感动、泪水及欢乐还历历在目。
从前都是一群赶路的人,都争先恐后的在跳动的故事里烙上了脚印。
从前的日子我从不曾仔细看过,但当她随水东流之后我细细品味,才蓦然的发现原来你我竟是如此的纯真、如此的亲近、如此的可爱!雨停了,但落花却远逝了。
太阳开始初露笑脸,我望望前路,心中一阵暖流涌过,使我充满了无限的信心;当我再一次回首,想起这落花的心事,猛然间,眼前又一次模糊了,我的心中又充满了所有的伤楚和柔情……第2篇二月尽了,春天才姗姗地来,没有阳光的天空,氤氲着一层薄薄的雾气,渐渐地凝结成看不见的水珠,润湿了蓬松的地面。
龙源期刊网 影响学术大师一生的师友作者:来源:《教育与职业·综合版》2011年第07期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要受到各种各样人物的影响。
一个学术大师的成长更是要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其中师友的影响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在泰斗一级的学术大师的身上也是适用的。
季羡林先生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的长篇回忆文章中说:“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
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
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
”这六位恩师季羡林指出的是陈寅恪先生、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西克先生、胡适之先生、傅斯年先生、汤用彤先生。
事实上,对季羡林起过重大影响的恩师远不止这六位。
季羡林的老师给他的影响是关键性的。
正是由于所有这些恩师的培养和影响,造就了季羡林,成就了一个学术大师。
在季羡林的成才之路上,师友的作用大矣。
《荀子·大略》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
”清代诗人唐甄有言:“学贵得师,亦贵得友。
师者,犹行路之有导也;友者,犹涉险之有助也。
”(《潜书·讲学》)清代大学士李惺有言:“师以质疑,友以析疑。
师友者,学问之资也。
”《西沤外集·冰言补》谭嗣同在《浏阳算学馆增订章程》中告诫世人:“为学莫贵于尊师。
”在他们看来,从师是解答疑难,交友是辨析疑难,成才离不开师友。
以文会友、师友辅仁,这些用在季羡林的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
“人生而蒙,长无师友则愚。
是道义由师友有之,而得贵且尊,其义不亦重乎!其聚不亦乐乎!”柳宗元更认为所谓师生关系可以成为一种朋友关系;提出“交以为师”的主张,即以师为友,以友为师:师友并称,将师生关系转变为师友关系。
(《柳河东集》卷十九《师友箴》)宋代妙喜普觉、竹庵士硅二禅师于江西云门寺所辑录的《禅林宝训》有:“父母养汝身,师友成汝志。
新时期下的“我的朋友胡适之”作者:暂无来源:《廉政瞭望》 2011年第1期◎文_秦德君“我的朋友胡适之”是句很有分量的话。
胡适除了博学,就是平和而极有睿智。
他有“一多一少”。
“一多”,是他获得世界著名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多,有35个;“一少”,是身后财物少,除了102 箱的书籍,身后别无长物。
林语堂说:“胡适之先生在道德文章上,在人品学问上,都足为我辈师表。
一时的毁誉,他全不在乎。
”1962 年,胡适猝然逝世,季羡林后来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的文中,叹惜“仁者不寿”。
蒋介石对这位向自己提出过尖锐“不同意见”的文化巨擘,亲笔写下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当年,凡文人士子、贤达名流,皆以结识胡适为荣。
“我的朋友胡适之”,一时成为社会流行语,是一种社会“荣耀”。
胡适先生仙逝久矣,但有趣的是,“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个语式,今天似仍在进行着。
当然,它有了一些演化,与时俱进嘛。
试举几例——句式一:“我的朋友×××”(或“×××是我好朋友”)。
如:“上周,××部长(或主任、主席、书记)请我吃饭——他是我的好朋友,席间我们相谈甚欢,他给我敬了酒,我们喝的是人头马,饭后我们单独谈了好几分钟……”如:“本山是我好朋友……”,“老谋子(张艺谋)打电话来,要我出席酒会……”。
句式二:“我刚从××回来”(如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
“我刚从法国回来,参加了法国总统的一个私人聚会。
××与我聊了很长时间,我们谈了萨达姆喜欢吃的食品……”再如,“我在英国访问期间,××与我聊了很长时间——我们关系很好,属于无话不谈的那种,本来计划20 分钟,后来谈了2 个小时30 分钟零4 秒,秘书进来好几次……”句式三:“ 我被邀请参加××重要会议”。
如“最近被邀请参加一个内部高层会议,本来不想参加,但他们打电话来催了8 次,发伊妹儿来催了5 次,××亲自打电话来,一定要我参加,小范围的。
季羡林散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通用一篇季羡林散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1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
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__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
此时,__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
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们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还有点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__。
适逢北大校庆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孑民堂中,举行庆典。
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作了简短的讲话,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
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
大家相互开玩笑说:"__给北大放礼炮哩!"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往南京去了。
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我想改写一下,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
"我哪里知道,我们这一次会面竟是最后一次。
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话,这是含笑不起来的。
从此以后,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扬镳,"世事两茫茫"了。
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
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
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
据说__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没有能呆多久,"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他也逃往__。
后来又到__去住了几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它不复存在。
后来又回到__,最初也不为__所礼重。
往日"总统候选人"的迷梦,也只留下了一个话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
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散文
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散文
我在上面谈了一些琐事和非琐事,俱往矣,只留下了一些可贵的记忆。
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到了望九之年,居然还能来到宝岛,这是以前连想都没敢想的事。
到了台北以后,才发现,五十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老朋友,比如梁实秋、袁同礼、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等,全已作古。
我真是“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了。
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规律,是人力所无法抗御的。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
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挚友墓前焚稿的故事。
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
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但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
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
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
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颓唐之感。
我现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万里”之感。
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