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有感
- 格式:doc
- 大小:22.50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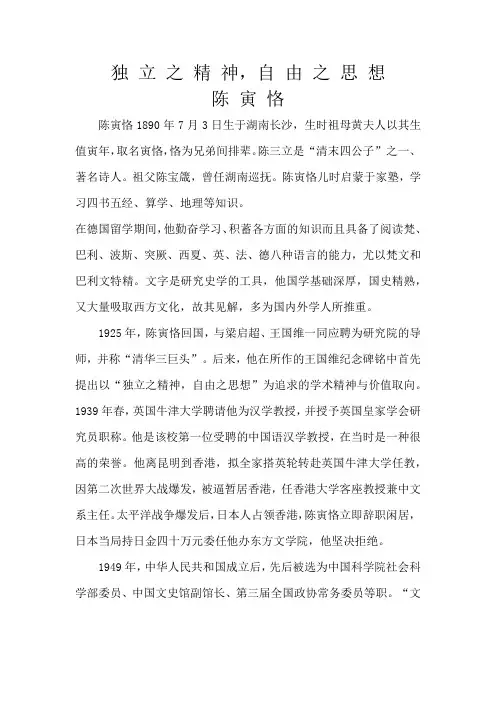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陈寅恪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辈。
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
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
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
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后来,他在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
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文革”开始之后,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
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陈寅恪去世,享年79岁。
摘录“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已。
其弟子手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
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
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
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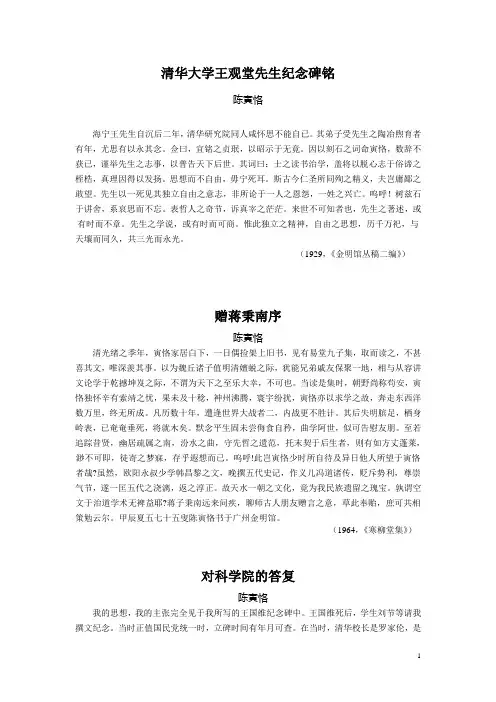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陈寅恪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
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
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
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
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
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929,《金明馆丛稿二编》)赠蒋秉南序陈寅恪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捡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
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蜕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
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
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
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
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
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
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蒋子秉南远来问疾,聊师古人朋友赠言之意,草此奉贻,庶可共相策勉云尔。
甲辰夏五七十五叟陈寅恪书于广州金明馆。
(1964,《寒柳堂集》)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

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已。
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
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
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
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
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附录: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的家里,汪钱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
汪钱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陈寅恪的一篇口述长文。
全文如下:对科学院的答复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
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集念。
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
在当时,清华校长罗家伦,他是二陈派去的,众所周知。
我当时是清华国学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字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
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扬。
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学说有错误是可以商量的,我对王国维也是如此。
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的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
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
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
我写给王国维的文中,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
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为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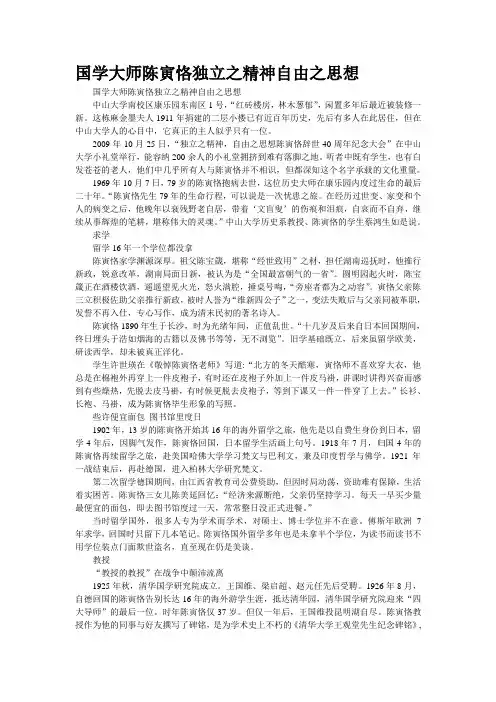
国学大师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国学大师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山大学南校区康乐园东南区1号,“红砖楼房,林木葱郁”,闲置多年后最近被装修一新。
这栋麻金墨夫人1911年捐建的二层小楼已有近百年历史,先后有多人在此居住,但在中山大学人的心目中,它真正的主人似乎只有一位。
2009年10月25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辞世40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山大学小礼堂举行,能容纳200余人的小礼堂拥挤到难有落脚之地。
听者中既有学生,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中几乎所有人与陈寅恪并不相识,但都深知这个名字承载的文化重量。
1969年10月7日,79岁的陈寅恪抱病去世,这位历史大师在康乐园内度过生命的最后二十年。
“陈寅恪先生79年的生命行程,可以说是一次忧患之旅。
在经历过世变、家变和个人的病变之后,他晚年以衰残野老自居,带着‘文盲叟’的伤痕和泪痕,自哀而不自弃,继续从事辉煌的笔耕,堪称伟大的灵魂。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的学生蔡鸿生如是说。
求学留学16年一个学位都没拿陈寅恪家学渊源深厚。
祖父陈宝箴,堪称“经世致用”之材,担任湖南巡抚时,他推行新政,锐意改革,湖南局面日新,被认为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圆明园起火时,陈宝箴正在酒楼饮酒,遥遥望见火光,怒火满腔,捶桌号啕,“旁座者都为之动容”。
寅恪父亲陈三立积极佐助父亲推行新政,被时人誉为“维新四公子”之一,变法失败后与父亲同被革职,发誓不再入仕,专心写作,成为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
陈寅恪1890年生于长沙,时为光绪年间,正值乱世。
“十几岁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
旧学基础既立,后来虽留学欧美,研读西学,却未被真正洋化。
学生许世瑛在《敬悼陈寅恪老师》写道:“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师不喜欢穿大衣,他总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时还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马褂,讲课时讲得兴奋而感到有些燥热,先脱去皮马褂,有时候更脱去皮袍子,等到下课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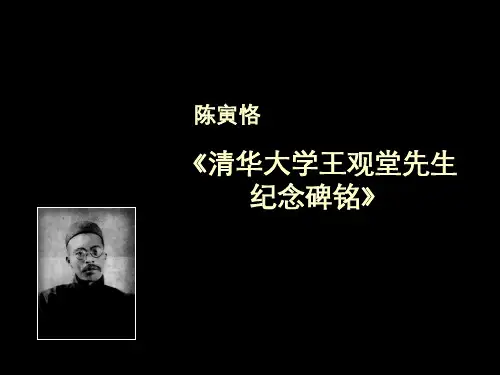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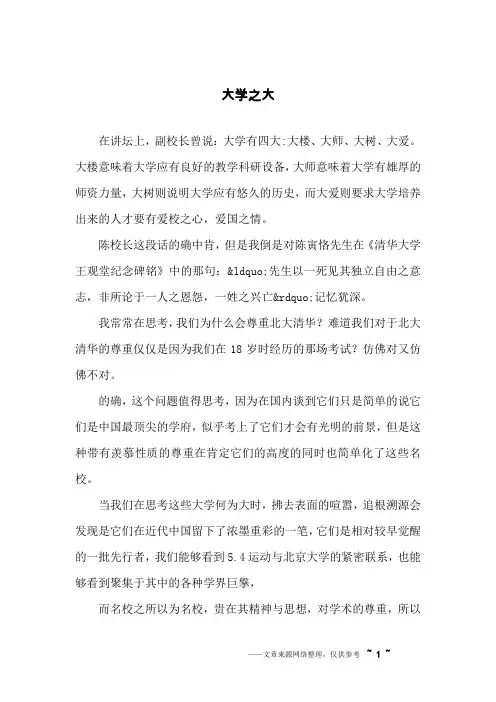
大学之大
在讲坛上,副校长曾说:大学有四大:大楼、大师、大树、大爱。
大楼意味着大学应有良好的教学科研设备,大师意味着大学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大树则说明大学应有悠久的历史,而大爱则要求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要有爱校之心,爱国之情。
陈校长这段话的确中肯,但是我倒是对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纪念碑铭》中的那句:“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记忆犹深。
我常常在思考,我们为什么会尊重北大清华?难道我们对于北大清华的尊重仅仅是因为我们在18岁时经历的那场考试?仿佛对又仿佛不对。
的确,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因为在国内谈到它们只是简单的说它们是中国最顶尖的学府,似乎考上了它们才会有光明的前景,但是这种带有羡慕性质的尊重在肯定它们的高度的同时也简单化了这些名校。
当我们在思考这些大学何为大时,拂去表面的喧嚣,追根溯源会发现是它们在近代中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是相对较早觉醒的一批先行者,我们能够看到5.4运动与北京大学的紧密联系,也能够看到聚集于其中的各种学界巨搫,
而名校之所以为名校,贵在其精神与思想,对学术的尊重,所以
能出伟人。
因为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以产生了大师。
而这就应是大学的精华,相比于你学到了什么知识,更重要的是你学到的这些知识引发了你的哪些思考?学习就应学到的是观点,大学需要不一样的观点,否则大学不再是大学,而是小学,是中学,是没有生命力的大学。
大学之大,大在其自由独立之意志,在观点与观点间不断碰撞出的新的火花。
这才是大学的真正的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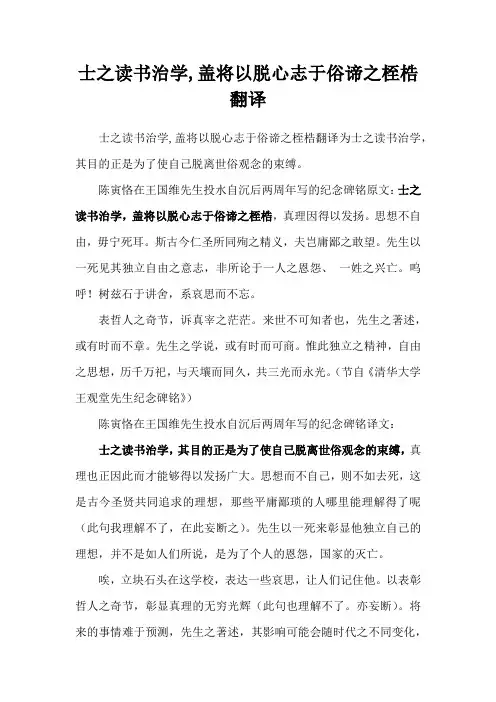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翻译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翻译为士之读书治学,其目的正是为了使自己脱离世俗观念的束缚。
陈寅恪在王国维先生投水自沉后两周年写的纪念碑铭原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
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节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陈寅恪在王国维先生投水自沉后两周年写的纪念碑铭译文:
士之读书治学,其目的正是为了使自己脱离世俗观念的束缚,真理也正因此而才能够得以发扬广大。
思想而不自己,则不如去死,这是古今圣贤共同追求的理想,那些平庸鄙琐的人哪里能理解得了呢(此句我理解不了,在此妄断之)。
先生以一死来彰显他独立自己的理想,并不是如人们所说,是为了个人的恩怨,国家的灭亡。
唉,立块石头在这学校,表达一些哀思,让人们记住他。
以表彰哲人之奇节,彰显真理的无穷光辉(此句也理解不了。
亦妄断)。
将来的事情难于预测,先生之著述,其影响可能会随时代之不同变化,
先生之学说,将来也可能有需要修正的地方。
只有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即使经过千百万年,也会与天地一样长久,和日月一样永远闪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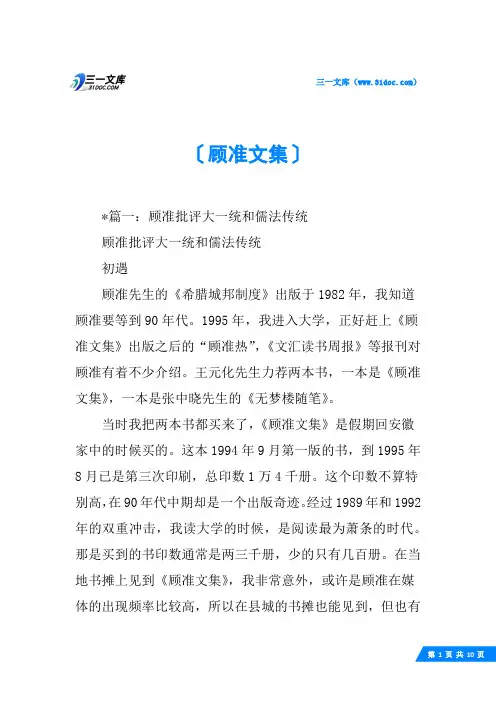
三一文库()〔顾准文集〕*篇一:顾准批评大一统和儒法传统顾准批评大一统和儒法传统初遇顾准先生的《希腊城邦制度》出版于1982年,我知道顾准要等到90年代。
1995年,我进入大学,正好赶上《顾准文集》出版之后的“顾准热”,《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对顾准有着不少介绍。
王元化先生力荐两本书,一本是《顾准文集》,一本是张中晓先生的《无梦楼随笔》。
当时我把两本书都买来了,《顾准文集》是假期回安徽家中的时候买的。
这本1994年9月第一版的书,到1995年8月已是第三次印刷,总印数1万4千册。
这个印数不算特别高,在90年代中期却是一个出版奇迹。
经过1989年和1992年的双重冲击,我读大学的时候,是阅读最为萧条的时代。
那是买到的书印数通常是两三千册,少的只有几百册。
在当地书摊上见到《顾准文集》,我非常意外,或许是顾准在媒体的出现频率比较高,所以在县城的书摊也能见到,但也有可能是书店老板把顾准当成了顾城。
我最初没怎么读《顾准文集》。
那时对顾准的介绍主要偏向于经济学层面,说他是第一位提出市场经济理论的学者。
我那时是文学青年,对经济学没有太大兴趣。
如果顾准仅仅是最早提出市场经济,那主要是经济学史上的价值,很难说著作是否值得重读。
当时读了《无梦楼随笔》,稍微有些失望。
张中晓的价值在于道德人格,他在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坚持鸡鸣不已。
王元化这样评价张中晓和顾准:“他们都命运坎坷,并不是为了立言传世而著书立说,只是由于不泯的良知写出自己的内心独白。
”(《无梦楼随笔·序》)可是,张中晓的格言体著作,很难让我有太大的触动。
他使用的语言有些“陈旧”,比如“真理是矛盾的统一,而不是可以抓住不放的东西,是活的,不是死的东西”,这种思考在那个晦暗的时代非常难得,却也只有在那个时代才显得独特。
《顾准文集》的一些文章标题,《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种表述方式很难唤起我的兴趣,那时还读不太出来“旧瓶装新酒”的涵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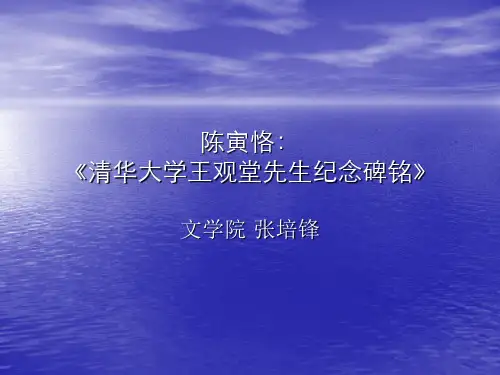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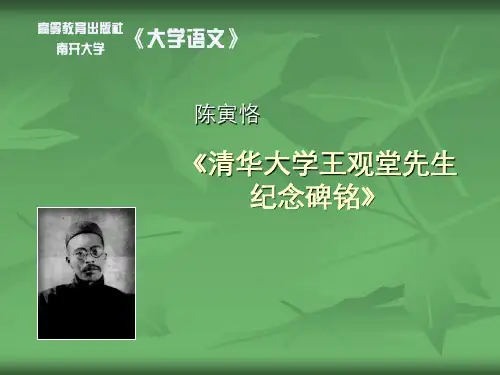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读后感陈寅恪在本篇碑铭中首先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而且一定会成为现代化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
可以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非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有的,甚至其语言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有的。
首先引进“自由”这个词儿的是严复。
他在日本学习西方变法维新而变成强国以后,在甲午海战中打败中国海军、朝野震动之际,于1895年提出,西方之所以强、中国之所以弱,原因就在于国民之“自由不自由异耳”。
二十年之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自由”在全国知识界得到广泛的讨论,也得到广泛的拥护,然而以干脆的语言标举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个原则的,则不能不首推陈寅恪先生。
王国维纪念碑铭一共不过二百五十三个字,而“独立”之词儿三见,“自由”之词凡四见,其中甚至套用美国独立时的英雄帕特立克·亨利的话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结句则为:“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根据蔡仲德先生对王国维生平事迹的评密论证,王国维的一生可以以辛亥为界,分成前后期。
他前期致力于哲学、美学、文学,有开辟创新之功,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提出:“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
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来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
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
” 照这样的言论,这样的治学态度,说王国维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完全恰当的。
但是,到了辛亥以后,王国维接受罗振玉的劝告,一变而为大清的纯臣,不但受溥仪之封为“南书房行走”、“恩赏五品衔”、“赏食五品俸”,而且在学术上也“尽弃前学,专治经史”,甚至著诗歌颂慈禧“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
他以后还参与张勋复辟的密谋,书札暗通,间关奔走,不遗余力。
《人间词话》读书笔记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两年后,陈寅恪在清华园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其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句流传甚广,评论颇多。
它是文人治学的重要思想,是对王国维一生和他的学术态度的重要概括,对王国维的人格和学术的“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做了高度评价。
英国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读书随笔中有过这样的一句话:“一个小说家要构筑自己的作品,一开始总需要有许许多多的临时材料,这些材料虽然有可能使作品具有真实性,但大多数到后来都会被证明是无用的。
”所以人们在读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时总会想到一个问题——中国从古至今遗留了千万首词,这短短的64则评语怎么能道尽个中妙处。
可是,当你读完第一则,马上就会被作者的语言所吸引。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间所以独绝者在此”。
再没有什么语言能如此精炼地概括一个时代的词的特点。
仅仅境界一词便能延展出如此深厚的内涵,怎能不让人产生强烈地继续往下探寻的求知欲呢?王国维在《人间词活》提出了著名的“境界说”:“古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
”原本三首不相关的诗词,经过王氏巧妙的组合,便造成了出人意料的效果,由此也可见王氏对词的研究之深。
但凡流传于世的经典文学作品,开篇定是独树一帜。
就像《百年孤独》的开头那般:“多年以后,面对们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归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时空跨度,社会背景顿时跃然纸上。
王国维的《人间法》中亦是如此,立足于境界,跨越五代至南宋。
并且以境界为标准,两宋之间,高下立判,真可谓名家手法,不外如是。
接着王国维又抛出了‘造境’与‘写境’两种手法。
在指出两者无高下之分的同时,又详细说明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区别。
海宁王先生之碑铭读后感
清华园,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历百年沧桑,已然斑驳。
正是这座简朴的墓碑,却承载着中国思想史上一次振聋发聩的呼喊,而成为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信仰和追求的一个不可磨灭的精神图腾。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先生自沉于昆明湖,两年后,清华大学国学院立碑纪念,由陈寅恪先生撰写碑铭。
彼时,外界对王国维自沉猜测颇多,有“愚忠殉清”说,有“逼债”说,甚至有“惊惧”说,俨然一桩公案,扑朔迷离。
对此,作为多年知交的陈寅恪在碑铭中则言:“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进而发出“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的百年之叹。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由此发端,并成为“五四运动”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之一,历久而弥新,至今被无数世人奉为人生价值的追求目标。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虽为人耳熟能详而津津乐道,也有着无数的解读和阐发,然而,言之者众而行之者寡,能够秉此信仰并在实践中一以贯之努力行为者寥如晨星。
何以如此,在其有二难,一为知其所以然之难,二为践行始终之难。
前者之难,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
志于俗谛之桎梏。
”对大多数人而言,脱俗谛之桎梏不仅需要勇气,更需心志与智慧的合力。
若无健全的人格,深厚的学养,理性的思维,以及强大的内心,坚定的信念,则很难建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内在根基。
作文素材积累: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释读陈寅恪(1890-1969),著名史学大师,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为王国维先生所撰碑铭中,流传最广、最为人们称道的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甲骨四堂之一。
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
1927年阴历五月初三,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
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所有之学人”。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
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要点翻译:君子读书治学,都是为了让心智和志向摆脱俗世陋见的枷锁,也只有这样,真理才能得以发扬传播。
思想如果不能自由,则不如去死。
这一古往今来的仁人圣贤一同为之以死守护的理念,又岂是那些庸俗僻陋之人能够理解的呢。
王国维先生用他的死来彰显自己独立自由的意志,他的死并不是人们议论的是为了一人的恩怨,或者一姓之天下的兴亡。
呜呼!在讲堂旁边树立这块石头,是为了寄托对先生的哀思,表示我们永不忘怀,也为了表彰这位哲人难能可贵的气节,彰显真理大道的无边。
读《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有感《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为陈寅恪在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沉两年后,为其撰写的碑文。
虽寥寥数语,但字字用义深刻精要,发人深省。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
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
来世不可知者也。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
王国维之死,可以说是一个谜,当时对此的说法不一。
有人认为是和罗振玉有关,有人以为是和清朝的灭亡有关。
而独陈寅恪对其死的诠释最深刻最合理,“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为大多人所接受。
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曾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迨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能对王国维死亡的原因看得如此深刻,一是缘于陈老阅历丰富,学识渊博,洞悉时代变化,对变化中的事物把握得透彻;二是因为陈老与王国维的深厚友谊,陈老深知其苦。
故而陈老痛其忘,亦乐其亡。
陈老能正确评价王国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不是一概地肯定他,也不是一概地否定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王国维的可贵之处,“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而不是只着重其国学功底,此乃真知矣。
陈王之情,堪比马恩之谊,甚甚于马恩之谊。
陈老高度赞扬王国维所具有的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其实正是他自己学术的灵魂,是他自己人格的灵魂。
他与王国维,在那些烽火连战,政治混乱的年代,生活拮据困顿,依然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自由的意志,“脱心志与俗谛桎梏”一丝不苟地做学问。
他们像寒冬高耸的松柏,虽形容枯槁,但直刺青天。
他们坚持,甚至因为太多坚持而显得有些固执;他们叛逆,甚至因为太过叛逆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可是他们所坚持的是学术的灵魂啊,那是学术还真真实实存在,流淌着鲜活血液的依据保证啊!那是高于生命的东西啊!你叫他们怎能不坚持呢!
反观一些文人,为政治而学术,无自己独到之见解,卑微地徘徊在政治门口,自己所做的学问只是暂时地服务于少数人,而无益于世。
因为某领导说了一句话,便围绕这句话“旁征博引”地论证这句话的正确性。
因为某领导对某事件得出自己的论断,便把其当做真理,然后从论断出发,究其依据,最终一无所获。
与两位大师相比,此不亦悲乎!
每每念及陈老之死,总觉痛心疾首,同时竟深深庆幸王国维之自沉早死,免受许多难事折磨。
《陈寅恪传》中曾写道:“综观先生一生,屯蹇之日多,安舒之日少。
远客异国,有断炊之虞。
漂泊西南,备颠大
连之苦。
外侮内忧,销魂铄骨。
奇疾异遇,困顿(失明却无人陪伴)于天竺,英伦,纽约之际。
虽晚年遭逢盛世,而失明之后,继以摈足,终则被迫害致死”,虽一生困顿交叠,但能保其独立之人格,实在难能可贵。
观今之时代,实乃一个可悲之时代,缺乏文化,缺乏大师,人文落寞,科学独霸,学风浮躁,社会风气中到处充斥着铜臭味,人们随波逐流,崇洋媚外,在种种诱惑冲击中丢失自我。
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正是陈老身上这种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意志。
我们需要找回自己的灵魂,树以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
于个人,坦荡大气,能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保持自我本性,很好地生活。
于人文,能弃其落寞,渐趋平稳,实现复兴。
于民族,能团结一致,高屹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