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
- 格式:doc
- 大小:12.74 KB
- 文档页数: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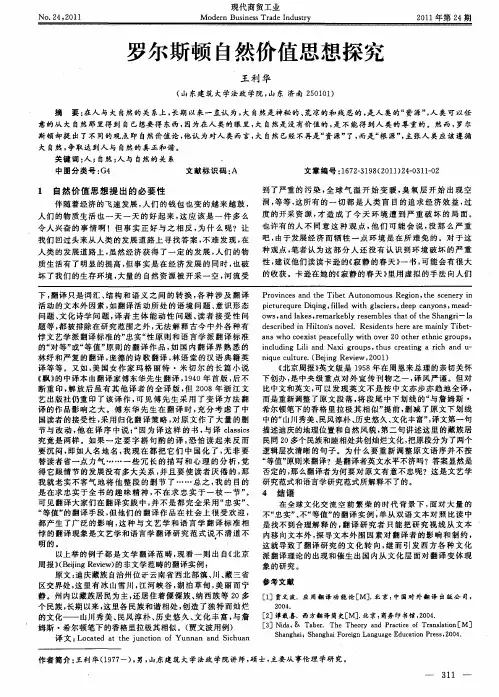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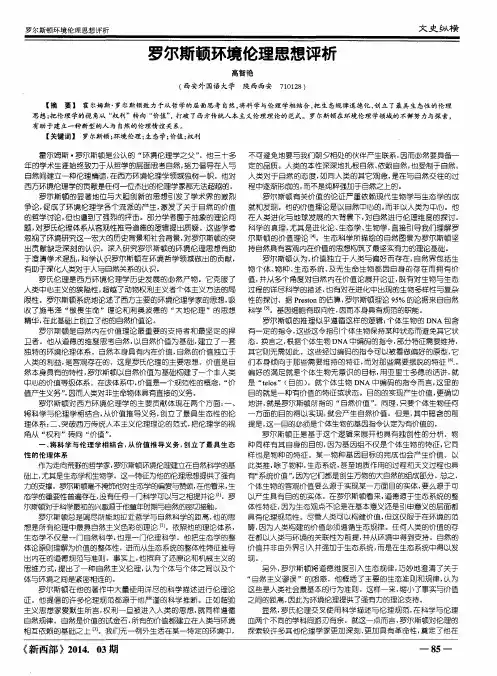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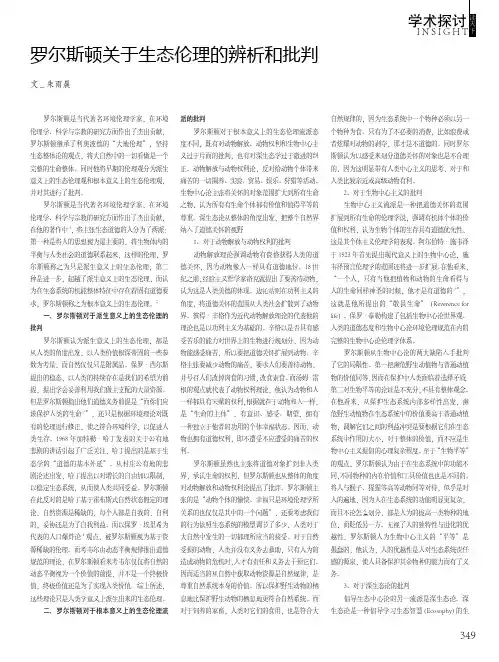
文_学术探讨349罗尔斯顿是当代著名环境伦理学家,在环境伦理学、科学与宗教的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罗尔斯顿继承了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坚持生态整体论的观点,将大自然中的一切看做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整体。
同时他将早期的伦理观分为派生意义上的生态伦理观和根本意义上的生态伦理观,并对其进行了批判。
罗尔斯顿是当代著名环境伦理学家,在环境伦理学、科学与宗教的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他的著作中1,将主张生态道德的人分为了两派:第一种是将人的思想视为最主要的,将生物体内的平衡与人类社会的道德联系起来,这样的伦理,罗尔斯顿称之为只是派生意义上的生态伦理;第二种是进一步,超越了派生意义上的生态伦理,而认为在生态系统的机能整体特征中存在着固有道德要求,罗尔斯顿称之为根本意义上的生态伦理。
2一、罗尔斯顿对于派生意义上的生态伦理的批判罗尔斯顿认为派生意义上的生态伦理,都是从人类的角度出发,以人类价值根深蒂固的一些参数为考量,而自然仅仅只是附属品。
保罗・西尔斯提出的稳态,以人类的持续存在是我们的希望为前提,提出学会妥善利用我们做主支配的大量资源。
但是罗尔斯顿指出他们道德义务前提是“而你们应该保护人类的生命3”,还只是根据环境理论对既有的伦理进行修正,使之符合环境科学,以促进人类生存。
1968年加特勒・哈丁发表的关于公有地悲剧的讲话引起了广泛关注,哈丁提出的是基于生态学的“道德的基本外延”。
从村庄公有地的悲剧论述出发,哈丁提出以对增长的自由加以限制,以稳定生态系统,从而使人类共同受益。
罗尔斯顿在此反对的是哈丁基于霍布斯式自然状态假定的理论,自然资源是稀缺的,每个人都是自我的,自利的,妥协还是为了自我利益。
而以保罗・埃里希为代表的人口爆炸论4观点,被罗尔斯顿视为基于资源稀缺的伦理。
而考韦尔由动态平衡规律推出道德规范的理论,在罗尔斯顿看来考韦尔仅仅将自然的动态平衡视为一个价值的前提,并不是一个终极价值,终极价值还是为了实现人类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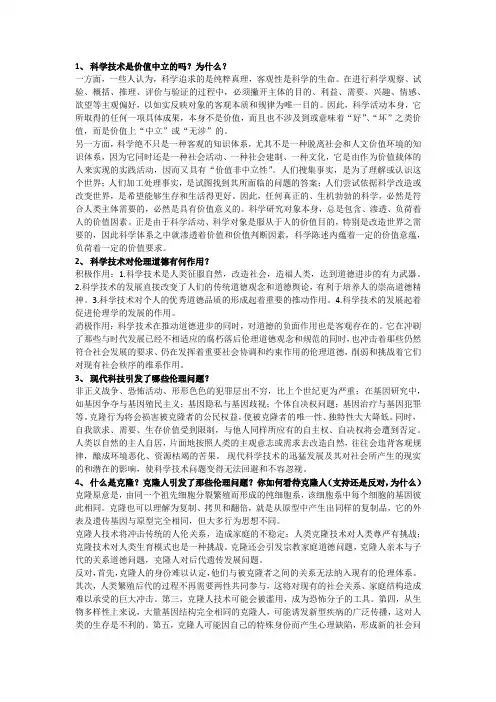
1、科学技术是价值中立的吗?为什么?一方面,一些人认为,科学追求的是纯粹真理,客观性是科学的生命。
在进行科学观察、试验、概括、推理、评价与验证的过程中,必须撇开主体的目的、利益、需要、兴趣、情感、欲望等主观偏好,以如实反映对象的客观本质和规律为唯一目的。
因此,科学活动本身,它所取得的任何一项具体成果,本身不是价值,而且也不涉及到或意味着“好”、“坏”之类价值,而是价值上“中立”或“无涉”的。
另一方面,科学绝不只是一种客观的知识体系,尤其不是一种脱离社会和人文价值环境的知识体系,因为它同时还是一种社会活动、一种社会建制、一种文化,它是由作为价值载体的人来实现的实践活动,因而又具有“价值非中立性”。
人们搜集事实,是为了理解或认识这个世界;人们加工处理事实,是试图找到其所面临的问题的答案;人们尝试依据科学改造或改变世界,是希望能够生存和生活得更好。
因此,任何真正的、生机勃勃的科学,必然是符合人类主体需要的,必然是具有价值意义的。
科学研究对象本身,总是包含、渗透、负荷着人的价值因素。
正是由于科学活动、科学对象是服从于人的价值目的,特别是改造世界之需要的,因此科学体系之中就渗透着价值和价值判断因素,科学陈述内蕴着一定的价值意蕴,负荷着一定的价值要求。
2、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有何作用?积极作用:1.科学技术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造福人类,达到道德进步的有力武器。
2.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改变了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和道德舆论,有利于培养人的崇高道德精神。
3.科学技术对个人的优秀道德品质的形成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4.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促进伦理学的发展的作用。
消极作用:科学技术在推动道德进步的同时,对道德的负面作用也是客观存在的。
它在冲刷了那些与时代发展已经不相适应的腐朽落后伦理道德观念和规范的同时,也冲击着那些仍然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仍在发挥着重要社会协调和约束作用的伦理道德,削弱和挑战着它们对现有社会秩序的维系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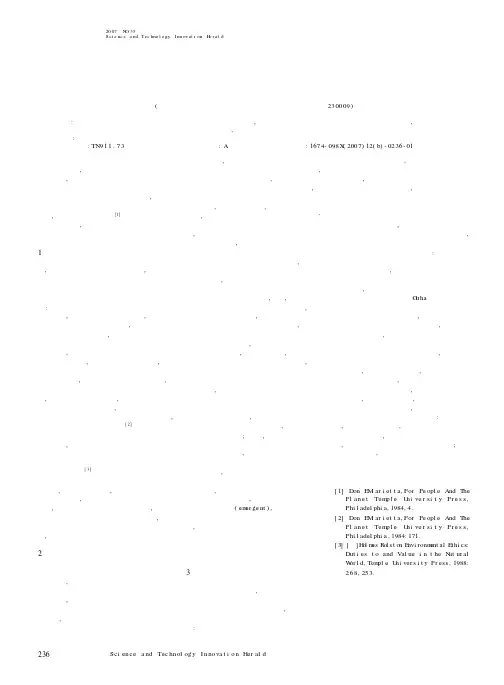
36科技创新导报S T y I 2007N O .35Sci e nc e a nd Tec hno l o gy I nn ov at i on H e r al d 科教平台科技创新导报当前环境伦理学论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就是价值了,这个字眼被许多环境伦理学家频繁使用,甚至成为某些环境伦理学家构建自己环境伦理学的核心。
“环境伦理学的许多理论都立基于自然中的价值这个概念上,一些伦理理论的论证途径是把内在价值赋予动物、生物圈,或者整个生态系统。
”[1]其中罗而斯顿就是主要代表之一,他可以说是现代环境伦理学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1自然价值的逻辑论证罗而斯顿认为不仅要肯定自然价值的存在,还要肯定自然价值事实上就存在,为此罗而斯顿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去界定自然价值的内涵、特征和客观性证明。
罗而斯顿关于自然价值的内涵的三个观点:第一,自然价值就是自然的性质,无论是无机物还是有机物都是有价值的,是由自然系统或自然物的结构决定的,因此自然中的价值是客观的。
第二,罗而斯顿主张价值属性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创造性,大自然不仅创造了万物,还创造了具有评价能力的人。
自然是朝着产生价值的方向进化的,并不是我们赋予自然以价值,而是自然把价值馈赠给我们的。
从系统的角度看,评价行为不仅属于自然,而且存在于自然之中。
大自然是生命的源泉,这整个源泉——而非只有诞生于其中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大自然是万物的真正创造者。
[2]大自然创造了万事万物。
第三,内在价值、工具价值和系统价值的同意构成了自然价值的另一属性。
“内在价值是指那些能在自身中发现价值而无须借助其他参照物的事物”[3]“工具价值指某些被用来当作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的事物。
从生态系统的整体看,他具有系统价值,系统价值不是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不是生态系统对有机体的工具价值,更不是生态系统中所有价值之和,而是系统的创造过程和趋势。
就像罗而斯顿说,我们已接触到了某种需要用第三个术语来描述的事物,那就是系统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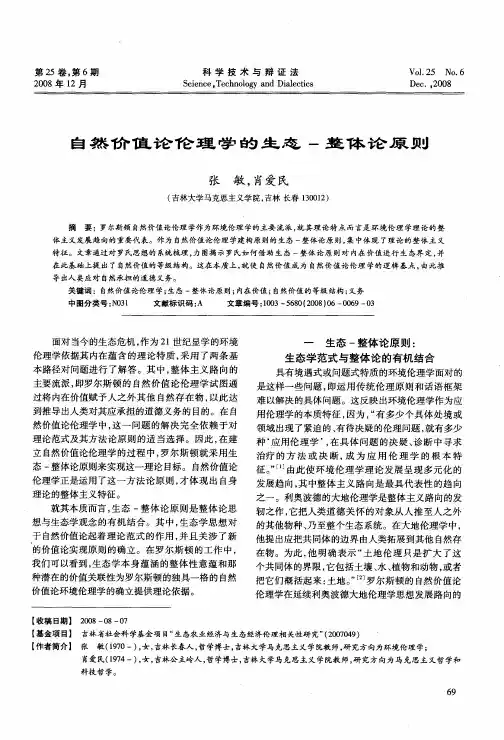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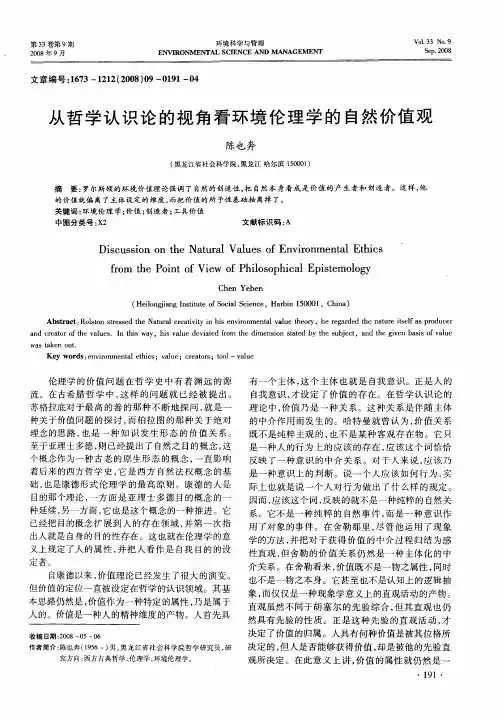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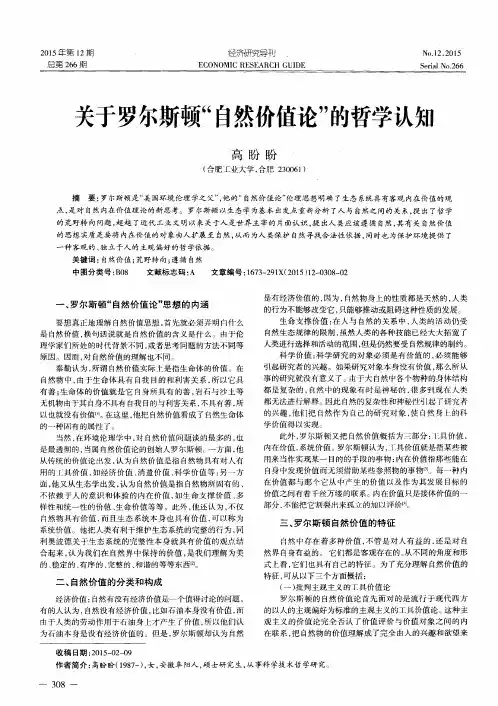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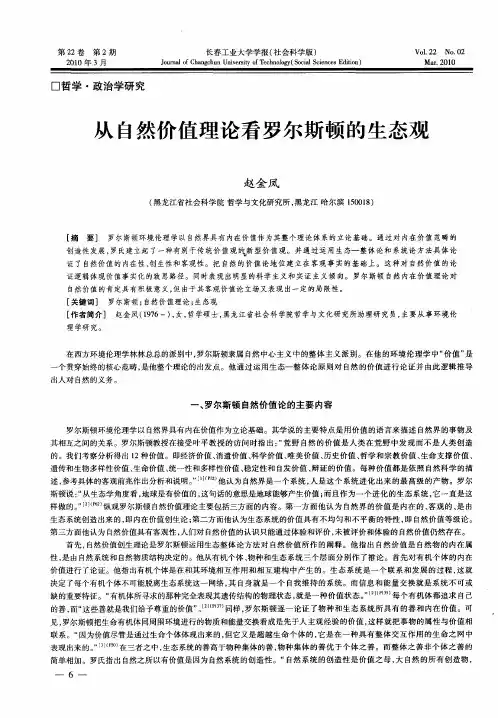
马克思与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观之异同作者:张洁来源:《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3期摘要:在人类文化史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历久弥新。
马克思的自然观中蕴含着丰富的自然价值观思想。
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系统研究了自然的内在价值,转向了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新路向。
分析马克思和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观的差异和相同之处,进行有益的比较,对现代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普遍而深刻的哲学意义和社会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罗尔斯顿;自然价值;生态文明哲学作为一门爱智慧的科学,从其产生就致力于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关注的基本话题之一。
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生态术语,但自然价值观始终贯穿于其理论系统中。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荒野哲学家,他指出,一个人如果对地球生命共同体,也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支持我们生存的生命之源缺乏一种应有的关心,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
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现代化”的问题,使得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现实的冲突要求哲学家们进行理论的反思。
马克思所处的年代,生态问题还没有凸显出来,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马克思对自然的关注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上,以劳动价值论为核心内容。
罗尔斯顿亲历了现代社会严峻的生态危机,他从自然本身出发,试图建立“一个涵容更广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理论”2。
具体地、历史地比较马克思和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观,厘清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我们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与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观的比较马克思的自然观被称为“人与自然和解的生态伦理学”,这种称赞建立在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上。
在马克思那里,人与自然具有不可割舍的内在联系,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3,同时自然为人类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人在自然界中具有双重属性。
罗尔斯顿自然内在价值论深层解析作者:王鹏伟来源:《鄱阳湖学刊》2019年第03期[摘要]罗尔斯顿的自然内在价值论是以自然物本身及其属性和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即所谓自然的内在价值,来主张自然物的道德地位的。
因此,从表面上看它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但实际上却是泛内在价值论,是等级主义的、整体主义的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因而也是“非人类中心论”中最可取的。
[关键词]罗尔斯顿;自然内在价值论;环境哲学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Ⅲ)是现代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哲学自然内在价值论的典型代表。
他认为,环境伦理学不是传统的人际伦理在环境事务中的应用,而是一种原发型的伦理学,因为我们是根据大自然本身来评价它们的,是从自然的内在价值来推导出人类对它们应尽的义务的,因而可以将其称为自然内在价值道德论。
从表面上看,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确实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原发型的,然而事实上,罗尔斯顿的自然内在价值论是泛内在价值论的、等级主义的、整体主义的,因而是“人类中心主义”的。
一、罗尔斯顿的自然内在价值论是泛内在价值论罗尔斯顿是个泛内在价值论者。
他认为:“内在价值指那些能在自身中发现价值而无须借助其他参照物的事物。
”①首先,大自然的内在价值具有先在性。
大自然是客观的内在价值的创生者、承载者和推动者,大自然中的一切存在都具有内在价值,它们早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各就各位,人类只是一个后来的加入者。
大自然像人一样也可以是主体,具有评价和选择的能力、目的和利益,并能够以自身的行动来实现自身的目的和利益。
当然,在人出现以后,人可以通过体验认识到自然客观存在的价值,人对大自然的评价也导致某些新价值的产生,但这些新价值是附丽在大自然的客观价值之上的,是以大自然的客观的内在价值为基础的。
总之,“大自然创造了所有的价值,在这些价值中,有些是客观的,有些则是人的主体性与客观自然相互结合的产物”②。
因此,罗尔斯顿视野中的价值有两类:一类是其所谓的大自然的客观的内在价值,实际上就是指自然物本身及其属性和相互间的作用。
生态主义“伦理”—“道德”形态的逻辑进路在人类文明的演化史上,生态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关注生物个体—关爱生命整体—关怀生态实体的生命演进历程。
如果说,“生物中心主义”关注生物个体的生命权益,但由于缺乏普遍的“实体性”依托,最终处于“作恶的待发道德”形态的分裂与对峙,那么,“生态中心主义”则将伦理点上”,遭遇“伦理”—“关怀的中心由个体生命拓展到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但是“居留地”的可靠性遭遇道德”形态的悖论与风“意志自由”的抽象普遍性,同样无可避免地陷入“伦理”—“险之中。
人类生态觉悟的辩证运动继續向前推进,未来社会应当建构接纳、包容、整合甚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多元对话的生态主义“伦道德”共生互动的价值生态和理论形态,这是生态时代人与世界关系的文理”—“明生态觉悟,也是一场世界观的革命和“形态论”的理论自觉。
道德”形态;文明的生态 标签: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伦理”—“在人类文明的演化史上,生态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关注生物个体—关爱生命整体—关怀生态实体的生命演进历程,也是人类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不断拓展、道德关怀的范围不断扩宽、道德知识和视野不断丰富和开阔的过程。
生态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流派从彼此诘责对立到对话交流、沟通融合,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进程,但是,如果沉浸在西方生态主义为我们设计的理性王国中并不断进行“学派”和“流派”的碎片化式的解读,那么,我们不仅无法走出不同生态学派和流派的理论冲突,而且容易遮蔽生态主义理论思想的“精神”内涵,因此,“入流”之后如何“出流”,并在“出入流派”之间进行生态主义的“形态论”的研究方法的革命和“伦理精神”的呈现成为可能的研究趋向。
道德”辩道德”的分裂和对峙形态向生态主义“伦理”—“从生态主义“伦理”—“证同一的价值生态方向的演进,是人类道德哲学发展的逻辑进路,也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走向。
如果说“生物中心主义”关注生物个体的生命权益,但由于缺乏普遍道德”形态的分裂的“实体性”依托,最终处于“作恶的待发点上”,遭遇“伦理”—“与对峙,那么,“生态中心主义”则将伦理关怀的中心由个体生命拓展到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但是“居留地”的可靠性遭遇“意志自由”的抽象普遍性,同样无可避免道德”形态的悖论与风险之中。
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人得目光被迫逐渐地聚焦在生态问题上。
生态危机的出现引起了全球范围内人们的广泛关注,生态问题的恶化成为了世界性的重大话题。
人类在与自然的不和谐相处中不仅仅是尝到了苦果,更是接受了严重的教训。
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归根结底是一个哲学问题,表现上即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深入研究这两种主义背后的关节,不难发现环境问题本质上只是一个自然价值的问题。
自然的价值是什么?是否有内在价值?如果有内在价值,如何实现自然从传统价值论到内在价值论的一种转变?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人类后续的生存,更关系到人类和世界的发展。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对传统意义上的自然价值论进行研究和分类,在传统意义上的自然价值论中,我们很容易能够找到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根据,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论体系严重误导了人类的行为方式,并且毫无疑问地遮蔽了人类的双眼,使人类与自然处在一种单纯地无限制攫取的关系之中,将人类与自然敌对起来,人类以主宰的姿态恣意地攫取,破坏性地开发自然。
我们在传统自然价值论中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却无法从中找到一种合理的解决途径,甚至是无法找到一种折衷的调解方式。
而这种解决途径的寻找不仅仅是一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追究,更是在实际意义上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合理的途径找到人与自然相处和谐的关键,是改善人与自然关系中迫在眉睫的一项任务。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作为一位在环境伦理学中颇具影响力的学者,通过他的自然价值理论,确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并且实现了一个从自然的工具价值到内
在价值的转换,这种转变机制是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家利奥波德的研究的继承。
利奥波德就是致力于由自然的外在价值向内在价值的一种转变,认识到了自然有自为目的,有其内在价值。
在这种自然观的基础之上,罗尔斯顿提出了以自然内在价值作为核心的自然价值观,通过其自然价值理论,真正实现了从自然的工具价值到内在价值的转换。
当然,罗尔斯顿的这种转换机制也存在一些缺陷,存在继续完善的空间。
罗尔斯顿的这种转换机制在其领域内也饱受质疑与攻击,但是无法掩盖这种转换机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罗尔斯顿的这种转换机制,有效地解决了人与自然在观念上的不和谐,为自然的内在价值进行了证明,通过对价值概念的重新定义以及对于环境伦理学研究起点的转换,构建起一套完整的自然价值理论,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更是给处于环境困境中的人类一条合理的出路,在当今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境况下有着鲜明的实际意义。
本文会重点恢复出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理论体系,并且着重解释这种从自然的工具价值到内在价值的转换机制,与传统的自然价值论进行比较,明确这种转换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对人类与自然的相处方式进行一个前瞻性的引导,力求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健康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