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社会廉洁政治的历史沉思-读王夫之《读通鉴论》
- 格式:doc
- 大小:32.50 KB
- 文档页数: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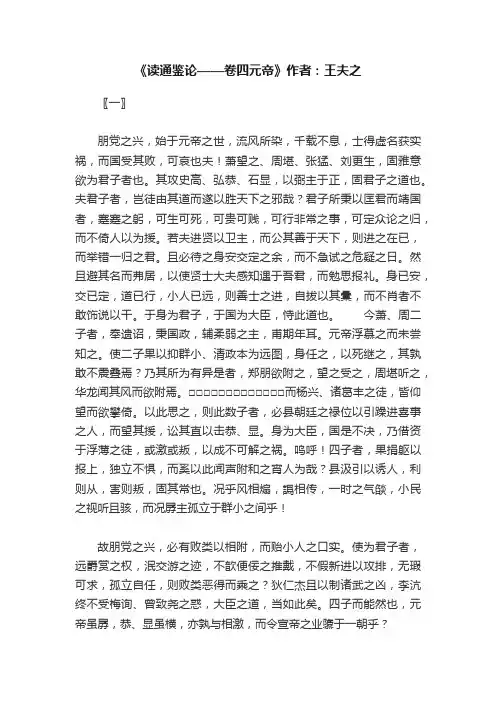
《读通鉴论——卷四元帝》作者:王夫之〖一〗朋党之兴,始于元帝之世,流风所染,千载不息,士得虚名获实祸,而国受其败,可哀也夫!萧望之、周堪、张猛、刘更生,固雅意欲为君子者也。
其攻史高、弘恭、石显,以弼主于正,固君子之道也。
夫君子者,岂徒由其道而遂以胜天下之邪哉?君子所秉以匡君而靖国者,蹇蹇之躬,可生可死,可贵可贱,可行非常之事,可定众论之归,而不倚人以为援。
若夫进贤以卫主,而公其善于天下,则进之在已,而举错一归之君。
且必待之身安交定之余,而不急试之危疑之日。
然且避其名而弗居,以使贤士大夫感知遇于吾君,而勉思报礼。
身已安,交已定,道已行,小人已远,则善士之进,自拔以其彙,而不肖者不敢饰说以干。
于身为君子,于国为大臣,恃此道也。
今萧、周二子者,奉遗诏,秉国政,辅柔弱之主,甫期年耳。
元帝浮慕之而未尝知之。
使二子果以抑群小、清政本为远图,身任之,以死继之,其孰敢不震叠焉?乃其所为有异是者,郑朋欲附之,望之受之,周堪听之,华龙闻其风而欲附焉。
□□□□□□□□□□□□□而杨兴、诸葛丰之徒,皆仰望而欲攀倚。
以此思之,则此数子者,必县朝廷之禄位以引躁进喜事之人,而望其援,讼其直以击恭、显。
身为大臣,国是不决,乃借资于浮薄之徒,或激或叛,以成不可解之祸。
呜呼!四子者,果捐躯以报上,独立不惧,而奚以此闻声附和之宵人为哉?县汲引以诱人,利则从,害则叛,固其常也。
况乎风相煽,譌相传,一时之气燄,小民之视听且骇,而况孱主孤立于群小之间乎!故朋党之兴,必有败类以相附,而贻小人之口实。
使为君子者,远爵赏之权,泯交游之迹,不歆便佞之推戴,不假新进以攻排,无瑕可求,孤立自任,则败类恶得而乘之?狄仁杰且以制诸武之凶,李沆终不受梅询、曾致尧之惑,大臣之道,当如此矣。
四子而能然也,元帝虽孱,恭、显虽横,亦孰与相激,而令宣帝之业隳于一朝乎?申屠嘉之困邓通,困之而已;韩魏公之逐内竖,逐之而已;何所藉于群不逞而为之羽翼?司马温公任二苏以抑王安石,而秦观、张耒以狭邪匪人缘之,以忝清流之选,故终绌于绍述之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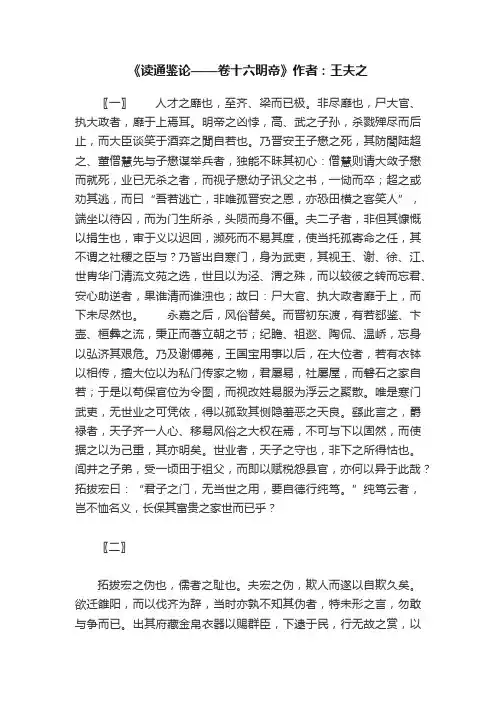
《读通鉴论——卷十六明帝》作者:王夫之〖一〗人才之靡也,至齐、梁而已极。
非尽靡也,尸大官、执大政者,靡于上焉耳。
明帝之凶悖,高、武之子孙,杀戮殚尽而后止,而大臣谈笑于酒弈之閒自若也。
乃晋安王子懋之死,其防閤陆超之、董僧慧先与子懋谋举兵者,独能不昧其初心:僧慧则请大敛子懋而就死,业已无杀之者,而视子懋幼子讯父之书,一恸而卒;超之或劝其逃,而曰“吾若逃亡,非唯孤晋安之恩,亦恐田横之客笑人”,端坐以待囚,而为门生所杀,头陨而身不僵。
夫二子者,非但其慷慨以捐生也,审于义以迟回,濒死而不易其度,使当托孤寄命之任,其不谓之社稷之臣与?乃皆出自寒门,身为武吏,其视王、谢、徐、江、世胄华门清流文苑之选,世且以为泾、渭之殊,而以较彼之转而忘君、安心助逆者,果谁清而谁浊也;故曰:尸大官、执大政者靡于上,而下未尽然也。
永嘉之后,风俗替矣。
而晋初东渡,有若郄鉴、卞壶、桓彝之流,秉正而著立朝之节;纪瞻、祖逖、陶侃、温峤,忘身以弘济其艰危。
乃及谢傅薨,王国宝用事以后,在大位者,若有衣钵以相传,擅大位以为私门传家之物,君屡易,社屡屋,而磐石之家自若;于是以苟保官位为令图,而视改姓易服为浮云之聚散。
唯是寒门武吏,无世业之可凭依,得以孤致其恻隐羞恶之天良。
繇此言之,爵禄者,天子齐一人心、移易风俗之大权在焉,不可与下以固然,而使据之以为己重,其亦明矣。
世业者,天子之守也,非下之所得怙也。
闾井之子弟,受一顷田于祖父,而即以赋税怨县官,亦何以异于此哉?拓拔宏曰:“君子之门,无当世之用,要自德行纯笃。
”纯笃云者,岂不恤名义,长保其富贵之家世而已乎?〖二〗拓拔宏之伪也,儒者之耻也。
夫宏之伪,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
欲迁雒阳,而以伐齐为辞,当时亦孰不知其伪者,特未形之言,勿敢与争而已。
出其府藏金帛衣器以赐群臣,下逮于民,行无故之赏,以饵民而要誉,得之者固不以为德也,皆欺人而适以自欺也,犹未极形其伪也。
至于天不雨而三日不食,将谁欺,欺天乎?人未有三日而可不食者,况其在豢养之子乎!高处深宫,其食也,孰知之?其不食也,孰信之?大官不进,品物不具,宦官宫妾之侧孰禁之?果不食也欤哉!而告人曰:“不食数日,犹无所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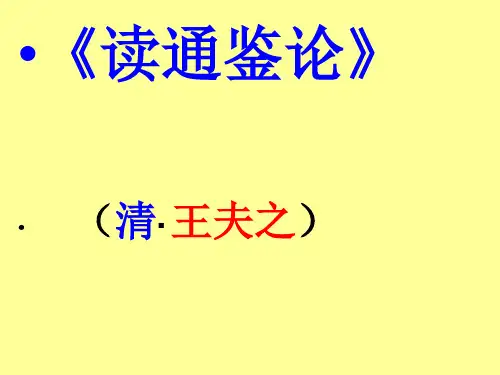

《读通鉴论》名词解释
一、《通鉴》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历史巨著,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它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详细记载了从周威烈王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的历史,共涵盖了1362年的历史。
二、《读通鉴论》
《读通鉴论》是清代学者王夫之的一部史论集,通过对《通鉴》的解读,对秦汉以来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评论。
王夫之在书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对于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编年体
编年体是一种历史著作的体裁,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编排史实,以年代为线索,叙述史实的演变。
编年体的优点在于能够清晰地展现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但缺点在于不易于表现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
四、司马光
司马光是北宋时期的一位著名史学家、政治家,也是《通鉴》的编纂者。
他主张历史研究要“以史为鉴”,强调历史的实用性。
他的编纂方法对后世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王夫之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后一位思想家。
他的思想深邃、博大,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
《读通鉴论》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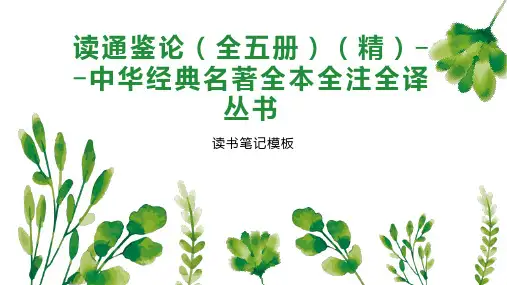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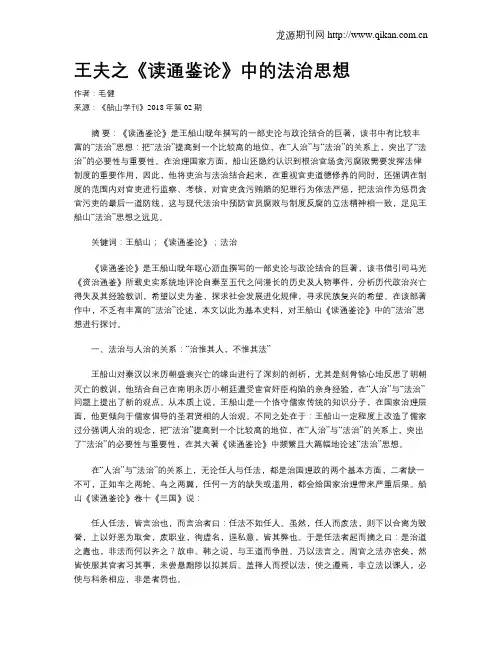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的法治思想作者:毛健来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02期摘要:《读通鉴论》是王船山晚年撰写的一部史论与政论结合的巨著,该书中有比较丰富的“法治”思想:把“法治”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地位,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上,突出了“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在治理国家方面,船山还隐约认识到根治官场贪污腐败需要发挥法律制度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将吏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在重视官吏道德修养的同时,还强调在制度的范围内对官吏进行监察、考核,对官吏贪污贿赂的犯罪行为依法严惩,把法治作为惩罚贪官污吏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与现代法治中预防官员腐败与制度反腐的立法精神相一致,足见王船山“法治”思想之远见。
关键词:王船山;《读通鉴论》;法治《读通鉴论》是王船山晚年呕心沥血撰写的一部史论与政论结合的巨著,该书借引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史实系统地评论自秦至五代之间漫长的历史及人物事件,分析历代政治兴亡得失及其经验教训,希望以史为鉴,探求社会发展进化规律,寻求民族复兴的希望。
在该部著作中,不乏有丰富的“法治”论述,本文以此为基本史料,对王船山《读通鉴论》中的“法治”思想进行探讨。
一、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治惟其人,不惟其法”王船山对秦汉以来历朝盛衰兴亡的缘由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尤其是刻骨铭心地反思了明朝灭亡的教训,他结合自己在南明永历小朝廷遭受宦官奸臣构陷的亲身经验,在“人治”与“法治”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
从本质上说,王船山是一个恪守儒家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国家治理层面,他更倾向于儒家倡导的圣君贤相的人治观。
不同之处在于:王船山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儒家过分强调人治的观念,把“法治”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地位,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上,突出了“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其大著《读通鉴论》中频繁且大篇幅地论述“法治”思想。
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上,无论任人与任法,都是治国理政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缺一不可,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任何一方的缺失或滥用,都会给国家治理带来严重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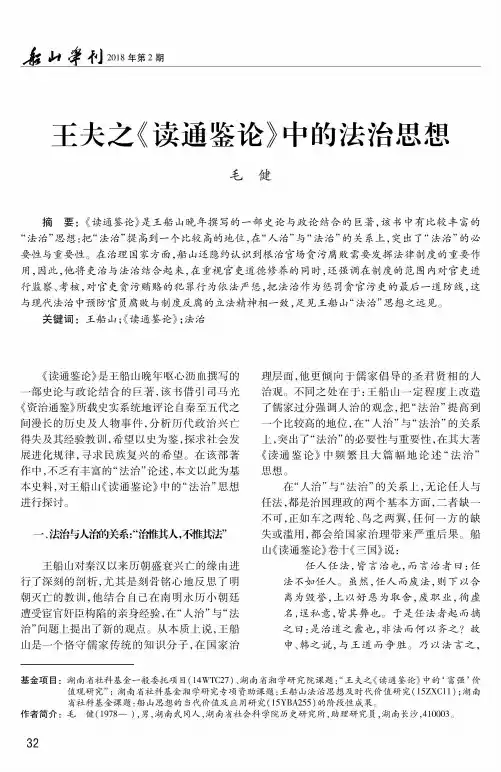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的法治思想毛健摘要:《读通鉴论》是王船山晚年撰写的一部史论与政论结合的巨著,该书中有比较丰富的 “法治’’思想:把“法治’’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地位,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上,突出了 “法治’’的必 要性与重要性。
在治理国家方面,船山还隐约认识到根治官场贪污腐败需要发挥法律制度的重要作 用,因此,他将吏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在重视官吏道德修养的同时,还强调在制度的范围内对官吏进 行监察、考核,对官吏贪污贿赂的犯罪行为依法严惩,把法治作为惩罚贪官污吏的最后一道防线,这 与现代法治中预防官员腐败与制度反腐的立法精神相一致,足见王船山“法治’’思想之远见。
关键词:王船山;《读通鉴论》;法治《读通鉴论》是王船山晚年呕心沥血撰写的 一部史论与政论结合的巨著,该书借引司马光 《资治通鉴》所载史实系统地评论自秦至五代之 间漫长的历史及人物事件,分析历代政治兴亡 得失及其经验教训,希望以史为鉴,探求社会发 展进化规律,寻求民族复兴的希望。
在该部著 作中,不乏有丰富的“法治”论述,本文以此为基 本史料,对王船山《读通鉴论》中的“法治”思想 进行探讨。
一、法治与人治的关系雛其人,不惟其法”王船山对秦汉以来历朝盛衰兴亡的缘由进 行了深刻的剖析,尤其是刻骨铭心地反思了明 朝灭亡的教训,他结合自己在南明永历小朝廷 遭受宦官奸臣构陷的亲身经验,在“人治”与“法 治”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
从本质上说,王船 山是一个恪守儒家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国家治理层面,他更倾向于儒家倡导的圣君贤相的人 治观。
不同之处在于:王船山一定程度上改造 了儒家过分强调人治的观念,把“法治”提高到 一个比较高的地位,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 上,突出了 “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其大著 《读通鉴论》中频繁且大篇幅地论述“法治”思想。
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上,无论任人与 任法,都是治国理政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缺一 不可,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任何一方的缺 失或滥用,都会给国家治理带来严重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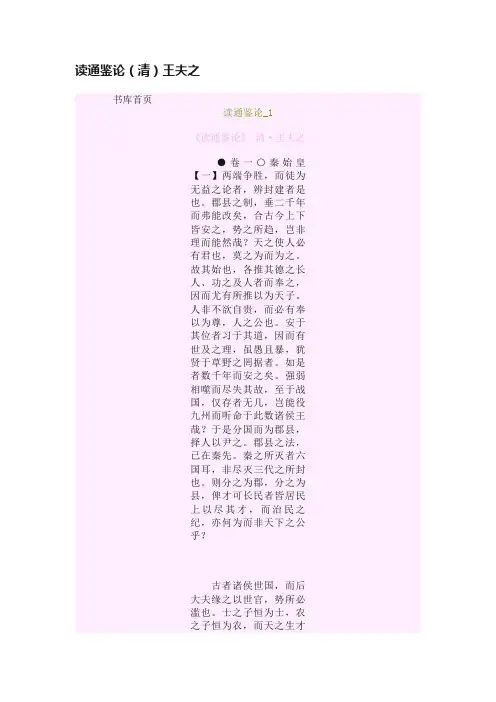
读通鉴论(清)王夫之书库首页读通鉴论_1《读通鉴论》清·王夫之●卷一○秦始皇【一】两端争胜,而徒为无益之论者,辨封建者是也。
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为而为之。
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长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为天子。
人非不欲自贵,而必有奉以为尊,人之公也。
安于其位者习于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虽愚且暴,犹贤于草野之罔据者。
如是者数千年而安之矣。
强弱相噬而尽失其故,至于战国,仅存者无几,岂能役九州而听命于此数诸侯王哉?于是分国而为郡县,择人以尹之。
郡县之法,已在秦先。
秦之所灭者六国耳,非尽灭三代之所封也。
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古者诸侯世国,而后大夫缘之以世官,势所必滥也。
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而天之生才也无择,则士有顽而农有秀;秀不能终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
封建毁而选举行,守令席诸侯之权,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
势相激而理随以易,意者其天乎!阴阳不能偏用,而仁义相资以为亨利,虽圣人其能违哉!选举之不慎而守令残民,世德之不终而诸侯乱纪,两俱有害,而民于守令之贪残,有所藉于黜陟以苏其困。
故秦、汉以降,天子孤立无辅,祚不永于商、周;而若东迁以后,交兵毒民,异政殊俗,横敛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数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则后世生民之祸亦轻矣。
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而为天下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
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世其位者习其道,法所便也;习其道者任其事,理所宜也。
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人得而习之。
贤而秀者,皆可以奖之以君子之位而长民。
圣人之心,于今为烈。
选举不慎,而贼民之吏代作,天地不能任咎,而况圣人!未可为郡县咎也。
若夫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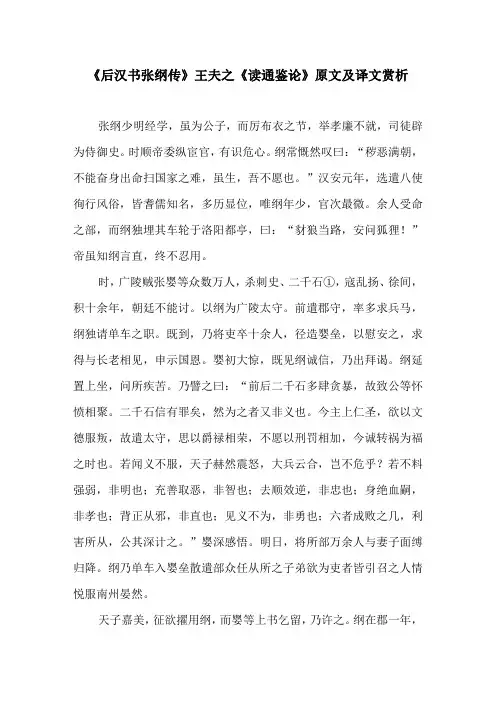
《后汉书张纲传》王夫之《读通鉴论》原文及译文赏析张纲少明经学,虽为公子,而厉布衣之节,举孝廉不就,司徒辟为侍御史。
时顺帝委纵宦官,有识危心。
纲常慨然叹曰:“秽恶满朝,不能奋身出命扫国家之难,虽生,吾不愿也。
”汉安元年,选遣八使徇行风俗,皆耆儒知名,多历显位,唯纲年少,官次最微。
余人受命之部,而纲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帝虽知纲言直,终不忍用。
时,广陵贼张婴等众数万人,杀刺史、二千石①,寇乱扬、徐间,积十余年,朝廷不能讨。
以纲为广陵太守。
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马,纲独请单车之职。
既到,乃将吏卒十余人,径造婴垒,以慰安之,求得与长老相见,申示国恩。
婴初大惊,既见纲诚信,乃出拜谒。
纲延置上坐,问所疾苦。
乃譬之曰:“前后二千石多肆贪暴,故致公等怀愤相聚。
二千石信有罪矣,然为之者又非义也。
今主上仁圣,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禄相荣,不愿以刑罚相加,今诚转祸为福之时也。
若闻义不服,天子赫然震怒,大兵云合,岂不危乎?若不料强弱,非明也;充善取恶,非智也;去顺效逆,非忠也;身绝血嗣,非孝也;背正从邪,非直也;见义不为,非勇也;六者成败之几,利害所从,公其深计之。
”婴深感悟。
明日,将所部万余人与妻子面缚归降。
纲乃单车入婴垒散遣部众任从所之子弟欲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悦服南州晏然。
天子嘉美,征欲擢用纲,而婴等上书乞留,乃许之。
纲在郡一年,年四十六卒。
百姓老幼相携,诣府赴哀者不可胜数。
张婴等五百余人制服行丧,负土成坟。
(《后汉书·张纲传》)张纲单骑诣贼垒,谕张婴而降之,言弭盗者侈为美谈。
然纲卒未几,婴复据郡以反,纲何尝能弭东南之盗哉!民行为盗,无以自容,使游泳于非逆非顺之交,翱翔而终思矫翮②;抑且宠而荣之,望其悔过自惩而不萌异志,岂能得哉?张纲者,以缓一时之祸,而不暇为国谋也,何足效哉!(王夫之《读通鉴论》)【注】①二千石:汉制,郡守俸禄为二千石,世因称郡守为“二千石”。
②翮:鸟翼,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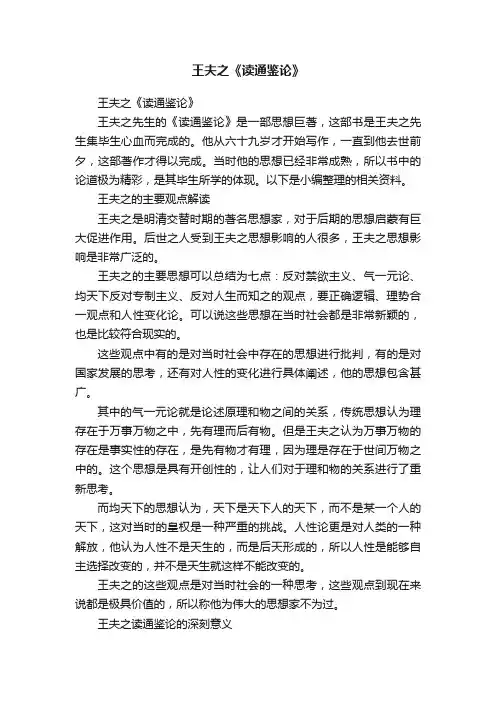
王夫之《读通鉴论》王夫之《读通鉴论》王夫之先生的《读通鉴论》是一部思想巨著,这部书是王夫之先生集毕生心血而完成的。
他从六十九岁才开始写作,一直到他去世前夕,这部著作才得以完成。
当时他的思想已经非常成熟,所以书中的论道极为精彩,是其毕生所学的体现。
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相关资料。
王夫之的主要观点解读王夫之是明清交替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对于后期的思想启蒙有巨大促进作用。
后世之人受到王夫之思想影响的人很多,王夫之思想影响是非常广泛的。
王夫之的主要思想可以总结为七点:反对禁欲主义、气一元论、均天下反对专制主义、反对人生而知之的观点,要正确逻辑、理势合一观点和人性变化论。
可以说这些思想在当时社会都是非常新颖的,也是比较符合现实的。
这些观点中有的是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思想进行批判,有的是对国家发展的思考,还有对人性的变化进行具体阐述,他的思想包含甚广。
其中的气一元论就是论述原理和物之间的关系,传统思想认为理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先有理而后有物。
但是王夫之认为万事万物的存在是事实性的存在,是先有物才有理,因为理是存在于世间万物之中的。
这个思想是具有开创性的,让人们对于理和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
而均天下的思想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天下,这对当时的皇权是一种严重的挑战。
人性论更是对人类的一种解放,他认为人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所以人性是能够自主选择改变的,并不是天生就这样不能改变的。
王夫之的这些观点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思考,这些观点到现在来说都是极具价值的,所以称他为伟大的思想家不为过。
王夫之读通鉴论的深刻意义这本书根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蓝本,对于先秦到五代之间的各个朝代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论述,其中有对历史规律的探寻,也有对当时人物的批判,他的观点独到,文采飞扬,是史学著作中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这本著作体现了王夫之的历史进化的'观点,他认为历史是在发展进步的,其中的每一项改革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人们凭空想象出来的,只是当时的社会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人们顺应历史去做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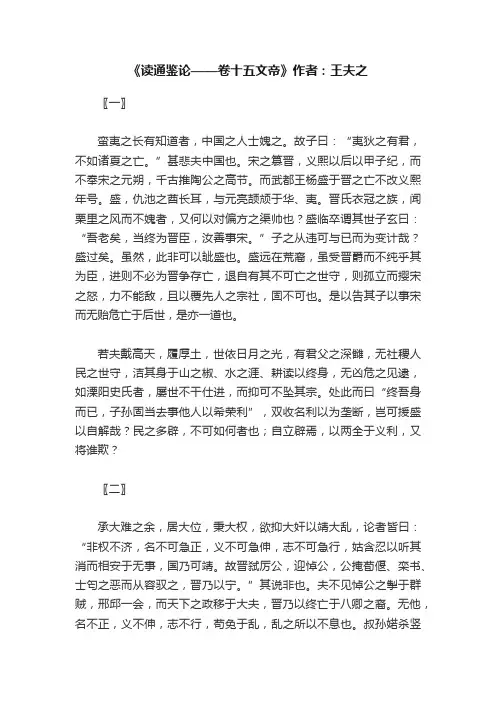
《读通鉴论——卷十五文帝》作者:王夫之〖一〗蛮夷之长有知道者,中国之人士媿之。
故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
”甚悲夫中国也。
宋之篡晋,义熙以后以甲子纪,而不奉宋之元朔,千古推陶公之高节。
而武都王杨盛于晋之亡不改义熙年号。
盛,仇池之酋长耳,与元亮颉颃于华、夷。
晋氏衣冠之族,闻栗里之风而不媿者,又何以对偏方之渠帅也?盛临卒谓其世子玄曰:“吾老矣,当终为晋臣,汝善事宋。
”子之从违可与已而为变计哉?盛过矣。
虽然,此非可以訿盛也。
盛远在荒裔,虽受晋爵而不纯乎其为臣,进则不必为晋争存亡,退自有其不可亡之世守,则孤立而撄宋之怒,力不能敌,且以覆先人之宗社,固不可也。
是以告其子以事宋而无贻危亡于后世,是亦一道也。
若夫戴高天,履厚土,世依日月之光,有君父之深雠,无社稷人民之世守,洁其身于山之椒、水之涯、耕读以终身,无凶危之见逮,如溧阳史氏者,屡世不干仕进,而抑可不坠其宗。
处此而曰“终吾身而已,子孙固当去事他人以希荣利”,双收名利以为垄断,岂可援盛以自解哉?民之多辟,不可如何者也;自立辟焉,以两全于义利,又将谁欺?〖二〗承大难之余,居大位,秉大权,欲抑大奸以靖大乱,论者皆曰:“非权不济,名不可急正,义不可急伸,志不可急行,姑含忍以听其消而相安于无事,国乃可靖。
故晋弑厉公,迎悼公,公掩荀偃、栾书、士匄之恶而从容驭之,晋乃以宁。
”其说非也。
夫不见悼公之掣于群贼,邢邱一会,而天下之政移于大夫,晋乃以终亡于八卿之裔。
无他,名不正,义不伸,志不行,苟免于乱,乱之所以不息也。
叔孙婼杀竖牛,而安其宗。
汉献帝不能正董卓之罪,待其骄横而始杀之,故李傕、郭氾得以报雠为名,杀大臣,逼天子,而关东州郡坐视不救,韩馥、袁绍且以其为贼所立,欲废之而立刘虞。
夫唯弑君之罪为神人所不容,而兄弟之痛根于性而弗容隐,受其援立,与相比暱,名不正,义不伸,志不行,忘亲贪位,如是而曰权也,是岂君子之所谓权乎?文帝初立,百务未举,首复庐陵王之封爵,迎其柩还建康,引见傅亮,号泣哀恸,问少帝、庐陵薨废本末,悲哭呜咽,亮、晦、羡之自危之心惴惴矣。
浅析王夫之的政治思想【摘要】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著名启蒙思想家,其政治思想历来为人们所重视。
王夫之的政治思想十分庞杂,主要包含四方面:“以民为基”的政治思想,“均天下”的均平思想,“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反专制思想和“宽以养民,严以治吏”的政治主张。
这些思想对当今社会的民富国强和反腐倡廉这两方面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王夫之;政治思想;意义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一壶道人,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故世称“船山先生”。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与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末四大学者。
王夫之学识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
他的著作很多,最重要的有《读通鉴论》、《宋论》、《黄书》等,他的政治思想基本上反映在这些著作中。
王夫之的政治思想内容丰富,体系十分庞杂。
我们可以把王夫之的政治思想体系看成一棵树,他的政治思想的基础或者说是树干就是“以民为基”的民本思想,这是他整个思想的核心。
从这个根本思想出发,他又提出了许多政治思想,主要包括“均天下”的均平思想,“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反专制思想和“宽以养民,严以治吏”的政治主张。
1“以民为基”的民本思想王夫之目睹明王朝封建统治者对民众实行重压政策最后葬身于农民起义风浪中的事实,认真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深深地认识到民众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他从维护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以民为基”的民本思想。
他说:“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人君之当行仁义,自是体上天命我作军师之心,而尽君道以为民父母,是切身第一天职”。
他认为,君民二者的关系,君主应该以民为根基,民心的向背是统治者地位是否稳固的关键,作为君主应当推行仁义的君道,真正关心民众,体察民情,应该以此作为“第一天职”来看待。
《读通鉴论》有一条“社稷不存以能保民者为重”,这也是王夫之引用史实对民本思想的具体阐释。
王夫之的民本思想对后世产生重大的影响,他以此被人称为“东方孟德斯鸠”。
史类《读通鉴论》清·王夫之撰卷六读通鉴论卷六后汉更始一为名而有所推奉者,其志不坚;人为名而尊己者,其立不固;项梁之立怀王,新市、平林之立更始是已。
天下愤楚之亡而望刘氏之再兴,人之同情也,而非项梁与张卬、王凤、朱鲔之情也。
怀王、更始不思其反,受其推戴而尸乎其位,名岂足以终系天下而戢桀骜者私利之心乎?怀王任宋义、抑项羽,而祸发于项氏;更始终恃诸将、而无与捍赤眉之锋。
徇不坚之志,立不固之基,疑之信之,无往而非召祸之门。
呜呼!其危也,非一旦一夕之故也。
而士之处斯世也难矣!彼以名而立君,而我弗事焉,则世且责我以名义;顺而与之,则今日之输忱,且为他日党贼之地。
荀彧所以退不保其身,进不全其节也。
嬴氏之暴,楚之亡,莽之篡,汉之中绝,苟有心者,孰不愤焉?而斟酌于从违,在间不容发之顷,一往之志,义未审而仆其生平。
无他,不揣其实而为名所动也。
慎之哉!二力均则度义,义均则度德;力可恃也,义可恃也,至于德而非可以自恃矣。
伯升果有天下之志,与更始力相上下而义相匹,则以德相胜,而天下恶能去已?诸将之欲立更始,无亦姑听之而待其自獘。
如其不弊,则天且授之,人且归之,而恶能与争?如其獘,则姑顺诸将之欲,自全于祸福之外,遵养以待时。
故高帝受巴、蜀、汉中之封,而待三秦之怨、三齐之反以屈项羽,而羽终屈。
伯升不知出此,婞婞然与张卬、朱鲔争,夫天下之大宝,岂有可自争而自得者乎?其见害于诸将也,不揆而犯难也。
李轶且扼腕而思害焉,况他人乎?三王莽既诛,更始定都雒阳,赤眉帅樊崇将渠帅二十余人入见,安危存亡之大机也,于此失之,而更始之亡决矣。
定天下之纷乱者,规模有可素定而未可全定也。
莽之未诛,汉之力全注于莽;莽平,群盗方兴而未戢,固其所不豫谋者。
一旦而莽诛矣,释其重忧而相庆以大定,猝然授以赤眉而不容其踌蹰以审处,豫谋所不及矣。
莽未诛,赤眉者,莽之赤眉也;莽已诛,赤眉者,汉之赤眉也。
以新造之邦,代莽而受赤眉之巨难,周章失措而不知所裁;及其算失事败,而后知前此之疏。
从《读通鉴论》看王夫之历史借鉴思想的特点从《读通鉴论》看王夫之历史借鉴思想的特点有以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言已终,卷已掩,好恶之情已竭,颓然若忘,临事而仍用其故心,闻见虽多,辨证虽详,亦程子所谓‘玩物丧志’也。
”[3](卷末,《叙论四》之二)显然,这里借解释司马光“资治”二字的深意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读史并非仅仅止于知道历史上的善恶美丑并感慨一番而已,关键的是要从中取资而反思,“临事而仍用其故心”当所深戒。
第二,他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从历史中求鉴这一主观意愿的重要作用。
他举诸多历史事实证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如:“君以柔嘉为则,而汉元帝失制以酿乱;臣以戆直为忠,而刘栖楚碎首以藏奸。
攘夷复中原,大义也,而梁武以败;含怒杀将帅,危道也,而周主以兴。
”凡此,说明了这样的道理:历史情境是复杂多变的,同样的原则和行事方式可能会有迥异的结局。
可见,历史“无不可为治之资者,无不可为乱之媒”。
而要避乱求得“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
王夫之深刻地阐释道:“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
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
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
”[3](卷末,《叙论四》之二)联系起来看,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历史实践主体的意愿(所谓“心”者)是从历史中求得借鉴的重要前提。
二是将这种求鉴的意愿用于指导政事具有重要的价值,有“宜民”并“成乎可久”之功。
三是指出了将这种主观意愿落到实处的具体路径,可用“设身处地”以蔽之,既是心态和方法,也可视为对认识主体的修养要求。
第三,他从认识论上注意到了历史何以能为当世之借鉴的问题,并进一步强调认识主体的主观动机(也包含修养)。
从过往历史中获得现实借鉴,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历史家的认知中是不成问题的前提存在[4],颇不同于西方古典文明的认知。
史类《读通鉴论》清·王夫之撰卷八读通鉴论卷八顺帝一惜天下之不治者,曰有君无臣。
诚有不世出之君矣,岂患无臣哉!所谓有君者,君在中材以(下)〔上〕[1],可与为善,而庸谫之臣,无能成其美而遏其恶也,则顺帝是已。
帝之废居西钟下也,顺以全生;群奸不忌,非不智也。
安帝崩;不得上殿亲临,悲号不食,非不仁也。
孙程等拯之危亡之中而登天位,一上殿争功,而免官就封,不使终持国政,非不断也。
谅虞诩之谏逐张防,听李固之言出阿母,任左雄之策清吏治,非不明也。
樊英、黄琼、郎凯公车接轸,纳翟酺之说,广拓学宫,非不知务也。
使得丙吉之量,宋璟、张九龄之节,韩琦之忠,姚崇、杜黄裳之才,清本源,振纲纪,以纳之于高明弘远之途,汉其复振矣乎!而桓焉、朱宠、朱伥之流,皆衰病瓦全,无生人之气,涂饰小康,自寡其过,不能取百年治乱之大端谨持其几。
而左雄、虞诩因事纳忠之小器,遂为当时之杰。
区区一庞参。
为时望所归,乃悍妻杀子于室而不能禁,本已先缺,而求物之正,必不能者;盈庭物望,遽尔归之,则其时在位之人才,概可知已。
帝德不终,而汉衰不复,良有以也。
夫岂天于季汉之世吝于生才哉!才焉而不适于用,用焉而不尽其才者多矣。
而其故有二:摧之,激之,成于女谒、宦竖、佥人之持权者则一也。
女谒、宦竖、佥人互相起伏,此败彼兴,而要不出于其局。
其摧焉而不克振者,仰虽忧国,俯抑恤己,清谨自持,苟祈免于清议,天下方倚之为重,而不知其不足有为也,则桓焉、朱伥之流是己。
近世叶福清贺江夏以之。
其激焉而为已甚者,又有二焉:一则愤嫉积于中,而抑采艸野怨读之声以求快于愚贱,事本易而难之,祸未至大而张之,有闻则起,有言必诤,授中主以沾直之讥,而小人反挟大体以相难,则李固、陈球之徒是也。
近世谏臣大抵如是。
一则伤宿蠹之未消,耻新猷之未展,谓中主必不可与有为,季世必不可以复挽,傲岸物表,清孤自奖,而坐失可为之机,则黄宪、徐穉、陈寔、袁闳之徒是也。
唐宋以下无其人矣。
激而争者,详于小而略于大,怒湍之水,不可以行巨舟。
《读通鉴论——卷十三国》作者:王夫之〖一〗国之亡,有自以亡也,至于亡,而所自亡之失昭然众见之矣。
后起者,因鉴之、惩之,而立法以弭之;然所戒在此,而所失在彼,前之覆辙虽不复蹈,要不足以自存。
汉亡于宦官外戚之交横,曹氏初立,即制宦者官不得过诸署令,黄初三年,又制后家不得辅政,皆鉴汉所自亡而惩之也。
然不再世,而国又夺于权臣。
立国无深仁厚泽之基,而豫教不修,子孙昏暴,扑火于原,而燄发于烓竃,虽厚戒之无救也。
自其亡而言之,汉之亡也,中绝复兴,暴君相继,久而后失之;魏之亡也不五世,无桀、纣之主而速灭;以国祚计之,汉为永矣。
乃自顺帝以后,数十年间,毒流天下,贤士骈首以就死,穷民空国以胥溺,盗贼接跡而蔓延;魏之亡也,祸不加于士,毒不流于民,盗不骋于郊;以民生计之,魏之民为幸矣。
故严椒房之禁,削扫除之权,国即亡而害及士民者浅,仁人之泽,不易之良法也。
乃昏主则曰:外戚宦官,内侍禁闼,未尝与民相接,恶从而朘削之?且其侈靡不节,间行小惠,以下施于贫乏,何至激而为盗?其剥民以致盗者,士大夫之贪暴为之也。
夫恶知监司守令之毒民有所自哉?纨袴之子,刑余之人,知谀而已,知贿而已;非谀弗官也,非贿弗谀也,非剥民之肤弗贿也,则毒流四海,填委沟壑,而困穷之民无所控告。
犹栩栩然曰:吾未尝有损于民,士大夫吮之以为利,而嫁祸于我以为名。
相激相诋,挟上以诛逐清流,而天下箝口结舌,视其败而无敢言。
汉、唐、宋之浸败而浸亡,皆此繇也。
其能禁此矣,则虽有夺攘之祸,而民不被其灾。
故司马篡曹,潜移于上而天下不知。
勿曰防之于此,失之于彼,魏之立法无裨于败亡也。
〖二〗魏从陈群之议,置州郡中正,以九品进退人才,行之百年,至隋而始易,其于选举之道,所失亦多矣。
人之得以其姓名与于中正之品藻者鲜也,非名誉弗闻也,非华族弗与延誉也。
故晋宋以后,虽有英才勤劳于国,而非华族之有名誉者,谓之寒人,不得与于荐绅之选。
其于公天爵于天下,而奖斯人以同善之道,殊相背戾,而帝王公天下之心泯矣。
贪腐行为是封建社会政治中的顽疾。
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虽然也极力打造吏治清明的形象,但少有成功的经验,更多的是失败的教训。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一书,对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述公元前403年-公元959年近1400年间的史实进行考察,分析了历代王朝反贪腐的情况及利弊得失,提出了自己的廉政主张,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政治镜鉴。
郭树伟《古代中国社会廉洁政治的历史沉思——读王夫之<读通鉴论>》一文,从三个方面分析概括了王夫之的廉政主张,即应把廉政贯穿于国家政策制定中,视廉洁政治为基本国策;加强官员廉政教育,廉政应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反对官员“清而矜、清而伪、清而朋、清而钝”;重视胥吏贪腐预防,提出“简法治吏”措施。
本版从今日起,分三期刊发此文,敬请关注。
——原编者王夫之(1619-1692)又称王船山,湖南衡阳人,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世称“船山先生”。
王夫之著述甚丰,《读通鉴论》、《宋论》是其代表作。
《读通鉴论》一书对古代中国社会从秦汉到唐五代时期的政治举措作了考察。
其中,对历朝统治者反贪腐、澄清吏治的措施和效果的考察,是这部书的一个重要方面。
该书所揭示的历代王朝在廉政方面的利弊得失,尤其是贪腐亡国的深刻教训和廉政主张,为我们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留下了有益的镜鉴。
一、应把廉政贯穿于国家政策制定中(一)《读通鉴论》一书认为,统治者应把廉政作为国家政治建设的基本国策之一,在确立政治、经济、法制、思想文化宣传等方面制度时,都应顾及廉政的内容。
对此,王夫之揭示了隋唐两朝经济政策和廉政制度失误的教训。
他指出,隋文帝“重税渔民、竭泽而渔、财聚民散”的贪吝财政政策,导致了国家的分崩离析;而唐朝改隋朝“贪吝财政”为“散财于民”的财政政策,又引发了“朝士以贿而容奸、逆臣亦以贿而自固”、“竞为奢侈”的官员文化风尚,以致“贿赂之败人国家,如鸩之必死”,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鲜明的警示。
王夫之认为,隋唐两朝实行的两种财政政策最终宽严皆失,原因是国家廉政制度的缺失。
隋朝实行贪吝财政政策的结果是“财聚民散”,并没有走向统治者所期望的国富民强的初衷。
而唐朝实行“散财于民”的财政政策,又引发了“竞为奢侈”的贪腐奢侈之风,最终导致国家覆亡。
这两种财政政策都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后果。
隋文帝奉行“富有四海,求盈不厌,侈其多藏,重毒天下,为恶之大而已矣”。
其财政政策最初设想是以富国为目的,却没料到过度的聚敛搜刮,竟导致天怒人怨、国家败亡。
“大俭之后,必生奢男”。
随后,隋炀帝穷奢极欲、挥霍浪费,正是对隋文帝的贪吝财政政策的一种报复。
而隋末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对隋文帝贪吝财政政策极具讽刺意味。
因朝廷过度聚敛,迫使老百姓啸聚山林,其聚敛的粮财反成为农民起义军的粮饷。
而这批粮饷一直用到唐高祖李渊时期,诚可谓“多藏厚亡”。
王夫之分析认为:“隋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财也。
”隋文帝的“节约政策”不能说是节约,不与天下百姓共享其财,其实是一种贪婪和吝啬,亡国破家是其必然结果。
继之而起的唐朝统治者,借鉴隋朝亡国的教训,采取“散财于民”、藏富于民的财政政策,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盖唐自立国以来,竞为奢侈,以衣裘仆马亭榭歌舞相尚,……李林甫、元载、王涯之狼藉;姚崇、张说、韦皋、李德裕之豪华;……朝士以贿而容奸,逆臣亦以贿而自固”。
唐朝的财政政策虽然没有“财聚民散”之弊,却导致了世风日下、道德滑坡。
国家高层官僚李林甫、元载、王涯等贪腐事件层出不穷,而姚崇、张说、韦皋、李德裕等高层官僚,极尽奢侈浮华之能事,官员风尚败坏。
即如该书所说:“唐之乱,贿赂充塞于天下为之耳。
凡三百余年,自卢怀慎、张九龄、裴休而外,唐之能饰簠簋(为官廉洁称为‘饰簠簋’)以自立于金帛之外者无有。
”唐朝官员的集体腐败,以致“贿赂之败人国家,如鸩之必死”。
王夫之认为,这是统治者在国家政策方面的缺陷导致的恶果。
《读通鉴论》一书认为,如果整个社会贪腐之风盛行,各级官吏层层盘剥,老百姓无疑是难以转嫁损失的社会底层,最后为贪腐“买单”,进而引发社会动乱,最终危及国家安全。
因此,反贪腐、澄清吏治与国家政权存亡攸关。
王夫之在此为我们描述了贪腐亡国的路径:先是老百姓为完税而疲于奔命,继而是作为社会单元的个体家庭寅吃卯粮、财务透支,造成百姓居家生活艰难,即如唐诗所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其后是社会底层抗税的百姓,身陷囹圄、“死于桁杨(即套在囚犯脚或颈的一种枷)”。
再其后是百姓“流亡日苦、起为盗贼”。
这种不安定的社会局面,又进一步为官吏贪腐提供了温床:“墨吏得此以张其威焰,猾胥得此以雠其罔毒。
”最后是“国日蠹、民日死”。
隋朝的社会发展全局如此,唐朝“安史之乱”之后的江南局势,亦复如此。
因贪腐而亡国的情形,在历朝演变的路径大致相似。
由此可见,廉洁政治是保证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和谐的重大课题,应当引起统治者的足够重视。
廉洁政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涉及国家的财政政策、思想文化、官员风尚等,统治者应通盘考虑,切不可顾此失彼。
王夫之总结了隋唐两朝财政政策的利弊得失,为统治阶级的廉洁政治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二)《读通鉴论》一书,并没有停留在对社会贪腐现象的观察上。
王夫之由表及里,深入挖掘了官员贪腐的思想文化根源,为廉洁政治建设开出了一剂良药。
封建社会的“家天下”结构,使皇帝过分考虑皇族利益,为一己之大私。
隋文帝过分顾及自己的“家天下”,厚敛于民,于是有了“贪吝”的报应。
而官员则考虑自己“天下之家”的利益,为一己之大私。
唐朝大臣元载过分考虑自己的“天下之家”,则有“蝜蝂”之祸。
王夫之从分析“家天下”的封建社会结构入手,揭示了官员贪腐的社会学原因:“故贪墨者,其人也;所以贪墨者,其子孙也。
”王夫之认为,由于官员贪腐是为其子孙后代打算,所以,反贪腐应标本兼治,“拔本塞源,施以禁锢之罚”。
换言之,既要反贪腐,也要加强官员廉政教育,要对官员子弟的吃穿用度,从法制和道德等方面予以监督和制约,并以此为契机,打造一种廉洁的社会风气。
应该让官员及其子弟懂得,如果自己享用贪腐之财,则将被社会所谴责。
“为子孙者,虽拥肥奡立,而士类弗齿;……人士羞与为朋侣”。
在王夫之看来,如果官员子弟受到约束,“子孙先怵,妻妾内忧”,官员就不会有过分的贪念,贪腐行为就会收敛。
如果官员没有贪腐行为,又会减少朝廷与百姓争利,“亦可藉手以寡怨于百姓”,造成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
采取这样的防治措施,可以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时也是对官员子弟的一种保护,是国家移风易俗、反贪腐、打造和谐社会的有益途径。
“非但弭生民之蟊贼,且以旌则善类,曲全中材,而风俗亦由之易矣”。
(三)《读通鉴论》一书在建立高层廉政战略方面,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分配国家高层反贪腐所得的财货?而这类财货的数量往往很大。
比如,清朝大贪官和珅贪腐事发,世人称之为“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嘉庆皇帝这种处理贪腐财货的方法,给后人留下了笑柄。
这虽然是王夫之以后的事情,但王夫之对此类问题确有先见之明。
王夫之认为,国家反贪腐所得的财货,本是贪官污吏盘剥百姓而来,国家不应苟得,应该还之于民,或减税于民。
他在书中说:“乱国之财赋,下掊克于民,而上不在官,民乃殄,国乃益贫,民罔不怨,天子闻之,赫然以怒,皆所必然,而无不快其发觉者。
然因此而句勘之以尽纳于上,则害愈浸淫,而民之死也益剧矣,是所谓‘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也。
假公科敛者,正以不发觉而犹有所止耳。
发觉矣,上顾因之而收其利,既无以大服其心,而唯思巧为掩饰以自免。
”通俗地说,贪官污吏的“乱国之财赋”,如果被收缴上来,老百姓当然高兴,但作为最高统治者,不能据为己有。
因为,这样做,很难赢得民心。
如果皇帝经常以反贪腐之名增加国家收入,实际上是国家对老百姓的税外之税。
朝廷又会形成一种印象:国家税赋已经收了一部分,而反贪腐又能获得这笔财货,看来,老百姓还能再拿出一些税。
于是,统治者就会滋生增税的念头:“有句勘之赢余,列于正供。
”这也正如俗语所说:“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
”牵牛者因牛践踏了别人的田地,人家把牛抢走了。
因为牛踩了别人田地,牵牛者确实有罪,但抢牛者的罪行更为严重。
如果国家占有反贪腐获得的财货,实质上是在“抢别人的牛”,是变相鼓励贪腐。
因此,老百姓会怀疑你的本意不是反贪腐,而是聚敛财货,会导致社会舆情恶化。
政府贪恋小利,甚至将其作为制度来执行,老百姓就会苦不堪言。
王夫之认为,如果国家得到反贪腐的财货,就应视其为“诚恶墨吏之横征”,这也是取之于民的财富。
朝廷应该量入为出、为生民计,体恤百姓完税之难;应视具体情况,减少以后的赋税。
“恤民困而念国之匮也,句勘得实,以抵来岁之赋,可以纾一时之急,而民亦苏矣”。
这样做,既能取悦于民,又能减少百姓之困,从而使“民知税有定额,而吏亦戢”。
让老百姓知道政府没有额外之税,官吏的贪腐行为也会有所收敛,从而扩大反贪腐的社会效果。
这才是处理反贪腐所得财货的正确方法。
二、应加强官员廉政教育,反对官员“清而矜、清而伪、清而朋、清而钝”(一)《读通鉴论》一书认为,朝廷官员(包括皇帝)的道德操守如何,始终是反贪腐的重大课题。
“人之能为大不韪者,非其能无所惧也,唯其能无所耻也。
故血气之勇不可任,而犹可器使;唯无所耻者,国家用之而必亡……故管子曰:廉耻,国之维也”。
基于这种认识,王夫之认为,统治者要对各级官员进行廉政教育,高层官员尤其要不贪苟得之财,注意自身的清廉。
接着,王夫之阐述了贿赂公行的社会危害性:“贿行于中涓(亲近之臣),而天子慑;贿行于宰相,而百官不能争;贿行于省寺台谏,而天子宰相亦不能胜”。
这就是说,如果贿赂发生在朝廷,皇帝就应该惧怕;如果宰相收受贿赂,其臣下就不敢驳斥;国家行政系统普遍贪腐了,政务就会壅蔽,那么皇帝、宰相也无可奈何。
书中说:“唐之乱,贿赂充塞于天下为之耳。
”唐朝的衰亡,贿赂公行是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皇帝和权臣坚持清正廉洁,是对一般官员廉政教育的源头之水。
皇帝和权臣不仅要自身清廉,还要选好身边的“十数人”和“二三人”,抓好身边官员的清廉。
“上官则九州之大,十数人而已,司宪者弗难知也;居中司宪者,二三人而已,天子弗难知也。
顾佐洁身于台端(侍御史别称),而天下无贪吏,握风纪之枢,以移易清浊之风者,止在一人”。
皇帝固然不能具体抓每一起贪腐案件,但应选好身边人,抓好身边人的清廉。
皇帝应从身边官员的选拔抓起。
“顾佐洁身于台端,而天下无贪吏”,“举直错诸枉”,努力造成一种廉洁的风尚,取得以小搏大、以寡驭众的效果。
所谓“慎之于选任之日,奖之以君子之道”,是说在官员选拔之初,就应以君子的标准要求他们,用道德廉耻观教育他们,引导官员走清廉之路。
在这本书中,王夫之批评了东汉灵帝、北齐高洋帝“不教而杀”的反贪腐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