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视域下的甘谷汉简
- 格式:doc
- 大小:22.50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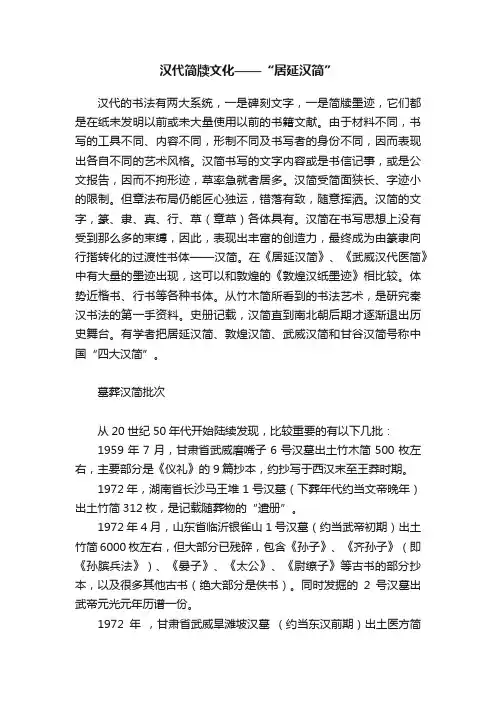
汉代简牍文化——“居延汉简”汉代的书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简牍墨迹,它们都是在纸未发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书籍文献。
由于材料不同,书写的工具不同、内容不同,形制不同及书写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
汉简书写的文字内容或是书信记事,或是公文报告,因而不拘形迹,草率急就者居多。
汉简受简面狭长、字迹小的限制。
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独运,错落有致,随意挥洒。
汉简的文字,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具有。
汉简在书写思想上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缚,因此,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最终成为由篆隶向行揩转化的过渡性书体——汉简。
在《居延汉简》、《武威汉代医简》中有大量的墨迹出现,这可以和敦煌的《敦煌汉纸墨迹》相比较。
体势近楷书、行书等各种书体。
从竹木简所看到的书法艺术,是研究秦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
史册记载,汉简直到南北朝后期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有学者把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和甘谷汉简号称中国“四大汉简”。
墓葬汉简批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发现,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批:1959年7月,甘肃省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竹木简500枚左右,主要部分是《仪礼》的9篇抄本,约抄写于西汉末至王莽时期。
1972年,湖南省长沙马王堆 1 号汉墓(下葬年代约当文帝晚年)出土竹简312枚,是记载随葬物的“遣册”。
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约当武帝初期)出土竹简6000枚左右,但大部分已残碎,包含《孙子》、《齐孙子》(即《孙膑兵法》)、《晏子》、《太公》、《尉缭子》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很多其他古书(绝大部分是佚书)。
同时发掘的2号汉墓出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一份。
1972年,甘肃省武威旱滩坡汉墓(约当东汉前期)出土医方简牍一批。
1973年,河北省定县40 号汉墓(为西汉晚期的中山王墓)出土一批已经炭化的残碎竹简,字迹尚可勉强辨认。
其中有《论语》、《文子》、《太公》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内容大都见于《孔子家语》、《说苑》、《大戴礼记》等书的一些儒家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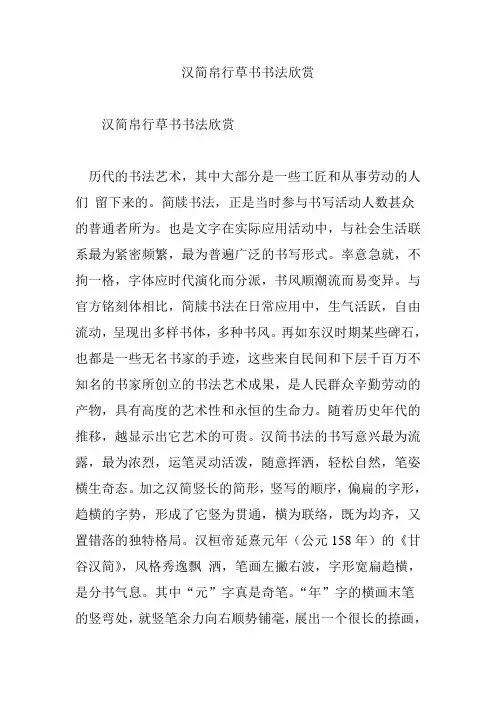
汉简帛行草书书法欣赏汉简帛行草书书法欣赏历代的书法艺术,其中大部分是一些工匠和从事劳动的人们留下来的。
简牍书法,正是当时参与书写活动人数甚众的普通者所为。
也是文字在实际应用活动中,与社会生活联系最为紧密频繁,最为普遍广泛的书写形式。
率意急就,不拘一格,字体应时代演化而分派,书风顺潮流而易变异。
与官方铭刻体相比,简牍书法在日常应用中,生气活跃,自由流动,呈现出多样书体,多种书风。
再如东汉时期某些碑石,也都是一些无名书家的手迹,这些来自民间和下层千百万不知名的书家所创立的书法艺术成果,是人民群众辛勤劳动的产物,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永恒的生命力。
随着历史年代的推移,越显示出它艺术的可贵。
汉简书法的书写意兴最为流露,最为浓烈,运笔灵动活泼,随意挥洒,轻松自然,笔姿横生奇态。
加之汉简竖长的简形,竖写的顺序,偏扁的字形,趋横的字势,形成了它竖为贯通,横为联络,既为均齐,又置错落的独特格局。
汉桓帝延熹元年(公元158年)的《甘谷汉简》,风格秀逸飘洒,笔画左撇右波,字形宽扁趋横,是分书气息。
其中“元”字真是奇笔。
“年”字的横画末笔的竖弯处,就竖笔余力向右顺势铺毫,展出一个很长的捺画,逆入起笔,平出回锋,末一横之波磔,姿态婉妙,势刚力柔,“蚕头燕尾”,兴味绵长。
捺画的夸张,长竖的放纵,即是意兴,亦是匠心。
每行各为气势,又互为照应;这一行此外字形如小,那一行彼外字形必大;此行生波磔书,彼行发竖笔直下,错落参差,极露灵性。
章法启行草,布白比汉印,细读起来很有兴味。
也正是以其活泼而浪漫的笔法,形成了汉简书法妩媚天然,生机蓬勃的风采神韵。
书法艺术是一种线条的搭配和变化的艺术,它的艺术美是通过线条的错综变化表达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书写的材料、工具对书法艺术效果的产生关系极大。
简牍书体的形式,是与它的书写工具密切相关,用具有弹性的毛笔写在硬性狭长的竹木条上,这是汉简书法成功的基本保证。
先看两汉人所作的笔。
从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一支毛笔来看,笔头的蕊及锋用黑紫色的硬毛,外面用一层较软的黄褐色毛,显而易见这样的笔基本上达到了毛笔的四德,即为尖、圆、齐、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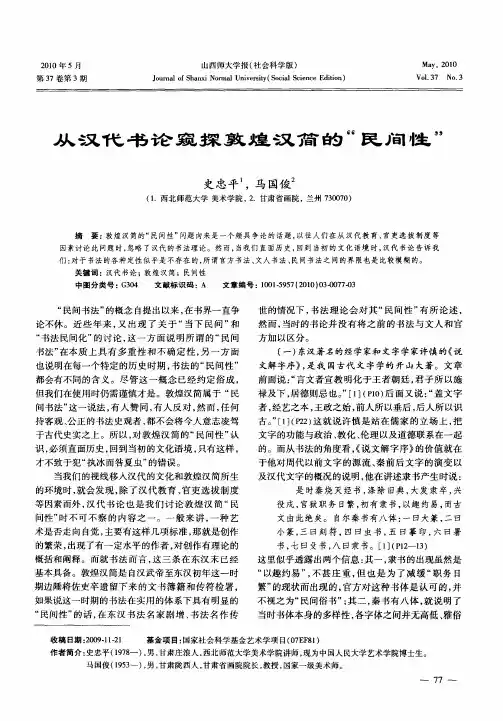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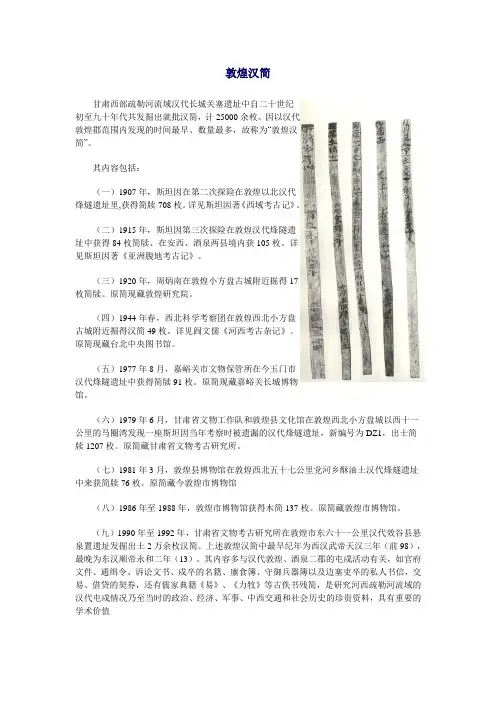
敦煌汉简甘肃西部疏勒河流域汉代长城关塞遗址中自二十世纪初至九十年代共发掘出就批汉简,计25000余枚。
因以汉代敦煌郡范围内发现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故称为“敦煌汉简”。
其内容包括:(一)1907年,斯坦因在第二次探险在敦煌以北汉代烽燧遗址里,获得简牍708枚。
详见斯坦因著《西域考古记》。
(二)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探险在敦煌汉代烽隧遗址中获得84枚简牍、在安西、酒泉两县境内获105枚。
详见斯坦因著《亚洲腹地考古记》。
(三)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盘古城附近掘得17枚简牍。
原简现藏敦煌研究院。
(四)1944年春,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西北小方盘古城附近掘得汉简49枚。
详见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
原简现藏台北中央图书馆。
(五)1977年8月,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在今玉门市汉代烽隧遗址中获得简牍91枚。
原简现藏嘉峪关长城博物馆。
(六)1979年6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敦煌县文化馆在敦煌西北小方盘城以西十一公里的马圈湾发现一座斯坦因当年考察时被遗漏的汉代烽燧遗址,新编号为DZ1,出士简牍1207枚。
原简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七)1981年3月,敦煌县博物馆在敦煌西北五十七公里党河乡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中来获简牍76枚。
原简藏今敦煌市博物馆(八)1986年至1988年,敦煌市博物馆获得木简137枚。
原简藏敦煌市博物馆。
(九)1990年至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市东六十一公里汉代效谷县悬泉置遗址发掘出土2万余枚汉简。
上述敦煌汉简中最早纪年为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最晚为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3)。
其内容多与汉代敦煌、酒泉二郡的屯戍活动有关,如官府文件、通缉令、诉讼文书、戍卒的名籍、廪食簿、守御兵器簿以及边塞吏卒的私人书信,交易、借贷的契券,还有儒家典籍《易》、《力牧》等古佚书残简,是研究河西疏勒河流域的汉代屯戍情况乃至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中西交通和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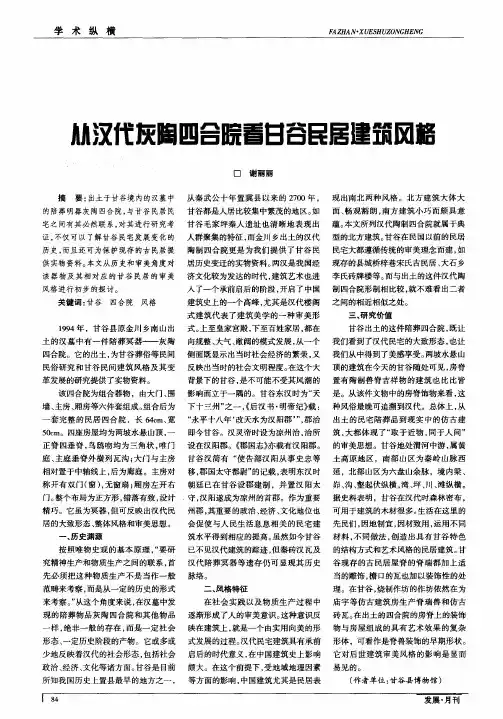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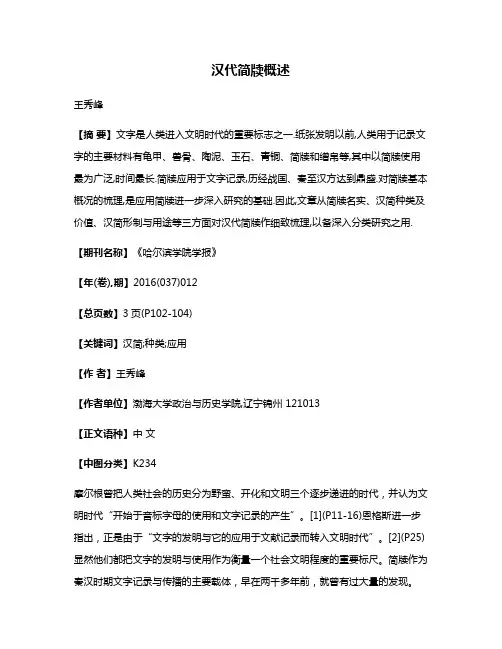
汉代简牍概述王秀峰【摘要】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纸张发明以前,人类用于记录文字的主要材料有龟甲、兽骨、陶泥、玉石、青铜、简牍和缯帛等,其中以简牍使用最为广泛,时间最长.简牍应用于文字记录,历经战国、秦至汉方达到鼎盛.对简牍基本概况的梳理,是应用简牍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因此,文章从简牍名实、汉简种类及价值、汉简形制与用途等三方面对汉代简牍作细致梳理,以备深入分类研究之用.【期刊名称】《哈尔滨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37)012【总页数】3页(P102-104)【关键词】汉简;种类;应用【作者】王秀峰【作者单位】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锦州 12101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34摩尔根曾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分为野蛮、开化和文明三个逐步递进的时代,并认为文明时代“开始于音标字母的使用和文字记录的产生”。
[1](P11-16)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与它的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转入文明时代”。
[2](P25)显然他们都把文字的发明与使用作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
简牍作为秦汉时期文字记录与传播的主要载体,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曾有过大量的发现。
《晋书·卫恒传》载:“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
”[3](P1061)囿于时代所限,这些古代遗存并未保留下来。
直到20世纪以后,随着考古学的传入与发展,才有了古代简牍的大量出土以及由此形成的简牍学研究。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的概称。
“简”是经过修治的细竹条,细木条称为“札”或“劄”;较宽的木板或竹板称为“牍”。
[4](P22)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简,从竹,间声”;“牍,书版也,从片”,片就是剖开的木头。
[5](P291;P458)《辞源》曰:“简牍,即书牍。
古时无纸,书于木片曰牍,书于竹版曰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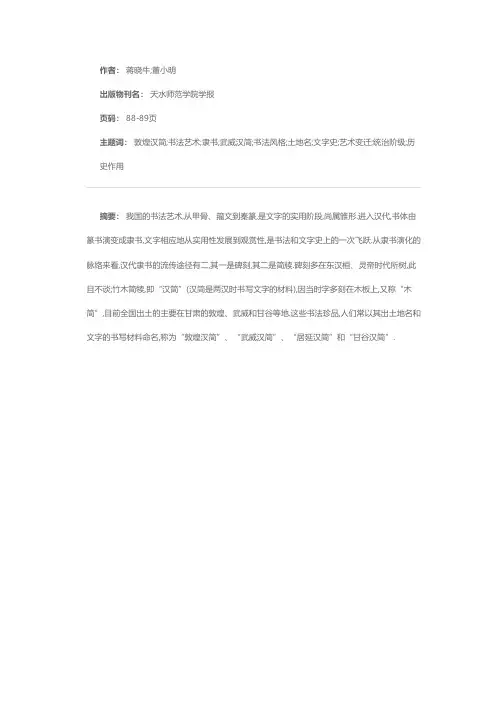
作者: 蒋晓牛;董小明
出版物刊名: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页码: 88-89页
主题词: 敦煌汉简;书法艺术;隶书;武威汉简;书法风格;土地名;文字史;艺术变迁;统治阶级;历史作用
摘要: 我国的书法艺术,从甲骨、籀文到秦篆,是文字的实用阶段,尚属雏形.进入汉代,书体由篆书演变成隶书,文字相应地从实用性发展到观赏性,是书法和文字史上的一次飞跃.从隶书演化的脉络来看,汉代隶书的流传途径有二,其一是碑刻,其二是简牍.碑刻多在东汉桓、灵帝时代所树,此且不谈;竹木简犊,即“汉简”(汉简是两汉时书写文字的材料),因当时字多刻在木板上,又称“木简”,目前全国出土的主要在甘肃的敦煌、武威和甘谷等地.这些书法珍品,人们常以其出土地名和文字的书写材料命名,称为“敦煌汉简”、“武威汉简”、“居延汉简”和“甘谷汉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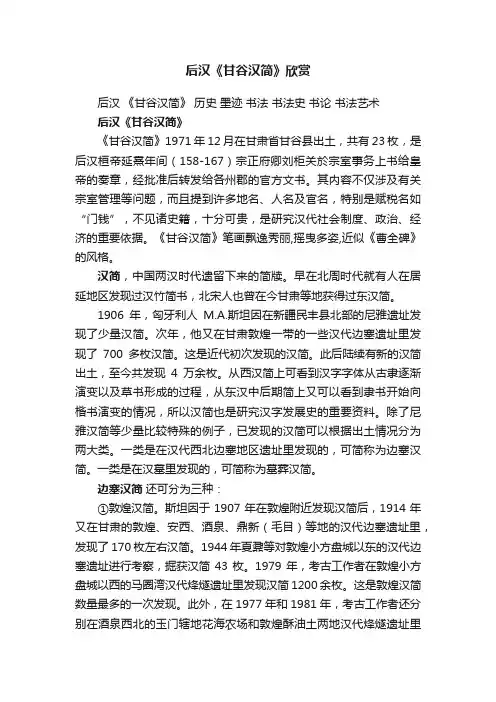
后汉《甘谷汉简》欣赏后汉《甘谷汉简》历史墨迹书法书法史书论书法艺术后汉《甘谷汉简》《甘谷汉简》1971年12月在甘肃省甘谷县出土,共有23枚,是后汉桓帝延熹年间(158-167)宗正府卿刘柜关於宗室事务上书给皇帝的奏章,经批准后转发给各州郡的官方文书。
其内容不仅涉及有关宗室管理等问题,而且提到许多地名、人名及官名,特别是赋税名如“门钱”,不见诸史籍,十分可贵,是研究汉代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的重要依据。
《甘谷汉简》笔画飘逸秀丽,摇曳多姿,近似《曹全碑》的风格。
汉简,中国两汉时代遗留下来的简牍。
早在北周时代就有人在居延地区发现过汉竹简书,北宋人也曾在今甘肃等地获得过东汉简。
1906年,匈牙利人M.A.斯坦因在新疆民丰县北部的尼雅遗址发现了少量汉简。
次年,他又在甘肃敦煌一带的一些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700多枚汉简。
这是近代初次发现的汉简。
此后陆续有新的汉简出土,至今共发现4万余枚。
从西汉简上可看到汉字字体从古隶逐渐演变以及草书形成的过程,从东汉中后期简上又可以看到隶书开始向楷书演变的情况,所以汉简也是研究汉字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除了尼雅汉简等少量比较特殊的例子,已发现的汉简可以根据出土情况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在汉代西北边塞地区遗址里发现的,可简称为边塞汉简。
一类是在汉墓里发现的,可简称为墓葬汉简。
边塞汉简还可分为三种:①敦煌汉简。
斯坦因于1907年在敦煌附近发现汉简后,1914年又在甘肃的敦煌、安西、酒泉、鼎新(毛目)等地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170枚左右汉简。
1944年夏鼐等对敦煌小方盘城以东的汉代边塞遗址进行考察,掘获汉简43枚。
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敦煌小方盘城以西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里发现汉简1200余枚。
这是敦煌汉简数量最多的一次发现。
此外,在1977年和1981年,考古工作者还分别在酒泉西北的玉门辖地花海农场和敦煌酥油土两地汉代烽燧遗址里采集了一些汉简。
斯坦因1914年发现汉简的地点横跨汉代敦煌、酒泉两郡,70年代发现汉简的玉门花海也应属酒泉郡,但是习惯上把这些汉简统称为敦煌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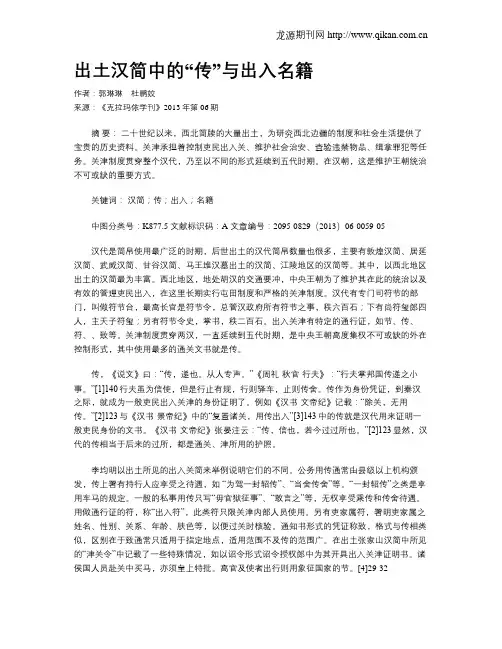
出土汉简中的“传”与出入名籍作者:郭琳琳杜鹏姣来源:《克拉玛依学刊》2013年第06期摘要:二十世纪以来,西北简牍的大量出土,为研究西北边疆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关津承担着控制吏民出入关、维护社会治安、查验违禁物品、缉拿罪犯等任务。
关津制度贯穿整个汉代,乃至以不同的形式延续到五代时期。
在汉朝,这是维护王朝统治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汉简;传;出入;名籍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6-0059-05汉代是简帛使用最广泛的时期,后世出土的汉代简帛数量也很多,主要有敦煌汉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甘谷汉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汉简、江陵地区的汉简等。
其中,以西北地区出土的汉简最为丰富。
西北地区,地处胡汉的交通要冲,中央王朝为了维护其在此的统治以及有效的管理吏民出入,在这里长期实行屯田制度和严格的关津制度。
汉代有专门司符节的部门,叫做符节台,最高长官是符节令,总管汉政府所有符节之事,秩六百石;下有尚符玺郎四人,主天子符玺;另有符节令史,掌书,秩二百石。
出入关津有特定的通行证,如节、传、符、、致等。
关津制度贯穿两汉,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是中央王朝高度集权不可或缺的外在控制形式,其中使用最多的通关文书就是传。
传,《说文》曰:“传,递也。
从人专声。
”《周礼·秋官·行夫》:“行夫掌邦国传递之小事。
”[1]140行夫虽为信使,但是行止有规,行则驿车,止则传舍。
传作为身份凭证,到秦汉之际,就成为一般吏民出入关津的身份证明了。
例如《汉书·文帝纪》记载:“除关,无用传。
”[2]123与《汉书·景帝纪》中的“复置诸关,用传出入”[3]143中的传就是汉代用来证明一般吏民身份的文书。
《汉书·文帝纪》张晏注云:“传,信也,若今过过所也。
”[2]123显然,汉代的传相当于后来的过所,都是通关、津所用的护照。
李均明以出土所见的出入关简来举例说明它们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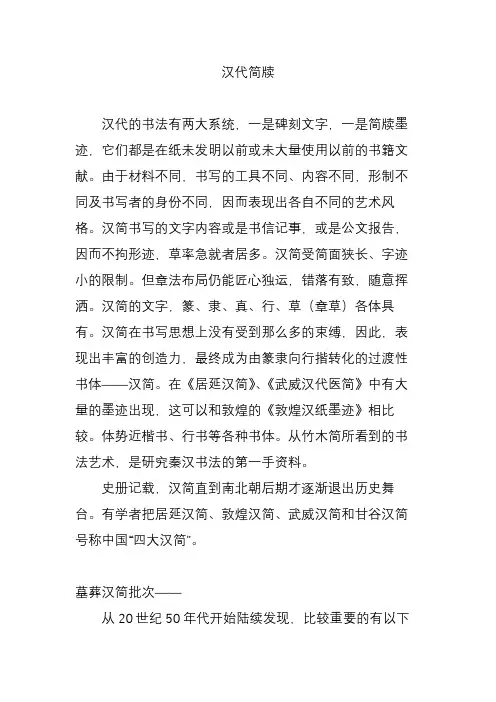
汉代简牍汉代的书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简牍墨迹,它们都是在纸未发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书籍文献。
由于材料不同,书写的工具不同、内容不同,形制不同及书写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
汉简书写的文字内容或是书信记事,或是公文报告,因而不拘形迹,草率急就者居多。
汉简受简面狭长、字迹小的限制。
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独运,错落有致,随意挥洒。
汉简的文字,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具有。
汉简在书写思想上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缚,因此,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最终成为由篆隶向行揩转化的过渡性书体——汉简。
在《居延汉简》、《武威汉代医简》中有大量的墨迹出现,这可以和敦煌的《敦煌汉纸墨迹》相比较。
体势近楷书、行书等各种书体。
从竹木简所看到的书法艺术,是研究秦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
史册记载,汉简直到南北朝后期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有学者把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和甘谷汉简号称中国“四大汉简”。
墓葬汉简批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发现,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批:1959年7月,甘肃省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竹木简500枚左右,主要部分是《仪礼》的9篇抄本,约抄写于西汉末至王莽时期。
1972年,湖南省长沙马王堆1 号汉墓(下葬年代约当文帝晚年)出土竹简312枚,是记载随葬物的“遣册”。
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约当武帝初期)出土竹简6000枚左右,但大部分已残碎,包含《孙子》、《齐孙子》(即《孙膑兵法》)、《晏子》、《太公》、《尉缭子》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很多其他古书(绝大部分是佚书)。
同时发掘的2号汉墓出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一份。
1972年,甘肃省武威旱滩坡汉墓(约当东汉前期)出土医方简牍一批。
1973年,河北省定县40 号汉墓(为西汉晚期的中山王墓)出土一批已经炭化的残碎竹简,字迹尚可勉强辨认。
其中有《论语》、《文子》、《太公》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内容大都见于《孔子家语》、《说苑》、《大戴礼记》等书的一些儒家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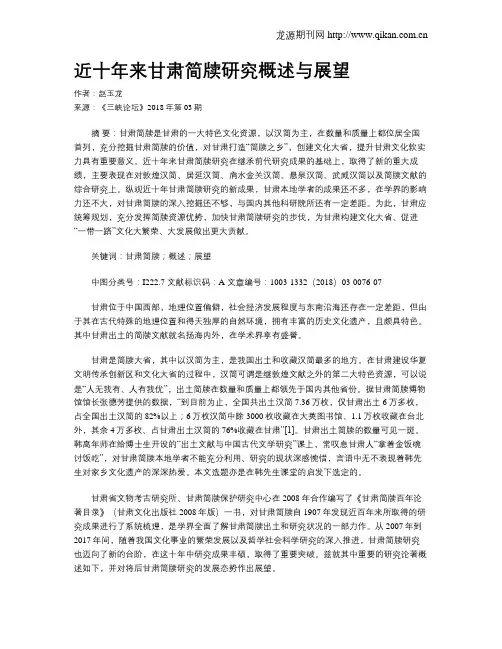
近十年来甘肃简牍研究概述与展望作者:赵玉龙来源:《三峡论坛》2018年第03期摘要:甘肃简牍是甘肃的一大特色文化资源,以汉简为主,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位居全国首列,充分挖掘甘肃简牍的价值,对甘肃打造“简牍之乡”,创建文化大省,提升甘肃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近十年来甘肃简牍研究在继承前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重大成绩,主要表现在对敦煌汉简、居延汉简、肩水金关汉简、悬泉汉简、武威汉简以及简牍文献的综合研究上。
纵观近十年甘肃简牍研究的新成果,甘肃本地学者的成果还不多,在学界的影响力还不大,对甘肃简牍的深入挖掘还不够,与国内其他科研院所还有一定差距。
为此,甘肃应统筹规划,充分发挥简牍资源优势,加快甘肃简牍研究的步伐,为甘肃构建文化大省、促进“一带一路”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甘肃简牍;概述;展望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3-0076-07甘肃位于中国西部,地理位置偏僻,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与东南沿海还存在一定差距,但由于其在古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且颇具特色。
其中甘肃出土的简牍文献就名扬海内外,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甘肃是简牍大省,其中以汉简为主,是我国出土和收藏汉简最多的地方。
在甘肃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和文化大省的过程中,汉简可谓是继敦煌文献之外的第二大特色资源,可以说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出土简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领先于国内其他省份。
据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张德芳提供的数据,“到目前为止,全国共出土汉简7.36万枚,仅甘肃出土6万多枚,占全国出土汉简的82%以上;6万枚汉简中除3000枚收藏在大英图书馆、1.1万枚收藏在台北外,其余4万多枚、占甘肃出土汉简的76%收藏在甘肃”[1]。
甘肃出土简牍的数量可见一斑。
韩高年师在给博士生开设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课上,常叹息甘肃人“拿着金饭碗讨饭吃”,对甘肃简牍本地学者不能充分利用、研究的现状深感惋惜,言语中无不表现着韩先生对家乡文化遗产的深深热爱。
⼭西境内⾸批汉代简牍出⼟,来感受下北⼤考古的含⾦量!编者按⼭西境内、黄⼟⾼原半⼲旱地区⾸次发掘的汉代简牍成套的漆奁盒与铜镜、琴瑟乐器组合漆案、漆盘、漆⽿杯、漆纚冠铜印、⽟印、串珠……今年夏天这些汉代⽂物从太原东⼭古墓中重见天⽇太原东⼭古墓M6的实验室考古⼯作。
参与这次考古⼯作的,不仅有北⼤太原市⽂物考古研究所合作,从今年暑期开始展开了太原东⼭古墓北京⼤学考古⽂博学院与太原市⽂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学考古⽂博学院⽂物的发掘与保护当中,北⼤考古⽂博学院的师⽣,还有⼏位来⾃北⼤化学与分⼦⼯程学院的同学。
考古实践中,他们把书本上的化学知识书本上的化学知识真正⽤到了⽂物的发掘与保护跨学科的优势得到集中体现和应⽤。
接下来,就⼀起来分享这些北⼤师⽣挖到国宝的神奇经历吧!01新式实验室考古在太原东⼭汉墓展开2013年以来,⼭西省太原市的⽂物考古⼯作者在太原东⼭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古墓群,并推测其主墓可能属于西汉代王及王后,这是近年汉代考古的重⼤发现之⼀。
2018年暑期,北京⼤学考古⽂博学院受邀参与了该墓地祔葬墓M6的实验室考古⼯作,与当地的考古⼯作者⼀起,实践了⼀种新的实验室考古⼯作模式。
实验室考古⼯作现场北⼤研究⽣进⾏红外摄影北⼤研究⽣进⾏取样应急保护⼏个步骤有机结合,能有效辨识腐朽严重的⽂物遗存,提取易被忽略的考古学信息,实施针对分析鉴定、应急保护⼏个步骤有机结合发掘清理、分析鉴定这种实验室考古新模式将发掘清理性保护措施。
这次考古⼯作出⼟了成套漆奁盒与铜镜、琴瑟乐器组合、漆案、漆盘、漆⽿杯、漆纚冠、铜印、⽟印、串珠等珍贵⽂物,并获得重⼤发现,出⼟⼤批⽊质简牍。
现已运抵北京⼤学考古⽂博学院,即将开展后续保护和整理⼯作。
这是在⼭西境内、同时也是黄⼟⾼原半⼲旱地区⾸次发现简牍⽂物。
这批汉代简牍现已运抵北京⼤学考古⽂博学院联合⼯作组开展实验室考古发掘考古发掘中的⽂物02考古⽂博学院的⽊质⽂物保护研究在北京⼤学考古⽂博学院⽂物保护专业,胡东波教授从事⽂物保护⼯作与科研已经有三⼗多年了。
「鉴赏」河西黄土高原出土的简——甘谷汉简河西黄土高原出土的简——甘谷汉简书法报 2019-11-29 11:51:00甘谷是甘肃天水市的一个县,它位于天水市西北的渭河流域,其地貌属于陇西的黄土高原,这与甘肃省内出土简牍的大部分戈壁沙漠地貌不同,加之其内容和书体的重要性,使其在甘肃出土的数以万计的汉简中占有特殊地位。
甘肃出土的汉简最著名的有敦煌汉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这三批汉简都是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形制多样的具有代表性的西北汉简,而甘谷汉简一共才出土了23枚,但由于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竟跟敦煌汉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并列为甘肃所出的西北汉简中最著名的四大汉简。
甘谷汉简甘谷汉简1971年12月发现于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新兴镇刘家屲(wā)的一座汉墓中,共23枚。
其简多系松木制作,长23.5cm,宽2.5cm,厚0.4cm,两道编绳,先编后写,整齐划一,原件现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谷汉简局部这是一组标准的“两行”木简,保存完好,每简上抄写两行文字,一般每行抄写30字左右,每枚简上大致60余字,第5枚简上所抄的字最多,有74字。
简的背面编有简序,分别标注为“第一”“第五”“第二十三”等字样。
甘谷汉简局部根据同墓出土的陶罐上朱书“刘氏之泉”“刘氏之冢”的记载,可以确定这批简牍的主人姓刘,简文内容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158—167)宗正府卿刘柜关于宗室事务上书给皇帝的奏章,经批准后转发给各州郡的官方文书,包括汉阳郡太守转发给所属县、乡的诏书、律令及敕命文书等。
其中第1至第21枚记的是东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宗正府卿刘柜关于维护刘姓皇帝宗室特权的文书。
第22和23枚是凉州刺史(刘)治与汉阳太守(刘)济逐级下移“属县令长”优复宗室的诏书。
其内容不仅涉及有关宗室管理等问题,而且其中所出现的许多地名、人名及官名,特别是赋税名如“门钱”,多不见诸史籍,故十分可贵,是研究东汉时期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第一章 甘谷民间文化遗产的现状综述公元前688年,偏居中国西北一隅的秦国在秦武公的带领下西伐冀、邽的氐戎族部落,西伐告捷后旋于冀、邽之地建立由秦国中央政府直接统辖的冀、邽二县。
此举不仅使秦国势力不久到达关中渭水流域,也宣告秦国开始的西伐东进,为其逐鹿中原拉开了序幕。
四百余年后的公元前221年,秦一统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邽、冀二县归入陇西郡。
正如清代邑人巩建丰在《伏羌县志》中所写:“封建改为郡邑,虽职不世守,人民社稷存焉。
”由此拉开了中国君主集权的郡县制治理体系的帷幕。
秦国的冀、邽二县县城所在地大致在今天的甘肃省天水市辖区的秦州区、甘谷县、清水县区域。
冀县所在地基本与现甘谷县县城重合,邽县则介于天水秦州区、清水县间。
就行政区划来说,古冀县所在的甘谷县所在地,自其开始建县以来,虽然经历了两千七百余年的风风雨雨,名字也几经更迭,但其基本县治没有多大变化,这从侧面印证了古冀县——甘谷——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甘谷县地处甘肃省东南部,黄土高原西南麓,渭河中游。
东邻天水市秦安县、麦积区,南接天水市秦州区、陇南礼县,西与天水市武山县接壤,北与定西市通渭县相连。
其南北长60千米,东西宽49千米,总面积1 572 6平方千米,整体介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交界处。
黄河最大支流——渭河,出渭源鸟兽山,由西向东横贯甘谷全县,在甘谷县境内长度达40余千米,穿城北而过。
“诗圣”杜甫在“安史之乱”后,流寓秦州时描写的“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大致也可说是甘谷县城的写照。
甘谷县境内梁、峁、沟、壑起伏纵横,湾、坪、川、滩交错如棋,平均海拔1 972米。
渭河南北差异较大,渭河北为黄土覆盖的六盘山余脉,散渡河河谷将北部山区由北至南横切而过,形成南北走向的河谷通道,该区域基本为黄土峁梁沟壑区,山势较为低而平缓,干燥少雨,土地贫瘠,但可耕面积大,北宋时抵御西夏的甘谷堡和安远寨即位于此区域。
渭河南部山区为秦岭山脉西延——朱圉山脉,禹疏渭入河之踪迹。
甘肃地区汉简研究对于现代书法发展的意义摘要:在汉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多样化,书法风格也在以往的形态模式上呈现出差异性,这些书法风格的转变为后世的书法发展提供了广袤的发展基础和较为深远的影响。
在汉简出土以前,人们了解书法主要通过汉碑上的刻字,汉碑刻字虽然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汉字从篆到隶的发展,但是并不能很好地诠释书写汉字的轻重缓急,也不能体现出两汉劳动人民的书法风格,且在碑文中,体现东汉内容居多,西汉较少。
故而在20世纪简牍出土以前,人们对于汉代书法的发展变迁还处于猜测和推想阶段,并无过多实物可证实。
上世纪初汉简在敦煌一经发现便震惊于世,随后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分析研究。
汉简作为重要的史料弥补了这一段时期的书体发展的缺失,也让我们更加直观的看到两千年前的书法手迹,从中探析到两汉时期人们的生活状态及书法习惯。
甘肃有汉简之都的美誉,这里出土了全国将近五分之四的简牍,包括人们熟悉的敦煌汉简,居延汉简,以及武威汉简。
而这些对于汉代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为汉简文化研究打下了基础。
关键字:甘肃简牍汉简书法汉代筒牍是研究我国汉代历史最珍贵的资料。
同时也是研究两汉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
甘肃敦煌地区的汉代遗址中先后出土了约17480多枚汉代简牍,在我国已发现的汉代简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敦煌汉简的出土,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从中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
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开启了后世的楷、行、草书。
文字到了汉代,即由篆到隶这个阶段,在文字发展史上是一次革命,一次巨大的进化,在书法史上更是如此,它对后来书法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郭沫若说:“本来中国的文字,在殷代使便具有艺术风味。
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有好些作品都异常美观。
留下这些字迹的人,毫无疑问,都是当时的书法家,虽然他们的姓名没有流传下来。
但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是春秋时代末期开始的。
汉代画像石的审美研究以陕北、晋西北地区为中心一、本文概述Overview of this article汉代画像石,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遗产,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历史内涵,成为了学术界和艺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
本文旨在以陕北、晋西北地区为中心,对汉代画像石的审美特征进行深入的研究。
通过梳理和分析这一地区画像石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制作工艺以及文化内涵,揭示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
Han Dynasty portrait stones, as an important heritage of ancient Chinese art, have become a hot topic of continuous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and artistic circles due to their unique artistic style and profound historical connotations. This article aims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Han Dynasty portrait stones, centered around the northern Shaanxi and northwestern Shanxi regions. By sorting and analyzing the subject matter, artistic style, production technique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portrait stones in this region, we aim to reveal their uniqueaesthetic value and social significance.陕北、晋西北地区作为汉代画像石的重要分布区,其画像石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审美视域下的甘谷汉简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7-0020-01
《管子》中说:“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宝”。
两汉时代的简牍,就是巍巍华夏这“万世之国”所留给我们的“万世之宝”。
号称是中国“四大汉简”之一的甘谷汉简就是有着2700年建县史的古城甘谷十分珍贵的文物遗存。
甘谷汉简自1971年12月甘谷县新兴镇刘家屲的一座汉墓中以来,就引起了考古界以至书法艺术节的极大重视,从历史的、艺术的多个角度对甘谷汉简的研究从未中断。
但就甘谷汉简的美学意义及其审美价值方面的研究稍显薄弱。
本文试就此对甘谷汉简的审美价值加以阐述。
甘谷汉简中的自然美。
清代著名的唯物论者叶燮认为:“凡物之美者,美本乎天者也,本乎天自有之美。
”甘谷汉简成简的年代正是东汉王朝行将灭亡的桓帝延熹元年,皇室业已衰落,战乱纷起,政令不通。
如简中所述:“列令小民怀怨,远愬纷纷连年”。
而在此背景下产生的甘谷汉简,简文内容是当时汉阳郡太守转发给所属县、乡的诏书、律令及敕命文书。
是作为皇室诏令的实用文本,也即甘谷汉简首先是实用性的,其审美价值是自然形成的。
就简文书法而言,只是当时通用的规范书体隶书而已,书写者完全没有如今天的所谓“书法艺术创作”的意识,更没有什么书法艺术的功利性目的。
因此,抛开其历史背景,简书是在极其自然纯粹的状态下完
成的,这是符合事物的使用价值先于审美价值的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的。
现存的23枚甘谷汉简正文中尚可辨识的569字中,完全看不到雕琢做作的痕迹,字字精彩绝伦,整体飘逸,挥洒自如。
不仅如此,甘谷汉简也反映了中国书法艺术与世事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出汉代书法趋向成熟的风格状态。
甘谷汉简中的含蓄美。
中国的传统艺术,包括文学、书法、绘画、雕刻、建筑无不讲究含蓄美,甘谷汉简也不列外。
中国美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几千年封建体制下的闭关自守形成了独特的闭合体系。
从先秦时老庄的“大音希声”到刘勰的“秘响旁通,伏彩潜发”,都表现了含蓄美的观点。
甘谷汉简书法的特征也在于此,笔画以圆带方,以静饰动,结体由竖展横,内密而外舒,波磔敛中有放,收放有度,即可看到篆书的意蕴,又略带夸张地显现出汉隶的总体风格。
第九简中“从民家贷钱”数余字,几乎都在末笔笔画在竖弯处,就势铺毫,展出一个很长的捺画,用笔大胆而夸张,但如细心玩味,又会感受到“纡余委曲,若不可测”(《世说新语》)的含蓄与深邃。
这些就在整体上构成了甘谷汉简“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米芾语)的风格特色。
甘谷汉简中的气韵美。
中国传统艺术十分讲究气韵美,尤其是书法艺术中强调“韵、法、意”。
就是气韵韵在书法上的表现形态,具体说,就是书法的气、神、骨、肉等。
一般认为,气韵美是以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魏晋书法的风格特征,即所谓“晋人取韵”。
但若观甘谷汉简的气韵,真可见“象人之美,张得其肉,
陆得其骨,顾得其神。
”的美感。
虽然甘谷汉简在出土时的破损率超过了50%,但我们认可从所存的简牍中看出其整体的流畅与贯通,可见甘谷汉简是在实用目的的前提下一气呵成的。
这些都可在保存较为完整的第一、九、十五、二十二、二十三等诸简中得到体味。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气韵美并非晋唐书法的专属,甘谷汉简表明,气韵美在西汉就得到了重视并有所表现。
总之,甘谷汉简在自然美的前提下所展现的审美价值是极高的,对其审美价值的探讨与挖掘也是十分有现实意义的。
因为,“一件艺术品——任何其他产品也是如此——创造了一个了解艺术而且
能够欣赏美的公众。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204页)甘谷汉简所蕴含的审美意义,对于我们的启迪、教育和振奋是客观实在的,它不仅能够满足我们的审美需求,而且可以激发我们“在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具有积极的创造美的意向。
”(巴斯图赫夫《审美教育的任务》)就此而言,我们在文物考古的相关研究中,是不能舍弃审美意义而使之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