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汪曾祺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
- 格式:doc
- 大小:45.50 KB
- 文档页数: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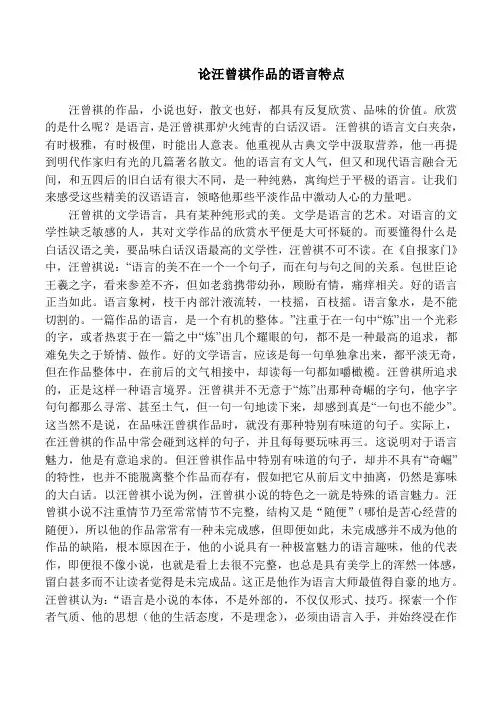
论汪曾祺作品的语言特点汪曾祺的作品,小说也好,散文也好,都具有反复欣赏、品味的价值。
欣赏的是什么呢?是语言,是汪曾祺那炉火纯青的白话汉语。
汪曾祺的语言文白夹杂,有时极雅,有时极俚,时能出人意表。
他重视从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他一再提到明代作家归有光的几篇著名散文。
他的语言有文人气,但又和现代语言融合无间,和五四后的旧白话有很大不同,是一种纯熟,寓绚烂于平极的语言。
让我们来感受这些精美的汉语语言,领略他那些平淡作品中激动人心的力量吧。
汪曾祺的文学语言,具有某种纯形式的美。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对语言的文学性缺乏敏感的人,其对文学作品的欣赏水平便是大可怀疑的。
而要懂得什么是白话汉语之美,要品味白话汉语最高的文学性,汪曾祺不可不读。
在《自报家门》中,汪曾祺说:“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
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
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语言象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
语言象水,是不能切割的。
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注重于在一句中“炼”出一个光彩的字,或者热衷于在一篇之中“炼”出几个耀眼的句,都不是一种最高的追求,都难免失之于矫情、做作。
好的文学语言,应该是每一句单独拿出来,都平淡无奇,但在作品整体中,在前后的文气相接中,却读每一句都如嚼橄榄。
汪曾祺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语言境界。
汪曾祺并不无意于“炼”出那种奇崛的字句,他字字句句都那么寻常、甚至土气,但一句一句地读下来,却感到真是“一句也不能少”。
这当然不是说,在品味汪曾祺作品时,就没有那种特别有味道的句子。
实际上,在汪曾祺的作品中常会碰到这样的句子,并且每每要玩味再三。
这说明对于语言魅力,他是有意追求的。
但汪曾祺作品中特别有味道的句子,却并不具有“奇崛”的特性,也并不能脱离整个作品而存有,假如把它从前后文中抽离,仍然是寡味的大白话。
以汪曾祺小说为例,汪曾祺小说的特色之一就是特殊的语言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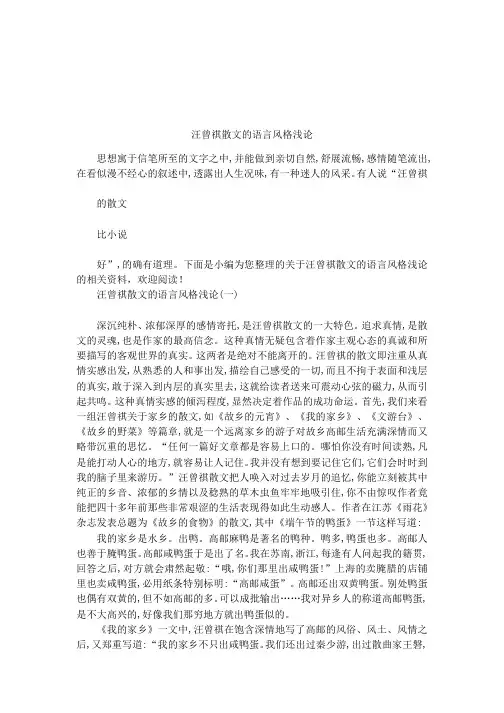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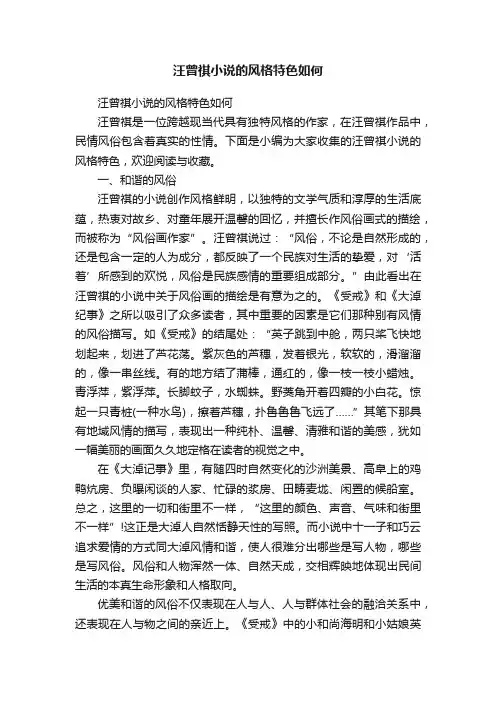
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如何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如何汪曾祺是一位跨越现当代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在汪曾祺作品中,民情风俗包含着真实的性情。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欢迎阅读与收藏。
一、和谐的风俗汪曾祺的小说创作风格鲜明,以独特的文学气质和淳厚的生活底蕴,热衷对故乡、对童年展开温馨的回忆,并擅长作风俗画式的描绘,而被称为“风俗画作家”。
汪曾祺说过:“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看出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关于风俗画的描绘是有意为之的。
《受戒》和《大淖纪事》之所以吸引了众多读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们那种别有风情的风俗描写。
如《受戒》的结尾处:“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其笔下那具有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出一种纯朴、温馨、清雅和谐的美感,犹如一幅美丽的画面久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
在《大淖记事》里,有随四时自然变化的沙洲美景、高阜上的鸡鸭炕房、负曝闲谈的人家、忙碌的浆房、田畴麦垅、闲置的候船室。
总之,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正是大淖人自然恬静天性的写照。
而小说中十一子和巧云追求爱情的方式同大淖风情和谐,使人很难分出哪些是写人物,哪些是写风俗。
风俗和人物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交相辉映地体现出民间生活的本真生命形象和人格取向。
优美和谐的风俗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群体社会的融洽关系中,还表现在人与物之间的亲近上。
《受戒》中的小和尚海明和小姑娘英子爱听青蛙打鼓、寒蛇唱歌,看荧火虫飞动。
《天鹅之死》中的白蕤对美丽的天鹅情有独钟。
《昙花?鹤和鬼火》中的李小龙爱那雪白的昙花、美丽的野鹤和绿色的鬼火。

《胡同文化》的语言风格浅析汪曾祺是一位非常讲究语言艺术的作家。
他主张文学作品的语言不只是载体,也是本体。
因而不论是小说创作还是散文写作,汪曾祺都极力追求实现语言本身的魅力。
在当代文坛上,他的作品也是以语言有特色著称的——“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开了每个字都是平平常常的话,放在一起就有味道了”,这是评论家说的;“我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这是他自己说的。
总之用“淡而有味”四个字,大致可以说明汪曾祺作品的语言风格。
语文阅读教学中,语言风格的品味总是最难的一部分,而“淡而有味”又是难中之难的部分。
那么如何在教学中让学生真切感受到汪曾祺“看似寻常最奇崛”的语言魅力呢,本文试以教材中的《胡同文化》为例,略作分析,与大家探讨。
一、平中见奇的叙述《胡同文化》开篇,似乎只是平平实实地将作者观察到胡同的诸多特性一一道来,如取向的方正,得名的来源广,数量的多,环境的静……语言平淡到了极点,就连用比喻,也是“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家常的不能再家常了!说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也似乎是老老实实地一一列举而已,然而且慢,这段果真只是简单平实的列举叙述吗?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
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
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
大雅寶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
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
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
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
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
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状的。
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
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
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
我们再细读这段,发现作者表明胡同取名来源时,一般是以两条胡同名为例,如“计数的”“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可是到了“有名的人物”时,却一口气列出了五条胡同名,这难道不是一种“奇”处吗?教学中我把“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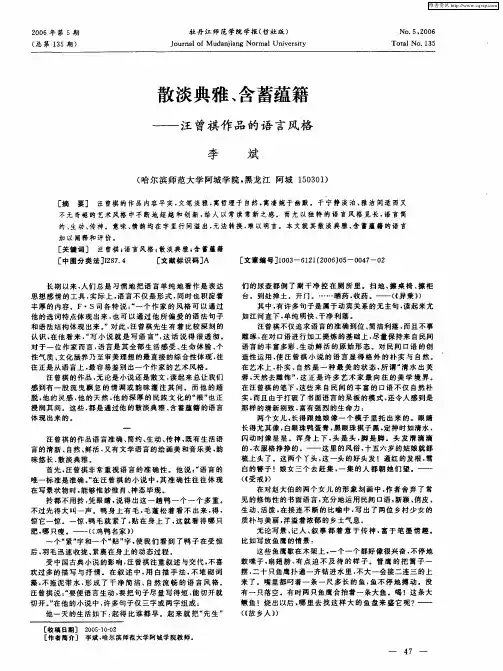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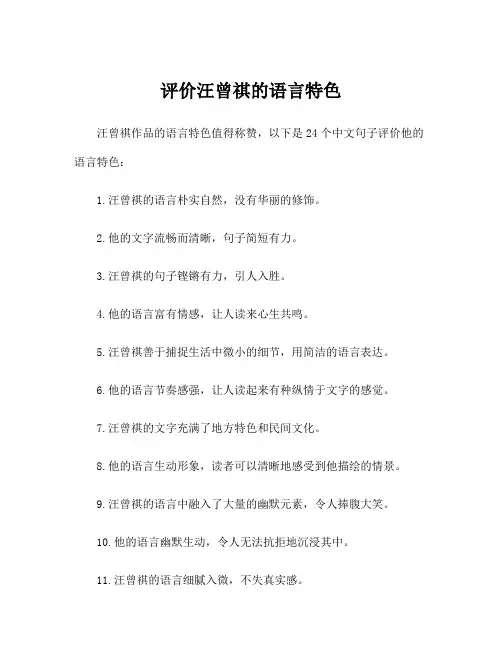
评价汪曾祺的语言特色
汪曾祺作品的语言特色值得称赞,以下是24个中文句子评价他的语言特色:
1.汪曾祺的语言朴实自然,没有华丽的修饰。
2.他的文字流畅而清晰,句子简短有力。
3.汪曾祺的句子铿锵有力,引人入胜。
4.他的语言富有情感,让人读来心生共鸣。
5.汪曾祺善于捕捉生活中微小的细节,用简洁的语言表达。
6.他的语言节奏感强,让人读起来有种纵情于文字的感觉。
7.汪曾祺的文字充满了地方特色和民间文化。
8.他的语言生动形象,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描绘的情景。
9.汪曾祺的语言中融入了大量的幽默元素,令人捧腹大笑。
10.他的语言幽默生动,令人无法抗拒地沉浸其中。
11.汪曾祺的语言细腻入微,不失真实感。
12.他的文字充满了对人性的洞察和思考。
13.汪曾祺的句子简洁有力,富有修辞手法。
14.他的语言节奏感强,让人读来有一种流畅感。
15.汪曾祺的语言中融入了丰富的地域特色,增添了鲜明的色彩。
16.他的文字中透露出智慧和阅历的痕迹。
17.汪曾祺的语言中隐约带有一种乡愁,令人怀念故乡。
18.他的描写独特而鲜活,让人有如身临其境之感。
19.汪曾祺的语言富有感染力,读者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故事。
20.他的句子简短有力,能够迅速抓住读者的注意力。
21.汪曾祺的语言真实而质朴,给人一种亲切感。
22.他的描写细腻入微,让读者能够深入感受到情感的细节。
23.汪曾祺的语言富有生活情趣,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24.他的句子流畅清晰,让读者能够轻松理解和消化其中的意义。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观和他在小说文体创造上的自觉意识。
(1)在汪曾祺重新开始创作的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学流派和文学潮流不断兴起,又不断更替的时代,许多作家都被卷入了各种潮流之中,而汪曾祺则为少数几位只按照自己的文学理想写作的“潮流之外”的作家。
汪曾祺与当代大多数小说作家不同,他从不涉足长篇小说,从来也没想过要写一部“史诗性”的或“全景式”的长篇作品。
他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中说:“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
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
”(2)虽然我们还不能说汪曾祺主观上想创造出一种新的小说文体,但是,他在“小说散文化”方面的努力却是自觉的。
正如他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中所说:“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
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
”汪曾祺的小说虽然也涉及他曾生活过的昆明、上海和北京等城市,但大多取材于他的童年和家乡的生活,既不特别设计情节,也不有意制造矛盾和冲突,而是专注于风俗民情的表现,而这些风俗民情也不是推动故事发展和人物性格变化的主要因素。
因此,他的小说不但没有较强的故事性,而且故意在要与“戏剧化小说”背道而驰,使小说呈现出如日常生活一般的自然形态,在“散文化”中创造一种生活的“诗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汪曾祺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
2.汪曾祺在废名、沈从文,与阿城、贾平凹之间承前启后的作用。
(1)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受到废名和沈从文的较大影响。
废名作品的特别之处,是田园牧歌的情调加上古典式的意境的营造,致力于乡村的风土人情,特别是乡村的儿女情态,他所写的是“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也就是说,他不但是把小说当作散文来写,而且还要把散文化的小说写成抒情诗。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则较多地受到废名的影响,一方面以“乡下人”的眼光看城市,对现代文明进行无情的讽刺和批判,另一方面,则立志要成为湘西生活的叙述者和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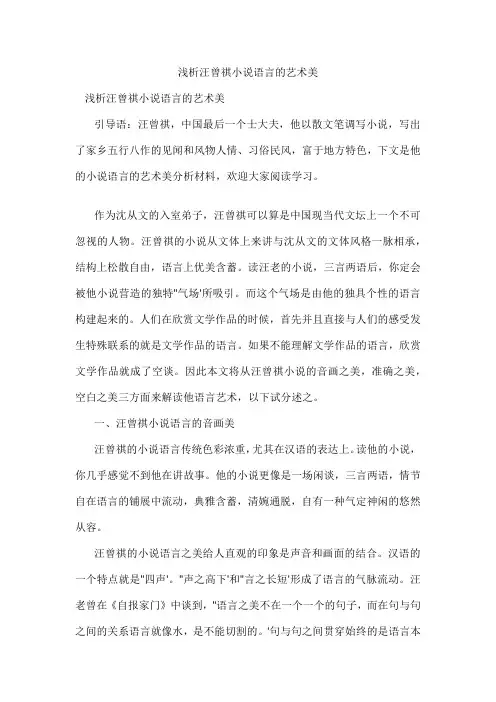
浅析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艺术美浅析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艺术美引导语:汪曾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下文是他的小说语言的艺术美分析材料,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作为沈从文的入室弟子,汪曾祺可以算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上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汪曾祺的小说从文体上来讲与沈从文的文体风格一脉相承,结构上松散自由,语言上优美含蓄。
读汪老的小说,三言两语后,你定会被他小说营造的独特"气场'所吸引。
而这个气场是由他的独具个性的语言构建起来的。
人们在欣赏文学作品的时候,首先并且直接与人们的感受发生特殊联系的就是文学作品的语言。
如果不能理解文学作品的语言,欣赏文学作品就成了空谈。
因此本文将从汪曾祺小说的音画之美,准确之美,空白之美三方面来解读他语言艺术,以下试分述之。
一、汪曾祺小说语言的音画美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传统色彩浓重,尤其在汉语的表达上。
读他的小说,你几乎感觉不到他在讲故事。
他的小说更像是一场闲谈,三言两语,情节自在语言的铺展中流动,典雅含蓄,清婉通脱,自有一种气定神闲的悠然从容。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之美给人直观的印象是声音和画面的结合。
汉语的一个特点就是"四声'。
"声之高下'和"言之长短'形成了语言的气脉流动。
汪老曾在《自报家门》中谈到,"语言之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语言就像水,是不能切割的。
'句与句之间贯穿始终的是语言本身所蕴含的气脉,它会跟随句子的衔接和扩展得以流动。
具体来讲,"言之长短'是指长短句的搭配,汪曾祺在小说语言中常常用到。
例如在《大淖记事》中,介绍大淖南岸的繁荣景象,几乎全用的长短句搭配:"小轮船漆得花花绿绿的,飘着万国旗,机器突突地响,眼瞳冒着黑烟,装帧,卸货,上客,下客,也有卖牛肉的,高粱酒,花生瓜子,芝麻灌糖的小贩幺幺喝喝,是热闹过一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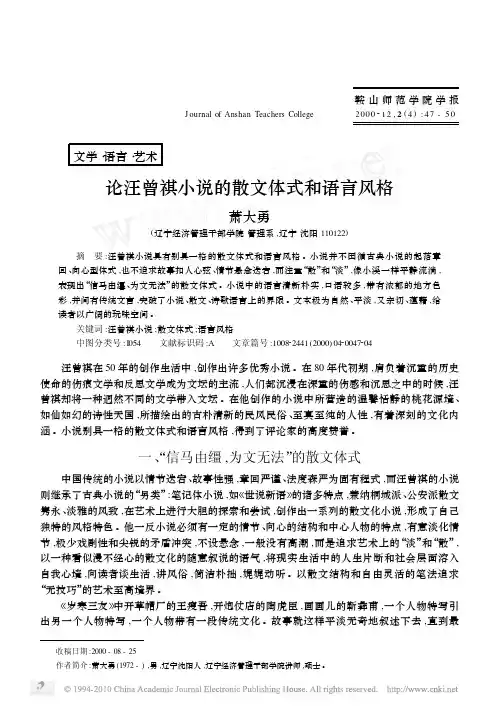
鞍山师范学院学报J ournal of Anshan Teachers College2000212,2(4):47-50文学·语言·艺术论汪曾祺小说的散文体式和语言风格萧大勇(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管理系,辽宁沈阳110122)摘 要:汪曾祺小说具有别具一格的散文体式和语言风格。
小说并不因循古典小说的起落章回、向心型体式,也不追求故事扣人心弦、情节悬念迭宕,而注重“散”和“淡”,像小溪一样平静流淌,表现出“信马由缰、为文无法”的散文体式。
小说中的语言清新朴实,口语较多,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并间有传统文言,突破了小说、散文、诗歌语言上的界限。
文本极为自然、平淡,又亲切、蕴藉,给读者以广阔的玩味空间。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体式;语言风格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篇号:100822441(2000)0420047204汪曾祺在50年的创作生活中,创作出许多优秀小说。
在80年代初期,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成为文坛的主流,人们都沉浸在深重的伤感和沉思之中的时候,汪曾祺却将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学带入文坛。
在他创作的小说中所营造的温馨恬静的桃花源境、如仙如幻的诗性天国,所描绘出的古朴清新的民风民俗、至真至纯的人性,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小说别具一格的散文体式和语言风格,得到了评论家的高度赞誉。
“信马由缰,为文无法”的散文体式一、中国传统的小说以情节迭宕、故事性强,章回严谨、法度森严为固有程式,而汪曾祺的小说则继承了古典小说的“另类”:笔记体小说,如《世说新语》的诸多特点,兼纳桐城派、公安派散文隽永、淡雅的风致,在艺术上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创作出一系列的散文化小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特色。
他一反小说必须有一定的情节、向心的结构和中心人物的特点,有意淡化情节,极少戏剧性和尖锐的矛盾冲突,不设悬念,一般没有高潮,而是追求艺术上的“淡”和“散”,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散文化的随意叙说的语气,将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片断和社会层面溶入自我心境,向读者谈生活,讲风俗,简洁朴拙,娓娓动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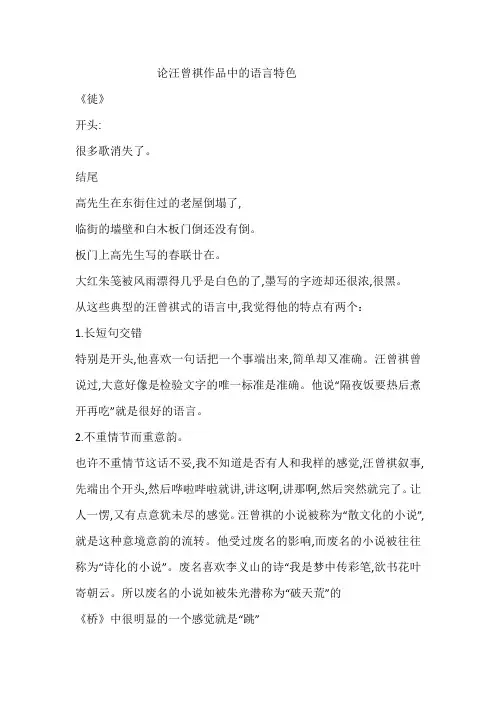
论汪曾祺作品中的语言特色《徙》开头:很多歌消失了。
结尾高先生在东街住过的老屋倒塌了,临街的墙壁和白木板门倒还没有倒。
板门上高先生写的春联廿在。
大红朱笺被风雨漂得几乎是白色的了,墨写的字迹却还很浓,很黑。
从这些典型的汪曾祺式的语言中,我觉得他的特点有两个:1.长短句交错特别是开头,他喜欢一句话把一个事端出来,简单却又准确。
汪曾祺曾说过,大意好像是检验文字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他说“隔夜饭要热后煮开再吃”就是很好的语言。
2.不重情节而重意韵。
也许不重情节这话不妥,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和我样的感觉,汪曾祺叙事,先端出个开头,然后哗啦哔啦就讲,讲这啊,讲那啊,然后突然就完了。
让人一愣,又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汪曾祺的小说被称为“散文化的小说”,就是这种意境意韵的流转。
他受过废名的影响,而废名的小说被往往称为“诗化的小说”。
废名喜欢李义山的诗“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
所以废名的小说如被朱光潜称为“破天荒”的《桥》中很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跳”在这里列举她们望着小林哩,还低声的讲些什么。
小林看牛,好一匹黄牛,它的背上集着一只八哥儿。
翻着翅膀跳。
但他不敢下去,截然的一转身,“回去”。
回头走不过十步呀!抬起头来稀罕一声了再有,树上的花不形得少了,依然黄的,白的,绿叶之中,古干之周,小林的手上却多得不可奈何,沿着颈圈儿挂。
忽然他动也不动的坐住——一树脚下是那放牛的小姑娘。
暂时间两双黑眼睛猫一般的相对。
下得树来,理出一串花,伸到小姑娘面前“给你“琴儿,谢谢。
”而汪曾祺的行文也带上一点这种“跳”的感觉。
如《八千岁》,写一个有钱的吝啬鬼一般的米店老板,在被人强取豪夺一笔钱后,气愤地把桌子一拍是晚茶的时候,儿子又给他拿了两个草炉烧饿八千岁把烧饼往帐桌上一拍,大声说“给我去叫一碗三鲜面!”这里一种跳动感摄人魂魄,但细细思量又不知是何意韵再如《卖眼镜的宝应人》中宝应人信誓旦旦:”是真是假,一试便知。
玉不怕火,”化学“的见火就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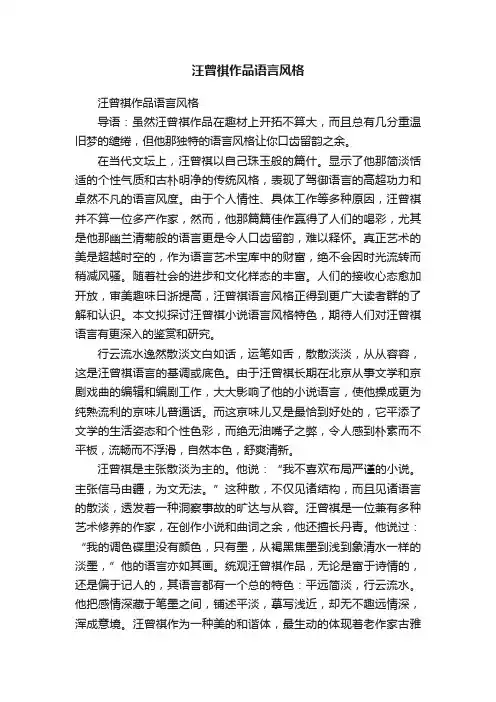
汪曾祺作品语言风格汪曾祺作品语言风格导语:虽然汪曾祺作品在趣材上开拓不算大,而且总有几分重温旧梦的缱绻,但他那独特的语言风格让你口齿留韵之余。
在当代文坛上,汪曾祺以自己珠玉般的篇什。
显示了他那简淡恬适的个性气质和古朴明净的传统风格,表现了驾御语言的高超功力和卓然不凡的语言风度。
由于个人情性、具体工作等多种原因,汪曾祺并不算一位多产作家,然而,他那篇篇佳作赢得了人们的喝彩,尤其是他那幽兰清菊般的语言更是令人口齿留韵,难以释怀。
真正艺术的美是超越时空的,作为语言艺术宝库中的财富,绝不会因时光流转而稍减风骚。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样态的丰富。
人们的接收心态愈加开放,审美趣味日浙提高,汪曾祺语言风格正得到更广大读者群的了解和认识。
本文拟探讨汪曾祺小说语言风格特色,期待人们对汪曾祺语言有更深入的鉴赏和研究。
行云流水逸然散淡文白如话,运笔如舌,散散淡淡,从从容容,这是汪曾祺语言的基调或底色。
由于汪曾祺长期在北京从事文学和京剧戏曲的编辑和编剧工作,大大影响了他的小说语言,使他操成更为纯熟流利的京味儿普通话。
而这京味儿又是最恰到好处的,它平添了文学的生活姿态和个性色彩,而绝无油嘴子之弊,令人感到朴素而不平板,流畅而不浮滑,自然本色,舒爽清新。
汪曾祺是主张散淡为主的。
他说:“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
主张信马由疆,为文无法。
”这种散,不仅见诸结构,而且见诸语言的散淡,透发着一种洞察事故的旷达与从容。
汪曾祺是一位兼有多种艺术修养的作家,在创作小说和曲词之余,他还擅长丹青。
他说过:“我的调色碟里没有颜色,只有墨,从褐黑焦墨到浅到象清水一样的淡墨,”他的语言亦如其画。
统观汪曾祺作品,无论是富于诗情的,还是偏于记人的,其语言都有一个总的特色:平远简淡,行云流水。
他把感情深藏于笔墨之间,铺述平淡,摹写浅近,却无不趣远情深,浑成意境。
汪曾祺作为一种美的和谐体,最生动的体现着老作家古雅超俗的美学趣味,鲜明地映照着他那淡泊闲和的艺术人格和胸襟气象。
大淖记事阅读理解
《大淖记事》是汪曾祺的一篇著名小说,主要讲述了在苏北里下河地区一个叫大淖的小镇上,几个普通小人物的故事。
这些人物包括挑夫、锡匠、船娘、小贩等,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却拥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哲学和人生智慧。
在阅读这篇小说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1.人物形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
他们虽然生活
在艰苦的环境中,但并没有被苦难压垮,而是用自己的方式顽
强地生活下去。
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绘,作者展示了人性的多
样性和复杂性。
2.语言风格:汪曾祺的语言风格朴实自然,充满了地方色彩和乡
土气息。
他通过对大淖地区的风土人情、方言俚语的生动描绘,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之中。
3.主题思想:小说的主题思想深刻而多元。
一方面,它通过对底
层人物生活的描写,揭示了社会的残酷和不公;另一方面,它
也展现了人性的善良和坚韧,以及人们在面对困境时所展现出
的智慧和勇气。
此外,小说还通过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
系的探讨,表达了作者对于人性和生活的深刻思考。
在阅读理解中,读者可以通过对小说中人物形象、语言风格和主题思想的深入分析,来把握作品的整体意义和价值。
同时,也可以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对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进行联想和想象,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所传达的思想和情感。
汪曾祺作品的语⾔风格1.流畅⾃然的语⾔阅读汪曾祺的⼩说,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作品的特点,那就是语⾔的朴素⾃然。
李振鹏曾说过:“汪曾祺的⼩说创作,极⼤部分是以他的故乡江苏⾼邮地区三四⼗年代乡镇⽣活为素材的。
时代的久远,地域的局限,本来会使⼈有点隔膜感,然⽽读过他作品的⼈,⽆论南北,⽆论⽼幼,却都有⼀种既陌⽣新奇⼜熟悉亲切地现实感。
”[1]他认为汪曾祺的作品之所以会让⼈有这种熟悉亲切地现实感,是因为汪曾祺创作的语⾔是平淡朴素⽽⼜⾃然的,⼈们能够轻易读懂他的⼩说⽽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汪曾祺认为语⾔是具有流动性的,他的作品语⾔具有显著的⽔性特征,他既注重单个句⼦上的锤炼,也注重句与句之间或段与段之间的关系。
⽤⼀句话来总结汪曾祺锤炼作品语⾔的经验,那就是⽂⽓在句、段之间的贯通,这些丰富的经验在他作品中有着很好的体现。
阅读汪曾祺的作品,尤其是他的短篇⼩说,读者⼏乎感觉不到⼩说的语⾔运⽤了夸张、双关等具有技巧的修辞⼿法,就连作家们最常运⽤的⽐喻⼿法,在汪曾祺的作品中也极少被使⽤,这样不加修饰的语⾔让他的作品如同清⽔芙蓉⼀般去掉了所有的繁杂和浮夸,只留下⽔⼀般的纯净明快、⾃然流畅,如果细细品读,就会让⼈感到余味绵长。
如果说语⾔是⽓质的外化,那么汪曾祺的作品语⾔就好⽐被⽔磨练洗刷过的⽯⼦,⼲净圆润同时⼜赏⼼悦⽬。
汪曾祺在六⼗多岁时创作了《⼤淖记事》、《受戒》等著作,在创作之前,他所经历过的漫长⼈⽣历程让他对社会和⽣活都有了独属于⾃⼰的深刻感受,⼈⽣路上的坎坷不平让他参透了⼈⽣,从⽽拥有了平淡的品性,这样的品性渗透到他的作品中,就内化成了作品语⾔独特的⽔性特征,这种⽔性的特征让他的作品语⾔在拥有如⽔⼀般流动⽓韵的同时,⼜拥有了清⽔芙蓉似的⼲净,还具备了如同落花流⽔般沉静的⽓质。
2.⾏云流⽔的散⽂化结构汪曾祺⾃⼰曾经说过,“严格意义上的⼩说有⼀点像⼭,⽽散⽂化的⼩说则像⽔。
”[2]他所创作的⼩说正有着⾏云流⽔般的散⽂化风格,呈现给读者的是散漫连贯⽽⼜舒缓的叙事特征。
汪曾祺的行文风格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语言的口语化。
口语化是汪曾祺小说中最大的特点。
汪曾祺早年曾师从沈从文。
朴实明净的语言风格是沈、汪二人共同的行文特点。
汪曾祺的文章大量使用其故乡高邮的方言,且十分贴近人物生活,其叙事角度也通常从人文方向出发,娓娓道来,随意而为。
例如在《受戒》中,汪曾祺如是描写道:“赵大伯是个能干人。
他是一个全把式,不但田里场上样样精通,还会罩鱼、洗磨、凿砻、修水车、修船、砌墙、烧砖、箍桶、劈篾、绞麻绳。
他不咳嗽,不腰疼,结结实实,像一棵榆树。
人很和气,一天不声不响”。
除了普通的方言,其作品中大多还穿插着民俗民谣的使用。
例如“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
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
毫无矫饰,直白易懂。
第二,淋漓尽致的诗意与乐感。
汪曾祺主张小说应该像诗、像散文、像戏剧。
他曾经说过“我要写,要写着自己玩,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诗意”。
他的作品从不拘泥于结构的束缚与行文的规则,洋洋洒洒,淋漓尽致,信马由缰,为文无法。
读者往往能从他看似平白无奇的文章中读出一种别样的姿态与韵律。
如《收字纸的老人》中,“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
化纸之后,关门独坐。
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
”文白夹杂,遣词妥帖,韵味悠长。
又如《晚饭花》中,“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
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
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
”简净优美,极具诗意。
第三,明净的赤子之心。
汪曾祺的作品其独特的审美与笔触,来源于他对生活的热爱与细腻的观察。
人性美,人物美,风俗美构成汪曾祺作品的美学主题。
诗化,美化,古韵绵长,温暖,热忱,恬淡清新,质朴自然。
在他的作品中,中国传统文学,民俗风景都充满灵性,活泼可爱,亦书亦画。
_(:з」∠)_小时候可喜欢看汪曾祺的作品,因为总是讲很多好吃的,馋得人口水直流(感觉暴露了吃货的本性),当时也觉得他的文风特别有趣,特别可爱,视角十分独特,和别的作家的文章相比十分有特色。
专科毕业报告论文题目:关于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姓名:毛仙付专业:应用中文专业年级:2012年秋层次:高起专学习中心曲靖培训学习中心完成时间:2014年9 月20 日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内容摘要】:汪曾祺的小说俭省、疏放、淡远,而又从中透出凝重、显现奇崛。
在其小说中,我们能够发现蕴藏在文中的真、善、美。
作者传承着祖国的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以极其虔诚的态度来表达其内心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性的赞美。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优美,不管是叙述事件还是描绘景物,是写对话还是描写人物,都显示出和谐、风俗的风格。
【关键词】:小说语言真实性文言文人性美和谐与风俗汪曾祺就像是一阵清风在新时期的文坛上刮过,让人眼前为之一亮。
许多人都喜欢汪曾祺,十分喜爱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
他的小说语言如同是铺在池底的鹅卵石一般,干净清爽,十分圆润。
一、语言的真实性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来源。
脱离生活的艺术其生命价值较低。
例如,贾平凹本来对农村生活,民间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写出了《商州初录》等优秀作品。
但后来他转入写城市生活,由于没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因此比较肤浅,文学价值不高,如《废都》,引起了广大读者的争议。
汪曾祺就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把握,很多小说里的人物、语言、环境可以在他的故乡、他熟悉的环境中能找到原型。
在《逝水<大淖记事>是怎么写出来》中,有这样的描述:“我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路过铁匠店,我走进去看老铁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虎头帽上的小罗汉。
路过画匠店,我歪着头看他们画‘家神菩萨’……”《大淖记事》里的大淖、铁匠、妇女、人物的习性,说话的腔调几乎都能从他的故乡中找到原型。
其语言来源于生活,朴质真实,体现在口语化和地方方言的使用。
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
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 不加过多的粉饰,信马由鞭。
汪曾祺小说语言特点分析摘要汪曾祺作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其作品注重对古典文化的描写,有很深的意境美,在文学史上,他的小说不可复制,独一无二,具有独特的地位。
丰富的民间体验为其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又因其曾经师从沈从文,因而他的小说带有一种散文的笔调,其中,精确、简练的形容词的使用塑造了其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
这篇文章以汪曾祺的小说为研究范围,了解概括汪曾祺小说语言的特点的使用,从词性、修辞、和短句对汪曾祺的语言进行研究,对其自然、清新、生动的文体风格的塑造进行探讨。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语言AbstractWang Zengqi as the last scholar in China, his works focus on the description of classical culture, there is a deep artistic beauty,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his novel can not be copied, unique, unique position. The rich folk experience provides a rich material for his novels, and because of his former division from Shen Congwen, his novel has a prose style, in which the use of precise and concise adjectives shapes its fresh and natural language style. This article takes Wang Zengqi's novel as the research scope,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ng Zengqi's novel language, and studies the language of Wang Zengqi from the part of speech, rhetoric and phrases, and explores the shaping of his natural, fresh and vivid style.Key words: Wang Zengqi; novel; language目录TOC \o "1-3" \h \u 摘要IAbstract II引言 1一、汪曾祺小说语法词汇的特点 1(一)、形容词 11、表示颜色的形容词的使用 22、叠词33、其他形容词 4(二)、动词51、汪曾祺动词的连用常用来表达人物的心理状态52、汪曾祺小说的动词连用常用来刻画人或物的行为特征 63、汪曾祺动词的连用有时常用来表现主人公的某种特殊的情感7(三)、数词8(四)、小结8二、汪曾祺小说中句子结构的特点9(一)、短句9(二)、短句的建筑美9(三)、小结10三、汪曾祺小说中修辞的特点10(一)、比喻10(二)、比拟111、拟物112、拟人11(三)、小结12四、汪曾祺小说语言研究的目的及意义12参考文献13附录14致谢15引言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之后,汪曾祺因师从沈从文常常被认为文风与沈从文相似,但沈从文却说“他比我写的好。
浅析汪曾祺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论文关键词:汪曾祺作品语言风格论文摘要:汪曾祺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具有独特地位的作家,也是一位深受读者欢迎的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
汪曾祺的作品充分汲取了古典文学的营养,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形成了其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学语言。
本文以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为研究对象,拟探讨汪曾祺小说语言风格特色, 对于进一步理解汪曾祺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帮助,也期待人们对汪曾祺语言有更深入的鉴赏和研究。
在当代文坛上,汪曾祺以自己珠玉般的篇什,显示了他那简淡恬适的个性气质和古朴明净的传统风格,表现了驾御语言的高超功力和卓然不凡的语言风度。
由于种种原因,汪曾祺并不算一位多产作家,然而,他那篇篇佳作赢得了人们的喝彩,尤其是他那幽兰清菊般的语言更是令人口齿留韵,难以释怀。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且由于汪曾祺长期在北京从事文学和京剧戏曲的编辑和编剧工作,大大影响了他的小说语言,使他操成更为纯熟流利的京味儿普通话。
而这京味儿又是最恰到好处的,它平添了文学的生活姿态和个性色彩,而绝无油嘴子之弊,令人感到朴素而不平板,流畅而不浮滑,自然本色,舒爽清新。
这种语言的功底和魅力显然得益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完美化合。
汪曾祺将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独创了一种新文体。
一、口语化的语言汪曾祺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一文中曾经写道: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
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
这种文化的积淀自古就有之,从《诗经》到《楚辞》,从唐诗宋词到明清小说,经过了几千年的积淀和蕴蓄,就形成了一种“书面文化”。
这种文化可以增添文章的底蕴与深奥,让文章显得悠长而具有深味。
与这种“书面文化”相对的则是一种“口头文化”,它是一种民间文化,可以是方言,也可以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话。
它集中就表现在通俗易懂,平易近人,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很接近。
他自己也说:我对民间文学是有感情的,民间文学丰富的想象和农民式的幽默,民歌比喻的新鲜和韵律的技巧使我惊奇不置。
而当这种“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一结合,就变得雅俗共赏,俗中见雅,既符合知识分子的阅读要求,也给平民带来了阅读的方便。
下面就分析汪曾祺作品中口语的运用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红油冒出来,本来只能观其形,用上“吱——”仿佛能闻其声,这一声“吱——”让食咸鸭蛋的过程变得有声有色,有情有趣。
“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干脆利落的一个“有”,石破惊天的一个“!”,“以稚童的语气呼之欲出,真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王安忆语)。
从上面的两个例子便可体会到,正如王安忆说过的“汪曾祺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
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确实如此。
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
”汪曾祺小说散文的语言特色重要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
举个例子,“我家后园有一棵紫薇。
这棵紫薇有年头了,主干有茶杯口粗,高过屋檐。
一到放暑假,它开起花来,真是‘紫得’不得了,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
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
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
真是乱。
乱红成阵,乱成一团。
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囔囔。
”又如他的《虎头鲨、昂嗤鱼、阵鳌、螺蛳、蚬子》这篇专讲吃的散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苏州人特重塘鳢鱼。
上海人也是,一提起塘鳢鱼,眉飞色舞。
塘鳢鱼是什么鱼?我向往之久矣。
到苏州,曾想尝尝塘鳢鱼未能如愿,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瞎!”一声“瞎”韵味无穷,意境高远。
自五四以来,尝试把口语溶入写作的人当然绝不只是汪曾祺一个,但汪曾祺可说是最为成功。
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很天真,很古老很愚钝地讲一个闲来无事的故事,从头说起地,‘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地开了头。
比如‘西南联大有个文嫂’(《鸡毛》);比如‘北门有一条承志河’(《故里杂记》);比如‘全县第一个大画家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鉴赏家》)然后顺着开头徐徐往下说,从不虚晃一枪,弄的扑朔迷离。
他很负责地说完一件事,在由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来”(3)我认为王安忆对汪曾祺的小说的叙述和语言的特征,描写得相当准确。
读汪曾祺的小说确乎如此,什么都平平淡淡,但读完之后,你却不能平静,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隐隐地激动。
李陀曾在《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花城》,1998,5)一文中,对现代汉语形成的历史作了一番回顾,他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最大弊病就在于书面语言的贵族化倾向,产生的是一种“文绉绉的脱离日常生活口语甚远的书面语言。
”“若是白话文写作不想陷入某种‘贵族主义’,那就必须向活生生的‘群众’使用的口语打开大门。
”汪曾祺的白话文带给人一种“解放感”,就来自以鲜活的口语来改造白话文之“文”,“一方面使书面语的现代汉语有了一个新面貌,另一方面使汉语的种种特质有机会尽量摆脱欧化语法的约束。
”观汪曾祺的口语化,却多了一些他自身独有的优势:他对古今中外文化语言资源兼容并蓄的态度,他的打破了地域界限的口语化,他对民间口语资源的重视等。
同时,汪曾祺小说散文中大量采用了地道的方言,文章读来琅琅上口,倍感亲切。
汪曾祺对吴语非常稔熟,颇知其传神妙处。
他在小说《星期天》、散文《安乐居》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上海方言。
如“操那起来”、“斜其盎赛”等,既有地方色彩,又写活了人物,吴地读者赏来自有动人情趣。
在上海,卖糖炒热白果的小贩在街头吆喝道:“阿要吃糖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那句中的“糯”字,使汪曾祺竟“嚼”出细腻柔软而有弹性的韵味来,他在形容女作家铁凝的小说《孕妇和牛》的语言风格时,便油然想起吴语里的这个字:糯。
他怕这位北方作家不能体会这种语感,就说:“什么时候我们到上海去,我买一把烤白果让你尝尝。
”再如《岁寒三友》中一段“早!早!吃过了?偏过了,偏过了!”极富情趣。
运用方言实际是用了老百姓自己的语言贴近生活,象这样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中是唾手可得的。
有人说他的语言看起来很普通,但是一连串起来就很有意味。
这就是对俗中见雅的最好阐释。
二、个性化的语言除了口语的应用外,汪曾祺的文章也很有性格。
一是文章中破折号的运用很多。
这可能是任何作家都经常使用的语言符号,但是汪曾祺的使用数量是值得关注的。
“金岳霖先生”一文中破折号的运用有7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一文中有6处,“名优逸事”一文中有8处,“铁凝印象”一文中有11处……诸如此类的破折号的运用还有很多,而在他的文章中,这些破折号大多是表示解释说明,还有则是两人对话之间的区分。
二是汪曾祺的文章中除了用破折号解释说明,还大量的使用括号来解释说明前边的内容,而且使用的非常频繁。
“沈从文转业之谜”中有12处,“我的家”一文中有14处,“我的家乡”一文中有13处……他很善于用会追括号的方式进行追加式的解释说明或增添内容,这些括号中的内容有的是单纯的解释说明,有的是幽默诙谐的语言——“我的家乡”一文中写到“终于,我记得是七月十三(可能记错),倒了口子。
”三是文章中多用“俏皮”的词语,这与汪曾祺的幽默是分不开的。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一文中写沈从文来到北平“经常为弄不到一点东西‘消化消化’而发愁。
”文中写“沈先生很好客,朋友很多。
老一辈的有林宰平、徐志摩。
沈先生提及他们时充满感情。
没有他们的提携,沈先生也许就会当了警察,或者在马路旁边‘瘪了’。
”这里的“瘪了”一词不仅读起来惹人发笑,而且它确实准确地说明了沈从文当时的境况;“铁凝印象”中汪曾祺接受了写写铁凝的任务,但快到交卷时才发现自己并不了解铁凝时写到“文章发排在即,只好匆匆忙忙把一枚没有结熟的‘生疙瘩’送到读者面前——张家口一大把不熟的瓜果叫做‘生疙瘩’。
”这些语言不仅给他的文章增添了很多生机和趣味,而且这些“俏皮”的词语就像人们听自己的家乡话一样,很容易理解。
四是文章中多引经据典,而且文末多有一句慨叹之句。
从汪曾祺引经据典的数量可以看出,他的确是受到了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是为知识渊博的学者,更是一位治学严谨的人,每写到一个地方,总是尽量用典故来进行阐释。
而且,他喜欢在文章的结尾感慨一下,这些慨叹之句或是引文,或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表达。
如:“谭富英佚事”的结尾则是:赞曰:生老病死,全无所谓。
抱恨终生,无端“劝退”。
三、韵律化的语言汪曾祺的小说就像一段优美而简短的乐章。
时而急促,时而舒缓。
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小说的体裁上(短小而精悍),更多的则表现在小说的句式上。
小说大多采用短句,偶尔夹杂一些长句,长句的娓娓道来和短句的戛然而止结合,一收一放,使语言富有极佳的节奏感和层次感。
例如在《受戒》的开头部分这样描写道: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他是十三岁来的。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
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
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
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
庵,是因为有一个庵。
庵叫苦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
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
“宝刹何处?”——“荸荠庵。
”庵本来是住尼姑的。
“和尚庙”、“尼姑庵”嘛。
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
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
且不说刚开始以两个短句为段,第三段在描述庵赵庄的时候,语言就极富艺术性。
看起来像大白话,实则是暗藏的长短句。
开头提到庵赵庄,然后分别解释这三个字,以介绍名字的来历。
一短一长,起承转合之间安排的非常和谐,错落有致。
读起来跌宕起伏,犹如诗词一般。
汪曾祺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可见一斑。
同时,在《受戒》里,作者为达到节奏和谐跃动的效果,精心设置了不少精当的细节。
如明子被舅舅领着过河,乘坐英子父女的船时,下面有一个精彩的细节。
它通过对话来呈现:“‘是你要到荸荠庵当和尚的吗?’明子点点头。
‘当和尚要烧戒疤呕!你不怕?’明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含含糊糊地摇了摇头。
‘你叫什么?’‘明海。
’‘在家的时候?’‘叫明子。
’‘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
我家挨着荸荠庵。
——给你!’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
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哗——许!哗——许!’”读者可以想象船在河面上行走的画面。
画中人是怎么样的呢?作者借助对比描写以产生节奏。
首先是小英子主动问话,引出了一段对答。
多么亲切生动的一幅画面啊!画中的英子是那样的活泼可爱,表现出水乡女孩的大方好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