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鲍尔吉
- 格式:doc
- 大小:29.00 KB
- 文档页数: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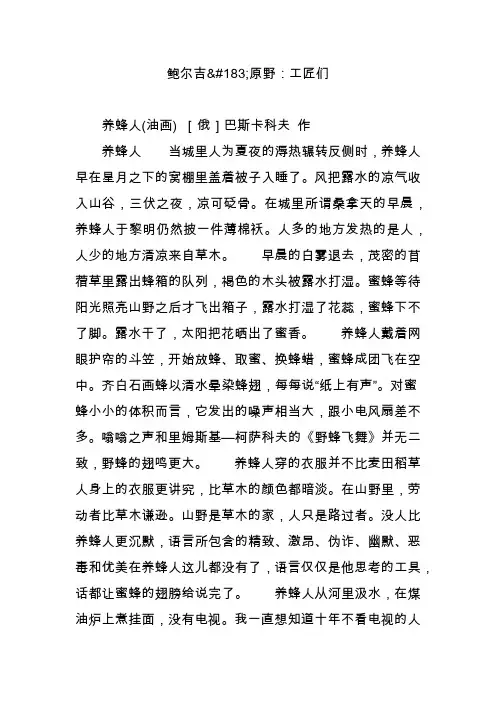
鲍尔吉·原野:工匠们养蜂人(油画) [俄]巴斯卡科夫作养蜂人当城里人为夏夜的溽热辗转反侧时,养蜂人早在星月之下的窝棚里盖着被子入睡了。
风把露水的凉气收入山谷,三伏之夜,凉可砭骨。
在城里所谓桑拿天的早晨,养蜂人于黎明仍然披一件薄棉袄。
人多的地方发热的是人,人少的地方清凉来自草木。
早晨的白雾退去,茂密的苜蓿草里露出蜂箱的队列,褐色的木头被露水打湿。
蜜蜂等待阳光照亮山野之后才飞出箱子,露水打湿了花蕊,蜜蜂下不了脚。
露水干了,太阳把花晒出了蜜香。
养蜂人戴着网眼护帘的斗笠,开始放蜂、取蜜、换蜂蜡,蜜蜂成团飞在空中。
齐白石画蜂以清水晕染蜂翅,每每说“纸上有声”。
对蜜蜂小小的体积而言,它发出的噪声相当大,跟小电风扇差不多。
嗡嗡之声和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野蜂飞舞》并无二致,野蜂的翅鸣更大。
养蜂人穿的衣服并不比麦田稻草人身上的衣服更讲究,比草木的颜色都暗淡。
在山野里,劳动者比草木谦逊。
山野是草木的家,人只是路过者。
没人比养蜂人更沉默,语言所包含的精致、激昂、伪诈、幽默、恶毒和优美在养蜂人这儿都没有了,语言仅仅是他思考的工具,话都让蜜蜂的翅膀给说完了。
养蜂人从河里汲水,在煤油炉上煮挂面,没有电视。
我一直想知道十年不看电视的人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心智澄明。
电视里面即使是最庄重、最刻意典雅的节目,也是造作的产物。
电视对一切都在模拟,不仅新闻在模拟,连真诚也是模拟和练习的产物。
而养蜂人一生都围着蜂转,心中只想着一个字:蜜。
天天想蜜的人生活很苦。
他们被露水打湿裤脚,在山野度过幽居的一生。
他们知道月上东山的模样,见过狼和狐狸的脚印,扎破了手指用土止血,脚丫缝里全是泥土。
他们熟悉荞麦地的白花,熟悉枣树的花,熟悉青草和玉米高粱的味道。
他们身旁都有一条忠诚的老狗;他们把一本字小页厚的武侠书连看好几年;他们赚的钱从邮局飞回老家;他们不懂流行中的一切时尚;他们用清风洗面,用阳光和月色交替护理皮肤;他们一辈子心里都安静;他们所做的一切是换来蜜蜂酿的、对人类健康有益的蜂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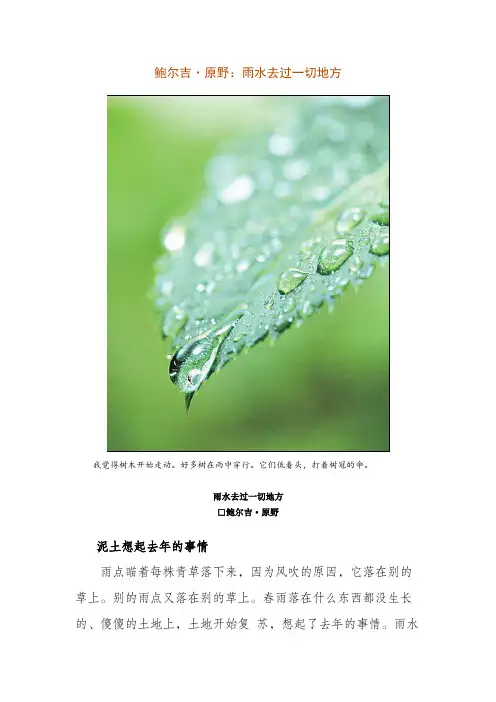
鲍尔吉·原野:雨水去过一切地方我觉得树木开始走动。
好多树在雨中穿行。
它们低着头,打着树冠的伞。
雨水去过一切地方□鲍尔吉·原野泥土想起去年的事情雨点瞄着每株青草落下来,因为风吹的原因,它落在别的草上。
别的雨点又落在别的草上。
春雨落在什么东西都没生长的、傻傻的土地上,土地开始复苏,想起了去年的事情。
雨水排着燕子的队形,以燕子的轻盈钻入大地。
这时候,还听不到沙沙的声响,树叶太小,演奏不出沙沙的音乐。
春雨是今年第一次下,边下边回忆。
有些地方下过了,有些地方还干着。
春雨扯动风的透明的帆,把雨水洒到它应该去的一切地方。
春雨继续下起来,无需雷声滚滚,也照样下,春雨不搞这些排场。
它下雨便下雨,不来浓云密布那一套,那都是夏天搞的事情。
春雨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打雷谁不会?打雷干吗?春雨静静地、细密地、清凉地、疏落地、晶亮地、飘洒地下着,下着。
不大也不小,它们趴在玻璃上往屋里看,看屋里需不需要雨水,看到人或坐或卧,过着他们称之为生活的日子。
春雨的水珠看到屋子里没有水,也没有花朵和青草。
春雨飘落的时候伴随歌声,合唱,小调式乐曲,6/8拍子,类似塔吉克音乐。
可惜人耳听不到。
春雨的歌声低于20赫兹。
旋律有如《霍夫曼的故事》里的“船歌”,连贯的旋律拆开重新缝在一起,走两步就有一个起始句。
开始,发展下去,终结又可以开始。
船歌是拿波里船夫唱的情歌小调,荡漾,节奏一直在荡漾。
这些船夫上岸后不会走路了,因为大地不荡漾。
春雨早就明白这些,这不算啥。
春雨时疾时徐、或快或慢地在空气里荡漾。
它并不着急落地。
那么早落地干吗?不如按6/8的节奏荡漾。
塔吉克人没见过海,但也懂得在歌声里荡漾。
6/8不是给腿的节奏,节奏在腰上。
欲进又退,忽而转身,说的不是腿,而是腰。
腰的动作表现在肩上。
如果舞者头戴黑羔皮帽子,上唇留着浓黑带尖的胡子就更好了。
春雨忽然下起来,青草和花都不意外,但人意外。
他们慌张奔跑,在屋檐和树下避雨。
雨持续下着,直到人们从屋檐和树底下走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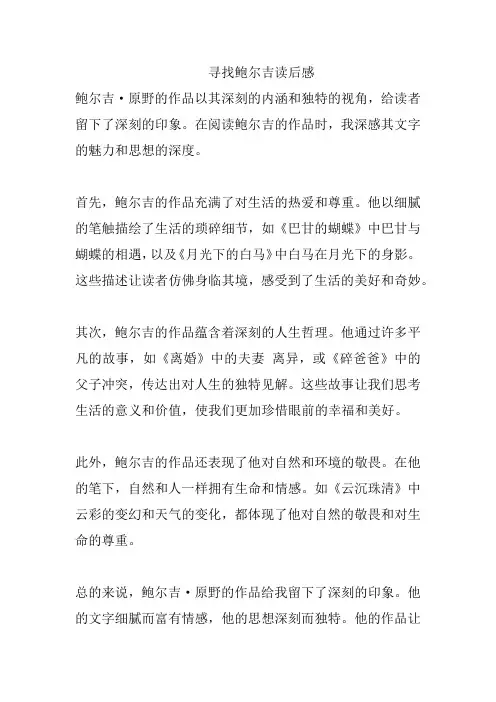
寻找鲍尔吉读后感
鲍尔吉·原野的作品以其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视角,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阅读鲍尔吉的作品时,我深感其文字的魅力和思想的深度。
首先,鲍尔吉的作品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尊重。
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生活的琐碎细节,如《巴甘的蝴蝶》中巴甘与蝴蝶的相遇,以及《月光下的白马》中白马在月光下的身影。
这些描述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奇妙。
其次,鲍尔吉的作品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他通过许多平凡的故事,如《离婚》中的夫妻离异,或《碎爸爸》中的父子冲突,传达出对人生的独特见解。
这些故事让我们思考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使我们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和美好。
此外,鲍尔吉的作品还表现了他对自然和环境的敬畏。
在他的笔下,自然和人一样拥有生命和情感。
如《云沉珠清》中云彩的变幻和天气的变化,都体现了他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尊重。
总的来说,鲍尔吉·原野的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文字细腻而富有情感,他的思想深刻而独特。
他的作品让
我更加热爱生活,更加珍惜每一个瞬间。
同时,他的作品也让我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
我相信这些思考会对我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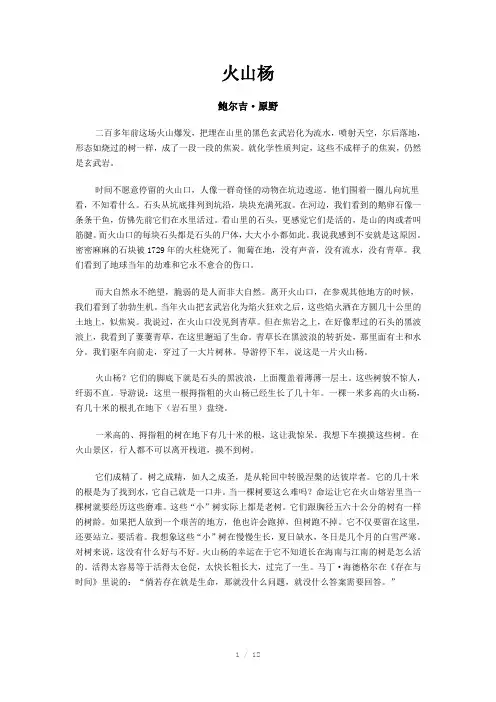
火山杨鲍尔吉·原野二百多年前这场火山爆发,把埋在山里的黑色玄武岩化为流水,喷射天空,尔后落地,形态如烧过的树一样,成了一段一段的焦炭。
就化学性质判定,这些不成样子的焦炭,仍然是玄武岩。
时间不愿意停留的火山口,人像一群奇怪的动物在坑边逡巡。
他们围着一圈儿向坑里看,不知看什么。
石头从坑底排列到坑沿,块块充满死寂。
在河边,我们看到的鹅卵石像一条条干鱼,仿佛先前它们在水里活过。
看山里的石头,更感觉它们是活的,是山的肉或者叫筋腱。
而火山口的每块石头都是石头的尸体,大大小小都如此。
我说我感到不安就是这原因。
密密麻麻的石块被1729年的火柱烧死了,匍蔔在地,没有声音,没有流水,没有青草。
我们看到了地球当年的劫难和它永不愈合的伤口。
而大自然永不绝望,脆弱的是人而非大自然。
离开火山口,在参观其他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勃勃生机。
当年火山把玄武岩化为焰火狂欢之后,这些焰火洒在方圆几十公里的土地上,似焦炭。
我说过,在火山口没见到青草。
但在焦岩之上,在好像犁过的石头的黑波浪上,我看到了萋萋青草,在这里邂逅了生命。
青草长在黑波浪的转折处,那里面有土和水分。
我们驱车向前走,穿过了一大片树林。
导游停下车,说这是一片火山杨。
火山杨?它们的脚底下就是石头的黑波浪,上面覆盖着薄薄一层土。
这些树貌不惊人,纤弱不直。
导游说:这里一根拇指粗的火山杨已经生长了几十年。
一棵一米多高的火山杨,有几十米的根扎在地下(岩石里)盘绕。
一米高的、拇指粗的树在地下有几十米的根,这让我惊呆。
我想下车摸摸这些树。
在火山景区,行人都不可以离开栈道,摸不到树。
它们成精了。
树之成精,如人之成圣,是从轮回中转脱涅槃的达彼岸者。
它的几十米的根是为了找到水,它自己就是一口井。
当一棵树要这么难吗?命运让它在火山熔岩里当一棵树就要经历这些磨难。
这些“小”树实际上都是老树。
它们跟胸径五六十公分的树有一样的树龄。
如果把人放到一个艰苦的地方,他也许会跑掉,但树跑不掉。
它不仅要留在这里,还要站立,要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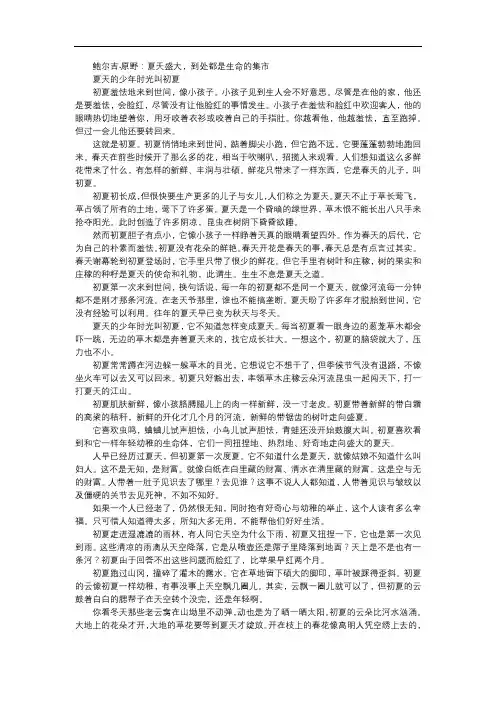
鲍尔吉·原野:夏天盛大,到处都是生命的集市夏天的少年时光叫初夏初夏羞怯地来到世间,像小孩子。
小孩子见到生人会不好意思。
尽管是在他的家,他还是要羞怯,会脸红,尽管没有让他脸红的事情发生。
小孩子在羞怯和脸红中欢迎客人,他的眼睛热切地望着你,用牙咬着衣衫或咬着自己的手指肚。
你越看他,他越羞怯,直至跑掉。
但过一会儿他还要转回来。
这就是初夏。
初夏悄悄地来到世间,踮着脚尖小跑,但它跑不远,它要蓬蓬勃勃地跑回来。
春天在前些时候开了那么多的花,相当于吹喇叭,招揽人来观看。
人们想知道这么多鲜花带来了什么,有怎样的新鲜、丰润与壮硕。
鲜花只带来了一样东西,它是春天的儿子,叫初夏。
初夏初长成,但很快要生产更多的儿子与女儿,人们称之为夏天。
夏天不止于草长莺飞,草占领了所有的土地,莺下了许多蛋。
夏天是一个昏暗的绿世界,草木恨不能长出八只手来抢夺阳光。
此时创造了许多阴凉,昆虫在树阴下昏昏欲睡。
然而初夏胆子有点小,它像小孩子一样睁着天真的眼睛看望四外。
作为春天的后代,它为自己的朴素而羞怯。
初夏没有花朵的鲜艳。
春天开花是春天的事,春天总是有点言过其实。
春天谢幕轮到初夏登场时,它手里只带了很少的鲜花。
但它手里有树叶和庄稼,树的果实和庄稼的种籽是夏天的使命和礼物,此谓生。
生生不息是夏天之道。
初夏第一次来到世间,换句话说,每一年的初夏都不是同一个夏天,就像河流每一分钟都不是刚才那条河流。
在老天爷那里,谁也不能搞垄断。
夏天盼了许多年才脱胎到世间,它没有经验可以利用。
往年的夏天早已变为秋天与冬天。
夏天的少年时光叫初夏,它不知道怎样变成夏天。
每当初夏看一眼身边的葱茏草木都会吓一跳,无边的草木都是奔着夏天来的,找它成长壮大。
一想这个,初夏的脑袋就大了,压力也不小。
初夏常常蹲在河边躲一躲草木的目光,它想说它不想干了,但季候节气没有退路,不像坐火车可以去又可以回来。
初夏只好豁出去,率领草木庄稼云朵河流昆虫一起闯天下,打一打夏天的江山。
初夏肌肤新鲜,像小孩胳膊腿儿上的肉一样新鲜,没一寸老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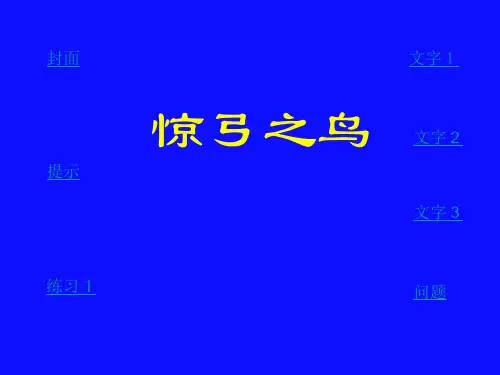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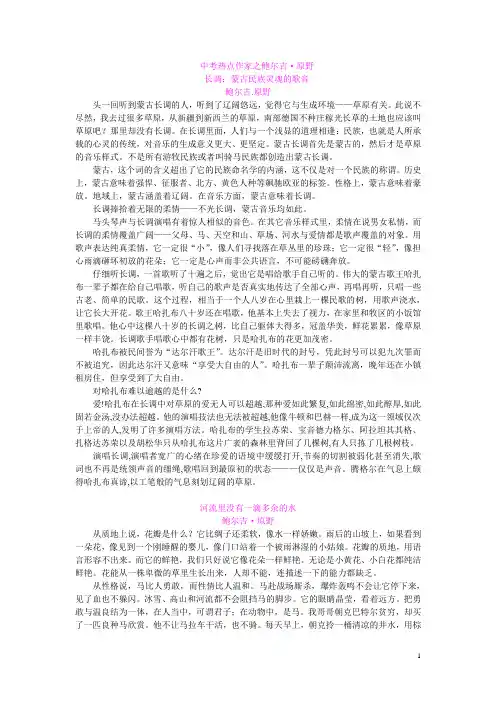
中考热点作家之鲍尔吉·原野长调:蒙古民族灵魂的歌音鲍尔吉.原野头一回听到蒙古长调的人,听到了辽阔悠远,觉得它与生成环境——草原有关。
此说不尽然,我去过很多草原,从新疆到新西兰的草原,南部德国不种庄稼光长草的土地也应该叫草原吧?那里却没有长调。
在长调里面,人们与一个浅显的道理相逢:民族,也就是人所承载的心灵的传统,对音乐的生成意义更大、更坚定。
蒙古长调首先是蒙古的,然后才是草原的音乐样式。
不是所有游牧民族或者叫骑马民族都创造出蒙古长调。
蒙古,这个词的含义超出了它的民族命名学的内涵,这不仅是对一个民族的称谓。
历史上,蒙古意味着强悍、征服者、北方、黄色人种等飙驰欧亚的标签。
性格上,蒙古意味着豪放。
地域上,蒙古涵盖着辽阔。
在音乐方面,蒙古意味着长调。
长调捧拾着无限的柔情——不光长调,蒙古音乐均如此。
马头琴声与长调演唱有着惊人相似的音色。
在其它音乐样式里,柔情在说男女私情,而长调的柔情覆盖广阔——父母、马、天空和山、草场、河水与爱情都是歌声覆盖的对象。
用歌声表达纯真柔情,它一定很“小”,像人们寻找落在草丛里的珍珠;它一定很“轻”,像担心雨滴砸坏初放的花朵;它一定是心声而非公共语言,不可能磅礴奔放。
仔细听长调,一首歌听了十遍之后,觉出它是唱给歌手自己听的。
伟大的蒙古歌王哈扎布一辈子都在给自己唱歌,听自己的歌声是否真实地传达了全部心声,再唱再听,只唱一些古老、简单的民歌。
这个过程,相当于一个人八岁在心里栽上一棵民歌的树,用歌声浇水,让它长大开花。
歌王哈扎布八十岁还在唱歌,他基本上失去了视力,在家里和牧区的小饭馆里歌唱。
他心中这棵八十岁的长调之树,比自己躯体大得多,冠盖华美,鲜花累累,像草原一样丰饶。
长调歌手唱歌心中都有花树,只是哈扎布的花更加茂密。
哈扎布被民间誉为“达尔汗歌王”。
达尔汗是旧时代的封号,凭此封号可以犯九次罪而不被追究,因此达尔汗又意味“享受大自由的人”。
哈扎布一辈子颠沛流离,晚年还在小镇租房住,但享受到了大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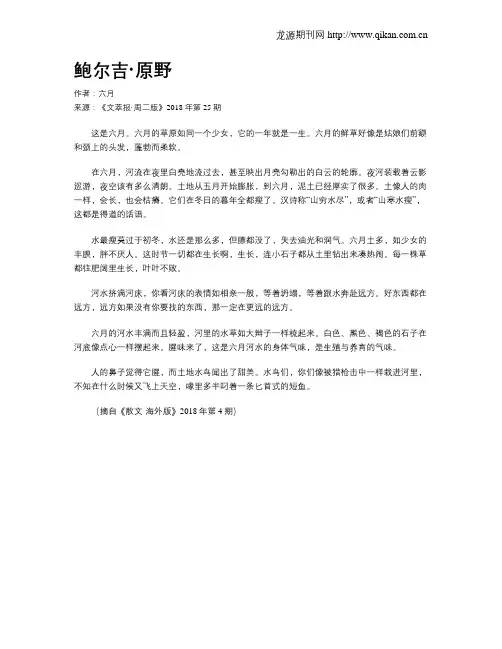
龙源期刊网
鲍尔吉·原野
作者:六月
来源:《文萃报·周二版》2018年第25期
这是六月。
六月的草原如同一个少女,它的一年就是一生。
六月的鲜草好像是姑娘们前额和颈上的头发,蓬勃而柔软。
在六月,河流在夜里白亮地流过去,甚至映出月亮勾勒出的白云的轮廓。
夜河装载着云影巡游,夜空该有多么清朗。
土地从五月开始膨胀,到六月,泥土已经厚实了很多。
土像人的肉一样,会长,也会枯瘠。
它们在冬日的暮年全都瘦了。
汉诗称“山穷水尽”,或者“山寒水瘦”,这都是得道的话语。
水最瘦莫过于初冬,水还是那么多,但膘都没了,失去油光和润气。
六月土多,如少女的丰腴,胖不厌人。
这时节一切都在生长啊,生长,连小石子都从土里钻出来凑热闹。
每一株草都往肥阔里生长,叶叶不败。
河水挤满河床,你看河床的表情如相亲一般,等着坍塌,等着跟水奔赴远方。
好东西都在远方,远方如果没有你要找的东西,那一定在更远的远方。
六月的河水丰满而且轻盈,河里的水草如大辫子一样梳起来。
白色、黑色、褐色的石子在河底像点心一样摆起来。
腥味来了,这是六月河水的身体气味,是生殖与养育的气味。
人的鼻子觉得它腥,而土地水鸟闻出了甜美。
水鸟们,你们像被猎枪击中一样栽进河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飞上天空,喙里多半叼着一条匕首式的短鱼。
(摘自《散文·海外版》2018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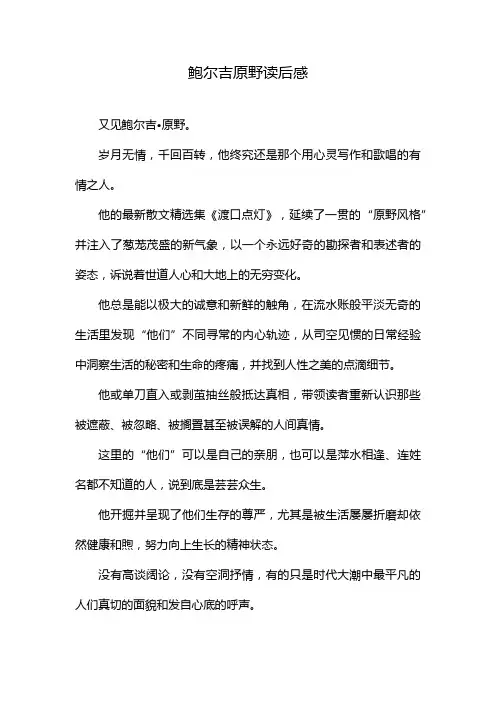
鲍尔吉原野读后感又见鲍尔吉•原野。
岁月无情,千回百转,他终究还是那个用心灵写作和歌唱的有情之人。
他的最新散文精选集《渡口点灯》,延续了一贯的“原野风格”并注入了葱茏茂盛的新气象,以一个永远好奇的勘探者和表述者的姿态,诉说着世道人心和大地上的无穷变化。
他总是能以极大的诚意和新鲜的触角,在流水账般平淡无奇的生活里发现“他们”不同寻常的内心轨迹,从司空见惯的日常经验中洞察生活的秘密和生命的疼痛,并找到人性之美的点滴细节。
他或单刀直入或剥茧抽丝般抵达真相,带领读者重新认识那些被遮蔽、被忽略、被搁置甚至被误解的人间真情。
这里的“他们”可以是自己的亲朋,也可以是萍水相逢、连姓名都不知道的人,说到底是芸芸众生。
他开掘并呈现了他们生存的尊严,尤其是被生活屡屡折磨却依然健康和煦,努力向上生长的精神状态。
没有高谈阔论,没有空洞抒情,有的只是时代大潮中最平凡的人们真切的面貌和发自心底的呼声。
于是,我们在《来,把手给我》中,看见了白长岁不顾路途遥远,在大年初一突然来到老战友家,却只为看一眼老战友的儿子,对他说一句“把手给我!”;在《墓碑后面的字》中,记住了那个并未露面却用尽全力写下“妈妈,我爱你”的男孩儿。
当然,我们也忘不了英年早逝、骨灰撒在北京昌平阳光直射的麦田里的作家苇岸——“他痛恨暴虐、欺诈、贪婪和安逸,但他是个容易被欺负的人,也是不通顺便的人,或许还由于固执自己的信念而变得孤愤。
然而这些都没有使他放弃用辽远的目光和朴素的爱日夜倾听大地心脏的声音,当他把清澈的思想如根须一样延伸到土地深处的时候,一切却突然静止”。
他热爰和敬畏那些如大地上的草木一般诚实善良、平凡坚忍的劳动者,在他的眼中,他们是高贵而有智慧的人。
他不仅把自己灼热而又清澈的眼泪给了他们,还把深情的、洁净的、如朝露般新鲜跳跃滴答作响的笔触也给了他们。
在《养蜂人》中,他就写了这样一群“用清风洗面,用阳光和月色交替护理皮肤”的劳动者:“天天想蜜的人生活艰苦,他们被露水打湿裤脚,在山野度过幽居的一生,他们知道月上东山的模样,见过狼和狐狸的脚印,扎破了手,用土止血……”“没人比养蜂人更沉默,语言所包含的精致、激昂、伪诈、幽默、恶毒和优美在养蜂人这里都没有了,语言仅仅是他思考的工具,话都让蜜蜂的翅膀给说完了。

名家鲍尔吉.原野精美散文鲍尔吉·原野,小说、散文、诗歌、文学报告等均多次获奖。
鲍尔吉·原野与歌手腾格尔、画家朝戈被称为中国文艺界的“草原三剑客”。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带来的名家鲍尔吉.原野精美散文,供大家欣赏。
名家鲍尔吉.原野精美散文:那些大词我们生活在大词的时代,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处于大词的包围中。
就我的同龄人而言,始终有大词陪伴成长。
大词不是粮食,不是水,也不是冬天的棉被,但它从广播、报纸和电视里冲出来,钻进你耳朵里并影响你的心灵。
记录这些大词一点困难都没有,它们是辉煌、激荡、滚滚、壮丽、冲天、突破、昂扬、坚决、壮志、奔、冲、赶、搞。
原本归于自然被借用的大词有黄河、泰山、长江、珠峰、波浪。
新的大词有峰会、宏大、后现代等等。
有人天生跟大词站在一起,包括“大”这个词,好多人喜欢用诸如大突破、大决战这些词,还有大什么,我也记不清了。
有人觉得多说多占一些大词显得自己气势磅礴,即使身板儿单薄也显得有块头,显得勇猛或义无反顾,跟历史、正义和永恒都能沾上边儿。
词和人的关系,与生活习惯与人的关系一样。
比如沾上烟草就不容易跟它说拜拜。
爱说大词的人离开大词手里空落落的,不知道说点什么好。
人如果自小就被大词包围着,浸润着,终将被大词所驱使。
别小看词语对人心灵的占有,它会影响人的心地或者叫思维方式。
词一定会变成工具或者叫手足与人共生。
那么大词是什么样的工具手足呢?对普通人,特别是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大词什么也不是,它只是个恐龙般的躯壳,里面并没有血肉。
那些大词,看上去很厉害,然而仔细想一想,什么叫辉煌?除了太阳,还有其它什么东西辉煌?是LED屏吗?太阳也不每天辉煌,从地球看上去太阳像人一样有阴有晴,辉煌只是它一部分功能。
还有,激荡和壮丽是什么意思?想象不出来,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
大词是文人造出来的装饰性的花样,古人称之为“文”,和“纹”同义。
这个文与质无关,是装修上去的,基本上是一个伪词汇。
大这个词,前边和后面常常挨着两个词,一个叫假,一个叫空。
鲍尔吉原野经典散文在线阅读鲍尔吉·原野,1958年7月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现为辽宁省公安厅专业作家,辽宁省作协副主席。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带来的鲍尔吉原野经典散文,供大家欣赏。
鲍尔吉原野经典散文:河在河的远方对河来说,自来水只是一些幼稚的婴儿。
不,不能这么说,自来水是却生生的、带着消毒气味的“城里人”。
它们从没见过河。
河是什么?河是对世间美景好无留恋的智者,什么都不会让河流停下脚步,哪怕是一分钟。
河最像时间。
这么说,时间穿着水的衣衫从大地走过。
河流阅历深广。
它分出一些子孙缔造粮食,看马领着孩子俯身饮水。
落日在傍晚把河流烧成通红的铁条。
河流走到哪里,空中都有水鸟追随。
水鸟以为,河会一直走到最好的地方。
天下哪有什么好地方,河流到达陌生的远方。
你从河水流淌的方向往前看,会觉得那里不值得去,荒蛮、有沙砾,可能寸草不生。
河一路走过,甚至没时间解释为什么来到这里。
茂林修竹的清幽之地,乱石如斗的僻远之乡,都是河的远方。
凡是时间要去的地方,都是河流的地方。
河流也会疲倦,在村头歇一歇,看光屁股的顽童捉泥鳅、打水仗。
河流在月夜追向往昔,像继续行军几天几夜的士兵,一边一边睡觉。
它伤感自己一路收留了太多的儿女——鱼虾禽鸟乃至泥沙,也说不好它们走入大海之后的命运。
也许到明天,到一处戈壁的古道,河水断流。
那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河流被埋藏。
而河流从一开始就意气决绝,断流之地就是故乡。
河的辞典里只有两个字:远方。
远方不一定富庶,不一定安适,不一定雄阔。
它只是你要去的地方,是明日到达之处,是下一站,是下一站的远方。
常常,我们在远方看到河流,河流看到我们之后又去远方。
如果告诉别人的去向,只好说,河在河的远方。
鲍尔吉原野经典散文:春雪的夜雪下了一天。
作为春雪,一天的时间够长了。
节气已经过了惊蛰和春分,下雪有点近于严肃。
但老天爷的事咱们最好别议论,下就下吧。
除了雨雪冰雹,天上下不来别的东西。
下雪也是为了万物好。
我站在窗边盼雪停是为了跑步,心里对雪说:你跑完我跑。
品味I115|寻找鲍尔吉•《梨花与我共白头》鲍尔吉•原野著鲍尔吉是我的蒙古族姓氏,在《元朝秘史》的汉译本中被写作学儿只斤。
这个姓我平常不用,因为在汉人居多数的城市,使用这么复杂的姓要用大量的时间去解释,累.发表作品时,我偶尔标上姓,使之成为“鲍尔吉•原野”,有人说这叫“蒙汉合璧”。
但这也遇到过麻烦。
我的一首名叫《乡音》的诗被国内某家用英文印行的刊物选载,给了一点稿费。
事先我不知这是稿费,这是一份中国银行的通知,告我凭此去一家较远的分理处取钱。
到了地方,拿凭证一看是稿费六元。
支这些稿费约需十来道手续。
如要买一个铜牌再去换什么等等,每道手续都依次排队。
在这些排队的人中,大多是企业和个体户提备用金的,六元钱肯定是最小的数目。
当那位小姐把铜牌清脆地掷来时,我见她掩口一笑。
我猜想,咸亨酒店里的人笑孔乙己,大约就是这样的笑法。
临了,到了取款的时候。
“那个人是谁?”我急忙回头瞅.不知付款小姐在说什么。
她提高了声音:“鲍尔吉是谁?”“鲍尔吉是我呀。
”我和蔼地回答。
小姐和我隔着钢管焊的为了防止抢钱的栅栏,而且大理石的台面也有一米宽。
“那原野又是谁?”她用圆珠笔杆敲着台面,案例出现了。
“我就是原野。
”事情麻烦了。
“你,到底叫什么? ”她镇定质问。
我虚弱地解释,原野是我的名字,而鲍尔吉是姓,但没提《元朝秘史》与李儿只斤。
她笑了,向同事问:“你听说有姓鲍尔吉的吗?”她那同事轻蔑地摇摇头。
我有些被激怒了,但念她无知,忍住。
子曰:“不知者不愠。
”我告诉她:“我是蒙古族人,就姓这个姓。
”她的同事告诫我:“就算你姓复姓,顶多姓到欧阳和诸葛这种程度,鲍尔吉?哼。
”我不想当着那么多人和她们争辩或进行更可笑的学术性讨论,为了六元钱不值得。
我仍耐心解释。
“在欧阳之外,不是还有罗纳德•里根吗?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
”众人笑了,我知道他们在嘲笑我卖弄学问。
“你说怎么办呢?”我尽量悠闲地问那小姐。
“你要证明鲍尔吉是你。
”她手拿着我的工作证和身份证,“但这已经不可能了,这上面写的都是原野。
鲍尔吉·原野琥珀里的黄金,我遇见了我到中原看新农村建设。
一个村子,家家住上新楼房,高墙大院。
我问户主,墙多高?他自豪地说,四米五。
全村统一规划住房,家家院墙都四米五高。
屋里面,农民用上了沼气,这是清洁能源,还有其它的先进之处,确实是新农村。
我对高墙感到压抑,虽然农民对此自豪。
今年夏天,我去内蒙古翁牛特旗巴音拉和海拉苏两个地方游历。
牧区家家都没有墙,老远就看到房子,门和窗户像房子脸上的嘴和眼睛。
在夏天,门永远开着。
晚上关门,是防止进蚊子而不是进人。
有的人家晚上睡觉也不关门窗,点蚊香。
普通家宅的院墙四米多高,我是第一次看到。
以前只看到监狱有这么高的墙。
垒高墙不是由于村里砖头多得用不了,而为防盗贼。
两个身高一米七的盗贼,一人踩在另一人肩上约三米二,伸臂,加起来三米八左右,还是翻不过这样的墙。
我估计砌墙者正是这样谋划的。
若鲍喜顺踩着另一个鲍喜顺也翻不过去,虽然已经四米八了,他们不灵巧。
我去的翁牛特旗正是鲍喜顺的老家。
这里的人们压根儿就没有偷窃的观念。
派出所几十年没处理过偷抢的案子,偶有也是外来人干的。
我去一个叫沙湖的地方,白茫茫的沙漠中间有一座湖,水蓝得耀眼。
水里肥笨的野鲤鱼金红一片,没人打。
一户承包湖的蒙古人,是老俩口。
他与其说承包,不如说承担动物保护工作。
劝说游人别拣野鸭蛋,别用炸药炸鱼。
他们过得不怎么富裕,心情却好。
去他家,屋里没人。
电视什么都不缺,茶碗里的水还冒热气。
另一间房子是满满的农具。
我上炕睡了一觉也没见主人回来。
陪我的人说,老汉放羊去了,他有手机,沙漠上信号不好。
我们去花火绣村一户牧民家,也没人。
陪同者找来奶豆腐,切开吃。
我问你认识这家人吗?他说,嗨,牧区不管认不认识,吃东西喝茶都是正常的。
我问:门窗四敞大开,没人偷东西吗?他反问我:为什么要偷别人的东西呢?你听说过蒙古人偷别人的东西吗?我说没有。
过一会儿,主人回来了,他骑摩托把女儿送到旗里的幼儿园。
见我们在屋,他不好意思了,仿佛怠慢了我们。
寻找鲍尔吉
鲍尔吉是我的蒙古姓氏,在《元朝秘史》的汉译本中被写作孛儿只斤。
这个姓我平常不用,因为在汉人居多数的城市,使用这么复杂的姓要用大量的时间去解释,累。
发表作品时,我偶尔标上姓,使之成为“鲍尔吉·原野”,诗人赵健雄说这叫“蒙汉合壁”。
在作品上注姓,表示不去掠其“原野”之美。
其它深意是没有的。
但这也遇到过麻烦。
我的一首名叫《乡音》的诗被国内某家用英文印行的刊物选择,给了一点稿费。
事先我不知这是稿费,这是一份中国银行的通知,告我凭此去一家较远的分理处取钱。
我知道中国银行是一家与外币有涉的金融机构,美元什么的。
我并未兴奋,没干过和美元有关的事,怎能和它相亲呢?
到了地方,拿凭证一看是稿费六元。
支这些稿费约需十来道手续。
如要买一个铜牌再去换什么等等,每道手续都依次排队。
在这些排队的人中,大多是企业和个体户提备用金的,六元钱肯定是最少的数目。
当那位小姐把铜牌清脆地掷来时,我见她掩口一笑。
我猜想,咸亨酒店里的人笑孔乙己,大约就是这样的笑法。
临了,到了取款的时候。
“那个人是谁?”我急忙回头瞅,不知付款小姐在说什么。
她提高了声音:“鲍尔吉是谁?”
“鲍尔吉是我呀。
”我和蔼地回答。
小姐和我隔着钢管焊的为了防止
抢钱的栅栏,而且大理石的台面也有一米宽。
“那原野又是谁?”她用圆珠笔杆敲着台面,案例出现了。
“我就是原野。
”事情麻烦了。
“你,到底叫什么?”她镇定质问。
排队的人,目光已经转向我。
我不是电影演员,很难在这么多人的逼视下保持气定神闲。
我虚弱的解释,原野是我的名字,而鲍尔吉……等等,但没提《元朝秘史》与孛儿只斤。
她笑了,向同事问:“你听说有姓鲍尔吉的吗?”她那同事轻蔑地摇摇头。
她又问栅栏外排队的人:“你们听说有姓鲍尔吉的吗?”她那用化妆品抹得很好看的脸上,已经露出戳穿骗局后的喜悦。
我有些被激怒了,但念她无知,忍住。
子曰“不知者不愠。
”我告诉她:“我是蒙古人,就姓这个姓。
”
她的同事告诫我:“就算你姓复姓,顶多姓到欧阳和诸葛这种程度,鲍尔吉?哼。
”
这一位并不无知,并且戴一条蓝珠石项链。
她知道复姓,但竟提到“姓到”这样的限制。
以双人的倨傲,如果我是泰戈尔,那么“罗宾德拉纳特”这个姓定会使她们目眦尽裂了。
我不想当着那么多人和她们争辩或进行更可笑的学术性讨论,为了六元钱不值得。
我仍耐心解释。
“在欧阳之外,不是还有罗纳德·里根吗?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
”
众人笑了,我知道他们在嘲笑我卖弄学问。
有人说“他肯定念过大
学。
”而银行小姐向我投来明确的侮慢的眼神。
原来中国人不配姓复杂的姓氏。
这与阿Q想恢复自己的赵姓而不可得一样。
“你说怎么办呢?”我尽量悠闲地问那小姐。
“你要证明鲍尔吉是你。
”她手拿着我的工作证和身份证。
“但这已经不可能了,这上面写的都是原野。
所以,你要把鲍尔吉找来,和他一同领款。
”
为了六元钱去寻找鲍尔吉。
我想起一句歌词:“为了一块牛排出卖巴黎。
”
鲍尔吉,你在哪里?我怅然离开取款台,在心底呼唤。
对任何人来说,为了六元钱罹此磨难,就应该罢手了。
但我如看电影一样,想知道此事是怎样一个结局。
我站在门口观察。
我发现一个面相善良的人,上前叙说我的处境,简言之,请他充任鲍尔吉。
“这怎么行?”他瞪着眼睛,原来善良的人瞪起眼睛也不善良。
我忽悟,这种作弊的事不能选择好人。
我又找到了一个衣冠不整如无赖样的人,约二十多岁。
谈过之后,他狡猾地问:“这事好办,你给多少钱?”
多少钱?这事不能超过六元钱。
我告诉他“三元钱”。
“三元?”他简直想咬我一口,“你那笔款多少钱?”
“六元。
”我给他看提款单。
他笑着看我的脸,那目光在我眼睛鼻子之间滑行。
用目光蹂躏别人就是这个样子。
他提一提后裤腰,问:“你是知识分子吗?”在“知识分子”这个词里,他的语调充满了恶毒的挪揄。
“我是你爹。
”我告诉他。
他要动手,这从他肩上可以看出来。
《武当拳法》曰“挥拳者其肩先动。
”我上前掐住他的两腮,酸痛是难免的了。
我把他的嘴捏成喇叭花一般,里边洞黑黄牙森然。
如果换了别人,必朝里边吐一口唾沫。
但我没这样,不文明。
我一推,他踉跄而去。
他是那种在社会底层游荡的人。
我后悔了,怎么能找这样的人担任鲍尔吉呢?凡吾鲍尔吉氏,乃贵族血统,铁木真即是此氏中人,当然又是此氏的先祖。
最次也要找一个电大毕业的,这是我对新鲍尔吉的要求。
不好找,我只得打电话给在附近的一位,请他襄助。
他叫刘红草,在某机关当科长。
我道出原委,他摇头。
“六元钱,嗨。
我给你十元,走吧!”
我表示此事如何如何,他迟疑地俯就了。
中国银行分理处,人已稀少。
我们来到付款台。
“他就是鲍尔吉。
”
我骄矜地向小姐介绍,像推荐一件珍宝。
“是,就是。
”刘红草点头。
“工作证。
”小姐扔一句。
刘红草假装找工作证。
“哎呀,忘带了。
”
“回去取。
”小姐连头都不抬了。
“嗨,六元钱。
”我恳求她,“开开面吧。
”
小姐有点通融的意思:“拿名章也行。
”
“快拿名章。
”我指示刘红草。
他又上下假装找。
“小姐,你看没带名章。
”
小姐坚拒。
我问:“那一会儿拿来名章,他还用来吗?”
“随便。
”
出门,我和刘红草握别,感谢大力支持。
我独自找一个刻章的老头。
“鲍尔吉是啥玩意儿?”刻章的老头茫然发问。
“什么啥玩意儿,”我恶狠狠地说,“这是姓!”
“姓?”老头更茫然,“我刻了一辈子名章……”
又来了,我只好安抚“刻吧刻吧……”
刻好了,牛角名章,十元。
“十元?我最多出六元。
”
“八元。
”
“六元。
”
“七元,少一分不行。
”
“七元钱就赔了。
”
“赔了?”老头从花镜上方看我。
“什么赔了?”
我的事情无人可以解释。
我拿著名章取出了按惯例应该在邮局取来的稿费。
我看到结局了。
主要的,当我手携着“鲍尔吉”的名章时,便不惮惧来自各方的质询了,可以雄视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