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的意象分析
- 格式:doc
- 大小:28.50 KB
- 文档页数: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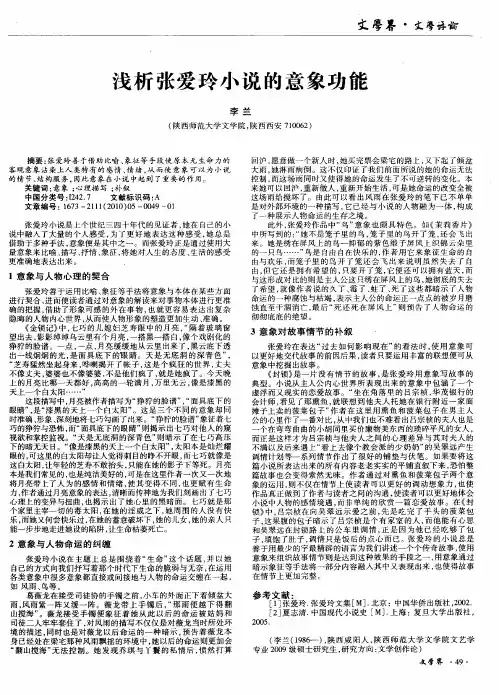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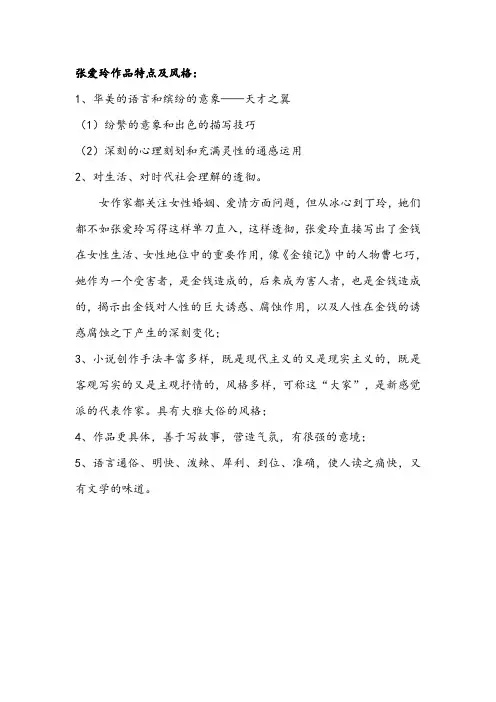
张爱玲作品特点及风格:
1、华美的语言和缤纷的意象——天才之翼
(1)纷繁的意象和出色的描写技巧
(2)深刻的心理刻划和充满灵性的通感运用
2、对生活、对时代社会理解的透彻。
女作家都关注女性婚姻、爱情方面问题,但从冰心到丁玲,她们都不如张爱玲写得这样单刀直入,这样透彻,张爱玲直接写出了金钱在女性生活、女性地位中的重要作用,像《金锁记》中的人物曹七巧,她作为一个受害者,是金钱造成的,后来成为害人者,也是金钱造成的,揭示出金钱对人性的巨大诱惑、腐蚀作用,以及人性在金钱的诱惑腐蚀之下产生的深刻变化;
3、小说创作手法丰富多样,既是现代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既是客观写实的又是主观抒情的,风格多样,可称这“大家”,是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
具有大雅大俗的风格;
4、作品更具体,善于写故事,营造气氛,有很强的意境;
5、语言通俗、明快、泼辣、犀利、到位、准确,使人读之痛快,又有文学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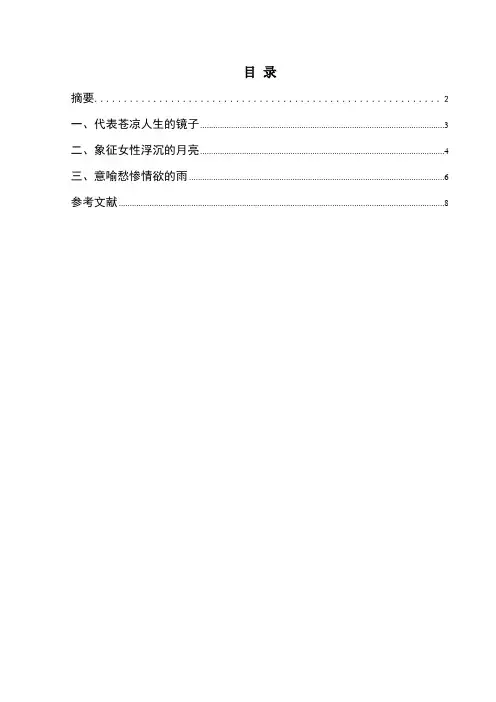
目录摘要 (2)一、代表苍凉人生的镜子 (3)二、象征女性浮沉的月亮 (4)三、意喻愁惨情欲的雨 (6)参考文献 (8)摘要:张爱玲小说在对人物思想、情感、心理、性格、命运、环境和自然景物的描写上具有意象的直观性、隐喻性和意境性特点,正是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张爱玲小说具有意象性特点。
解析张爱玲小说存在的意象,对于了解张爱玲小说中人物的心理及作家的悲剧意识,从而深刻地把握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征都是很有帮助的。
关键词:张爱玲,意象,镜子,月亮,雨,女性意象是人的主观之意与外在的客观之象的有机结合。
张爱玲的小说意象繁复,多如繁星,不胜枚举,意象经营独具匠心。
她尤其擅长华美凄艳的意象构造自己笔下的“荒凉之城”,向我们道尽那个世界的爱与死、色与空、真与假。
打造了无数人百转千回的幻想,又在顷刻之间灰飞烟灭。
张爱玲这种独具特色的意象艺术创作风格让小说显得格外个性,其中对于“镜子、月亮、雨”的意象更是频繁出现。
对此,本文将对“镜子、月亮、雨”的意象的研究,深刻了解张爱玲的女性思想。
一、代表苍凉人生的镜子作为人类的日常用品,镜子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供人自照。
单纯的照,自然和文学无关。
但照镜的如果是美人,镜子便作为美人的伴侣进入文学――美人照镜;照镜的如果是仁人志士,镜子便作为仁人志士的伴侣进入文学――对镜抒怀;照镜的如果是智者,镜子便成为智者自省的工具。
有时,照镜者爱上了镜中的自己(镜恋);有时,照镜者不认识镜中的自己(昏镜);有时,照镜者分不清镜中之我和对镜之我(变形镜),甚至在镜中看到心灵的影像。
这时,镜子就不仅仅是一件日用品,而是自我的映射。
张爱玲是一个驾驭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作家,在她笔下,古典镜意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取舍与发挥。
镜子在日常生活中是易碎的,不牢固的,在张爱玲小说中的镜子意象正好说明了小说中人的生存环境是靠不住的,仿佛一捏就碎。
在《沉香屑·第一香炉》中,周吉婕在浴室对镜补妆时,薇龙上楼请吉婕下去弹钢琴,引得吉婕向薇龙发了一串牢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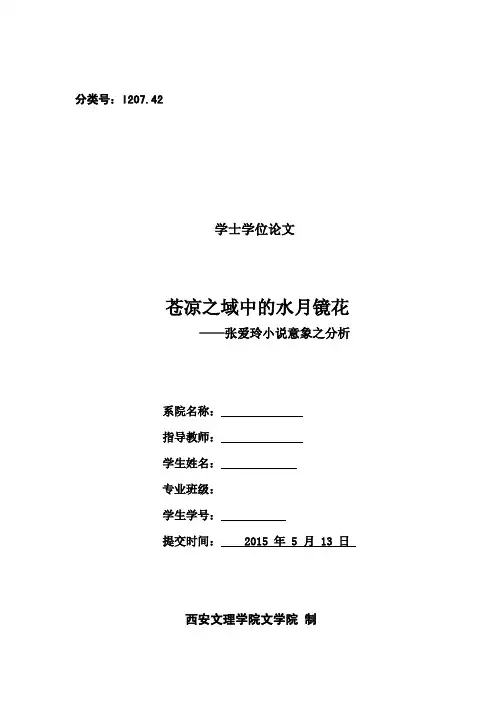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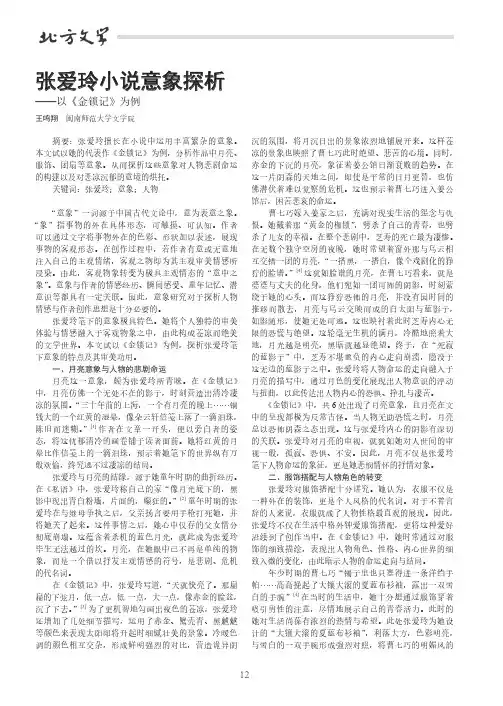
12张爱玲小说意象探析——以《金锁记》为例王鸣翔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摘要:张爱玲擅长在小说中运用丰富繁杂的意象。
本文试以她的代表作《金锁记》为例,分析作品中月亮、服饰、团扇等意象。
从而探析这些意象对人物悲剧命运的构建以及对悲凉沉郁的意境的烘托。
关键词:张爱玲;意象;人物“意象”一词源于中国古代文论中,意为表意之象。
“象”指事物的外在具体形态,可触摸、可认知。
作者可以通过文字将事物外在的色彩、形状加以表述,展现事物的客观形态。
在创作过程中,若作者有意或无意地注入自己的主观情绪,客观之物即为其主观审美情感所浸染。
由此,客观物象转变为极具主观情态的“意中之象”。
意象与作者的情感经历、瞬间感受、童年记忆、潜意识等都具有一定关联。
因此,意象研究对于探析人物情感与作者创作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张爱玲笔下的意象极具特色。
她将个人独特的审美体验与情感融入于客观物象之中,由此构成苍凉而绝美的文学世界。
本文试以《金锁记》为例,探析张爱玲笔下意象的特点及其审美功用。
一、月亮意象与人物的悲剧命运月亮这一意象,颇为张爱玲所青睐。
在《金锁记》中,月亮仿佛一个无处不在的影子,时刻营造出清冷凄凉的氛围。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1]作者在文章一开头,便以旁白者的姿态,将这忧郁清冷的画卷铺于读者面前。
她将红黄的月晕比作信笺上的一滴泪珠,预示着她笔下的世界纵有万般欢愉,终究逃不过凄凉的结局。
张爱玲与月亮的结缘,源于她童年时期的曲折经历。
在《私语》中,张爱玲称自己的家“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2]童年时期的张爱玲在与继母争执之后,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并将她关了起来。
这件事情之后,她心中仅存的父女情分彻底崩塌。
这蕴含着杀机的蓝色月光,就此成为张爱玲毕生无法越过的坎。
月亮,在她眼中已不再是单纯的物象,而是一个借以抒发主观情感的符号,是悲剧、危机的代名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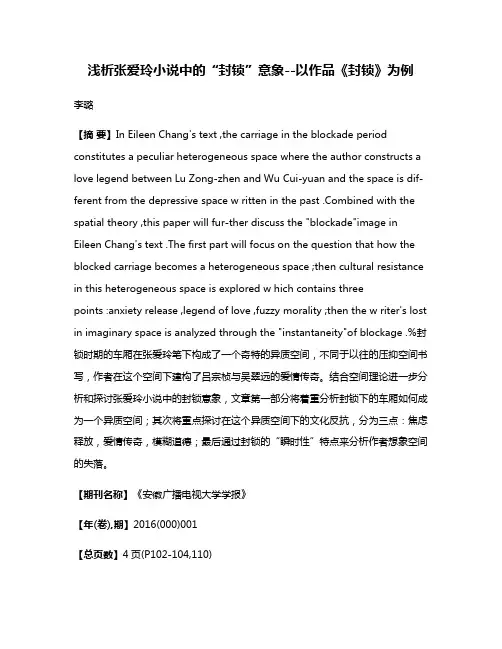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封锁”意象--以作品《封锁》为例李璐【摘要】In Eileen Chang's text ,the carriage in the blockade period constitutes a peculiar heterogeneous space where the author constructs a love legend between Lu Zong‐zhen and Wu Cui‐yuan and the space is dif‐ferent from the depressive space w ritten in the past .Combined with the spatial theory ,this paper will fur‐ther discuss the "blockade"image in Eileen Chang's text .The first part will focus on the question that how the blocked carriage becomes a heterogeneous space ;then cultural resistance in this heterogeneous space is explored w hich contains threepoints :anxiety release ,legend of love ,fuzzy morality ;then the w riter's lost in imaginary space is analyzed through the "instantaneity"of blockage .%封锁时期的车厢在张爱玲笔下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异质空间,不同于以往的压抑空间书写,作者在这个空间下建构了吕宗桢与吴翠远的爱情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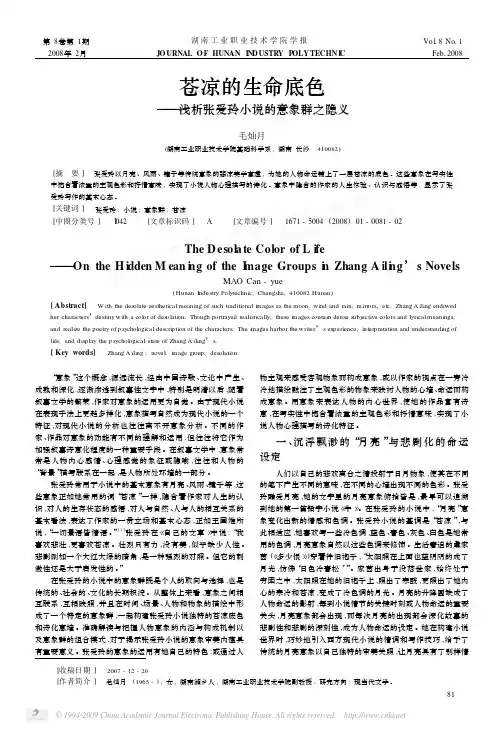
第8卷第1期2008年2月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 URNAL O F HUNAN IND USTRY POLY TECHN I CVol 18No 11Feb 12008苍凉的生命底色———浅析张爱玲小说的意象群之隐义毛灿月(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基础科学系,湖南长沙 410082)[摘 要] 张爱玲以月亮、风雨、镜子等传统意象的悲凉美学意蕴,为她的人物命运铺上了一层苍凉的底色。
这些意象在写实性中饱含着浓重的主观色彩和抒情意味,实现了小说人物心理描写的诗化。
意象中隐含的作家的人生体验、认识与感悟等,显示了张爱玲写作的基本心态。
[关键词] 张爱玲;小说;意象群;苍凉[中图分类号] I 042 [文章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004(2008)01-0081-02The D esol a te Color of L i fe———On the H i dden M ean i n g of the I mage Groups i n Zhang A ili n g ’s NovelsMAO Can -yue(Hunan I ndustry Polytechnic,Changsha,410082Hunan )[Abstract] W ith the des olate aesthetical meaning of such traditi onal i m ages as the moon,wind and rain,m irr ors,etc,Zhang A iling endowedher characters ’destiny with a col or of des olati on 1Though portrayed realistically,these i m ages contain dense subjective col ors and lyrical meanings,and realize the poetry of p sychol ogical descri p ti on of the characters 1The i m ages harbor the writer ’s experience,inter p retati on and understanding of life,and dis p lay the p sychol ogical state of Zhang A iling ’s 1[Key words] Zhang A iling ;novel;i m age gr oup;des olati on [收稿日期] 2007-12-20 [作者简介] 毛灿月(1965-),女,湖南湘乡人,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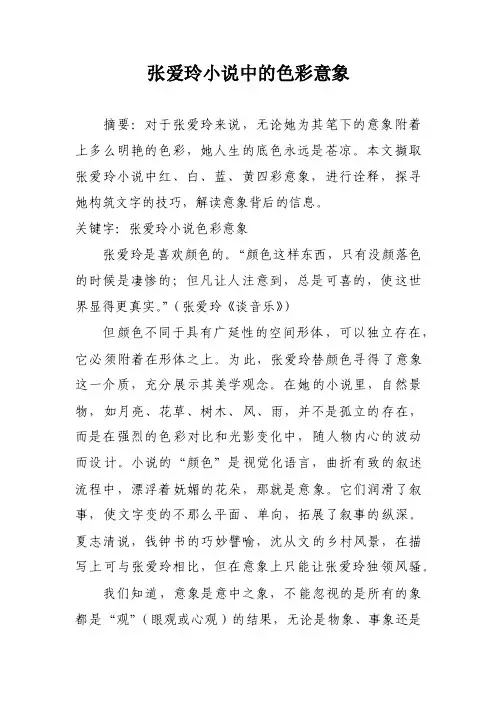
张爱玲小说中的色彩意象摘要:对于张爱玲来说,无论她为其笔下的意象附着上多么明艳的色彩,她人生的底色永远是苍凉。
本文撷取张爱玲小说中红、白、蓝、黄四彩意象,进行诠释,探寻她构筑文字的技巧,解读意象背后的信息。
关键字:张爱玲小说色彩意象张爱玲是喜欢颜色的。
“颜色这样东西,只有没颜落色的时候是凄惨的;但凡让人注意到,总是可喜的,使这世界显得更真实。
”(张爱玲《谈音乐》)但颜色不同于具有广延性的空间形体,可以独立存在,它必须附着在形体之上。
为此,张爱玲替颜色寻得了意象这一介质,充分展示其美学观念。
在她的小说里,自然景物,如月亮、花草、树木、风、雨,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在强烈的色彩对比和光影变化中,随人物内心的波动而设计。
小说的“颜色”是视觉化语言,曲折有致的叙述流程中,漂浮着妩媚的花朵,那就是意象。
它们润滑了叙事,使文字变的不那么平面、单向,拓展了叙事的纵深。
夏志清说,钱钟书的巧妙譬喻,沈从文的乡村风景,在描写上可与张爱玲相比,但在意象上只能让张爱玲独领风骚。
我们知道,意象是意中之象,不能忽视的是所有的象都是“观”(眼观或心观)的结果,无论是物象、事象还是意象,只有“如在目前”,能够“看得见”,才能被称作“象”。
而一个倾向于视觉中心的意象,一方面表现在“色”上,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形”上。
张爱玲小说意象以色附形,将红、黄、白、绿、蓝等色彩自然调和,寻求并把握色彩的冷暖变化和相互作用,突出一种色彩,产生出强烈的视觉效果。
这使她的行文颇似西洋油画,涂涂抹抹,色彩斑斓。
一、红色,摇曳出多彩的人生红色,作为热血、生命、亢奋的表情色,最能体现原始经验意象,有着狩猎、战争、人类繁衍的明显特征,是原始单色崇拜最早最普遍的色彩。
张爱玲的母亲曾教她油画,教导她画图背景最避忌红色,因为背景看上去应有相当距离,红背景总觉近在眼前。
这对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使得她在对背景色彩的处理上,几乎彻底摒弃了红。
但这并不妨碍她将红色作为画面的主色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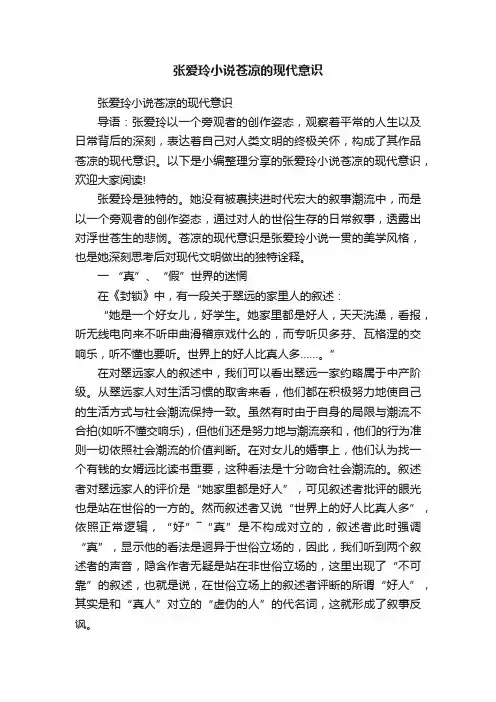
张爱玲小说苍凉的现代意识张爱玲小说苍凉的现代意识导语:张爱玲以一个旁观者的创作姿态,观察着平常的人生以及日常背后的深刻,表达着自己对人类文明的终极关怀,构成了其作品苍凉的现代意识。
以下是小编整理分享的张爱玲小说苍凉的现代意识,欢迎大家阅读!张爱玲是独特的。
她没有被裹挟进时代宏大的叙事潮流中,而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创作姿态,通过对人的世俗生存的日常叙事,透露出对浮世苍生的悲悯。
苍凉的现代意识是张爱玲小说一贯的美学风格,也是她深刻思考后对现代文明做出的独特诠释。
一“真”、“假”世界的迷惘在《封锁》中,有一段关于翠远的家里人的叙述:“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
她家里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
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
”在对翠远家人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翠远一家约略属于中产阶级。
从翠远家人对生活习惯的取舍来看,他们都在积极努力地使自己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潮流保持一致。
虽然有时由于自身的局限与潮流不合拍(如听不懂交响乐),但他们还是努力地与潮流亲和,他们的行为准则一切依照社会潮流的价值判断。
在对女儿的婚事上,他们认为找一个有钱的女婿远比读书重要,这种看法是十分吻合社会潮流的。
叙述者对翠远家人的评价是“她家里都是好人”,可见叙述者批评的眼光也是站在世俗的一方的。
然而叙述者又说“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依照正常逻辑,“好”―“真”是不构成对立的,叙述者此时强调“真”,显示他的看法是迥异于世俗立场的,因此,我们听到两个叙述者的声音,隐含作者无疑是站在非世俗立场的,这里出现了“不可靠”的叙述,也就是说,在世俗立场上的叙述者评断的所谓“好人”,其实是和“真人”对立的“虚伪的人”的代名词,这就形成了叙事反讽。
这篇小说写了封锁前(常态)――封锁(非常态)――封锁解除(常态)三个时间段。
其实,在每个时间段里,都充斥着“真”―“假”的二元对立。
在封锁前、封锁解除的常态时间段里,也就是现实生活世界里,“假”被誉为“好”,得到社会的肯定,人人都争做“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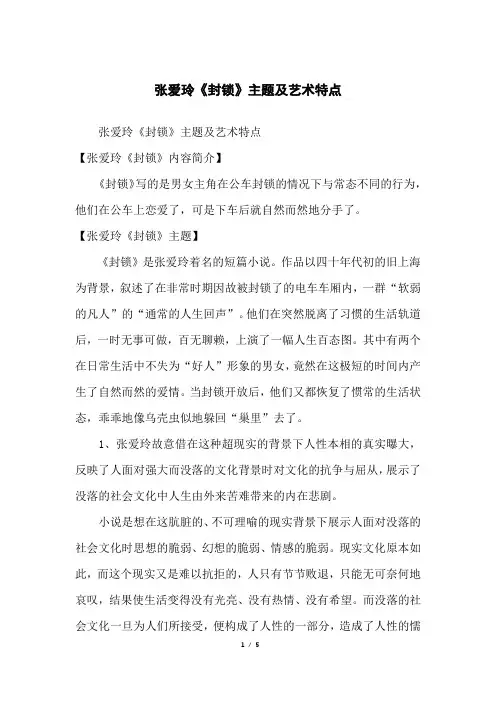
张爱玲《封锁》主题及艺术特点张爱玲《封锁》主题及艺术特点【张爱玲《封锁》内容简介】《封锁》写的是男女主角在公车封锁的情况下与常态不同的行为,他们在公车上恋爱了,可是下车后就自然而然地分手了。
【张爱玲《封锁》主题】《封锁》是张爱玲着名的短篇小说。
作品以四十年代初的旧上海为背景,叙述了在非常时期因故被封锁了的电车车厢内,一群“软弱的凡人”的“通常的人生回声”。
他们在突然脱离了习惯的生活轨道后,一时无事可做,百无聊赖,上演了一幅人生百态图。
其中有两个在日常生活中不失为“好人”形象的男女,竟然在这极短的时间内产生了自然而然的爱情。
当封锁开放后,他们又都恢复了惯常的生活状态,乖乖地像乌壳虫似地躲回“巢里”去了。
1、张爱玲故意借在这种超现实的背景下人性本相的真实曝大,反映了人面对强大而没落的文化背景时对文化的抗争与屈从,展示了没落的社会文化中人生由外来苦难带来的内在悲剧。
小说是想在这肮脏的、不可理喻的现实背景下展示人面对没落的社会文化时思想的脆弱、幻想的脆弱、情感的脆弱。
现实文化原本如此,而这个现实又是难以抗拒的,人只有节节败退,只能无可奈何地哀叹,结果使生活变得没有光亮、没有热情、没有希望。
而没落的社会文化一旦为人们所接受,便构成了人性的一部分,造成了人性的懦弱、卑怯和可笑可怜,他们即使在特殊的环境中偶尔对.生命的真相有所了悟,也不可能长久地停留在这一点上,生活真相的可怕与恐怖是一般人的意识难以负荷的,于是他们只好回到纷扰的现实中去,埋头于眼前的琐事之中。
吕宗祯不愿意进入理性,他没有了封锁的那种环境,就连情欲的一而也没有了。
现实生活中有多少这样的人让真实的人性受环境屈抑着,不敢表现不愿表现,然而他们也不做极恶的坏事,他们软弱虚伪,心中却还是有着真实的挣扎,一且给予他们一个“封锁”的良好大环境,他们仍然能够在外界的冲击下回复到人性的纯真。
封锁限制了人的行动自由,行动停滞了,闪躲在内心深处的欲望恰好借机挣脱束缚,晃了出来,虚伪与真实仅一条虚线之隔。

张爱玲写作风格一、在主题思想上,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内省、孤傲以及都市人的优越感与孤独感交织起来形成她对时代“荒凉”特色的心理感受。
张爱玲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
这与她的身世密不可分的,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
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张爱玲过早的成熟,并形成了她怪异顽强的性格和自立于世的人生态度。
这对其创作心态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
由于她悲凉的家庭经历和特定的生活环境,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由于张爱玲社交范围窄,朋友不多,知心者更少。
她沉默寡语,冷眼审视人生,在这样的创作心态支配下,其笔端写出扭曲的人格,变态的灵魂。
把读者逐步引入她营构的苍凉世界,同时,也展示了其小说独特的艺术美。
在那个“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中”,张爱玲似一颗彗星划下一道美丽的轨道,在浩渺的宇宙瞬间辉煌而过,留下了《传奇》和《流言》,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
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营造了一个阴气森然的世界,男男女女如在鬼蜮进进出出。
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
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
张爱玲的悲剧意识表现在对人性的探索中,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
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触摸到了“人性恶”的一面,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
他们在习俗的挤压下沉沦,精神苍白,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情、互助,哪怕是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妯娌叔嫂;他们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人性变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全是现代社会“病”了的人。
张爱玲的小说几乎全具悲剧和苍凉色彩,而这种苍凉意味的形成,则归功于她对那些颇具悲剧意蕴的典型意象的大量运用,这正如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所言:“凭张爱玲灵敏的头脑和对于感觉快感的爱好,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①张爱玲小说中带有苍凉意味的意象随处可见,如镜、月、风、墙、窗、空房、胡琴等。
而这些众多意象中,最具代表性的可谓“镜”意象。
作为人类的日常用品,镜子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供人自照。
单纯的自照,自然与文学无关。
但照镜的如果是美人,镜子便作为美人的伴侣进入文学——美人照镜;照镜的如果是仁人志士,镜子便作为仁人志士的伴侣进入文学——对镜抒怀;照镜的如果是智者,镜子便成为智者自省的工具。
有时,照镜者爱上了镜中的自我(镜恋);有时,照镜者不认识镜中的自我(昏镜);有时,照镜者分不清镜中之我和对镜之我(变形镜),甚至在镜中看到心灵的影像。
这时,镜子就不仅仅是一件日用品,而是自我的映射。
张爱玲是一个驾驭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作家,在她笔下,古典镜意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取舍与发挥。
一、扭曲变形的魔镜《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想与姑妈的情人乔琪由爱而走向婚姻,但乔琪却是一个如《倾城之恋》中柳原般,不求婚姻只求快乐的浪荡子。
当两人亲吻之后,小说这样写道:她竭力在他的黑眼镜里寻找他的眼睛,可是她只看见眼镜里反映的她自己的影子,缩小的,而且惨白的。
②这里张爱玲非常巧妙地运用了镜子的变形功能。
这种形体的缩小,正说明葛薇龙在乔琪心中地位的卑微和无足轻重。
脸色的惨白,体现了葛薇龙心中的恐慌与失望。
对着这变形的镜子,一股被玩弄后的苍凉之意袭上心头。
如果说上面所说的变形,还与眼镜本身造成的原因相关,它只是介于镜子的写实功能与变形功能之间,那么《金锁记》中七巧对镜的描写,则完全是镜子变形功能的恰好体现。
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
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
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
午夜兰花深度解析午夜兰花深度解析《午夜兰花》是中国作家张爱玲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于1950年开始创作,1957年完成。
小说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背景,通过讲述三位女性角色的命运,展现了社会变革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探讨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困境和选择。
本文将从小说的主要人物塑造、情节安排、意象运用和主题阐述四个方面对《午夜兰花》进行深度解析。
首先,小说的人物塑造是其深入探讨主题的重要手段之一。
小说主要围绕三位女性角色展开,分别是花幽草、幽韵儿和韵竹。
花幽草是一个身世卑微、经历坎坷的女子,她的命运被社会的环境和她自身的选择所左右。
虽然她在感情上曾经历了许多曲折和痛苦,但她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对爱情的执着和追求。
幽韵儿则是一个典型的“新女性”,聪明、独立、追求自由和平等,但她却在婚姻中陷入了痛苦和无奈之中。
韵竹则是一个充满活力、渴望改变命运的女子,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机智最终脱离了家族的束缚。
这三个角色在小说中共同组成了一个多维度的女性形象,展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不同命运和选择。
其次,小说的情节安排精心而巧妙。
整个小说以花幽草的爱情经历为主线,通过回顾的方式展现她的命运。
小说以幽韵儿在某个午夜收到花幽草的来信为序章,同时也是小说的高潮之一。
接着,小说回到花幽草年轻时的经历,讲述她与富家子弟书香、贵族徐和、商业巨头刘家栋之间的关系。
小说通过这些个人命运的交错和碰撞,展现了民国时期上海社会的多样性和变迁。
最后,小说以韵竹的故事作为结尾,通过她的努力和机智,展示了一个女性如何逆袭改变自己命运的过程。
小说的情节安排紧凑而有层次感,吸引读者的眼球。
再次,小说的意象运用也值得注意。
其中最著名的意象就是“午夜兰花”。
兰花是华夏民族的象征,代表高贵和尊贵。
而午夜则是黑暗和不见光明的时刻。
作者通过这个意象,表达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困境和挣扎。
花幽草作为一个普通女子,她的命运就像仅开花的兰花,美丽而短暂,她渴望得到尊贵和尊重,但却始终受到挫折和折磨。
红颜弹指老,长恨歌无尽
——简析《长恨歌》中王琦瑶的爱情《长恨歌》完成于1995年,作者王安忆用近30万字的篇幅,浓缩了上海40年的岁月变迁,也展现了一个女人——王琦瑶40年哀婉动人的情与爱。
作者以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将一段尘封已久,早已被人遗忘的历史生活艺术的再现出来。
王琦瑶是一个典型到极致的上海弄堂女儿。
她爱漂亮,会打扮,有点小虚荣,平日里没事就喜欢幻想。
她美丽却不张扬,有一股天成的气质和风韵,这也就成就了她上海“三小姐”的美誉。
虽说只是“三小姐”,远没有大小姐、二小姐来得光彩艳丽,但是三小姐其实是最体现民意的。
“大小姐二小姐是偶像,是我们的理想和信仰,三小姐却与我们的日常起居有关,是使我们想到婚姻、生活、家庭这类概念的人物。
”(59)
王琦瑶的一生是可以用华丽来形容的。
四十年代,还是中学生的王琦瑶就被选为了“上海小姐”,从此就走上了繁华的上层生活,看尽上海的纸醉金迷。
虽然其后的人生命运多舛,但是在他人眼里,她依旧是那个惹人艳羡的“上海小姐”,即便委身于曲折深长、藏污纳垢的平安里,她也是那些柴米夫妻吵架时作比的对象。
“那女的会说:我不如去做三十九号里的王琦瑶!男的就嘲笑道:你去做呀,你有那本事吗?”她的一生就像张爱玲曾说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
(197)
但是张爱玲也说过这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
没有谁
的人生可以用完美来形容,在王琦瑶看似风光无限的外表下面,实际上是一段暗淡无光的人生。
她的一生都被一个“情”字所围困。
王琦瑶是不缺乏爱情的,她的身边总是不乏追求者,在她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有一个看似可以白头偕老的男人,但是终究也还是没有一个男人可以给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李主任是在“上海小姐”的决赛上认识王琦瑶的。
这样一位军政界的大人物,走过许多地方,也见过了各地的女人,而这次却单单对这位十几岁的小姑娘动了心。
王琦瑶打动他不仅仅是因为那娇媚的面庞,而是王琦瑶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的稍显稚嫩的羞涩,让这个四十岁的男人心生怜惜,在他的眼里王琦瑶更像是个孩子。
王琦瑶最初也不是爱他的,只是他的生命中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男人,让她有点心生畏惧,但是又有点兴奋。
深知这个男人不可能给她一段平静的生活,但是那个年纪的女生谁没点向往与憧憬,于是也就这样深深地陷进去了。
本以为自己一生就这样在“爱丽丝”的温柔富贵乡里度过的王琦瑶,怎么也不会想到那绵延无情的战火会烧掉她安身立命的梦想。
一九四八年的春天王琦瑶搬进爱丽丝公寓,一九四八年的深秋李主任死于飞机失事。
阿二是王琦瑶在邬桥避乱认识的。
阿二是邬桥的孤独者,他看不起邬桥一事一物,自觉地将邬桥与自己划分开来,发誓要走出邬桥,到大世界里去闯荡一番。
阿二初见王琦瑶就被王琦瑶所吸引,但是吸引他的不是王琦瑶自身,而是王琦瑶身上所带有的那种上海繁华梦的景象。
在阿二的眼里王琦瑶就像是他的影子,是他那个未完成的梦。
他对王琦瑶的向往,可能有爱的成分,但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膜拜。
而王琦瑶也只是把阿二的心当成少年之心来领会。
虽然此时的王琦瑶比起阿二来说不算老,但是在经历了李主任这件事后,王琦瑶的心远比外表来的苍老。
阿二在王琦瑶的生命中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他缓解了王琦瑶在避乱时荒凉孤寂的心,也再一次勾起了王琦瑶对上海的思念。
毛毛娘舅,也就是康明逊,是书中最应该给王琦瑶一个家的男子。
在我看来,他也是王琦瑶唯一真心喜欢的男子,“是王琦瑶心里那一半明,也是那一半晦,虽是不敢想,却还是要去想。
”(165)王琦瑶在听完严家师母叙述康明逊小时候当伴童的故事,去想象他穿西装的样子,“竟有些怦然心动”。
(145)这是王琦瑶第一次主动对一个男人动心。
在康明逊的眼里,王琦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
她简单朴实的装扮下蕴藏着一段凄艳的历史,难以被人猜透。
正是因为这种美丽与那些难以被人猜透的历史,深深地吸引了康明逊。
在亲戚朋友的眼里康明逊是个极乖顺的孩子,周旋于大妈二妈之间,为姐姐妹妹跑前跑后。
但是康明逊的内心又是极度压抑的,他是家中唯一的男丁,虽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是又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地做人,他需要一个人来听他倾诉,而王琦瑶正是这样一个人。
康明逊和王琦瑶之间的爱情就像是在“捉迷藏”,你来我往,既怕捉,又怕不来捉。
王琦瑶知道自己的身份与经历是不配与康明逊在一起的,也知道必然会遭到康明逊家里人的反对。
康明逊也知道,“王
琦瑶再美丽,再迎合他的旧情,再拾回他遗落的心,到头来,终究是个泡影。
”(171)但是爱情这个东西,不是“明知道”就可以“不能为”的,纵使康明逊对王琦瑶说出“我没有办法”,王琦瑶也只是说“我求的是你的心”。
在知晓康明逊内心的压力和抑郁之后,王琦瑶更是对他心生怜惜,所以王琦瑶在知道自己怀孕以后,毅然决然就决定去医院打掉,并且坚持不要康明逊陪她一起去。
为了她爱的这个男人,王琦瑶是什么都愿意做的。
他们之间不仅是爱,还是体恤。
萨沙与王琦瑶之间本可以只是下午茶上的一个朋友,但是因为康明逊,王琦瑶不得不牺牲他。
王琦瑶初识萨沙是非常不喜欢他的,自以为是,傲慢,刁钻,再加上康明逊对他万般迁就,萨沙就像个上海小瘪三。
其实萨沙是很可怜的,虽说是革命的混血儿,但也正是因为这种血缘冲突让他在人群中显得特立独行,总是惹来人群中好奇的目光,其实他更像是这个城市的流浪者。
萨沙对女人,是当做衣食父母那么来喜欢的。
但他的内心又是恨女人的,因为透过女人,他看出了自己的无能。
对于王琦瑶,萨沙是将她当做许多喜欢他的女人中的一个。
因此当王琦瑶主动向他示好时,他竟当作了理所应当。
王琦瑶最初找萨沙当“替罪羔羊”时,内心是有不忍的,可是当看到萨沙内心的可怕时,王琦瑶在内心里认定了找他来承担这件事是对了。
萨沙是书里很无辜的一个男人。
他很无赖,但是他的无赖是因为他那略带凄凉的身世,他只是以这种无赖的方式隐藏自己内心的软弱。
当最终王琦瑶咬定他时,他终于崩溃了,“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如此的委屈却无处哀告,最终只能选择远走他乡。
程先生与王琦瑶是命里的有缘无分。
他给王琦瑶拍的照片,也是他把照片推荐给《沪上名媛》杂志。
在王琦瑶竞选“上海小姐”时也是他尽心尽力的出主意,是他一手将王琦瑶推向了人生的最高峰。
他爱王琦瑶,却不知道怎么表达,而王琦瑶也只是对他“不承诺”。
因为不承诺,以此减轻内心的罪孽感。
与程先生故人重逢时,王琦瑶怀着身孕在黑市典当衣物。
这是的王琦瑶看起来有点狼狈,但丝毫不影响她在程先生心目中的感觉,反而这种久别重逢更加深了程先生对王琦瑶的感情。
“程先生与王琦瑶的再度相遇,是以吃为主。
这吃不是那吃,这吃是饱腹的,不像以往同严师母几个的下午茶和夜宵,全是消磨时光。
”(196)程先生照顾王琦瑶依旧像以前那样无怨无悔,不求回报,王琦瑶不说他也不说。
而这时的王琦瑶对程先生是充满感恩的,曾想晚上留他在这过夜,但却又怕程先生嫌弃她。
这样的想法里没有欲望和爱,只是单纯的想报恩。
本以为两人就可以这样糊涂下去,但终究是敌不过现实,当程先生知道孩子的亲生父亲时,还是难以掩盖内心的委屈,这种委屈让他难以再去面对王琦瑶,于是选择了不告而别。
老克腊与王琦瑶的爱情被人称为“畸恋”,而我更愿意称之为“忘年恋”。
老克腊初见王琦瑶是在一次年青年人的聚会上,那时老克腊早已对这位“上海小姐”的名字如雷贯耳。
老克腊热爱怀旧,王琦瑶就是那段历史。
两个人在激烈的迪斯科音乐下跳着四步,他们是舞池中的异类,他们处在这个时代之外的孤岛。
其实对于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我很难用爱情去定义。
王琦瑶更像是把老克腊当做一个孩子一
般在疼爱,就像当初李主任对她一般;而老克腊最初是被王琦瑶的身上的历史感所吸引,越接近越了解这个女人的委屈和体谅,于是就滋生出一种同情。
“他其实有些把王琦瑶当成了好莱坞电影的女主角了,他倒并不充当男主角,当的是忠诚的观众,将戏剧当人生的那类观众。
”(300)因此注定他们的爱情是无果的,但是这次王琦瑶却是看不开了,硬是想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甚至不惜用金钱留住他,但是爱情不是用金钱就可以换来的,会离开的还是会离开的。
王琦瑶的心一次次被交付出去,一次次的被撩拨起来,可往往是“情”才刚刚开始就结束了。
与李主任共眠的那些夜晚,与李主任的那些生离死别,在王琦瑶的记忆里渐渐模糊,留给她的仅是那个西班牙风雕花的木盒,但是这个盒子最终也让她死于非命;与康明逊虽有爱情的结晶,但最终两人也只能以老熟人相称,你知我,我知你,却是桥归桥,路归路。
其他的几个人也终归只是王琦瑶生命里的过客。
爱情于她是可望不可即的,爱情于她更像是一件奢侈品,她和多个男人的爱情不是时间不对,就是人不对。
“呼唤人的和被呼唤的,很少能互相答应;恋爱的人和恋爱的时机,也不容易凑巧相合”(哈代.德伯家的苔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60),男女之缘往往只是“半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