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曼和哈贝马斯的争论
- 格式:wps
- 大小:11.50 KB
- 文档页数: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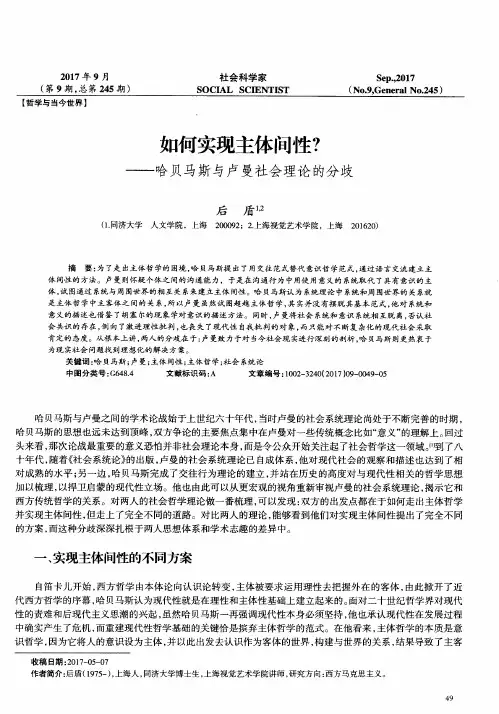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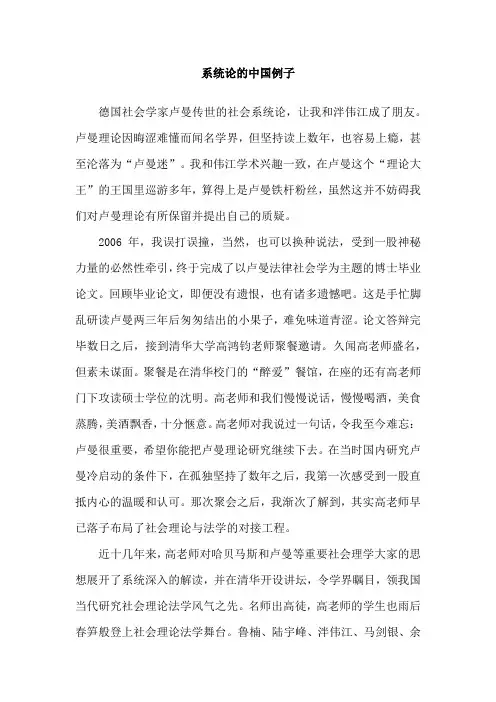
系统论的中国例子德国社会学家卢曼传世的社会系统论,让我和泮伟江成了朋友。
卢曼理论因晦涩难懂而闻名学界,但坚持读上数年,也容易上瘾,甚至沦落为“卢曼迷”。
我和伟江学术兴趣一致,在卢曼这个“理论大王”的王国里巡游多年,算得上是卢曼铁杆粉丝,虽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卢曼理论有所保留并提出自己的质疑。
2006年,我误打误撞,当然,也可以换种说法,受到一股神秘力量的必然性牵引,终于完成了以卢曼法律社会学为主题的博士毕业论文。
回顾毕业论文,即便没有遗恨,也有诸多遗憾吧。
这是手忙脚乱研读卢曼两三年后匆匆结出的小果子,难免味道青涩。
论文答辩完毕数日之后,接到清华大学高鸿钧老师聚餐邀请。
久闻高老师盛名,但素未谋面。
聚餐是在清华校门的“醉爱”餐馆,在座的还有高老师门下攻读硕士学位的沈明。
高老师和我们慢慢说话,慢慢喝酒,美食蒸腾,美酒飘香,十分惬意。
高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令我至今难忘:卢曼很重要,希望你能把卢曼理论研究继续下去。
在当时国内研究卢曼冷启动的条件下,在孤独坚持了数年之后,我第一次感受到一股直抵内心的温暖和认可。
那次聚会之后,我渐次了解到,其实高老师早已落子布局了社会理论与法学的对接工程。
近十几年来,高老师对哈贝马斯和卢曼等重要社会理学大家的思想展开了系统深入的解读,并在清华开设讲坛,令学界瞩目,领我国当代研究社会理论法学风气之先。
名师出高徒,高老师的学生也雨后春笋般登上社会理论法学舞台。
鲁楠、陆宇峰、泮伟江、马剑银、余盛峰、张文龙、杨静哲等青年才俊,个个身手不凡,圈内一时异彩纷呈。
其中,泮伟江专精卢曼理论,对卢曼的系统论法学用功最勤,感情最深,切入最透彻。
我几乎不与人私下聊学术,聊得更多的是学术八卦。
但与伟江的交往是个例外。
相隔京沪之远,除了开会,我与伟江见面并不多。
每每抓住机会,就会向他刺探学术情报。
我有所问,他必爽快答。
有一回他讲,正在翻译卢曼的《社会的社会》和《社会的政治》,并谈到了翻译进度,也坦承遇到的麻烦,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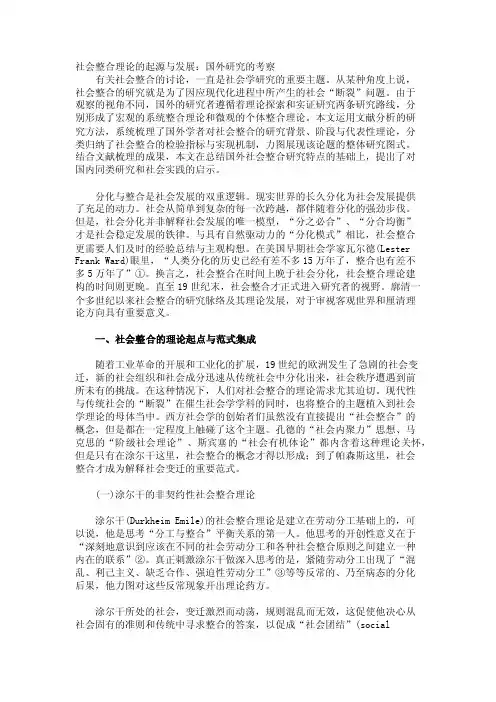
社会整合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国外研究的考察有关社会整合的讨论,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
从某种角度上说,社会整合的研究就是为了因应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断裂”问题。
由于观察的视角不同,国外的研究者遵循着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两条研究路线,分别形成了宏观的系统整合理论和微观的个体整合理论。
本文运用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系统梳理了国外学者对社会整合的研究背景、阶段与代表性理论,分类归纳了社会整合的检验指标与实现机制,力图展现该论题的整体研究图式。
结合文献梳理的成果,本文在总结国外社会整合研究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国内同类研究和社会实践的启示。
分化与整合是社会发展的双重逻辑。
现实世界的长久分化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的每一次跨越,都伴随着分化的强劲步伐。
但是,社会分化并非解释社会发展的唯一模型,“分之必合”、“分合均衡”才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铁律。
与具有自然驱动力的“分化模式”相比,社会整合更需要人们及时的经验总结与主观构想。
在美国早期社会学家瓦尔德(Lester Frank Ward)眼里,“人类分化的历史已经有差不多15万年了,整合也有差不多5万年了”①。
换言之,社会整合在时间上晚于社会分化,社会整合理论建构的时间则更晚。
直至19世纪末,社会整合才正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廓清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整合的研究脉络及其理论发展,对于审视客观世界和厘清理论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整合的理论起点与范式集成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和工业化的扩展,19世纪的欧洲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变迁,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分迅速从传统社会中分化出来,社会秩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社会整合的理论需求尤其迫切。
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的“断裂”在催生社会学学科的同时,也将整合的主题植入到社会学理论的母体当中。
西方社会学的创始者们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社会整合”的概念,但是都在一定程度上触碰了这个主题。
孔德的“社会内聚力”思想、马克思的“阶级社会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都内含着这种理论关怀,但是只有在涂尔干这里,社会整合的概念才得以形成;到了帕森斯这里,社会整合才成为解释社会变迁的重要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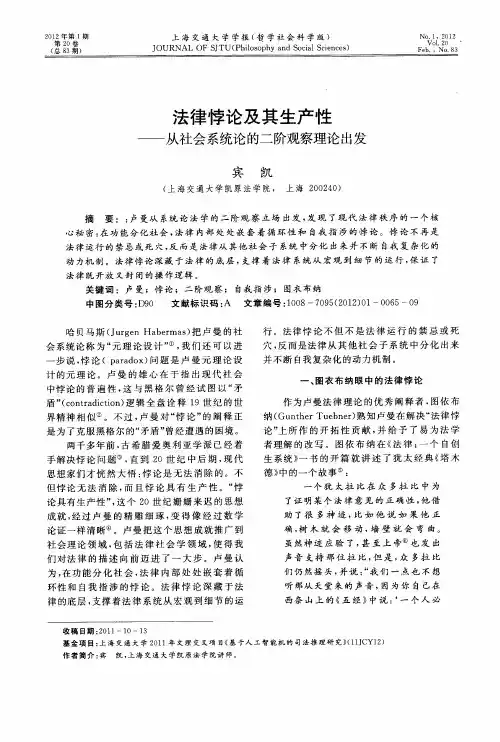
2012年第1期第20卷(总83期)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 O U R N A I。
O F SJTU(P hi l os ophy and Soc i al Sci en ces)N o.1,2012V01.20F e b.,N o.83法律悖论及其生产性——从社会系统论的二阶观察理论出发宾凯(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上海200240)摘要::卢曼从系统论法学的二阶观察立场出发,发现了现代法律秩序的一个核心秘密:在功能分化社会,法律内部处处嵌套着循环性和自我指涉的悖论。
悖论不再是法律运行的禁忌或死穴,反而是法律从其他社会子系统中分化出来并不断自我复杂化的动力机制。
法律悖论深藏于法律的底层,支撑着法律系统从宏观到细节的运行,保证了法律既开放又封闭的操作逻辑。
关键词:卢曼;悖论;二阶观察;自我指涉;图衣布纳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095(2012)01—0065—09哈贝马斯(J ur gen H aber m as)把卢曼的社会系统论称为“元理论设计”∞,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悖论(par adox)问题是卢曼元理论设计的元理论。
卢曼的雄心在于指出现代社会中悖论的普遍性,这与黑格尔曾经试图以“矛盾”(c ont r adi ct i on)逻辑全盘诠释19世纪的世界精神相似②。
不过,卢曼对“悖论”的阐释正是为了克服黑格尔的“矛盾”曾经遭遇的困境。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爱奥利亚学派已经着手解决悖论问题③,直到20世纪中后期,现代思想家们才恍然大悟:悖论是无法消除的。
不但悖论无法消除,而且悖论具有生产性。
“悖论具有生产性”,这个20世纪姗姗来迟的思想成就,经过卢曼的精雕细琢,变得像经过数学论证一样清晰④。
卢曼把这个思想成就推广到社会理论领域,包括法律社会学领域,使得我们对法律的描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卢曼认为,在功能分化社会,法律内部处处嵌套着循环性和自我指涉的悖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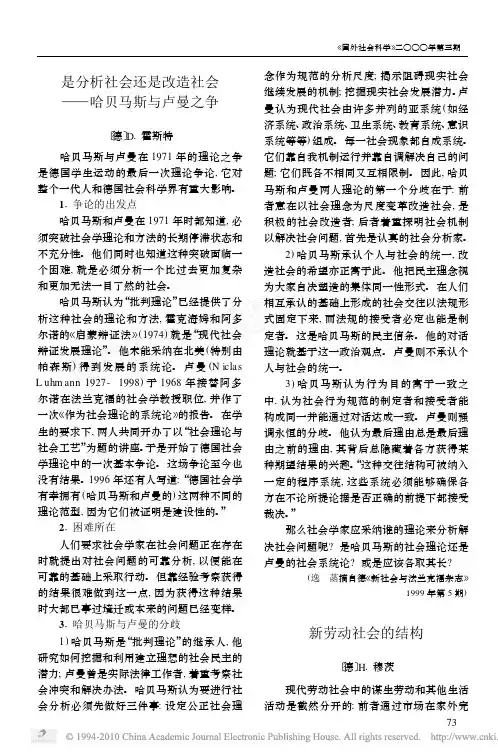
是分析社会还是改造社会——哈贝马斯与卢曼之争〔德〕D.霍斯特 哈贝马斯与卢曼在1971年的理论之争是德国学生运动的最后一次理论争论,它对整个一代人和德国社会科学界有重大影响。
11争论的出发点哈贝马斯和卢曼在1971年时都知道,必须突破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长期停滞状态和不充分性。
他们同时也知道这种突破面临一个困难,就是必须分析一个比过去更加复杂和更加无法一目了然的社会。
哈贝马斯认为“批判理论”已经提供了分析这种社会的理论和方法,霍克海姆和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1974)就是“现代社会辩证发展理论”。
他未能采纳在北美(特别由帕森斯)得到发展的系统论。
卢曼(N iclas L uhm ann1927-1998)于1968年接替阿多尔诺在法兰克福的社会学教授职位,并作了一次《作为社会理论的系统论》的报告。
在学生的要求下,两人共同开办了以“社会理论与社会工艺”为题的讲座。
于是开始了德国社会学理论中的一次基本争论。
这场争论至今也没有结果。
1996年还有人写道:“德国社会学有幸拥有(哈贝马斯和卢曼的)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型,因为它们被证明是建设性的。
”21困难所在人们要求社会学家在社会问题正在存在时就提出对社会问题的可靠分析,以便能在可靠的基础上采取行动。
但靠经验考察获得的结果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获得这种结果时大都已事过境迁或本来的问题已经变样。
31哈贝马斯与卢曼的分歧1)哈贝马斯是“批判理论”的继承人,他研究如何挖掘和利用建立理想的社会民主的潜力;卢曼曾是实际法律工作者,着重考察社会冲突和解决办法。
哈贝马斯认为要进行社会分析必须先做好三件事:设定公正社会理念作为规范的分析尺度;揭示阻碍现实社会继续发展的机制;挖掘现实社会发展潜力。
卢曼认为现代社会由许多并列的亚系统(如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卫生系统、教育系统、意识系统等等)组成。
每一社会现象都自成系统。
它们靠自我机制运行并靠自调解决自己的问题;它们既各不相同又互相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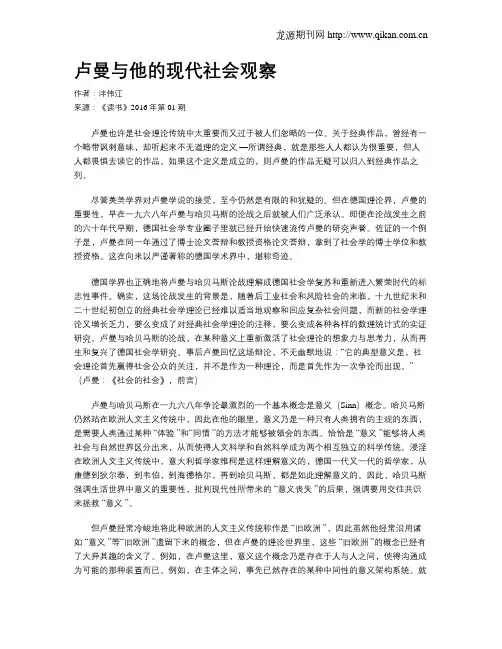
卢曼与他的现代社会观察作者:泮伟江来源:《读书》2016年第01期卢曼也许是社会理论传统中太重要而又过于被人们忽略的一位。
关于经典作品,曾经有一个略带讽刺意味,却听起来不无道理的定义—所谓经典,就是那些人人都认为很重要,但人人都畏惧去读它的作品。
如果这个定义是成立的,则卢曼的作品无疑可以归入到经典作品之列。
尽管英美学界对卢曼学说的接受,至今仍然是有限的和犹疑的。
但在德国理论界,卢曼的重要性,早在一九六八年卢曼与哈贝马斯的论战之后就被人们广泛承认。
即便在论战发生之前的六十年代早期,德国社会学专业圈子里就已经开始快速流传卢曼的研究声誉。
佐证的一个例子是,卢曼在同一年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和教授资格论文答辩,拿到了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和教授资格。
这在向来以严谨著称的德国学术界中,堪称奇迹。
德国学界也正确地将卢曼与哈贝马斯论战理解成德国社会学复苏和重新进入繁荣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确实,这场论战发生的背景是,随着后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来临,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创立的经典社会学理论已经难以适当地观察和回应复杂社会问题,而新的社会学理论又增长乏力,要么变成了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注释,要么变成各种各样的数理统计式的实证研究。
卢曼与哈贝马斯的论战,在某种意义上重新激活了社会理论的想象力与思考力,从而再生和复兴了德国社会学研究。
事后卢曼回忆这场辩论,不无幽默地说:“它的典型意义是,社会理论首先赢得社会公众的关注,并不是作为一种理论,而是首先作为一次争论而出现。
”(卢曼:《社会的社会》,前言)卢曼与哈贝马斯在一九六八年争论最激烈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意义(Sinn)概念。
哈贝马斯仍然站在欧洲人文主义传统中,因此在他的眼里,意义乃是一种只有人类拥有的主观的东西,是需要人类通过某种“体验”和“同情”的方法才能够被领会的东西。
恰恰是“意义”能够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区分出来,从而使得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成为两个相互独立的科学传统。
浸淫在欧洲人文主义传统中,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是这样理解意义的,德国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从康德到狄尔泰,到韦伯,到海德格尔,再到哈贝马斯,都是如此理解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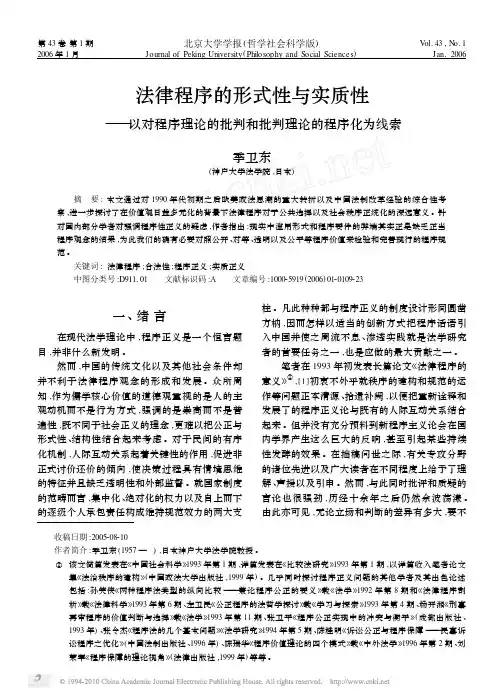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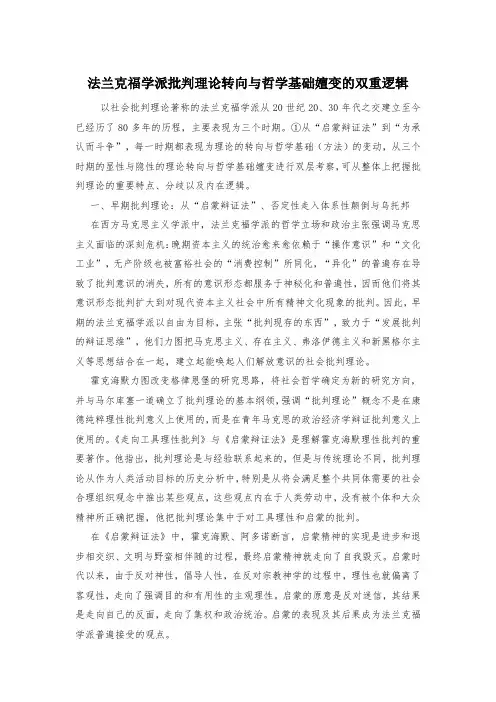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转向与哲学基础嬗变的双重逻辑以社会批判理论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从20世纪20、30年代之交建立至今已经历了80多年的历程,主要表现为三个时期。
①从“启蒙辩证法”到“为承认而斗争”,每一时期都表现为理论的转向与哲学基础(方法)的变动,从三个时期的显性与隐性的理论转向与哲学基础嬗变进行双层考察,可从整体上把握批判理论的重要特点、分歧以及内在逻辑。
一、早期批判理论:从“启蒙辩证法”、否定性走入体系性颠倒与乌托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立场和政治主张强调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深刻危机: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愈来愈依赖于“操作意识”和“文化工业”,无产阶级也被富裕社会的“消费控制”所同化,“异化”的普遍存在导致了批判意识的消失,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服务于神秘化和普遍性,因而他们将其意识形态批判扩大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精神文化现象的批判。
因此,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以自由为目标,主张“批判现存的东西”,致力于“发展批判的辩证思维”,他们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等思想结合在一起,建立起能唤起人们解放意识的社会批判理论。
霍克海默力图改变格律恩堡的研究思路,将社会哲学确定为新的研究方向,并与马尔库塞一道确立了批判理论的基本纲领,强调“批判理论”概念不是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在青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辩证批判意义上使用的。
《走向工具理性批判》与《启蒙辩证法》是理解霍克海默理性批判的重要著作。
他指出,批判理论是与经验联系起来的,但是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从作为人类活动目标的历史分析中,特别是从将会满足整个共同体需要的社会合理组织观念中推出某些观点,这些观点内在于人类劳动中,没有被个体和大众精神所正确把握,他把批判理论集中于对工具理性和启蒙的批判。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阿多诺断言,启蒙精神的实现是进步和退步相交织、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过程,最终启蒙精神就走向了自我毁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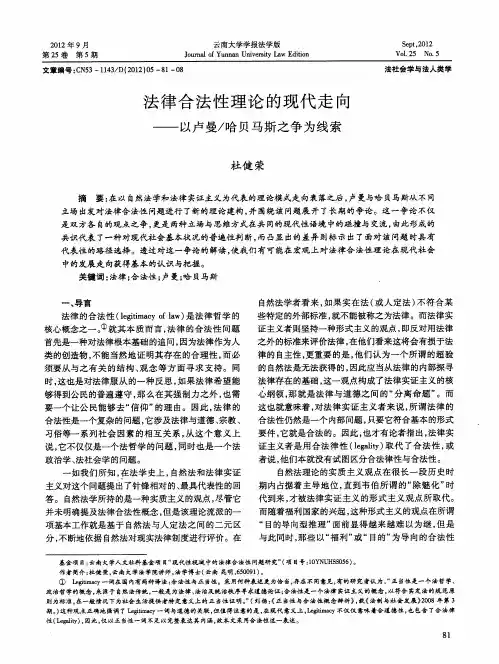
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 1927-1998)是当代德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是一位博学的、活跃的、入世的学者,其研究触角遍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宗教学、艺术理论、生态学、科学理论等诸多学科领域。
他提出的“社会系统理论”以其思辨、抽象特点著称,同时也体现了对于生活世界和社会问题的深切感悟。
这一理论不仅引发了社会学界的热烈讨论,而且受到哲学界的广泛关注,他曾与哈贝马斯就这一理论进行过争论并联名出版了反映这场争论的文集《社会的理论或社会技术——系统研究提供了什么?》(1971)。
但迄今为止卢曼的主要著作还没有中译本问世。
从2000年开始,我们组织翻译了一批卢曼的著作,这里选择其中《社会诸系统》、《社会的法律》、《社会的经济》的部分内容率先发表,以飨读者。
为使大家更多地了解卢曼,本专栏对他的基本情况和学术观点作简要介绍,并将《社会的社会》内容梗概在本专栏中一并刊出。
相信对卢曼著述的译介将会为我国当今的社会哲学研究提供新的助力。
——摘自《卢曼专栏》“主持人的话”一1927年12月8日,尼可拉斯·卢曼降生在德国西北部小城吕内堡(Lüneburg)一个啤酒厂主家庭。
1944年,17岁的卢曼在动荡的战争环境下中断学业,应征到空军服役。
1945年被美军俘虏,度过一段战俘营生活。
战争结束后重获自由,于1946年到弗莱堡大学学习法学并接受预备行政官员培训。
1949年毕业,在汉诺威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工作。
1952-1953年开始建立他著名的“卡片箱”,这是卢曼做学问的独特方式,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引证收集在卡片箱中的文献,使各种文本之间形成一种无言的对话,体现出他的对比研究的风格。
1954年在吕内堡高级法院任职。
1955-1962年就职于下萨克森州文化教育部,从事法务及公共行政工作。
卢曼的仕途是平坦的,几年功夫已经成为州议会参议员,但强烈的学术兴趣很快就把他引向了另外一条生活道路。
卢曼的后人文主义式媒介系统论许栋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420)摘要:作为系统论社会思想家,卢曼基于“差异即沟通”的定位来理解广义、一般的媒介,并阐发了媒介本身作为"自创生”系统的运作原理,在此基础上解析沟通媒介的社会意义,并考察作为技术性传播系统的大众媒体运作问题。
从人与媒介的系统性关系来看,卢曼的媒介-沟通-传播思想包含着去人化、将人视为系统运作而非独立自主个体、强调差异而非理性沟通的观念,是一种后人文主义式的媒介系统论。
关键词:卢曼媒介自创生系统论后人文主义媒介(media)本质上即为传播/沟通/交往(communication)之中介、载体或渠道、场域,是作为事物相互之"间性"(inter-ness)的具身存在,是社会系统构成不可或缺的枢纽环节。
在媒介研究中,以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等为代表的北美媒介生态-环境学,在广义媒介层面,将作为社会环境系统的媒介进行了富于洞见的阐释;而欧洲大陆以弗雷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A. Kittier)等为代表的媒介思想家,则更主要从技术维度,考察媒介之于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及话语形态的建构作用。
同样进行一种广义的媒介研究,与这两种路径皆不相同,德国当代著名社会思想家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在更广义且更基础的层面,也在相当抽象的维度上来谈论媒介;既以“系统”来替代“生态/环境”,也以此为视域来探讨媒介技术问题。
卢曼从社会系统视角出发,将沟通/交往/传播中的中介物或环节乃至中间地带,都视为"媒介”,进而剖析媒介作为社会系统性运作的沟通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论述社会沟通媒介和大众媒体问题。
与麦克卢汉强调媒介作为"人的延伸”和基特勒认为媒介决定了"人的状况"不同,卢曼的系统论媒介观呈现出一种激进的"去人化”的立场,具有鲜明的后人文主义意涵。
试论从本体论到差异论的建构引言早在20 世纪80 年代初期,卢曼就指出了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缺陷: 社会学缺少足够的自己的理论,也即缺少出色的感知装置,以至于它发现不了近几十年来跨学科的运动中对它的发展具有特定意义的内容和结果,感知不到这些运动在以特殊的方式挑战社会学。
他认为,一般来说,一个专业在理论上的封闭性和坚实性与跨专业的开放性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它们处于一种互相提升的关系中。
在他看来,帕森斯的理论就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范例。
作为古典社会学以后唯一的一位社会学理论家,帕森斯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方案,借此,他得以接受来自控制论以及其他学科的刺激。
除了理论短缺以外,卢曼认为,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导致社会学走不出固有的思考范式即从人出发进行思考,不能通过接受其他学科的研究结果而做出创新。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学与社会的合谋: 社会不停地要求社会学在自己为自己所描绘的图象上添彩加色,也即生产出能够被日常的语言世界所认可的理论; 而出于多种动机,社会学也在试图不停地满足这一要求。
这样,通过对社会关心的一些主题如技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现象的研究,社会学提出了一些公式用以说明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不利处境,而这一点恰恰能够唤起很多人的同感。
但是,卢曼认为,这种理论短缺虽然被热情和人性感所平衡,但这种平衡的后果却是,社会学无法感知来自跨专业运动的刺激,长时期处于驻足不前的状态。
对本体论的认识论的批判与韦伯的观点相似,卢曼认为,只有旧欧洲的传统即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教的思想产物促进和陪随过现代社会的产生,并且至今还在影响针对这一社会的期待。
但是,他强调,孕育了这一思想传统的社会其独特的沟通方式和分化形式已不再存在,所以,虽然这一传统仍然是欧洲历史流传的组成部分,并且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但它已显然不合时宜,实际上在不停地被否认。
卢曼认为,旧欧洲传统中具有支配地位的世界观可以用本体论概念加以描写。
而本体论具有两个根本缺陷: 一是它将认识的前提设想为事实,这种设想与物理学或自然论的设想相似,可以被称为形而上学。
Rethinking of Norm and Normativity 作者: 章永乐[1]
作者机构: [1]不详
出版物刊名: 中外法学
页码: 5-6页
年卷期: 2019年 第1期
主题词: 编者按;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系统论;60年代;20世纪;理论学派;法兰克福
摘要:20世纪60年代,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学派的继承人哈贝马斯与系统论的代表者卢曼曾经有过一场引人瞩目的争论。
哈贝马斯致力于探寻促进人的解放的社会秩序,他批判西方工业社会出现了“系统”对“生活世界”进行“殖民”的现象。
法律原本应当立足于“生活世界”,抵制“系统”的“殖民”,但在现实中却成为“殖民”的工具,而这就带来其自身正当性(legitimacy)的流失。
在哈贝马斯看来,从帕森斯到卢曼的系统理论具有很强的保守现状的色彩,缺乏批判的力量。
观察现代性*———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新视野肖文明提要:本文对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研讨凸显了卢曼超越主体哲学的反人本主义和非规范取向的理论建构特点,勾勒了社会系统理论所带来的范式转换之诸种面向。
本文随后介绍了社会系统理论对我们重新理解社会与个人以及诸实质议题所提供的新视角,强调了卢曼坚持系统理性和功能分化的立场,并对该立场提出了批评。
本文认为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为我们观察和理解现代性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理论话语和视角。
关键词:自我再制系统 沟通 系统理性 功能分化一、导 言美国学者斯蒂芬·塞德曼在回顾社会理论的历史时曾指出,社会理论对现代性之命运的讨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千禧年的主题,高歌并坚信人类理性年代的到来和人类社会的持久进步;另一类则是启示录主题,它以悲观的论调描绘出一个灰暗阴沉的未来,只是带着一丝绝望的希望等待先知的来临①(Seidman,1990)。
由此观照,德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就显得有些特别,因为我们很难轻易地将其理论纳入上述任何一类主题。
一方面,他承认无法否认现代社会所遭遇的风险乃至危机,而社会学正应承担起认识风险危险的使命(Kneer&Nassehi,1998);他的进化理论也并不支持任何社会永久进*本文是北京大学方文教授主持的200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社会转型:转型心理学的路径》(项目批准号:08BSH063)的部分中期成果。
本文写作首先要感谢导师陈海文教授的悉心教诲,也得益于方文、李康、秦明瑞、陶林等诸位师长建设性的评论,还要特别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吴欢小姐在我于外地修改本文期间不辞辛劳地帮我数次查找和邮寄资料。
当然,文责仍由笔者自负。
① 雅斯贝斯也指出19世纪后的时代意识分化为两支,而这两支具体内容大体同于塞德曼的说法(雅斯贝斯,2003)。
社会学研究 2008.5步的迷思。
由此来说,他并不怀抱一种千禧年的企盼和信念。
哈贝马斯:论卢曼的系统理论对主体哲学遗产的接受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卢曼(Niklas Luhmann)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普通社会理论的“基本轮廓”。
而且,他还用这种社会理论对几十年来不断跨越不同领域的理论扩张进行了清算,让我们对他的计划有了清楚的了解。
人们总是会认为自己能更好地理解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卢曼的研究与其说是想和从孔德到帕森斯的社会理论专业传统联系起来,不如说是想延续从康德到胡塞尔的意识哲学问题史。
他的系统理论并没有让社会学走上科学的康庄大道,相反,它把自己表现为一个被弃哲学的继承者。
它力图继承主体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提问方式,同时又想超越主体哲学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样,它就完成了一种研究视角的转向,使自我分裂的现代性的自我批判失去了对象。
运用在自身当中的社会系统理论,对不断复杂化的现代社会只能采取一种肯定的态度。
而我所关注的是,卢曼从一定的距离出发,对主体哲学的遗产重新进行了研究,那么,立遗嘱者(主体哲学)所面对的问题是不是会进入系统理论呢?我们知道,自黑格尔死后,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对作为现代性原则的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广泛怀疑。
1系统概念是在控制论和生物学语境中发展起来的。
我们如果想在同等水平上用它来取代从笛卡尔到康德的认知主体概念,我们就必须对系统概念重新进行定义。
具体内容如下:系统-周围世界-关系(System-Umwelt-Beziehung)取代了认知主体与(作为可以认识的对象总体性的)世界之间的内外关系。
对于主体的意识活动而言,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构成了核心问题。
但现在,这一问题要让位于如何维持和扩展系统的问题。
系统的自我关涉性是按照主体的自我关涉性模式建立起来的。
系统如果不与自身建立起联系,并通过反思为自身提供保障,就无法与其他系统建立联系。
但系统的“自我”有别于主体的“自我”,因为它并未凝聚成为统觉意义上“我思”的“自我”,按照康德的说法,这种我思的“自我”必然会伴随着我的一切想象。
要了解卢曼与哈贝马斯之争,考察其各自的人生履历和师承关系是一个有趣的切入点。
卢曼是美国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帕森斯的学生,而帕森斯则是第一个将马克斯•韦伯的作品译介到美国的学者。
与卢曼不同,哈贝马斯则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当代传人,而“批判理论”的思想源头可追溯至马克思。
卢曼早年曾经担任政府公务员,而哈贝马斯则做过短时间的记者。
从这个意义上讲,来自政治系统、弃官从学的卢曼夹带着马克斯•韦伯的“价值无涉”和对现代性的悲观立场,与来自公共领域、立意接续现代性香火的哈贝马斯碰撞到了一起。
这种碰撞所引燃的思想烈火注定要照亮法学理论的琐碎争论所带来的昏暗。
比起当代后现代潮流中纷繁复杂的社会学主分支的碎片化解释中,卢曼思考的出发点显得更为坚实。
卢曼看到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当代社会是一个在规模和复杂性上都无比繁复的时代,社会已经不仅是能够用“分割”或“分层”来解释的,而是一个不断进行“功能分化”的时代,其背后的根据就在于社会复杂性的持续增长和级数级增长。
卢曼吸取了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教训,将“结构——功能”的逻辑关系倒转了过来:社会的形成并非因结构分配了功能,而是在功能的需求上逐渐凝聚出结构。
在他的系统论功能主义看来,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根源于一种日益明晰的功能分化形式。
卢曼之社会系统理论的基本因素在于沟通。
在卢曼看来,网络的自我再制是那些被界定为统一体的系统,界定为构成要素的生产网络(network)的系统,这些构成要素透过它们的互动往复地生成与实现(generate and realize)这种网络,这种网络产生了这些构成要素,而且这种网络在这些构成要素存在的空间中,构成网络的界限,此界限作为网络的构成要素,参与在网络的实现过程中。
沟通的过程不仅是在它是所是者的意义下的自动指涉(auto-referential)的过程,它被自己的结构所驱迫去分离及再结合异己指涉性和自我指涉性,并再将两者重新结合起来。
当其指涉到自己时,这个过程就必须区分讯息和告知,而且必须要指出这个区分的那一个面向,被用来作为进一步的沟通的基础。
自我指涉性可以被视为单一价值的事物,而且只可以被具有二致的逻辑所描述,亦即真和假。
卢曼用系统与环境这一对“区划”来描述功能分化的社会图景,这一区划是卢曼自己对现代社会进行观察时所采用的“二值代码”。
卢曼洞彻了这样一条真理,任何信息在实质上都是由某种类型二值代码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