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否还在人间》的身份认同问题
- 格式:pdf
- 大小:272.07 KB
- 文档页数: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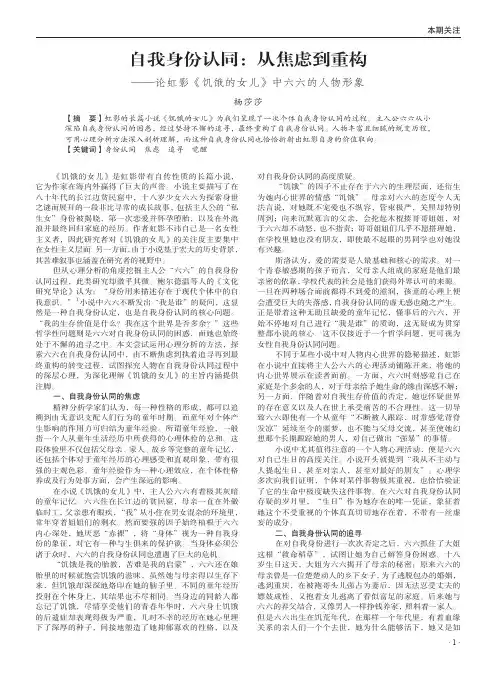
本期关注· 1 ·《饥饿的女儿》是虹影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它为作家在海内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小说主要描写了在八十年代的长江边贫民窟中,十八岁少女六六为探索身世之谜而展开的一段非比寻常的成长故事,包括主人公的“私生女”身份被揭晓,第一次恋爱并怀孕堕胎,以及在外流浪并最终回归家庭的经历。
作者虹影不讳自己是一名女性主义者,因此研究者对《饥饿的女儿》的关注度主要集中在女性主义层面。
另一方面,由于小说基于宏大的历史背景,其苦难叙事也涵盖在研究者的视野中。
但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挖掘主人公“六六”的自我身份认同过程,此类研究却微乎其微。
鲍尔德温等人的《文化研究导论》认为:“身份用来描述存在于现代个体中的自我意识。
”①小说中六六不断发出“我是谁”的疑问,这显然是一种自我身份认定,也是自我身份认同的核心问题。
“我的生存价值是什么?我在这个世界是否多余?”这些哲学性问题则是六六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而她也始终处于不懈的追寻之中。
本文尝试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探索六六在自我身份认同中,由不断焦虑到执着追寻再到最终重构的转变过程,试图探究人物在自我身份认同过程中的深层心理,为深化理解《饥饿的女儿》的主旨内涵提供注脚。
一、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精神分析学家们认为,每一种性格的形成,都可以追溯到由无意识支配人们行为的童年时期。
而童年对个体产生影响的作用力可归结为童年经验。
所谓童年经验,一般指一个人从童年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
这段体验里不仅包括父母亲、家人、故乡等完整的童年记忆,还包括个体对于童年经历的心理感受和直观印象,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
童年经验作为一种心理效应,在个体性格养成及行为处事方面,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小说《饥饿的女儿》中,主人公六六有着极其灰暗的童年记忆。
六六住在长江边的贫民窟,母亲一直在外做临时工,父亲患有眼疾,“我”从小住在男女混杂的环境里,常年穿着姐姐们的剩衣。
然而要强的因子始终植根于六六内心深处,她厌恶“赤裸”,将“身体”视为一种自我身份的象征,对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保护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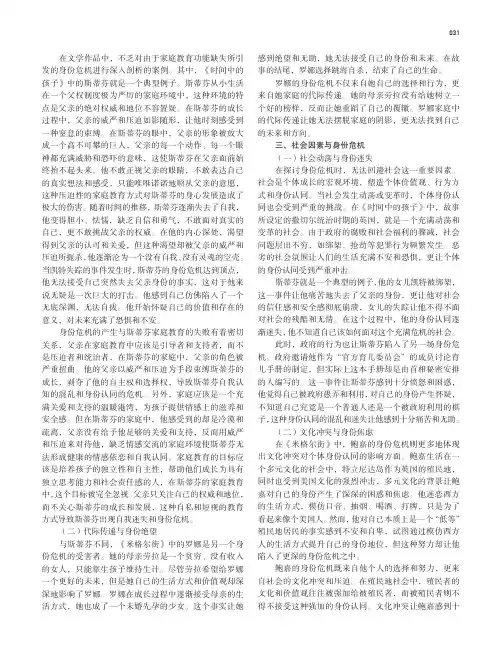
031在文学作品中,不乏对由于家庭教育功能缺失所引发的身份危机进行深入剖析的案例。
其中,《时间中的孩子》中的斯蒂芬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斯蒂芬从小生活在一个父权制度极为严厉的家庭环境中,这种环境的特点是父亲的绝对权威和地位不容置疑。
在斯蒂芬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威严和压迫如影随形,让他时刻感受到一种窒息的束缚。
在斯蒂芬的眼中,父亲的形象被放大成一个高不可攀的巨人,父亲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充满威胁和恐吓的意味,这使斯蒂芬在父亲面前始终抬不起头来。
他不敢正视父亲的眼睛,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只能唯唯诺诺地顺从父亲的意愿,这种压迫性的家庭教育方式对斯蒂芬的身心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随着时间的推移,斯蒂芬逐渐失去了自我,他变得胆小、怯懦,缺乏自信和勇气,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更不敢挑战父亲的权威。
在他的内心深处,渴望得到父亲的认可和关爱,但这种渴望却被父亲的威严和压迫所扼杀,他逐渐沦为一个没有自我、没有灵魂的空壳。
当凯特失踪的事件发生时,斯蒂芬的身份危机达到顶点,他无法接受自己突然失去父亲身份的事实,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他感到自己仿佛陷入了一个无底深渊,无法自拔。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和不安。
身份危机的产生与斯蒂芬家庭教育的失败有着密切关系,父亲在家庭教育中应该是引导者和支持者,而不是压迫者和统治者,在斯蒂芬的家庭中,父亲的角色被严重扭曲。
他的父亲以威严和压迫为手段束缚斯蒂芬的成长,剥夺了他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导致斯蒂芬自我认知的混乱和身份认同的危机。
另外,家庭应该是一个充满关爱和支持的温暖港湾,为孩子提供情感上的滋养和安全感。
但在斯蒂芬的家庭中,他感受到的却是冷漠和疏离,父亲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关爱和支持,反而用威严和压迫来对待他,缺乏情感交流的家庭环境使斯蒂芬无法形成健康的情感依恋和自我认同。
家庭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帮助他们成长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人,在斯蒂芬的家庭教育中,这个目标被完全忽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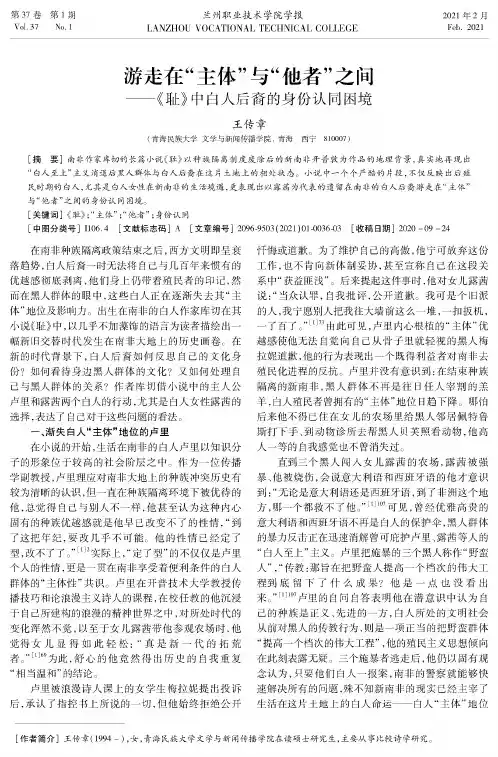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LANZHOU VOCATISNAL TECHNISAL COLLEGE第37卷第1期Vod 27 No. 42021 年 2 月Fe.42021游走在“主体”与“他者”之间——《耻》中白人后裔的身份认同困境王传章(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青海西宁81()()27)[摘要]南非作家库切的长篇小说《耻》以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的新南非开普敦为作品的地理背景,真实地再现出“白人至上”主义消退后黑人群体与白人后裔在这片土地上的相处状态。
小说中一个个严酷的片段,不仅反映出后殖民时期的白人,尤其是白人女性在新南非的生活境遇,更表现出以露茜为代表的遗留在南非的白人后裔游走在“主体”与“他者”之间的身份认同困境。
[关键词]《耻》;“主体”;“他者”;身份认同[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9503(2021)01-0036 93 [收稿日期]2020 -09 -24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之后,西方文明即呈衰 落趋势,白人后裔一时无法将自己与几百年来惯有的 优越感彻底剥离,他们身上仍带着殖民者的印记,然 而在黑人群体的眼中,这些白人正在逐渐失去其“主体”地位及影响力。
出生在南非的白人作家库切在其 小说《耻》中,以几乎不加藻饰的语言为读者描绘出一幅新旧交替时代发生在南非大地上的历史画卷。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白人后裔如何反思自己的文化身 份?如何看待身边黑人群体的文化?又如何处理自己与黑人群体的关系?作者库切借小说中的主人公 卢里和露茜两个白人的行动,尤其是白人女性露茜的选择,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
一、渐失白人“主体”地位的卢里在小说的开始,生活在南非的白人卢里以知识分子的形象位于较高的社会阶层之中。
作为一位传播 学副教授,卢里理应对南非大地上的种族冲突历史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但一直在种族隔离环境下被优待的他,总觉得自己与别人不一样,他甚至认为这种内心 固有的种族优越感就是他早已改变不了的性情,“到 了这把年纪,要改几乎不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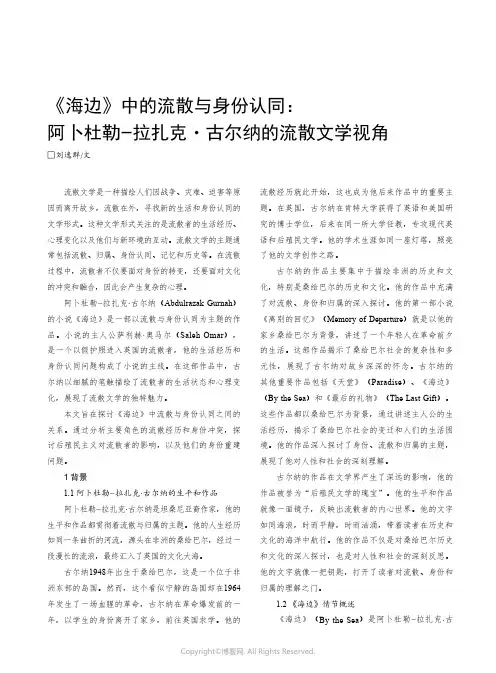
海外艺术 |14《海边》中的流散与身份认同: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流散文学视角□刘逸群/文流散文学是一种描绘人们因战争、灾难、迫害等原因而离开故乡,流散在外,寻找新的生活和身份认同的文学形式。
这种文学形式关注的是流散者的生活经历、心理变化以及他们与新环境的互动。
流散文学的主题通常包括流散、归属、身份认同、记忆和历史等。
在流散过程中,流散者不仅要面对身份的转变,还要面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因此会产生复杂的心理。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 )的小说《海边》是一部以流散与身份认同为主题的作品。
小说的主人公萨利赫·奥马尔(Saleh Omar ),是一个以假护照进入英国的流散者,他的生活经历和身份认同问题构成了小说的主线。
在这部作品中,古尔纳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流散者的生活状态和心理变化,展现了流散文学的独特魅力。
本文旨在探讨《海边》中流散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
通过分析主要角色的流散经历和身份冲突,探讨后殖民主义对流散者的影响,以及他们的身份重建问题。
1 背景1.1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生平和作品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是坦桑尼亚裔作家,他的生平和作品都贯彻着流散与归属的主题。
他的人生经历如同一条曲折的河流,源头在非洲的桑给巴尔,经过一段漫长的流浪,最终汇入了英国的文化大海。
古尔纳1948年出生于桑给巴尔,这是一个位于非洲东部的岛国。
然而,这个看似宁静的岛国却在1964年发生了一场血腥的革命,古尔纳在革命爆发前的一年,以学生的身份离开了家乡,前往英国求学。
他的流散经历就此开始,这也成为他后来作品中的重要主题。
在英国,古尔纳在肯特大学获得了英语和美国研究的博士学位,后来在同一所大学任教,专攻现代英语和后殖民文学。
他的学术生涯如同一座灯塔,照亮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
古尔纳的作品主要集中于描绘非洲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桑给巴尔的历史和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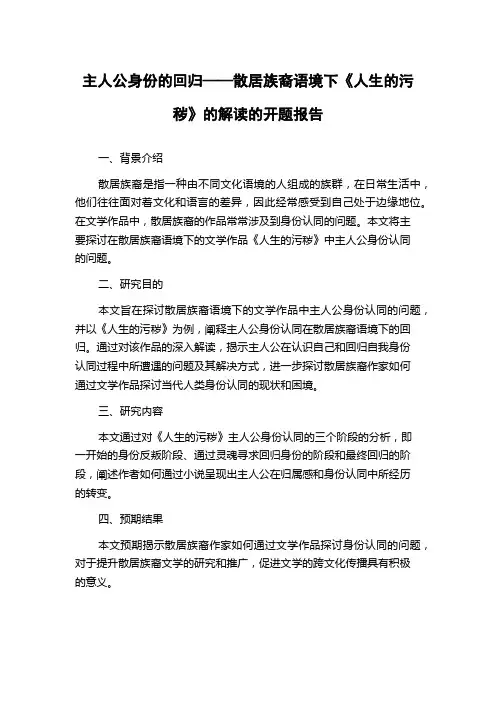
主人公身份的回归——散居族裔语境下《人生的污
秽》的解读的开题报告
一、背景介绍
散居族裔是指一种由不同文化语境的人组成的族群,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往往面对着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因此经常感受到自己处于边缘地位。
在文学作品中,散居族裔的作品常常涉及到身份认同的问题。
本文将主
要探讨在散居族裔语境下的文学作品《人生的污秽》中主人公身份认同
的问题。
二、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探讨散居族裔语境下的文学作品中主人公身份认同的问题,并以《人生的污秽》为例,阐释主人公身份认同在散居族裔语境下的回归。
通过对该作品的深入解读,揭示主人公在认识自己和回归自我身份
认同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进一步探讨散居族裔作家如何
通过文学作品探讨当代人类身份认同的现状和困境。
三、研究内容
本文通过对《人生的污秽》主人公身份认同的三个阶段的分析,即
一开始的身份反叛阶段、通过灵魂寻求回归身份的阶段和最终回归的阶段,阐述作者如何通过小说呈现出主人公在归属感和身份认同中所经历
的转变。
四、预期结果
本文预期揭示散居族裔作家如何通过文学作品探讨身份认同的问题,对于提升散居族裔文学的研究和推广,促进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具有积极
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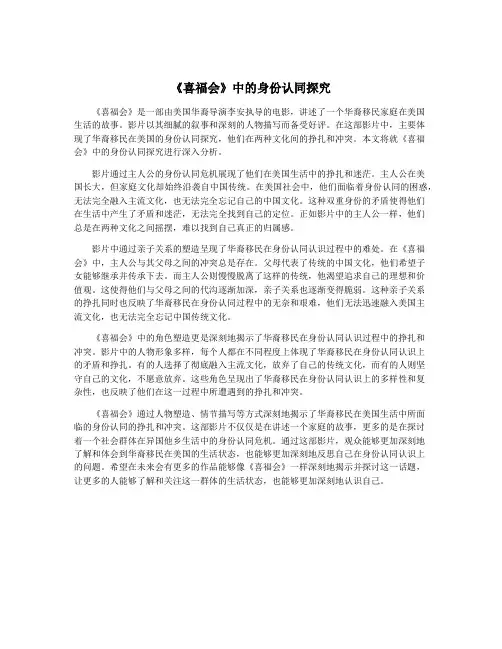
《喜福会》中的身份认同探究《喜福会》是一部由美国华裔导演李安执导的电影,讲述了一个华裔移民家庭在美国生活的故事。
影片以其细腻的叙事和深刻的人物描写而备受好评。
在这部影片中,主要体现了华裔移民在美国的身份认同探究,他们在两种文化间的挣扎和冲突。
本文将就《喜福会》中的身份认同探究进行深入分析。
影片通过主人公的身份认同危机展现了他们在美国生活中的挣扎和迷茫。
主人公在美国长大,但家庭文化却始终沿袭自中国传统。
在美国社会中,他们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惑,无法完全融入主流文化,也无法完全忘记自己的中国文化。
这种双重身份的矛盾使得他们在生活中产生了矛盾和迷茫,无法完全找到自己的定位。
正如影片中的主人公一样,他们总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摇摆,难以找到自己真正的归属感。
影片中通过亲子关系的塑造呈现了华裔移民在身份认同认识过程中的难处。
在《喜福会》中,主人公与其父母之间的冲突总是存在。
父母代表了传统的中国文化,他们希望子女能够继承并传承下去。
而主人公则慢慢脱离了这样的传统,他渴望追求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
这使得他们与父母之间的代沟逐渐加深,亲子关系也逐渐变得脆弱。
这种亲子关系的挣扎同时也反映了华裔移民在身份认同过程中的无奈和艰难,他们无法迅速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也无法完全忘记中国传统文化。
《喜福会》中的角色塑造更是深刻地揭示了华裔移民在身份认同认识过程中的挣扎和冲突。
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多样,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华裔移民在身份认同认识上的矛盾和挣扎。
有的人选择了彻底融入主流文化,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而有的人则坚守自己的文化,不愿意放弃。
这些角色呈现出了华裔移民在身份认同认识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反映了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挣扎和冲突。
《喜福会》通过人物塑造、情节描写等方式深刻地揭示了华裔移民在美国生活中所面临的身份认同的挣扎和冲突。
这部影片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家庭的故事,更多的是在探讨着一个社会群体在异国他乡生活中的身份认同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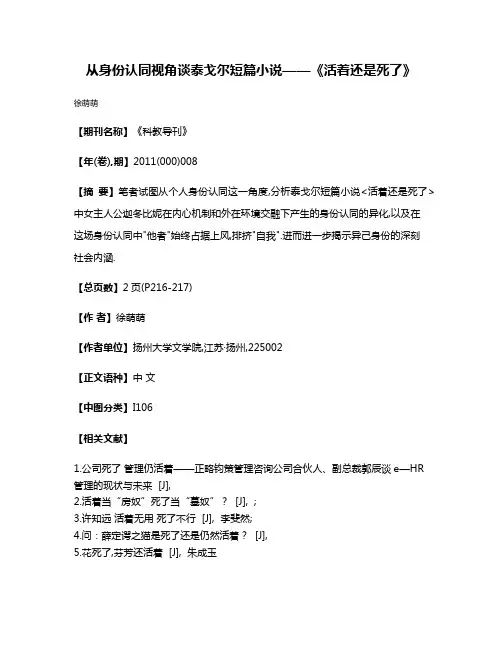
从身份认同视角谈泰戈尔短篇小说——《活着还是死了》
徐萌萌
【期刊名称】《科教导刊》
【年(卷),期】2011(000)008
【摘要】笔者试图从个人身份认同这一角度,分析泰戈尔短篇小说<活着还是死了>中女主人公迦冬比妮在内心机制和外在环境交融下产生的身份认同的异化,以及在
这场身份认同中"他者"始终占据上风,排挤"自我".进而进一步揭示异己身份的深刻
社会内涵.
【总页数】2页(P216-217)
【作者】徐萌萌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106
【相关文献】
1.公司死了管理仍活着——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公司合伙人、副总裁郭辰谈e—HR 管理的现状与未来 [J],
2.活着当“房奴”死了当“墓奴”? [J], ;
3.许知远活着无用死了不行 [J], 李斐然;
4.问:薛定谔之猫是死了还是仍然活着? [J],
5.花死了,芬芳还活着 [J], 朱成玉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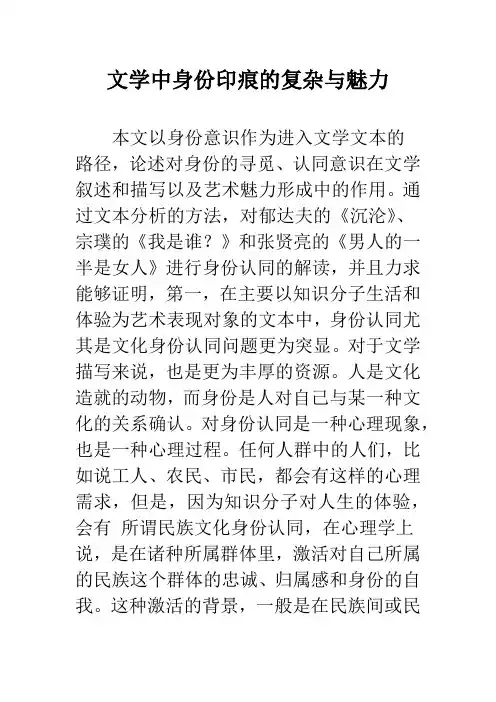
文学中身份印痕的复杂与魅力 本文以身份意识作为进入文学文本的路径,论述对身份的寻觅、认同意识在文学叙述和描写以及艺术魅力形成中的作用。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对郁达夫的《沉沦》、宗璞的《我是谁?》和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进行身份认同的解读,并且力求能够证明,第一,在主要以知识分子生活和体验为艺术表现对象的文本中,身份认同尤其是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更为突显。对于文学描写来说,也是更为丰厚的资源。人是文化造就的动物,而身份是人对自己与某一种文化的关系确认。对身份认同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过程。任何人群中的人们,比如说工人、农民、市民,都会有这样的心理需求,但是,因为知识分子对人生的体验,会有 所谓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在心理学上说,是在诸种所属群体里,激活对自己所属的民族这个群体的忠诚、归属感和身份的自我。这种激活的背景,一般是在民族间或民族国家间发生事实的联系,或者发生文化冲突的时候。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是在不同民族关系框架中进行的。比如,我国多民族文学的框架中,某一少数民族文学对自己民族形象的塑造,对自己民族情感的体验,对文化身份的强调、认同和艺术表现愿望等。而当作家以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为情感背景,描绘跨民族和跨文化交往中的情感体验时,则是另一个层次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郁达夫的《沉沦》中的主人公“他”所经历的文化身份认同即属于后一个层次的。 小说叙述一个中国留学生“他”在日本的经历和体验。“他”所处的时代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而且又经历了八国联军对中国的瓜分后的时代。作为积贫积弱的中国青年,“他”原本就有早熟的性情,这种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绝不相容的境地去”,随着大哥来到日本之后,“他”竟然发展到抑郁症。“他”在人群中感到的是孤独、忧伤、自卑,尤其是在女性面前,一方面渴望获得女性的青睐,另一方面又自卑、忧郁。随着青春欲求的萌生和发展,对于异性的关注、追求和追求中的受挫感和失落感,日益加深地折磨着“他”。他将自己受挫和失落的痛苦体验和祖国的积贫积弱联系起来。每当“他”失意时,就归咎于自己是“支那人”,愤慨地说“狗才!俗物!你们都敢来欺侮我么?复仇复仇,我总要复你们的仇………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吧。” 这种极为失落的情绪,以及和对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的眷恋而又怨怼的情感体验,具有怎样的典型意义呢?一方面,“他”的民族之根毕竟在中国,华夏文化滋养了“他”,他的精神归宿理当在中国和中国文化之中,可是另一方面,此时的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是处于弱势的、被异邦他国所歧视的国家,“他”在跨民族和跨文化的情境中,必然感到若有所失,似乎生活总不在“他”的身边,而在别处。这是小说主人公的体验,也是作家本人体验的投射。郁达夫在《忏余独白》中说自己“因为对现实感到不满,才想逃回到大自然的怀中,在大自然的广漠里徘徊着,又只想飞翔开去;可是到了处固定的地方之后,心理的变化又是同样的要起来,所以转转不已,一生就只能为Wanderlust的奴隶,而变作着一个永远的旅人(Aneternal Pilgrim)”。对于这种总是追求别处的生活,而对现实所处失望、悲观,郁达夫自己认为是一种天性。而我们在对《沉沦》的文本分析中更愿意认为,这是在跨民族和跨文化交往中,作为弱势国家和民族的人们的一种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心态和个人命运。 主人公“他”在失落情绪中生发出的对故国的眷恋和怨怼,与中国文学传统中哀婉、凄凉的风格有着内在的联系。或者说,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在20世纪初远在异国他乡的年轻人心理引起子文化的回应。文本中多次出现月亮意象。“露是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这些蕴涵着凄凉、悲伤、离别的意味早已沉潜在人们的美学感受中,所以,《沉沦》中出现的“半轮寒月,高高挂在天空的左半边”,“月光射到他的面上,两条泪线倒变了叶上的朝露一样放起光来”。身在岛国的“他”和故乡共着一个月亮,月亮寄托了“他”对祖国的思念,“他”看到,在西天青苍苍的天底下,有一颗明星,在那里摇动。他自语到“那一颗遥遥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颗星的底下,也曾送过十八个秋冬。我的故乡吓,我如今再不能见你的面了。”向往回归祖国,可是回归祖国后,“他”还会生出别样的失落,这是那个时代国家积贫积弱,而游子在他国经验了新兴现代性文化之后所必然的。小说的叙述逻辑已经将这样的可能展示给读者了。后来,郁达夫在《忏余独白》中说过自己“兴浓浓地我就回到了上下交争利,先后不见人——是‘人少畜生多’的意思——的故国。碰壁,碰壁,再碰壁,刚从流放地点遇赦回来的一位旅客,却永远地踏入了一个并无铁窗的故国的囚牢……到此我才领悟到了彻底。愁来无路,拿起笔来写写,只好写些愤世疾邪,怨天骂地的牢骚,放几句破坏一切,打倒一切的狂呓。越是这样,越是找不到出路。越找不到出路,越想破坏,越想反抗。这一期中间的作品,大半都是在这一种心情之下写成。”郁达夫的失落,这段话印证了《沉沦》中“他”的文化身份认同的惶惑和无所归依的时代性。 这样现代意义上的飘零感,渗透在文本的叙事风格中。虽然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视点,却是第三人称小说中内聚焦叙事。小说中景物的描写大多出自于主人公的眼光所见,那些景物都是“有我之境”,带有凄凉、失落的感情色彩,比如对月亮的描写;聚焦人物的行踪则是顺着人物的心理走向而外显的结果。“秋天又到了。浩浩的苍空,一天一天的高起来。他的旅馆旁边的稻田,都带起金黄色来,朝夕的凉风,同刀也似的刺到人的心骨里去,大约秋冬的佳日,来也不远了。”但是“同刀也似的”等字眼,显然有一个体验的主体存在而使之然。主人公“他”的眼光已经渗透到或者代替了叙事者的眼光。虽然故事外的叙述者似乎还存在,但是叙事眼光却存在于故事内的聚焦人物“他”的身上。“他”带着读者一起前行在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心理旅程中。在当下的全球化过程中,“他”是个可以反复地被当代中国人不断体味的艺术形象。 二、《我是谁》之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 宗璞1979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我是谁?》,因为形而上地提出“我是谁?”的询问,而具有不断地解读和再阐释的可能。在这篇小说里,宗璞用第三人称深情地塑造了一个女性知识分子韦弥的形象,刻画了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精神上极大的伤害之后的苦闷、绝望,以至最终走向选择死亡的心路历程。宗璞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耳濡目染于知识分子的操守、人格和情操,她和她的父亲冯友兰乃至家人,中国知识分子在半个多世纪里所可能经历的一切。这种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成为她描写韦弥的丰厚资源,也成为她切入肺腑般地询问“我是谁”的思考根据。但是,韦弥毕竟是宗璞笔下的人物,我们依然从文本入手,分析这个人物所可能给予我们的。这篇小说诞生之后正值我国政治运作轨迹的伤痕和反思阶段,这样的思潮性背景,形成了对这样作品解释和理解的语境:那就是,是对极左思潮和历史的控诉、声讨,乃至反思。而我们现在试图从身份认同的视角分析韦弥。 韦弥在被人们斥责为大毒虫,回到家里看到丈夫孟文起吊死在厨房后,失神落魄地冲出家门,摔倒在路旁,又受到冷漠的斥责,在神经质般地追问“我是谁”的痛苦中投向湖水。在韦弥整个痛苦体验中,有两个意象是饶有深意的,第一个是大雁。韦弥将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己和迷路的大雁对应起来,产生了隐喻意味。痛苦中,她看到了迷路的大雁,是的,“它们迷了路,不知道应该飞向何方。韦弥一下子跳了起来,向前奔跑。她伸出两臂,想去捕捉那迷途的、飘零的鸿雁”。“她觉得自己也是一只迷途的孤雁,在黑暗的天空中哭泣”。为什么会将自己喻为孤雁?在韦弥的意识屏幕上有一段闪回式的叙述:韦弥和丈夫孟文起在解放初,从国外回了到祖国怀抱,他们曾经“飞翔在雁群中”,而那时,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心里是安然的。从韦弥的意识或者也包括潜意识,是将自己和像母亲一样的祖国联系在一起的感受、认同的。他们的安然在于能够为祖国贡献力量。韦弥如今的失落、不知道自己是谁,皆因为母亲消失了,自己才无所认同,无所归依。她回忆到自己曾和丈夫孟文起,努力“把自己炼成干将、莫邪那样两口斩金切玉的宝剑,以披斩科学道路上的荆棘。剑是献给母亲的。可是如今剑在哪里?母亲又在哪里”?这是在一个扭曲了的世界里的呼唤。 第二个意象是虫子。和孤雁的体验联系的,是虫子的消极痛苦的自我感知。或者说,因为如今自己成了虫子,而有了孤雁的断零体验。在韦弥模糊的意识中,自己是一条大毒虫,何止是自己,“韦弥看见,四面八方,爬来了不少虫子”,这些虫子还发出了“咝咝”的声音,韦弥能听懂这“咝咝”的声音,它们说的是“我——是——谁?”如果说,大雁由过去时态中是与雁群合而为一的,所以即便在韦弥现在时的断零体验中,也依然是肯定性的形象。而大毒虫,没有与任何有价值的事物相联系,并且因为成为了大毒虫后而失去和雁群联系的可能性,所以是否定性的形象。大雁是飞翔的,而虫子是爬行的。失落的形象和现在的存在状态构成极大的反差,更加深了韦弥的“我是谁”的身份询问。 如果我们深入思考韦弥的体验,会发现她对知识分子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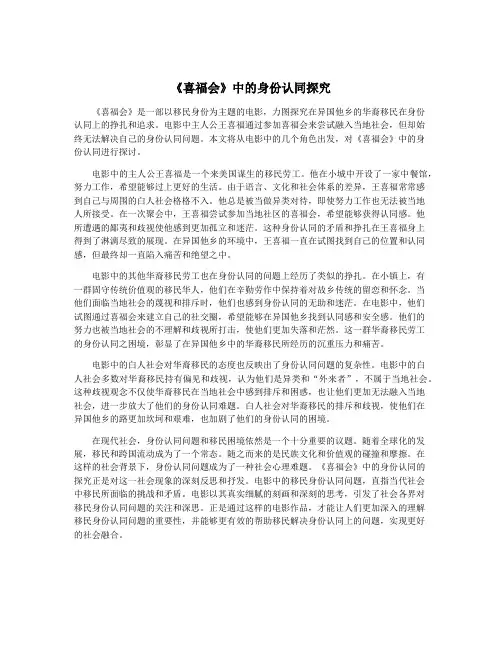
《喜福会》中的身份认同探究《喜福会》是一部以移民身份为主题的电影,力图探究在异国他乡的华裔移民在身份认同上的挣扎和追求。
电影中主人公王喜福通过参加喜福会来尝试融入当地社会,但却始终无法解决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
本文将从电影中的几个角色出发,对《喜福会》中的身份认同进行探讨。
电影中的主人公王喜福是一个来美国谋生的移民劳工。
他在小城中开设了一家中餐馆,努力工作,希望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由于语言、文化和社会体系的差异,王喜福常常感到自己与周围的白人社会格格不入。
他总是被当做异类对待,即使努力工作也无法被当地人所接受。
在一次聚会中,王喜福尝试参加当地社区的喜福会,希望能够获得认同感。
他所遭遇的鄙夷和歧视使他感到更加孤立和迷茫。
这种身份认同的矛盾和挣扎在王喜福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在异国他乡的环境中,王喜福一直在试图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认同感,但最终却一直陷入痛苦和绝望之中。
电影中的其他华裔移民劳工也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上经历了类似的挣扎。
在小镇上,有一群固守传统价值观的移民华人,他们在辛勤劳作中保持着对故乡传统的留恋和怀念。
当他们面临当地社会的蔑视和排斥时,他们也感到身份认同的无助和迷茫。
在电影中,他们试图通过喜福会来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希望能够在异国他乡找到认同感和安全感。
他们的努力也被当地社会的不理解和歧视所打击,使他们更加失落和茫然。
这一群华裔移民劳工的身份认同之困境,彰显了在异国他乡中的华裔移民所经历的沉重压力和痛苦。
电影中的白人社会对华裔移民的态度也反映出了身份认同问题的复杂性。
电影中的白人社会多数对华裔移民持有偏见和歧视,认为他们是异类和“外来者”,不属于当地社会。
这种歧视观念不仅使华裔移民在当地社会中感到排斥和困惑,也让他们更加无法融入当地社会,进一步放大了他们的身份认同难题。
白人社会对华裔移民的排斥和歧视,使他们在异国他乡的路更加坎坷和艰难,也加剧了他们的身份认同的困境。
在现代社会,身份认同问题和移民困境依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

探析苏曼殊小说创作中的身份认同问题作者:李志秋来源:《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14期摘要:苏曼殊作为清末民初动荡历史中“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传奇人物,其哀感顽艳的“小说六记”和半译半著的《惨世界》,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其小说创作中的身份认同上的冲突入手,对苏曼殊其人其文进行更深刻的解读。
关键词:小说六记;惨世界;身份认同;女性形象作者简介:李志秋(1990-),女,上海市闵行区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5)-14-0-02苏曼殊天才绝世,被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誉为“近代中国文学史上之一彗星”。
1903年,20岁的苏曼殊以半译半著的《惨世界》在文坛上崭露头角,1912年,又因自叙传色彩浓厚的悲情小说《断鸿零雁记》文名大噪,在文坛立足。
而后,又分别在《民国》、《甲寅》、《青年杂志》、(《新青年》)《小说大观》发表了《天涯红泪记》、(未完)《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构成了其“小说六记”,并以其特有的清新典雅的文调,凄凉初测的风格,震撼了众多读者的心。
天性浪漫,身世坎坷的苏曼殊与北宋词人秦少游一样“将身世之感,大并入艳情”,成为淮海,小山之外,又一古今之伤心人。
而“诗僧,情僧,革命僧”的多重身份,也造成了其小说文本的复杂性,和意旨的多重性。
身份认同的问题,一直贯穿于苏曼殊的小说创作中。
对自身血统的问题的困惑和纠缠,使苏曼殊的小说呈现出哀伤凄清的漂泊之感;而对文化身份的认同,更让苏曼殊的小说呈现出激进入世的革命情结和淡泊出世的佛禅情调以及隐微幽深的遗民心态。
同时,作者苏曼殊自己对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身份认同问题,更暴露出了在历史转型期间,受西方文化冲击和传统文化浸淫的知识分子的矛盾和困惑。
探析苏曼殊小说创作中身份认同问题,有助于我们对苏曼殊的传奇人生赋予其小说的特性和和变革的历史大背景赋予其小说的共性进行更清晰地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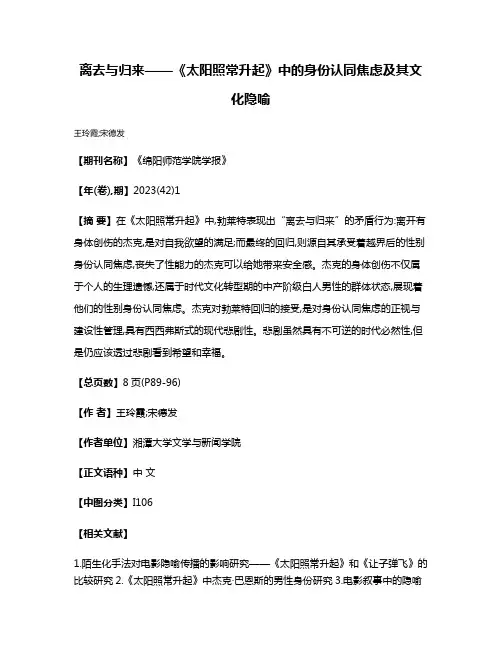
离去与归来——《太阳照常升起》中的身份认同焦虑及其文
化隐喻
王玲霞;宋德发
【期刊名称】《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23(42)1
【摘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勃莱特表现出“离去与归来”的矛盾行为:离开有身体创伤的杰克,是对自我欲望的满足;而最终的回归,则源自其承受着越界后的性别身份认同焦虑,丧失了性能力的杰克可以给她带来安全感。
杰克的身体创伤不仅属于个人的生理遗憾,还属于时代文化转型期的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的群体状态,展现着他们的性别身份认同焦虑。
杰克对勃莱特回归的接受,是对身份认同焦虑的正视与建设性管理,具有西西弗斯式的现代悲剧性。
悲剧虽然具有不可逆的时代必然性,但是仍应该透过悲剧看到希望和幸福。
【总页数】8页(P89-96)
【作者】王玲霞;宋德发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106
【相关文献】
1.陌生化手法对电影隐喻传播的影响研究——《太阳照常升起》和《让子弹飞》的比较研究
2.《太阳照常升起》中杰克·巴恩斯的男性身份研究
3.电影叙事中的隐喻
美学阐释——以姜文近作《太阳照常升起》为例4.太阳升起后的思考——电影《太阳照常升起》叙事和审美分析5.梦、隐喻——《太阳照常升起》解读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浅析东野 O钱列英 士--I--吾I-"l作旦I=lI=i —I卜 中的身份认同 【摘要】本文通过精神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的方法,对东野圭吾的作品文本进行分析,研究其作品中的身份认同主题,并结合 日本的传统文化,对日本社会中的身份认同进行了探讨。 【关键字】东野圭吾身份认同 文本分析
日本推理作家东野圭吾是一个偏好 科技发展的“技术派”,他的作品中充斥 着埘科技的好奇与怀疑,对科技发展暴露 m的人性弱点进行深入探讨。在科技的助 推下,脑科学取得突飞猛进的成就,医生 可以给病人更换脑切片;克隆人在社会中 无法找到自己的身份;社会发展造成了人 的性别认同障碍等主题都显示出现代社 会中人类的身份认同危机。 从东野圭吾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其作 品中的身份认同主题比比皆是,无论是因 为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份变换,还是社会变 革导致的人格扭曲,东野圭吾一直致力于 探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自己身份的认 识,对于人格的求索。 一、身份理论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身 份”已成为全世界学者热切关注的议题。 在英文中,identity一词既可翻译为“认 同”,同时也有“身份”、“同一性”等含 义。“认同危机”这一心理学术语是由美 国心理学家艾里克・艾里克森于2O世纪 50年代提出。艾里克森认为,在人的成长 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注意外界”并“与 外界相互作用”的需要,而个人的人格便 是在与外界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① 身份认同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 的认同。它主要解决我(现代人)是谁、从 何而来、到何处去等核心问题。从2O世纪 60年代开始,身份理论被广泛运用到社 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对于身份的研究之 中。身份理论主要认为自我的社会本质来 耪嗣嘞簪 自一个人所处的角色位置,而角色身份因 其显著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因此,自 我是一个多层面的、有组织的社会结构, 源自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自我概念的变 化决定于角色身份的变化。② 霍格、特里等人的理论指出,身份理 论“解决了‘与人们在社会中扮演的行为 角色相联系的’身份的结构问题和功能 问题”。自我处于社会之中,由社会所构 成,不能独立于社会之外,人们可以通过 与他人相似性或差异性的比较来获取身 份认同。 现代社会中,身份认同涉及到个体认 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等众 多方面。自我身份认同,强调的是自我心 理和身体体验。如《变身》中的成濑纯一, 他对移植于大脑中的脑片耿耿于怀,这个 拯救他生命的脑片的原主人是一个杀人 犯,成濑纯一因为这种强行的植入而感觉 到人格的丢失,“你必须信!我的脑正在 被移植的京极的脑取代!”③经历脑移植 手术的主人公不停地追寻“我是谁”,他 希望对自己的身份做出明确的自我定位, 以强化其身份的存在感。 二、身份的自我与主体性 “自我”指的是个体对自己存在的觉 察,这种觉察是一种心理经验,也是一种 主观意识。而“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过 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地位,即人的 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 地位和特性。 自我是一个整体陛的概念,一般来说 它指的是主体对自己的全部身心状况的 知觉,对自己全面的认识,它是个人有意 识的部分,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对每 一个具体的个体来说,自我就是自己感知 到的关于自己的一切,包括对他人对自己 的感知。自我是关于自己的过去的一切的 产物,并且将在未来持续下去并发生变化 及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自我意识好比我们 的世界观,是主体对世界的主体性的认 识。 从弗洛伊德的理论看,一个人的人格 由“本我、自我、超我”三个部分组成。在 《白夜行》中,唐泽雪穗与桐原亮司就在 “本我、自我、超我”中不断挣扎。从“本 我”上,桐原亮司认为自己弑父的行为是 为了保护雪穗,他对于雪穗来说是恩人, 也是爱人。但从“自我”角度,桐原亮司是 犯下弑父罪行的杀人犯。在往后的生活 中,他为了保护自己,不断地加害别人,陷 害同学,对女同学施暴,进行金融犯罪,是
《喜福会》中“他者”的身份认同作者:陈妍来源:《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05期摘要: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已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
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中,脱离本族文化的华裔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已被边缘化为“他者”,在两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混杂的文化身份,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而是处于东西方边缘的“第三空间”。
关键词:身份;他者;混杂;第三空间作者简介:陈妍(1985- ),女,湖南株洲人,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文学。
谭恩美是美国华裔文学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一位女作家。
处女作《喜福会》一经出版,就引起了美国文坛的关注,获得包括“全美图书奖”和“全美图书评论界奖”在内的多个奖项。
究其成功的原因,可以发现作品将个人、家庭的经历放大阐释为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历程,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本文拟从后殖民批评的视角来解读以谭恩美为代表的华裔群体在东西方异质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如何沦为“他者”致使身份丧失,后又以何种方式找到了重新建构身份认同的出路。
“身份认同”(identity)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
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像谭恩美这样的后殖民状态下的族裔散居者都在争取建立和巩固其独特的新身份。
而身份认同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牵涉到了安身立命的基本问题:我(现代人)是谁?我从何而来?我将到何处去?在西方主流文化中,作为被边缘化的“他者”,认同已经成为了区分“我们”和“他们”的标志。
由此,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的选择与定位,让错位之后的华裔美国人陷入了共同的困惑。
一、身份认同的困境早在移民初期,美国主流社会就利用文学、艺术等各种媒介手段将包括华裔在内的少数族裔妖魔化、他者化,强迫他们接受主流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
首先种族上,作为第一代移民,怀着对故土的无限眷恋,不远万里来到了憧憬中的美国。
然而,自称为大熔炉的主流文化却并非想象的那样宽容。
《喜福会》中的身份认同探究《喜福会》是一部由王家卫执导的电影,讲述了在1960年代香港的移民社区中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这部电影通过展现各种不同身份认同的角色,让观众深入了解了移民社区中的复杂关系和个人挣扎。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喜福会》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并分析影片中角色们的内心挣扎和文化冲突。
电影中的主要角色之一是阿涛,一个擅长拉小提琴的年轻人。
阿涛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到困惑,他既想摆脱家庭的束缚,又想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
他在片中与父亲的矛盾也正是代表了身份认同的矛盾。
父亲希望阿涛成为商人,继承家业,而阿涛却希望通过音乐追求自己的梦想。
这种矛盾反映了许多移民家庭的内心挣扎,他们在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之间徘徊。
阿涛的故事让人们思考了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的身份认同问题。
除了阿涛之外,电影中的其他角色也面临着身份认同的挑战。
珊珊是一个在新移民社区长大的年轻女子,她在面对婚姻和家庭的压力时感到困惑。
她的父亲希望她按照传统的方式生活,而她却希望追求自己的事业和自由。
另一个例子是红姨,一个在移民社区中经营鸡尾酒酒吧的女人。
她在新移民社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也面临着身份认同的挑战。
电影中的这些角色反映了移民社区中的复杂身份认同问题。
在移民社区中,人们往往面临着家庭传统和现代生活的冲突。
他们希望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但同时也想融入新的社会环境。
这种矛盾带来了身份认同的挑战,让人们陷入内心挣扎之中。
在电影中,王家卫通过精致的镜头语言和细腻的情感刻画,展现了这些角色内心的挣扎和文化冲突。
在电影中,王家卫通过独特的摄影手法和音乐叙事,展现了阿涛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对于传统文化的留恋。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追求也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的挣扎。
而对于珊珊和红姨这样的女性角色,王家卫也通过细腻的情感描写和深刻的内心独白,展现了她们面对身份认同问题时的挣扎和纠结。
除了个人层面的内心挣扎,电影中也展现了移民社区整体的身份认同问题。
在片中,王家卫通过细腻的叙事和丰富的人物塑造,展现了移民社区中不同族裔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