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简介
- 格式:ppt
- 大小:439.50 KB
- 文档页数: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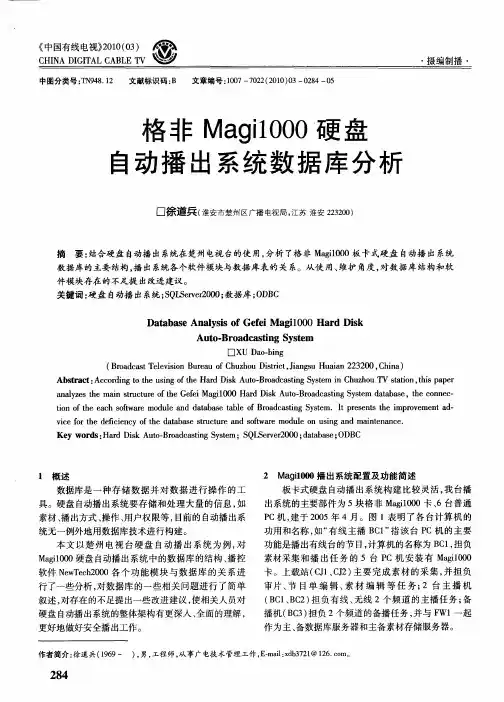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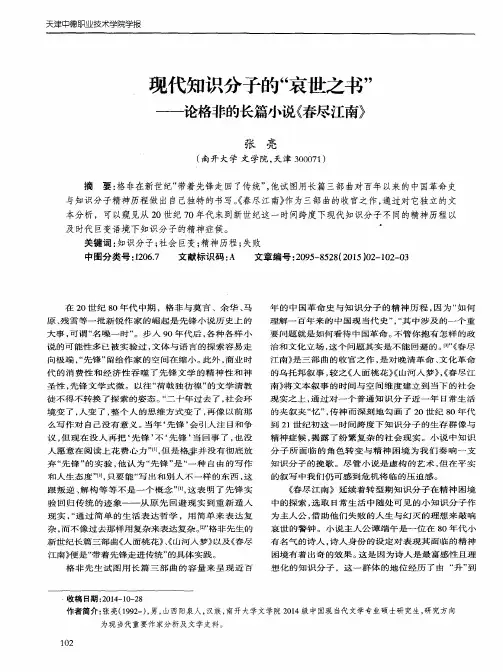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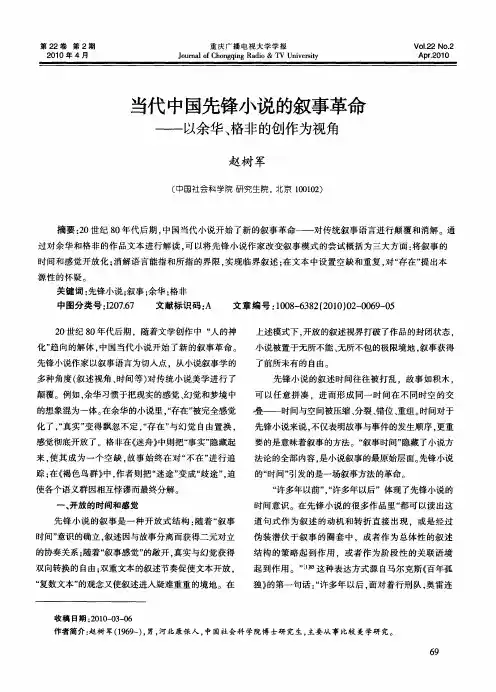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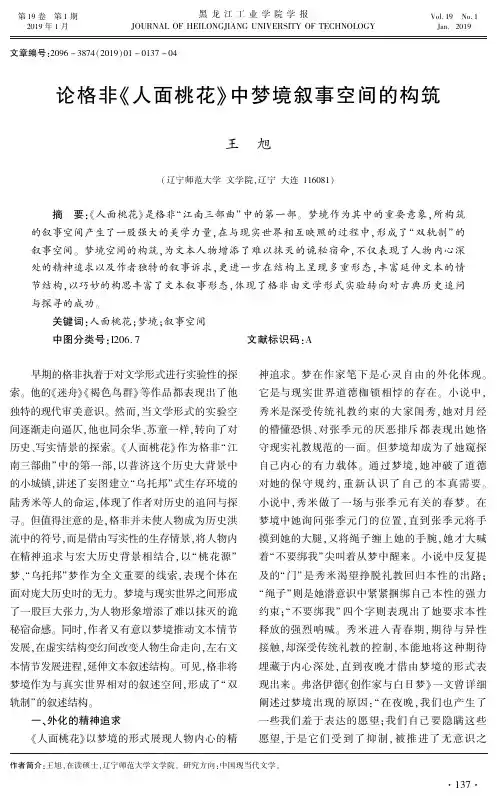
作者简介:王旭ꎬ在读硕士ꎬ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ꎮ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ꎮ文章编号:2096-3874(2019)01-0137-04论格非«人面桃花»中梦境叙事空间的构筑王㊀旭(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ꎬ辽宁大连116081)摘㊀要:«人面桃花»是格非 江南三部曲 中的第一部ꎮ梦境作为其中的重要意象ꎬ所构筑的叙事空间产生了一股强大的美学力量ꎬ在与现实世界相互映照的过程中ꎬ形成了 双轨制 的叙事空间ꎮ梦境空间的构筑ꎬ为文本人物增添了难以抹灭的诡秘宿命ꎬ不仅表现了人物内心深处的精神追求以及作者独特的叙事诉求ꎬ更进一步在结构上呈现多重形态ꎬ丰富延伸文本的情节结构ꎬ以巧妙的构思丰富了文本叙事形态ꎬ体现了格非由文学形式实验转向对古典历史追问与探寻的成功ꎮ关键词:人面桃花ꎻ梦境ꎻ叙事空间中图分类号:I206.7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文献标识码:A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早期的格非执着于对文学形式进行实验性的探索ꎮ他的«迷舟»«褐色鸟群»等作品都表现出了他独特的现代审美意识ꎮ然而ꎬ当文学形式的实验空间逐渐走向逼仄ꎬ他也同余华㊁苏童一样ꎬ转向了对历史㊁写实情景的探索ꎮ«人面桃花»作为格非 江南三部曲 中的第一部ꎬ以普济这个历史大背景中的小城镇ꎬ讲述了妄图建立 乌托邦 式生存环境的陆秀米等人的命运ꎬ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追问与探寻ꎮ但值得注意的是ꎬ格非并未使人物成为历史洪流中的符号ꎬ而是借由写实性的生存情景ꎬ将人物内在精神追求与宏大历史背景相结合ꎬ以 桃花源 梦㊁ 乌托邦 梦作为全文重要的线索ꎬ表现个体在面对庞大历史时的无力ꎮ梦境与现实世界之间形成了一股巨大张力ꎬ为人物形象增添了难以抹灭的诡秘宿命感ꎮ同时ꎬ作者又有意以梦境推动文本情节发展ꎬ在虚实结构变幻间改变人物生命走向ꎬ左右文本情节发展进程ꎬ延伸文本叙述结构ꎮ可见ꎬ格非将梦境作为与真实世界相对的叙述空间ꎬ形成了 双轨制 的叙述结构ꎮ一㊁外化的精神追求«人面桃花»以梦境的形式展现人物内心的精神追求ꎮ梦在作家笔下是心灵自由的外化体现ꎮ它是与现实世界道德枷锁相悖的存在ꎮ小说中ꎬ秀米是深受传统礼教约束的大家闺秀ꎬ她对月经的懵懂恐惧㊁对张季元的厌恶排斥都表现出她恪守现实礼教规范的一面ꎮ但梦境却成为了她窥探自己内心的有力载体ꎮ通过梦境ꎬ她冲破了道德对她的保守规约ꎬ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本真需要ꎮ小说中ꎬ秀米做了一场与张季元有关的春梦ꎮ在梦境中她询问张季元门的位置ꎬ直到张季元将手摸到她的大腿ꎬ又将绳子缠上她的手腕ꎬ她才大喊着 不要绑我 尖叫着从梦中醒来ꎮ小说中反复提及的 门 是秀米渴望挣脱礼教回归本性的出路ꎻ 绳子 则是她潜意识中紧紧捆绑自己本性的强力约束ꎻ 不要绑我 四个字则表现出了她要求本性释放的强烈呐喊ꎮ秀米进入青春期ꎬ期待与异性接触ꎬ却深受传统礼教的控制ꎬ本能地将这种期待埋藏于内心深处ꎬ直到夜晚才借由梦境的形式表现出来ꎮ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一文曾详细阐述过梦境出现的原因: 在夜晚ꎬ我们也产生了一些我们羞于表达的愿望ꎻ我们自己要隐瞒这些愿望ꎬ于是它们受到了抑制ꎬ被推进了无意识之731 第19卷㊀第1期2019年1月㊀㊀㊀㊀㊀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JOURNALOFHEILONGJIANGUNIVERSITYOFTECHNOLOGY㊀㊀㊀㊀㊀㊀Vol.19㊀No.1Jan.2019中ꎮ [1]而秀米梦见死去的 总揽把 王观澄向自己诉说建立 桃花源 花家舍的始末ꎬ并告诉她 我知道你和我是一样的人ꎬ或者说是同一个人ꎬ命中注定了会继续我的事业 [2]ꎮ王观澄作为一个死去的人当然不会给人托梦ꎬ这样的梦中对话ꎬ是秀米内心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 桃花源 的反向展现ꎮ现实社会中的秀米是一个深受传统礼教影响的少女ꎬ虽然她拥有寻求自由乌托邦的雄心壮志ꎬ但却不肯在现实世界中表露分毫ꎮ她甚至妄图压抑内心的真实追求ꎬ认为那只是连她自己也说不清的古怪想法ꎬ可最终却被听过她梦境的韩六一语道破: 你在想ꎬ这个王观澄这般的无能ꎬ这花家舍要是落到我的手里ꎬ保管叫它诸事停当ꎬ成了真正的人间天国 [2]韩六的话其实是对秀米与王观澄梦中对话的现实验证ꎮ作为与秀米朝夕相处的人ꎬ韩六深感秀米并不如表面那样温顺无争ꎬ她只是暂时被现实封建礼教制度压制住了内心深处的精神追求ꎬ但 梦境正好突破现实中的条条框框ꎬ把物理规律和社会规范放到一边ꎬ让情感在这里汪洋恣肆ꎬ让潜意识的 意志 在这里随意任性地行事ꎮ [3]可以说ꎬ梦在文本中是作为展现人物心理内在矛盾存在的ꎮ秀米一方面想做一个温顺规矩的传统女性ꎬ但梦境却真实地展现了她渴望不平凡ꎬ期待寻求 乌托邦式 生存环境的真实心理状态ꎮ可见ꎬ梦境是展示人真实心灵需求的载体ꎬ为表现人物内心审美追求提供了完美的话语空间ꎬ从而使内在精神世界与外在现实生活形成一股巨大的张力ꎬ最终使人意识到自身潜藏的㊁被理性所压抑的本真意识ꎮ二、独特的叙事诉求«人面桃花»以梦境的形式展现作者独特的叙事诉求ꎮ作者在文中采用虚实相生的手法ꎬ将虚幻的梦境和真实的现实相融合ꎬ使文本浸润在一股难以言喻的诡秘氛围之中ꎮ胡河清曾评价格非: 格非者ꎬ灵气所锺之异才也ꎮ他不仅处事有机心ꎬ且秉赋颇高ꎬ能闻天籁ꎬ所以有此诡秘的叙述语调就非咄咄怪事了ꎮ [4]可见这种诡秘氛围的来源正是格非本人区别于其他叙述者的独特叙事风格ꎬ而 梦 在格非的«人面桃花»中正是这种诡秘叙事风格的最佳反映ꎮ在他的文本中ꎬ梦总是以以下两种叙事形式展现作者独特的叙事诉求:第一ꎬ以梦指向现实ꎬ表现作者希望以梦境指引现实的叙事期待ꎮ梦境之所以能够成为文本中重要元素ꎬ是因为梦境最不具有欺骗性ꎮ它总能最真实地展现人物内心的需求ꎬ从而为文本提供一重比现实更加真实的叙事路径ꎮ文本中秀米梦到的葬礼情景与现实中真正参加的葬礼一模一样ꎻ小东西在梦中迷迷糊糊地说要下雨了ꎬ屋顶便立刻响起了雨声ꎮ这些梦境都真实地指向现实世界ꎬ成为现实世界的指导ꎬ为文本提供了另一重叙事空间ꎬ这一重叙事空间是比现实空间更为真实ꎮ它使文本产生了双重叙事意义ꎬ以现实反衬梦境的真实ꎬ从而使读者进入文本人物更加真实的情感体验和精神世界ꎮ第二ꎬ梦与现实融合ꎬ表现作者有意虚化梦境与现实界限的意图ꎮ以梦境作为文本叙事线索ꎬ使得整篇小说都弥漫着一股诡秘色彩ꎬ进而深刻地展现人与世界㊁与命运难以言喻的勾连关系ꎮ在«人面桃花»中ꎬ常常出现 尽管她现在是清醒的ꎬ但却未尝不是一个更大㊁更遥远的梦的一部分 [2] 所有这些事ꎬ只不过是她在轿内打了一个盹ꎬ做的一个梦 [2] 你有的时候会从梦中醒过来ꎬ可有的时候ꎬ你会醒在梦中ꎬ发现世上的一切才是真的做梦 [2]这样的句子ꎮ文本中的主人公总是在总是在怀疑现实与梦境的虚实关系ꎬ认为现实不过是一场巨大的梦ꎮ这其实是作者在有意虚化梦境和现实之间的界限ꎮ他认为梦境与现实或许本没有那么大的差异性ꎬ也不具有明确清晰的分界线ꎮ将现实与梦境相互映照ꎬ不仅离间了读者在阅读时的真实感ꎬ更使作品增添了浓厚的虚幻色彩ꎮ他仿佛是故意将整部作品置于一个巨大的梦境中ꎬ时刻借主人公的感受来提醒读者不要过分沉溺其中ꎮ格非正是以这样超脱现实的笔法展现自己寄予在作品中的独特叙事诉求ꎮ这显然有他早期作品中现代性的延续ꎬ但却并非全部ꎮ在他的笔下ꎬ梦境作为«人面桃花»中的关键意象ꎬ呈现出了比现实更多的真实性ꎮ这种梦境真实是文本的画外之音ꎬ是庞大历史的一部分ꎬ更是作者真正的创作意图ꎮ它能够真正表现格非的创作诉求ꎬ或许他本身就在期待以这种虚幻的方式使自己的文本与读者产生某种对话关系ꎬ从而使读者理清一条更为靠近他创作意图的叙述道路ꎬ而不是单纯地故弄玄虚ꎬ刻意虚化文本831第1期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2019年脉络ꎬ混淆梦境与现实的关系ꎮ三、情节的多重建构«人面桃花»以梦境的形式对文本情节进行多重建构ꎮ读者在阅读文本过程中ꎬ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宿命感ꎬ觉得文本中的人物仿佛都被牵上了一条命运之绳ꎬ而这条绳正是梦境ꎮ梦境对文本情节的建构首先体现在梦是小说中 乌托邦 桃花源 式生存状态的象征ꎮ文本以梦作为情节的核心要素ꎬ全文都围绕 梦 进而展开ꎮ无论是将生活比喻成巨大的梦ꎬ还是文中那两句关键诗句 未谙梦里风吹灯ꎬ可忍醒时雨打窗 [2]ꎬ都是文本情节的一种重要构建ꎮ 未谙梦里风吹灯ꎬ可忍醒时雨打窗 是格非在文本最后部分中创作的诗句ꎬ既是秀米在人生最后的内心写照ꎬ也是全文的核心情节概括ꎮ作者借这一 梦 一 醒 ꎬ侧面展现人物徒劳半生虽渴望建立理想生存世界ꎬ苦心经营却仍毁于一旦的苍凉之感ꎮ这其实是格非由多种文本形式实验转入对古典㊁历史探索ꎬ将现代性与历史性进行的完美杂糅后的象征性情节构建ꎮ他将梦作为情节构建的核心意象ꎬ将它置于结构金字塔的顶端ꎬ以虚境的形式使其在文本中一以贯之地呈现ꎮ其次ꎬ梦境虽然作为虚幻的存在ꎬ却能够推动情节发展ꎬ改变人物心理历程ꎬ甚至改变人物人生走向ꎮ文本中ꎬ少女秀米开始正视自己的情感需要ꎬ 不管表哥说什么ꎬ她都答应ꎻ不管表哥做什么ꎬ她的眼睛和心都将保持沉默 [2]ꎬ正是发生在她窥见自己对张季元产生情感冲动的梦境之后ꎮ可以说ꎬ正是由于那场突如其来的奇怪春梦ꎬ才导致秀米正视自己内心的真实诉求ꎬ从而使她的 人生道路发生了偏转ꎬ一头扎进了中国近代史的惊涛骇浪ꎮ [5]这显然是对秀米的一生都具有决定性意义ꎻ而大金牙的母亲反对大金牙参加革命也是因为她昨晚梦见大金牙的爹 坟头上落了一群白鹤ꎬ这是不祥之兆ꎬ只怕这事就应验在你的身上ꎮ [2]梦中出现的白鹤作为不详物ꎬ使大金牙的母亲更加坚定地反对儿子参加革命ꎮ可见ꎬ梦境在文本中虽作为虚境存在ꎬ但却能够引领实境中人物的心理状态ꎬ为文本情节发展起到推动作用ꎮ最后ꎬ梦在文本结构中起到全方位构建情节的作用ꎮ梦作为虚境暗线与现实实境明线相互映衬出现在文本中ꎬ与实境交替形成二重情节线索构建文本结构ꎬ从而使文本结构趋向完整ꎮ如在文本第二部分ꎬ 总揽把 王观澄托梦于秀米ꎬ以梦境叙事透露自己并不是如传闻中病死而是被人迫害致死ꎮ作者大可以借某个人物之口使读者直接明晰真相ꎬ却以梦境作为叙事手段ꎬ侧面暗示王观澄的死因ꎬ进而以韩六的观察作为佐证ꎬ为文本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ꎮ不仅如此ꎬ作者还会将梦境与实境相对照ꎬ形成强烈的反差冲击ꎮ秀米再次回到普济后便开始构建自己 乌托邦 式家园的理想ꎬ但普济百姓却并不理解她的举动ꎬ甚至妖魔化秀米ꎬ妖魔化革命ꎮ文中老虎梦见秀米的屋子摆设 屋子里光线暗淡ꎮ木椅㊁梳妆台㊁屏风㊁雕花大床㊁摆着花瓶的条案ꎬ都坚硬如铁ꎬ泛着冷冷的光 [2]ꎬ这样的描述表现了普济百姓对于秀米这个革命者的形象异化ꎮ他们认为秀米爱享奢华且生性残酷ꎬ因此房间灯光必是黑暗且家具也一定跟她一样高贵且冷冷的ꎮ但当老虎真正走进秀米的屋子才发现ꎬ 这个房间与他的梦中所见完全不同ꎮ 没有黑漆描金的大屏风ꎬ没有光滑锃亮的花梨木桌椅ꎬ没有镶着金边的镜子ꎬ没有鸡血红花瓶ꎮ他留意到ꎬ校长睡的那张床也是那么的寒碜ꎬ蚊帐打着补丁ꎬ床脚绑着麻绳ꎬ床上被褥凌乱ꎬ床前有一块简易的踏板ꎬ上面搁着一双黑布的阔口棉鞋ꎮ [2]虚境与实境对照所形成的巨大反差ꎬ使文本结构更加丰满的同时ꎬ也更为生动地表现出了理想革命者在面对现实世界时产生的无奈窘境ꎮ格非在文本多处以梦境展现现实困境ꎬ使梦成为与现实世界成为 双轨制 的存在ꎮ这都体现了他在文本建构上的匠心独运ꎮ梦境作为«人面桃花»中一以贯之的重要意象ꎬ现实世界相互映照ꎬ为文本构筑了完整的叙事空间ꎮ它既表现了人物内心深处的精神追求以及作者独特的叙事诉求ꎬ又在结构上呈现多重形态ꎬ丰富延伸文本的情节结构ꎬ以巧妙的构思丰富了文本叙事形态ꎮ因此ꎬ«人面桃花»作为格非 江南三部曲 的第一部ꎬ实现了现代性与历史性的完美融合ꎬ体现了他由文学形式实验转向对古典历史追问与探寻的成功ꎮ参考文献[1]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M].林骧华ꎬ译.上931㊀第1期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论格非«人面桃花»中梦境叙事空间的构筑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2019年㊀海:上海译文出版社ꎬ1983(6).[2]格非.人面桃花[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ꎬ2004(99).[3]王文革.文学梦的审美分析[M].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ꎬ2006(259).[4]胡河清.论格非㊁苏童㊁余华与术数文化[J].中国现代㊁当代文学研究ꎬ1992(11).[5]张清华.春梦㊁革命以及永恒的失败与虚无 从精神分析的方向论格非[J].当代作家评论ꎬ2012(2).ConstructionofDreamNarrativeSpaceCreatedbyGeFeiinHisACharmingFaceAmongPeachBlossomsWangXu(SchoolofLiteratureꎬLiaoningNormalUniversityꎬDalianꎬLiaoning116081ꎬChina)Abstract:PeachblossominHumanFaceiswrittenbyGeFei's.Thedreamlandꎬasanimportantimageꎬcreatesapowerfulaestheticforceinthenarrativespaceꎬforminga"two-track"narrativespaceintheprocessofmutualreflectionoftherealworld.Theconstructionofthedreamlandnotonlyincreasesthecharacter sinnerspiritualpursuitꎬbutalsofurtherextendstheplotofthetextstructureandenrichesthetextnarrativeformꎬwhichembodiesthetransitionfromtheliteraryformexperimenttotheclassicalhistorysearch.Keywords:GeFeiꎻPeachblossominHumanFaceꎻdreamlandꎻnarrativespaceClassNo.:I206.7㊀㊀㊀㊀㊀㊀㊀DocumentMark:A(责任编辑:蔡雪岚) 041第1期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20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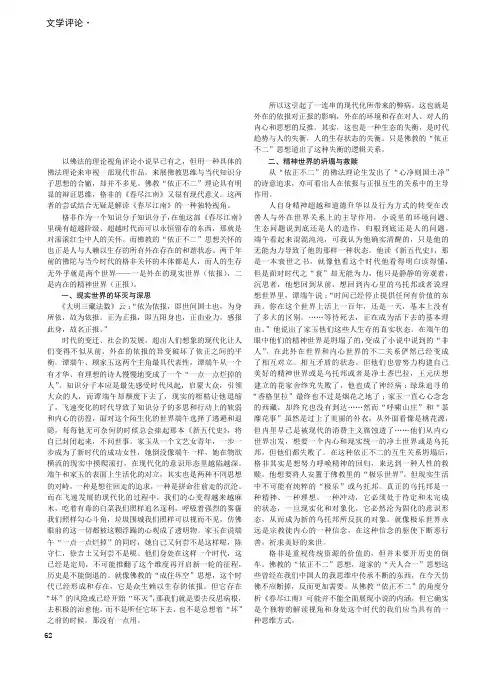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从佛教“依正不二”思想看境与人——评格非《春尽江南》宋新乐 山东理工大学作者简介:宋新乐,山东理工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专业方向为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2-062-01以佛法的理论视角评论小说早已有之,但用一种具体的佛法理论来审视一部现代作品,来展佛教思维与当代知识分子思想的合辙,却并不多见。
佛教“依正不二”理论具有明显的辩证思维,格非的《春尽江南》又很有现代意义。
这两者的尝试结合无疑是解读《春尽江南》的一种独特视角。
格非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他这部《春尽江南》里确有超越阶级、超越时代而可以永恒留存的东西,那就是对滚滚红尘中人的关怀。
而佛教的“依正不二”思想关怀的也正是人与人赖以生存的所有外在存在的和谐状态。
两千年前的佛陀与当今时代的格非关怀的本体都是人,而人的生存无外乎就是两个世界——一是外在的现实世界(依报),二是内在的精神世界(正报)。
一、现实世界的坏灭与深思《大明三藏法数》云:“依为依报,即世间国土也,为身所依,故为依报。
正为正报,即五阳身也,正由业力,感报此身,故名正报。
”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超出人们想象的现代化让人们变得不似从前。
外在的依报的异变破坏了依正之间的平衡。
谭端午、顾家玉这两个主角最具代表性,谭端午从一个有才华、有理想的诗人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一点一点烂掉的人”,知识分子本应是最先感受时代风起,启蒙大众,引领大众的人,而谭端午却颓废下去了,现实的桎梏让他退缩了,飞速变化的时代导致了知识分子的多思和行动上的软弱和内心的彷徨,面对这个陌生化的世界端午选择了逃避和退隐,每每他无可奈何的时候总会捧起那本《新五代史》,将自己封闭起来,不问世事。
家玉从一个文艺女青年,一步一步成为了新时代的成功女性,她倒没像端午一样,她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中摸爬滚打,在现代化的意识形态里越陷越深。
端午和家玉的表面上生活化的对立,其实也是两种不同思想的对峙,一种是想往回走的追求,一种是拼命往前走的沉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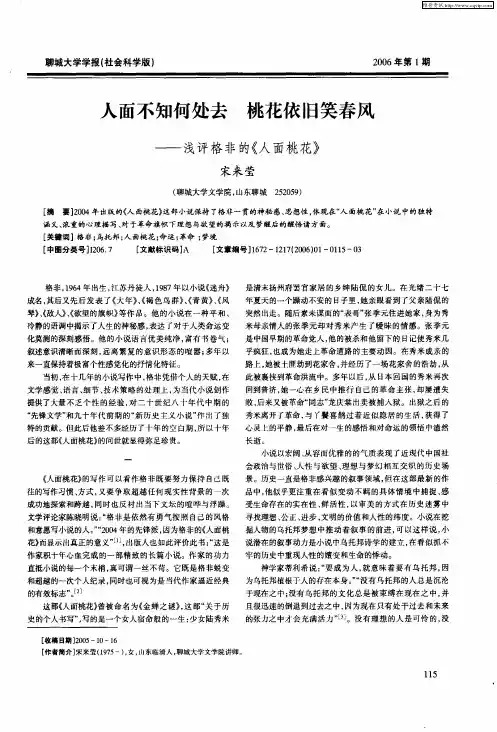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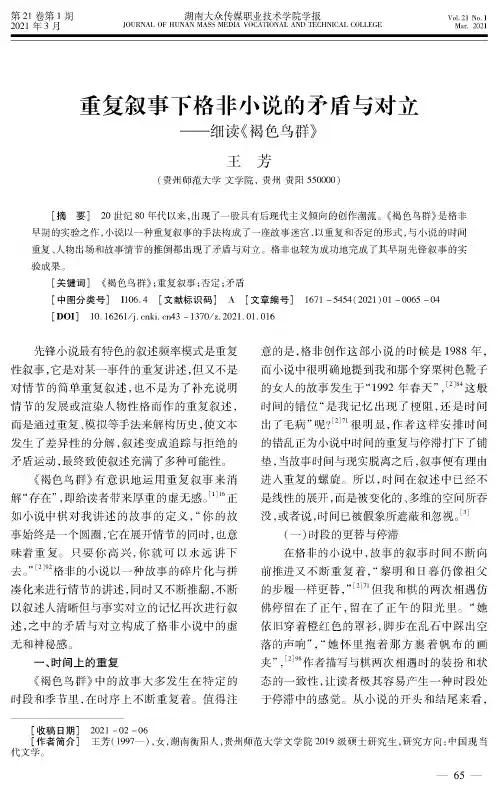
第21卷第1期2021年3月JOURNAL0F H点懿众传媒职业誌学院学U a SLECE Vol.21No.1Mar.2221重复叙事下格非小说的矛盾与对立——细读《褐色鸟群》王芳(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2)[摘要]20世纪82年代以来,出现了一股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创作潮流。
《褐色鸟群》是格非早期的实验之作,小说以一种重复叙事的手法构成了一座故事迷宫,以重复和否定的形式,与小说的时间重复、人物出场和故事情节的推倒都出现了矛盾与对立。
格非也较为成功地完成了其早期先锋叙事的实验成果。
[关键词]《褐色鸟群》;重复叙事;否定;矛盾[中图分类号]11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454(2021)01-0065-04[DOI]10.16261/43-1370/z.2021.06016先锋小说最有特色的叙述频率模式是重复性叙事,它是对某一事件的重复讲述,但又不是对情节的简单重复叙述,也不是为了补充说明情节的发展或渲染人物性格而作的重复叙述,而是通过重复、模拟等手法来解构历史,使文本发生了差异性的分解,叙述变成追踪与拒绝的矛盾运动,最终致使叙述充满了多种可能性。
《褐色鸟群》有意识地运用重复叙事来消解“存在”,即给读者带来厚重的虚无感丿66正如小说中棋对我讲述的故事的定义,“你的故事始终是一个圆圈,它在展开情节的同时,也意味着重复。
只要你高兴,你就可以永远讲下去。
”2"2格非的小说以一种故事的碎片化与拼凑化来进行情节的讲述,同时又不断推翻,不断以叙述人清晰但与事实对立的记忆再次进行叙述,之中的矛盾与对立构成了格非小说中的虚无和神秘感。
一、时间上的重复《褐色鸟群》中的故事大多发生在特定的时段和季节里,在时序上不断重复着。
值得注意的是,格非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是1688年,而小说中很明确地提到我和那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的故事发生于“1992年春天”严这般时间的错位“是我记忆出现了梗阻,还是时间出了毛病”呢?[2]71很明显,作者这样安排时间的错乱正为小说中时间的重复与停滞打下了铺垫,当故事时间与现实脱离之后,叙事便有理由进入重复的螺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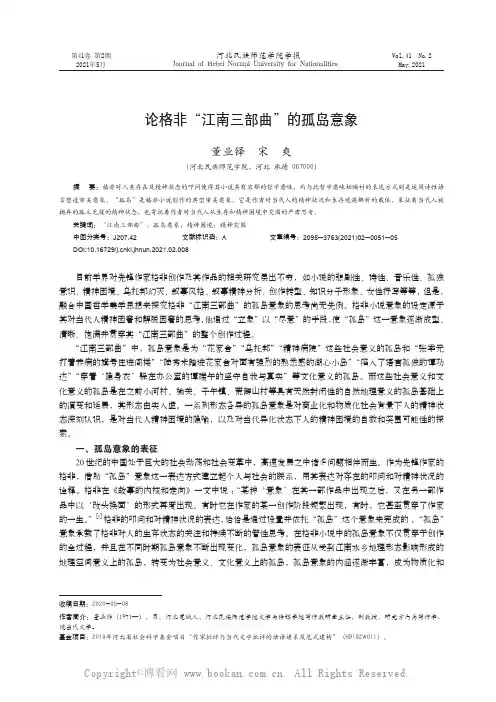
第41卷 第2期2021年5月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Vol.41 No.2May.2021收稿日期:2020-05-08作者简介:董业铎(1971—),男,河北宽城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写作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写作学、现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2019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作家批评与当代文学批评的话语谱系及范式建构”(HB19ZW011)。
目前学界对先锋作家格非创作及其作品的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如小说的悲剧性、诗性、音乐性、孤独意识、精神困境、乌托邦幻灭、叙事风格、叙事精神分析、创作转型、知识分子形象、女性抒写等等,但是,融合中国哲学美学思想来探究格非“江南三部曲”的孤岛意象的思考尚无先例。
格非小说意象的设定源于其对当代人精神困窘和解脱困窘的思考,他通过“立象”以“尽意”的手段,使 “孤岛”这一意象逐渐成型、清晰、饱满并贯穿其“江南三部曲”的整个创作过程。
“江南三部曲”中,孤岛意象是为“花家舍”“乌托邦”“精神病院”这些社会意义的孤岛和“张季元打着养病的旗号住进阁楼”“陆秀米踏进花家舍对面有强烈的熟悉感的湖心小岛”“陷入了语言孤独的谭功达”“穿着‘隐身衣’躲在办公室的谭端午的坚守自我与真实”等文化意义的孤岛。
而这些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孤岛是在之前小河村、榆关、子午镇、荒僻山村等具有天然封闭性的自然地理意义的孤岛基础上的演变和延展,其形态由实入虚。
一系列形态各异的孤岛意象是对商业化和物质化社会背景下人的精神状态深刻认识,是对当代人精神困境的隐喻,以及对当代异化状态下人的精神困境的自救和突围可能性的探索。
一、孤岛意象的表征20世纪的中国处于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变革中,高速发展之中诸多问题相伴而生。
作为先锋作家的格非,借助“孤岛”意象这一表达方式建立起个人与社会的联系,用其表达对存在的叩问和对精神状况的诠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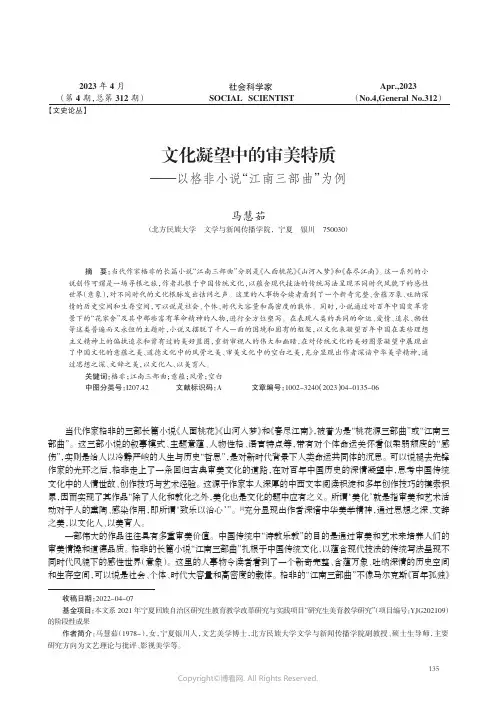
【文史论丛】社会科学家SOCIAL SCIENTIST 2023年4月(第4期,总第312期)Apr.,2023(No.4,General No.312)收稿日期:2022-04-07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研究生美育教学研究”(项目编号:YJG202109)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马慧茹(1978-),女,宁夏银川人,文艺美学博士,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批评、影视美学等。
文化凝望中的审美特质———以格非小说“江南三部曲”为例马慧茹(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宁夏银川750030)摘要:当代作家格非的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分别是《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
这一系列的小说创作可谓是一场寻根之旅,作者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蕴含现代技法的传统写法呈现不同时代风貌下的感性世界(意象),对不同时代的文化根脉发出诘问之声。
这里的人事物令读者看到了一个新奇完整、含蕴万象、吐纳深情的历史空间和生存空间,可以说是社会、个体、时代大容量和高密度的载体。
同时,小说通过对百年中国变革背景下的“花家舍”及其中那些富有革命精神的人物,进行全方位塑写。
在表现人类的共同的命运、爱情、追求、牺牲等这类普遍而又永恒的主题时,小说又摆脱了千人一面的困境和固有的框架,以文化来凝望百年中国在某些理想主义精神上的偏执追求和曾有过的美好蓝图,重新审视人的伟大和幽暗,在对传统文化的美好图景凝望中展现出了中国文化的意蕴之美、道德文化中的风骨之美、审美文化中的空白之美,充分显现出作者深谙中华美学精神,通过思想之深、文辞之美,以文化人、以美育人。
关键词:格非;江南三部曲;意蕴;风骨;空白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40(2023)04-0135-06 当代作家格非的三部长篇小说《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被誉为是“桃花源三部曲”或“江南三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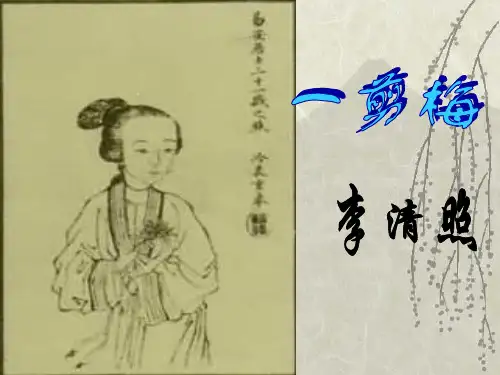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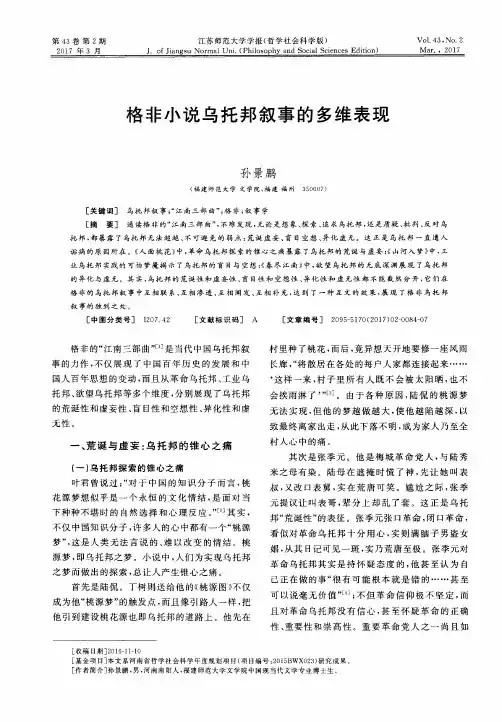
语文课堂YuWenKeTang教师·TEACHER2019年4月Apr.2019037意象,属于诗学范畴,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席位。
格非的小说善于运用大量意象,这些意象的使用不仅蕴含作者广阔的心理能量,又带有鲜明的可变性,使他的小说在语言表层意义的基础上又蕴含着深层的意义[1]。
文章主要分析时间、梦境、自然和人物四大意象在文中的作用。
一、时间意象时间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文学作品要依照时间顺序发生发展。
然而,物理上的时间是一维且整一的,读者必须按照历史顺序解读故事情节;文学上的时间则是多维且破碎的,读者好比乘坐时光机感受时间的无限循环、生命的无处不在和个体的多重身份。
格非的《锦瑟》就是典型的“循环型”意象。
时间不是解读作品的线索,而是隐藏于小说结构和角色之后的主题之一。
《锦瑟》真正的线索是主人公冯子存扮演的四种角色的四种经历, 作者通过四个不同角色的自然交替有条不紊地向我们讲述冯子存的四个世界和四种人生。
隐士冯子存虽然归隐村庄,却好像仍然置身于世俗尘网,无法摆脱时间的宿命。
他认为混乱的时间模糊了现实与梦境的边界,因此他一直恍惚在过去与现在的时光中,最终敌不过死亡的呼唤。
考生冯子存胸怀大志,立志考取功名,然而乏味的赶考旅途、枯燥幽静的考场和略显平庸的考题时常让他恍如梦中,置身于时间之外,最终应验了临行前的预言而客死他乡。
茶商冯子存虽然一生富贵荣耀,终究逃不开宿命的安排,游离于时间轨道的他怀揣对生命的留恋而病死病榻。
国君冯子存面对敌军攻城、儿子逼宫的严峻形势,写下“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一联,最后梦中之梦又返回到隐士冯子存的故事。
四个冯子存表面上生活在自己独立的时间轨道,实则与其他的时间轨道时而交汇、时而相撞、时而冲突、时而联络。
正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四,四生一,四个生命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故事就在这个圆形结构中发生并发展。
宿命的时间又赶上了冯子存死亡的脚步,但另一个梦中复活的虚空同时向他敞开。
2021.01名家研究·新纪实09论格非《江南三部曲》中先锋叙事策略的延续□ 杨 文武汉大学文学院[摘 要] 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格非早期作品以对小说结构形式、叙事策略的大胆探索和实验蜚声文坛。
新世纪问世的《江南三部曲》有意向中国传统小说写作范式回归,同时杂糅了先锋文学的某些叙事元素,在叙事策略上表现出一种内在延续性,这与中国传统叙事资源相结合,为当代中国文学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 格非 江南三部曲 叙事策略 内在延续[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003(2021)01-0009-0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先锋文学的式微和文学“向内转”的趋向,中国传统文学叙事资源备受关注。
面对新的时代转折和多重文化语境,格非对先锋时期的创作予以反思,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学中寻找突围之路,《江南三部曲》便是他向传统回归的鼎立之作。
与先锋时期乐于讲述支离破碎的故事不同,《江南三部曲》描写了20世纪中国云谲波诡的历史图景下家族三代人的理想追寻、精神嬗变与命运沉浮,内容的连贯性和内在的逻辑性有所增强,体现了格非向中国传统文学的靠拢;叙事上采取的诸如空缺与重复的设置、多重叙事视角的转换、对宏大历史叙事的解构,表明了其文学创作中对先锋叙事策略的一种内在延续。
一、空缺与重复“故事观念的彻底革新是从对传统故事的两大特性(时间的延续和因果关系)提出强烈的质疑开始的”,《江南三部曲》的故事被置于一个前后相继的历史框架之下,而格非有意打破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结构,将“空缺”与“重复”在文本中加以叙事策略的改造,以“碎片化”的历史记忆、隐喻式意象的重复来表现历史的真实,进而引发对存在、欲望、理想等问题的追问与思考。
叙事内容的“省略”所引起的“空缺”并非使故事内容中断,“作为叙事技巧的有意省略虽然在文本中是空白,但它参与故事的运作,并在文本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它的缺席实际意味着在场,由于这种省略或空白的存在,故事的疆域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
论“江南三部曲”中的“边缘人”形象作者:张林来源:《青年文学家》2019年第02期摘; 要:格非的力作“江南三部曲”又被称为“乌托邦三部曲”,他用细致而充满诗意的笔调描写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追梦的心路历程。
这些知识分子或执着,或疯癫,或放浪形骸,或消极避世。
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追寻理想,无一不具有“边缘人”气质。
这些“边缘人”的命运与他们追寻的“乌托邦”理想紧密相关,他们在理想与欲望的泥潭中挣扎,最后成为了岸上的边缘人,以理性的目光审视这一切。
本文把这些“边缘人”分为执着追梦的痴狂者,天真无邪的理想者和独守内心的避世者。
这些“边缘人”所遭受的精神困境是具有普世意义的。
关键词:江南三部曲;理想;乌托邦;边缘人作者简介:张林(1993-),女,汉族,江西新余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学学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2-0-01“江南三部曲”中“边缘人”形象的反复出现,体现了格非对近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和精神困境的关注。
这些知识分子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望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从而成为了与世界格格不入的“边缘人”。
为一幅“桃源图”疯癫出走的陆侃,隐居山野的教书先生丁树则,为爱革命的陆秀米,异想天开的县长谭功达,蜗居地方志办公室,终日无所事事的“废人”谭端午都是典型的“边缘人”形象,他们在寻梦道路上不断求索,带着不被理解的激情孤独地前行。
1、执着追梦的痴狂者罢官回家的士大夫陆侃回到普济,终日侍弄花草,赋诗饮酒,俨然一副隐者形象。
但是他的现实处境和心理状态却被丁树则一语道破:“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盛世开太平。
”这样的人生理想一直被保留在陆侃的心中,即使幽居普济,他的心依然在官场,在仕途。
在得到一幅桃源图之后,他妄想在普济这样一个地方实现理想中的桃源盛景,想建一条风雨长廊来把家家户户连接起来。
第40卷第2期2019年2月哈尔滨学院学报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V〇1.40 No.2Feb.2019[文章编号]1004 —5856(2019)02 —0101 —04格非小说《青黄》的“多重主述”与“多元解码”汪岚(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福建福州350002)[摘要]中国作家格非的小说《青黄》通过小说中不同人物的“回忆”来推动叙事,这种方法类似于推理小说的“多重主述”手法。
与推理小说不同的是,格非的“多重主述”更凸显了 “多元解码”的可能性,《青黄》的价值不是传统文学里对故事“意义”的建构,而是催生无限“意义”的可能性。
文章针对“多重主述”的开放性,对《青黄》中“回忆叙事”进行多元层面的“解码”,并以《青黄》为样本,来分析中国“先锋派”小说中的“可阐释性”价值。
[关键词]“多重主述”;回忆叙事;可阐释性[中图分类号]1207. 42 [文献标识码]A语言,从诞生之日起,就背负着重要的使命,人类为繁复的词汇规划性别,褒贬、意义 ……让语言渗透强烈的人性痕迹以及情感肌理。
人类用语言去表达自身的感情色彩、身份 地位、文化涵养,用语言去“建构”情感、思考以 及亲历的生活。
“建构”包含两个方面一有 意识和无意识。
“回忆”就是一种“无意识”建 构的方式,当个体在回忆经历的事件时,无论时 间久远,只要用语言去呈现回忆,就无法完整还 原,因为其中增加了个人自我经历的判断经验和语言经验,将回忆加工成经验式建构。
格非的代表作《青黄》就是利用这种“经验 式建构”,即通过故事中不同人物的“回忆”来 完成一个充满悬念的故事,这种方法类似推理 小说中的“多重主述”手法。
“多重主述”源于 英国侦探小说之父威尔基•柯林斯巅峰时期的 代表作《月亮宝石》。
作者让每个人物分别用自己的回忆接龙叙述一个复杂至极的故事,直 至真相大白,结局出人意料。
柯林斯企图通过;多元解码doi:10. 3969/j.issn. 1004 - 5856. 2019. 02. 023“多重主述”的形式把一个繁琐的结解开,这种 叙事方式让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