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陈染小说中的缺失意境——以《私人生活》《无处告别》为例
- 格式:pdf
- 大小:285.46 KB
- 文档页数:3

2012.05学教育4“私人写作”、“身体写作”与女性文学——陈染、林白小说再解读魏天真经过时间的淘洗,呈现在现时读者眼中的作品,相比它处在生成环境中的原初面目,会更纯粹、客观化,现时读者的眼光和需求也肯定与当初读者的很不一样。
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在“当下现实”中被重新评估;这些评估和重新评估本身,也就是文学批评或接受活动,也要被一再地审视,这样许多文学现象乃至社会问题才可以得到更深入具体的理解。
对女性小说的再解读正是基于这些理由。
“私人写作”、“身体写作”曾经风行一时,并经常被批评家置于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的框架下予以讨论。
而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虽然其影响日渐深广,读者大众对它们的理解也未必全然真实。
本文选取当初反响强烈的几篇作品进行重读,希望对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的认知更加理性、如实。
女性意识与超性别眼光如果要将陈染当作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那么,可以代表其“女性主义”特征的作品是《无处告别》,而不是《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等引起极大关注的所谓“描写身体”的作品。
无论从哪方面看,这篇小说也的确是陈染的最成熟和优美的作品之一。
它可以再次说明,只要是文学作品,无论被划归何种流派或阵营,无论打什么旗号,那些使它成为“优秀”之作的素质总是超越个人立场、思想观念和表现方式的限制,而契合阅读者各自的情感或美感体验,导致我们心灵的激荡。
和陈染的其他小说相似,《无处告别》的题材和人物、叙事和作者的态度(全凭我们读者揣摩和猜测出),显示出那种人们称之为“小资情调”或精神贵族式的趣味。
这个小说文本充斥着“雅谑”,我们可以从潇洒率性的语言表达、透着急智而又暗藏机锋的人物对话中,体察到作者的这种趣味;看到在清高自傲而又无奈无助的女主人公之上,有一双不动声色的眼睛。
事实上,陈染的许多小说表明,作者惯于以这种“趣味”来组织素材,安排故事和描写人物。
不过这篇小说自有它的独到之处,而且并未被充分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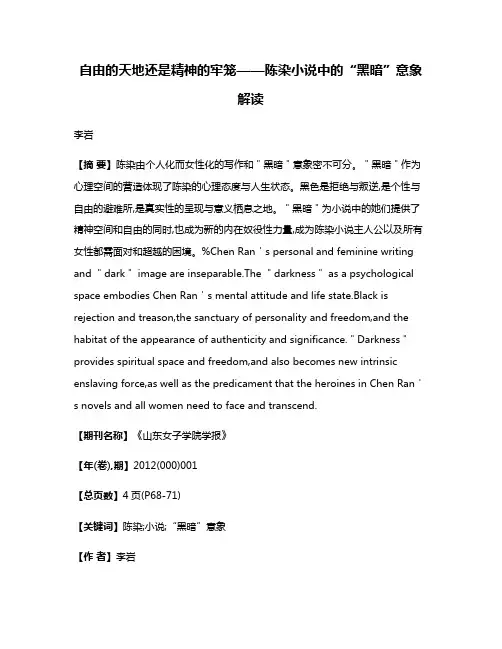
自由的天地还是精神的牢笼——陈染小说中的“黑暗”意象解读李岩【摘要】陈染由个人化而女性化的写作和"黑暗"意象密不可分。
"黑暗"作为心理空间的营造体现了陈染的心理态度与人生状态。
黑色是拒绝与叛逆,是个性与自由的避难所,是真实性的呈现与意义栖息之地。
"黑暗"为小说中的她们提供了精神空间和自由的同时,也成为新的内在奴役性力量,成为陈染小说主人公以及所有女性都需面对和超越的困境。
%Chen Ran's personal and feminine writing and "dark" image are inseparable.The "darkness" as a psychological space embodies Chen Ran's mental attitude and life state.Black is rejection and treason,the sanctuary of personality and freedom,and the habitat of the appearance of authenticity and significance."Darkness"provides spiritual space and freedom,and also becomes new intrinsic enslaving force,as well as the predicament that the heroines in Chen Ran's novels and all women need to face and transcend.【期刊名称】《山东女子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00)001【总页数】4页(P68-71)【关键词】陈染;小说;“黑暗”意象【作者】李岩【作者单位】滨州学院,山东滨州25660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7作为“个人化”写作的代表性作家,陈染把自我当做最大的写作资源进行开掘,她的个人化和女性书写,孤独及自恋,忧郁而与世隔绝的精神探索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氛围和梦魇,弥漫在几乎其所有的作品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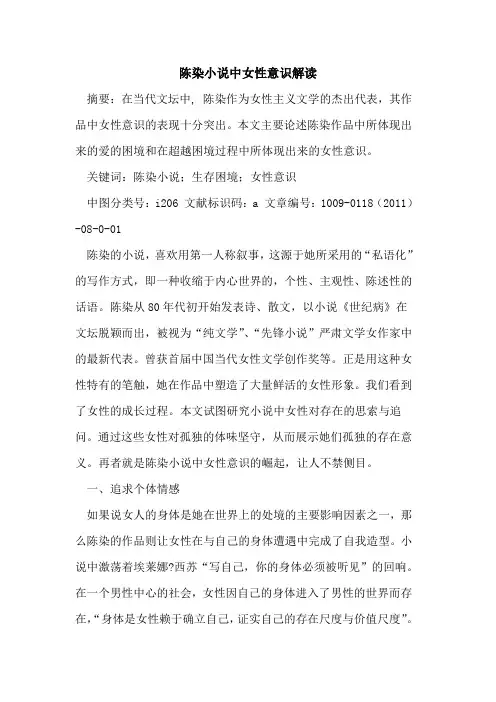
陈染小说中女性意识解读摘要:在当代文坛中, 陈染作为女性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作品中女性意识的表现十分突出。
本文主要论述陈染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爱的困境和在超越困境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陈染小说;生存困境;女性意识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8-0-01陈染的小说,喜欢用第一人称叙事,这源于她所采用的“私语化”的写作方式,即一种收缩于内心世界的,个性、主观性、陈述性的话语。
陈染从80年代初开始发表诗、散文,以小说《世纪病》在文坛脱颖而出,被视为“纯文学”、“先锋小说”严肃文学女作家中的最新代表。
曾获首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奖等。
正是用这种女性特有的笔触,她在作品中塑造了大量鲜活的女性形象。
我们看到了女性的成长过程。
本文试图研究小说中女性对存在的思索与追问。
通过这些女性对孤独的体味坚守,从而展示她们孤独的存在意义。
再者就是陈染小说中女性意识的崛起,让人不禁侧目。
一、追求个体情感如果说女人的身体是她在世界上的处境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那么陈染的作品则让女性在与自己的身体遭遇中完成了自我造型。
小说中激荡着埃莱娜?西苏“写自己,你的身体必须被听见”的回响。
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女性因自己的身体进入了男性的世界而存在,“身体是女性赖于确立自己,证实自己的存在尺度与价值尺度”。
陈染将这种价值尺度进一步凸现为一种解放、自由和摧毁男性伦理的女性欲望的标识。
在陈染的绝大部分小说中,女性性经历体验无疑是她写作的重心。
个体情感还表现为另一个词语——自恋。
对男性以及外界的极度失望使她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突出表现之一便是对自身躯体的关注与迷恋。
《无处告别》中的黛二,“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两膝曲着,侧身而卧,这姿势让她产生某种空虚,由于空虚,又产生某种幻想,又由于幻想,使她感到某种深刻的孤独。
”黛二极度自恋以至于她的朋友墨非觉得她不能一个人在河边漫步,怕她因自恋而跳下水拥抱自己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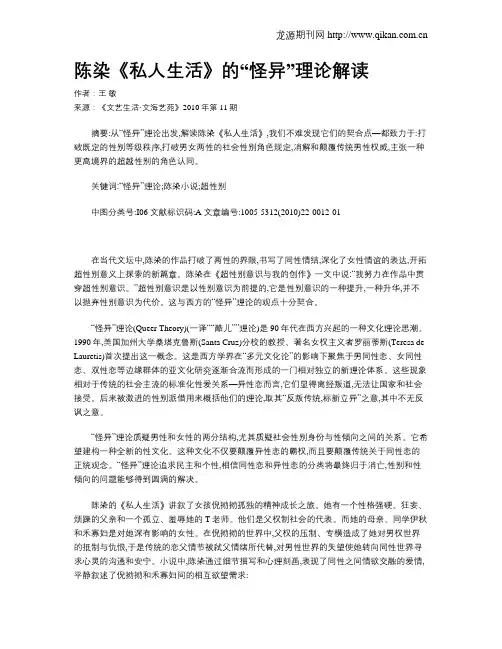
陈染《私人生活》的“怪异”理论解读作者:王敏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0年第11期摘要:从“怪异”理论出发,解读陈染《私人生活》,我们不难发现它们的契合点—都致力于:打破既定的性别等级秩序,打破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规定,消解和颠覆传统男性权威,主张一种更高境界的超越性别的角色认同。
关键词:“怪异”理论;陈染小说;超性别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2-0012-01在当代文坛中,陈染的作品打破了两性的界限,书写了同性情结,深化了女性情谊的表达,开拓超性别意义上探索的新篇章。
陈染在《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一文中说:“我努力在作品中贯穿超性别意识。
”超性别意识是以性别意识为前提的,它是性别意识的一种提升,一种升华,并不以抛弃性别意识为代价。
这与西方的“怪异”理论的观点十分契合。
“怪异”理论(Queer Theory)(一译““酷儿””理论)是9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文化理论思潮。
1990年,美国加州大学桑塔克鲁斯(Santa Cruz)分校的教授、著名女权主义者罗丽蒂斯(Teresa de Lauretis)首次提出这一概念。
这是西方学界在“多元文化论”的影响下聚焦于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等边缘群体的亚文化研究逐渐合流而形成的一门相对独立的新理论体系。
这些现象相对于传统的社会主流的标准化性爱关系—异性恋而言,它们显得离经叛道,无法让国家和社会接受。
后来被激进的性别派借用来概括他们的理论,取其“反叛传统,标新立异”之意,其中不无反讽之意。
“怪异”理论质疑男性和女性的两分结构,尤其质疑社会性别身份与性倾向之间的关系。
它希望建构一种全新的性文化。
这种文化不仅要颠覆异性恋的霸权,而且要颠覆传统关于同性恋的正统观念。
“怪异”理论追求民主和个性,相信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分类将最终归于消亡,性别和性倾向的问题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
陈染的《私人生活》讲叙了女孩倪拗拗孤独的精神成长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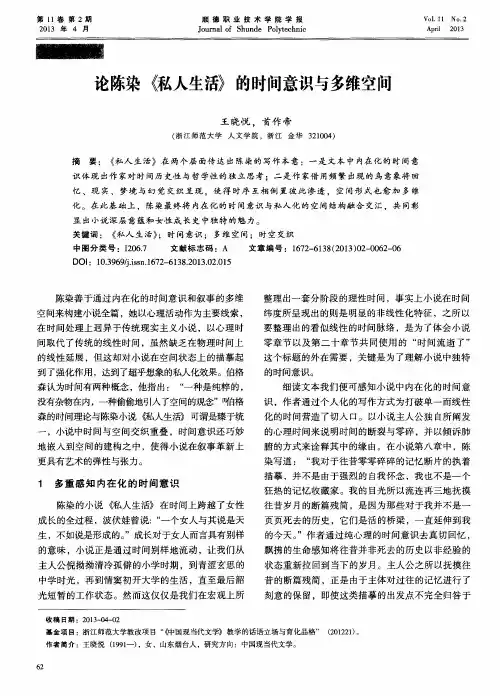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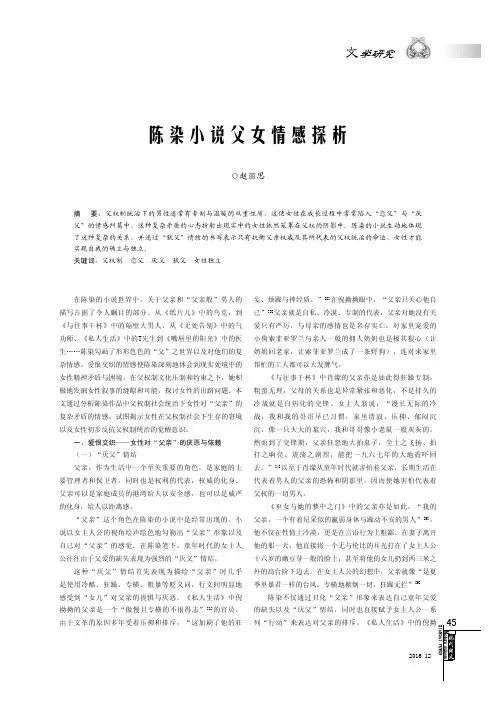
2016.12文陈染小说父女情感探析○赵丽思摘 要:父权制统治下的男性通常有专制与温暖的双重性质,这使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常常陷入“恋父”与“厌父”的情感纠葛中,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态折射出现实中的女性依然笼罩在父权的阴影中。
陈染的小说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复杂的关系,并通过“弑父”情结的书写表示只有抗衡父亲权威及其所代表的父权统治的命运,女性才能实现自我的确立与独立。
关键词:父权制 恋父 厌父 弑父 女性独立在陈染的小说世界中,关于父亲和“父亲般”男人的描写占据了令人瞩目的部分。
从《纸片儿》中的乌克,到《与往事干杯》中的隔壁大男人,从《无处告别》中的气功师、《私人生活》中的T先生到《嘴唇里的阳光》中的医生……陈染勾画了形形色色的“父”之世界以及对他们的复杂情感。
爱恨交织的情感使陈染深刻地体会到现实处境中的女性精神矛盾与困境。
在父权制文化压制和约束之下,她积极地发掘女性叙事的缝隙和可能,探讨女性的出路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陈染作品中父权制社会统治下女性对“父亲”的复杂矛盾的情感,试图揭示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下生存的窘境以及女性初步反抗父权制统治的觉醒意识。
一、爱恨交织——女性对“父亲”的厌恶与依赖(一)“厌父”情结父亲,作为生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是家庭的主要管理者和保卫者,同时也是权利的代表,权威的化身。
父亲可以是家庭成员的港湾给人以安全感,也可以是威严的化身,给人以距离感。
“父亲”这个角色在陈染的小说中是经常出现的。
小说以女主人公的视角绘声绘色地勾勒出“父亲”形象以及自己对“父亲”的感觉。
在陈染笔下,童年时代的女主人公往往由于父爱的缺失表现为强烈的“厌父”情结。
这种“厌父”情结首先表现为描绘“父亲”时几乎是使用冷酷、狂躁、专横、粗暴等贬义词,行文间明显地感受到“女儿”对父亲的畏惧与厌恶。
《私人生活》中倪拗拗的父亲是一个“傲慢且专横的不很得志”[1]的官员,由于文革的原因多年受着压抑和排斥,“这加剧了他的狂妄、烦躁与神经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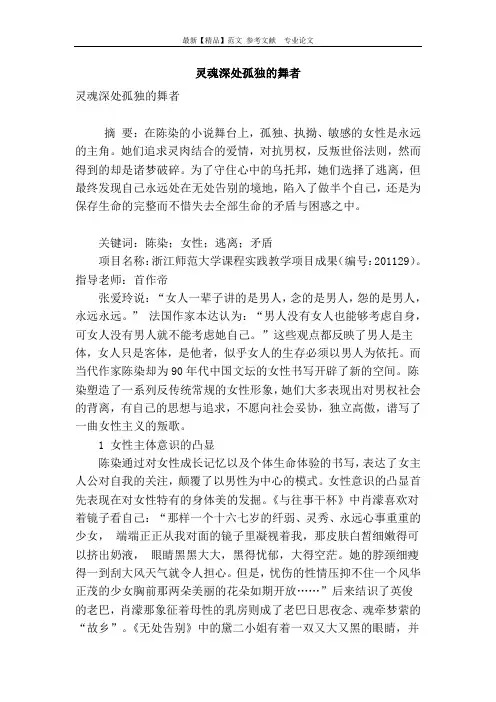
灵魂深处孤独的舞者灵魂深处孤独的舞者摘要:在陈染的小说舞台上,孤独、执拗、敏感的女性是永远的主角。
她们追求灵肉结合的爱情,对抗男权,反叛世俗法则,然而得到的却是诸梦破碎。
为了守住心中的乌托邦,她们选择了逃离,但最终发现自己永远处在无处告别的境地,陷入了做半个自己,还是为保存生命的完整而不惜失去全部生命的矛盾与困惑之中。
关键词:陈染;女性;逃离;矛盾项目名称:浙江师范大学课程实践教学项目成果(编号:201129)。
指导老师:首作帝张爱玲说:“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 法国作家本达认为:“男人没有女人也能够考虑自身,可女人没有男人就不能考虑她自己。
”这些观点都反映了男人是主体,女人只是客体,是他者,似乎女人的生存必须以男人为依托。
而当代作家陈染却为90年代中国文坛的女性书写开辟了新的空间。
陈染塑造了一系列反传统常规的女性形象,她们大多表现出对男权社会的背离,有自己的思想与追求,不愿向社会妥协,独立高傲,谱写了一曲女性主义的叛歌。
1 女性主体意识的凸显陈染通过对女性成长记忆以及个体生命体验的书写,表达了女主人公对自我的关注,颠覆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模式。
女性意识的凸显首先表现在对女性特有的身体美的发掘。
《与往事干杯》中肖濛喜欢对着镜子看自己:“那样一个十六七岁的纤弱、灵秀、永远心事重重的少女,端端正正从我对面的镜子里凝视着我,那皮肤白皙细嫩得可以挤出奶液,眼睛黑黑大大,黑得忧郁,大得空茫。
她的脖颈细瘦得一到刮大风天气就令人担心。
但是,忧伤的性情压抑不住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女胸前那两朵美丽的花朵如期开放……”后来结识了英俊的老巴,肖濛那象征着母性的乳房则成了老巴日思夜念、魂牵梦萦的“故乡”。
《无处告别》中的黛二小姐有着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并且她还赋予了这双眼睛丰富而混乱的内容。
在接待墨非前,黛二精心地为自己化妆,从具有迷濛神秘魅力的眼影到妩媚而性感的嘴唇,她都毫不疏忽。
在《私人生活》中倪拗拗的“不小姐”(胳膊)和“是小姐”(腿)像珊瑚石一样白皙,同时她还发现禾寡妇的乳房犹如桃子般嫩白而透明,像吐丝前的春蚕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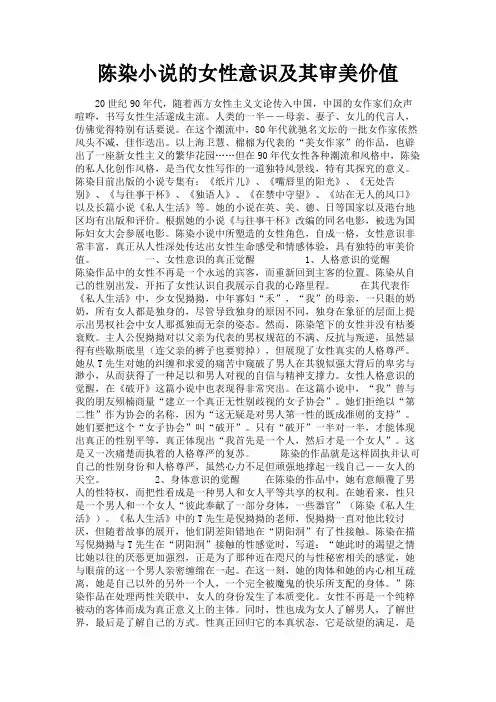
陈染小说的女性意识及其审美价值20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传入中国,中国的女作家们众声喧哗,书写女性生活遂成主流。
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的代言人,仿佛觉得特别有话要说。
在这个潮流中,80年代就驰名文坛的一批女作家依然风头不减,佳作迭出。
以上海卫慧、棉棉为代表的“美女作家”的作品,也辟出了一座新女性主义的繁华花园……但在90年代女性各种潮流和风格中,陈染的私人化创作风格,是当代女性写作的一道独特风景线,特有其探究的意义。
陈染目前出版的小说专集有:《纸片儿》、《嘴唇里的阳光》、《无处告别》、《与往事干杯》、《独语人》、《在禁中守望》、《站在无人的风口》以及长篇小说《私人生活》等。
她的小说在英、美、德、日等国家以及港台地区均有出版和评价。
根据她的小说《与往事干杯》改编的同名电影,被选为国际妇女大会参展电影。
陈染小说中所塑造的女性角色,自成一格,女性意识非常丰富,真正从人性深处传达出女性生命感受和情感体验,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一、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1、人格意识的觉醒陈染作品中的女性不再是一个永远的宾客,而重新回到主客的位置。
陈染从自己的性别出发,开拓了女性认识自我展示自我的心路里程。
在其代表作《私人生活》中,少女倪拗拗,中年寡妇“禾”,“我”的母亲,一只眼的奶奶,所有女人都是独身的,尽管导致独身的原因不同,独身在象征的层面上提示出男权社会中女人那孤独而无奈的姿态。
然而,陈染笔下的女性并没有枯萎衰败。
主人公倪拗拗对以父亲为代表的男权规范的不满、反抗与叛逆,虽然显得有些歇斯底里(连父亲的裤子也要剪掉),但展现了女性真实的人格尊严。
她从T先生对她的纠缠和求爱的痛苦中窥破了男人在其貌似强大背后的卑劣与渺小,从而获得了一种足以和男人对视的自信与精神支撑力。
女性人格意识的觉醒,在《破开》这篇小说中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在这篇小说中,“我”曾与我的朋友殒楠商量“建立一个真正无性别歧视的女子协会”。
她们拒绝以“第二性”作为协会的名称,因为“这无疑是对男人第一性的既成准则的支持”。

论陈染的逃亡意象陈染是个不同凡响的女性作家,作为一个清醒的女性写作者,她以个人的身体和心灵体验歇斯底里般地撞击着她所认为的关于女性的种种幻想,扰乱着主流文学的话语规范和象征秩序,展现了女性的真实自我。
这一切使她的作品成为女性在当下时代中自觉的文学范本。
长期以来,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陈染作为女性作家表达女性命运及特殊存在的努力,而忽略了作品中更为深层的含义。
陈染在《不可言说》的对话录中宣称:“我关心个人和人性。
”可以说,对人性的复杂性、多样性的关注,这个姿态本身就是一种立场、一种态度。
她的小说穿透人性的深处,具有强烈的震撼力量。
逃亡作为陈染对人性复杂性、多样性思考后的一种结果,或说一种姿势,在她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使作品的思想内容在反映女性自主意识的同时,拓展到更广阔、更深远的领域。
一逃亡是陈染作品中一个突出的意象。
所谓“我最大的本领就是逃跑,而且此本领有发扬开去的趋势。
”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小说中主人公出走的情形反复出现:“我将独自漫游”,“我将不再有家”(《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故乡是它乡,总是在寻找、思念着远处不知在哪的模糊不清的家乡”(《凡墙都是门》);“我将开始茫茫黑夜漫游了”(《空的窗》)。
其次,逃亡的方式多种多样:从黑衣到“秃头欲”;从孩子气地试图隐遁到“疯人院”,到不断徘徊在“潜在自杀者的迷失地”;从隐遁在写作中,到逃入为盲目所庇护的想象里。
她在逃什么呢?逃避“强大的社会环境,强大的官僚主义的人际网络”,逃避现实,逃避文明,逃避角色累赘……逃离所有不愿面对的事物。
陈染曾在《私人生活》中说道:“一个人凭良心行事的能力,取决于她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她自己社会的局限,而成为一个世界公民……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有勇气说一个‘不’字,有勇气拒不服从强权的命令,拒不服从公共舆论的命令。
”逃亡,是某种无力而有效的拒绝,是勇于对世界说“不”,对外界采取拒绝与反叛的姿势,远离尘嚣,将自我封闭起来,而专注于倾听自己,不断捕捉心灵的声音,书写自身对个人和人性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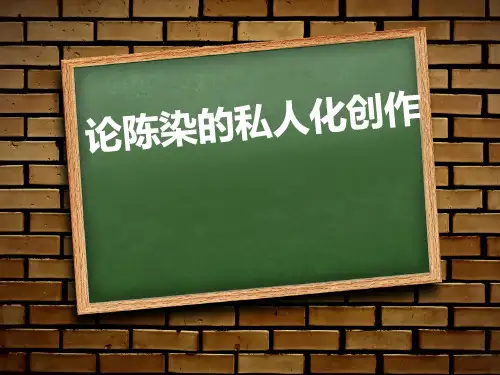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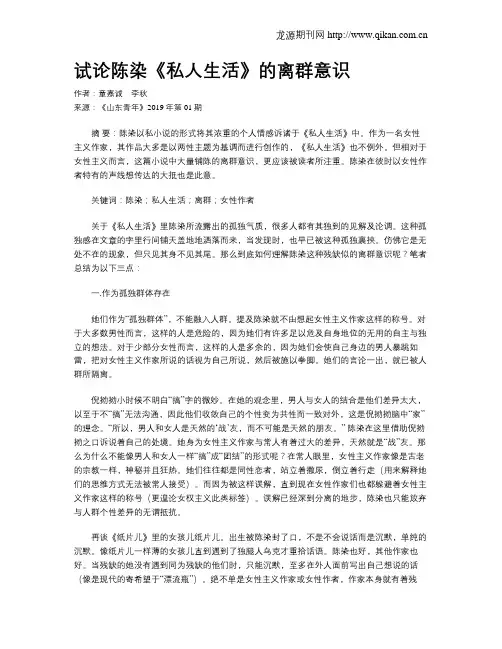
试论陈染《私人生活》的离群意识作者:童嘉诚李秋来源:《山东青年》2019年第01期摘要:陈染以私小说的形式将其浓重的个人情感诉诸于《私人生活》中。
作为一名女性主义作家,其作品大多是以两性主题为基调而进行创作的,《私人生活》也不例外。
但相对于女性主义而言,这篇小说中大量铺陈的离群意识,更应该被读者所注重。
陈染在彼时以女性作者特有的声线想传达的大抵也是此意。
关键词:陈染;私人生活;离群;女性作者关于《私人生活》里陈染所流露出的孤独气质,很多人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及论调。
这种孤独感在文章的字里行间铺天盖地地洒落而来,当发现时,也早已被这种孤独裹挟。
仿佛它是无处不在的现象,但只见其身不见其尾。
那么到底如何理解陈染这种残缺似的离群意识呢?笔者总结为以下三点:一.作为孤独群体存在她们作为“孤独群体”,不能融入人群。
提及陈染就不由想起女性主义作家这样的称号。
对于大多数男性而言,这样的人是危险的,因为她们有许多足以危及自身地位的无用的自主与独立的想法。
对于少部分女性而言,这样的人是多余的,因为她们会使自己身边的男人暴跳如雷,把对女性主义作家所说的话视为自己所说,然后被施以拳脚。
她们的言论一出,就已被人群所隔离。
倪拗拗小时候不明白“搞”字的微妙。
在她的观念里,男人与女人的结合是他们差异太大,以至于不“搞”无法沟通,因此他们收敛自己的个性变为共性而一致对外,这是倪拗拗脑中“家”的理念。
“所以,男人和女人是天然的‘战’友,而不可能是天然的朋友。
” 陈染在这里借助倪拗拗之口诉说着自己的处境。
她身为女性主义作家与常人有着过大的差异,天然就是“战”友。
那么为什么不能像男人和女人一样“搞”成“团结”的形式呢?在常人眼里,女性主义作家像是古老的宗教一样,神秘并且狂热。
她们往往都是同性恋者,站立着撒尿,倒立着行走(用来解释她们的思维方式无法被常人接受)。
而因为被这样误解,直到现在女性作家们也都躲避着女性主义作家这样的称号(更遑论女权主义此类标签)。
题目埃莱娜·西苏“身体写作”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以陈染的《私人生活》为例院(系)文学院专业汉语言文学年级学生姓名学号指导教师二○○一五年四月目录内容摘要 (1)关键词 (1)一、引言 (1)二、“身体写作”理论概述 (1)(一)理论提出 (1)(二)思想来源 (2)三、“身体写作”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3)(一)“身体写作”进入中国 (3)(二)“身体写作”给女作家带来的影响 (4)四、陈染的践行 (5)(一)书写女性身体 (5)(二)解构男女性关系的既定秩序 (5)五、结语 (6)参考文献 (6)内容摘要:本文主要对法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戏剧家、文学理论家、女性主义的代表之一的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提出的“身体写作”理论做一个简介,并对于它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做一个大体的介绍,最后以陈染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为例来谈中国女作家对“身体写作”的践行。
关键词:西苏身体写作女性主义陈染一、引言20世纪80年代,作为法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戏剧家、文学理论家、女性主义的代表之一的埃莱娜·西苏关于女权主义的文论传入中国,她提出的“身体写作”的口号鼓舞了一批中国青年女作家们,如:林白、陈染、徐小斌等。
她们在“身体写作”的口号的鼓舞下,以此为思想的渊源进行写作,向社会发出女性的声音。
“身体写作”发展到今天出现的作家和作品众多,所以本文仅以陈染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为例来谈西苏的“身体写作”理论在中国的实践。
二、“身体写作”理论概述(一)理论提出“身体写作”也被称为“身体书写”、“身体话语”、“身体修辞学”等等。
最早在埃莱娜·西苏的《美杜莎的笑声》( 1975 年) 中提出来。
“是西方女权运动的产物,是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种女性主义文学理念。
”①当然,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埃莱娜·西苏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她在提出“身体写作”的理论之前,就有英国女权主义批评家伍尔夫提出了“一间自己的屋子”的主张,还有法国女权主义者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躯体”理论。
试论陈染的同性私小说∗
刘花蕊
【期刊名称】《《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3(000)002
【摘要】私小说是由日本传入中国的一种独特的小说形式,在中国当代文坛,陈染的作品充分体现了私小说强调自我暴露和自我书写的特点。
作为女性作家,其小说《无处告别》《破开》《私人生活》等多部作品都对女性自我进行了深度书写,并涉及到同性情感这一边缘性的敏感私密的话题。
陈染在作品中试图打破性别界限,从爱情本身出发,并力图消解加之于爱情上的外在因素,以一种超性别意识赋予了同性情感以合理性。
陈染以同性恋小说拓宽了私小说的题材,也奠定了陈染在私小说创作领域的重要地位。
【总页数】4页(P88-91)
【作者】刘花蕊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7
【相关文献】
1."私小说"创作流变--郁达夫、陈染小说比较 [J], 刘智民
2.中西现代私小说中的“自我”——评陈染、夏洛蒂·勃朗特小说 [J], 段晓玲;张雪梅
3.试论陈染的同性私小说 [J], 刘花蕊;
4.日本“私小说”与中国“私人化写作”——以志贺直哉与林白、陈染为中心 [J], 陈秀敏
5.仵埂专栏:前沿观察私小说与大时代——从陈染的私小说到博客“极地阳光” [J], 仵埂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以陈染和林白为例看边缘叙事中的姐妹情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文学以深刻的自觉,以倾覆男权话语的书写策略,以前所未有的主体意识和女性视角审视着女性的现实存在,迎来了她在规模和深度上的颠峰时期。
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在男性话语体系中进行着决绝而艰难的突围,否定男性秩序中既定的角色框定,把自我从男性依附、母性神话中剥离开来,把自我救赎的书写投向了一贯被男性所忽略的女性同性,同性之间的相互拯救成为女性自我救赎的一种追求和尝试,一向处在边缘状态的“姐妹情谊”得到纵深探索。
女性文本对这种姐妹场景的书写内涵十分复杂,既有女性之间真挚的眷恋之情,又充满诸多排斥与疑虑,凸显了女性寻求自我救赎的尝试与艰难,同时也表露出女性在走向个体独立道路上的个性缺失。
一、姐妹情谊的缔结和救赎意味在这方面做出大胆而深入探索的是陈染、林白,她们对“姐妹情谊”有进一步的理解和诠释,通过对姐妹情谊的深层心理剖析,探讨了这种自我心灵需求的丰富内蕴、矛盾性及不稳定性等方面。
陈染曾经说过“我对于男人所产生的病态的恐惧心理,一直使我天性中的亲密之感倾投于女人”(《空心人的诞生》)。
在她长长短短的叙述中,着力刻画了女性同性间精神之爱的故事,这些故事构成了她的作品中回环往复、动人心魄的部分,那燃烧在女性心灵深处的相互理解、信赖与依恋的至上情境,俨然一个东方同性精神之爱的女性神话,这使她的写作不仅具有女性文学的意识,而且具有道德方面的叛逆性。
阅读陈染的作品,可以体会到她对于女性之间独特的“姐妹情谊”探讨的深度。
陈染一直强调这种情谊的精神性,也一直在实践着,从心理的角度指认姐妹情谊,对女性建立自己的话语中心做出了尝试和努力。
她认为,为了在这个充满对抗性的世界生存,女人选择一个男人作为精神上的依靠,那只是“几千年遗传来的约定俗成的带有强制性的习惯”,女人和女人之间也有亲和力,而且会更深刻和忠诚,是“我们女人之间长久以来被荒废了的一种生命潜能。
”(《破开》)陈染所表现的这种女性乌托邦的理想,蕴含了丰富的女性文化及现实社会的症候,她把寻找真正的情爱、心灵沟通的希望寄予在同性之间,她提到,“情爱来自何方?异性之间肯定会有,同性之间也可能出现”,女性渴望的温馨与信赖的情感很难在现实中的男人那里找到归宿,而同性比异性更容易构成理解和默契,顺乎天性,“女人们是比较容易相互接近并亲密起来的性别类群”,她营造了一个个温馨自足的充满女性世界意味的家――女性之邦,互相护卫着面对艰难的世界和危险的处境,相互抚慰着长期以来形成的心灵焦渴和精神枯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