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国后电影中的三种女性形象
- 格式:doc
- 大小:55.00 KB
- 文档页数: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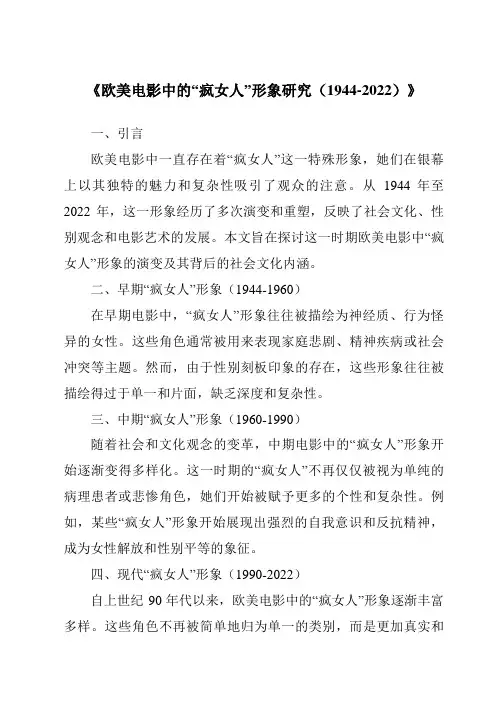
《欧美电影中的“疯女人”形象研究(1944-2022)》一、引言欧美电影中一直存在着“疯女人”这一特殊形象,她们在银幕上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复杂性吸引了观众的注意。
从1944年至2022年,这一形象经历了多次演变和重塑,反映了社会文化、性别观念和电影艺术的发展。
本文旨在探讨这一时期欧美电影中“疯女人”形象的演变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
二、早期“疯女人”形象(1944-1960)在早期电影中,“疯女人”形象往往被描绘为神经质、行为怪异的女性。
这些角色通常被用来表现家庭悲剧、精神疾病或社会冲突等主题。
然而,由于性别刻板印象的存在,这些形象往往被描绘得过于单一和片面,缺乏深度和复杂性。
三、中期“疯女人”形象(1960-1990)随着社会和文化观念的变革,中期电影中的“疯女人”形象开始逐渐变得多样化。
这一时期的“疯女人”不再仅仅被视为单纯的病理患者或悲惨角色,她们开始被赋予更多的个性和复杂性。
例如,某些“疯女人”形象开始展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反抗精神,成为女性解放和性别平等的象征。
四、现代“疯女人”形象(1990-2022)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电影中的“疯女人”形象逐渐丰富多样。
这些角色不再被简单地归为单一的类别,而是更加真实和立体地反映了当代女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她们可能具有强烈的情感波动、复杂的心理世界和独特的个性魅力。
同时,这些角色也经常涉及到性别、权力、家庭、爱情等多元主题,为观众提供了更丰富的思考空间。
五、影响“疯女人”形象的因素1. 社会文化因素:欧美电影中的“疯女人”形象受到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
随着社会进步和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电影中的“疯女人”形象逐渐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
2. 电影艺术发展:电影技术的发展和艺术观念的更新也为“疯女人”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导演和演员们通过精湛的表演技巧和创新的拍摄手法,将这一特殊形象塑造得更加生动和立体。
3. 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为电影中的“疯女人”形象提供了更多的灵感和启示。

中国电影的女性视角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历程中,女性视角逐渐得到了重视和关注。
传统上,中国电影中对女性的描绘主要偏重于家庭角色和传统性别观念的强调。
然而,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女权意识的崛起,中国电影开始呈现出更为多样化和真实的女性形象,女性视角也逐渐得到了展现。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中国电影中的女性视角,并分析其中的变化和影响。
一、传统影片中的女性视角中国电影的早期发展,受制于历史背景和社会观念,女性在电影中的形象多被设定为传统的家庭角色。
她们往往是温柔、贤良的妻子、母亲或女儿,被期望承担家庭的责任和传统性别角色的扮演。
这种角色设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性的个性发展和真实性格的展现。
二、现代电影中的女性视角嬗变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女性权益的提升,中国电影中的女性视角逐渐发生了嬗变。
现代电影开始更多地关注女性的内心世界、职业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女性不再仅仅是家庭的附属品,而是有着独立思想和追求的个体。
电影作品中,女性形象呈现出了更多元化的特点。
1. 强调女性的职业发展现代电影中,女性角色开始涉及各个职业领域,展现了她们在职场上的努力和价值。
例如,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中,女主角从一个普通的小职员逐渐崭露头角,最终成为了公司的精英。
这种形象的呈现,帮助观众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女性在职场上的困境和付出。
2. 探索女性的情感和内心世界在现代电影中,女性的情感和内心世界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电影《某某》中,女主角经历了一段感情的痛苦与成长,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这种情感上的探索,使得女性角色更加真实和立体,也使观众更容易产生共鸣。
三、女性视角对中国电影的影响女性视角的崛起对中国电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它给予了女性更多的话语权和自我表达的空间。
女性视角的出现使得女性可以更加真实地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追求,为观众传递更加真实和立体的观影体验。
其次,女性视角的崛起也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创新和多样化发展。
以女性为主题或角色的电影作品逐渐增多,探讨了女性在家庭、职场、情感等方面的困境和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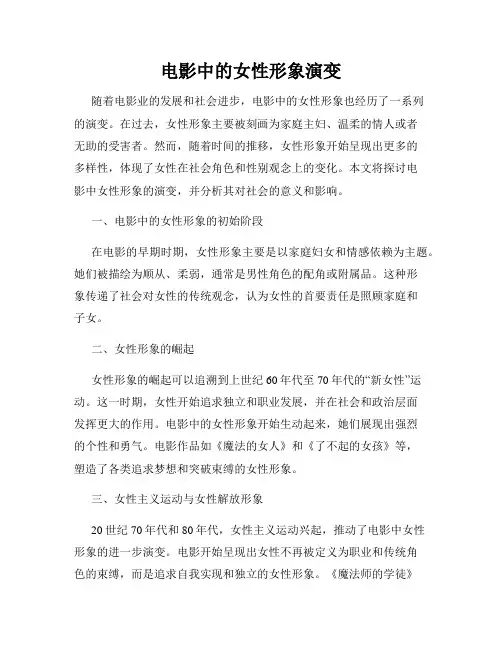
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演变随着电影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
在过去,女性形象主要被刻画为家庭主妇、温柔的情人或者无助的受害者。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形象开始呈现出更多的多样性,体现了女性在社会角色和性别观念上的变化。
本文将探讨电影中女性形象的演变,并分析其对社会的意义和影响。
一、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的初始阶段在电影的早期时期,女性形象主要是以家庭妇女和情感依赖为主题。
她们被描绘为顺从、柔弱,通常是男性角色的配角或附属品。
这种形象传递了社会对女性的传统观念,认为女性的首要责任是照顾家庭和子女。
二、女性形象的崛起女性形象的崛起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新女性”运动。
这一时期,女性开始追求独立和职业发展,并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开始生动起来,她们展现出强烈的个性和勇气。
电影作品如《魔法的女人》和《了不起的女孩》等,塑造了各类追求梦想和突破束缚的女性形象。
三、女性主义运动与女性解放形象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兴起,推动了电影中女性形象的进一步演变。
电影开始呈现出女性不再被定义为职业和传统角色的束缚,而是追求自我实现和独立的女性形象。
《魔法师的学徒》和《霸王别姬》等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展示了女性聪明、自信和坚强的一面。
四、女性超级英雄的崛起近年来,女性超级英雄形象在电影中的崛起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
电影作品《神奇女侠》和《黑寡妇》等,突破了传统男性超级英雄的形象,赋予女性以强大的力量和独立的人格。
这些电影不仅推动了女性角色在电影中的地位,还传达了女性自主性和平等的价值观。
五、女性导演和故事的多样性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导演进入电影行业,电影故事越来越多元化。
女性导演带来了对女性经历和故事的深入理解和刻画。
电影如《小姐》和《喜宴》等,展现了女性的力量、激情和复杂性。
这些作品引起了观众对不同女性生活经验的关注和理解。
六、电影中女性形象的社会意义和影响电影中女性形象的演变不仅是电影艺术的发展,也反映了社会对女性地位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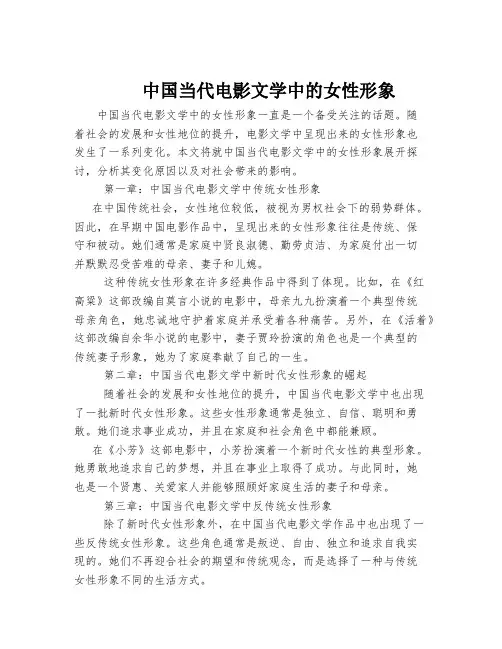
中国当代电影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中国当代电影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地位的提升,电影文学中呈现出来的女性形象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本文将就中国当代电影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展开探讨,分析其变化原因以及对社会带来的影响。
第一章:中国当代电影文学中传统女性形象在中国传统社会,女性地位较低,被视为男权社会下的弱势群体。
因此,在早期中国电影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女性形象往往是传统、保守和被动。
她们通常是家庭中贤良淑德、勤劳贞洁、为家庭付出一切并默默忍受苦难的母亲、妻子和儿媳。
这种传统女性形象在许多经典作品中得到了体现。
比如,在《红高粱》这部改编自莫言小说的电影中,母亲九九扮演着一个典型传统母亲角色,她忠诚地守护着家庭并承受着各种痛苦。
另外,在《活着》这部改编自余华小说的电影中,妻子贾玲扮演的角色也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妻子形象,她为了家庭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第二章:中国当代电影文学中新时代女性形象的崛起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地位的提升,中国当代电影文学中也出现了一批新时代女性形象。
这些女性形象通常是独立、自信、聪明和勇敢。
她们追求事业成功,并且在家庭和社会角色中都能兼顾。
在《小芳》这部电影中,小芳扮演着一个新时代女性的典型形象。
她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并且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
与此同时,她也是一个贤惠、关爱家人并能够照顾好家庭生活的妻子和母亲。
第三章:中国当代电影文学中反传统女性形象除了新时代女性形象外,在中国当代电影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一些反传统女性形象。
这些角色通常是叛逆、自由、独立和追求自我实现的。
她们不再迎合社会的期望和传统观念,而是选择了一种与传统女性形象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芳华》这部电影中,女主角刘峰扮演了一个反传统女性形象。
她是一个独立自主、追求自由和梦想的女性。
她选择了参军,与传统女性角色不同,她在军队中经历了一系列苦难和挑战,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第四章:中国当代电影文学中女性形象对社会的影响中国当代电影文学中呈现出来的新时代女性形象和反传统女性形象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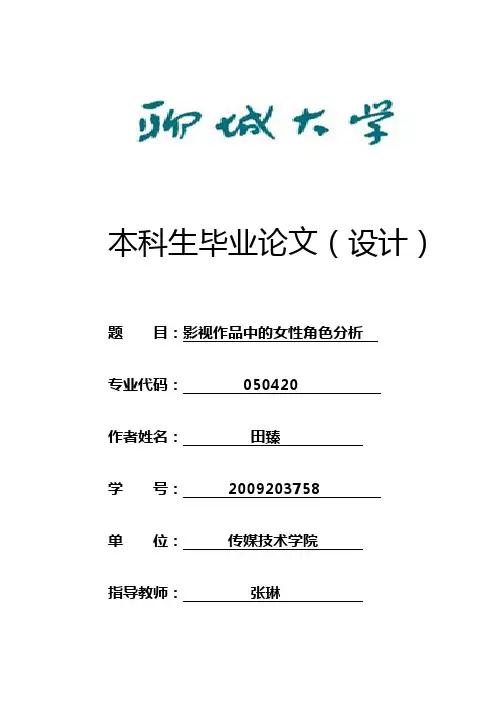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题目:影视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分析专业代码:050420作者姓名:田臻学号:**********单位:传媒技术学院指导教师:**2013 年 5 月30 日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题目:影视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分析专业代码:050420作者姓名:田臻学号:**********单位:传媒技术学院指导教师:**2013年5 月30 日原创性声明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取得的成果。
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论文中不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聊城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
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
本人承担本声明的相应责任。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日期指导教师签名:日期目录摘要 (1)Abstract (2)前言 (1)一、中国影视剧中女性角色的转变和发展历程 (1)二、影视剧中的四种女性角色类型 (2)(一)盖娅类型—大地之母形象 (2)(二)潘多拉类型—女性诱惑 (4)(三)灰姑娘类型—等候“王子”的救赎 (6)(四)花木兰类型—自我救赎的新型形象 (8)三、新媒体时代影视剧作中女性角色的转变与不变 (10)(一)新媒体对影视剧作的影响 (10)(二)新媒体时代影视剧作中女性角色的转变与不变——以热播剧《后宫甄嬛传》为例 (11)结语 (12)参考文献 (13)致谢 (14)摘要在中国影视作品中,女性总是扮演着温柔婉约、体贴入微、相夫教子的角色。
他们的这种贤妻良母、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们为之动容,为之惊叹。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女性的选择权也大大增加了,她们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自己的生活。
这使生活在当今的女性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等同于男人的尊严,她们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争取明天的发展权,对婚姻,对事业,对人生观价值观的看法都由她们自己来主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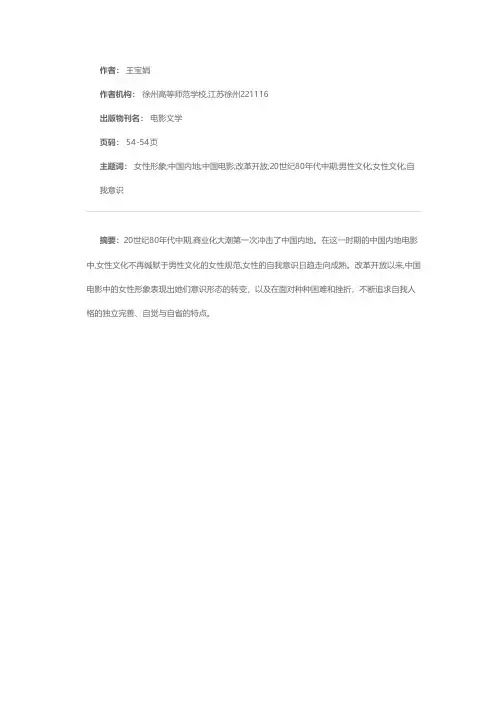
作者: 王宝娟
作者机构: 徐州高等师范学校,江苏徐州221116
出版物刊名: 电影文学
页码: 54-54页
主题词: 女性形象;中国内地;中国电影;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中期;男性文化;女性文化;自我意识
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业化大潮第一次冲击了中国内地。
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内地电影中,女性文化不再缄默于男性文化的女性规范,女性的自我意识日趋走向成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表现出她们意识形态的转变,以及在面对种种困难和挫折,不断追求自我人格的独立完善、自觉与自省的特点。

![论1930年代左翼电影中革命女工形象[论文]](https://uimg.taocdn.com/d56ad0234b73f242336c5f26.webp)
论1930年代左翼电影中革命女工形象1933年,夏衍创作了一部《前程》,讲述了30年代娜拉的故事,不过主角换成了女伶苏兰英,抛弃舞台生活,成为全职太太后,为家庭尽心尽责。
但当丈夫平步青云后立马驱逐她。
最终她又重新回到了舞台自力更生。
影片放映后,关于“娜拉”的出路引发了巨大争议。
一种认为,只有劳动人民的苦难才是唯一值得描写的题材;一种认为,女主人公从家庭回到舞台并非妇女的“前程”,而应该走入工厂和参加革命斗争,成为革命女工。
且不论两者的分歧,我们可以发现,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女工才是严格符合左翼意识的女性之“前程”。
然而,当左翼意识投射在左翼银幕上,如《现代一女性》的王安琳,《三个摩登女性》的周淑贞,《新女性》的李阿英等。
虽然革命女工占有思想高地,往往扮演拯救者/启蒙者的角色,但在影片中却往往不是令人瞩目的主角,而且备受左翼剧评人的批评与争议。
为何?一、处于影像边缘的拯救者左翼电影常常在一个影片中构建两个/三个不同的女性形象,而且这些女性形象在故事结构中的行动范畴不同,往往形成被拯救/拯救的模式。
如《现代一女性》中王安琳是“小资产阶级女性”萄萄的启蒙者。
当沉迷于爱情的萄萄对情人心灰意冷时,恰巧王安琳对她的同志之爱填补了俞冷的情人之爱,萄萄最终听信了王安琳的劝诫“恋爱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分。
我们不应当为恋爱而牺牲,我们要做的事多着呢,”而走向了“光明的路”。
[1]相比萄萄而言,这位拯救者的戏份却很少。
而且,王安琳在萄萄心中的形象从讨厌变得“伟大”的过渡显得突兀。
《新女性》中阿英不仅成功制止了韦明自杀,帮韦明用武力打击了王博士,轻易地把王博士摔在地上。
编剧孙师毅在《新女性作意》:“虽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女性之中,却也正不难发现出‘新的女性’型之临盆的预兆;而这在别一阶级,却并不是如此难产的。
在剧中曾经触及面掠过的另一个工人女性;便略略可以看出是已经成长了的新型的一幅剪影。
”[2]故事层面,李阿英不仅是韦明生命的拯救者,是思想上的启蒙者;话语层面,阿英是编剧所冠冕的“新女性”。

作者: 何静[1];胡辛[2]
作者机构: [1]南昌大学影视艺术研究中心;[2]南昌大学中文系,江西南昌330031
出版物刊名: 江西社会科学
页码: 243-246页
主题词: 中国电影;女性形象;女性主义
摘要:电影百年,女性成为银幕上一道绚丽的风景,但电影在多大程度上还原女性真实的生存状况?本文从女性主义理论和电影叙事实际出发,探讨了1915-1949年间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内涵,对男性导演视角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女性主义的解读,发现1949年前的中国电影中,女性只不过是作为“被看”的对象,作为客体满足着男性看的欲望。
作为银幕上被表达与被隐瞒的对象,她们仍然是无言无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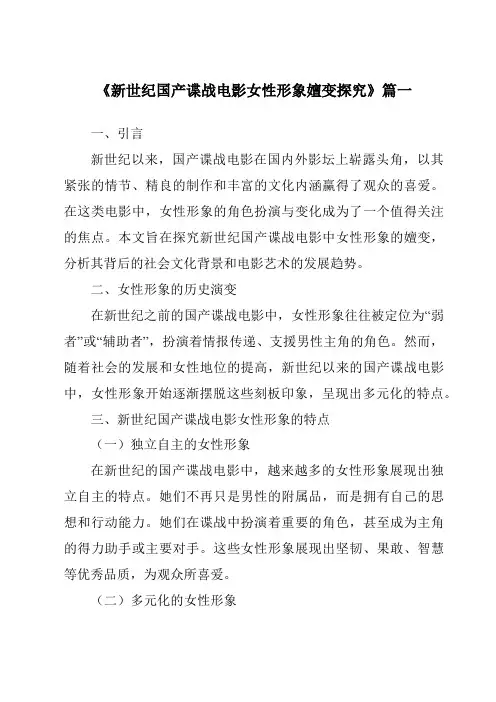
《新世纪国产谍战电影女性形象嬗变探究》篇一一、引言新世纪以来,国产谍战电影在国内外影坛上崭露头角,以其紧张的情节、精良的制作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在这类电影中,女性形象的角色扮演与变化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
本文旨在探究新世纪国产谍战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嬗变,分析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电影艺术的发展趋势。
二、女性形象的历史演变在新世纪之前的国产谍战电影中,女性形象往往被定位为“弱者”或“辅助者”,扮演着情报传递、支援男性主角的角色。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地位的提高,新世纪以来的国产谍战电影中,女性形象开始逐渐摆脱这些刻板印象,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三、新世纪国产谍战电影女性形象的特点(一)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在新世纪的国产谍战电影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形象展现出独立自主的特点。
她们不再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而是拥有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能力。
她们在谍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主角的得力助手或主要对手。
这些女性形象展现出坚韧、果敢、智慧等优秀品质,为观众所喜爱。
(二)多元化的女性形象除了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外,新世纪国产谍战电影中还出现了其他多元化的女性形象。
例如,有些女性形象展现出柔情似水、温婉可人的特点,成为男性主角的恋人或知己;有些则展现出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
这些多元化的女性形象使得电影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加符合现实生活中的多样性。
四、女性形象嬗变的原因分析(一)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地位的提高,社会对于女性的认知和期待也在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反映在电影中,使得女性形象变得更加多元化和独立。
此外,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国内电影市场也更加开放和多元化,这为女性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空间。
(二)电影艺术的发展趋势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发展和变化也影响着女性形象的塑造。
新世纪以来,国产电影在制作和技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使得电影能够更加真实地展现出现实生活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新世纪以来农村题材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建构分析作者:王成来源:《戏剧之家》2016年第09期【摘要】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农村题材电影发展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机遇期。
受国家政策和商业化驱动等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电影在制作水平和叙述内容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主义这一视角之下,新世纪以来农村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多元化的嬗变,女性形象的建构以及其艺术文化价值的呈现带给我们以诸多思考。
【关键词】新世纪;农村题材;女性形象;思考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5-0134-02一、引言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我国农村题材电影的发展开始走向一个下坡,不仅数量不多,其质量也乏善可陈。
新世纪之后,党和国家开始重视农村题材电影的创作和普及,加之数字技术等的广泛应用,基础设施等的逐步完善,我国的农村题材电影开始迎来一个崭新的机遇期。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电影中,涌现出一大批具有不同性格的典型性的女性形象。
有对传统女性的怀旧想象,有反映新时期在自我和被动中矛盾抗争的女性形象,也有着重表现新世纪积极进步的女性形象,等等。
这些女性形象的影视化呈现,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也给所有研究者带来一些思考。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即使在现代城市化高度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农村依然是我国社会最本质方面的反映,即农村代表了我国社会最原始和本质的方面。
在女性主义这一视角之下,农村题材电影的发展过程中女性形象的崛起反映了中国怎样的普世价值的变化,女性形象在农村题材电影中的呈现存在着怎样的问题,还在引发我们的思考。
二、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建构新世纪以来的农村题材电影本身就呈现出一种内容丰富和题材广泛的态势。
“农村题材电影的创作,挖掘了独特的本土人文资源和人文亮点,并将这种人文亮点转化成审美化的故事。
”[1]在这样资源转化的过程中,经过审美加工过的社会现实,就以艺术化的方式呈现在电影屏幕上。
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一部舞台剧的演变在电影史上,女性形象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和关注的话题。
从早期的沉默电影时代到现代荧幕上的超级女英雄,女性在电影中的角色和形象一直在不断演变和发展。
而这种演变过程,有时候也像是一场精彩纷呈的舞台剧,展现了女性在电影世界中的力量和多样性。
早期的女性形象:柔弱娇媚早期的电影中,女性形象通常被描绘为柔弱、娇媚、需要男性拯救的角色。
这类形象在默片时代尤为突出,女性常常扮演着需要被拯救的公主、受害者或是家庭妇女的角色。
她们往往被置于男性角色的背后,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
这种形象在当时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下得以延续,女性被传统观念所束缚,缺乏表现自我和自我实现的机会。
后起之秀:独立自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地位的提升,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也开始发生变化。
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独立、坚强、自主的女性形象逐渐走入荧幕。
代表性的电影如《魔法黑森林》、《铁达尼号》等,塑造了一批具有勇气和智慧的女性形象。
她们不再是被动接受命运安排的角色,而是拥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勇敢面对挑战,成为故事的主角和推动剧情发展的力量。
当代女性:多元包容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和多元化的呼声,当代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愈发多元丰富。
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刻板印象,女性在电影中展现出更多元、更真实的一面。
无论是职业女性、母亲、超级英雄,亦或是个性张扬、独具魅力的女性,她们在银幕上展现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和精彩故事。
这种多元包容的态势,让女性形象在电影世界中呈现出更加立体和生动的画卷。
女性形象在电影中的演变如同一部精彩的舞台剧,从柔弱娇媚到独立自主,再到多元包容,每一个阶段都展现着女性的力量和魅力。
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不断演变,彰显着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希望未来电影能够继续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真实的女性形象,让每一个女性都能在银幕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在电影中,女性形象的演变历程展示了社会观念的变迁和女性力量的崛起,呼应着现实世界中女性不断探索和突破的可能性。
浅谈当代中国电影艺术中的女性角色[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中国电影社会制约[论文摘要]在我们看到过的影视作品中,总有这样一个群体,她们光鲜亮丽,温柔婉约,她们戴着与生俱来的母性光辉,让我们为之动容,为之惊叹。
在中国的传统意念中,女性应当是扮演着温柔体贴,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角色,在我们生活的时下,随着女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女性有了更多层次的开展空间,和更多生活途径的选择权。
这使生活在当今的女性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等同于男人的尊严,她们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争取明天的开展权,对婚姻,对事业,对人生观价值观的看法都由她们自己来主宰。
以前那些只有男人拥有的特权之门,在现如今已经不能再把女性阻挡在外。
电影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变相传达,女性如此巨大的改变,自然也逃不过摄影机的镜头。
在中国现代的电影艺术中,我们惊喜地从中看到中国女性动人的蜕变,从封闭保守的表到达开放张显的张示,这期间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转变,是值得我们寻味的。
19世纪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女性开始反省自身的价值,并确定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奉献被充分揭示出来。
在女权主义运动方兴未艾,电影艺术中的女性意识也渐渐觉醒,同时期出现了“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理论〞,女性主义电影也崭露头角。
运动中的电影批评主要是针对一些男性电影中出现的女性形象进行犀利的批评,进一步揭示对女性的探讨,描写更细腻的女性感情世界。
由此,女性角色被史无前例的关注和讨论。
中国女性由于其所受的思想文化背景的特殊性,所散发出的气质与其他地区的女性有很大不同,而在讨论中国电影中的女性角色时,自然也摆脱不了时代和地域的烙樱那些闪耀的荧幕之星,她们的出现曾带给多少人沉醉的喜悦和游离的梦想,也带给人多少无奈的追问与失落的伤感。
正是因为她们的付出和努力点缀了那苍白的灰色的大荧幕,幻化出一场场惟妙惟肖的尘世闹剧。
一、第五代电影创作者对女性的表达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第五代电影的崛起,给中国电影带来了光辉的新时代,中国电影从此走上了国际影坛,并频频获奖,伴随着商品经济的悄然兴起,电影也开始面临商业化的挑战。
戴锦华对当代中国电影女性形象的解读一、引言作为一名在电影批评、女性写作研究和大众传媒文化研究领域均有建树的学者,戴锦华在国内外一直有着超高的人气。
她还曾是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文化思潮的先驱和推动者,有着“中国苏珊?桑塔格”的美誉。
她以自己独有的智慧与锋芒成为学界“传奇”。
虽然在上述三个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但戴锦华始终坚持认为电影才是她“真正”的专业,称自己只是一个电影研究者。
不过事实也的确如此,无论之后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还是大众文化研究,戴锦华始终坚持以电影作为自己研究的窗口,从中探寻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脉络与轨迹。
1982 年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戴锦华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学院任教,从此开始她的学术生涯。
在之后的几年里,她直接参与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电影理论专业,填补了中国电影理论的学科空白,并且积极参加西方电影学术培训班,尝试翻译电影理论专著,正是因为这样的治学态度和学术经历,使得戴锦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
她以开阔的中西文化比较视野,将西方电影理论快速地引入了中国的电影研究领域,极大地拓展了当时中国电影理论狭窄的研究视域[1] 。
戴锦华如今已出版了多部电影理论专著,包括:《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镜与世俗神话一影片精读18例》《雾中风景一中国电影文化 ( 1978-1998 )》等,她将自己极富才情的文字表达,自然流畅地贯注于电影文本,并且还以敏捷灵便的思维在多种文化角度中自如地行走。
但是戴锦华对电影批评的研究脚步却没有停留在文本细读的阶段,从最初侧重于文本解读,运用经典影片挑战西方理论,再到之后渐次明晰了的女性主义立场和大众文化批评的方法,戴锦华始终不断的开阔、融通自己的研究领域[2] 。
女性主义是戴锦华在电影批评的过程中逐渐明了并坚持的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她认为电影将“性别角色与男性的欲望结构深刻的内在于影片的叙事机制”[3] 。
对于电影这个行业,时至今日也不得不承认它依旧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行业,那么对于这些“摄影机里的女人”,在男权为上的行业规则下,不同时代的导演们究竟会赋予她们哪些不同的特质?戴锦华也在她的电影批评中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1 君子兰 · 康乃馨 · 梅花 ——试论建国后电影中的三种女性形象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200104班 亢烨 指导老师:杨矗
摘要 伴随着女性主义的不断深入,女性电影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在电影中塑造什么样的女性形象,让女性在电影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成为我们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前,好莱坞电影中塑造出的女性都是缺乏独立人格的人,将女性作为男性捕捉的对象——男人性欲的猎物,压倒了她们作为母亲的本性。新中国的影片则改变了这种情况,在中国电影中女性形象是被正面描绘的,她们有自我存在的价值,有母亲般包容的品质,有独立的人格魅力,好比君子兰、康乃馨、梅花这三种不同特质的花。“君子兰”式的女性是政治化的女性,她们像男人一样勇敢、无畏,甚至比男人还男人;“康乃馨”式的女性是母亲化的女性,她们温柔、博爱,但有时包容的失去了自我;“梅花”式的女性则是我们现在需要树立的女性形象,她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独立、自主、爱他但不丧失自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女性。 关键词 中国电影 女性形象 女性意识
马克思曾经指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在这个意义上,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就成为了衡量人类社会的历史性进步和文明进展的一个重要尺度。 随着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首都北京召开,妇女问题、女性主义问题再一次引起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从当代女性主义的观点来探讨和考察妇女在一种最有影响力的传播媒体——电影中究竟是如何被表现的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从电影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从妇女作为重要的观影群体这个事实出发,也必然提出妇女形象在电影中如何被表现的问题。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新角度的思想观念对传统的电影分析会提供方法上、观念上的启示,而如何运用女性主义分析电影中的女性也就成为电影接受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女性电影在西方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与女权运动紧密相联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女性电影区别于一般的关于妇女题材的影片,不仅描写妇女和妇女问题,其关键还在于塑造什么样的妇女形象,让妇女在电影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以前,好莱坞经典影片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影片中所描绘的妇女形象,基本上都是缺乏独立人格的人。她们一直以男性的附属物身份而存在,没有独立的存在价值。由于影片将妇女形象作为男人眼睛捕捉的对象——男人性欲的猎物,压倒了她们作为母亲的本性,因而大量的影片中所反映出来的是男性目光注视下的女性,并总是采取暴露的方法,把女性作为男性的欣赏物。女性电影则是对这种好莱坞电影模式的否定。在这类影片中,创作者十分强调女性的独立性,让女性享有和男性同等的地位。女性形象是被正面描绘的。即使有些影片所表现的女性的沦落,也是由于各种不同因素,被迫走上此路的。创作者选择的角度,目的正是在于暴露女性在以往社会所受的压抑与屈辱。如果与此相比,中国影片中表现妇女命运、妇女题材的电影,都可以称之为西方电影意义上的女性电影。从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神女》、《女性的呐喊》、到五六十年代的《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到八十年代的《小街》、《人到中年》、《谁是第三者》以及进入新世纪后的《我和爸爸》、《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等,都可以看到与那种意义上的西方女性电影的相同处。这是因为文化上的原因如“道德化”、“不善于言性”和“新的意识形态” 2
统摄的结果。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女性电影早已存在。这样,西方女性电影与中国的根本不同就主要在于:表现妇女形象背后的各自不同的时代社会背景内容。新时期电影中女性电影的根本特点是受西方女性电影理论的影响而形成的。西方女性电影理论,是承接着六十年代末期欧美的妇女解放运动之势而发展起来的。女性电影理论的目的,就是要“力求瓦解目前在电影中存在的女性在创造力上的压抑和形象上的被剥削。以上的现象根源于男权社会中男女性的不平等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已自然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文化和其表意系统中。”[2]与此相联的女性电影批评,则是“让女性对其自身的不利情况产生觉醒,并做出反应的行为,合力创造出更多以女性为主的文化现象,令旧的男权文化开始产生一种‘断裂’,并由此变化出更有利于男女平等的情况来。”[3]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目的和它的批评化应用,对中国女性电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由于受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影响,中国电影开始有了质的变化,即不再是以往的通过女性形象反映社会对女性在婚姻、恋爱、家庭、社会方面价值体现的变迁,而是着意从女性意识入手,思考女性欲望、性别差异和主体性问题。我认为,女性意识是指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待事物,以女性的眼光来体察生活中的一切的一种自觉认识。当这种女性意识深入到电影里,以女性的眼光看女性的婚姻、恋爱、家庭等生活现象,便无疑不仅使中国的电影开拓了表现的视野,同时也有助于塑造更加完整的女性形象。然而这一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经历了君子兰、康乃馨、梅花这三种不同性格的女性形象的演变。下面,本文就对建国后电影中的这三种女性形象以及她们所传达出的独特的意识形态做一大略的考察。
一、 君子兰——政治化的女性形象 “君子兰”型的女性形象主要集中于1949——1966年这十七年间的电影中。之所以把这一时期电影中的女性喻为君子兰主要是从这些女性的性格特征来考虑的。1949年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对中国文化、社会、艺术等各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妇女也在很大的程度上解放了(尽管从五四运动起就有许多变化,但是那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运动,所以一般中国人认为从这时候起女性才得到全面的解放)。妇女像男人一样无论处于战场、偏僻的农村都一样地和男性那样参加劳动、甚至做出牺牲,成为“花木兰”式的革命女英雄、女战士,甚至比男人更坚强、更有毅力。这一点就好比花卉中的君子兰——有着娇美红艳的花朵却以“君子”来命名。 研究革命文艺的一位学者说“红色审美的‘艺术标准’可能具有相当固定、相当有效的形式控制力和相当微妙的形式建构,才可能获得高效率的红色教化功能„„红色文学的教化功能并不只停留在概念的演绎上,而是要以活生生的形象去展现革命的体验可能带来的幸福感(包括受虐状态下的幸福感觉),借助各种‘革命美感’的表达,去赢得青年读者的阅读注意力”[4]“君子兰”型的女性也正是在这种红色文艺、主旋律电影中被塑造起来的。正如这位学者所说的 ,红色电影中的女性就是以她们“活生生的形象去展现革命的体验可能带来的幸福感(包括受虐状态下的幸福感觉)”,传达出“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能做到”这样一种“花木兰”式的女性意识。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类型中有代表性的两位女性形象——赵一曼和吴琼花。 《赵一曼》(1950)由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沙蒙担任导演,是一部向抵抗日军侵略的共产主义战士致敬的影片。赵一曼是个历史人物,在丈夫被日军杀害以后,她接过了丈夫的工作,成为地下共产运动的领导人。赵一曼在战斗中负伤、被捕之后,屡遭折磨仍拒绝泄露机密。在医院人员的帮助下,她逃离了魔爪,再次被捕直到牺牲,至死不曾背叛她的事业和人民。 吴琼花是《红色娘子军》(1961)中的主要人物,她在逃离地主的压迫后,参加了海南岛上的女子游击队,成为巡逻侦察队中的一员。最后在共产党人洪常青的指导下成了一名像赵一曼一样的革命女英雄——坚强、无畏、毫不动摇的理想主义女性,她置中国人民尤其是工人、农民的解放事业于一切之上,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3
电影正是通过这些女性形象,想让当时的中国女性都立志成为“赵一曼第二”、“吴琼花第二”。在这些电影中“那种使女性成为男性欲望的对象、引起视觉快感的好莱坞电影模式和男女性别对立与差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物间阶级与政治上的对立与差异”[5],同一阶级的男人与女人是纯洁无染的兄弟姐妹,如《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和洪常青在原剧本中是“同志、首长、领路人、爱人”的关系,而在电影中属于个人的、感情的东西则全部被去掉了,吴琼花与洪常青一样成为同一非肉身的父亲——党/人民的儿女。女人只是作为“受苦人”翻身/获救,并随即在革命群体中成为无性或化妆为男性的“战士”,成为“党的女儿”,一如“君子兰”,我们无法界定它是花中的“公主”还是花中的“王子”。 之所以出现“君子兰”型的女性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社会需要人们都成为坚定的革命者,有力的建设者,男性以他们勇敢的品质从古到今都被视为民族的脊梁,而女性要解放,要实现自己的价值,要为社会做贡献,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参照男性,以男性为标准塑造自己,甚至比男性要更加勇敢、坚强,只有这样才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纳入主流社会。这似乎是一种“无选择的选择”,好比花木兰需要隐藏好自己的女儿身,象男人那样冲锋陷阵。另外“君子兰”型的女性的出现,我们在电影理论中也可找到其依据:拉康的“认同”论应用于西方电影中被视作是“欲望投射的过程,有人甚至把观影过程看成是满足窥视欲的过程,认同是通过窥视来转移观影者的‘力比多’,从而使观影者由本能的快感上升为意识形态快感。”[6]而对中国电影来说,产生认同的是观影者对银幕情境的认同,银幕情境是对现实生活革命化和理想化的结果,因而也是典型化的过程。影片要求观影者通过对银幕情境的认同来了解生活,认识生活的主流和本质。同时银幕中塑造出的人物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她是观影者所要学习、崇敬的对象,是“革命”、“党性”和“胜利”的一个能指,所以“君子兰”型的女性一旦塑造起来,必然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们出色地完成了她们的任务,与历史一样,电影也强调她们作为战士和英雄的女性形象,但无论是“铁胳膊、铁腿、铁肩膀”的“铁姑娘”,还是“站在高坡上,穿着红衣裳,挥手指方向”的“女性”共产党人,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这一时期的女性意识也只是停留在Sex上的平等,而非Gender上的平等。电影中男女演员在穿着、外貌、言行方面上都几乎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当时要打倒资产阶级,消除差别,建设平等社会,所以平凡而普通的穿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竟极端化到没有男女的区别,问题还在于其服装和言行都是以男性的标准为标准的。回想在1949年以后出现的大部分电影中,究竟有没有穿裙子的女性的党的干部、女性英雄?在中国十七年时期的电影中,不如说新时期以前主旋律的电影中,女性穿裙子与不穿裙子其实是起到了政治身份的识别作用的,是一种界划政治身份的标志:穿裙子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和不革命的,还没受到党的恩惠,不穿裙子则是已经受到了党的恩惠、变成了党的子女。巨大的阶级政治对立取代了男女差异成最基本的一种叙事张力。文化中的“女性”变为一种子虚乌有,“花木兰”式的女性和一个化妆为男人的、以穿男性服装为荣的女性则成为主流文化中女性的最为重要的镜象。于是,当时的中国妇女在她们获准分享话语权力的同时,在文化中却失去了她们与其话语的性别身份;在她们真实地参与历史的同时,女性的主体身份消失在一个非性别的(确切地说,是男性的)假面背后,遭遇和深陷“君子兰”式的困境。